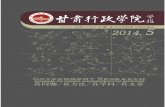Modern pedigree of the views on despotism in China(in...
Transcript of Modern pedigree of the views on despotism in China(in...
·专题论文·
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侯旭东
内容提要 19 世纪末以来 ,秦至清的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为专制政体、皇帝为专制皇帝
的论断影响广泛 ,流行不衰 ,并成为中国史研究的基本观点之一。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
这一说法产生、传播的历史及其后果加以分析 ,指出此一论断并非科学研究的结果 ,而是
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18 世纪时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
国 ,19 世纪末以后经由日本广为不同立场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 ,并通过辞书与历史教
科书渗透到大众中 ,罕有质疑者。这一说法实际未经充分的事实论证 ,不加反思地用它来
认识帝制时代中国的统治机制只会妨碍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 专制主义 专制政体 孟德斯鸠 明治维新 梁启超
时下的各种著作、报刊文章乃至各种课本在涉及中国历史上秦至清的帝制时代时 ,频频会出现
“专制”、“专制皇权”或“专制政体”、“专制主义”之类的表述。具体说来 ,“专制”既用来描述个别皇
帝 ,如秦始皇、汉武帝、明太祖 ;亦用来概括秦代以来的两千多年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这一论断成
为中国史研究的基本观点之一 ,流传之广 ,影响之深无需详论。此说不仅盛行于国内 ,在日本研究
中国历史的学者中也有一定影响。① 正是由于这种深厚久远的影响以致学界几乎视之为当然 ,而
丧失了对此论断的反省能力②,使得这一论断成为众多学者认识中国历史的无意识框架 ,影响了研
究的深入。同时 ,这一论断不仅成为 20 世纪以来书写“历史”的重要中介 ,自出现之时起 ,它就直接
卷入历史实践 ,清朝的灭亡与此说的流行有相当的关系。将它视为“深刻改变了 20 世纪几代中国
4
①
② 目前所见 1940 年代只有钱穆对此说持有异议 ,说详下文。直至近年 ,中国关于“专制主义”的研究均是在认可这一说法
的前提下开展的 ,具体概况参王义保《近年来国内专制主义理论研究述论》,《学术论坛》2006 年第 10 期 ,第 57 —60 页。
日本“中国史研究会”的学者就坚持这一观点 ,其具体论述见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专制国家论》,《历史评论》第 504 号 ,
东京 ,校仓书房 1992 年 4 月 ,第 71 —93 页 ,特别是 87 —92 页 ;足立启二《中国专制国家の发展》,《历史评论》第 515 号 ,东京 ,校仓
书房 1993 年 3 月 ,第 59 —73 页 ;足立启二《专制国家史论 :中国史から世界史へ》,东京 ,柏书房 1998 年版。这些学者的有关中文
论述收入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日本学者已经开始研究“专制论”如何在近代中国出现、流行 ,并着重讨论“专制”与“自由”的关系 ,见近藤慎一《近代中国的体
制构想》,收入所著《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232 —273 页 ;亦有学者开始意识到
盲目接受“专制说”的负面意义 ,见小岛毅《中国的皇权———〈礼治和政教〉导论》,收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 ,孙歌等译《中国的思
维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344 —349 页。
人感受力”的重要论断之一并不为过。①
其实 ,如果我们挖掘一下这一论断的根底 ,不难发现它并不是什么科学研究的结果 ,而是亚里
斯多德以来的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偏见 ,18 世纪时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 ,19 世纪
末以后则经由日本广为中国思想界所接受 ,并未经过充分的事实论证。关于这一问题 ,台湾学者甘
怀真做过初步的梳理②,大陆学者也开始关注③,笔者亦曾有所涉及④,这里将对这一说法产生与流
传的过程 ,被接受的背景、影响与后果作进一步的探讨。除了对该说的西方渊源与日本中介作简单
的回顾外 ,讨论的重点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希望能有助于中国学者认清这一论
断所包含的问题 ,进而有助于推进今后对帝制时期统治机制的重新认识。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 ,本文只是对关于中国古代政体及皇帝本性的一种“论断”的传播、发展历史
的剖析。具体说属于词汇史⑤、观念史 ,泛言之 ,属于思想史的范畴 ,并不是对帝制时代二千多年中
实际运转的中国统治体制本身的研究 ———对统治体制本身的研究绝非一篇短文所能完成。
思想史研究大体有两种路数 ,一是侧重探讨学说内在逻辑发展变化的“内在理路”⑥,一是注重
学说发展与社会、局势乃至权力间的关系的“外在理路”⑦。后文首先厘清这一论断的发展脉络 ,在
此基础上对其流行的背景做些分析 ,可以说是两种路数并重。“知识考古”一词出自福柯 ( Michel
Foucault) ,指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 ,这里则借用来分析一种具体论断的发展史。⑧
“专制”一词很早就见于中国文献 ,《左传·昭公十九年》有“晋大夫而专制其位”的说法 ,《韩非
子·亡征》在讨论导致亡国的种种现象时指出“种类不寿 ,主数即世 ,婴儿为君 ,大臣专制 ,树羁旅以
为党 ,数割地以待交者 ,可亡也”,后面又说“出军命将太重 ,边地任守太尊 ,专制擅命 ,径为而无所请
也 ,可亡也”。的确 ,中国传统文献中“专制”一词并不罕见 ,但其含义几乎都是指大臣或太后、外
戚、宦官等掌管应属于君主的职权 ,具体又分为受命专制与不受命专制两类 ,前者是合法的 ,后者属
5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本文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与后殖民理论研究学术史的思路相吻合 ,据刘禾的介绍 ,后殖民理论主张将“学科行为”作为思
想史的有机部分来研究 ,通过学术传统的来龙去脉 ,去检讨“学科行为”的历史作为和意识形态功能。见刘禾《语际书写———现代
思想史写作批判提纲》,上海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第 6 页。
这方面的代表作如爱德华·W. 萨义德著 ,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此种方法为美国学者诺夫乔伊所倡导 ,见所著《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有、高秉江译) ,江西教育
出版社 2002 年版 ,亦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近年来 ,黄兴涛致力于此 ,但似乎尚未涉及“专制”一词 ,参《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
史”之认识》,收入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323 —341 页 ;
《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兼论“思想现代性”与现代性“社会”概念的中国认同》,《天津社会科学》2005 年第 4
期 ,第 128 —136 页 ;《日本人与“和制”汉字新词在晚清中国的传播》,《寻根》2006 年第 4 期 ,第 41 —46 页 ;《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
兴”观念之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 年第 3 期 ,第 121 —123 页 ;《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实
践》,《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6 期 ,第 1 —34 页 ;《“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2007 年第 2 期 ,第 149 —
163 页。
许兆昌、侯旭东 :《阎步克〈乐师与史官〉读后》,《中国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 ,第 163 —165 页。
大陆学者也开始反思这一观点 ,见罗志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战略与管理》1996 年第 3 期 ,第 45
页 ;后来他亦指出“传统中国政治是否‘专制’及怎样被近代国人视为‘专制’,还需要深入的专门讨论”,见所著《国家与学术 :清季
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第 40 页注 3 ;胡玉娟《“古代国家政治发展道路”学术研讨会综
述》中刘家和、廖学盛与马克 的发言 ,《史学理论研究》2000 年第 3 期 ,第 150、151 页。
甘怀真 :《皇帝制度是否为专制》,《钱穆先生纪念馆刊》第 4 期 ,1996 年 9 月 ,后收入所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 :中国古
代政治史研究》“附录”,台北 ,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 2003 年版 ,第 511 —524 页。此前 ,王尔敏在研究近代民主问题时亦涉及
甲午以后士人对中国历代政体的批判 ,见《晚清士大夫对于近代民主政治的认识》,收入所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91 —195 页。
刘禾 (Lydia H. Liu)著 ,宋伟杰等译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中国 ,1900 —1937)》,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第 45 页。
侯旭东/ 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于擅权 ,并非用来描述君主 ,更不是指一种政治体制。① 现在所说的“专制主义”、“专制政体”乃是
近代引入的新含义 ,是对西方政治学术语“despotism”的翻译 ,“专制君主”则出自英语“despot”一
词。亦有人用“专制主义”翻译英语“absolutism”,实际是错误的 ,该词正确的译称是“绝对主义”或
“绝对君主制”,在欧洲历史上有特定的含义。②
一、西方的“专制政体”说与“中国专制说”
关于“despotism”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来龙去脉 ,前人已有系统的介绍③,不拟详细引述。这
里仅就与本文有关的内容稍作讨论。
追根溯源 ,“despotism”来源于“despot”,最早为希腊语“δ:σπóтηs”④,在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
中就有很多关于它的描述。诚如论者所概括的 :
专制政体很明显的 ,从一开始就是欧洲人用来理解亚洲政府和习俗所用的概念 :一般总认
为 ,欧洲人生来就是自由的 ,而东方人却是有天生的奴性。因而专制政体常常是用来认定、解
释或者指责奴隶制度、对外征服 ,以及殖民或帝国统治。
具体说来 ,“从波希战争那时代开始 ,希腊人就把专制政体看成是带有非希腊特征的一套体制 ,或是
野蛮民族天生奴性的思想 ,亚洲人习惯的王权形式”。⑤ 如亚里斯多德说“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
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 ;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
政体的变态 (偏离) 。这类变态政体都是专制的 [他们以主人管理其奴仆那种方式施行统治 ]
(1279a)”,“在研究君主政体 (王政)时 ,我们也谈到了两种僭主政体 ⋯⋯这两种是 (一) 某些野蛮民
族 (非希腊民族)中所尊崇的具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 ,以及 (二) 在古希腊城邦中曾经一度存在的
类似君主的所谓民选总裁 (1295a)”。⑥
上引希腊语到东罗马帝国时仍一直通行于当地 ,13 世纪出现了《政治学》最早的拉丁文译本 ,
自此 ,“专制”说开始流行于西欧。此后从中世纪至 18 世纪的西欧理论家关于“despotism”的思想不
断得到发展 ,不过 ,此间有些理论家用“专制政体”来谴责西欧的僭主统治 (tyranny) ,也有人继续将
“专制政体”与亚洲国家联系起来 ,此时的靶子则是土耳其帝国 ,其中只有霍布斯 ( Hobbes)赋予该词
正面的意义。⑦
稍后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 (1689 —1755)以专制政体为三种基本的政府形态之一 ,使得专
6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Melvin Richter :“专制政体”(Despotism) ,《观念史大辞典》第 1 卷《政治与法律卷》,第 529、534、535、539 页 ;施治生、郭方 :
《“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1993 年第 3 期 ,第 39 —43 页。
〔希〕亚里斯多德著 ,吴寿彭译 :《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 ,第 132、203 页。
Melvin Richter :“专制政体”(Despotism) ,《观念史大辞典》第 1 卷《政治与法律卷》,第 530、531 页。
Oxf ord English Dictionary (sec. ed. , Oxford : Clarendon Press ,1989) , Vol. IV , p . 533.
Melvin Richter :“专制政体”(Despotism) ,《观念史大辞典》第 1 卷《政治与法律卷》(蔡采秀译) ,台北 ,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1987 年版 ,第 529 —561 页 ;施治生、郭方 :《“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1993 年第 3 期 ,第 36 —55 页。
北成 :《关于“专制君主制”的译名》,《史学理论研究》1996 年第 2 期 ,第 135 —136 页。
参日知《东方专制主义问题———政治学、历史学二千多年来的误解》,收入《中西古典学引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365 —366 页 ;罗志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战略与管理》1996 年第 3 期 ,第 50 —51 页注 1 ;最新的研
究见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解读》,《中国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 ,第 173 —174 页。
2008 年第 4 期
制政体成为 18 世纪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核心主题①,不仅如此 ,他还是西方思想家中第一个将中国
划入“专制政体”的。他说 :“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 ,它的原则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 ,疆域没
有这么辽阔 ,政府的专制的精神也许稍微差些 ;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相反。”② 因此 ,孟德斯鸠被认
为是“从否定方面将中国列入一种世界模式的第一人 ⋯⋯为法国和欧洲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中国
形象”③。其说尽管在当时受到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的反对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则逐渐成为西方人
看待中国的基本前提。18 世纪是西方中国观发生根本变化的世纪 ,即从以“颂华”(sinophilie) 占优
转为以“贬华”(sinophobie)为主。此外 ,他亦认为专制主义是亚洲各国的特点。④
这里有必要对欧洲人的中国观做一扼要的回顾。从 13 世纪的马可·波罗到 18 世纪的西方耶
稣会传教士 ,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主流都是积极的 ,是西方效法学习的对象。⑤ 著名的利玛窦
(1552 —1610)在中国生活了 30 多年 ,在北京居住了 10 年⑥,他根据亲身经历 ,认为明朝万历年间
中国朝廷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他说 :
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 ,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很明显 ,而且下面还要
说得更清楚 ,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虽然所有由大臣制订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
给他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准 ,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 ,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
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 ,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 ,那就
是 :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加对任何人的赐钱 ,或增大其权力 ,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
要求这样做。⑦
即使在 18 世纪的欧洲 ,孟德斯鸠以外的更多的人仍坚持传统的看法。意大利哲学家维科 (1668 —
1744 年)就认为中国的皇帝是最人道的。⑧ 伏尔泰 (1694 —1778) ⑨ 与魁奈 (1694 —1774) 也不同意
孟德斯鸠的判断。魁奈也将中国的政体归为“专制”,不过 ,他所说的“专制”与孟德斯鸠不同 ,含义
近似于“君主制”。魁奈说“用专制一词来称呼中国政府 ,是因为中国的君主独掌国家大权。专制君
主意指主管者或当权者 ,因此这个称呼可以用于执行法定绝对权力的统治者 ,也可以用于篡夺权力
的统治者 ,而后者执政不论好坏 ,其政府都不受基本法则的保护。这样就有合法的专制君主与为所
欲为的或不合法的专制君主之分 ⋯⋯君主、皇帝、国王以及其它等等 ,都是专制君主。”对于中国 ,他
认为“中国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 ,皇帝执行这些法律 ,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守
这些法律。”他还专门设立一节讲“皇帝的绝对权力受到制约”,并对孟德斯鸠的看法加以反驳 ,认为
7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他的看法见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 :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上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66 —72 页。
〔意〕维科著 ,朱光潜译 :《新科学》,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560 页。
详细的介绍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第 48 页。
〔法〕费赖之著 ,冯承钧译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第 38 —40 页。
Colin Mackerras , Western I mages of Chi na (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9) , pp . 11 —37. 张国刚和吴莉苇对
于 18 世纪法国思想家关于中国专制的批判有较详细的介绍 ,见所著《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上海
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293 —301 页。
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上册 ,第 278 —279 页。参施治生、郭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
1993 年第 3 期 ,第 46 —47 页。
钱林祥 :《孟德斯鸠的中国文化观》,《汉学研究》第 2 辑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167 页。
〔法〕孟德斯鸠著 ,张雁深译 :《论法的精神》上册 ,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 ,第 129 页。
Melvin Richter :“专制政体”(Despotism) ,《观念史大辞典》第 1 卷《政治与法律卷》,第 543 页 ;施治生、郭方 :《“东方专制主
义”概念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1993 年第 3 期 ,第 46 —47 页。
侯旭东/ 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他夸大了专制权力。① 此后 ,在 1770 年 ,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公使波特 ( Porte) 也对孟德斯鸠关于
土耳其人专制主义的过分简单化的思想表示反对。②
应该指出 ,除了魁奈与波特 ,孟德斯鸠的论断问世后不久又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 ,一个名叫安
格迪尔 —杜贝隆 (Abraham2Hyacinte Anquetil2Duperron , 1735 —1805) 的法国学者根据他在印度多
年的生活 ,发现欧洲人对印度、土耳其、波斯乃至整个亚洲的宗教、历史与社会、政治制度抱有许多
错误的观念。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 ,对孟德斯鸠提出的“东方专制政体”说的论据做了批驳。他
认为事情的真相是专制政体的概念只被当作工具 ,用以证明欧洲人在亚洲进行的压迫是合理的。③
东方专制说尽管遭到有力的狙击 ,也被证明并无实据 ,但这种批驳的声音最终被欧洲人遗忘 ,
在欧洲人头脑中逐渐占据主流的依然是“东方及中国专制说”。黑格尔与马克思分别继承了这种观
点。黑格尔说“它 (指中国 ———引者)的统治并不是个人的识见 ,而是君主的专制政体”,“中国人既
然是一律平等 ,又没有任何自由 ,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天子实在就是中心 ,各事都由
他来决断 ,国家和人民的福利因此都听命于他”。④ 20 世纪以后 ,对现当代欧美中国研究有深刻而
持久影响的马克斯·韦伯也接受了这一论断 ,他认为“秦王当了皇帝以后 ⋯⋯建立了一个真正的专
制制度 ,取代了古代的神权封建秩序”,在介绍完秦始皇的政策后他又指出 :“这样 ,纯粹东方式苏丹
制的任人唯亲与等级公平和专制独裁相结合的制度似乎就在中国登场了。”⑤ 20 世纪 50 年代 ,在
冷战背景下 ,随着魏特夫 ( Karl Wittf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出版 ,视中华帝国为“专制政体”一度
成为西方学界的流行观点。⑥
西方人 20 世纪以前关于中国的概括 ,无论偏重正面还是负面形象 ,都是在对中国一知半解的
状态下形成的 ,依据主要是几部游记、有限的传教士的通信集与译成西文的若干中国典籍。据研
究 ,孟德斯鸠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靠阅读来华耶稣会士及一些到过中国的商人、游客所写的游记 ,
如柏应理的《中国贤哲孔子》、基尔歇的《中国图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与《耶稣会士书简
集》。此外 ,中国人黄嘉略与返回欧洲的来华耶稣会士傅圣泽对孟德斯鸠的中国观也有重要影
响。⑦ 而魁奈关于中国情况的主要来源 ,甚至可以说唯一的来源就是入华耶稣会士的书信和著
作。⑧ 伏尔泰的情况也是如此。⑨ 因此 ,得出的结论包含相当的想象与幻象的成分。
直至 20 世纪初 ,情况并没有根本的变化。马克斯·韦伯并不通中文 ,研究中国时所依据的是欧
8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张西平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 372 —377 页。
张西平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 393 —394 页。
许明龙 :《欧洲 18 世纪“中国热”》,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39 页 ;张西平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
东方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407 —408 页。
〔美〕魏特夫著 ,徐式谷等译 :《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该书出版 10 年后作者依然在关注“东方
专制主义”问题 ,见 Karl Wittfogel ,“Results and Problems of the Studies of Oriental Despotism”, Journal of Asian S t udies , Vol. 28 ,
No. 2 ( Feb. 1969) , pp . 357 —365。对魏特夫理论的批判 ,参林甘泉《怎样看待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史学理论研究》1995
年第 1 期 ,第 5 —17 页。
〔德〕马克斯·韦伯著 ,洪天富译 :《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54、56 页。
〔德〕黑格尔著 ,王造时译 :《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23、130 —131、132 页 ;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
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64 —67 页 ,马克思在文中提出了“东方专制制度”的说法。
详细介绍见 Franco Venturi ,“Oriental Despot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 Vol. 24 , No. 1 (Jan. —Mar. 1963) ,
pp . 136 —138.
转自〔法〕安田朴著 ,耿升译《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第 497 页 ,并参格力高利·布鲁《“中国”与近代
西方社会思想》,收入〔加〕卜正民与格力高利·布鲁主编 ,古伟瀛等译《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新星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07 —112
页。
〔法〕魁奈著 ,谈敏译 :《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 ,第 1、73 —76、93 —104 页。
2008 年第 4 期
洲学者对少数中国文献的翻译 ,如理雅格 (Legge)译的《中国经典》、沙畹译的《史记》片段 ,及其他欧
洲学者的初步研究①,论说亦包含了许多推断。他们对中国的研究 ———更确切地说是半研究半想
象 ———所经历的变化 ,与其说是因信息丰富而生 ,不如说是随中西力量对比变化而出现的 ,均缺乏
足够的事实依据。尽管如此 ,这些想象下的中国对后来许多西方人 (包括学者) 理解中国历史与现
实都带来挥之不去的深远影响 ,成为认识的起点。
这种论断 ,原本只是 18 世纪西欧个别人并无多少根据的论断 ,如果没有后来的广泛推行 ,处境将
和顾炎武的思想差不多 ,只不过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不会有多大世界性影响。但是随着工业革命与
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 ,包括“中国专制说”在内的西方学说 ,随着西方的商品 ,一同被输送到世界
各地 ,在坚船利炮的辅佐下 ,逐渐成为支配性的话语 ,成为众人俯首称臣而罕加质疑的普遍“真理”。②
这种变化显然不能仅从学理内部加以解释 ,更多的需要考虑思想生存的外在环境。正如萨义
德所说 ,“所有的表述 ,因其是表述 ,都首先受表述者所使用的语言 ,其次受表述者所属的文化、机构
和政治氛围的制约”③。18 世纪末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的发展 ,西方崛起 ,中西力
量对比因而变化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也由羡慕的对象演变成了批判的靶子 ,专制是其中一项重要
“罪名”。④20 世纪 ,特别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 ,以及东西方冷战对立局面的形成 ,这一论断又进
一步沦为西方借以攻击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工具。
二、中国人接受与传播“专制说”的考察
不仅如此 ,关于中国“专制”的想象也经由日本传入中国 ,直接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
响。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在中国仁人志士寻求救国道路之时 ,这种想象的观点通过日本在海外中
国知识分子中产生共鸣 ,并逐步流行开来 ,成为推翻清政府的有力思想武器 ,同时也被用作分析中
国历史、解释落后原因的利器 ,以致演变为一种无须论证的先验结论而传诵至今 ,罕有质疑者。
就目前所见 ,最早将“despotism”翻译为“专制政体”的应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人⑤,19 世纪末逃
亡日本的中国维新人士及留日中国学生最早通过日语接受了这一翻译 ,时间大约是在 1899 年。
1.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思想界对“despotism”的翻译与理解
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日本接受“专制政体”说的具体过程。“专制”一词很早就从中国引入日
本。公元 797 年完成的《续日本纪》卷 7“天正天皇灵龟二年 (716 年) 五月庚寅”条 ,天皇诏书云“自
9
①
②
③
④
⑤ 王力认为现代汉语中的“专制”一词来自日本 ,并确定“专制”是日本人对“autocracy”一词的翻译 ,见《汉语史稿》,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第 521 —522 页 ;刘禾亦接受了王力的观点 ,并将该词归入“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 :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见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中国 ,1900 —1937)》“附录D”,第 406 页。罗志田也有类似的推测 ,见《中国文
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第 45 页。此说并非无据 ,1886 年 ÷ …Ó·赫夫姆 (J . C. Hephurn) 著的《和英语林集成》第 3 版
中就是将“autocracy”译为“专制政治”,见松村明《÷ …Ó著〈和英语林集成〉第 3 版について》,收入所著《近代国语———江户 から现
代へ》,东京 ,樱枫社 1977 年版 ,第 248 页。
将“专制”的英语语源归为“autocracy”在当时是有根据的 ,但并非唯一且通行的语源。更通行的语源应是“despotism”。目前 ,
英语中由于“despotism”的出身带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背景 ,逐渐被弃用 ,转而用“autocracy”表示“专制”的意思。罗志田《中国文化
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对于“专制”说引入中国知识界的过程做了粗略的推测 ,其中忽略了日本的桥梁作用 ,也是需要补
充的。近藤慎一指出“专制”是从日本引进的 ,但未做具体考订 ,见《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 236 页。
Colin Mackerras , Western I mages of Chi na , pp . 38 , 55.
萨义德 :《东方学》,第 349 页。
参格力高利·布鲁《“中国”与近代西方社会思想》,收入卜正民与格力高利·布鲁主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第 90 —91 页。
韦伯所据资料的详细说明见《儒教与道教》,第 3 —5 页注 1。
侯旭东/ 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今以后 ⋯⋯其所有财物田园 ,并须国师、众僧及国司檀越等相对检校 ,分明案记。充用之日 ,共判出
付 ,不得依旧檀越等专制”①,就已使用了该词。1827 年成书的《日本外史》卷 1“源氏前纪”养和元
年亦载 ,清盛临终前说“我自平治年间建功王室 ,专制天下 ,位极人臣 ,为帝者外祖 ,复何所遗憾”云
云。② 不过 ,上述语境中出现的“专制”的含义与中国传统文献中是一致的 ,即独断专行 ,指的往往
是侵夺他人 (多指君主)职权而独断专行 ,并非是一种政体。③
作为政体的“专制”来自明治前后日本知识分子对西方学说的翻译。1861 年 ,日本藩书调所的
洋学者加藤弘之 (1836 —1916)著《邻草》,介绍“世界万国的政体”,称“虽然大凡世界立国无数 ,若论
其政体无外乎君主政治 (洋名 Â ª Ë � } ④)官宰政治 (洋名 Ì • Æ ∂ Ê } � ) 两者 ⋯⋯君主政治的
政体分为君主握权 (洋名 � Ó ≠ º Ë � ƒ Â ª Ë � } ) 上下分权 (洋名 ≠ º Ë � ƒ Â ª Ë � } ) 两
种”。⑤ 7 年后 ,即 1868 年 ,加藤弘之在《立宪政体略》的“政体总论”中则进一步将《邻草》中称为“君
主握权”的政体分做两种 ,改称为“君主擅制”与“君主专治”,并分别予以解释。君主擅制是“君主以
天下为一己之私有 ,而擅制亿兆 ,生杀予夺之权唯心所欲之政体”,君主专治是“君主私有天下 ,其一
人专礼乐、征伐之权 ,其臣民不得参与国事。与君主擅制稍有不同的只是习俗自然成为法律 ,此则
对君权稍有所限制而已”。⑥ 在日语中 ,“擅制”与“专制”发音相同 ,均为“せんせぃ”。1866 年福泽
谕吉所译的《西洋事情》将“despot”音译为“§ � ½ ≤ ¨”,并意译为“立君独裁”。⑦ 1872 年中村正直
翻译穆勒 (John S. Mill)的《自由论》( O n L iberty)为《自由之理》,其中将“despotism”音译为“§ � ½
ƒ � � À”,并意译为“霸政”。⑧ 而 1874 年 12 月 ,尾崎三良 (1842 —1918)在华族会馆所做的关于英
国历史的讲座中有一篇名为“君民同治论”,讲述世界各国的政体 ,其中说到 :“晚近论及国体 ,往往
分为四类 ,曰君主专裁 ,曰君民同治 ,曰贵显共和 ,曰百姓共和。”这里用的是“君主专裁”,下面接着
说 :概括而言 ,为立君、共和两类 ,后文进一步指出 :
政事多出于君主之专断 ,以是或目之为专制之国体 ,以是知其为长君主之私欲、助其无道
的阶梯。
0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原文作“� Ì ° , § � ½ ¡ � À [霸政 ]即 ¡君主己 �意 Ò以 ƒ 为 � ¯ ,凡 �夷狄 ®国暗愚 ®民 Ò治 À ¯正法 ª Ê”。收入
《明治文化全集》第 2 卷“自由民权篇”,东京 ,日本评论新社 1955 年版 ,第 14 页。
福泽谕吉 :《西洋事情》“备考·政治”,庆应二年 (1866)尚古堂出版 ,此据《日本 の名著》33 ,东京 ,中央公论社 1979 年初版 ,
第 357 页。
加藤弘之 :《立宪政体略》,原文做“君主擅制 :君主天下 Ò私有 �亿兆 Ò擅制 � ƒ 生杀与夺 ®权独 Ê其欲 � Ë所 «任 � Ë
者 Ò云 µ。君主专治 :君主天下 Ò私有 �独 Ê礼乐征伐 ®权 Ò专 «� ƒ 臣民 Ò � ƒ 国事 «参与 � Ë ㄟÒ得 � � Á � Ë Â ®Ò云
µ。惟习俗自 É法律 ¨ ª Ê ƒ 稍君权 Ò限制 � Ë所 � Ê、盖 � 擅制 ¨相异 ª Ë所以 ª Ê”。收入《明治文化全集》第 3 卷“政治
篇”,第 18 页。
加藤弘之 :《邻草》,原文做“凡そ世界甚广く国を立ると无算 なりと虽 ども、其政体 を论 ずれぱ君主政治 (洋名 Â ª Ë �
一)官宰政治 (洋名 Ì • Æ ∂ Ê一 � ) の二政体 に外 るµ者 なし⋯⋯君主政治 の政体 は君主握权 (洋名 � Ó ≠ º Ë � ƒ Â ª Ë �
一)上下分权 (洋名 ≠ º Ë � ƒ Â ª Ë �一) の二 ⁄ となり”。收入明治文化研究会编《明治文化全集》第 3 卷“政治篇”,东京 ,日本
评论新社 1955 年版 ,第 6 页。君主政治 (洋名 Â ª Ë �一)原文是荷兰语 monarchie ;君主握权 (洋名 � Ó ≠ º Ë � ƒ ·Â ª Ë �一)
原文是荷兰语 ombeperkte monarchie ;上下分权 (洋名 ≠ º Ë � ƒ ·Â ª Ë �一)原文是荷兰语 beperkte monarchie。关于加藤弘之的
生平 ,参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200 —206 页。
此词现在则做“Â ª } � } ”,是英语“monarchy”的音读。
关于“专擅”一词在日本的《日本书纪》以下的古典文献中的用法与含义 ,参宫村治雄《(新订) 日本政治思想史 :“自由”の
观念を轴にして》,东京 ,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 2005 年版 ,第 12 —18 页。作者注意到“专擅”与古典文献中“自由”在意义上的紧密
联系。
赖山阳 :《日本外史》卷 1 ,日本嘉永元年 (1848 年)刻本 ,第 30 页。
国史大系编修会编 :《续日本纪》“前篇”,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普及版 ,京都 ,吉川弘文馆 1978 年版 ,第 65 页。
2008 年第 4 期
将“君主专裁”称为“专制之国体”,此文次年 (1875 年) 3 月刊登在《会馆记事》第 2 号附录中。① 这
是目前所见最早提出“专制”国体的。前此尾崎三良曾随三条实美的世子留学英国多年 ,此说当是
根据他在英国的见闻与英语说法 ,加上他个人的理解提出的。不过 ,讲稿中“专制的国体”并没有明
确与“despotism”对应起来 ,亦没有和中国联系起来。这一联系一年后因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被
译成日文而突显出来。
1876 年日本人何礼之 (1840 —1923)根据英译本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翻译成日文《万法精
理》时② 开始采用“专制政治”这样的词汇来译“despotism”。译者在《万法精理》卷 2 第 1 回中说 :
政府之三类称为共和政治 ( Ì • ⁄ ∂ Ê ≤ � ) 、立君政治 ( Â ª Ë � } ) 与专制政治 ( § � …
ƒ #〔Ê〕� À) 。③
其中的“§ � …ƒ # � À”就是英语“despotism”的音读 ,译者将其意译为“专制政治”。该书以下部
分反复使用“专制”、“专制政治”一词。在该书卷 8 第 21 回“论支那帝国”中 ,译者根据英译 ,明确将
中国归为专制国家 :
据此所见 ,支那是专制国 ,其精神是畏惧。④
这是笔者所见最早明确将中国政体划归“专制”的日文著作。上引福泽谕吉所著的《西洋事情》中已
将中国 (文中称“支那”)政治归为“立君独裁 ( § � ½ ≤ ¨)”⑤,只是当时还没有将“§ � ½ ≤ ¨”译成
“专制君主”。《西洋事情》在日本幕末至明治时期影响极大⑥,书中的这一观点亦应广为人知。不
过 ,将这种政体固定译为“专制政体”应是到了《万法精理》出版以后。此后 ,专制政体一词逐渐流行
于日本。
1881 年中江兆民发表的《君民共治之说》的开头指出“政体的名称有数种 ,曰立宪 ,曰专制 ,曰
立君 ,曰共和”⑦,便是将专制视为政体。1885 年出版的末广铁肠的政治小说《雪中梅》中就有“不知
1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原文作“政体の名称数种あり,曰く立宪、曰く专制、曰く立君、曰く共和なり”,原载明治十四年 (1881) 三月二十四日《东
洋自由新闻》第 3 号 ,收入《日本现代文学全集 2·福泽谕吉·中江兆民·罔仓天心·德富苏峰集·三宅雪岭》,东京 ,讲谈社 1980 年增
补改订版 ,第 129 页。
参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第 54、83 —84 页。
福氵尺谕吉 :《西洋事情》,第 357 页。原文作“ただ国君一人 の意 に随 いて事 を行 なうものを立君独裁[ § � ½ ≤ ¨ ] と言
う。Í � Ä、支那等のごとき政治、これなり。”
原文作“此 «据 ¡之 Ò见 Ì ¯支那 ¯专制 ®国 «� ƒ ,其元气 ¯畏惧 «”,何礼之译 :《万法精理》卷 8 ,第 30 —31 页。
原文作“Ì • ⁄ ∂ Ê ≤ � (共和政治) ª Ê , Â ª Ë �一 (立君政治) ª Ê , § � …ƒ #〔Ê〕� À(专制政治) ª Ê之 Ò政府 ®
三类 ¨称 �”,何礼之译 :《万法精理》卷 2 ,第 1 页 ,明治九年 (1876)一月刻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图书馆藏。
具体背景与英译本情况 ,参井上幸治《Â Ó ƒ � � Å一の思想的生涯》“前言”,收入《世界の名著》28 ,东京 ,中央公论社 1980
年第 6 版 ,第 8 —9 页。关于何礼之的生平事迹见大久保利谦《幕末英学史上における何礼之—とくに何礼之塾と鹿儿岛英学との交
流—》,收入《大久保利谦历史著作集 5·幕末维新洋学》,京都 ,吉川弘文馆 1986 年版 ,第 345 —367 页。
原文分别作“挽近国体 Ò论 � Ë Â ®、往 四々类 «分≤ 。曰 � 君主专裁、曰 � 君民同治、曰 � 贵显共和、曰 � 百姓共和”,
“政事多 � ¯君主 ®专断 «出 ∞。是 Ò以 ƒ 或 ¯之 Ò目 � ƒ 专制 ®国体 ¨云、以 ƒ 君主 ®私欲 Ò长 �其无道 Ò助 � Ë ®楷梯 ¨为
Ë Ò知 É � 。”见尾崎三良《君民同治论》,收入田中彰、宫地正大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13·历史认识》,东京 ,岩波书店 1991 年版 ,
第 381 —382、385、386 页。
侯旭东/ 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当今西洋事情 ,将专制政治理解为最好的政体”,“不同于立宪政体 ,将专制国家确立为优胜者的地
位”① 之说 ,亦是在政体的意义上使用“专制”一词。1888 年底至 1889 年初陆羯南在《东京电报》上
刊登的评论 (1891 年汇编成《近时宪政考》,作为《近时政论考》的附录出版) 中更是明确提到 ,他是
从何礼之翻译的《万法精理》中吸取的三政体说 ,不过 ,文中作者依然是“擅制”、“专制”混用。②
除了“专制政体”的日译史之外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日本思想界、政界对各种政体的认识。
概括而言 ,自加藤弘之以降 ,明治时期无论日本的思想家还是政治家 ,根据欧美历史发展 ,均视“专
制政体”为落后政体 ,为未开化的国度所采用 ,而立宪政体则是更好的制度。
在前引《立宪政体略》(1868 年) 中 ,加藤弘之在介绍完世界上五种政体 ,即属于“君政”的君主
擅制、君主专治与上下同治 ,属于“民政”的“贵显专治”和“万民共治”后指出 :
在此五种政体中 ,如君主擅制、君主专治与贵显专治等均为未走向开化文明国家的政体。
其中如擅制作为蛮夷的政体属于其中尤为恶贱者。
而“君主专治”则是人文未辟愚蠢的民众众多的国家采用的制度 ,随着逐渐开化 ,转变为上下同治或
万民共治制。作者指出 :
五政体中确实能制定公明正大、确然不拔之国宪 ,以求得真正治安之政体 ,唯有上下同治
与万民同治二政体。因之称之为立宪政体。③
突出了上下同治与万民共治政体的优越性与正当性 ,这种观念成为日后思想界与政治界在讨论国
体、政体问题时的基调。1873 年 11 月 ,即征韩论决裂后次月 ,主政的大久保利通在向政府提交的
“关于立宪政体的意见书”中就指出世界的政体分为君主政治或民主政治 ,政体发展方向是归于民
主 ,至于当时的日本则“维新以来 ⋯⋯我国 ⋯⋯政治依然因袭旧套 ,保留君主擅制政体”,尽管他亦
承认未来应实行“君民共治”,当时依然因循旧制 ,实行的是君主擅 (专) 制政体 ,且认为此制适用于
当时的风俗人情④,自然在他眼中过去的江户时代亦属于君主专制。因当时加藤弘之任天皇侍读 ,
为天皇讲欧美的政体、制度与历史⑤,大久保所使用的“君主擅制”当根据加藤的翻译。1874 年因
征韩论下野的板垣退助等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批评政府为“有司专裁”与“任意放行”,认为
21
①
②
③
④
⑤ 参中村尚美《明治国家の形成と� � �》第 1 章“明治政权の指导理念”三“君民共治体制の主张”,东京 ,龙溪书舍 1991 年
版 ,第 17 —18 页 ;坂田吉雄《天皇亲政 :明治期の天皇观》三“有司专制と君德培养”,京都 ,思文阁出版 1984 年版 ,第 41 页。
明治六年 (1873)十一月《立宪政体に关すゐ意见书》,原文作“维新以来 ⋯⋯我国 ⋯⋯政 ¯依然 � Ë旧套 «因袭 � 、君主
擅制 ®体 Ò存 �”,见日本史籍学会编《大久保利通文书》(五) ,覆刻本 ,东京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8 年版 ,第 183 —185 页。这里大
久保使用的是“君主擅制”,而伊藤博文谈话在引述概括大久保建议的精神时用的则是“君主专制”或“专制”,《大久保利通文书》
(五) ,第 205、206 页。
原文分别作“此五政体中 «于 ƒ 君主擅制、君主专治、贵显专治等 ®如 � ¯ 皆未 � 开化文明 «向 ¯ � Ë国 ®政体 ª Ê。
就中擅制 ®如 � ¯蛮夷 ®政体 «� ƒ 尤 Â恶 À ÷ �贱 À ÷ �  ®ª Ê”、“五政体中公明正大确然不拔 ®国宪 Ò制立 �以 ƒ 真 ®
治安 Ò求 À Ë Â ®¯ 、独 Ê上下同治万民共治 ®二政体 ®¿ 、因 ƒ 之 Ò立宪政体 ¨称 �”,前引《明治文化全集》第 2 卷“政治篇”,
第 19 页。
见陆羯南《近时宪法考》“绪言”及第 4 章《泰西主义及支那主义の注入》,收入西田长寿、植手通有编《陆羯南全集》第 1 卷 ,
东京 , みすず书房 1968 年版 ,第 3 页下、10 页上 ;原发表出处据第 686 页“解说”。
原文作“今日西洋こと何にも知らず、专制政治を无上の政体と心得たり”;“立宪政体の场合と违ひ,专制の邦国 にて优
者の地位に立ち”,《日本近代文学大系 2·明治政治小说集》,东京 ,角川书店 1974 年版 ,第 350、352 页。
2008 年第 4 期
不应以百姓不学无智、未臻开明为由而拒绝设立民选议院①,实际是对执政的大久保利通等施加压
力 ,希望尽快建立代议制政体。这批自由民权派与执政者在政体问题上的区别与其说是目标不同 ,
不如说是在实现途径与方式、实现的速度上有分歧。这一点从 8 年后 ,即 1882 年板垣退助发表的
《自由党组织 の大意》演说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板垣指出确立立宪政体的 7 条障碍 ,其中就指出日
本原来处在封建制 ,而封建制是通过专制来治民②,这一看法与执政的大久保的观点并无根本差
别。实际到了 1890 年 ,著名政论家陆羯南还认为从史迹看 ,古代以来日本人习惯于专制政治 ———
尽管不一定是君主专制 ,因而认为倡导自由、排斥政府干涉的自由论派的思想脱离日本的历史与现
实。③
明治初年以来 ,日本思想界出现不少提倡共和、民选议院以及代议制 ,强调民权的人物 ,亦有将
居于主流的主张君权的帝政论派斥为“专制论派”的说法。④ 各派追求的政体目标相去不远 ,而实
现的途径差别较大 ,却几乎没有人否认“专制”与“专制政体”代表了落后与野蛮。⑤ 此外 ,1889 年明
治宪法颁布以前 ,日本各派思想家提出了许多种《宪法草案》⑥,亦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时人对立宪政
体的追求与渴望。
《明治宪法》颁布后 ,尽管宪法规定天皇的实际权力相当大⑦,近于专制独裁者 ,但在形式上确
立的日本国体是君主立宪制。当时即便是激进的思想家如幸德秋水也只是批评首相伊藤博文为专
制的政治家 ,而不否认日本是立宪政体 ,且这种声音极其微弱 ,更重要的是当时几乎没有人公开批
评日本国体的专制性⑧,思想界与社会主流对明治体制 ,对于天皇的权力是认同和支持的⑨。可以
说 ,从加藤弘之最早介绍西方政体学说以来 ,“擅 (专)制”便成为描述政体或政治时一带有负面意义
的词汇 ,位于政体进化链条的低端 ,而立宪政体则处在更高的位置上 ,对应于文明与开化。
总之 ,如果不考虑政治的实际运作状况 ,幕末明治初年以来 ,通过翻译、学习西方政治思想 ,特
别是政体进化思想 ,日本思想界与政界接受了“专制政体”说 ,并视之为未开化国家实行的落后政
体。译成日文的西方学说中亦包含将中国归入此一政体的内容。在这一思想氛围下抵达日本的中
国留学生与维新派等自然难免其影响 ,他们后来主要从负面接受“专制政体”观念与“中国专制说”,
3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当时生活在日本的梁启超亦认同日本的政体 ,见《答某君问德国日本裁抑民权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 ,中华书局
1945 年版 ,第 53 —54 页。并见陆羯南《近时政论考》,第 51 页上。
时至今日 ,日本学界对于明治时期国体的研究依然很少称之为“专制”政体 ,反而是日本以外的学术界多持此说 ,见殷燕
军《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第 8 —12、202 —206 页。
《明治宪法》条文见家永三郎等《明治前期の宪法构想》“附录”,第 435 —440 页 ,分析参殷燕军《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175 —189、206 —213 页。
详见家永三郎、松永昌三、江村荣一编《明治前期の宪法构想》(增订第 2 版) ,东京 ,福村出版 1987 年版。
如自由论派、改进论派与帝政论派均主张立宪制 ,只是前两派强调的是个人自由 ,后者突出国家主义 ,见《近时政论考》,
第 53 页下—54 页上 ;甚至连思想转向后的加藤弘之也还是主张“立宪的族父统治的政体”,参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
景》,第 215 页 ;亦有如中村正直者 ,认为提高人民素质为首要任务 ,改革政体应放在第二位的思想家 ,郑匡民 :《梁启超启蒙思想的
东学背景》,第 107 页 ;只有少数 ,如陆羯南所代表的国民论派 ,认为“专制”有些正面价值 ,见前引《近时政论考》,第 68 页。
参陆羯南《近时政论考》,第 41 —46、47 —55 页 ;关于当时政论的分析亦参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第 122 —
135 页。
陆羯南评论自由论派时语 ,原发表在明治 23 年 (1890) 8 月 11 日《日本》,收入前引《陆羯南全集》第 1 卷 ,第 51 页下、689
页。
板垣退助 :《自由党组织の大意》,收入井出孙六编《思想 の海 へ“解放 と变革”》7《自由自治元年 の梦》,东京 ,社会评论社
1991 年版 ,第 82 —83 页。
板垣退助等 :《民选议院设立建白》,收入植手通有编《思想 の海 へ“解放 と变革”》6《明治草创 = 启蒙 と反乱》,东京 ,社会
评论社 1990 年版 ,第 135 —139 页。
侯旭东/ 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应与此背景不无联系。
此外 ,18 世纪以来日本的国学派思想家不断地贬低中国历史与政治 ,视之为“恶之国”①,加之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落败 ,使得无论从现实 ,还是透过日本 ,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的更多是中国的负
面形象与表述。可以说 ,日本思想界的翻译与认识成为后来中国思想界流行的“专制主义”、“专制
政体”说的直接源头。
2. 清末中国思想界对“专制说”的接受与传播
在近代接触西方之前 ,中国人头脑中并没有政体的观念 ,以往文献中的“政体”指的是为政的要
领 ,与国家政权的构成没有关系。梁启超说“中国自古及今惟有一政体 ,故政体分类之说 ,中国人脑
识中所未尝有也”②,确有几分道理。其实 ,中国不仅没有政体分类的观念 ,恐怕连政体的观念也不
曾存在。近代海开以后才逐渐对此有所了解 ,王韬是较早介绍西方立国原则的知识分子。③ 当时
人们所接受的政体说是君主、民主与君民共主三类说。④
在这种新知识的影响下 ,遭遇甲午战争惨败的刺激 ,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政治 ,此
时一个重要现象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等人的思想盛行一时 ,成为人们批判传统制度的武器。⑤
不过 ,此时黄宗羲等人的思想的重新兴起 ,是带有实用目的的“比附”,包含了对其说的许多拔高。
正如陈旭麓所指出的 ,“近代中国的民主不是从黄宗羲等人的思想直接孕育出来的 ,乃是由转述西
方思想及其政制为起点 ,是在西方民主思想传入之后才去追溯中国固有的民主思想 ,在其开始 ,且
怀有与视其它西方事物为中国古已有之的同样心理 ,说尧舜禅让就是民选总统 ,明堂则是议院的先
河。”⑥
由于黄宗羲等锋芒所指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为君者 ,而非具体的某个“君”,受到其说的启发 ,
并借助于西方引进的新思想 ,维新派知识分子开始从总体上批判中国的君权 ,这为数年后接受将秦
以来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概括为“专制”的观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谭嗣同在 1896 —1897 年完成的《仁学》中说 ,“两千年来之政 ,秦政也 ,皆大盗也”,“西人辄诋中
国君权太重 ,父权太重 ⋯⋯二千年来君臣一伦 ,尤为黑暗否塞 ,无复人理 ,沿及今兹 ,方愈剧矣”,提
出“废君统 ,倡民主 ,变不平等为平等”。⑦ 二千年来的政治就是“秦政”,就是大强盗 ,这里已是将两
千年的政体一以贯之 ,加以概括 ,且表现出了强烈的反传统的态度 ,充满了感情色彩。此说承袭了
明末唐甄《潜书》中的思想 ,并补充了西方的“民主”、“平等”等观念 ,而他的其他观点亦明显继承了
黄宗羲的思想。⑧ 当时严复、梁启超也持类似的看法。梁启超在《与严幼陵先生书》(1896 年) 中引
4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侯外庐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11 页。王尔敏亦指出当时其他人的类似论述 ,参《晚清政治
思想史论》,第 191 —195 页。
蔡尚思、方行编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第 337 页。
见《陈旭麓文集》第 4 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209 —210 页。沟口雄三亦有类似的批评 ,见《中国前近代思
想的屈折与展开》,收入《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索介然、龚颖译) ,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第 234 —236 页。关于黄宗羲等人的思
想有许多溢美的评价 ,比较确当的分析见张师伟《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具体情况可参朱维铮《在晚清思想界的黄宗羲》,收入所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
第 356 —358 页 ;朱俊瑞《黄宗羲的“君主论”对戊戌维新思想家的影响》,《福建论坛》2000 年第 2 期 ,第 44 —48 页 ;谢贵安《〈明夷待
访录〉的近代“误读”与“新民本”思想的历史影响》,《哲学研究》2003 年第 2 期 ,第 52 —57 页。
参耿云志等《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17 —19 页 ;近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
第 238 —240 页。
王韬 :《重民下》,《 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18 —19 页。此书最早刊行于 1882 年。
梁启超 :《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第 60 页。
牛建科 :《试析日本国学家的中国观》,《延边大学学报》2007 年第 4 期 ,第 9 —14 页。
2008 年第 4 期
严复看法 ,并表认同 :“先生谓黄种之所以衰 ,虽千因万缘 ,皆可归狱于君主 ,此诚悬之日月不刊之言
矣。”① 一年后 ,他在《西政丛书叙》中又有进一步的论述 ,说 :“中国三代尚已 ,秦汉以后 ,取天下于
马上 ,制一切之法 ,草一切律则 ,咸为王者一身之私计 ,而不复知有民事。其君臣又无深心远略 ,思
革前代之弊 ,成新王之规 ,徒因陋就简 ,委靡废弛 ,其上焉者 ,补苴罅漏 ,涂饰耳目 ,故千疮百孔 ,代甚
一代 ,二千年来之中国 ,虽谓之无政焉可已”②,对秦汉以下的中国政治持全盘否定态度。梁氏此说
或许是受到谭嗣同的直接影响。③ 此后无论改良派、革命派在概括中国历代政体时均沿袭了这种思
维方式 ,只是此时尚没有使用“专制”一词来概括中国政体④,却在思想上为接受“专制”说做了铺垫。
就笔者所知 ,日本出现的“专制政体”说在 1899 年首先为梁启超所注意。⑤ 此前的 1897 年 ,他
根据严复的译著 ,了解到欧洲政制有三种。他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中说 :“严复曰 ,欧洲政制 ,
向分三种 ,曰满那弃者 (疑指“monarchy”———引者) ,一君治民之制也 ;曰巫理斯托格拉时者 ,世族贵
人共和之制也 ;曰德谟格拉时者 ,国民为政之制也。”⑥ 此时他并没有区分出君主独揽大权的政制 ,
而只是说“专行君政之国”,并未云“专制”国。而到了 1899 年 ,他在该年 4 月 20 日出版的《清议报》
发表的译作《各国宪法异同论》的前言中说 :
故苟凡属国家之大典 ,无论其为专制政体 (旧译为君主之国) ,为立宪政体 (旧译为君官共
主之国⑦) ,为共和政体 (旧译为民主之国) ,似皆可称为宪法。
在正文第一章“政体”中 ,又有 :
政体之种类 ,昔人虽分为多种 ,然按之今日之各国 ,实不外君主国与共和国之二大类而已。
其中于君主国之内又分为专制君主、立宪君主之二小类。
随后简单介绍了欧洲诸国从专制发展到立宪的情况。⑧ 文中梁启超首次使用了“专制政体”、“专制
5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引自《清议报》第 12 册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67 年影印本 ,第 2 册 ,第 747 页。这三种政体的“旧译”最早似出自王韬《重民
下》,《 园文录外编》,第 18 —19 页。唯“君官共主”,王韬做“君民共主”。
“君官共主”疑误。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 71 页载此文则做“君民共主之国”,似应从之。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 ,第 10 页。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 ,1898 年 8 月)中有“吾国行专制政体 ,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 ,国安
得不弱 ?”(收入康有为《戊戌奏稿》,此据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第 338 页) 似乎使用“专制政体”一说要
早于梁启超 ,但据黄彰健等的研究 ,该折内容为康有为逃亡日本后改写的 ,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增订本)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687 —689、902 —903、916 页 ;孔祥吉《〈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收入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
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292 —294 页。故可不置论。
参耿云志等《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第 32 —33 页 ,作者在这里依然使用了“批判封建专制”一类的说法 ,但实际上当时并未
出现“专制”一词。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仍然在大臣独断意义上使用“专制”一词 ,如《日本国志》卷 3“国统志”,“(明治十年)是年复
开地方官会议”注云“政府欲以地方官会议为议院始基 ,稍变官吏专制之治 ,藉以塞民权自由之口”,后面注文又云“而政权所属 ,上不
能专制于朝廷 ,次不能委寄于臣隶 ,又不得不采泰西上下议院之法以渐变君民共主之局。”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
(96)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4 年版 ,第 125、126 页。
张灏指出 ,虽然《仁学》在谭嗣同死后发表 ,但梁在此之前对它的内容和一些主要思想早已相当熟悉。梁启超后来认为《仁
学》在他的思想形成中是最有影响的著作。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 —1907)》,第 44 —45 页。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 ,第 62 —63 页。关于梁启超批判王权的分析 ,见张灏著 ,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与中
国思想的过渡 (1890 —1907)》,新星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68 —69 页。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第 108 页。
侯旭东/ 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君主”、“专制国”等词。① 应该说 ,按照此文的观点 ,君主国只有专制君主与立宪君主两类 ,且专制
乃是政体发展的必经阶段 ,可自然引申出中国为专制国、专制政体的结论 ,因为中国是君主国且无
宪法。由于上述政体分类中已将“立宪君主国”从“君主国”分出 ,余下的所有“君主国”就都是“专制
君主国”了。据此 ,梁启超在前言中指出的看来并不是完全对应的新旧译法 ,尤其是在内涵与外延
之间有相当的不同的专制政体与旧译君主之国间的对应 ,实际也能解释得通。君主之国即严复所
说的“满那弃”,是“一君治民之制”,专制政体只是其中君权极度发达的一种形态。梁启超将两者对
应起来 ,似乎为他将中国君主统治归为专制做了铺垫。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下文所揭示的他在中国
政体归属上的摇摆。依梁启超的这种对应 ,专制说自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时起就有些含混乃至
误解。稍后 ,梁启超在 9 月 15 日《清议报》上发表的《草茅危言》中首次指出 ,中国三千年历史就是
专制独裁统治。该文开头说文章录自日本深山虎太郎发表在《亚东时报》上的文章 ,实际夹杂了不
少梁启超个人的话。其中指出 :
今欲举秦汉以来积弊 ,摧陷而廓清之 ,以举自强维新之政 ,则必自恢复民权始 ⋯⋯余尝读
史 ,汉以下历朝帝王不下数百人 ,而求其聪明睿知天下真主者 ,百中仅得一二耳。中材之君则
百五六 ,庸劣之主则百九十矣。故天下百年而无十年之治 ⋯⋯若有人于此 ,其力能摆脱三千年
宿敝 ,变专制独裁之治 ,作众思公议之政 ,中国之天下不足治也。②
这里梁启超首次将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归纳为“专制独裁之治”。应该说此时梁启超对中国政体的
认识尚处在游移状态 ,同年 12 月 13 日他在《清议报》发表《蒙的斯鸠之学说》一文 ,在介绍孟德斯鸠
的三大政体说 ,即专制政体、立君政体与共和政体的同时 ,也加了一些按语 ,其中有 :
任案 :蒙氏所谓立君政体者 ,颇近于中国二千年来之政体。其实亦与专制者相去一间耳。
若英国之君民共治不与此同科也。窝的儿尝评之曰 ,蒙氏所论专制立君二者 ,其性质实相同 ,
特其手段稍异耳。③
梁启超介绍孟德斯鸠的学说依据的应是前引何礼之的日译本。称《论法的精神》一书为《万法精理》
当是据何礼之而来 ;孟氏的三大政体 ,梁启超用的是“专制政体”、“立君政体”与“共和政体”,基本依
照何礼之的译法 ,只是将“政治”改为“政体”,人名则没有照用何译 ,而做“蒙的斯鸠”。这里 ,梁启超
又将中国历代政体归入“立君政体”,即通常所说的“君主政体”,并说与专制政体差距不大 ,说明此
时梁启超对这一问题尚无确定一致的看法。④
这种情况到 1901 年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明显趋于一致。值
61
①
②
③
④ 1902 年梁启超又撰文详细介绍了孟德斯鸠的学说 ,见《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 ,第
18 —27 页。
《蒙的斯鸠之学说》,《清议报》第 32 册 ,影印本 ,第 4 册 ,第 2078 页。
《草茅危言》,《清议报》第 27 册 ,影印本 ,第 4 册 ,第 1746 —1747 页。
徐复观对此做过考察 ,他认为“专制政体一名之使用或即始于梁氏 (指梁启超———引者) ;而其取义则系来自西方 ,殆无可
疑”,时间是 1899 年 ,并举此文为证。徐复观对这种轻率地比附中西政体的做法也持批评态度。均见所著《两汉思想史》第 1 卷
“中西专制的不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76 —77 页。近藤慎一亦认为最早在 1899 年 4 月为梁启超所使用 ,出自对
欧美政治学说的介绍 ,具体则是伯伦知理的《国家论》,见《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 241 页。近藤似没有注意到《各国宪法
异同论》一文。
2008 年第 4 期
得注意的是在 1900 年 12 月发行的、由中国留日学生编辑的《译书汇编》第 1 卷第 1 期上开始连载
《万法精理》的最早的中译本。据《万法精理》译文按语 ,这个中译本依据的是何礼之的日文本。①
中译本一共连载了 3 期 ,到 1901 年 4 月出版的第 1 卷第 3 期中止。全书只翻译了前 4 章 ,相当于
译完 1961 年张雁深译本的第 4 章“教育的法律应该和政体的原则相适应”。这个译本沿用了何礼
之的译法 ,称 :
万国政府之形质 ,可以三大别概括之 ,曰共和政治 ,曰立君政治 ,曰专制政治 ⋯⋯以一人之
喜怒裁决政务 ,不受法律之节制 ,而唯〔为〕所欲为者 ,专制政治也。②
译文中论及专制政治之处很多 ,如“专制政治 ,无所谓法宪以定其基本 ,自无所谓府库以藏其法
宪。故此类邦国宗教常有大权。宗教者即彼所谓法宪之府库而为一线之延者也。不然 ,则必有一
定之风俗习尚而不让于法律之权力者”。又说 :
专制政治之所以为专制者 ,君主以一人而有无限之君权 ,又以行此君权之权力 ,举而再委
诸一人。其人居至尊之地 ,其外皆仆妾也。彼其意一若万事唯我一身 ,一身之外 ,无复有他人
者 ,则虽欲不骄盈矜夸 ,不涂聪塞明 ,不可得也。故专制君主 ,怠于政务而不顾 ,亦出于必然之
势。当是时也 ,设官分职 ,以理庶事 ,同僚之间 ,争竞无已 ,莫不逞其私智 ,上以固其恩宠 ,下以
恣其威福 ,故君主不得不亲揽大权 ,不得已则举国而听之于冢宰 ,使之专决政事 ,其权与人主
同。东方诸国大抵如斯。③
由于《万法精理》中译本只有前 4 章 ,所以没有涉及何礼之日译本中关于“中华帝国是专制国”部分。
不过 ,上引一段已将东方诸国归入“专制政治”之列 ,不能不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联想。更为直接的
是 ,《译书汇编》第 1 卷第 1 期刊登的日本人鸟谷部铣太郎的《政治学提纲》就明确将“中国”视为专
制国。他说 :
又吾人所不可不知者 ,第一 ,近代之君主政体 ,如古代之用专制至极点者亦甚少。除俄国、
支那、土耳其数国外 ,大抵皆以宪法为主 ⋯⋯所以如俄国、支那、土耳其等数国之专制政体 ,在
今日已可称为各国例外之政体 ,将来亦不得不变 ⋯⋯今日之世界 ,专制政体居十分之一 ,立宪
政体居十分之七八。专制已败 ,立宪已胜 ,故专制之后 ,必成立宪也无疑矣。④
鸟谷部铣太郎的论述不仅明确将中国政体定性 ,并进一步以世界大势为据 ,指出这一政体必将为立
宪所取代 ,提出了变革的方向。这种论断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没有启发与帮助。
受以上思想资源的刺激与启发 ,约自 1901 年起 ,“专制”说逐渐为中国的海外知识分子所了解 ,
71
①
②
③
④ 《译书汇编》第 1 卷第 1 期 ,1900 年 12 月 ,第 24 —25 页。
以上分见《译书汇编》第 1 卷第 1 期 ,1900 年 12 月 ,第 54 —55 页。
《译书汇编》第 1 卷第 1 期 ,1900 年 12 月 ,第 41 页。
《译书汇编》第 1 卷第 1 期 ,1900 年 12 月 ,第 35 页。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关于《译书汇编》的一般情况 ,参丁守和《〈译书
汇编〉宣传西学提倡改革》,收入所著《中国近代思潮论》,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446 —461 页。
侯旭东/ 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并迅速成为他们批判的武器。① 1901 年 5 月 10 日《国民报》第 1 期刊出的《二十世纪之中国》说 :
嬴秦暴兴以降 ,独夫民贼无代不作 ,率皆敝屣公理 ,私土地、人民为己有 ,使天下之人 ,知有
朝廷不知有国家 ;又恐其民之秀杰者 ,不满于己之所为 ,乃施以种种牢笼、束缚、压制、威胁之
术 ,以便其私图。故夫学术者 ,所以智民也 ,而民贼愚之。取古先儒言论之最便于己者 ,作一姓
机关之学术 ;利于民者 ,辟之为邪说 ;专以柔顺为教 ,养成奴隶之性质 ,以便供己轭束役使之用
⋯⋯中国二千年之学术、政治、法律及一切 ,一人一家之私教养成之者也。
作者在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时并没有使用“专制”一词 ,不过其具体描述与后来“专制”说所概括的
并无区别。作者显然了解“专制政体”,他在后面叙述欧洲历史时多次提到“专制”问题 ,如“十八世
纪之末 ,大革命起 ,倡自由平等之义者 ,声震全欧 ,列国专制之君闻声震骇 ⋯⋯于是列国乘之缔结维
也纳大同盟 ,主张君主专制之政体 ,将以全欧国力 ,压抑民权之说”等等。② 一个月以后 ,即 1901 年
6 月 10 日《国民报》第 2 期刊登的《说国民》一文引述流行观点则直接将中国自秦以来的政体归为
“专制”。文云 :“说者曰 :秦汉以来 ,中国人之屈服于专制者 ,二千年于兹矣 ,故每谓三代以前有国
民 ,而嬴秦以后无国民。”③ 此文发表上距《万法精理》中译本问世只有半年。
此后 ,各种批判中国历代“专制”的文章不断见诸在日中国知识分子所办的各种报纸。
梁启超在 1902 年 5、6、10 月第 8、9、17 号《新民丛报》及 1904 年 6 月第 49 号《新民丛报》发表
了《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在 1902 年 11 月第 21 号《新民丛报》又发表了《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
君主而无一利》。前文中他提到了孟德斯鸠对政体的分类 ,后文中作者根据史书记载 ,对二千年的
政治制度做了一番宏观概括。他说“今民间稍有知识者 ,莫不痛心疾首于专制政体。其恶之也 ,殆
以此为吾害也”,并将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均归结为专制之祸 :
中国数千年君统 ,所以屡经衰乱灭绝者 ,其厉阶有十 ,而外夷 衅、流贼揭竿两者不与焉。
一曰贵族专政 ,二曰女主擅权 ,三曰嫡庶争位 ,四曰统绝拥立 ,五曰宗藩移国 ,六曰权臣篡弑 ,七
曰军人跋扈 (如唐藩镇之类) ,八曰外戚横恣 ,九曰佥壬 削 (如李林甫、卢 之类) ,十曰宦寺盗
柄。此十者 ,殆历代所以亡国之根原。凡叔季之朝廷 ,未有不居一于是者也。至求此十种恶现
象所以发生之由 ,莫不在专制政体。专制政体者 ,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原也。④
以下 ,梁启超历数各代衰亡的原由 ,最终无不落实在专制政体上 ,所谓“中国君统之乱本何在 ? 在彼
十种恶业。十种恶业之乱本何在 ? 在专制政体。专制政体一去 ,则彼十种者无所附以自存 ,不必以
人力防之也。”“苟非专制政体 ,则此十种恶现象者 ,自一扫而空 ;若是乎 ,吾中国数千年脓血之历史 ,
果无一事焉而非专制政体贻之毒也。”⑤ 此文痛快淋漓 ,可以说是声讨中国二千年专制政体的一篇
战斗檄文 ,其思路与观点对时人的影响不可低估。应该说 ,此文对于中国的专制历史做了系统的梳
81
①
②
③
④
⑤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第 93、95 页。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第 90 页。
《时论选集》第 1 卷上册 ,第 76 页。
张 、王忍之编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以下简称《时论选集》)第 1 卷上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3 年版 ,
第 67 —68、70 页。
关于《译书汇编》的影响 ,近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 242 页有扼要的分析。
2008 年第 4 期
理 ,此后 ,知识分子则更多是直接接受这一论断 ,基于“专制”说展开论述。
1903 年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也接受了中国“专制”说 ,此前他多次谈到或写到政体与朝廷情
况 ,他只是称为“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没有提到“专制”。① 1903 年 9 月 21 日他在《支那保全分割
合论》一文中说 :
支那国制 ,自秦政灭六国 ,废封建而为郡县 ,焚书坑儒 ,务愚黔首 ,以行专制。历代因之 ,视
国家为一人之产业 ,制度立法 ,多在防范人民 ,以保全此私产 ;而民生庶务 ,与一姓之存亡无关
者 ,政府置而不问 ,人民亦从无监督政府之措施者。故国自为国 ,民自为民 ,国政庶事 ,俨分两
途 ,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别。②
这里孙中山第一次提出秦行“专制”。数月后他在檀香山发表演说 ,亦云 :
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 ,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 ,效法美国选举总统 ,废除专制 ,实行共
和。③
此时“专制”已是与“共和”相对的制度 ,不过 ,孙中山尚没有明确将中国数千年帝王统治归为“专
制”。到了 1906 年 ,他也如梁启超 ,开始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 ,这种政体 ,不是平等
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④。此后 ,专制成为他所常用的概念。
这种论断出现不久就迅速开始在国内传播 ,传播的桥头堡应是上海。1900 年郑观应出版了
《盛世危言》8 卷本 ,增加了《自强论》一篇 ,其中指出 :“论者谓变法之易 ,莫如专制政治。所言不为
无见 ,然蒙谓专制政治 ,究不如立君政治之公。何则 ? 专制政治即君主之国 ,乾纲独断 ,令出而人莫
敢违。”“蒙谓”当是指孟德斯鸠 ,看来他亦是从孟氏思想论著中接受的“专制”论。此前 ,作者心目中
的政体概念还是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 (14 卷本《议院上》) ,此时作者尽管已经接受了
“专制政治”这个概念 ,却没有明确将中国视为专制政治 ,或是有所忌惮 ,或是抱有幻想。⑤
1902 年甘韩编撰的《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收入了前引《国民报》刊发的《论二十世纪之中国》、
《说国民》等文 ,包含了抨击秦以来二千年专制的内容 ,此外 ,《君民权平议》与《尊民权》亦从不同角
度批判专制 ,伸张民权。其中所收《孟德斯鸠学说》更是用相当篇幅介绍了孟氏三大政体说。⑥
1903 年邹容所著《革命军》在上海出版 ,其一开篇就说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 ,脱去数千年
种种之奴隶性质”,后面回顾历史指出“自秦始统一宇宙 ,悍然尊大 ,鞭笞宇内 ,私其国 ,奴其民 ,为专
制政体 ,多援符瑞不经之说 ,愚弄黔首 ,矫诬天命 ,搀国人所有而独有之 ,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
9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甘韩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 18“民政”,第 3 页下—8 页上、14 页下—16 页上 ,卷 4“法律”,第 13 页上—19 页下 ,商绛
雪斋书局 1902 年刻本。收入卷 4 的《孟德斯鸠学说》一文作者不详 ,似非梁启超。
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解读》第 173 页指出 ,1892 年郑观应《盛世危言》就多次提到君主“专制”,不确。引文出自郑
观应著、王贻梁评注《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111 页及第 112 页注释 1。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1906 年 12 月 2 日)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 ,第 325 页。
《在檀香山正埠荷梯厘街戏院的演说》(1903 年 12 月 13 日)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 ,第 226 页。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 ,第 220 页。
如《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1897 年初) 、《中国的现在与将来》(1897 年 3 月 1 日) 、《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
(1897 年 8 月下旬) ,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 1 卷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第 86、87 —106、172 —173
页。
侯旭东/ 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业”,而他思想来源是 :“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得斯鸠‘万法精理’⋯⋯等书译而读之
也”,理论基础是 :“一国之政治机关 ,一国之人共司之 ,苟不能司政治机关 ,参预行政权者 ,不得谓之
国 ,不得谓之国民 ,此世界之公理 ,万国所同然也。”① 其上述思想亦应是源于孟德斯鸠等的著作甚
明。
1903 年发表于上海《国民日报》,并收入次年《国民日日报汇编》第 1 集的无畏 (刘师培) 的《黄
帝纪年论》亦说 :“中国政体 ,达于专制极点 ,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今纪年用黄帝 ,则君主年
号 ,徒属空文 ,当王者贵之说 ,将不击而自破矣。”② 这亦是出于反对专制提出要改用黄帝纪年。时
人的思考已经从抽象的“专制政体”发展到对其具体表现的改造 ,可见“专制政体”说已成为思考的
一个支点 ,表明该说已深入人心。
又如同年发表于该报 ,后收入《国民日日报汇编》第 2 集的《中国古代限抑君权之法》说 :“环地
球而国者以百数 ,而专制之国 ,独以亚洲为多 ;环亚洲而国者以十数 ,而专制之国 ,又以中国为最
⋯⋯及秦有天下 ,变封建而为统一 ,地方分权之制变为中央集权之制 ,君民共主之世变为君权专制
之世 ⋯⋯至秦而民权尽亡 ,及宋而臣权尽亡 ,至明末而汉人之权尽亡 ,凌夷至今 ,遂成一君权专制达
于完全极点之时代。”以下则述历代限制君权的思想以及怂恿发展君权的思想 ,以证明“专制之祸”
“溯其原因 ,皆起于中国人民之思想”。③ 这亦是以中国为“专制政体”作为论述的出发点。作者的
分析将政体的不同落实在空间上 ,特别是将“专制之国”与亚洲联系起来 ,有明显的“自我矮化”的味
道。
此后 ,专门论述中国历代专制的文章虽已不多 ,但正如熊范与 1907 年所说 :“今日中国救亡之
道 ,首在改革政体。斯说也 ,固已成为今日舆论之势力。”④许多文章都是以此为立论的一个前提。
如 1905 年 2 月孟晋在《论改良政俗自上自下之难易》一文中指出 :“然观我政府 ,自数千年专制以
来 ,积习相沿 ,已若牢不可破。”⑤ 同年 10 月孙中山在《民报》第 1 号发刊词中说 :“今者中国以千年
专制之毒而不解 ,异族残之 ,外邦逼之。”⑥ 1906 年 1 月觉民的《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一文称 :“夫
专制流毒之浸淫于中国者 ,二千有余载矣。”⑦ 同年 4 月署名扑满的《革命横议发难篇》一文亦说 :
“中国自秦以来 ,专制之术 ,日益进化 ,君之所以待其民者 ,无虑皆钤制束缚之策也。”⑧ 1907 年 5 月
署名与之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一文认为 :“中国夙以专制国闻于天下 ,近数年来 ,自
由民权之学说 ,膨胀于国民之脑中 ,莫不愤慨于国权之衰弱 ,而切齿于政府之腐败者。”⑨
除了批判“专制政体”,亦有人提出应利用“专制”以实现“立宪”,显示了更为深入的思考。1905
年 5 月刊发的 生《利用中国之政教论》一文亦指出 :“吾中国之政教 ,可以一语蔽之曰 ,寡人专制。”
不过 ,作者不赞成“立宪而后中国可兴”的主张 ,提出“中国兴而后可立宪”,具体做法是“莫如即专制
之政教 ,而因以为功”,通过专制的力量发展教育 ,不适于生存者 ,“一以专制之力戋刂绝之”,“其有合
0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新民丛报》第 4 年第 20 号 ,1907 年 5 月 ,第 30 页 ,国家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下同。
《民报》第 3 号 ,影印本 ,第 7 —8 页。
《东方杂志》第 2 年第 12 期 ,1906 年 1 月 ,“社说”,第 246 页。
《民报》第 1 号 ,影印本 ,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第 2 页。
《东方杂志》第 2 年第 1 期 ,1905 年 2 月 ,“社说”,第 1 页 ,国家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下同。
《国会与地方自治》,1907 年 5 月《中国新报》第 5 期 ,“论说四”,第 87 页 ,国家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下同。
《国民日日报汇编》第 2 集 ,第 342 —343、349 页。
《国民日日报汇编》第 1 集 ,影印本 ,收入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A15. 1 ,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
编纂委员会 1968 年版 ,第 276 页。
《时论选集》第 1 卷下册 ,第 651、652 —653、654 页。
2008 年第 4 期
于强国者 ,一以专制之力提倡之”,并批评说“世人不察 ,徒诟厉专制之政教 ,欲举一切蹂躏之 ,盖亦
炫于立宪之美名 ,而不知所处耳”。① 其说认识到立宪无法一蹴而就 ,需利用专制力量 ,较之简单的
批判要深刻得多 ,在当时也显得另类。1906 年 1 月刊出的章太炎《演说录》亦云 :“我个中国政治 ,
总是君权专制 ,本没有甚么可贵 ⋯⋯(但) 不好将专制政府所行的事 ,一概抹杀。就是将来建设政
府 ,那项须要改良 ,那项须要复古 ,必得胸有成竹 ,才可以见诸施行。”② 这也是超越了全盘否定的
二元对立观。但是 ,这种看法并非主流。
其实 ,同在 1905 年 ,最早将中国归入专制政体并加以批判的梁启超在游历美国目睹其民主制
度的弊端与旅美华人的状况后 ,思想亦发生了相当的变化。他在该年发表的《开明专制论》中指出
中国民智不开 ,施政机关未整备 ,实行君主立宪的条件尚不具备 ,转而歌颂开明专制的优点 ,希望通
过一强大而开明的朝廷来行使国家主权 ,抗衡西方。③ 此说看似倒退 ,实际反映了梁启超更深的观
察与思考。不过 ,衬托在当时主张立宪与革命的两派的高亢旋律下 ,这类声音颇为微弱。其实 ,孙
中山后来所说的“训政”的含义与梁启超的“开明专制”并无原则性的差别 ,两人的区别只在于实现
的途径不同 :孙是在推翻清朝后实行 ,而梁则寄希望于清廷。
20 世纪初 ,上海的报刊与日本的中文报刊内外呼应 ,一道成为传播“专制”说的阵地。
经过几年的宣传 ,尽管在如何对待“专制”上意见并未统一 ,但视中国过去二千年为专制上并无
异词。此说影响之大不仅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力主此说 ,就是如康有为、黄遵宪与杨度这样反对革
命 ,倡导保皇改良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向此说低头。
早在 1902 年 9 月发表的《辨革命书》中 ,康有为就称 :“又历朝皆少失德 ,无有汉桓、灵 ,唐高、
玄 ,宋徽、光 ,明武、 之昏淫者。若夫政治专制之不善 ,全由汉、唐、宋、明之旧 ,而非满洲特制
也。”④ 强调专制并非满族所创设 ,而是沿袭汉代以来的旧制 ,潜台词并不否认中国自汉代以来就
存在“政治专制”。次年 1 月 13 日黄遵宪在《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中说 :“吾非不知中国专制之害 ,
然专制政体之完美巧妙 ,诚如公语 ,苟非生于今日 ,地球无他国无立宪共和之比较 ,乃至专制之名 ,
习而安之 ,亦淡焉忘之 ⋯⋯(中国)风俗之敝 ,政体之坏 ,学说之陋 ,积渐之久 ,至于三四千年 ,绝不知
民义民权之为何物。”⑤ 所说不无道理。杨度在 1907 年 1 月出版的《中国新报》“叙”中说 :“今地球
上以大国被称者十数 ,而中国居其一。虽然 ,以中国之大言之 ,固有非各国所能及者 ,若以言乎富与
强 ,则反在各国下数等。此其故何也 ? 则以中国之政体为专制之政体 ,而其政府为放任之政府故
也。”⑥ 此三位均反对革命 ,却同样不否认中国历来专制政体之存在 ,可见此说影响之深广。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中国为专制政体说出现 10 年后 ,甚至连清廷的大臣、官员也屈从于这一论
断。武昌起义爆发后 ,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奉天代表曾有翼等致内阁袁世凯函称 :“革命风潮浸
及东省 ,东省人士非不知脱离专制 ,尊重自由。无如默观时局 ,知非君主政体不足以自立。”一个多
月后甘肃谘议局议长张林焱等致袁世凯转伍廷芳等电反对共和 ,支持君主立宪 ,其中亦称 ,“查我中
原民族 ,休养于专制政体之下者四千余年 ,服教畏神 ,久成习惯”,因此认为不能急于实行共和。⑦
1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国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 8 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151、158 页。
《中国新报》第 1 卷第 1 号 ,1907 年 1 月 ,第 1 页。
《新民丛报》第 24 号 ,1903 年 1 月 13 日 ,第 39 页。
《新民丛报》第 16 号 ,1902 年 9 月 16 日 ,第 63 —64 页。
梁启超 :《开明专制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 ,第 77 —83 页 ;参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 (1890 —1907)》,第
173 —177 页 ;董萍平《论梁启超由主“变法”到主“开明专制”的思想演变历程》,《益阳师专学报》1989 年第 2 期 ,第 37 —42 页。
《民报》第 6 号 ,影印本 ,第 11 —12 页。
《东方杂志》第 2 年第 4 期 ,第 80 —81 页。
侯旭东/ 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尽管这些人反对共和 ,但他们却已在使用与“共和”密切相联的“专制政体”一词来概括历代政体 ,至
少在语言层面上已经屈服于新思潮。“专制政体”说开始成为清廷部分官员自我认识的一部分 ,为
其覆灭提供了思想基础。宣统宣布退位后两天 ,即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河南巡抚齐耀琳致电袁
世凯等亦称 :“此次中华改革国体 ,由专制一跃而为共和 ,阅时不过四月 ,潮流迅急 ,亘古所无。”①
此人视清廷为“专制”显非始于清帝退位之时。从这一角度看 ,“专制”说并不只是一种流行世间的
论断 ,它亦参与到历史实践中 ,成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总之 ,无论维新派、革命派、保皇派 ,还是清政府 ,均接受了“中国专制”说 ,确如佐藤慎一所指出
的 :“在对现状的分析上 ,各持不同的未来图景的论者之间 ,其意见却奇妙地一致。这就是将从秦始
皇开始到 20 世纪初延绵不绝的中国的政治体制都一并视为专制政体。”②
3.“专制说”在中国大众中的传播与学界的不同见解
“专制政体”之说不仅很快见诸国内的书籍、报端 ,国内新出现的百科辞书中不久也开始出现
“君主专制”的条目。1908 年根据日本辞书翻译的《东中大词典》就设有此条 ,解释作“君主总揽国
务 ,一切大小政事 ,均由其独断独行 ,恣意处理者是也”③。1911 年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虽未
见“专制政体”或“君主专制”的专条 ,但亦有一些条目内容涉及“专制政体”或“专制国”。④ 1915 年
首版的《辞源》也有“专制”一条 ,释义二做“政令之权 ,全出于一国之君者 ,曰专制 ,参看专制政体
条”。同时设“专制政体”一条 ,云 :“国家之元首有无限权力 ,可以独断独行者 ,谓之专制政体 ,为立
宪政治之对。”⑤ 表明来自西方、表示政体的“专制”,作为一个新词已在汉语日常词汇中占据了合
法的位置 ,预示它将逐步成为中国人认识历代政体 ,乃至历史的概念工具。
此外 ,扩大“专制”说社会影响的另一重要渠道是 20 世纪以后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自 20 世纪
初起 ,一些历史教科书开始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皇帝描绘成“专制君主”,一些朝代描绘成“专制”王
朝。目前所见 ,1903 年夏曾佑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最早的一部按新式章节体撰写的中
学历史教科书 ,后更名为《中国古代史》再版 ,其中就有不少地方使用了“专制”与“专制政体”之说。
该书第二篇“中古史”第一章“极盛时代”的第五节“秦于中国之关系上”云 :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 ,至二世三年而亡 ,凡十五年 ,时亦促矣 ,而古人之遗法无不革
除 ,后世之治术 ,悉已创导。甚至专制政体之流弊 ,秦亦于此匆匆十五年间 ,尽演出之 ,诚天下
之大观也。⑥
第十七节“文帝黄老之治”云 :
文帝好黄老家言 ,其为政也 ,已慈俭为宗旨 ,二十余年 ,兵革不兴 ,天下富实 ,为汉太宗。其
专制君主之典型哉。⑦
2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夏曾佑 :《中国古代史》,第 253 页。
夏曾佑 :《中国古代史》,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 ,第 232 页。
《辞源》,商务印书馆 1915 年初版 ,1922 年第 17 版 ,寅集 ,第 94 页。
黄摩西 :《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立宪政体”条 (5. 1009) 、“法治国”条 (8. 268) ,上海国学扶轮社 1911 年版 ,分见丙集第 91
页、辰集第 27 页。
转自钟少华编《词语的知惠———清末百科辞书条目选》,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58 页。
佐藤慎一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 236 页。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 8 册 ,第 190 页。
2008 年第 4 期
第二十节“汉外戚之祸一”云 :
推其 (指母后临朝之制 ———引者)原理 ,大约均与专制政体相表里。①
第六十五节“文学源流”云 :
(以文辞取士)与中国相始终 ,推其原意 ,皆立谈之变相耳。此专制政体之不得不然也。②
对于历史上的许多现象均以“专制政体”来解释 ,无论现象与专制政体间是否存在联系 ,“专制政体”
似乎成了包治一切的妙药。
此外 ,1914 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钟毓龙编《新编本国史教本》第二编第一章第一节“秦之内
治”指出 :
始皇为专制之大枭桀 ,故其内治多为专制 ,与后世关系甚多 ,约计之有六端 (下略) 。
此书 1914 年 8 月发行 ,至 1920 年已印行 16 版③,发行量之大 ,影响之广可想而知。又如 1924 年出
版的顾颉刚、王钟陵编 ,胡适校订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中册)云 :
明太祖由平民得帝位 ,乃不料君权的膨大 ,反比从前加厉 ,这为什么呢 ? 其实只是君主专
制的自然趋势 ,明朝适逢其会 ,便得更上一层罢了。④
再如 1932 年出版的周予同著《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 ,第三编“中古史 ———中央集权制的确立与平
民革命的暴兴”中说 :
从此以后政权遂集中于君主的掌握 ,官吏变为君主的仆从 ,而确定二千余年来的君主专制
的基石。
次年出版的下册中称 :
明太祖的开国政术不仅将政权总中于君主一身 ,而且滥施淫威 ,竭力扩张君主的权势 ,明
代官僚所受待遇的恶劣 ,远甚于前代。
君主专制的局势 ,到明代而达于极点 ,但这样的政制 ,便于英主而不利于庸君。⑤
32
①
②
③
④
⑤ 周予同 :《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 ,开明书店 1932 年版 ,第 60 页 ;下册 ,开明书店 1933 年版 ,第 116、118 页。
顾颉刚、王钟陵编 ,胡适校订 :《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中册 ,商务印书馆 1924 年版 ,第 61 —62 页。
钟毓龙 :《新编本国史教本》,中华书局 1914 年初版 ,1920 年第 16 版 ,引文见第 57 页。
夏曾佑 :《中国古代史》,第 355 页。
夏曾佑 :《中国古代史》,第 257 页。
侯旭东/ 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再如 1933 年出版的金兆梓著《新中华本国史》上编 ,第三章“政治的演化”中说 :
汉代盛时的政治中心 ,实在是在皇帝一人手里。所有那时的政治 ,实在可说是君主专制政
治 ,和上古的贵族专制不同了。①
应该指出 ,1949 年以前的各政府所颁布的各种中小学历史课程标准中均没有将秦以来的政体称为
“专制政体”的条目与要求 ,只是个别标准提到欧洲“中古教会之专制”、“十八世纪世界专制政治及
其所引起之反动”② 或“十八世纪的开明专制政治”③。明确将秦以后的政体与专制联系起来的是
1956 年以后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④ 上述教科书中的论述均是出自编者本人的观点 ,这些作者 ,除
了钟毓龙生平待考外 ,余下的大都经历过五四运动 ,经受了民主思潮的洗礼 ,在教科书中做如此判
断并不奇怪。
私塾蒙书退场后 ,历史教科书成为塑造广大国民历史记忆的重要工具 ,“中国专制”说从为中国
知识分子所了解到开始进入中学教科书 ,前后不过几年时间 ,其间没有时间进行认真的思考、消化
与鉴别。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 ,一种舶来的新词汇、新论断就被视为当然的结论采入中学教科书 ,
传授给青年 ,不难看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焦急心态。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专制”说不过是民国学术界主流思想的延伸。1911 年以后学术界的共
识之一就是中国历代王朝为“专制政体”。1929 年出版的吕思勉《中国政体制度小史》说 ,“(中国)
习于一君专制之治 ,以为国不可一日无君”,“中国后世之政体 ,虽若一君专制之外 ,更无他途可
出”。⑤ 1939 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 ,就建立了专制
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⑥ 这一表述对 1949 年以后的大陆学界有深远的影响 ,其实除了“封
建国家”说之外 ,接受的均是民国时期通行的观点。专门研究政治制度的曾资生亦认为中国古代政
治制度为君主专制政体。⑦ 杨熙时在讨论中国历代政制的时代划分时指出 :“第二 ,有秦一代 ,是封
建政治与专制政治交替时代。第三 ,秦代以来专制一尊 ,成了政治的常轨 ,所谓魏晋南北朝的门阀
政治 ,中唐的藩镇 ,元清的种族专制等 ,都在这个自秦以来的专制一尊的政治环境里盘桓。”⑧ 王亚
南在 1947 —1948 年曾概括说 :
新旧历史学家、社会史家已公认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轫的朝代。而由秦以后 ,直到现代
4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杨熙时 :《中国政治制度史》,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 ,此据《民国丛书》第 4 编第 20 册 ,第 14 页。
曾资生 :《中国政治制度史》第 2 册 ,南方印书馆 1943 年版 ,此据《民国丛书》第 4 编第 20 册 ,上海书店 1992 年影印版 ,第
21、35 页。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 ,第 618 页。
此书原为 1929 年上海中山书店出版 ,后收入《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445 页。
《1956 年初级中学中国历史教学大纲 (草案)》初中一年级的说明中有“完成了统一全国事业的秦始皇采取了各种措施来
加强统治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确立了”的表述 , 收入《历史卷》,第 137 页。同年的《高级中学中国历史教学大纲 (草案)》
在秦、明与清代亦有类似的表述 ,收入《历史卷》,第 198、207、208、209、212 页 ;此后《1963 年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 (草案)》、
《1978 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1980 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与《1986 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
学历史教学大纲》均有类似的内容与要求 ,收入《历史卷》,第 275、277、278、342、393、400、401、402、403、455、463、464 等页。
《1929 年高级中学普通科外国史暂行课程标准》教材大纲 (四)“近世史”,收入《历史卷》,第 40 页。
徐则陵起草的《1923 年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第 46 课与第 90 课 ,收入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 世纪中国中小
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以下简称《历史卷》)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18、19 页。
金兆梓 :《新中华本国史》,中华书局 1933 年版 ,第 108 页。
2008 年第 4 期
化开始的清代 ,其间经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 ,除了极少数的场合外 ,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
了不起的变更 ,换言之 ,即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 —官僚政治的支配。①
确如王亚南所说 ,在中国王朝时期的政体问题上 ,不同立场的史学家 ,无论是倾向自由主义 ,还是赞
同共产主义 ,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只是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各派见解不同。就连更早的“国粹派”也频
繁使用“专制”来描述中国传统政体。②
民国时期 ,大概惟有钱穆明确反对将中国王朝时期的政体归入专制之列。1941 年 10 月钱穆
在《思想与时代》发表了《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一文 ,对辛亥革命前后“一辈浅薄躁进者流 ,误
解革命真义 ,妄谓中国传统政治全无是处 ,盛夸西国政法”的风气强烈不满。关于政体 ,则指出 ,“西
人论中国政制 ,每目之曰专制 ,国人崇信西土 ,亦以专制自鄙”,认为自称中国专制是“自鄙”。对于
中国为何不是专制 ,他也做了简单的分析。他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与西方有很大区别 ,其结论是“若
目西国政权谓‘契约政权’,则中国政权乃一种‘信托政权’”。③ 几年后 ,他在《中国传统政治与五
权宪法》中指出 :“西方学者言政体 ,率分三类 :一、君主专制。二、贵族政体。三、民主政体。中国自
秦、汉以下 ,严格言之 ,早无贵族 ,中国传统政治之非贵族政治 ,此不待论矣。中国虽有君主 ,然固非
君主专制 ,此如英伦虽至今有君主 ,然不害其为民主政体也。中国传统政治 ,既非贵族政治 ,又非君
主专制 ,则必为一种民主政体矣。”④ 不过 ,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中国存在过“专制”,同是在 1945
年发表的《论元首制度》中 ,他说 :
细按中国历代政制 ,惟满清君主 ,始为彻底之专制 ,其所以得尔者 ,盖为满洲王室有其部族
武力之拥护。其专制之淫威 ,虽甚惨毒 ,而亦尚不至于黑暗之甚 ,则因中国传统政制 ,虽此君权
相权衡平调节之妙用已为破弃 ,而此外尚多沿袭 ,故最高政令虽常出之满洲皇帝一人之专断 ,
而其下犹得弥缝匡救 ,使不致流为大害也。⑤
以上是钱穆一贯坚持的观点。在此前出版的《国史大纲》(1940 年初版) 与 1950 年代出版的《中国
历史研究法》等书中 ,钱穆也表达了类似的见解。⑥ 尽管如此 ,此说一出 ,犹激起了萧公权与张君劢
等人的批评 ,可见主张中国古代为专制政体者之固执。仔细分析 ,钱穆的论断尽管反对专制论 ,从
更深一层来看 ,他与专制论者均接受了亚里斯多德三大政体说的基本框架 ,同样是以西方的政体说
作为普遍标准来衡量中国政体 ,与主流的区别只是在于部分否认中国为专制 ,而代之以民主政体
说。这不过是一种“颠倒的”东方学 ,更多体现的是民族主义情绪与西方政体学说的对抗。钱穆立
说依然没能挣脱西方学术话语的笼罩。
5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见《国史大纲》“引论”八 ,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第 14 —16 页。《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 ,
第 24 页。此外 ,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晚年则在《国史新论》中继续坚持这一观点。关于他的这一观点近来亦有学者提出反
驳意见 ,见万昌华《钱穆若干历史观点商榷》,《文史哲》2005 年第 4 期 ,第 117 —118、119 —120 页。
《东方杂志》第 41 卷第 10 期 ,1945 年 5 月 ,第 2 页 ,《钱宾四先生全集》第 40 册 ,第 42 页。
1945 年 3 月发表于《东方杂志》第 41 卷第 6 期 ,第 2 页 ,后收入《政学私言》上卷 ,《钱宾四先生全集》第 40 册 ,第 5 —6 页。
收入《政学私言》下卷 ,《钱宾四全集》第 40 册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8 年版 ,第 123、133 —135 页。
参罗志田《国家与学术 :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 40 页。
王亚南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39 页。此书原作为文章发表 ,1948 年初版 ,1981 年再
版。
侯旭东/ 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三、中国接受“专制说”的背景与后果
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 ,中国知识分子从听说到接受“中国专制”说历时甚短 ,前后不过一二
年。短短的一二年显然不可能对秦以来二千年的中国政治史做充分的研究 ,而且当时也不存在安
心从事研究的外部条件与环境。这一论断可以说是在没有经过认真论证的情况下匆忙接受的 ,并
随即应用到实践中。从学术的角度看 ,是犯了结论先行 ,以论代史的错误。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能
在很短的时间内接受这一并无多少事实根据 ,且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论断 ?
从中国本土方面考虑 ,最直接的是甲午战争与戊戌维新的失败 ,中国知识分子遭遇到的空前挫
折促使他们反省自己的历史 ,意识到自己的政体存在问题 ,关于这一点 ,前人的研究已多①,不拟赘
述。这里仅就政治局势背后隐藏的深层“心态”做些分析。
进一步观察 ,支持这种认识的是中国人看待“过去”时长期存在的“成王败寇”逻辑。这种逻辑
集中体现在史书中 ,中国历史上“正史”编撰的基本方式是本朝只修起居注与实录 ,由后代为前朝修
史 ,更强化了这种逻辑。权力斗争中取胜的一方 (新王朝)拥有最终的叙述前代王朝历史的权力 ,失
败的一方 (覆灭的王朝)只能被表述 ,不能自己去陈述自己的“过去”。在这种格局下 ,历史的叙述 ,
特别是涉及新旧王朝交替时期的人物与事件时 ,自然多呈现出“曲笔”与“回护”,将历史进程描述为
向新王朝迈进的“线性的历史”,贬低前朝的政绩与功绩。史家往往成为枪手 ,负责执行“曲笔”任
务。② 同时 ,还应注意到 ,所有的士人 ,即知识分子 ,都是在不断阅读这些呈现出“线性历史”的史书
中步入士林 ,进入官场的 ,难以逃脱浸透在“史书”中的这种史观的潜移默化影响。即便到清末 ,当
他们走出国门后 ,这种逻辑也会潜藏在他们头脑中继续发挥作用。只不过在清末巨大冲击中所遭
遇到的是亘古未有的变局 ,取胜的不再是某个从中国内部产生的新王朝 ,或某个周边的外族 ,而是
远道而来 ,挟坚船利炮的“夷人”,落败的不仅是清王朝 ,而且是以清王朝为代表的有数千年历史的
中国。这一次 ,中国知识分子通过“专制说”等等对自身历史的批判与重新论述 ,再次充当了执行
“曲笔”的枪手 ,只不过这次目的发生了变化 ,目的是拯救中国 ,而不仅仅是证明某个中国王朝的无
能与失败。
1902 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分析中国史学的正统问题时就曾指出 :“谚曰‘成即为王 ,败即为
寇’,此真持正统论之史家所奉为月旦法门者。”③ 不幸的是 ,他虽然意识到这一问题 ,但在他自己
的实践中却依然重蹈覆辙。
62
①
②
③ 《新史学·论正统》,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第 24 页。
关于正史的曲笔 ,清人赵翼等已做过不少分析。这里不妨以前人很少提起的《汉书》为例 ,再做一具体说明。班固为了维
护汉朝的正统 ,不惜在记述王莽与新朝时加以“曲笔”。不仅将对王莽的记载归入“传”,且安排在全书的最后 ;就是具体的记述中
也通过特定“笔法”加以贬斥 ,如对王莽所下诏书 ,《汉书·王莽传》书做“下书”而非“下诏”,见《汉书·王莽传》,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
第 4128、4130、4131、4154、4158、4159、4161、4174、4175、4178 页等 ,只有两处用了“下诏”,见第 4152、4164 页 ,恐是没有改尽。据
该传载群公奏言“臣等尽力养牧兆民 ,奉称明诏”(第 4134 页) ,田况上言云“窃见诏书 ,欲遣太师、更始将军”云云 (第 4172 页) ,可
知当时仍用“诏书”,说“下诏”。班固写作“下书”是为了将王莽贬入“闰位”,不承认其为皇帝 ,这自然是一种歪曲。此外 ,为了证明
王莽无计可施 ,云“(莽)性好时日小数 ,及事迫急 , 为厌胜”,并举出若干事例 ,最后说“如此属不可胜记”(第 4186 页) 。根据《论
衡》以及几十年来出土的大量简牍 ,我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汉代人“好时日小数”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对此 ,班固并没有正面记述 ,
而在这里却格外专门举出王莽好时日小数 ,一无一有 ,似乎衬托出王莽到了穷途末路 ,实际上 ,汉人在日常生活中离不了“时日小
数”,并非走投无路才如此。班固如此记述是为了证明历史在向汉朝发展而有意安排的 ,也是一种曲笔。
彭明、程啸 :《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第 4 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72 —184 页 ;佐藤慎一指出了 4 点原因 ,
见《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 241 —242 页 ,可参。
2008 年第 4 期
这种逻辑也同样应用到打败清朝的“洋人”身上 ,因为自 1840 年以来洋人多次打败清军 ,显示
了船坚炮利的力量 ,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对西洋人、西洋学说由漠视到佩服与羡慕 ,从而出现了带有
“虚无主义”倾向的自我否定历史的潮流。20 世纪以后出现“全盘西化”说不过是这种潮流的极端
而已。这种逻辑说穿了是一种“以今度古”的“非”历史的态度 ,类似于对历史的辉格解释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 。①更深一层讲 ,体现了权力对“历史”叙述的操纵。如果说近代西方逻辑
是“知识就是力量 (权力)”,中国古代在一定程度上则是“权力就是 (历史)知识”,拥有权力也就获得
了解释历史知识的权力。
从西方的角度看 ,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专制”说则是一种“自我东方化”,如学者所指出的 ,“在二
十世纪 ,欧美东方学的理解与方法在中国自我形象的形成与中国对过去的理解中成为一个可见的
组成部分”,无论是儒教、专制政体、官僚政治、家族主义还是特别的种族特性 ,都可以溯源至欧美东
方学的描述。所有这些描述的共同之处在于使用出自西方观念的形象、概念与标准来“重新书写”
中国历史。传播这种西方意识的不仅是西方的传教士 ,还包括海外的中国人②,实际上还包括作为
重要桥梁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人。这几股力量共同作用将西方对东方的表述 ,如中国专制之类 ,译
成中文 ,引入中文世界 ,并变成自己的表述加以传播 ,进而重新塑造中国人自己的历史记忆。③
其结果是中文世界中出现的中国史 ,表面看来由中国人自己做出的论述 ,用的是中国的“语
言”———实际已经不是传统中国的语言 ,而是经过翻译、引进与创造的“近代汉语”语汇 ,骨子里则是
欧美东方学对中国漫画式认识的重复、再现与拓展 ,中国“历史”因此丧失了依据自身的脉络表达自
己的机会与能力 ,从而实现了在物质层面之外的“文化与表述层面上”对西方的依附。
同时 ,这种舶来的论断又直接卷入清末的实践活动 ,为推翻清朝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当中国人
在对自己历史的描述中用“专制政体”来概括秦代以来的二千年政治时 ,就等于在替西方人宣传他
们对中国历史的歪曲 ,正是由于是中国的历史学家自己如此表述 ,才更具有欺骗性与“说服力”,才
更容易为百姓所接受。接受这一论断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走向自我东方化的过程 ,即按照西方人
的观念重新塑造对中国自身历史认识的过程。其结果是我们在空间上是生活在西方以外的东方 ,
但是 ,从商品、品味、感觉到表述 ,实际都难以挣脱西方制造的牢笼。
“中国专制”说从出现到流行于中国学界与社会的历程是中国近代遭遇危机背景下国人思想上
经历西方理论殖民的一个缩影。如果说中国在现实中仅仅是半殖民化 ,但在思想观念上受到的殖
民却更加严重。近代中国学术可以说几乎都是在西方的刺激下形成的 (其中不少是取道日本而获
得的) ,许多基本前提与判断 ,和“中国专制”说一样 ,都是没有经过认真的论证就接受下来 ,作为学
术积累与流行观念的基础。追根溯源 ,这类中国观大多不是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形成的 ,加以西方
“东方主义”的歪曲 ,其中的问题必然不少 ,不可等闲视之。这种歪曲的中国观通过各种渠道流行于
世 ,所以 ,即便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当代学者也并非直接、透明地面对史料 ,而是透过包含着近代
以来 ,乃至早到传教士时代以来所形成积累的“中国观”在内的观念来认识过去 ,因此 ,近代历史对
于研究古代的学者也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72
①
②
③ 关于这一问题 ,参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 :中国 ,1898 —1910》,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193、195 页 ;桑
兵《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解说》,收入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 :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 2006 年版 ,第 3、14、17 —19 页。两位强调的是 19 世纪末以来的变化 ,实际还应追溯到明清传教士时代。
Arif Dirlik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 Vol. 35 , No. 4 (Dec. 1996) , pp . 106 —
107.
H. Butterfield , The W 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 Charles Scribner’s Sons , 1951) , pp . 1 —7 ,107.
侯旭东/ 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清末救亡图存的斗争年代 ,以“专制政体”与“专制君主”说作为批判的武器无可厚非 ,随后未经
认真充分的研究 ,将这种因想象而生的观点作为定论引入学术界 ,则遗害不浅。这不仅严重束缚了
中国学者对自身历史的理解 ,忽略并遮蔽了许多历史现象 ,妨碍对帝国体制的把握 ,也暗中应和了
西方人对中国的歪曲 ,无意间为西方的“东方学”做了不少添砖加瓦之事。即便是似乎远离理论问
题的具体研究 ,实际也难以摆脱其间接的影响。如果没有对以“专制”说为代表的西方中国观的彻
底清理 ,具体研究很可能会在不自觉中为这些歪曲之说推波助澜。
如果以上分析不误 ,现在亟需摘掉这类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把历史上的“国家”重新开放给
学者。通过系统、全面地探讨历史上的君臣关系、统治的运作机制 ,将官场中反复出现的主要现象
均纳入分析的视野 ,逐步提炼和概括出关于中国政体、皇帝与官吏的认识。① 在缺乏对中国历史上
的皇帝制度以及君臣关系全面清理的情况下 ,贸然以“专制”论作解 ,可能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其
言论愈有条理统系 ,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②。这一重新探索的过程也许需要几十年 ,甚至上
百年 ,其间也许充满艰辛与曲折 ,但对于中国学术来说 ,却是值得的。
本文写作、修订过程中得到本所黄正建先生、马一虹女士及本院近代史研究所崔志海先生的惠
助 ,在近代史研究所吕文浩先生的安排下曾于 2005 年 6 月在该所青年沙龙上宣读过此文初稿 ;后
曾将此文提交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的“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5 年 6 月 ,上
海) 、北京大学与哈佛 —燕京学社主办的“全球化进程中的东方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5 年 11
月 ,北京) ,以及《历史研究》编辑部、中山大学历史系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办的“承传与创新 :新
世代的历史学”学术会议 (2007 年 12 月 ,香港) ,得到与会学者 ,特别是葛兆光、罗志田、王东杰、于
庚哲、张建华、章清与孙宏云等先生的指教 ;关于日本思想界的一节得到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
际关系学院杨宁一先生的指点 ,谨此一并致谢。
〔作者侯旭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xudonghou @sina. com〕
(责任编辑 : 杜承骏)
82
①
② 陈寅恪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收入所著《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 ,第 280
页。
小岛毅《中国的皇权———〈礼治和政教〉导论》第 348 页亦提到这一点。
2008 年第 4 期
Modern Chine se History Studie sNo . 4 , 2008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Ancient Chinese Despotism Thesis Hou Xudong (4)⋯⋯⋯⋯⋯⋯⋯ Since late 19th century , the thesis that the imperial Chinese polity from Qin to Qing was despotic and that Chinese
emperors were despots has been popular and influential. Indeed , it has constituted one of the basic theses employed in
studies of Chinese history. This paper looks at this thesis from the angl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 analyzing its emergence ,
its spread and its consequence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is thesis was not a resul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 but a Western
bias towards the Orient dating to Aristotle that a few Western thinkers began to use in the 18th century to describe China.
I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via Japa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was widely accepted by Chinese intellectuals of all
standpoints. Through dictionaries and history textbooks , it also seeped nearly unquestioned into the general populace. The
despotism thesis has not been sufficiently demonstrated by historical facts , so if we use it without any re2considerations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ruling mechanism in imperial times , it will only hinder our research.
Off icial Duties of the Magistrate of Guangdong’s Foremost County during the Tongzhi and Guangxu
Periods : Reading the Nanhai County Magistrate’s Diaries Qiu J ie (29)⋯⋯⋯⋯⋯⋯⋯⋯⋯ The main data used in this article are the diaries of Du Fengzhi , who was magistrate of Nanhai county during the
Tongzhi and Guangxu periods. In addition to performing the routine official duties of a prefect or magistrate , Du Fengzhi
was also the official in direct control of Guangdong’s provincial capital (jurisdiction over Guangzhou city was divided be2tween Nanhai and Panyu counties) . From his diaries , we can see the local government’s system for administering the
provincial capital and many details of the city’s social life. Du Fengzhi took part in many“foreign affairs”activities under
orders from the Governor2general , and his diaries recorded some of the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in Guangdong at the time.
Moreover , as the magistrate of the province’s foremost county , Du Fengzhi always directly reported to the Governor2gen2eral , the Governor , the Financial Commissioner and the J udicial Commissioner , discussed official duties with senior offi2cials of all levels , and participated in such affairs as appointing and removing officials. In fact , he was an important assis2tant to Guangdong province’s senior officials. The diary’s record of Du Fengzhi’s official and private intercourse with of2ficials of all levels reveals the specific operations of local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and illuminates various regulation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On the System of Awarding Degrees in Schools in the Qing Dynasty Zuo Yuhe (45)⋯⋯⋯⋯⋯⋯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as a system for selecting talented persons in ancient China , whereas the new style
school system was a system for educating students. The natures and functions of the two systems were very different . The
system of awarding degrees in schools , established around the time tha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as abolished ,
was simply a dislocated graft of the two systems. In fact , it was an extension of the traditional idea of“awarding office to
excellent students ,”and created and encouraged the general mood of“using learning to seek office ,”while it reinforced
the pattern of“integrating officials and students.”For these reasons , it was fiercely criticized by forward2thinking men.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of awarding degrees in Qing dynasty , this paper anal2yses the functional and intrins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schools , and reveals the in2herent conflict in the design of the system of“mixing schools and officialdom”and“integrating the selection of talented
persons with the education of students.”The paper goes on to explain the complexity and inevitability of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examination degree system to the system of awarding degrees in school , and the turn towards the
modern of academic degree system.
Famine and Foreign Trade : Centered on the Port of Tianjin , 1867 —1931 J ia Hongwei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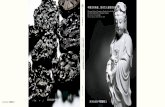

![On Watermill Technology from Ancient Chinese Paintings(in Chinese)[从古代绘画看我国的水磨技术]](https://static.fdokumen.com/doc/165x107/6320feaabc33ec48b20e2432/on-watermill-technology-from-ancient-chinese-paintingsin-chinese.jpg)









![[12]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说明书](https://static.fdokumen.com/doc/165x107/631b4d907d4b3c24320cc190/1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