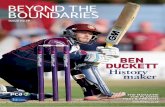Ben Jonsons Poetry the Seventeenth-Century‘s Critique on His Works
Transcript of Ben Jonsons Poetry the Seventeenth-Century‘s Critique on His Works
[收稿日期]2011 -07 -10 [基金项目]2009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HB09BWX006。 [作者简介]郭 晖,女,副教授,英语语言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英语诗歌、基督教文学、诗歌翻译研究。
第 33卷 第 1期2012年 1月
哈尔滨学院学报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
Vol.33 No.1Jan.2012
[文章编号]1004—5856(2012)01—0062—09
本· 琼生的诗及 17世纪对其作品的批评郭 晖
(河北工程大学 文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本· 琼生的闻名一半是靠莎士比亚的提携,一半是靠他自身文学的修养与积累:他在戏剧方面对古典戏剧有继承有创新,他自创情节,开创了英国“性情剧”;他的诗歌一改叙事诗和十四行诗的体裁,警句体、挽诗、信体诗等多种体裁,题材上也有多个创新,如亲情诗和乡间别墅诗等。 然而,一朝出名并非意味着享誉终生,17世纪即琼生曾经生活的世纪,人们对其作品的接受就有了较大落差,从褒扬到贬斥。 文章详细综述并探讨了这种批评走向,加以实例分析了琼生诗歌的独创性,提倡客观公正地评价琼生的作品,特别是其诗歌作品。
[关键词]本· 琼生;接受史;诗歌独创性;客观公正;评价[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现代读者在读琼生的成名喜剧枟个性互异枠时,却常常为时代和地域差异而不解其中奥妙,或许还会感觉该剧结构松散,缺乏统贯全剧的故事情节主线,或少某种中心线索贯穿全剧;剧中采用的早期现代英语与现今英语的距离也是造成当今读者欣赏障碍的因素。 早在18世纪托马斯· 戴维斯就注意到诗人剧作语言外来味过浓的问题,抱怨后者剧中太多地借用拉丁语词汇,使得其语言刻板、怪诞也刺耳,当时的观众要相当有耐心去听枟卡蒂利内枠一剧中西塞罗长达 170 行的道白。 事实上,他的另一部悲剧枟塞扬努斯枠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一些人物的道白过长,读来也不觉令人烦躁,如剧中人物台比留在第一场第二幕中看过信后有一
段道白长达 65行,即使看该剧的演出也会有同感。
琼生主要以喜剧作品闻名于世,然而,并非说他只是一名剧作家,他还有另外更重要的成
就长期受到相对的忽视,这便是他的诗歌与文论,如果英国诗歌宝库里缺少了他的诗歌作品就缺少了一些奇珍异宝,如赞颂同行诗人莎士比亚的那首挽诗,琼生用了“丰厚遗产”一词,可见,他对这位同时代诗人的文学作品的认识和评价甚高,其实用这个说法来称呼他自己的作品也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下文将讨论“作品本身的优质与否与读者的接受是否成正比”的问题。
一、接受美学与琼生作品的接受史①[1](P54)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接受美学理论给人以很好的启示,这个理论学派以德国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接受美学的创立者姚斯为代表,对作者、作品和读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较为合理的观点,他提出了对这三者以动态的眼光去看待,指出“文学作品并非是一个对每个
时代的每个观察者都以同一面貌出现的自足的
客体,它也不是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本质的纪念碑”。[1](P54)
这最后一句话似乎否定了琼
生在颂扬莎士比亚挽诗里的这一句,“他不是一个时代,是超时代!”其实,琼生这句诗表明诗人极富预见性,这句诗里的“超时代”实际含有这样的意义:无论时代如何变幻,读者如何不同,人们会不断地阅读这些作品,依据自己的价值体验去阅读这些作品,得出自己的评价。 所以姚斯没必要否定“超时代”的本质,因为作品的确是以同一面貌出现,但是它在读者眼中的投影是不同的,即客观物质有其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特点,而个人的主观意识可能会使其眼中的客观事物变形。 这个变形不是无意义的,相反,这个变形往往可以帮助我们把物质本体彰显出来,研究某一物质的变形度也是研究某一物质本体的一部分。
当我们在议论任何一位作家的作品时都离
不开对前面提到的三者的考察,尤其是对读者(观众)的考察,因为单一的考察作品的原意是不可能实现的,即我作为考察者同时也是一名有主观意识的读者,其绝对值不是数学里的概念。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作品的绝对原意是只有作者可以了解的,有些作品原意甚至是存在于作者潜意识里的,他本人对其中一些原意甚至是完全忽略的;也就是说每一个考察者在阅读和考察其作品时不自觉地、也不可避免地要带上个人色彩,翻译中对同一原文百篇不一的译作就将这种现象放大出来。 这也说明考察一位作家的作品时,连带考察共时和历时的读者接受其作品的情况是十分必要的。 这个考察将会揭示出仅凭这一作家的作品所不能揭示
的深层问题,如为什么对同一作品会出现正反截然相反两种观点。 而这截然相反的观点又告诉我们什么,特别是对于一个民族文学的发展方向的问题。
虽然,姚斯提出阅读赋予文本生命的说法不无道理,但是,这也有形而上学之嫌,因为应当说,好的文本经过作家的创作本身是有生命的,而且这种生命力的现实性体现在通过阅读这一行为对读者施加的有益的影响中,阅读使
文本的生命被明白地展现出来,从而获得“现实的生命”。[1](P54)
也就是说,本身没有生命的文本,即使曾经有人阅读,未必具有现实的生命。 不过,他的一些主张是辩证且合理的。②
因
此,当我们审视琼生的作品时,特别是审视其诗歌作品时,回顾其作品面世以来对其作品的接受情况是与研究其作品原意分不开的,而且是大有益处的。 事实上,通过这次回顾,我们看到对琼生作品的接受情况主要表现出正反两派的
观点主线,一是以迪格斯和德莱顿为首的反方,批驳琼生的仿古学古,作茧自缚,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不受大众欢迎;二是以雪利和弗莱克诺牵头的正方,赞许诗人的古为今用的做法。下面将分析 17世纪时琼生作品的接受史,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前两节的文献来源主要依赖于克雷格编辑的枟本· 琼生:批评遗产枠一书。③
二、17 世纪的琼生批评从褒扬走向贬斥
确切地说,对琼生作品的评论始于 16世纪末,即 1599年约翰· 威弗以诗体对马斯顿和琼生作品所作的简评为始。 由于 16 世纪的评论仅此一篇,这里权且将其合于 17世纪对诗人作品的评论。 有趣的是,17 世纪近 90 篇的评论里(除其自己的文论或作品序言外)还是威弗的评论(1601)一炮当先,但是此时这位评论者的语气已从褒扬转向贬斥,这似乎代表了整个世纪对诗人作品评论的总趋势,因为 1698 年剧作家威廉· 康格里夫和教士杰里米· 柯里尔的枟论琼生的喜剧枙巴塞罗缪集市枛里对主的亵渎枠可说是该世纪对琼生作品的最后一篇低调的评论。
17 世纪对其作品的关注与争议,从整体看,聚焦于天分、才气与学识的主题,与现代的评论相比,此时的批评过于简约、浅散、空泛,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1599 年到 1637 年,即诗人生前这段时间内出现的评论,其中只有近三分之一是严厉的批评。 在这些评论中,只有七篇论及其诗歌,余下的均是对其戏剧,尤其是对其喜剧的评论。 而这七篇评
36第 1期 郭 晖:本· 琼生的诗及 17世纪对其作品的批评
论中,只有一篇具体的评论,即枟评琼生的警句讽刺集枠,以抑扬五音步的诗体形式言辞激烈的抨击诗人的警句讽刺集,④[2](P122)
说其中没有
一首诗可称得上是警句诗,不过是剧本的边角料乱集于此,这一点倒不出诗人所料,⑤其余六
篇是赞扬琼生在诗歌方面的造诣,较为笼统,没有确指,因为当时戏剧也被看成是诗的一个分支。 爱德华· 赫伯特写诗称琼生是英国最好的诗人,是其时代的贺拉斯;埃德蒙· 博尔顿从语言角度评述琼生的诗歌,说其语言生动、内涵丰富且最为实用;托马斯· 伦道夫也是以诗评诗,从其诗歌的音乐性入手,也用了夸张的手法,写到其诗所传达的音乐优美,艺术是那么高超,甚至希神潘都深深为其曲调所迷;剧作家詹姆斯· 雪利从其喜剧成就说起,认为其他诗人的诗在与琼生的诗相比之下黯然失色;威廉· 卡文迪什对诗人评价也很高,称诗人的去世带走了他的时代,诗人是国家的荣誉;乔治· 斯图特威尔也对诗人在戏剧方面的成就大加赞誉,但是也没有冷落其诗歌的成就,认为其松散的诗词并不会令阿波罗丢脸,令人惊魂的诗词格律是诗人得宠宫廷的直接因素。
因此你的诗应当受到尊重
每一细节未曾错过你的观察
相称的启示;或者这也许可纠正粗俗的世风,使值得褒奖的人闻名演出如此生动的实例⋯⋯ [2](P98)
这是乔治· 查普曼写的一首较长的诗评论枟塞扬努斯枠,其中虽然提到诗这一词,但并非指狭义的诗歌,而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应指其戏剧成就。 下面谈到的是观察、演出和叙述如何教诲观众,起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另一人也在评论该剧时提到“诗”这一词,[2]( P100)也属于
同一指对,只是他是以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比较的角度品评的。
亨利· 切特尔也把琼生比作过贺拉斯,但那却是就诗人在讽刺喜剧方面的成就而论的,“我们英国的贺拉斯也不必(用诗词装点灵柩),他坚硬的笔/可塑造出永生不朽的人物”。另外,枟沃尔波内枠的成功招徕较多的称许,其中有博尔顿从古典继承的角度高度评价诗人的
才学,认为他是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丰碑以类似译介的方式呈现给英国百姓,是戏台上的太阳,在喜剧和悲剧两方面造诣相当,“沃尔波内,让人欢笑;塞扬努斯,令人垂泪”。 多恩和弗朗西斯· 博蒙特都是以诗赞颂的,多恩尤其对诗人继承古典的做法赞不绝口,这样写道:如果,你大胆用技巧在此表现的情景,呕,诗人,那些对上帝和人之律条的循规蹈矩者也敢于追随并且仿效古人,我们无人不可品尝为人拯救的滋味。可对于此类人古人不过是一片蜘蛛网;无人如你这般追寻古人的足迹,因唯你将古老收藏,将认可的遵循。总是锲而不舍地追求;愿你的大作从问世之刻起即放出古代之光辉
故文学作品自然忌讳稚气,这些书必是沉酿已久的精汁,由此让你的功力永垂不朽。天分与辛劳令你与古人
齐名;超越他们,这样你可能将后人从吾辈之腐朽中赎救,如此吾辈超越昔时与来世。[2](P109)
这不只是在褒扬琼生,更在于向世人阐明这样的道理:文学作品的流芳百世,必然要承前启后、厚积薄发,与魏征在劝谏唐太宗时说的“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讲的是同样的道理。对其戏剧的负面评价最值得一提的是剑桥
匿名剧作家、剧作家托马斯· 德克尔、合作者伊尼戈· 琼斯和伦纳德· 迪格斯的见解。 前两者的评价见于戏文,剑桥匿名剧作家是指名道姓地说他是讨厌的家伙,把贺拉斯弄来给当世诗人下一剂苦药,而他们的同仁莎士比亚却给了他一副泻药让他丢丑;德克尔是与琼生展开戏剧之战的一员,所以采用的是含沙射影的方式,以对剧中贺拉斯一角的丑化来讥讽诗人。 琼斯是写诗评的,他因个人的恩怨对诗人自己的创作大肆贬斥,却不否认对手有“好的翻译”,实际是肯定了诗人对古人的借鉴,该诗最后一句也是众多琼生研究者津津乐道的引语———“最好的诗人却是最糟的君子”———因为对手都赞
46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2年
扬诗人其诗学成就足以称道。[2](P132)琼斯并非
孤雁独鸣,约翰· 马斯顿也是戏剧之争的一员,但于 1604年在献给诗人的剧中,称赞诗人的博学,认为其艺术高于自然,鉴赏高于艺术,在评论枟塞扬努斯枠时他诗中写到,“从未有英国人,将来也不会有何人/说得如此优雅。 他能说得很多,恰如其分”。[2](P100)
迪格斯是继剑桥匿名
剧作家之后第一个明确将琼生的剧作与莎士比
亚的剧作进行比较的人,他的论理诗中的观点极其偏激,主观色彩过浓,仿佛夹杂着个人恩怨似的,开篇即驳斥琼生在纪念莎士比亚的诗里所写的“诗人天生亦需后天努力(For a good po-et’s made,as well as born)”的诗行,认为任何诗人只能像莎士比亚这样天生,而将琼生指称为当代寒酸的蹩脚诗人,说其作品不过是应付差事,他的悲剧令人生厌,喜剧虽然令所有的古人逊色,却会凸显出前辈作家满载荣誉桂冠的价值。[2](P161)
1616年,英王赐予琼生年度津贴决非偶然,因为在此举十一年前就有人这样倡议了,这是一位匿名作者在枟托马斯· 斯密斯爵士在俄国的游历娱乐记枠的小册子里发出的。 他是继赫伯特之后也把诗人比作贺拉斯的人,“英国翻版的贺拉斯在每个词上精益求精的推敲,以其辛劳教给读者,甚至我们有名的桂冠诗人琼生,其缪斯批准他以(我们的母亲)希伯来语的含义去写⋯⋯”。[2]( P94)无独有偶,纳撒尼尔·菲尔德在盛赞诗人的枟卡蒂利内枠振兴了衰落的古罗马艺术,也提到桂冠诗人,“如此的缪斯会将它们(快乐和恐惧)撒进我们的年月。 /可是对我们来说竟是痛苦:因为你戴桂冠的额头/如果罗马乐于拥有,我们现在也渴求。”“桂冠”这个词从约翰· 萨克林爵士口中说出来就带着讽刺的辣味,⑥[2](P175)
在另外一首诗里他批评诗
人的恃才自傲,这样写道,“这顶桂冠预留了如此之久/现在落入他当之无愧之手”。[2](P178)
第二阶段可称为纪念阶段,从 1638 年到1667年,这里不包括德莱顿的评论;既然是纪念曾经一度为文坛坛主的诗人,顾名思义,自然都是颂扬之声,加上颂扬者和被颂扬者之间的私人感情,有时不免夸大其词。 在这三十二篇
评论里,克雷格收在枟本· 琼生:批评遗产枠一书里有十四篇诗体评价选自福克兰编辑的枟琼生的威耳比俄斯纪念诗集枠,占了这一阶段近二分之一的评论篇幅。 另有十余篇也采用诗体的形式,剩余的三分之一是散文体的评论。 从枟纪念诗集枠里选来的十四篇中有十篇赞扬诗人在戏剧方面的成就,其中有四、五篇兼评其诗歌,多从诗人的古典学识的角度切入,其中福克兰提到诗神赐予诗人音乐,令后者以友谊作自己作品(应指其诗歌)的主题。 这位评论者的褒扬之词并无过分夸张的成分,较为全面地肯定了诗人的艺术成就,指出诗人在作品中扬善弃恶,如何鄙夷富贵者的无知,而且融合了前人、包括马斯顿提出的“艺术”和“鉴赏”的优点,明确提出了琼生文学作品的五大特点:智慧、艺术定位(鉴赏力)、学识、艺术性和(创作的)辛勤。 这些也为后来的评论者继承下来。约翰· 博蒙特即弗朗西斯· 博蒙特的兄弟在其诗中阐释,琼生是诗歌的锤炼者,将当世的邪恶在其作品中彰显出来,让世人观看,他鞭笞的是邪恶而不是针对某个人,接着他从语言角度赞誉了诗人的文学成就。 托马斯· 霍金斯爵士诗赞琼生的诗是地球之火,慢慢地送来暖流,激发力量,灌输知识和智慧等,他也和约翰· 德蒙特一样看到诗人针砭的是鄙陋的世风,而非某个人。[2](P187)威廉· 卡特赖特也是从诗人的戏剧和诗歌两方面的成就论述的,他提出诗人的精神是神圣自由的,其艺术不只是外在的表演动作,而是深入其心,表现生活,即“将生活展现给生活”,[2](P199)其喜剧里并没有为哗众取宠而
写的台词,他的讽刺反映了他不同凡响的艺术定位等。 这一时期当属牛津神学博士理查德·韦斯特的批评最为深刻,其在诗中称诗人是“王中诗人,诗人之王”,指出庸人为表象所惑,随之以比较的方法将诗人与莎士比亚和德蒙特
进行了比较,一反迪格斯的态度,认为只有琼生值得研究,他的每一句话“不是教人去笑,而是教人去生活”;可以说给了诗人一个公正的评价,不过也有观点偏激之嫌。 韦斯特还指出他的戏剧遭人鞭笞、毁谤,只因为它们是佳作,表现了英国的品味,诗人的作品是经艺术锤炼的
56第 1期 郭 晖:本· 琼生的诗及 17世纪对其作品的批评
结果,而他人的作品则是偶然为之;还说他的作品应被视作古代经典研习;韦斯特最后在诗的结尾 提 出, “言 胜 于 行, 文 学 素 材 胜 于言”,[2](P210)
将文学素材的重要性推崇备至。余下的十八篇短评里,有五篇将琼生与莎
士比亚进行了比较,有三篇还将前者与德蒙特和弗莱彻等诗人进行了比较,当然,结论是前者的学识与艺术品味远在后者之上。 不过显而易见,这些评论是为纪念刚去世不久的当时文坛坛主的诗人,此时评论者多少都在评价时带有一定的私人感情,略有厚此薄彼现象;六篇对诗人的戏剧从演出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有两位第一次对诗人的译作即贺拉斯的枟诗艺枠进行了简评。 詹姆斯· 雪利认为,莎士比亚不过是一时取悦了观众,而琼生的艺术则是精湛的,如果后者操起竖琴连阿波罗都不敢再弹琵琶;[2](P222)玛格丽特· 卡文迪什承认莎士比亚的才智,也遗憾他的才学比琼生要浅;托马斯·富勒的比喻特别形象,不无道理,他将琼生比作西班牙巨型帆船,渊博的学识令其船身高大、坚实,行动起来却较慢,而莎士比亚则是英国战舰,体积偏小,航行轻便,易于应对各种海上的风浪;[2](P235)塞缪尔· 巴特勒将琼生比作维吉尔需要天分,将莎士比亚比作奥维德需要勤学苦练,这个比喻事实上认可了两位诗人的创作成就各有千秋、不亚于古人;理查德· 弗莱克诺虽是爱尔兰天主教神父,却对戏剧颇有见地,也成为琼生作品持赞许观点的代表。 他认为一部好的戏剧应当像纺出的均匀密实的纱线,没有断头或松松的须子,或像一幅精心构思后绘制的图画,或是一座精心布置的花园。 因为他认识到戏剧家的作品包罗万象,是个杂学家(现在人们更长以此名号冠以小说家)不像数学家或哲学家限于某个领域,而且人人都可加以品评。 他说戏剧家之于戏台犹如轮船的驾驶员,或是建筑师之于建筑工人们,导师之于学子们,这个比喻今天看来颇有影响力。 A· W· 约翰逊或许受此启发,就在 1994年以建筑与诗歌的角度切入琼生的作品,出版了枟本· 琼生:诗歌与建筑枠这本研究专著。[3]
弗莱克诺认为莎士
比亚改变了传统的戏剧风格,将了无生趣的历
史剧转变成轻喜剧,而琼生则使这样的喜剧文雅高尚,他的庄重与篇幅冗长的风格与莎氏的自然和弗莱彻的机智相对照,进而阐发了如果琼生少将他的博学揉进戏剧里一些,那些戏剧会比现在的版本更加令人赏心悦目。[2](P237)
有三篇从戏剧语言和剧情安排落笔评论。杰斯珀· 梅恩在他的纪念诗人的长诗里对其戏剧的演出作了只言片语的记述,说他的戏剧里没有污秽、松散的台词浪费他的才智。 卡特赖特在 1647年写诗从表演的角度评述了琼生戏剧里爱情戏的安排,认为其写实性较强。 海军官员塞缪尔· 佩皮斯在他的日记里记述了他观看琼生戏剧演出或是阅读其剧本后的感受,十分称许枟阴阳人枠一剧,特别提到该剧主角在台上的三个扮相;认为枟巴塞罗缪集市枠虽然不错,却为剧中太多亵渎神灵和谩骂的台词感到遗憾。 他后来再看该戏时,反感剧中穿插木偶戏的片断。 他读过枟个性互异枠的剧本后,剧中精炼的台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2]( P239)
巴顿· 霍利迪是第一个论及琼生译的贺拉斯的枟诗艺枠评论者,在他的长诗里,将诗人与古希腊和古罗马喜剧诗人比较,夸张地赞扬了前者在戏剧和诗歌两方面的造诣,“你是一首内容丰富的讽刺诗,里面/投入最多的精力”。朱驰· 汤利也说琼生用学识的汗水令一种语言简明易懂,徜徉于希腊和罗马的古老文学王国里,在他的诗里这两种文学变得更加富丽堂皇。[2](P217)
第三阶段是褒扬与贬斥参半的阶段,贬斥的评论以德莱顿为首,约翰· 丹尼斯等追随,而理查德· 弗莱克诺和桂冠诗人托马斯· 沙德韦尔则据理以争。 德莱顿在其著名的枟戏剧诗论枠中以对话散文体对琼生的戏剧从古典作品的学识的角度进行了批评,应当说这篇评论虽然颇多偏颇之处,可还是对诗人的一些戏剧方面的独创和成就给予了肯定。 比如,琼生戏剧情节的复杂多样性,塑造的性情不一的人物等。尽管他自己的这篇文论有模仿柏拉图的枟理想国枠之嫌,可他在此文中批驳琼生的学古仿古,褒扬莎士比亚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在他眼中琼生只是循规蹈矩地写出规矩的剧本,缺乏莎
66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2年
士比亚那样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天分和才气。 在枟戏剧诗论枠中不乏名句为后人引用,如“他不只是坦白对贺拉斯的模仿,还是一个剽窃其他经典作家的学究;你从古人的雪地里到处可找到他的足迹”;“他公开打劫,根本不怕任何法律的制裁;就像一个君王那样侵占那些先哲,在别的诗人那里是盗窃的行为,在他身上竟只是成功”。[4](P169)
他在随后的两篇诗体评论里进一
步重申了这一观点,对莎士比亚推崇备至。 应当说在承接纪念和夸赞琼生文学成就成风之
时,敢于像萨克林似的出面力避颂歌也表现出一种令人钦佩的勇气。 他在 1671 年解释自己的观点时也提到不愿盲目地敬仰琼生,而无视其缺陷,进一步阐释在剧中表现一些人物的愚鲁只是观察的结果,缺少艺术品味,且其剧中只是自然地模仿愚鲁,他强调戏剧的娱乐性,还分析了琼生剧中时间的安排和人物的塑造。 此年经过与他人论争,他的批评力度愈加加大,说琼生性情剧是机械的表演,对话粗俗沉闷,借鉴古人是因为自己的才智疏浅,除了性情外,模仿不算完美,“因为爱是用其他语言所写的喜剧的基础,而在其戏剧中却极少提及”,[2](P304)对于
性情,他又说他那时代的绅士们看到相互间的蠢气还可接受,尽管也会允许科布和提布⑦以
其方式去说,对那些人手举大酒杯、身穿破衣烂衫却不能接受。 为什么不能接受? 如果生活本是如此,观众也没有什么理由否认,虽然说艺术真实与社会现实有距离,但是艺术真实也不能彻底脱离社会现实而存在,可见,此时的德莱顿的观点已经与中产阶级的立场混合在一起,似乎戏剧艺术只能表现一些可令中产阶级看来体
面的社会场景。 在 1676和 1683年两篇诗体的评论中,德莱顿批评了诗人不该将学识掺入戏剧,又指责后者在枟沃尔波内枠中加入低俗的滑稽剧。 然而,在 1694年致威廉· 康格里夫的诗中又写到“伟大的琼生以艺术鉴赏的威力愉悦一时:/竟是弗莱彻功力的两倍,他需要安逸”,[2](P337 -38)
又一反先前的观点,认为诗人盖过弗莱彻之名。
弗莱克诺在其 1670至 1671年间的诗里严正地还击了德莱顿的偏激,赞誉了琼生、弗莱彻
和莎士比亚三人,提出如果琼生有错,是时代的错,也不是他个人的错;还假设诗人如果依然在世,一定写得比德莱顿好,而倘若德莱顿生在彼时,一定写不出琼生那么好的作品来。 沙德韦尔不仅在枟幽默家枠一剧的收场白中为其好评诗人辩护,还在刊印该剧的前言中与德莱顿争辩,挑出后者文中自相矛盾之语,比如,又是规矩,又是沉闷平板,又是缺乏才智等,指正德莱顿认为的琼生剧中只表现世人的愚钝,指出此外还有一些人的邪恶和阴险狡猾,还辩护道诗人塑造的人物与现实相近,各人物的谈吐与其身份相符,塑造好管闲事的傻瓜和英雄人物需要同样的心智。 杰拉尔德· 兰贝恩也指出了德莱顿评语里的矛盾性,并借用诗人枟木材,或发现随笔集枠(或简称枟发现枠)里的名句申辩道,“(琼生的)模仿是以辛勤的蜜蜂为榜样,即从百花中吸取花蜜”,[2](P324)
诗人从不极力掩饰自
己对古人的借鉴,他也举出一些实例,证实诗人在其作品里翻译或模仿古人之处;相反,他严正指出德莱顿的戏剧没有一部是其自己脑力的结
晶,他不仅向古人借鉴,还向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本国人借鉴。 最后,他申明诗人在戏剧上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即便是与莎士比亚相比亦是如此。[2](P273)
约翰· 奥尔德姆在枟题琼生的作品枠这一首颂诗里也回击了来自诗人对立面的指责,认为那些人也是艺术的仇敌,颂扬诗人是英国戏剧功不可没的奠基人,在诗歌方面也是一扫他人空洞、不成形的诗风,诗人的心灵向读者展现出勃勃生气和烈火,其诗歌构成新创的美丽的世界,洋溢着自由、协调、秩序与和谐的气息,自然和艺术在其作品中结合并统一起来,在诗歌领域里诗人是强大的征服者,在学识世界里也不可小觑,他著述的经典经历了最尖刻的指责,接受了最严峻的挑战。
三、本· 琼生诗歌的独创性
近年来,国外琼生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层出不穷,但涉及其诗歌的比对其戏剧研究的成果相对要少多了,即便如此,大多论著也是针对某一类诗,或是二三类诗,甚或单独一首诗的研
76第 1期 郭 晖:本· 琼生的诗及 17世纪对其作品的批评
究,而全面的、专题的研究自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至今并不多,有关专著,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只有 5 部,国外的世界著名大学学位论文数据库收集的有关其诗的博士论文有 20 篇(1900 -2004年),且有二十多年来没有一篇全面评述其诗歌的论文,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博士论文仅有笔者的一例,本文侧重对其诗歌的评述,试图弥补这一空白。
现代许多版本的枟十七世纪英国诗歌选集枠里收入琼生的诗都不算少,道森和杜普雷合编的枟十七世纪英语诗歌详注集枠所收 17 世纪诗人的诗歌作品最多的当属琼生的,共 22首,每一首都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折射出诗人的才学与为人。[5 -6]
可以说,他们选录的诗是其诗中精华的精华,因为像枟以女性口吻写的诗枠、枟照贺拉斯说枠和枟题著名的旅行枠等也是上乘之作,却未编入其内。
琼生的诗形式多样,主题繁多,在 17 世纪的地位如何,在当时以及后来有什么样的影响,其诗中继承了什么,又反映了些什么,在其生前为什么形成一个“本之部落”或称“本之子”,等等,都值得深入细致的研究。 更重要的是研究琼生对今天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就会提出文学应该怎样发展的问题。 琼生是主张积极地向古人学习,而且主张向外族的著名诗人学习,但是从对其作品的整个欣赏和接受情况来看,贬抑的呼声不亚于褒扬的声音。 那么,文学向外族学习借鉴是对还是错,是值得嘉许还是应当受到批判;是天分、才气占统治地位,还是学识、艺术创造力占统治地位,或者说在文学创作中如何对待这四种元素,将会是琼生研究所要揭示的深层问题。 渐渐地笔者发现琼生研究这一块有很多待解决的问题,国内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专著仅笔者一例,其他大多数文献也是针对诗人的戏剧的研究。
自1947年赫福德和辛普森编辑的枟本· 琼生作品全集枠第八卷开始,琼生的诗历来被分为四个集子,前两个集子:枟警句讽刺集枠和枟森林集枠是在诗人生前即1616年出版的作品集中就收入的,于其过世三年后即 1640年凯内尔·狄格拜爵士编辑的第二个对开本作品集里又编
入了枟草木集枠。[7] 1947 年赫、辛二位学者又搜集编入了第四个集子:枟未辑集枠。 此后,又有三版诗歌全集,收编诗歌数目各有差异,甚至顺序也略有不同。 无论如何,目前琼生研究者们将赫、辛版的全集视为权威,尽管已有将此版现代化的呼声。⑧不管有什么样现代化的版式或
拼写,琼生诗歌全集前两集基本上是按写作时间分割的,诗集中主题不一,后两集则更甚。 若按四个诗集分别加以研究,分析其主题时势必重复,若按中心主题分别加以研究当是更为理想,须将总数 417 首诗一一归类,所耗时间不说,有些诗也是很难归入某一主题的。 所以,琼生诗歌研究的难度可想而知,比如下文分析的枟悼长子枠内容似乎与其诗体警句讽刺诗体名不相符的情况,但是因其是一首悼亡诗,很容易将之归入到挽诗系列,也还恰当。 诸如此类,不再一一分述。尽管琼生的诗歌语言与其戏剧也大致相
同,却相对更显精练、平易而言简意赅,每每情理交融,如下面这首广为人称颂的警句体挽诗:别了,你,我右手上的孩子与快乐。我的罪是对你寄太高的希望,爱子。你被
⑨借给我七载,为你我已偿还了,
命中注定分毫不差,就是这个日子,呕,我若能完全失去父亲之名! 为何人对应该羡慕的情形却悲痛欲绝?这么快便逃脱人世和肉身的狂躁,即便没别的苦难,老龄不也难熬?静悄悄地安息吧,问起,答:这里长眠着本· 琼生平生最好的诗文,缘此,从今往后,他所有的愿望是所喜爱的再也不要那么一往情深。(琼生枟悼长子枠⑩)抒情如此深切哀婉的诗,即便是铁石心肠
的读者也会为之所动吧。 首先,在诗人生活的年代,孩子夭折恐为常事;多恩的 12 个子女中在1613年到1617年的四年间就有五个夭亡,皕瑏瑡
可因为丧失年幼子女而写挽诗的诗人,从乔叟到琼生为止的英国著名诗人中,怕只有琼生一人,至少此诗可证明亲情在其心目中的分量。皕瑏瑢
其次,琼生给亲子的挽诗不是仅此一首,还有
86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2年
枟悼长女枠是为其半岁大就夭折的长女而写,诗中不仅表达了对亲人浓浓的深情,还有对宗教的笃信,正是这种坚定的信仰使其在痛失亲人之时有一种难得的心理支持,从“完全失去父亲之名”悲痛的极点突然转向孩子是在“天堂获得永生”这种自我劝慰的心态,即抒情又述理。 事实上,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抒情诗虽然强调对自然的热爱与感情的抒发,也是含有很强的理性的。 比如,雪莱的枟致———如果柔美之音死去枠:
如果柔美之音死去,乐曲将回响于记忆;如果娇美的紫罗兰病萎,清香将沁人心脾长相随。 /如果玫瑰谢世,玫瑰瓣被堆起为爱人的床;如果你去了,爱也将安睡在我那些情思上。
当然,雪莱的诗句充满柔情、凄美,像一曲动人心弦的小提琴曲,琼生的则更显得古朴平实,宛如古朴幽抑的竖琴曲。
在琼生之前,有善写叙事诗的乔叟,有善写十四行诗的怀特、西德尼、莎士比亚等,有善写史诗的斯宾塞,而琼生和多恩等 17 世纪诗人给英国诗坛带来了一个诗歌体裁和题材都焕然一
新的时代,比多恩更善于开拓英诗疆土的琼生,在其诗歌全集中有献给其资助者罗伯特· 西德尼、号称开创英国乡间别墅田园诗的枟题彭斯赫斯特枠、借戏剧情节而创作的温文尔雅的情诗枟致西莉亚枠、表现高尚之士情调的枟邀友共进晚餐枠、政治讽刺抒情诗枟照贺拉斯说枠、独特的代女性之诗枟以女性口吻写的诗枠和前文提到、常为评论家引用的枟纪念我最敬爱的大师威廉· 莎士比亚,及他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枠等,真是千情百理,无所不诗。 从某种意义上,英诗多样的形式开启了其内容的丰富与繁荣。
从以上三节可看出,尽管琼生的戏剧与诗歌作品有多部在英国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独创
性,仅在其作品成熟的世纪读者及学者对其作品的接受都是褒贬不一,而今天的读者和学者发现,对其作品持贬评观点的人并非彻头彻尾的无理取闹,但是对其作品中的古典与创新的结合的误读是不乏其人的,其代表人物是迪格斯和德莱顿。 而那些对其作品持褒扬观点的人除了少数格外慕名出于讨好诗人外,可以说的
确是真正理解琼生作品内涵的人,也是古典与创新相结合观点的支持者。 无论如何,琼生独创的英语诗歌是任何其他英国诗人所不能替代
的,尽管其作品在 17世纪的接受史与其质量不成正比,但还是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注释:①“接受史”一词源于王岳川的枟后现代主义文化
研究枠一书,他在书中是这样阐释的:“文学的历史就不
仅是作家和作品史,而(且)是作品的效果史”。 王岳川
所用的这个效果史,应是从整个文学来说,即广义上
的,而此处笔者想延伸这一用法,指某一位作家的作品
面世后各位读者根据各自的天资、经历和修养对该作
家作品的理解和评论即该作家的作品对某一位读者呈
现出与对其他读者不同的意义,这些意义随着时间的
积累而积累,所形成的历史称为该作家作品的效果史,
这里笔者称作接受史。
②比如说“文学的历史不仅是作家和作品史,而
(且)是作品的效果史”,同上。
③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时至今日,17 和 18 世
纪对琼生的研究资料原本很少,在国内这段时期的第
一手研究资料则更为匮乏,实难得之,只集中于克雷格
编辑的枟本· 琼生:批评遗产枠一书,虽然是二手研究资
料,也是相当系统、完善,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在布
拉德利和亚当斯合编的枟琼生研究的相关资料汇编枠一
书里大部分是书信等传记资料,即便有些评论也与克
雷格的 17世纪琼生作品的批评部分重合。 因而,只有
部分参考价值。
④该诗显然针对琼生印刷版的讽刺诗(“epigrams”一译枟警句讽刺集枠)。
⑤枟警句讽刺集枠的第二首即是枟致我的书枠,里面
写道:“书,某些人看到书名枟讽刺集枠/和我的署名会以
为/汝定是无耻、下流、满是敌意,/尖利如矛,至酸而
苦;/遂成狂妄无理之物,智墨糊涂,/如疯人掷石,无论
谁。 ⋯⋯”
⑥“谁,那个桂冠诗人?”编者节选了萨克林的悲剧
枟伤心之人枠第四场第五幕一段,并认定该剧中的人物
马尔提卡尼(Multecarni)先生无疑是为丑化琼生而塑造的。
⑦科布和提布均为琼生的喜剧枟个性互译枠中的人
物。
⑧参见马丁· 巴特勒的枟重新再现本· 琼生:文
本、历史和表演枠。
⑨指由上帝借给。
⑩文中诗歌若非特别注明,均为本文作者所译。
96第 1期 郭 晖:本· 琼生的诗及 17世纪对其作品的批评
皕瑏瑡参见帕特里德,枟多恩英诗全集枠中“多恩生平略述及时代背景”一节。
皕瑏瑢在枟牛津新版十七世纪诗歌选集枠和枟牛津新版十六世纪诗歌选集枠中我们读到安妮· 霍华德和约翰· 霍斯金斯分别写给儿子的诗篇,确切地说前者的诗篇虽然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但是该诗却不是诗人直接写给自己亲子的,因为该诗题目为枟摘自记善良的牧羊人痛失爱子的悲哀:挽诗:我在黑灰的草丛中哀
叹枠;此外,该诗中抑扬格三音步间以二音步的诗句,类似我国词的长短句,十行一节,共五节,这种诗歌形式与琼生的这首悼亡诗相比,淡化了悼念的沉痛感情,或许是由于短节奏易使人产生欢快情绪的缘故。 后者的是枟致我儿贝内迪克特· 霍斯金斯枠,“贝内迪克特,爱尔尚年幼。 未解言玄机,汝幸享自由;舌关须把好:禁之或被囚”。 像十六世纪的沃尔特· 雷利写给儿子的十四行诗一样,属于类似枟彦子家训枠的家训一类。 另
外,早在 1540 年约翰· 哈林顿在赶赴战场之前写有枟致母亲枠一诗,还写有枟丈夫致妻子枠和枟妻子致丈夫枠两首,都是给生者的,类似杜甫枟月夜枠写给远在陕西延安地区的妻儿的家书诗,而非悼亡死者的悼亡诗。
[参 考 文 献][1]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Craig,DH.Ben Jonson:the Critical Heritag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
[3] Johnson,A.W..Ben Jonson:Poetry and Architecture[M].Oxford: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4.
[4]Richter,David H., ed.,John Dryden,“An Essay ofDramatic Poesy”;William Wordsworth,“Preface to theSecond Edition of Lyrical Ballads”;P.B.Shelley,“ADefense of Poetry”.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M].Boston:BedfordBooks,1998(2).
[5]Dawson,Terence & Robert Scott Dupree.,ed.Seven-teenth-Century English Poetry:the Annotated Antholo-gy[M].England:Harvester Wheatsheaf,1984.
[6]Cummings,Robert ed.Seventeenth-Century Poetry:anAnnotated Anthology [ M ].Oxford, UK; Malden,Mass.:Blackwell,2000.
[7] Herford,C.H.and Percy Simpson, eds.Ben Jonson[M].Oxford:Oxford Clarendon Press,1925&1947.
责任编辑:张新潮
Ben Jonson’ s Poetry & the Seventeenth-Century’ sCritique on His Works
GUO Hui(Hebei Civi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Ben Jonson’s reputation depends half on Shakespeare’s support and half on hisown literary accomplishment: his drama inherit the classic one with innovation; the plots in hisplays started “humor plays” in England; his poems, different from the mainstream narrativeverse and sonnets, are written in epigram, elegy, letter and other styles; the subjects are alsoinnovative concerning family bond, rural life, and others.However, Jonson could hardly enjoyhis reputation peacefully with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here he lived,and the reader and thescholar commented his works with approval as well as condemnation.This paper includes an e-laborate review and discussion of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ticisms of Jonson’ s works with ananalysis of Jonson’s innovations in poetry and proposes a balanced and fair comment on Jon-son’s works,especially his poems.
Key words:Jonson;reception;innovation in poetic writing;balanced and fair;comment
07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