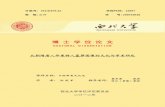《洛渭地区蒙元墓随葬明器之政治与文化考》,《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10期,页61-78。(A...
Transcript of 《洛渭地区蒙元墓随葬明器之政治与文化考》,《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10期,页61-78。(A...
061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JOU
RN
AL
OF
N
AT
ION
AL
MU
SE
UM
OF
C
HIN
A
古代史与文物研究
A Study of Yuan Dynasty Burial Objects from Luo-Wei Region in a Political-Cultural Perspective
内容提要:
洛渭流域蒙元时期的墓葬具有明显而统一的地域特征:表现出明显的仿古化趋势。随葬品中出现了大批
所谓仿“三代礼器”的陶明器,在墓葬结构和随葬品类别上则与唐代墓葬十分接近。这种墓葬面貌的复
古化实则反映出蒙元统治者在社会秩序和“礼乐”建设上的政治追求,也与当时这一地区曾作为忽必烈
潜邸、聚集了大批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潜邸旧部”密切相关,是区域文化、政治诉求和人群特点综合作用
的结果。
关键词:
洛渭地区 蒙元 明器 仿古 忽必烈潜邸
Abstract: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Yuan dynasty tombs discovered along the Luo-Wei river valley is the imitation
of the archaic style: a lot of earthenware burial objects are imitation of ritual vessels of the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he tomb format and burial objects show clear style of Tang tombs. Th ese phenomena refl ect the political
ideal of Mongol rulers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in keeping social order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a
large group of Confucianism-minded scholars and offi cial were active in the Luo-Wei region, where Kublai was the
administrator before he came to the throne.
Key Words: Luo-Wei region; Yuan dynasty; burial object; imitation of archaic style; Kublai’s qiandi [潜邸]
洛渭地区蒙元墓随葬明器之政治与文化考袁 泉 Yuan Quan
洛渭地区横跨今河南、陕西和甘肃三省,在蒙元时期分属中书省南部、河南江北行省北部以及陕
西行省辖下。这一地区曾属唐代两京范围,6-9 世纪时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墓葬面貌上更
确立了“两京模式”。入宋以后,这一区域的墓葬面貌则呈现出文化的滞后性与保守性,早期宋墓基
本上是唐墓的延续 ;北宋末期到金代,此区墓葬虽部分保存了唐代遗风,但最为盛行的还是装饰繁
缛的砖雕壁画墓。13 世纪前期以降 ,洛渭流域的墓葬风貌又为之一变,虽然在墓室结构与随葬品组
合上有所差异 [1],但均出土有一套古今并用的陶质明器,体现出明显的铄古铸今趋势 :包括车马、仪
俑等出行仪仗明器、以簠簋壶爵为代表的仿古陶器、以茶酒之具为代表的时器组合、谷仓和灶台类的
仓厨模型,以及小型动物俑(图一-六)。根据当前刊布的墓例,这批共性极强的蒙元墓葬主要集中在
洛水—渭水沿线,如洛水流域的焦作、洛阳、三门峡、洛川和延安,以及渭水两岸的西安、兴平、咸阳、
户县、宝鸡和漳县。
在这批面貌独特的随葬品中,陶制仿古礼器最为引人注目。这批仿古陶明器的参仿依据、组
袁
泉/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
0048
二○
一三年第一○
期
︵总第 123
期︶
062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JOU
RN
AL
OF
N
AT
ION
AL
MU
SE
UM
OF
C
HIN
A
古代史与文物研究
合模式、使用人群以及成批出现在特定区域、特定时段的原因,无不折射出蒙元时
期洛渭地区特殊的政治与文化面貌,更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蒙元统治者建设正统化“礼
乐”社会的政治追求。
图一 河南洛水流域蒙元墓随葬品组合 1:洛阳道北王英墓(1317年)随葬品
063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JOU
RN
AL
OF
N
AT
ION
AL
MU
SE
UM
OF
C
HIN
A
古代史与文物研究
图二 河南洛水流域蒙元墓随葬品组合2:洛阳赛因赤答忽墓(1365年)随葬品
二○
一三年第一○
期
︵总第 123
期︶
065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JOU
RN
AL
OF
N
AT
ION
AL
MU
SE
UM
OF
C
HIN
A
古代史与文物研究
图四 陕西洛渭流域蒙元墓随葬品组合2:西安曲江李新昭墓随葬品
二○
一三年第一○
期
︵总第 123
期︶
067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JOU
RN
AL
OF
N
AT
ION
AL
MU
SE
UM
OF
C
HIN
A
古代史与文物研究
图六 陇右渭水流域蒙元墓随葬品组合: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随葬品
一 关陇与伊洛:两种模式的仿古陶器
陕西西安 [2]、宝鸡 [3]、延安 [4] 等地的蒙元墓,甘肃漳县元代汪氏家族墓 [5] 和洛阳
王述墓 [6]、赛因赤答忽墓 [7] 中均集中出土了大批仿古陶礼器,这些发现近年来引发了研
究者对蒙元时期随葬陶器仿三代器用的探讨。谢明良通过对关陇和伊洛两地蒙元墓中出
二○
一三年第一○
期
︵总第 123
期︶
068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JOU
RN
AL
OF
N
AT
ION
AL
MU
SE
UM
OF
C
HIN
A
古代史与文物研究
土的簠、簋、爵、豆等陶器与礼书图示的系统对比,考证出原报告中定名为“仓”、“盒”
之属的龟钮容器应为簠、簋组合;并进一步指出:“跨越今陕甘两省的部分地区曾存在着
一股模仿《三礼图》礼器以为随葬仪物的风潮。与此相对的,洛阳地区元代墓葬陶器则
是采行了北宋宣和年间重修的《宣和博古图》的系统。”[8] 其考证为蒙元墓葬中这批所
谓“异形器”正其名、定其源,引发了学术界对墓葬器用仿古化现象的重视。许雅惠则
指出,《宣和博古图》对宋元以降州府庙学以及民间祭器系统的影响,更大程度上是通
过以《博古图》为基础修纂的《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等礼图来完成间接流传的 [9]。
然而,如果进一步深入考虑,蒙元墓葬仿古礼器面貌的差异似乎不仅仅是地域文
化和本据礼书体系的不同,还牵扯到礼器系统早晚时段各自有别的发展特征。所谓关中、
陇右蒙元墓中“仿《三礼图》系统”的陶礼器组合也并非全为聂崇义勘定的礼器面貌 :
虽然簠、簋组合完全与聂氏《三礼图》一致,但西安、宝鸡等地几乎每墓必出的一对
贯耳陶壶在形制上却属于《重修宣和博古图》的礼器系统,同时漳县汪氏家族墓中的
爵杯样式也与聂氏《三礼图》所记“雀别置杯于背以承酒”不同(图七)。倒是洛阳两
座元末墓葬所出陶礼器全合《重修宣和博古图》的器用规范(图八)。再结合关陇和伊
洛两地相关墓葬的年代考虑 [10],则可发现所谓仿聂氏《三礼图》系统的墓例最晚下葬
于1344 年,而洛阳两处元墓的时代则分别为1350 和 1365 年。此即言这种仿古陶器面
貌上的差异很可能也反映了蒙元礼器在不同时段的发展特征。换言之,与其说洛渭流
域两种随葬古器面貌上的差异反映了对《三礼图》和《重修宣和博古图》这两部礼书的
模仿,不如说蒙元礼器体系经历了一个由“杂宋金祭器而用”到“始造新器”的发展过程。
那么,到底“宋金祭器”的器用模式如何?“始造新器”又采用了怎样的礼器类型呢?
《元史·祭祀志》载 :“中统以来,杂金、宋祭器而用之。至治初,始造新器于江
浙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11] 这里提到的“宋金祭器”代表着什么样的礼器体系呢?这
就要从北宋时期的礼器建设溯源。
宋代古礼用制的研究,计有两种途径。一则鉴于“考汉时去古未远,车服礼器尤有
存者” [12],故查据汉唐以来诸儒著说,考诸版本定为一家而成书集册,最有代表性的当
为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一则基于两宋“太平日久文物毕出”[13],以存世的金石之器
为朝廷订正礼文,以备稽考 [14],大观年间的《重修宣和博古图》即属此列。需要注意的是,
聂氏《三礼图》模式的影响非常广泛,虽然徽宗政和年间见依《重修宣和博古图》确立
了中央和皇室的祭器系统,高宗绍兴年间也依此例确定所谓“新成礼器”的祭器模式 [15];
但地方州县和民间大多沿用了聂氏祭器的模式 [16]。由此可见,有宋一代所确立的祭器制度,
是在以《三礼图》和《重修宣和博古图》为代表的两种范式的相互补正中建立起来的。
金人南下占据淮水以北之后,劫掠了北宋皇室南渡时所携的大批祭器,继而参据
唐宋礼乐沿革,确立了金廷的祭器系统 [17]。宋廷祭器体系兼用聂氏《三礼图》和《重修
宣和博古图》模式,那么,金代所参据的唐代礼器模式又是怎样的呢?虽然唐代礼书
散佚不传,但从四库馆臣为《三礼图集注》所作的提要中,可见聂氏成书所据的六大
古本尽皆著录在隋唐史籍《经籍志》和《艺文志》中 [18]。换言之,聂氏《三礼图集注》
所勘定的礼器模式应与隋唐祭器颇多相似,一脉相承。除上述文献线索,唐恭陵哀皇
后墓 [19] 中出土的一套仿古陶器也为唐代礼器模式提供了实物依据 :其中“雀背负盏”
的爵杯、绘饰山峦的山尊和龟饰顶盖的陶簋完全可在聂氏《三礼图集注》中找到对应
的图像。也就是说,金代的礼器模式是杂糅了以《三礼图集注》和以《重修宣和博古图》
069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JOU
RN
AL
OF
N
AT
ION
AL
MU
SE
UM
OF
C
HIN
A
古代史与文物研究
为代表的两类礼器系统,而代表了隋唐器用传承,并在北宋时期流传甚广的聂氏《三
礼图集注》模式似乎影响更大。
由是可见,中统以来蒙元礼器的样式中存在着《三礼图集注》和《重修宣和博古图》
两套范式 ;换言之,蒙元礼器系统杂糅了隋唐器用和宋代“新成礼器”两套模式。这也
可以解释关中和陇右墓葬中不同体系仿古陶器并存的现象。那么伊洛地区两座元末墓葬
中全部采用《重修宣和博古图》模式的仿古陶器组合又作何解释呢?
1 2
3
4
5
图七 关陇地区蒙元墓出土仿古陶器与礼书图示对比图1. 宝鸡元墓陶贯耳壶 2.《宣和博古图》贯耳弓壶 3. 延安虎头峁元墓陶爵 4.《三礼图集注》爵 5、6. 宝鸡元墓陶簠、簋 7、8.《三礼图集注》簠、簋 9、10. 漳县汪氏墓陶豆、登 11、12.《三礼图集注》豆、登 13. 漳县汪氏墓铜爵 14.《宣和博古图》商爵
149 10 11 12 13
6 7 8
二○
一三年第一○
期
︵总第 123
期︶
070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JOU
RN
AL
OF
N
AT
ION
AL
MU
SE
UM
OF
C
HIN
A
古代史与文物研究
按《元史·祭祀志》记载,自至治年间礼器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始造新器于江
浙行省”。这里虽未说明所谓“新器”的样式,但南宋时期数次兴造《重修宣和博古图》
模式的“新成礼器”均是颁照江浙行省施行 [20],再考虑到朱熹《绍熙州县释奠仪图》
在淮水以南的影响,则江浙之地很可能确立了政和、绍兴礼器模式的地方传统。元廷
至治年间在江浙始造新器的样式,也很可能系统采用了《重修宣和博古图》体系的礼
器模式。洛阳王述墓尊、罍、簋、豆,赛因赤答忽墓中的牺象二尊、簠、簋、豆、壶,
均可与《重修宣和博古图》和《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中列出的礼器图示相对应。此类
“新器”模式元廷在至治年间既已颁定,为什么洛渭流域的墓葬直到元末才体现出这
种变化呢?事实上,中央和地方礼器制式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同步的,地方器用往往具
有明显的滞后性,前文提到的绍兴“新成礼器”颁定日久而州县祭祀仍用聂氏旧器就
图八 伊洛地区蒙元墓出土仿古陶器与礼书图示对比图1、2. 赛因赤答忽墓出土陶簋、簠 3. 《宣和博古图》周太师望簋 4. 《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簠 5. 赛因赤答忽墓出土陶著尊 6. 《宣和博古图》著尊 7、8. 赛因赤答忽墓出土陶象尊、牺尊 9、10. 《宣和博古图》象尊、牺尊 11. 赛因赤答忽墓出土陶山尊 12. 《绍熙州县释奠仪图》山尊
9 10 12
11
1 2 3
4 5 6
7 87
071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JOU
RN
AL
OF
N
AT
ION
AL
MU
SE
UM
OF
C
HIN
A
古代史与文物研究
是典型的例证。
综上,洛渭流域蒙元墓葬中仿古陶器组合的差异,反映出蒙元礼器制度从杂宋、金
模式到“别置新器”的发展过程。同时,也确如谢明良所说,这种差异一定程度上也与
区域文化传统相关。伊洛地区深受许衡儒学体系的影响,而许衡是“朱学”北传和普及
中最重要的人物 ;朱熹认同的礼器系统是《重修宣和博古图》确立的器用模式,这种模
式也在洛阳元末墓葬中仿古陶器的类别和造型上得以承袭。而从唐恭陵哀皇后墓中的随
葬礼器可见,关中地区自唐代以来确立的仿古礼器制度在当地的蒙元墓葬中依然得以沿
用,很可能代表了这一地区经学传统在器用规范上的取向。再结合山东济宁张楷墓中造
型独特的随葬陶器 [21],或可推知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在仿古陶器的使用上存在由于经
学渊源不同造成的地区差异。
总之,不管是《三礼图》模式还是《重修宣和博古图》体系,仿古礼器规制的讨论、
器形的勘定以及使用的普及均反映出统治者试图建立其心目中礼乐有序、堪比“三代”
之治的理想社会。对于南下尽收汉地的蒙古族统治者而言,这种传统礼制建设的努力更
是其确立正统化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另一方面,除了仿“三代礼器”,洛渭地
区的蒙元墓葬在墓室结构和随葬器用上也显现出明显模仿唐墓规制的现象。
二 礼乐追求:洛渭元墓与唐代两京墓葬的相似性
关中和伊洛地区的宋金墓葬虽然也有土洞墓,但并不普及,主流墓葬形制还是仿
木构砖雕壁画墓,随葬品组合上也未见不同于周边地区的殊异之处。然而逮至蒙元时期,
这一地区的墓葬结构却突然流行起长斜坡墓道的近方形、无装饰土洞墓和砖室墓,左
右小龛和前后双室的情况也十分常见。这种墓室形制很难在同区宋金墓中找到类比对象,
反而与唐代两京地区的墓葬面貌十分相似。
同时,这些蒙元墓葬的随葬品中除了仿三代礼器的陶器组合外,由车马、仆从组成
的出行仪仗俑及鸡、犬、猪、牛、羊等小型动物俑也和唐墓明器组合相仿佛 ;尤其是胡
人俑和骆驼俑更是沿用了唐墓随葬陶俑中的代表类型 [22](图九-一一)。
为什么该区域内的蒙元墓葬跳过了宋金模式而选择模仿唐代的墓葬特征呢?这种特
殊现象可能要与蒙元统治者对“贞观故事”的特殊态度有关。日本学者箭内亘曾著《元
世祖与唐太宗》一文,考证忽必烈以洛渭流域为潜邸时曾将唐太宗李世民作为欣赏和钦
羡的对象,其建立藩府、招揽四方人才的行为即是对太宗“秦王幕府”的仿效 [23]。潜邸
旧臣徐世隆记 :“上之在潜邸也,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文学四
方之士,讲论治道,终始太平,喜而慕焉。”[24] 明确提出忽必烈集结藩邸一念是在唐太宗
招致十八学士启发下的产物。以此为目标,忽必烈广纳各色人才,时有“史天泽、刘秉忠、
廉希宪、许衡、姚枢等实左右之,当时称治比唐贞观之盛”[25]。不仅世祖朝如此,整个
元代的上位统治者均以建立所谓“贞观之盛”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同时以唐太祖与谏臣
魏征的相处模式作为理想化的君臣关系。《贞观政要》一书也获得了广泛重视,不仅皇
帝与群臣通读之,更将其译作蒙古语大加推广。如忽必烈初即位,在征召人才时就提出聘
“魏征之臣”:“上即位,首召至都,问曰:‘朕尝命卿访求魏征等人,有诸乎?’对曰:‘许
衡即其人也。万户史天泽有宰相才,可大用。’”[26] 仁宗、英宗朝时,更命儒士将《贞观政
要》译作蒙古语,山东嘉祥元墓的墓主曹元用就曾“奉旨纂集甲令为通制,译唐《贞观政
二○
一三年第一○
期
︵总第 123
期︶
072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JOU
RN
AL
OF
N
AT
ION
AL
MU
SE
UM
OF
C
HIN
A
古代史与文物研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图九 洛渭地区蒙元墓随葬品组合1. 赛因赤答忽墓陶豆 2. 西安红庙坡元墓陶簠 3. 西安红庙坡元墓陶壶 4. 西安电子城元墓陶灶 5. 西安刘义世墓陶井筒 6. 西安刘义世墓陶仓 7-12. 西安南郊元代王世英墓动物模型 13. 户县贺氏墓陶胡人控驼俑14-16、19、20. 西安南郊元代王世英墓车马仪仗俑 17. 西安电子城元墓陶骆驼俑 18、21、22. 西安曲江孟村元墓车马仪仗俑
2218 19 20 21
073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JOU
RN
AL
OF
N
AT
ION
AL
MU
SE
UM
OF
C
HIN
A
古代史与文物研究
图一○ 唐恭陵哀皇后墓随葬品组合1. 陶簋 2. 陶山尊 3. 陶爵 4. 陶灶 5. 陶碓(与蒙元墓中的陶仓具有相似指代意义) 6-8. 车马仪仗彩绘陶俑
6 87
4 5
31 2
要》为国语”,“书成皆行于时”[27]。直至元末顺帝朝,依然盛行以“纳言魏征”来譬喻
理想化的君臣模式 [28]。
由是观之,蒙元统治者对唐太宗和其治下的贞观盛世颇多钦羡,在政策制定上也多
有借鉴。需要注意的是,元世祖忽必烈仿效“秦王幕府”组建潜邸、征召人才的重要据点,
就是以怀孟路和奉元府为中心的洛渭流域 ;从碑志材料看,洛渭流域所见蒙元墓葬的所
属人群也多为忽必烈潜邸旧部及其家族成员:这就为这一地区蒙元墓葬中追仿唐墓制度
的现象提供了合理的注脚。
二○
一三年第一○
期
︵总第 123
期︶
074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JOU
RN
AL
OF
N
AT
ION
AL
MU
SE
UM
OF
C
HIN
A
古代史与文物研究
三 潜邸旧部:洛渭地区蒙元墓的所属人群
从碑志和墓券材料出发,结合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用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笔者发现,
洛渭流域这批在墓葬面貌上多仿唐制,并随葬一套仿古礼器的蒙元墓基本归属于忽必
1 2 3 4
5 6
图一一 偃师杏园唐墓随葬品组合1-4. 小型动物俑模型 5. 车仗模型 6. 胡人控驼俑 7、8. 仪仗俑 9、10. 男女仆侍俑
8 9 107
075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JOU
RN
AL
OF
N
AT
ION
AL
MU
SE
UM
OF
C
HIN
A
古代史与文物研究
烈潜邸旧部及其家族成员,这一群体均有一定的儒家化倾向。
忽必烈于1251年获得了对中国北部的宗王管理权,随即在怀孟、京兆和邢州进行了
一系列改革,计划在这些地区重新建立“中国”模式的政府,恢复经济。1252 年,当蒙
哥向皇室成员分配新封地时,忽必烈采纳了儒士幕僚姚枢的建议,要求并得到了位于战
略要地又极为富饶的渭水流域作为他的私人封地 ;借助谋士们的帮助,继续管理体制的
改革和恢复经济的努力 [29]。
《元史》卷四《世祖本纪》载 :“甲辰(1244 年),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
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经世大典·序录·典礼》“讲进”条言:“世祖之在
潜藩也,尽收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而顾问焉。”[30] 赵孟 也提及:“世祖潜
邸,延四方儒士,咨取善道,故能致中统至元之治。”[31] 明人叶子奇《草木子》则阐述了
儒士在大元建朝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世祖既得天下,足赖姚枢牧庵先生、许衡鲁斋先生
诸贤启沃之力。”[32] 这批洛渭之地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潜邸旧侣”主要包括“儒士”、“方
技”和军政人员三类人群。
1. 尊崇儒学的知识分子,即所谓的“儒士”
蒙元早期的“儒士”群体中既有忽必烈专门遣使礼聘的正统儒学名流,也有自
金代起就律科及第的儒学世家,还包括了大批隐而不仕的地方精英。这一集团往往
是尊崇程朱礼学的儒者,在潜邸中多处于师儒地位,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当推许衡 [33]、
姚枢和窦默。这些儒士努力将程朱儒学传播进蒙古汗廷,以确立其在汉地统治的正
统性 ;另一方面,也极力促成传统礼制在整个社会的普及,杨惟中的“慨然欲以道济
天下”、姚枢的“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许衡的“不如此则道不行”均反映出这种“援
俗入礼”和“以礼规俗”的治世理念,所谓“礼从宜、使从俗”。洛渭地区蒙元墓中
兼用古今之器随葬的墓葬传统,或与这一人群讲求礼制传承又强调结合时宜的治世
理念相关。
2. 业有专精的技术人员,又名“方技”
这批人员或擅长医药、或精于建筑、或长于水利、或精通语言、或专于吏治,也有
因特殊机遇而被忽必烈收作近侍、宿卫的。与前类儒士群体相较,这一群体的贡献不在
于经世之学的理论构建,而是践履笃实的实行者 [34]。如焦作中站元墓墓主靳德茂 [35] 就
是以擅长医术而入招潜邸的,先被征为尚药太医,忽必烈即位后被擢升为太医院副使,
死后又因上位者“念藩邸之旧”而追赠嘉议大夫、怀孟路总管。而官至中书左丞的贺
胜家族,则是自先祖贺贲起即被收入忽必烈宿卫近侍的“大跟脚”汉人勋贵集团,历
朝均凭借“世祖旧部”享有封赐。
3. 军政人员
西安曲江池元墓墓主段继荣家族五世在金代皆有官阶,段继荣本人于金同知昌武节
度使在任期间归顺大蒙古国。而漳县汪氏家族则是世掌巩昌路军政大权的军政世家 :金
元之际,巩昌汪氏以武功起家,称雄陇右;入元后仍世袭其地,门阀显赫。从金朝末叶起,
到元朝灭亡的百余年里,汪氏六代握持兵柄,世袭巩昌等处便宜都总帅府都总帅,是元
代传世最久、在西北地区有较大影响的世侯之家。
二○
一三年第一○
期
︵总第 123
期︶
076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JOU
RN
AL
OF
N
AT
ION
AL
MU
SE
UM
OF
C
HIN
A
古代史与文物研究
以上三类人群虽然进入忽必烈潜邸的方式各有不同,但都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元
代大儒许衡家族墓自不待言;以医术征召入藩邸的靳德茂“自幼勉学”,且丧葬之礼“小敛、
大敛皆尊古制”,墓志碑文更假怀孟路学正之手 ;洛阳大都路总管府判王英是金代律科
及第的儒学世家 ;贺胜师从许衡,“通经传大义”[36] ;连兵马起家的漳县汪氏家族也颇重
儒学,《汪氏祠堂碑》载其家“虽在军旅,崇儒重道,不废讲习”[37]。
四 小 结
洛渭流域蒙元时期的墓葬风貌尽管在墓葬形式和随葬品组合上存在河南、关中和陇
右三个小区域的局部差异,但均体现出相对统一的地域和时代特色 :具有明显的仿古化
趋势。随葬品中出现了大批所谓仿“三代礼器”的陶明器,在墓葬结构和器用类别上则
与唐代墓葬十分接近。这批墓葬中的仿古礼器分别依据了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和《重
修宣和博古图》两套器用模式,在反映出区域差异的同时,也代表了蒙元礼器建设由“杂
宋金祭器而用”到依绍兴礼器模式“别置新器”的阶段性发展脉络。另一方面,洛渭流
域这批随葬有成套陶明器的土洞和砖室墓在墓葬结构和随葬品组合上与唐代墓葬十分接
近,可以说是在时隔宋金两朝后重新再现了唐代“两京模式”的墓葬模式 ;这和统治者
对贞观盛世的推崇密切相关,故而从潜邸组建、人才征召到治国策略上均对唐代“秦王
幕府”故事颇多借鉴。
洛渭地区蒙元时期墓葬面貌的复古化和墓主人群的集团化,实则反映出蒙元统治者
在社会秩序和“礼乐”建设上的政治追求,也与当时这一地区作为忽必烈潜邸、聚集了
大批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潜邸旧部”密切相关,是区域文化、政治诉求和人群特点综合
作用的结果。
附记:本研究分别受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蒙元时期墓葬研究”(项目批号11YJC780004)、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蒙元时期墓葬研究”(项目批准号13CKG015)资助。
注释 :
[1] 根据墓室结构与随葬品类别的差别,可将
洛—渭流域这一横跨豫、陕、甘的墓葬文
化区分作三个小区 :其一是以焦作、洛阳
为中心的河南地区,墓葬形制全为弧顶土
洞墓 ;其二是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地区,
墓葬形制兼有土洞墓和砖室墓两类,随葬
明器类别丰富,包括了仪俑和器物组合 ;
其三是为以漳县为中心的甘肃地区,墓葬
形制仍然沿用了这一地区宋金时期流行的
攒尖顶砖雕壁画墓,随葬品仅见器物组合,
未发现仪俑。
[2] 西安地区刊布的蒙元墓例计有 :曲江池至
元三年(1266 年)段继荣墓(陕西省文物
管理委员会 :《西安曲江池西村元墓清理
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 6 期)、
电子城泰定年间墓(翟春玲等 :《西安电
子城出土元代文物》,《文博》2002 年第 5
期)、至正四年(1344 年)刘义世墓(刘
安利 :《西安东郊元刘义世墓清理简报》,
《文博》1985 年第 4 期)、玉祥门外元墓
(陕西省文管会 :《西安玉祥门外元代砖墓
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 1
期)、南郊山门口墓(王九刚、李军辉:《西
安南郊山门口元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
物》2006 年第 2 期)、南郊王世英墓(西
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西安南郊元代王世
英墓清理简报》,《文物》2008 年第 6 期)、
北郊红庙坡墓(卢桂兰等 :《西安北郊红
077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JOU
RN
AL
OF
N
AT
ION
AL
MU
SE
UM
OF
C
HIN
A
古代史与文物研究
庙坡元墓出土一批文物》,《文博》1986 年
第3期)、曲江孟村墓和泰定二年(1325年)
李新昭墓(马志祥等:《西安曲江元李新昭
墓》,《文博》1988 年第 2 期)。
[3] 刘宝爱、张德文:《陕西宝鸡元墓》,《文物》
1992 年第 2 期。
[4] 延安市文化文物局:《延安虎头峁元代墓葬
清理简报》,《文博》1990 年第 2 期。
[5] 甘肃省博物馆等:《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
族墓葬》,《文物》1982 年第 2 期。
[6] 洛阳市博物馆 :《洛阳元王述墓清理记》,
《考古》1979 年第 6 期。
[7] 洛阳市铁路北站编组站联合考古发掘队 :
《元赛因赤答忽墓的发掘》,《文物》1996
年第 2 期。
[8] 谢明良:《北方部分地区元墓出土陶器的区
域性观察—从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陶
器谈起》,《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九卷第四
期,2002 年。
[9] 许雅惠:《〈宣和博古图〉的“间接”流传—
以元代赛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与〈绍熙
州县释奠仪图〉为例》,(台北)《国立台湾
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十四期,2003 年。
[10] 受材料刊布的局限,漳县汪氏家族的仿古
陶器自元及明尚看不出明显的阶段变化 ;
同时结合这一地区墓葬形制同样沿袭宋元
旧制的“滞后性”特点,也可以将此区仿
古陶器面貌缺少变化的原因归诸陇右地处
偏远的文化保守性与发展滞后性上。
[11] 《元史》卷七四《祭祀志》“祭器”条,中
华书局,2005 年,第 1847 页。
[12] (明)刘绩:《三礼图》卷首《提要》,文渊
阁《四库全书》本,第 129 册,第 285 页。
[13] (宋)王黼等 :《重修宣和博古图》卷七
“象尊”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840 册,第 512 页。
[14] (宋)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尚
书省牒议礼局”条载 :“大观二年十一月
二十日,承尚书省札子,朝议大夫试兵部
尚书兼侍郎充议礼局详议官薛昻札子奏 :
臣窃见有司所用礼器如尊爵簠簋之类与大
夫家所藏古器不同,盖古器多出于墟墓之
间,无虑千数百年,其规制必有所受,非
伪为也。礼失则求诸野今,朝廷欲订正礼
文,则茍可以备稽考者,宜博访而取资焉。”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647 册,第 10 页。
[15] (清)徐松 :《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
一》:(绍兴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礼部
太常寺言,勘会国朝祖宗故事,遇大礼其
所用祭器并依三礼图用竹木制造,至宣和
年做博古图,改造新成礼器,内簠簋尊罍
爵坫豆盂洗用铜铸造,余用竹木,今来若
并仿博古图样制改造。”《续修四库全书》本,
第 822 册,第 35 - 36 页。(宋)朱熹:《晦
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八《释奠申礼
部检状》记:“某伏见政和年中议礼局铸造
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
象淳古,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
法,故绍兴十五年曾有圣旨,以其样制开
说印造,颁付州县遵用。”《四部丛刊》初编,
133 - 37 函。
[16] 成书于南宋的《事林广记》作为一部日用
百科全书,其列出的祭器组合图示明显可
见聂氏《三礼图集注》的巨大影响。详
见(宋)陈元靓 :《事林广记》戊集卷一
《祭器仪式门》,中华书局,1999 年,第
365 - 366 页。而朱熹修撰《绍熙州县释
奠仪图》的动机,则源于南宋州县祭器仍
多用聂氏《三礼图》模式而不合绍兴确立
的“新成礼器”式样。
[17] “世宗既兴,复收向所迁宋故礼器以旋,乃
命官参校唐宋故典沿革,开详定所以议礼,
设详校所以审乐。”《金史》卷二八《礼志》,
中华书局,1975 年,第 691 - 692 页。
[18] “《隋书·经籍志》列郑元及阮谌等《三礼图》
九卷,《唐书· 艺文志》有夏侯伏朗三礼
图十二卷、张镒《三礼图》九卷,《崇文总
目》有梁正《三礼图》九卷⋯⋯《四部书
目》内有《三礼图》十二卷,是开皇中勅
礼部修撰⋯⋯所谓六本者,郑元一、阮谌二、
夏侯伏朗三、张镒四、梁正五、开皇所撰
六也。”(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提要》,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9册,第2页。
[19] 参考唐恭陵哀皇后墓可见,关中地区在唐
代墓葬中已使用成套的仿簠、簋、爵、尊
之类的仿古陶明器。详见郭洪涛 :《唐恭
陵哀皇后墓部分出土文物》,《考古与文物》
2002 年第 4 期。
[20] (清)徐松 :《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
一》:(绍兴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今看详欲乞先次将圆坛上正配四位合用陶
器,并今来所添从祀爵坫并依新成礼器仿
博古图,内陶器下平江府烧变,铜爵坫令
建康府铸镕,其竹木祭器令临安府制造。”
第 35 - 36 页。
又《中兴礼书》卷五九《明堂祭器》:“绍
二○
一三年第一○
期
︵总第 123
期︶
078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JOU
RN
AL
OF
N
AT
ION
AL
MU
SE
UM
OF
C
HIN
A
古代史与文物研究
兴元年三月八日,太常寺少卿迟等言,堪
会将来大礼合祭天地并配祖宗所有合用大
乐祭器,乞令两浙江东路转运司取索所属
州军县镇⋯⋯祀天并配位用匏爵陶器,乞
令太常寺具数下越州制造,仍乞依见今竹
木祭器样制烧造。”第 242 页。
[21] 济宁市博物馆:《山东济宁发现两座元代墓
葬》,《考古》1994 年第 9 期。
[22] 这批墓葬虽然墓室结构有异、墓主身份不
同,但都随葬一套灰陶的明器,其中以簠、
簋、尊、壶等仿古器物,车马和男女侍俑
等出行仪俑,以及鸡、羊、猪、牛、龙、
龟等一组小型动物俑最具特色。尤其是在
蒙古国时期至元代前期(1213 - 1320),
该地区蒙元墓葬中的出行仪俑中体现出明
显的“唐代模式”,骑驼或牵驼的胡人俑和
头梳鹦鹉髻的女俑均可在同一地区的唐墓
明器中找到原型。关于洛-渭流域蒙元墓
葬的区域特征与发展规律,详见袁泉:《略
论“洛-渭”流域蒙元墓葬的区域与时代
特征》,《华夏考古》2013 年第 3 期。
[23] (日)箭内亘著、陈捷等译《元世祖与唐
太宗》,《蒙古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32
年,第 94 - 105 页。 萧启庆在论述忽必
烈潜邸集结的历史背景时,也论及这一问
题。详见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
《内蒙古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
2007 年,第 118 页。
[24] (元)苏天爵辑撰、姚景安点校《元名臣
事略》卷一二“太常徐公撰墓碑”条,中
华书局,1996 年,第 238 页。
[25] 《元史》卷一七六《王寿传》,第 4103 -
4104 页。
[26] (元)苏天爵辑撰、姚景安点校《元名臣
事略》卷八“内翰窦文正公”条,第 152 页。
[27] 《元史》卷一七二《曹元用传》,第 4026 -
4027 页。
[28] 《顺帝本纪》载:“帝曰:‘昔魏征进谏,唐
太宗未尝不赏。汝其受之。’”《元史》卷
三九《顺帝本纪》,第 838 页。
[29]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
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6 年,第 421 页。《元史·地理志》
卷五八“怀庆路”条:“宪宗六年,世祖在
潜邸,以怀孟二州为汤沐邑。”第 1362 页。
[30] (元)苏天爵:《元文类》卷四一,文渊阁《四
库全书本》,第 1367 册,第 508 页。
[31] (元)赵孟 :《靳公墓志铭》,载《松雪斋
文集》卷九,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台北)世界书局,1988 年,第 402 册,
第 346 页。
[32] (明)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中华书局,
1997 年,第 47 页。
[33] 许衡神道碑的材料详见郭建设等 :《许衡
神道碑述考》,《中原文物》2006 年第 4 期。
其弟许衎和许衎之子许师义的石墓志则见
刊于索全星 :《焦作市出土二合元代墓志
略考》,《文物》1996年第3期;索全星:《许
衎、许师义墓志跋》,《华夏考古》1995
年第 4 期。
[34] 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内蒙
古而外中国 :蒙元史研究》,第 123 页。
[35] 靳德茂家族墓相关资料详见焦作市文物工
作队等:《焦作中站区元代靳德茂墓道出土
陶俑》,《中原文物》2008 年第 1 期。
[36] 《元史》卷一七九《贺胜传》,第 4149 页。
[37] 张维 :《陇右金石录》卷五,《中国西北文
献丛书》第182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
转引自汪小红:《元代巩昌汪氏家族研究》,
兰州大学 2007 年硕士学位论文。
(责任编辑 丁鹏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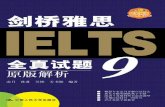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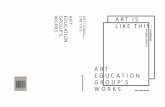
![方形折页EinScan HX[EN]V1.2](https://static.fdokumen.com/doc/165x107/6316a3f61e5d335f8d0a130f/einscan-hxenv1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