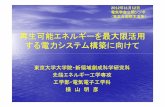“是”类系词再研究
Transcript of “是”类系词再研究
“是”类系词再研究* ①
张新华
提要 “是”类系词表事物之为其自身的成立方式,语义为一般性
的“运行”,为所述名词指派“个体、体事”的论元角色。个体与体事
有四种表现层次,因而形成系词句的不同构式。历时看,系词有代
词、动词两种来源,动词“为”可直接提示系词的功能实质。“为”虽
后来基本被“是”取代,但仍保留在“V-系词”这样更深的句法环
境中。
关键词 “是”;“为”; 个体; 体事; 系词化
一、“是”类系词研究概述
汉语系词有“是、发”两类,“发”主要与形容词组合,如“脸发红”,“是”
主要与名词组合。本文讨论“是”类,相关研究包括三方面: 演化过程、功能
实质、搭配情况。
1. 1 关于系词的演化
演化是一个语法成分形成其功能实质的具体过程,系词意义很抽象,通
过观察演化过程有助于了解其实质。类型学的考察表明,不同语言的系词
有代词、动词两种来源。自王力( 1937) 以来,学界多认同汉语系词“是”为指
示代词源。阿拉伯语等系词则由第三人称代词虚化而来。但方法论上,代
词系词化的考察预设了如下前提: 原来主谓或同位语的二成分间本存在等
同判断的语义关系,只是未予编码,后来其间由于常出现回指代词,所以后
者就被解释为编码该功能的语法成分。因此,这方面的考察只从现象上追
①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叙实谓词的构式与语篇接口研究”( 项目
号 14BYY124) 的支持,特此鸣谢!
73“是”类系词再研究
溯了一个词语如何成为系词,却并不能揭示系词自身的功能内涵。
动词源可提示系词的功能实质,这以印欧系的多数语言为代表。据海
德格尔( 1935) 考证,古希腊语系词 eimi( 即多数现代印欧语 be 类系词的语
源) 有三种来源: 1 ) 最古老的词根是 es,及梵文中的 asus,形态变化包括
esmi、esi、seti、asmi 等,拉丁文是 esum、esse,意思是“生活、活着”。2 ) bh、
bheu,指“起来、起作用、做”一类意义。3) sein,其形态变化如印度语 vasami、
日耳曼语 wesan,指“居、停、留”一类意思。从深层看,三种用法其实相同:
都表事物自身的运演,即事物的成立方式,而这正是系词内涵的核心。房德
里耶斯( 1992: 139,1921) 也发现了这个演化关系,并指出: “我们可以把这
种降级的工作一直追寻下去,把表示‘存在’的动词缩小到系词的作用。”此
说法有点含糊,实际指系词在语义上要比“存在”更具一般性,“缩小到”的意
思其实是“概括为”,即系词指事物最一般性的存在。
汉语界对系词的演化多只关注代词“是”,其实汉语二源兼有: “为”是
动词源,类似印欧语 bh,先出,“是”为代词源,后出。
1. 2 关于系词的实质
这方面的研究最为薄弱,争议也最多。从名字看,“系词”之称“系”
( copular,linking) ,着眼于其功能是把名词或形容词联系于主语,但这只是一
种纯形式的空洞说法,并未说出系词的实质。另有“判断词、断词、决词”等
说法,这着眼于说话人对事物的语用关系,该语义要素在系词内涵中的地位
也有待阐述。
马建忠( 1898) 认为系词的功能是表主宾“所指相同”“为一”,类似的,
Halliday( 1968) 称系词句为“等同句”,表“等同格”,相关成分为“等同项”与
“被等同项”。“等同”的提法很准确,但只是对经验事实的宏观描述,不能指
出决定系词用法的深层机制。例如,所谓“等同”实际预设存在两个项目,且
其间有所差异,所以系词的一般用法是“A 是 B”,如“他是工人”,而绝对等
同是 A=A,如“他是他”,是系词的有标记用法。这就提示我们,事物在差异
中保持同一的具体情形才是系词功能的基本内涵。对系词的关注,哲学界
要比语言学界多,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一直是热点话题,ontology( 本体论) 的
词根 ont 即古希腊语系词。康德( 1878) 一方面认为系词“仅设定一事物或某
种规定,一若其自身存在者”,另一方面却又认为系词不是一个谓词,不能对
事物做出陈述。这个观点后来在哲学界影响甚大。其实一般看,普通谓词
74语言研究集刊( 第十三辑)
表事物的某具体展开样式、存在方式,可概括为存在谓词,系词则表事物自
身的最一般成立,属本体谓词,但二者对事物都是有所述谓的,把它们完全
对立起来,不可取。
系词的语法属性很特别。一方面,它意义非常空,却并非虚词而是动
词; 另一方面,系词功能很复杂,如,可充当谓语部分的核心,作为某些语法
意义( 如人称、情态、时间等) 的总和、载体,以及使非述谓成分具有述谓功能
等。另外,由于系词动作性极弱,所以对一般谓词好用的论元理论似乎不适
合它,因而有学者指出系词并非谓语的一部分,小句的语义只取决于谓语的
其他部分。这实际就使系词的本性变得不可知。Geist( 2008) 指出,系词句
对当前的句法语义理论是个困境。还有学者认为,研究系词句的最大困难
在于正面给出一个关于系词本质和功能的定义,这甚至是不可能的。实际
情况并非如此。
1. 3 关于系词的搭配
一般认为系词的功能是联 系 名 词、形 容 词,这 种 说 法 并 不 全 面。据
Pustet( 2003) 考察,系词在不同语言中的使用有四种情形: 1. 名词、形容词、
动词都可直接做谓语,都无需系词,如塔加路语( Tagalog) ; 2. 只有名词需要
系词以做谓语,如缅甸语( Burmese) ; 3. 名词和形容词需系词,如英语、德语;
4. 三类词都需系词,如曼丁哥语( Bambara) 。这个事实有两方面意义: a. 动
词、形容词、名词三种词与系词的组合表现为一种蕴含关系; b. 与名词组合
显示了系词的典型功能,但与形容词、动词组合却显示系词在语义上进一步
虚化,形态化程度更高,成为一个指纯述谓性的语法标记。这对汉语“为”系
词性的认识颇有启发。学者对系词多关注“是”,其实“为”在古汉语中是一
个系词性更强的语法成分,一个重要根据就是它常与形、动组合,详后。同
样,现代汉语“是”也有由名词而逐步扩大为与形容词、动词组合的趋势,这
就显示了其系词性在增强,如“他们是在跳舞、丙肝是通过血液传播”,“是”
语音上轻读,并非强调用法。总的来看,组合限制对认识一个语言成分的性
质有帮助,但终究不能代替关于对象自身的说明。如 Mikkelsen( 2005) 所指
出,这种“侧面”式的研究根本上是一种“循环论证”。
概之,以往研究涉及系词问题的各方面,但尚待深入。本文拟系统揭示
系词的功能实质。
75“是”类系词再研究
二、系词所述名词的论元角色及小句构式
学者多认为系词只有纯句法的关联作用,并无语义内容,本文不同意该
说法。无论实词虚词,语言成分的句法功能都以其自身的语义内涵为根据,
系词也不例外。
2. 1 系词的语义内涵
系词属动词,且是一种语义最概括的动词,要认识系词的内涵须先了解
谓词的一般功能原理。谓词对名词有所“展开”。名词表事物,这是一种整
体统括的编码方式,即把事物的全部物质内涵统摄为一个整体,因此,名词
有无限的存在可能性,但一切都尚未实现。不同谓词区别的根据就在于对
事物分化的具体程度、情形不同,如,形容词对事物的展开是连续性的,动作
动词是离散性的,形成明确分开的不同环节,后者抽象看即时间。普通谓词
指一种特定的展开样式,涉及事物内涵的多方面。如“拿”以手部从全身的
分化为前提,且手自身又进一步特殊分化,因而形成复杂的环绕方式; 整体
的“人”对“手”则表现为控制关系。对事物在一个维度上的展开就形成动词
的一个语义参数,而普通动词必然是多参数的,因此都具有复杂性的特征。
系词则不同,它对事物未做任何局部殊指化,而只表事物全身最一般性
的运行、演绎,这在现象上就表现为事物的一般成立、存活。例如,怎么就算
“他是人”呢? 具体机制就在于: 抽象的“他”本一无所是,通过对“人”这种
特殊功能角色的实际运演,就把“人”确立为自己的真实本体,在此特定方
面,“他”就与“人”直接等同,合二为一。正因为普通谓词的内涵中都具“运
行”这个语义要素,而系词指一般运行,因此,系词可作为各种述谓功能的代
表,即它可依次用于连接名词、形容词、动词三种实词的根据。在这三种功
能里,系词的虚化程度就越来越高,动因是: 名词自身所含展开义最弱,所以
最需系词的帮助才能具有述谓功能,形容词次之,而动词自身的运行义最显
著,因此其前系词就只表现为单纯的形式标记。
可见,与连接形容词、动词相比,连接名词的系词在语义上还是很实在
的,很接近实义动词,并不像一般想象的那么虚。这个虚的度就是,与普通
动词一样,系词也具有时的语法特征,只是缺乏体的特征。时指一个事态整
体所占据的时间位置,是外部离散性的: 此事态所处之时与其外别的相分
76语言研究集刊( 第十三辑)
别。体则刻画事态自身的进程、步骤,是内部离散性的。系词表事物的一般
成立,这总是表现为一种特定的身份面貌,在时特征上就表现为一个时间阶
段、相位,与其他阶段相分别,其内部则未离散化。例如,“他是警察 /是小
偷”构成两个分立的时位,就“他是警察”这个成立阶段自身看,“他”就从整
体上与“警察”直接等同,并无内部的操作步骤。时间名词与时间副词表时,
动态助词表体。因此,系词前可用“在这个场合、以前、已经、仍”等修饰,指
事态的整体时位。“是”类系词一般不与“在、着、过”组合,因为它们指事态
的内部进程,与系词整体性的语义特征相矛盾。“是”后偶可加“了”,如“他
也是了美国人了”,“了”表完成,这是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整体转换,
因此与“是”兼容。状语方面,系词不能用“竭力、仔细地、怎样”等方式副词
修饰,因为它们指动作自身的进行样式,是内部性、动态性的,与系词的语义
特征不相容。系词句也不能构成祈使句,后者不但要求动词的动态性,还要
求主体控制性,系词无此特征。
动作动词“为”虚化为系词的语义根据就在于: 去除实义动词的动态
性,相应也从内部视角转换为外部视角,这就与说话人相衔接,因而获得主
观确认的语义特征,具体请看下文详述。
2. 2 系词所述名词的论元角色及系词句的一般构式
学者多认为系词无自身语义内涵,因而也就不大谈其论元角色的问题,
前述 Halliday 把相关成分称为“等同项、被等同项”,是一种尝试,却也只是
同语反复,并未指出问题的实质。系词的论元角色确实与普通实义动词有
所不同。实义动词指事物在多维度上的复杂展开、关联方式,事物在其中所
起具体作用不同,就表现为不同的论元角色。与普通动词不同,系词只表事
物之为其自身的一般成立机制,并未具体分化特定的展开方式,因此,系词
对名词的作用层面只在于“事物”这种功能身份。一般认为难以处理系词的
论元角色,原因就是未能深入分析“事物”这个范畴的具体内涵,而视之为认
识活动的当然起点了。
具体看,系词为所述名词指派的论元角色为“个体”与“体事”,二者指
“事物”在不同层面的存在面貌,但又合而为一,这即所谓系词表等同的实际
内涵。“个体”指事物的直接成立,范畴意义是“哪个”,语法特征有三点: 个
别性、直接性、整体性。个别性指,个体表示从同类事物中分立出来的一个
单独成立的特定事物,这是事物成立的基本方式,否则,一切皆为混沌,就无
77“是”类系词再研究
所谓“事物”这个范畴。直接性指,个体范畴是人们与外部世界建立连接并
确定事物对象的基本语言手段,反映人们对事物的初始面对,这时尚未获知
其内部实质,对象只表现为一种直接存在的单纯个体。整体性指,个体范畴
是统摄事物之所有内涵的框。个体范畴的基本编码形式是代词和专名,即:
在对事物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也仍可用代词把它指出、确定下来,其次是专
名。例如,“这、他、张老三”指一个人的单纯个体,并未编码任何实质内涵,
可以是一切却具体什么也不是。正因“个体”范畴对事物并未限于特定内
涵,所以才有承载一切的功能。
“体事”指事物的内层存在,作用是进一步指出事物的功能角色,也就是
为个体做具体赋值,事物因此就成为一种具体的所是。体事的语法特征是
内涵性、殊指性,范畴意义是“什么”,编码的是人们对事物的具体认识: 认
识事物即不断地追问“这是什么”,也就是把内涵赋予个体。个体与体事是
人们认识事物的两个基本阶段: 认识总是始于个体,止于体事,即由“这”到
“何”,因此,“个体+是+体事”就成为系词句的一般构式。如:
( 1) a. 这是什么? 这是苹果。 b. * 什么是这? * 苹果
是这。
( 2) a. 他是什么人? 他是老板。 b. * 什么人是他? * 老板
是他。
a 句成立,“这、他”指事物的个体性,“什么”指事物的体事性,“这、他”与“什
么”表示同一事物,但指其在不同层面的不同存在面貌,系词表二者贯穿为
同一本体的具体机制。b 句一般不成立,因为“这、他”不表实质内涵,不能对
主语赋值。
从数量上看,个体与体事间的对当关系可图示为:
个体: A
同一事物 A 可具有不同的体事角色 a1、a2、……,它把什么样的角色执
行起来,就现实地是什么。任何一种特定体事都只表个体在某方面的特殊
化,都不能包括其全部,而众多不同体事汇聚起来仍为同一个体。因此,形
78语言研究集刊( 第十三辑)
式上,个体进入主语位置,是认识、言谈的起点,句法地位高于体事。反过
来,同一体事也可为不同个体所具有,在此意义上,体事就表现为特定个体
的类本质,并以此与外面的其他事物具有同一性。这在日常感知方面就表
现为“识别、断定”。可见,有学者对系词的作用称“类属”,其他学者却称
“殊指”,两种提法看似相反,其实并不矛盾: “类属”着眼于体事对个体的归
类作用,“殊指”则着眼于其赋值作用。
个体与体事间也有一对一的情形,这是系词等同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
在这种小句中,主宾语位置也可交换,但信息结构不同。如:
( 3) a. 他是杀害史密斯的凶手。 b. 杀害史密斯的凶手是他。
( 4) a. 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 b. 《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
小句的特殊性只在于,“杀害史密斯的凶手、《红楼梦》的作者”在内涵上只
能指单一事物,所以不能与其他事物建立同一关系。但系词在 a、b 两种小
句中的功能并无不同: 二者都是“个体+是+体事”构式,这就带来信息结
构的差异。a 是一般形式,因为代词“他”、专名“曹雪芹”的基本功能就是
指个体,表直接确认的信息,一般进入主语位置;“……凶手、……作者”的
基本功能则是指具体的体事角色,进入宾语位置,语义上为代词和专名赋
值,语用上提供新信息。而在小句 b,“……凶手、……作者”占据主语位
置,获得个体的身份,即指一种事先已知的空的事物框架,宾语“他、曹雪
芹”则临时获得体事身份,功能是对主语所表形式框架予以赋值,提供新
信息。
2. 3 “个体”与“体事”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系词句构式的进一步分析
个体与体事有绝对和相对两方面的意义。从绝对的意义看,代词和专
名天然指个体,所以一般都进入系词句的主语位置。普通名词则编码事物
的特定内涵,一般指体事。从相对的意义看,一个层次的体事相对其下层就
表现为个体,因此普通名词在系词句总是既可充当主语又可充当宾语。具
体机制为: 事物在每个层面的存在都是一种当下直接性,即个体性,而该个
体又总是对其内层体事的汇集,事物的成立也就表现为个体性与体事性的
交替循环。因此形式上,任何存在层面的事物都可用“这、他、小王”等典型
个体成分直接指出,例如,“这是苹果”句,“苹果”对“这”表现为体事,但还
可进一步问,“苹果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它是一种水果”,这时“苹果这
种东西”的功能就表现为个体,“一种水果”则为其体事。具体看,名词语在
79“是”类系词再研究
个体性与体事性上分化为如下系统:
代词和专名是指个体的典型形式,核心功能都是指别,这同时包括自身
确定和对外分开两个方面。因此,指示成分是确定事物的起点,编码纯粹的
个体性。一般所谓“代词”的命名并不准确: 其基本功能是“指”而非“代”。
代词对事物是在每次言语活动都临时指出,专名则摆脱了当下语境的限制,
可一劳永逸地指别个体。因此,从代词到专名就构成系词功能的第一种形
式。体事范畴是对事物功能内涵的具体揭示。有两个次类,“实体”次范畴
指事物之实的物质躯身方面,如“石块、砖头、桌子”; 量词用“堆、块、张”等。
“本质”次范畴指事物之虚的性能功用方面,即“身份、职位、职务”等,如
“人、爸爸、食品、乐器、坐具、服务生、作家、司机”,画线语素即对体事角色的
范畴化; 量词用“种、位”等。以“人”为例,它也可指物理躯身方面,如“小王
昨天人在哪”,指性能用法如“小王人很善良”。体事范畴都蕴含“做什么”
或“用于做什么”的深层述谓结构,如“石块用于砌墙、司机是开车的”。代词
和专名则无此语义结构。以上所述是词项形式,这是语言社团把一种体事
类型高度范畴化,词组形式则是临时确定的体事,如“村子里他是唯一去过
香港的人、戴眼镜的人”,修饰语指事物的一种偶然实质,据此就可确定一种
特殊的体事。
综上,系词的功能就在于指出事物在上层个体与内层体事间的自我等
同,这即事物之为其自身的一般成立方式。代词①所指事物的存在层次最
浅,其后专名②、实体名词③、本质名词④递相深入。这样,就可对系词句的
构式具体分化为“①是②”,“②是③”,“③是④”等,因此得到如下句式
系统:
80语言研究集刊( 第十三辑)
( 5) A1. 那是什么? B1. 那①是天坛②。
A2. 天坛是什么? B2. 天坛②是祈年殿③。
A3. 祈年殿是什么? B3. 祈年殿③是祈谷的专用建筑④。
( 6) A1. 那是谁? B1. 那①是小王②。
A2. 小王是什么人? B2. 小王②是个男人③。
A3. 男人是什么? B3. 男人③是要勇于承担的人④。
A4. 小王是做什么的? B4. 他①是医生④。 /B5. 小王②是医
生④。
主语表事物的当下个体性,功能在于设出一个认识的基点,宾语表体事
性,功能是进一步指出主语事物的具体实质。从这个角度看,系词就表
达了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深化、具体化。例( 6 ) 中 B3 宾语“要勇于承担的
人”的中心语泛义名词“人”常可省略,这样,处于句尾的“的”就演化为
语气助词。
以上所谈是系词的基本用法。另外,系词宾语还可是谓词性成分,如
“他是去接人、我是不知道”( 朱德熙 1982) ,谓语表一般陈述,主宾间不是等
同关系。这种用法可认为是由省略一个代词“这、那”之类小主语而引申形
成的,“这、那”与“是”的宾语仍为等同关系。系词还有其他一些引申用法,
但都要根据基本用法才能说明,这里不详述。陈振宇等( 2008) 基于外延性
和内涵性两个参数对各种名词形式做了详细分化,以说明“是”字句的组合
情况,其核心精神与本文有相通之处。
2. 4 系词的绝对用法
“个体+系词+体事”是系词句的一般构式,可称相对用法,此外,系词还
有一种不带宾语的用法,称为绝对用法。如:
( 7) I think,therefore I am. ( 8) Cogito,ergo sum. ( 拉丁语)
( 9) God is. (《圣经》)
以上小句都表主语事物的最一般成立,这种情况是无法分化为任何一种特
定的体事角色的,因为后者就把事物限制在一个特殊的功能内涵上,无法表
示出 事 物 的 全 部。例 如,个 体“我”可 以 是“男 人、学 生、小 偷、商 人、
官员……”等无限的体事角色,但任何一个甚至其总和都不能说出“我”的全
部,只有“我是我”才能说出“我”的一切。在其体系内,God 指最概括的事
物,根本上无法再做个体与体事的分别,所以系词后不能添加任何宾语,这
81“是”类系词再研究
里不是省略,而是绝对没有。有人认为“上帝是”实际结构是“上帝是……”,
“是”后面是什么,由个人选择,这样就给了人们宗教自由的空间,这只是常
识层面的误读,并非原句本意。
汉语系词“是”在古代也有宾语悬空的绝对用法:
( 10) 风景是,光阴易,叹新声浑在,断云难觅。( 韩元吉《满江红》)
( 11) 泪落碑存,鹤归城是,不堪回首。( 李曾伯《水龙吟》)
( 12) 山川四望是,人事一朝非。( 骆宾王《夕次旧吴》)
马贝加等( 2006) 认为句中“是”相当于存在动词“在”,一般学者用“我思故
我在”译 I think therefore I am 也是这种观点,均不准确。“是、在”都是本体
意义的谓词,表事物的最一般存在,但一般性的程度不同。“在”的一般性程
度低,它指事物的现实展开,具有明确的离散性,这就形成时间、空间两种范
畴,时空在经验意义上则表现为场景,所以“在”具有“相对……而在场”的语
义结构,如“风景在、我思故我在”都暗示“在那里、在世”这样的时空义。
“是”为一般程度最高的谓词,它对事物的分化离散性程度极弱,只指事物自
身的一般运行,因此无时空义。“风景是、城是、山川四望是”表达了诗人对
主语事物全部内涵的联想,并不限于物理时空义,只做后者解是不能体现诗
句的深意的。成语“物是人非”还保留系词的绝对用法。
把抽象的事物分化为特殊的功能角色,这是一种具体化的认知、表达方
式,构成系词的一般用法。而系词的绝对用法其构式就只是“事物+系词”,
这时,系词为主语名词只指派最一般的“事物”这种论元角色。该构式全无
宾语,因此,所谓系词只起句法联系作用及“系词”的命名,都是不准确的,但
因已普遍接受,故本文仍沿用。
“是”在现代汉语中一般不能宾语悬空,但主宾同形的用法在表达功能
上与之接近,如“小王是小王,你是你”。从连续体看,绝对用法“A 是”指事
物全部自身的一般存活,语义上一般性程度最高,时间义最弱; 普通用法“A
是 a”指事物在一种特殊体事角色中的存活,一般性程度最低,时间义则最
强; 主宾同形的“A 是 A”则介于二者之间。
三、“为”的系词性及“是”对“为”的取代
学者一般只认为“是”是系词,本节要证明动词源“为”的系词性。
82语言研究集刊( 第十三辑)
3. 1 “为”的系词化
“为”是一个古老的动词,泛指一般性的动作“做”,有泛义动词和致使动
词两种用法,二者都可系词化。泛义动词“为”指 NP1 通过对 NP2 内涵的
“做、运行”,而使 NP2 的内涵义成立。例如,“为人”指通过“为”的实际运
行,而使“人”的内涵现实存在。对此事态做去动态化解读,“为”就形成系词
功能。如:
( 13) 谁为君夫人? 余胡弗知? (《左传》)
可设想两种语境: 1. 现在要从一些女子中选一个去做君夫人,“谁为君夫
人”用于征询她们的想法。这个“为”表施事的当下动作,是普通实义动词,
其前可加助动词“能、愿”等及趋向动词“来、去”,并可用方式状语( 如“善、
难、如何”) 修饰。在这种小句中,主语与宾语被视为两种各自成立的不同事
物,就是说,主语只在当下执行的动态过程中把宾语运行在其身上,退出该
动作后仍回归所认为的本我。2. 一个官员长期出国现在回来,想了解国家
当前的人事情形,“谁为君夫人”用于咨询另一官员。这个“为”全无施事性、
动态性,就是系词,其前不能加助动词、方式状语等。在这种小句中,宾语就
被视为主语自身的一般存活方式,主语也无另外一个所谓本我,主宾是全同
关系,合二为一。
对“为”的系词性确有不易断定的情况,这与古汉语时间范畴语法化程
度不高有关,而时间性是系词区别于实义动词的关键,所以有时只能根据所
述名词自身的语义特征或语境进行判断。比较:
( 14) 孔子为鲁司寇。(《孟子》) ( 15) 韩万御戎,梁弘为右。(《左传》)
例( 14) “为”应读为系词,因为“鲁司寇”指一种稳定的职位,即主语的一般
存活方式,而例( 15) “为”应读为实义动词,因为“右”指一种当下战斗中的
临时职务。
“制作”义“为”包 含 三 个 参 与 者,事 件 结 构 为: “NP1 ( 用 NP2 ) ( 为
NP3 ) ”,NP1 指具体发出“为”之动作的施事,NP2 指被改造的材料,NP3 指行
为结束后成立起来的新事物,如“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 《左传》) 。“为”
指致使性制作行为,包括动作过程和结果状态两个次事件,如撇开其动作部
分,纯从 NP3 的当前成立看,“为”就表现为系词。可设想,如果小句对“制
作”的具体行为用另一实义动词专门编码,“为”只指该动作完成后事物的一
般成立,那么这个“为”就成为系词。实际上,这种用法在古汉语中很普遍,
83“是”类系词再研究
且出现甚早,即连动、兼语结构的后一动词及动补结构补语发生虚化:
( 16) 造舟为梁,不显其光。(《诗经》)
( 17) 又北播为九河。(《尚书》)
( 18) 视一为两。(《荀子》)
( 19)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为卿士。(《尚书》)
四句“为”都是系词用法。前两句,前一动词“造、播”指具体的制作行为,后
面的“为”无实义内涵,只指前面的动词完成后,“梁、九河”自身所处的一般
成立状态。后两句,前一动词“视、以”动作性极弱,“为”就更显著地表“两、
卿士”的一般成立,其系词的特征也就更明显。
已有学者指出,与“为”相似,英语动词 make 从实质看也可演化为系词。
致使用法如 Mary will make John a good husband( 玛丽会让约翰成为一个好丈
夫) ,泛义动词用法 Mary will make John a good wife ( 玛丽会做约翰的好妻
子) ,后句 make 即系词式功能,只是未虚化。
3. 2 “为”作为系词的典型用例
王力( 2000 /1937) 看到了“为”的系词性质,但认为它并未成为真正的系
词。王先生指出: “‘为’字可认为纯粹系词的很少,但稍带系词性者则颇常
见。所谓稍带系词性者,因为仍含若干动作性在内。”“系词性、动作性”的提
法触及系词的功能本质,但王先生未具体分析。本文认为“为”是典型系词,
且很早就完成了这个演化。下面五种用法都可表明“为”已全无动作性,成
为纯粹的系词。
1) 主语或宾语是代词或专名:
( 20) 召周子而立之,是为悼公。(《国语》)
( 21) 此为先王之所舍也。(《吕氏春秋》)
( 22) 孔子问于守庙者曰: “此为何器?”(《荀子》)
( 23) 桀溺曰: “子为谁?”(《荀子》)
如前述,系词句的典型形式即“代词+系词+名词”,类似的,王力( 1937) 也注
意到,“张先生是我的朋友”句式的“是”“可称为典型的系词”,而以上小句
即该构式。例( 20) 则是“代词+系词+专名”构式,又是系词用法中最典型
的,因为专名编码事物的全部内涵,主语对它不可能是动态临时的处于关
系。因此,这种小句连时范畴也不能加,如不能说:“他以前是小王”,而普通
名词宾语系词句就可以,可以说:“他以前是厨师”。
84语言研究集刊( 第十三辑)
2) 主语或宾语是数词,如:
( 24) 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 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
(《礼记》)
( 25) 此为一也。……此为二也。(《吕氏春秋》)
数是事物最抽象的形式,不可能具有施事性、受事性,“为”也就不可能具有
动作性。
3) 表示定义的句子:
( 26) 凡平原出水为大水。(《左传》) ( 27) 其名为鹏。(《庄子》)
定义句陈述的是一般情形,其中“为”无动作性、时间性,成为典型系词。
4) 主宾语完全同形:
( 28)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
( 29) 尔为尔,我为我。(《孟子》)
A=A 是系词等同功能的极端形式,实义动词“为”无此用法。可比较同义的
普通动词“做”,“做人要诚实”成立,这个“做”也可换为“为”,动态性强,是
系词前的用法,类似前述英语 make,但“尔为尔”的“为”就不能换为“做”,因
为这个“为”已虚化。A=A 形式多用于对比,这不难解释: 事物与其自身完
全等同指的是一种单纯的个体性,就自然暗示与外面的同类事物处于对比
关联,A=a 则是向内指出事物的体事角色,故无外部对比关系。
5) 连接形容词、动词词组。如前述,这反映了系词语法化程度的加强,
在古汉语中,“为”的这种用法是很普遍的:
( 30) 礼之用,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
( 31) 意孰为高? 意孰为下? 行孰为厚? 行孰为贱? (《晏子春秋》)
( 32)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论语》)
( 33)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
例( 30) 、( 31) 宾语是形容词,例( 32) 、( 33) 宾语是动词,其中“为”语义高度
虚化,完全远离其原初的一般性“做”义。
6) 作为复合词的词尾:
( 34) 立成器以为天下利。(《易·系辞上》)
( 35) 其视为天子也与为舆隶同。(《吕氏春秋》)
词法是句法的高级形态,“为”向词内发展表明其形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一个值得指出的现象是,一些平时并不强制使用系词的小句,用在强调
85“是”类系词再研究
( 如“唯天为大”) 、对比、否定、疑问等语境时,却多出现“为”。王力( 1937)
已关注此类现象,但把它们看作是“为”非典型系词的证据。本文认为,这些
用法反而更可证明“为”确已形成典型的系词功能。强调、对比、否定、疑问
等的共同特征是强调( 另见蒋勇 2013) 。谓语的功能是述谓,系词则可充当
谓语部分之述谓功能的核心、代表,因此,添加系词这个专门的语法形式,就
更易达到强调的效果。显然,现代汉语系词“是”及英语 be 分裂句的强调用
法也出于同样的动因。
3. 3 谓词性“是”的系词化
学者对“是”多关注其代词功能的系词化,这其实是一种外在的演化,即
语境吸收,并非代词以其自身的内涵而会自然发展为系词。该过程的语法
动因涉及两方面: 1. 为何主语后要引入一个回指成分,及具体选择何种成
分执行该功能。前者主要是因为主语复杂或与谓语有间隔,无须多谈。后
者,代词的选择是具有自身语义根据的,例如,用名词就不如代词经济。但
这里具体选哪个代词用于回指,却并不具有必然性,如“是、此、斯”以至人称
代词等都可供选择。实际上,不少学者都指出它们确实都可演化为系词。
2. 回指代词如何具体地发展为系词。显然,该环节才是系词问题的核心,但
代词在这一点上却完全是外在性的。大致情形为: “是”用为回指代词时,
小句是双主语构式,前面的名词是大主语,“是”是小主语,直接与后面的谓
语部分构成判断关系,而该判断是采取零形式,所以其后也可另加系词
“为”,如“老而不死,是为贼”。后来,因为大主语与原来的谓语部分在语义
上本是等同关系,而系词“为”又多不出现,所以代词“是”就不再视为与动词
部分构成主谓词组,而直接被解释为表等同的语法成分。
可见,方法论上,代词源“是”系词化的考察是把等同当成本来成立的前
提而进行的,因此,它只能从现象上告诉人们“是”是如何具体地由代词改变
为系词,却并不能揭示系词自身的功能实质到底如何,而后者才是问题的
关键。
实际上,“是”成为系词并非只有代词源,也有一种谓词源,后者确实基
于其语义内涵,因此也可显示系词的功能本质,而其原理又与“为”不同。代
词“是”有两种用法: ① 对事物个体的指出,指称性,可读为“这、此”。② 对
事物存在样式的一般指示,述谓性,读为“像那样、如此”一类,其中“像、如”
这样的实义要素即系词内涵。这个“是”与古汉语另一个谓词性代词“然”很
86语言研究集刊( 第十三辑)
相似,而单独回答问题的“然( 也) ”其实也是系词内涵。③ 可更直接地演化
为系词,它表示对一种情形如其自身的指认、断定,这即系词功能。与体词
性代词“是”类似,谓词性代词“是”也是回指用法,但充当谓语,并在该位置
直接系词化,形式为“A,B 是( 也) ”。如:
( 36)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论语》)
( 37) 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庄子》)
语义上,“是”回指前面的 A 段( 滔滔者、地籁、人籁) ,句法上,“是”充当 B 段
( 天下、众窍、比竹) 的谓语。小句的表达结构为: “说到 A( 么) ,B 就像那
样”,即,其等同关系并非一般表达结构的“A 是 B”,而是“B 是 A”: “天下皆
是滔滔者也”“众窍是地籁”。
“A,B 是( 也) ”本来是语篇性质的,这是一种较笨拙的表达形式: A 段
是话题,自成一个表述单位,其后可停顿或加提顿词“者”,“B 是( 也) ”是另
一个表述单位。后来则句法化,合为一个表述单位,途径为: A 非话题化,被
重新解释为“是”的前置宾语,这就形成了普通主动宾的构式。如:
( 38) 曰: “汝非豫让邪?”曰: “我是也。”(《史记》)
问句中的宾语部分“豫让”为 A 段,答句的“我”是 B 段,但“我是也”以独立
小句的形式出现,这样就很容易把 A 段解释为承前省的宾语,读为“我是( 豫
让) 也”。这种结构模式稳固化以后,本来形式反而会读为宾语前移的话题
化操作。
“A,B 是( 也) ”形式在汉语史上延续的时间相当久,但解读方式发生
改变:
( 39) 自家李山儿的便是。(《李逵负荆》)
( 40) 这 位 便 是 东 京 八 十 万 禁 军 枪 棒 教 头 林 武 师 林 冲 的 便 是。
(《水浒传》)
小句读为“A 是 B”: “自家便是李山儿的”。这样,“是”只是形式上出现在 B
项之后,实际语义关系与一般判断句无别,这就与代词源系词“是”实现
合流。
3. 4 “是”对“为”的取代
“为”很早就成为典型系词,但当时汉语系统对其并无强制要求,而后来
又有另一个系词“是”形成并逐渐取代“为”,成为系词的基本形式,所以整个
看“为”的使用不很普遍。但是,一个句法成分即便退出语言系统的主要舞
87“是”类系词再研究
台,也仍会退守到一些更深的句法环境中,补语位置即其中之一。这即现代
汉语能产度很高的“V-为”形式,其中系词“为”相当于一种形态成分,如“处理
为、转为、换为、扩大为、视为、表现为”等,动词表处置或变化的过程,“为”指事
物的当前一般成立。如“改变为资本家”,“改变”以后,就当前状态看也就一般
地“是资本家”了。这个位置的“为”不能换为“是”,表明“为”作为系词,其语
法性更强: 在语法性程度上,形态成分要高于词内组合,又高于句法组合。现
代汉语的系词“是”只出现在“当、算”等类系词之后,不能挤占“为”的普通动
词后位置: 只说“视为、转为、扩大为”,不说“视是、转是、扩大是”。可见,直到
今天,系词“是”在功能上仍没能完全取代“为”。另一方面,一些早期形成的
“V-为”构式有固化为一个词项的趋势,这时其后就可再加“是”,成为一种叠床
架屋的形式,如“以为是、认为是”,这表明“为”的系词功能确有磨灭,而“是”
的功能在增强。由此看来,将来“是”确有可能全面取代“为”。
利用补语位置,还可观察其他一些从语义实质看为系词功能,但未虚化
的动词。补语撇开了述语所表具体事态自身,而指一种一般的成立阶段,所
以是一定程度虚化的语法成分,因而成为诸多形态成分形成的重要途径。对
一些谓词而言,何者可相对出现在述语或补语位置,就可作为鉴定其虚化程度
的根据。具有类系词功能的实义动词包括“做、作、成、充、当、算、等于、叫”等,
如: “做人、成才、充胖子、当市长、算男人、他等于小王的哥哥、这叫不打自招”,
其中动词都表等同,但动态性很强,所以只是一些类系词功能的实义动词,并
未成为真正的系词。这可从它们做补语的能力上看出来。与“当、算、叫”相
比,“作、成”只能出现为补语: 只能说“当作 /成、算作 /成、叫作 /成”,不能说
“作当、成算、成叫”; 而与“为”相比,“作、成”又只能出现为述语: 只能说“作
为、成为”,不能说“为作、为成”。这表明,“作、成”的虚化程度要比“当、算、
叫”高些,但比“为”低。“为、是”之间不能构成述补词组,也都不可以其他动词
为补语而充当述语,而只做补语,这表明二者都是典型的系词。
四、结 论
系词有连接名词、形容词、动词三种用法,连接名词是最常见的功能,在这
种小句中,系词表事物自身的一般成立方式,为所述名词指派“个体、体事”的
论元角色。系词指事物在一种功能身份上的现实成立,因此有“时”但无“体”
88语言研究集刊( 第十三辑)
的语法特征。跨语言看,系词有动词、代词两种来源,汉语则二者兼备。泛义
动词“为”指事物的一般性运行,对此去动态化即系词功能。学者多关注系词
“是”的体词源,其实它也有谓词性代词用法的来源,并与系词功能的关系更直
接。直到今天,“是”虽大体取代“为”,但仍不能进入其“V-为”这样更深的句
法环境,表明“是”的形态化程度没“为”高,而“为”仍保持其句法活性。
参考文献
陈平( 2012) 话语分析与语义分析,《当代修辞学》第 1 期。
陈振宇、朱庆祥( 2008) “X 是谁 /哪( 一) 个 /什么( 人) ”与“谁 /哪( 一) 个 /什么( 人) 是谁”
格式,载《语言研究集刊》( 第五辑)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方 梅( 2013) 谈语体特征的句法表现,《当代修辞学》第 2 期。
蒋勇( 2013) 极量负极词用于问句的双向关联分析,《当代修辞学》第 5 期。
陆俭明( 2014) 句子的合格与不合格,《当代修辞学》第 7 期。
马贝加、蔡 嵘( 2006) 温州方言存在动词“是”的来源,《方言》第 3 期。
马建忠( 1898) 《马氏文通》,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
梁银峰( 2013) 上古汉语指示词“是”的语义属性,载《语言研究集刊》( 第十一辑)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王 力( 1937) 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清华学报》12 卷 1 期,又见《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北
京: 商务印书馆,2000。
张新华( 2010) “发”的系词功能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第 3 期。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北京: 商务印书馆。
房德里耶斯( 1921) 《语言》,岑麟祥、叶蜚声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2。
康 德( 1878) 《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
海德格尔( 1935) 《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
亚里士多德著( 1997) 《范畴篇 解释篇》,方书春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Geist,L. ( 2007) Predication and Equation in Copular Sentences: Russian vs. English Studies
in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84.
Halliday,M. A. K. ( 1968 ) Notes on Transitivity and Theme in English. Journal of
Linguistics 4.
Mikkelsen,L. ( 2005) Copular Clauses: Specification,Predication and Equation.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stet,R. ( 2003) Copulas.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433 上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zhangxinhua@ fudan. edu. cn)
327CONTENTS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Grammar,followed by an elaboration of what
makes Construction Grammar and construction proper. Then it shows the status
quo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at home and abroad,along with the current
unmarked approaches to it. Finally,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prospect of
Construction Grammar,that is its interface study approaches like study of
psycho-cognitive linguistics,rhetoric,pragmatics,pragma-rhetoric,pragmatran-
slatology,contrastive ( interlanguage) linguistics and so on.
Key words: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Grammar; Goldberg; status quo;
prospect
The Motivation of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V-disyllabic + A-disyllabic”
Forming Different Grammatical Relations
Li Jinrong & Gao Anhui ( 59)……………………………………………
Abstract: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V-disyllabic + A-disyllabic” has three
kinds of grammatical relations,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 of verb-complement,
verb-object and subject-predicate,which depends on whether the components
can realize the referentiality. B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e component is
associated with the grammatical attributes of the collocation components. This
reflect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and the
components. The difference of these three kinds of grammatical relations is
very big by the numbers,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subject-predicate hold a
strong majority. This reflects the overall outlook of the double syllable verbs'
referentiality,double syllable adjectives' description in Chinese parts of speech
system.
Key words: “V-disyllabic + A-disyllabic”; structural relation; nominaliza-
tion / referentialization; self-reference-transferred reference
Rethinking on the“shi”-like Copulas Zhang Xinhua ( 72)………………
Abstract: The“shi”-like copulas denote the mechanism of things coming into
existence. They mean a very general sense of“function”,and assign the role
of “individual” and “specificator” for the nouns they predicate. The
“individual”and“specificator ”may have four levels of forms,and this makes
the different constructions of the copular clauses. Historically,the way of the
328语言研究集刊( 第十三辑)
verb“wei”evolving into a copula throws light on the essence of copulas. In
the later time in Chinese,although“wei”was replaced by“shi”by and large,
“wei”keeps down its copular function in the deeper circumstance of“V-
copula”.
Key words: “Shi”; “Wei”; individual; specificator; copularization
Another Investigation on the Semantic Emergence of“youdeshi”and the
Problems Concerned Zhang Ailing ( 89)…………………………………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emantic emergence of“youdeshi”,i. e.
the semantic change of“youdeshi”experienced as a part of“S youdeshi NP”
during its fossilization to an idiom.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entence “S
youdeshi NP”experienced the following semantic change: “S have NP”( →“S
have only NP”) →“all what S have are NP”→“S has many /much NP( s) ”.
During the semantic change course,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perspective
shift, the interconversion law between restrictive operator and universal
quantifier,and the subjectivisation of the meaning of“dou”,all work . When
the meaning of“S has many /much NP( s) ”fossilized into the literal meaning
of “S youdeshi NP”,“S youdeshi NP” became a construction. Its
constructional meaning reacts upon its part so that“youdeshi”obtained the
meaning“only”. The semantic change of“suoyou”,polysemy of“jing”and
the condition on which“lauter”in German appeared are all the circumstantial
evidences for the semantic change“youdeshi”experienced.
Key words: youdeshi; enough quantity rule; perspective change; the
interconversion law between restrictive operator and universal quantifier;
pragmatic inference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Function of“bu
zhi”: A Review of Chinese Functional Sentence Patterns
Wang Xiaoman ( 103)………………………………………………………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stribution and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emantic function of the phrase“bu zhi”from the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aspects. We found that the differentiation in semantic functions of“bu zhi”
appeared as early as in the Wei-Jin period, and had formed a m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