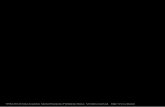臺灣的人口問題:迷思與因應
Transcript of 臺灣的人口問題:迷思與因應
楊靜利
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光復初期由於台灣人口快速成長,人口問題的焦點乃集中在人口總量多寡上,當時人口政策的主要目標
就是降低生育率。在積極追求低生育率的過程中,卻逐步埋下人口老化的因子,於今則人口結構所引發的問題逐漸浮現出來。本文從人口密度影響生活品質的迷思談起,將人口問題集中在人口結構的討論上;其次以人口動態的觀念說明台灣人口年齡結構變遷的機制,同時討論人口年齡結構變遷(人口老化)可能引發的問題;最後則討論有關於阻止生育率持續下降的相關議題,包括鼓勵生育與鼓勵結婚。
「人口密度過高有害生活品質」是我們熟悉的論述,但此一論述並未得到實證資料的支持。有兩個重要原因促使此一「迷思」的產生:一是馬爾薩斯《人口原理》之主張影響深遠,二是政府為降低家庭計畫推行之阻力而強力「教化」人口成長之害。人類 19 世紀以來的發展並不支持馬爾薩斯的「預測」,而各國的經驗也不斷顯示:欲提高生活品質,維持政治安定、促進經濟發展、加強公共建設、重視環境保護以及提高人民素質等,都比降低人口密度更為關鍵有效。拋棄「人口密度過高有害生活品質」的迷思,我們才能將人口問題的討論集中在人口結構上。台灣自 1920 年以來的人口變遷過程,使得人口結構將快速老化。由於人口老化的主要成因來自於生育率降低,也就是幼年人口減少,教育資源過剩或教育成本提高將是首當其衝的挑戰,接下來則是勞動力短缺以及勞動力老化的問題,爾後養老負擔才排山倒海而來。藉由人口政策立即改變年齡結構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須改變社會經濟制度以為因應。在教育方面,開拓學生來源(例如回流教育)與退場機制的引入將是不得不面對的結果;在勞動力方面,勞動內容(也就是勞動需求)與產業型態必須配合人口老化而有所調整;在老年照護方面,建立一個能替補家庭養老功能的社會制度,必須更加積極的進行。快速提高生育水準既不可行也不能行,但任由生育率持續下跌也不是辦法。因此生育率仍是須要想辦法提升,只是應該緩慢的提高,以時間換取空間,避免對特定年齡組人口造成嚴重的傷害。今日媒體總是充斥著「養兒不能防老」的說法,那是沒有深思熟慮、人云亦云的結果;對個人來說,「養兒防老」其實是理性經濟的抉擇,由於子女參與經濟生產取得當期的所得,老年人自子女家庭取得的資源既不受通貨膨脹的威脅,也正好趕上家庭的當期生活水準,多養幾個孩子則家庭的人力供給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只是生兒育女也十分辛苦,尤其當大量的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之後,雙薪家庭在工作與家務間的衝突成為普遍的問題,需要廣泛的社會政策介入協助,如彈性工時、產假與育嬰假、普遍的托兒措施,以及照顧者津貼等。另外,在青少年傾向於選擇墮胎來結束懷孕的現況中,建立完善而有效率的收養制度,使得各種原因被放棄的嬰兒能夠順利長大成人,是特別值得呼籲的重點。而突破傳統性別角色態度,緩和教育擴張所帶來的結婚率下降趨勢,也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過去由於台灣人口快速成長,人口問題的焦點集中在人口總量多寡上,當時人口政策
的目標就是降低人口成長的速度。如果不考慮遷移因素,人口成長源於出生人數減掉死亡
人數,生得少或死得多,人口總量就能有效控制;既然長壽是人類自古以來追求的目標,
減緩人口成長自然就得從降低生育率(生得少)著手。在積極追求低生育率的過程中,卻
也逐步埋下人口結構急速老化的因子,晚近由於學者大聲疾呼,人口結構問題才逐漸引起
關注。過去七十多年來的人口轉型過程,使得未來「降低人口總量」與「減緩人口老化速
度」兩個議題成為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衝突。本文將從人口總量(亦即人口密度,因為土
地面積固定不變)影響生活品質的迷思談起,將人口問題集中在人口結構的討論上,其次
以人口動態的觀念說明台灣人口年齡結構變遷的機制,同時討論人口年齡結構變遷(人口
老化)可能引發的問題,最後則討論有關於阻止生育率持續下降的相關議題,包括鼓勵生
育與鼓勵結婚。
談到台灣的人口問題,目前最熱門的應該是生育率過低的問題,不過那是報章雜誌的
觀點,一般民眾首先想到的人口「問題」,恐怕是「人口太多」了。因為台灣土地面積有
限,人口多密度就高,而我們相信人口密度高有害生活品質。但是觀察一下台灣內部與世
界各國的情形,其實我們大可質疑:「人口密度高真的有害生活品質嗎?」台灣 1905 年
時人口約 300萬人,目前約 2,300萬人,一百年來人口密度增加了將近七倍(2000年台灣
的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583人,世界排名第九),雖然台灣的生活品質還不夠好,但與
過去相比是漸入佳境還是每況愈下?再看看國外的例子, 2000 年荷蘭的人口密度為每平
方公里 1,010 人,排世界第 18 名,越南的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615 人,排世界第 40 名
(內政部統計處, 2002),荷蘭的生活品質比越南差嗎?再回到台灣內部, 2003 年高雄市
與台北市之人口密度分居台灣的前二名(內政部統計處, 2004a),其生活品質與台灣其
他縣市比起來如何呢?也許不是最好的,但至少不會比雲林縣(第13名)、嘉義縣(第21
名)等地遜色。為什麼我們現在的生活品質比以前好,因為技術進步、所得增加。為什麼
荷蘭的生活品質比越南好?因為政治安定、環境宜人。為什麼台北市、高雄市的生活品質
比雲林縣、嘉義縣好?因為就業機會高、生活機能強。所以人口密度與生活品質或社會發
展並無必然的關聯,就 2000 年的洲際資料來看,西歐的人口密度最高,其文明發展程度
台灣的社會問題2005●
040
與生活品質也最高;就地區來看, 2000 年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為中國澳門,孟加
拉雖然名列第八,但香港、新加坡、韓國、荷蘭、日本也都在20 名以內,而台灣則名列
第九(內政部統計處,2002),顯然人口密度高並不代表發展程度差。換句話說,就算人
口密度是影響生活品質的因素之一,其影響力排名也是明顯居後;要提高生活品質,維持
政治安定、促進經濟發展、加強公共建設、重視環境保護以及提高人民素質等,應該都比
降低人口密度更為關鍵有效。
那為什麼我們普遍有這種觀念呢?一方面是馬爾薩斯(T.R. Malthus, 1766-1834)於
1798年發表的《人口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影響深遠,二是政府
為降低家庭計畫推行之阻力而強力「教化」人口成長之害。馬爾薩斯認為人口數量將呈指
數成長,而食物的供給卻只是線性成長,由於指數成長快於線性成長,總有一天食物供給
將無法滿足人口的需求,因此人口成長會造成食物、資源短缺。在此一論證中,資本(或
土地)、技術都不是短期內能亦步亦趨改變,屆時工資率下降、糧食不足,因此過多人口
將侵蝕農業剩餘、影響經濟發展。不只是馬爾薩斯,當時的經濟學者亞當斯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與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也持相同的看法(Wrigley,
1986)。但人類 19 世紀以來的發展並不支持上述「預測」,今日我們面臨的與其說糧食不
足,倒不如說是生產過剩(分配不均是另一個問題),馬爾薩斯等人未能預期技術變遷的
速度可以超越人口成長的速度,而技術變遷根源則在於人類的積極創造與發明,甚至於來
自於人口成長的壓力。 Kuznet(1960: 328)指出:社會進步依賴的是少數天才所創造的
知識,其他人只是追隨者;如果天才占人口的比重不變,則人口成長能夠帶來更多具備創
新潛力的尖端人才。Simon(1998)也認為人口增加「長期」而言有助於經濟發展:由於
資源因人口增加而暫時性短缺,因此價格上漲,高價格促使追求利潤的企業家與關懷社會
的發明家致力於新技術與新產品的開發。開發過程中有些人失敗了,他們自行吸收失敗的
成本;有些人成功了,他們獲得利潤並造福人群。所以人口可能造成壓力,但同時也是促
使社會進步的動力。資源無限因為人的創造力無限,除非人類喪失想像力,否則社會不可
能因為人口增加而停滯不前,或者陷入貧窮。此一主張並非認為人類可以無節制的消耗地
球資源,作者想強調的是一味地憂慮人口成長,甚至阻止人口成長,其實錯置了問題的重
點,其並以南、北韓,東、西德,以及台灣與中國為例,說明社會與政治制度是影響經濟
發展更關鍵的因素。 1台灣過去的經濟成長也與勞動投入的增加(包括數量與品質)有相
當密切的關係(劉克智,1973;Mueller, 1977)。
雖然學術界對於人口成長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有不同的意見,但政府為降低家庭計畫推
行的阻礙,卻一面倒地支持馬爾薩斯觀點。二次大戰以後美國利用經濟援助主導亞洲開發
中國家(包括台灣)的發展方向,死亡率下降所導致的人口成長(主要是幼年人口增加)
使得美國的援助壓力倍增,故而要求受援國控制人口成長,台灣在此一情境下,開始強調
●
第二章 台灣的人口問題 041
人口成長對家庭負擔與經濟成長的影響,產生了以節制人口為主要目標的家庭計畫(郭文
華,1998),透過家庭訪視、媒體宣傳與學校教育等管道,不斷宣導人口成長之害,相當
成功地教化此一觀念。 2 另一方面,台灣在反攻大陸的旗幟下,重國防預算而輕基礎建
設,缺乏永續經營的規劃,往往犧牲自然環境、第一級產業來成就經濟奇蹟,待民眾環境
意識崛起,要求改善居住品質,人口密度太高乃成為政府行政成效不彰的代罪羔羊。 3一
直到今天,即使生育率已降到超低水準,有識之士體認到人口數量不是人口問題的重點,
但任一可能促使(或維持)人口數量成長的討論,還是招致許多從人口密度觀點而來的批
評與質疑。質疑者雖然不會否認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但仍主張降低人口密度,以減輕環境
負荷,使生活品質得以「進一步」提昇。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降低人口密度的確能夠減輕環境負荷,但一味地強調降低
人口數量,將遭致人口結構扭曲,尤其是年齡結構的老化,產生更難解決的社會問題,因
為台灣人口變遷的過程使得人口總量降低與人口老化速度減緩,成為必然的衝突。為什麼
一定是衝突?我們先從人口年齡結構中的兩個重要觀念談起。
人口年齡結構指的是各年齡層人數占總人數的比重,通常我們用人口金字塔描繪人口
的性別/年齡,表現人口下寬(幼年人口多)上窄(老年人口少)的靜態結構。由於各年
齡層有不同的人生任務,彼此之間不容易替代,例如我們無法在幼年先工作,青壯年退
休,老年再受教育,因此人口結構變化如果過於劇烈,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就來不及反
應。舉個例子來說,如果幼年人口每年快速的增加,學校的教室與課桌椅就不敷使用,課
桌椅可以馬上購買,興建教室卻至少需要一年半載;等硬體設備擴充完畢,還要大費周章
聘任足夠且適任的師資。當這些小朋友逐漸長大離開學校就業之後,雖然他們眾多的人數
為社會挹注大量的勞動力,上層職缺有限卻使他們必需面臨更激烈的升遷競爭。而當他們
逐漸年華老去,相偕步入老年,如果後繼的人口數量衰減,則社會又將面臨養老負擔加重
的威脅。反過來說,如果幼年人口每年快速減少,雖然學校的班級規模可以縮小,師生比
提高、教育品質跟著提升,但教育設備閒置、教育成本提高、甚或教職人員過剩,卻也是
不得不仔細思考的問題;同樣地,當這些小朋友逐漸長大離開學校就業之後,上層職位的
大量空缺雖然使他們不必面臨激烈的升遷競爭,但對雇主來說,適當的人才不易尋覓,難
以維持原有的競爭力,整個社會也可能面臨勞動力短缺,必須引進外籍勞工以為因應;除
了勞動力不足之外,勞動力結構老化也可能降低社會創造力,不利於社會進展。綜上所述
我們可以瞭解,人口結構的重點不在於每一個年齡組有多少人,而是某一年齡層人口相對
台灣的社會問題2005●
042
於其他年齡人口數量的變化。
除了相對數量的變化之外,討論年齡結構時必須念茲在茲的是:每個人都是由母親生
育而來,然後一年加一歲地長大。這個天經地義的概念,是瞭解人口變遷的重要關鍵。所
以今年剛入學的小朋友六年前就出生了,今年大學畢業的年輕人二十二年前就出生了,今
年退休的老年人六十五年前就出生了(假設 65 歲退休);再換個角度來看,今年剛入學
的小朋友,二十年後已陸陸續續進入勞動市場、完成婚事並開始生育,今年大學畢業的年
輕人,二十年後成為職場的主力,同時也差不多完成生育大事,今年退休的老年人,二十
年後如果還活著,大概也白髮蒼蒼,齒牙動搖,生活起居相當仰賴他人照顧。換句話說,
今天的年齡結構早在數十年前就開始形成,且持續影響未來數十年的年齡結構。因此當我
們警覺到未來年齡結構的走向不利於現有社會經濟制度,想藉著人口政策立即改變年齡結
構乃是不可能的,只能緩進改變社會經濟制度來因應年齡結構的變化。所以人口政策(如
鼓勵生育)只有長期或延宕人口老化的效果,沒有立竿見影的作用,也無法獨立解決年齡
結構變化所衍生的問題。
從上述觀念來看台灣地區的人口變遷,就容易瞭解問題所在了。台灣地區人口死亡率
自1920年開始因公共衛生改善、疫病受到有效控制而顯著下跌(陳紹馨,1979;Barclay,
1954),由於年齡別死亡率的特徵是 U型曲線,也就是幼年及老年兩端的死亡率比較高,
死亡率下跌的成效會明顯作用在幼年及老年兩端。自 1920 年以來,至少有五成以上的死
亡率下跌係嬰幼兒死亡率之下跌,老年死亡率之顯著減少則是相當晚近的發展(Mirzaee,
1979; Tu, 1985)。嬰幼兒死亡率既然下降,在生育率不變的情況下,每對夫妻所擁有的存
活幼年子女數增加,帶動了人口數量的成長與年齡結構的幼年化。
死亡率於1920年就開始下降,生育率則自1951年才開始下跌,兩者時間相距約一代
其實相當符合常識,在嬰幼兒死亡率高的期間,父母為了確定將來有足夠的成年子女數,
自然需要多生一點以防患未然,嬰幼兒死亡率如果下降,這種多生一點的準備就可以減
少。在死亡率剛開始下降時,正值生育期的父母並不知道嬰兒死亡率要下降了,因此照著
過去的習慣與規範生育,直到死亡率下降期間出生的嬰兒長大後,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不再
常有兄弟姐妹或鄰居小朋友死亡的經驗,這種有備無患的觀念才漸漸淡出,生育率也才隨
之下跌(王德睦,1988、1989)。
生育率雖然自1951年就開始下跌,但新生嬰兒數量卻自1976年後才開始顯示減少的
動向。「生育率」用以測量平均一位婦女生育多少小孩;「新生嬰兒人口量」則是每位婦
●
第二章 台灣的人口問題 043
女生育的小孩數之加總,生育率愈低理應新生嬰兒數量就愈低,但二者是否完全同步變動
還受到另一個因素的影響,也就是母親數量。由於嬰幼兒死亡率自 1920 年就開始下降,
日據時期乃累積越來越多的嬰幼兒人口,他們於光復後陸續晉入生育的年齡,雖然生育率
開始下跌了,但因為母親的數量相對龐大,因此每年出生的嬰兒人數仍是有增無減,一直
要到生育率有更大的跌幅,其影響力逐漸超過總體母親數量的影響時,每年出生的嬰兒人
數才會開始減少(Preston, 1986)。換句話說,出生人數多寡除了取決於每一對夫婦生育的
子女總數之外,也受可生育婦女人數(也就是母親數量)的影響,而這一代母親的數量當
然又決定於上一代母親的數量與生育率,如此代代繁衍。所以我們說:「每個人都是由母
親生育而來,然後一年加一歲地長大」是瞭解人口變遷的關鍵,在人口學上,此一關係稱
為「人口動能」(population momentum)。1951至1976年間出生的嬰兒,在人口結構上乃
形成了一個峰期人口,許多人誤以為這是台灣的「嬰兒潮」;事實上,歐美戰後嬰兒潮現
象指的是實質的生育率上升,也就是每位婦女生育的子女數增加,而台灣自日據時代迄
今,生育率除了於部分龍年稍有反彈之外,一直維持下跌的趨勢,這個峰期人口只是前述
「人口動能」之作用(陳寬政等,1986)。
將死亡率與生育率變化的時間點抓住,再掌握人口動能的作用,就能清楚刻劃出來台
灣的人口結構變遷過程。 1920 年死亡率下降,許多原來可能死亡的嬰幼兒存活下來,人
口開始增加,存活下來的小孩長大後(約 1950 年代)生育率方開始下跌;生育率雖然下
跌,但因為母親數量很多,因此人口仍繼續快速成長,爾後生育率繼續下跌,母親的數量
也慢慢減少,人口成長的速度才緩和下來;迨生育率降低至替換水準(replacement level)
以下,人口負成長成為不可避免的結果。替換水準指平均一位母親擁有一個「成年」女
兒,這裡的成年定義為母親生育該女兒時的年齡,概念上表示一位條件相同(至少活到母
親生育她之年紀)的新人「替換」一位舊人,如此下一代的人口數量可維持與上一代相
同。替換水準以下表示平均一位母親擁有不到一個成年女兒,則替換不足,人口自然產生
負成長。由於生育率低於替換水準,幼年人口將逐代縮減(但不會馬上縮減,剛開始時因
為母親數量仍高,仍會持續增加一段時間),使得幼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相
對地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則不斷提高,人口的年齡結構乃逐漸老化。
從上面的說明我們瞭解人口老化的主因是生育率下跌,而另一方面,高齡人口的死亡
率也呈下降趨勢,高齡人口的壽命及數量不斷增加,使得人口老化的程度加深。所以阻止
人口老化必須阻止生育率繼續下跌(提高死亡率雖然也是方法之一,但這是不可能的對
策),也就是允許較多的人口總量,所以我們於前面說:「人口總量的降低與人口老化速
度的減緩,乃是必然的衝突。」
為了呈現人口老化的發展趨勢,我們將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人口年齡結構繪如圖 2-
1。1920年代到1950年代期間,人口金字塔的底部逐漸擴張,1950年迄1976年峰期人口
台灣的社會問題2005●
044
開始進入,至2000年時約位於25∼50歲之間,人口結構也慢慢地往紡綞形狀(或稱彈頭
型)轉變。當這群人逐漸往高齡方向推移的時候,由於生育率沒有回升的跡象,後繼人口
縮減,人口老化將持續而來,於二十年後加速發展,迨峰期人口完全退出生命歷程,也就
是2040至2050年之間,人口結構才可能趨於穩定,屆時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可能接
近35%,相對於工作人口的比例(老年依賴比)則接近於63%。相較於目前不到9%的老
年人口比例,以及 13% 左右的老年依賴比而言,變化不可不用劇烈來形容,此一人口老
化速度與日本並駕其驅,名列世界前茅(楊靜利等,1997),對社會的衝擊將甚於其他各
國。更令人憂心的是,圖2-1所列之人口結構乃是假設未來的總生育率 4維持在1.2155的水
準不變,而台灣兩個發展的火車頭:台北市與高雄市, 2003年的總生育率則分別為 1.085
與 1.005,如果台北市與高雄市是其他縣市追隨的對象,人口老化的挑戰將比我們想像中
的大。
●
第二章 台灣的人口問題 045
圖2-1 台灣人口年齡結構之變遷(1920-2046)
資料來源: 1920 年之資料來自於《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1947), 1951 年資料來
自於《中華民國台閩地區人口統計》(內政部, 1965), 2003 年資料來自於內政統計資訊服務網的〈九十二年
底各縣市戶籍登記現住人口數按五歲齡組分〉(內政部, 2004), 2046 年資料來自《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民國 93年至140年人口推計》(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力規劃處,2004)。
老年照護問題是人口老化中最受矚目的焦點,但養老問題卻不是立即的問題;由於人
口老化的主要成因來自於生育率降低,也就是幼年人口數的減少,教育資源過剩或教育成
本提高才是首當其衝的挑戰,接下來是勞動力短缺以及勞動力老化的問題,爾後養老負擔
才排山倒海而來。
我國學制自幼稚園至研究所的修業年限共二十二年以上,其中包括幼稚園二年;國民
小學六年;國民中學三年;高級中等學校分別為高中三年、或職校三年;專校學校依入學
資格不同,分別招收國民中學畢業生入學之五年制專科,及招收高級職業學校畢業生為主
之二年制專科;大學及獨立學院,除師範院系為五年(1994 年以後入學的師範校院學
生,修業年限改為四年)、牙科為六年、及醫科為七年外,一般均為四年;1982年起增設
學士後「醫學系」、「中醫學系」,各修業五年;碩士學位研究所及博士學位研究所修業至
少二年;至於大專夜間部之修業年限,各按上述年限分別增加一年;特教學校及補習學校
之修業年限分別比照同等之正規學校。其中幼稚園為自由入學,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為分
發入學,之後各級教育均為考試入學。高中職雖然為考試入學, 2001 年國中畢業生的升
學率已達96%(教育部,2004a),高中職可視為現今的「國民」教育了。
我們將 2003 年各級學校學生人數、及未來各階段入學學生數整理如表 2-1 與表 2-2 。
表2-1第二列數值,為該教育階段總學生人數除以修業年數,得出年級平均人數,即學校
每年實際的學生容量。表 2-2 則是未來各教育階段「預期」的學生人數。表 2-2 顯示生育
率快速下跌後,新生人數大幅減少,使得既有教育品質之下(例如維持固定的班級人數與
師生比)的教育「容量」即將過大。首先反應在 2004 年的國小入學問題,這群小朋友在
台灣的社會問題2005●
046
說明:五專(3)指五專前三年,專科(2)包含二專及五專後兩年,其中二專修業年限2年。
資料來源:〈歷年度各級學校年齡別學生人數(65∼92)〉,教育部網站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STATISTICS/EDU7220001/user1/student_age.xls(2004/8/19)
表 2-1 2003 年各級學校學生人數
幼稚園 國小 國中 高中 高職 五專(3) 專科(2) 大學本科
總人數 241,009 1,913,105 957,495 393,739 360,079 68,103 220,922 837,602
年級平均 120,505 318,851 319,165 131,246 120,026 22,701 110,461 209,401
人數 273,974 319,862
各級學校
人數
1998 年出生,該年為孤鸞年,是生育率的局部低點,生育數不到 27 萬人。除了順應縮小
班級人數之外,短期內我們也無法做太多的因應措施,因為再隔兩年馬上又得面對生育率
局部高點出生的入學人口,這些小朋友出生於 2000 年,該年為生肖龍年,又是西洋的千
禧年,生育數量較前後兩年均來得大,但 2006 年之後的可入學人數則一路下跌,容量供
給過剩成為不可避免的問題。目前國小的班級人數已降低到30∼35人之間,人口趨勢使
得班級人數得以再下降。 2003 年台灣地區國小師生比(學生人數/教師人數)為 18.4 ,
美國與德國於1999年則分別為15.8與19.8(教育部,2003),雖然台灣的師生比還有下降
的空間,相較於其他國家來說並不算高,不過繼續壓低師生比不見得能有效提升教育品
質;而且就教育成本來看,師生比降低是財務負擔加重的同義詞。國中階段面臨的問題與
國小相同,只是發生的時間延後。
高中、職由於入學制度與國民教育不同,可入學人數不足對不同學校造成不同的壓
力,所以這個問題無法單靠縮小班級人數、提高教育品質來因應。因為對明星學校來說,
其入學人數不會受到影響,不需要縮小班級規模;對已有招生困難的學校而言,情況會持
續惡化,一旦其招生人數過低,將威脅到學校營運。雖然學校並非營利機構,入不敷出卻
非長久之道,顯然必須另謀因應對策。以特色與品質代替招生數是一般常見的提議,但創
新特色與提高品質經常伴隨著教育成本的提升,則學費上漲成為無可迴避的選擇。對目前
已不受青睞的非明星學校來說,提高學費之前必須先提高學校的聲望,則如何找到高品質
與高學費這個循環的起點,將成為未來的重要挑戰。
●
第二章 台灣的人口問題 047
表2-2 未來各入學年齡人數推計
年期 4歲 6歲 12歲 15歲 18歲
2004 305,172 266,772 319,562 309,292 299,051
2006 245,170 305,061 321,653 317,606 340,032
2010 227,312 229,045 266,594 323,414 318,988
2012 224,605 227,238 304,862 322,367 321,100
2013 222,754 225,692 255,946 266,447 323,069
2015 216,476 222,687 224,525 304,708 322,042
2016 212,243 220,117 228,903 255,823 266,187
2021 195,231 201,714 222,559 227,005 224,219
2031 162,963 169,902 187,867 198,305 208,342
2041 129,515 134,823 155,018 166,415 176,822
2051 110,909 114,538 125,701 131,751 140,252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民國 93 年至 140 年人口推計》,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人力規劃處,2004。
高中、職之後則進入大學或獨立學院就讀。晚近幾年高等教育快速擴張,目前高中、
職畢業生的升學率已超過七成(高中 74.85% 、高職 62.63%)(教育部統計處, 2004a),
大學(含學院)雖稱不上「國民」教育,卻也相當普遍了。不過要補充說明的是:大學聯
招的錄取率達七成或八成是以報考及申請人數為分母,錄取人數為分子的計算結果,不表
示特定世代人口(例如 18歲的國民)有七成或八成的人可以進入大學。以 2003年為例,
該年大學一年級學生占 18 歲人口的 57% ,若併入二專一年級學生則占 72% ,若再加計五
專四年級學生則占81%。81%表示目前所有各級學校的「容量」,約十年後此一容量即過
剩。如果專科持續萎縮,大學本科規模過大的問題可以稍微緩和,但表2-2的數據仍顯示
大學終究必須面臨招生困難的問題,除非能夠開拓學生來源(例如回流教育),退場機制
的引入將是不得不面對的結果。
生育數量降低導致既有教育資源過剩,進一步將引發勞動力不足與老化的問題(王德
睦、陳寬政,1991)。勞動力是指有意參與勞動者,如果因為就學、老殘、或養育子女等
因素而未進入勞動市場者,不納入勞動力的計算;勞動力與就業機會媒合,達成充分就業
的狀態是各國努力的目標,但充分就業與否常受到人口結構與產業型態的影響,前者可視
為勞動力供給面的特色,後者則與勞動力的需求面相關。當人口結構改變,產業型態若能
因勢利導,善用人口轉型帶來的契機,則能創造充分的就業機會,反之則易形成失業問題
(Bloom et al., 2003)。
以過去的經驗來說,台灣嬰兒死亡率自 1920 年下降,日據時代以來累積的大量嬰幼
兒人口,造成人口結構幼年化的現象。 1950 年後,往昔的幼年人口逐漸成為青壯年,因
為當時產業結構仍以農業為主,這批人數眾多的勞動力,在水土資源有限、單位產量集約
耕作已達到極限下,1951至1955年間只有64%的人完全就業,大多數是不完全就業的無
酬家屬工作者。隨後工業部門擴張、農產品價格貶抑,農村不完全就業的勞動力轉移至傳
統勞力密集產業,提供大量年輕而低廉的勞動力(劉克智,1975),形成工業區位上的優
勢。
1980 年代末期與 1990 年代初期,台灣景氣繁榮,幾乎處於完全就業的狀態,失業率
平均不到 2% ,其中多數為磨擦性失業(轉換或尋找工作中的暫時失業狀態)。失業率
低、勞動條件改善, 6帶動工資上漲,當時的傳統產業因為勞動成本提高面臨經營窘境,
逐漸興起西進大陸的風氣。即使如此,台灣仍因失業率低、缺工數高,政府逐步開放外籍
勞工引進以為因應。為了避免影響台灣民眾的就業機會,外籍勞工多限制從事當時國內勞
工「不願」(指年輕勞動者)或「不能」(指老年體衰者)的工作:目前外籍勞工主要從事
台灣的社會問題2005●
048
製造業(55.1%)、看護(39.2%)、以及政府重大工程(2.8%),絕大部分為體力勞動。
1992 年外勞在台人數共 15,924 人,至 2004 年 6 月,已增加到 302,044 人(勞工委員會,
2004)。
1990 年代末期,台灣開始浮現失業問題,根據行政院主計處 2004 年 7 月的人力資源
調查資料,台灣失業人數約為 47 萬人。失業似乎顯示勞動力過剩的景象,但根據調查,
2004 年 6 月份時仍缺工 15.1 萬人(行政院主計處, 2004),廠商尋找人力以 20 ∼ 39 歲之
青壯年為主,占總缺工人數的66.55%,職類以技術工、機械操作工及組裝工占30.37%最
多,教育程度要求專科程度以上者占48%(行政院主計處,2003a);失業者的特徵則為
低年齡、低教育程度、從事體力勞動,失業前從事製造業、營造業及批發與零售業等(行
政院主計處, 2003b)。這些數據隱含兩個失業族群,一為剛踏出校門,對原有工作不滿
意而頻繁轉換工作的青年;一為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而失業的中高齡勞工,他們多為
家庭生計的主力,也使得失業問題更形嚴重。但台灣目前並非勞動力過剩(缺工15.2萬人
加上外籍勞工30.2萬多人,二者合計也逼近失業的人數了),而是勞動力供給與需求未能
相互配合。擴大引進外勞雖能紓解勞動力供給不足的燃眉之急,但卻非長久之道。一旦失
業的時間持續,則失業勞工可能開始出現排外的聲音,而如果為了解決失業問題而縮小外
籍勞工的數量(假設台灣的失業者願意接受低薪從事這些工作,或是雇主願意以較高的工
資聘僱國內勞工),當景氣復甦時某些工作又乏人問津,屆時豈能立即引進外籍勞工以為
補充?外勞引進顯示內需頻仍,隨著生育率下降,未來市場可補充的年輕勞動力將日益減
少;中高齡勞工失業卻說明產業結構與勞動力供給不平衡,使失業問題益形複雜。
勞動力供給與需求未能相互配合,與景氣循環、產業結構、人力資本、就業資訊等均
有相關,隨著勞力密集產業外移、年輕勞動力逐漸減少,本該調整勞力密集產業往資本密
集產業升級,但產業升級需要時間因應,一旦勞動力減少或老化的速度過快,個人、廠
商、以及經濟制度都容易因應不及。另一個因應的面向是增加勞動人口。勞動力數量並非
完全由人口數量決定,另一個影響勞動力多寡的因素為勞動參與率;勞動力除以可參與勞
動人口(又稱民間人口,在台灣為 15 歲以上的一般民眾,不包含現役軍人與監管人口)
是為勞動參與率。台灣不論男、女性,低年齡組的勞動參與率均因就學而較多數國家低,
男性在其他年齡組則與歐美國家不相上下,女性相對於許多已開發國家,則仍有成長的空
間;不過男性晚近卻有下降的趨勢,尤其是高年齡組部分,下降的速度更快,需要進一步
探究其原因,避免繼續下跌。由於生育率降低,未來可補充的民間人口將逐漸減少,緩和
勞動力減少的速度勢必得從提高勞動參與率著手(Tsay, 2003)。
目前男性勞動參與率最高的國家為日本,女性為瑞典,但日本女性在高年齡組部分則
遠高於瑞典。若以這些最高水準為目標,台灣兩性的年齡別勞動參與率可有如圖2-2的發
展。圖 2-2 假設女性 25 ∼ 64 歲者的年齡別勞動參與率在十五年後達到瑞典 1996 年的水
●
第二章 台灣的人口問題 049
準, 65歲以上則於十五年後到達日本女性在 1996年的水準(台灣女性低年齡組的勞動參
與率雖低於瑞典,但多因就學之故,未來不太可能上升),如實線部分。男性30歲以上者
則於十五年後到達日本男性在 1996年的水準(男性的教育程度一般較女性高, 30歲以前
有相當的比例仍在學,上漲的空間有限),如虛線部分。則未來各年齡別的勞動力人數以
及平均年齡如表2-3。由於我們設定的勞動參與率逐年上漲,因此勞動力人口可持續增加
到2018年左右,到2048年以後,勞動力人口才會少於目前的人數,但由於增加的勞動力
多為高齡勞動力,因此勞動力的平均年齡持續上漲,將由目前的 38歲上升至 2051年時為
48.8歲,顯然未來的勞動內容(也就是勞動需求)必須配合勞動力的老化而有所調整。
人口老化就是老年人口相對於年輕人口的比重增加,我們知道老年人口的生產力較低
或者完全沒有生產力,當其比重上升時,表示養老的負擔加重。台灣目前仍由家庭承擔大
部分的養老工作,人口結構的變化卻會削弱傳統家庭養老功能。
目前有八成以上的家庭為核心家庭(包括獨居、僅與配偶同居、夫婦及未婚子女同
居、以及單親與未婚子女同居等)(行政院主計處, 2000),表面上看來似乎顯示小家庭
興起;不過若從老年人的角度來看,大部分的老人仍與子女同住。這當中的矛盾其實不難
瞭解:台灣自 1920 年以來的人口轉型過程,使得目前的老年人擁有相當數量的子女,如
果只有一個子女與其同居,其他子女各組核心家庭,自然就形成了這樣的現象。所以當討
論台灣的家戶型態核心化趨勢時(謝高橋,1980;徐良熙、林忠正,1984),許多學者一
台灣的社會問題2005●
050
圖 2-2 台灣勞動參與率之變遷期望(2003_2018)
勞動參與率%
年齡
資料來源: 2003 年資料來自於〈台灣地區歷年年齡組別勞動力參與率總計〉(行政院主
計處, 2004),其中年齡別勞動參與率使用2003 年的月平均值。 2018 年資料則參考日本
與瑞典之年齡別勞動參與率(US Census Bureau 2004)設定。
再強調必須注意人口結構變遷的影響,適當控制子女數量的變項後,才能瞭解家戶結構的
真正變化(Freedman et al., 1982; Thornton and Lin, 1994;陳寬政、賴澤涵,1980;王德
睦、陳寬政,1988)。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果平均一對老年夫妻擁有三個成年兒子(或女
兒,若從母居),且假設每個老人擇一兒子同住,則另外兩個兒子將自主小家庭,整體而
言將有三分之一的折衷家庭與三分之二的小家庭;而如果只有兩個兒子(或女兒),同樣
擇其一同居,則小家庭與折衷家庭將各占二分之一,當兒子的數量降為一時,假設老年父
母仍然選擇與兒子同住,則所有家庭將均為折衷家庭,而如果兒子的數量低於一時,有些
人在老年時候將沒有兒子同居,核心家庭乃再度出現。
當然,事實上並非所有老年人都會選擇與子女同居,但上述的例子明確指出子女數量
多寡對居住安排的可能影響。目前生育率已降到替換水準以下,迨低於替換水準生育條件
下出生的人口大量步入婚育年齡時,將有許多老人沒有子女可以選擇同居而被迫同居。假
設未來有子女的老人中,有六成與兒子同住,四分之一與女兒同住,家戶推計(楊靜利、
曾毅,2000)指出未來的獨居家戶將大部分為老年人。圖2-3顯示1990年時獨居家戶裡有
27%為老人,其中男性多於女性,主要是因為退伍軍人之故,隨著退伍軍人的凋零,老年
獨居占獨居家戶的比率將逐漸下降。 2010 年左右退伍軍人的因素消失殆盡,女性因壽命
較長,人數乃逐漸超越男性,同時無子女可供同居的因素逐漸凸顯出來(2010 年後,其
生育率低於替換水準的年輪人口逐漸邁入老年),獨居老人的比率大幅上漲,2040年獨居
家戶超過一半都是老人家戶。我們將這些家戶相對於所有的家戶來看,也就是圖2-3圓形
點狀圖部分,2050年時老人獨居家戶將占所有家戶的17%左右。圖2-3方形點狀圖部分則
是再加上僅與配偶同住的部分,2050年時約為27%。
家庭養老受到衝擊並不表示家庭不願意養老,或者說孝道中落;一旦老年經濟發生困
難,尋求子女的協助、或者反過來說由子女提供協助,仍是台灣大部分家庭的寫照
●
第二章 台灣的人口問題 051
表2-3 未來勞動力
年期 15-24歲 25-34歲 35-44歲 45-54歲 55-64歲 65歲以上 合計 平均年齡
2004 1,249,154 3,111,790 3,060,207 2,341,899 772,073 84,120 10,619,243 38.65
2006 1,151,844 3,193,455 3,106,585 2,565,231 983,967 155,167 11,156,249 39.56
2011 1,060,734 3,200,502 3,186,201 3,038,282 1,673,666 333,912 12,493,297 41.72
2016 1,040,903 2,919,972 3,486,400 3,335,995 2,335,385 658,544 13,777,199 43.68
2021 910,740 2,803,066 3,482,101 3,370,475 2,649,736 998,753 14,214,871 45.05
2031 721,064 2,259,838 2,959,484 3,431,743 2,575,023 1,324,702 13,271,854 46.87
2041 612,781 1,861,312 2,378,591 2,921,889 2,598,808 1,401,786 11,775,167 48.13
2051 500,874 1,577,593 1,964,043 2,345,383 2,245,465 1,435,864 10,069,222 48.84
(Chen, 1999)。而前述家戶推計設定有子女的老人中,仍有六成與兒子同住,四分之一與
女兒同住。家庭養老受到衝擊的主要原因是許多老人沒有足夠的子女或者根本就沒有子女
可供同居。許多人認為儲蓄與生產力提高可以解決人口老化的威脅,但儲蓄要行有餘力,
並確保投資利潤不被通貨膨脹侵蝕,最近幾年存款利率大幅下跌,清楚顯示儲蓄的風險所
在;而生產力提高的同時,老年的生活水準也會水漲船高,我們很難想像隨著時代的進
步,老年人與同一時代的年輕人的生活水準差距必須愈來愈大,則生產力的提高並不能解
決人口老化的威脅。 7就未來家庭結構的變遷趨勢來看,我們需要有一個能替補家庭養老
功能的社會制度,代間移轉的社會安全制度(主要包括健康照護與老年年金)是必須考慮
的方式之一。
代間移轉的社會安全制度與家庭內父母與子女之間的相互照顧是同樣的機制,只是前
者多加了同代成員之間的風險分攤,使得父母較早死亡或所得能力較高者,能夠協助父母
存活較久或所得能力較差者。但人口結構變遷使得家庭養老機制受到威脅,同樣也會使得
社會安全制度面臨財務危機:老年年金涉及代間移轉的公平性與資金運用管理的問題;健
康保險則因承保對象高齡化,老年人口生理退化導致的慢性病與老年殘障,可能演變為財
務運作上的潛在威脅(陳寬政、楊靜利,1996)。因此在維持一定給付水準的條件下,工
作人口的負擔必須逐年加重。但這不表示工作人口未來就會抗拒社會安全制度而導致兩代
之間的衝突;兩代人口並不是毫不相干的兩組人口,大部分的工作人口有父母在領取社會
台灣的社會問題2005●
052
圖 2-3 台灣地區獨居以及僅與配偶同居的老人家戶
百分比數
年期
說明:獨居(65+,女)/獨居,指獨居家戶中,戶長為 65 歲以上女性老人之比
率;獨居(65+,男)/獨居,指獨居家戶中,戶長為 65 歲以上男性老人之比率;
獨居(65+)/總家戶數,指老年獨居家戶占總家戶數之比率;獨居及僅與配偶同
住(65+)/總家戶數,指老年獨居及僅與配偶同居的家戶占總家戶之比率。
安全給付,大部分領取社會安全給付者有子女在繳交保費,兩代合作共體時艱應該是較兩
代衝突更能說明社會安全制度的遠景,就如同個別家庭會在行有餘力,或雖然捉襟見肘但
預見後代子孫的困難,而企圖預先代為解決一樣,社會安全制度自然也可以相同的作法,
讓負擔較輕的年輪人口在工作期間除了負擔當時的養老費用外,也為後代先行儲蓄未來的
養老費用。因為沒有了社會安全制度,撫養老年父母的責任將回歸家庭,財務的壓力仍然
存在,而欠缺大規模的風險分攤將使得負擔加重。
除非我們立即在人口結構圖的底部補充大量的幼年人口,否則快速的人口老化已是不
可避免的趨勢。立即補充大量的幼年人口必須大幅提高生育率,使得人口數量再繼續成
長,而台灣目前的總生育率已經低於替換水準,也就是一對夫婦所擁有的子女數不足以替
換他們自己的死亡,在這樣的低生育習慣下,想立即要求再多生幾個,恐怕不是一件簡單
的事情;而即使能夠做到,則目前已出生的幼年人口未來就相當可憐,因為當他們長大成
人之後,他們上面有峰期人口壓頂,下面有龐大的幼年人口要負擔,整個人口結構可能變
成沙漏形狀(或稱葫蘆型),恐怕是更嚴重的問題。快速提高生育水準既不可行也不能
行,但任由生育率持續下跌也不是辦法,因為人口總量雖然得以減少,減少的部分卻集中
在幼年人口上。因此生育率仍是須要想辦法提升,只是應該緩慢的提高,以時間換取空
間,避免對特定年齡組人口造成嚴重的傷害。
許多研究顯示婦女勞動參與對生育行為的負向影響(Anker, 1978; Collver, 1968;
Galloway et al., 1994; Gertler and Molyneaux, 1994; Stycos and Weller, 1967; Ware, 1976;于
若蓉、朱敬一,1988;張清溪、曹惠玲,1981),而隨著生活期望的上漲、婦女工資率的
提高與職業生涯的發展,婦女進入勞動市場的需要與意願逐漸上升。為解決雙薪家庭在工
作與家務間「蠟燭兩頭燒」問題,許多國家透過社會政策來提高大眾生育意願,這些措施
大致分為三類:(1)減輕女性在工作與家務間的衝突,如彈性工時、產假與育嬰假等,
用以增加家庭擔負子女養育的功能;(2)針對育有子女的家庭提供工具性協助教育功
能,如托兒與托幼政策;(3)提供經濟支持減輕生育負擔,如生產給付、幼兒津貼與稅
式優惠。 8 台灣也有一些零散的相關政策(余多年, 1999),但相對歐洲國家仍嫌不足,
例如:親職假仍屬留職停薪,恐怕使得職業婦女裹足不前;幼兒機構收托比率低,家務與
職場工作的衝突仍然普遍;而缺乏兒童津貼相關措施使得養育成本大部分仍落在個別父母
身上。
最近的研究指出幼兒津貼對於生育率的提高似乎效果不大(張明正, 2000 ;
●
第二章 台灣的人口問題 053
Thomson and Hoem, 1998),不過一項針對17個OECD國家的研究(Winegarden and Bracy,
1995)卻指出:延長育嬰假(maternity leave program)的時間可以有效的提高生育率、降
低嬰幼兒死亡率、而且增加年輕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育嬰假的疑慮在於增加雇主的勞動成
本,以及中斷工作流失人力資本,反而可能使得婦女的就業機會減少。但換一個角度思
考,如果我們體認養兒育女乃是國家繼往開來的基礎,家庭(而非個人)是社會的基本單
位,那麼競爭不在於男性和女性之間,而在於家庭與家庭之間;也許單身者與頂客族最為
雇主所喜,但其非多數家庭的狀況,雇主仍需順勢而為。我們並不是說育嬰假毫無困難,
而是指出那是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 17 個 OECD 國家都有育嬰假的措施,其經濟實力無
庸置疑;八○年代社會安全制度遭受全面的檢討,但最後不僅未縮減育嬰假方面的給付標
準,許多國家還放寬規定,有酬育嬰假或許可以成為我們未來考慮的措施之一。
育嬰假與托兒政策的目的是減輕婦女工作與家務之間的衝突,其思考邏輯是婦女基本
上希望就業又想生育,只是就業後生育的機會成本太高,因此裹足不前。事實上,社會經
濟的變遷使得婦女的偏好發生多樣化的改變,「蠟燭兩頭燒」是許多婦女的問題,卻不是
全部婦女的問題。有些婦女仍然秉持「家庭優先」的價值觀,「賢妻良母」仍是她們最終
的生涯成就;另一方面,有些婦女不再認為「養兒育女」是女性必經的生活歷程,她們與
男性一樣追求事業的成功。Hakim(2000)將新世紀婦女的生活型態分為三類,分別為家
庭生涯取向婦女(home-centered women ,以全職家庭主婦為代表,所占人口比例愈來愈
小)、彈性生涯取向婦女(adaptive women ,有子女與工作的雙生涯婦女占最多數)以及
工作生涯取向婦女(work-centered women ,以無子女的職業婦女為代表,人數比例有增
加的趨勢)。
絕大部分的社會政策是為了解決第二類婦女的問題,而在婦女就業成為潮流之際,全
職家庭主婦的社會地位不僅愈來愈低,也甚少獲得社會政策的關照。其實就兒童的利益來
看,全職的母親仍是值得鼓勵的照顧安排,而前述的離職假與托兒補助對於全職母親來說
根本沒有任何協助,她們生育之前如果沒有就業,就沒有離職假;他們自己照顧小孩,所
以沒有托兒補助。相對於就業婦女,她們在家庭政策上處於不利的地位。有鑑於此,九○
年代歐洲開始推行「家庭照顧津貼」(homecare allowance)措施,提供自行照顧幼年子女
者(不一定是母親,父親亦可)一定金額的補助,以芬蘭為例,每生育一位子女所支付的
照顧者津貼約女性受僱者平均薪資的40%(Hakim, 2003)。 9
除了給予生育家庭某些「補助」以鼓勵生育之外,晚近也出現針對無子女者額外課稅
以「提醒」其社會責任的意見。此概念主要來自於古代「人丁稅」的「以賦代役」(鄧海
波, 1984)精神。經濟體制與社會安全運作需要源源不斷的「子女」投入勞動市場,無
子女者年老後因為別家子女的貢獻,得以同享社會運作的結果,因此需要對無子女者課稅
以養育未來的勞動人口。在具體措施上可以調整綜合所得稅之免稅額方式來實現,例如降
台灣的社會問題2005●
054
低個人免稅額但調高子女免稅額;亦可在國民年金保費的徵收辦法中,納入子女數量因
素,例如無子女者繳交較高的費率(劉一龍等,2003)。這裡的子女包括親生或收養的子
女,此一措施除了公平性的考量之外,也希望能夠配合建立廣泛、有效率並具公信力的收
養機制,促使無子女者收養子女,以挽救眾多人工流產所排除的嬰兒。 10
上述不論是「鼓勵」或「提醒」的措施,乃著眼於生育的成本,包括因為生育而新增
的成本,以及不生育的外部成本,基本上為家庭經濟學(Becker, 1981; Cochrane et al.,
1990)之思考架構:認為女性教育程度與就業率提高使得生育數量愈少,因為生育與女性
就業互為機會成本,教育程度提高則延後結婚年齡、降低避孕成本、形成小家庭偏好、並
促使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然而,婦女教育程度以及勞動參與率的提高並無法完全解釋生
育率的差異,尤其是1990年代以後的歐洲,婦女勞動參與率較高的國家其生育率也愈高 11
(De Laat and Sanz, 2004; Rindfuss and Brewster, 1996),有關性別角色平權態度(sex-role
egalitarian attitudes)的討論乃逐漸受到重視。所謂性別角色平權態度是指對性別角色沒有
刻版印象,認為男性也應該分擔家務,花比較多的時間陪伴子女,給予家庭內務與家庭外
的工作較一致的評價,夫妻共同參與家庭各方面的決策; 12而傳統態度則相反,認為男主
外女主內是基本的家庭分工方式,家務決策主要由妻子決定,其他決策(包括生育及妻子
是否外出工作)則丈夫負責。
平權態度與生育行為有一個很有趣的關係,相對於傳統的女性,平權女性的期望子女
數較低,傾向少生育(Chapman, 1989; Kaufman, 2000; Morgan and Waite, 1987),但是平權
的男性卻較傳統的男性希望較多的子女數,而且也傾向於多生育(Affleck et al., 1989;
Kaufman, 2000)。Kaufman(2000)的解釋是:生兒育女有許多喜樂,但也十分辛苦,傳
統的家務分工讓這些喜樂與辛苦均由女性來承擔,女性乃備感壓力,因此平權態度的女性
會傾向掙脫這些束縛而少生育;而男性進入養育一事時,乃是夫妻雙方共同承擔責任,因
此男性較能夠享受其中的樂趣,而傾向多生育。平權男性除了傾向多生育之外,其離婚率
較低(Gerson, 1993; Perry-Jenkins and Crouter, 1990),婚姻的滿足感較高(Lye and Biblarz,
1993),同時還可以降低離婚對生育的影響。
結婚雖然不是生育的必要條件,在台灣,卻是生育的重要條件。2003年台灣25∼29
歲女性仍處於未婚狀態的比率占 55.8% ,男性占 74.3% ; 30 ∼ 34 歲者則分別為 25.1% 與
38.9% ;到 35 ∼ 39 歲者也分別還有 13.8% 與 20.0% 的人未婚(內政部統計處, 2004b),
這麼高的未婚率無怪乎生育率節節下降,鼓勵結婚乃成為提升生育率的重點之一。前述的
●
第二章 台灣的人口問題 055
平權觀念不只需要實踐於性別角色態度上,對於婚姻配對的傳統看法也需要進一步的突破
才能達到真正的兩性平權。
社會學上對於婚姻配對的型式主要有兩個基本假設:第一種是「同質性地位通婚」,
主張人類社會最普遍也最盛行的配對方式是社會地位相近者聯姻的「內婚」方式;第二種
則是「男高女低」的配對,認為女性傾向於嫁給社會地位比自己高的男性。兩種假設均由
社會階層化的角度切入,第一個假設反映社會階層結構的制約,不同的階層有不同的價值
體系與偏好,同質性地位通婚可以穩固既有的階層順序,並保持既有的階層特質
(Goldthorpe, 1980)。第二個假設則反映性別階層化現象,傳統上,男性角色的價值高於
女性,同時掌握大部分的「社會」資源(如財產繼承、教育成就、職業、收入等),女性
必須利用「自然」資源(如年輕、貌美等),透過「上嫁」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男性
則必須「下娶」以維持自己在家庭中的權威(Lipman-Blumen, 1976)。
台灣相關的研究基本上支持「同質地位通婚」的假設。不論是就賦予地位(如族群、
與階級背景等)(蔡淑鈴, 1994)或是成就地位(如教育取得、職業身分)(蔡淑鈴,
1994;Tsay, 1996)來看,台灣地區民眾傾向和自己社會位置相近者結婚。而在教育配對 13
方面,內婚傾向雖然明顯,但必須加入「男高女低」的假設才能充分解釋教育配對模式,
且此一模式並不因為世代(光復前或光復後出生)的不同而不同(蔡淑鈴,1994),只是
夫妻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愈是晚近的世代,教育階層的外婚愈集中於一個位階差(即夫
妻教育程度只差一級)(Tsay, 1996; Tsai, 1996)。上述研究乃是使用1990年前後的調查資
料,討論的對象橫跨戰前與戰後的出生世代,他們結婚的時候男女性教育程度有明顯的差
距,「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可以運作的空間相當大。隨著女性地位的提昇,女性與男性
的教育程度差距愈來愈小,加上高等教育大幅擴張,使得「男高女低」外婚模式的空間受
到擠壓。
「男高女低」的空間受到擠壓後,婚姻行為可以產生三種反應,一是內婚的比率增
加,二是「女高男低」外婚模式成長,三是未婚率提高。最近的研究(楊靜利、陳寬政,
2004)的確顯示教育程度上的「男高女低」婚配比例有下降的趨勢,其不僅移轉到「男女
相等」上,「女高男低」比例的上升幅度更大。但若進一步將這些「女高男低」之婚配再
依女性的教育程度來區分的話,可以發現擴張主要來自於大學教育程度以下之女性,研究
所以上者則有從「女高男低」之婚配移往「不婚」的趨勢。換句話說,過去高教育程度的
女性在「單身」與「降低擇偶標準」上傾向於選擇後者,如今則不再視婚姻為人生必經的
過程。如果我們仍繼續維持傳統的婚配習慣,未來隨著高等教育的擴張,未婚率將持續上
漲,只是男性的未婚率增長主要來自於低教育程度者(他們不容易找到更低教育程度的婚
配對象),女性的增長則主要來自於高教育程度者(她們不容易找到更高教育程度的婚配
對象),如果「成家立業」仍是男性的重要任務,外籍新娘的需求將不斷地上升。
台灣的社會問題2005●
056
由於外婚的最大障礙在高中與大學之間(蔡淑鈴,1994),也許我們可以順勢而為,
將大學以上視為同一教育程度, 14只要夫妻均是大學以上,不論是名目上是男高女低或是
女高男低,仍視為門當戶對。例如在大學教育中告訴學生:研究所階段其實類似工作而非
之前的教育,也就是說,大學畢業後,有些人當工程師,有些人當業務員,有些人當祕
書,而有些人進入研究所當學徒,接受研究工作的訓練;所以,取得學位就如取得技師執
照、完成公司訓練課程、或是累績工作經驗一般,那麼或許可以「稍微」刺激結婚率的上
升。我們說「稍微」是因為「男高女低」的內容並非只有教育程度,其他如身高、年齡、
收入、職業等都包含在內,但教育程度地位指標濃厚,從其入手,或可降低一些結婚阻
礙。
除了給予研究所教育程度新內涵之外,接受並鼓勵「家庭生涯取向」之男性,也是值
得關懷的方向。在女性逐步走出家庭的過程中,社會卻未同時輔助男性走入家庭,使得家
務工作負擔大部分仍落在女性身上。此一結果與其說是因為男性拒絕參與家務工作,倒不
如說是他們未獲得足夠的訓練與肯定。目前大部分已成家立業的男性,可能鮮少耳濡目染
父親示範家務,父母亦未要求或訓練他們從事家務工作,如何期望他們自組家庭之後能夠
積極參與?偶有一些善良體貼、勤勞持家但收入微薄的「賢夫良父」,他們又是否得到社
會或妻子的尊敬與疼惜?肯定家務勞動的價值不僅要肯定女性家務勞動者的價值,也要肯
定男性家務勞動者的價值;我們需要營造對女性友善的市場勞動環境,也需要營造對男性
友善的家庭勞動環境,如此或可消解女性社會經濟條件迎頭趕上男性之後所帶來的婚姻配
對阻礙。
由於人口具有自我再生的特性,人類壽命又相當長,因此人口結構變遷的因子往往數
十年前就已埋下,未來人口老化的最終水準可能有所變化,此一趨勢卻已無法避免。因此
當我們觀察到人口結構的變化不利於既有的社會經濟制度時,企圖在人口政策上有所做為
往往為時已晚,勉力為之也只能在長期得到效果,短期之道還是必須調整社會經濟制度來
因應。而目前的長期人口政策事實上就是阻止生育率繼續下跌、甚或促使生育率反向回升
的政策。改變生育習慣除了前述排除生育障礙或者直接提供誘因等方法之外,透過人口教
育瞭解人口結構變遷對生活的影響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
目前除了大學相關科系(社會、經濟、公共衛生與地理系等)有專業的人口學課程之
外,學校提供的人口教育主要在高中地理。一般的高中地理課本均介紹了生育率、死亡
率、人口成長、人口結構(人口金字塔)、以及人口密度等概念,但卻僅止於個別概念的
●
第二章 台灣的人口問題 057
介紹,對於這些概念的關聯性既著墨不多,又經常指引至錯誤的方向。例如:多數課本會
介紹生育率減去死亡率就是人口自然增加率,再說明人口數量除以土地面積為人口密度,
然後列舉某些國家的人口密度資料,顯示台灣相對高密度的情形,一再凸顯「人口密度」
的重要性,此一指標雖有其內涵,但社會意義不大,若要強調,應著重於破除過去「台灣
人口密度過高之迷思」。
人口的重點在於分布與結構。高中地理教材中雖然利用人口金字塔說明台灣人口老化
的情形以及未來養老的威脅,卻未強調人口結構變化的動態過程,利用「總生育率」概念
指引生育率過低的事實與衝擊,以誘發思考「生兒育女」的「理性面」,來扭轉長期過度
壓抑生育率之錯誤。在個人主義盛行的社會中,能夠為國家養育未來的生產力、勞動力,
是一件值得讚揚的事情。「養兒防老」對個人來說也是理性經濟的抉擇,因為老年所需的
生活措施與醫療照應可以就子女家庭取得,由於子女參與經濟生產取得當期的所得,既不
受通貨膨脹的威脅,也正好趕上家庭的當期生活水準,多養幾個孩子則家庭的人力供給取
之不盡用之不竭。只是生兒育女也十分辛苦,尤其當大量的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之後,雙
薪家庭在工作與家務間的衝突成為普遍的問題,需要廣泛的社會政策介入協助,如彈性工
時、產假與育嬰假、普遍的托兒措施,以及照顧者津貼等。從這個角度切入,才有可能全
面性地關懷人口結構變遷的挑戰,而非片面地指引至以養老政策解決所有的問題。
另外,結婚雖然不是生育的必要條件,卻是生育的重要條件。就婚外生育而言,在青
少年傾向於選擇墮胎來結束懷孕的現況中,建立完善而有效率的收養制度,使得各種原因
被放棄的嬰兒能夠順利長大成人,是特別值得呼籲的重點。 15而突破傳統性別角色態度,
緩和教育擴張所帶來的結婚率下降趨勢,也是值得努力的方向。突破傳統性別角色態度不
僅是給予女性更多的社會參與空間,也需要給予男性更多的家庭參與空間。傳統上,女性
是受壓抑的群體,社會突破的焦點在於撤除加諸女性的各種藩籬,雖然篳路藍縷,總不斷
有新的社會支持(包括社會政策、民間組織或媒體輿論等)加入;但在女性逐步踏入男性
的舞台之際,男性並未開發新的舞台,社會對於男性的肯定仍停留在事業的功成名就上。
前述Hakim(2000)對新世紀婦女生活型態之分類,何嘗不能推廣到男性身上?我們也可
以鼓勵男性發展多樣性的生涯,包括家庭取向之生涯(home-centered men)、彈性取向之
生涯(adaptive men)以及工作取向之生涯(work-centered men),如此或可促使「女高男
低」婚配之發展,相信亦有利於育嬰假、托兒補助以及照顧者津貼等措施之推行。
� 作者感謝馮曉蘋在資料蒐集及文字彙整上的大力幫忙;陳寬政、張苙雲、林季平等諸位教授提供修改
建議;劉曉融、張立群、顏純純等同學預先試讀協助潤稿。本文疏漏難免,歡迎批評指正。
台灣的社會問題2005●
058
註解
1 有關人口成長之利弊影響,可參考李少民等(1990)。2 此一說明並非認為家庭計畫政策不當。台灣的家庭計畫相當成功,工作人員深入每一個鄉村部落,提供方
便便宜的避孕措施,有效地協助高齡婦女杜絕不需要的生育(Sun and Soong, 1979),更於 1987 、 1992 及1997 年獲得國際人口行動委員會(Population Action International)評定為全世界 95 個開發中國家的第一名。我們所欲強調的是,為了實施家庭計畫而不斷灌輸的「人口成長之害」觀念,既缺乏明確的事實根據,亦無札實的理論基礎,但卻深植人心,成為社會的普遍迷思。
3 如 1991 年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公布的國家建設六年計畫(1991 至 1996 年)就指陳人口、產業往都市集中,造成交通壅塞、廢氣污染、公共設施及環境負荷過重,影響居住品質,也拉大城鄉差距,解決之道唯有疏導過密的人口與產業,視人口密度為惡化生活品質的客觀因素。事實上,國民政府遷台以來「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策略下,政府刻意壓抑農產品價格,導致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出「向都市-工業的傾斜」
(夏曉鵑, 2000),加上缺乏適當都市計畫、土地混合使用程度高,才衍生「人口密度」影響居住品質的說法。
4 生育測量指標之一,其概念類似於一位女性終其一生生育的子女數量,由於男性無法生育且非所有嬰兒均能存活,總生育率必需略高於二,才能維持替換水準。
5 2003 年的總生育率為 1.235 ,這包含外籍配偶的生育率。隨著跨國婚姻的需求量逐漸飽和,移入的外籍配偶人數會逐年減少,總生育率也會跟著降低,因此經建會調降預測值為1.215。
6 1984年7月30日制定公布《勞動基準法》。7 舉個例子來說:假設二十年前的老年人的生活所需是腳踏車、風扇、粗茶淡飯等,再假設現在勞動人口的
生產力是二十年前的五倍,如果撫養二十年前的老人,撫養能力自然上升五倍;但社會不可能要求或期望老年人一直活在過去,今日的老年人也需要擁有汽車、冷氣與清新健康的飲食等,則撫養能力無法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同步變動。
8 相關內容可參閱Wennemo(1992)、余多年(1999)、林佳慧(2001)以及劉一龍等(2003)等人之介紹。9 此一措施與台灣 2002 年通過的「自由處分金」並不相同,前者的精神在於強調「家務有價」與夫妻「夥伴
精神」,以避免辛苦操持家務者成為經濟弱勢一方,基本上是家戶內的所得重分配;後者的精神則在於肯定「親職」的價值,是由政府透過稅收而進行的家戶間所得重分配。
10 台灣每年的墮胎人數有多少並不清楚,出現的數值範圍從 8 ∼ 50 萬都有,但多是主觀猜測。婦產科醫學會理事長李茂盛則指出:醫學會從每年服用 RU486 墮胎的人數、人工流產人數、接生人數等推估,晚近一年懷孕人次約 30 萬,生下來的只有 21 萬,因此,約有 30% 的小孩被拿掉了(民生報, 2004 年 7 月 3 日)。另外根據健保資料統計, 2002 年 20 歲以下未婚流產共 12,300 人次(民生報, 2004 年 8 月 13 日),唯屬於「治療性墮胎」之案例醫療院所才會申報健保給付,如果胚胎本身無異常即未包括在健保資料裡,而 20 歲以下未婚者之資訊也無法估計出總數。
11 2000 年的總生育率:北歐五國平均為 1.76 ;荷、比、盧、德、澳、瑞平均為 1.53 ;西班牙與義大利平均為1.16;波蘭、捷克、保加利亞三國平均為1.23(US Census Bureau , 2004)。
12 用日常生活用語來說,就是新好男人的意思,其對於「家庭任務」的履行(doing family),比「男性任務」的履行(doing gender)更熱衷。
13 教育同質性只是「同質性地位通婚」中的一種,卻是最受矚目的一種(Smiths, 2002)。雖然父母親的社會經濟條件以及個人的職業、收入等變項也是衡量社會地位的指標,但越是現代社會,教育程度的角色就愈重要:社會經濟條件佳的家庭仍需透過教育來維持一定的社會地位,高階職業的取得也經常必須先取得一定的教育程度。
14 我們是指在觀念上視為同一教育程度,而非資料登錄上。15 避免墮胎的首要方法當然是以積極的性教育來預防懷孕,此處所強調的是給予萬一懷孕者多一種生下小孩
的選擇。
參考書目
政府與媒體資料內政部統計處
1965 《中華民國台閩地區人口統計》。
●
第二章 台灣的人口問題 059
2002 千禧年全球洲際區域及國家地區人口及其密度排名分析。 http://www.moi.gov.tw/W3/stat/home.asp
(2002/12/5)
2004a 《內政統計月報》。http://www.moi.gov.tw/stat/month/list.htm (2004/8/16)
2004b 《內政統計年報》。http://www.moi.gov.tw/stat/year/list.htm (2004/8/16)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1947 《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台北: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
民生報
2004 〈未成年懷孕生下的拿掉的1:1〉。 8月13日。
2004 〈增產 報國 一個實在嫌少〉。7月 3日。
行政院主計處
2000 台閩地區住戶數。http://www.dgbas.gov.tw/census~n/six/lue5/cen8906_main.htm (2004/8/31)。
2003a 《九十二年台灣地區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結果綜合分析》。 http://www.dgbas.gov.tw/census~n/ five/92
事業人力/92年事業人力報告 pdf.pdf (2004/8/31)
2003b 《人力資源統計年報》。http://www.dgbas.gov.tw/census~n/four/htyrtab.HTM (2004/8/31)
2004 《人力資源統計月報》。http://www.dgbas.gov.tw/census~n/four/htmotab.HTM (2004/8/31)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1991 國家建設六年計畫(民國80至 85年)第三冊《促進區域均衡發展》。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力規劃處
2002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民國91至 140年人口推計》。http://www.cepd.gov.tw/people/index.htm (2002/11/19)
2004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民國 93 至 140 年人口推計》。 http://www.cepd.gov.tw/manpower/Population/
main.htm (2004/8/19)
教育部統計處
2003 《中華民國教育統計指標92年》。台北:教育部。
2004a 各級學校畢業生升學率。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statistics/edu7220001/user1/ index01.xls
(2004/8/19)
2004b 歷年校數、教師、職員、班級、學生及畢業生數。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
STATISTICS/EDU7220001/user1/seriesdata.xls (2004/8/30)
勞工委員會
2004 《勞動統計月報》。http://dbs1.cla.gov.tw/stat/catlg00.htm (2004/8/31)。
中文文獻于若蓉、朱敬一
1988 〈婦女勞動參予對生育行為之影響──兩制內生轉換模型之應用〉,《經濟論文叢刊》,第十六輯第二
期,頁225-249 。
王德睦
1988 〈台灣地區嬰幼兒死亡率對生育率之影響〉,《人口學刊》,第十一期,頁1-17 。
1989 〈台灣地區人口成長之若干可能〉,台灣轉型後期的人口現象與分析研討會論文。台北:中國人口學
會。
王德睦、陳寬政
1988 〈現代化人口轉型與家戶組成:一個社會變遷理論之驗證〉,見楊國樞與瞿海源主編,《變遷中的台灣
社會》,頁45-59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91 〈台灣地區的勞動力老化〉,見賴澤涵主編,《光復後台灣地區發展經驗》,頁 261-74 。台北﹕中央研
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余多年
1999 《各國學齡前兒童照顧支持政策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少民、陳寬政與涂肇慶
1990 〈人口成長與經濟發展〉,《台灣大學人口學刊》,第十三期,頁107-24 。
台灣的社會問題2005●
060
林佳慧
2001 《美國、德國與瑞典的親職假政策研究:從福利國家制度面探討》,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
夏曉鵑
2000 〈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以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三十九
期,頁45-92 。
徐良熙、林忠正
1984 〈家庭結構與社會變遷:中美單親家庭之比較〉,《中國社會學刊》,第八期,頁1-22 。
張明正
2000 〈新世紀的生育問題與對策〉,見內政部主編,《新世紀之婚姻、生育與家庭問題與政策研討會論文
集》,頁152-154 。
張清溪、曹慧玲
1981 〈台灣地區生育率的決定因素──與婦女勞動參與率的聯立模型分析〉,《台灣大學人口學刊》,第五
期,頁71-118 。
郭文華
1998 〈美援下的衛生政策: 1960 年代台灣家庭計畫的探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三十二期,頁 39-
82。
陳紹馨
1979 《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聯經。
陳寬政、王德睦與陳文玲
1986 〈台灣地區人口變遷的原因與結果〉,《人口學刊》,第九期,頁1-23 。
陳寬政、楊靜利
1996 〈台灣地區人口變遷與社會安全〉,見陳肇男、劉克智、孫得雄與江豐富編,《人口、就業與福利》,
頁277-307 。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陳寬政、賴澤涵
1980 〈我國家庭制度的變遷──家庭形式的歷史與人口探討〉,《中研院三民所專題選刊》,第二十六號,
頁1-24 。
楊靜利、涂肇慶與陳寬政
1997 〈台灣地區人口轉型與人口老化速度之探討〉,見孫得雄、李美玲與齊力編,《人口老化與老年照
護》,頁15-38 。台北:中華民國人口學會。
楊靜利、陳寬政
2004 《台灣教育擴張與婚姻變遷》,人口、家庭與國民健康政策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台灣人
口學會。
楊靜利、曾毅
2000 〈台灣的家戶推計〉,《臺灣社會學刊》,第二十四期,頁239-279 。
劉一龍、陳寬政與楊靜利
2003 〈 鼓 勵 生 育 與 所 得 免 稅 額 調 整 〉, 《 台 灣 社 會 福 利 學 刊 》, 第 四 期 , 頁 53-77 。 ( 2003/9/3)
http://www.sinica.edu.tw/asct/asw/journal/0403.pdf。
劉克智
1973 〈一八九五年以來台灣經濟發展與人口之全面觀察〉,《經濟論文》,第一卷第一期,頁45-74 。
蔡青龍、吳惠林、李育靜譯
1975 《臺灣人口成長與經濟發展》。台北:聯經。
蔡淑鈴
1994 〈台灣之婚姻配對模式〉,《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六卷第二期,頁335-371 。
鄧海波
1984 《中國歷代賦稅思想及其制度》。台北:正中。
謝高橋
1980 《家戶組成、結構與生育》。台北:政大民社系人口調查研究室。
●
第二章 台灣的人口問題 061
外文文獻Affleck, M., Morgan, C. S. and Hayes, M. P.
1989 “The Influence of Gender Role Attitudes on Life Expectations of College.” Youth and Society, 20: 307-319.
Anker, R.
1978 “An Analysis of Fertility Differential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0 (1):
58-69.
Barclay, G. W.
1954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in Taiw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ecker, G. S.
1981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loom, D. E., Canning, D. and Sevilla, J.
2003 The Demographic Divided: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 Santan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hapman, B. E.
1989 “Egalitarian Sex Roles and Fertility in Canada.” Pp. 121-139, in The Family in Crisis: A Population Crisis?,
edited by J. Legate, T. R. Balakrishnan and R. P. Beaujot. Ottawa: Royal Society of Canada.
Chen, Chaonan
1999 “Changes of Living Arrangement among the Elderly in Taiwan.” Proceedings of the NSC, Part 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國科會研究彙刊:人文與社會科學》,第九卷第二期,頁 364-375。
Cochrane, S. H., Khan, M. A. and Osheba, I. K. T.
1990 “Education, Income, and Desired Fertility in Egypt: A Revised Persp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 38: 331-339.
Collver, A.
1968 “Women’s Work Participation and Fertility in Metropolitan Areas.” Demography, 5 (1): 55-60 .
De Laat, J. and Sanz, A. S.
2004 Working Women, Men’s Home Time and Lowest-Low Fertility in Europe. (http://econ.pstc.brown.edu/
~asanz/thesis/genderole.pdf)
Freedman, R., Cheng, M. C. and Sun, T. H.
1982 “Household Composition, Extended Kinship and Reproduction in Taiwan, 1973-1980.” Population Studies, 36:
395-411.
Galloway, R. P., Hammel, E. A. and Lee, R. D.
1994 “Fertility Decline in Prussian, 1875-1910: a Pooled Cross-section Time Series Analysis.” Population Studies,
48: 135-158.
Gerson, K.
1993 No Man’s Land: Men’s Changing Commitments to Family and Work. New York: Basic Books.
Gertler, J. P. and Molyneaux, J. W.
1994 “How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amily Planning Program Combined to Reduce Indonesian Fertility.”
Demography, 31 (1): 33-63.
Goldthorpe, J. H.
1980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akim, C.
2000 Work-Lifestyle Choices in the 21st Century: Preference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A New Approach to Explaining Fertility Patterns: Preference Theor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9 (1): 349-374.
Kaufman, G.
2000 “Do Gender Role Attitudes Matter? Family Formation and Dissolution among Traditional and Egalitarian Men
and Wome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1 (1): 128-144.
台灣的社會問題2005●
062
Kuznets, S.
1960 “Population Change and Aggregate Output.” Pp. 324-51, in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ipman-Blumen, J.
1976 “Toward a Homosocial Theory of Sex Roles: An Explanation of the Sex Segregation of Social Institutions.” In
Women and the Workplace, edited by M. Blaxall and B. Reag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ye, D. N. and Biblarz, T. J.
1993 “The Effects of Attitudes toward Family Life and Gender Roles on Marital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4: 157-188.
Mirzaee, M.
1979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of Mortality in Taiwan, 1895-1975. Ph. D. Dissertation, Center for Popul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organ, S. P. and Waite, L. J.
1987 “Parenthood and the Attitudes of Young Adul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541-547.
Mueller, E.
1977 “The Impact of Demographic Factor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 (1/2): 1-22.
Perry-Jenkins, M. and Crouter, A. C.
1990 “Men’s Provider-role Attitudes: Implications for Household Work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1: 136-156.
Photius Coutsoukis
2000 Population Country Rank – Population Density . http://www.photius.com/wfb1999/rankings/
population_density_2.html (2004/8/18)
Preston, S. H.
1986 “The Relation between Actual and Intrinsic Growth Rate.” Population Studies, 40: 343-351.
Rindfuss, R. R. and Brewster, K. L.
1996 “Childrearing and Fertility.” Pp. 258-289, in Fert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Patterns, New Theories. A
supplement to Vol. 22,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edited by J. B. Casterline, R. D. Lee and K. A.
Foote.
Simon, J. L.
1998 The ultimate resource 2: People, Material and Environment.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miths, J.
2002 “Social Closure among the Higher Educated: Trends in Educational Homogamy in 55 Countri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2: 251-277.
Stycos, J. M. and Weller, R.
1967 “Female Working Roles and Fertility.” Demography, 4 (1): 210-217.
Sun, T. H. and Soong, Y. L.
1979 “On the Way to Zero Growth: Fertility Transition in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Pp. 117-148, in Fertility
Transition of the East Asian Populations, edited by Lee-Jay Cho and K. Kobayashi.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Thomson, E. and Hoem, J. M.
1998 “Couple Childbearing Plans and Births in Sweden.” Demography, 35 (3): 315-322.
Thornton, A. and Lin, Hui-Sheng, eds.
1994 Social Change and the Family in Taiw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sai, Shu-Ling
1996 “The Relative Important of Ethnicity and Education in Taiwan’s Changing Marriage Market.” Proceedings of
the NSC, Part 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國科會研究彙刊:人文與社會科學》,第六期,頁301-
315.
●
第二章 台灣的人口問題 063
Tsay, Ching-Lung
2003 “Below-Replacement Fertility and Prospects for Labour Force Growth in Taiw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earch, 20 (1): 67-87.
Tsay, Ruey-Ming
1996 “Who Marries Whom?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Wives’ and Husband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Class in
Taiwan.” Proceedings of the NSC, Part 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國科會研究彙刊:人文與社會
科學》,第六期,頁258-277.
Tu, E. Jow-Ching
1985 “On Long-term Mortality Trends in Taiwan, 1906-1980.”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9: 145-64.
US Census Bureau
2004 IDB (The International Data Base) Data Access-Display Mode. http://www.census.gov/ipc/www/ idbprint.html
(2004/9/4)
Ware, H.
1976 “The Fertility and work-force participation: The Experience of Melbourne wives.” Population Studies, 30: 413-
427.
Wennemo, I.
1992 “The Development to Family policy: A Comparison of Family Benefits and Tax Reductions for Families in 18
OECD Countries.” Acta Sociologica, 35: 201-217.
Winegarden, C. R. and Bracy, P. M.
1995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Maternal-Leave Programs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Fixed-
Effect Model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61 (4): 1020-1035.
Wrigley, E. A.
1986 “Elegance and Experience: Malthus at the Bar of History.” Pp. 46-64, in David Coleman and Roger Schofield
(eds.) The State of Population Theory: Forward from Malthu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Inc.
台灣的社會問題2005●
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