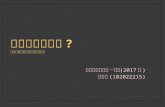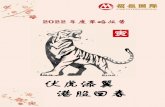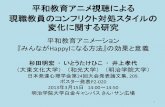宗教、社會運動與民主化 —左翼社會主義、自由派還是伊斯蘭主義?(Religion, Social Movement, and Democratization)
試論稼軒詞中之「春歸」意義及其婉約表現
Transcript of 試論稼軒詞中之「春歸」意義及其婉約表現
125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三期 2013 年 7 月 頁 125-154 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試論稼軒詞中之「春歸」意義及其婉約表現
余佳韻
提 要
稼軒詞歷來研究多著眼於其豪放風格,然除此之外,其詞作中亦不乏「穠纖
綿密」、「體情細緻」之婉約作品,特別是與「春歸」的相關敘寫。稼軒選擇了富
於女性特質之詞體作為個人心緒之傳遞,並且,其春秋兩季的創作於數量亦有差
別。是故,文體及創作時節的擇選與個人情意的表露的密切關係便值得留意。
由於「春歸」一詞包涉了歸去與歸來之雙重方向性,成就了詞中春日的主體
性與流動感。依循此種流動感而生的時空場景,其涵攝範圍亦較他詞人更為開
闊;在空間留白中成就了詞人抒情自我形成的空間。其次觸及詞中婉約表現,分
就對鏡之行為以及惜春體物的姿態摹寫兩點為論,分析其筆下女性姿態與口吻敘
寫的特色。本文試從稼軒春歸敘寫的詞篇為觀察基點,以詞以婉麗為宗的角度切
入,觀察稼軒在此一富於女性特質的題材中如何展現個人特色,其豪壯之情如何
在婉約詞體中展現。借重春歸意義的考索以及詞篇中女性的語言形象的討論,抽
藴繹出稼軒獨特的精神意態之餘,重新認識稼軒詞情的內在意 。
關鍵詞:春歸、氣、豪、婉、動態、稼軒詞
現為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三期
126
一、前言
辛棄疾(1140-1207),1生當南北宋之交,始終未能於政治上一展長才為
其終身之憂,亦影響了其文學創作。《宋史》謂其「豪爽尚氣節,識拔英俊,……
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2論者多著重其「激揚奮厲」3、「橫絕六合,掃空
萬古」4等抒發個人的豪情以及壯志未酬的不平之鳴之篇章5;縱然注意到稼
1 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山東濟南人。生於北方金人淪陷區,成年後隨耿京農民軍起義,
入南宋前事蹟未詳。入宋後不久,乾道元年(1165)任江陰簽判,旋即任滿去職。四年(1168)通判健康府,淳熙九年(1182)因監察御史王謙仲奏劾落職。遂退居上饒帶湖,開啟了第一次的退居生涯(1182-1191)。至紹熙二年(1191)起任福建提點刑獄,未久,慶元元年(1195)又落職。隔年(1196)帶湖宅地毀於祝融,遷居鉛山瓢泉(1196-1207)。晚年因病多次辭詔不就,開禧三年(1207)九月,上以稼軒為樞密都承旨,未及受命遂歿。稼軒一生最為精華的時期幾乎都處在退居的狀態,晚年終得朝廷倚重,卻已是桑榆晚景,北復失土的夙願終究齎
志以歿。眼見自身生命在此種無盡地虛擲以及交錯中流逝,其內在的不安以及憤懣可想而
知。此處稼軒生平為筆者據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臺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2007)其後所附錄之《辛稼軒先生年譜》以及鄭騫,《辛棄疾年譜》(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兩書整理之。附帶一提者為:日本學者村上哲見曾於《宋詞研究.南宋詞》一書曾就辛棄
疾南渡之初是否得到賞識一事提出不同意見。文中徵引史書中數例為證,極力辨明辛棄疾
南渡當時並非僅擔任低級文官,而是得到了皇帝的破格任用。惟其就事後為何未得持續晉
用,其間轉折原因則未見進一步論述。由於此非本文所關切之點,暫不細論。詳細論述可
參見日.村上哲見著,楊鐵嬰、金育理、邵毅平譯,《宋詞研究.南宋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391-396。本文所引之稼軒詞作皆以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臺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2007)為本,再次徵引僅列出人名、書名與頁碼,其餘不另注。
2 元.脫脫,《宋史》,卷四百一十,〈辛稼軒列傳〉(臺北: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0),頁 12165-12166。
3 沈謙語,全文如下:「稼軒詞以激揚奮厲為主,至『寶釵分,桃葉渡』一曲,昵狎溫柔,魂銷意盡。」見沈謙,《填詞雜說》,載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630。
4 語出劉克莊〈辛稼軒集序〉,載辛更儒編,《辛棄疾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01。
5 關於蘇辛異同之分,自宋以來,即有相關論述。如范開〈稼軒詞甲集序〉以稼軒詞「清而麗,婉而嫵媚」之處為東坡所無,而稼軒獨有之論;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九云:「讀
蘇辛詞,知詞中有人,詞中有品,不敢自為菲薄。然辛以畢生精力注之,比蘇尤為橫出矣。
蘇風格自高,然性情頗歉,辛卻纏綿悱惻,且辛之造語俊於蘇。」等論。今人作品相關著
作論述,其數甚夥,恕不一一列出,茲僅列舉部分如下。如:李浚植,〈蘇辛豪放詞的形成
試論稼軒詞中之「春歸」意義及其婉約表現
127
軒未嘗沒有婉約一類的創作,但此類作品始終未能成為論述主軸。6現今可見
關於稼軒詠春詞之研究,最具代表性者,當為嚴迪昌先生〈論辛稼軒的咏春
詞〉以及劉靜〈試論稼軒的咏春情結和咏春詞〉二文。前者為首先注意到稼
軒詞中的「春」之元素並進行初步析論之作;後者基於前文的基礎,更深入
地分析了稼軒詠春情緒的成因與表現。除此之外,多數研究仍不出於傳統論
述,主要圍繞蘇辛風格態樣之別或是析理稼軒作品風格與南宋偏安之時代脈
絡的關係為主。7然正如《柯亭詞論》所言,稼軒詞中既有:「沉鬱頓挫之作,
及其成就研究〉(臺北: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陳滿銘,《蘇辛詞論稿》(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頁 106-167。張璟,《蘇詞接受史研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頁 133-239。吳清,〈蘇辛詞異同比較研究述評〉,《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第 6期,頁 13-16。就稼軒豪放風格及作品之論述,學者龍榆生〈試談辛棄疾詞〉文中亦以稼軒之愛國精神為其本懷,配合其生平事蹟以及詞作論其特色。葉嘉瑩亦有〈論
辛棄疾詞〉之相關著作。其後論者大抵亦不出於根於性情的忠愛纏綿與作品表現等論。詞
評引文可參見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頁 596。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詞話叢編》,頁 3444。又論文部分,龍榆生,〈試談辛棄疾詞〉,《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392-407。葉嘉瑩,〈論辛棄疾詞〉,《唐宋詞名家論稿》(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頁 233-274。
6 關於稼軒的婉約詞的相關論述,尚可參考孫虹〈婉約-稼軒詞被忽視的藝術淵源〉一文,文中主要以文體的越界(即破體為文)作為考察基點,觀察稼軒如何承繼清真之筆法。詳
見孫虹,〈婉約——稼軒詞被忽視的藝術淵源〉,《寶雞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 4期,頁 58-62。
7 關於稼軒春日的相關研究,為數甚多。在本文中列舉的兩篇以外,尚有劉慶雲〈辛稼軒「摸
魚兒」春詞在詞史上的典範意義〉以及許采甄學位論文〈兩宋詠春詞研究〉。前者以典範形
塑的角度,著眼於稼軒在〈摸魚兒〉詞中賦予春詞特殊的政治象徵意義,以及通過後代文
人倡和所成就之「寓忠憤於春日」的抒情模式,特出稼軒詠春詞的典範意義。後者處理之
主題集中在兩宋詞人如何吟詠春日,以及「詠春」此一題材在宋代的整體發展趨勢,屬於
概論式的研究。或因兩者處理主題之故,文中較未論及春日的動態感以「春歸」此一命題
的個別情意本質等問題。除此之外,葉嘉瑩〈從花間詞的女性特質看稼軒豪放詞〉一文雖
未正面論述春歸,亦對稼軒詞中的婉約情致有十分精到而細緻的分析梳理,對本文多有啟
發。以上引述之論文依序可參見:嚴迪昌,〈論辛稼軒的咏春詞〉,收入孫崇恩、劉德仕、
李福仁主編,《辛棄疾研究論文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3),頁 136-149。劉靜,〈試論稼軒的咏春情結和咏春詞〉,《紀念辛棄疾逝世 800 周年——辛棄疾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山東 : 辛棄疾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07。劉慶雲,〈辛稼軒「摸魚兒」春詞在詞史上的典範意義〉,收入劉慶雲、陳慶元編,《稼軒新論》(福州:海風出版社,2005),頁 375-391。許采甄,《兩宋詠春詞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6)。葉嘉瑩,〈從花間詞的女性特質看稼軒豪放詞〉,《古典詩詞演講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三期
128
有纏綿悱惻之作,殆皆有為而發。其修辭亦種種不同,焉得概以『豪放』二
字目之。」8如承認創作的過程必有「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
顯,因內而符外」9的思考過程,情感接於外物而有應,使得隱於其內之情透
過語言文字彰顯於外以成其理,而成就合於文體的體式。既為一「觀文者」,
自當「披文入情」、「沿波討源」,挖掘文本自身幽而不顯之處。如立基於詞
以婉約為宗,要眇宜修之表現為當之立場,在稼軒詞被認定兼具豪婉兩種風
格,且彼此間具本質性的相通之前提下,兩者於詞篇中所表現的體用關係為
何,或即為一值得切入之觀察角度。是故,在此試由詞人外顯之語言形象回
溯至內隱之情韻內涵及詞人本體意識,辨明豪婉兩種風格之內在繫聯,以觀
察其「氣」在婉約詞之發現處。
再者,「春女思、秋士悲」既為傳統士人表達其不遇憤懣之情的主要敘
寫模式,其所呈現的書寫態樣自然為文人當下的心理狀態之流露。稼軒詞中
多以春日作為個人私密之情思寄托的主要季節便為值得注意之所在10。此種
借助女思型態以托士悲襟懷展現出的「弱德之美」11,即與原本稼軒詞與人
1998),頁 364-385。
8 見《柯亭詞論》,《詞話叢編》,頁 4913。按:稼軒詞風兼具了豪壯激憤與柔媚婉麗兩種看似迥然相異的風格面貌,自南宋以來實有定論。如南宋劉克莊〈辛稼軒集序〉即謂稼軒詞「大
聲鏜鎝,小聲鏗鍧,橫絕六合,掃空萬古。其穠纖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惟明
代以後,特別是清初陽羨詞人,言蘇辛多不出「豪放」,而較少就蘇辛兩者之內在情意本質
進行深層思索。其餘評述則多就個別詞作為論,而非整體風格評述。如沈謙「稼軒詞以激
揚奮厲為主,至『寶釵分,桃葉渡』一曲,昵狎溫柔,魂銷意盡。」或馮煦《蒿庵論詞》「〈摸
魚兒〉、〈西河〉、〈祝英臺近〉諸作,摧剛為柔,纏綿悱側,尤與粗獷一派,判若秦越。」
皆為就個別詞作評述之例,但並未就豪放與婉約兩者彼此間的體用問題為論。關於稼軒詞
在明末清初的傳播情形,可參見:陳水雲,《唐宋詞在明末清初的傳播與接受》(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頁 241-258。引文分見於辛更儒編,《辛棄疾資料彙編》,頁 101;《詞話叢編》,頁 630、3592。
9 語出《文心雕龍.體性》,見劉勰著、詹鍈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頁 1011。 10 根據嚴迪昌先生之統計,稼軒詞中與春日相關之作品約為六十闋,約佔其現存作品的十分之一,尚不包含雖為春日所作,但未明示作於春日者。見嚴迪昌,〈論辛稼軒的咏春詞〉,《辛
棄疾研究論文集》,頁 136-149。 11 「弱德之美」此一觀念為葉嘉瑩先生所提出的詞體美感特質,其定義道:「這種美感所具含
試論稼軒詞中之「春歸」意義及其婉約表現
129
之印象大相逕庭。12進而,春日作為一書寫主題,稼軒敘寫、架構以至於藉
「春歸」之旨反映詞人內在心象與具體意識則有探討之必要。
本文主要為考察「春歸」一詞在稼軒詞中的代表意義以及其展現形態,
著眼於這些深具「委婉清麗」、「穠纖綿密」等婉約詞篇並進行分析。13首先
檢討小令中春歸的描寫為始,其次論及春歸詞中體現的春日動態。在辨明稼
軒與他詞人差異之餘,亦能彰顯其內在情志與外在環境兩相衝擊之「氣」如
何被驅策,進而凝聚出稼軒與眾不同的婉轉之態。其次由詞中反映的詞人情
感所在切入,分析詞篇中所展現的詞人形象與精神意態。希冀藉此釐清稼軒
詠春詞中的春日躍動感以及其間內涵之餘,亦能重新認識稼軒「纖穠細密」
作品之特殊性及價值。
二、試問春歸誰得見?——春日的迷離光景與躍動感
的乃是在強大之外勢壓力下,所表現的不得不採取約束和收斂的屬於隱曲之姿態的一種
美。不僅《花間集》中男性作者經由女性敘寫所表現的『雙性心態』,是一種『弱德之美』,
就是豪放詞人蘇軾在『天風海雨』中所蘊含的『幽咽怨斷之音』,以及辛棄疾在『豪雄』
中所蘊含的『沈鬱』、『悲涼』之慨,究其實,也同是屬於外在環境的強勢壓力下,乃不
得不將其『難言之處』變化出之的一種『弱德之美』的表現。」由引文可知,所謂「弱德
之美」,實為一委屈隱微、甚至可以是借重女性身份而為言說表現所產生的美感特質。參見
葉嘉瑩,〈從豔詞發展之歷史看朱彝尊愛情詞之美學特質〉,《清詞叢論》(石家莊:河北教
育出版社,1998),頁 71。 12 據筆者依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所收 629 首詞作統計,以作品中明確出現春字或與春日意象相關的詞作為標準,與春季相關者共計 127首,佔 20.1%;與秋季相關者,計 76首,佔 12.0%。由統計資料可知,稼軒詞中以春季作為主要寫作背景之詞約占現存詞總數之五分之一,以數量而言,實不應忽視春日在稼軒詞中所代表的意義。另,劉靜亦於〈試論稼
軒的咏春情結和咏春詞〉一文實已注意到稼軒「厚春薄秋」的現象,惟其討論仍以春日敘
寫中關於風雨等意象的解析,就春日本身的特異性則尚未深入述及。 13 就「春歸」一詞在詩詞中的使用狀態,日本學者中原健二依《全宋詞》所為之統計資料指
出,以〈春+動詞〉型作為分類依據,在南宋詞中「春歸」與「春去」連用之詞語各佔 118首及 116 首。而本文統計稼軒作品中「春歸」之連用例即有十四首,約佔南宋詞的十分之一。可見此一詞語無論是在稼軒詞或是南宋詞皆有其特殊意義可言。其餘論述詳見〈詩語
「春帰」考〉,收入中原健二,《宋詞と言葉》(東京:汲古書院,2009),頁 207-218。合先敘明者為:本文使用「春歸詞」部分,所指均為稼軒詞中出現春歸一詞之具體作品總稱。
此種指稱或有未能全盤切合之處,然為避免行文冗雜,暫將這一類的作品統稱為「春歸詞」。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三期
130
「春歸」作為詞體意象聯想的素材之一環,或寫立春或清明之外圍景象;
或與暮春情狀相繫,以落花風雨抒展詞人之悲。詞人體感外物,受物色相招
之情內化為詞人抒情自我的一部分,形而於外,則成就一份融情於景的美感
特質。此一抒情模式並非限於詞體,而是源自於漢魏六朝以來重視物色與人
情間的相互對應的繫連,以及人之體感與外物間感會的抒情傳統。14挪借學
者對抒情詩的理解:「一首抒情詩描寫的對象是詩人自我的活動,因此即使
這對象牽涉到他人、外物,伸延到過去、想像,最後仍舊必須自然地歸返、
溶入詩人的創作活動當中。」15抒情詩的內容無論是追憶過往或是仰望未來,
最終皆須回歸到現下。詞人將自我活動的經驗透過內省的反芻篩選凝結成內
在心象,以成就文本中的抒情自我—人透過內在被養成的一套理解態度以及
與自身情性相融自省而成就的自我形象。當抒情自我透過具體的「情」之發
抒體現於外,自我的深刻才能得到他人理解認同的可能。本節擬從小令中的
春歸起筆,而後延伸至稼軒長調作品,希望透過春歸內涵以及詞中的時空敘
寫之分析,呈現稼軒詞中之「春」的特異性。
(一)小令中「春歸」的回顧
自唐末五代以來,由於詞本身應歌之特質以及小令篇幅所限,本來就不
宜抒以縱橫開闊的情感與曲折詳密的敘述模式。傳統令詞中所敘寫「春歸」
多與落花連結而展現在對春日離去的喟嘆。詞人在詞中捕捉個人所觀察到的
春歸場景作為抒情材料,最後終結於寓情於景的抒情模式。16首先分析幾首
14 關於物色以及身體類感之深入論述,相關文章可參考鄭毓瑜,〈身體時氣感與漢魏抒情詩
——漢魏文學與楚辭、月令的關係〉,《漢學研究》第 22期(2004.12),頁 1-34。及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臺北:大安出版社,1986),頁 53-107。
15 高友工,《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頁 98。 16 按:關於「春歸」一詞的問題,日本學者中原健二在其〈詩語「春帰」考〉一文中已就「春
歸」一詞的出現以及歷史脈絡有詳細考察,依其研究結果,「春歸」一詞應在南朝梁時已經
出現,但當時多採「歸來」之意,因此,其推測春日已盡那份惜春傷春之感慨,在當時大
概並非那麼深刻且普遍的事物。這樣的情況延續到盛唐以前仍是,如杜審言〈春日懷歸〉:
試論稼軒詞中之「春歸」意義及其婉約表現
131
小令中的敘寫元素:
殘春一夜狂風雨。斷送紅飛花落樹。人心花意待留春,春色無
情容易去。 高樓把酒愁獨語。借問春歸何處所。暮雲空闊
不知音,惟有綠楊芳草路。
(歐陽修〈玉樓春〉) 17
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 春
無蹤跡誰知。除非問取黃鸝。百囀無人能解,因風飛過薔薇。
(黃庭堅〈清平樂〉)18
落紅鋪徑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園憔悴杜鵑啼。無奈春歸。
柳外畫樓獨上,憑闌手撚花枝。放花無語對斜暉。此恨誰知。
(秦觀〈畫堂春〉)19
「心是傷歸望,春歸異往年。」中唐元和以後,「春歸」一詞才大量出現採用「春歸去」之
例,特別是白居易詩中出現頻率甚高。如白居易〈送春〉:「三月三十日,春歸日復暮。惆
悵問春風,明朝應不住。」又〈三月三十日題慈恩寺〉:「惆悵春歸留不得,紫藤花下漸黃
昏。」換言之,唐代「春歸」連用之例,實以詩例為多。再者,全唐五代詞中「春歸」之
連用例,現可見者尚有李煜兩首作品,〈子夜歌〉:「尋春須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縹
色玉柔擎,醅浮盞面清。 何妨頻笑粲,禁苑春歸晚。同醉與閒平,詩隨羯鼓成。」與〈臨江仙〉:「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鉤羅幕,惆悵暮煙垂。 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煙草低迷。爐香閒裊鳳凰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第一闋寫作
背景為入宋之前的宮廷生活,在此「春歸」僅為單純地指向禁苑中尚能尋得一絲春意,而
與歸去等傷春惜春之嘆無涉。次闋為李煜為宋兵所圍之際所作。由櫻桃花落意識春歸至登
樓惆悵、空嘆愁恨等敘寫結構觀之,似已初步開展了後文所論的北宋小令的結構方式。就
「春歸」一詞的考察,見中原健二,〈詩語「春帰」考〉,《宋詞と言葉》,頁 207-218。另,日本學者松浦久友與青山宏已就中國文學的「落花」在詞中代表的意義以及特殊象徵已有
初步論述。可參見松浦友久、鄭天剛譯,《中國詩歌原理‧詩與時間》(臺北:洪葉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1993年),頁 3-41。青山宏,《唐宋詞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1),頁 521-545。青山宏文章譯收入王水照、保苅佳昭編,《日本學者中國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1),頁 85-98。 17 邱少華,《歐陽修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1),頁 112。 18 黃寶華,《黃庭堅詩詞文選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53。 19 按:根據學者徐培鈞將秦觀此詞編年於元豐五年(1082),秦觀第一次落第後於返鄉途中所作。因而有一解為秦詞中之「春歸」一詞則在傷春之餘,尚寄託科舉不第後的憤懣。如依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三期
132
三闋引詞都觸及了春日歸去的場景,以落紅代表春歸一去無蹤的悵然。從歐
詞「斷送紅飛花落樹」、黃詞「因風飛過薔薇」到秦詞的「落紅鋪徑水平池」,
詞人皆因暮春風雨落紅察知春日的離去。特別是歐、秦兩家,兩者皆由落紅
起興,引動人惜春感物之情,同時點出人意與花情的落差之餘,對照無言造
物者之無情。下片同抒登樓遠眺,透過靜止的畫面延展懷憂抱恨的未盡情
緒,象徵對季節遞嬗不能自主之無奈。黃詞則先敘寫個人戀棧不捨之情於上
片,透過兩次的設問自答,刻畫出人對春歸的懸想癡態;以眼見薔薇因風散
去收束全詞,承認了春日已盡的傷情。觀諸上揭詞中重覆出現的意象,或可
初步歸納小令中與春歸相關的數個構成元素:「眼見落紅」之物色引動人心
之景象、「意識春歸」、為排遣清愁所為之「詞人獨自行止(如登樓等)」及
欲訴難言、「春恨已成(靜態描寫)」的嘆息。這幾個元素的出現順序或可交
錯,但無論是哪種配置,或如秦詞展示一連串靜態景物的手法,或似歐、黃
以詞人主觀的抒情感受為本,體現情景交融的場景。將「春歸」作為一整體
現象加以描繪,喟嘆春逝無蹤以開展詞中鋪陳,最後流入無望情緒幾乎是共
同的敘寫結構。
人感於節氣流轉而有物色之興,情亦因物之屢遷而有所起伏。春愁所
生,多是好景不常、歡會難再的深刻體感,衍生出對回憶的倚仗與耽溺。「春
歸」在此透露的是詞人對造物者的不解與怨懟,春去無蹤之後,人情也隨之
寂滅。「春歸」作為時光流逝的象徵,小令中敘寫仍多與落紅飛雨以及美人
遲暮等與時光流轉的自然規律相繫,而尚未就「春歸」之意義進行思辨並賦
予深層意義。並且,此時的春歸描寫亦近於靜態的自然現象陳述而缺乏流動
感。
其本事,秦詞中之「春歸」似已包含個人情懷的託喻,而不限於徒然的傷春意緒;然如不
依託本事,僅就文本為論,秦詞在此的「春歸」仍為傳統傷春脈絡之下的感發,文人積極
的精神意態尚未清楚顯現。引詞見徐培均箋注,《淮海居士長短句箋注》(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9),頁 82。
試論稼軒詞中之「春歸」意義及其婉約表現
133
(二)稼軒詞中「春歸」的特殊性——「動」之情態敘寫
情景作為詞人內在心境與外在景物交融的情狀之反映,欲達到詞中景語
皆情語此種「情景交融」之地步,使得「在意義徹悟的目瞬間,形式呈現為
整體,表層表現了深層」20之境界成為描寫可能,適於鋪寫的長調作為詞人
有心安排思索的構篇便是進入詞人深層世界的徑路。時間既為詞人內在憂懼
的來源,又是情狀敘述的核心,詞篇空間布局的因果關係、場景描寫以及春
日如何為人所感知的過程便是此一流動感的體現所在。試看稼軒〈漢宮春〉
一詞:
春已歸來,看美人頭上,嫋嫋春幡。無端風雨,未肯收盡餘寒。
年時燕子,料今宵、夢到西園。渾未辦、黃柑薦酒,更傳青韭
堆盤。 卻笑東風從此,便薰梅染柳,更沒些閑。閒時又來
鏡裡,轉變朱顏。清愁不斷,問何人、會解連環。生怕見、花
開花落,朝來塞雁先還。21
本詞據鄧廣銘編年於孝宗隆興元年(1163),為稼軒方才南渡寓居京口,在江
陰簽判任內之作。首句點明主題,而後羅列數塊獨立的春日圖象證實「春已
歸來」的不虛。由春幡落筆,鋪展春日再臨的生機以及駐足於萬物之痕跡,
並扣緊立春乍暖還寒的微涼氣氛,充斥著詞人內心恍惚不安、搖擺難定的心
理狀態;並以洞庭春色之典22反襯「渾未辦」之無心經營應景節物的情緒。
詞人主體的時間意識因外緣環境以及個人心緒之影響恍若靜止於詞篇。主觀
的想望及客觀時光流逝的相違,對應著生機盎然的春日以及無心外務之冷落
情懷和對不久後的春歸隱然的不安與憂慮。從上半片羅列春日應景節物至換
20 高友工,《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頁 41。 21 鄧廣銘,《辛稼軒編年箋注》,頁 5。 22 典出蘇軾〈立春日小集呈李端叔〉:「辛盤得青韭,臘酒是黃柑。」王十朋集注引趙次公曰:「黃柑以釀酒,乃洞庭春色也。」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
局,1982),卷三十七,頁 2014。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三期
134
頭處東風「沒些閒」的流動感,對比詞人當時「賦閒」的境遇,動靜間的差
異更為強烈。此外,就其構篇著眼,「春來」與「笑」是起,「無端」與「清
愁」為伏,起伏交錯,延展成一迭宕氣勢,收束於低沈掩抑的情緒。詞人心
理狀態與外物景象的平衡在下半闋的「照鏡」之後被打破,衍生出面對時間
流轉所生的諸種情緒。當春日所引發之情緒已非「悅豫之情暢」,而牽涉了
人與時間的拉扯之時,人自處自安之所的尋求便是在此中得以自立的線索。
春日的流動感在此與稼軒主觀希冀自外於流轉,成為相對的靜止的意志相
違,某程度亦與詞中動、放與靜、斂兩種互相纏繞的情結相類。
類似的敘寫尚可見於〈蝶戀花〉——「春未來時先借問,晚恨開遲,早
又飄零近。今歲花期消息定,只愁風雨無憑準」。通過現時的春來到設想不
久後的春歸,透過身處於不同時空座標軸的彼此互相凝視:在未來定點回想
現下,此刻也將成他時;然而由現下望向至他日,卻又是一片春歸的淒迷景
象,深契著「便需準備落花愁」的自我預言。此種在時間線段上相互窺探所
表露出的愁極深憂之嘆與無所適從的情狀,成為春歸敘寫的一大特色。「春
歸」的流動感實因「歸來」與「歸去」兩種層次的互相交疊,象徵自我的生
命就在此來去之間,在無止境的等待中虛耗而去。然縱使如此,稼軒卻仍願
正視自然流轉的物理常然,而非封閉自身與外物的接觸可能。此外,稼軒將
此種積極情態轉而為對周遭之物流轉移動察知的動態描寫,相較於前之小令
詞中靜態的春歸,不單僅是體現空間存在感,更彰顯了詞人抒情本體的意識
所在——一份勇於承擔的意態。23
23 《聖經的敘事藝術》一書以《聖經》為作為分析對象,闡述其中關於敘述在時空間的展現。書中提到:「在空間領域,沒有像敘述時間和情節時間這樣的平行關係。空間存在於敘事當
中但敘事並不存在於空間當中,所以敘事的內在空間不是通過外在空間(如繪畫),而是透
過外在時間來實現的。……當有人察覺到人物移動的時候,我們就間接獲取到了一種空間
存在感。」詞中稼軒為一觀察春日輾轉於萬物的觀察者摹寫其流動之狀態。春日被視為一
能動主體而加以描述的過程,便是移動痕跡的記錄。通過此種記錄,讓我們更能進入稼軒
構築出的,帶有個人經驗價值的抒情空間。西蒙.巴埃弗拉特,李鋒譯,《聖經的敘事藝術》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6),頁 204-205。
試論稼軒詞中之「春歸」意義及其婉約表現
135
辛詞中春的動態與不定又可見於〈滿江紅暮春〉與〈玉樓春〉兩首暮春
時節的作品。引文如下:
可恨東君,把春去春來無跡。便過眼、等閒輸了,三分之一。
晝永暖翻紅杏雨,風晴扶起垂楊力。更天涯、芳草最關情,烘
殘日。湘浦岸,南塘驛。恨不盡,愁如織。算年年辜負,對他
寒食。便恁歸來能幾許,風流早已非疇昔。憑畫欄、一線數飛
鴻,沈空碧。〈滿江紅暮春〉
風前欲勸春光住。春在城南芳草路。未隨流落水邊花,且作飄
零泥上絮。 鏡中已覺星星誤。人不負春春自負。夢回人遠
許多愁,只在梨花風雨處。〈玉樓春〉 24
兩闋詞的時間線段皆集中於「春日將歸—春已歸去」一段,情緒亦多與留春
不得、送春歸去相涉。25〈滿江紅〉一闋以「等閒」與「辜負」貫穿全篇。「來
去無跡」、「過眼等閒」等句體現出春日來去的倏忽無跡;「晝永暖翻紅杏雨」
與「風晴扶起垂楊力」並列,「暖翻」與「扶起」兩個動詞,再次強調詞人
眼目所觀察到的春日流動之事實與力道。紅杏吹落,暗喻時節已近初夏。結
句以「更」字推衍下面芳草天涯的惆悵情緒,呼應開頭春日過眼將逝,季節
逐漸移轉的跡象。暮春景象與殘日形構出詞人廣闊寂寞的內在圖樣,以空間
延展出的遼闊感暗指與春日相共的時日無多之外,亦有春日蹤跡難以掌握之
喻。此處之「關情」,實為對東君之恨轉化而生,藉此扣緊過片「湘浦」和
「南塘驛」帶出「恨不盡、愁如織」以下的自我敘述。次闋的〈玉樓春〉直
白述明留春意欲之切,然感知已遲,僅能在泥絮中掇拾些暮春殘留的記憶。
24 以上兩闋詞分別見於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頁 76、頁 397。 25 相關詞例尚有〈定風波〉(少年春懷似酒濃):「卷盡殘花風未定。休恨。花開元自要春風……
試問春歸誰得見?飛燕,來時相遇夕陽中。」及〈踏歌〉(攧厥):「向人道,不怕輕離別,問昨宵,因甚歌聲咽。……舊家事卻對何人說。告第一莫趁蜂和蝶,有春歸花落時節。」
其時間亦落在花將謝未謝之前以及開始凋零的當下。分見於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
頁 223、頁 225。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三期
136
過片語氣一轉,脫去悽惻情懷而轉向為自身極力辯駁——「人不負春春自
負」,指出並非人沒有賞玩春色的閒情雅致,而是春日不與人多所纏綿。陳
廷焯曾評另一闋〈滿江紅〉(家住江南)為:「亦流宕,亦沈切。」26借用其
評,「流宕」所指,為春日遊走於萬物間那份流暢恣肆,不受拘檢的風神動
貌;而「沈切」則是詞人內在對於外緣環境的反應所糾結出的一段既愛且惱
的心理。此評或可作為此處的春日流動樣態與詞人心理狀態之補充。
再者,「春歸」作為對人生的虛擲與浪費的焦慮的象徵,亦得由詞中空
間為觀察。稼軒在詞中營造出了一個迥異於向來限於個人內在私密處或是閨
閣臥房等有限空間,而將人導引向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春日形貌所蘊含的
流轉於其間、往來不定且無可捉摸的流動感便躍然紙上。「詩人借助詩歌空
間發現了一個並不把我們封閉在某種感受中的空間,從而達到更深入的地
方。無論給空間染上色彩的是哪一種感受,無論這種感受是悲傷還是沉重,
一旦它被表達出來,以詩歌的方式表達出來,悲傷就會緩解,沉重就會減輕。
既然詩歌空間被表達出來,它就獲得了擴張的價值。」27抒情空間作為個人
自我經驗價值的顯現28,文人利用詩歌創作上原本就預留的空白作為基底,
經驗透過書寫進入文本的同時,也將個人價值滲透至留白處,使得詩歌所營
造的空間成為抒情自我的展演。當詞人處於春日流轉之中,借其行動而將原
本屬於靜態描寫的春歸化為動態描寫,使人情感會透過「動」延展出深層的
抒情況味。詞的側豔特質提供了異於詩文的創作空間以表露一份幽眇難言的
26 案:原詞如下:〈滿江紅〉:「家住江南,又過了、清明寒食。花徑裡、一番風雨,一番狼藉。紅粉暗隨流水去,園林漸覺清陰密。算年年、落盡刺桐花,寒無力。庭院靜,空相憶;無
處說,閒悉極。怕流鶯乳燕,得知消息。尺素如今何處也,彩雲依舊無蹤跡。漫教人、羞
去上層樓,平蕪碧。」亦寫寒食之際的暮春景象。《稼軒詞編年箋注》,頁 6。引文出自《雲韶集》卷五:「幼安〈滿江紅〉、〈水調歌頭〉諸作俱能獨闢機杼,沈著痛快之致。亦流宕,
亦沈切。」孫克強、楊傳慶點校整理,〈《雲韶集》輯評之一〉,《中國韻文學刊》,2010 年第 3期,頁 63。
27 加斯東.巴什拉著、張逸婧譯,《空間的詩學》(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頁 220。 28 此處借用許銘全就「抒情空間」之定義,即「蘊有抒情經驗的內容與價值意涵的空間。詳細論述可參考許銘全,《唐前詩歌中「抒情空間」形成之研究——從空間書寫到抒情空間》(臺北:臺灣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10),頁 1。
試論稼軒詞中之「春歸」意義及其婉約表現
137
情致。此種抒懷詠唱的文字化入詩歌,便有抒情空間之產生。當人從封閉的
閨閣中出走至更廣闊的空間,真實面對外物之際,潛藏於內部個人主觀經驗
必須尋找得以解放的空間示現,藉此達到個人內外在的平衡狀態。當「春歸」
此一無可奈何的、自然流轉的悲傷與沉重被減緩同時,抒情空間被擴張的結
果,便是視野的擴大與情感質地的提升。在此,稼軒所營造的抒情空間吸納
了過盡飛鴻的愁緒與風雨後的殘敗背後的負面波動,將世界的廣闊性轉化為
內心存在的強度;餘下的空間留白延展出詞人抒情片刻形成的抒情範圍,彰
顯「人不負春」此一宣告,透露出詞人個人無負天地,僅時不我予的姿態。
從而,稼軒的抒情自我尋繹到了暫棲之所。在生命本質中那份亟欲維護之情
與外在現實的扞格激盪而生的憂懼透過空間得到某種釋放與緩解,即前文所
謂擴張價值。
最後試舉清真〈六醜〉詞中所描述的春日對照,尤其可見稼軒突出之處。
引詞如下:
正單衣試酒,恨客裡、光陰虛擲。願春暫留,春歸如過翼,一
去無跡。 為問花何在?夜來風雨,葬楚宮傾國。釵鈿墮處
遺香澤。亂點桃蹊,輕翻柳陌。多情最誰追惜?但蜂媒蝶使,
時叩窗隔。 東園岑寂,漸蒙籠暗碧。靜繞珍叢底,成歎息。
長條故惹行客。似牽衣待話,別情無極。殘英小、強簪巾幘。
終不似、一朵釵頭顫袅,向人欹側。漂流處、莫趁潮汐。恐斷
紅、尚有相思字,何由見得?(周邦彥〈六醜〉薔薇謝後作)29
開篇「願春暫留,春歸如過翼,一去無跡」,點出事與願違的留春之情,同
時提點自身客居異鄉的悵懷,呼應小題「薔薇謝後作」,在繁花落盡後追尋
春日消逝的蹤跡,並以設問引出後文落花情致的鋪陳以及個人的設想。儘管
只剩殘英,仍是腸枯思竭地想留住那最後一點美,綿密地扣緊春逝的惘然惆
29 周邦彥撰,孫虹校注,《清真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81。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三期
138
悵—對往日的執著與眷戀的凝聚,試圖透過重述得到示現與補償。因而,此
處春的生命力與動感於詞中幾乎消逝殆盡,取而代之的只剩凝滯與孤寂以及
詞人試圖挽留的癡態。需特別注意的是,在此的凝滯並非時光,而是往日影
像的再現。詞人刻意營造出彷彿時光已回溯而停留於往日某時間點的模糊場
景。以今昔不斷分合的影像交錯,營造出虛實難辨的恍惚情態。
對照兩家同寫「春去」或「春歸」之作品,不難發現兩者寫作脈絡與結
構之差異:周詞多為凝滯且定著的糾纏情意,情緒低掩卻不失冷靜;平穩莊
重而迭宕之姿略顯不足。相較清真執著於回憶所帶來的溫情,稼軒則相對淡
化了回憶的溫度。在詞人書寫追憶的當時,由於再經驗之故而不免帶有「復
現的衝動」30。惟此種「復現」的意欲並非當下場景的完整重現。實際上,
為避免現實成分的滲入削弱了抒情意欲,詞人也無意進行細部敘述,而僅擷
取了被時光篩落的回憶片段,透過對往日的懷想與追悼,架構出得以棲息耽
溺的世界以撫慰內在傷口。稼軒詞中的回憶僅為與現今相對的往日之存在,
「春歸」所帶來的時不我予的憂愁憤懣與時光人事必然流逝的不安,是對現
下當前的感嘆而非就往日的亟欲再返。此種生命的焦慮源自於現下的無以為
繼。縱然現實不如己意,卻仍保有最為昂揚的積極情懷,展現出個人生命抉
擇與實踐的書寫力道。鄭騫先生曾引伸王國維對蘇辛兩家的豪曠之分,而說
到:「曠者,能擺脫之謂;豪者,能擔當之謂。能擺脫故能瀟灑,能擔當故
能豪邁。」31稼軒之「動處」所展現出的昂揚情懷以及個人生命抉擇的堅守,
或正為此處「擔當」之意。
「春歸」此一主題向來以靜態的景物描寫或借景抒情之靜態活動為多,
30 原文引於下:「凡是回憶觸及的地方,我們都發現有一種隱秘的要求復現的衝動。……我們
所復現的是某些不完滿的,未盡完善的東西,是某些在我們的生活中言猶未盡的東西所留
下的瘢痕。」宇文所安著、鄭學勤譯,《追憶》(北京:三聯書店,2004),頁 113。 31 此為鄭騫先生闡發王國維之語。原文為:「東坡之詞豪,稼軒之詞曠。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也。」見王國維,《人間詞話》,《詞話叢編》,頁 4250。其餘論述可參見可參見鄭騫,〈漫談蘇辛異同〉,《景午叢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72),卷上,頁 268。
試論稼軒詞中之「春歸」意義及其婉約表現
139
而稼軒一反前人,轉靜為動,將個人意識透過春日的流動感表露,而不凝滯
於單一物象的靜態描寫。學者顧隨曾以稼軒擅於「以健筆寫柔情」32。其中
所述之「健筆」,或為意氣縱橫的精神形於外的流動感,形成一種勁切的風
格之餘,筆觸卻能維持細膩柔婉。其次,「春」作為有意識的存在,打破了
詞中時間感緩慢的常態;與此相續而來,是由時間流逝之焦慮轉化而成的春
歸惆悵,醞釀出稼軒獨樹一格的抒情特色—面對生命走向老衰的必然與命運
難解的衝突的積極情態,稼軒筆下之春光並非只是表面上須臾轉瞬的流動,
而與詞人內在底層迴蕩著因「風節建豎,卓絕一時,惜每有成功,輒為議者
所沮」33所致生的深切蒼涼的不平之鳴相為呼應。周濟以稼軒改變了詞體向
來以婉約為正的表情樣態,是謂稼軒將根植於內心那份幽微柔軟的體物之情
與難以自抑之氣,一變而成就帶有士大夫氣質的,哽咽難訴的悲涼情狀而成
就「變溫婉、成悲涼」之意34。葉嘉瑩歸納稼軒詞中欲飛還斂的意氣35、王國
維《人間詞話》謂辛詞有「傍素波、干青雲之概」36,稼軒春日的動態描寫,
或正為此處之「氣概」或是「意氣」之展現,而與時間的流逝感緊密相連。
也由於這份深藏之內的體悟會心屢為外在環境摧折之氣在詞中轉化為春日
32 顧隨,《駝庵詞話》,收入朱崇才編纂,《詞話叢編續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 3209-3210。
33 劉熙載,《詞概》,《詞話叢編》,頁 3693。 34 語出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稼軒斂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見《詞話叢編》,頁 1643。
35 葉嘉瑩以「『欲飛還斂』者,固是眼前之水勢,而同時也就是辛棄疾內心中的激蕩悲憤的情懷。」筆者按:葉氏在此處引辛棄疾〈水龍吟〉詞中之句子藉以說明其內心蘊藏之雄心壯
志與外在環境的作用,此一內蘊或即意氣之所在。又趙尊岳評論辛劉詞亦有謂「以真性情
發清雄之語,足以喚起四坐靡靡,別立境界……實則清根於性情,雄由於筆力。綜覽全集,
亦有〈祝英臺近〉等不雄之作,而無不清之作,斯實由於真性情所寄託。」如統合兩家之
言,稼軒詞中之氣實為其真性情之顯現,或即謝章鋌所謂的「奇氣真氣」。趙氏所謂「清」
的另一層展現,或即稼軒春日之動態感的延伸。引文分見於葉嘉瑩,《唐宋名家詞論稿》(石
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頁 247-248。趙尊岳,《珍重閣詞話》,收入張璋等編纂,《歷代詞話續編》(河南:大象出版社,2005),頁 777。
36 語出王國維,《人間詞話》:「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氣象論,亦有『傍素波、干青雲』之概。」見《詞話叢編》,頁 4249。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三期
140
在事物間所展現的流動感,始能形塑出與婉約詞家迥不相侔,既有蒼涼而無
處可依之悲,又帶有纏綿悱惻的「婉媚」情態。此動態感或正為稼軒春歸詞
中「豪」之發現處。
三、詠歎春歸——婉約情態的具體表現
(一)迥異於豪放的內在世界
前文已就春歸之表現方式及其內涵先為初步探討,以春光的流動與時間
的焦慮感為論述主軸,並以此為稼軒豪氣在婉約詞篇中之顯現處。如果創作
是自我內在的再次剖析和表述,文人語言的使用必然地體現了自我心理意
識。如對照蘇、辛兩家不難發現,東坡風格之「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
37,是以根於性情與學養所流露的端正莊重之姿、剛勁健朗的之態為本;而
流麗婀娜為意氣生動之形,藉以調節剛健莊重可能出現的生硬,以求剛健之
中仍帶華美輕盈、不滯於物情的美感表現。因此,東坡詞篇縱不乏詠物體情
細密之作,然幾無纖穠側艷之語。反觀稼軒看似豪情萬丈,不可一世,詞評
家亦多有「豪放」、「豪壯」、「豪雄」、「豪爽」、「豪雅」、「豪邁」38等詞彙評
述稼軒詞風;又因文如其人的傳統印象,故往往以「豪放」兩字概括其風格。
37 關於東坡詞本質情意的論述,詳見劉少雄,《東坡以詩為詞論題新詮》(臺北:里仁書局,
2006),頁 115-162。 38 此處相關詞評甚多,在此僅列舉部分為例。如「辛稼軒詞,慷慨豪放,一時無兩,為詞家別調。」(李佳,《左庵詞話》,卷上)、「稼軒求勝於東坡,豪壯或過之,而遜其清超,遜其
忠厚。」(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八)「一派為稼軒,以豪邁為主,繼之者龍洲、放翁、
後村,猶禪之北宗也。」(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續編三)「稼軒豪邁是真……味在酸
鹹之外,未易為淺嘗人道也。」(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稼軒有吞吐八荒之概,
而機會不來。……故詞極豪雄,而意極悲鬱。」(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六)「華亭宋
尚木徵璧曰:『辛稼軒之豪爽,而或傷於霸。』」(江順詒輯,《詞學集成》,卷五)「近日作
詞者……徒狃於風情婉孌,則亦易厭,回視稼軒所作,自覺豪爽。」(陳子宏語)(馮金伯
輯,《詞苑萃編》,卷五) 「稼軒豪雅。」(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十二) 依序分見於唐圭璋,《詞話叢編》,頁 3107、3969、3511、3925、1645、3272、1871、3470。
試論稼軒詞中之「春歸」意義及其婉約表現
141
所謂「豪放」,楊廷芝《詩品淺解》解曰:「豪邁放縱。豪以內言,放以外言。
豪則我有可蓋乎世,放則物無可羈我。」39指稱一種不受拘束,行止自如無
礙的表現。如就語彙本身更進一步思考,「豪」指稱氣魄,指精神上不受拘
束,爽直大方的體現;為受外物環境影響下,個人性情與外物激盪後的反應。
若以東坡行文風格為剛強勁健,則言其內在精神之飽滿,發而為文,展露其
精力彌滿、饒具風骨的姿態。相對於此,諸家詞評卻從未有人以「剛」字論
稼軒,似乎暗示稼軒「豪」之表象下的內緣深層的意識與「剛」之風格略有
未能全然類同之處。如果豪在婉的發現處是以動態感為表層,且豪婉兩者兼
具一體兩面之關係,豪放作為一外緣的形式,立於相對面的婉約是否即是內
緣情性?傳統多以「文如其人」之說連結作者人格與作品風格之間的相似
性。40自是,如能創作出「風流嫵媚」作品之詞人,其內心深處必然也有柔
軟轉折之處,絕非僅限於表面上所見之雄傑豪放。
透過前一節的分析,對稼軒內心幽微怯懦而難以言明的意緒已有初步了
解。在與春歸相關的詞篇中,由於作品間的脈絡思致亦多反覆纏繞、曲折婉
轉之故,穠纖綿密之情致,其所使用的語態亦多近於女性口吻,往往被譽為
「不在小晏、秦郎之下」41。不難想見在詞評家的眼裡,這一類作品實近於
小山及少游等婉約詞人纖細纏綿之風格,而與「春女思」傳統的內在情意相
類。其次,如以創作季節為分類,春秋二季的寫作主題與抒情樣態亦有分別。
大體而言,稼軒的秋日詞多由送別起興,以友朋相別,歡會難再的別情為敘
寫主軸,由事即詞,而少見內省式的自我探索與剖析。如〈太常引〉(一輪
39 清•袁枚注、郭紹虞輯注,《詩品集解.續詩品注》(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頁
23。 40 魏慶之《詞話》曾引稼軒〈祝英臺近〉(寶釵分)謂此闋詞「風流嫵媚,富於才情,若不類其為人矣。」此處或已先預設豪放為稼軒基本風格,因而有「不類其人」之疑惑。然《文
心雕龍.體性》有謂「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反之,
如文本風格為婉約嫵媚,則詞人內心必有類似的情韻存在。形於外之風格差異,實為人情
多變所致,不應逕以單一風格之作品論斷作家人格性情。 41 語出馮煦《蒿庵論詞》「〈摸魚兒〉、〈西河〉、〈祝英臺近〉諸作,摧剛為柔,纏綿悱側,尤與粗獷一派,判若秦越。」見辛更儒編,《辛棄疾資料彙編》,頁 367。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三期
142
秋影轉金波)寫中秋月夜與個人的情懷,或〈滿江紅〉(快上西樓)、〈昭君
怨〉(人面不如花面)、〈滿江紅〉(塵土西風)或〈踏莎行〉(夜月樓臺)等,
則為贈友離別之作。縱然其間亦不免間雜自身感慨,但無論在數量上或是抒
情深度皆與春詞不類。相對春日詞多與個人情懷中寂寞自傷的情狀、理想追
尋之落空與游移連結,反而更近於悲秋傳統中士人對個人生命的出處無以為
繼的焦慮與哀嘆,連帶時光流轉而老大無成的落寞情懷。並且,由稼軒詞中,
春詞多於秋詞一倍的數量亦能反映出在春秋兩季所代表兩種抒情模式下,稼
軒毋寧選擇了春日此一富於女性特質,兼之得與香草美人之隱喻傳統相互呼
應者作為個人表情之用。換言之,春日的隱喻特質似更能喚起稼軒內在感
應,而與柳永藉秋日羈旅詞中所承繼的「不減唐人高處」的士人登高悲秋、
感傷不遇的詩學傳統表現略有不同。
附帶一提的是詞體與「擬代」傳統的關係。「擬代」一體原為詩人藉由
人物身份性別移形換位,以達成其藉詩言說的目的,形成一份橫越性別的共
同哀情本質。梅家玲曾定義擬代為「讀者/作品/作者間之辯證融會過程」。 42
此一創作意識奠基於文人對模擬對象透過移情、類比而得到感同身受的領
會,藉此使文人之情與模擬對象之意得到融整。而「由於『擬』、『代』之基
本質性使然……別後的相思、忠貞的情愛,幽居獨處、花落色衰的哀怨,依
然是貫串全詩的不變基調。」43擬代作為詩的用言模式之一,具有托寓人臣
的忠貞以達引起在上位者注意的功效。此種刻意模仿女性心理的寫作樣態,
到了以「婉約為尚」、「以豔為本」的詞體中,擬代原本的特殊政治指涉則往
42 按:學者孫康宜亦有類似言論,其道:「文學中的模式與創作實與男女彼此的社會處境息息相關。所謂『男女君臣』的托喻美學也同樣反映了中國傳統男性文人的艱難處境。……無
論是『男女君臣』或是『女扮男裝』,這些一再重複地以『模擬』為其價值的文學模式,乃
是傳統中國文化及歷史的特殊產物。」亦將此種模擬的現象作為傳統士人特殊的敘寫模式。
孫康宜:〈性別的困惑——從傳統讀者閱讀情詩的偏見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六期(1999),頁 117-118。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94。
43 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頁 97。
試論稼軒詞中之「春歸」意義及其婉約表現
143
往因難以遽指本事而被削弱。然文體擇選既為內(情)外(形)相互定義的
指標,填詞亦為個人內在情感活動的表露,其目的在於利用近於獨白的敘述
方式確保在單一語境下潛藏於自身內在的哀愁與幽怨能夠被傳遞,而成就一
個精美的心象世界。詞人擇詞體抒情必因心理活動的情意特質與文類有所會
通,而文體本身亦提供了真實情感一處遮蔽,使得相較於詩情更為幽渺的情
緒得到發抒可能。此即為託詞體表情與擬代的本質的相類之處。稼軒的春歸
之思較他男性詞人有著更為纖細的體物感會,或可由此種與女性心理相通的
內在情意為觀察。
(二)春歸的表現形態——「婉約」之姿及內涵
就詞中語言之使用及其內涵,下文即就照鏡以及惜春的諸種舉措為論試
圖探索其間所反映的內在情意世界。
——
「鏡」作為一詩詞中經常出現的語彙往往反映出自我或外人以怎麼樣的
眼光去審視鏡中所反射出來的影像,進而使主人公得以藉此建構自身價值進
而決定自身定位。44在詞此一富於女性陰柔特質的文體之中,「照鏡」更與女
性的姿態緊密連結。早期詞如晚唐溫庭筠〈菩薩蠻〉「照花前後鏡,花面交
44 關於鏡與自我形成之論述,拉康與羅蘭巴特皆有「鏡作為一視角的投射,以形構出照鏡人的自我」之意見。在拉康的「鏡像階段」理論中,其利用兒童借助自己在鏡子中的影像認
識自身,而非通過自己客觀的身體獲得自身的同一性。藉此認定兒童的自我建構為一「想
像的再認」(reconnaissance imaginaire)。羅蘭巴特則進一步指出「鏡像階段就是通過我認同處在我之外部的鏡中形象,把我自身構成一個具有整體性的肯定的形象的過程」。拉康之
目的在突出人不能在自身內部發現自己,而必須透過他者中才能發現自我。兩者所指涉者
實不外為人之自我建構以及意義的發現必仰賴他者的存在,此處之照鏡等行為正好提供了
女子審視自我的視角,在鏡內鏡外兩者的觀照下,對照出個人形貌的形構與其意義。關於
鏡像理論,可參考福原泰平著、王小鋒、李濯凡譯,《拉康——鏡像階段》(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 40-46。羅蘭.巴特著、懷宇譯,《羅蘭.巴特自述》(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頁 3-128。另,學者方秀潔亦有鏡與女性視角的相關討論。詳見方秀潔,〈論詞的性別化〉,《詞學》第 14輯(2003.8),頁 82-108。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三期
144
相映」(之一)、「鸞鏡與花枝」(之十)等45,以鏡緣之雕飾成雙反襯花枝雖
美而無人共賞的寂寥。銅鏡內外所對映出的形象往往恰為主人公內心的諸多
懷想的示現。如果鏡本身為自我的顯像與投射,詞人必對鏡中倒影有著先行
預設或期待;當其間有所落差之時,閒愁便隨之而生。諸如現實的紛擾、理
想的失落與自我疑懼,乃至對大化萬物莫不處於變化流轉的憂慮,無非如
是。是故,稼軒詞中反覆敘寫的「磨鏡」、「攬鏡」,而後內省思索、到棄置
不看的互動過程,實際上反映出的是更為嚴肅的主題—人如何在時光流轉之
中尋覓個人定位?「春歸」一事在此被具體化為攬鏡過程的描寫,使得春→
歸、美人→遲暮、鏡→華髮成為互為連結的概念。上一節引到的〈玉樓春〉
(風前欲勸春光住)「鏡中已覺星星誤,人不負春春自負」以及〈漢宮春〉(春
已歸來)「閒時又來鏡裡,轉變朱顏」,前者寫春去,後者寫春來,無論是鬢
髮抑或容顏,都是個人由鏡中察知自身外貌的變化。在相對乍見的驚疑之
後,對照出歲月流逝的飄忽感以及人居於四時流轉之中的渺小。在另一闋〈念
奴嬌〉(書東流村壁)詞中,稼軒以客居異鄉的羈旅身分起筆,寫對故人回
憶的眷戀,鏡與花的對照更為鮮明。試見引詞:
野棠花落,又匆匆、過了清明時節。剗地東風欺客夢,一夜雲
屏寒怯。曲岸持觴,垂楊繫馬,此地曾輕別。樓空人去,舊游
飛燕能說。 聞道綺陌東頭,行人長見,簾底纖纖月。舊恨
春江流未斷,新恨雲山千疊。料得明朝,尊前重見,鏡裡花難
折。也應驚問,近來多少華髮。46
本詞為稼軒於淳熙五年(1178)二、三月間在江西安撫任上被召赴臨安臨安
途中所作,抒發清明時分的羈旅感懷。由詞題「書東流村壁」,便暗喻著物
是人非的落寞,對應稼軒數年間輾轉來往於臨安與豫章之間的經歷,不難體
45 引詞分見於曾昭岷、曹濟平、王兆鵬、劉尊明編著,《全唐五代詞》(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99、102。
46 鄧廣銘,《辛稼軒編年箋注》,頁 52。
試論稼軒詞中之「春歸」意義及其婉約表現
145
會其心理轉折。「落」、「匆匆」至「過了」,表現出季節流動(長時間),過
往人事的倏忽;而後轉至一夜東風(短時間)冷凝雲屏的寒意,增添了詞中
時光倏忽的冷冽感,加強個人幡然覺知春歸卻無從把握的悵然。下句所述為
被驚醒的「客夢」往事,上片結尾回到醒後的現實,「樓空人去,舊游飛燕
能說」,在時間淘洗後人得以感知的變動,只剩飛燕能夠見證。過片承上敘
述,以「聞道」起頭,藉由引述他人之言引出一種虛實難辨的情懷。舊時「曲
岸持觴,垂楊繫馬」的輕別映照今日「綺陌東頭,行人長見,簾底纖纖月」
的聞見,兩個相對的斷片描述各自為獨立的片段回憶,利用對面言情手法錯
落出回憶的層次,迴盪出詞人內心的起伏迭宕。「鏡裡花難折」,既是相聚片
刻難以久暫,又有往昔容顏不容稍留的暗示。回憶以斷片形態出現之際,亦
留下了無數待修補的縫隙。此種等待讀者,甚至詞人自己的想像與添附的裂
罅,相較於連鎖環節的因果關係呈現,更能錯落出個人對生命的思索與擇
選。47
「鏡」象徵著詞人所有想望的交會,也是認定自身價值成就的媒介。利
用人工的鏡映照出時間的痕跡對照自然世界以花落為表徵的春歸。是故,「春
歸」與照鏡之間的聯繫不單指個人照鏡之後自慚貌不如昔,而是以照鏡作為
與往事的聯結點。縱然心知鏡裡之花難折,但在重新省察過往歷程的同時,
亦從中得到了生命意態的確認並從其間汲取面對現實的勇氣。
2 ——
稼軒婉約詞篇中最為人所稱道者,當屬其「摧剛為柔」之筆法,主要指
稼軒寫作手法,將極具男性表徵的剛強及動態融入詞中,而出之以柔婉委
屈、風姿綽約的情狀。然如果先承認摧剛為柔此一前提為是,則便有稼軒之
47 呂正惠〈「內斂」的生命形態與「孤絕」的生命境界──從古典詩詞看傳統文士的生命境界〉一文中也寫到:「辛棄疾非常明白地意識到,他的一生最大的悲哀的本源。……孤獨來自生
命的虛擲與浪費。」這種對生命流逝的緊張感構成稼軒詞中低迴幽怨的部分,透過女子形
象與行為敘說的抒情表現,成就一份雙重意蘊的特美品質。原文收錄於柯慶明、蕭馳編,《中
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頁 381。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三期
146
內在本性為剛強之預設。正如前文所道,稼軒詞中既選擇了春日作為主要抒
發對象,又多以女性形象或是言動作為自身情感的借代,則不應當將此情形
視為偶然,而有重新檢視的必要。
關於詞中的女性敘寫,「人物活動乃顯現為寥寥可數幾種固定的模式。
而且每一種行動都因為活動幅度不大而靜態傾向居多。如梳妝、照鏡、思憶、
做夢、倚望、愁悵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女性活動」48或倚樓望江、或攬鏡而
照,多半為足不出戶的封閉樣貌,俯仰棲息的處所只剩繡閣與花園的一方天
地。透過空間的限定,置身於閨閣中的女性恆久等待之形象亦被定著,情感
隨著時光積累延伸出女性生命的感傷意識成為詞體本色定調。學者顧隨曾道:
「稼軒寫詞有特殊作風,其字法句法便為他詞人所無。中國詞傳統是靜,而
辛是動。」49稼軒個人涵養所驅策之典故以及由內至外所煥發的意氣呈現於
文體的結果,便是其個人的獨特性的顯現處。而所謂「動處」,一為上文所
言之「氣」體現於春日流動感之描寫,另一則為與詞中靜態描寫搭配出現的
細微動作舉措。〈祝英臺近〉一闋,以花卜所思之人歸期以及春愁難解、春
歸不返的傷懷,呈現出稼軒筆下女子的特殊言動。試見引文如下:
寶釵分,桃葉渡。煙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
片片飛紅,都無人管,倩誰喚、流鶯聲住。 鬢邊覷。試把
花卜心期,才簪又重數。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
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將愁歸去。〈祝英臺近.晚春〉50
小題點明晚春以明示寫作時節。起句以下三句連用「寶釵」、「桃葉」與「南
浦」,埋下後文離散的伏筆,以達渲染氛圍的效果。稼軒在此未透露其敘寫
對象,而「暗」字的使用,讓柳絲如煙的場景所堆砌起離愁的重量頓時一落
48 張淑香,〈男性情色幻想的美典——溫庭筠詞的女性再現〉,《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7 期(2000.9),頁 69-138。
49 顧隨,《駝庵詞話》,朱崇才編纂,《詞話叢編續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3209-3210。
50 鄧廣銘,《辛稼軒編年箋注》,頁 96。
試論稼軒詞中之「春歸」意義及其婉約表現
147
而下,原本構築出的遼闊的空間就此黯淡,眼前可見的範圍也隨之限縮。
「怕」,一方面承接了上文低迷的氛圍,另一方面也引領出詞人對登樓遠眺
此一空間轉換的疑懼。下半闋轉入女子自述,省略了女子對鏡興嘆的過程,
而以數其簪花之瓣數推算良人歸期作為詞人抒情表現。由「才簪」、「重數」
的輾轉反側,羅帳燈火漸暗,良人歸期未知的無望。51從對春的質疑反轉出
意識到時光流動的深層悲哀。值得注意的是,春日被擬制成為眷戀所思的對
象,留春的執著渴求由日至夜,進而夢中相尋,然對春物的護持愛惜之情終
成徒然的無奈。全篇獨白式的敘述,似控訴人如春去負情,怨春卻又問春。
當時間成為人事更迭的最大變因,人亦僅能處於被動的位置送春遠去。
近人陳匪石以沈謙評此詞「昵狎溫柔,魂銷意盡」未盡完整,而以本詞
「終覺風情旖旎中時帶蒼涼淒厲之氣。」52又梁啟勛亦以此詞「態妍意婉,
如有物在喉」53。「蒼涼淒厲」源自於無以為繼、躊躇不得的現實情狀;「有
物在喉」,便是其欲吐難言的低回掩抑。究其源頭,實為深藏於內的春心被
引動後無處可安之哀感。所謂「摧剛為柔」,是一種語言表現形式的轉換,
將英雄豪傑的動態之氣轉化為近似女性情思之柔情。在看似婉妍的字裡行
間,莫不充斥著憂懼而不定的內在與外來環境的接觸下所產生的難以言說,
且被百般壓抑的蒼涼無依之感——無人能解,無人得見的寂寥落寞。其他詞
例尚有〈惜分飛〉(翡翠樓前芳草路)「望斷碧雲空日暮。流水桃源何處。聞
道春歸去。更無人管飄紅雨。」化用江淹「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敘
寫等待無望的情癡以及春逝後無人見管之殘紅,猶如自身漸次幻滅的理想與
51 筆者按:此處所卜之花,吳則虞《辛棄疾詞選集》以「古無以花卜者,此花為燈花之省。」又以「下句『才簪又重數』,言以簪挑燈花,故與簪及鬢邊連稱,非謂花也」。然鄧廣銘《稼
軒詞編年箋注》以此處為:「當是以所簪花瓣之單雙,占離人歸信之準的。」周邦彥〈渡江
雲〉(晴嵐低楚甸)亦有「沉恨處,時時自剔燈花」句。觀諸兩者意見,如以簪挑燈花,才
簪又重數,燈花似乎難以簪一挑再挑。此處似仍應以鄧說為是。分別引自吳則虞,《辛棄疾
詞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 197。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頁 97。 52 陳匪石,《宋詞舉》(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頁 74-75。 53 梁啟勛,《詞學》(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下編,頁 9。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三期
148
情感。另一闋〈摸魚兒〉亦可見相似之詞筆意態: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
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
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 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
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
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
煙柳斷腸處。
風雨落紅引發的暮春感懷原生自一份「晚恨開遲,早又飄零近」的不安。由
遠處落紅顯見留春無望,而後詞人又將視點拉至近處觀察靜置一角的「畫網
蛛簾」,以明其欲強留春色殘跡的癡執與堅定,卻僅剩斷紅飛絮,猶如自身
縮影。過片以降,長門之典故,代表本質的美好卻因種種緣由而未能被人所
傾聽理解,脈脈無言成為不得不為的沈默。此為個人情感上得不到反饋與理
解的隱喻。其下的玉環、飛燕兩者與漢唐國運相繫的美人典故,利用歷史所
帶出的微妙繫連,暗指對國勢的憂心。此處所述的情感易變與歷史回顧,捨
棄了英雄將相的典故而改以美人為例,便是稼軒因應詞體婉約本質所為之調
度。再者,就典故的連綴手法,語序倒置而散亂的語言構篇方式亦能視作是
純女性的言說樣態。54因此,長門、飛燕等典故作為不遇與徒然的隱喻,呼
應上片亟欲留春之願。不能自安自適之情湧現,而致生「詞意殊怨」此一肇
因於個人與現實的落差。
稼軒婉約詞作向來被以「摧剛為柔」概括,往往強調其剛強豪放之氣在
婉約詞中的呈現形態,其暗含的假設便是稼軒本性為豪放不羈之態,因情立
體,故展現的是剛強的豪傑形象。但如將情體之間的關係逆推,有婉約之形
則必有幽微體物之性,婉約柔情應為其自本自根而生的幽微情懷所外顯的表
54 此處借用葉嘉瑩〈從花間集的女性特質看稼軒豪放詞〉文中認為稼軒豪放詞中雖然用的是男性的口吻,但語法亦帶有女性語言凌亂、不整齊的特點。詳見葉嘉瑩,《古典詩詞演講集》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頁 364-385。
試論稼軒詞中之「春歸」意義及其婉約表現
149
現,而與詞體本質融通;而春歸題材正能切合此種幽婉情性的表現。在春歸
所帶來的一連串情感轉折中,這種以纏綿哽咽之語言表露內在之怨情,便是
婉、怨的表現。而在其間所流動的英姿颯爽之氣,則為稼軒嘗試擔負人事種
種不如意情緒之努力。另一闋〈滿庭芳〉(誰將春色去)將自身化為尋春之
人,然而尋覓的結果,僅為「夢裡尋春不見」與「空腸斷、怎得春知。」55所
有的歡會遇合終究成為時間的灰燼,曾經執著的一切也會變成徒然,僅能憑
藉著自我表述對抗一切時間流轉。此處之「去」、「不見」與「怎得春知」,
皆有指責春日未能體察人意,使人當下無法感知時光流動之意味。末段「休
惆悵」三句接續前文尋春不見,腸斷亦不得春知的喟嘆,最後語氣一轉為決
然。既然自然事物的遷變由不得人,留春之願亦僅為徒然,人在現世又應該
如何證明自己?稼軒在此縱使明知刻碑為記,百千年後,是否還能留下些甚
麼不得而知;但「刻碑」本身所隱含的書寫意識,便是稼軒試圖對「春歸」
所象徵的時光流逝所作的抵抗。
除卻上述型態,另一種便是將自身化身為等待的女子,在詞人塑造的密
閉空間中,詞人將女子的等待化為恆長的一抹幽怨身影。時間因太長的等待
而呈現凝結靜止,人傾盡心力追求事物之執著便溢滿了整個畫面。試引詞如
下:
敲碎離愁,紗窗外、風搖翠竹。人去後、吹簫聲斷,倚樓人獨。
滿眼不堪三月暮,舉頭已覺千山綠。但試將、一紙寄來書,從
頭讀。 相思字,空盈幅。相思意,何時足。滴羅襟點點,
淚珠盈掬。芳草不迷行客路,垂楊只礙離人目。最苦是、立盡
月黃昏,欄干曲。〈滿江紅〉56
55 原詞錄於下。〈滿庭芳〉:「急管哀絃,長歌慢舞,連娟十樣宮眉。不堪紅紫,風雨曉來稀。惟有楊花飛絮,依舊是、萍滿芳池。酴醾在,青虬快剪,插遍古銅彝。 誰將春色去,鸞膠難覓,絃斷朱絲。恨牡丹多病,也費醫治。夢裡尋春不見,空腸斷、怎得春知。休惆悵,
一觴一詠,須刻右軍碑。」鄧廣銘,《辛稼軒編年箋注》,頁 84。 56 鄧廣銘,《辛稼軒編年箋注》,頁 77。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三期
150
本闋為稼軒在兩湖任官(1179-1180)之時所作。開頭利用「敲」字為伏筆,
利用知覺性動詞以集中人的感官體驗,風動翠竹的萬葉千聲使得原本凝聚的
離愁情懷一瞬間散落,搖盪窗內人的心緒;人去不見的惆悵落寞與留春無計
的寂寥疊合,內心的焦躁不安,源自於「倚樓人獨」的孤絕。觸目所及的滿
山綠意既是時節流轉之象,亦為相思綿綿不盡之喻。而芳草垂楊,一不為己
挽留行客,二又阻去了離人身影,亦阻斷了身後痴戀的目光。陳廷焯《雲韶
集》卷五評此詞「情致楚楚,那弗心動,低徊宛轉,一往情深,非秦、柳所
能及。」57指出詞中女子低迴嫻雅、百轉千折的思致樣貌,連結暮春與女子
待人未果的愁情。「立盡月黃昏」,是現時等待的無望,同時暗示此一等待可
能無限延伸至無窮無盡。「一往情深」所指,正是顧而不返,縱然為苦,亦
無放棄之願的執著。辛詞中的女性在纖柔的神態言動之下,蘊含著人正面應
對「春歸」此一不可逆之必然的勇氣。稼軒被譽為秦、柳所不及的情深處實
為其精神意態之深刻處。其內在性格中極為纖細易感而富於女性特質的一面
並非詞人有意模擬,而是詞人不自覺地流露的內心風景與詞之本質有所疊
合。周濟所謂「蘇必不能到」的辛當行處,或即是歷來詞評者稱許之「摧剛
為柔」之表情體物纖細深美的「情至處」,實為源自稼軒天性本然。而此種
內心本質的流露,或正為稼軒以春日為主要抒情時節之理由。
四、結論
「春」之意象作為隱喻,往往與青春年華、美好初始相繫;詞人反覆書
寫歸去之悲以成就春歸的沈寂色彩,其歸去亦不免與家國之恨難平,或是青
春年華流逝的喟嘆連結。而稼軒的「春歸」之意,由於包含「歸來」與「歸
57 見孫克強、楊傳慶點校整理,〈《雲韶集》輯評之一〉,《中國韻文學刊》2010年第 3期,頁
63。
試論稼軒詞中之「春歸」意義及其婉約表現
151
去」雙重意涵,因而在「歸去」的敘寫中亦潛伏着「歸來」的期待,即便迂
迴壓抑,亦不類同於他人一味陷入春歸惆悵無望之情緒,而特出了春日的主
體性與其流動來去的躍動感。相較於清真的靜定而耽溺,稼軒在詞中所延伸
的空間感透過其眼目所見的距離範圍拉長而更顯遼闊,春去無蹤的失落感也
因時空幅度的延展更增添其對比,人獨立於四方空間中的不安感更為深沈。
另一方面,透過抒情空間的延展,描寫春日動感、喟嘆春歸的同時,延展後
的留白部分成為個人情懷自我形成的空間而轉化為一股積極意態。並且,在
春歸的敘寫中,其間柔媚中時見氣魄,風情旖旎之餘又見蒼涼的表現,或為
歷來詞評家評論稼軒詞的「氣」之所在,亦為氣在婉約詞章中之發現處。
其次,稼軒發抒喟嘆春歸之懷抱,多託女子之口吻與行為傳達一份對於
春歸之後必定再返之日的等待與冀盼。向來僅在悲秋傳統中感知的士人對個
人生命的出處無以為繼的焦慮與哀嘆,連帶時光流轉而老大無成的落寞情
懷,在稼軒詞中卻轉而以春日作為主要敘寫季節,而與「春女思」的傳統暗
合,顯見稼軒內在潛藏的一份與春日女性心理相通的情意特質。透過描寫照
鏡理妝、以花為卜及立盡月黃昏的女子痴執樣貌;個人亟欲留春的積極情
態,反映出稼軒個人對生命之承擔以及對生命的堅持與擇善固執。縱然失落
卻始終保有再振的一絲希冀的意態,成為其喟嘆「春歸」作品中的深層意念。
「春歸」主題作為稼軒內心風景的流露,以人花對照的方式反差出內在
幽微而難辨的情懷。花作為人類生命週期的濃縮,縱使在世上存續時間有短
長不同,共同的走向卻都是寂滅凋零。詞人栖惶終日、難以自安的內心投影,
便具象地呈現在這些深具婉約特質的詞篇中。稼軒書寫春歸之詞篇所表露
者,是在婉約為本的美感基礎下,豪放風格如何被詞人所驅策融整,而在不
偏離「要眇宜修」的詞體美感本質要求下,成就一份帶有文人氣味的特殊美
感體式。鄭騫先生曾以「詞之代表陰柔之美,是無可置疑的。……柔並不是
一味的軟綿綿,而要有一種韌性。」 58詞體雖以豔科為主,表情亦以陰柔要
58 鄭騫,〈詞曲的特質〉,《景午叢編》,卷上,頁 61。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三期
152
眇為佳。但文學既根於人情,並為情形於外之展露,則必然有其複雜多樣的
內在性。觀諸稼軒春歸詞中富於女性特質的表現,縱然傷感抑鬱,卻仍能回
應以相對的堅韌力量展現個人的主體性和人敢於和時間對抗的意志力。鄭騫
先生此處所謂之「韌性」,或正為人面對外在世界的變幻無常時所煥發出的
內在力量,藉以激盪出迭宕的姿態,情之力量始能貫通而開展。
責任編輯:吳儀鳳
試論稼軒詞中之「春歸」意義及其婉約表現
153
Euphemism in Xin Jiaxuan’s Ci:
A Preliminary Study
Jia-yun YU *
Abstract
Most of the researches on Jiaxuan Xin’s Ci focus on his uncon-
strained writing style; however, there are also works with
well-propositioned condense quality (穠纖綿密) and high sensitiveness
(體情細緻), especially those related to the motif of the return of the spring.
Jiaxuan chooses Ci, inherently feminine, as the genre for representing his
personal emotions. Jiaxuan produces different amount of poems in the days
of spring and autumn respectively. It is therefore worth our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his selection of genres and emotional represen-
tations in writing and seasons.
The term, the return of the spring, involves double conditions: the
re-coming and the departing of the spring; both of them result in the sub-
jectivity and mobility of the season spring. In Jiaxuan’s Ci, the time and
space, originated from the sense of movement, are more magnificent and
infinite than those in poems by other poets. In a sense, Jiaxuan creates a
space of representing himself in the blank. On the other hand, as far as eu-
phemism is concerned, Jiaxuan’s Ci will b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piction of the speaker’s looking into the mirror and the sensitive
* Ph-D. student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東華人文學報 第二十三期
154
appreciation of the returning of spring; this feminine way of narration will
be analyzed. Based on my observations of Jiaxuan’s method of composing,
his Ci will be looked deeper into how the poet displays his personal char-
acteristics and how he demonstrates his unconstrained vitality through this
inherently feminine subject matter. For these purposes, this paper engages
in both a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Return of the Spring” and discussions
about the feminine way of narr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attempting to re-
veal Jiaxuan’s unique spirit besides re-understanding the connotations of
his Ci.
Keywords: “The Return of the Spring,” vitality, unconstrained,
euphemism, movement, Jiaxuan’s 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