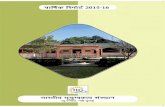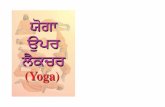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系統理論觀點(Emergence...
Transcript of 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系統理論觀點(Emergence...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第 36期 2011年 3月 頁 39-86SOCIETAS: A Journal for Philosophical Study of Public AffairsNo. 36, March 2011, pp. 39-86
突現作為弔詭:
從整體/部分到形式/ 媒介之區別的社會系統理論觀察 *
劉育成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博士候選人
Emergence as Paradox: From Whole/Part to Form/Media through Social
Systems Theory
by Yu-Cheng Li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email protected]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2010年 5月 17日由中研院社會所主辦之「世界社會中的魯曼系統理論:來自台灣的回響」研討會,並承蒙評論人萬毓澤惠賜卓
見。作者另外感謝湯志傑、黃厚銘、曹家榮,以及兩位匿名評審詳細的審查
意見與寶貴建議。若文中尚有之錯誤與疏漏等,當由本人負責。
收稿日期:2010年 7月 1日;通過日期:2010年 12月 10日
40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摘 要
本文企圖探究的是「突現」概念與 Luhmann的社會系統理論
之間的關係。一般而言,「突現」概念與複雜系統的自組織(self-
organization)過程有關,在此過程中所出現的嶄新且具連貫性的結
構、類型與性質等,乃被視之為突現概念的主要內涵。有研究者認
為 Luhmann在其社會系統理論中並未處理此概念。這樣的看法或許
有失公允。本文所主張的是,在系統形成之運作中,「突現」就是弔
詭。透過對系統/環境的這組差異以及系統在自身之中再引入這組
差異之運作的討論,或許對突現概念提供了不同的理解。「系統即差
異」的觀點以及媒介/形式之區別則提供了理解突現的較好途徑。
關鍵詞:突現、社會系統理論、媒介/形式、區別、弔詭
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系統理論觀察 41
一、突現論及其爭論
「突現」(emergence)1概念在社會科學中的爭論由來已久。近年
來的系統理論發展則對此議題有越來越多的關注,尤其是在所謂的第
三波系統理論,亦即複雜性理論中有著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突現
是探討關於整體以及整體與部分之關係的問題。一般而言,突現現象
乃是發生在整體(whole)的層次,而非構成該整體的個別組成部分
(part)之層次。此一整體與個體之關係的爭論在社會科學的發展中
可追溯至對個人與社會之關係的討論。然而,有關此一議題的大量
研究則是在複雜科學(complex science)中獲得較多的關注與發展。
在社會科學中對突現概念的討論,一方面是機械論(mechanistic)
與生機論(vitalist)觀點之間的爭議(Stephan, 2004),另一方面則
是整體與部分之間的爭論(Gregersen, 2006)。在社會科學研究中
有關整體與組成部分之關係的討論中,主要區分「方法論上的個體
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與「方法論上的整體主義」
(methodological holism)。前者主要是一種強調分析或化約、還原的
方法,認為個別組成部分的特質可以用來解釋整體的特質,或者,整
體的特質可以從個體的特質中推論出來。據此,整體是部分的總和。
相對於此的是方法論上的整體主義(或集體主義)。其主張是,整體
所擁有的「突現」性質無法從個體的特質延伸出來。就此而言,整體
是大於部分的總和。然而,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為以此來表述突現
1 中文有另譯為「聚現」(萬毓澤,2009)、「迸生」(葉啟政,2008)、「浮現」(一般字典的翻譯,例如譯點通)等。本文統一以「突現」一詞表示,原
因在於社會學對突現的討論多半將之視為一種不同於個體集合但卻是屬於整
體的特殊性質。在此,我也要先保留「整體」、「個體(或部分)」一詞的使
用,至少在本文脈絡中,其所表現的內涵可能與傳統上的界定有些許差異。
42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性質毋寧是不足的。例如,Richard Langlois即指出突現性質的問題
並非是一個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之間的議題。他主張社會現象總是
「突現的整體」(emergent wholes),對其之理解無法完全地將之化約
成個體的行為。因此,他認為重點不在於是否能夠從個體的特質演繹
出整體的特質,而是「我們是否無論如何都應該考慮組成部分」的這
個問題。他認為「整體主義的要旨並不是說我們應該去研究突現現
象;整體主義的要旨在於:我們應該直接研究整體,而無需以任何
有意義的方式來考慮其組成成分的運作」(Langlois, 1983: 584)。2然
而,這只不過是有關整體與部分之關係的其中一個觀點,就本文而言
所指出的是,「整體等於部分之和」與「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的看法
在後來不同學科的研究中均獲得不同程度的修正。
對突現的研究與 20世紀六○、七○年代的複雜系統理論之發展
有密切關係。然而,在此之前許多不同學科背景的研究者便或多或少
地關注此概念。例如哲學家 John Stuart Mill發現,化合物(chemical
compound)具有不同於其組成部分的性質(Mill, 1882/1843: 267);
G. H. Lewes則從Mill的同徑(homopathic)與異徑(heteropathic)
法則出發,提出了結果力(resultant)與突現之間的差異(Lewes and
Mill, 1993/1874);Engels「量變到質變」的論述認為突現乃是其結果
(Engels, 1878/1969);數學家 Norbert Wiener則以反饋迴路來說明系
統的自我修正運作過程(Wiener, 1948);社會學家 James Coleman則
2 例如,Langlois以文學批評為例指出,沒有人會否認文學作品不只是文字與句子的總和,然而現代批評家卻堅持仔細地學習這些文字與句子(1983: 584)。此外,顏澤賢等(2006)也持此種看法,認為整體雖然表現了組成部分所不具有的性質,但也在此同時,一方面失去了組成部分的某些性質,另
一方面卻也保留了某些性質。因此,他們認為較適當的表述應該是:整體不
等於部分之和。這是其所謂的系統整體性原理(2006,頁 108-109)。
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系統理論觀察 43
認為社會學的核心問題乃是研究集體層次所突現之規律性(Coleman,
1964);最後,心理與社會學家 Jean Piaget則比較涂爾幹對社會的
分析與心理學的「完形」(Gestalt)概念,將突現與整體性相連結
(Piaget, 1995/1965)。3這些對突現的討論隨著複雜系統理論的發展
而重新受到重視。Sawyer在《社會突現》(Social Emergence, 2005)
一書中將社會系統理論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波是所謂的結構功
能論,代表人物為 Talcott Parsons。第二波是一般系統理論(GST)
與混沌理論,Luhmann的社會系統理論被歸於此。第三波則是所謂
的突現與複雜系統理論(Sawyer, 2005: 10-26)。根據他所區分的三波
社會系統理論之發展,本文所關注之對象為後兩波,其間之異同略
述如下。這兩波社會系統理論均同意系統的動態性與非線性特質。
然而,兩者之差異則表現在,後者較前者更關注微觀層次的行動者、
行動者的溝通、社會突現(social emergence),以及社會的獨特性
(society is unique)等面向(2005: 23)。他稱此第三波系統理論為
「複雜動態系統理論」(complex dynamic systems theory)或者是「複
雜適應系統理論」(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theory)。本文並無意詳
細討論 Sawyer對此之區別,僅指出一點作為參考。就其將 Luhmann
的社會理論歸類第二波系統理論,且宣稱所有對此波理論有所貢獻的
社會科學,均是從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社會學家而來的說法,似乎必
須有所保留(2005: 21)。至少,Luhmann的社會理論便不會輕易地
被歸類為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討論社會科
學如何受到突現論與複雜系統理論的影響與貢獻。
此外,Sawyer在對個體與整體主義的討論也指出,突現論
(emergentism)是一種非化約主義,但它與整體主義不同,因為它
3 其他可參考 Bunge(2003)、謝愛華(2006)、顏澤賢等(2006)。
44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只接受組成成分及其互動的存在(2005; also cf. Gregersen, 2006)。它
接受的是物質論式的本體論立場。根據此觀點,突現論僅接受組成
元素與其彼此間的互動,而避免了整體論式的本體論問題(Sawyer,
2005: 29; Stephan, 1999)。然而,他也指出突現論者同樣拒絕個體主
義,包括化約論、機械論等。突現論者不僅拒絕個體主義(原子論)
式的觀點,也不採取整體主義的立場。由於採物質論立場,這些突
現論者主張的是,某些複雜的自然現象乃是複雜系統,其更為複雜
與分化的「高層次」結構乃是突現於較簡單、「低層次」的組成部分
之組織與互動中(Sawyer, 2005: 29)。因此,他們認為較高層次的特
質乃是伴隨發生(supervene)於較低層次之組成物上。就此而言,
這是對因果關係的強調。換句話說,較高層次的特質之所以能夠出
現,必須是較低層次的組成份子之組織或互動先出現。或者,是一種
由下向上的影響力。Sawyer指出,「伴隨發生」乃是在兩個分析層次
之間的一種關係:「如果較低層次的組成部分之組織與互動沒有發生
改變,那麼較高層次的特質也不會出現或改變」(2005: 30)。然而,
他也認為儘管這些突現論者接受此種「伴隨發生」的概念,他們也不
否認較高層次的結構對較低層次的組成部分也具有因果力量(causal
power,上對下的影響力)(2005: 30; Pepper, 1926: 241)。然而,此種
物質論與還原或化約論的觀點也不斷地受到科學社群的質疑。例如物
理學家 Stephan Barr即認為新的物理學指出,我們對較低層次之實在
的知識並未保證化約(還原)論或物質論的假設(Barr, 2003)。他認
為物質論並非是科學,其只不過是一種哲學觀點。4簡單來說,許多
關於「突現」的討論關注的是,「對於突現性質的分析與解釋是否可
4 儘管如此,Barr並未否定科學對實在之研究的可能性與貢獻。對於物質論的討論並非本文要處理的對象。在此僅併陳不同的觀點以供參考。
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系統理論觀察 45
能?」以及「如何解釋?」等問題,而這些問題也突顯了不同學科與
不同系統理論觀點彼此間的差異。5
到底什麼是「突現」或其「突現性質」?6一般而言,突現及
其突現性質具有以下特徵:新奇性或新穎性(radical novelty)、連
貫性、屬於整體層次、動態性,以及外顯性(Goldstein, 1999: 50;
Teller, 1992)。除此之外,突現性質尚有不可預測性與不可還原性等
特性(顏澤賢等,2006)。7在 Goldstein與 Sawyer對新突現論(neo-
emergentism)與複雜系統理論的討論中均認為突現現象在早期模控
論、訊息理論,與一般系統論中並未成為研究的焦點,他們認為其原
因在於這些理論將系統視為是簡單、線性且是均衡的。相對於此,在
複雜性理論中,由於強調複雜、非線性與非均衡(動態)的特性,因
而得以解釋突現現象(Goldstein, 1999: 55; Holland, 1998)。8據此,
Sawyer對突現的定義是,「在一個複雜系統之內,較高層次之特質是
從較低層次的組成物中突現出來,且無法被化約為這些較低層次的
5 本文並不會特別處理不同學科或不同系統理論觀點對「突現」及其解釋的
不同看法。然而,必須指出的是,不同學科與系統理論觀點關注或處理的對
象,以及其所持的預設並不一定相同,因此無須在孰優孰劣的問題上打轉。
這也是 Luhmann以差異而非同一(identity)為出發點所提出的社會理論對此之期待。此外,他對「社會」這個概念的想像是:社會是差異與同一的結
合、分化與重構之統一體的結合,或者是,部分與整體的結合。這一點毋寧
是具有啟發性的(Luhmann, 1997)。6 突現(emergence)、突現物(emergent)、突現性質(emergent property)為不同概念,在本文的使用上,突現乃是作為一種現象,而突現性質為突現
現象所產生之突現物所具有的性質。7 在複雜系統研究中,對突現性質的討論又可分為強突現、弱突現與標準突
現等主張。由於篇幅與主題限制,在此無須加以詳述。8 Goldstein指出複雜系統乃是具有以下特徵:非線性、自我組織、非均衡性,以及吸引子(attractors)等(Goldstein, 1999)。
46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組成物」(2005: 36)。然而,與此稍有不同的是,Paul Teller從性質
(property)與關係(relation)的概念出發對突現予以定義,他認為
整體所具有之性質是由關係所構成。就關係而言,假如其所表現出來
的性質無法在該關係中的個別組成元素中獲得解釋,那麼其所表現出
來的性質就是該關係的突現物(Teller, 1992: 139)。換句話說,假如
一整體的性質無法被化約或還原為組成部分的性質,那麼該性質便可
稱之為是一種「突現性質」(1992: 140)。Teller對突現的論述方式不
止於此,他從關係性/非關係性的這組區別出發,對突現性質予以重
新定義:假如一整體的性質無法被化約或還原為組成部分的非關係性
性質,那麼該性質便可稱之為該整體的突現性質(1992: 141)。9換
句話說,這裡所謂的非關係性質指的是不需要或不是透過關係來定義
的性質,或者簡單地說就是,「去脈絡化的」性質,或者「去鑲嵌性
的」性質。相反地,若是可以被化約或還原為組成元素的非關係性性
質,或者去脈絡化的性質,那麼該性質便無法稱之為該整體的突現性
質。Teller對突現的看法在某種程度上與 Luhmann的社會系統理論有
相類似之處。10本文稍後將會對此進行探究。
9 Teller對化約或還原的看法是:明白的可定義性(explicit definability)(Teller, 1992: 141)。就字義上而言,化約或還原指的是能夠被明確定義之意。就整體與其組成部分而言,兩方均具有關係性與非關係性的性質。整體
的非關係性性質就是能夠與其他整體區別開來的性質,此整體所具有的非關
係性性質便是一種突現性質,因為其無法化約或還原為其組成部分的非關係
性性質。10 其他對突現性質較著名的定義尚有 Ackoff與 Fuller:一個系統具有它的組成部分所不具有的性質,每一個系統組成部分具有作為整體系統所不具
有的性質。整體系統的行為不能從它的組成元素或從整體中分離開來的組
成元素的集合之行為中加以預測(Ackoff, 1971; Fuller, 1975;顏澤賢等,2006)。另外可參考,新英格蘭複雜系統研究會(NECSI)(網站:http://necsi.org/guide/concepts/emergence.html)。此外,Ludwig von Bertalanffy的一般系
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系統理論觀察 47
綜上所述,對突現的討論,無論是站在物質論或非物質論的立
場,大多同意整體所具有的突現性質無法被化約或還原至組成元素
的性質,而獲得理解。此外,上述的「關係性」概念在理解突現性
質上獲得很大的支持。這些研究者也試圖在整體與部分、個人與社
會、系統與環境、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之間尋求一種調和的方式。
例如 Jochen Fromm便認為化約論(或還原論)與突現論(或聚現
論)乃是相互補的,他從 Kant在《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中所說的「沒有認知的概念是空泛的,沒有概念的認知則
是盲目的」出發,指出突現論需要背景與基礎,而化約或還原論需
要連結與一致性,「沒有化約論的突現論是模糊且不清楚的,沒有
突現論的化約論則是斷裂且不一致的」(Fromm, 2004: 6)。11 Elder-
Vass在對 Luhmann的批評中指出其並未重視突現的概念,而是關
注於意義與自我指涉的問題。他採取的路徑也是一種「關係性的
突現論」(relational emergentism),而這種關係性的論述也受到 Roy
Bhaskar、Margaret Archer、John Holland、John Searle、Mario Bunge
等人的青睞(Elder-Vass, 2007: 412-413)。他對突現的說明是:假如
組成部分不是構成如此之整體,那麼該整體的性質不會為組成部分
所擁有(2007: 415)。此外,他認為突現性質能夠透過「因果機制」
(causal mechanisms)來解釋,這些「因果機制」指的是:組成部分
彼此之間的互動過程,這些互動過程只會出現在當這些組成部分以特
定的方式予以組織起來,並將其建構為擁有突現性質的整體時。換句
統理論(GST)中對突現的論述也是採取偏向整體性的觀點。由於本文並不處理有關突現定義的問題,僅舉例說明複雜性系統研究中對突現的一般性表
述。11 另外可參考 Niels Henrik Gregersen(2006)。
48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話說,這是一種關係性的論述。互動過程的出現與組成部分構成整體
的組織方式之間是一種相對性的關係。
本文認為「關係性」的概念在 Luhmann的社會理論中也以某種
形式而存在,但在關於「層次的理解」上則有所不同。此外,除了指
出因果關係並非是 Luhmann探究的可能解釋之外,前述觀點並未脫
離其貢獻。從還原(化約)與整體論的爭論到關係性突現論的轉向,
在複雜系統理論的發展中獲得更豐富的成果。如馬克斯主義唯物論
者也同樣以此方式來理解歷史。例如 Alex Callinicos在《創造歷史》
一書對突現概念與結構、行動、整體與個體之關係進行了討論。他
從對馬克斯主義的分析指出,基本上「社會結構無法化約至個人」。
他以「行動者透過行動來行使力量」的簡單看法出發,進一步指出
這些力量包括了個人所具有的,以及受到結構所決定的兩種類型。
換句話說,「這些力量取決於行動者在主要的社會結構中所佔據的位
置」(Callinicos著,萬毓澤譯,2007,頁 15)。就此而言,他也是以
「關係」的角度來重新定義結構與行動者之間的關連性,從而避免
結構決定論或者是強調行動者力量(agency)的單一且不足之論述。
Callinicos解決此困境的方式是,「社會結構連結的並非是有名有姓的
個人,而是任何一個佔據了由社會關係所指定位置的人,換句話說就
是在社會角色或在關係中扮演某些角色的個人」(2007,頁 21)。然
而,雖然他對突現的看法或許也類似於 Luhmann的觀點,但其物質
論的傾向卻是為 Luhmann所保留的。基本上,Callinicos認為社會結
構是關係式的:它們是「那些內部的、必然的關係,它們必然與物質
資源有關,不論是物理的或是人類的,而且會生產出關係本身特有的
力量」(2007,頁 28-29)。12
12 然而,Callinicos也指出,有越來越多人對歷史唯物論與自然選擇演化論
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系統理論觀察 49
Mario Bunge在對政治本體論的討論中也採取較為調和的看法,
認為最好的社會科學應該是系統主義(systemism),而非個體主義或
整體主義(Bunge, 2009: 3)。他對實在論與科學主義的擁護立場致使
拒絕 Luhmann將溝通而非個人視為社會系統的根本元素之作法。13他
並未將 Luhmann視為是方法論或本體論式的個體主義,而是更接近
他所謂的「本體論式的整體主義」(ontological holism)。此外,他認
為此種論述所可能導致之結果便是將諸如法律、科學等制度視為是具
有行為能力的實體(或系統),從而視之為一個空殼:激進的整體論
等於是虛無主義(Bunge, 2003: 87)。14就此而言,本文除了一方面
之間可能具有的親近性感興趣。這中間當然可以補充一點論述,從達爾文演
化論到社會達爾文主義,或者從生物演化到社會演化的論述,或許可提供作
為歷史唯物論對結構之看法的進一步表述。13 這個差異也是 Sawyer所區分的 Luhmann社會理論與第三波系統理論發展的重要差異(2005)。14 Mario Bunge將「社會」定義為諸多系統中的一個系統,例如家庭、公司、學校、國家等。「社會學」則是對所有種類與規模的社會系統進行科
學性與同時性的(synchronic)研究,尤其是對它們的結構與變遷之研究(Bunge, 1998)。Bunge視「結構」為一組關係,尤其是連結或力量,一種在系統組成元素之間,以及在這些系統組成元素與環境中之項目彼此間的關
係。據此,他認為「結構」乃與「組織」、「構造」(architecture)是同義的。他認為社會系統可以被分析為下列四個部分:組成或成員(Composition or membership)、環境或脈絡(Environment or context)、結構或關係(Structure or relationships),以及機制或使其運作之過程(Mechanism or processes)。這就是其所謂的 CESM觀點(Bunge, 2003: 61-62)。在其 CESM模型中,將個人視為社會的組成單元。因此,對他而言,要理解系統的突現與其突現性
質,便可以這四個部分作為出發點,進行科學式的分析與探究。對於虛無主
義的批評,Luhmann曾經提出一些論述。他從觀察者出發,「對觀察進行觀察能夠特別注意到被觀察的觀察者使用了何種區別。它能夠問自己,觀察者
使用區別能夠看到什麼,以及不能看到什麼。對觀察進行觀察能夠對其自
身使用區別的盲點感到興趣」。對此的思考並不必然會導致虛無主義,因為
「這樣的結論只有在使用存有(being)與非存有(non-being)的這個區別的
50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對此論點持保留態度之外,另一方面要指出的是,Luhmann的理論
立場或許也無法完全地符應於 Bunge所謂的本體論式的整體主義。
若是僅從「社會是由個人所組成」之觀點而將 Luhmann的理論視為
一種虛無主義,或許是誤解了該理論的重要內涵。Luhmann並未忽
略個人在社會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只是,這個重要性並非是以「社會
乃由個人所組成」這樣的觀點來表達而已。這一點在理解其理論上
毋寧是重要的。至少,Luhmann可能不會同意這樣的說法,認為個
人在社會系統中不再重要或者不再佔有重要位置(例如,Luhmann,
1984/1995: 212)。相反地,他從觀察的運作出發而指出,無論是系統
或個人,在作為觀察者系統進行「認知」運作的層次上並無二致。15
例如:
當生命系統(細胞、免疫系統、大腦等)作出區別並對其自身之
區別作出反應時,觀察就發生了。當透過意識處理過的思想固著
於並區別出某物時,觀察就出現了。當一個可溝通、可整合的對
所傳遞之訊息的理解─無論是語言或非語言的─獲得實現之
時,觀察也就出現了(無論何種心理過程可能出現於參與個體的
心智之中)。(Luhmann, 2002: 147)
綜上所述,本文一方面主張 Luhmann對突現的討論並非是如此貧
乏。另一方面,也嘗試說明其社會系統理論對於突現性質的可能理
解,以及對當代突現論者所持觀點的回應。本文認為對突現的討論
本體論式的參照架構中才會有意義」(Luhmann, 1998/1992: 46)。15 參考 Gregory Bateson(2002),從器官或有機體的覺察出發,Luhmann在發展其社會系統理論時採取了 Bateson的觀察與區別的概念。
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系統理論觀察 51
有以下幾個假定:第一,突現必須且只能在「操作上封閉」(operative
closure)的系統運作中出現。第二,這個所謂「操作上封閉」指的是
系統與環境的這組區別。第三,除了系統與環境之區別外,在不同層
次上考慮另外兩個區別,亦即元素與關係(element/relation)、媒介與
形式(media/form)之區別。第四,突現現象必須被置於系統的自我
指涉運作中始能獲得理解。第五,包括系統自身,也是系統的自我生
產運作出來的突現物。關於這幾個假定將會持續地在本文中予以分
析、說明。
二、Luhmann社會系統理論與突現
若要理解 Luhmann對突現的論述或觀點為何,及他的社會系統
理論是否給出了相關的適切解釋等問題,必須要從他對社會的理論
(the theory of society)與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的討論出發。簡
單地說,其目的在於提出一個有關社會的理論,而非社會理論。他認
為社會理論所調查的對象乃是一個正在演化的系統,而關於社會的理
論則必須是具有反身性的,亦即,該理論必須也要反省其自身的歷史
突現(historical emergence),以及其作為一個理論的地位(Luhmann,
1982a: 255)。當 Luhmann試圖要建構一個關於社會的理論時,他提
出了三個可供汲取的面向:系統理論、演化理論與溝通理論。從對這
些理論的分析出發,他指出一個關於社會的理論應該關注的是:社
會演化的理論與系統分化的理論(1982a: 192)。在他的理論架構中進
一步區分了三個不同類型的社會系統:互動系統、組織系統與社會系
52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統(societal system)。16以此作為出發點,Luhmann便是從互動理論
與社會的理論來討論個體與整體的問題,而非僅以其中之一來理解兩
者之關係。一方面,他認為互動理論無法處理集合現象,也無法處理
突現結構的問題。另一方面,他指出社會的理論在處理「向下因果作
用」(downward causation)的問題上出現了困境(Luhmann, 1981)。17
這兩種理論所呈現的正是部分與整體、微觀與鉅觀的主要爭論。然
而,對他而言,問題不在於區別不同層次的實在,而是在於下列事
實:「一旦此區別(總體層次的實在與微觀層次的實在之區別)被使
用時,該區別便會在從這些層次的其中一個來捕捉整體的企圖中被棄
絕」(1981: 235)。因此,他認為社會系統理論或許能夠對此區別提供
更為精確的認識。互動系統與社會系統之間的關係構成了 Luhmann
對突現的看法。這是一種很精緻但要求高度抽象化的論述。例如在互
動的層次,社會系統的出現是因為溝通必須要進行選擇,且他人的
出現(co-presence)使得溝通變成是無法避免的;而在社會的層次,
所有的溝通均必須假定正在參與溝通的人也在其他的社會關係中進
行溝通,如此一來,社會系統才得以出現。據此,Luhmann宣稱,
「社會,作為所有在溝通上可獲得之行動與經驗的整體(totality),
其本身就是一個社會系統。它也是奠基於選擇性建構的結構(互動系
統),且奠基於排除異於系統之環境的界線之上(社會系統)」(1981:
16 Luhmann所區分的這三種系統均是屬於社會系統:互動的社會系統、組織的社會系統,以及社會作為社會系統。這與以往社會學中將個人的互動視為
是在社會中所進行的看法是不同層次。對 Luhmann而言,較為適當的提問毋寧是:在社會中,互動系統是如何與心理系統進行耦合(或「互動」)?17 對突現性質的理解同時包含向上與向下因果作用。前者指的是,低層次元
素在形成高層次系統之後,對高層次系統的運作仍具有決定作用。後者則是
指高層次系統對低層次的組成元素仍具有支配、控制與影響的作用(顏澤賢
等,2006)。
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系統理論觀察 53
235)。18這一點倒是與 Bunge所主張的路徑相似,亦即,能夠作為真
正的社會科學用以理解社會實在的既非是個體主義,也非整體主義,
而是系統主義(systemism)(Bunge, 2009)。
從互動與社會的討論出發,這個區別必須假定另一個更為抽象
的脈絡或理論層次,Luhmann稱之為關於社會系統的一般性理論(a
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systems)(1981)。這個理論便是要處理突現的
「社會秩序」之問題。根據 Luhmann,這個社會系統的一般性理論
如下:
在每一個分析中,分析者(觀察者)必須要指出系統指涉物
(system referents),分析者將會使用這些系統指涉物來完成其
分析。這意謂的是,分析者(觀察者)必須要選擇何者將會是系
統,何者是環境。就此而言,這個選擇意謂著是放棄普遍性的宣
稱。只有以此方式,分析才能夠由系統與環境的差異來指引、功
能分析才能夠具體化、我們才能夠賦予下列一般性宣稱實質性的
意涵:「系統化約其環境的複雜性」。(Luhmann, 1981: 236)
對他來說,無論是使用互動理論或社會理論來進行研究所指出的不過
是:將這些理論所希望研究的對象視為一個具體的系統。然而,在更
為抽象的關於社會系統的一般性理論之層次,情況便不必然是如此。
在這兩個例子中(互動理論與社會理論),社會系統的一般性理論將
能夠引導其各自的分析,因為這些理論均是透過使用系統與環境的
這組差異而得以運作。就此而言,我們便可根據這組差異來區分鉅
觀研究與微觀研究(1981: 236-237)。因此,就社會系統的一般性理
18 對互動系統的突現性質之討論,可見 Stephan Fuchs(1988; 1989)。
54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論而言,分析者(觀察者)是有可能同時考慮幾個不同的參照系統
(reference systems)。對 Luhmann而言,微觀觀點與鉅觀觀點、互動
分析與社會分析之結合的可能性就在於,分析者(觀察者)必須要能
夠持續地記得兩件事,第一,「在系統形成之層次中的差異」;第二,
「以該差異為基礎並試圖釐清:作為一個在其環境中的互動系統所具
有的可能性,如何得以限制作為社會之系統所具有的可能性,以及反
之,作為一個在其環境中的社會系統所具有的可能性,如何得以限制
作為互動系統所具有的可能性」(1981: 237)。這兩件事意謂著是突現
的社會秩序之分析,首先必須要從系統與環境的這組差異出發,再者
則是探討「系統在自身之中再製這組差異的運作是如何得以實現」的
這個問題。19
19 對於秩序或失序(disorder)的觀察必須要從一組差異或區別出發。在對全球化與世界社會的討論中,Luhmann指出 20世紀末,我們的問題乃是要去定義差異(1997)。唯有如此,觀察才是有可能的。對於道德判斷與倫理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須要先「做出一個區別」,無論是好/壞、善/
惡、適當/不適當、合法/不合法、道德/不道德、科學/不科學、客觀/
不客觀、物質/非物質、本體建構/認識建構、含括/排除等,而作出區別
意謂著要進行選擇,選擇必然要涉及價值的問題(Luhmann, 1986b: 133)。然而,弔詭也正是出現於每一個作出區別的當下。Garfinkel的破壞性實驗論述在某種程度上也相當正確地指出,無論是一般人或是專家學者,均是將此
運作當下才會出現的弔詭「視為理所當然」。Bourdieu所提出的「habitus」概念也有類似的論述。他認為在兩個具有相同 habitus之行動者或團體之間的互動中,其各自之行動就像是以關連於具有相同 habitus之對方的反應而獲得組織,以致於其均客觀地暗示著這些反應所導致的對下一個反應之期
待(Bourdieu, 2003/1977: 73)。據此,habitus便成為引導、繼續或修正行動者彼此間之行動與回應的基礎。然而,行動者(包括對方)均必須在運
作上(當下)將己身所具有之 habitus視為理所當然,或者是說,透過這個 habitus所作出的區別便成為行動與回應的那隻「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又或者如 von Foerster(1984)所謂的「非恆定的機器」(non-trivial machines)般的運作,其無法計算自身的狀態。
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系統理論觀察 55
上述有關社會系統的一般性理論轉變了傳統對整體與個體之關
係的論述。Luhmann認為傳統的想法是,複雜系統(主要是有機體
系統)作為「整體」,是由「部分」所構成。其基本概念是:整體的
「秩序」解釋了組成部分自身從未能擁有的特質。然而,他進一步指
出系統理論的發展則是透過對「環境」概念的明確指涉而放棄了上述
觀點(1984/1995: 212)。他認為這個環境的概念不是要說明在系統之
外存在著某物,而毋寧是:
系統的結構與過程只有在關連於環境時才是可能的,並且這些結
構與過程只有在考量此關係時才能被理解。只有指涉於環境,在
任何既有系統中才有可能區別「元素」與「元素之間的關係」。
因此,系統就是其與其環境的關係,或者系統就是系統與環境的
這個差異(1982a: 257)。
這個「系統即差異」(system is difference)的論述時常被使用
Luhmann社會理論的研究者誤解,其重要性也多被低估。此外,這
組差異經常被認為是與整體/部分之區別是相互排斥的,因而導致有
研究者認為 Luhmann得以忽略有關於「部分」的影響之問題(Elder-
Vass, 2007; Wan, 2009)。20這在本文稍後對媒介/形式之差異的探究
或可提供更清楚的說明。就目前而言,雖然 Luhmann是以系統/環
20 Luhmann將 Hegel的整體論哲學抽離出所謂「唯心」的成分,透過系統與環境的差異作為系統形成的主要運作內容,進一步論述到這個差異事實上也
僅能在系統自身中獲得「實現」。據此,對 Hegel而言的部分與部分彼此間的聯繫作為整體的內在特性之觀點,在 Luhmann的論述中便獲得了修正。其結果是,對整體與部分之關係的傳統表述便轉向可由系統與環境的這組區別來
重構之。
56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境之區別來取代整體與部分之區別,但這樣的作法僅可視之為一種知
識論上的轉向,而非具有本體論上的內涵。因此,傳統上的整體與部
分之差異的論述被轉化為關於系統分化(system differentiation)的理
論。他認為系統分化不過是:「在系統中重複系統與環境的差異」:透
過這樣的方式,該系統將自身作為環境以形成自己的次系統,並在這
些次系統的層次上,透過更為嚴謹地篩選一個無法受到控制的環境,
而獲得較高的非必然性(improbability)(1984/1995: 7, 18)。21據此,
一個分化的系統不再是僅由某個數量的組成部分,以及其彼此間之關
係所構成。相反地:
其是由一個相對而言相當大數量的在操作上可使用的系統/環境
差異(differences,複數)所構成,其中的每一個系統/環境差
異均將整體系統重構為次系統與環境(次系統自身的環境,同
時也指的是整體系統作為其環境)的統一體(unity)(1984/1995:
7)。每一個次系統與(系統而非次系統的)內部環境之差異就是
該系統整體(the entire system)。據此,系統分化就是一個增加
複雜性的過程,這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何者能夠被觀察為
整個系統的統一體(1984/1995: 18)。22
21 此種「在系統中重複系統與環境之區別」並以此作為對突現之理解的觀
點在數學上也獲得說明。Bird(2003)認為許多混沌系統與自組織系統乃是「重複」(iteration)過程的產物,甚至包括有機體,亦可視之為由計算過程所構成的。儘管此種將萬物化約為計算之結果的作法並未受到本文所支持,
但其主張「決定論的不可預測性」(unpredictability of determinism)而非過去牛頓世界觀所認為的「決定論是可預測的」看法,仍然具有參考價值。22 Luhmann認為有多少功能系統就對應多少個環境。例如經濟系統及其環境、政治系統及其環境、法律系統及其環境等。這些環境彼此間並非是可等
同的。此外,每一個次系統均建構自身的環境。系統的環境在本質上是內在
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系統理論觀察 57
這一點也正是許多研究者誤解 Luhmann的社會系統理論之開端。或
者,這些研究者並未注意到此系統形成的重要性。Luhmann認為這
樣的作法一方面可處理構成整體的組成部分之同質性的問題。23因
此,就「社會是由個人所組成」的觀點而言,這些「個人」是否具
有同質性的問題便無法透過之前對整體/部分之論述而獲得解決。24
此外,他也指出傳統的整體與部分之區別,對於「在次系統的分化
中同時使用多種觀點的可能性之理解」也無法獲得令人滿意的解答
(1984/1995: 8)。在這裡,我們並不細究其是否成功地解決上述問
題。就本文旨趣而言,Luhmann至少提供了不同於傳統上對系統的
看法,而這樣的嘗試在目前對複雜系統或社會理論的研究中獲得許多
證明(例如 Urry, 2003; Castells, 2000; Rosa, 2009等)。
在提出其觀點之前,Luhmann指出至少有兩種對系統的看法,
其一為傳統上主張「整體大於部分之和」。25其二則可追溯到中世紀
晚期,傾向於將系統建構為是一個「在邏輯上具有一致性的關係網
絡」。然而,他認為就社會學的目的而言,這兩種方法或許都是不充
足的:第一種不夠清楚;第二種則是太過於清楚,以致「無法應用於
於該系統的,但是系統視其為外在於系統自身,且界定了何謂系統與何謂環
境(Luhmann, 1988; King and Thornhill, 2003: 283)。23 Luhmann給的例子是,構成房子的組成部分乃是房間,而非磚塊;構成書本的組成部分是章節,而非字母。然而,將個別的人類視為是構成社會的組
成部分這樣的觀點,對 Luhmann而言則缺乏在理論上對這些個人也是具有同質性的證明。24 John Urry(2003)也指出「在社會科學中,理性行動論者支持將社會模式化約為許多個人式的理性、線性行動之模式。這樣的作法似乎是錯誤的。因
為其假定了一個清楚的、不可化約的『個人』,這些個人的理性行動便能夠
解釋這些社會現象」(2003: 77; Goldthrope, 2000)。25 此觀點可上溯至 Plato(Theaetetus 203 E; cf. Laws 903 B-C),以及斯多噶物質論者(Stoic materialists)的論述(Gregersen, 2006)。
58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高度複雜、自我建構的具有意義之互動的脈絡」(1982a: 190)。他對
這兩種觀點的不足之處可簡述如下:這兩種方式所關注的對象均是系
統的內部關係。近年來系統理論的發展則關注的是系統的環境,這些
發展主要可簡述為:系統就是世界的複雜性之化約。因此,系統必須
要不斷地維持與其環境的不確定關係,而該環境本身卻非以相類似的
方式而被化約的(1982a: 192)。因此,Luhmann對系統的定義是從
差異出發,從系統與環境的這組差異出發,而非從整體與部分之關
係出發。他說,「系統就是系統與環境的這個差異」(2006: 38; 1982a:
257)。或者,系統的形式就是系統與環境的這個差異(Luhmann,
1993/2002: 106)。26 Luhmann從 Saussure對語言的分析指出,語言
中所使用的差異是能夠與其指涉的問題分離開來的,換句話說,就
是與對方所想要表達的東西分離開來。但無論如何,總有一個差異
是被假定的(2006: 40)。此外,Luhmann也從 Bateson的訊息理論
(Bateson, 1972)出發,進一步分析此差異(稍後在社會系統中便
是「溝通」)如何能夠作為系統的組成元素。然而,Luhmann對「差
異之統一」(unity of difference)的論述來自於其對 Spencer-Brown與
Kauffman的討論。他指出我們在使用「區別符號」的時候必須將此
區別(由兩個部分)所構成的「符號」當作一個「統一體」來對待。
因此,我們是從一個區別出發,亦即構成上述符號的兩個部分。然
而,因為該區別的結果必須作為一個統一體才具有功能,該區別既無
法被指出來,也無以名之:它就只是在那裡(Luhmann, 2006: 43)。
26 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代由美籍數學家Mandelbrot提出的分形理論(Fractal Theory)與 Luhmann對系統與環境之論述的看法相類似。1920年代的「不確定性原理」與其後的分形幾何學與量子力學的發展等,均同樣
說明了觀測者與被觀測者之間存在一種「不可消除的相互作用」之關係。
Luhmann的「系統即差異」在某種程度上也符應於此觀點。
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系統理論觀察 59
這就是 Luhmann所謂的「弔詭」(paradox)。因此,Spencer-Brown會
說,「做出一個區別」(Draw a distinction)(1979/1969: 3)。除非做出
一個區別,否則什麼事也不會發生,他將此區別所標示的界線稱之為
形式(form)。27
在進入媒介與形式的討論之前,我們有必要對上述的形式概念
稍作說明。從 Spencer-Brown的「形式邏輯」出發,我們知道一個
「形式」具有或區別了兩個面向。藉由這個區別可以觀察到兩個「空
間」,而這個區別(形式)由這兩個空間之間的界線所連結起來。雖
然這兩個空間藉由中間的界線被區分開來,但在運作或觀察的層次
上,只能有一個空間被標示出來。例如在決定某一個行為是否為合
法的觀察之運作的當下,無論如何只能有一邊被標示出來,要不就
是合法,要不就是非法。就此而言,透過區別所標示出來的對象物
是具有脈絡性的,而那個「未被標示出來的空間」則是不具有脈絡
性的。Luhmann指出,「形式」就是關於兩面的事物,亦即系統與環
境。換句話說,被標示為系統的這一邊必然是具有脈絡性的,而被
標示為環境的(unmarked)則是無脈絡性的。如果我們用秩序與擾
素(noise)來說明,那麼系統便是前者,而環境則是後者,無論這
個秩序是無序之有序(disordered order)還是有序之無序(ordered
disorder)。此外,秩序與擾素之間的關係也不是直接的,突現現象即
為一例。我們或可以形式與媒介的這組區別來說明系統與環境的差
異:媒介乃是形式的環境,形式是由媒介彼此間較緊密的耦合而構
成。媒介就如同環境或環境中的「擾素」,在擾素彼此間存在的僅是
鬆散耦合的狀態,當其以某種指涉於「系統」的方式予以緊密關連
27 就此而言,「創造」只不過就是「做出一個區別」。更有甚者,Luhmann(1993/2002)指出,在世界中沒有任何事物是對應於我們所使用之區別的。
60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時,便會形成某種以「議題」或關連性較緊密的內容而出現的形式。
然而,這不是說形式便得以被化約為個別的媒介。形式與媒介仍然
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元素,就如同系統與環境、整體與個體之間的關
係一般。
從「系統即差異」的命題出發,Luhmann認為傳統上的「整體
大於部分的總和」的說法或許是有問題的,其毋寧是「整體小於部分
之和」(Luhmann, 1982a: 238)。這樣的看法似乎否定了系統具有突現
性質的可能性。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首先,我們可以先這麼說,
「總體大於部分之和」的論述仍是易於流入化約論邏輯。儘管此概念
是試圖用作為一種反化約論述的隱喻,但其進一步以不同層次之間的
向上與向下因果作用來解釋整體與部分、社會與個人之關係時,卻仍
無法跳脫化約論式的邏輯,或者是物質論觀點,無論其試圖化約為組
成部分或者是組成部分之間的關係或關連性網絡。因此,這是一種
「收斂式的」論述,具有「約束」的性質。28例如,社會是由個人所
組成的,因此,一方面社會對個人具有約束力,另一方面,個人或個
人的集合對社會也具有影響力。無論從哪一個方向來看,這都是一種
收斂式而非擴散式的運作觀點。據此,整體與伴隨之突現性質在某種
程度上是會影響或構成對其組成部分所具有之性質的解釋,從而約束
了個體本身所具有的自主性與自我指涉之運作。29例如,社會的「秩
28 關於此論述,可參考顏澤賢等(2006)合著之《系統科學導論─複雜
性探索》,第四章。作者認為整體與部分之間的關係或許不是「整體大於部
分之和」,而應表述為「整體不等於部分之和」。這是其所謂的系統整體性原
理。29 將構成整體的個體想像為具有自我指涉與自我生產之運作的單元確實是理
解 Luhmann的「系統即差異」之門檻。包括心理系統與社會系統之「互動」均必須要在此背景之下才能獲得適當理解。另外可參考 Luhmann(1986a: 172-192; 2009/2002: 143-156)。
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系統理論觀察 61
序性」被用作為約束個人行動的解釋,從而主張個人也必須服從或遵
照社會的指示,或經由「社會化」而取得一種「秩序性」的特質。相
反地,「整體小於部分之和」或者「部分之和大於整體」的觀點則是
具有一種「創新」性質。其提供了系統動態的特性。尤其是在以功能
分化為主的現代社會,某一種功能系統已然無法為所有的系統/環境
關係提供一套整合公式,或者是提供最小限度的倫理,以進行社會的
整合。然而,正是因為如此,當這些功能次系統透過提高己身之複雜
性而得以化約環境的複雜性之時,其也同時增加了環境的複雜性,從
而提供了「創新」或「其他可能性」的機會(Hornung, 2006: 200)。
這原因便在於:整體小於其部分之和(Luhmann, 1982a: 238)。換句
話說,社會的複雜性只能夠透過同時考量數個系統/環境指涉之模型
(亦即,數個功能分化的次系統),才能夠獲得適當的說明。30據此,
「系統即差異」指出的是,系統就是由無數個「差異」所構成,亦
即,其元素所展開的系統與環境之差異的弔詭之再進入。甚至是,系
統本身就是這個差異,系統與環境的差異(或區別)。我們可以將這
個差異或區別類比為是物理學上所謂的「吸引子」(attractor),最簡
單系統的吸引子可能是一個「點」,而較為複雜的系統,其吸引子可
能是一個空間。31就物理學與數學而言,吸引子有其界線,但這個界
30 Jantsch(1979)對自組織系統的分析調和了宏觀與微觀角度,或者整體論與還原論(個體主義)的看法,並以此說明了突現與演化之間的關係。系統
一方面透過自組織與內部分化的過程增加複雜性,這是一種向下因果作用的
程序,另一方面,在系統中的組成元素同樣也是透過自組織形式進行合成與
整合,而突現出複雜的系統,這是所謂向上因果作用的運作。據此,他認為
宏觀與微觀演化及其層次上的突現並非相互衝突,而是緊密聯繫且相互依存
的關係。這樣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也呼應了 Luhmann的社會系統理論對突現的看法。31 Luhmann在對媒介與形式的討論中也提及這個類比。藝術的媒介存在於每
62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線的運作與維持是模糊的,換句話說,吸引子本身具有不穩定性、動
態性的特徵。構成系統的無數個差異也具有同樣的特性,並且實際上
這些差異也都是同一個差異。
對於突現性質的討論,再帶入 Luhmann對社會系統理論的討論
之後,我們或可說,整體所具有的性質要能夠被「視為」是突現性
質,則該性質在某種程度上必須變成整體自我描述的一部分或全部。
此外,該性質之所以有機會或有潛力被視為「突現性質」,其中一個
重要關鍵乃是,具有該突現性質的整體必須要能夠成為其他整體(系
統或觀察者)的環境,並成為其他整體(系統,或觀察者)論題化的
對象。例如宗教系統以內在性/超越性這組區別作為其觀察的運作,
製造出「宗教溝通」(溝通就是事件、區別、弔詭等)。這個宗教溝通
在某種程度上便是宗教系統的突現性質。然而,宗教系統所製造、自
我生產出來的溝通,之所以能夠被辨認為是「宗教」溝通,則在於其
能夠成為其他功能次系統論題化或溝通的對象。換句話說,政治系統
將宗教系統製造出來的溝通,經過系統自身的二次編碼運作之後,而
得以將之溝通為「宗教溝通」。因而,這在政治系統內便可被其視為
一種與自身所製造出來的「政治溝通」有所不同且是可作為來自宗教
系統(政治系統的環境)的溝通(突現性質)。這是現代社會以功能
分化為主要運作原則的結果之一。以下便從 Luhmann所提出的另一
組「媒介/形式」之區別,進一步說明此論點。
一件藝術作品之中,然而,它是不可見的,因為它只會在另外的一邊運作著
─那個沒有被標示出來的那一邊─作為一種吸引子(attractor)以提供進一步的觀察(2000/1995: 118-119)。
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系統理論觀察 63
三、從整體/部分、系統/環境,到形式/媒介:如何理解突現?
從 Spencer-Brown的形式理論,Luhmann討論了形式與媒介的這
組區別,並以之作為描述系統形成的社會演化發展。此外,在對藝術
系統作為自我指涉系統及其自主性的分析中,媒介/形式之區別構成
了理解系統突現性質的重要「媒介」:
媒介/形式之區別的獨特性指出了這些形式之特徵的突現。⋯⋯
形式總是較媒介更為有力且更為肯定的。媒介提供的不是抗
拒⋯⋯媒介限制人們能夠以其來完成之事物。媒介是由元素所構
成,因此是非任意性的(Luhmann, 2000/1995: 105)。
對 Luhmann而言,媒介不必然要具有物質性(或等同於物質),因
為與物質不同的是,媒介是能夠被高度地分解的(Luhmann, 1982b:
215)。甚至是在抽象的層次上,我們不需要想像有一種物質性媒介
的存在。媒介與形式的關係是相對性的,其僅具有相對上的差異。
然而,這兩者均必須是自我指涉的,其間之差異是透過演化而改變
(1982b: 216)。媒介在時間的面向上也是由元素或事件(行動)所組
成,但是這些元素彼此間僅是鬆散地連結著。這些元素或事件實際上
是彼此相互獨立的。相反地,形式則是透過元素(事件、媒介)彼此
之間較為緊密的耦合關係,亦即,透過媒介所提供的可能性且從中進
行的選擇所構成。32簡單地說,構成媒介之元素彼此間僅是鬆散連結
32 這與 Smith區別社會系統中的「強互動」(strong interactions)與「弱互動」(weak interactions)有類似之處。然而,他的研究導向的是另一個結果。
64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著,因此容易分離。Luhmann認為這正解釋了為何媒介是不容易被覺
察到的,而只有透過媒介元素彼此間的緊密耦合所形成的「形式」才
會被覺察到。換句話說,相對於媒介構成的形式而言,因為媒介本身
太過分散,以致於我們僅關注得到「形式」,而不會注意到構成該形
式的媒介。
Luhmann認為媒介與形式之間是相對性的關係,但仍可視之為
一組差異:既不存在一種沒有形式的媒介,也不存在一種沒有媒介的
形式。對他而言,這是一個關於元素間相互獨立與元素間相互依賴
之間的差異之問題(1982b: 217)。媒介提供了選擇性與可能性,「形
式」則是化約這些由媒介提供的選擇性,透過此運作而使媒介提供的
選擇性受到控制並獲得組織,因而得以形成「形式」。在媒介與形式
的關係中,「形式」毋寧是較為嚴謹的。由於「形式」的嚴謹性導致
其必須不斷地透過宣稱其具有嚴謹性而與媒介區別開來。此種宣稱自
身具有不同於媒介的嚴謹性之運作必須不斷地在「形式」自身之中再
製或重複。換句話說,「形式」本身的出現便已經是包含了形式與媒
他指出強互動的出現是因為在社會系統出現了較為強大的力量而導致其非線
性狀態,而弱互動則是出現在複雜組織中透過制度化而減少互動的狀態。
後者的發展被認為是一種有利於「理性」的狀態(1992; Smith and Stevens, 1996: 150)。若是本文稍後對藝術作為社會系統的討論為例,事實上,藝術作品被視為「藝術作品」之形式而相對於構成其之媒介時,我們已經觀察到
的是一種對於「藝術」的驚奇感覺,這種驚奇感覺就其作為形式的突現性質
而言,確實是可視之為非線性、不穩定的。相反地,若是當該藝術作品不被
視為形式時,換句話說就是成為媒介,其相對而言確實是較為理性的。例如
我們對構成木雕作品的木頭所持的態度多半是較為理性的。由於 Smith以此來回應 Luhmann對自我生產之社會系統的論述,因此也必須在此命題之下檢視其對 Luhmann社會理論的認識。至少就其分析而言,僅指出 Luhmann對自我組織的看法過於複雜以致於無法在該文中處理。這樣的論述是否足以用
來否定 Luhmann社會理論的貢獻,或許是需要深思的。
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系統理論觀察 65
介的這組區別。否則,該形式將無法宣稱其有別於媒介。因此,形式
必須在自身之中製造較嚴謹的元素連結關係,以使其持續進入形式的
這一邊,假如該形式認為自身是較不嚴謹的元素連結,那麼就有可能
會變成為媒介而非形式了。Luhmann對藝術作為社會系統的分析提供
了理解媒介與形式、系統與環境、整體與個體之關係的清晰途徑。首
先,藝術(art)既是形式也是媒介,當然這也是就形式與媒介的相
對性關係而言是如此。然而,問題是,藝術本身如何是一個媒介,一
個溝通媒介? Luhmann指出,「形式」只不過是一種「較高的媒介」
(higher medium),相對於構成該形式的媒介而言,其是一種「二度
媒介」(a second-degree medium),同樣使用著媒介/形式的這個差異
(1982b: 218)。33例如就噪音而言,相對於寧靜而成為受到注意的形
式。然而,就音樂而言,其則是應用了第二個差異,亦即媒介與形
式之差異,而將噪音視為媒介,音樂則是形式。據此,Luhmann指
出,「藝術建立了自身的含括規則(rules of inclusion),這些規則是藉
由媒介與形式之區別,(將此區別)作為媒介來提供」(1982b: 219)。
換句話說,藝術作為自我生產與自我指涉之系統的內涵即在於此,那
些能夠被視為「藝術作品」而非僅是「產物」的溝通,必須是在藝術
系統中重複或再製「媒介/形式」的這組區別,而獲得的自我指涉
運作之結果。此外,由於媒介的特性導致其結合的可能性是無窮盡
的。換句話說,藝術「形式」所具有的不穩定與動態性,或者是「創
新」、「驚奇」的感受均與此有關。34
33 Luhmann舉的例子有音樂、視覺藝術、書寫藝術品、科技與自然、社會學與社會等。34 葉啟政在談迸生(突現)與驚奇之間的關係時指出,「迸生」內涵的心理
特徵,他認為這就是 Vico、Durkheim、Berger和 Berger所謂的驚奇感覺。而在驚奇之後,便出現的所謂「例行化」(2008,頁 16)。「迸生」現象(例
66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從形式的角度觀之,「形式」也創造出自身的藝術性媒介,藉著
使用這些媒介來達成「形式」表現的目的(Luhmann, 1982b: 220)。
然而,Luhmann指出社會演化固然會增加系統的複雜性,同時也增
加其「分解與重新組織的能力」,換句話說,也就是增加「新媒介」
的演化與發展。但這不會導向一種無窮盡的延伸。社會作為媒介
(相對於社會學作為形式而言),媒介的發展仍有其限制,這些限制
在於我們無論如何都必須要使用知覺媒介(1982b: 222)。35然而,
Luhmann指出藝術作為社會系統的說法要能夠成立,則必須將媒介
如社會)乃是具有一種能夠激發驚奇感覺的特質。諸如Weber所論述的神才性(charima)帶出了驚奇經驗,而此經驗正是創造文明(社會)的起源因子。亦即,「文明(因而社會)乃起源於例外而非凡的驚奇經驗」(2008,頁27)。在驚奇經驗之後而來的例行化,是無法持久的。這可與目前不斷追求創新、變化的訴求相連結。一旦開始了例行化之後,便注定了將會有下一波
驚奇經驗的可能性。而此可能性則是必須在「迸生」現象或特質中尋求。假
如找不到的話,則會自行創造出一個來。例如以革命或社會運動的方式來對
抗例行化的有效性之衰退。例行化的科層制度之運作與所產生之行動會隨著
時間而降低有效性或正當性,因而必須以其他方式來製造驚奇經驗,以之作
為提高有效性與正當性的基礎。據此,「迸生」可視之為一種跳躍,是一種
在不同層次之間的跳躍,是從個體特質到整體特質的一種跳躍,並且會反過
來對那些個體產生影響。我們必須將「時間」面向納入對此一過程的考量。
就社會系統理論的語言來說,「迸生」是一種不間斷、持續地「區別的再進
入」之暫時性產物。當系統將一組差異不斷地再引入自身之中時,其再引入
的時間點是不斷改變的,也不會與之前使用該區別的時間點相同。這是一種
動態性。系統的「穩定」必須要在此動態性的運作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然
而,這個「穩定」並非是一種系統運作的動機,也非其必然的產物。換句話
說,系統並非是有意識地要產生穩定的運作模式。這裡所謂的「穩定」毋寧
是一種「系統維持自身認同的暫時性狀態」,亦即,系統為維持自身與環境
的區別或界線之暫時性狀態。葉啟政的論述在某種程度上也正說明了此一觀
點。35 例如文字的使用總是必須是可以被看見的,而音樂則無論如何也都必須是
可以被聽到的。
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系統理論觀察 67
視為一種「象徵概化的溝通媒介」。換句話說,媒介與形式的這組差
異必須反過來作為一個「媒介」而發揮功能,亦即,作為一個開啟
媒介與形式之結合的可能性以透過溝通而形成(形式)的「媒介」
(1982b: 222)。這一點毋寧是相當重要的。媒介與形式的相對性關
係指出的是,在時間面向上,當下的形式是由過去的媒介所組成,而
這個當下的形式也可能在下一個時間點上變成為構成另一個形式的媒
介。形式與媒介的關係變成是耦變的、不必然要是如此的耦合關係。
就此而言,媒介與形式的相對關係指出的正是區別的兩邊在某個時間
面向上均具有自我指涉與自我生產的運作特性。
據此,媒介與形式之差異為我們指出了另一個理解 Luhmann社
會理論處理突現的方式。縱使媒介與形式之區別有可能表現出一種
「同步突現」(synchronic emergence)的性質,然而,這在考量時
間面向之後便僅是部分正確的(Protevi, 2009; Luhmann, 2000/1995:
126)。正是因為媒介提供了無法窮盡的選擇性與可能性,在藝術表
演中的即興創作(improvisation)才是有可能的且能被賦予「藝術」
的內涵(Landgraf, 2009)。此外,媒介與形式的區別也使得觀察者得
以受到藝術作品的引導,而關注其突現性質(Luhmann, 2000/1995:
126)。就此而言,這使得藝術品激發不同情感的潛力是可能的。若我
們回到前文中 Teller的論述,其關係性/非關係性之區別便獲得了更
深一層的擴展,這個「關係性」所指的不僅是整體中組成部分之間的
關係,還必須包括自我指涉與異己指涉這組區別所指出的「關係」。36
事實上,Luhmann所論述的三種系統指涉(次系統與社會的關係、
次系統與其他次系統的關係、次系統與自身的關係)便涵蓋了上述的
「關係性」內涵,並且可對突現性質提出其看法。
36 儘管這組關係就單一事件或溝通而言不過是耦變的。
68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綜上所述,從差異的統一作為系統運作的弔詭而言,「突現」
或突現性質的弔詭便正是表現在「系統就是其與環境的關係」或者
「系統就是系統與環境的這個差異(區別)」之上(Luhmann, 1982a:
257)。37這裡我們將可進一步說明整體與部分、系統與環境這兩組區
別為何不是相互排斥的。或者,這裡所謂的「相互排斥」或者「本體
論上的排除」均必須附加上另一件事,亦即,系統與環境之耦合的可
能性並未因此也被排除在外。我們可以說,整體與部分之間的關係
乃是:相互獨立且是相互依賴的(independent and interdependent)。
換句話說,其是個別地作為自我生產與自主性運作的系統。38我們
必須想像這樣一種整體與個體之間的區別,縱使不需要否認整體是
由個體所組成。然而,這不是說對整體的考量必須化約或還原至個
體的層次,才有可能理解整體或其突現特質。39若是以 Garfinkel對
俗民方法(ethnomethod)之研究的洞見為例,或可進一步釐清。
37 King和 Thornhill指出社會的環境是內在於系統之中,而非外在於其自身的溝通,這樣的看法對現代社會的組成而言具有關鍵重要性。社會在自身
之中再現與其環境之關係乃是現代社會的「終極弔詭」(supreme paradox),此一「終極弔詭」引起了豐富的自我描述、自我欺騙與自我辯護(self-justifications),就此而言,系統本身是盲目的,且只能夠藉由外部觀察者而看到此盲目的特性(King and Thornhill, 2003: 283)。38 在對時間面向的分析中,Luhmann(1997)指出系統在運作的當下區別過去(記憶)與未來(「擺盪」於各種區別之間)以作為維持界線(認同)
的機制。當時間面向的這組區別,亦即,「過去/未來」,得以在自身中再製
或重複該區別時,其結果是,過去現在(past presents)與未來現在(future presents)也會具有其各自的時間面向,亦即其自身的過去與未來。39 這樣的論述在社會學研究中發展為一般性的看法,亦即社會是由個人所組
成,且社會秩序與規範等乃是從個人互動中突現出來。Luhmann即試圖重構此一個人與社會的關係,而 Garfinkel對「社會秩序如何可能」的觀察在某種程度上也指出了另種理解的途徑。換句話說,系統與環境的差異,或者是
Garfinkel的解明與解明實作的區別,構成了所謂「秩序」的內涵。
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系統理論觀察 69
Garfinkel指出,社會成員對(其解明所運作或構作出來的)場景之
解明,構成該場景的「特徵」(1992/1967: 8)。首先,這是關於反身
性(reflexivity)的論述,同時也指出兩件事:第一,在分析上,「解
明實作」(accounting practices)與「解明」(accounts)得以先被區別
開來(independence);第二,這兩者之間必然存在著相互依賴的關係
(interdependence)。因此,這包含了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為「解
明實作」,第二個層次則是「解明」。社會成員的解明實作指的是其
正在對場景進行解明的過程。這是實作的層次,同時也對解明實作
本身所具有的反身性不感到興趣的層次,亦即,社會成員在進行解
明的當下,並不會將「解明實作」本身當作其研究或感興趣的對象
(1992/1967: 9)。然而,在成員對場景的解明實作中卻已包含了成員
對場景的解明,這是說,成員將場景中的某些「東西」(=具有類法
則性質的秩序,或突現物)視為是理所當然,並且是「視而不見」
(seen but unnoticed),而這個特徵控制了成員解明實作中的其他特徵
(1992/1967: 36)。
據此,社會場景中所具有的「秩序」必須是在「解明實作/解
明」這組差異及其作為統一體(弔詭)的使用,並且在解明實作中再
製或重複這組差異的持續運作過程中才會「突現」出來,無論這個
秩序是否有被這些正在進行解明實作的社會成員所意識到。40這一點
對 Garfinkel而言毋寧是重要的。因此,突現作為弔詭的內涵在於,
其作為整體的性質乃是必須與組成部分有所區別。社會秩序作為突現
40 Garfinkel將此視為一種對社會成員而言是「視而不見」的性質。相關討論亦可參考Michael Polanyi。他對「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在科學實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強調指出除了表面上的科學知識之外,在科學實作或實
驗室研究中必須依賴許多默會知識的協助,才有可能完成所謂的科學研究
(Polanyi, 1966)。
70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物(具有突現性質),必須是在社會成員的解明實作中而得以存在,
且同時(事實上並非是同時的)被社會成員使用著。換句話說,成員
的解明實作必然也必須是此解明實作得以進行之場景的一部分(特
徵)。41其所具有的突現性質在某種程度上無法在整體運作的當下被
覺察。換句話說,系統的自我指涉運作(正在進行觀察)與其自我描
述必須被區別開來。例如社會成員對場景可能具有的秩序之說明,
在考量時間面向之後,必須脫離對該秩序的使用才有可能實現。這個
「社會秩序」必須包含了社會「與」社會成員的自我觀察與自我描
述,縱使在時間面向上得以將之區分開來。因此,唯有在帶入時間面
向對系統運作與觀察之區別的討論之後,我們便可以更進一步說明整
體與部分各自作為具有自主性與自我指涉之運作並予以區別開來的必
要性。
舉例而言,在一個討論課的場景中,所有在場景中得以作為對該
場景進行解明的素材均必須為該場景中的社會成員所使用。這不是說
所有的素材均會被使用,而是有選擇性地進入成員對此場景的解明實
作。社會成員對這些素材的使用也必須是一個選擇性的過程與持續
不斷地完成。討論課這個場景所具有的突現性質即為其得以被辨識為
「討論課」(具有某種秩序)的這件事。換句話說,在該場景中有一
個所謂討論課的「秩序」在社會成員對其的解明實作中存在著,同
時也構成成員解明實作的素材。這一點在尚未將時間面向納入考量之
前是無法獲得釐清的,亦即,這兩個面向看起來是同時發生的。「討
論課秩序」包含在這個場景中被使用的解明素材,同時也包含著社會
41 例如,根據 Luhmann的論述,「對一個突現之藝術作品所進行的每一個操作上的介入,其轉變的遠超過該介入所指出的。⋯⋯對藝術的觀察等於對一
個突現秩序的觀察⋯⋯」(2000/1995: 73)。此外,心理與社會學家 Piaget對「我」與「我們」的分析也提出相類似的論述(1995/1965: 33-34)。
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系統理論觀察 71
成員對場景的解明。我們可以想像幾個可能存在的討論課秩序,但卻
無法窮盡這個秩序的內涵。就此而言,我們可以說,這個討論課秩序
便是該場景作為整體的突現性質。當然,就這個討論課場景而言,秩
序也不是唯一的突現性質。但這僅得到的是一個事實面向與社會面
向,而非時間面向上對此秩序的認識。本文所要強調的是,這個作為
討論課且具有突現性質之「秩序」,在帶入時間面向的分析之後,必
須要能夠與構成該秩序的「部分」予以區別,這是與在事實與社會面
向上僅關注整體或部分的作法是不同的。換句話說,無論是「秩序」
作為討論課的整體,還是成員對場景解明以及該場景提供的解明素材
(事實上,成員的解明在下一個時間點上也會成為場景的特徵,進而
繼續構成成員對場景的解明與解明實作)作為討論課場景的「組成部
分」,在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必須是相互獨立且相互依賴的。成員的解
明離不開場景,成員對場景的解明乃是自我指涉的。簡單而言,這指
出的是,整體及其突現性質在某種程度上是與構成其之組成部分是
相互排除的。因此,「相互排除」指出的不過是「相互獨立卻相互依
賴」的運作,而更重要的是,這個運作會在系統中再製或重複。這才
可能是對此「相互排除」與系統之突現性質較適當的理解。
我們或可以另一個例子來說明。John Urry對「全球複雜性」
(global complexity)的分析也持有類似的論述邏輯。首先,他對突
現與複雜系統的分析較為傾向整體論的觀點,至少就其對突現的看
法而言,亦即他認為「在整體層次上的確存在突現特性」,還原或化
約論的作法並未令他滿意。此外,他也指出若是要有效地描述個體
的特徵,就必須要去描述各種社會聯繫(social linkages),因為這些
社會聯繫決定了那些突現特性(Urry, 2003: 76)。然而,這並未肯定
整體必然是大於部分之總和的一般性看法。對此,Urry正確地觀察
72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到「整體大於部分之和」這樣的論述毋寧是有問題的,他認為更適
切的表述方式應該是將「系統效果」(system effects)與其各組成部分
予以區別開來(2003: 76)。這樣的看法一方面符應於 Luhmann以系
統與環境之差異來取代整體與個體之區別的爭論,另一方面也符應
於本文主張將整體與部分各自作為自我指涉系統,且以系統與環境
之間的相互排斥、相互獨立且相互依賴的自主性、自我指涉之運作
等,作為適切地對待「突現」概念的看法。就複雜性而言,Urry認
為突現是不可化約的、相互依賴的、流動的且是非線性的。這樣的
觀點當然是拒絕了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式論述(2003: 78)。從物理
學的角度,Urry指出在任何系統中,模式化(patterning)的出現均
源自於吸引子(attractor),其基本概念為:若一個動態系統並未隨
著時間而穿越一個潛在或相空間(phase space)中的所有可能區域,
反而是佔據其中的某個特定部分,這種現象便是由「吸引子」所引
起的(2003: 26; Capra, 1996)。此外,在某些複雜系統中,存在著所
謂的「奇異吸引子」(strange attractors)。這些是不穩定的空間,動態
系統的運作軌道透過無數次的重複而被吸引到這些「奇異吸引子」
之中。重要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會出現所謂的「正反饋」(positive
feedbacks),這些正反饋可能會使系統遠離任何的平衡點(2003: 27;
Byrne, 1998: 26-29)。42在此先不論吸引子的物理或數學上的應用。對
Urry而言,他指出我們可以將「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視為是
奇異吸引子的一個特例。據此,他主張世界中許多社會系統的運作軌
道會不斷地被拖入「全球地方化」的這個吸引子之中,因而表現為一
種「全球化—強化—地方化—強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deepens-
42 在另文中,或可討論這個吸引子的概念如何類比於構成社會系統的區別
(distinction)或差異(difference)。
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系統理論觀察 73
localization-deepens-globalization)的持續性過程。這個過程是具有一
種平行、不可逆且相互依賴的特質:
全球與地方透過一種動態關係不可避免地且不可逆地結合在一
起,伴隨著大量「資源」的流動來回於彼此之間。全球與地方均
不能沒有彼此而存在。全球—地方發展為一種共生、不穩定且不
可逆的一組關係,在此關係中,每一方均透過無數次遍及全世界
的重複運作且動態地隨著時間演化而獲得轉變(Urry, 2003: 84,
黑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Urry對此的觀察主要是從「訊息」(information)的分析出發,在 19
世紀之後,訊息得以脫離其物質形式而自由地流動:無論從地方上或
是全球上可使用的訊息或多或少都是相同的,或至少是不可逆地變成
是相同的。他認為,正是此種得以與空間脫離的訊息構成了全球地方
化的這個奇異吸引子(2003: 85)。據此,既使深處於世界上的任何一
個角落,只要是能夠獲得訊息的地方,都可以是全球化的開端。Urry
對複雜系統與突現特質的分析指出了三點可供參考。首先,他對系統
效果與組成部分之區別一方面修正了整體論的觀點,另一方面他也不
同意對於整體的突現特質之理解必須要化約或還原至對其組成個體的
分析。這樣的作法在某種程度上與 Luhmann以系統與環境之差異來
代替整體與部分之討論有異曲同工之處。第二,Urry將時間面向帶
入對複雜系統的討論毋寧是正確的。就此而言,在考量時間之後,系
統的動態性、不可逆性、不穩定性、非線性與耦變性等性質將變得更
為清晰。43第三,由奇異吸引子所引起的複雜系統之形成,或許也沒
43 另外,亦可參考 Garfinkel(1992/1967)。
74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有脫離 Luhmann的社會理論論述。作為一種不穩定空間卻具有不確
定界線的奇異吸引子,在某種程度上或可類比於在系統提高(同時也
是化約)複雜性的同時所使用的「區別」。換句話說,「系統即差異」
(system is difference)的內涵便在於指出,構成系統的組成元素就是
系統與環境的這個差異,透過這個差異的再引入,或者是在系統中不
斷地再製或重複這組差異,而成為系統形成(identity)的自我指涉
運作模式。這個差異在社會系統中便是「溝通」,在心理系統中則是
「意識」。
讓我們再回到 Urry對全球複雜性的論述,進一步闡釋本文之
論點,亦即對突現的討論首先必須以系統與環境的區別作為出發
點,在此觀點的轉變上繼而視整體與其組成部分彼此間乃是相互
獨立且相互依賴的不可逆之共生關係。以 Urry所謂「全球化—強
化—地方化—強化—全球化」的持續性過程而言,這個共生關係及
其突現性質必須在考量時間面向之後始能獲得清楚說明。全球與地
方之關係的互動就如同前述 Garfinkel所謂社會成員的「解明實作」
與「解明」之區別一般。沒有所謂純然的,或具有實在性的「全球
化」,也沒有所謂的「地方化」概念,這兩者在 Urry論述的全球突
現(global emergence)概念下是一種如同系統與其環境之間的結
構耦合關係(structural coupling)。任何關於「全球化」的溝通,亦
即 Urry所謂的訊息,必須在「地方化」的運作過程中予以再編碼
(second-coding),才得以為其所理解。換句話說,「全球地方化」
(glocalization)作為全球複雜性的突現性質,必須是在「全球化/
地方化」(globalization/localization)這組差異及其作為統一體的使
用,並且在該區別的其中一邊再製或重複這組區別,全球複雜性的
突現性質才能獲得適當理解。然而,也必須指出的是,Urry的討論
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系統理論觀察 75
與 Luhmann的論述並不完全相同。他雖然認為我們可以用「自我生
產」(autopoiesis)的概念來理解全球複雜性這個突現性質,但他毋寧
是選擇了對其論點有益的面向進行闡述,而未能注意到「自我生產」
的真正內涵。換句話說,Urry將社會系統理解為是開放而非封閉的
系統。就此而言並未充分掌握 Luhmann論述的核心,亦即系統的開
放性必須是以其自身的封閉性運作為基礎。44自主性與自我指涉運作
包含了系統與環境之區別,以及在系統中重複該組區別。透過這樣的
運作,系統始能將自我描述為「該」系統,而非其他東西。然而,若
我們同意 Urry所說的,亦即將全球複雜性系統描述為「自我生產」
是適當的且可能的,那麼在某種程度上,這個複雜性系統也必須是封
閉的,否則我們將無法描述或指出「全球地方化」為何得以作為這個
複雜性系統的奇異吸引子,引起系統的持續不斷且不可逆之運作軌
道,如同 Urry所論述的一般。45
四、結論
綜上所述,本研究嘗試指出幾件事,首先,無論是突現論者或是
複雜系統理論,在有關突現性質的討論並未與 Luhmann的社會系統
44 自我指涉的封閉性能夠擴大對環境的開放性(Luhmann, 1986b: 132)。45 複雜科學中對吸引子的討論或可提供看法。在簡單系統中,吸引子是
一個「點」(point),在較為複雜的系統中,其可以是一條線或是一個空間(space)。以「點」而言,其就必須是自我指涉的,否則將無法與其他不是「點」的東西區別開來。同樣地,既使是「線」或者是「空間」,就此論述
而言,都必須先是具有自我指涉的封閉性運作,才有可能其環境進行互動,
例如由「點」構成「線」,其有可能是直線、曲線、不規則的線等。這裡當
然也包含了「相對性」的看法。
76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理論有很大差異。在許多面向上,這兩個陣營對突現性質的看法是類
似的。Luhmann固然不是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者,他也無法被歸類
於方法論上的集體主義。包括 Bunge所發展的 CESM模型在內,大
多數的複雜系統理論在對社會系統的分析上仍然未能跳脫 Luhmann
的嘗試:亦即系統與環境與區別不一定要與整體與部分之區別相互
排斥。其間或有對社會系統之主張的根本性差異,然而,以個人作
為社會系統之組成元素的觀點一直是 Luhmann試圖釐清的。縱使他
將「溝通」視為社會系統的根本組成元素,但這並非表示個人在社會
系統中不再重要,也不是如傳統結構論者所主張的一般。這樣的嘗試
所指出的不過是下列事實:我們需要重新看待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
係,如果社會系統是以溝通作為其構成元素,那麼社會與個人的關
係應該如何重新表述?此外,這個重新表述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作為
現代社會的自我描述,或許才是 Luhmann社會理論關注的重點。任
何偏離這個問題而對其提出之批評在認識論的層次或許都是不夠充
分的。第二,Luhmann的社會理論一開始便不是要建立一種所謂的
社會突現理論(a theory of social emergence),這不是說他並未處理或
觸及處此類議題。情況毋寧是如此,從本文所述,Luhmann的「系
統即差異」以及他對形式/媒介之差異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便可
提供一個良好的視野以理解何謂突現的內涵。這一點是大多數的突
現論者與九○年代後出現的複雜系統理論者未能注意到的。其原因
可能很多,也不需在此詳述。第三,有關 Luhmann社會系統理論缺
乏物理學知識或科學背景的批評,在某種程度上也有失公允。這不
是要為 Luhmann的社會系統理論辯護。持平而論,對於其建構一個
關於社會的理論之企圖心是應該予以肯定,但對此「社會理論」的
想像卻有可能受到科學或其他系統的自我指涉運作所限制。Luhmann
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系統理論觀察 77
從不同的學科中借用一些概念,並嘗試將這些概念轉化用以建構一
個理論,試圖描述現代社會的運作。這樣的作法儘管可受公評,但
也非全無貢獻。就如同本文中用以為例的「解明」與「解明實作」
而言,如果我們可以想像某種社會秩序的突現是這兩者在時間面向
上的耦合,或者以 Luhmann的話來說,其具有的是「連續性的同時
發生」(simultaneity of sequentiality)之弔詭,那麼我們應該可以同意
Luhmann將系統視為是自我生產且自我指涉之運作的論述,在某種
程度上的確可作為對突現性質的理解。
78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參考文獻中文部分
Alex Callinicos
2007 《創造歷史:社會理論中的行動、結構與變遷》,萬毓澤
譯。台北:群學。
萬毓澤
2009 〈讓盧曼的系統理論(重新)成為問題:一個本黑式的視
角〉,《社會理論學報》,12卷 1期,頁 147-194。
葉啟政
2008 《邁向修養社會學》。台北:三民。
謝愛華
2006 《突現論中的哲學問題》。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顏澤賢、范冬萍、張華夏
2006 《系統科學導論─複雜性探索》。北京:人民出版社。
外文部分
Ackoff, Russell
1971 “Towards a System of System Concepts,” Management
Science 17(11): 661-669.
Barr, Stephan
2003 Modern Physics and Ancient Faith.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Bateson, Gregory
1972 Steps to an Ecology o f Mind: Col lec ted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sychiatry, Evolution, and Epistem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系統理論觀察 79
2002 Mind and Nature: A Necessary Unity. Creskill, N.J.: Hampton
Press.
Bird, Richard
2003 Chaos and Life: Complexity and Order in Evolution and
Thou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ierre
2003/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nge, Mario
1998 Social Science under Debate: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3 Emergence and Convergence: Qualitative Novelty and the
Unity of Knowledge.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9 Political Philosophy. New Brunswick &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Byrne, David
1998 Complexity The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Routledge.
Capra, Fritjof
1996 The Web of Life: A New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Living
Systems. London: HarperCollins.
Castells, Manuel
200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U.K.;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80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Coleman, James
1964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Sociology. 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
Elder-Vass, Dave
2007 “Luhmann and Emergentism: Competing Paradigms for Social
Systems Theory?”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37(4):
408-432.
Engels, Frederick
1878/1969 Anti-Dühring: Herr Eugen Dühring’s Revolution in
Scienc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Fromm, Jochen
2004 The Emergence of Complexity. Kassel: Kassel University Press.
Fuchs, Stephan
1988 “The Constitution of Emergent Interaction Orders: A
Comment on Rawls,” Sociological Theory 6(1): 122-124.
1989 “Second Thoughts on Emergent Interaction Orders,”
Sociological Theory 7(1): 121-123.
Fuller, Buckminster
1975 Synergetics. New York &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Garfinkel, Harold
1992/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oldstein, Jeffrey
1999 “Emergence as a Construct: History and Issues,” Emergence
1(1): 49-72.
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系統理論觀察 81
Goldthrope, John
2000 On Soci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egersen, Niels Henrik
2006 “Emergence and Complexity,” in Philip Clayton and Zachary
Simpso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Religion and Scienc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767-783.
Holland, John
1998 Emergence: From Chaos to Order. Redwood City, California:
Addison-Wesley.
Hornung, Bernd R.
2006 “The Theoretical Contexts and Foundations of Luhmann’s
Legal and Political Sociology,” in Michael King and Chris
Thornhill eds., Luhmann on Law and Politics: Critical
Appraisals and Applications. Oxford: Hart Publishing, pp.
187-216.
Jantsch, Erich
1979 The Self-Organizing Universe. Oxford: Pergamon Press.
King, Michael and Chris Thornhill
2003 “Will the real Niklas Luhmann Stands Up, Please. A Reply to
John Mingers,”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1(2): 276-285.
Landgraf, Edgar
2009 “Improvisation: Form and Event—A Spencer-Brownian
Calculation,” in Bruce Clarke and Mark Hansen eds.,
Emergence and Embodiment.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179-204.
82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Langlois, Richard
1983 “Systems Theory, Knowledge,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Fritz Machlup and Úna Mansfield eds.,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Interdisciplinary Messages. New York: John
Wiley, pp. 581-600.
Lewes, George H. and John Stuart Mill
1993/1874 Foundations for a Science of Mind. London: Routledge/
Thoemmes Press.
Luhmann, Niklas
1981 “Communication about Law in Interaction Systems,” in
Karin Knorr-Cetina and Aaron V. Cicourel eds., 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Micro- and Macro-Sociologies. Boston,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pp. 234-256.
1982a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trans. by Stephan Holmes and
Charles Larmo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b Essays on Self-Refer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1995 Social Systems, trans. by John Bednarz and Dirk
Baecker.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a “The Autopoiesis of Social Systems,” in Felix Geyer and
Johannes van der Zouwen eds., Sociocybernetic Paradox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pp. 172-192.
1986b “The Theory of Social Systems and Its Epistemology: Reply
to Danilo Zolo’s Critical Comments,”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系統理論觀察 83
Sciences 16(1): 129-134.
1988 “Closure and openness: On the Reality in the World of Law,”
in Gunther Teubner ed., Autopoietic Law: A New Approach
to Law and Society. Berlin and New York: De Gruyter, pp.
335-348.
1993/2002 Risk: A Sociological Theory, trans. by Rhodes Barrett.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7 “Globalization or World Society: How to Conceive of Modern
Societ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7(1): 67-80.
1998/1992 Observations on Modernity, trans. by William Whobre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1995 Art as a Social System, trans. by Eva M. Knodt.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Theories of Distinction: Redescribing the Descriptions of
Modernity, trans. by Joseph O’Neil et al.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System as Difference,” Organization 13(1): 37-57.
2009/2002 “Self-Organization and Autopoiesis,” in Bruce Clarke
and Mark Hansen eds., Emergence and Embodiment.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143-156.
Mill, John Stuart
1882/1843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8nd
e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epper, Stephan
1926 “Emergence,” Journal of Philosophy 23(9): 241-245.
84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Piaget, Jean
1995/1965 Sociologic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olanyi, Michael
1966 The Tacit Dimens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Protevi, John
2009 “Beyond Autopoiesis: Inflections of Emergence and Politics
in Francisco Varela,” in Bruce Clarke and Mark Hansen eds.,
Emergence and Embodiment.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94-112.
Rosa, Hartmut
2009 High-Speed Society.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Sawyer, R. Keith
2005 Social Emergence: Societies as Complex System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mith, Thomas
1992 Strong Interac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Smith, Thomas and Gregory Stevens
1996 “Emergence, Self-Organiz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rousal-Dependent Structure in Social Systems,” Sociological
Theory 14(2): 131-153.
Spencer-Brown, George
1979/1969 Laws of Form. London: Geroge Allen and Unwin Ltd.
突現作為弔詭:從整體/部分到形式/媒介之區別的社會系統理論觀察 85
Stephan, Achim
1999 “Varieties of Emergentism,” Evolution and Cognition 5(1):
49-59.
2004 E m e r g e n z : V o n d e r U n v o r h e r s a g b a r k e i t z u r
Selbstorganisation (Emergence: from unpredictability to self-
organization). (2nd ed.) Paderborn: Mentis Verlag.
Teller, Paul
1992 “A Contemporary Look a t Emergence ,” in Ansgar
Beckermann et al. eds., Emergence or Reduction? Essays on
the Prospects of Nonreductive Physicalism.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pp. 139-153.
Urry, John
2003 Global Complexity. Cambridge, Oxford, UK: Polity.
von Foerster, Heinz
1984 “Principles of Self-Organization in a Socio-managerial
Context,” in Hans Ulrich and Gilbert Probst eds., Sel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ocial Systems: Insights,
Promises, Doubts, and Questions. Berlin: Springer, pp. 2-25.
Yu-Ze, Wan
2009 “Emergence à la Systems Theory: Epis temological
Totalausschluss or Ontological Novelty,”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40(4): 1-33.
Wiener, Norbert
1948 Cybernetics: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SOCIETAS: A Journal for Philosophical Study of Public AffairsNo. 36, March 2011, pp. 39-86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elucidate the idea of “emerg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Niklas Luhmann’s social systems theory. Some critics claim
that Luhmann overlooks the idea of emergence which can be defined
as “the arising of novel and coherent structures, patterns, and properti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self-organization in complex systems”. By contrast,
I contend that in fact the idea of emergence exhibits the paradox in
the operations of systems formation and can be solved. The emergent
property can be explicated through system/environment difference with
which system unfolds the paradox within itself. The concept of “System
is difference” and its extensive media/form distinction can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a of emergence.
Keywords: emergence, social systems theory, media/form distinction,
Niklas Luhmann, parad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