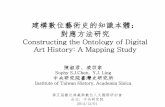我在丹青外-沈周的畫藝成就 Four Great Masters of the Ming Dynasty- Shen Zhou
Click here to load reader
Transcript of 我在丹青外-沈周的畫藝成就 Four Great Masters of the Ming Dynasty- Shen Zhou
沈周│明四大家特展 │ 286287 │
豐碩,無論是生平交遊、詩書畫藝術、文物收藏等方面,皆已有相關數量
的專文進行論述。在此僅舉出部分與沈周繪畫成就論題略加介紹,祈能寬
諒於篇幅所限不免疏漏之虞。
一九六二年美國學者艾瑞慈(R
ichard Edw
ards)
以英文出版沈周畫藝
專論, 15
是現代研究沈周的先驅學者。該書為艾瑞慈博士論文改寫出版,他
一方面運用歐美收藏,同時將日本以及故宮藏品納入,與其他仍受限於畫
論文字的介紹大相逕庭,艾瑞慈更落實於作品畫風掌握沈周的繪畫成就。
而在這一研究視野的刺激,也促成更多畫作典藏機構致力於相關的策展研
究,並進而出版展覽圖錄等。一九七五年江兆申主辦的︽吳派畫九十年展︾
與其圖錄,就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成果。江兆申對吳門畫派的研究十
分重要,一九六九年他曾受艾瑞慈邀往美國一年進行﹁十六世紀蘇州地區
畫家活動情形﹂研究,將存世作品與文獻記錄整合為蘇州畫家們的活動年
表。 16
此研究成果成為一九七五年﹁吳派畫九十年展﹂的重要框架,藉本院
藏畫架構出一個蘇州畫壇的時空;後亦於一九七八年出版︽文徵明與蘇州
畫壇︾一書,是吳派畫研究的重要參考,也為沈周四十四歲以後的活動軌
跡提供認識脈絡。 17
高居翰(Jam
es Cahill)
同年出版的︽江岸送行︾有長篇
幅介紹沈周繪畫成果,經由實際作品的畫風分析,勾勒並區分出沈周畫風
的階段特色。此書中對於本院藏品的畫風與內容分析,至今讀來仍時有所
得。 18八
〇年代以後,針對畫家生平活動與畫作序列的討論有更多累積,
其中如日本學者中村茂夫、林樹中等。 19
但在研究視野的拓展,應可注意
一九八三年方聞︽心印︾書中對沈周臨古畫風的分析。例如︿溪山秋色圖﹀
︵美國大都會藝術館藏︶畫卷上,沈周將元四家倪瓚、黃公望、王蒙與吳
鎮的山水筆法逐一演示,卻巧妙地將個人筆墨融彙其中。方聞特別指出沈
周詩畫的緊密呼應,甚可達以畫﹁言志﹂的境地;輔以沈周轉譯古人用筆,
將倪瓚筆法轉為自己的詩意化表達,以黃公望長皴傳達恬靜質樸山景等,
凸顯著繪畫形式中的人文意義。正因在沈周藝術中流露出如同哲人般的
表達,方聞說道﹁宋代畫家在藝術中追求自然,沈周則將他的畫變成了自
然。﹂ 20
方聞的分析,預示著將沈周畫風內容提至可資探討時代與人文精神
的層次。 21
一直持續關注沈周課題的艾瑞慈,在一九八九年︽中國藝術家的世界︾
據其演講內容出版的書中,他除概述沈周畫風發展外,則試圖直接闡述沈
周與其接觸的自然景致之關係。畫家與自然的亙古糾纏並非沒有贏家,畫
家參考眼見實景製作圖繪從不令人意外;但其因人而異的成就,讓人一再
驚嘆。艾瑞慈指出沈周的畫作表現,就與明畫可見的特色一般,雖可說是
心靈作用的過程,但這一糾結的過程,多是其正視了外在自然世界後的產
物。 22
一九九〇年十月北京故宮召開﹁吳門繪畫國際學術研討會﹂,意在匯
聚各方學術能量探究吳派畫風,涵蓋課題甚廣。其中有考察吳派畫風成因
者,無疑是將畫史的研究視野轉向文化脈絡的指標。此外,在沈周畫風研
究原以山水畫為主的研究,於此會議中亦有多篇花鳥畫的專文,顯示出吳
派研究已日趨多元。 23
而這一課題的關心也見於鈴木敬對沈周的分析,其文
章納入日本所藏沈周畫作討論,並且指出沈周花鳥孕育自南宋牧谿以來的
水墨蔬菜畫傳統。 24
觀察沈周的研究視野,也與明代畫史研究的整體脈動息息相關。
一九八七年因王鎮墓出土書畫作品,研究者得到一個掌握明代前期畫風與
收藏情況的契機,遂能增補對沈周的收藏內容的認識。 25
在沈周生平與藝術
活動的全面掌握上,一九九六年出版的阮榮春︽沈周︾一書十分重要。 26
阮
榮春從文獻、存世作品等方面,彙整了更趨全面的沈周相關史料與作品,
勾勒了沈周生平及其詩書畫三方面成就的重要架構。其中將沈周的交遊與
旅遊,各以獨立篇章整理相關資料,為其後的學者研究既提供了良好基礎。
正因透過沈周生平活動的認識,不少研究也試圖進一步聯繫沈周生平與畫
風變化的關係。 27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蘇州博物館舉辦﹁石田大穰—
—
吳門畫
我在丹青外—
沈周的畫藝成就
陳韻如
沈周,字啓南,號石田,晚年又號白石翁,生於明宣德二年
︵一四二七︶十一月二十一日,卒於正德四年︵一五〇九︶,蘇州府長洲
縣相城里人。其家族世居蘇州,曾祖父沈良琛拓展耕地、經營田產,為家
族奠立豐厚基業。祖父沈澄︵孟淵︶、伯父沈貞︵貞吉︶、父親沈恒︵恒
吉︶皆讀書隱居,以文藝為尚,不追求仕進。因世代雅好文藝,沈周家族
不僅富於書畫文物收藏,甚至傳說其家中僕役也解文墨。 1
沈周在此一家風
薰陶,終生居家養親不仕科舉,博覽群書,專意於詩書畫等文藝活動,又
與諸多文友唱和交遊,可說是明代中期蘇州地區文藝活動的重要靈魂人物
之一。 2
其中,沈周的繪畫成就最是顯著,在明代畫壇享有盛名;相關的存
世流傳作品數量龐大、畫風題材多樣,山水人物或花鳥蔬果皆有佳作,當
前學界將之與文徵明、唐寅、仇英等人並稱明四大家。
在繪畫成就上,沈周被視為﹁吳門畫派﹂ 3
之重要開創奠基者,亦有稱
他為吳派的精神領袖。關於﹁吳派﹂的畫風樣式,或者所謂﹁吳派﹂的認
識與定義等問題,學者間多有申論亦累積了不少成果。﹁吳門﹂原指蘇州
一地,因而將蘇州畫家歸為﹁吳門畫派﹂︵又稱﹁吳派﹂︶。其後,﹁吳
派﹂遂更進一步衍伸,亦是指稱蘇州畫家群體的繪畫風格樣式。 4
暫且不論
這類的風格樣式是否能有明確的形式共相,從實質畫風表現看來,吳派的
第二代畫風主體似乎更多是以文徵明畫風樣式為核心。相較之下,對於沈
周畫風樣式的直接繼承者成果並不顯著。從這個角度而言,沈周於﹁吳派﹂
所扮演的角色,顯然不能單由畫風樣式的普及流行遽下論斷,其重點更在
於思考沈周畫藝成就的特點與關鍵價值。 5
以畫史評價而言,沈周的畫風確實很早即享有盛名。就如︽明史︾雖
將沈周歸入﹁列傳.隱逸﹂,並凸顯沈周決意隱居心志,但也指出其畫﹁評
者謂為明世第一﹂, 6
亦給予沈周畫藝極高評價。根據為沈周撰寫墓誌銘的
王鏊︵一四五〇
-
一五二四︶形容,沈周處世平易近人,﹁販夫牧豎持紙
來索,不見難色。或為贗作求題以售,亦樂然應之。﹂ 7
一方面說明沈周無
論畫作真偽都樂於題字,另方面也足茲證明沈周的畫藝名聲在他仍在世之
時就流傳廣布。據說,他的訪客們早在天色未明,就已經絡繹前來,﹁每
黎明,門未闢,舟已塞乎其港矣。﹂ 8
而沈周也以親近口吻向朋友吳寬訴苦
道﹁吳人有求于太史者,輒來求予畫以餌之,遂使予之客座無虛日,每嘆
為太史所苦。﹂ 9
作為沈周門生的文徵明︵一四七〇
-
一五五九︶也曾提到
當時﹁內自京師,遠而閩浙川廣,莫不知有沈周先生也。﹂ 10
沈周的繪畫聲
名此後未有稍減,王穉登︵一五三五
-
一六一二︶稱﹁沈周先生…
…
下逮
童隸並諳文墨,先生繪事為當代第一。﹂ 11
至董其昌時仍讚譽沈周為﹁…
…
我朝則沈啟南一人而已。此冊寫生更勝山水,間有本色然皆真虎也。﹂ 12
對於沈周畫史定位的評估,還可從他本人的畫藝成就進一步闡述,換
言之,必要仰賴存世作品的研究分析。現存沈周名下的流傳書畫作品數量
相當龐大,且不論真偽辨識問題,據現已發表資料統計海外︵大陸與歐美
地區︶公私收藏,粗略估約有兩百多組件。 13
此外,本院所藏沈周名下書畫
作品則將近一百餘組件,若排除一些明確偽作,本院藏品中仍約有五十件
上下可為沈周書畫藝術代表,且其中不少精品,這在世界的單一收藏單位
中質量均可稱善。 14
本文將以本院所藏沈周繪畫作品為主,試舉出其畫風特
色與意義,期待能作為認識沈周畫藝成就的一個初步參考。
一、研究課題與成果
自二十世紀初期開始至今,現代學者針對沈周的學術研究成果已十分
沈周│明四大家特展 │ 288289 │
派之沈周特展﹂與研討會,是近年難得一見地彙整海內外藏品於蘇州的沈
周專題特展。 28
另外,關於沈周作品圖像資料的整理與出版方面更在近年有
多部巨作。 29
然而近十年來,針對明代繪畫的研究已不再限於文人畫範疇;更多
展覽、研究課題開始轉向宮廷或職業畫派等。而這一趨向並不只是研究興
趣的改變,實與吳派繪畫研究角度所面臨的挑戰有關。二〇〇四年柯律格
(Craig C
lunas)
︽雅債︾一書,從社會互動關係中考察文徵明的畫作與市場
活動,隨即引起許多回響。 30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柯律格後曾直言他仍堅
信風格與其製作背景有關,雖然他在書中無法深入說明其中細膩的關係。 31
而這一缺口,或許正是石守謙在其對沈周應酬畫的研究中所試圖切入。石
守謙舉出沈周在不同人際關係中的畫作,並且試圖從中理出畫風、畫意如
何因這些人際互動而有調整,檢視畫作與其觀眾之間的多層關係。 32
沈周成
功地透過畫意的運用來區隔他與觀眾之間的親疏關係,讓他得以保有自我
卻又不失親密互動或應酬交際的不同需要。繪畫與文人文化之間的關係,
未必是孤芳自賞的結果;也絕非需與市場取向斷然切割。換言之,從文人
文化角度而言,沈周的文藝活動十分複雜,這在石慢︵Peter Sturm
an︶從
︿落花詩﹀觀察沈周書法藝術與相關的文化意義的研究中亦能有所說明。 33
就此而言,沈周的文人畫家身分並未因此類應酬活動而稍有貶低,透過此
一檢視過程,更使吾人注意到明代中葉文人畫的盛行,實際上還伴隨著十
分複雜的文化競爭情境。整體而言,沈周的藝術成就確實亟待文化史的宏
觀評價。但在評價之際如何落實在作品上,卻仍一再挑戰著各領域學者。
本文擬從本次展出畫作,試藉個人的掌握與認識,拋磚以待來者。以下將
分別從沈周的前期與中晚期山水畫風、水墨花鳥畫風、扇面藝術以及其詩
畫成就等加以說明。
二、沈周的前期畫風與︿廬山高﹀
沈周的繪畫基礎顯然來自於家學薰陶。沈周的祖父沈澄︵一三七六
-
一四六二︶、伯父沈貞︵一四〇〇
-
?︶、父親沈恒︵一四〇九
-
一四七七︶都熱愛文藝,也能作畫。沈澄即已開始積極經營居所,名其莊
園為﹁西莊﹂,曾是文人雅士的集會之處,甚至還被比擬為元末收藏名家
顧仲英。天順二年︵一四五八︶,當時年已八十三歲的沈澄也正因為見到
顧仲英﹁玉山雅集﹂的圖作,而請沈遇︵一三七七
-
一四五八以後︶描繪
那次在四十年前舉行的西莊雅集,再由杜瓊︵一三九六
-
一四七四︶追憶
此事寫成圖記。 34
沈周雖未能親逢雅集盛事,但必能見到沈遇所畫的雅集圖
卷。據稱沈周於十六歲曾從伯父沈貞學畫,而不論這類的學習實況如何,
沈周家族裡的各式文藝活動理應是沈周創作的重要養分來源。
除了家學涵養之外,為沈澄作雅集圖記的杜瓊則是另一位影響沈周畫
藝的關鍵人物。沈周曾為杜瓊編寫年譜,並自稱為門人。杜瓊以儒行見長,
兼長詩畫,雖早有聲名卻也如沈澄一般,堅辭地方官的薦舉,不求仕進。
在十五世紀的蘇州地區,類似杜瓊這類不事科舉的士人並不算少數。沈周
的父執輩們即多如此,沈周本人也採相同態度。有學者指出當時北京宮廷
政事動盪不安,派系整肅鬥爭不斷,一方面阻卻人們前往北京發展的意圖,
另一方面也造成人們受迫離開北京。而這群拒絕北京或被北京拒絕的人
們,陸續回到家鄉蘇州隱居不仕,進而形成一個不同於北京文化氛圍的群
體。
35
杜瓊給予沈周的影響層面,更可能是包含著這樣的一種人生態度的
實踐,他們在詩書畫優遊自得,並且積極地以藝文知識作為交遊的重要資
本,彼此增補、流通文藝的訊息,凝聚出新的文化共識群體。
沈周的繪畫創作活動約在一四六〇年代前後開始, 36
現今仍存世流傳的
早期紀年作品並不多見,再因為他的早期畫風樣式不清晰,部分作品真偽
仍有爭議。 37
作於成化三年︵一四六七︶︿廬山高﹀︵圖版01︶是其中較能
為據之重要作品。此為縱高約一九四公分、橫寬九十八公分的大幅畫軸。
軸上有篆題﹁廬山高﹂,並書寫長篇詩文一首, 38
即沈周四十一歲為其師陳
寬賀壽所作。此段長題的文字相當重要,是理解此一大軸畫面的重要參照。
文字前半描寫廬山景觀,字句之間,沈周描述了廬山綿延盤據之山脈,以
及高聳危峭的山峰;接著,沈周以﹁雲霞日夕吞吐乎其胸﹂形容廬山的雲
霞變幻,接著提到﹁迴崖沓嶂鬼手擘,磵道千丈開鴻蒙。瀑流淙淙瀉不極,
雷霆殷地聞者耳欲聾。﹂沈周描寫山澗瀑流奔瀉氣勢,甚至點出瀑布奔流
所造成的巨大﹁聲響﹂。接著則是提到顏色的字句,﹁時有落葉於其間,
直下彭蠡流霜紅。金膏水碧不可覓,石林幽黑號綠熊。﹂這些文字的運用
有對景象的直述,如﹁流霜紅﹂指因霜寒而轉紅的落葉;也有採用更為抽
象的聯想,如稱﹁石林幽黑號綠熊﹂,則是把山林景觀與擁有罕見長毛毛
皮的綠熊並置,在文字上營造一種獨特又新奇的聯想與比擬。
39
若再回到
︿廬山高﹀畫面,不難先注意到畫幅上半的山峰與雲霧表現,應即是詩文
所描述的景觀。
就在︿廬山高﹀的山體構成上,沈周也巧妙地運用造型,適切地讓詩
文圖像二者之間有著相互的呼應。首先,是透過細分為條狀型態般的山體,
相互層疊推壓,就如同有神力向上推擎一般地呼應﹁迴崖沓嶂鬼手擘﹂。
此外,針對畫中從高聳山頂流洩而下的瀑布,與其所造成轟天震耳的水流
衝擊聲響,亦不僅止於詩文字面上的陳述。流水的﹁聲響﹂當然不可能直
接畫出,但是沈周卻能在畫面構成一個﹁聽得見﹂聲響般的場面。其實,
畫家並未直接描繪瀑布的澎湃奔騰,反倒是著力於緊鄰著瀑布水流的山谷
石壁。在此,沈周以極淡的墨色處理此部分山石,透過淺淡清雅的色調,
更營造出有著如同玉石般的溫潤效果。如果對比周圍以焦墨筆觸畫成的騷
動山石,這一處山石似散發出光亮,使得瀑布所在之處,既創造出空間量
感,更展現了一種視覺能量。因為這處明亮的山石,讓人視線得以直接聚
焦於此,隨而注意自下方向上生長的蒼鬱高聳松樹。曲折的松枝與山石圓
洞的造型互有呼應,或因此而讓人聯想到聲音的迴盪一般。這樣一來,那
位畫中唯一的人物,雖然身形十分渺小,但仍然成為畫中各種能量的匯聚
焦點。這位人物,應該就是沈周祝壽的對象
-
陳寬。
陳寬祖籍江西,沈周以當地名勝廬山作畫題,有意藉廬山的浩蕩氣勢
比擬其人。再又將廬山五老峰與紫陽妃並稱為六老,進而祈願陳寬長壽頤
年,﹁不妨添公相與成七翁﹂。陳寬是元末陳汝言之孫,名儒陳繼之子。
由於陳汝言與王蒙熟識,不少研究也注意到沈周採王蒙畫風作成此畫贈予
陳寬,應有此層對陳寬家系淵源的考慮。不僅是山石筆墨皴法,︿廬山高﹀
的精采構圖手法,沈周確實也曾參照王蒙山水樣式。學者已指出其與王蒙
︿具區林屋﹀︵圖一︶的關係,特別是此畫下段三分之二部分,就如︿具
區林屋﹀一樣,被糾結扭曲的山石填滿,僅留下部分曲折的水面透氣。 40
︿廬山高﹀與︿具區林屋﹀的關係確實十分密切。但是,儘管兩者的
畫面構圖相近,但二者之間同中有異的效果也值得玩味。關於山體的分塊、王蒙〈具區林屋〉(圖ㄧ)
沈周│明四大家特展 │ 290291 │
皴筆的濃密等手法,沈周顯然是沿用了王蒙的特色。也正因此,︿廬山高﹀
就與︿具區林屋﹀一樣,都能夠顯示出山體騷動的生命活力。不過,兩者
的整體效果卻說明著兩人不同的追求。王蒙︿具區林屋﹀的林木紅葉,使
用了更為濃艷的色彩,讓此一山岩石壁間的隱居所在更顯絕俗而非塵世,
流露著奇異脫俗的神仙境界。相較之下,沈周所使用的色彩顯得溫和許多,
山谷中雖仍有紅葉,但是彩度減低不少。此外,瀑布一側的淺淡墨色山壁
也減低了對比,而流露出如同玉石般的溫潤特質。︿廬山高﹀的山中景象,
雖同樣具有生命靈動之氣,卻因溫和的設色手法顯得親近怡人。透過這樣
的處理,沈周或許是要塑造出陳寬那種﹁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的君子師
道。
整體而言,︿廬山高﹀雖屬沈周早期畫作,卻已是一件具備縝密構思,
並能融匯前代樣式的精采傑作。然而,︿廬山高﹀的精采成就,也不應該
成為理解沈周早期畫風樣式的限制。換言之,在此畫軸中,沈周所精采地
詮釋、轉換的王蒙畫風,很可能僅是沈周豐富繪畫淵源的一部分展現而已。
以本院藏品實例也能說明一二。例如題有﹁米不米,黃不黃﹂的︿山水﹀︵圖
版02︶,顯然就是一個複雜畫風綜合的成果。沈周此畫上並無紀年,兩段
題詩書風也顯得較為放逸,但因是畫贈劉珏之作,可確定是繪於成化八年
︵一四七二︶二月劉珏辭世之前。 41
而約一四七〇年沈周另有︿崇山脩竹﹀
︵圖版03︶一軸,乍看之下該畫風與此軸並不相類。江兆申藉由樹法用筆
的相似度聯繫二軸年代相近的意見,目前仍普遍受到重視與接受。只是單
從畫風樣式而論,正如許郭璜所指出︿崇山脩竹﹀的平台疊山、皴法用筆
都可見王蒙風格的影響;
42
︿山水﹀卻以淋漓筆墨揮灑,山體物象亦不多
講究,明顯傾向於米氏雲山的放逸傳統,而非縝密用筆的王蒙畫風。
沈周在此軸︿山水﹀畫上的題稱,實際也可說明他對前輩畫風的態度。
﹁米不米,黃不黃,淋漓水墨餘清蒼。執筆大笑我欲狂,自恥嫫母希毛嬙。﹂
沈周顯然要藉米氏雲山與黃公望筆墨,追求一種淋漓水墨的表現手法。然
而,當他執筆之後,卻發現自己就像醜女妄想自比為美女般不堪。這幅小
軸山水是沈周自稱酒後醉筆,不僅劉珏未有嫌棄,還得到賀甫︵一四一四
-
一四八九︶、陳蒙等人的讚譽。若從﹁米不米,黃不黃﹂的沈周自謙說詞
看來,究竟畫中如何整合米氏雲山與黃公望樣式也令人好奇。畫面用筆瀟
灑放逸、水氣淋漓,即便沒有直接運用墨染米點的手法,卻也貼近米氏雲
山的筆墨特質。至於其中的黃公望山水特色,雖不見平台山體的堆疊,但
運用墨色染出遠山、以筆墨描畫峰頂交界等手法,也正是黃公望山水重要
的表現特徵。實際上,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圖二︶確實可見這類表現,
墨染的遠山、山體層疊、交錯的筆墨處理等。
沈周對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十分熟悉,該卷後有沈周於弘治元年
︵一四八八︶所題,指出此卷曾為其舊藏,但後為樊節推所有。而就在前
一年︵一四八七︶沈周即曾憑記憶背臨畫成一卷仿本,現為北京故宮博物
院藏本。
43
沈周雖沒有表明他在何時收藏︿富春山居圖﹀,但從﹁舊在余
所既失之﹂字句推敲,具當時應已有一些時日。再以︿山水﹀︵圖版02︶
軸上的筆墨表現而言,沈周不無可能已對黃公望畫風有不同於他人的認識
與掌握,特別是其筆墨上的細微表現;而這樣的掌握,非常可能來自於沈
周對︿富春山居圖﹀這類真蹟作品的收藏與實際觀察所得。
︿崇山脩竹﹀︵圖版03︶是另一種黃公望山水樣式的運用。根沈周自
題此畫原贈予馬抑之,後轉歸劉珏弟劉竑︵以規︶,一四七〇年劉珏題詩
其上以表達對劉竑的期許,畫上另有劉竑邀得吳寬、文林二人題詩。在此
狹長山水畫幅,沈周特意營造出山嶺層疊聳峙景觀。在畫幅上方可見峰巒
與平台相互推擁,其間又可見雲層、瀑布水流,形成奇特的山水景致。這
些山頂平台的造型以及山體之間的簇擁效果,不免令人想起黃公望︿九珠
峰翠﹀︵圖三︶山水之境。畫幅下方則營造一處平淡恬靜的水澤居處,而
中段景處為叢竹環繞的屋舍,其間有一人正持書坐讀。吳寬於題詩指出此
即劉竑讀書處,或許是與其家鄉穿山勝景有關。整體而言,此畫中所用皴
筆較為繁密,確實有近乎王蒙之處。換言之,在此軸中,沈周可說是巧妙
地混融了黃公望與王蒙的山水特色,進而營造出一個不同於元人面貌的新
山水。沈
周早期作品畫風顯示了他對不同古代傳統的學習與融會。其中雖以
王蒙最為人所注意,但實際上其筆墨的特色與山體組構的手法,卻不斷看
到黃公望的影響力。由於沈周最早收藏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的時間並不
明確,他在一四八八年題寫於︿富春山居圖﹀上稱曾﹁舊藏﹂此卷,或許
果真可早於十多年前。而當然,對於沈周山水畫風的影響必不限於此。如
現存北京故宮的︿仿董巨山水軸﹀、日本所藏的早期畫作等,都顯示了不
同的古人面貌,當可豐富其所藏作品的更多面向。本院所藏︿江山清遠﹀
︵圖版25︶雖是後仿本,但保留不少沈周特色,又與本院所藏夏珪︿溪山
清遠﹀十分相近;有學者指出此卷或可說明沈周向南宋院體畫風的學習例
證。 44 三
、沈周的中晚期山水畫風
沈周早期山水畫中可見其師法古人的努力,但也能看到沈周企圖於融
貫古人之中,創出新的山水意象,而在中晚期的畫風特色即是此一趨勢的
總成。成化十二年︵一四七六︶沈周五十歲,約在此年或之後作︿山水﹀
︵圖版04︶。此畫中山頭造型秀麗,不用皴筆勾畫而僅以墨點畫成山頭樹
叢。此類山頭部分的表現手法,雖是延續北宋以來的董巨風格,但更為直
接相關的應是元代的吳鎮畫風。例如院藏吳鎮︿中山圖﹀︵圖四︶山頭的
造型略聳,稍近於錐狀,比董源、巨然的山石面貌更為秀潤,而所用墨點
雖簡但並不工巧, 45
沈周︿山水﹀應是繼承此類吳鎮風格而來。學者曾指出
畫中筆墨與早期山水不同,已漸顯圓熟, 46
應可說是沈周自我面貌正在醞釀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二)
黃公望〈九珠峰翠〉(圖三) 吳鎮〈中山圖〉(圖四)
沈周│明四大家特展 │ 292293 │
的重要階段。︿山水﹀︵圖版04︶畫上沈周長題記述的作畫原委也值得注
意。原來,沈周的朋友曾邀他一同陪吳珵游賞虎丘,但沈周當日未能成行,
次日才攜酒趕去。由於朋友們已發舟離去,沈周徘徊山水之間,遂有詩句
稱﹁雨後振孤策,迢遙追往蹤。﹂後因為吳珵表弟︵吉之︶又來求畫,才
作此並錄題當時吟誦詩句相贈,期能﹁使知後期之人之落寞也﹂。畫中下
半描繪林中屋舍數間,又以飽滿水墨用筆點染林木,為畫中營造雨後濕潤
效果,適切地與﹁雨後振孤策﹂的詩句相互呼應。沈周山水畫作常是人情
交遊活動的一環,而其所憑藉的正是詩畫二者互為參照的緊密關係。吳珵
字元玉,成化己丑︵一四六九︶進士,曾任南京工部主事。吳珵本人也喜
好繪事,沈周此年另曾為其畫作題。 47
在沈周五十歲︵一四七六︶以後,有許多此類融入吳鎮畫風的畫軸,
這些作品風格可視為構成沈周個人獨特面貌的基調。舉如︿溪橋訪友﹀︵圖
版07︶、︿抱琴圖﹀︵圖版08︶、︿松巖聽泉圖﹀︵圖版09︶、︿杏林書
館﹀︵圖版10︶、︿扁舟詩思﹀︵圖版14︶等都採一河兩岸的基本樣式,
而於主山部分略予變化。︿溪橋訪友﹀並無明確紀年,學者指出此畫用印
與成化十二年︵丙申,一四七六︶沈周題林逋︿手札二帖﹀相同,而畫上
用筆風格則略晚於︿參天特秀﹀,推測為晚於︿參天特秀﹀一年之作,即
一四八〇年,沈周時為五十四歲。
此軸畫中山頭傾斜而出,略可見留白的
山頂平台處,雖有部分黃公望山水趣味,但已摻入更多吳鎮山水特色。沈
周的用筆更顯簡約,其山體的層疊效果與吳鎮︿漁父圖﹀︵圖五︶畫中山
體構成手法有異曲同工之妙。此軸題為﹁貞父﹂作,推測或是贈予當時人
在南京的毛珵。毛珵︵一四五二
-
一五三三︶為蘇州人,字貞甫,號礪菴,
少年即從學賀恩︵賀感樓次子︶門下學易,成化十三年︵一四七七︶曾領
應天鄉薦資格,後於成化二十三年︵一四八七︶取得進士。
49
另一件立軸︿松巖聽泉圖﹀的畫幅更為狹長,同樣採一河兩岸的構圖。
此畫主山採巨然山體樣式,但顯然已是一種經過元代吳鎮改造後的樣式,
吳鎮︿清江春曉﹀︵圖六︶的主山可作為一例。
50
︿松巖聽泉圖﹀畫上除
沈周自題之外,另有周鼎題詩,兩人詩句中分別有﹁占得此溪好﹂、﹁得
此一溪名﹂等呼應詩句,推測是與周鼎相互唱和之作。周鼎︵一四〇一
-
一四八七︶,字伯器,號桐邨︵桐村︶,雖較沈周年長,但兩人交遊互動
親密,沈周有詩句形容周鼎為﹁白髮烏紗將八十,文章談笑見揚雄;風流
不减三年别,未許尊前稱阿翁。﹂
51
周桐邨過世後,沈周還有詩句弔念稱
之﹁生死通心夢裡人﹂。
52
周鼎曾有題跋於吳鎮︿嘉禾八景﹀卷後﹁成化
十五年(一四七九)己亥秋七月廿六日書於江南水竹邨上。桐邨老牧。時
年七十有九。﹂所謂﹁水竹邨﹂,應是指姚綬居所,可推測該卷當時應是
姚綬所藏。無論沈周是否有機會見得此件吳鎮︿嘉禾八景圖﹀︵圖七︶,
周鼎應不會吝於與沈周分享他所見到的吳鎮畫風,沈周當可從周鼎這類文
友得到更多的畫藝知識與見聞。
除了吳鎮畫風的融彙之外,沈周中晚期山水畫風也從倪瓚風格汲取養
分。本院所藏作品中有︿仿倪瓚筆意﹀︵圖版05︶、︿策杖圖﹀︵圖版12︶、
︿秋林讀書﹀︵圖版20︶等可舉為例。︿仿倪瓚筆意﹀︵圖版05︶採一河
兩岸構圖,但其筆墨與倪瓚乾筆皴畫方式不同,更為濕潤,藉以表現山體
質面上的層次變化。畫中遠景與前景坡岸都有花青染色,雖是倪瓚空寂山
水形貌,但更加入閑適清雅風貌。沈周對於倪瓚畫風的詮釋,就如他在︿潤
色舊臨倪雲林小景﹀詩中所言﹁妄意加潤色,泥塗還附塗﹂, 54
顯然已不再
追求倪瓚畫風的蕭瑟荒蕪。沈周的這種新詮釋角度,或許有可能是受到家
藏倪瓚畫風的影響。根據杜瓊的記錄,沈周祖父︵絸菴︶曾藏有一件倪瓚
畫作,但是因一般人依據書風辨識畫作真偽,卻忽略了畫家早期風格如人
之﹁妙嫩﹂,而﹁此圖人皆以為非本真﹂,沈絸菴卻能獨具慧眼識之。 55
根
據這段記錄也說明沈周家族所藏倪瓚畫風,應與一般常見荒疏風格略顯不
同。除此之外,根據沈周的說法,倪瓚畫作在當時江南地區亦已成為熱門
藏品, 56
︿松亭山色﹀畫上沈周即題﹁雲林先生戲墨,在江東人家以有無為
清俗。﹂ 57
這股對倪瓚畫的追求熱潮,自然促成倪瓚風格於江南地區的流布,
沈周所能接觸的倪瓚畫風應十分多樣。從實際的作品看,沈周對於倪瓚風
格與樣式的新理解,當以︿策杖圖﹀的創造最為重要。
︿策杖圖﹀據學者推測為五十九歲︵一四八五︶之作。此軸採元代倪
瓚常用的一河兩岸構圖,主山據有畫面上半,下半則是高聳林木所在的坡
岸橋徑。雖然畫法上也有採近似倪瓚的淺淡皴筆,不過整體畫中氣氛卻已
異於倪瓚的蕭散景觀,在此,沈周營造出一個更為渾厚宏偉的山水景致。
沈周透過幾個重要的改造手段達此成效,首先,針對畫中主山,沈周改採
黃公望畫中常見的緩坡層疊手法,遂以構造出渾圓厚實的山體。其次,畫
家也調整其高聳林木與杵杖行人的比例,藉著山大人小的差異,更能形塑
畫中山水的渾厚空間。沈周對於倪瓚畫風的調整,應受惠於他師習多家所
獲得的豐富養分。例如主山的構成樣式,確實與黃公望︿富春山居圖﹀中
的圓弧山體相近,只是原來橫向聯繫的脈動,在︿策杖圖﹀中改為縱向的
動勢。再因元代的黃公望山水依循著北宋的董巨傳統,若要說此畫中也可
見到董巨山水特色,自不令人意外。沈周在畫上自題稱﹁逍遙遺世慮,泉
石是安居。﹂表明此處山水是沈靜又能安居的所在。畫中身形微小的杵杖
行人,沈周詩題﹁獨行固無伴,微吟韻徐徐﹂,也意味著他所營造的山水
景觀絕非孤立絕世,就如同畫中策杖之人亦能自得其樂,更而流露出怡然
氣氛。沈周曾收藏黃公望名蹟︿富春山居圖﹀,其後更有臨仿作品現仍存吳鎮〈漁父圖〉(圖五)
吳鎮〈清江春曉〉(圖六)
吳鎮〈嘉禾八景〉(圖七)
世。此一︿策杖圖﹀軸與其說是一種倪瓚畫風的再造,或更可說是沈周對
黃公望畫風體悟後融貫古人之所得,充分展現出他於元人畫風中追求個人
新意的成果。
沈周的︿畫雪景﹀︵圖版13︶也是大畫面之作,學者據畫上題詩書風
推測是中晚年,約六十歲左右之作。 58
此一雪景山水乍看與沈周其他山水畫
風不盡相同;通幅淡染出水天一色,映襯山石以表示雪景。沈周詩句稱雪
裡探梅行人,正於西湖六橋頭聞得撲鼻新香。畫面構圖也如︿策杖圖﹀為
一江兩岸之景,但是山體的組合手法則與之有別。︿畫雪景﹀以碎石層疊
的高聳主山,具微傾側倚之態,後則有澗水涔涔。隨處山石造型皆精巧,
畫中小亭一側,畫翠竹三兩叢,更為此白茫山水添入雅緻情韻。究竟此景
與西湖關係如何並不要緊,關鍵在於沈周已成功地藉元人筆墨,將北宋大
觀山水化為清麗之境。
雖然一般認為沈周在早期積極臨仿古人,實際上其博採多家畫風的實
例並未限於早期。紀年丁未︵成化二十三年,一四八七︶的︿雨意圖﹀︵圖
版15︶為沈周六十一歲所作。在此小軸上,沈周以飽滿水份的筆墨,重新
詮釋米氏雲山畫風。 59
沈周所採用的米氏山水也是經過調整的結果,畫中山
體略具輪廓,而橫向米點的運用更添飽滿水氣。畫幅下方是淋漓筆墨畫成
的林木山景,其中有二人相對晤談的屋舍所在則清晰可見。沈周透過淺淡
染墨,經營出一個雨後又瀰漫雲霧的夜景,讓原多不見人蹤的米氏雲山手
沈周│明四大家特展 │ 294295 │
法,至此成為知交親友隨時可共遊共賞的優雅自在山水。雖有學者指出沈
周曾見方從義山水,此類雲山表現或與元代方從義的手法有關,或參考元
代雲山圖的另一位畫家高克恭。但從︿雨意圖﹀的成果而言,沈周雖採自
古人畫風,卻已能將之轉換而成就出個人面貌。其他如與吳鎮風格有關的
︿扁舟詩思﹀︵圖版14︶、︿蒼崖高話﹀︵圖版24︶,或是倪瓚風貌的︿秋
林讀書﹀︵圖版20︶等都可資為例。
在沈周中晚期山水畫風中︿夜坐圖﹀︵圖版21︶無疑是一重要的畫作。
此軸畫幅不大,軸面上半為沈周約四百五十字的︿夜坐記﹀,篇中詳述沈
周於夜中醒後安坐沉思之心境與所得。沈周自稱﹁性喜夜坐﹂,在詩文集
中也確可見多首夜坐詩文。 60
關於︿夜坐記﹀與明代理學思想的關聯,方聞
曾指出沈周與陳獻章思想上的相近性,後亦有王正華對之深入考察。 61
此畫上︿夜坐記﹀的書風與沈周常見風格並不十分相類。部分字體雖
仍可見沈周所慣用的斜傾結構,但個別用筆表現上似乎顯得不夠端謹,整
體而言其書寫品質稱不上精緻講究。有些筆劃十分隨意,時有顯露粗黑醜
態,時則是纖弱敗筆。這樣的書寫品質確實容易啟人疑竇,雖未曾有學人
直接提出疑義,卻仍有必要正視此一書風的效度。近因學者注意到此段︿夜
坐記﹀內容,亦見收於一卷傳祝允明︿遠遊詩﹀帖後, 62
而究竟此段內容是
否為沈周之作,隨之成為必須探討的課題。經初步考察,該段內容與︿夜
坐記﹀字句僅有數字之差。 63
在此即使不論祝允明書蹟真偽,也仍須處理沈
周可否為︿夜坐記﹀原創者的可能性。對此問題,現階段雖未能深入探討
︿夜坐記﹀的論理邏輯與遣詞用句的關聯,暫從幾項外部因素初步推斷。
首先,在現存祝允明詩文集中並不見有關於他個人夜坐的其他詩文,但於
沈周詩文集中卻經常可見提及夜坐詩文。而從︿夜坐記﹀文中題﹁余性喜
夜坐﹂,顯然是比較符合沈周習性。其次,祝允明書題時間為弘治辛酉
︵一五〇一︶,已晚於沈周的紀年壬子︵一四九二︶,不能排除此是抄錄
沈周原作的結果。 64
若文本本身的原創性無有堪慮處,這一品質稱不上精緻
的沈周︿夜坐記﹀書風,反而更能真實顯示出沈周的自然隨性。 65
︿夜坐圖﹀畫幅下半即是描繪夜坐所在場景。這個場景是由山水環繞
一處書齋,山水的安排乍看簡單,在前景坡石、後景山峰之間的谷間平台
上,有一組屋舍以較淡筆墨畫成。屋舍由數間房屋組成,一間室內點著燭
火,一位士人盤坐其中,正是沈周本人夜坐寫照。在︿夜坐圖﹀中,沈周
一改水墨為主的山水畫風,運用了更多的清淡染色增添此畫的清雅情調。
例如屋後竹叢在以淡墨勾畫枝葉後,又染上淺色花青,成功地與屋舍與山
峰間的留白空間巧妙融合,似乎真有雲霧瀰漫其中,為此場景增添不少延
伸效果。而畫中多處坡岸側面染上藤黃,顯出溫暖的土岸效果;平坡面上
也似乎淡染上薄薄一層花青,成功地讓這些地面如因夜光映照般顯得迷人
雅緻。畫中山石則以水墨為主,然而沈周以最具個人特色的淡墨皴筆鋪成
自然質面,讓此山水顯得平易近人;其後,再於峰頂、坡石塊面邊緣畫上
看似隨性的焦濃墨點,就如在平靜的山水間添上生命活力般。沈周至此已
經完成他最具個人特色的畫風樣式,據說此年夏天沈周曾臨仿吳鎮畫作,
但顯然︿夜坐圖﹀所顯示的畫藝成就,已非從古人面貌所可想見。在此有
圖、有文的畫軸上,其文本內容雖是理解畫面意涵的關鍵,但從視覺效果
而言,畫中場景卻已是直接引發對此靜夜追念的重要媒介。沈周畫中的視
覺能量正要突破那畫面的限制,直達人心成為蘇州文人文化的重要基調。
四、沈周的花鳥畫風與︿寫生冊﹀
關於沈周水墨花鳥風格,已有學者指出是與南宋法常︵牧谿︶有關。
其最主要根據是以一件傳為法常之︿水墨寫生圖卷﹀︵北京故宮博物院
藏︶卷後有沈周題跋,題稱是於吳寬家中見此畫卷。 66
然而,學者也質疑
此卷畫幅已非牧谿真蹟,惟沈周題跋尚屬可信。 67
而無論該卷是否為法常
水墨花卉真蹟,沈周所掌握的水墨花卉樣式,確實與這類傳稱為法常的畫
作關係緊密。本院另藏有一卷傳為沈周之︿寫生卷﹀︵圖版28︶,其內
容題材與前述法常畫卷相近,除描繪花卉、蔬果、坡石禽鳥之外,最後一
段則又畫有雞、鴨、兔等三種家中豢養的禽畜。全卷共描繪二十四段,各
段皆有一首詩題並隨附沈周款名;卷後有一長題,署年款為﹁弘治甲寅﹂
︵一四九四︶。
68
此卷的書風、畫風雖都帶有沈周形貌,但書風較為僵化
不自然,實屬仿本並非真蹟。圖繪部分如畫雞、鴨兩個段落,於沈周︿寫
生冊﹀可見有造型十分相近者。不過這件手卷中的筆墨表現手法卻遠不及
︿寫生冊﹀中自然,亦較無生物的神采。即便如此,此卷仍能視為掌握沈
周寫意花鳥畫風師承與創新的重要接點,既可將沈周與法常加以聯繫,又
可掌握沈周的自我面貌。例如畫卷最後一段以水墨畫兔,其圓滾的兔子造
型,又搭配上詩題﹁世上空碌碌,無人知卯君﹂,與沈周︿寫生冊﹀中描
繪貓的畫意趣味有異曲同工之妙。
由此而論,原歸入法常名下的︿寫生卷﹀︵圖版29︶的意義與其定
年問題應值得重加關注。此畫卷中描繪內容包含花卉、蔬果,最後段落則
是鳥禽棲停坡岸景象。雖原被視為南宋作品,但若仔細比對後段的坡石畫
法,特別是在山塊結構的表現上,實已非元人筆意,遑論南宋。
69
若從山
石畫法而論,其淡墨皴筆與略微橫向的墨點筆法,似乎能與沈周的︿策杖
圖﹀山頭表現略有相通。此外,本畫卷前段鈐有吳寬藏印兩方,與沈周前
述題跋所稱﹁近見牧谿一卷匏庵吳公家﹂的作品關係如何,值得再議。而
無論實情如何,單從此卷題材與筆墨的表現判斷,其與沈周當有極高可能
相關。 70
實際上,在不少沈周花鳥畫作中,仍可一再見到這些卷中的蔬果鳥
禽造型,例如︿蔬菜﹀︵圖版31︶、︿鳩聲喚雨﹀︵圖版35︶等。而在一
套︿寫意﹀︵圖版38︶沈周也再度運用了相似的題材,如第六開﹁枇杷﹂、
第七開﹁蔬菜﹂、第八開﹁慈烏﹂、第十開﹁芙蓉﹂等,而第十一開﹁紅柿﹂
則枝葉造型都與︿寫生卷﹀段落相仿。
沈周的水墨寫意畫風的影響深遠,但並非僅是畫風或內容題材而已,
更在於沈周對於物象的觀察詮釋。其中雖有與南宋禪僧法常的影響有關,
然而若以︿寫生冊﹀︵圖版27︶的表現而論,沈周個人的詮釋也是重要關
鍵。這套畫冊現存共計十六開,分別描繪花果、家禽、貓、驢等日常所見
之物,各開雖無沈周自題,但皆鈐蓋印章。另前副葉有篆書題寫﹁觀物之
生﹂四字,現雖無書寫者款印,但從書風特色觀察,與沈周好友李應禎
︵一四三一
-
一四九三︶篆書特色十分相近。
71
後副葉有沈周六十八歲自
題,此段跋語用筆灑脫不羈,是以黃庭堅書風為基調而自創個人面目的標
準書風。﹁我於蠢動兼生植,弄筆還能竊化機;明日小窗孤坐處,春風滿
面此心微。戲筆此冊,隨物賦形,聊自適閒居飽食之興。若以畫求我,我
則在丹青之外矣。弘治甲寅(一四九四)。沈周題。﹂
此冊中,沈周雖未針對各開題寫詩文,但冊後跋語仍可觀察他的作畫
態度。在題識中,沈周自稱對動植物的描繪不僅是在描繪形象而已,還希
望﹁竊化機﹂以得知物象的自然生命。詩句所謂﹁明日小窗孤坐處,春風
滿面此心微﹂,正是在表達能於提筆作畫後,在明日獨坐觀看畫冊時,雖
僅僅是春風拂面而來,也能讓心中微動而感知其中的生命能量。沈周稱此
畫冊為﹁戲筆﹂之作,但顯然是自謙的說法。實際上,在此冊中沈周將日
常所見物象的生趣,憑藉其獨特造型手法竊得化機。︿寫生冊﹀無論在構
圖、造型、描繪手法等,都有別出心裁的創意巧思。從水墨技法而言,其
中如第一開﹁玉蘭﹂全幅淡染花青,以墨線勾出花瓣留白,藉而襯出玉蘭
花朵的白皙潔淨;第四開﹁荷蛙﹂則改以水墨大肆暈染,再藉墨筆之間的
細微留白,巧妙地形塑出生動的青蛙身影。另外如第五開﹁葡萄﹂上藤蔓
的提頓轉折猶如書法運筆,而葡萄則採深淺紫色墨染成形,濃淡之間盡得
葡萄果實的渾圓意趣。沈周的寫意花卉全憑水墨濃淡的處理,無需施彩就
可畫出花卉的嬌豔形貌,如第七開﹁雞冠花﹂,又或者是第十一開﹁蟹﹂
藉著墨染之間的空隙白邊即可有生動造型,將水墨沒骨筆法發揮至絕佳境
沈周│明四大家特展 │ 296297 │
界。
在沈周的寫意花卉成就中,出眾的水墨技巧並非唯一指標。沈周對物
象的形貌詮釋更具匠心,以出人意外的視點、別出心裁的選擇,沈周塑造
出深具創意的生物姿態。其中如已食畢的空蚌殼第十開﹁蚌﹂,透過幾筆
線條圈成就如日常食桌上所見。沈周筆下描繪的鳥禽,如第十二開﹁鴿﹂、
第十三開﹁雞﹂、第十四開﹁鴨﹂都是採正側向的立姿,加上睜大的圓眼,
充滿著拙趣。鴨的長頸下側還隱約可見另一層淡墨,鴨嘴微張,似乎還在
生動地啼叫一般。這樣的生動姿態,正是沈周所精心設計而成。第十六開
﹁驢﹂的頭部也有類似的處理,一些將要進行或正在進行的動作,讓這些
紙上之物,都栩栩如生、歷歷在目。
其中,又以第十五開﹁貓﹂的渾圓模樣最常被舉出,這一少見於畫
貓模式的處理,流露出沈周對家中寵物的親暱情感。依據沈周詩文︿失貓
行﹀ 72
可知他在家中確實曾經養貓,當他回憶這隻貓的外型,說道﹁憶昔烏
圓狀雖小,爪牙稜稜威比屋﹂,在他的印象中,這隻貓是﹁烏圓﹂的圓滾
滾黑貓,但爪牙卻十分銳利。﹁堆床圖籍任縱橫,所貯殽核無不足﹂堆滿
屋子的圖書典籍也都任牠奔來跑去,毫不加阻擋,即使家裡儲藏的食物也
未有禁止。但後來﹁勞多飼缺忽他走,渾舍驚呼巨能復﹂,沈周自嘲說或
是因家中鼠輩太多,此貓﹁勞多飼缺﹂而離去。至此﹁失貓招鼠知貓福﹂,
沈周這般對貓的寵暱,似乎也投射在︿寫生冊﹀畫中的烏圓貓上。而在此,
他所憶起的寵貓,其實並不盡然是能除鼠害的捕鼠角色,反是當牠蜷曲著
圓滾身體、彎著尾巴地暱在腳邊地上,那偶然慵懶地微抬著望著主人的可
愛模樣。
沈周從日常瑣物掌握生機,以獨特造型傳達意趣。不論是花草蔬果,
或是禽鳥走獸,有時乍看用筆草草,但其中物象形貌情趣卻已十足。或許
就如學者所言,沈周自稱﹁我在丹青之外﹂,可能是指其作品在完成之後,
便具備了自我獨立的生命。 73
五、沈周的詩畫與扇面
沈周詩書畫三者皆行,各有所成難分軒輊。李東陽︵一四四七
-
一五一六︶在一篇為沈周詩集所寫的序文中指出沈周﹁多以畫掩其
詩﹂,
74
前亦提到畫評者對其畫藝評價甚高。然而,沈周本人究竟如何看
待他的這三方面才能,確實也讓人好奇。至少,從不少例證可知沈周晚年
仍十分積極作詩,李東陽在這篇題序中最後提到﹁今既梓行而人誦,則詩
掩其畫亦未可知﹂,
75
似乎已體會到沈周對他的詩人身分之執著。對於沈
周詩文成就,自然須由文學史角度加以評估。
76
但從沈周的整體藝術成果
而言,對於沈周畫上自題詩文的表現,特別是從畫與詩兩種藝術型態的相
互作用,理應多予以關注。
77
其中最為突出者,則可見於沈周的扇面藝術。
摺扇並非中國原有文物。約在宋元時期自高麗、日本傳入,而在十五
世紀更因交流頻仍遂得大為流行,可說是一項十分值得重視的東亞藝術交
流產物。
78
正因摺扇廣受歡迎,沈周的前輩師友王紱就有詩文記錄了當時
人仿製日本摺扇之事。十七世紀收藏家高士奇︵一六四五
-
一七〇四︶認
為在摺扇上﹁揮灑翰墨,則始於成化間(一四六五
-
一四八七)﹂,或許
正因摺扇受到歡迎,成為士人彼此書畫題贈的重要媒材。不難想見原以畫
軸、卷冊相贈的山水,在輕巧可隨身的摺扇上更能有所發揮。摺扇書畫藝
術,自此開始成為明清文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學者亦已指出沈周當是此
發展中的主要人物,可說是﹁早期文人摺扇山水的第一個焦點﹂。 79
沈周︿秋景山水﹀︵圖版16︶即是一件掌握沈周配合扇形開展弧形畫
面上,加以構思扇面山水的佳例。這一在弧形畫面上的山水景觀,乍看下
方延伸的坡石似為一處,實則具有兩個視覺上的焦點。左側是平坡亭子,
亭中有一人獨坐賞紅葉;右側是另一處屋舍門前的二人相揖,這兩個場景
或如學者所言是﹁草亭獨坐﹂與﹁山居客至﹂兩種情節,都屬於隱居生活
中的理想意象。 80
這一左一右的視覺焦點,既各自具有獨立空間感,但又能
在弧形扇面畫幅中相互呼應。而沈周也巧妙地於中央天空留白處題上﹁己
酉仲秋寫﹂,也呼應著左右畫面中的若即若分。此一畫扇材質為金箋紙,
當以淡墨擦染山體,都能流露出細膩的光澤效果,前景山石塊面顯得晶瑩
細緻。而樹葉點紅、遠山染青,讓這一山水小品畫風更為清麗,流露出雅
緻可人的情調。本幅小扇面雖無沈周自題詩文,但不難猜想,沈周所構思
的場面或許與﹁虛亭不碍秋,落葉直入座;可人招不來,幽事如何作。﹂ 81
所傳達的詩境有關。這兩人相揖的文會雅興,正是沈周所謂的﹁幽事﹂;
而那亭中獨坐者,或許就是期待著友人來訪共游的吟詩文士。至於,這位
文士會不會就是沈周本人的寫照可能已非關緊要。因為,這類的文人生活
雅事,已是當時江南文人生活中一再反覆的共同企盼。
︿蕉陰橫琴﹀︵圖版17︶是另一有趣例子,因畫上有沈周自題,可以
更進一步說明沈周的詩畫成就。此幅扇面為人物小品,構圖同樣注意了左
右推展延伸的扇形畫面。扇幅右側為庭石與芭蕉,旁有一文士抱琴獨坐。
對照這位文士的身形看來,這庭石、芭蕉顯得十分龐大而突出。坡石地面
延伸至畫面左半部,但已無其他物象。據滿整個左側留空處的,是沈周一
首五言詩:﹁蕉下不生暑,坐生千古心;抱琴未須鼓,天地自知音。﹂寫蕉、
寫琴,也寫蕉下獨坐的士人。字裡行間流露著沈周的豁然與自得,蕉下獨
坐何極簡單容易,如此卻能澄心定意而感知千古之理。有著這樣的體悟之
後,就如抱琴未彈的文士,也能在天地之間得到知音。畫中文士身形雖小,
但經與詩文內容對照之後,其所流露的達觀自得情態卻已能有更清晰的呼
應。詩文與畫意於此扇面中相融,並藉彼此的表達而有延伸餘韻。
沈周的扇面藝術正奠基於詩畫之間的巧妙互動。對此一詩畫成就的理
解與欣賞,似乎也非僅限於熟識的朋友文人圈;
82
李東陽為人在沈周畫卷
上題跋時就曾提到﹁沈啟南以詩畫名吳中,其畫格率出詩意,無描寫界畫
之態。﹂接著說明此卷擁有者︵楊貫之︶是由另一人︵趙中美︶獲得,正
因趙氏與沈周相識,李東陽指出此卷遠比其他吳人攜出的贗本更佳,但﹁近
吳人所攜贗本充人事,似此卷者蓋少。指彼而議此,又可乎哉。﹂ 83
怎可因
畫風與他本不似而妄加論偽。許多詩文記錄都可確認沈周的詩畫受到歡迎,
並於當時文人之間就有請託求畫、得畫轉贈的各種交換情況。根據一些記
錄,不僅不少人特意到蘇州拜訪沈周,獲藉之求畫;更值得注意的是,原
在沈周生活圈的﹁吳人﹂們,也以多種角色積極地參與了﹁以沈周之名﹂
的藝術交流活動。關於現存沈周名下作品的真偽混雜的情況,多少也是在
這樣的熱潮之中不得不然的結果。只是李東陽所謂的﹁畫格率出詩意﹂仍
僅著眼於沈周畫作中的詩意傾向,即使如此,沈周詩畫二者的巧妙互動,
或許難從文字清晰描述,卻才是一直引人﹁壅塞﹂沈周家門的不言之妙。
此次展出院藏作品中,除了前述扇面作品外,亦有冊頁屬於此類詩畫
合作,但可惜此類畫冊真偽參差。其中較佳者如︿寫意﹀冊︵圖版38︶,
共計十六開,現裝潢為推篷裝,詩在上幅,畫在下幅,畫中多數題材見於
沈周其他寫生花鳥蔬果作品,此冊因有題詩而更有情思。此冊詩文與畫面
的搭配在平淡中也可見沈周自由豁達性格,如第二開畫岸邊釣者,詩作﹁一
竹自入手,江湖在竹中;無人知此意,持去問漁翁。﹂水際釣者是隱逸文
化常見意象,沈周以﹁江湖在竹中﹂喻其自得,還要﹁持去問漁翁﹂顯出
平易可近。第十開的芙蓉畫上的題詩﹁秋冷江空處,孤芳不及時;還如老
溪叟,默默有誰知。﹂原為美人意象的芙蓉,此時也被換為默默無名的﹁老
溪叟﹂。第五開詩為﹁落落數株樹,蕭蕭一箇亭;亭空人不到,辜負四山
青。﹂沈周的隱居生活即使是空亭林子,也要期待友人到訪,以免﹁辜負
四山青﹂。也正因此元代倪瓚筆下的空亭,在沈周的運用中卻已不再是潦
落空寂的孤獨,而是充滿著恬靜山色的待訪佳景。這類山水共遊的情懷,
此後也成為吳派山水中一再揚起的基調。
沈周詩畫藝術成為當時蘇州文化焦點,除是因為沈周的個人魅力之外,
沈周│明四大家特展 │ 298299 │
也與蘇州的經濟、文化的共榮盛景自十四世紀展開序曲有關。 84
以吳地山水
而言,其景色親近宜人,再因文人交流互動頻仍遂而成旅遊勝地。沈周與
友人徜徉吳中,不少沈周詩畫寫景寫情隨之傳誦流布。史鑑︵一四三四
-
一四九六︶曾記錄與沈周同遊西湖西山後,﹁啟南秉燭作圖,相與賦詩其
上,留山中為故事。﹂ 85
這類經歷不勝枚舉,︿山水﹀︵圖版04︶在朋友邀
訪後遲到,卻仍在山水間作詩的沈周形象,也是此一產物。而除這類吟詠
山水的畫作外,沈周另有一批被視為更忠實於自然景觀的地景山水的吳中
山水圖繪,例如院藏︿蘇州山水全圖﹀︵圖版26︶。此一長卷將近十七公尺,
描繪吳中勝景二十處,各有題書分別識之﹁山塘、虎丘、滸墅、天池、凰
現嶺、涅槃嶺、天平山、支硎山、支遁菴、獅山、何山、橫塘、木瀆、靈巖、
九龍塢、上方山、石湖、吳山、胥口、虎山橋、光福、太湖。﹂卷後有沈
周書風題跋。此卷應是後人摹作,但根據詩文記錄,沈周以吳中勝景為題
材的畫作必然不在少數, 86
友人吳寬甚至稱其畫比詩文更能表現勝景。
87
只
是,沈周所描繪的吳中山水卷實際面貌,卻仍有待申論。 88
而無論沈周的吳
中圖繪如何,已如其詩畫般成為明中文化的重要面向。
結論一
四九二年七月十五日沈周夜起一人獨坐,完成︿夜坐圖﹀︵圖版
21︶之際,哥倫布仍在籌劃他的發現美洲之旅;在世界兩端的二者彼此沒
有直接關連。 89
但是,兩人卻可說是未來一百年間世界文化脈動的兩個重
要觀察點。哥倫布的功績或已無需贅言;至於沈周的藝術,則不盡然僅是
蘇州相城里的小事件。沈周曾自嘲,都是因為朋友吳寬文采受到歡迎,大
家為求吳寬題字,才來求畫。根據︿和吳匏菴所題拙畫詩韻﹀後一長記,
沈周詳述了這段互動因緣。文中甚至還引旁人轉述,提到其實吳寬︵吳太
史︶當時也在抱怨太多人拿沈周畫來索題,沈周笑稱﹁不知予累太史耶?
太史累予耶?﹂豈知,吳寬此次更在題過沈周畫後又來﹁索和﹂,簡直﹁累
外生累乎﹂。如此掌握兩人互動實況後,讀起沈周這首短詩更添意趣:
﹁城裡人人要寫山,扁舟一繫即忘還;以渠褚筆忙終日,城外看山他自
閑。﹂
90
一方面道出書畫文藝的追求熱潮已然浮現,另一方面也將知交互
動的文債雅事表露無遺。這雖可解析為社會人際關係的一環,但在沈周、
吳寬之間,卻因此產出詩書畫三種不同形式彼此成就的文化平台。透過這
樣的文化脈絡,︿夜坐圖﹀的圖與文雖是十分個人的成果,卻不免也成為
傳誦、抄錄的對象。文人們彼此是作者,也是觀眾。而此後的吳派文化主
調,都是在這類似的文化平台中產製精鍊的成果,或更可說是明代中後期
文人文化的成功之處。
沈周於︿寫生﹀冊後題寫﹁若以畫求我,我則在丹青之外矣﹂,雖然
他稱﹁我在丹青外﹂,卻未必同意﹁畫﹂與﹁我﹂是對立或從屬的二元關係。
而無論畫中物象是否如學者所稱已具備生命,沈周藉此必然是在表達﹁畫﹂
與﹁我﹂的緊密相生。他所要喚起的不僅是物象生態,還在與觀看之際那
隱藏在形象外的聯繫,這一聯繫是意韻情趣上的感知融通。或許就如同︿蕉
陰橫琴﹀︵圖版17︶的詩畫要旨,即使琴未彈奏,精神心靈層面的交流自
有知音。也正因此,沈周與這些文人所建立的文化平台,似乎具備深厚的
感染力,甚至不再侷限少數親近至交。而他的朋友或求畫者,想來也正是
被這種心靈知音般的魅力所吸引。就在一次為人作畫的場合,沈周竟然把
畫題從﹁雪圖﹂錯為﹁蕉石﹂,將錯就錯寫下︿友人索雪圖誤寫蕉石﹀一詩,
﹁故人書來索寫雪,兩足楚瘡臥如折。蕉蔭小簟竹颸涼,即事便圖忘所說。
旁人笑我妄且迷,我自于時乖更戾。勸君索驥莫按圖,長可度兮大可絜。
世間萬事多是非,未必覆羹吾手捩。﹂ 91
雖然錯畫題目,但沈周勸稱﹁索驥
莫按圖﹂,世間是非又豈須介意。不過,若有更豐富文史知識背景者,必
然也已聯想到沈周雖是玩笑戲謔,表面上是錯將雪圖誤寫蕉石,實際上,
卻可能是要以﹁雪中芭蕉﹂這個古老圖式潛藏其中。而這些複雜又細膩的
文化涵養,凝聚於畫面,亦能跨越時空傳遞至今,透過作品依舊動人。
註釋
1︽明史︾︵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卷二九八,頁七六三〇。
2關於沈周的師友交遊與書法藝術,請參考本書專論陳階晉,︿沈周的藝術淵源與交遊
-
以展品選件為例﹀;何炎泉,︿沈周書法風格之發展與文化意義﹀。
3本院約三十九年前曾舉辦吳派畫特展並出版圖錄,參見江兆申,︽吳派畫九十年展︾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七五︶。
4關於吳門畫派︵吳派︶定義的討論,可參見單國強,︿"
吳門畫派"
名實辨﹀,收錄
於故宮博物院編,︽吳門畫派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一九九三︶,頁八八
-
九五。
5針對沈周的影響力與其畫史地位,艾瑞慈認為沈周堪稱﹁吳派指導者﹂,由於他的藝
術觀、人生觀的影響甚大,說是十五世紀蘇州地區最早、最明確的主導人物並不為過。
參見リチャード.エダワーズ (R
ichard Edw
ards)
,︿沈周と文徵明の藝術﹀,收錄於
︽文人畫粹編:沈周.文徵明︾︵東京:中央公論出版社,一九七八︶,頁一一九。
6︽明史︾,卷二九八,頁七六三〇。
7︵明︶王鏊,︿石田先生墓誌銘﹀,︽震澤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二九,頁
四四〇
-
四四一。
8同註7,頁四四〇。
9︵明︶沈周,︽石田稿︾,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〇二︶,冊一三三三,頁四九五。
10︵明︶文徵明,︿沈先生行狀﹀,︽甫田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二五,頁
一八四。
11︵明︶王穉登,︽國朝吳郡丹青志︾,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
一九九六︶,子部冊七一,頁八八二。
12︵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二,頁三四。另關於董其昌
對吳派的看法,參見張子寧,︿董其昌論"
吳門畫派"
﹀,收錄於故宮博物院編,︽吳
門畫派研究︾,頁一四〇
-
一五六。
13此數量仍是不完全統計之結果,主要依據︽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中國繪畫總合目
錄︾等包含中國大陸地區、日本、歐美等地公私收藏,尚未包含本院收藏。中國古代
書畫鑑定組,︽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七︶、鈴木敬編,
︽中國繪畫總合圖錄︾︵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八二
-
八三︶、戶田禎佑、
小川裕充編,︽中國繪畫總合圖錄.續編︾︵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九八
-
二〇〇一︶。
14本院所藏文物歸為沈周名下的書畫作品,參見︽故宮書畫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
物院,一九八九
-
︶,第六冊、第十八冊、第二二冊。
15
Richard E
dwards, T
he Field of Stones : A Study of the A
rt of Shen Chou (1427-1509).
Freer Gallery of A
rt. Oriental studies 5, (W
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62).
16江兆申,︿序﹀,︽吳派畫九十年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七五︶。
17江兆申,︽文徵明與蘇州畫壇︾︵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七七︶。
18
James C
ahill, Parting at the Shore: C
hinese Painting of the E
arly and Middle M
ing
Dynasty, 1368-1580. (N
ew York: W
eatherhill, Inc., 1978), pp.82-96.
此書中譯,參見
高居翰,︽江岸送別:明代初期與中期繪畫(
一三六八
-
一五八〇)
︾︵臺北:石頭出
版社,一九九七︶,頁七七
-
一〇一。
19參見中村茂夫,︽沈周ー人と藝術︾︵東京:文華堂書店,一九八二︶;林樹中,︿從
新出土沈氏墓志談沈周的家世與家學﹀,︽東南文化︾,一九八五年,頁一四一
-
一四九。
20方聞,李維琨譯,︽心印:中國書畫風格與結構分析研究︾︵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
版社,二〇〇三︶,頁一六五。
21這與傳統畫學所強調的重點不同,方聞更重視畫家與其時代思維的關聯。他將沈周
︿夜坐記﹀與陳憲章思想加以聯繫,即可見此傾向。參見方聞,︽心印:中國書畫
風格與結構分析研究︾︵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〇三︶關於此一課題的
申論,見王正華,︿沈周︿夜坐圖﹀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八九︶。
22
Richard E
dwards, T
he World around the C
hinese Artist: A
spects of Realism
in Chinese
Painting. Michigan M
onographs in Chinese Studies. (T
he University of M
ichigan, 1989),
pp.57-101.
23此一研討會後出版論文集見故宮博物院編,︽吳門畫派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一九九三︶。其中討論吳派整體議題者如單國強、周積寅、李維琨、張子寧等論文。
另針對沈周花鳥畫則有陳傳席、蕭燕翼、徐書城、顧森等論文。
24鈴木敬,︽中國繪畫史.下︾︵東京: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五︶,頁一五一
-
沈周│明四大家特展 │ 300301 │
一八四。文中,鈴木敬透過日本所藏沈周畫作討論其早期畫風部分值得重視。此一研
究課題,近有板倉聖哲持續關注。見板倉聖哲,︿九段錦??﹀,︽東洋文化研究所??
研究紀要︾︵二〇一五年預定刊登︶
25關於王鎮墓出土的書畫作品,參見徐邦達,︿淮安明墓出土書畫簡析﹀,︽文物︾,
一九八三年三期,頁一六
-
一八,九九
-
一〇四;尹吉男,︿關於淮安王鎮墓出土書
畫的初步認識﹀,︽文物︾,一九八八年一期,頁六五
-
七五,九二。運用此新發現,
檢視沈周收藏於畫史意義,參見K
athlyn Liscomb,"Shen Z
hou's Collection of E
arly
Ming Paintings and the O
rigins of the Wu School's E
clectic Revivalism
." Artibus
Asiae 52, no. 3/4 (1992): 215-254. K
athlyn Maurean Liscom
b,"Social Status and Art
Collecting: T
he Collections of Shen Z
hou and Wang Z
hen." The A
rt Bulletin 78, no.
1 (1996),PP.111-136.
26阮榮春,︽沈周︾︵長春:吉林美術出版社,一九九六︶。
27關於沈周研究,另有強調其藝術家族角色,如婁瑋,︽石田秋色:沈周家族的興盛與
衰落︾︵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書中對於沈周家族三代文藝
活動掌握深入,關於沈周收藏、書法、繪畫等各方皆有涉及。此外,由於近十年來
的沈周研究累積甚多,在此擬舉部分學位論文略以說明趨向。例如有考察沈周詩文
集︽石田稿︾編修情況者,見吳剛毅,︿沈周山水繪畫的風格與題材之研究﹀︵中
央美術學院博士論文,二〇〇二︶,頁一二
-
四〇。另有試圖從社會網絡的建立考
察沈周的繪畫活動意義,參見羅中峰,︿沈周的生活世界﹀︵中國美術學院博士論
文,二〇一一︶。另有從作品試圖檢視其與沈周思想的關聯,如前舉王正華,︿沈
周︿夜坐圖﹀研究﹀或劉梅琴、王祥齡,︿沈周﹁夜坐圖﹂與莊子︿齊物論﹀思想
研究﹀,︽故宮學術季刊︾,十四卷二期︵一九九六︶,頁一二七
-
一六七。其他
從文學史角度切入者,可見游美玲,︿沈周題畫詩研究﹀︵臺北市立師範學院碩士
論文,二〇〇五︶;顧明和,︿沈周詩畫的隱逸思考與空間對話﹀︵國立臺灣大學
碩士論文,二〇一一︶等。另亦可參考沈周研究回顧評述,徐慧、石芳,︿沈周研
究評述﹀,︽中國詩歌研究動態︾,第六輯︵二〇一〇︶,頁三七四
-
三八七。
近年新完成英文學位論文部分也見新研究取向,舉如W
etherell, Ann E
lizabeth.
"Reading B
irds:Confucian Im
agery in the Bird Paintings of Shen Z
hou (1427--1509)."
University of O
regon, 2006; Lee, C
hun-yi. "The Im
mortal B
rush:Daoism
and the
Art of Shen Z
hou (1427--1509)." Arizona State U
niversity, 2009.
28關於此一展覽與其研討會介紹,參見盧素芬,︿學者交遊,蘇州遇見沈周﹀,︽典藏.
古美術︾,二〇一二年十二月,頁二〇〇
-
二〇七。該展覽圖錄見蘇州博物館主編,︽石
田大穰-吳門畫派之沈周︾︵蘇州:蘇州博物館,二〇一二︶。
29舉如田洪、田琳,︽沈周繪畫作品編年圖錄︾︵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二〇一二︶。
30
Craig C
lunas, Elegant D
ebts: The Social A
rt of Wen Z
hengming, 1470-1559. (L
ondon:
Reaktion, 2004).
對
於
此
書
的
評
論,
參
見Susan E. N
elson,”E
legant Debts: T
he
Social Art of W
en Zhengm
ing." Ats O
rientalis 35 (2008), pp.247-51.
中文評論部分,
參見凌利中,︿︽雅債—
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辨—
暨從文徵明友人看其交游觀﹀,
︽美術史與藝術史︾,第十一期︵二〇一一︶,頁??;郭偉其,︿偉大的藝術家傳記-
讀柯律格︽雅債︾札記﹀,︽藝術觀察︾,二〇一〇年十一期,頁一三二
-
一三六;
張長虹,︿文徵明為誰作畫﹀,︽東方早報︾︵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七日︶,B
08
版︵書
評︶。
31柯律格(C
raing Clunas)
為其E
legant Debts
一書中譯出版所寫序。參見柯律格著,劉
宇珍等譯,︿致中文讀者﹀,︽雅債: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臺北:石頭出版社,
二〇一二︶,頁六
-
八。
32石守謙,︿沈周的應酬畫及其觀眾﹀,收錄於氏著,︽從風格到畫意:反思中國美術史︾
︵臺北:石頭出版社,二〇一〇︶,頁二二七
-
二四二。
33石慢(Peter Sturm
an)
,︿傳佈︿落花﹀:沈周晚年書風之複製與形塑(Spreading
Falling Blossom
s: Style and Replication in Shen Z
hou's Late C
alligraphy)
﹀,︽清華
學報︾,新四十卷第三期︵二〇一〇︶,頁三六五
-
四一〇。
34︵明︶杜瓊,︿西莊雅集圖記﹀,︽杜東原集︾︵國家圖書館影印本,一九六八︶,
頁九〇
-
九七。
35石守謙,︿隱居生活中的繪畫
-
十五世紀中期文人畫在蘇州的出現﹀,頁二〇七
-
二二六。
36關於沈周早期繪畫活動一直是重要課題。除前已指出的鈴木敬、板倉聖哲等研究外,
另可參考李鑄晉,︿沈周早年的發展﹀,收錄於故宮博物院編,︽吳門畫派研究︾,
頁一九四
-
二〇三。
37鈴木敬也曾討論日本所藏作品定年問題,鈴木敬,︽中國繪畫史.下︾,頁一六一
-
一六四。
38畫上長題見於沈周詩文集中,見︵明︶沈周,︿廬山高贈醒庵陳先生﹀,︽石田稿︾,
頁三〇五。原多依據題中稱﹁丘園肥遯七十禩﹂,推測是年陳寬七十歲。惟學者注意
到其年歲或略有兩年的差距,見吳剛毅,︿沈周山水繪畫的風格與題材之研究﹀,頁
五〇
-
五一。
39所謂﹁綠熊﹂的典故有待釐清,其中有稱﹁綠熊席﹂者,是以此熊皮毛極長而稀有。
如見︽太平御覽︾稱﹁西京雜記曰:朝陽殿設綠熊席,毛皆長一尺餘。﹂︽太平御覽︾
︵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七百九,頁十。
40何傳馨,︽沈周.中國巨匠美術週刊︾︵臺北:錦繡出版社,一九九四︶,頁六。
41江兆申據畫中山頭樹叢畫法,推測其創作年代接近︿崇山脩竹﹀,即約在一四七〇年
前後。許郭璜持相近意見。吳剛毅曾進一步從題跋內容與題跋人物活動考論,推測是
在成化五年至八年期間︵一四六九
-
一四七二年間︶畫成。參見許郭璜,︿淋漓水墨
餘清蒼--
關於本院藏沈周畫山水﹀,︽故宮文物月刊︾,第二一〇期︵二〇〇〇年九
月︶,頁六八
-
八三;吳剛毅,︿﹁米不米、黃不黃﹂
-
談院藏沈周﹁畫山水﹂軸的
創作及風格問題﹀,︽故宮文物月刊︾,第二三〇期︵二〇〇二年五月︶,頁九六
-
一一三。
42許郭璜,︿水墨微蹤認始真—
沈周︿崇山修竹﹀之畫風檢討﹀,︽故宮文物月刊︾,
三一三期(
二〇〇九年四月)
,頁一〇二
-
一一五。
43圖版參見︽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二〇一〇︶,頁一一八
-
一三三。
44王耀庭,︿沈周畫馬夏情﹀,收錄於︽中華文物學會二〇一三年刊︾︵臺北:中華文
物學會,二〇一三︶,頁四四
-
五七。
45吳鎮︿中山圖﹀屬於︿元人集錦卷﹀合卷的一段,繪於至正二年︵一三三六︶。此合
卷於明代中期屬項元汴所藏,更早之前的流傳經歷仍值得考察。現卷中有﹁金文鼎﹂
一印,金文鼎︵一三六一
-
一四三六︶生平參見楊士奇撰,︿封從仕郎中書舍人金君
墓表﹀,︽東里續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三二,頁一。
46江兆申,︽吳派畫九十年展︾,頁二九五。
47︵明︶沈周,︿題吳元玉所畫山水卷﹀,︽石田稿︾,頁四五二。
48江兆申,︽吳派畫九十年展︾,頁二九六。
49毛珵︵一四五二
-
一五三三︶生平參見︵明︶文徵明,︿毛公行狀﹀,︽甫田集︾︵文
淵閣四庫全書︶,卷二六,頁十九
-
二八。另外依據︿賀感樓先生墓誌銘﹀得知賀感
樓次子名賀恩,在家設館教學,見︵明︶吳寬,︽家藏集︾,卷六三,頁六
-
七。
50吳鎮的畫作在蘇州地區流傳情況值得進一步考察。此一︿清江春曉﹀軸上籤紙上有萬
曆時張覲宸記﹁辛巳︵一五八一︶仲冬望日。以五十金易之王越石。張覲宸識。﹂
51︵明︶沈周,︿送周桐村﹀,︽石田詩選︾,卷七,頁三九。此詩亦收入︽石田稿︾,
且可知作於乙未年︵一四七五︶。︵明︶沈周,︿送周桐村歸嘉禾二首﹀,︽石田稿︾,
頁四二四。
52︵明︶沈周,︿病中挽周桐村﹀,︽石田詩選︾,卷七,頁四七
-
四八。
53郁逢慶提及︿嘉禾八景﹀時則補述﹁後又贊畫一首雲東仙館句,似曾入姚公綬家。﹂
見︵明︶郁逢慶,︽書畫題跋記︾︵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七,頁六。
54︵明︶沈周,︽石田詩選︾卷八,頁二六。
55︵明︶杜瓊,︽杜東原集︾,頁一二三
-
一二四。﹁以其書而辨其畫之真膺,殊不知
自有早歲之作,其筆意如人之妙嫩者焉,庸可概論也。﹂
56︽石田詩選︾卷八﹁迂倪戲於畫,簡到更清臞。名家百餘禩,所惜繼者無。況有沖淡篇,
數語弁小圖。吳人助清玩,重價爭沽諸。後雖有學人,紛紛隨繁蕪。崔子彊我能,依
求胡盧。﹂卷八,頁二五。
57Richard M
. Barnhart, A
long the Border of H
eaven: Sung and Yüan Paintings from the C
.
C. W
ang Collection, (N
ew York: T
he Metropolitan M
useum of A
rt, 1983), fig. 78, pp.
164-165.
58江兆申,︽吳派畫九十年展︾,頁二九七。
59關於明代米氏山水在明代前期的流行與畫史意義,參見尹吉男,︿關於淮安王鎮墓出
土書畫的初步認識﹀,︽文物︾,一九八八年第一期,頁六五
-
七五、九二。
60︽石田詩集︾約有五首與夜坐相關。如︿立秋夜坐﹀稱﹁霜毛隨葉落,搔首忽心驚。
節物其如我,乾坤聊且生。誰家無月色,何樹不秋聲。好在清哦地,戛然庭鶴鳴。﹂、
︿秋暑夜坐﹀﹁星河垂地夜闌珊,坐久幽懐
百事關。畏老欲逃如鏡裏,苦塵難脫限人
間。一亭多竹還妨月,二水宜家又欠山。世好茫茫誰是足,秪除心迹自高閒。﹂,︿八
月一日病中即事﹀﹁旬時惟有藥追陪,斷不思拈舊酒盃。慮靜爐香宜夜坐,眼酸書卷
怯朝開。江蘋白應松鱸出,庭草紅催朔鴈來。老去苦驚時節換,壯心那復傲寒灰。﹂,
分別見於︽石田詩集︾,卷一,頁十五、頁二二。
61方聞,李維琨譯,︽心印:中國書畫風格與結構分析研究︾,頁一六四;王正華,︿沈
周︿夜坐圖﹀研究﹀,頁七
-
三八。
62此卷小楷錄有遠遊二首、少年行、江南曲、擬古、鄧攸論及夜坐記等詩文,皆不見收
於祝允明存世詩文集中。其中︿遠遊二首﹀與文震孟︵一五七四
-
一六三六︶︿擬古
遠行﹀文句有三分之二相同,確實應考慮書蹟本身的真偽。然因此卷書風與祝允明小
楷的鍾王意趣相近,也讓人驟難判偽。筆者尚無緣得見真蹟,暫以個人觀點待方家指
正。圖版見︽明祝允明遠遊二首小楷︾︵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二〇〇四︶。本項
資料為何炎泉博士提供,何博士曾多次不吝對此課題提供討論意見,謹此申謝。惟此
處所述應由筆者個人自負文責。
63其中部分文句,祝允明本讀來或有更符合文意處。但也有部分,是沈周的文理比較自
沈周│明四大家特展 │ 302303 │
然。然而,筆者以為此與文意上下文有關,仍需待深入申論。且若從︽石田稿︾稿本
的刪改情況看來,沈周詩集在出版前確實有可能進行文句增刪,現階段亦不能排除後
人所見本與原創者可能略有差異的可能性。
64依據祝允明此卷遠遊書蹟已混入後人文震孟詩文的情況而言,該卷所抄錄的︿夜坐記﹀
極可能是創作圖詩以後的再傳文本。筆者以為無需藉此質疑︿夜坐圖﹀上題記文本的
原創性。
65關於此一書風的疑慮,許郭璜曾推測或是因書寫之毛筆本身不夠講究有關。或可想像
沈周隨性拿作畫的禿筆寫成此題,筆毛既禿,當已不能操使隨心。
66﹁余始工山水,間喜作花果、草蟲,故所畜古人之製甚多,率尺紙殘墨,未有能兼之者。
近見牧溪一卷於匏庵昊公家,若果有安榴、有來擒、有秋梨、有蘆橘、有薢茩;花有
菡萏;若蔬有菰蒻、有蔓青、有園蘇、有竹萌;若鳥有乙舄、有文鳧、有鶺鴒;若魚
有鱣、有鮭;若介虫有郭索、有蛤、有螺。不施采色,任意潑墨瀋,儼然若生,回視
黃筌、舜舉之流,風斯下矣。且紙色瑩潔,一幅長三丈有咫,真宋物也。宜乎公之寶
藏也歟。﹂此卷圖像,參見︽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繪畫編.三.宋︾︵北京:紫禁
城出版社,二〇〇八︶,頁十八
-
二五。
67徐邦達推測畫卷已被換置,但沈周題跋書風卻仍可信,應是真蹟。見徐邦達,︽古書
畫偽訛考辨︾︵揚州: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下卷,頁??。
68此卷曾為︽石渠寶笈︾初編著錄,題跋稱是為王可學作。︽景印祕殿珠林石渠寶笈︾︵臺
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七一︶下冊,頁七七七。
69此卷鈐有一方司印半印,惟司印的識別問題仍有待進一步考察。丁羲元,︿典禮紀察
司印考﹀,︽故宮文物月刊︾,第二一四期︵二〇〇一年一月︶,頁六四
-
七八。
70此卷畫者是否即是沈周仍有待更多研究考察,其所牽涉的問題也十分複雜。例如本卷
雖與︽石渠寶笈.初編︾所著錄﹁宋僧法常花卉翎毛一卷﹂十分相近,但著錄稱前隔
水有﹁纈香幢鑒藏宋僧法常牧谿真蹟﹂等十三字,卻不見於現存畫卷。此外,現存卷
後查士標題則未收入著錄。有趣的是,在查士標題跋中則特別提到沈周可能是最得牧
谿之意者,﹁視此卷在離合之間,而工緻差不逮矣﹂。
71針對此一書風作者的判別,由何炎泉博士首先提出。其論依據李應禎相關書風比對,
並可參考沈周︿為孫氏作安老亭圖卷﹀︵私人收藏,圖版見︽中國繪畫總合圖錄︾第
二冊,頁一一二。︶其引首篆題亦屬李應禎所作。然而,仍有待考慮的則是李應禎逝
於弘治癸丑年︵一四九三︶七月,但沈周題跋則已是次年甲寅︵一四九四︶。在此由
於沈周並未表明作畫時段,亦不能排除李應禎題字可能早於沈周自題,惟二者關係仍
有待思考。
72︵明︶沈周,︿失貓行﹀,︽石田稿︾,頁三〇〇。
73何傳馨,︽沈周
-
中國巨匠美術週刊︾︵臺北: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九四︶,頁二六。
74︵明︶李東陽,︽懷麓堂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七四,頁四。
75︵明︶李東陽,︽懷麓堂集︾,卷七四,頁四。
76關於沈周詩文方面成就的考察,可參考范宜如,︿明代中期吳中文壇研究
-
一個地域
文學的考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二〇〇一︶;游美玲,︿沈周題畫詩研究﹀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碩士論文,二〇〇五︶。
77關於沈周詩畫藝術的討論,多篇論文曾有關注,然或多以題詩是為為解畫之文本,又
或者將題畫詩視為文學本身的材料進行討論。Peter Sturm
an
對於沈周︿落花詩并題﹀
的研究,則有意進一步掌握書法藝術與詩文內容,并聯繫到文人交遊網絡等文化課題,
或可資考慮詩畫關係之參照。
78關於摺扇藝術於東亞文化的角色,參見石守謙,︿物品移動與山水畫
-
日本摺扇西傳
與山水扇畫在明代中國的流行﹀,收錄於氏著,︽移動的桃花源︾︵臺北:允晨文化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頁二七七
-
三四四。
79石守謙,︿物品移動與山水畫
-
日本摺扇西傳與山水扇畫在明代中國的流行﹀,頁
三〇七。
80同註79,頁三〇九。
81︵明︶沈周,︽石田詩選︾,卷八,頁十九。
82石守謙曾經指出﹁沈周的應酬作品性質讓他們總是充滿了人際關係的敘事﹂。但筆者
以為從不少詩文例證可以看到這類人際關係,還應加以區分層次。不難想像,這些人
際關係如同心圓般擴大,從至親密友到殊途陌路都可能於關係網中層層外推。當然其
中仍有一些細膩的差別,讓沈周的作法並未如同職業畫家一般。石守謙認為無論親
疏,沈周都試圖與求畫者︵觀者︶建立獨特的關聯,而正因此,即便應酬客套仍可見
沈周在畫意表現上的獨特用心與創意調整。石守謙,︿沈周的應酬畫及其觀眾﹀,頁
二二九。
83︵明︶李東陽,︽懷麓堂集︾,卷四一,頁九。
84
Michael M
arme, Suzhou: W
here the Goods of A
ll the Provinces C
onver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54-186.
85︵明︶史鑑,︿記韜光庵三天竺寺四﹀,︽西村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七,頁九。
86如︵明︶王鏊,︿沈石田寄太湖圖﹀,︽震澤集︾,卷三,頁二七;︵明︶吳寬,︿跋
沈石田游張公洞詩後﹀,卷五五,頁五。
87︵明︶吳寬,︿題啟南寫遊虎丘圖﹀,︽家藏集︾,卷十二,頁九。
88這類全境式的吳中山水仍有真偽判斷的必要,其中多數冊頁已確定為後人所造。參見
曾君,︿沈周晚年︽吳中山水圖︾辨偽﹀,︽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九九年三期,
頁四七
-
六五。關於這類沈周紀遊圖繪研究狀況,可參見吳剛毅,︿沈周山水繪畫的
風格與題材之研究﹀,頁一六八
-
二二八;Jen-M
ei Ma, "Shen C
hou's Topographical
Landscape." U
niversity of Kansas, 1990.
89對此二人於同一年的活動,感謝學友盧素芬曾不吝分享其所得。關於哥倫布發現
美洲的一四九二年,當時世界各地的文化藝術活動,曾於一九九一年在美國國
家藝廊︵N
ational Gallery
︶舉辦過跨區域的展覽"C
irca 1492:Art in the A
ge of
Exploration"
,當時本院亦提供十餘件作品參展。圖錄見Jay A
. Levenson ed., C
irca
1492: Art in the A
ge of Exploration,(W
ashington, DC
: National G
allery of Art, 1991).
90︵明︶沈周,︿和吳匏菴索題拙畫詩韻﹀,︽石田稿︾,頁四九五。
91︵明︶沈周,︿友人索雪圖誤寫蕉石﹀,︽石田詩選︾,卷八,頁六
-
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