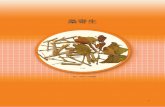,生態美學與生態普遍通訊, 2012年第十期, 2012
-
Upload
brooklyn-cuny -
Category
Documents
-
view
3 -
download
0
Transcript of ,生態美學與生態普遍通訊, 2012年第十期, 2012
台北的野狗与狗妈妈社会现象:一个生态女性关怀论述、实践与批判
張嘉如撰
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美国
除北美、欧洲的许多大城市以外,那些常被视为“公害”的野猫狗生活在人
口密集的市区中心是一个非常普遍现象。台北也不例外 。 台湾由于深受西方人类
中心主义现代化(anthropocentric modernity)之影响,也效法西方国家以扑杀的方式
来消灭资本都会中的“剩余品”。 本文将运用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即
把连结动物问题和妇女问题)来分析台湾社会对“狗妈妈”族群与野狗的威吓与排
挤。本文认为,在台湾由男性主导的消费主义社会秩序与都市空间下,狗妈妈在文
明都市的公共领域喂养非人类“野”/“狗”的行为颠复了人类男性中心主义
(androcentrism)与父权家族子嗣的价值观。台湾一般民众(多半为男性)对野狗及
狗妈妈的威吓与暴力凸显出社会上普遍缺乏一种另类“生态女性主义” 跨物种关
怀意识及尊重动物生命的生态伦理观 。从另一个角度,在台湾生态女性论述还在
尝试开辟一条具有本土色彩的佛教生态女性跨物种伦理论时,草根狗妈妈的实际照
顾行动早已超越了本土的生态女性学者的脚步。
一、颠覆男性中心主义的生态女性学说:概述西方生态女性主义跨物种关怀理论
“生态女性主义"(法文: écologie-féminisme)一词最早出于法国作家法兰
索‧多朋(Françoise d'Eaubonne) 于 1974 年出版的书。作为挑战主流生态论述的生
态女性主义有着近 40 年的历史,其流派及其庞大与复杂,本文无法详尽介绍,但
基本上,生态女性主义将人类对自然的剥削与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连结起来,认为此
两者皆为西方父权社会压迫下的产物(即压迫的对象不同,但逻辑是一样的)。西
方生态女性主义学者认为西方父权意识形态为一二元思维方式的产物。例如,澳大
利亚的生态女性主义学者普鲁姆德(Val Plumwood)认为西方文化随处充斥着“层
级二元对立”(hierarchical dualism)的观念如人/自然、男性/女性、理性/情绪、
心/身、文明/野蛮,白人/黑人或非白人,等等, 而在此二元思维当中前者总
是支配着(或被视为凌驾于)后者,进而进行占有、剥削及统治。普鲁姆德认为唯
有放弃二元式(主/客体)的意识形态,以及西方传统的理性至上、笛卡儿式的
“自我观”, 即身、心二分法的自我 (ego) 建构,以及开辟一种与外界相依连结的自
我观(relational self),以及以“关爱” 为本(care-based)、尊重万物她/它者的不同
性、以及“我-世界”互融一体的平等生态伦理观才能解决当前环境危机。1
印度生态女性学者及行动家席瓦(Shiva Vandana) 则认为第三世界女性与大
自然或土地有着更深的连结,因为她们经济与日日维生的方式多半围绕在为西方富
裕的人从事劳动生产,跟自然有着一种特殊的同伴、相依的关系。同时她们也是自
然生态知识的专家(如她们的土地农耕知识、接生婆知识)。2 但她们的知识却不
被“资本主义那过于简化的范式" (capitalist reductionist paradigm)所受到重视,因为
隔离分工的资本主义从未将自然、女性与富人的族群的兴起的这三件事情连结起来
思考。如今全球化跨国资本主义更是变本加厉地对非西方贫困或正在加速经济发展
之地区的妇女、动物和自然进行无节制的剥削,更深化全球贫富不均、环境恶化的
现象,使得全球社会/环境/动物正义成为生态批评学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议
题。
生态女性主义者最重要的贡献在于解构二元式的思维,其思维被视为剥削的
意识形态基础,以及提出扩张式的“我”、“社区”、“族群”等观念。次者,生
态女性主义批评倾向于将人的问题如阶级、性别、种族等等与非人类动物问题(如
物种歧视、动物虐待与物种灭绝等等)合并、重叠、杂揉起来一起分析。 在这里,
生态女性主义者对“它/他/她者”(the other)这个概念有一较宽容的含摄 (如
女性她者、种族他者、双性或同性恋、非人类动物它者等等)并矫正社会正义
(social justice) 与环境正义论述里的人类中心取向,动物与自然不在被视为人类资
源。第三、生态女性主义者对人的问题的含摄矫正了西方男性在分析环境或动物保
1 Palmer, Joyce. 50 Key Thinkers on the Environment. Routledge, 2001, pp. 283-8. 2 Shiva, Vandana, Staying Alive: Women,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ZedBooks, 1998, 24.
护问题常带有白人男性中产阶级环境观的偏见及“憎恨人类”(misanthropist) 之情
愫,在此“憎恨人类”情愫里的人类通常指是少数民族或低收入户的贫民。最后,
生态女性主义论述的另一贡献是对女性(或阴性)价值/特质(如情感、关怀、慈
悲等等)予以正面的肯定,不管此肯定是否基于女性在生理上与自然的认同,或来
自马克思社会主义的阶级思想(即视女性/自然/动物为被压迫者) 。玛缇‧吉儿
(Marti Kheel) 在《自然理论:生态女性主义之视角》指出西方男性环境哲学家都
“有意无意地认可男性特质优越性的想法。”3 她用“男性主义” (masculinist) 一
词来形容这些男性思想家大整体宏观式(holistic) 之 思考倾向(如用科学的统计数
字来衡量生态的平衡与否来决定哪一种物种需要被保护),以及轻蔑女性视动物为
个体及其照顾思维(如同情弱者、照料流浪动物常被视为是妇人之仁)。她认为生
态女性主义的情感(empathy) 和照顾(care)理论能够弥补现今男性主导的生态
环境论述过于理性的不足。
二、台北街头照料野狗的狗妈妈:台湾生态女性主义行动家?
任何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去过台北的人都不禁会发现在这城市中闲荡的阿猫
阿狗无处不在:它们在街上狗群狗党地在人群里窜流,跟台北都市人平行地共存在
这台北盆地里。其实猫狗早在台湾都市化前就存在,为台湾文化史的一部分,都市
化之前的人类与猫狗关系是建立在狩猎与农业共生共存之关系的基础上。随着全球
市场资本主义的到来,“宠物” (其实是一个“活玩具”)此概念以及整个宠物
消费产业开始引进台湾,猫狗摇身一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消费商品。这些动物被重新
建构成玩物和象征社会地位的附属品。 宠物文化泛滥也因而成为都市流浪猫狗族
兴起的罪魁祸首。4
3 Kheel, Nature ethics:An Ecofeminist Perspective, NY: New York, 2008, 3. 4 林妤儒,《 宠物商品化与价值变迁:分析 1950年代后犬市场的形成与变迁》, 台北:台湾大学
社会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在 1980 后的湾社会出现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群女性默默地投身照顾野
狗。这群被视为都市问题制造者的女性通常被圈外人贬称“狗妈妈”。狗妈妈照顾
野狗的方式包括所謂的 TNG 行动(捕捉、结扎、放养),有的提供住所,有的只
在固定的地點(如公園、河堤旁)喂狗。 “狗妈妈”这个社会现象超越了经济阶
层、国籍 、年龄的界限。 许多狗妈妈私人动物收容所不乏几百只野狗,而她们收
容喂养野狗的全职事业经常把她们带到破产的边缘,在加上不受到家人与社会的支
持,她们的身心皆受到极大的压力。 (如图一)
(图一:在台北河滨公园喂狗的狗妈妈。关怀生命协会主任林忆珊提供)
台湾狗妈妈的喂养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人道主义,或者基于宗教,如佛
教里的慈悲护生、轮回报应、不杀生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另一动机可能与她们在父
权社会下的“女性经验”有关。她们边缘化女性经验使她们认同那些没有声音的野
狗。这群狗妈妈之于野狗有着浓烈的正义感与道德义务感,感叹人类消费社会下的
无情与残忍。她们的作为甚至可被视为是一种佛教里六度菩萨行的具体表现。但是,
她们照料行为的却常常受到男性对她们施予的语言威吓与身体暴力。(图二)
(图二:附近居民在喂狗地区留下的“打狗棒”已示警戒。 在此,狗妈妈照顾到野
狗因狗妈妈的顾养行为而成了无辜的代罪羔羊。而狗妈妈也因为野狗安全问题而忧
心忡忡,深怕野狗遭受虐待。林忆珊提供。)
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群女性照料行动者所受的待遇反映出台湾人
一种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思想以及父系亲生子嗣抚养的情结:一个正常的人类母亲
应该在“私领域”只抚养和照顾她合法的人类子女(或被视为家庭成员的宠物),
她的职责为人类父系家庭的守护者。喂养他人的子嗣(甚至是被视为“街头活垃圾”
的流浪动物)是直接与父系子嗣的价值观相抵触。但是,如果我们将母性关怀理解
为一种有意义的“社会实践的作用”(引自萨拉·鲁迪克Sara Ruddicks的术语),并
把它像生态女性主者佳德 (Greta Gaard) 那样将此女性特殊的社会实践扩及到非
人类动物的层面,那么,这群狗妈妈就是台湾第一批本土生态女性主义的实践者。
她们博爱的跨物种、跨领域的慈母式照顾行动(换句话说,在“公”领域“养”起
一群“野”“狗”)实为颠复父权下的亲生子嗣抚养的理论观,以及男性为中心的
城市空间想象和社会秩序,也用她们行为表达出她们的反抗资本主义的有情众生的
物化与冷漠。
三. 结语 :
甘地曾说过:“一个国家伟大与否与其道德进程可从他们如何对待他们的动
物里看出。”我想应将它扩至为: “一个个人、国家或世界伟大与否与其道德进
程可从他/她(们)如何对待其社会里的人类与非人类弱势团体里看出。”动物问
题应该与人类问题非二元地结合起来一起理解、分析。从这样的视角下,我们不难
理解社会对野狗的与狗妈妈的威吓之根源来自与父权社会与资本主义的“文明”对
女性特质、劳动与价值的贬低和动物生命的物化。 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女性比
较向同情流浪动物,进而身体力行地照养它们。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越“文明”
的地区对野性、生物性的掌控越强烈,如在光鲜亮丽之都市空间里的“生物性”、
“动物性”、“野性”皆需要进行科技或拟人化的改造,不然就得排除掉 。 如果
说台湾野狗是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全球宠物消费文化的累赘物,那么这群所承受庞
大精神、社会压力的狗妈妈则成了野狗问题间接受害者。也许我们不赞同狗妈妈这
种一厢情愿的的喂养方式,但换个方式思考, 这群处于社会边缘的“狗妈妈”的
行径重新定义了家庭、社区与照顾之概念,并将儒家理想的社群伦理,即“爱吾爱
以及人之爱”同心圈(circle of compassion) 之关怀精神向外拓展到都市生态层面,
把她们爱心延伸到那群被消费、遗弃的动物族群, 并为它们争取生存权。从大乘佛
教的角度来看,她们不就是现代的人间女地藏王菩萨,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
精神,义不顾身地解救台北市都市生态中随处可见的、最底层的有情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