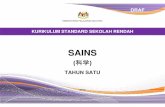王晴佳著,胡箫白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Transcript of 王晴佳著,胡箫白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学衡派”对中西文化的理解和诠释*
王晴佳 撰 胡箫白 译
内容提要 与胡适等人提倡的“新文化运动”相对立,以梅光迪为领袖的“学衡派”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
别样的诠释,对西方文明有着更全面的理解。梅光迪等人早年的教育以及留学经历极大影响了其学术旨趣。梅光迪早年接受了较完整的国学熏陶,到美国以后,又倾慕白璧德提倡的“新人文主义”,强调现代文明的成
功无法与传统相割裂。“学衡派”力图融合中西、汇通古今,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年代,突出人文的重要。“学衡
派”的努力在当时并不成功,但与现代诠释学或有异曲同工之处。
关 键 词 梅光迪 胡适 学衡派 白璧德( Irving Babbitt) 杜威
吾国之文化乃“人学主义的”(humanis-tic),故重养成个人。吾国文化之目的,在养
成君子 ( 即西方之 Gentleman and scholar orhumanist 也)。养成君子之法,在克去人性中
固有之私欲,而以教育学力发达其德慧智术。君子者,难为者也。故无论何时,社会中只有
少数君 子,其 多 数 乃 流 俗 ( The profane vul-gar)而已。弟窃谓吾国今后文化之目的尚须
在养成君子。君子愈多则社会愈良。故吾国
之文化尚须为孔教之文化可断言也。足下以
为然否?①
作为对胡适(1891 ~ 1962) 心存仰慕的老友,
梅光迪(1890 ~ 1945) 在听说胡适决意追随杜威
的实用主义后,立刻写了这封信给他。其时梅光
迪已转投白璧德门下,刚刚开始他在哈佛的学习,
而胡适已经在杜威的指导下开始了博士论文的写
作。对于梅光迪和胡适来说,美国都已不再是陌
生之地了。作为较早接受“庚款奖学金”②赞助赴
美的留学生,其时胡适已经结束了在康奈尔大学
的本科学习。而梅光迪则晚胡适一年,于 1911 年
渡至大洋彼岸,先入威斯康辛大学、再转学入西北
大学。对于当时在美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来说,
转学并不少见,转读研究生深造,更是如此。不
过,促使胡适和梅光迪最终分别选择哥伦比亚大
学和哈佛大学的原因,并非仅仅是为了取得学位,
而是如他们之间的早期交流所示,是一个综合了
个人兴趣、职业前景,并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之后
的结果。诚然,他们的选择并非完全出于个人意
愿,但也反映了他们在接受数年美式教育之后对
西方文化的理解。而他们择校深造之后造成的影
21
* 本文原题为“Toward a Humanist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 The Hermeneutics of the‘Critical Review Group’”,载 Ching - i Tu,ed. ,
Interpretatio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Chinese Hermeneu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5,蒙作者同意,
翻译成中文发表,特此致谢! ———编者。
响则非常重大:胡适、梅光迪在学成回国之后,都
成为左右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领袖人物。而他们
早年求学美国的经历,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两人
日后于文化运动中的言行、举措。虽皆求学于美国,胡适在哥伦比亚接受的教
育与梅光迪在哈佛受到的影响全然不同。在当
时,杜威和白璧德分别代表了美国迥然有别的两
股思想潮流。作为实用主义的坚决拥护者,杜威
对达尔文主义青睐有加,并认为进化论对人类不
断演进、不断适应新环境的强调已经颠覆了传统
的“精神—肉体”二元分法,因之推翻了“人类历
史演进具备必然性与目的性交织之秩序”的概
念。因此,既然精神与肉体、人类与自然不再被视
为相互独立的客体,那么先前仅仅被科学家所倡
导的科学方法亦应当可以被运用于解决人类自身
的问题。在先贤如查尔斯·皮尔士及威廉·詹姆
斯的学术成就的基础上,杜威建构了其独特的哲
学体系,即一如大卫·赫费勒所言:“注重‘现实’的问题层面。”③基于这一新颖认识,杜威开始将
研究的重点转向科学之方法应当如何运用于服务
人类社会复杂的实际和迫切需要这一问题上。作
为杜威的门徒,胡适在中国竭力宣扬乃师的此一
哲学观点,并援引杜威在氏著《我们如何思维》中
提出的“五个步骤”,用以对中国听众诠释现代科
学的概念和方法。受“工具主义”的影响,胡适将
杜威的“实用主义”翻译为“实验主义”,并在之后
以两句话简化了学说的要旨:“大胆假设,小心求
证。”胡适坚信,这两句话实际上道出了科学实验
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步骤,并且可以运用于一切形
式的学习,其中亦包括胡适日后扬名显赫的人文
学科。胡适在美期间倾心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并不为
奇。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杜威的学说同时风
行于中美两地,然而动因却不同。中国自 19 世纪
中叶开始,频繁屈服于列强的炮火之下,整个国家
为之震惊。面对这样的态势,动摇的不仅仅是清
廷危如累卵的政治统治,还有长久以来作为世界
文明领跑者的姿态与自信。对于其时中国的有识
之士来说,问题不仅仅关乎中国还能不能维系
“天下之中国”的地位,更在于这个国家究竟能否
在这场“千古未有之变局”中幸存下来。达尔文
学说中“适者生存”的概念给国人带来了强烈的
冲击,使得他们切身感受到了现代文明极具“侵
略性”的进取精神。著名者如严复,在英国的数
年间他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如何将偏于一隅的孤
僻岛国塑造成为体量庞然的殖民帝国,并刺激其
国民进行政治和文化改革。与此同时,正在上海
念高中的胡适,则正着迷于梁启超激进的时评文
章,尤其是关于帝制中国“思想进化”之必要性的
大力宣扬。虽然之后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但
胡适仍未放弃此一兴趣,身处大洋彼岸,胡适得以
阅读更多达尔文和赫胥黎的著作,因之对进化论
产生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于达尔文主义,胡适的理解其实异于其他
中国的进化论者,究其原因,则是胡适对进化论的
认识受到了他在美国所接受教育的影响。与在中
国被视为政治哲学不同,达尔文主义在 20 世纪初
以另一种表征流行于美国社会。受惠于工业革命
以及随之而来的先进科学技术,美国人步步亦趋
于“科学至上”的观念,坚信科学之于社会进步、环境改良、历史演进的无限潜力,达尔文主义中
“不断进化”的观念因之非常流行。对于“不断改
善人类生活”的渴求导致了实用主义的盛行,进
而使得达尔文主义中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的
观念转化成了社会理论和文化哲学。胡适曾论及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对此的理解:
这种进化的观念,自从达尔文以来,各种
学问都受了他的影响。但是哲学是最守旧的
东西,这六十年来,哲学家所用的“进化”观
念仍旧是海智尔④的进化观念,不是达尔文
《物种由来》⑤的进化观念。到了实验主义一
派的哲学家,方才把达尔文一派的进化观念
拿到哲学上来应用;拿来批评哲学上的结果,
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怎么叫做历
史的态度呢? 这就是要研究事务如何发生,
怎样来的,怎么样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
史的态度”。⑥
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胡适身体力行地实践
这一理念,借用余英时的话说,就是着力将之建立
成中国学术界的新“典范”。⑦为了获取有力的证
31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学衡派”对中西文化的理解和诠释
据解释“事务怎么样到现代的样子”,胡适在对中
国历史进行研究时,对资料进行严格的考订,因之
暴露了传统学术的诸般弊病,尤其是史料的保存
和流传的问题。胡适认为,如清儒所揭示,大量
窜、伪史料的存在,使得学者接受科学之训练,而
后得以重新检审史料的可靠性显得尤为必要。质
言之,即需采取运用“历史的态度”。胡适之于传
统学术的批评,尤其是置放在 1919 年爆发的“五
四”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中,使得一股“反传统”的
潮流盛行一时。虽然仅仅是一名北大的年轻教
授,学成归国不到两年,胡适立刻成为了其时中国
学界的耀眼新星,成为采用新式科学方法治学的
代表人物。然而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美国,同样风
行于全社会的达尔文主义却导出了与中国大相径
庭的后果。大卫·赫费勒分析道:“从‘进化论’的思维模式中得出的最极端的看法便是将人性与
自然现象等而视之。”这种理解否定人的精神性,
无视人类社会有其自身亘古不变的普世价值和绝
对秩序。⑧这对于那些坚信“恒常的道德秩序和文
化价值是维系现代社会健康发展之基石”的人来
说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白璧德以及他的同志穆尔
(1864 ~ 1937) 便是批判达尔文主义对于美国文
化和教育造成的不良影响的两大主力。他们强调
回归古希腊、罗马文化,坚信这样一种“复古”是
拯救现代社会的一剂良药,因此被时人冠以“新
人文主义”和“美国人文主义”领袖的称号,其中
又以白璧德最为典型。面对“杜威们”孜孜不倦
于从方法论上整合对人与自然的研究,白璧德则
心存极高的保留态度,坚持认为应该区别对待二
者,从而捍卫“人”之“完全”,而避免“科学”的无
端侵扰。在白璧德的作品中,他常常引述爱默生
的诗句,以赞颂为杜威及其拥趸因信奉达尔文主
义和科学主义而排斥的二元论调:
存在着两种法则,彼此分立而无法调和:
人类法则与事物法则;后者建立城池船舰,但
它肆行无度,僭据了人的王座。⑨
正是基于对“人类法则”“事物法则”之二元
论调的强烈执著,白璧德在美国学界擎起了“新
人文主义”的大旗,而标志其地位确立的,则是
1908 年《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一书的付梓。又尤
为引人 注 目 者,为 该 书 的 副 标 题“捍 卫 人 文 主
义”,不仅凸显了本书写作的真实意图,更是白璧
德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的确,如很多白璧德的
人物传记所论,尽管日后还出版了一些著作,但白
璧德更多是在本书中抛出了他的学术观点,至为
重要的是,该书预示了他日后的学术计划。真正
让白璧德担心的问题,一如他最敬仰的诗人爱默
生所言,是“事物在马鞍之上,驾驭着人类”⑩。换
句话说,面对“科学”对于“人文”领域的入侵,白
璧德心存担忧而奋起呼吁,号召对其进行捍卫。面对从“人文”角度尝试理解人性的做法日益衰
微,目睹“人”之独立性与自主性的逐步丧失,白
璧德哀叹道:“根据斯宾诺莎的一句著名格言,人
在自然界中并不傲然自立,而是从属于自然,是其
一部分而已。”瑏瑡
因为在现代社会,人受控于“事务法则”,丧
失了自主性,白璧德观察到了美国大学中一些不
必要、同样也叫人不愉快的改变。比如大学课程
设计中的一些传统科目,如最吸引年轻时代白璧
德的古典语言课程,便因为感兴趣的学生越来越
少而停止开设。因此,虽然于 1889 年从哈佛大学
古典系毕业,白璧德却只能在蒙太拿州的一所大
学找到教职,亦仅有几个学生愿意投其门下。同
时,他的教学任务也被限定为基础的拉丁语语法
以及沉闷的日常背诵,这让他和他的学生都感到
非常无聊。瑏瑢尽管后来白璧德将自己对古典语言
的学术兴趣由西方扩展到了东方,先赴巴黎的法
国高等研究院随列维(Sylvain Lévi)学习梵文和巴
利文,而后回到哈佛向蓝曼(Charles Lanman)继续
学习,但都无法 使 他 的 事 业 更 上 一 层 楼。1894年,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白璧德得以回到哈
佛执教,但亦非如他所愿去古典系执掌教鞭,而是
去拉丁语言文学系给低年级学生讲授初级的法语
语法,并帮助他们修改作文。白璧德接受了这样
的安排并且一年又一年地干了下去。他与校方的
合同每年一签,有时甚至面临拿不到下一年聘书
的尴尬。1912 年,在出版了两本专著以后,这位
已经在哈佛待了十八个年头的四十七岁老教师终
于拿到了终身教职,并晋升为正教授。但终其一
41
2014. 4
生,白璧德回到古典系复兴古典文化的志向一直
未能如愿。白璧德对古典文化的倡导反映在他的个人兴
趣和教学生涯的方方面面。在《文学与美国的大
学》一书中,他公开批评哈佛校长艾理特(CharlesW. Eliot)进行的课程改革。他认为,大学教授、学生和行政人员之所以对古典文化丧失兴趣,表
现出一副现代文明的傲慢态度,原因不仅仅源于
对科学幼稚的崇拜( 或如白璧德概括的“自然主
义”),还来自于“人道主义”的影响。后者在卢梭
的作品中被阐释得最为全面,然而其“自然的”及
“科学的”两种呈现方式则由培根提出。白璧德
认为,培根的哲学中“整个人类会通过科学的调
查和发现取得进步”的观念忽视了人文主义者对
个人道德和文化进行双重培养的强调。在白璧德
看来,卢梭关于“自由”的理解,尤其是他提倡人
可以不顾后果、随心所欲、放纵自我,并且身体力
行、对自己的孩子撒手不管,更为有害,因为这完
全无视了对人类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的重要性。白璧德认为,艾理特校长在哈佛推行的选课制度
便是卢梭之“人道主义”的典型实践。一旦这个
系统开始运作,哈佛学子便可以在不咨询导师的
情况下自由选课。这就意味着“与一个大学二年
级学生的爱好相比,一切时代的智慧都变成了毫
无价值的东西。任何对这种爱好的制约都是一种
不合理的限制,甚至被视为一种不可容忍的专制
暴政”瑏瑣。白璧德对此改革深表惋惜。同时,因为
很多学生不愿意学习艰深的古代语言,此一选课
系统还导致了修习古典文学的人数大为减少。白
璧德观察到:“在哈佛大学,现代文学专业( 包括
英语专业)录取的学生人数是古典文学专业录取
学生人数的五倍以上。”瑏瑤而白璧德自己也多少能
够想到,古典文学课程修课人数的减少便意味着
他再也没法一偿夙愿,回到心仪的系所任教。白璧德对美国大学中古代语言课程量减少的
担忧是他对传统文化全面考量的一个缩影。事实
上,白璧德的思想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文
主义者有不少相通之处,他们都崇尚古典文化,认
为其价值可以运用在现代文明之中。托马斯·内
文认为:“白璧德对古代语言的重视反映了他的
信仰,即他认为这些语言是文化瑰宝,其价值在提
供一种道德训诫,同样适用于现代文明。这种训
诫不但能培养硕学鸿儒,而且能促进人之操守并
开发民智。”瑏瑥18 世纪的英法知识界曾经爆发了
一场“古今之争”,白璧德则成功地调和了二者。他虽然无意重申“古典文明卫道士”的身份,却仍
然坚信古代文明,无论是西方的古希腊、罗马亦或
是东方的印度和中国,终究是维系现代社会秩序
的基础。虽然都对所处时代不满,然而白璧德与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则是他
们反驳对象的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
反对超自然的宗教力量对社会的控制,呼吁“感
官和才智的解放”;而白璧德则对科学过度自信
于其促进人类进步的能力感到不满。对他来说,
对“科学”盲目的崇信还体现在了对现代民主制
度的过度热情上。瑏瑦虽然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
主义者所做的贡献啧啧称赞,认为他们“迈出了
追求个人主义的重要一步”,他仍对“自我放纵和
自作主张”的做法持谨慎态度,而提倡“规训与选
择”。此处,“规训”一词指如何对人及其社会行
为的约束。而“选择”则表现了新人文主义的根
本原则之一,即“追求个体的养成和完善,而非笼
统地关注崇高的人类进步的问题”。对于白璧德
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尽量避免卢梭那种多
愁善感、矫情造作的人道主义。“真正的人文主
义者在同情与选择之间求得平衡”瑏瑧,白璧德如是
写道。在他看来,这是区别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
最重要的一点。新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在自我控制和
自我规训的过程中保持“平衡”。在托马斯·内
文看来,“白璧德便将文化设想为和科学具备同
等的原则性、而和宗教所提出的伦理要求相契合
的‘共同体’”瑏瑨。出乎他意料的是,白璧德对于
东西双方古代语言的熟稔使得他在这些古代文明
中找到了诸多先辈,他们的哲学帮助白璧德建构
了属于他自己的人文主义框架。不妨这么说,正
是白璧德对古希腊、印度和中国文化的精深研读
为他的哲学观念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基础,他也非
常纯熟而充满热情地将这些先贤的智慧转用至自
己的著述当中。为了诠析“自我规训”对于达成
51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学衡派”对中西文化的理解和诠释
人文主义“泰然而相宜的生活”之理想的重要性,
白璧德援引了法文中“frein vital”一词来强调人需
要“内在制约”,以控制“随心所欲”(élanvital)。瑏瑩
如果真的有所谓“人之法则”存在的话,此一“内
在制约”便是其基础,助人规避极端,而寻求生活
的平衡。这一理念不仅仅与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
和亚里士多德反复提倡的“节制与约束”相契合,
更和东方哲学互通有无。白璧德曾说:“适度的
法则乃是人生最高的法则,因为它限制并囊括了
所有其他法则。无疑,正是由于认识到了这一事
实,远东最杰出的人———佛祖———在他第一次训
诫的起首几句里便说,极端的即是野蛮的。”瑐瑠而
针对于此,托马斯·内文评论道:“白璧德从爱默
生和科尔布鲁克那里借鉴了‘内在制约’的说法,
而科尔布鲁克实际上是从东方的神秘主义中学到
了这一概念。”瑐瑡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白璧德提出
的两个概念“适度法则”与“内在制约”其实根本
不陌生,因为他们与儒家的核心思想关联密切:
“适度法则”和“中庸”内涵接近,而“内在制约”的
概念则和儒家经典,尤其是《论语》中随处可见的
“克己”含义极其相似。的确,如侯健所概括,对
于中国读者来说,“白璧德的思想与传统的中国
思想有太多相似之处了”瑐瑢,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一些白璧德的中国学生并未感觉从老师处学到很
多,却无一例外拜倒在他的足下。对于梅光迪来
说,从西北大学转学至哈佛使得他在这大洋彼岸
寻得了一位儒家贤哲:“也许我于 1915 年秋来到
剑桥的主要目的就是能够聆听这位新的圣哲的教
诲。”瑐瑣而这种敬重也是双向的。在结识了不少中
国学生之后(梅光迪应当是首位),白璧德在自己
的著作中也越来越频繁地引述儒家的观点。在早
期的作品《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中,白璧德还常常
引用《佛经》中的语句,这无疑表现出旧日学习梵
文和巴利文对他的影响。然而在 1915 年以后,白
璧德开始频繁引用儒家经典。比如在他的第三本
著作《卢梭与浪漫主义》中即有:“远东的经验还
以一种最令人感兴趣的方式完善和证明了西方的
经验。如果我们想提出一种真正世界性的智慧来
反对我们目前流行的自然主义的可怕的片面性,
我们就不能忽略这一点。”他亦认可了梅光迪在
他学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所提供的帮助。瑐瑤而对
于白璧德 1930 年写作的充满东方气质的“人文主
义:一个解释”(Humanism: A Definition),在侯健
看来,那“几乎就是一份中文作品”瑐瑥。白璧德的
另一中国学生张歆海(1900 ~ 1971) 同样也注意
到在白璧德后期的作品中,将儒家视作“伟大的
人文主义运动”瑐瑦。可以说,白璧德于佛教和儒教
之浓 厚 兴 趣,同 时 代 的 学 者 中 无 人 可 出 其 右。1960 年,当哈里·拉文被哈佛委任为比较文学专
业的“欧文·白璧德讲座”教授时,他敏锐地指
出:“白璧德对全世界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
他发掘了来自亚洲的思想对人类文明所具备的启
发意义……他也许是当时对孔子现世的哲学最具
同情的(西方 /美国———译者)学者。”瑐瑧
的确,白璧德在面对旧日的文化遗产时所秉
持的谦逊态度让不少来自亚洲的学生很有亲切
感。1923 年他在法国的巴黎大学(索邦) 讲课时,
已经被一群亚洲学生簇拥。马库斯·高曼(Mar-cus S. Goldman) 回忆道:“不少亚洲学生甚至专
门来到巴黎,只为和他聊上几句。这些学生中多
数是中国人,当然还包括不少日本人、韩国人和印
度人。这些学生将白璧德视作当世圣贤。”高曼
还转述了白璧德的朋友和同事穆尔的评论:“在
我们那时,白璧德也许是唯一的一位被东方人认
为是智者的美国学者,他也知道如何用恰当的方
式接受他们这种对老师的崇敬。”瑐瑨马西尔(LouisJ. A. Mercier),白璧德在哈佛的年轻同事(将新人
文主义引介到欧洲的第一人),亦有题为“Mouve-ment Humaniste aux tats - Unis”的回忆性文章。该文曾由吴宓翻译,发表在《学衡》杂志上。一位
中国读者评论道:“我读尽了白璧德和穆尔的所
有作品,我认为他们两人比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更为深刻。他们的作品超越了时兴
的那些肤浅轻薄、短暂易逝的学说,是人类文明与
思想的高度结晶。”瑐瑩
如果说中国学生们对于白璧德的学识感到印
象深刻的话,白璧德其实亦对这些中国学生在写
作深度和创作速度方面皆超乎美国同辈的能力感
到惊奇。吴宓曾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学生,从巴
师(译者按:即白璧德) 受学者,悉能洞明巴师讲
61
2014. 4
学之旨意,深致尊崇。又皆聪慧勤劬,课业成绩极
佳。故巴 师 及 其 夫 人,均 甚 喜 之,逢 人 辄 为 奖
誉。”瑑瑠这 在 弗 雷 德 里 克·曼 彻 斯 特 ( FrederickManchester)的回忆文章中亦能得到印证。他对白
璧德课堂上的一幕印象深刻:一天,白璧德问一个
中国学生:“为什么你比课上其他人更容易地懂
得我所讲的东西?”那位中国学生在回答时无疑
想到了中国的一个类似西方浪漫主义的运动,于
是说道:“道理很简单啊,因为中国两千年以前就
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了。”瑑瑡
尽管白璧德和他的中国学生们关系融洽( 他
的中国出生的太太朵拉·德鲁在这方面可能助力
甚多),当然,也不能说白璧德的治学路径对每一
个其时在美国的中国学生都有吸引力。事实上,
正如 1921 年他在一次中国学生年度聚会做主题
演讲时略显伤感地说道:“只有不到十个在美的
中国学生对西方学术中的艺术、文学、哲学领域感
兴趣,这太少了,应该至少有一百人才像样。在你
们的学术界中,应该有那种能够对孔子《论语》和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进 行 对 比 研 究 的 学 者 才
对。”瑑瑢最让他懊恼的是,大多数在西方留学的中
国学生都只对科学感兴趣,至多学习社会科学,而
对人文学科较少问津。瑑瑣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对于
人文主义的提倡也许相较于美国,对其时的中国
来说更为必要。而即使是在美国学习人文学科的
中国学生,如胡适,也对提倡将科学方法运用于历
史学的实用主义更加感兴趣。虽然在白璧德看
来,作为人道主义之“现代”范式的实用主义,事
实上是对人类文明失之偏颇的歪曲理解。那么那所谓的“不到十个”的勤勉的中国学
生究竟如何呢? 对这些人的学术兴趣、思想以及
在何种情况下他们做出了来到哈佛、并师从白璧
德的决定做一细致检审,实属必要之举。其中,梅
光迪是一重要人物,因为他不仅仅是白璧德的
“中国大弟子”,更在 20 世纪 20 年代成为反对新
文化运动的学生们的精神导师。梅光迪和他的同
侪之间实际存在诸多差异。与多数毕业于由美国
退还“庚款”而创立的清华学堂的学友们不同,梅
光迪在中国时所受的英语教育还极为有限。因此
1910 年他在第一次庚款考试中名落孙山便可想
而知,而他的同乡胡适则一举成功。虽然梅光迪
第二年再试成功,并被威斯康辛大学录取,但蹩脚
的英文还是让他最初的学习困难重重。然而两相
对比,他的旧学功底则非常扎实。在 1905 年清政
府取消科举考试之前,梅光迪已经应了童子试,这
在他的平辈人当中比较少见,更不用说那些留学
美国的同学了。梅光迪甚至还带了些中国古代经
典著述赴美,希望在美国上大学时把它们读完。但他很快便发现,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
乡,他所面对的困难比预想中要大得多。一方面,
他时常卖弄学问的行为引起了同学的不满,背地
里还被称为“老学究”,另一方面,他对西方文化
与语言的茫然生疏则遭到了同学们的蔑视和嘲
讽。梅光迪被迫深居简出,独自咀嚼这“人生中
最为黑暗而痛苦的日子”。而胡适的中英文都非
常流利,因此在与胡适的通信中,梅光迪常常表达
出羡慕之情。但无论如何,梅光迪仍坚持自己儒
家信徒的身份。梅光迪在 1913 年转学西北大学、结认了刘伯
明(1887 ~ 1923) 之后,处境有所改善。作为西北
大学的尖子生,刘伯明认为哈佛大学是个更好的
选择,这也最终刺激梅光迪在两年以后再次转学,
进入哈佛。瑑瑤梅光迪逐步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和学
习,他的英文也愈加流利,然而他仍然坚定地认可
自己儒学门徒的身份,并渴望调和刚毅冷静的西
方文学与中国的儒家传统。因此在听到西北大学
一位教授的无心提及之后,梅光迪立刻找到白璧
德的作品开始疯狂阅读,并将它们全部买下。梅
光迪这样回忆道: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或者
说,是个被赋予了全新意义的旧世界。第一
次,我意识到中国也必须在相同的精神的引
导下做些事情;过去二十年,我们对自己的文
化基础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无情的批判,造
成新旧文化间的差距愈拉愈大。现在,我们
要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非常时期,凭借日益积
累的资源财富,跨越这种鸿沟;要在中国人的
思想中牢固树立起历史继承感并使之不断加
强。瑑瑥
在结识白璧德 20 年后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梅
71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学衡派”对中西文化的理解和诠释
光迪表达了对乃师最真实的崇敬。正如白璧德不
愿退缩一般,梅光迪也坚持自己的信仰,那就是让
当时的中国人重拾属于自己的文化遗产,让儒家
的理念重焕生机。虽然因为这种观念,梅光迪被
同学们戏谑为“老学究”,但他还是不愿意放弃自
己的主张。恰在此时,白璧德,这位身处大洋彼岸
的“圣哲”出现了,可想而知当时的梅光迪是多么
兴奋,甚或欣喜若狂。对于梅光迪以及和他志趣
相投、以拯救中国文化为己任的中国学生来说,白
璧德的学问真正给了他们“开眼看世界”之感,那
就是用人文的、而非科学的方法来诠释东西方的
文化。这让他们开始尝试以“阐释学”的角度来
思考中国的文化改革。理查德·罗斯 (RichardRoss)这样评论道:
在白璧德的西式教育的指导下,儒家的
保守主义与西方哲学原理逐渐融合。如果儒
家时代的中国可以永垂不朽,就像文艺复兴
之前的西方持之不变一样,那就没有必要向
西方寻求科学或政治的解脱了。的确,传统
中国缺乏专门的科学技术或是普罗大众的民
主,但这亦并不重要。因为这对于一个文明
的延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瑑瑦
在得到美国导师的支持以后,梅光迪备受鼓
舞,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给胡适写了本文开头
引述的那封信,宣称不仅儒家学说是人文主义的,
而且整个中国在当时也对人文主义有着非常迫切
的需要。梅光迪 1915 年被哈佛录取,胡适则同时
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这是他们两人友情变化的
一个转折点。梅光迪不再是那个常常向胡适诉
苦、寻求答案和安慰的仰慕者了,而成为胡适推进
中国文化的民主、科学大业道路上最坚决的反对
者。当然,这个转变也非朝夕发生:梅光迪早前的
个人经历,包括他幼时的科考以及初到美国的前
几年间苦闷的日子共同为他铺就了一条通向新人
文主义的道路。的确,在从西北大学毕业之前
“发现”白璧德对他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这不仅使得他可以去哈佛投在白璧德门下,更
让他和胡适之间严肃的论辩成为可能。1915 年,
在赴波士顿途中,梅光迪前往造访了住在纽约州
旖色佳的朋友。他们和胡适的朋友们一起,就胡
适关于“文学革命”的理念进行讨论。胡适对杜
威实用主义的信奉,以及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兴趣
已经将他塑造成了对中国语言、尤其是文言文非
常坚决的批评者。他认为文言文已经不合乎时代
主流了,其讳莫如深的用典、对日用白话居高临下
的傲慢态度都让胡适认为一场“文学革命”势在
必行。而梅光迪对儒学的信奉,以及他新近接受
的人文主义信条使得他成为聚会中最为保守的一
个,并且对胡适的理念表示强烈的反对。瑑瑧
在那个炎炎夏日的激烈论辩中,双方都说服
不了对方。尽管有不断的发问与回击,但讨论本
身并无甚进展。很明显,辩论的核心已经不仅仅
是一个文言与白话的问题了,它关涉的是两拨人
对中国文化的不同见解。自从发现了令他心生敬
仰的“圣哲”以后,梅光迪更加坚信科学和理性的
时代不应该向那些保留了人类最美好之渴望与想
象、并曾经孕育了世界文明中最伟大艺术与文学
的永恒信仰宣战。瑑瑨在哈佛学习期间,梅光迪勉力
地劝说其他中国学生来跟随白璧德学习,其中即
包括吴宓、张歆海、楼光来和汤用彤。但比较而
言,梅光迪的“对手”胡适则更为成功。在 1917年回国之后,胡适不仅仅掀起了“文学革命”的热
潮,更在此成功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传统展开一
全盘而彻底的“扫荡”,也将自己塑造成了举国知
名的 思 想 领 袖。又 一 次,梅 光 迪 落 后 了。1919年,在胡适回国两年之后,梅光迪也漂洋过海回到
中国,希望和胡适进行面对面的对决。然而一开
始,梅光迪未能进入北京,仅能在天津南开大学求
得一教职,直到一年以后,经老友刘伯明邀请赴南
京的东南大学任教,梅光迪才终于找到了一处阵
地,用以向胡适及其支持者们宣战。他还催促吴
宓赶紧回国,与他并肩作战。这之后,越来越多的
白璧德门人,比如汤用彤和楼光来都加入了他们
的阵营。至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由东南大学副
校长兼教务长的刘伯明支持、英文系主任梅光迪
领导,东南大学成为反对以北京大学为阵地的新
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这场与“新文化运动”针锋相对的运动以对
中国文化传统的别样诠释为人所铭记。诠释角度
的差异在于对传统文化的革新路径不同,尤其是
81
2014. 4
在与西方文化整合的问题上。与“胡适们”要求
对传统进行“科学”的重构不同,梅光迪和他的
“战友”们认为,虽然科学的论证及研究是现代社
会的傲人产物,但它不能、也无法将人类文明演进
过程中所有的文明成就一笔抹杀。现代文化的健
康表征应该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求得平衡,一如
白璧德所言,找到“适度法则”,或如儒家经典中
的“中庸”概念所指涉的意涵一般。1922 年,由梅
光迪发起、但多数时候由吴宓负责编辑的《学衡》杂志创刊,梅光迪和同仁们郑重承诺,杂志会做到
如下几点:
(甲)本杂志于国学则主以切实之功夫,
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
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
光之价值。而后来学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
索之正轨。不至于望洋兴叹,劳而无功,或盲
肆攻击,专图毁弃,而自以为得也。(乙)本杂志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
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
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至道听途说,呼号
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丙) 本杂志行文则力求明畅雅洁。既
不堆积饾饤,古字连篇,甘为学究,尤不敢故
尚奇诡,妄矜创造,总期以吾国文字,表西来
之思想,既达且雅,以见文字之效用,实系于
作者之才力。苟能运用得宜,则吾国文字,自
可适时达意,固无须更张其一定之文法,摧残
其优美之形质也。瑑瑩
与其他目标相比,“文字力求明畅雅洁,既达
且雅,以见文字之效用”而“无须更张其一定之文
法,摧残其优美之形质也”似乎对现代的读者来
说实显琐碎,然而在当时的语境中,则是“学衡
派”区别于“文化运动者”的一大关键,表达了他
们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态度。同时,这个争辩亦是
对若干年前发生在旖色佳的激烈讨论的延续,只
不过如今这成为了两场文化运动交锋的起点。终
《学衡》存世的数十年中,它只刊发由文言文写作
的文章。而为了凸显文言文之“优美之形质”,杂
志还在每期选登对仗工整、平仄和谐的古体诗歌。学衡派对文言文的坚持,以及他们以语言问题为
切入角度理解中国文化转型的态度其实和现代阐
释学的旨趣不谋而合。正如布莱斯·瓦柯特豪瑟
尔(Brice R. Wachterhauser)所言:“语言和历史是
诠释学最重要的两个面向。”瑒瑠像很多西方现代的
诠释学家一样,学衡派也认识到语言往往是管窥
人们思想和认知的优选途径,而在这一点上,他们
和胡适的认识迥然不同。胡适认为,白话文冲出
了传统语文习惯的重重枷锁,必然会加深国人对
“科学”的现代文化的认识。尽管没能和西方的
诠释学家一样,对“人类智识超越语言和历史,从
而得以更加纯粹的认识自身”之有限性有所讨
论,但学衡派激烈地反对由胡适和陈独秀发起的
“文学 革 命”运 动,并 且 认 为 他 们 所 给 予 的 理
由———“中国语言中缺少与西方科学、艺术和文
学相对应的术语”实在是太过荒谬。对于学衡派
来说,发起如此规模的“语言改造”运动在当时实
在是没有必要,因为正如西方语言的先例一般,语
言本身会适应文化发展的步伐,而针对其间所产
生的表达和语汇问题进行不断的自我调适。瑒瑡
如果说学衡派对于语言问题的重视与诠释学
家们不谋而合的话,那么它对中西文化的历史认
知,或者说对两种文化之“历史性”的检审其实更
加符合现代诠释学的旨趣。作为“诠释学”研究
的一大关键所在,“历史性”关注“历史”和“认知”的内在联系:人类参与历史、在历史中寻求归属
感,进而得以加深对其的理解。一如海德格尔所
言,人的生命在存在论意义上是属于历史与时间
的,就像伽达默尔评论的那样,“理解不是主体诸
种可能性之一,而是‘此在’的存在方式”瑒瑢。对于学衡派来说,“历史感”对于理解文化传
统以及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重
要。早在 1917 年亦即《学衡》杂志创办之前,梅
光迪就已经在一篇写作于美国的论文中坦言:
“对于我们的生活,以及对于西方生活的诠释必
须基于一‘历史’的认知。两种文明孰优孰劣,我
们又该如何取舍,都应该建立在对它们‘历史’的
充分认知之上。毕竟,对‘历史’的洞察是规避异
想天开的现代人轻率、肤浅和华而不实举止的最
明智选择。”瑒瑣
梅光迪和其同事不仅仅想把这种理念应用在
91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学衡派”对中西文化的理解和诠释
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之上,还想借此刷新国人对西
方文明的理解。1923 年 1 月,当《学衡》创刊 1 周
年之际,杂志社特地刊印了一则内容详细、篇幅不
小的声明,阐明《学衡》杂志的创刊原因,并重申
杂志意图融汇东西方文明的宗旨。声明称,《学
衡》在当时发行的所有文学杂志中立足点特别、目的亦明确,即专注于复兴中国哲学、文学、艺术
的文化意义。同时,杂志也着力介绍西方文明之
精粹。声明最后提倡,应对东西方文明做一系统
关照和理解。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说,声明中
写道:“凡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说明、领悟、阐释、批判、系统整理、重新评价,抑或是讨论其在当代
的应用的文章,杂志统统欢迎。”而对于西学的引
介来说,则挑战更大。因为在当时,对于西方学术
的引入既缺乏必要的手段,旨趣亦容易失之偏颇。所以国人常常接受的是片面而遭曲解的西学,不
能察其全貌。如此,适度的纠正则有必要,因为
“时事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对西方文明做一次全
盘展示,揭示其真正面貌,把西方文明中最为伟大
的哲学、文学介绍给国人,让普罗大众知晓西方何
以能够成为今日之西方,确为当务之急”瑒瑤。《学衡》对“历史意识”的强调在其刊载的文
章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杂志虽由文学专业出身的
梅光迪、吴宓主持,但在他们的眼里,批评家之责
任除却博学、中正、具有道德感之外,还需要具备
“历史”之眼光。瑒瑥梅光迪言道:“凡治一学,必须
有彻底研究。于其发达之历史,各派之比较得失,
皆当悉其原委,以极上下古今融汇贯通之功,而后
能不依傍他人,自具心得,为独立之鉴别批评,其
关于此学所表示之意见,亦足取信于侪辈及社会
一般之人,此之谓有专长。”瑒瑦梅光迪认为,以历史
的角度理解问题是通往笃实学问的正确途径。学
衡派对历史的兴趣在杂志的刊选目录中表现得很
明显,作为一份文学杂志,《学衡》刊载了很多历
史学家的文章,包括王国维、柳诒徵、陈寅恪、缪凤
林、张荫麟,皆为一时之选。此外如张文建所概
括,《学衡》杂志对史学理论和方法,尤其是西方
史学领域的成果都很感兴趣,这在同时代的杂志
中显得独树一帜。比如在杂志的第一期里,便有
徐则陵对西方史学发展状况的介绍;而张荫麟基
于在西方受到的学术训练而对历史哲学的分析则
刊载在之后的一期杂志中。同时,对中国历史的
研究也受到了杂志的青睐,比如柳诒徵就在杂志
中首次连载了他著名的《中国文化史》,而陆懋德
的同名著作亦然。瑒瑧
《学衡》对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兴致既彰显
了其融汇中西文化的想法,又表现在其他的方面。杂志宣称:“《学衡》对思想与文化持一适度、温和
和中庸的态度。”瑒瑨这一态度亦表明《学衡》杂志
的“新人文主义”和“儒家”思想倾向,而在“新人
文主义”的方面表现得更突出一些。对于白璧
德、梅光迪和其他人来说,他们不愿意接受达尔文
主义的“进化论”学说,或是历史发展所遵循的绝
对秩序。借用马修·阿诺德所言,白璧德最根本
的出发点在于“聆听了解世界上最伟大的言行”。换句话说,他们不赞成现代科学的成功能够全盘
否定人类历史上取得的诸般成就。相反,如吴宓
转述阿诺德的话一般,“对古今中外最具智慧的
思想和语言”做一了解极具必要。瑒瑩而这所谓的
“思想和语言”当然亦包括那些保存在中国文化
遗产中的精粹。有鉴于此,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
统文化声势浩大的全盘否定让学衡派感到非常痛
心。但与幼稚的保守主义者不同,他们亦对西方
深邃的思想持尊敬的态度,其中不仅囊括了人文
学科的经典,亦包含现代科学之精华。学衡派对人文主义传统的崇敬、对科学主义
的抵制以及他们对新人文主义的激赏与现代阐释
学的早期学术倾向非常契合。学衡派诸君意图寻
求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之道,亦即诠释学家口中的
“历史性”来增进他们对人类的理解。伽达默尔
在其成名作《真理与方法》(Truth and Method) 第
一章中,细致地爬梳了欧洲历史中的“人文主义
传统”,并提出了另一种对其进行理解的可能性。通过对屈赖顿、狄尔泰诸人作品的讨论,伽达默尔
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差别进行厘清,而对实
证主义者力图将两者进行类比的做法提出质疑。伽达默尔之后更围绕认识论对此问题进行解释,
而凸显出人文科学的特质。这表明了现代诠释学
思想的基本前提便是接受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
差别,并且对人类思想和生活的独特性有所估计。02
2014. 4
进一步论,伽达默尔对“历史意识”的讨论,对“体
验”的重视,对“视域融合”概念的提出,遑论全书
架构中体现出来的历史视角,都与学衡派的关怀
和旨趣不谋而合。吊诡的是,早在伽达默尔之前半个世纪,白璧
德便开始挑战科学主义之权威,当时他所针对的
对象或许可以德国的历史学派为代表。德国历史
学派常常以兰克的作品为人所知,他们力图把科
学的方法运用在对人类生活的研究中,并将人文
主义置于科学主义的对立面。该学派倾向于对原
始资料进行考辨,用历史文献学(philology) 亦或
考证学的方法进行历史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然
亦产生了一些不良结果。比如在文学领域内,学
者们开始转向对文本版本流传展开探讨,而故事
内容则不再是他们关注的对象。在中国,胡适的
名声卓著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此种风潮的盛行。傅斯年创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即日后最能够代
表中国历史学发展水平的研究机构之一,亦在此
背景下应运而生。作为他们的对手,学衡派则意
图对此进行反拨。然而不客气地说,白璧德和他
的中国门徒在东西方的两场较量中其实都败下阵
来。但反过来看,其实他们对于人文主义的捍卫
亦未输得太多。让白璧德、梅光迪、吴宓甚至是他
们的对手们亦始料未及的是,在孕育了德国历史
学派的文化土壤中,同样也出现了关注文化并对
人类生活进行别样诠析的思潮。现代诠释学的兴
起正与此思潮相关。而现代诠释学的间接渊源,
又可追溯到 20 世纪初年的中美学术圈。
①胡适:《梅光迪信四十五通》,载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
书信》第 33 卷,黄山书社 1984 年版,第 466 页。②义和团运动以后,美国政府将部分“庚子赔款”用作奖学金,
支持中国学生赴美留学。③⑧大卫·赫费勒:The New Humanism: A Critique of ModernAmerica,1900 ~ 1940,夏 洛 特 维 尔: 弗 吉 尼 亚 大 学 出 版 社
1977 年版,第 30 ~ 31、29 ~ 30 页。④今多做“黑格尔”。⑤今多做“《物种起源》”。⑥胡适:《实验主义》,《胡适文存:问题与主义》第一集第二卷,
(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1986 年版,第 66 ~ 67 页。⑦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载氏著《中国思想传
统的现代诠释》,(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5 年版,第
528 页。
⑨瑏瑡转引自白璧德“What is Humanism?”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 Essays in Defense of the Humanities,波士顿:霍
顿·米夫林出版公司 1908 年版,第 29 页。中译文见白璧德
《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张沛、张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扉页。
⑩转引自白璧德“What is Humanism?”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College: Essays in Defense of the Humanities,波士顿:霍顿·米
夫林出版公司 1908 年版,第 30、29 页。又见中译本第 21 页。瑏瑢史蒂芬·布伦南、史蒂芬·亚伯勒:Irving Babbitt,波士顿:特
韦恩出版公司 1987 年版,第 15 ~ 16 页。瑏瑣白璧德:“Two Types of Humanitarians: Bacon and Rousseau”,
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 Essays in Defense of the Hu-manities,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 1908 年版,第 47 页。
瑏瑤转引自白璧德“What is Humanism?”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College: Essays in Defense of the Humanities,波士顿:霍顿·米
夫林出版公司 1908 年版,第 205 页。又见中译本第 125 页。瑏瑥瑏瑨瑐瑡托马斯·内文:Irving Babbitt: An Intellectual Study,教堂
山: 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6、19、49 ~ 50 页。瑏瑦关于白璧德对现代民主制度的看法,详参白璧德著,乔治·
帕尼查斯编 Irving Babbitt: Representative Writings,“Democracyand Standards”,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35 ~ 187 页。瑏瑧本段中引文皆译自白璧德“What is Humanism?”Literatureand the American College: Essays in Defense of the Humanities,波
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 1908 年版,第 29 页。中译文
见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张沛、张源译,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04 年版,第 1 ~ 31 页。瑏瑩白璧德:“What I Believe?”Irving Babbitt: Representative Writ-ings,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10 页。
瑐瑠白璧德:“What is Humanism,”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 1908 年版,第 23 ~ 24页。又见中译本第 16 ~ 17 页。
瑐瑢瑐瑥侯健:“Irving Babbitt in China”,纽约州立大学斯托尼布鲁
克分校博士论文,第 9、8 页。瑐瑣瑑瑥详参梅光迪回忆白璧德的文章,载弗德里克·曼彻斯特、
奥德尔·谢泼德编 Irving Babbitt: Man and Teacher,纽约:普
特南森出版公司 1941 年版,第 112 页。又见罗岗、陈春艳编
《梅光迪文录》,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9 页。瑐瑤白璧德:Rousseau and Romanticism,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
版公司 1919 年版,序言第 19 页,正文第 381 页。瑐瑦张歆海:“Irving Babbitt and Oriental Thought”,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1965 年第 4 期,第 235 页。瑐瑧哈里·拉文:Irving Babbitt and the Teaching of Literature,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7、19 页。瑐瑨瑐瑩瑑瑡弗德里克·曼彻斯特、奥德尔·谢泼德编: Irving Bab-bitt: Man and Teacher,纽约:普特南森出版公司 1941 年版,
第 238、194、130 ~ 131 页。瑑瑠吴宓著,吴学昭编:《吴宓日记》第二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第 152 页。瑑瑢白璧德,“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第 17 卷第 2 期,第 91 页。瑑瑣详参汪一驹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 ~ 1949,教
12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学衡派”对中西文化的理解和诠释
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 1966 年版;叶维力 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1900 ~ 1927,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瑑瑤梅光迪:《九年后的回忆》,《梅光迪文录》,( 台北) 联合出版
中心 1968 年版,第 28 ~ 29 页。瑑瑦理查德·罗斯: The National Heritage Opposition to the NewCulture and Literary Movement of China in the 1920s,加利福尼
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第 19 ~ 20 页。瑑瑧详参胡适的回忆文章,载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
稿》,第一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4 年版,第 214 ~215 页。瑑瑨瑒瑣梅光迪:“The Task of Our Generation”,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第 12 卷第 3 期,第 152 ~153、154 ~155 页。
瑑瑩此宣言见于各期《学衡》杂志目录之前。瑒瑠布 莱 斯:“Introduction: History and Language in Understand-ing”,载布莱斯编 Hermeneutics and Modern Philosophy,奥尔
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 页。瑒瑡详 参 吴 宓“Old and New in China”,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第 16 卷第 3 期,第 198 ~ 209 页。又可参吴宓《论新
文化运动》,《学衡》第 4 期。该文重刊于孙尚扬、郭兰芳编
《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8 ~ 96 页。瑒瑢伽达默尔:Truth and Method,纽约:十字街出版社 1988 年版,
序言第 18 页。瑒瑤详参《学 衡》第 13 期,( 台 湾) 学 生 书 局 1971 年 编 辑,第
1811 ~ 1814 页。瑒瑥详参胡先骕《论批评家之责任》,载孙尚扬、郭兰芳编《国故
新知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0 ~ 291 页。瑒瑦梅光迪:《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载孙尚扬、郭兰芳编
《国故新知论》,第 139 ~ 140 页。瑒瑧张文建:《学衡派的史学研究》,《史学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本段中其他引述皆见《学衡》各期杂志。瑒瑨详参《学衡》第 13 期,第 1811 页。瑒瑩吴宓:《文学研究法》,《学衡》1922 年第 2 期。
作者简介:王晴佳,1958 年生,北京大学历史
学系长江讲座教授,美国罗文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译者胡箫白,1989 年生,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
研究生。〔责任编辑:潘 清〕
陈田《明诗纪事》小传补正周录祥
清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一四下,收闪继迪诗一首,
小传云:“继迪字允修,保山人。万历乙酉举人,除囗囗学
官。历翰林院孔目,迁吏部司务。有《两岑园》、《秋兴》、《吴越游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09 页)
按:此段小传存几处问题。其一,“除囗囗学官”,具
体某地某职未能考知。考明高出《镜山庵集》(明万历刻本) 卷七有《送闪允
修广文擢翰林院孔目三首》。《镜山庵集》亦有数诗称闪
继迪为“闪允修广文”,广文为明清时教官( 教谕或训导)
雅称,故其先官某地教官,后任翰林院孔目。《明诗纪事》此小传盖本此,然亦未能考知具体何地何种教职。
今考民国《大名县志》卷一四《官师表·县长》,明万
历间县令有高出,云:“莱阳进士,二十五年任。”同卷《官
师表·教谕》明万历间有闪继迪,云:“云南举人。”前一人
为马华如,保山人,二十一年任;后一人为曹光彦,杞县举
人,三十一年任。又此书卷二九《艺文》录有闪继迪《礼贤
台》诗,作者小注云“闪,云南举人,万历二十五年大名教
谕”。则闪继迪于万历二十五年前后任大名教谕,或同乡
马华如所荐,而其离任大名县教谕,官翰林院孔目,则在
万历三十一年。而后又转任吏部司务。则《明诗纪诗》“除囗囗学官”,当是缺乏资料,故付阙如,今可补作“除大
名教谕”。其二,“《两岑园》、《秋兴》”应作“《雨岑园秋兴》”。光绪《永昌府志》卷六四《艺文·永人著述》有:“《雨
岑园秋兴》、《吴越吟草》,闪继迪撰。继迪,保山人,万历
乙酉举人,官吏部司务。”同书卷四二《永昌府人物志·乡
贤·明》有其小传,云:“闪继迪,字允修,保山人。……著
有《羽岑园秋兴》、《吴越游草》诸集。”则《雨岑园秋兴》,
一作《羽岑园秋兴》。明薛冈《天爵堂文集》( 明崇祯刻
本)卷三有《羽岑园秋兴诗序》,云:“……余喜不寐,因从
人望叩若翁山中十九年踪迹,遂出《羽岑园秋兴诗》见示
……允修《秋兴诗》前后各三十首,前为戊午,后为壬戌,
咸成于羽岑园,咸尽上下平韵,其间遥闻迩睹,与时迁移,
其事不一,而宣泄于声音者亦如之,惊怖其言,犹河汉而
无极……”人望即闪继迪长子闪仲俨字。又卷一七有《与
闪允修吏部》云:“……及闻仁兄山中起居康胜,《羽岑秋
兴诗》奕奕神王,足为百岁之征,而一腔忠愤,时露笔下。”盖薛冈所见诗稿,即题“羽岑园秋兴”,而羽、雨音同,故又
作“雨岑园秋兴”,至陈田《明诗纪事》撰小传不察,又形近
而讹作“两岑园秋兴”,整理者又误断作两书。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22
2014.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