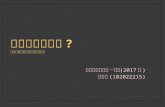尋找自己的顏色 談凱瑟琳‧佩特森小說之 ... - 學位論文上傳系統
-
Upload
khangminh22 -
Category
Documents
-
view
2 -
download
0
Transcript of 尋找自己的顏色 談凱瑟琳‧佩特森小說之 ... - 學位論文上傳系統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尋找自己的顏色尋找自己的顏色尋找自己的顏色尋找自己的顏色
────談凱瑟琳談凱瑟琳談凱瑟琳談凱瑟琳‧‧‧‧佩特森小說之認同意識佩特森小說之認同意識佩特森小說之認同意識佩特森小說之認同意識
研 究 生:李明珊 撰
指導教授:杜明城 先生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
誌誌誌誌 謝謝謝謝 辭辭辭辭
是我內心深處那個長不大的小孩敦促這故事的誕生,一直無法忘記小時候繾
綣在童話中的喜悅,在課堂中盡情抒發情感的寫作況味,大學時代得到陳國政兒
童文學新人獎的怦然心跳。之後有好長一段日子,我靜默了,遙想迦葉與佛祖的
拈花微笑,我抑制了從筆尖流露出的紛亂思緒。然而,與文字的緣是一只風箏的
線,再度引領我回到兒童文學的天空。
總覺得與兒文所的老師與同學相逢,是一段奇緣。參與每一次的課堂,就像
是赴一場心靈的盛宴。我在諸多少年小說中,尋回許多感動,也對於世事有了另
一層的領悟。如果說閱讀是一種洗禮的過程,那麼寫論文就是一項修鍊的工程。
從找到自己喜愛的作家,到發現論文題目的狂喜,到隨機受教育的驚喜,到搜索
枯腸的困頓,到功德圓滿的篤定,我一路走過春夏秋冬。而當我從作家的心靈隧
道中走了出來,我竟然切身體會到書中角色的痛,也為作家在童年時所遭遇到的
疏離,掬一把辛酸的淚。原來作家的成功能量,是來自生命所釜鑿的最深刻痕。
感謝凱瑟琳‧佩特森寫出好作品供我研究;感謝論文中參考書目的所有作者
其對學術的貢獻;感謝杜明城老師為我們安排了許多好課程,指引我論文的方
向,其博學多聞點燃了我對學術的熱情;感謝張子樟老師為我打開閱讀的一扇
窗,也教導了我正確的學習態度,其字字珠璣讓我學會簡潔;感謝郭建華老師帶
領我領略美感教育,其誠懇熱切讓我明白文學與藝術結合的可能性;感謝楊茂秀
老師教我如何思考故事,其哲學思辯讓我學會反思自己與他人的生命故事;感謝
林文寶老師在課堂上給我的鼓勵,要我再重拾寫筆;感謝家人這些日子以來的支
持,其諄諄鼓勵是我進入研究所進修的推手;感謝所有「童鞋」們的陪伴,其群
策群力促成了這段仙履奇緣。
然而故事真的畫下句點了嗎?一個故事的結束,是另一個故事的開始。我
相信當另一片光和影再度結為果子時,我們都不再是昨日的灰姑娘。
尋找自己的顏色─談凱瑟琳‧佩特森小說之認同意識
作 者作 者作 者作 者 :::: 李 明 珊李 明 珊李 明 珊李 明 珊
國 立 台 東 大 學 兒 童 文 學 研 究 所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筆者所選擇研究的作家為凱瑟琳‧佩特森(Katherine Paterson),是美國當代
重要的兒童暨青少年文學作家,其作品數量累積已多達三十多部,曾獲獎無數,
除了在美國當地擁有廣大的讀者群外,代表的幾部作品也已印成多國文字發
行。由於凱瑟琳‧佩特森成長環境特殊,其在與祖國離散並歷經一再遷徙的狀
況,使她面臨比同儕更加艱難的認同問題。
筆者以其三本少年小說《孿生姊妹》(Jacob Have I Loved)、《太平天國》(Rebels
of the Heavenly Kingdom)、《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Bridge To Terabithia)為研究文
本,並發現書中所呈現的共同脈絡:認同意識,並在文本中發現自我追尋的影
子,以此分別來談自我認同、社群認同與地方認同。本研究首先定義何為「認
同」,而筆者所欲探討的正是認同的多重樣態,輔以多稜的光線去照亮文本,
找出認同之光與影,找尋文本所呈現的心理、社會與文化意義,給予「認同」
較完整的面貌。
研究結果發現凱瑟琳‧佩特森對於青少年所面臨的心理困境有著細膩與精
準的刻畫,她的作品呈現了一種開放與包容的人生觀,而她筆下的主角也大多
能再造並擴大一己的認同。佩特森的作品之所以能擁有廣大讀者,筆者以為除
了是因其內涵的「深度」外,更在於其視野的「廣度」。藉由其文本,成年讀
者可以深入了解青少年的認同心理,而青少年讀者可以獲得一種參照與領悟。
認同確實有其不可忽視的力量,人在認同的過程中與他者互動並建構起自己的
主體, 而反身性地自省與有組織的生活規劃,成為結構自我認同的核心特徵,
也正是重塑自我的新契機。文末並指出人應該擴大其認同範圍,跳脫自我本位,
朝向整個生態圈並能包容差異。而佩特森的作品正蘊含了後現代主義重新勘定
自身邊界的可能性。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少年小說少年小說少年小說少年小說、、、、追尋追尋追尋追尋、、、、認同認同認同認同
Searching for Our Own Colors :
Identity in Katherine Paterson’s Novels
Mingshan Lee
Abstract
Katherine Paterson is the author of many award-winning books for children and yo-
ung adults. She has written more than thirty books. Her works are not only accepted by a
large number of readers but also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Becau
-se of the special growing environment and keeping moving with her parents in her child-
hood, she has more difficulties in self-identity than other peers do.
Based on the three young adult novels: Jacob Have I Loved, Rebels of the Heavenly
Kingdom, and Bridge to Terabithia, the researcher finds that identity is presented as the
common topic in the three works. Self-identity, community-identity and place-identity are
discussed respectively. The study defines first what identity is. The researcher treats the
multiple forms of identity from various angles for searching for the meanings of psycholo-
gy, society and culture and presenting a complete aspect of identity.
The study shows Katherine Paterson has fine and delicate characterization on descri-
bing the psychological difficulties of young adults. Her works have an open and tolerant
outlook on life. The characters in her works can remake and expand their identity. The
reason why Paterson’s works can attract so many readers is that her works have the dep-
th and the breadth. By reading her works, adult readers can realize teenagers’ identity
and teen readers can receive consultation and comprehension. Identity indeed has an influe
-ntial force. People build up self-identity through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ng with others, re-
flect on themselves, and organize their life plans, which becomes a core feature of constr-
ructing self-identity and a new chance of remolding. At the end of the study, it points out
that people should expand their identity and leave their own position for the main stream
with tolerating differences. Paterson’s works encompass every possibility of post-modern
-ism to explore self-boundaries.
.KeyKeyKeyKeywordwordwordwords: young adult novels, ss: young adult novels, ss: young adult novels, ss: young adult novels, search, identityearch, identityearch, identityearch, identity
目目目目 次次次次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拼圖中的自我----------------------------------------------------------------- 1
第二節 在故事中追尋------------------------------------------------------------------5
第三節 認同的光與影----------------------------------------------------------------- 10
第貳章 書寫生命-----認同意識的重構---------------------------------------------------19
第一節 作家的生命故事-------------------------------------------------------------- 20
第二節 歷史與重構-------------------------------------------------------------------- 25
第叁章 我與自己-----《孿生姊妹》中的自我認同---------------------------------- 34
第一節 生命中的認同危機-----------------------------------------------------------35
第二節 自我投射的場域-------------------------------------------------------------- 43
第三節 疏離與認同間的迴旋之旅------------------------------------------------- 55
第肆章 我與社群-----《太平天國》中的社群認同-----------------------------------61
第一節 進入另一個國度-------------------------------------------------------------- 62
第二節 自我的擴散---------------------------------------------------------------------70
第三節 逃離同一性---------------------------------------------------------------------79
第伍章 我與地方-----《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中的地方認同-------------------87
第一節 認同形塑的地方-------------------------------------------------------------- 88
第二節 認同與遷移---------------------------------------------------------------------96
第三節 小我與大我的共生----------------------------------------------------------- 103
第陸章 結論-------------------------------------------------------------------------------------110
第一節 流動的自我---------------------------------------------------------------------110
第二節 自省的力量與認同的再造--------------------------------------------------119
◎參考書目 ----------------------------------------------------------------------------------124
◎附錄 ----------------------------------------------------------------------------------------133
1
第壹章第壹章第壹章第壹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拼圖中的自我拼圖中的自我拼圖中的自我拼圖中的自我
我是我,是因為我生來如此,
而你是你,是因為你生來如此。
如果我因為你,才成為我,
你因為我,才成為你,
那麼,
我不是我,你也不是你。
──猶太教祭司孟德爾(RabbiMendel)1
一一一一、、、、....追尋自我追尋自我追尋自我追尋自我
「變色龍走到那兒就會改變自己的顏色,在檸檬上就變成黃色;在石南林中
就變成紫色;在老虎身上就出現條紋,他想說如果自己能一直停留在一片葉子,
就會永遠是綠色了;他爬到了一片最青綠的葉子上,但是葉子到秋天就轉變成
黃色,變色龍也變成黃色了………」繪本大師李歐‧李奧尼(Leo Lionni)在 A Color
of His Own 中描述一隻變色龍尋找自己顏色的故事。
許多人終其一生在追尋一個答案:「我是誰?」-------我是誰?誰是我?我
究竟可以是誰?而誰可以是我?就如同那隻變色龍不停的在尋找自己的顏色,
為了追尋自己,我們一路走來不停的被分類、被辨識、被標記,於是身上的顏
色似乎越來越斑斕,符號也越來越駁雜。當我們走進電影院,一張電影票成了
辯識我們的身分證;當我們加入一個慈善團體,一件制服提供了歸屬感的象徵;
當我們到達一個陌生的國度,黑頭髮黃皮膚提示了我們的來源。這些固定而不
斷游移的「認同」,構成了支離破碎的「我」。那麼到底什麼才是真正的我?
1 約翰‧布雷蕭 (John Bradshaw ),鄭玉英、趙家玉著,《家庭會傷人》(BRADSHAW ON:THE
FAMILY)(台北:張老師文化,2006.3),頁 65。
2
托爾斯泰曾說:「人類經常表現得不像真正的自己。」那個真我似乎常被
深深隱藏著,而假我卻高高站在人生舞台上演出糊塗的戲碼。當薛西弗斯每日
辛勞將一塊巨石推上山時,不知那塊巨石對他的意義是什麼?是一種負擔,還
是一種必然?還是那塊巨石儼然成為他的一部分了?能否無可諱言地,人自一
出生起就背負著許多「必然」,這必然來自歷史、種族、文化、社會、家庭、
遺傳等等不可抗拒的因素,我們也會遭遇到許多「偶然」,這些偶然提供人更
多的機會與面向。在這些相互依存的關係中,有些人如英雄般勇敢地踏上自我
追尋的旅程;有些人卻帶著殘障的意志為自我築起層層防衛。
人渴望完整。卡爾‧雅斯培 (Karl Jaspers,1883-1969)曾說:「所有的此在就
其自身而言 ,似乎都是圓轉的。」2,現象學也教導我們還原事物的本質,回到
事物自身。或許我們已活在生命的圓整之中,只是自己並未察覺。是的,我們
需要的只是更多的自我覺察。蘇格拉底曾言:「未經反省的生活不值得過」,
柏拉圖曾言:「認識你自己」,這些都是人生的大哉問啊!我們可以自問:是
什麼造就了我的自我認同?是什麼使我快樂?是什麼使我不快樂?那些一會兒
哭、一會兒笑的情緒是我嗎?屬於我的獨特性又是什麼?從一連串抽絲剝繭的
覺察,再經由反省而得到醒悟,才能發覺什麼是屬於自己的真我。
二二二二、、、、抹平抹平抹平抹平的的的的新新新新世界世界世界世界
筆者任教於小學,發現班上的「新移民」有日漸增多趨勢,而這些新移民
的子女比一般孩子提早面臨到「認同危機」的問題。
「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一詞最早由艾瑞克森(Erik H. Erickson,1902-1994)
提出。艾瑞克森認為:「我是由意識組成,認同(identity)指的是個體認同意
識,以自我各方面的綜合做為標準,維持一種與團體理想的內在一致性。」3認
2 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著。龔卓軍、王靜慧譯。〈圓的現象學〉,《空間詩學》(LA
POETIQUE DE L’ESPACE) (台北:張老師文化,2006.6),頁 339。 3 羅倫斯‧佛萊德曼(Lawrence J. Friedman )著,廣梅芳譯,《艾瑞克森─自我認同的建構者》
3
同強調的雖然是「同一」的建構,但也由差異造成。舉例來說,我們認同自己
為「黃種人」,那麼這世上必定還存在著其他膚色的人種,我們之所以會將自
己投入到「黃種人」的身分中,也是因有白種人、黑種人等等的存在。所以說,
認同的形成與他者認同有關。在有些種族主義刻板印象的文章中,將那些被界
定為「他者」或局外人排除在外,來建構差異。認同造成了「分別」,也因此
產生了邊緣化的否定行動,歷史上的一些迫害與戰爭,也是由此而生。
然而,在現在這個各方面交流日益頻繁的世代中,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現
象,使民族國家與舊有的社群結構崩解,產生了經濟與文化間的跨國化,也孕
育出嶄新、共享的認同:吃漢堡、穿牛仔褲不是美國人的專利,墨西哥的護國
聖像都是中國貨,在台灣吃的到各國進口的水果,你可以出國並發現和家鄉一
樣的商店與音樂等等,這些皆是文化與生活風格上匯流的現象,而且每個人都
有不同的經驗,我們如何在這個時代思考「地域性」(locality)?再者,遷徙也促
成了新的認同的出現: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移民人口增加,「在地人」與「外
地人」的通婚使得種族的界線日益模糊,更凸顯了多元性、異質性以及混合性
的存在(以台灣地區為例,在 2007 年,新移民人數已高達三十九萬人)。人們在
全球各地散佈開來,在不同的地區也形塑了各種認同。Kathryn Woodward 指出:
「這種認同既是易變的,也是使人不安的。」4
人們一方面渴望「同一性」,一方面也樂見差異的存在。全球行銷推動了
「文化同質性」,也強化了某些國家與本土的認同,它也可能導致抵制與反抗,
於是「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呼聲四起,使新的認同位置出現。這是個逐
漸被抹平的世界,競爭的型態也更加激烈,伴隨大眾傳媒尤其是電子傳媒的發
展,網路世界的發達,自我發展和社會體系間的相互滲透,正朝向全球體系邁
進。面臨各種變遷,我們再現自己的方式,例如女人、男人、父母親及勞工,
(Identity’s Architect—A biography of Erik H. Erickson)(台北:張老師文化,2001.9),頁 14。 4 Kathryn Woodward 等著,林文琪譯,《認同與差異》(Identity and Difference)(台北:韋伯文化,
2006.10),頁 29。
4
已經有了不同的樣貌。這世界存在著普遍性的認同危機,個人也在各種社會關
係中體會到了一種支離破碎的認同經驗。「越來越明顯的是生活風格的選擇,
在地方性與全球性的交互關係的情境中,引發一系列的道德難題」5,在急速抹
平的世界中,我們必須接受改變、開放心胸,去正視現代性帶來的種種差異與
例外。另外,「新社會運動」6召喚了種種形式的政治參與,也顛覆了某些既存
的固定認同,像是種族、階級、性別、以及性慾特質等等認同難題。
許多新移民的故事正是晚期現代性自我認同問題的真實縮影。新移民的認
同過程顯然比一般人辛苦。生活在台灣或美國、在家庭、學校、同儕團體或其
他場域中,在所有不同的邂逅與互動中,他們可以將自己看作是「相同的人」,
但卻也總感覺到自己是「不同的人」。這種感覺除了來自自己的特殊外表,也
因自己在不同的時間與地方中,所被定位在不同位置上的關係。不同的場合中
有不同的情境與人物,不同的人物有著不同的身分,這些人對於他們也有不同
的觀看方式,這些都影響著他們的「認同」。例如參加某場足球賽、某場音樂
會、或是參觀某個機構,或許他們會感受到彼此是相同的,但是社會期望與各
種限制,也會將他們定位在不同的位置上。如何建立自我認同永遠是人類的重
要課題,而新移民的認同問題看似冰山一角,卻讓我們發覺在晚期現代性社會7
裡「認同」這個議題的複雜性與必要性。
5 安東尼‧紀登斯著,趙旭東、方文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晚期現代的自我與社會》(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台北:心靈工坊,2005.6),頁 29。 6 同註 3,頁 41-42。一九六 0 年代以後,「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陸續在西方國家中出現,包括學生示威運動、反戰的行動主義、民權鬥爭運動、女權主義、同志運動等等。 7 「晚期」現代性又可稱為「高度」現代性,即我們現今的世界,見安東尼‧紀登斯著,趙旭
東、方文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晚期現代的自我與社會》(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頁 27。
5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在故事中追尋在故事中追尋在故事中追尋在故事中追尋
創作中的作品成了詩人的命運,並決定著他的心理發展。
不是哥德創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創造了哥德。
──榮格(C. G. Jung)8
每一個人就是一個故事,每一個故事都蘊藏一個人生。神話大師喬瑟夫‧
坎伯 (Joseph Campbell ,1904—1987)說:「人類的心總是在追求意義」9我們在成
長過程中逐漸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必須經歷的是什麼的故事,也在其中追尋存
在的經驗。我們也從其他形形色色的故事中去體會人生,與故事中角色一起悲
喜起舞、感同身受。或許,那些角色的心情是我們有過的心情,那些角色的處
境正是我們身處的囹圄,讓我們能從中獲得慰藉、頓悟與淨化。
故事是一種陪伴、一種隱喻、一種說明,我們藉由故事認識世界,了解自
己。瑞士心理分析大師榮格(Carl G. Jung, 1875-1961) 曾說:「經驗上來說,自我
(self)是以人格的形象呈現在夢境、神話與童話當中。」10榮格認為可以藉由〈灰
姑娘〉的故事,來了解原型的運作,也曾引用格林童話的故事來說明命名對無
意識所產生的作用,他認為神話與故事可以將人們與充滿情緒能量的原形結合
起來,而原型乃是一種「活生生的心靈力量」。心理分析學家阿德勒(Alfred Adler,
1870-1937)也曾說:「我們從童話中了解了相當多的人性」,11他曾以安徒生童
話 〈醋瓶〉來解釋人們任其虛榮心發展的不良後果。存在主義分析心理大師羅
洛‧梅(Rollo May, 1909-1994 )則肯定神話的重要性與功能,他認為神話能夠成為
重新了解自己的工具,神話正是我們對內在自我與外在世界關係的詮釋與整
合。他也指出,神話提供了我們個人的認同感,回答了「我是誰?」這個問題。
8 榮格 (C. G. Jung)著,蘇克譯,《尋求靈魂的現代人》(台北:遠流,1990.5),頁 167。
9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莫比爾(Bill Moyers)著,朱侃如譯,《神話》(Myth)(新店:立
緒文化,2005.7),頁 8。 10 引自耿一偉,〈導讀 女性的分析之道〉,《童話治療》(Marchen als Therapie)(台北:麥田,2004.5),頁 5。
11 阿德勒(Alfred Adler)著,陳蒼多譯,《了解人性》(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台北:大中國圖書,1991.5),頁 164。
6
當伊底帕斯哭喊著:「我必須弄清楚我是誰?我來自哪裡?」便是在描繪神話
的首要功能。12
童話是故事,神話是故事,小說是故事,還有許許多多種類的故事,伴隨
著我們的一生。從小到大,我們聽過也讀過許多故事,這其中總有我們自己特
別喜愛的故事,我們常常發現自己總是一而再的被某個故事所感動。那些特別
能打動我們的故事,正說出了我們心底的話,或許主人翁也跟我們一樣遇到相
同的困境,可喜的是最後難題通常能被解決。所有的故事表達出某一種自我理
解,故事中的主人翁則像是讀者的化身,在故事中追尋自我、追尋人生。在閱
讀故事的過程中,我們彷彿歷經一場自我探索的旅程。故事是一種象徵,背後
藏著一些概念,讀者在閱讀之前帶著自己的先驗知識,在閱讀過後,讀者從中
汲取概念與自己的先驗知識融合,同時在不自覺中形成自己的新概念。新的概
念形成後,我們看待事情有了新的角度,也展開了新的人生。而那些深深觸動
我們的故事主題,正是我們心理狀態的象徵,只是有時我們無從表達,而故事
替我們表達,也治療了我們。
舉例來說,「傳記文學」應該是最真實的故事,我們在故事中直接看到主
人翁寫實的生活,藉由此我們對照自己的人生。而在十九世紀末,宗教改革為
個人主義的興起推波助瀾,新教思想中的其中一項主張是:「將自我意識提升
到精神層次」13,個人精神意識漸漸抬頭,帶動了小說形式寫實主義的發展。像
是狄福所著的《魯賓遜漂流記》,敘述一個人如何在艱難的環境中生存,將孤
獨的生活轉化為致勝之道,也因此這本小說吸引了許多孤獨之人。柯立芝(Sam
-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 還指出魯賓遜其實:「代表所有人,他是每個讀
者都可以取而代之的角色……,他的行為、思想、痛苦、慾望,其實是每個人
12 羅洛‧梅(Rollo May)著,朱侃如譯,《哭喊神話》(The Cry For Myth)(新店:立緒文化,2003.3),頁 21。
13 艾恩‧瓦特 (Ian Watt) 著,魯燕萍譯,《小說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Novel)(台北:桂冠圖書,2002.2),頁 77,「新教思想中的兩項主張對「魯賓遜漂流記」和決定小說形式寫實主義之先決條件的發展,有兩點關鍵性的影響:一是將自我提升到精神層次,二是將道德觀與社會觀加以民主化。」
7
都可能表現出的行為、思想、感受或希求。」14 不只是寫實的作品包含真實,
而其他虛構的故事,也隱含了真實。很多故事往往牽涉到個體化(individuation)
的過程。根據榮格學派童話心理分析師瑪莉‧路易斯的分析:「其實《小王子》
這本著作正是聖艾修伯里將自身陰影(shadow)個人化的歷程。」15事實上,我們
在很多作品中看到了作家的身影。作家將自己的人生經驗投入在故事中,也同
時投射了自我意識與無意識,企圖為人生尋求出路,發現解決之道。
依榮格所言:「我們可以把個體化轉變為『走向自己』或者『實現自己』,……
自體不僅是一個人的自我……是指個人的自體,也指其他所有人的自體(selves)
:個體化並不是讓自己與世隔絕,而是收集整個世界成為他自己」。16誠如艾瑞
克森所強調的,認同的問題會出現在心理治療案主和我們每個人身上,解決之
道則在傾聽案主可能提出的各式各樣神話。綜上所述,神話處理了人的集體潛
意識,而多數的故事(包含童話與小說)則牽涉個人的個體化過程,神話與故事皆
將人們與充滿情緒能量的原型結合起來。作家所寫的故事,正代表了作家個人
的神話,它創造了作家自己,也帶領著讀者認識自己,走向自己的人生。
本研究企圖在故事中進行追尋,這故事包括作家自己本身的故事及作家筆
下的故事。其追尋目的在於研究人類的認同心理,包括認同的形成原因、過程、
結果,及認同心理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所具的影響力。榮格在〈心理學與文學〉
一文中曾指出:「人類心理是一切科學與藝術的母胎」。17所以就文本來說,必
須進行研究的是一個複雜心理過程的產物,一個顯然是有目的和有意識形成的
產物;而對作者來說,而應研究其心理機制本身。
本研究首先定義何為「認同」,筆者所欲探討的正是認同的多重樣態,包
括個人認同、社群認同、地方認同等等。由於「認同」是個複雜的課題,「認
14 同註 11,頁 81。
15 同註 8,頁 7。
16 榮格 (C. G. Jung)著,劉國彬、楊德友合譯,《榮格自傳 ─回憶、夢、省思》(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台北:張老師文化,2006.5),頁 464。
17 榮格 (C. G. Jung)著,蘇克譯,《尋求靈魂的現代人》(台北:遠流,1990.5),頁 165。
8
同」從早期哲學式的單一想像,慢慢移轉到對社會、性別、國家與文化屬性等
等,對於認同的多元意義,筆者試著用不同的理論去詮釋,所以本研究並不侷
限於一家之言。筆者所選擇研究的作家為凱瑟琳‧佩特森(Katherine Paterson), 是
美國當代重要的兒童暨青少年文學作家,其作品數量累積已多達三十多部,曾
獲獎無數,包括美國國家圖書獎、紐伯瑞獎、國際安徒生獎,更於 2006 年獲得
瑞典林格倫紀念獎的殊榮,除了在美國當地擁有廣大的讀者群外,代表的幾部
作品也已印成多國文字發行。由於凱瑟琳‧佩特森成長環境特殊,她雖然為美
國人,但由於父母在中國傳教的關係,所以出生於中國,其在與祖國離散並歷
經一再遷徙的狀況,使她面臨比同儕更加艱難的認同問題。在文獻探討部分,
筆者分別從心理學與哲學的角度去定義與說明「認同」,接著從文化屬性的角
度去探討「認同」,筆者列舉幾位具有移民背景的作家,並探討其離散經驗與
雙重文化屬性對其認同意識與文學作品產生的影響。
接著探討凱瑟琳‧佩特森自身的生命故事,而凱瑟琳‧佩特森的作品與她
的家庭背景、生活遭遇息息相關,她筆下的主角多半是孤兒、或與父母關係疏
離、或自我懷疑的孩子。她對人性的描繪相當深刻而清晰,她所刻畫的角色每
每在追尋自我認同以及愛與被愛。摩爾(John Noell Moore)曾對《孿生姊妹》(Jacob
Have I Loved)一書進行分析,他把這本書的多重閱讀(multiple readings)稱之為「稜
鏡理論」(theory as prism)。稜鏡隱喻點出,不同的光線不會以相同的方式去照亮
同一文本。18筆者以其三本少年小說《孿生姊妹》(Jacob Have I Loved)、《太平天
國》(Rebels of the Heavenly Kingdom)、《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Bridge To Terabithia)
為研究文本,並發現書中所呈現的共同脈絡:認同意識,分別來談自我認同、
社群認同與地方認同,並以心理分析為主、輔以哲學與現象學的多元角度,以
多稜的光線去照亮文本,找出認同之光與影,找尋文本所呈現的心理與社會意
義,企圖從本論文中給予「認同」較完整的面貌。
18 張子樟,〈從「閱讀」到「文本研究」─淺述文學理論與批評的應用〉,兒童文學學刊第十一期(台北:萬卷樓,2004.7),頁 130。
9
凱瑟琳‧佩特森所著的《孿生姊妹》是紐伯瑞金牌獎得獎作品,寫的正是
她小時候與同胞姊姊之間的情結,其文中所表露的情感是自傳式的,她自己曾
表示在寫作此書時歷經了極度的自我掙扎。其故事的主角露易絲生長在芮絲
島,也活在島上「重男輕女」的文化傳統之中,在加上她自覺自己只是美麗而
又才華洋溢的妹妹凱若琳的陰影,在此雙重的包夾之下,使得露易絲總在疏離
與認同間徘徊。《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是另一部紐伯瑞金牌獎得獎作品,也
是佩特森最廣為人知的一部作品。這本小說在美國十到十二歲的中的兒童普及
程度相當高,作者一生的作品共發行五百多萬本,其中本書就佔了二百多萬本,
其受歡迎的程度由此可知。此書在 1985 年曾被拍為電影,在 2007 年再度被重拍
為電影,在台灣的片名譯為「尋找夢奇地」,很貼切地點出文本的主題。《通
往泰瑞比西亞的橋》寫的是作者兒子的故事,怯懦的傑西與隨著父母不斷遷徙
的主角柏斯萊,在現實生活中與同學有些格格不入,他們所需要的只是屬於他
們兩個自己的地方(a place just for us),終於他們在另一個空間中創造了溫馨的王
國,藉由認同他們所創造的地方「泰瑞比西亞」,產生了無比的愛與勇氣。而
在《太平天國》一書中,佩特森追溯自己第二個家鄉 ──中國當時的一段歷史
事件,以一個外國移民及傳教士的觀點去重現中國文化、生活與價值觀,也釐
清一些基督教的教義,描繪這樣一個曾經「真實」存在過的「烏托邦」,筆者
認為從中去探討主角的認同意識,更具說服力也別具歷史意義。主角王立對於
太平天國這樣一個宗教社群所抱持的心態是先從懷疑,再到認同,最終選擇逃
離,對於這樣的心理過程,佩特森也有深入的描寫。
本研究由於以中文撰寫,採取的研究樣本為東方出版的《孿生姊妹》,漢
聲出版的《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及小魯出版的《太平天國》等中譯本。但慮
及作者原以英文寫作,中譯本將無可避免產生語言及文化差異等問題,筆者將
於必要時對照其原文作品,期能達到引證詳實的目的。
10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認同的光與影認同的光與影認同的光與影認同的光與影
內容死亡,平衡形式依舊存在
肉體死亡,美麗依舊存在
真實死亡,真理依舊存在
我死亡,自我依舊存在
──艾瑞克‧艾瑞克森(Erik H. Erickson)19
一一一一、、、、認同認同認同認同與心理與心理與心理與心理
「認同」是一種心理過程,這或多或少是一個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過程。所有
的認同都含有「我」的心理投射,是在自己許可的範圍之內發生的。在認同的
過程中,主體吸收另一個主體的某個方面,之後根據那主體所提供的模式,原
來的主體可能部份或全然的被改造,也因此自我是在一系列的認同中形成。「認
同」也可以視為一種「移情作用」, 它是與對象情感聯繫的原初形式。佛洛伊
德(Sigmund Freud, 1856—1938) 認為認同作用(identification)在伊底帕斯情結的早
期史起一定的作用。在小男孩形成伊底帕斯情結之前,是認同父親的,他因為
把父親當成典範,所以處處要取代他的地位,而男孩也在此同時或之後,以依
戀的形式貫注在母親身上。然而,男孩會逐漸發覺父親横阻在他與母親之間,
於是他與父親的認同就帶有敵意的色彩,伊底帕斯情結於焉產生。由此觀之,
認同的心理是矛盾而易轉變的。佛洛伊德將我分成本我、自我、超我,本我受
快樂原則的支配,一味追求滿足;自我代表理智和常識,按照現實原則來行事;
超我則以自我理想等至善原則來規範自我。而認同作用是自我的對象,如果認
同作用變得為數過多或過分強大,不同的認同作用被抵抗所相互隔斷,可能會
引起自我的分裂。
根據拉岡(Jacques Lacan,1901-1981)的精神分析指出,嬰兒會認同某個自
19 羅倫斯‧佛萊德曼 ( Lawrence J. Friedman),廣梅芳譯,《艾瑞克森─自我認同的建構者》(Identity’s Architect—A Biography of Erik H. Erickson)(台北:張老師文化,2001.9),頁 49。
11
身之外的形象,不管它是真實的形象,或只是另一個嬰兒的形象,所以「自我 (亦
我)乃是嬰兒基於身體與神經系統的不完備,而認同了與他疏離的外在他人。」
20。拉岡認為如果自我是基於某個外於我們的形象建構出來的,那麼我們的自我
認同始終就在疏離之中。所以自我有種虛妄不實的性格,佛洛伊德和拉岡皆認
為這是自我無時無刻不具有的基本特性。在拉岡的精神分析學當中,自我應被
理解成「鏡中的我」,是他人眼中的我,或是我們所願意讓別人見到的一種我,
這類似榮格所說的「人格面具」(persona)21。榮格認為自我傾向認同它在生活中
所扮演的角色,但是,自我並不限於人格面具的認同。在個人此端,自我是會
受到外在力量影響所貫穿的,這會排擠到內在的真正認同,因為當自我認同新
的內容時,這些影響會深入自我把純粹的「我是」推到一旁。一個人如果太過
認同自己的人格面具,甚至認為人格面具即是自己,則會產生危險。榮格認為
人格面具的發展在青少年時期及成年初期是個典型的重大問題,正可以與艾瑞
克森的生命週期理論相對照。
艾瑞克森用他生命的體驗,敘述著「艾瑞克森生命週期理論」。艾瑞克森
出生於德國,他的生父成謎,使他對於任何地方都沒有歸屬感,以致於一直在
遷動。他曾經改過國籍,他在美國特別強調:「一個失去國土與語言的人,特
別需要重新定為自己。」22,找尋生父、年輕時的流浪以及美國的移民,這些事
讓他始終都是邊緣人,更促使他研究「認同危機」理論。他曾在手稿中寫到:
「我就是經驗本身,其他的經驗不是我,我是由意識組成。」23艾瑞克森提到的
我或是自我,都和認同結合。艾瑞克森強調自我內在與社會的交互影響,他比
任何自我心理學家都還強調外在世界,他認為認同是自我最主要的功能,而認
同也是社會建構之下的產物。他最重要的作品是《童年與社會》(Childhood and
20 立德 (Leader, Darian)著,《拉岡》(新店:立緒文化,1998),頁 23。
21 榮格:「人格面具………是個人適應或他用來對付世界體系的方式。」(同註 15,頁 466。)
22 羅倫斯‧佛萊德曼(Lawrence J.Fruedman)著,廣梅芳譯,《艾瑞克森─自我認同的建構者》(Identity’s Architect—A biography of Erik H. Erikson),頁 92
23 同上,頁 49。
12
Society),在這本書中他將生命分為八個階段,後一個階段其實就存在於前一個
階段,每個階段都擁有共同的問題---------- 都要面對改變自己以及與別人發生
關係的部分,而「我是誰」這個問題在不同的人生階段會得到不同的答案。艾
瑞克森很重視親子的關係,他的生命週期一開始討論「信任對不信任」,接著
是「自主對羞愧及懷疑」、「主動對罪惡感」,在這早期的階段著重的是父母。
他認為自我的意識起源於小孩和他人(通常是父母)相視而笑的共同認知,在早期
自我的意識和他人的意識是分不開的,這和拉岡的「鏡像階段」非常類似。而
生命週期中最重要的階段,第五階段「自我認同對角色混淆」,此認同危機是
發生在青少年時期,艾瑞克森同意佛洛伊德「動力能量的增加是造成青春期分
裂的原因」,但他認為這只是一部分的原因而已。青少年也因新的社會衝突和
要求而變得困擾和疑惑,而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建立一種新的「自我認同感」。
. 「認同」無疑是心理學上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從嬰兒時期,到青少年時期
再延伸到成年初期,如果在這個過程中沒有審慎面對「自我認同」的問題,它
也會影響到老年時期的整合問題。
二二二二、、、、認同與存在認同與存在認同與存在認同與存在
除了從心理學的角度去分析「認同」意識,「認同」也是自古以來的哲學
家所探討過的重要命題。在哲學的研究範疇中,從柏拉圖到海德格等人,均將
「同一」( identity)和「差異」(difference)相互對照。「認同」(identification)又可
解釋為「同一性」。近代現象學家羅伯‧索柯羅斯基(Robert Sokolowski ) 認為:
「我們所經驗到的事物的同一性是在其多重表象給出。我們的自己,我們的自
我,同樣是由多重表象中給出的同一者而現身。」24現象學指出自我具有兩個對
等卻非常不同的狀態,一是「經驗自我」:把自我當做世上的種種事物之一;
24 羅伯‧索柯羅斯基(Robert Sokolowski) 著,李維倫譯,《現象學十四講》(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台北:心靈工坊文化,2007.3),頁 168。
13
一是「超越自我」:自我不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是在知覺上與認知上對世界
的擁有者。 動物有意識,但沒有超越自我,而人類的超越自我是具有公共性的,
因為人類的理性生活是在眾目睽睽的生活活動之中。「現象學的任務之一即是
從超越態度中細細地發掘出,我們種種感官知覺與運動方式如何建立出我們的
肉身存在性。」25 所以現象學所承認的自我是經由知覺、記憶、想像、選擇與
認知行動這種種成就所建構出來的同一性,它是經由延遲與差異而落實的。自
我可被視為一個行使者,而即使是強烈認同的自我都不是絕對的,因為自我是
能夠回憶與預期其他處境的我,自我並不是一個固定的點,而是一個在豐富與
多重表象與行為之中的自我。因此,以現象學的角度來分析,「認同」即是自
我(主體)持續地認取世界上的事物(客體)(包含它自己的肉身),它也持續地認取
它自己。
「現象學讓我們承認並恢復這失落的世界。曾經一度被宣稱是心理上的
(psychological)事物,現在被發現是存有上的(ontological)事物,是事物存
在的一部分」。26在現象學中,一個很重要的名詞為「意向性」,我們所有的覺
知都是指向事物,例如意識總是「對於某事某物的意識」,意向指的是我們與
事物之間的意識關係。依此來分析認同意識,那麼認同意識即是「對於某事某
物的認同意識」,而這種意識並非封閉於內心之中,這個內在的東西也同時通
達於外在,而外在的世界皆可現於內在。意向性呈現了一個共有的世界,而「認
同」更加彰顯了這個共有的世界。比方說,我認同一個社群,我的意識必然朝
向這個社群,此社群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性質,跟我的某一部分是有所相通而契
合的,於是我吸納了社群的某一部分,而此一社群就變成了擴大的「我」。
依此類推,如果我認同了某一空間,我的意識必然朝向這個空間,我為這
個空間的居有者,我賦予了這個空間意義和價值,此空間包含了我的「主體意
向性」(subjective intentionality),此即我創造了「存在空間」。「存在空間」是「人
25 同上,頁 187。
26 同註 23,頁 33。
14
文主義地理學」,特別是「存在現象學地理學」的最重要概念。27「存在空間」
必須如海德格(M. Heidegger, 1889-1976)之認為實乃一種「存有」之在世界的展現
(being-in-the-word),此意思是說居有群不僅僅在「存在空間」中消極地投射其「意
向」之影像而已,更重要的乃是居有群在其「存在空間」,積極地依據其「存
有的關懷」而不停地進行著「主體的創造」。「存在空間」的實際運作焦點,
即所謂「所在」(place,又譯為「地方」),「地方」是人們不斷地發生其「存有
意義」的場所。依照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的觀念來說明「所在」的意義如
下:「世界唯一的中心,對任何人而言,只是『我』以一個『存在的個體』所
佔有的位置。」28依此觀之,自我作為空間的中心點兒往外擴展,在此擴展的過
程中,「主體之人」不斷地投射賦予層層空間以意義和價值。「空間」與「地
方」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簡言之,「地方」為有意義的空間。
地方認同(place identity)即是由不同文化位置和地方所形成的。瑪西 Doreen
Massey)在〈全球地方感〉(A Global Sense of Place)一文中提到,質疑了視地方為
關聯於根著且真實之認同感的意義核心。她提到:「尋找『真正的』地方意義、
發掘襲產等,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是回應了置身這一切回應與變遷中,那種渴
求穩定性和認同安全感的慾望。」29她認為每個地方確實有「自己的性格」,但
它絕對不是一種沒有缝隙、連貫一致的認同,一種每個人共享的單一地方感。
因為每個人也會到不同的所在,他們所造成此地和其他地方的關聯(這包括電
話、網路、郵遞、記憶、想像等等不同物理或心智的行動),而這些都有很大的
差異。所以如果人有多重認同,那麼地方也有多重認同。「認同可以是豐富的
泉源,也可以是衝突的肇端,或者兩者皆是。」30地方應可被視為一種過程,外
27 見潘朝陽,《心靈‧空間‧環境------人文主義的地理思想》,台北:五南,2005.12,頁 68:「『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兩支現代西方哲學大流脈原本是源流同有血濃親深的關係,因此以此兩支哲學為方法論之『現象學地理學』以及『存在主義地理學』,實亦可匯合通融為『存在現象學地理學』(existential phenomenological geography)。」
28 同註 25,頁 73。
29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a short introduction)(台北:群學,2006.12),頁 109。
30 同上,頁 112。
15
界本身也構成了地方的一部分。但瑪西並未否定地方,或地方特殊性的重要,
地方確有其獨特性的根源,地方的特殊性仍不斷地被生產,而全球化並未單純
地引發同質化。
依瑪西的看法,「地方認同」應是屬於當代著名哲學家里柯(Paul Ricoeur)
所言的「敘述認同」(ipseidentity)。「敘述認同」是透過文化建構、敘事體和時
間的累積,而在時空脈落對應關係下所產生的。「『敘述認同』是在不斷流動
的建構與斡旋(mediation)過程中方能形成,它是隨時而移的,它是隨時而移
的,它不但具備多元且獨特的節奏和韻律,也經常會在文化的規範與預期形塑
下,產生種種不同的形變。」31
三三三三、、、、認同與文化認同與文化認同與文化認同與文化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了「認同」其實是個複雜的課題,在不同的情境、不
同的角度、不同的折射下,顯現出它多重的光影。「認同」從早期哲學式的單
一想像,慢慢移轉到對社會、性別、國家與文化屬性、地方認同的探討,尤其
在九 0 年代以後,「認同」這個字眼更成為跨學門與跨科際研究的重要課題。
在旅行、交流、移民等跨國行動的影響之下,許多作家皆具有雙文化的背
景,文學兼文化批評大師薩伊德(Edward W. Said)即是一例。他出身自阿拉伯裔
的基督教家庭,這個身分認同使他在他的阿拉伯祖國和在自我流放的僑居地美
國,都感受到格格不入。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他曾自述:「打從我
有記憶開始起,我就感覺到我屬於兩個世界,且無法完全地屬於任何一方」32他
也指出「流亡」並不意指有什麼悲哀或被剝奪的事情,與此相反,他認為同屬
於帝國分立的兩邊,使他能夠更容易了解他們。然而他也質疑,是否如此一種
31 廖炳惠,《關鍵詞 200》(台北:麥田,2006.7),頁 135。里柯(Paul Ricoeur)認為「認同」基本上有兩種類型,其一是「固定認同」,其二是「敘述認同」。
32 Edward W. Said 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台北:立緒,2001.10),頁 25。
16
狀態,可以真的被視為是對於屬於唯一文化、感覺只效忠於一個國家的常態之
有益的替代方案。
遊走在雙重文化的作家們,在兩個不同屬性之間,也蘊含了激盪出生命更
強大能量的可能性。薩伊德也以吉卜林(Joseph R. Kipling)(被稱做帝國主義的
吟遊詩人)及其作品為例來說明這個現象。吉卜林出生在英國,卻在被英國殖民
的印度生長,其所創作的長篇小說《金姆》33 ,為他贏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小
說中的金姆,是古怪的孤兒,他是印度的愛爾蘭人,與其生存環境無法調和。
薩伊德將《金姆》和湯姆斯‧哈代的《無名的玖德》(Jude the Obscune)拿來做參
照,他認為:兩位男孩,金姆和玖德 ,不像一般「正常」男孩,有雙親和家庭
照顧,保障其一生的平順,他們的困境之核心問題為「認同」-------是什麼、到
哪裡、做什麼的問題。他們是誰呢?他們是永不休止的追尋者和流浪者。34約克
大學的豪頓教授是研究吉卜林的權威,他則認為吉卜林藉金姆這個人物寫出了
他自己對英帝國和印度抱有的矛盾情感。金姆的身份不斷變換著,通過刻劃人
世的無常和金姆多變的性格,吉卜林鮮活地描繪出了大英帝國和印度複雜性。
而薩伊德給予吉卜林的藝術評價相當高,他在書中寫到:「他的最佳作品之力
量來自其平易和流暢,他的敘事和人物的刻畫自然而生動,他創造力之令人目
不暇給的多樣性,是可和狄更斯與莎士比亞匹敵的。」35而這樣的創造力與多樣
性,筆者以為其源頭活水來自作家精神上所處的流亡狀態。
英籍印度裔作家魯西迪在《想像的故國》(Salman Rushdie,”Imaginary
Homelands”)一文中曾提到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e),並對於流落異域的作
家其認同問題有如下的說法,此說法與薩伊德的感受是不謀而合的:「我們的
認同既是複數的又是片面的。有時我們覺得自己橫跨兩個文化;有時我們又兩
頭落空。」36 在華裔美國作家中,湯亭亭無疑是自 1970 年代後期以來,最受矚
33 《金姆》在國內也被改寫為兒童文學作品,題名為《小吉姆的追尋》,由天衞文化出版。
34 同註 33,頁 284。
35 同上,頁 286。
36 轉引自單德興,〈湯亭亭的認同〉,《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台北:麥
17
目的一位,其作品暢銷於美國市場且頗獲好評。早期對於湯亭亭----尤其是對於
《女戰士》的研究,許多是以女性書寫及自傳的角度來探討湯亭亭的自我成長、
肯定和認同,這些都與文化認同的問題息息相關。單德興在《銘刻與再現-----
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中,即針對湯亭亭的認同問題進行個案研究。他又
提及第一本亞裔美國文學選集《亞美作家》,緒論一開始就提出兩位華裔作家
趙健秀和李金蘭對於認同的不同見解:趙堅持要問「你的認同何在?」(“Where
is your identity?”),而李則自稱「沒有認同的掛念」(“I have no identity hang-ups
”) 。編者以此引出認同的問題,認為族裔意識對於亞裔美國人意義重大。單
德興認為亞裔文學選集伊始,認同便是主要議題,其重要性至今未休。37另一位
著名的華裔作家譚恩美(Amy Tan),其暢銷小說《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 ,
雖是以探討母女系為主軸,但其中我們也看到了中國女性在異鄉成長的困難與
掙扎,也看到了作家在其中所鑲嵌的認同影子,在〈兩面〉這一章,她如此寫
著:「我思忖著我的意向。那一面是美國的?那一面是中國的?那一面占上風?
如果你展現其一,妳總要犧牲另外一面。」38或許就是這種失去歸屬感所產生的
不安,使得這部作品更具張力,也更見其深刻。這部暢銷長篇小說繼而被改編
成配有插圖的兒童文學、電影,成為不同呈現方式的文化產品。
誠如 Paul Ricoeur 所提及的,在看待文本寫作的時候,同時也必須注意到文
本寫作的環境背景。具有移民背景的作家由於空間的變革、時間的輾轉,都造
成其身份/屬性的變質,於是,他們要「重建」知識分子的文化身份--在一
個與祖國離散的空間之中。在這樣的時空中,往昔的文化屬性不再固定,血緣
也不再是身份的判準,身份已然是一種「尋找定位」(positioning)的工程。在作
家的心理,不同的空間不但會交流,空間本身也無法沈滯如死水。那麼,由空
間培烤出來的身份(identity)當然不會永久定型。它可能時時變異,因循現實的節
田,2000.9),頁 176。 37 轉引自單德興,〈湯亭亭的認同〉,《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頁 248。
38 譚恩美(Amy Tan)著,于人瑞譯,《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台北:聯合文學,1990.3),頁 293。
18
拍而作不同的律動。許多擁有雙重文化背景的作家,其內心的空間屬性(如故國
懷鄉情結)會隨著政治或經濟局勢的變遷而轉換風情,而此情結在現實環境的挾
制下,通常呈現出更複雜曲折的文本。
在兒童文學的領域中,也有一些具有雙重文化背景的作家,除了前文所提
及的英國作家吉卜林,近期還有紐伯瑞得獎作家 Jean Fritz(琴‧弗利慈)和葉祥添
(Laurence Yep)。Jean Fritz(琴‧弗利慈)與凱瑟琳‧佩特森生長背景很類似,她出
生於中國漢口,父母同樣是美國傳教士,身為傳教士家庭中的獨身女,經常感
到孤單,感覺被錯置了國家。因為對美國產生強烈的情感連結,而萌發出思鄉
情懷,而寫出她的童年故事《家在地球的另一端》(Homesick, My Own Story): 故
事中住在地球這一端的琴,並不覺得自己像是真正的美國人。而在 China-Home
coming 此書中,她重新發覺自己的生命根源,書寫的過程正是她重新發現自己
的經驗,而我們在其書中發現認同與鄉愁也正是文化建構的產物。同樣地,擁
有雙重文化背景的華裔作家葉祥添(Laurence Yep),在成長過程中也難免產生格
格不入的情感,認同問題帶給他許多困擾與不安,他筆下的主角常表露一種異
於他人的疏離。《龍翼》與《龍門》皆是作者刻意回到過去,試圖爲遭受貶抑
的華人祖先重新定位的作品。
由上述這些實例,筆者發現認同無所居處的困頓感所導致之精神流亡狀態
,確實可為種種形式的創作帶來許多動能;透過創作,個人於其間將記憶、情
感、欲望、想像等元素進行放空、追蹤、接合、拼湊、跳接,在這自我與實物
往返的過程中,對認同的焦慮也彷彿才得以賦形,而轉化。而具有雙重文化背
景的作家,其認同心理未必相同,而其離散經驗對作品也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凱瑟琳‧佩特森也有著中國與美國的雙重文化背景,其「認同」問題也深
深影響著她的成長過程,在下一章節筆者將再深入探討佩特森的生命故事,以
更能了解其寫作背景及其對作品的影響。
19
第貳章第貳章第貳章第貳章 書寫生命書寫生命書寫生命書寫生命————認同意識的重構認同意識的重構認同意識的重構認同意識的重構
筆者之所以選擇凱瑟琳‧佩特森(Katherine Paterson)的作品作為研究的文
本,是因為在她多本書中發現認同的濃厚影子,她的第一部作品的書名即為:
Who am I?(1966)。凱瑟琳‧佩特森的成長環境特殊:她是美國人,卻在中國出
生。既有美國如生父,中國如養父,佩特森的身分顯得多重而模糊。因為父母
親都是傳教士的關係,所以童年過著四處遷徙的生活,在她十八歲之前,搬家
的次數超過十五次之多,在二十五歲那年又遠赴日本傳教。佩特森從小就要學
會與自己不同膚色的孩子相處,不斷的與舊朋友分離、與新朋友相識,還要面
臨不停轉換的空間。凱瑟琳‧佩特森的童年在認同與離散間輾轉,跟艾瑞克森
一樣,早年不停地流浪,她的童年確實過得比別人艱辛,也迫使她提早思索:
Who am I?的認同課題。不同的是,艾瑞克森從心理學中尋找生命的答案,而
佩特森則從文學中找到抒發的管道與治療的能量。她承認自己小時候是個「怪
小孩」,她甚至孤立自己,埋首書堆,她說:「我相信很多好作家都克服過一
段不尋常的生活困境,進而成就一番事業。」她的著作偏重於孩子的內心世界,
而書中所反映的內容情節,正是她童年生活的寫照。「不可思議地,我生命的
原型是一個真實的故事」,39她自己覺得不可思議的是她的生命已有一條規劃好
的情節線,她覺得自己一直持續在寫自己的自傳,只是為了給予故事可信度,
她必須以小說的形式書寫出來。
凱瑟琳‧佩特森的特殊經歷正是其寫作的泉源,藉由書寫,她探索與重構
了自己的生命故事。
39 Alice Cary, Katherine Paterson (California:The Learning Works, Inc,1997), p123.
20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作家作家作家作家的生命故事的生命故事的生命故事的生命故事
通常你搬到一個新的社區或一個新的學校,會讓你憶起自己是一個無
名小卒。如果人們跟你說話,也帶著一種充滿優越感的語氣:『既-然-
你-連-午-餐-室-在-那-兒-都-不-知-道-,我-會-很-和-善-地-帶-你
-去。』」但多數時候你是被忽略的。我們多多少少都了解被當成局外
人的感受,那種被看待成較低下、隱形、或無用的感覺,或至少不被
全然尊重。
──凱瑟琳‧佩特森(Katherine Paterson),《Who am I?》40
一一一一、、、、以他鄉為故鄉以他鄉為故鄉以他鄉為故鄉以他鄉為故鄉
凱瑟琳‧佩特森於 1932 年 10 月 31 日出生於中國江蘇省的清江市 (這一天
同時也是西洋的萬聖節),當時這個金色捲髮的美國小女孩並不明瞭自己是個外
國人,對她而言,中國,這個有著廣大農田與山林的地方,才是她的家。而她
父母常提起的美國只是一如歐茲國般遙遠又神秘的國度。佩特森有四個兄弟姊
妹,哥哥雷蒙、姊姊伊莉莎白(莉莉)、妹妹海倫,而另外一個哥哥查理是在出生
後幾個星期就夭折了,最小的妹妹是安。由於佩特森的生日剛好在萬聖節,也
因此兄姐給她取了個綽號叫做「幽靈小孩」。比起她那漂亮的姊姊莉莉,佩特
森並不喜歡這個綽號,她總覺得自己像隻醜小鴨。尤其是在最小的妹妹誕生後,
有人將她的兄弟姊妹比喻成兩雙完整的筷子,其中一雙是年紀相近的雷蒙與莉
莉,另一雙則是海倫與安,而敏感的佩特森覺得不平:難道自己只是多餘?
在當時的中國,政治情況相當不穩定,這也正是佩特森父母所憂心的。當
時蔣介石與毛澤東的勢力對峙兩頭,而日本又覬覦著中國。在 1937 年,日軍襲
擊中國,在 1938 年,佩特森一家人因為戰爭的關係,被迫離開中國。經過輾轉
40 Alice Cary, Katherine Paterson, p34..
21
的長途跋涉,他們搭上一艘德國船艦,繞過歐洲許多國家,最後終於平安的抵
達美國。佩特森知道父母只是把美國當成一個暫居的地方,他們一直在等待中
國脫離險境後,能再回去中國。所以佩特森沒有辦法喜愛她的新家,她認為問
題是出在那不會永遠是她的家,果然父母來到美國後仍繼續四處遷徙,而佩特
森依然想念中國的一切。這時的佩特森除了要學習許多的美國文化之外,最大
的挑戰是要不停適應新的學校,以她當時的年紀,是很艱難的課題。佩特森甚
至認為「流浪」是她與生俱來的傳承。影響她最深的是聖經中的故事,尤其是
上帝派遣亞伯拉罕離家去尋找新大陸的故事。
上了小學一年級的佩特森,最需要的是一個能與他談心的朋友,然而事與
願違,她覺得同學認為她很怪,而自己果然像「幽靈小孩」般的孤單,再加上
難以親近的老師、無趣的課程,佩特森成了做白日夢的專家。她想像自己能在
情人節收到許多同學的禮物,然而那一天卻一個禮物也沒拿到,當時美國對她
而言是全世界最寂寞的地方了。(多年以後當她成為作家時,她曾提起自己所寫
的所有故事都是有關她那天沒有拿到任何禮物的時候。)
二二二二、、、、沼澤中的蘆葦叢沼澤中的蘆葦叢沼澤中的蘆葦叢沼澤中的蘆葦叢
在 1939 年,佩特森一家再度回到中國,然而戰爭未歇,回到淮安市並不安
全,所以他們選擇來到上海市。在上海有許多英國家庭,佩特森的英語也因此
帶著濃厚的英國腔。在經歷多次的搬家,恐懼著子彈、士兵及強盜,佩特森覺
得自己就像《綠野仙蹤》裡的桃樂絲,被龍捲風吹走,不知道自己將歸根何處。
41。在 1940 年的 12 月,佩特森一家人被告知要撤離中國,回到美國。儘管佩特
森並不喜歡待在維吉尼亞州,但比起中國危險的情況,這仍是比較好的選擇。
41 華裔作家葉祥添也很喜歡歐茲國(OZ)的故事:「在 OZ 的書中通常會有某一個孩子被帶到一個新奇的世界去,在那裡他或她必須去學習新的語言和習俗,並且適應新的人。這種情形在葉祥添讀來更為真實,就像自己從住家要到中國城的感受一樣。」,見陳佳秀,〈葉祥添小說中華人形象的自我再現〉,頁 22。
22
然而回到美國,上了四年級後,她所承受的恐懼與屈辱並未減輕。雖然到最後
她總能戰勝一切,而不可否認地那一年的歲月正為她日後的寫作播下了許多種
子。在新學校裡,同學們不喜歡靠近她,認為她是「雜種小孩」------一個傳教
士的女兒操著奇怪的英國腔調。她的穿著也令人覺得困窘,她穿的是別人捐給
教會的破舊衣服,因為家裡買不起新衣服。更糟的是,在 1941 年 12 月,日軍
偷襲珍珠港,羅斯福總統正式向日本宣戰,在這段期間佩特森吃不下也睡不好,
深怕世界末日的到來。她開始發現同學們對她竊竊私語,一位男孩直接向她挑
明:「妳不是美國人吧?」同學們談論著報上曾刊登佩特森一家人來自中國的
消息,同學們甚至誤認並指控她是日本來的間諜。佩特森知道自己無法改變自
己的來歷,能改變的只有自己的腔調,於是她努力模仿老師及同學的嘴型和發
音,數月後她的口音終於像個本地的北卡羅來納人。除此之外,佩特森還面對
其他種種難題,像是老師同學們認為她很笨,不會寫草寫字,只會寫正體字;
被一位高大的女孩潘西和她的同黨們欺負等等。對佩特森而言,新學校就像個
牢籠,是她急欲逃脫的地方。
如同醜小鴨為了躲過獵人的槍林彈雨,找到了沼澤中的蘆葦叢------佩特森
找到一個讓她可以獲得平靜的地方,那就是學校的圖書館。她一本接一本的讀,
許多作家的名著她讀來都津津有味,尤其是《秘密花園》,是她最喜愛的一本
書。佩特森也很想要擁有自己的秘密花園,這讓她想起了伊甸園,她迫切需要
這樣一個秘密花園,即使她知道這不是真實的。書本帶著佩特森到她想去的任
何地方,佩特森深深沉浸在書本的世界中。後來,佩特森當起了圖書館小助理,
唸書給小學弟妹聽、為圖書分類、檢查新書、修補舊書,她都樂在其中。在學
校她也遇到了幸運的事,她交到了一個好朋友,一個圓圓胖胖的小男生,有了
他的支持,佩特森得以撐過四年級。上了五六年級後,佩特森的成績變好了,
老師們讚賞她,同學們也漸漸對她友善。上了七年級,佩特森甚至被選為學生
代表主席。這一切讓佩特森感到喜悅,但卻沒有真正改變她,她常常跌入自我
懷疑的泥沼中,難以忘卻的是曾經被孤立的感覺 。
23
三三三三、、、、跨越彊界跨越彊界跨越彊界跨越彊界
即使佩特森的父母很想回到中國,但因為種種原因,卻未能再回到中國。
後來他們搬到了維吉尼亞州,佩特森在此完成了中學學業,後來進入了田納西
州的金恩學院就讀,主修英國文學。1954 年,她畢業後回到維吉尼亞州的一所
小學(Lovettsvile)任教。數年後,她所寫的《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其中傑西
和柏斯萊所唸的學校,正是以這個學校作為藍本(像是他們的教室是在地下室,
雲雀小學沒有午餐室和圖書館等等)。1957 年,佩特森在一所基督教育學院完成
了神學碩士的學位,她這才出發前往日本,開始了四年的傳教生涯。到了日本,
佩特森漸漸拋開以往關於日本這個國家的成見與仇恨。她努力地學習日文並適
應當地的生活民情,她開始欣賞日本一些古老的傳統文化,也從茶道中認識了
禪宗的佛理:和諧、尊重、純淨與寧靜。在日本,佩特森建立了自己的生活,
而且過得很愉快,佩特森似乎與東方結下了一份不解之緣。
回到美國之後的佩特森已年近三十了,也超過適婚年齡了。1961 年她繼續
攻讀另一個神學碩士學位,也認識了一位來自紐約的傳教士,約翰‧派特森。
約翰長相英俊,既幽默又認真,很快地博得佩特森的好感。在 1962 的 7 月 14
日,他們步入了結婚禮堂。婚後的第二年,佩特森任教於紐澤西的一所私立男
子中學,儘管這些孩子們叛逆不聽話,佩特森還是用眼神馴服了他們。1963 年,
佩特森產下一子,取名為小約翰。夫婦兩人非常興奮,他們打算生兩個小孩,
領養兩個小孩,因為他們知道很多小孩無家可歸。小約翰出生後,他們領養了
一個中國女孩,取名叫琳。琳初來到佩特森家時很焦躁不安,佩特森很有耐心
及愛心的幫助她度過難關。1966 年,約翰到華盛頓特區當牧師,隔不久小兒子
大衛出生了,他的長相酷似他哥哥。琳也很希望擁有一個像她的妹妹,兩年後,
她們又領養了一個五個月大的小女孩,名叫瑪莉。琳很興奮的歡迎她,因為瑪
莉與她擁有相同的髮色、眼睛和膚色。一家成員總算到齊了,佩特森找到了她
24
遺失的筷子,她很滿足地擁有這完整的、不同顏色的兩雙筷子。
此時的佩特森跨越種族、膚色的疆界,正如一隻蛻變的天鵝媽媽,充滿愛
心的孵育著一個色彩繽紛的家庭。
四四四四、、、、飛向兒童文學的池塘飛向兒童文學的池塘飛向兒童文學的池塘飛向兒童文學的池塘
佩特森很喜歡自己母親的角色,然而這份工作很吃力,有時讓她忘了她自
己。她決定為自己設下一個新目標,然而這個目標是什麼呢?除了傳教工作,
她從未考慮過其他事。研究所的一位教授在看過佩特森的某篇學期報告,曾建
議她可以考慮當一個作家。當時的佩特森不敢想,她曾經看過托爾斯泰、莎士
比亞等名家的作品,她如何能跟他們競爭?冒險成為一位平庸之才?然而她想
這也許這是上帝的旨意,透過了教授的口來讓她明白。在小約翰出生後,教授
向一個基督教育機構推薦佩特森為教會學校寫書,讀者是五、六年級的小學生。
佩特森覺得受寵若驚,她很快地答應了。這個計畫比她想像中的困難,因為她
是為一個有著眾多不同意見,甚至持相反意見的組織寫書。
最後,這本書終於出爐了,書名叫做 Who am I?。書中探討許多問題,都
是日後她在她的小說中所表露的,像是:上帝在哪裡?我歸屬何處?我的目的
是什麼?佩特森以她特有的、淺顯易懂的筆觸勾勒出有趣的故事,其中揉合了
激發思考的宗教議題討論。
之後,佩特森每天在照顧孩子之餘,忙裡偷閒地抽出十五分鐘來進行寫作,
而當孩子大了一點,她所投入的時間就更多了一些。她也曾參加創意寫作班,
寫的都是成人的作品,連續七年,她不停地寫稿、投稿、被退回,其中只有一
作品被刊登。最後,佩特森想既然她的成人文學不受青睞,那何不改寫兒童作
品?如同蛻變後的天鵝,佩特森決定飛向兒童文學那座清澈而豐美的池塘。
25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歷史與重構歷史與重構歷史與重構歷史與重構
歷史不只是一種科學,它同時也是一種再回憶的形式,科學所觀察到
的,回憶可以將它改變。再回憶可以把未完成的事物(幸福),轉化
為完成,把完成的事物(苦難),轉化為未完成。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說故事的人》42
一一一一、、、、歷史場域的選擇歷史場域的選擇歷史場域的選擇歷史場域的選擇
如前所述,佩特森曾經說過自己的生命原型就是一個故事,而佩特森藉由
書寫故事,與書中主人翁合作,去回憶重述自己的歷史,建立了一個個新的故
事,也形塑了新的自我身分。記憶對於佩特森的意義不是恰巧記住,而是重活、
重構(reliving, reconstructing);記憶可能是故事、工具或自我掙扎。
佩特森計劃寫一本關於日本的歷史小說,這給了她一個機會做有趣的研
究,並讓她覺得自己又再度成為日本人。雖然照顧小孩減少了她寫作的時間,
但她家人卻啟發了她的靈感。正當她嘗試去決定書中的情節內容時,當時才五
歲的琳有了麻煩。她不說話、不哭,也不看任何人,只是坐在那兒瞪大眼睛。
佩特森試著跟她說話、抱抱她都沒有用,這種情形嚇壞了他們。有一天,琳在
佩特森的逼問下終於開口了:「為什麼那個女人要遺棄我?」佩特森和約翰從
未隱瞞琳的身世:她是被母親遺棄,被一位警察發現,把她送到孤兒院的。佩
特森把琳擁入懐中,告訴她:「我想她把你放在那兒是因為她知道你會被發現
而且會得到照顧。她這樣做是因為她愛妳。」琳不停地問:「她還活著嗎?」
「她好嗎?」
經過了這次的談話,佩特森開始思考一個小孩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否安好
42 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林志明譯,《說故事的人》(台北:台灣攝影,1998.12),頁
98。
26
或健在會是什麼樣子。一個不明白自己來源的小孩,會有什麼樣的經歷與遭遇?
這個思考推動了書中的情節:「在二十世紀的日本,有一位名叫木那的小男孩,
離家尋找自己的父親-----一位高貴的勇士。」佩特森曾說:「對我而言,背景不
只是故事上演的地方,而是故事本身的一部分。人物不會決定背景,是背景來
決定人物的性格和行為。」43佩特森趁著孩子去上學時,到圖書館尋找關於日本
二十世紀的生活資料,回家後經過一番書寫、改寫與潤飾,她終於完成了《菊
花的標記》(The Sign of the Chrysanthemum )這本小說。歷經幾番折騰,她找到了
一位剛從日本回來的編輯------Crowell,他表示喜愛這個故事並有出版的意願。
佩特森的第一本小說終於在 1973 年出版了。
佩特森的第二本小說是:《哭泣的夜鷹》(Of Nightingales That Weep),一樣
是以二十世紀的日本為故事背景。她的朋友建議她應該以女英雄作為主角,而
後克服種種困難,因為她的女兒需要這樣的故事。於是書中的女主角 Takiko 誕
生了,她真的很堅強,但是也很虛榮自私,換言之,她是個擁有優點和缺點的
圓型人物。佩特森雖然是個傳教士,但是她寫書沒有任何說教的意味,相反地,
她總是忠於她所創造的角色與故事,並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
佩特森接著著手寫第三部小說,她問她的孩子想看什麼故事,她的孩子回
答:「偵探小說」。佩特森認為自己沒有足夠的腦力去構思一部偵探小說,但
是為了不讓孩子失望,她就試著寫一個充滿懸疑的冒險故事。幾天後,佩特森
在報上看到一個日本戰士人偶的相片,相片中出現的人偶劇場,令她憶起了自
己曾在大阪看過的人偶劇場,那逼真的畫面仍歷歷在目。她想人偶劇院是偵探
故事最好的場景了。1973 年,佩特森再度遠赴日本,尋查有關人偶劇場的資料、
她帶著琳親身體驗人偶劇場,與人偶師和一些專家談話,也了解了十八世紀的
大阪是飽受內戰與瘟疫的折磨。根據這些資料,她創造了一個男主角名叫 Jiro,
是人偶師的兒子,在大阪當學徒。佩特森原以她能很快地完成這部小說,然而
43 約翰‧洛威‧湯森(John Rowe Townsend)著,謝瑤玲譯,《英語兒童文學史綱》(An Outline of English-Language Children’s Literature)(台北:天衛文化,2003.1),頁 203。
27
卻因為突如其來的病痛中斷了她的寫作,她發現自己得了癌症,必須開刀切除
腫瘤。後來佩特森漸漸康復,一直到 1976 年,《人偶師》 (The Master Puppeteer)
終於出版了,這本書在在 1977 年同時獲得了美國國家圖書獎和偵探小說作家
獎。佩特森終究完成了一本偵探小說。
佩特森的前三本小說內容都與日本歷史有關,直到第四本,故事的場景才
又回到美國本土。
二二二二、、、、秘密空間與生死議題秘密空間與生死議題秘密空間與生死議題秘密空間與生死議題
《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Bridge To Terabithia)談及友誼的秘密空間並觸及生死
議題,正是改寫自佩特森小兒子大衛的真實故事。
當佩特森生病時,她的家庭正上演著另一齣戲。她的小兒子大衛原本就讀
的學校被迫關閉,不得不轉到另一間新學校。他喜愛畫畫,然而新同學卻認為
他的畫看起來很蠢,大衛每天吵著不要去上學。有一天,他從學校回來興奮地
告訴佩特森他和麗莎畫了一張「大樹林中的小房子」的透視圖。有了新朋友麗
莎,大衛的學校生活顯得有趣多了。她不只喜愛他的畫,他們倆還可以天南地
北、無所不談。他們倆在樹林中發現了一間小屋子,放學後他們常常一起去那
兒,他們彼此共享並認同這樣的秘密空間,也藉由這個地方鞏固他們的友誼。
他們不是男女朋友,只是最要好的朋友。佩特森知道對一個二年級生而言,能
擁有這樣一段特殊的友誼,是一件很幸運的事。
當暑假來臨,大衛和麗莎較少見面。佩特森一家人到紐約的喬治湖去度假,
她們在那兒租了一個由穀倉改建而成的小木屋。不久之後,他們一家人度假回
來,佩特森接到了一通令人震驚的電話。麗莎死了。當她們一家去德拉瓦州的
伯大尼海灘度假的時候,麗莎被閃電擊中當場就死亡了。事情怎會如此糟呢?
佩特森甚至不敢告訴大衛。當她強迫自己告訴大衛後,大衛甚至不想相信。在
麗莎的追思儀式中,大衛很傷心,他爲麗莎的媽媽畫了一張有趣的畫像,試圖
28
讓她覺得好過一些,也藉此安慰自己。當學期開始後,大衛更加想念麗莎了。
他假裝麗莎仍在那兒,然而,當音樂課沒有人跟他一起坐在角落合唱:「做自
己的主人……」時,他了解到自己全然的孤獨。
後來他告訴佩特森:「我知道麗莎為什麼死了,因為上帝討厭我,接下來
他也會奪走瑪莉。」他認為上帝將殺死任何他喜歡的人來懲罰他。當他喜愛的
三年級老師因病住院時,大衛逃離學校,他認為是他造成的。校長安慰他,學
校也提供了友善的環境來幫助他,不但不責備他為何不交作業,還派他幫忙做
一些事。對他最有幫助的是麗莎的奶奶提供的陶藝課程,還有邀請大衛一起種
鬱金香球莖,這是她和麗莎生前就打算種下的。麗莎是不會被遺忘的,因為陶
藝課和鬱金香正代表著麗莎的旺盛的創造力和生命力。
後來一些文友建議佩特森把這個故事寫下來,有一個編輯認為主角不能死
於雷擊,因為這樣的悲劇是不合理的。對佩特森而言,她如何能夠寫一個連自
己都不敢去想的故事?但她還是開始了,因為這個事件始終在她腦海中揮之不
去。一開始她只能擠出幾個字,後來她寫著:「我不能確定我能不能說出這個
故事。那傷口依然疼痛,如何能化成理性的篇章?但我會試試看,為了大衛、
為了麗莎,爲了麗莎的母親,為了我。」
她寫了兩個角色,一位名叫傑西,一位是柏斯萊,她對 Lovettsvile 小學的記
憶,則幫助了她描寫雲雀小學的種種細節。她發明了泰瑞比西亞王國,因為她
小時候曾經創造這樣的世界。起初她以為自己捏造了「泰瑞比西亞」(Terabithia
)這個地方的名字,後來她才知道 C.S.路易斯在《黎明行者號》(Voyage of the Dawn
Treader)這本書中稱呼一個島為「泰瑞比西亞」。她一定是在無意識中借用了這
個名字。而路易斯取的這個名字,是聖經中所提到的松節油樹的諧音。她在寫
這本書的時候,小約翰偷看了她的手稿,質疑的問她:「為什麼一開始傑西看
起來像我,後來卻變成了大衛?」佩特森向他解釋到:傑西就是傑西,是她的
發明,他既不是約翰也不是大衛。其實傑西更像她自己,因為她是用自己的思
想及情感來描述傑西的。有一天,她突然停筆了,因為她寫到柏斯萊要死的那
29
一部分了。她告訴她的朋友她無法再次面對麗莎的死亡,而她的朋友深思的說:
「佩特森,其實妳無法面對的是自己對死亡的恐懼。」佩特森認為她的朋友是
對的,縱使她爲麗莎心碎,但她更害怕自己有一天也會死亡。當她完成這個故
事後,她寄給了出版社的編輯,維吉尼亞‧巴克莉,維吉尼亞很喜歡這個故事,
因為故事前面約三分之二的部分令她歡笑,而後面的部分卻令她哭泣。她給了
佩特森一些建議,她認為柏斯萊在故事中應有一些成長及轉變,佩特森想起了
自己小學時曾被同學潘西欺負的情景,於是她在書中塑造了珍妮絲等惡霸的角
色,給予柏斯萊和傑西打擊,這樣使得故事變得更有說服力。另外,她也被告
知應該讓讀者覺得傑西是個藝術家,不只是畫得藝術,而是思考像個藝術家。
佩特森想從梵谷的書信中尋找靈感,但沒有一點幫助。後來,她問大衛:「你
為什麼不畫大自然的景物?」大衛回答:「我沒有辦法抓住樹林的詩意。」這
樣的一句話正是佩特森想要的,她藉由傑西的口中說出來了,這是她唯一一次
刻意地將真實生活中的對話放進她的書裡。最後她為了讓讀者知道這本書的靈
感是來自大衛和麗莎,她註明這本書是爲他們而寫的。
《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Bridge To Terabithia)於 1977 年出版,在 1978 年獲
得紐伯瑞金牌獎。佩特森在頒獎典禮上,述說了自己的癌症、麗莎的死亡、她
寫這本書的掙扎等等,她的演說令在場的每個人感動地落淚。
三三三三、、、、自我認同的交戰自我認同的交戰自我認同的交戰自我認同的交戰
不管佩特森出版多少書,得過多少獎,寫初稿對她而言總是充滿痛苦和自
我懷疑。「對自己真實」是她唯一能提供的座右銘。「當我在寫書的時候,我
不知道自己寫得好或不好,或是人們想不想讀它,我只希望我完成後,不會使
我的出版社蒙羞,而小孩會想閱讀它。」44 在 1977 年的秋天,她計劃寫一本書
Jacob Have I Loved,一開始她不知道自己想說什麼故事,當朋友問及她的書時,
44 Alice Cary, Katherine Paterson,p123.
30
她總是滿腹牢騷。有一次和約翰討論過後,她知道自己要寫什麼了。她想寫的
是手足競爭,因為很多人在童年時期飽受忌妒心的折磨,甚至延續到成年期。
她自己也有有手足競爭的問題,但她告訴自己思考不要只侷限在自己的家庭,
她想到聖經中典型的手足競爭:該隱和亞伯、雅各伯和以掃、拉結和利亞。一
開始她為書中的主角取名叫拉結,但是要住在哪兒?是城市或在鄉村,也可能
是在日本。知道她的父母在做什麼也很重要。拉結會因為和她哥哥之間的關係,
而使得她和上帝對立嗎?拉結深深地背負著自己的罪惡感,她要如何把宗教帶
入這個故事?她可以寫兄妹,也可以寫姊妹,但是如果寫姊妹,又怕跟自己的
故事太像。有一度佩特森很焦躁不安,她找不到開啟故事的鑰匙。她曾花時間
去尋訪東南亞的孤兒院,希望能找到書中的角色,但仍一無所獲。諷刺的是,
是佩特森的妹妹提供了這把鑰匙。聖誕節時,她送給小約翰一本書,書名是:
《美麗的泳者:漁夫、螃蟹和綺沙比克灣》。當佩特森讀到那動人的敘述時,
她找到了故事的場景:在海灣中的小島,這是一位寂寞的十四歲女孩的家。於
是拉結變成了芮思島上的露意絲‧布雷蕭。芮思島是根據綺沙比克灣中的小島
想像出來的地方。她開始去尋找有關海灣的種種書籍。
後來,生活外在的種種轉變包括自己得到癌症、家的搬遷等等,都拖延了
此書的進度。然而,佩特森明白真正影響進度的原因是來自於她的內在。每當
她坐下來準備打字時,她的胃就因為焦慮而翻攪。這個故事進行困難是因為對
她來說意義重大,它提醒了她對自己姊妹的忌妒心。有一度,她幾近絕望。她
告訴維吉尼亞‧巴克莉:『如果我能完成這本書,維吉尼亞,我會用牛皮紙包
裹起來寄到妳家。妳必須答應我,如果作品不好,妳不但要拒絕出版它,更不
能告訴任何人它曾經存在過。』故事本身就像是一個好戰的青少年,不想服從
她的創造者。舉例而言,佩特森不喜歡用第一人稱敘述觀點,她認為它提供的
視野太狹隘。但是,露意絲‧布雷蕭堅持用她自己的聲音說出自己的故事,不
顧佩特森較理性的判斷。事實上,她有限的觀點是必須的,因為本書的核心就
是在描寫露意絲對於家人及朋友關愛的盲目。後來她開玩笑地說,她有辦法完
31
成此書的理由是她經常地遺失她的筆記,這迫使她放棄很多想法,形成新的點
子。最後,約翰怕她無法結束這個故事,建議她先把草稿寄給維吉尼亞‧巴克
莉過目,維吉尼亞收到後兩天馬上來電表示她喜歡這個故事。一如往常,修改
是必要的,在一個有靈感的早晨,佩特森形容修改是一項「恩典」。
經過多年與露意絲‧布雷蕭的自我認同交戰,Jacob Have I Loved(《孿生姊
妹》) 終於在 1980 年出版了。1981 年,她在台上接受紐伯瑞金牌獎時,她說:
「我覺得很興奮、光榮、感激,但是並不震驚。」而每一本書,儘管得到多高
的讚賞與榮耀,總是有人批評。有些評論家抱怨此書的結局:事情發展得太迅
速,露意絲是一個可憐的典型角色,在愛情和職業上做了可憐的選擇。這樣的
評論令她傷心,她覺得不平,她深深地關心她的角色,一如她對好友和家人一
樣。當然,讀者的反應是最重要的,而非評論家。曾經有一位七年級生,在圍
繞她的同學旁等待,只為了悄悄告訴她:「I loved Jacob Have I Loved.」在這個
時候,她的靈魂飛揚了起來,她說:「對一個作家而言,這一切已經足夠。」45
與她其它的少年小說相較之下,Jacob Have I Loved 讀來像是一篇赤裸裸而
精采的心理傳記,涵蓋了相當長的時間範圍。繼 Jacob Have I Loved 之後,佩特
森翻譯圖畫書作品,也寫一些兒童文學理論的書,在 1983 年,她又再度出版一
本小說 Rebels of the Heavenly Kingdom(《太平天國》),這一本書又讓佩特森重回
神秘的遠東地帶-------十九世紀中期的中國南方,這一本書也是她對中國這個
「異鄉的故鄉」一段歷史的追緬。故事描述年輕的農家子弟王立被土匪綁架,
並且和他的救命恩人美玲有了一段男女情懷,並敘述他們兩從認同加入一個社
群到脫離的過程。娓娓道來的故事內容,不但透露了佩特森「對正義和憐憫的
訴求」,也藉此帶領著讀者進入中國人傳統的生活和思想,也讓讀者認識到「太
平天國」此宗教結社的歷史傳奇事件。
45 以上關於佩特森的生命故事,大部分參照轉譯自 Alice Cary, Katherine Paterson 此書。
32
四四四四、、、、生命圓舞曲生命圓舞曲生命圓舞曲生命圓舞曲
藉由書寫,佩特森也邁向了榮格所謂的「個體化歷程」。「『敘事治療』
關注我們怎樣說有關我們自己的故事,包括我們的能力、與他人的關係、工作、
成就或失敗等等,因為我們的故事---- 對過去的理解----往往會影響我們怎樣理
解現在的自己,以及對未來的態度,換句話說,這是關於「我是誰?」的身分
問題。」,46不同於敘事治療的部分是,佩特森將自己的生命故事化為小說,但
她並沒有將「問題外化」,47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在〈說故事的人〉
一文指出:「小說形成於孤獨個人的內心深處,而這單獨的個人,不再知道如
何對其所執著之物作出適合的判斷,其自身已無人給予勸告,更不知如何勸告
他人。」48的確,佩特森無勸告的意味與能力,她筆下的角色堅持說出內心深處
的故事,如果讀者也曾經有過類似的處境,那麼他所得到的不是勸告,而是慰
藉。佩特森大部分的作品都是跟自己的故事有關,除了前述的作品,其它像是
The Great Gilly Hopkins(中譯名:《吉莉的抉擇》),描述的是一個小女孩與其寄
養家庭互動的故事。佩特森自己也曾經當過寄養家庭的父母,曾經收留過來自
柬埔寨的兩個男孩,其中一個男孩名叫 Vorin,個性暴躁、桀骜不馴,吉莉正有
如他的化身。而書中的特拉特太太,是她自己無法做到又渴望成為的角色,是
她想像中最完美的養母。佩特森總是深入挖掘回憶的寶藏去重述她的故事,她
的書充滿了真實的情感與人物。舉例而言,當寫 Flip-flop Girl 這本書時,故事
一開始女主角 Vinie 必須面臨轉到一所她不喜歡的學校的命運,而佩特森清楚的
知道當 Vinie 的媽媽帶她去新學校時,在遊樂場時那種被忽略的感覺。Jip:His
Story 是描寫一個失去雙親的男孩的故事,她知道當 Jip 第一次上學時有多緊張,
當老師在唸 Oliver Twist 這故事時,他是如何期待故事下一步的發展。在 The
46 尤卓慧、岑秀成、夏民光、秦安琪、葉劍青、黎玉蓮編,《探索敘事治療實踐》(台北:心理,2005.6),頁 21。
47 問題外化指的是:將人與問題分開,人不是問題,問題才是問題。
48 班雅明著,林志明譯,《說故事的人》,頁 24。
33
Master Puppeteer 這本書中,當 Jiro 小心翼翼地黏合父親製的人偶時,她憶起自
己在圖書館時修補舊書時有多麼地仔細。
以佩特森的生命故事而言,她可以是自己生命故事的主體,編寫及活出不
同的故事和經歷,但她也可以反過來成為故事的客體,讓故事的情節主導著他
的身分認同和個人發展。藉由書寫,她探索問題的故事的意義,並開發另類故
事和另類情節,藉以提供自己多一些選擇,創造自己較喜好及更具有充權意義
的身分和故事。她藉由一本又一本的創作,填補了自己生命一個又一個的缝隙,
一段又一段的篇章,交織成屬於自己生命的圓舞曲。
Paul Ricoeur 說:「人無法直接瞭解自己,而是要透過某種媒介才能認識自
己。」「Ricoeur 突顯出像小說、傳奇的敘事系統內部,如何透過行動事件與角
色的運作,而接合故事看倌的經驗以形成他或她的敘事認同。」49佩特森因其特
殊的生長背景,在其小說中反映的認同意識,也牽引著讀者去認識自己的認同
意識。故事的情節來自剪裁經驗世界的事件,筆者依此敘事媒介,梳理出認同
意識的脈絡。
49 方孝謙,《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台北:巨流,2001.6),頁 73。
34
第參章第參章第參章第參章 我與自己我與自己我與自己我與自己
────────《《《《孿生姊妹孿生姊妹孿生姊妹孿生姊妹》》》》中的自我認同中的自我認同中的自我認同中的自我認同
《孿生姊妹》在 1981 年獲得紐伯瑞金牌獎,故事的場景在海灣中的小島---
芮思島,是根據綺沙比克灣中的小島想像出來的地方,也是一位寂寞的十四歲
女孩-─露意絲‧布雷蕭的家。藉此,作者營造出一種特殊的氛圍與地方感,讓
讀者很快地投入其中,再加上這是主角追尋自我的生命故事,故事中有大量的
內心獨白,更帶給人一種赤裸裸的真實感。凱瑟琳‧佩特森自己曾言《孿生姊
妹》一書其實是在寫自己的故事,在小時候她曾經因為忌妒自己的姊妹,而陷
入自我懷疑的交戰之中,露意絲‧布雷蕭這個角色可以說是童年時期的凱瑟琳‧
佩特森的「再現」,作者透過自傳式的感情和虛構的細節,而編織出這部記憶
之作。在國內探討《孿生姊妹》的論文目前已出版的有吳文薰所撰的〈女性成
長之孤獨、希望與自我覺醒----從凱瑟琳‧怕特森三本作品談起〉,然其主要論
述是從「成長小說」的觀點切入。而筆者所欲進行的是認同心理的分析,在第
一節中首先以艾瑞克森的理論來說明露易絲所面臨到的「認同危機」,並聚焦
於認同問題所帶來的孤獨、自卑、忌妒、競爭等心理,並探討作者所引用聖經
中「手足競爭」的典故。第二節則探討《孿生姊妹》中「雙重概念」的隱喻,
如同凱瑟琳‧佩特森自己所言:「我們的生命都包含光明與黑暗,我們就是自
己的孿生。」50所以凱若琳是另一個露易絲,凱若琳是一個「他者」,也是一個
「鏡像」,是露易絲的自我投射,本節試圖從天秤的一端去探討造成認同失衡
的現象與原因。第三節則將鏡頭拉遠,以生命進程的觀點去看待認同的課題,
認同是一個流浪者並經之路,露意絲經過了認同與疏離間的迴旋之旅,心中的
孿生姊妹終於合而為一,也透露著作者心中的異域也要合而為一。
50 網頁〈美國西北大學網站〉http//www.northern.edu/hastingw/Jacob.htmll,2007.9.5
35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生命中的認同危機生命中的認同危機生命中的認同危機生命中的認同危機
「我一向以我的妹妹為榮;可是,那一年,光榮底下卻不明所以的生瘡、
化膿了。我的人生,在我十三歲那年,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錯亂和迷失。
現在,我終於能夠理解當年的變化了。」
─凱瑟琳‧佩特森(Katherine Paterson),《孿生姊妹》51
一一一一、、、、對抗性的自我認同對抗性的自我認同對抗性的自我認同對抗性的自我認同
《孿生姊妹》中的主角露易絲,有著一個優秀的孿生妹妹凱若琳。在露易絲
的眼中,妹妹佔盡了一切優勢:出眾的外貌、甜美的歌聲、優秀的才能及家人
的寵愛。露易絲是自卑的。她身體強健,卻覺得飽受冷落,因為家人總是付出
較多的關懷在嬌弱的凱若琳身上;凱若琳到了九歲就能彈蕭邦的曲子,而她似
乎永遠只停留在彈「王老先生有塊地」;凱若琳永遠乾淨美麗,而她為了要做
出海捕蟹、捕牡蠣的工作,常把自己搞得一身腥臭;凱若琳自信、爽朗、纖巧
而令人愉悅,而她與之相較只會顯得更加灰澀黯淡。
「凡物不平則鳴。其鳴之大小抗卑雖不同,而其不平氣則一也。」露易絲的
不平來自與妹妹的比較,也因此造成了她的「認同混淆」。很顯然地,她們倆
雖是孿生姊妹,但卻有著不同的性格與命運。露易絲認為妹妹佔盡優勢,而造
成了負面的自我認同,然而這些都是來自自己一廂情願的看法,事實卻未必如
此。凱若琳的美麗與嬌弱,充分顯現了女性特質,代表了一個完美的女性形象;
而露易絲剛強健壯,能幹獨立,展現男性化的特質,這是作家有意顯現的一個
對比。蔡源煌在〈文學中男人如何看女人〉中指出:
51 凱瑟琳‧佩特森 (Katherine Paterson),鄒嘉容譯,《孿生姊妹》(Jacob Have I Loved)(台北:東
方,2005.12),頁 40。
36
女性角色的塑造往往只是作家的一個概念而已,這個概念至少融合了
男性潛傾、女性潛傾、潛影等三個層面。…………對於男性作家來說,
通常他都希望女性潛傾出現的較多些;而對女性作家來說,則希望男
性潛傾較明顯 些。52
蔡源煌並指出,一部電影或一部小說作品,如果出現有兩個女主角時,經
常會是一個金髮,一個黑髮。凱若琳是金髮,露易絲是黑髮,金髮美女是女性
潛質的延伸,而黑髮美女則偏向男性潛質。金髮女子多半較稚嫩,像溫室中的
花朵一般;黑髮女子精明有餘,多半陪侍於金髮女子的身旁。露易絲總認為自
己只是凱若琳的陪襯角色,永遠當不了主角一般。凱若琳的光環映照出露易絲
的陰影,也淹沒了她存在的價值,她自述到:「在這個世界上,我最不想聽的
故事就是我妹妹的;因為在她的故事裡,我這個孿生姊姊,只不過是個跑龍套
的角色而已。」(頁 29)
如果說凱若琳是天之驕女,那麼露易絲也是上帝的寵兒。然而充滿忌妒情
緒的露易絲,看不到自己的優勢,也忽略了自己的智慧與堅強。問題是出在露
易絲將自我認同建立在別人的眼光與掌聲之中,比起她的妹妹,她似乎無法獲
得週遭的肯定評價,而無法接受自己本來的模樣,以致於產生了負面認同。露
易絲的問題來自於內部的、心理的騷亂,而這騷亂是源於某種難以忍受的自卑
感。露易絲的認同危機正發生在十三歲的那一年,也就是在青春期這個動盪不
安的時期,尤其是女孩到了少女期時,心理上和生理上都發展的比男孩迅速。
榮格認為:「我們從青年時期發現了幾乎是難以窮盡的、各式各樣的人生問題。」
53艾瑞克森認為:動力能量的大量增加是造成青春期分裂的原因,可是他將之視
為問題的一部分而已。54青少年也因新的社會衝突和要求而變得困擾和疑惑,所
52 蔡源煌,《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台北:雅典,1991.11),頁 78。
53 榮格 (C. G. Jung)著,蘇克譯,《尋求靈魂的現代人》,頁 109。
54 William Crain 著,劉文英、沈秀靖合譯,《發展學理論與應用》(台北:華騰文化,2005.10),頁 287。
37
以青少年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建立一種新的自我認同感(ego identity),也就是一個
人在大社會的秩序中,對自己的角色及地位的感覺。此時的危機就是認同(identity)
和角色混淆(role confusion)的對抗。雖然認同形成是終生過程,而認同問題是在
青春期達到關鍵點。這時候,一個人早期的認同,看來似乎是不足夠讓他來做
他必須做的選擇和決定。
依阿德勒的看法,「認同」可視為一種「感情移入」,他認為人類的這種
心理機能發展極為良好,其範圍很廣大,在心靈生命的每個角落都可以發現它。
55我們可以認同的對象極其多,包括任何人、事、物,在認同的過程中,由於感
情移入的作用,使得我們擴大自身的主體性,去感同身受。露易絲曾也經以她
妹妹為榮,並努力工作負擔家計,讓妹妹能順利求學。但是,進入了青春期的
露易絲,多麼渴望被別人認同,她也希望藉著別人對她的認同而認同自我。然
而,長期以來那種自卑、不足和不安全的感覺,使她更需要別人對她的注意,
也形成了需要被賞識的欲望,在自卑感的伴隨影響下,她的慾望不斷發展,其
目的是希望自己能勝過凱若琳、勝過環境。然而在欲望未被滿足時,她顯現了
人類的種種弱點,包括嫉妒、羨慕、憎恨、焦慮及懦弱等等。於是她開始無法
認同凱若琳,而處處顯現出拒絕的態度。露易絲嫉妒的產生,主要是因為她感
覺受到忽視和歧視。打從一出生,父母就因為凱若琳的嬌弱而給予較多關照,
與之相較,露易絲就被忽視了,也感到自己被歧視。由於自卑情結的壓迫,她
對自己的低估,以及她對生活的不滿足,便經常表現出來。她不斷地衡量凱若
琳的成功,也使得自己羨慕的感覺不斷增長,這樣的感覺不斷使她無法快樂,
更使她對於未來的希望是一片黯淡。阿德勒在《了解人性》一書中指出:
羨慕之情迫使我們制定所有的標準和規則,其目的是建立人類的平等地
位。最後,我們會以理性的方式討論我們已經直覺到的一個命題:所有
55 阿德勒(Alfred Adler)著,陳蒼多譯,《了解人性》(台北:大中國圖書,1991.5),頁 40。
38
人類一律平等之原則。這是人類的基本律則之一,一旦有人違背了這個
律則,就會立刻造成對抗和爭論56
露易絲渴望能與凱若琳有同等的待遇,甚至能超越她,加上她們倆是孿生
姊妹,這使得她競爭與對抗的心更加強烈。伴隨著羨慕之情而來的是憎恨的情
緒,然而露易絲的憤恨之情無從宣洩,在另一方面,露易絲也是懦弱的,她也
從未在父母面前埋怨過,她眷戀依賴著家人的情感,只能日復一日的重複她的
生活,埋首在補蟹的工作或書堆之中。而「夢」宣洩了她憎恨的情緒,她經常
夢到自己親手殺死了自己的妹妹。依榮格所講,絕大多數的夢是具有心理補償
作用的。57夢將隱藏在內心深處的事物帶到意識之中,使人的心靈成為一個和諧
的整體,因此可以說夢是對意識中欠缺部分的補償。夢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解釋:
客觀方面,是指夢者生活的外在環境;主觀方面,是夢者內心情境與過程的顯
現。當然,有些夢是具有前瞻性的,它可預言到未來要發展的事件等等。而露
易絲的夢,應比較接近佛洛依德對夢的看法:夢是以喬裝的方式來表達乃至宣
洩多種不被接受的無意識欲望。儘管露易絲如何壓抑自己的情緒,不在別人面
前發作,但夢顯露也平衡了她的內在意識,露易絲夢的內容雖然是不健康的,但
從心理平衡的角度看來,做夢是有益身心健康的。
二二二二、、、、通過轉化變形之門通過轉化變形之門通過轉化變形之門通過轉化變形之門
露易絲的夢也蘊含了「手足競爭」原型的神話主題。露易絲所面臨的心理
危機,也正是從古至今人類在成長淨化的歷程所會面臨的問題之一。只是古人
依他們神話和宗教遺產中象徵及精神鍛鍊的引導所通過的心理危機,今日的我
們卻必須單獨面對,或者最多只能得到暫時、隨機的引導。坎伯在《千面英雄》
56 同上,頁 173。
57 羅伯特‧霍普克 Robert H. Hoecake ,《導讀榮格》(A Guided Tour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新店:立緒文化,2005.1), 頁 15-16。
39
中提出:「你以為自己不用走過前人歷經的試煉,就能進入幸福的樂園嗎?」58
露易絲所面臨的認同危機,正代表了一個轉機,帶領她走上試煉與重生之路。
佩特森在構思露易絲的故事時,曾經想過聖經中該隱與亞伯、雅各伯和以
掃、拉結和利亞等手足競爭的故事。這即是宗教遺產中所象徵的珍貴原型,佩
特森在此得到隨機的引導,並比照自己的親身經歷,鋪陳出露易絲的試煉之路。
筆者以下列舉四個手足競爭的神話原型:
(一)原型之一:該隱與亞伯
創世記四章二節告訴我們該隱和亞伯兩兄弟的故事:該隱和亞伯是亞當和夏
娃所生的兒子,哥哥該隱種地,弟弟亞伯牧羊。地為人出產食物,羊主要是為
著獻祭給神。因此,我們看見該隱服事地─世界,亞伯服事神。後來神接受了亞
伯的祭品,而拒絕了該隱的,該隱卻因此發怒,變了臉色。耶和華對該隱說,
「你為甚麼發怒呢?你為甚麼變了臉色呢?你若行得好,豈不蒙悅納,你若行
得不好,罪就伏在門前…。」神要該隱快快悔改,好制伏罪,不要讓罪勝過他。
然而該隱並沒有聽進神的話,將他的心轉向神並且悔改;反而心更剛硬。他對
亞伯從嫉妒轉成仇恨,他開始恨他的弟弟亞伯。有一天,當兄弟二人在田間說
話時,該隱便起來打了他的弟弟亞伯,又把他殺了。這是聖經中第一個兄弟鬩
牆的故事。
(二)原型之二:雅各與以掃
另外一個是露易絲祖母口中的故事:雅各和以掃的故事。雅各自幼和雙胞
胎哥哥以掃爭家族的繼承權,用欺騙的手段取得長子的名份,但是卻因而引起
哥哥憤怒,不得不遠離家鄉,逃到母舅拉班之處,雖然雅各機靈一生,但是卻
為了喜歡表妹拉結的關係,受盡母舅欺壓和剝削,最後,雅各終於回到家鄉與
胞兄和好。在「保羅寫給羅馬人的書信」(羅馬書,九章,十三節)有這麼一段典
故。上帝確實曾說過這一段話:"Jacob I loved, but Esau I hated."( 雅各是我所
58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新店:立緒文化,2003.8),頁 106。
40
愛,以掃是我所惡) ,這意旨上帝選擇了雅各做為以色列的繼承人,並要大的服
恃小的。經上又說 :"What then shall we say? Is God unjust? Not at all! For he
says to Moses, I will have mercy on whom I have mercy, and I will have compass
ion on whom I have compassion." 這意旨上帝會賜予祂所選擇及召喚的子民慈悲
與同情。而為什麼上帝選擇了弟弟雅各,是因為哥哥以掃輕視了其長子的名份。
而故事中的露易絲正是認同了以掃的際遇,認為自己不受上帝的寵愛。
(三)原型之三:拉結和利亞
聖經中另一姊妹競爭的故事是拉結和利亞的故事。在創世紀第二十九章
中,描述拉班有兩個女兒,大的名叫利亞,眼睛沒有神氣;小的名叫拉結,卻
生得美貌俊秀。雅各先遇見的是拉結,先求婚的也是拉結,但先娶的卻是利亞。
雅各愛拉結勝似愛利亞。但是神來了,神是扶助軟弱的人。神使利亞生育,拉
結卻不生育。拉結見自己不給雅各生子,就嫉妒她姐姐。她求人而不求神的對
雅各說:「你給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她生氣的說:「叫你不生育
的是神,我豈能代替他作主呢?」然後她又倚靠自己的辯法,不倚靠神。她把
自己的使女辟拉給雅各為妾,使使女生子在她的膝下,她便因此而得孩子。最
後她終於也知道有神,而求告神,神顧念拉結,應允了她,使她能生育。拉結
就懷孕生了約瑟。在創世紀第三十章則描述,同父同母同夫的兩姊妹在家裏,
一直不停的爭丈夫、爭兒子、爭吃。雖是同胞姊妹,遇事總是不能相容相讓,
何況同事一夫,更充滿了肉體的嫉妒、紛爭。
(四)原型之四:伊娜娜與伊瑞虛堤卡
在蘇美人神話之中,天后伊娜娜統治太陽上升之地的天界,而她的姊妹兼
敵人伊瑞虛堤卡則統治了死亡與黑暗冥界。有一天,她準備進入不歸之地,意
即她姊妹所統治的黑暗冥界,她因為怕伊瑞虛堤卡會置她於死地,於是指示她
的使者尼秀布,萬一她三天後沒有歸返,便到天堂去在眾神聚集的大廳為她叫
嚷申訴。
伊娜娜降到不歸之地,被守衛納提要她留在原地。納提奉伊瑞虛堤卡命爲
41
天后開啟七重門柵,但要遵從習俗,在每一道門的入口處去除她部分的衣飾。
在第一道門時,她頭上的「平原之冠」被摘了下來;在第二道門,她的琉璃權
杖被拿走了;在第三道門,她脖子上戴的小天青石被摘掉;在第四道門,她胸
前的閃亮寶石被拿走;在第五道門,她手上的金戒指被摘了下來;在第六道門,
她的護胸被取了下來;在第七道門,她身上所有代表淑女身分的服飾都被卸除
了下來。名府的七位判官坐在伊瑞虛堤卡的王座之前,以他們死亡之眼的目光
投注在伊娜娜身上,使伊娜娜變成一具死屍。後來,尼秀布為她在集會大廳中
哭訴,為她在神殿裡奔走,為她找來「生命之糧」與「生命之水」,在死屍上
噴灑六十次之後,死屍終於甦醒與復活。
伊娜娜的故事也代表了英雄的一個旅程。英雄為了要了悟某種事物,個人
必須要致力於某種程度的淨化與謙卑,甚至如浴火鳳凰般,歷經死亡後,以獲
得重生。坎伯如此分析這則蘇美神話:
伊娜娜與伊瑞虛堤卡兩姊妹分別代表光明與黑暗,根據古老的象徵習
俗,她們兩者代表同一女神的兩個面向;而她們的對抗更市困難試煉之
路的縮影。不論是神或女神、是男人或女人、是神話中的人物或作夢的
人,英雄要發現、同化他的對立面 (也就是他沒有懷疑過的自我),不
是吞下它就是被它吞下。障礙被移一個一個突破。它必須把自己的驕
傲、美德、外貌、和生命拋開,像那絕對無可容忍的事物低頭屈服。然
後他會發現它與自己的對立面並非不同種類,而是一體的。59
同樣地,該隱與亞伯、雅各與以掃、拉結與利亞、露易絲與凱若琳也是一
體的兩面。一個人若要成為完整的,就必須要有黑暗的一面,只要他意識到了
他的陰影,他也就記住了他是一個人,同其他人一個樣。人為了要發現、同化
59 Joeseph Campbell 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頁 111。
43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自我投射的場域自我投射的場域自我投射的場域自我投射的場域
一一一一、、、、自我與鏡像自我與鏡像自我與鏡像自我與鏡像
「自我」是如何形成的?我們常從別人的眼中看見自己,形塑自我。露易絲
認為週遭的人都不關心她,也同時貶低了自我的價值。如果凱若琳是露易絲的
一面鏡子,這面鏡子卻讓露易絲顯得自慚形穢。鏡子理論,又稱鏡緣或鏡像階
段(the mirror stage),由法國精神分析巨擘拉岡(Jacques Lagan, 1901~1981),
在 1936 年首次提出。拉岡認為「鏡像」是塑造自我的第一階段。嬰孩從六個月
到十八個月,會對自己的鏡像顯出莫大的興趣,試圖藉由鏡像所提供的完形
(Gestalt),來實現自己期望成熟的目的。鏡像理論可看作是一種認同作用,不過
精神分析學者不斷強調走出鏡像的重要。拉岡解釋,當主體透過鏡像來認識自
己,其實是藉由「他者」,才認識到自己的存在,雖然鏡像過程幫助嬰兒發現
「自我」,拉岡強調經由鏡中認識的自我,並不是真實的,而是一種鏡中幻象。
60
我們透過露易絲的眼睛,看到了露易絲所處的世界。而露易絲是透過彼此
不斷照鏡子,在不斷的人際互動中,形成自我形象。然而,露易絲的價值觀有
些是扭曲變質的,所以她的生命曾被侷限。就如同有些孩子,多半會承受來自
長輩的不當教導和影響,這些不良的童年經驗,全都內化為自我的一部分。這
令人想起白雪公主中的那面「魔鏡」,魔鏡告訴皇后的多半不是真實的答案,
而皇后卻無法自拔的認同魔鏡,並隨之悲喜起舞。好比 2006 年牧笛獎得獎童話
《皇后的鏡像》,皇后受了宮中種種規矩的限制,被迫成為他人眼中的自己,
而失去了自己的鏡像。
「創世記」記載人類墮落之前,神宣稱所創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亞當第一
次看到夏娃,甚至發出「你是我骨中骨、肉中肉」的讚嘆!當人類從神的角度
60 廖炳惠著,《關鍵詞 200》,頁 238。
44
彼此對看,原本十分美好,然而,罪的意識入侵之後,始祖立即從對方的臉上,
照到自己「不被喜歡」,急忙拿無花果樹的葉子,遮住羞恥部位。一個個不健
康的生命劇本於焉形成,就這樣,人類雖然獲得了從外部看自己的能力,卻一
路奔向廣受局限的宿命。聖經上說:「神就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照著祂的形
象造男造女。」又說:「當那神聖者,受讚的祂,創造了第一個男人時,祂將
男人造成雌雄同體。」將女性移到另一形體,乃是從完美墮落到二元世界開始
的象徵;而接下來的發展自然是好壞二元性的發現、逐出上帝在地球上漫步的
花園,形成了對立的同時存在,人類 (現在已是男人和女人)不僅從上帝的影像
中分離出來,甚至也不記得此一意象了。
依榮格所言:當春分點進入雙魚座世紀時,雙魚座所隱含的雙重特性,正
反映出基督教教義中水火不容的對立成分。光明 VS.黑暗,精神 VS.物質,太陽
VS.月亮,父親 VS.母親。凡是一神論的宗教系統,皆須將天神的「二元」特質
合而為一:天神顯現出來的形象既是正面、亦是負面,是男性、亦是女性,是
精神、亦是物質。天神通常被視為是將對立特質容唯一體的本來面目,然而不
幸的是,基督教卻在調和二元對立中面臨了困難。61假如邪惡的勢力能自絕於上
帝的掌握範圍之外,而獨立存在,那麼這也就意味著上帝不是全能的。而此一
想法也就暗示著上帝其實是透過善與惡來運作,且其本身也是善惡兼備的,不
過,這項另類說法同樣也被基督教的教義所排拒。由此一來,耶穌基督的形象
全然光明,欠缺黑暗的一面,而這個失衡的現象則反映在撒旦(Satan)此一不可或
缺的角色當中,也展現在強調人類邪惡的本質之中。倘若邪惡的力量不肯能是
來自於上帝,那麼它勢必是由人類的意志或無知,亦即他/她的原罪(original sin)
所造成。而其實在中國和日本,崇高的慈悲菩薩不僅以男身相,也以女身相來
表示,如觀世音菩薩。菩薩雌雄同體的特色正如道家所謂的「道」,是陰陽相
生的;又一如中國流傳的地母經所指出「陰陽會合真造化」;而中國古代紀事中的
61 見 Maggie Hyde 著,趙婉君譯,《榮格與占星學》(Jung and Astrology)(新店:立緒文化,2001.12),頁 9。
45
「太初」,即聖女太元(Tai Yuan),結合了男性(陽)與女性(陰)質素於一身。而這
個「太初」其實是最原始的「本我」形象。
榮格曾提出一種集體精神的假定,這種集體的精神包含意識與潛意識的雙
重成分,它們會透過人類的共同文化當中的神話、圖像等,自由自在地跨越時
間與空間的藩籬。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會將它自身投射到外在的世
界,於是創造出一種超越性的意義秩序。換言之,生命具有一種模式、一種次
序或是一種意義,超越於個人的理解之上。它顯現在我們對於宇宙秩序的看法
之中,會藉由人類集體潛意識的投射而釋放出來。而此一投射出來的影像,也
就是榮格所說的-------人類的「本我」(the self)形象。
無論是集體或是個人的精神,都會在潛意識中夾帶這個「本我」的形象,
那是一個代表秩序與完整的形象,而榮格式心理分析(Jungian analysis)的任務之
一,也就是要朝向這個形象接近。在個人的精神世界中,想促使對立的元素彼
此握手言和,將是一個永無休止的過程。榮格對於基督教時期的研究,主要就
是將耶穌基督當作是一個自我象徵而加以分析。人類集體地將耶穌基督等同於
自我的形象,但我們在祂的身上卻只看到光明的一面,而將黑暗的那一面,亦
即陰影的部分摒除在外。集體潛意識則會對此一棄暗投明的舉動加以補償,其
方法便是將集體的陰影投射到天空,或是投射到世界上。此一黑暗面即被視為
罪惡,或是以女性的形象加以呈現,亦即由永遠無法得到喜悅的聖母瑪莉亞作
為代表,因而壓抑了人類有性生殖過程中的「動物」本質。對立元素的調和問
題,也因此不斷地出現在基督教之中,以及個人企圖了解自我的掙扎裡,而此
一對自我的試圖理解,則被榮格稱為「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的過程。62
而關於伊底帕斯想重回子宮和母親懷抱的渴望,在榮格在《轉變的象徵》
(Symbols of Transformation)一書中,重新閱讀伊底帕斯的願望時,他的解讀卻是
62 榮格( C. G. Jung),《榮格自傳─-回憶、夢、省思》(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頁 464:「榮格:『我使用『個體化』一詞,旨在表示一個人變成心理學上的『個人』過程,即變成一個分離、又不可分割的一體或『整體』』。」
46
伊底帕思索慾望的對象,其實並非個人的母親,而是那個無上老母,亦即萬物
之母,如此說來,這整個重返母體的過程中,也就標示著一個人精神重生的開
始。這也就代表一個人重返他自己源頭過程,像是榮格在某個時期遇見了他自
己,艾瑞克森將自己的名字改名,他要自己成為自己的來源一樣。
而露易絲重返母親懷抱,多少也有這樣的象徵意涵。而活在非善即惡、二
元對立的現實生活中,魔鏡裡歪曲的自我形象,常以極其強大的力量,主宰著
我們每個人的人生,大大限制了生命的健全成長。如果露易絲一直持續認同這
歪曲的自我形象,那麼她勢必走不出成長的僵局。令人可喜的是,露易絲能嘗
試去覺察並體會自己內在的情感,重新理解自我,並在另一個空間中重建了自
己的生命。露易絲正在邁向她的個體化過程。
二二二二、、、、傲慢與傲慢與傲慢與傲慢與偏見偏見偏見偏見
傲慢與偏見即是一對孿生姊妹:在露易絲歪曲的自我形象中隱藏著許多的
偏見,她看到了凱若琳的傲慢(即使凱若琳在別人眼中如天使般燦爛)。露易絲的
偏見很多是非理性的想法,她的偏見包括:「自以為要負起照顧家人的責任」、
「一個人應該被周圍的每一個人所愛與稱讚」 、「、「、「、「不幸福或不快樂是由外在情
況所引起」、「一個人必須非常能幹、完美及成功才有價值」、「有一些人是
不好的、邪惡的、卑鄙的﹔他們應該被責備、被處罰。」「期待不得償,或計
劃不能實現,是一件可怕的災禍。」、「一個人應該依賴他人,且必須有一個
強者為靠山。」、「一個人應為別人的問題與適應不良感到難過。」…….等等。
63以艾理斯(A. Ellis,R. A. Harper)所創的理性情緒療法觀點來看,情緒是伴隨
著思惟而生,而種種不合理的想法會造成情緒上的困擾。
露易絲的內在宇宙之投射,形成了她所相信的世界。在珍‧奧斯丁在她名
垂不朽的的《傲慢與偏見》一書中,藉著達西先生與伊莉莎白小姐,淋漓盡致
63A. Ellis ,R. A. Harper 著,何長珠、何真譯,《你不快樂---合理情緒療法》(台北:大洋,1988.3)。
47
的寫出人如何走出巨大的自我,縱身泅泳於愛的海洋。而露易絲最終要走出自
己的偏見,與凱若琳自在共舞,才能擁抱生命的喜樂。彭樹君在為《傲慢與偏
見》的序文中這樣寫著:
我們都有一個巨大的自我,……因為這個巨大的自我,我們總是看不
見真正的自己,當然更看不見真正的對方。透過自我偏執的習性,我
們製造了不同顏色的鏡片,適用於不同的對象。於是我們不是把對方
想得太好,就是把對方想得太壞,可是這一切想像中就只發生在我們
自己的大腦皮質層裡而已,看見的是自己心裡自以為是的畫面,與對
方一點關係也沒有。64
正如同珍‧奧斯丁所想要表達的概念:傲慢與偏見根源於同一母體,一個
巨大的自我。佩特森‧帕特森也視孿生姊妹為同一靈魂的兩面:「我們的生命
都包含光明與黑暗,我們就是自己的孿生。所以最後沙拉‧露易絲為了要成為
一個完整的人,就必須愛凱若琳,這樣她才能同時愛她自己裡面的雅各與以掃。」
65露易絲唯有放下自己的偏見,謙卑的去愛凱若琳,當她認同了凱若琳,也就等
於認同了她自己。這與美國奇幻作家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1929-)
在《地海傳說》中一系列作品,表達的「一體制衡」理念相通。在娥蘇拉‧勒
瑰恩的筆下,沒有絕對的善與惡,沒有絕對的成功與失敗。而書中的主角們開
始時通常是為了應付一些危機或解答一些疑問而做出行動,但當旅程開始後,
便發現原來最不理解, 最困難解決的是自己的內心。
三三三三、、、、自卑與超越自卑與超越自卑與超越自卑與超越
64 彭樹君,〈到處都是達西先生與伊莉莎白小姐〉,《傲慢與偏見》(台北:商周,2006.10)。
65網頁〈美國西北大學網站〉http//www.northern.edu/hastingw/Jacob.htmll 2007.9.5
48
露易絲是自卑的。個體心理學的一個重大發現之一,是所謂的「自卑情結」。
精神分析大師阿德勒曾指出:「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為我們
發現我們自己所處的地位是我們希望加以改進的。」66有自卑感的人不一定都是
顯得柔順、安靜的,自卑感表現的方式有千萬種。有人會在舉止間處處故意要
凌駕他人(這就像有些小孩怕自己個子太矮,總要惦起腳尖走路,以使自己顯得
高一點一樣);有人選擇逃避、畏縮;有人反倒用一種優越感來自我陶醉或麻木
自己,但卻逐步將自己導入「自欺」之中,而他的各種問題也會以日漸增大的
壓力壓迫著他;有人甚而為了保護自己,而去攻擊他人,使自己陷入罪惡之中。
而露易絲又是如何表現她的自卑呢?她在心裡不停抱怨,把所有不快樂的
原因全歸咎於凱若琳、奶奶、母親,自己、甚至戰爭。她恨凱若琳,但她不會
瘋狂地跟她爭吵,她只是不斷地壓抑自己的恨意,她甚至常夢到凱若琳死亡,
甚至夢到自己和嫉妒的「該隱」一樣,是殺死手足的兇手。她也知道留在島上
毫無發展可言 ,但又自覺對家中的經濟有一份責任(或許這也是身為長女的宿
命吧!) 。一方面,她緊抓著家人不放,深怕一旦鬆手,就會躺回那孤單寒冷
的搖籃裡。所以,她不敢對家人表示她的需求,只好默默醞釀並培養自己另一
方面的才能,像是寫詩及讀書。
阿德勒認為,脫離自卑感最直接、實際而完美的唯一方法,是保持勇氣,
並能「改進環境」。「憤怒和眼淚或道歉一樣,都可能是自卑情結的表現,……..
但有些人只是苦心孤詣的要避免失敗,而不是追求成功。」67露易絲的自卑感總
是會造成緊張,所以爭取優越感的補償動作必然會同時出現,她多麼渴望成為
眾人注意的中心。而最後,露易絲靠著老船長的帶領,華萊士船長對她如此說:
「妳妹妹知道自己要什麼,所以機會來的時候,她就懂得把握。……..妳,莎
拉‧露易絲,別抱怨別人沒有給妳機會,妳不需要別人給妳什麼,機會是要靠
自己去創造的。不過你必須先弄清楚妳要的是什麼。」(頁 260)找到了自己的方
66 阿德勒著,黃光國譯,《自卑與超越》(台北:志文,2006.9),頁 51。
67 阿德勒著,黃光國譯,《自卑與超越》,頁 129。
49
向,那就是成為一名醫生。而在她鼓不足勇氣開家鄉時,母親的愛振奮了她,
母親表示她將想念露易絲更多,那「更多」兩個字幫助了她脫離孿生妹妹的陰
影,建立了自己未來的勇氣。再者,露易絲以極優異的成績畢業,這些種種都
幫助了露易絲走出她的自卑感。
四四四四、、、、戰爭與和平戰爭與和平戰爭與和平戰爭與和平
書中多次論及戰爭,露易絲的父親參戰負傷回家,並帶著心理和身體的創
傷出海工作,娶了一名年輕高貴的女教師,生下了一對雙胞胎的女兒。在一九
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露易絲一家人也籠罩
在戰爭的陰影下。而外在的戰場,也同時影射了露易絲內心的戰場。
戰爭的開端究竟為何?在這個世界到處都有戰爭,兩性的戰爭、母女的戰
爭、手足的戰爭、婆媳的戰爭、族群的戰爭、宗教的戰爭等等不計其數,戰爭
起源於對立的兩造,起源於認同與差異。而人內心的戰爭,起源於何處呢?人
內心的戰爭常起源於認同問題。
依榮格所見,他自身的一號人格,因為與當下的世俗活動脣齒相依,以至
於會特別關心自身的歷史地位與身分認同。榮格的一號人格滋事好動,總是要
再此時此地就把事情解決了當。這個一號人格喜歡研究科學,野心勃勃地想要
出人頭地。它渴望社會地位,並且期待坐享高上的生活型態,然而令他最挫折
的地方莫過於-----他老想起自己還擁有另一號人格。68而與他二號人格傾向息息
相關的,則是上帝的世界、永恆及超越時空的智慧,此種智慧乃與「點點繁星
與無垠宇宙」互為一體。每當榮格在描述他的一號人格與二號人格之時,更確
切地說,其實他是在描述「靈魂」(soul)的兩種不同特質。在榮格早年針對心理
學所做的演講當中,他曾引述康德的看法:「……人類的靈魂與精神世界中所
關有非物質的種種,彼此水乳交融地形成一個共同體………而只要一切相安無
68 Maggie Hyde 著,趙婉君譯,《榮格與占星學》(Jung and Astrology),頁 30-32。
50
事,人類的本質將無法意識到靈魂由非物質世界所接收到的感覺。」69在此,康
德所暗示的是靈魂具有兩種不同的傾向,一種是以世俗關懷為中心,另一種則
與精神領域有所接觸。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世俗與精神之間的關聯被等閒視
之,而為有當生活發生異常現象時,我們才會更加警覺到靈魂的精神面向。榮
格曾說:
在我所描繪的世界圖畫中,有一片廣闊的外部領域,也有一片同樣廣闊的
內部領域。人就站在這兩個領域之間,時而面對著這個領域,時而又面對
著那個領域。人們根據自己的情緒或氣質,通過否定或犧牲一方,而把另
一方當作了絕對的真理。70
一個人如果太過認同外部領域,會有危機的產生;同樣地,如果一個人太
過認同內部領域,與這個世界失去聯繫,也會有危機的產生。事實上,榮格在
中年時期也曾面臨認同危機,這樣的危機引發了他與佛洛伊德的決裂。顯然地,
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傾向於物質層面的。佛洛伊德最初把性慾作為唯一的心
理驅力,在他與榮格決裂之後,他才給予了其他心理活動以平等的地位。榮格
認為佛洛伊德心理學所導致出的危機是它無法指出任何道路可以走出生物那毫
無變更的循環。與佛洛伊德決裂後的榮格,發現了人類更廣大的心靈世界,他
發現自我之所以生病,是因為它被割裂開來,離開了整體,失去了與人類以及
與精神的聯繫。而筆者仔細探究,自我為何會被割裂,也是與認同問題有關。
太過認同某物,而抗拒它物,造成精神上的偏執,也引發了心靈的交戰。
戰爭起源於認同與差異,個人認同的細件如身體、種族、階級、性別、社
會、宗教等等;個人主義凸顯了人與人之間的個別差異,也獨立於所謂的「傳
統」之外。佩特森在故事當中,凸顯了個人的獨特性,也強調了「同一」的重
69 同註 56。
70 榮格 (C. G. Jung) 著,蘇克譯,《尋求靈魂的現代人》,頁 130。
51
要性。例如,我們從中看到了她對傳統基督教的挑戰,文本中露易絲的奶奶堅
守所謂基督教的教義,到了「食古不化」的境地,並排斥與她不同信仰的人,
將他們視為「異教徒」。而露易絲與奶奶的衝突不斷,也是作者急欲表達對傳
統某些的不認同,在書末,露易絲身為衛里公會教徒,嫁給了約瑟這個天主教
徒,彼此和平相處,並能互相包容,並從未因信仰的差異引起戰端。
除了信仰,在文本中也探討性別差異的議題。在露易絲所生長的芮思島,
兒子代表財富與保障,女性在這裡注定要扮演弱勢的角色。在芮思島上,男女
工作的區分涇渭分明,而且船夫的船是女人家踏不得的的聖地,露易絲陽剛的
個性及健壯的身體,使得她肩負起男孩子粗重的工作,露易絲無時無刻不盼望
著,能變成男孩子,登上父親那艘船。在舊有封閉的社會中,總是特別強調兩
性之間的差異,而所謂的「性別不平等」是認為女性身體「軟弱」與「性情不
穩定」的直接結果。「事實上,男女兩性之間存在著相當多的重疊之處,再加
上環境因素也可能使此重疊之處為之改變」71,佩特森筆下的露易絲超越了女性
陰柔、男性陽剛等性別特質的特定形象。如果環境壓迫露易絲認同所謂的「女
性形象」,如毫不矯飾就等於粗野等等刻板印象,那麼必定會掀起露易絲內心
的一番交戰。佩特森似乎有意藉露易絲來說明:「女性與男性並非對立的兩造。」
很多少女,一直處在美貌競賽的巨大壓力中。「許多女性在他們少女時代,
便由內在形成自我仇恨的意識。幾乎每一個女人都認為她的身體某個部分『不
對勁』」72露易絲也是如此,像她發現自己愛上了老華萊士船長,才赫然發覺自
己一雙醜陋的手,她認為有強壯、潔淨雙手的男人,絕不會凝視像她這樣的女
人。於是她開始擦乳液、修指甲等等,企圖改變自己醜陋的手。身為女人悲哀
的一點是:我們似乎很難避免和模特兒的幽靈競爭,我們以鏡中平凡的自我形
象和模特兒競爭!而可憐的露易絲,她競爭的對象就是和她朝夕相處的孿生妹
71 Kathryn Woodward 等著,林文琪譯,《認同與差異》(Identity and Difference)(台北:韋伯文化,2006.10),頁 127。
72 Susan Alice Watkins 著,朱侃如譯,《女性主義》(Feminism)(台北:立緒,2002.12),頁 143。
52
妹。
在榮格的精神結構當中,擁有一些條例分明的種類,讓我們所掌握依循,
並能在分析心理作用的過程中運用。舉例來說,當露意絲戀愛了,那麼她血脈
賁張的情緒,也許會與潛意識中的某些部分連結起來,此時她的潛意識便會設
法成為她的意識,並且投射在她所愛慕的對象─老船長的身上。因此說穿了,
其實露意絲所愛的並不是老船長,而是她自己心理那個未被認知的部分。又從
另一方面來看,露易絲憎惡驕傲的凱若琳,那麼凱若琳很有可能是露易絲自身
陰影的傳達媒介;也許是露易絲自己的驕傲,才是她所忌恨與力求抵制的對象。
但是,這類投射是在「唯有一個人情緒對於某個情境的反應,遠大於該情境所
應得的分量」時,才會發生的。73
這些觀念雖然引發了我們對「他者」地位的疑問,但這與拉岡的鏡像理論
正有不謀而合之處。拉岡曾提出「愛米亞」這個案例,愛米亞這個案例曾在法
國轟動一時,他對此案例做了精神分析學的分析,此分析也構成了他博士論文
的一部分。愛米亞的案例是這樣的:
愛米亞是一個 38 歲的鐵路單位的職員,一天晚上,在巴黎的一家劇院
裡當一個著名的女演員走進來時,愛米亞莫名其妙的衝上去,用刀子刺
傷了這位演員。--------但她又承認未見過這位演員。愛米亞具有文學
的抱負,但她的小說和詩歌卻被出版商一次又一次的退回。74
依據拉岡的分析,愛米亞襲擊的演員,其實是她自我理想的化身。她透過
在文學上的努力,希望達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婦女形象,一個具有影響力的作
家。而這位女演員正是她的「鏡像」,她努力尋求認同的他者。然而當她的文
73 見 Maggie Hyde 著,趙婉君譯,《榮格與占星學》(Jung and Astrology),頁 173。在這裡作者提出一個疑慮:「榮格的學說若是推展到極致,將會使外在世界遭到內在化的威脅,如此一來,所有的他者都會被看成是我們個人的延伸而已。」
74 見王國芳、郭本禹著,《拉岡》,頁 131。
53
學實踐失敗時,這一「鏡像」反映出的不是完美的自我,而是自我的另一面,
是「缺失」與「匱乏」的前鏡像狀態,因此激起了她焦慮與仇恨的負面情緒,
她透過攻擊她的理想(化身)來懲罰她自己。
在拉岡的精神分析學當中,自我應被理解成「鏡中的我」,是他人眼中的
我,或是我們所願意讓別人見到的一種我,這類似榮格所說的「人格面具」
(persona )75。由於自我極易認同「他者」的種種物件,所以也造成了自我的割
裂。然而精神有一種傾向是追求整體的,榮格認為:「一切心理過程的集合,
包括意識與潛意識………..,精神係由兩個對立但卻互補的領域所構成:亦即
意識與潛意識。」76潛意識對於意識態度有補償作用,「人格面具」這個屬於意
識範疇的元素,將會被榮格稱為「靈魂形象」(soul image) 的潛意識元素所彌補,
而至個形象也就是女人身上的「阿尼瑪斯」(animus)或男人身上的「阿尼瑪」
(anima)。無論「人格面具」或「靈魂形象」皆因以下的四種功能而顯得多采多
姿:思維(thinking)、 情感(feeling)、感覺(sensation)、直覺(intuition);另外,內傾
(introvert)與外傾(extrovert),這兩種型態的作用,這兩種型態的作用,同樣也在
形塑「人格面具」的特質與潛意識的「靈魂形象」中佔有某種地位。
露意絲常被她自己強烈的情緒所牽引著,那麼在意識上的她,所扮演的應
該是屬於「情感型」 的角色,她對待這個世界的方式,經常是根據個人的情緒
判斷,那麼她的潛意識就會透過一個理性的角色,也就是雄性的靈魂形象,以
便對此做出補償。身為一名女性,她的「阿尼瑪斯」成分可能會以一名男性的
角色或是一個屬於雄性的意象出現在夢中。另外還有一種可能是,它會投射於
外在的世界中。像是露意絲愛上了老船長,此時老船長這個對象正夾帶了露易
絲「阿尼瑪斯」的成分;露意絲也喜愛讀書,拿到了芮思島上破紀錄的高分,
75 見羅伯特‧霍普克(Robert H. Hopcke)著,蔣韜譯,《導讀榮格》(A Guided Tour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新店:立緒文化,2005.1),頁 86。人格面具:「「面具」在拉丁語的意思是演員所戴的面罩,代表他在劇中的角色。榮格將其用在心理學上表示我們在社會交往之中,發展出來並不斷被使用的那一部分個性,是我門意識的表層部分,也是我們的社會面具。」
76 Maggie Hyde 著,趙婉君譯,《榮格與占星學》(Jung and Astrology),頁 170。
54
通過了畢業考,此時她的「阿尼瑪斯」正由那些強烈吸引它的知性媒介所承載。
所以依此觀點分析,使我們更加確信每個人都擁有男性和女性的成分,性別差
異確實存在,但也不應被過度強化,而造成個人的悲劇。
然而令人可喜的是,佩特森安排了一個美好的結局,露易絲終於也能登上
了父親的那艘船,這時誰也沒提起島上女人不能上船的禁忌。當性別的差異被
人們遺忘,露易絲在蘇坡娣號上的奇妙冬日,成了她一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時光。
湯普曼在《世界是平的》一書中提到了,「要解釋何以有的國家能順利工業化,
別的國家卻不能,雖然氣候、天然資源、地理條件都是因素,最大的關鍵卻是
文化,特 別是對勤儉、誠實、耐心、恆心的重視程度,還有願不願意接受改變、
新科技、男女平等。」77在抹平的世界中,我們除了要跨越種族、階級、社會、
宗教等等的界線,還有文化的界線:這其中包括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男
女平等。在文本的最後,露易絲接下「助產士」的工作,也代表了女性在生產
及控制受孕的醫藥應用上,由男性偏見及自私的曖昧歷史中解放出來。78在古
代,接生婆、女性醫療師及「有智慧的女性」都是在所謂的「原始」社會中受
到尊崇的人物,而露易絲的成功,也是女性地位再度抬頭的象徵。
在本書中,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露易絲內在與外在的戰火也漸漸平息,
一切終究回歸於和平。
77 湯馬斯‧佛里曼 9Thomas Friedman)著,楊振富、潘勛譯,《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台北:雅言文化,2005.11),頁 281。
78 .Susan Alice Watkins 著,朱侃如譯,《女性主義》,頁 156。
55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疏離與認同間的迴旋之旅疏離與認同間的迴旋之旅疏離與認同間的迴旋之旅疏離與認同間的迴旋之旅
《孿生姊妹》一書聚焦在一段特別的時空背景,而書中涵蓋的故事時間相當
長,主角露意絲以自傳回憶錄的方式,從小時候一直敘述到自己結婚生子,深
深刻劃一位少女如何走出自我陰影,重建生命的故事,並讓讀者跟隨著主角的
心路歷程,備受感動與洗禮。露意絲的生命旅程代表著某種新女性成長的英雄
典範,我們在她的各個生命階段,看到了不同的生命原型,也看到她如何度過
疏離與絕望的經驗,擊潰了駭人的巨龍。而佩特森對於人性真實而深刻的描述,
更讓我們體會到了生命中任何好與壞的經驗都只是學習的課題,生命最終的意
義不是獲得如鬥士般的勝利,而是得到靈性的成長,對自我的了悟與認識。
露意絲從小一直在尋求父母親的庇護與照顧,比起凱若琳所得到的關愛,
她感受到的是孤兒的無力和被遺棄的恐懼。這份恐懼如此巨大,使她產生明顯
的憤怒情緒,她一面向內譴責自己的無能,一面向外怪罪上帝及父母,任何被
認定沒有照顧她的人或事都在她的指控之列。憤怒之火不停地蔓延燃燒,漸漸
地她把自己活成一座孤島,囚禁在自我意識中,對於家人的愛是如此盲目。矛
盾地是,她不信任自己的能力,而傳達出「我不知道要如何照顧自己的訊息」,
年少的露意絲,在尚未發展的人格部分,就像個孤兒,深深依賴著別人。「如
果『孤兒』的故事由天堂開始,那麼『流浪者』就從囚禁中起步。」79 卡羅‧
皮爾森在《內在英雄》一書中,指出孤兒原型是一種很困擾人的原型,她或他
要成就的是跳脫無知和否定的習性:「孤兒原型所述說是一種喪失能力的感覺,
渴望重回天真的原初狀態那種像童稚般的天真,在那裡所有的需要都被慈愛的
父親或母親型的人照顧妥貼。」80露意絲甚至願意拋棄自主性和獨立性,來換取
一棵無限給予的愛心樹,好讓她遮蔭。然而依賴造成了她的軟弱,也使她無法
學會信任和希望。露意絲只有放下對安全的執著,並能不求回報的付出,才能
79 Carol S. Pearson 著,徐慎恕、朱侃如、龔卓軍譯,《內在英雄》(The Hero Within)(台北:立緒,2005.10,頁 73。
80 同註 67,頁 40。
56
愈來愈不覺得自己是孤兒,當她轉出依賴的漩渦之後,才能真正地踏上英雄之
旅。
英雄之旅也是探索內在生命之旅,卡羅‧皮爾森博士融合了榮格心理學的
「個體化過程」及「原型」概念,並汲取坎伯神話學的若干洞見,將英雄歷險
的原型過程得以從古典的陳跡故事,一躍成為生活中人人正在展開書寫的當代
傳奇。她在《內在英雄》一書中提到六種吾人在生活中自我認定的原型為:天
真者(Innocent)、孤兒(Orphan)、流浪者(Wanderer)、鬥士(Warrior)、殉道者(Martyr)、
魔法師(Magician)等,不同於艾瑞克森的生命週期理論,這六種原型並不是呈線
性發展的軌跡,而是呈循環或迴旋式的推進。每個階段都有它要教導我們的功
課,我們則一再與這些階段相遇,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前面的階段。這使我們得
以在新的層次上複習認知和情緒的複雜型及精緻性。人類的發展受到這些原型
的影響,在相當程度上是可以被預期的。「天真者」學習的功課是墮落,恐懼
的是失去天堂;「孤兒」學習的功課是希望,恐懼的是被遺棄;「殉道者」學
習的功課是放下,恐懼的是自私;「流浪者」學習的功課是認同,恐懼的是順
從;「鬥士」學習的功課是勇氣,恐懼的是軟弱;「魔法師」學習的功課是喜
悅信念,恐懼的是膚淺。我們可以一再重複這些原型和它們所代表的每個階段,
直到神奇的鏈金術完成為止。只要我們能堅持走上精神成長之路,願意通過英
雄之旅減輕身上的重負,我們終於回到伊甸園,再度成為天真者,也了解信任
自己、別人和宇宙是安全的。
而皮爾森認為:「生命的不同事件會影響我們學習的順序和強度,任何重
大改變或危機都要求我們在認同(identity)這個題目上多加注意。」81舉例說
來,尚未處理自我認同問題就進入戰鬥狀態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鬥士」,
他們不知道為何而戰,或者只是為了證明自己的優越而戰。而「流浪者」所需
面臨的主要議題是「認同」,對許多人而言,「囚禁中的疏離」乃是流浪的最
81 同註 63,頁 19。
57
初階段,接著便是有意識的選擇踏上個人的旅程。皮爾森並指出,最典型的男
性發展是由孤兒階段直接到達鬥士階段,並且停留在那裡,唯有到了中年危機,
被迫面臨整合問題時,才可能產生改變。男人典型的進裎看起來像是:孤兒、
鬥士、流浪者、殉道者、魔法師。而傳統的婦女則由孤兒直接踏入殉道者的階
段,而且常常一待就是一輩子,除非有某種特殊的事件推動她成長;有時是孩
子長大離家、丈夫出軌、她自尊被踐踏、或接觸到自由的思想等這些自我認同
的危機,才會迫使她面對並開始探尋自己。她的模式可能是:孤兒、殉道者、
流浪者、鬥士、魔法師。通常婦女被侷限在殉道者的角色,比起男人困在鬥士
角色中更加嚴重。不過令人慶幸的是,愈來愈多的現代文學皆替女性從傳統的
犧牲角色解放出來,而《孿生姊妹》也是這樣的一部作品。
由於露易絲小小年紀便要出海補蟹、補貼家計,她同時經歷了鬥士與殉道
者的歷程,這時自我認同的課題在互不相容的兩個價值衝突中被激發出來,露
易絲這才學習到流浪者的課題,她的生命進程是有別於一般傳統女性的。露易
絲原本扮演著「殉道者」的角色,認為自己爲家人而犧牲,而她內在的「鬥士」
原型卻認定打倒別人以保護自己是必然的,因為她也很想肯定自己的能力,覺
得自己有權受到與凱若琳同等的重視與尊敬。然而她也從未思考自己真正想要
的事物,她並非真的知道自己是誰。她曾經一邊埋怨,一邊重複自己過去的生
活,然而事情沒有任何改變,她仍然認為自己在妹妹的光環下扮演的只是一個
跑龍套的角色。在人生的旅途之中,有時似乎是需要遊蕩一段時間才能成長。
就像心理學家艾瑞克森,在高中畢業後他感覺到迷失,並且對他未來的生命感
到不確定。所以他遊走歐洲一年,而沒有上大學,之後他回到家並研習藝術。
一段時間後,他又再次出發開始他的旅程。他經歷了他後來所謂的自我放逐
(moratorium),也就是一段年輕人花時間試著尋找自我的時期。
在還未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露易絲經歷的是「認同延宕」(identity preclo-
sure) 的過程。艾瑞克森指出,認同的形成大部分是潛意識過程。然而年輕人通
常是痛苦地察覺到們無法做出永久的承諾。他們感覺到有太多事情需要做決
58
定,以至於無法很快做出決定,並且每個決定都會降低他們未來可能的選擇機
會。82很多的年輕人會在達到無憂無慮的「中場」遇到困難。他也在露易絲在這
尋求自我的「中場」時段,她也無法確定自己未來的職業,不知道在她的生命
中到底要做些什麼,即使是她奮力投注的海上工作都只是她的逃避方式,她經
歷到孤立感和一種無法在任何的活動中找到意義,和一種生命只不過就這麼發
生的感覺。
歷史上一些出眾的理論家,例如皮亞傑、佛洛伊德、艾瑞克森和其他人都
花了一些時間尋找他們真正的使命。而他們的追尋雖不總是令人愉悅的,可是
最後都能引領到他們職業上的新澈悟和有意義的改變。雖然延遲認同的追尋是
痛苦的,而露意絲最終能抗拒在傳統的職業認同中安定下來的誘惑,找到了自
己內心真正想要的職業(助產士),並藉由這份工作奉獻自己,在這個時候,「鬥
士」和「殉道者」發現它們可以合而為一,此時分裂的自我有了歸一的感覺。
露易絲藉由另外一種角色扮演,找到一種更高形式的個人整合,邁向個體化的
歷程。
這個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並以行動滿足它們的過程,對建立自我認同是很
需要的,最幸福的人也就是敢冒險做自己的人。然而,人總要堅持對自己的承
諾,這個承諾就是對自己的承諾,人的一生總是有自己對理想的堅持,然而這
個堅持或許是跟主流價值背道而馳的,所以有時候去迎合一個江湖,就是背叛
了自己的夢想。而「流浪者」堅稱生命中最重要的內涵是冒險,「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他不能向命運低頭,寧願死在自己的挑戰裡,也不要沉緬在過去
的榮耀裡。
露易絲將穿戴已久,用來保證安全和取悅他人的社會角色拋掉,勇敢離開
家庭,試圖去尋找自己,去探索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而她最初的自傲感是來
82 Crain, William,劉文英,沈秀靖合譯,《發展學理論與應用》(台北:華騰文化,2005.10),
頁 201。
59
自成功的扮演角色,而我們對扮演角色的選擇,正是選擇認同的基本嘗試。露
易絲也可以選擇繼續留在家中做補螃蟹的工作,然而她對此扮演的角色感到不
滿與空虛,依她的能力、才華與膽識,她覺得自己能有更好的出路。她可能明
白過去所選擇的角色已預先設定好了,而這些選擇受到文化和家庭期望的強烈
影響,但是它們都不是自由的。而當她在這些角色中選擇,並且嘗試著扮演新
的角色時,她開始有點了解自己是誰了。勇於採取行動,順從內心深處對獨立
自主的渴求,讓露易絲能脫困而出。
而弔詭的是,朝向孤立和寂寞的英雄之旅,最終回到了社群之中。露易絲
最終在阿帕拉契社區的崔魯特村到一份可以表達她精神的工作,結婚生子,能
夠擁有愛、做自己,並且可以與她相似的人一起生活 ── 她真正的家。於是
原型的「流浪者」,從依賴變成獨立,再變成共依存中的自主。
這時的露易絲要學的是「魔法師」的功課,學習接受愛、信任和歡樂。魔
法師是一個雌雄同體、整合兩者的人。露易絲剛強健壯、能幹俐落,而她的父
親總以對待兒子的方式對待她,這也使得露易絲偏向男性潛質,展現男性化的
特質。當露易絲將依附的特質暫放一旁,致力於發展獨立與果斷的特質,等到
她確認自己的力量與自主性之後,她扮演起妻子與母親的關愛角色,此時她與
適合她本性的陰性特質再度整合。如此結合起來的女性形象,會比傳統的女性
特質有更強大的能力和趣味。
從「流浪者」轉化到「魔法師」的過程,露易絲必須要重新發展當初壓抑
自己身上跟另一性共通的特質。在讓男性中的陰柔特質(阿尼瑪)及女性中的陽剛
特質(阿尼姆斯)得到重整時,這過程或許會有些窒礙難行。然而正如卡羅‧皮爾
森所言:
當每個獨立的個體變得越來越雌雄同體,兩性的特質獲得互相接纳,
男性特質(maleness)和女性特質(femaleness)就會獲得新的定義。而
且,當英雄愈來愈減少壓抑任何一性的特質,他們會愈來愈清晰、愈
60
來愈均衡,因而有更多轉化世界的力量。83
露易絲雖生為女性,但她所要認同的不只是自己的女性特質,還有男性特
質,當這兩項特質得以融合及平衡時,她才能實實在在活出自己──活出她的
獨立、果決、溫柔和愛,藉由她的工作,幫助了整個社區,也養育了這個地方。
阿德勒認為:「奉獻乃是生活的真義」,露易絲付出滿腔熱情實現夢想,並在
她的工作中體會到生活的真義。她已從奉獻中得到最大的快樂與滿足,也同時
創造了自己的魔法。
在故事的最後,露意絲幫人接生一對雙胞胎後,並以奶水餵養猶如卡羅蘭
般柔弱的女嬰,那時她才對於自己與卡羅蘭有了一種新的理解,並且打從內心
深處接纳了卡羅蘭,這種理解使她變得更加清晰而寬容,唯有愛卡羅蘭,她才
能均衡而完整。卡羅蘭是她生命中的一個重要「他者」,而這個他者正是露易
絲的另一個自我,是露意絲「主體」的形成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回家
走到雪地上,仰望星空時,露意絲耳裡好似聽到那段甜美純淨的旋律,筆者認
為這是她真正達成自我認同的一刻。
83 Carol S. Pearson 著,徐慎恕、朱侃如、龔卓軍譯,《內在英雄》(The Hero Within),頁 205。
61
第肆章第肆章第肆章第肆章 我與社群我與社群我與社群我與社群
────────《《《《太平天國太平天國太平天國太平天國》》》》中的社群認同中的社群認同中的社群認同中的社群認同
《太平天國》(Rebels of the Heavenly Kingdom,1983)是佩特森所撰的歷史小
說,此部是以中國為背景,從太平天國戰士的角度來看待太平天國歷史的始末。
隨著故事主人翁王立的敘述,一路深入接觸到(太平天國)及其中的幾位傳奇
性人物,如天王洪秀全、東王楊秀清、南王馮雲山、西王蕭朝貴、北王韋昌輝
以及奇女子(三娘)等人。作者利用這起歷史事件及人物,編織了以他們為背
景的傳奇故事,是歷史與小說結合的標準創作方式,使讀者透過欣賞小說,來
認識歷史,也藉此為中國歷史上的小片段做了細膩的補充。
在這一章中,筆者所欲探討的是青少年對於一個社群(尤指一個具有強烈意
識形態的社群)的認同心理與過程。在第一節中,先說明「太平天國」興起的時
代背景,其處在一個內憂外患、天災人禍的時代,正是一個「認同危機」的時
代。並分析主角王立為何會投入並認同此社群,其一來自其所處的年齡階段正
是屬於心理社會的「空檔」,其二是為了「逃避自由」,而有了對信仰奉獻的
需要。並探討王立如何建構對太平天國此結合了軍隊與宗教團體的認同。在第
二節中,則分析一個威權團體如何維繫人們對它的認同,其一是以「規訓」,
其二是以「思想的改造」,其對於領袖及團體的效忠,而產生了吸納與排除的
效應,即唯心觀念的結構以無限擴大的吸納系統,自成一套權力體系,而將任
何異質物劃分為必須排除的他者。第三節所探討的是人們對於烏托邦的迷思,
「太平天國」是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烏托邦,在本節中提出了一些描繪烏托邦
的作品做為對照,人們如何在烏托邦中放棄了顏色和差異性,而在這些烏托邦
中所付出無限高的代價就是失去自我,而主角王立最終能夠覺醒與逃離,保有
自己的自由意志,找回自己的選擇權。
62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進入另一個國度進入另一個國度進入另一個國度進入另一個國度
京都鍾埠 殿陛輝顯 林苑芳菲 蘭桂疊妍
宮禁煥燦 樓閣百層 廷闕瓊瑤 鐘罄將鏗
臺凌霄漢 壇焚牲畜 蕩滌潔修 齋戒沐浴
禮拜敬虔 讚美雍肅 懇籲居歆 自求茀祿
胡越貢朝 蠻夷率服 任多版圖 總歸隸屬
── 洪秀全,「御製千字詔」84
太平天國興起於清朝道光年間。這是個動盪不安的年代,天災不斷、飢荒
四起、再加上此時中國的人口已破四億大關,耕地成長的速度比不上人口成長
的速度,農民十分貧寒。社會上下階層的流動趨於平緩造成了龐大的仕紳階級,
底層貧窮的讀書人少有機會進入上層階級,這些情況也衍生出了許多弊端和社
會問題。而且清朝的秘密教派盛行,屢禁不絕,諸如白蓮教天地會在盛世時就
不斷作亂,到了嘉慶道光時,流民飢民和教派結合在各地不斷作亂,清廷八旗
兵早已不堪作戰,綠營兵也已腐敗不堪,幸虧還仍勉強鎮壓下去。西元 1842
年(道光二十二年)8 月 29 日,清朝政府簽下了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
南京條約,開啟了中國近代史滄桑的歲月。此時外國勢力興起,地方土匪與國
際軍隊皆橫行,這是個國家官僚及道德傳統面臨危機的時代,也是一個全球化
貿易、販賣毒品獲利的時代,印刷品散佈與大量文盲並存的時代,充滿不確定
性而絕望的時代,是一個認同危機的時代。
或許有人認為歷代大型的群起而攻,大都是因飢寒而揭竿起事,不過就是
地方勢力群集向中央討一碗飯吃而已,無關宗教信仰。然而筆者認為太平天國
84轉引自曼威‧柯斯特(Manuel Castells )著,夏鑄九、黃麗玲等譯,《認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 (台北:唐山,2002.11),頁 5,「御製千字詔」,太平天國甲寅四年(咸豐四年,1854年新刻,凡四言句,數上帝創造萬物、耶穌救世贖罪、洪秀全受命下凡起義、建都天京諸事。略似舊塾之千字文與三字經,為太平天國幼學啟蒙讀本。
63
的起因背後雖有其氣候、環境、政治、民生等誘發點,但其打著宗教旗幟的理
念,卻是吸引老百姓加入的主要原因。在這樣的亂世之中,宗教成了人民的精
神寄託所在,人們渴望得到「救贖」,另覓桃花源以安身立命。這時洪秀全所
建立的太平天國便適時的成了人民可以避難的烏托邦,這樣的宗教運動有其救
世的成分,企求一個至高的救世主,解世人於災厄,開創太平世道,結束以往
的一切。洪秀全得以自立為天王,究竟是英雄造時勢亦或時勢造英雄,恐怕也
難分的清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成了歷史上最詭奇的事件之一。
洪秀全出生於廣東花縣一個農民家庭,自幼接受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文
化教育,從十六歲開始他的應考生涯,然而,卻一再地名落孫山這段期間,他
接觸到了基督教徒梁發節引基督教教義並加以解說的一本小冊子-「勸世良
言」,他認為他是受命於天的真命天子,《勸世良言》是上帝賜給他的天書。
他深信自己是耶穌的幼弟,天父交付給他特殊的使命,要把神州從滿洲妖族的
統治下解救出來,帶領著選民,到他們自己的人間天堂去。洪秀全抱持著這樣
的信念,遂創「拜上帝教」,在一八五 0 年匯成太平天軍,他帶領著這支軍隊,
攻無不克,但也生靈塗炭。一八五三年中,洪秀全麾下的水陸聯軍攻佔了長江
重鎮南京,創建為她們的太平聖地,並以此作根據地達十一年之久,直到一八
六四年為止──其間有兩千多萬人或戰死、或餓死──洪秀全及其殘兵則死於
兵燹飢饉。
史景遷(Jonathan Spence,1936)在《太平天國》此書中指出:
洪秀全及其信徒在一種天啟式的靈視(apocalyptic visions)之中步
上這場驚心動魄的大浩劫。………本書卷首語引了濟慈的詩,它就是由
《啟示錄》而來,有些人相信自己身負使命,要讓一切「乃有奇美新造,
天民爲之讚嘆」,而洪秀全就是其中之一。那些從事這等使命的人極少
64
算計後果,而這就是歷史的一大苦痛。85
革命本身其實就是歷史上既傷痛又弔詭之處,開刀焉能不導致流血?然而
過多的流血,又傷了國家民族之體,太平天國最終無法太平,更遑論開啟千年
盛世?雖說「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然而太平天國也確實有力地打擊了清王
朝的封建統治。姑且不論太平天國的功過是非,筆者在此要探討的是人們如何
在一個認同危機的時代,去建構個人與集體的認同。曼威‧柯斯特(Manuel Castells)
在《認同的力量》一書中指出:「認同的建構所運用的材料來自歷史、地理、
生物、生產與再生產的制度、集體記憶及個人的幻想以及權力機器及宗教啟示
等。」86筆者意欲找尋人們對於「烏托邦」,一個「公社天堂」中的認同與意義,
解構其認同的主要材料包括權力機器及宗教啟示、戒律等等。
佩特森筆下的《太平天國》,其主角是一個十五歲的農家子弟:王立。他
原本屬於故鄉湖南的那片紅土壤,那片紅土壤原本應布滿綠油油的稻秧,然而,
自從來了滿清軍隊的逃兵及四處流竄的土匪之後,大地卻像被剝了層皮似的傷
痕累累。一小顆的甘藍和大頭菜、一隻生病的老母雞是他們一家三口僅剩的糧
食。儘管如此,希望總是有的,他們的希望就在東北牆角的第五塊磚裡,王立
的爹在那兒藏著稻米種子。然而圓夢之旅的坎坷與艱辛,超乎王立的想像,命
運把王立送進了幾個土匪的手中,迫使王立離開心愛的家園。
起先,王立是出於無奈的的脫離家庭,然而樂觀的他想到家裡少他一個人
吃飯,對他的爹娘來說還輕鬆些,再者,他也能藉此見識外面的世界,或許有
一天自己還能衣錦還鄉。當王立把希望寄託在未來時,他的離家之旅也不再那
麼孤單,當他先暫時切斷與家庭原始關係的臍帶時,他將自己投入了一個未知
與全新的世界。後來,王立以奴隸的身分被賣給了新主人,這位新主人帶他脫
85 史景遷著(Jonathan D. Spence),《太平天國》(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台北:商周,2006.10),頁 9-10。
86 曼威‧柯斯特(Manuel Castells)著,夏鑄九、黃麗玲等譯,《認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 ),頁 7。
65
離了土匪的魔掌,可以說是他的救命恩人,王立對這位救命恩人有說不出的感
恩和尊敬,這位救命恩人就是美玲。美玲是個沒有裹小腳,擁有一雙「天足」
的聰慧女孩,曾經因為幫助拜上帝會的兄弟,而成為他們的一份子,再加上豪
爽勇敢的個性,在太平軍中擔任隊長的職位。因著美玲的關係,王立必須加入
太平天國,一開始王立對於這樣的組織是抱著好奇與懷疑心態的,因為在這裡
但不能擁有有自己的姓氏,還得隨時對付惡魔。
「在太平天國裡,沒有男人、女人的分別。天父之下,人人平等。我們
生下來就應該有求知的權利,我們應該有自己的土地,而且,」他的
聲音突然變得低沉,「就算遇到惡魔的侵襲,我們也應該抗戰到底。」
(頁 56)
即使王立不怎麼認同這樣的團體,但還是在美玲及老朱的言談舉止中,去
試著了解太平天國中的一點一滴。或許是因為太累了,或是心存感激,更或是
滿心似的好奇,王立迷迷糊糊地加入了太平天國。太平天國的前身是拜上帝會,
它可以說是融合了教會和軍隊的組織。太平天國和西方的中古教會有很類似的
地方,中古教會強調人的尊嚴,強調人和上帝相像,感覺起來眾人平等,跟上
帝都很相像,同為四海兄弟。
起初,拜上帝會的最初成員是來自客家民族,事實上天王自己就是客家人。
客家人從廣州城之東北持續向桂平一帶遷徙,已有五十多年,遠早於海盜侵入
內地。因社會秩序動盪,遷徙不絕,以致在某些地區,客家人比土著還多,尤
其又以山區為然。對於處於如此艱困的客家人來說,洪秀全的救世之道尤其能
引起共鳴,而許多人急於跟著馮雲山皈依拜上帝會,不僅是因其宗教教義,也
因其人數與組織意味著團結一致,對付著各方的威脅。後來拜上帝會所吸引的
成員大都是屬於中下階層的人,除了客家農夫之外,有的是煤礦工人,有的甚
至當過土匪或是海盜。有了功名的人也很少加入拜上帝會。拜上帝會會眾也有
66
許多能識字,但這些人大多是科場失意,或是靠著粗通文墨而在社會邊緣討生
活:有些是在官府衙門謀差的小吏,有些憑著粗通律例幫人打官司,有些略通
醫理,四處行醫,有些則是當舖老闆、商店夥計、小業主,甚至還替有熱中功
名又無望中考的人去代考。87
王立在太平天國中所遇到的朋友像是美玲,她的出身是客家農民的女僕;
老朱,以前是個煤礦工人;老沈,曾經是鄉下私塾裡的老師,還教導王立識字。
來自四面八方、不同背景的人要在同一個團體中融合在一起並不容易,然而在
太平天國中這樣一個結合教會與軍隊的特殊團體之中,意識型態緊緊的將他們
聯繫在一起,既然是同為上帝的子民,那麼個人差異在無形當中被抹平了,異
質的東西被淹沒在同質的東西之中。在這時,構成群體一部分的個體在多大程
度上不同於孤立的個體。依據勒邦對群體心理的描述:無論組成心理群體的個
人是不管他們的生活模式、職業、性格或智力是相似還是不相似,他們被轉變
成一個群體這一事實,使得他們擁有一種集體心理(collective mind),這種集體心
理使得他們以完全不同於他們每一個人在獨處時的方式進行感覺、思維和行
動。88
不管是富商還是海盜,太平天國給了這群人看重自己的理由,換句話說,
它給了大家希望,這希望成了他們歸屬感的來源,也藉此建構了他們對太平天
國這群體的認同。王立從原先對太平天國的好奇與陌生,一直到熟稔與認同(這
也得歸功於美玲亦師亦友的教導與帶領),在太平天國中的王立已不再是以前的
王立了。他漸漸信服太平天國中的教條(即使他曾經懷疑過),然而在群體強烈的
意識之中,他的個人意識似乎漸漸薄弱,原先的性格以似乎被群體的性格所取
代,這種被團體浸潤的過程好似一種被催眠的狀態。王立在不知不覺之中順從
了烏托邦式的展望與教條的邏輯,他必須捨棄舊有的個人,甚至在必要時還要
87 史景遷著(Jonathan D.Spence),朱慶葆等譯,《太平天國》(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頁 137。
88 轉引自〈勒邦對群體心理的描述〉,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楊韶剛、高申春等譯,《超越快樂原則》(Fenseits des Lustprizips)(台北:Portico,2007.1),頁 106。
67
爲了信仰與團體犧牲。而對信仰奉獻的需要,是心理學家認為造成這些趨勢與
易感性的認同危機的一面。艾瑞克森認為十幾歲二十幾歲的青少年,就算是沒
有明確地表現他們的信仰或興趣,也會對個人領袖、對團體,或艱苦的活動或
技巧獻出自己。他在〈自我認同問題〉(The Problem of Ego--Identity)一文中指出,
在青年認同衝突之中,他們有許多迫切的問題與曖昧的心理狀態,而意識型態
供給了他們一些簡化的答案。89
對於王立這樣的青年而言,雖然將落葉歸根的希望深埋藏在心坎裡,但也
抱著在外面世界闖蕩的夢想,他不太清楚自己到底是什麼人,也不明白將來自
己想做什麼樣的人。由於物質生活的匱乏,王立只要有陽光與食物便高興萬分,
太平天國提供了一處他可以溫飽的地方;由於不識字,在思想方面,他純潔得
如一張白紙,這時太平天國的信念與教條,填補了這樣一個社會心理上的「空
檔」(moratorium)90,也成了他的啟蒙教育。其實王立不知道自己此時只是向暫時
的信仰獻身,透過識字雖使他達成啟蒙,但是反而更被矇蔽了。
中國自董仲舒以來獨尊儒術,道家站在了弱勢的這一方。儒家教人要移孝
做忠、忠於朝廷,此觀念也有利於朝廷的統治;而西方,透過基督教施行統治,
將希望寄託於來生,二者皆是承載了意識形態的國家裝置。太平天國也是政教
合一的一個國家裝置,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聲稱結合西方基督教義、中國儒家大
同思想、農民平均主義。不過,太平天國排斥儒家,稱儒家經書爲「妖書」,
洪秀全讓自己的一場奇夢染上反儒家的色彩,加入一大段對話,說明孔子的愚
蠢和可疑。他們接受基督教上帝,教名為「拜上帝教」,但其實對基督教一知
半解。他們的宗教思想,可能全部源於當時的中國籍基督教傳教士梁發所寫的
《勸世良言》。後來有外國傳教士知道了這件事,試圖向他講述聖經的道理,
反而被洪秀全斥為異端。不過,洪秀全從基督教得到啓示的這些思想對於當時
89 愛力克森 (Erik H. Erickson) 著,康綠島譯,《青年路德》(台北:遠流, 1999.9),頁 46。
90 同註 76,愛力克森認為:社會,由於認識到青年在最熱誠的獻身之中可能有很激烈的改變,當他們不再是兒童,而又還沒有在行為與道德上形成未來的認同感之時,會給他們一段時間,這段時間即稱為「空檔」(moratorium)。
68
處於半殖民地社會的群眾有著很大的號召力。
作者佩特森把太平天國天啟式的神蹟、看似合理的教義、同儕間的互助情
誼等等攤展在王立眼前,讓王立一步步獻身於這個社群,投入了他的忠誠。即
使他那可憐的腦袋如何混亂,但為了數個模糊的希望,他漸漸拋棄了過去的回
憶,告訴自己要全心全意的效忠於太平天國。這時的王立根本不清楚或不關心
真正問題在哪裡,他總是有些必須服從的紀律,某種程度的團體感,以及對於
一些不甚明確的價值的堅持。太平天國給予了王立一種新的身分、新的使命感,
讓他覺得自己不再是普通人,是被選上的,是從今開始要創造新事物的人。這
樣的使命感的情緒,原先只存在於幹部之中,但愈來愈擴散開來。剪掉髮辨,
在當時被視作異形,反而使他們共同體的意識更強,和他們對立者是天之敵人
的妖魔,而這時頭頂上的黑髮,感覺上就像是被挑選者的象徵。
與其說王立奉獻於這樣的宗教團體,到不如說王立是在這樣的團體中尋求
安全感。對於人類對宗教看似一致性的需求,佛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
也感到迷惑。他對這種需求的解釋是逃離自由。人們因為逃避因知覺到個體獨
立存在的無助與孤單,轉而投向教會的有力權威。他如此寫到:「強迫性的尋
求確定不是真信仰的表現,而是根植於壓制難以忍受疑惑的需要。」91我們是獨
立個體的想法,要為自我負責,並尋求生命中的意義,對很多人而言是可怕的,
而宗教則提供了一個逃離這些恐懼的管道。依據佛洛姆的理論,對於權威領導
者的屈服,可以帶給許多人力量與安全的感覺。同樣地,將他們的自我屈服於
上帝之下,亦帶給這些人的心靈一種充滿被保護的滿足感。
佛洛姆同時也區隔了權威式宗教(authoritarian)及人性化(humanistic)宗教的差
異。前者強調我們在一個強有力的上帝的控管之下,個人的行為必須符合上帝
的旨意,用上帝的紀律控制一切。在人性化的宗教中,人們必須發展他的思考
力,才能了解他自己,他與他人間的人際關係,以及他在宇宙中的存在地位。
91 佛洛姆(Erich Fromm)著,管韻鈴譯,《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台北:志文,2002.10),頁 83。
69
佛洛姆說:「人類的目的在於成就最大的力量,而非最大的無助。」權威式的
宗教,否定個人的認同,人性化的宗教,則給予個人成長的機會。92 佛洛姆對
於上帝的看法,與榮格有類似之處,榮格認為每個人的集體潛意識都遺傳了上
帝的原型,基督是一種象徵,藉著十字架上的四個點,對比著人類的好與壞、
精神與物質層面。佛洛姆則直接地表達,他認為上帝是內在形象的投射。
太平天國很顯然地是屬於權威性的宗教,而非人性化的宗教。洪秀全深信
自己是耶穌的幼弟,天父交付給他特殊的使命,天父天兄長藉著幾位太平天國
的首領以顯聖。天父皇上帝附在楊秀清身上,透過他的聲音傳達旨意,而天兄
耶穌則透過蕭朝貴傳諭洪秀全和拜上帝教教眾。在這裡,統治者皆成為傳達上
帝旨意的工具,上帝為在位者,而底下人的必須唯命是從。這樣的做法,筆者
以為無疑是將人與上帝切割開來,否定了人心中的上帝,而去崇拜一個外在的、
另創的上帝,危機也就在此發生,人們在這樣的宗教中極易迷失自我。
書中的主角王立,就是在這樣威權森嚴的社群之中,漸漸地聽不到自己內
心深處的聲音。
92 William Crain 著,劉文英,沈秀靖合譯,《發展學理論與應用》(台北:華騰文化,2005.10),頁 197。
70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自我自我自我自我的擴散的擴散的擴散的擴散
「在新朝代宣布之前,王立只不過是個孩子,一個貪心的農家子弟,
根本就是個豬仔。現在,他突然變成了男子漢,是太平軍的一員,
發誓要從滿州人手裡救回中國,讓全世界歸屬於太平天國。」
─凱瑟琳‧佩特森(Katherine Paterson),《太平天國》93
一一一一、、、、叢林規則叢林規則叢林規則叢林規則
由於時局的動盪,越來越多男女加入拜上帝會,太平天國的首領不但要供
養保護這些新教徒,也要維護自身的道德純潔,還要節制底下人互鬥或放縱。
洪秀全在創立拜上帝會之初,就曾定下戒律,對行為放蕩多所批評,又吸收《聖
經》和摩西十誡的內容,規矩更嚴。加上時而的天降神諭,例如:「眾小,頭
一定要聽爾天父教導,第二要聽哥教導。總要堅耐遵正,切不可反草也。」94「增
啟志氣來,頂起江山界人看,爭起爾天父天兄之綱常。」95洪秀全自己又撰寫了
許多文章如《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及《原道覺世訓》,也吸引了許
多年輕人感激崇拜地讀。縱然這些規律是屬於思想改造的一部分,但是它用以
維持團體的紀律、凝聚團體的向心力及塑造信徒們的認同起了很大的作用。而
這種道德勸誡背後還有嚴懲犯錯者來支持。另外太平天國將男女分別編入男營
女營的政策,須至天國成功之日,夫妻才能團聚。太平天國發展這項政策,不
僅對婦女生活有嚴格約束,也促成了「女軍」建立,且女性在太平天國的官僚
體系中有為官的權利。
書中的女主角美玲,可說是一位女中豪傑,她在太平天國中擔任的是隊長
的職務,以亦師亦友的身分帶領王立認識太平天國的種種規定和信條。需要遵
93 凱瑟琳‧佩特森 (Katherine Paterson),連雅慧譯,《太平天國》(Rebels of the Heavenly Kingdom)(台北:小魯文化,2005.7),頁 123。
94 史景遷著(Jonathan D.Spence),朱慶葆等譯,《太平天國》(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上) ,頁 154。
95 同上,頁 160。
71
守的十誡是:
「第一:只能敬拜上帝。第二:不可敬拜別的神明。第三:不可濫用
上帝的名。第四:要謹守第七天為安息日。第五:要孝敬父母。第六:
不可殺人。第七:不可姦淫。第八:不可偷竊。第九:不可說謊。第
十:不可忌妒、貪圖上帝給別人的東西。」(頁 89)
除了這些,王立在受洗之前還要跟著馮雲山唸信條,而這些信條都是一些
他們先前被要求寫下來,坦承犯過的罪惡。王立也曾坦承過自己的罪惡,包括
貪心、崇拜鬼神、虛偽撒謊,在這之後還要答應全心服從上帝的天條,覆誦一
條條戒規。對王立來說,這真是全新的生活。
太平天國頂著高道德標準,企圖創立一個理想國,代表著天理公道,是當
時無力實現的更高社會形式,是當時人民內心的真誠渴望。而提出「規律」,
是爲了要控制整個社群的成員,以規律作為生活的準則,加強此社群的秩序性
和社會性,其成員應該嚴守規律,生活才能幸福。傅柯( Michel Foucault,1926-1984)
在《規訓與懲罰: 監獄的誕生》一一一一書中,認為規訓從身體控制慢慢研發一系列
系統性的控制,形塑一種社會壓制的角色,後來整個社會變成一個「監視社會」,
權力無所不在,規訓無處不發生。在太平天國這樣一個結合教會與軍隊的社會
中,運用了宗教的意識形態,傅柯所言的層級監視、規範化裁決、檢查等規訓
手段,皆在此實施的淋漓盡致。
吉卜林(Joseph R. Kipling, 1865-1936)熟為人知的《叢林故事》裡,一再強
調「規律」的重要性。《叢林故事》講述的是嬰兒毛克利在印度叢林中被狼撫
養成人的故事。一位叫做毛克利的小孩,在一次遭到老虎的攻擊中,與父母走
散。他被狼群收養,從小在叢林中成長,遵守「叢林法則」,與動物們結下了
深厚的友誼。叢林裡的狼族,訂有各種規律,用來互相監督彼此間的行為,以
維護叢林間的和平與自由。毛克利以人的身分加入了狼族,成為叢林裡的自由
72
之民,必須也要接受叢林中的教育,要是他不懂叢林裡的規律的話,一天也沒
辦法生存下來。規律就是規律,並不會因毛克利的聰明活潑就隨便姑息,叢林
中的嚴正規律不勝枚舉,例如:「就是無論老虎、豹、硰者其他肉食性動物,
都不得咬殺到此地來喝水的任何走獸,違背者就得按照叢林的規律被處極刑。」
96「叢林裡流傳著,假如補殺了人類,就會染上嚴重的皮膚病,儘管是堅牢無比
的牙齒,也會掉得乾乾淨淨。」97在叢林中,為了得到自由就必須嚴守規律。
吉卜林藉由叢林社會來隱喻烏托邦的和平與安樂,也藉此對照當時印度社
會因為階級制度所造成的不平等現象。印度地方對於階級制度很重視,他們相
信:人的命運是註定的了,身分、階級的高低,早就由上天給安排好的了。叢
林裡的狼社會,並沒有這個規定,大家一律平等,更沒有貴賤高低之分。叢林
裡的規律是公平的,人類卻是為了自己的私利來制定的。而為了建立一個烏托
邦,有時戰爭是必須的,所以在書末提到了毀滅村莊,要把它納入叢林的版圖,
因為叢林裡是自由民族的安樂土。然而,即使毛克利遵守叢林規則,活在自由
的土地上,他的世界中也帶有深刻的不安全感,這讓我們想到:是否在規訓機
制下的被控制者的「配合」沒有了自主性?吉卜林在這裡也表露了毛克利的認
同問題:毛克利是一個具有思維能力的生物,從小就被迫在做人還是做狼之間
做出取舍。這就是這個故事的魅力所在,也是毛克利痛苦的根源,他不知道自
己是誰,也隱喻了青春期的不確定性。
如同毛克利在進入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必須接受叢林規律的制約,王立也
必須接受太平天國的教規洗禮。在這裡,我們歸納出一個論點,意即人在進入
一個社群之後,為了認同這個社群,思想的改造是必須的。艾瑞克森指出:思
想訓練的工作之一是將個人與外在世界分離,使他早先的價值與他的意向與期
望分開;這個過程可能創造出新的信念來,來取代他幼時與青少年時期學到的
96 吉卜林(Joseph R. Kipling)原著,劉原孝改寫,《叢林奇談》(The Jungle Books)(上)(台北:東方,1991.5),頁 27。
97 同註 87,頁 35。
73
東西。很明顯的,這種訓練必是一種震擊治療(shock treatment) ,因為他們的目
的是想在短時期裡取代長期培養出來的東西。98
因此,思想訓練在剝奪享受方面必須很尖刻,它必須把個人與他熟悉的世
界分開並加強他內溯與自我批評的能力,使他幾乎到達自我擴散的地步,但並
不讓他發生心理分裂的現象。同時,它也要想辦法教這個人帶著新的信念回到
世界上去,而這個新信念已深深嵌入它的無意識中。艾瑞克森認為,對思想訓
練來說,青少年晚期是最佳的時刻,而青少年是最佳的人選,因為在青少年時
期裡,思想的重新排列組合正在進行,而各式各樣的思想可能性也正等待著機
會、領袖或友誼的出現來安排高下前後。而人在任何時期,都不比青少年更感
覺到驅力雜亂地表現,也不比他更需要過度系統化的思想與過度高估的文字來
供給他一個類似內心世界的秩序。
王立原本過著淳樸的農家生活,對於家鄉以外的事物一無所知。在離開家
鄉以後,他所等待的正是無限的可能與機會,此時他需要某種帶領,他的自我
在不自覺中進入擴散。而進入了太平天國這樣的「叢林世界」,領袖與規律形
塑了他他的新信念,而他接受的正是一套過度系統化的思想。在太平天國中,
善惡的定義必須非常清楚,也必須是從來就如此,將來也不變的絕對力量。這
力量對過去的記憶必須壓抑下來或仔細地引導,所有的意向都必須集中在那共
同的烏托邦中。雖然這「叢林規則」的制定,是為了符合團體最大的利益而定
的,但是到最後卻成為符合領袖最大的利益而定。洪秀全所訂的規律雖是根植
於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基礎上,但是卻可以將自己摒除在規律之外(例如所有的成
員都必須男女分營,而自己卻可以妻妾成群等等)。
作者佩特森擅於描繪人物的心理細節,我們隨著故事一路地鋪陳,窺見王
立身處在太平天國的制度下,他的思想也在不自覺的情況下被改造了。艾瑞克
森認為,在近代的思想改造之下,可以找到一些心理學的法則,而所有的制度
98 愛力克森 (Erik H. Erikson) 著,康綠島譯,《青年路德》,頁 160。
74
都是開始使青少年認同擴散惡化後來卻能治療它的實驗。99嚴格說來,王立正是
太平天國的實驗對象。太平天國之所以能順利的對王立進行思想的改造,其成
功的因素如一些研究中共思想改造的學者所提出的:脫離家庭與團體、與外界
隔離、減少感官的刺激、文字力量的極度擴張、缺乏隱私、極度強調兄弟之愛;
以及向創造代表弟兄之愛的領袖集體的獻身。根據勒邦的群體心理學,生物一
旦以某些數量聚集在一起,不管它們是一群動物還是人的集合,它們都本能地
把自己置於一個頭領的權威之下。雖然一個群體的需要相應地迎合了領袖的產
生,為了喚起群體的信仰,他本人必須被強烈信仰入迷地支配著;他必須擁有
強烈並施加於人的意志,該群體……….它沒有自己的意志……..能從他那裡接
受意志。100所以在這樣的極權統治之下,領袖意志成為群體意志,而群體意志
取代了個人意志。這領袖需要的是無比的專橫,他所尋求的是:以「命令」和
「組織」能為他們帶來利益的職位。尤其是在國家動盪的不安時代,這樣性情
的人會應運而生、揭竿而起,這樣的人可以是篡漢的王莽,可以是納粹的希特
勒,也可以是太平天國的洪秀全。這樣的人利用人們深切的渴望------渴望出現
一位救世主保障他們的安全、領導他們、關愛他們。當一個知道怎樣扮演用心
善良的領袖這一角色的人物出現時,人們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確信他就是救
世主,即使當時他事實上是一個將會帶給他們和他們國家的災難的破壞者。而
洪秀全以為自己就是上天的力量,慢慢相信自己已經不受世道的評判,他甚至
將《聖經》據為己有,甚至覺得可以照自己的意思來對《聖經》進行修改,如
此便能以「更純正」的方式把上帝的旨意傳達給信眾。作者佩特森主修「聖經
學」,父親又是傳教士,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她對於此事件應有更深入的詮釋。
然而在書中,她不帶任何批判,只是藉王立這名少年的眼睛,來照亮這歷史事
件隱藏的幽暗之處。
99 同註 89,頁 160。
100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楊韶剛、高申春等譯,《超越快樂原則》(Fenseits des Lustprizips),頁 114。
75
「太平天國」是洪秀全「誤讀」《聖經》所掀起的歷史巨浪,就如同希特勒
妖魔化了英雄主義,確實造成了歷史上的最大災難。在洪秀全所樹立的權威及
明定的信條之下,造成了多少生靈塗炭,這歷史的一大苦痛,也是他這樣一名
威權領導當初所始料未及的吧!
二二二二、、、、吸納與排除吸納與排除吸納與排除吸納與排除
佛洛姆在《逃避自由》一書中寫到:「法西斯體系自稱為權威型,因為他
們的社會和政治結構中權威扮演主宰的角色。我們所謂『權威人格』是指它代
表法西斯主義人性基礎的人格結構。」101 洪秀全從《聖經》中得到力量、靈感
和使命感,認為他自己可以代表上帝行使他的權威,是一神格化的領袖。他以
一個救世主姿態出現,吸納許多受他感召的信眾,創建一個可供驅策的實踐基
礎,其對於新秩序與新生活皆具有內在的法西斯衝動。所謂的法西斯衝動是「對
於一個透明而理想化形象的渴求,以及向此形象之認同與順服」102洪秀全認同
的是上帝此一形象所代表的至高無上,而在法西斯式的妄想機制下,強調新秩
序、進步、正確與一致性,從而吸引所有分子的強烈投注。佛洛伊德在討論集
體心理學時,也曾指出:個人與群體的感情關係的內在聯繫是「認同」機制,
也就是自我在群體的領袖身上看到「自我理想」的成分,而發展出如認同父親
一般的認同心理。自戀力比多大量流向對象,對象成為我們所無法企及的自我
理想的替身,而且變得越來越崇高可貴,最後完全佔有自我自愛,而自我亦樂
意犧牲奉獻自己。這種對於領袖的認同紐帶起源於對於「原始父親」(primal father)
的認同:「群體希望受到沒有制約的力量支配,這是對權威的極端熱情,對於
101
佛洛姆(Erich Fromm)著,管韻鈴譯,《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頁 153。 102
引自周蕾〈我們之間的法西斯渴望〉(“The Fascist Longings in Our Midst”, 1998),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台北:麥田,2004.9),頁 293。
76
服從的渴望」。103
法西斯思維的唯心傾向是將主體絕對化,而主體與形式之間形成有機組織
的關聯;「心」即是形式的內涵,主體之「心」的擴大與實踐,便是有機而一
致的國家形體。當有機的國家形式發展到了極致,國家主體成為「先驗」而「唯
心」的精神主體,區分我/他,以及內群與外群,便成為必要動作。區分的同時,
排他性暴力亦隨之而生。佛洛姆在分析獨裁主義性格曾指出:獨裁主義的性格
特徵從其結構上看,具有一種先天的服從性,但也需要統治他人。而真正的民
主或革命的性格恰與這兩者相反,它既拒絕統治別人,也拒絕被別人統治。104洪
秀全不是屬於真正革命鬥士,因為他也需要群眾的追隨,進而去統治群眾。而
這些群眾,必須朝向同質性發展,個體的自然需求必須被壓抑或是棄絕。被壓
抑而受控制的被動群眾一則以自我施虐的方式排除個人之不潔與情慾,以便達
到「純淨」,再則以施虐方式主動排除團體之中的「不潔」,以便促成團體的
同質性。
在太平天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一種同質的基礎上,不屬於此
系統的異質物便會被排除。同質化的過程必然會造成異質化的運作,唯心觀念
的結構以無限擴大的吸納系統,自成一套權力體系,而將任何異質物劃分為必
須排除的他者。太平天國以上帝為最高價值的認同對象、依附、躍升、並且自
我淨化,甚至依此準則將異質對象妖魔化。對於太平軍而言,清軍就是對抗上
帝的妖魔鬼怪,必須加以殲滅。
書中主角王立盡其所能地透過長久的學習、背誦、教養,來服從紀律,棄
絕愉悅,嚴厲地打擊惡行。只崇拜上帝、不崇拜妖魔鬼怪、男女分居、奉行獨
身主義、尋求純淨的心靈等等,這些都漸漸地烙印在他的腦海裡。再加上他親
眼目睹天父上帝、天兄耶穌的顯聖:
103
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頁 289。 104
佛洛姆(Erich Fromm)著,林逸仁譯,《生命之愛》(For the Love of Life)(台北:南方,1988.9),頁 151。
77
我是天父,今天特地和你們的天兄降臨人世間。我的子民,現在你們必
須接受考驗。惡魔已經包圍你們,處處威脅你們。但是不要驚慌。我天
父,是天國裡的統治者,是造物者,是你們的救世主。我們要戰勝惡魔,
拯救世界。(頁 128)
所有的群眾受到這樣的激勵,一起高聲呼應「榮耀主!」。「榮耀主!」
這句話曾經是令他感到不屑的言論,如今他卻跟著群眾一次又一次不斷地呼喊
著,心中有說不出的喜悅歡暢,這句話已成了他的肺腑之言。因為,他認為這
一切都是真的。「至高無上的天父跟大家說話了,他並不是泥像或石雕,祂比
雷電還要權威。所以,王立選擇崇拜祂,他再也不會害怕了,崇拜上帝才是對
的。」(頁 129)在此時,王立經歷了共同整體的痙攣時刻,他與更大的對象結合
而達到一種宗教性的狂喜瞬間,這種感覺是神聖的。犧牲自己,失去自己,是
神聖的起點,這種與神聖結合的狂喜,甚至使王立有了「爲君捐軀」的使命感。
王立對於上帝、領袖與團體的認同漸漸穩固,於是跟著太平軍一起展開「聖戰」
行動,殲滅清兵。起初他的手碰到溫溫的鮮血時,還會顫抖不已,然而他一想
到這些是滿州的狗,是違抗天意的妖魔鬼怪,他就再也不手軟了,即使是小孩
和投降者也不例外。王立就這樣隨著太平軍攻佔全州,被擢昇為犀牛隊小隊長,
到長沙當間諜、並從長沙一路到南京。
這期間,他找到了第二位老師,大家稱呼他為老沈,曾經是鄉下私塾裡的
老師。他手上也有一本聖經在太平天國裡,這是只有天王才能擁有的,老沈讓
王立每天都讀上一小段聖經內容,並且還告訴他四書五經的故事。同樣的王立
將美玲先前教過他的天條、讚美詩、原道醒世詔的教義,一一解釋給老沈聽。
然而,王立覺得老沈越來越難教,他總會問一些奇怪的問題,例如:「如果楊
秀清是聖靈,而天父又透過他的身軀降臨世間,為什麼我們對他不像對天王一
樣尊敬呢?何況天王不過是天父的次子,不是嗎?」(頁 143) 「在太平天國裡,
78
四海皆兄弟,不是嗎?他們的靈魂也是來自上天,在上帝的眼裡,大家都是祂
的子民。人們之間相互殘殺,這是多麼可惜的一件事」(頁 149)等等。即使王立
驚覺老沈說的話正是他內心深處的聲音,但是他深怕老沈的懷疑會動搖他所堅
定的認同,於是他必須把老沈歸為團體中的一條毒蛇,是必須被驅趕的對象。
在這樣威權的團體中,是不容許有異己的聲音存在的,此時的老沈是屬於「我
們」之外的「他者」,是必須被排除的夷狄之輩。為了執行他的忠誠,王立必
須「滅私奉公」,清除污穢與混亂(即使老沈是他的良師益友),他向東王楊秀清
告了密,老沈就這樣被殘酷地處以極刑。
與其說王立意欲清除的是老沈,倒不如說他急欲清除的是自己內在的聲
音。當王立發現自己對美玲產生情愫,那種特別的感覺使他希望美玲能夠擁抱
他,希望自己能夠躲在美玲的懷抱裡。美玲像母親般溫柔地照顧著他,讓他實
質感受到愛的溫暖,讓他發現自己原來也有愛與被愛的需要。然而,那天條迴
蕩在他的腦海裡:「第七,不准通姦,不准有邪念…………」,他卻無法清除
自己的情意,這對他而言是無比的衝擊!王立進入的是一個善惡絕對的二分世
界,他無法同時擁有「善」與「惡」,在一連串的無意識激烈暴力之後,他這
才發現不知如何面對真實的自己。
79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逃離逃離逃離逃離「「「「同一性同一性同一性同一性」」」」
一一一一、、、、烏托邦的迷思烏托邦的迷思烏托邦的迷思烏托邦的迷思
王立排除了老沈,在當時是為了維持自己精神上的衛生與健康,然而在集
體唯心而浪漫激越的結合熱情之後,沉澱下來的是他理性的懷疑。當初美玲從
土匪手中救走王立,帶領王立加入太平天國這個團體,是機緣的安排,也是迫
於命運的無奈,然而太平天國確實成為王立精神與物質上的避風港,解決了王
立暫時的恐懼。它企圖藉由與佔領中國魔鬼的戰鬥以建立世俗的天堂,讓「所
有的人能共同生活於永恆的喜樂中,直到大家都升天而與天父相會」,更給了
王立無限的希望。這個烏托邦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而想像出自於普遍人
性之渴望:進步、文明、理性、平等,它宣稱能給大家帶來幸福,但卻要個人
拋棄人情、人欲、人愛等個人特質,以求達到群體的安定和諧。所以在烏托邦
裡遵守所謂的倫理規範是爲了帶給團體最大的利益,它所關注的是集體的幸福
更甚於個人的幸福。然而這種由外而內的灌輸,是強迫式的,太平天國以軍隊、
嚴格的司法制度、文字教條來控制並改造思想,正是結合了阿圖塞(Louis Althu
-sser,1918 ─)所言的兩種國家機器:一是壓制型國家機器(the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一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105
這種作為忽略
了人的個別差異性,也剝奪了人的自由選擇權,其所造成的平等,也只是一種
「假平等」而已。
湯瑪斯‧摩爾(Thomas Moore) 撰寫、1516 年出版的《烏托邦》(Utopia)造出
「烏托邦」這個字,「烏」既然是「好」的意思,也是「無」的意思,所以「烏
托邦」一字雙關,就是不存在的好地方。而烏托邦(Utopia)的反面就是「反烏托
邦」(Dystopia),也正是共無數科幻小說所描述的世界。有意思的是,烏托邦幾
乎都是虛構的,但,反烏托邦卻往往成為事實。柏拉圖的《理想國》(Republic),
105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吳叡人譯 ,《想像的共同體》(Imageined Communities)(台北時報:1999),頁 155-229。
80
是最早的真正烏托邦,它所描繪的理想世界是由哲學家所統治的,在這世界裡,
沒有痛苦,只有無憂無慮的完美生活。杜斯妥也夫斯基(F. Dostoevsky,1821-1881)
就認為烏托邦強調的進步、理性、快樂、幸福等都不是人類的終極關懷,他在
《地下室手記》(Notes From Underground)裡強調,人之所以為人最重要的是享有
選擇的自由,人一旦失去自由,就不再是人,而是「琴鍵」、「音栓」而已。106
至二十世紀三大反烏托邦小說薩米爾欽(Eugene Zamyatin)的《反烏托邦與自由》
(原名《我們》)(We)、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和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均對烏托邦的理
性萬能與可行性提出質疑。
最近的一部青少年小說《記憶傳授人》(The Giver)(Loise Lowry 作),一九九
四年摘下美國紐伯瑞兒童文學金牌獎,也是一部反烏托邦小說。書中沒有邦國
觀念,取而代之的是社區意識。在這個科幻故事中,為了讓農作物有最佳產能,
這裡恆溫,沒有春夏秋冬;為了將危險減到最低,不讓大家有病痛,這裡用薬
免費,婦女不用生育,而由職業「孕母」代理。為了避免增加社區成本,成長
遲緩的嬰兒、年紀過大的老人、第三次犯錯的犯人,都要被「解放」,也就是
「安樂死」。這裡崇尚一致性,避談個人特質,以免凸顯差異。因此周遭不需
色彩,每家每戶住同樣的房子,吃同樣的食物,過著單調統一的生活。在書中
提出許多發人深省的質疑如:「沒有痛苦,就是天堂嗎?」、「為什麼其他人
看不見?為什麼顏色會消失呢?是我們的人做了這樣的選擇,選擇同化。」、
「很久以前,我們放棄陽光的同時,也放棄了顏色和差異性,我們因此控制了
很多事物但也放棄了很多事物。」、「什麼東西都沒有顏色,實在不公平…」
「如果什麼東西都一樣,就沒有選擇的機會了……」、「像是一種洗腦過程,
沒有記憶,所有的東西都沒有意義……」、「記憶會帶來無比的痛苦……」、
106
劉美瑤,〈烏托邦的幻滅〉,《兒童文學學刊》第十四期(台北:萬卷樓,2005.12),頁 158。
81
「沒有記憶,就沒有智慧」等等。而最後主角喬那思才發現,在自己所處的烏
托邦社會裡,雖然不用擔心餓肚子,不用擔心沒工作,甚至不用擔心身體不適,
但是單調、沒有變化、沒有選擇權的生活竟是如此的無趣。或許跟四周無數的
機械人同一的人不會感到孤單和焦慮,但是卻要付出很高的代價:失去自我。
或許變化會令人覺得不安,與眾不同會令人覺得孤單,孤單會令人覺得痛
苦,但是人是註定要從這些喜、怒、哀、樂中學習,並從中獲得勇氣、力量與
智慧。天堂太樂、地獄太苦,只有人間才是一所最好的學校,而人們總在人間
嚮往天堂。雖然烏托邦是代表著人類社群發展的理想與方向,然而無論距離烏
托邦的極致之境是何等遙遠,它至少可呈現出:人類或許是無可避免地正朝向
它發展的光景。我們大可同意王爾德(Oscar Wilde)的話:「一張沒有烏托邦的
世界地圖是絲毫不值得一顧的」,然而烏托邦的實現不是一蹴可幾的。人類從
茹毛飲血、戰爭不斷的蠻荒時代,歷經君主集權的專制時代,直到現代尊重民
意的民主時代,這中間飽含了多少漫漫歲月。烏托邦的理想社會或許有實現的
一天,但是那應是要等到人心淨化到某種程度的時候,就像在《記憶傳授人》
中所提及的傳授人所必須具備的特質:聰明、正直、靈性、智慧與勇氣,更重
要的是要具備真正的愛心,那就是在關懷他人的同時,也能尊重並保有他人的
自由意志。
烏托邦主義尤其存在於受古典和傳統基督教影響的文化之中,而太平天國
所展現的較偏向烏托邦社會主義。烏托邦社會主義者認為:競爭性的資本主義
自由市場經濟違反公平原則,鼓吹以普遍的兄弟之愛替代階級鬥爭,並規劃完
整社會安排的計畫與建構想像中的社會合作模型。太平天國頒定天朝田畝制
度,規定土地公有,主張財富平均分配:又提倡男女平等,及破除社會陋習。
田畝制度的原則是:一土地公有。二計口授田。三豐荒相通。四為國庫可自給
自足。而它的思想在於 (一)按親緣和地緣關係建立基層社會單位。(二)農
副產品一律充公。(三)各農戶的生活資料平均分配(四)凡鰥寡孤獨疾免疫,
皆頒國庫以養。它以此來描畫出太平天國的烏托邦,然而其根本無法對現實有
82
充分的考量,只會產生不斷的矛盾,其結果祇是普遍的窮困而已,人民的生活
沒有因此過的更好,因此,這個制度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在天朝田畝制度中,
對婦女解放也有兩項重要的規定:第一是分田。第二是婚姻,這規定是根據上
帝教所宣示「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群」的男
女平等理論。然而,一如其他的制度,事時與理論往往相互矛--盾,婦女並未獲
得真正解放,且備受壓迫荼毒, 其一,女館以軍法部勒,善於女紅者,分入錦
繡營,於悉令解足,擔任勞役,折磨而死者,頗為不少。其二故:自一路以來,
所有不遵天命,夫婦私自團聚者,無不被天父指出,奉行天法。當天京城內大
部分人鄭再實行男女分居不得團聚的時候,太平天國諸王卻是妻妾成群,然而,
洪秀全卻說:「今上帝聖旨,大員妻不止。」大官員多妻制被說成是上帝所賦
予的特權。這個男女平等的制度雖然實施了,但是上層卻破壞了這個制度,中
國的婦女們並沒有達到真正的解放,太平天國的命令只是口號,而非實際的作
為。107
太平天國原本是為了解決人民的恐懼而產生,但是在這過程中卻剝除人類
天性的美好溫暖以及自由選擇的權利,它變成了另一種壓迫的裝置,帶給人們
更深的矛盾與痛苦。這個活生生而血淋淋的烏托邦,最終變成了「烏有之鄉」,
於是王立在幻滅之後,也終於有了另一種自我的選擇。
二二二二、、、、覺醒與逃離覺醒與逃離覺醒與逃離覺醒與逃離
如同王立之前對太平天國的相信是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他的覺醒也是經
由一些事件慢慢醞釀而成的。熟讀四書五經的老沈,教導了他許多做人的道理,
也讓他內心深處的聲音慢慢浮現。在歷經無數次的殺戮之後,他也曾向老沈吐
露了些許真心話:「太平天國不是一直教人們要和平共處嗎?」「人們互相殘
107
王戎笙,〈太平天國的理論和實踐〉,《歷史月刊》80 期,1994
83
殺是件可憐又殘忍的事。」有一次,王立手下的一名好兄弟死了,根據天條,
死亡其實是件幸運的事,因為其靈魂已經升天,不正好和天父一起在天堂裡嗎?
儘管他告訴他的弟兄:「我們不要為他傷心,我們要為他祝福,為他的靈魂升
天感到喜悅。」然而王立知道自己是言不由衷,自己的心頭是多麼哽咽,他暗
自地爲這位弟兄傷心好幾天。而當他從老沈口中得知「苛政猛於虎」、「聖經
中並沒有提到滿洲人是魔鬼,也沒有提到太平天國」的事實之後,他的內心更
加糾結。在他告發了老沈之後,老沈被處以極刑,人頭還被高高地掛在東門城
外,雖然王立刻意迴避,可是老沈的身影總是會出現在他夢裡,令王立總在惡
夢中驚醒。
雖然作者佩特森並無直接描述王立對太平天國的信心已然動搖,但是這些
情節的鋪排已有意無意地顯示王立內心的起伏掙扎與覺醒的萌芽,太平天國不
再是天國的保證,它已漸漸變成他想逃脫的牢籠。另外一個促使王立覺醒與逃
離的最大因素是他對美玲的愛情,當他發現自己愛上美玲,卻要受到天條的綑
綁與束縛。他深深擔心美玲的安危,爲美玲的生命安全而禱告,他鼓起勇氣向
美玲告白:「在我心裡,妳比太平天國還要可愛,還要重要。」而忠於太平天
國的美玲,卻要王立為自己所犯的戒律趕緊懺悔,這讓王立覺得無比心碎。而
後美玲被天王看上,要被天王迎娶為妾時,這才發現自己的真愛是王立,也同
時粉碎了她對太平天國的夢想,迎接了自己的真心。
王立最終選擇回到了自己的家鄉,與美玲結婚生子、播種耕耘,延續了父
親所交代的、也是自己最初的那一份夢想。他倆與大自然合而為一,這才是擁
抱自由的開始。王立的覺醒,讓他從「專制主義」與「機械式的順從」108中走
了出來,在之前,王立即使有批判意識,卻不敢表露批判意識,因為在太平天
國中有批判意識即是無法無天。覺醒的危險即是來自於對自由的恐懼,有些人
的疑慮是:「對於某一特定性不公義情境的覺醒是否會使他們陷入『毀滅性的
108
佛洛姆在《逃避自由》一書中,分析三種逃避機制為:1.專制主義 2.毀滅性 3.機械式的順從。
84
狂亂』或是導致『他們世界的全面崩潰』?」然而事實上,覺醒並不會導致人
們「毀滅性的狂亂」。相反地,它會使人們以負責任之主體的身分進入歷史過
程中,覺醒可以幫助人們尋求自我的肯定而避免盲從。109
王立確實已經盲從太
久,但是他如果不做冒險性的突破,突破自己的恐懼,他將無法獲得自由。依
佛洛姆(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一書中分析:人類愈是渴望得到自由,試圖
由原先人和大自然合為一體的狀態中走出來,愈是變成「個人」,而且勢必成
為沒有選擇餘地,只能以自發的愛和生產性工作與世界團結在一起,否則就只
好藉一種毀滅自由與個人自我完整的方式與世界聯繫,找尋安全感。段義孚在
《逃避主義》一書中,也曾提到:「一個人若想逃避孤獨、脆弱和自身不斷的
變化,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融入群體,融入這個群體中為數眾多的小團體當中。」
110之前孤單的王立在太平天國中找到了歸屬感,但由於過度認同太平天國,以群
體意識取代了個人意志。但他不知群體也有它的危險性,因為一個群體是格外
輕信和易受影響的,它沒有批判的能力,對它來說不存在不合適的事。太平天
國一度是王立這個個體自豪感的泉源,他曾為了這個群體或群體的價值而倍感
驕傲,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王立這個個體又是獨一無二的,如果自我太過融
入群體當中,又會壓抑了個人的需求。王立在這樣的群體之中,已失去個人的
自由與自我的完整,他選擇逃離太平天國,是再度尋回自由。如同黑格爾(G.Hegel)
所說的:
唯有藉著生命的冒險,才能獲得自由………那些未將自己生命做為賭
注的人,也許仍然無疑地可以被認定為一個人(a Person),但他並沒
有獲得作為一個獨立自我意識時所認定的真理。111
109
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著,方永泉譯,《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台北:巨流,2004.5),頁 36-37。
110 段義孚著,周尚意、張春梅譯,《逃避主義》(Escapism)(台北:立緒文化,2006.4),頁 20。
111 見黑格爾,《精神現象學》(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 New York, 1967),頁 233。
85
王立最終選擇回到自己的家鄉湖南,重建自己的家園,撒下稻米的種子,
也撒下了希望。王立逃回自己的家,是逃向了自然,逃向了真實。人是屬於家
的,這種附屬關係的形成是與人類在文化中所習得大量的思維習慣與行為習慣
緊密聯繫的。這些習慣很快就自然而然地融進人類的日常生活中,因而它們像
是原本就存在似地,是一個人的本質。一個人離開家或熟悉的地方,即使是自
願或短時間的離開,也讓人感覺那其實是一種逃避。王立身處在湖南這塊土地
上,雖然是與世隔絕,但卻能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來行動,他不必再為了一個
想像的天堂而被束縛,以故鄉為原鄉,落葉歸根的這份感覺是很踏實的。在書
末,王立這樣自述著:
現在南京已經淪陷,所有的大王都死了,整片大好江山就此拱手讓人,
再也沒有太平天國了,也沒有太平的日子。有人說大鼻子瞧不起我們,
認為我們是異教徒,所以才會聯合滿清均對來消滅我們。不管是滿洲人
還是歐洲人,總之我們不會被外國的惡魔所打敗。雖然我們了解天國的
精神,但是我們選擇了另外一條路,此後再也不受天條的限制了。(頁
259)
在王立的內心深處,或許已經領悟到,奔向烏托邦的逃避,從表面上看是
很好的,但其實這與奔向其他的目標一樣,看似真實,其實非常不真實。「天
堂」有時是錯覺和幻想的同義詞。太平天國這樣的烏托邦,最終如夢幻泡影般
消失。和洪秀全一樣出身廣東客家的國父孫文,在爲劉成禹寫《太平天國戰史》
的序(西元 1904 年)時,就曾提到:「嗟乎,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不知有民
主,此所以曾國藩諸人入滿清中興之績得以奏效。」在這樣偏向集權主義的統
治裡,漠視民意,個人的聲音被牢牢壓抑,又何能在其中找到自我的天堂呢?
佛洛姆認為,唯有民主發展成以個人成長和幸福為目標的社會,自由才有
可能勝利,在那樣的社會中,生命不需要成功等東西做為藉口,個人不臣屬於
86
國家或經濟體制等外在的力量,也不受其操縱;最後,那個社會中他的良心和
理想不是外在要求的內化,而真正是它能表現出自他自己獨特性的目標。112王
立的覺醒與逃離,將他帶向自我真正的成長,此成長是以自我的獨特性為基礎
的,此乃有機的成長。他不需要再臣屬於任何比自己高的力量,藉由認同一個
團體以獲取安全感,他以自發性生活的動作來擁抱世界,與世界建立關係,他
得到了個人的力量,也得到了新的安全感。在確認自己所「認同」的生活價值
後,他選擇了自己的「棲居」。在這裡,他不用懼怕被外國的惡魔所打敗,也
不需再受天條的限制,單純地愛、單純地工作、單純地做自己,天堂就在此時
此刻。
112
佛洛姆(Erich Fromm)著,管韻鈴譯,《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頁 241-242。
87
第伍章我與地方第伍章我與地方第伍章我與地方第伍章我與地方
────────《《《《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中的地方認同中的地方認同中的地方認同中的地方認同
在本章中,筆者所欲探討的是人們對於地方的認同意識。在第一節中,筆
者先論述孩子們對於空間的需要,這空間蘊含了不同的屬性,它可以是遊戲空
間、幻想空間、人情空間等等,並分析是什麼因素維繫了孩子對此空間的認同
感。再來探討「空間」如何變成「地方」,並對於「地方」此概念加以界說。
說明地方為「我」與「他人」的共同主體或相互主體形成的歷程之所在,此所
在即是一「存在空間」,並依循此觀點來透析「泰瑞比西亞」的形成。在第二
節中,談到的是認同與遷移,「泰瑞比西亞」是一想像中的王國,筆者論及人
們需要在真實與想像世界中遷移的重要性,並說明此雙向流動能打破固著的認
同,再造新的生命活力。再來談到現實世界中的遷移(從柏斯萊一家人的搬遷談
起)、並論及種種遷移模式如移民、跨國的網路交流等等,這些都挑戰了傳統的
地方形式,也模糊了對於「家」的認同,筆者在論述中重新釐清「家」的概念,
即家是心之所繫的地方。在第三節中,探討文本中所蘊含「回歸自然」的理念,
地方的概念可擴展為整個生態圈,人的「小我.」與生態圈此「大我」事實上是
共生共榮與互相成就的,筆者依深層生態學的兩個終極特質:自我實現與生命
中心平等說,來論證走出小我,擴大認同與包容差異的必要性。
88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認同形塑的認同形塑的認同形塑的認同形塑的地方地方地方地方
「我們需要一個地方,」她說:「一個只屬於我們兩人的地方,一個非
常神聖的地方,神聖到我們絕對不和任何人提起。」
─ 凱瑟琳‧佩特森(Katherine Paterson),《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113
一一一一、、、、尋找夢奇地尋找夢奇地尋找夢奇地尋找夢奇地
在孩童的心中,總是期待一個「芝麻‧開門」後的世界,在那個世界中充
滿了夢想與寶藏,孩童在其中可以無拘無束、盡情奔放。在《說不完的故事》
中,培斯提安在學校的閣樓中開啟他的幻想國度;在《獅子、女巫、魔衣櫥》
中,露西一行人由魔衣櫥進入了神奇的纳尼亞王國;在《秘密花園》中,柯林
在母親鍾愛的花園裡開啟了自己的新生命;在《哆啦 A 夢》中,大雄在房間的
抽屜中進入另一個時空。或許我們都有過相同的經驗,小時候,只要利用一條
棉被,不論是在床鋪中,或是在桌底下,我們就能建造屬於自己的空間。這空
間可以延伸再延伸,是心靈無限的想像空間,我們無法預測它會引領我們什麼
樣的國度?
「孩子目光所及,皆盛大莊嚴」,當他進入了夢想自身,即是浩瀚。這樣的
體會,中外皆然。沈復在《浮生六記》的《閒情記趣》紀錄自己的兒時體驗:
「夏蚊成雷,私擬作群鶴舞空,心之所向,則或千或百果然鶴也。昂首
觀之,項為之強。又留蚊於素帳中,徐噴以煙,使其沖煙飛鳴,作青雲
白鶴觀,果如鶴唳雲端,怡然稱快凹凸處、花台小草叢雜處,常蹲其身,
使與台齊,定神細視,以叢草為林,以蟲蟻為獸。以土礫凸者為丘,凹
113 凱瑟琳‧佩特森 (Katherine Paterson),鍾瑢譯,修文:許常德。《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Bridge
to Terabithia)(台北:漢聲,1990.10),頁 45。
89
者為塹, 神遊其中,怡然自得。」
其赤子之心之所向,事物之細微處皆有了廣大的印象,也因此常得物外之
趣。孩子的世界,就是他的想像,而無邊的想像帶來了自由。不只孩子需要自
己的世界,大人也需要一處心靈的桃花源。陶淵明在《桃花源記》所描述的那
個落英繽紛、芳草鮮美,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黄髮、垂髫並怡然自樂的
人間仙境,也是大人們心生嚮往之地。
佩特森所著的《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中,也有一個國度,它在河的彼岸
-----森林的一角------它叫做泰瑞比西亞。它是屬於傑西與柏斯萊這對好朋友的神
秘國度,在那兒,傑西是國王,柏斯萊是皇后。雖然這條河是乾涸的,但是他
們規定,要進入泰瑞比西亞必須抓住河邊山楂樹上的魔繩(其實只是一條廢置的
舊繩)盪過去-------才能得見那奇幻的王國。他們在老橡樹和冬青樹之間的金色光
影,用木塊建造了一座城堡。在城堡內朦朧的光線下,任何事情似乎都有可能。
在這裡,他們擁有整個世界,而且永遠不會被敵人打敗。
傑西是一個害羞內向的小男生,是家中五個小孩當中的唯一男孩,他很愛
畫畫,卻不敢在作文裡寫出自己的志願。而柏斯萊是一個剛來到鄉下的轉學生,
是一個不像女生的小女生,她的頭髮剪得比男生還短,她穿著褪了色、剪掉半
截褲管的牛仔褲以及藍色汗衫,還是五年級的飛毛腿。
這兩個人都曾經孤獨、與學校的同學格格不入,也一度成為被學校同學欺
負的「局外人」。但當他們在一起時,卻擁有了「自己的顏色」,也在他們倆
所營造的秘密空間中找到了歸屬感與無限感。這樣的私密空間裡,傑西也對柏
斯萊產生了一種信賴感,就像在一個圓實的原初窩巢裡,體驗到對世界的原初
信賴感。雖然現實情狀不盡如人意,但是他們在這空間中感覺到自己受到庇護,
這個空間可以說是他們的「庇護空間」、「神聖空間」、「遊戲空間」、「夢
想空間」,更是屬於倆人的「情感空間」。所以當傑西試著自己一人去泰瑞比
西亞國,就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了。「泰瑞比西亞國的神奇,必須有柏斯萊才
90
能顯現出來,就算他勉強自己去營造,但那神奇就是不肯出現,甚至還可能毀
掉一切。」(頁 109)因為泰瑞比西亞國是柏斯萊與他共同創造出來的。
人是群居的動物,需要夥伴,有了夥伴的陪伴,便能加強對自我的認同感。
在狄福(Daniel Defoe,1660---1731)所寫的《魯賓遜漂流記》中,即使魯賓遜一個
人孤零零來到荒島,仍然需要「星期五」這位夥伴與他一起建立家園。他圍籬
而居,先讓自己的居所變成一個安全庇護之地,而後家園變成了王國,荒島成
了一個海外的烏托邦。需要夥伴是人類的天性,尤其是小孩更需要玩伴。張倩
儀在《另一種童年的告別》中,曾提到童年玩伴的重要性。她舉黎東方的童年
故事為例:黎東方哥哥每天放學回來一定帶弟弟到花園玩。這哥哥在黎東方的
眼中是個多才多藝的羨慕對象:「他敢放爆竹,善踢毽子,又會抖空箏,下象
棋,推牙數牌,真是無一不精。」張倩宜認為:「這樣的年長玩伴對小孩子是
有吸引力的。他們近在身邊,有血有肉,不必講究形象。孩子羨慕模仿這些年
長玩伴,到成長後保持平等的友情,完全不同於現代都市中崇拜遠距離的偶像,
以致歇斯底里追逐的情況。」114
柏斯萊的聰慧、獨立、敢做敢當,對於怯懦的的
傑西來說,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傑西羨慕也模仿柏斯萊這位最佳玩伴。他需要
柏斯萊的帶領與陪伴,是柏斯萊將他從牧場帶入泰瑞比西亞國的,而且還把他
變成一個國王。
泰瑞比西亞是一個由友誼支撐起來的王國,也可以說是一個由童年玩伴所
組成的「人情空間」。(我們到處可以找到這樣的人情空間,在中國古老社會裡,
孩子們聚集遊戲的場所,如大樹下、街尾巷弄、胡同、三合院的稻埕等等。而
在現代社會,家屋鄰近的公園、社區的廣場、甚或網路上的部落格等等,只要
可以讓人們進行情感交流的地方,皆是人情空間之屬。)
然而是什麼緊緊維繫著傑西與柏斯萊對泰瑞比西亞此空間的認同感?除了
彼此間的友誼,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秘密」。泰瑞比西亞是屬於他們二人的秘
114
張倩儀,《另一種童年的告別》(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3),頁 227-228。
91
密,他們互相約定不向其他人提起這個秘密。在柯尼斯伯格所著的《天使雕像》,
對於「秘密」有一番獨特的詮釋。少女潛入紐約的博物館,熱切地想要發現天
使雕像的「秘密」,而知道此秘密的法蘭克威勒夫人是這麼說的:
「她真正想要的就是帶一個秘密回家。天使雕像是一個秘密,這個秘密
讓他覺得很興奮,覺得很重要。克勞蒂雅想要的並不是野外冒險,…….
但是秘密是一種她會喜歡的冒險。秘密是安全的,又可以讓你跟別人不
一樣。它的價值全是在心理面的;……」115
同樣地,傑西和柏斯萊也因為擁有一份共同的秘密,而使彼此成為不同於
以往的自己,秘密的存在也提高了他們自我的存在感,使他們變得更有力量、
更有價值。只有兩人知道的秘密,增進了彼此的關係,加強了他們對此空間的
認同感,也讓他們在泰瑞比西亞王國中成為獨一無二的存在。能與一個推心置
腹的朋友分享秘密是一件幸福的事,就像《天使雕像》中克勞蒂雅所說的:「當
你保有秘密一段時間之後,如果沒有人知道你有秘密,那就不好玩了。」116
二二二二、、、、從空間到地方從空間到地方從空間到地方從空間到地方
每個人都需要擁有自己的空間,自己的空間能為個人帶來心智上的自由,
而通常偉大的作品是來自這種心智上的自由。也無怪乎維吉尼亞‧吳爾夫會說:
「女性若是想要寫作,一定要有錢和自己的房間。」117
泰瑞比西亞王國最可貴之處,是它能讓柏斯萊與傑西在此處充分享受了心
智上的自由,它滿足了柏斯萊和傑西創造空間與重塑空間的慾望,也創作出自
115
柯尼斯伯格(Konigsburg, E. L.)著,鄭清榮譯,《天使雕像》(台北:東方,2003.4),頁 217-218。 116
同上,頁 229。 117
維吉尼亞‧吳爾芙 ( Virginia Woolf ),張秀亞譯,《自己的房間》(台北:天培文化,2000.1),頁 36。
92
己的故事。在似日夢的想像遊戲中,他們已變成自己意象的存有者,他們將自
身意象融入空間,使空間變成一個被改造過的虛擬空間,而將自身的認同感投
入此一空間後,此空間 (space)就變成地方(place)了!
什麼是「地方」呢?地方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基本概念,地方同時也是一
個包裹於常識裡面的字眼,和生活息息相關。假設你搬進一間新房間,一開始
它只是一個不具特別意義的空間,但是一旦你在書桌上擺放自己的書籍、插上
鮮花、放上相片,這個空間就變成你的「地方」了。又如學生搬進一間新教室,
一開始它可能只是一個平凡無奇的空間,但是學生們一旦有了自己的座位、自
己的置物櫃,佈告欄上貼著自己的作品,認同感提升了,於是教室這個空間就
變成學生的「地方」。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 此書中,提出
了此在(dasien)概念。海德格認為此在乃是存在的本質 ─ 人類存活於世間的方
式。海德格認為嚴格說來,真正的存在乃是紮根於地方的存在。而現象學家所
關切的是「意向性」(intentionality)的東西。意向性指的是人類意識的「關涉」
(about-ness),意識建構了自我和世界的關係。所以胡塞爾(Edmund Husserl)在其「現
象學」體系,提出了「生活世界」此一重要觀念。
所謂「生活世界」是指人們排除了抽象的科學理念之後而開展出生
活之原始領域……….日常生活中原來的世界,在這樣的世界裡,人之
生活的意義充盈著,這裡面包含了他在實際生活中直接經驗到的各種
行動、視覺、記憶、偏好、志趣………等,而這一切均以具體的方式
揉合整全地盈滿流動在它的生活世界裡,與他的親人、朋友、鄰居、
同胞………人類在它的家園、社區、聚落集各個土地、環境中發生了
互融互動的關係。118
118
潘朝陽,《心靈‧空間‧環境------人文主義的地理思想》(台北:五南,2005.12),頁 13。
93
易言之,「生活世界」就是「我」與「他人」的共同主體或相互主體形成
的歷程之所在,這個所在,亦即地理學者關注的所謂「地方」(places)。人文主
義地理學的「空間」理念,基本上是由「存在現象學地理學」119
(existential pheno-
menological geography)所強調的「主體性空間」(subjective space)。以「存在空間」
(existential space)名之。此「存在空間」若依段義孚之言,實則一種「自我中心
空間」(egocentric center)120
,即是由「主體之人」作為空間的中心點而往外圈擴
展,在此擴展的過程中,「主體人」不斷地投射賦予層層空間以意義和價值。
泰瑞比西亞王國是傑西與柏斯萊尋獲的夢奇地,這個私密空間是他們倆心
中的城堡,它是一個核心,一個胚胎,一個平衡的中心,他們的宇宙集中於這
個中心,這個中心強而有力,正因為它是一個想像的中心。在這個中心裡,他
們即是「主體之人」、宇宙的主宰,所以我們不難理解柏斯萊和傑西為何自命
為泰瑞比西亞王國的皇后和國王了。 我們也可以說泰瑞比西亞王國是柏斯萊與
傑西的「共同意向性」組成的存有空間,存有空間的實際運作焦點,即所謂「所
在」(place),此「所在」即他們二人不斷發生其「存有意義」的地方。
這樣一個「地方」,有其「生活向度」,也有其「神聖向度」。就如同柏
斯萊所言,泰瑞比西亞是一個「非常神聖的地方」,他們在此誠心禱告、獲得
力量,在進入泰瑞比西亞前,還得抓住河邊山楂樹上的魔繩,盪過去才能得見
那神聖的國度(這是他們二人所發明的儀式)。進入泰瑞比西亞國就猶如進入寺廟
教堂般莊嚴神聖,他們二人所發明的宗教儀式為其神聖向度之一,而兩人互相
承諾的秘密,與外界的隔絕,則維持其潔淨向度。
如果說,傑西與柏斯萊的相遇是點,在他們之間所架構起的是一條認同的
線,再以點為圓心,線為半徑,那麼所畫出的圓這個地方就是「泰瑞比西亞」。
119
以「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兩支現代西方哲學大流脈原本是源流相同,因此,以此兩支哲學為方法論之「現象學地理學」、「存在主義地理學」,實亦可匯合通融為「存在現象學地理學」(existential phonological )。
120 同註 100,頁 69。
94
泰瑞比西亞可以像松林的角落般微小,也可以像宇宙般浩瀚;它可以如人情空
間般溫馨平和,也可如神聖空間般莊嚴潔淨。泰瑞比西亞是一個具有多重向度
的空間,它因柏斯萊與傑西所投射的認同意識,而變成了有深刻意義的地方。
三三三三、、、、命名與地方命名與地方命名與地方命名與地方
此外,「命名」是賦予空間意義,也是使空間變地方的方式之一。如果柏
斯萊沒有為松林取名為「泰瑞比西亞國」,那麼松林也就只是松林而已。「泰
瑞比西亞」(Terabithia)這個地方的名字,恰巧與 C.S.路易斯在《纳尼亞傳奇》系
列中《黎明行者號》(Voyage of the Dawn Treader)這本書中稱呼一個島為「泰瑞比
西亞」。作者佩特森認為自己一定是在無意識中借用了這個名字。而路易斯取
的這個名字,是聖經中所提到的松節油樹的諧音。這個名字取得很巧,在路易
斯的筆下它正是奇幻王國中的一個島(《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被翻拍為電影,
電影中文名稱即為《尋找夢奇地》,2007 年 4 月在台灣上映)。「泰瑞比西亞」
所代表的是創造、想像、疏離、驚奇、感覺等等元素,它是一個奇想的實現之
地,也是一個自給自足的世界。
通常我們為一個人取名字,即是在賦予此人「獨特性」。人的名字可能是
在呼應此人的人格特質或是蘊含父母的期望等等,名字就像是一個人的「身分
證」(identity),是一個人存在的表徵,也代表了一個人的自我認同。同樣地,地
方也需要被命名,它也需要有自己的獨特性。空間的名字歸予名字所喚起的記
憶和景象,空間的名字加深了人們對它的認同感。
每一個名字都需要被召喚,在《說不完的故事》中,M‧安迪 透過書店老
闆告訴每一個經歷培斯提安心靈之旅的讀者:「你只能見月童一次,不錯!可
是如果你再給她新的名字,你就能夠再見到她。只要妳這樣做,不論做多少次,
就永遠是第一次,永遠是唯一的一次..」原來為女王取新名字,就是在參與全新
的幻想國的建造,女王透過新名字有了全新的開始,培斯提安透過為女王取新
95
名字,也有了全新的開始:那就是進入幻想國。「每一個人的名字,都不是自
己,而是當別人想起我們時用的,所以它的根源是愛。」121
同樣地,柏斯萊為她
的松林取了新名字,她賦予了此空間愛與意義,也帶領著傑西進入了全新的幻
想國。「泰瑞比西亞」這個名字,是一個 calling、召喚與使命,夢奇地因這名
字而生.。因為這名字,柏斯萊也創建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地方」!
121
山中康裕著,王真瑤譯,《哈利波特與神隱少女》(台北:心靈工坊,2006.1),頁 106。
96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認同與遷移認同與遷移認同與遷移認同與遷移
「我尋找一個屬於我的家...這便是我的考驗…在哪裡…我的家?這便
是我所要求和尋找的,這是我找過但沒有發現的。」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說故事的人》122
一一一一、、、、在真實與想像間在真實與想像間在真實與想像間在真實與想像間移動移動移動移動
泰瑞比西亞國是傑西與柏斯萊共同想像的空間,而對於傑西來說,「柏斯
萊不只是他的朋友,也是他內心的另一半,是他通往泰瑞比西亞國或其他世界
的通道。」(頁 82)傑西很難向別人解釋清楚泰瑞比西國到底是什麼,「每次去
泰瑞比西亞國,才步下山坡,他就覺得好像有一道暖流流過他的全身。當他的
雙腳輕輕地踏上那片神秘的土地時,他就覺得自己變得高大、強壯又聰明。」(頁
82)在泰瑞比西亞國裡,柏斯萊喜歡編些巨人威脅泰瑞比西亞的故事,也會和假
想的敵人格鬥。儘管有大批的敵人向他們蜂擁而來,他們依舊能夠使敵人吹起
撤退的號角,並把他們徹底驅逐出境,使泰瑞比西亞國重獲自由。泰瑞比西亞
雖是個想像世界,但柏斯萊與傑西透過角色扮演的遊戲,能使自己符合國王與
皇后的尊貴身分,這可說是一種心智上的自我鍛鍊。也由於在泰瑞比西亞的成
功經驗,使得他們有勇氣去面對真實世界中的敵人與困境,解決了現實生活中
的一些不如意(像是對付欺負他們的珍妮絲等等)。
在諸多奇幻故事中,作者常會刻意安排一個想像世界,讓主角在進入之後,
歷經一場洗禮而有了某些轉變。例如:在《少年噶瑪蘭》中,潘新格回到了的
過去,參與並見證了祖先的一段歷史,也重塑了自己對宜蘭這塊土地的認同情
感;在《地板下的舊懷錶》中,派翠西亞和身為名主播的媽媽,感情一直很疏
離,藉著一段時空穿梭的歷險,她以一個隱形人的身分,目睹了媽媽少年時的
122
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林志明譯,《說故事的人》,頁 102。
97
孤獨、苦悶,終於對媽媽的內心世界有了深切的了解與同情。在《說不完的故
事》中,培斯提安進到幻想國後,發現這是一個全然不同的國度,幻想國需要
一個來自真實世界,又能超越真實世界限制的人為孩童女王命名。推動他往前
的力量,不是按部就班的生活秩序,而是內心深處一個又一個的願望。其實每
一個願望都是他現實世界心靈的創傷。在幻想國中他的願望實現了,他獲得了
英俊、勇敢和意志力,但是他內在的惡也跟著浮現了,那就是他的權利慾與競
爭心,於是他在善惡之間沉浮掙扎,培斯提安放棄了權力的象徵「奧鈴」。將
「奧鈴」放到地下那一剎那,回返現實世界的門出現 ,培斯提安也成為一個新
造的人。
這個故事道出了現實與幻想這兩個世界是不可偏廢的,他們是互相依存的。
而諷刺的是,幻想國存在著最真實最真誠的事物,反而是真實世界存在著欺騙
與謊言。唯有進入幻想國,帶回生命水的,成了兩個世界的橋樑,才能讓說不
完的故事永遠繼續。同樣地,柏斯萊是傑西通往另一個世界的橋樑,在與他相
處的那段時空中,他已學會如何用廣闊的視野和勇氣,去關愛這真實的世界。
所以在柏斯萊死後,從悲傷走出來的傑西,決定把這個秘密公開,他造了一座
橋,來幫助任何想通往泰瑞比西亞的人。
河合隼雄在《小孩的宇宙》中指出:「教育學者蜂屋慶認為,這裡的世界
是個『技術世界』,那裡的世界是個『超越世界』,他批評現代教育的盲點之
一,就是熱衷於讓孩子學習技術、教導他們技術,而忘記超越世界的存在。」123
也就是說現實的世界是「技術世界」,而幻想的世界是「超越世界」,而通常
在「超越世界」中,我們才能發現人的真實樣貌和價值。而如果父母或教師接
觸到「超越世界」,那麼他就能在每個孩子的身上看到絕對的超越世界,因而
能夠把孩子當作無可替代的珍貴存在,來與他們相處。如果僅僅看見「技術世
界」,就會單純以學業成績來對孩子下絕對性的評價。但是我們人也不能完全
123
河合隼雄著,詹慕如譯,《小孩的宇宙》(台北:天下文化,2006.7),頁 118。
98
沉浸在「超越世界」中,否則會有失去生命的危險。124
愛因斯坦曾言:「想像的力量遠勝過知識」,「沒有想像力的頭腦,就像
沒有望遠鏡的天文台」,想像力可以帶領我們發現那超越的世界。但是在現代
功利的社會,人們忙於追求物質的利益,似乎失去了想像的能力。「幻想的流
失使空虛的惡魔吞噬世人的內心。」這是麥克安迪在《說不完的故事》中,為
世界敲響的警鐘。自詡「進步、文明」的現代人,不斷的用知識填塞內心,卻
沒有發現在心的深處有個無底洞越蝕越大。
其實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一座泰瑞比西亞王國,只是有人發現了它,有
人遺忘了它。如果我們都能像柏斯萊與傑西努力去推倒心靈上的那道高牆,並
造一座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每個人都可能是泰瑞比西亞的國王或皇后。泰瑞
比西亞,說穿了,就是人們心靈的家。當然,你不可能永遠留守在家中,有時
你也必須離家,再朝另一個目標邁進,但有一天你還是會想回家,因為家帶給
你的溫暖與撫慰是沒有任何地方比得上的。
我們必須在真實與想像的世界移動,有了雙向的流動,我們才能日新又新。
否則可能死守著固定的認同,無法為生命再造活力。所以我們每個人都需要一
個通往那裡世界的「通道」,一座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讓我們在心靈的世界
中旅行,也在現實的世界中有所行動。如同維吉尼亞‧吳爾芙所言:「說什麼
人應該覺得平靜就是福那對我是妄言,人們定得有所行動;假如有所未得,就
得自行創造。」125
二二二二、、、、移動的實踐世界移動的實踐世界移動的實踐世界移動的實踐世界
讓我們再回到那個老故事:「變色龍走到那兒就會改變自己的顏色,在檸
檬上就變成黃色;在石南林中就變成紫色;在老虎身上就出現條紋,他想說如
124
同上,頁 119。 125
維吉尼亞‧吳爾芙著,張秀亞譯,《自己的房間》,頁 124。
99
果自己能一直停留在一片葉子,就會永遠是綠色了;他爬到了一片最青綠的葉
子上,但是葉子到秋天就轉變成黃色,變色龍也變成黃色了──」變色龍移動
到不同的空間,就會變成不同的顏色。
「搬家」應該是多數人生命中都曾有過的體驗,有些人藉著空間移動,尋求
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有些人是為了生存的需要,選擇離開生長的地方,到異
鄉去求學或工作;有些人則是被迫離開家園,在多年的離散經驗後,再度展開
尋根之旅。柏斯萊一家人屬於第一種:柏斯萊的父母認為他們太受金錢和名望
束縛了,所以選擇搬到鄉下,買下一個舊農場,打算自己耕種,並且好好思考
在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對於柏斯萊而言,她雖然願意接受搬家這回事,但她仍
然要鼓起勇氣去割捨過去的一切,包括朋友、熟悉的環境等等,並面對一個與
她格格不入的陌生環境。
事實上,柏斯萊也可經由空間的轉換,來認識自己,雖然這個過程比選擇
「待在原地」還艱辛。「改變我們每日生活空間的行動本身,就是在賦予自己
一個界定自我的機會。」126
空間不正是自我認同滋養的所在?根據非裔美籍知識
分子柯爾諾‧韋斯特(1953)(Cornel West)的說法:「認同跟附屬有關,想要歸屬
於某處,求得保障和安全。」127
對於柏斯萊而言,她不僅在現實環境中旅行,也
在她的心靈時空中旅行。現實環境中的柏斯萊,以一個轉學生的身分,來到了
雲雀小學,也被大家認為是個不男不女的怪傢伙。「認同」將她的新同學們綑
綁在一起,「認同」也被一種「鄉里、狹隘、仇外」的觀念所綑綁,她的同學
們在不自覺把她當成了「局外人」。還好她找到了泰瑞比西亞,一個讓她感到
安全,滋養她認同意識的地方。「泰瑞比西亞」是她營造出意義歸宿的家。
到底什麼是家呢?一個居住的蛹是「家」,一個引退之所是「家」,一個
找到自己價值的地方是「家」,一個可以隨心所欲的地方是「家」,一個可以
展現自己的部落格也是「家」。人文主義地理學家段義孚主張,在各種尺度上
126
畢恆達,《空間就是權力》(台北:心靈工坊,2001.10),序言。 127
Ziauddin Sardar 著,陳貽寶譯,《文化研究》(台北:心靈工坊,2001.10),頁 126。
100
創造地方的行為,被當成是創造了某種在家感(homeliness)。家是地方的典範,
人們在此會有情感依附和根植的感覺。128
柏斯萊與父母親住在農場的破房子中,在他們還未搬進去之前,這棟破房
子只能稱為一棟平凡無奇的住屋(house),然而由於柏斯萊一家人(family)在此生
活,對這棟房子有了根植和依附的感覺,家就能稱做 home 了。在〈金色的房間〉
這一章節中,作者佩特森描述傑西如何與柏斯萊一家人一起改造他們的破房
子,他們拆下蓋住老壁爐的木板、撕下客廳的壁紙、漆上金色的油漆、把地板
打磨的發亮,完工之後他們感到一種金色的魔力,覺得自己也彷彿置身在泰瑞
比西亞王國之中。藉由家居環境的改造及物品之佈置安排來結合自我及對家的
認同,這應該是每個人都有過的經驗及想法。對 home 的定義應該回到那句話:
「家」是心之所繫,感情的存在之地,地點不重要,心的想像,人、親情、友
情的記憶,對家的認同,才是關鍵。沒有情感留存,space、place 都無法成為 home。
從 house 轉變為 home 的過程,即是由物質層面過渡到精神層面的過程。
「家」不只是個人自我認同的再現,也孕育了認同成長的環境。筆者在這裡
要探討的是,每個人都渴望家,但對於一個離散中或移動的人而言,他如何能
夠處處為「家」?每個人對家的想像,真的有很大的不同,那麼人都需要一個
家嗎?在世界每個角落就落居的旅人,對家的想像又是甚麼呢?魯西迪(Salman
Rush-die)在《想像的故土》(Imaginary Homelands)一書中就說到:『一個道地
的移民者總是遭遇三重的破碎之苦──失去自己的身分地位,開始接觸一種陌
生的語言,發現周遭人的社會行為和語意符碼與自己的大異其趣,有時甚至令
人感到憤怒與不安。』129
「認同是個問題,很多美國朋友都覺得在這方面並不充份。他們常常覺得自
己沒有價值,不知道他們有什麼感覺,…也許是因為每個人總是在變動中,總
是在經歷巨大的變動,所以他們覺得失去了可找到自己是誰的軌跡,所以要一
128
Tim Cre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 42。 129
轉引自網頁資料 2007 認同與差異部落格:http://blog.yam.com/identity2007,2008.1.8。
101
直標記自己要變成誰。」130
這段話表達了現代人常常經歷到的失落感,在巨大的
社會變遷下,常感覺到自己沒有歸屬感而若有所失。移民、遷徙是人類歷史不
斷上演的戲碼,在離散中存在著幾股張力,在建立新家時,對「家」的渴望仍
舊無所不在。
而現代,由於資訊的發達,網路資源的流通迅速,加速了人們之間無形的
「移動」。人們大量的「移動」,加速了改變的發生、疆界的瓦解與文化的旅
行,在多數和少數族群之中,有新(全球化)與舊(地域化)認同的緊張關係。由此
觀之,地方沒有單一、獨特的認同,地方充滿了內在衝突。移動的實踐世界嘲
弄了地方的正統形式,漂移多變的位置使得認同不固定,也不受限。那麼一個
時常移動的「異鄉人」究竟該如何自處呢?
後殖民理論學者薩伊德(Edward W. Said) 於《文化與帝國主義》引用一位 12
世紀日耳曼高僧所言:「凡是一個人若覺得其家園是甜蜜的,則他仍然只是一
位纖弱的初學者而已;認為每一寸土地都是其故土者,則已所是一位強者;若
將整個世界視為是異域,則他已是一位完人了。」131
他所揭示的是一種精神進化
的過程:「以故鄉為故鄉」→「以他鄉為故鄉」→「以故鄉為他鄉」,即放下
對「家」的執著。我們若能從人群和穩固的地方感中抽離,享受一種美學化的
差異,以各種多樣性為樂,把自己當做一位旁觀者,去欣賞如畫美景般的多樣
性,此時:「旁觀者擁有一種文化資本的感受……….也能因為有能力欣賞差異
而產生了自我價值感。」132 後殖民倫理學也爲我們提供了解答,那就是我們需
要擁有自省的力量,我們應視他人的存在為我們絕對的責任,我對他人的責任
是維繫它的獨特性,而不是去改變他。
「四處為家,卻沒有地方關的住我,這就是居住夢想者的座右銘。…我們必
須對他方的白日夢,永遠保持開放。」133
所以重點是,變色龍儘管會隨著空間
130
同註 116。 131
Edward W. Said 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頁 23。 132
Tim Cre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 128。 133
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頁 70。
103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小我與大我的共生小我與大我的共生小我與大我的共生小我與大我的共生
一一一一、、、、逃回自然逃回自然逃回自然逃回自然
柏斯萊的父親和母親都是成功的作家(媽媽寫的是小說,名氣比寫政論的爸
爸還大),但是卻選擇遠離喧囂的都市生活,不想被金錢和名望所束縛,來到了
鄉下,打算自己耕種,建立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他們全神貫注於這樣的熱情之
中。柏斯萊不被同學所接纳,因為她和其他同學太不一樣了,她的家庭選擇不
要有電視,她的穿著也很隨性而奇特。柏斯萊一家人選擇的是「自然」,這自
然不只包括自然的生活環境,也包括了自然的生活方式。
段義孚在《逃避主義》一書中指出,人類逃避的對象之一是「文化」:而
逃避喧鬧的城市生活,即是屬於逃避文化.。134
他認為,回歸自然是一個値得深
思的命題,其中有兩點需要關注,其中一點就是這種情感的古老與悠久,像古
代蘇美人(Sumer)造城之初,他們就很熱切地盼望著能重返純樸的自然。第二點
是:久居城市的人們會普遍地對自然懷有親切的嚮往,像生活在熱帶非洲卡塞
河(kasai River)流域的勒勒人(The Lele)他們定期返回河流對岸那隱密、涼爽、富
饒的熱帶雨林中,在他們的眼中,熱帶雨林是一切美好的泉源,是上帝賜予的
珍貴禮物。135 而筆者以為,「親自然性」是人類固有的一種天性,人類久居於
城市,總會想到郊外走走,或定期旅遊,稍長一點兒的則是在鄉間生活一段時
間。即使是在現代的家居中,也會擺上一些盆栽、植物;在生硬的鋼筋樓房旁,
也會種上一些行道樹,那是人類一種自然的需求。
在二十一世紀這樣物慾橫流的時代,也有越來越多人開始警覺到與大自然
的疏離,而提倡「慢活」的新哲學。在日本,一九九五年,「半農半 X」的理
念開始醞釀成形:順從天意經營簡單的生活,並將上天賦予的才能活用於社會。
134
段義孚著,周尚意、張春梅譯,《逃避主義》(Escapism)。段義孚在《逃避主義》中指出:人類逃避的對象有四:之一是自然、之二是文化、之三是混沌、之四是人類自身的動物性與獸性。
135 同上,頁 21-22。
104
從小規模的農業中獲取自給自足的糧食,用簡單的生活滿足最基本的需要,同
時也從事自己熱愛的工作、理想,更積極地與社會保持聯繫。136
柏斯萊的父母所
選擇的正是「半農半 X」的生活,他們一邊自己耕種,一邊發揮自己的天賦,
以寫作為職志,表達自己也關懷這個社會。他們知識豐富,能延展自己的觸角
到各個層面,關心政治,也關心生態環境(像是如何拯救灰狼、紅木、鯨魚等等)。
他們家沒有電視,但不能缺少音樂,家中有堆積如山的唱片;他們衣著簡單隨
性,常穿著牛仔褲,過著不像有錢人的生活,但在物質上也不虞匱乏。總而言
之,他們過的是素樸而有質感的生活,在別人眼中,他們看起來像是嬉皮,但
是他們卻能享受自己的生活並且樂在其中。作者佩特森還在書中安排另一個嬉
皮角色的人,那人就是傑西的音樂老師愛德蒙小姐。愛德蒙小姐有著一頭飄逸
的長髮,她不塗口紅、眼睛周圍卻塗滿化妝品,她也是雲雀小學第一個穿牛仔
褲的女老師,常被小孩拿來當做取笑的對象。然而她卻是唯一欣賞傑西畫作的
老師,她認為傑西是一顆未經打磨的鑽石,在傑西小小的心靈中,愛德蒙小姐
就是他完美的偶像,他認為他們倆是同一類型的人,皆不受世俗拘束。
作者佩特森把《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這個故事的時空背景放在越戰結束
之後,而嬉皮(HIPPIES)正好崛起於那一個年代,嬉皮的信念是,國家應當和平
共處,不是消滅敵人,這是非常人本的觀念。“嬉皮”的意思是:用怪異的服裝和
乖僻的生活習性來表現他們的個性,來排斥固有的社會習俗和慣例的人。嬉皮
文化是整個搖滾文化的基礎和土壤,它的口號是「愛與和平」。雖然等到這世
界不再打仗,他們也解散了,但是他們的任務並沒有結束,嬉皮當年所創造的
精神和價值仍是值得我們後人去反思的。
嬉皮是最需要心靈自由的一群人,他們需要真實感受世界上所有存在的東
西,一朵花,一塊泥土,一切生命都比打仗或當公司主管重要的多。然而現代
這個物質充裕的科技年代,不也是嬉皮最難發生的年代?人與人間實際的接觸
136
塩見直紀著,蘇楓雅譯,《半農半 X 的生活》(台北:天下,2006.10),頁 16。
105
變少了,代之而起的是網路的虛擬世界;人與自然的關係不再親近,亞馬遜河
的熱帶雨林正被大量砍伐,大自然反撲的結果使我們生活在全球暖化的危機之
中。人們為了更多的商機與利益,生活在偽善與謊言之中,不能自然地做自己。
奧修曾在一場演講〈嬉皮起義〉(Hippy Rebellion)中,提到嬉皮的許多觀點與他
很接近:一、嬉皮拒做應聲蟲 (yes-man),他相信按照他的感覺去做是對的。他
們說:「我們想要像自然的男人和女人那樣活著,就像我們這樣,沒有欺騙。
我們要嘗試既不欺騙也不偽善。我們知道我們的道路會布滿煩惱,但我們要忍
受這一切,並嘗試著按我們的方式生活。」137
嬉皮的第二條原則是「自然的生
活」——成為自己(to be as one is)他們希望:「我們就是我們。我們不希望妨
礙我們的自然行為。我們不希望隱藏任何東西。」138
當年講求回歸自然的嬉皮,
他們也不會穿釘鞋塑料或動物毛皮,而是簡單的手縫或印染,因為他們希望實
踐一種農庄生活。
其實嬉皮所說的,不也正是我們內心底深處想要吶喊的?我們除了想要做
自己,也想要有一方能做自己的自然空間,能滿足我們的心靈。從渴望回歸自
然、親近大自然、熱中野外活動,到生態旅遊、田園生活、退休歸農、務農、
園藝、自然藝術等等,大家的關注都日漸濃厚。不只是大人,小孩更是需要。
一隻昆蟲、一朵雲彩、一棵果樹,在孩子的世界中都顯得彌足珍貴。
所以在《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中,傑西在畫畫時,為了「抓不住樹林的
詩意」而煩惱;傑西與柏斯萊在橡樹與冬青樹之間蓋了心中最堅固的城堡;在
神聖松林裡釋放心靈,獲得新生的力量。在大自然中,他們自然地做自己,不
需要隱藏,也不受拘束,自然的世界真是人間最美的應許之地。
二二二二、、、、自我實現的路徑自我實現的路徑自我實現的路徑自我實現的路徑
137
此演講發表於 1969 年 3 月,見網路 http://www.eshana.com.tw/wherebuy/box1_05_43.htm 〈奧修對於嬉皮的印象〉,2008.1.12。
138 同上。
106
那麼人類究竟要如何才能走向自然呢?要走向自然,人類應先走出「人類
中心主義」。生態批評家在將後現代主義的去中心化方法運用到人與自然的關
係之維時,他們發現了人類中心主義的悖論:「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卻自認為
是獨一無二的。」正是由於人在對這個悖論無知的情況下展開了征服世界的可
怕競賽,生態圈的總體福祉才被破壞,也同時破壞了人類自己本身的福祉。在
《作為退隱者話語的生態學》一文中,利奧塔本人就曾追溯生態世界退隱的語
義學根源,明確表示「家(oikeion,生態世界)的退隱狀態是悲劇的起源」。生
態批評家辛西婭‧迪特英(Cynthia Deitering)以後現代主義的反諷口吻將人定義為
「廢物製造者」:「廢物進入了人的自我,成為人的一部分,我們開始將自己
的生殖角色理解為廢物製造者。」人作為「廢物製造者」本身也是廢物,他在
製造「自然之蝕」的同時在自我流放:在業已「衛生間化」的地球上,世界不
再是家。139
這樣的論調雖然聽起來很聳動,但卻揭穿了人類主體自主萬能的現代
性神話。
後現代主義世界觀承認「全球所有生物和非生物都是相互聯繫的」生態學
觀點,即人是與自然共生的。人與自然是互動的關係,彼此皆是生命的主體,
皆互相成就與被成就。這種成全和被成全的基本運動造就著無數生命主體共同
的家(okios)即生態圈(eco-sphere)。
人必須走出狹隘的自我,才能與自然共生共榮。莊子曾以「坎井」與「東
海」之兩種空間系統互相對照,坎井之蛙由於自我封閉領域的崩潰而「適適然
驚、規規然自失」,而東海則具有空間的開放性,是一種不停息地向外開放的
性質;其所謂「向外開放」就是指存有物之具有基本的從內流入且又向外流出
的自由流通性的緣故。能自由自在地流通而出入無礙,如此才可稱之為向外開
放的空間系統,也才能成就其宏遠恆一性。140
人之心要能擴大,以「無限心」
139
王曉華,〈後現代話語譜系中的生態批評〉,引自網頁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CulturalWorkshop/academia/critique/critique14.htm,2008.2.5
140 潘朝陽,《心靈‧空間‧環境------人文主義的地理思想》,頁 297-298。
107
才能知「無限空間」,也才能進入「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意境。
莊子建構了完全開放的大自在心靈,以此而投射出一個大自在的無侷限性空
間,此空間理念正是現今深層生態學的中心意涵。深層生態學一詞由挪威生態
哲學家奈斯博士(A. Naess)首創,德維(B. Devall)、雷森(G. Sessions)與斯尼
德(G. Snyder)等許多學者相繼推動。德維與雷森曾將深層生態學做如下的解釋:
「深層生態學並不僅從狹隘侷限的眼光看環境問題,而是試圖建立一個廣大圓
滿而孕含宗教和哲學的世界觀。……其基本深意在於兩個終極特質:自我實現
(self-realizations)與生物為中心的平等性(biocentric equalitarianism)。」141
「自我實現」是指人的潛能的充分展現,使人成為真正的人的境界,深層
生態學的創立者奈斯指出,自我的成熟需要經歷三個階段:從心理意義的自我
(ego)走向社會性的「我」(self);再從社會的「我」走向形而上(大寫的我
Self)。他用「生態我」(ecological self)來表達「大我」必定是在人類共同體
與大地共同體的關係中實現,我與自然之間並無明確的分隔。當我們達到「生
態我」的階段,便能在所有物中看到自己,也能在「大我」中看到所有物。
「生命中心平等說」的意義就是生物圈中的所有存在物都具有同等的生存、
繁衍的權利,並充分體現個體自身以及在大寫的「自我實現」中實現我的權利。
在生態圈中每個存在物都具有平等的內在價值的前提下,自我實現的過程是一
個不斷擴大與自然認同的過程,如果我們傷害自然界的其他部分,那麼我們就
是在傷害自己。這種意識促使我們尊重人類和非人類的權利,生物多樣性增加
了自我實現的潛能,因此,不需要在物種之間建立階級,將人類至於萬物至上。
142所以人是屬於「大化平衡」的一部分,個人的作為與整個世界是息息相關的,
也因此人要小心自己的作為,不輕率妄行、才不會破壞自然的平衡。
美國奇幻文學作家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1929-)的《地海傳
141
釋昭慧,〈佛法與生態哲學〉,哲學雜誌第三十期,頁 46-63。 142
林朝成,〈基進生態學與佛教的環境關懷(中)〉,引自網頁 http:// www.awker.com/hongshi/mag/61/61-10.htm- -1 ,2008.3.1。
108
說》系列,是含有深層生態意識的作品, 從道家的陰陽相生、一體制衡的觀點,
衍生出「生態平衡」的視野。人與自然共生共存也成了書中探討的主題之一。
所以書中的主角格得和一般奇幻文學中的法師很不一樣,他很少使用法術(除非
在有必要的情況下),這都是為了維持「大化平衡」。
「一顆石子被檢起來,土地因而變輕,拿石頭的手因而變重。把石頭丟
出去時,天上星辰以繞行相應。石頭打中或墜落,宇宙都因之改變。整
體的均衡,仰賴每項單一行動。風、海、水、地與光的力量,以及禽獸
植物都如此,一切都完好、合宜地搭配著。這一切都含括在『一體制衡』
當中。舉凡颶風、大鯨魚的號鳴、枯葉的吹落、蚊蚋的飛移,一切行動
都在整體均衡的範圍內。我們,既然身為具備力量操控世界、並互相操
控的人,就必須學會按照落葉、鯨魚、風的本性去行動。我們必須學會
保持那均衡。」143
從格得這段話中,我們窺見自然萬物彼此間都有著微妙的牽連,正所謂「牽
一髮而動全身」,而在自然中的人類,更不能違反自然的本性,才能保持整個
生態系統的均衡。所以不能小看自己的一個小動作,它往往引起無法想像的「蝴
蝶效應」。就像瘟疫是大自然「一體均衡」的一種運轉,萬物的均衡自然回正
時,可能造成一些負面的衝擊。又如勒瑰恩寫「開闊海」的子孫,他們靠海維
生,他們視海的生命為他們自己的生命。他們既不佔有自然,也不會失去自然,
這是一種尊重自然的深層意識。而格得在自我實現的道路上,最後選擇回歸自
然,也是因為他領悟到沒有一個王國能比得上自然的森林,而他在自然裡終能
學會一些他一直未學會,也是行動與力量不能教他的東西。
美國著名的作家司卡特‧歐德爾創作的《藍色海豚島》,描述一位女孩子(卡
143
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著,蔡美玲譯,《地海彼岸》(The farthest Shore)(台北:謬思,2002.7),頁 98-99。
109
拉娜)獨自一人在孤島上生活的故事。如果以卡拉娜在孤島上生活了十八年的歲
月來分隔,我們可以約略將她的成長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大自然中求
生存,由於孤立無援,此時的卡拉娜看起來是大自然裡最弱小的動物,因此她
努力掙扎於生死存活之際。第二階段是向大自然挑戰:經過多次磨練,她就像
女勇士一樣將大自然看做是一種挑戰,想要證明自己的能力。第三階段是與大
自然合而為一,她與大自然的動物成為好朋友。牠們不再是之前她眼中供吃用
的動物卡拉娜將牠們看成自己最喜愛的朋友,沒有這些朋友,生活就顯得單調
乏味。書中描述卡拉娜從害怕無助,到勇敢無畏,到與大自然和平共處的改變,
何嘗不也是我們成長歷程的反應?144
人類回歸自然、擁抱自然的過程,是從小我走向大我,也正是自我實現的
路徑。如果我們能領悟自然中的生態多樣性,萬事萬物皆互相成就的道理,擴
大自己的認同也意味著包容更多的差異、抿除更多的界線,那麼我們心中的橋
是四通八達的,它會帶領我們通往更廣大的宇宙。
144
余治瑩,〈來一趟大自然洗禮〉,《藍色海豚島》(Island of the Blue Dolphins)(台北:東方,2006.1)。
110
第陸章第陸章第陸章第陸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流動的自我流動的自我流動的自我流動的自我
凱瑟琳‧佩特森有著移民的特殊成長背景,其所著之少年小說正是心理、
文化與人生再現的文本。佩特森不是純粹的美國人或是中國人,她是獨特的。
不論她是 American-Chinese 或是 Chinese—American,她有她獨特的表達方式。她
將自身的生活經驗置入文本,作品中所反映的疏離感是她年少時所面臨的難
題。佩特森在游移不定的界線徘徊,在國籍與種族方面,無法認同週遭的中國,
並不代表她毫無疑問的可以擁有美國認同。而由於此成長背景,讓佩特森更加
深入去探究自我、找尋自我,也造就了一顆更加敏銳與易感的心,這使得她對
青少年所面臨的心理困境有著更加細膩與精準的刻畫。張子樟在《少年小說大
家讀》中提到:「尋找樂趣(pleasure)、增進了解(understanding)與獲得資訊
(efferent)是專家公認的閱讀功能。」145
筆者以為,佩特森的作品在「增進了解」
方面發揮了很大的功能,藉由其文本,成年讀者可以深入了解青少年心理,而
青少年讀者可以獲得一種參照與領悟,藉由讀者與作者對話的閱讀過程,在潛
移默化中有所成長。
《孿生姊妹》中所呈現的正是她成長時分裂的自我,另一方面也隱含了她所
具有的雙重身分。凱若琳與露易絲可以說是不同的人,也可以說是同一個人。
她自己也曾表示:「我們就是自己的孿生」,但她企圖將她在種族、政治、宗
教上體驗到的歧異與壓力兩股不同的力量匯整融合在創作中。就如同詹肯斯
(R.Jenkins)所言,認同型構的過程,除了自我與外在的反覆協商之外,同時也涉
及到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覺知與反思。146
佩特森認同的焦慮與成長期的孤單,來
自她自身人性的部分,也來自跨國的不愉快成長經驗。所以認同的型構事實上
是一種非常複雜的過程,一個人的認同可以是多重而多變的,就如同 Kathryn
145
張子樟,《少年小說大家讀》(台北:小魯,1999.8),頁 30。 146
轉引自古佳豔著,〈家在地球另一端:琴弗立茲的認同焦慮與雙重鄉愁〉,《生命書寫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2007.10),頁 5。
111
Woodward 在其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一書的緒論中所說的:「我們之中的每一
個人都可能經歷過某些內心的掙扎,而存在於相互衝突的認同之間的這些掙
扎,則是以我們在世界上不同的位置。」147
所有的認同都是植基於建構的歷程,
人的一生,也都在尋找出屬於他的位置, 並進而對這個 "位置" 做一扞衛或認同
的再深化,或者是放棄原來的認同而再去尋求另一認同,如此地循環。
佩特森在其生命的旅程之中,尤其是在她的青少年時期,面臨艱困的認同
危機。筆者在深入分析佩特森的三本文本之後,歸納出青少年自我認同的主要
受到家庭、學校、同儕團體及地方的影響,佩特森跨國際的移民體驗,延伸她
的人生觸角與視野,也使她文本中所再現的認同更加多元。再者,本論文所論
述的三本文本,其故事皆發生在不同的時代背景,《孿生姊妹》的故事發生在
40 年代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美國沿岸島嶼,《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則是發生在
60 年代戰後的小村莊裡,《太平天國》則是描述十九世紀的中國。佩特森由於
從小生長在國共交戰的時代,舉家常因戰爭原因遷徙,所以在她的書中常會看
到戰爭的影子。從這三本文本發現(尤其是《太平天國》),個人的認同意識會受
時代背景的影響,尤其是戰亂所帶來的「流離失所」與「不得其所」,給個人
心靈所帶來的衝擊可謂不小,當精神上呈現流亡狀態之時,個人對於歸屬感也
更有一種渴望。
整體看來,佩特森在人物塑造、心理層面這個部分刻劃的相當好。在《孿
生姊妹》中,當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方起,露易絲內心的戰場也正如火如荼的
展開。佩特森赤裸裸地把露易絲內心的忌妒、憤怒、不安、矛盾、怨恨等等情
緒攤開在讀者面前,讓讀者深切感受到此角色的立體與真實。在此書中,露易
絲無法達成自我認同的來源是她的妹妹,筆者發現佩特森所塑造的凱若琳是一
個完美的女性形象:美麗、嬌弱、溫柔、貼心、多才多藝,而露易絲的男性化
特質則使她自己陷入自我懷疑的泥沼中。然而露易絲與凱若琳奮鬥的過程,則
147
Kathryn Woodward 等著,林文琪譯,《認同與差異》(Identity and Difference) ,頁 2。
112
是女性覺醒的表徵:她們皆走出家庭、藉由在外工作開拓自己的世界,並拓展
自己的生命經驗 。
身為一個女性,露易絲認同心理的轉變過程是如此的:一切從無明的比較
開始,認為妹妹較受人肯定也得到較多的關愛,一開始由於忌妒心而後產生怨
恨,因為無法認同妹妹,所以也無法認同自己:認為自己不美麗、不乾淨、不
優秀等等。後來,她發現自己走不出去的原因之一是無法擺脫自己對家庭的依
賴,她下定決心離家求學與工作,肯定了自己的能力,最後在爲當地孕婦接生
雙胞胎時,找到了自我。露易絲真正達成自我認同的時刻,是在她從自己的往
事與眼前事實的對照中,得到一種理解,因為理解她終於能拋開多年在心中深
埋的成見,而能寬恕,而能體會天地之心。
艾瑞克森曾解釋達成認同的過程,是當一個人覺得最為活躍和有生命力,
每件事都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時候。一個人不會透過自問「我是誰」而正確的尋
找認同,而是透過內在的聲音說「這就是真正的我」。因此是要聆聽內在的聲
音,按照這個聲音去做,才是達成認同的時刻。148
在文本中,露易絲的認同意
識受到外界很多因子的影響,如性別、文化、風俗、宗教、外貌、地方等等,
然而這些都分割了她的自我,她如果認同了自己是芮思島上的傳統女性,那麼
她將永遠被囚鎖在島上;她如果認同了自己是被家人忽略的長女,那麼她會一
直孤單下去。過於認同外在事物的表象,不論是正面或負面的認同,都是一種
偏執,因為當人們不停地指認認同的對象,只是造就了更多的「人格面具」,
而這些人格面具都不是真正的、完整的自己。即使是現今女性主義的認同也不
是完整的,女性透過要求平等、點明差異或者是徹底分離,在各種事件上否定
由男性定義或由父權家庭銘刻的女性認同,然而如果是站在如此對立的兩造去
達成女性的自我認同,這樣的意識仍是斷裂而不穩固的。而自我中本來就同時
存有男性與女性的部分,自我中存在著兩性的圓滿特質,艾瑞克森認為如是,
148
羅倫斯‧佛萊德曼(Lawrence J. Freidman)著,廣梅芳譯,《艾瑞克森---自我認同的 建構者》(Identity’s Architect—A biography of Erik H. Erickson),頁 260。
113
榮格所見亦如是。所以當我們了解人活在世界上真正的功課並不是努力證明你
是誰,而是讓自己做那個本然的自己時,情況將會大大不同。
在《太平天國》中,顯現的是大環境對一個人認同意識的影響。在戰亂與
物資貧窮的年代,認同問題大都是社會問題。本質上,使青少年感到困擾的不
是因為身體成長或慢性衝動,而是他或許在別人的眼中並不是很好的,或是沒
有達到別人期望的一種想法,遠勝於此的,年輕人開始對他們未來在大社會環
境中的定位感到憂慮。隨著他們快速擴展的心智能力,青少年在面對眼前無數
的選擇和可能性時,感到無所適從。而文本中的王立,由於遭逢戰亂年代,更
有一種身不由己的感受,雖是在半推半就的情況之下加入太平天國這個團體,
然而他也經由認同這個團體而找到歸屬感。艾瑞克森認為:青少年對於他們究
竟是誰感到極不肯定,焦慮地,他們傾向『以團體方式』尋求認同。他們會「變
得非常團體排外、沒有寬容心、並且對於他們不同、被排除的人是殘酷無情的。」
149在他們被急於被認同時,他們會將『自己、他們的偶像和他們的敵人』刻板化。
王立很典型的是以團體方式尋求認同,他將自已和其他人放在一種「忠誠
度的試驗」中,並把他自己跟政治或宗教的意識形態並列為齊。從中,我們偵
測到年輕人對自我真實的價值的追尋。然而,依附團體只能讓人獲得短暫性的
認同,而過份的認同某個團體,不但會造成排外與敵對的心理,也會失去自己。
加上太平天國是一個極端社會的樣板,加入這個團體,人性被統一,也被標準
化。艾瑞克森在解釋「同一性阻滯」時,解釋有些年輕人在建立起健康的同一
感之前,可能會出於自願,也可能會被迫越過那個嘗試和探索的階段。在王立
的同一性阻滯過程中,他所採納的角色是以太平天國中的權威人物為他所設定
的目標為目的。王立是被迫併入這樣一個角色,在其中並沒有被賦予一段真正
「心理社會緩衝期」150
。他並沒有時間做其他的角色嘗試或是自我反思。一般而
149
William Crain 著,劉文英,沈秀靖合譯,《發展學理論與應用》,頁 257。 150
勞倫斯‧斯藤伯格著,戴俊毅譯,《青春期》(上海:科學研究院出版社,2007.5),頁 348,「所謂的緩衝期,即青春期中一段不會受到過度的責任和義務約束的『隔離時期』,而這樣的責任和義務會妨礙年輕人追求他們的自我發現。」
114
言,年輕人能接觸到的選擇越多,以及必須做出抉擇的領域越多,那麼在建立
同一感的過程中所要面對的問題也就越多。王立由於大環境的壓迫,也無從選
擇,所以越過了同一性危機,已然做出了不得不的抉擇,但是他在做出抉擇之
前,並沒有經歷過一段嘗試時期。因此,同一性阻滯是對同一性發展過程的一
種干擾,這種干擾阻礙王立發現他的所有可能性。然而同一感絕不會一勞永逸
的獲得或是維持下去的,在一連串的殺戮與動盪之後,王立依附在太平天國的
希望與舒適感是飄忽不定的,王立的認同危機終究是爆發了。他最後還是得真
實地面對自己人性的部分,他在一系列基本的方面做出了另一個選擇,並且承
擔起了相應的人生責任-----工作與家庭,他的同一性危機也因而化解
《太平天國》同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與歐威爾的《一九八四》是均為反
烏托邦的作品。特別的是,《太平天國》所描述的是歷史上確實發生的事件,
一個真實存在過的「烏托邦」,而《美麗新世界》與《一九八四》則是描述想
像中的烏托邦。《美麗新世界》所標榜的三樣事是:團結、劃一、穩定。「人」
是由試管製造出來的,稱為波卡諾夫司基群,依次分為五等,而在「孵育管制
中心」裡,一切人性均被摒除。而《一九八四》一書,也是一部反極權的作品。
在極權體制下,人的創造力一筆勾銷,一舉一動都有「老大哥在監視你」。《太
平天國》則結合了宗教與政治,描述另一個「神人共治」的極權社會。而人類
為何會認同這樣的社群呢?其實是出於一種心理與生理上的雙重需要,尤其是
在一個內憂外患的年代裡。在心理上,人們需要希望,需要依靠,需要彼此的
認同;在生理上,人們需要最基本的生存條件,那就是得以溫飽。在另一方面,
人類害怕跟別人不一樣,有時跟團體一致,會帶來安全感也能得到他人的認同,
然而太過一致,會喪失自己的獨特性。在烏托邦的標準之下,一切均自足而美
好,痛苦不存在,人不再是被上帝賦予自由意志,有位格的人,僅只是一些「制
約」的產物--當人以追求安逸為最終目的,實際上不過是一種逃避--對生
115
命本身的逃避--掩蓋事實的真相,以快樂舒服的感覺麻醉自己,拒絕使自己
不愉快或痛苦的所有因素,其實這不過是拒絕真相。
《太平天國》也留給我們一個值得深思的議題,信仰是否可能只是一種制約
的結果?宗教信仰也許被當作「索麻」151
來使用,因著人對於疾病,死亡的恐懼,
然而卻又必然遭遇,所以在這裡他成為人的慰藉,讓人可以克服痛苦恐懼?如
果問題僅止於恐懼本身,那麼只要設法消除恐懼即可。然則倘若問題不在恐懼,
而是所恐懼的事物,那真正的解決方法只有根除問題來源。然而建立一個烏托
邦社會就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方法嗎?《太平天國》中洪秀全千方百計只為建立
一個上帝的國度,但許多太過理想化的措施,泯滅人性,反而衍生更多的問題。
所以美麗新世界並不美麗,太平天國也不太平。
佩特森以一個外國傳教士的身分來看待太平天國的始末,她讓主角王立最
後選擇回歸家鄉,似乎也是在質疑宗教的制度與組織。佩特森告訴了我們,宗
教的外在形式不是那麼重要,最重要的是回歸到自己的內心,這一點在《孿生
姊妹》中我們也見端倪:在《孿生姊妹》中露易絲的奶奶恪守基督教傳統而食
古不化,而露易絲卻嫁給了一位天主教徒。佩特森似乎帶領了我們超越了狹隘
的宗教認同。而《太平天國》也告訴了我們:真正的烏托邦是在自己的內心,
並不需遠求。人因失去自己內心的淨土,才會盲目追求外在,靠著外在的戒律
來約束自己,都只是暫時,而不是永久。
在《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中,自我在遷徙中流動。柏斯萊以一個轉學生
的身分進入一個新的團體,卻顯得格格不入;而傑西是家中唯一的一個男孩,
卻在學校顯得羞怯而孤單,這兩個人都面臨了認同危機。青少年常會在同齡人
群體尋求認同,儘管柏斯萊在課業及體育方面都表現傑出,然而卻未能在班級
中被認同。而柏絲萊的男性化特質 (獨立性、進取心、攻擊性),帶領著具有女
151
在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中,用「索麻」麻醉不快的情緒,滿足所有的欲望,維持每個人在「快樂」的常態。
116
性化特質(害羞、合群、膽小)的傑西,這時柏斯萊成了傑西的「重要他人」。152
在學校中,他們遇到了許多不如意的事,學校是一個令他們覺得挫敗的「地方」,
所以他們必須創造另外一個屬於自己的「地方」,這個「地方」就是「泰瑞比
西亞」。「泰瑞比西亞」是屬於二人的神聖空間,是他們滋養友誼,衍生力量
的所在。「泰瑞比西亞」所象徵的是「心靈的原鄉」,在這個心靈的原鄉之中,
人們可以快樂的做原本的自己。所以「泰瑞比西亞」雖然是一個想像的王國,
但也是一處最真實的地方,在這裡柏斯萊與傑西勇於做自己,克服了任何困難,
此「真」的精神正是氣力與勇氣的展現。傑西在「泰瑞比西亞」中學會了愛與
勇氣,也明白了柏斯萊正是一座帶他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即使柏斯萊後
來離開人世,但是傑西也不會再孤單,因為他知道要再造一座橋,帶領更多的
人通往「泰瑞比西亞」,因為我們每個人都需要這樣一個「地方」。這個地方
是一個更活絡的空間,讓我們發揮更大的想像空間,讓我們盡情地生活與體驗,
這個地方不正是自我認同滋養的所在?
《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也點出了友誼的可貴,在「泰瑞比西亞」中,柏斯
萊與傑西的地位同等的重要,他們二人缺一不可,失去了彼此的認同,這個地
方就失去了意義。再想想那個故事吧!變色龍會隨著空間轉換自己的顏色,所
以他煩惱著沒有自己的顏色,但是當他遇到另一隻變色龍後,不管他們身處在
何種地方,他們便擁有了自己的顏色。柏斯萊與傑西也會隨著空間轉換自己的
顏色,在學校與在「泰瑞比西亞」,他們所擁有的自我概念是不同的。在學校,
他們是受同學欺負的可憐蟲;在「泰瑞比西亞」,他們則是叱吒風雲的皇后和
國王,他們的自我一起在真實與想像的世界之間流動,而在流動的過程之中也
同時獲得了力量。萊昂那多‧達芬奇(1452—1519)言:「兩個劣勢相互依靠在一
起便成了優勢。同理,這半個世界靠著另半個世界便相當牢固。」亞里士多德
(384BC—322BC)說:「朋友是什麼?是生活在兩個身體內的一個靈魂。」柏斯
152
在生活中對個人而言最重要的人物,心理學家稱之為「重要他人」。
117
萊與傑西彼此認同,一同成長,穩固的友誼讓他們在面對世界有了信心與勇氣。
好朋友能給對方的禮物無論是物質還是情感的,建設性的還是只有精神上的認
同與同情,只要我們樂於付出、與人分享、關愛別人,我們就有了目標。有了
這些目標,我們就永遠不會迷失,也不會孤單。
聖修柏里所著的《小王子》,點出了友誼中的獨一無二與珍貴:當小王子
來到地球上的一座玫瑰花園,他看到五百朵和他星球上那朵一樣的玫瑰花,他
想到自己擁有的不過是一朵平常的玫瑰花,自己也不過是一個平凡不過的王
子,他躺在草地上哭了。就在這個時候,狐狸出現了。狐狸告訴他「養馴」,
即「建立關係」的真義:
「對我來說,你不過是個小孩,和成千上萬的其他小還沒有兩樣。我不
需要你,而你也不需要我。對你來說,我和成千上萬的其他狐狸沒有什麼
不同。但若你養馴我,那們我們就互相需要了。對我來說,你就是全世界
獨一無二的。對你來說,我也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153
小王子和狐狸做了朋友,因此狐狸成了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狐狸。同樣地,
柏斯萊與傑西做了朋友,他們對彼此而言都是獨一無二的,他倆一同創造與認
同的「泰瑞比西亞」,也成為一個獨一無二的「地方」。這地方孕育了親密的
人際關係,也重構了一己賴以維生的價值與尊嚴。
「地方」可以從「泰瑞比西亞」這個兩人世界擴大到一整個社區。「地方」
的概念已越來越受重視,資訊的流通與交通的便捷,使越來越多人在移動世界
中創造地方。而跨文化的經驗,也使得地方的特色顯得混雜與多元。 現今的「社
區總體營造」是社會運動所採的在地化策略,仰賴對地域文化及生態的依附情
感,同時環繞著生物多樣性的議題,活化了全球網路,藉此重申地方特色的重
153
聖修柏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著,《小王子》(The Little Prince),頁 60。
118
要性,建構地方的文化生態。舉例而言,拉丁美洲如何「回歸地方」?像是哥
倫比亞以太平洋雨林的黑人社群為中心,連結了一組複雜的以地方為根基的認
同來對抗全球化的勢力。筆者不禁思索,「地方」既是蘊含人的意識在裡面的
一個概念,是人心參與互動的所在,那麼「回歸地方」即是回歸到自己的心,
所以「在地化」所隱含的一個重要概念也無非是:做自己。 像變色龍會隨著空
間轉換自己的顏色,但那顏色畢竟是外在的顏色,變色龍的本質不會改變,它
仍就是隻變色龍!
119
第二節自省的力量與認同的再造第二節自省的力量與認同的再造第二節自省的力量與認同的再造第二節自省的力量與認同的再造
藉由前文的分析與歸納,筆者發現認同來自人類一種自然的天性,這天性
也可說是一種原始的需要,這需要主要是來自心理上的,人需要認同的對象也
需要被他人所認同。依此看來,認同是一個必然的過程,人也在認同的過程中
建構起自己的主體。這裡呼應了巴赫丁的對話理論:巴赫丁認為主體的存在首
先是個體的,但因個體存在的不完整性,真正的主體性必須是共同的,是靠自
我與他者的責任感 / 回應性,靠對話、交流而實現的。154
而通常認同的傾向會
造成一種欲望,這個欲望是渴望跟認同的對象產生一致性 (這個認同的對象可
以是概念、個體、群體或是地方等等),而通常認同的方式是希望自己成為那個
樣子,所以有了模仿及跟隨的行為。 自我具有不斷變化的本性,它通過獨特的
行為而成為他自己。人們認同的對象不會一成不變,隨著生命的流轉,認同的
對象也一直在移轉。
人可以同時擁有多重認同,這點在現今的青少年身上更加顯而易見,隨著
多元文化的興起及大量資訊的唾手可得,個人在全球化的諸多影響下,個人的
認同區塊也是多元而重疊的。紀登斯言:「我們不應該忘記現代性就是產生差
異、例外和邊緣化」「依據於地方性全球性的交互辨証影響的日常生活愈被重
構,個體也就愈會被迫在多樣性的選擇中對生活風格的選擇進行討價還價。」155
舉例而言,青少年可能在家中吃著中式早點,而午餐選擇麥當勞的速食;在學
校念著余光中的散文,而在家則沉浸在好萊塢的肥皂劇當中;在學校他可能有
一個韓國籍或美國籍的朋友,與他分享不同的生活體驗,在家中他可能利用網
路與不同年齡層的朋友聊天。在面對現今社會生活的「開放性」,如何掌握「選
擇權」的課題變得更加重要。
154
劉康著,《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評述》(台北:麥田,2005.5),頁 21。 155
安東尼‧紀登斯著,趙旭東、方文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晚期現代的自我與社會》,頁 30。
120
而在生活中,只要與人互動,避免不了「認同」的問題。同時,我們也在
互動中,努力建立自己與他人之間的「同」與「異」。.然而互動關係,是否大
多建立在認同彼此「相同」的地方?而不是彼此的差異上。因為我們在面對與
別人的不同,心理上有「害怕」,也許害怕失去自己。或者與別人相同,比較
安全,不用承擔某些責任。也許全球化的「認同」,可以是一種對「差異」的
認同。如此一來,我們可以避免個人自我的分割,譬如:認同了某一種角色,
就會去排斥另一種角色。所以我們對某種生活風格的選擇,並不代表我們需要
去排斥另一種風格,那麼人如此一來既可愉悅的做自己,又可減少與他者間無
謂的紛爭。
在此,後殖民倫理學為我們找到了出路,後殖民倫理學重視自省的力量,
指出「他人的存在是我們絕對的責任,我對他人的責任是維繫他的獨特性,而
不是去改變他。」那麼如何實踐自省的力量,讓個人擁有合理穩定的自我認同
感?在此自我認同的反思建構是必須的。紀登斯借助容瓦特有關治療的本質及
其功用的特定看法或者其所蘊含的特定觀點作為方向:
一、自我可以看成是個體負責實施的反思性計畫。我們不是我們現在的樣
子,而是對自身加以塑造的結果。自我必須建構與重構連貫的値得獎賞的認同
感。
二、自我形塑著從過去到可預期的未來的成長軌道。個體依據對(組織化的)
未來的預期而篩選過去,借助這種篩選,個體挪用其過去的經驗。
三、自我的反思性是持續的,也是無所不在的。在每一時刻,至少在有規
則的時間間隔內,個體依據正在發生的事件要求實現自我質問。
四、作為連貫的現象,自我認同設定一種敘事,把自我敘事改變成鮮明的
記述。為了維持完整的自我感,日記和自傳的寫作是中心的推薦物。
五、自我實現蘊含著對時間的控制,即本質上個人時區的建立,「和時間
保持對話」是自我實現的真實基礎。
六、自我的反思性也拓展至身體,而身體成為行動系統的一部分,而不是
121
被動的客體。
七、自我實現可理解為機遇和風險之間的平衡。種種成長技術使個體從壓
迫性的情感習慣中解放出來,讓過去逝去,促發自我發展的無限可能性。
八、自我實現的道德線索就是真實性,它的基礎是「對自己的真誠」。
九、生命進程可以看做是一系列的「過渡」,個人必須協調生命中有意義
的轉變,這些轉變被拖入自我實現的反思性動員軌道之中,並且依據這種軌道
才得以跨越。
十、自我發展的線路是內在參照性的,作為真實自我的成就的個人完整性,
來源在於自我發展的敘事內對生活經驗的整合,這就是一種個人信仰體系的創
建。156
紀登斯更語重心長的指出:「正如『深度生態』保護者所主張的,力圖擺
脫經濟累加的運動,可能應該用個人成長,即培養個人的自我表現與創造潛力
的過程,來取代自由的經濟增長過程,因而,自我的反思性計畫在超越現在的
秩序而向一種全球化的秩序轉型中,可能是非常關鍵的。」 157
認同確實有其不可忽視的力量,而反身性地組織的生活規劃,成為結構自
我認同的核心特徵,也正是重塑自我的新契機。而經由深層生態學給我們的啟
示,人應該擴大其認同範圍,跳脫自我本位,見到生態環境中諸法相依互成的
法則,從而尊重所有不同形式生命的生存價值,告別二元對立世界。
有人認為對於「善」、「惡」二元觀念的強調,使得佩特森的作品具有濃
厚的教誨意義。然而筆者有不同的看法,像是《孿生姊妹》雖然是引援了聖經
故事使作品別具宗教意涵,然其重點在於少女主角如何化解成長經驗中的手足
之爭,「善」與「惡」在此並沒有絕對的定論。而《太平天國》雖描述了一個
「棄惡揚善」的烏托邦世界,但基本上它也是一部反烏托邦的作品。佩特森所
156
安東尼‧紀登斯著,趙旭東、方文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晚期現代的自我與社會》,頁 120-126。
157 同上,頁 312。
122
著墨的是自我覺醒的過程。重點是我們不需否定二元,但如何告別二元對立世
界而走向一元的共同意識?因為這種共同意識,並非鎖定某種特別條件才能生
起的,它不是由於狹隘的自我認同,族群認同,單位認同;它不預設家庭、國
族、人類或是族群的範疇,而是超越個己而包含了整個世界。
凱瑟琳‧佩特森的生命故事其實就是一認同再造的過程。她以一客居中國
的美國人身分,歷經一再的遷移,最後落葉歸根回到美國定居,這其中她所遭
遇到的自我認同課題,都在她的文本中以「他者」再現。誠如她自己所言,她
總感覺自己一直在寫自己的故事。她對書寫少年小說的積極參與,也體現了她
對自我的不停改寫、重構,顯然,她對自我的認同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事實
證明,佩特森最後終於能克服生命的難題,達成健全的自我認同。她以包容的
胸襟領養了與她不同膚色、國籍的孩子 (一個中國孩子與日本孩子),她的認同
已超越了國籍、膚色、種族種種界線。
就如同墨西哥著名女畫家費麗達(Frida Kahlo),她把女性自畫像推到了極
致:它們是一面鏡子,反射著女性個體的人生經歷;而佩特森的少年小說也像
鏡子般地反應著個人的認同情感歷史。她的作家的「自我」與 筆下主角的「他
者」,在靈魂與靈魂之間的交響對話中,相互交流、滲透、融匯、交替形成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重疊」,而這正是自我反思的形式之一 。透過這樣的
對話,佩特森也再造了自己的認同意識,逐漸能認同「差異」。就巴赫汀理論
內涵而言,「差異」( difference)、「他性」(alterity),而不是同一性和相似性,
才是根本的。如果沒有了「差異」,又何來 「同一性」?以宏觀的角度而言,
生態圈是差異的培育者、無中心的開放體系、眾多生命主體的複合體,眾多生
命體互相成就著「差異」,而個體既是成就「他者」者也是被「他者」成就者。
而對於一個作者而言,為了完成自我,必須創造一個「他者」,而這個「他者」
正是故事中的主角,所以「自我」與「他者」是互為主體的。
而既然生態圈註定是差異的代名詞,那麼單一物種的人就不應自詡為地球
上千萬物種的主宰,人與萬物一樣是互為主體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23
彼此的共生共存。所以人為了達成自我實現,就必須經過這樣一個自我覺醒的
過程,在這過程中,人漸漸了解自己與其他大地萬物必須相互依存。同樣地,
沒有眾多生命主體的互生和共生,文學就不可能誕生。從這個觀點來看佩特森
與佩特森的作品,我們發現佩特森多元文化的體驗,使她能以「累積」的方式
成長,雖然曾經感覺疏離,但卻能漸漸適應各個處境,使她非但沒有失去自己
的認同,反而擴大了認同的範圍,而她跨國收養的生命經歷,也印證了「家自
心中來」(“Home is right from the heart”)158
此一論點。也因此,她的作品呈現了
一種開放與包容的人生觀,而她筆下的主角也大多能再造並擴大一己的認同。
肯定「差異」,除了意味肯定別人的差異,也意味著肯定自己的差異,既然萬
物皆互為主體,那麼沒有人可以去支配他人,人理應當自己的主人。佩特森的
作品之所以能擁有廣大讀者,筆者以為除了是因其內涵的「深度」外,更在於
其視野的「廣度」。
就如同露易絲放下成見,做那本然的自己;王立不再依附團體與權威者,
找回自己的選擇權;傑西與柏斯萊在自己的地方「泰瑞比西亞」成為國王與皇
后,他們皆做了自己的主人。生命本是一連串的追尋,而原來尋找自己顏色的
過程,即是從「認同與差異」到「認同差異」的過程!尤其是在這個資訊交流
頻繁的世代,「移民」的體驗不再是一種「不得其所」的無奈,而變成一種功
課與需要,現在已有越來越多單一、雙重或重國籍的孩子,認同自己與他人的
差異,自詡為「世界公民」。而難能可貴的是,佩特森的作品正蘊含了後現代
主義重新勘定自身邊界的可能性。
158
轉引自馮品佳,〈血緣/血言:《血之語言與跨國收養書寫》〉,其中提到紀錄短片〈跨種族收養〉(“Transracial Adoption”2007)以一段黑白新聞短片開場,………..旁白以「家自心中來」(“Home is right from the heart”)結尾。片中的三位受訪者一為韓裔少女、一是成年的原住民女性、另一位則是收養黑人兒童的白人養母。三人對於跨種族收養皆承認有其困難之處,但其基本上都抱持相當正面的態度,可以說呼應了「家自心中來」的樂觀基調。
124
參考書目
壹、中文部分
◎研究文本
1. Paterson, Katherine (凱瑟琳‧佩特森)。鄒嘉容譯。《孿生姊妹》(Jacob Have
I Loved)。台北:東方。2005.12。
2. 。鍾瑢譯,修文:許常德。《通往泰瑞比
西亞的橋》(Bridge to Terabithia)。台北:漢聲,1990.10。
3. 。連雅慧譯。《太平天國》(Rebels of the
Heavenly Kingdom)。台北:小魯文化,2005.7。
◎參考文本
1. Austen, Jane (珍‧奧斯汀)。雷立美譯。《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台北:商周。2006.10。
2. De Saint-Exupery, Antoine (安東尼‧聖修柏里)。《小王子》(The Little
Prince)。台北:敦煌。1987.4。
3. Fritz, Jean (琴‧弗立茲)。陳素燕譯。《家在地球的另一端》(Homesick, My
Own Story)。台北:幼獅。1994. 3。
4. Konigsburg, E. L. (柯尼斯伯格)。《天使雕像》。台北:東方。2003.4。
5. Le Guin, Ursula (娥蘇拉‧勒瑰恩)。蔡美玲譯。《地海彼岸》(The farthest
Shore)。台北:謬思。2002.7。
6. Lowry, Louise (露意絲‧勞瑞)。鄭榮珍譯。《記憶傳授人》(The Giver)。
台北:東方,2002.12。
7. O’Dell Scott (司卡特‧歐德爾)。傅定邦譯。《藍色海豚島》(Island of the
Blue Dolphins)。台北:東方。2006.1。
125
8. Paterson, Katherine (凱瑟琳‧佩特森)。莫莉譯。《吉莉的抉擇》(The Great
Gilly Hopkins)。台北:智茂。1995.9。
9. 。傅湘雯譯。《逆風飛翔》(Lyddie)。台
北:中唐志業。1994.8。
10. Kipling, Rudyard (吉卜林)。謝瑤玲譯。《小吉姆的追尋》。台北:天衛
文化。1994.1。
11. 。劉原孝改寫。《叢林奇談》(The Jungle Books)(上)
。台北:東方。1991.5
12. 。劉原孝改寫。《叢林奇談》(The Jungle Books)
(下)。台北:東方。1991.5。
13. Tan, Amy (譚恩美)。于人瑞譯。《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台北:
聯合文學。1990.3。
◎中譯理論專著
1. Adler, Alfred (阿德勒)。陳蒼多譯。《了解人性》(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台北:大中國圖書。1991.5。
2. 。黃光國譯。《自卑與超越》(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台北:志文。2006.9。
3. A.Ellis ,R.A. Harper .(艾理斯)。何長珠、何真譯。《你不快樂---合理情
緒療法》.。台北:大洋,1988.3。
4. Benjamin, Walter (華特‧班雅明)。林志明譯。《說故事的人》。台北:台
灣攝影。1998.12。
5. Bradshaw, John (約翰‧布雷蕭)。鄭玉英、趙家玉著。《家庭會傷人》。(BRADSHAW
ON:THE FAMILY)。台北:張老師文化。2006.3。
126
6. Bachelard, Gaston (加斯東‧巴舍拉)。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
(LA POETIQUE DE L’ESPACE) 。台北:張老師文化,2006.7。
7. C. G. Jung (榮格)。蘇克譯。《尋求靈魂的現代人》。台北:遠流。1990.5。
8. 。劉國彬、楊德友合譯。蔡榮裕審閱。《榮格自傳---回
憶、夢、省思》(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台北:張老師文化。
2006.5。
9. Campbell, Joseph (喬瑟夫‧坎伯)。朱侃如譯。《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新店:立緒文化,2003.8。
10. 、Moyers, Bill(莫比爾)著。朱侃如譯。
《神話》(Myth)。新店:立緒文化。2005.7。。
11. Castells, Manuel (曼威‧柯斯特)。夏鑄九、黃麗玲等譯。《認同的力量》
(The Power of Identity) 。台北:唐山,2002.11。
12. Crain, William。劉文英,沈秀靖合譯。《發展學理論與應用》。台北:華
騰文化。2005.10。
13. Darian, Leade (立德‧德拉)。《拉岡》。新店:立緒文化。1998.6。
14. D. Spence Jonathan(史景遷)。朱慶葆等譯,溫洽溢審訂。《太平天國》(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台北:
時報文化,2005.12。
15. Erickson, Erik H. (愛力克森) 。康綠島譯。《青年路德》。台北:遠流。
1999.9。
16. Friedman, Lawrence (羅倫斯‧佛萊德曼)。廣梅芳譯。《艾瑞克森─自我
認同的建構者》(Identity’s Architect—A Biography of Erik H.
Erickson)。台北:張老師文化,2001.9
17. Freud, Sigmund (佛洛伊德)。楊韶剛、高申春等譯。《超越快樂原則》
(Fenseits des Lustprizips)。台北:胡桃木文化。2007.1。
18. Fromm, Erich (佛洛姆)。管韻鈴譯。《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
127
台北:志文。2002.10。
19. 。林逸仁譯。《生命之愛》(For the Love of Life)。
台北:南方。1988.9。
20. Fanon, Frantz (佛朗茲‧法農)。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Peau
Noire,Masques Blancs)。台北:心靈工坊。2005.6。
21. Friedman, Thomas (湯馬斯‧佛里曼)。楊振富、潘勛譯。《世界是平的》
(The World is Flat)。台北:雅言文化,2005.11。
22. Freire, Paulo (保羅‧弗雷勒)。方永泉譯。《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台北:巨流。2004.5。
23. Giddens, Anthony (安東尼‧紀登斯)。趙旭東、方文譯。《現代性與自我
認同---晚期現代的自我與社會》(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台北:左岸文化。2007.1。
24. Hoecake, Robert (羅伯特‧霍普克)。蔣韜譯。《導讀榮格》(A Guided Tour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新店:立緒文化。2005.1。
25. Kast, Verena (維瑞納‧卡斯特)。林敏雄譯 。《童話治療》(Marchen
alsTherapie)。台北:麥田。2004.5。
26. Kathryn, Woodward 等著。林文琪譯。《認同與差異》(Identity and
Difference) 。台北:韋伯文化,2006.10。
27. Maggie, Hyde。趙婉君譯。《榮格與占星學》(Jung and Astrology)。新店:
立緒文化。2001.12。
28. May, Rollo (羅洛‧梅)。朱侃如譯。《哭喊神話》(The Cry For Myth) 。
新店:立緒文化。2003.3。
29. Pearson, Carol (卡羅‧皮爾森)。徐慎恕、朱侃如、龔卓軍譯。《內在英
雄》(The Hero Within)。台北:立緒,2005.1。
30. Rowe Townsend, John (約翰‧洛威‧湯森)。謝瑤玲譯。《英語兒童文學史
綱》(An Outline of English-Language Children’s Literature)。台北:
128
天衛文化。2003.1。
31. Stein, Murray。朱侃如譯,譯文校定者:蔡昌雄。《榮格心靈地圖》(Jung’s
Map of the Soul)。新店:立緒文化。2006.10。
32. Steinberg, Laurence (勞倫斯‧斯藤伯格)。戴俊毅譯。《青春期》。上海:
科學研究院出版社。2007.5。
33. Sokolowski, Robert (羅伯‧索柯羅斯基)。李維倫譯,龔卓軍審閱。《現
象學十四講》(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台北:心靈工坊文化,
2007.3。
34. Sardar, Ziauddin。陳貽寶譯。《文化研究》。台北:立緒。2003.11。
35. Tim, Cresswell。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台北:群學,2006.12。
36. Tuan, Yi-Fu (段義孚)。周尚意、張春梅譯。《逃避主義》(Escapism)。台
北:立緒文化。2006.4
37. Virginia, Woolf (維吉尼亞‧吳爾芙)。張秀亞譯。《自己的房間》。台北:
天培文化。2000.1。
38. W. Said, Edward (薩伊德)。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台北:立緒。2001.1。
39. Watt, Ian (艾恩‧瓦特)。魯燕萍譯。《小說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Novel)。
台北:桂冠圖書。2002.2。
40. Woodward, Kathryn 等著。林文琪譯。《認同與差異》(Identity and
Difference) 。台北:韋伯文化,2006.10。
41. Watkins, Susan Alice 。朱侃如譯。《女性主義》(Feminism)。台北:立緒,
2002.11。
42. 山中康裕。王真瑤譯。《哈利波特與神隱少女》。台北:心靈工坊。2006.1。
43. 河合隼雄。詹慕如譯。《小孩的宇宙》。台北:天下文化。2006.7。
44. 塩見直紀。蘇楓雅譯。《半農半 X的生活》。台北:天下。2006.10。
129
45. 陳舜臣。姚巧梅譯。《太平天國》。台北:遠流,1996.10。
◎理論專著(依筆劃順序)
1. 王國芳 郭本禹。《拉岡》。台北:生智。1997.8。
2. 方孝謙。《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台北:巨流。2001.6。
3. 尤卓慧、岑秀成、夏民光、秦安琪、葉劍青、黎玉蓮編。《探索敘事治療實
踐》。台北:心理。2005.6。
4. 張子樟。《少年小說大家讀》。台北:小魯。1999.8。
5. 。《寫實與幻想》。台北:國語日報社。2001.5。
6. 張倩儀。《另一種童年的告別》。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3。
7. 單德興。《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台北:麥田。2000.9。
8. 畢恆達。《空間就是權力》。台北:心靈工坊。2001.10。
9. 廖炳惠。《關鍵詞 200》。台北:麥田,2006.7。
10. 潘朝陽。《心靈‧空間‧環境------人文主義的地理思想》。台北:五南。
2005.12。
11. 劉劍梅。《狂歡的女神》。台北:九歌。2005.8。
12. 蔡源煌。《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台北:雅典。1991.11。
13. 。《當代文學論集》。台北:書林。1996.8。
14. 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台北:麥田。2004.9。
15. 劉康著。《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評述》。台北:麥田。2005.5。
◎ 期刊論文(依筆劃順序)
1. 王戎笙。〈太平天國的理論和實踐〉。《歷史月刊》80 期。1994 。
2. 古佳豔。〈家在地球另一端:琴弗立茲的認同焦慮與雙重鄉愁〉,《生命書
寫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2007.10。
130
3. 張子樟。〈從「閱讀」到「文本研究」------淺述文學理論與批評的應用〉。
兒童文學學刊第十一期。台北:萬卷樓。2004.7。
4. 陳捷先。(戊戌變法前後的帝后黨爭)。《歷史月刊》126 期。1998。
5. 劉美瑤。〈烏托邦的幻滅〉。《兒童文學學刊》第十四期,台北:萬卷樓。
2005.12。
6. 釋昭慧。〈佛法與生態哲學〉。哲學雜誌第三十期。1990.10。
◎ 學位論文(依筆劃順序)
1. 吳文薰。〈女性成長之孤獨、希望與自我覺醒----從凱瑟琳‧怕特森三本作
品談起〉。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0.6。
2. 吳芸蕙。〈記憶、書寫與再現-----以認同為主軸探討《台灣真少年圖畫書》〉。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8.1。
3. 陳佳秀。〈葉祥添小說中華人形象的自我再現〉。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
究所。2004.8。
貳、西文部份
◎參考文本
Paterson, Katherine. Jacob Have I loved. New York:Harper,2001.
Paterson, Katherine. Bridge To Terabithia. New York:Harper,2007.
◎理論專著
Cary, Alice. Katherine Paterson. California:The Learning Works,Inc,
1997
131
◎網頁資源
1. 〈凱瑟琳‧佩特森官方網站〉
http:// Terabithia.com - The Official Site of Author Katherine
Paterson(2007.5.6)
2. 〈美國西北大學網站〉
http//www.northern.edu/hastingw/Jacob.htmll(2007.9.5)
3. 〈維京百科網站〉
http:// Katherine Paterson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007.12.3).
4. 〈2007 認同與差異部落格〉
http://blog.yam.com/identity2007.(2008.1.8).
5. 〈奧修對於嬉皮的印象〉
http://www.eshana.com.tw/wherebuy/box1_05_43.htm (2008.1.12).
6. 王曉華。〈後現代主義話語譜系中的生態批評〉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CulturalWorkshop/academia/
/critique/critique14.htm(2008.2.5)
7. 林朝成。〈基進生態學與佛教的環境關懷(中)〉
http:// www.awker.com/hongshi/mag/61/61-10.htm- -1(2008.3.1)
132
附錄一:
認同的成因
認同的途徑
認同的對象
結果
《孿生姊妹》
強烈需要被關
懷與重視。
負面的認同,藉
由忌妒仇恨,發
洩心中的不滿。
自我的鏡像(孿
生妹妹凱若琳)
在多年之後,
走出自我孤
島,達成自我
認同。
《太平天國》
尋求希望,安定
的庇護與溫飽。
融入群體,對首
領的絕對忠誠。
烏托邦(太平天
國)教義與領導
者
不再執著認同
太平天國,選
擇回到家鄉過
自己想要的生
活。
《通往泰瑞比
西亞的橋》
需要被肯定與
渴望同伴。
模仿與跟隨同
伴,在地方中建
立彼此的友誼。
1.好友柏斯萊
2.兩人共同創造
的地方「泰瑞比
西亞」
好友死亡,開
放認同的地方
「泰瑞比西
亞」與更多人
分享。
133
附錄二:
凱瑟琳‧佩特森(Katherine Paterson)寫作年表
◎青少年小說
Sign of the Chrysanthemum, 1973.
Of Nightingales That Weep, 1974.
The Master Puppeteer, 1975.
Bridge to Terabithia, 1977.
The Great Gilly Hopkins, 1978.
Jacob Have I Loved, 1980.
Rebels of the Heavenly Kingdom, 1983.
Come Sing, Jimmy Jo, 1985.
Park's Quest, 1988.
Lyddie, 1991.
Template:The Underground RailRoad,1992.
Flip-Flop Girl, 1994.
Jip, His Story, 1996.
Preacher’s Boy, 1999.
The Same Stuff as Stars, 2002
Bread and Roses, Too, 2006
◎圖畫書
The Angel and the Donkey, 1996.
The King's Equal, 1996
Celia and the Sweet, Sweet Water, 1998.
Tale of the Mandarin Ducks, 1990.
The Wide-Awake Princess, 2000.
Blueberries for the Queen, 2004
◎學齡前讀物
The Field of the Dogs, 2001.
Marvin One Too Many, 2001.
Marvin’s Best Christmas Present Ever, 1997.
The Smallest Cow in the World, 1991. (originally done for migriant farm kids)
Parzival: The Quest of the Grail Knight, 1998.
134
◎非小說類
Gates of Excellence: On Reading and Writing Books for Children, 1981.
Consider the Lilies: Plants of the Bible, 1986.
The Spying Heart: More Thoughts on Reading and Writing Books for Children,
1989.
Who Am I?, 1992.
A Sense of Wonder: On Reading and Writing Books for Children, 1995
(combined text of Gates of Excellence and The Spying Heart)
The Invisible Child: On Reading and Writing Books for Children, 2001
◎聖誕節故事
Angels & Other Strangers: Family Christmas Stories, 1979.
A Midnight Clear: Twelve Family Stories for the Christmas Season, 1995.
Star of Night: Stories for Christmas, 1980.
◎得獎紀錄
NSK Neustadt Prize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2007
Astrid Lindgren Award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2006
Literary Light, Boston Public Library 2000
Living Legend Library of Congress 2000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Medal for Writing 1998
Lion of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1998
Who's Who in American Women 1995 to present
King College, Outstanding Alumnus 1993-1994
Education Press Friend of Education Award 1993
Anne V. Zarrow Award, Tulsa Public Library 1993
New England Book Award 1992
US Nominee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 1989
Regina Medal, Catholic Library Association 1988
Children's Literature Award, Keene State College 1987
Kerlan Awar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83
University of Southern Mississippi Medallion 1983
Scott O'Dell Award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1982
US Nominee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Medal 1979
Who's Who in America 1978 to present
The Union Medal,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New York (以上資料參考自維京百科網站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