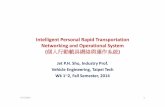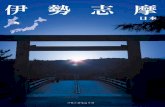為什麼馬殺雞? 視障按摩歷史的行動網絡分析
Transcript of 為什麼馬殺雞? 視障按摩歷史的行動網絡分析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八十三期│2011年8月│頁5-36
為什麼馬殺雞?視障按摩歷史的行動網絡分析 *
邱大昕 **
Why Massage?An Actor-Network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of Massage
by the Visually-Impaired in Taiwanby Tasing CHIU
收稿日期:2009年6月23日;接受日期:2010年1月27日。Received: June 23, 2009; in revised form: January 27, 2010.* 本文初稿曾於2009年4月18日在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年會發表。感謝吳嘉苓、雷祥
麟、傅大為、王秀雲、Joel Stocker、匿名審查者以及編委會對本文的指正與建議,使本文內容能更為完善。同時感謝薛玉欣與邱媽寅在日文資料翻譯的協助,在此致上
最誠摯之謝忱。
** 服務單位: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通訊地址:80708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 E-mail: [email protected]
關鍵字:身心障礙、視覺障礙、按摩、行動者網絡理論
Keywords: disability, visual impairment, massage, ANT
台灣社會研究 第八十三期 2011年8月006
摘要
台灣的盲人在日治時期,除了按摩之外,還從事針灸與電療等工
作。但是到了國民政府時期,台灣的視障者的工作卻逐轉變成現在的
按摩工作。為什麼盲人會從事「非醫療」的按摩工作呢?本研究採用行
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來分析這個「身體」與「工作」間
複雜動態的關係。在本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過去百年間法規、政
府、警察、教科書、針灸電療器具、中西醫專業團體,以及視障者如
何在這轉變過程中,共同形塑出現在所看到的視障按摩樣貌與內容。
2008年10月31日司法院釋字第六四九號解釋,宣告視障按摩保障違憲
後,許多視障按摩團體希望能改變視障者就業訓練過程,重新進入醫
療體系從事理療工作。然而從本研究的角度與立場來看,這雖然不是
不可能的目標,但卻是個百廢待舉重新建構網絡的龐大工程。
Abstract
The blind in Taiwan used to perform acupuncture, moxibustion, massage, and electrotherapy under the Japanese regime. Why did these blind physical therapists become “non-medical” massagers after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takeover of Taiwan? This is the main topic to be explored in the current study. Since the current disability models are incapable of explaining these complicated relations between body and work, this study adopts Actor Network Theory as a tool to analyze 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We will examine how government law and policy, medical professionals, blind workers and medical devices coproduce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today’s blind massage. On October 31, 2008, the Taiwan Justices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issued Judicial Yuan Interpretation No. 649, which proclaimed that i t i s unconstitutional to restrict massage work to vision-impaired individuals. Many of the blind-massage groups now intend to retrain the blind back into medical professions. However, though not impossible, there will be a lot of work to do to rebuild the network required.
007為什麼馬殺雞?
前言
為什麼台灣的「盲人」會從事「按摩」工作呢?盲人真的都只有在從
事按摩工作麼?又,為什麼按摩會成為台灣盲人的主要工作呢?當
然,這問題不能用簡單邏輯推論說,因為盲人看不見所以只好從事不
太需要視力的按摩工作。畢竟世界上多數視障者並不從事按摩相關工
作,而盲人在歷史上也曾從事過許多其他行業。另一個常見的說法
是,盲人之所以會從事按摩工作,主要是因為台灣曾受過日本統治的
緣故。可是在日治時期,台灣盲人除了不只從事按摩,還可以從事針
灸與電療。為什麼國民政府來台後,視障者會失去針灸電療工作項
目,變成只能從事按摩工作?很顯然地,「身體」與「工作」間有著非常
複雜且動態的關係。因此,本研究將運用打破人/非人、自然/社會
二元劃分的行動者網絡理論觀點,剖析現有的歷史資料以回答「為什麼
盲人會從事按摩?」此一問題。
本文所使用之資料並非來自單一研究計畫,而是在過去數年間幾
個不同題目上,陸續收集得到的訪談資料、法規檔案資料與次級資料
等。由於台灣最早的盲人學校與視障者職業訓練是由英國傳教士甘為
霖在台南所創辦,因此在探究這段歷史時主要依賴南部基督教會所保
留的史料 1。傳教士的記載主要是與宣教有關的內容,不過正是這些記
載「促動」了西方世界,使其持續不斷投入人力與資源試圖改造當時台
灣盲人的處境。因此就本研究目的而言,教會史料對認識這時期視障
工作網絡的建立過程是恰當且重要的。日治時期部份的資料則比較豐
1 目前南部教會共有四套彼此相關的史料系統,可供參照比對,即《使信月刊》(The Messenger)、《台南教士會議事錄》(Handbook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South
Fomosa)、《台灣教會公報》,與《南部大會議事錄》。
台灣社會研究 第八十三期 2011年8月008
富多樣,除了官方文獻檔案、統計調查資料 2外,還有方志報紙 3、時人
著作、文學作品、民間歌謠 4、傳記、回憶錄、期刊論文、訪談資料
等。國民政府時期部份主要次級資料來源為立法院公報、法規資料、
新聞媒體報導與訪談資料。為了瞭解視障者親身的工作經驗,本人過
去幾年間曾透過介紹訪問過六、七位在日治與國民政府兩個時期工作
過的視障按摩師,地域分佈南北都有。為了瞭解其他相關專業人員與
視障按摩師的互動,本人也曾訪問過十餘位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
師、中醫師,以及中青代的視障按摩師。這些訪談取樣多數是靠人際
網絡關係覓得,而不是很有系統的抽樣。不過訪談後都經過與其他資
料的交叉比對,因此這些訪談資料仍有一定的可信度。透過廣泛蒐集
相關資料,加以比對、整理、分析,本研究儘可能將其置回當時之歷
史情境脈絡,找出其中的因果關係,以理解台灣視障者工作百年來的
演變及其意義。
損傷/障礙二元論
在身心障礙領域中,「醫療模式」(medical model)一直是「障礙」
(disability)的主要論述,也就是認為損傷才造成障礙者工作能力或社會
功能的喪失,將個人疾病或外傷所造成的損傷(impairment)視為障礙
的主要原因。不過,實際上許多障礙問題是找不到生物醫學的病因,
也沒有任何相對應有效的治療手段。許多身心障礙者其實只是被隔
離,醫療人員扮演的還是社會控制者的角色。這種論述一直到1970年
代,西方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出現後才開始受到挑戰。最早出現於英
2 官方文獻主要以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所典藏之台灣總督府檔案、台灣總督府專賣局檔
案、行政長官公署檔案為主。國家圖書館台灣分館之「日治時期統計檔案」資料庫有
各類型詳細的統計資料可供查詢比對。
3 如《台灣日日新報》與《台南新報》等。
4 如王順隆製作的閩南與俗曲歌仔冊全文資料庫。
009為什麼馬殺雞?
國的「社會模式」(social model)將損傷和障礙區分開來,認為前者指肢
體、器官組織或身體機能有缺陷的狀況,而後者則指社會制度或組織
所造成的限制或不利地位。身體的損傷與病痛雖然需要醫療來介入處
理,但是「障礙」卻不是個人損傷的必然結果,而是制度、環境和態度
的排除與壓迫所造成(Barnes 1991;Finkelstein 1980, 1981;Oliver 1990,
1996)。
Vic Finkelstein(1980, 1981)根據馬克思的歷史唯物史觀,將身心
障礙者的處境依生產模式的轉變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是農業或小規
模工業時期,這時期的生產工具較為小型易於攜帶,能夠針對使用者
的身體特徵來加以修改調整。工作地點以家庭或社區為主,勞動型態
重視團體合作。因此身心障礙者即使未能完全參與社會生產活動,但
基本上不會被隔離於社會之外。第二階段為資本主義快速發展階段,
快速的工廠步調、嚴格的紀律管理、獨立的機器操作等以非身心障礙
者為主的生產工具和生產關係,都使得現代身心障礙者再也難以參與
生產活動。身心障礙在這時候開始成為社會問題,救濟院、收容所、
特殊學校等隔離機關於是出現。Finkelstein認為唯有到第三階段,身心
障礙者在新科技和專業人員的共同合作下,才能達到解放的目標,不
再被社會隔離。其中Finkelstein(2001)特別寄望於電子科技的發展,他
認為工業革命將身心障礙者排除於工業生產之外,現代的電子革命則
能讓身心障礙者重新回到職場。當然,Finkelstein的唯物史觀對資本主
義出現前的社會的描述過於簡化,且對未來科技的發展也過於樂觀。
社會模式的出現,可以被視為是對長期主宰身心障礙的「醫療模
式」的一種反動。為了與生物化約論對抗,損傷與障礙二元論是整個身
心障礙運動的政治與理論核心。損傷與障礙的兩極劃分,頗類似過去
女性主義者對性(sex)與性別(gender)的區別(Oakley 1972)。如同過去
女性主義讓許多同志能夠站出來一樣,社會模式也使得身心障礙者能
以全新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處境,把注意焦點從自己的身體轉移到社會
台灣社會研究 第八十三期 2011年8月010
制度與態度上。這個時期的激進的社會模式支持者即使私底下體認到
「損傷」的影響,公開場合也仍要堅定主張「障礙全是社會造成的」,而
不願說「障礙是社會和身體共同造成」。由於我們不可能清楚的劃出身
體與社會的,或者損傷與障礙的界線。在權力爭奪的過程中,一旦承
認損傷有某程度的影響之後,整個防線就很有可能全面潰堤。因此,
社會模式不論作為一種政治策略或理論分析,身體或損傷幾乎都是被
「存而不論」的(Hughes and Paterson 1997;Shakespeare and Watson
2002)。不過,將身體卻「存而不論」,某程度來說,等於是默認「損
傷」屬於醫療詮釋範疇。所以,當社會模式將身心障礙者的社會生活政
治化時,他們的身體卻繼續被醫療化。身體被化約為損傷與疾病,與
社會政策或政治無關,而被繼續交由醫療相關人員處理(Hughes and
Paterson 1997)。
「損傷」的社會建構
不論是疼痛、損傷還是障礙,其實都不是單純的生理現象,而是
身體與社會文化交相形構而生的歷史產物(Bendelow and Williams
1995;Foucault 1979, 1980;Hughes and Paterson 1997)。過去女性主義
也曾對性/性別做區隔,但是在 Jacques Derrida與 Judith Bulter等的批判
下,早已不再持此二元論的分法。同樣的,損傷/障礙的區隔在後結
構主義者與後現代主義者的批評下,也逐漸在身心障礙研究中失去其
立足點(Corker 1999;Shakespeare and Watson 2002;Thomas 1999)。社
會藉由各種途徑不斷在調整、控制和監視我們的身體,以及身體間的
關係,並且不斷的重新建構、生產和改造我們身體的能力。
過去異常身體充滿了神祕色彩,如報應惡兆、上天懲罰、巫術施
行等的結果或象徵。十八世紀科學興起後,這些神祕色彩逐漸降低,
異常身體才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從長頸鹿到獨角鯨,從侏儒到連體
011為什麼馬殺雞?
嬰,都被當作是大千世界多采多姿的證據(Thomson 1996)。在學界、
娛樂界和政府的推波助瀾下,當時西方的馬戲團、動物園、博物館等
經常上演「怪胎秀」(freak show),其中許多表演者在今天看來都是「身
心障礙者」。這時也有許多「有色人種」會被帶到歐洲和美國去展覽,
這種身體展示在十九世紀達到最高潮(戴麗娟 2004)。到了1940年代,
如火如荼的優生運動、持續不斷的大陸探索,以及逐漸穩固的醫療帝
國,使得西方的怪胎秀逐漸式微。不過「怪胎」的論述並沒有消失,只
是舞台移轉到醫院、教科書和標本室,異常身體不再是眾人驚嘆的「奇
觀」,而是社會必須予以清除的「錯誤」(Thomson 1997)。
人類社會為了否認生命不完美這個事實,將這種連續性的差異轉
化成兩極化的類別—障礙者與非障礙者。障礙者被區分出來成為社
會敵意的對象,他們的身體需要治療、隔離、懲罰、滅絕,以平撫社
會的焦慮與恐懼。至於哪些人會受排除,或者有多少人會受到排除,
則往往隨著時代不同而改變(Shakespeare and Watson 2002)。「身心障
礙」是個複雜、異質、多變的後現代的類屬,其本質上是社會建構與關
係性的產物,要給身心障礙找出共同特質或核心定義是不可能的。不
同時代或不同社會,對身心障礙的界定方式會有所不同(Bolt 2005;
Bury 2000;Hahn 1993;Shakespeare and Watson 2002)。社會建構論在
呈現身體是社會與歷史的建構的同時,將損傷的生物本質論(biological
essentialism)轉變成論述本質論(discursive essentialism)。社會建構論否
定主體的自由意志與動機,身體或損傷只是社會利益與需求投射的結
果,而這些利益或需求背後的權力關係才是真正的社會現實(Hughes
and Paterson 1997;Turner 1984)。因此,身心障礙研究在找回「身體」
的過程中,身體雖然脫離生物醫療的範疇,卻成為缺乏能動性和主體
性的虛無幻影。
台灣社會研究 第八十三期 2011年8月012
ANT的行動本體論
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簡稱ANT)的本體論觀點
介於實證論的「醫療模式」與建構論的「社會模式」之間。ANT主張不論
是「人」(如個人或團體)或「非人」(如工具、機器、技術、微生物或建
築物等)的能力或特性都不具先驗的本質,而是在網絡中被促動
(enacted)出來的結果。行動者共同參與網絡的創造與維持,協商出彼
此都能接受的角色身分、互動模式與行動策略,也因此決定了彼此的
存在與屬性。在各種行動者的行動與連結過程中,社會與個體同時萌
生。而不是像醫療模式所認為的,個體的損傷導致其社會位置與存
在。也不是像社會模式所主張,個體的存在是由社會結構或價值觀所
決定。由於行動者可能同時處於數個不同的網絡之中,任何網絡中的
變動都會牽動其他網絡中的行動者,因此行動者隨時處於極端不確定
的狀態(林文源,2007;Latour, 1983/2004;Callon, 1999)。在ANT的
本體論觀點下,現實無法不經人為介入而被認識,現實也並非外在於
人的介入而存在。不論自然世界還是社會世界的實體,都是需要經過
中介者(intermediary)才能出現其本體論歷程(ontological passage)中某
階段的相對穩定存在(Mol 1999)。
在Callon (1986)干貝復育的研究中,三名海洋科學家試圖建立由
他們和漁夫,以及干貝胚胎共同組成的網絡。但是海洋科學家不可能
觀察到當地所有的漁夫和干貝,必須透過參與會議的漁夫代表和著床
的干貝胚胎來判斷網絡建立是否成功。因此參與會議的漁夫代表和著
床的干貝都是一種物質符號(signifier),分別指涉了他們所代表的當地
所有漁夫與甘貝。如同文本符號是在符指鏈(chain of signifiers)中歷經
衝突與挑戰才逐漸穩定下來,物質符號也必須在具體行動與試煉中被
檢驗。漁夫代表代表了當地的干貝漁民、著床的干貝胚胎則代表St.
Brieuc灣的所有干貝。該網絡是否成功建立端視這些代表是否具有代表
013為什麼馬殺雞?
性,海洋科學家以收集器來讓干貝胚胎著床繁衍生存,以長期利益說
帖來讓漁民暫時禁捕。如果這些行動者願意留在網絡內,依共同的目
標前進,這個網絡便算成功建立,海洋科學家便能以期刊論文和會議
報告來讓科學社群知道說:他們成功地將日本的帆立貝養殖技術移植
到法國。這種根據行動者在符指鏈中的相對關係來確定其性質的分析
方式,有時也被稱為物質符號論(material semiotics) (Law 2007, 2009a,
2009b)。
在ANT的分析取徑中,不論是「人」或「非人」行動者的特性與能
力是在網絡相對關係來形成,而非被動地由社會結構或制度文化所決
定。因此ANT的分析焦點在行動者,而非社會結構。過去社會學所宣
稱的那個「先於且外在於個體、對個體有強制力」的社會結構,只能透
過不斷的中介與位移相互混雜之後,才能影響網絡中的行動者(Callon
1991)。比方「政府」這個社會制度本身是抽象的,它的具體作用必須
透過建築物、政府官員、制服配備、文書資料等中介物才能發揮影
響。也因此,ANT打破了損傷/障礙、身體/心理、自然/社會的疆
界,因此能顯現出其間複雜交纏的關係。網絡研究者不去判斷網絡行
動者的觀點或立場,而是承認實體的多重存在。研究者的主要任務就
在於追蹤轉譯過程中行動者的轉變,探究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各種事實
的萌生過程(Law 2004;Latour 1988;林文源 2007)。
傳統盲人工作
在西方旅人與傳教士的眼中,傳統漢人社會裡的盲人多以苦力、
算命、說唱或乞討為生。十六世紀中Galeote Pereira、Fr. Gaspar da
Cruz、O.P.、Fr. Martín de Rada、O.E.S.A.來到中國南方省份,他們看到
當時男性盲人從事推石磨之類的工作,女性盲人則常淪為娼妓,另外
在城市中常會見到的盲人乞丐。十九世紀中,美國傳教士 Justus
台灣社會研究 第八十三期 2011年8月014
Doolittle(盧公明)於1849年到福州市,在他的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書
中也提到多盲人算命師和乞丐(Doolittle 1868)。傳統中國盲人也靠唱
盲人調來謀生,這些盲人甚至組成紀律嚴明的自治組織「三皇會」,處
罰違反幫規的盲人(永井彰子 2002;Gamble and Burgess 1921)。
有人也許會問,這些紀錄是否反映當時盲人「真實」的生活?由於
在ANT的分析取徑中,並沒有先驗存在的實體,因此這問題並不存
在。不論社會還是自然的「實體」都是被「做」出來的,因此沒有所謂盲
人「真實」的生活面貌,只有盲人「被觀察到」或「促動」的生活面貌。
如前所述,ANT的本體論意義下,論述行動與被論述的現實也是相互
混雜的,傳教士和旅人並不是客觀地描述台灣社會的盲人,而是透過
這些中介手段來穩定它們所創造出來的「傳統漢人社會的盲人」。也有
人會問說,那麼為什麼要用西方傳教士的紀錄,而不用漢人社會自己
的觀察與記載呢?「傳統漢人社會的盲人」的確不會只有一種存在,不
同的觀察紀錄會產生不同的實體存在。但是這些以歐美支持者為對象
的作品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促動西方社會對「傳統漢人社會的盲
人」採取行動,以致形成本文所感興趣的「新台灣盲人」。
在天津條約開放港口之後,基督教開始進入台灣。英國長老會牧
師甘為霖(Rev. William Campbell)於1871年12月抵達台灣。根據他的
記載,當時台灣的盲人有的做生意、從事小買賣,有的做踏水車、搗
米等苦力工作,有的是靠走唱、算命、乞食維生(Campbell
1915/1996)。甘為霖在1887年例假回英國,整理出版「台灣佈教之成
功」為盲人籌募教育經費。甘為霖說他曾經碰到一名「看起來很聰明,
但兩眼空洞的」盲人,該名盲人「十多年前在附近鄉下路,有五、六人
從樹籬跳出來就拉他倒地,抉去他的兩眼。據他說約有100人就是這
樣的被⋯⋯惡霸抉去兩眼。」5 這件事引起甘為霖很多英國朋友的同
5 《台灣教會公報》1953期,1989年8月6日。
015為什麼馬殺雞?
情,後來甘為霖獲得格拉斯哥自由教會學生傳道會(Free Church
Students Missionary Society)及英國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等的捐助。1891年9月12日甘為霖在台南市二老街口(今衛民
街北門路口),租用洪公祠(Angkongsu)創立台灣第一所盲人學校—
「訓瞽堂」。甘為霖於1893年記道:
近來有加(多)設一項的法度來幫助這裡的艱苦人,他們簡單(kan-
ta,只有)識字是不夠額(不足),要緊著有什麼工作給他們通賺食
(than-chiah,謀生),若是無,本地的青盲人差不多攏總得去做乞
丐或是學算命。好佳哉(Ho-kai-chai,幸好),余醫生娘對祖家
(cho-ke,祖國)轉來,獻出真體貼的心,伊請青盲學生逐日到新
樓,拇那(m-na,不只)教他們讀冊寫字、算帳,擱教他們織
(chhiah,編織)掩頸帶(am-kun-toa,圍巾)。他們已經熟手,會快
快學織別物,親像帽仔、手束(chhiu-sok,手臂套)、袈仔(kah-a,
背心)、裳(sa,衣服)、襪仔。
現時那間青盲學有八個學生,他們也在學幾那項(好幾項)的手
藝,像是打網(phah-bang,編織魚網),索錢捲(so chi-kng,搓製
串銅錢的繩子)。阮不止(put-chi,非常)向望兄弟姊妹有時想念那
些青盲人,在咱中間已經有二、三十個,教會外面是全然多,因
為每一個所在攏有青盲人。咱若不求上帝替他們開一條路,走到
路尾(lo-boe,最後)他們的心會真黑暗,更加悽慘。(張妙娟
﹝1999﹞,黑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訓瞽堂為貧苦盲童免費提供書本與住宿膳食,當時安排的課程包
括聖經、點字、算帳、編織、製繩、作魚網等手工藝以及刻鑿凸字技
巧等。甘為霖給盲人安排的職業訓練課程,與當時西方傳教士在非西
台灣社會研究 第八十三期 2011年8月016
方社會提供給盲人、女性、貧民的課程內容相仿 6。雖然當時招募到的
盲生不多(只有八個),但是相對於「沉默」、「沒有聲音」、「未被觀察
到」的「一萬七千餘名盲人」而言,這八名學生就「代表」了台灣全體盲
人參與甘為霖所建立的網絡—不僅代表了男性視障者,也代表了女性
視障者—打造出台灣盲人的新身體、新技能與新面貌。不過,後來甘
為霖發現這些手工藝工資甚低,盲人畢業後根本無法獨立養活自己(甘
為霖 2006;Campbell 1915/1996)。訓瞽堂後因財務困難,於1897年3
月底將所租洪公祠歸還厝主而停辦 7。
當然,網絡建立的失敗並不是在歷史上就不會留下任何痕跡,也
並非表示對後來盲人的發展毫無影響。即使是成功建立的網絡,也不
保證可以持續維持原來的目的和功能。如同Callon(1986)干貝復育的
研究中所看到的,網絡中的行動者處於極端不確定(radical
indeterminacy)的狀態,在這個交互影響的動態過程中,行動者的能
力、特性、利益或興趣都不斷地被重新界定、安排和賦予。甘為霖所
創辦的學校、訓練過的盲人、以及經過一連串嘗試與失敗後自身也被
轉變的甘為霖本人,在往後台灣視障按摩網絡的建立仍扮演若干角
色。下節便是要繼續追蹤這些行動者在後來故事進行中的轉換。
日本統治時期
1895年4月17日台灣澎湖被清廷割讓給日本,同年10月21日日軍
進佔台灣府(台南)。隔年(1896年)甘為霖前往東京度假時,受邀拜訪
時任文部省大臣(同時也是台灣第一任總督)的樺山資紀男爵。甘為霖
希望樺山男爵能夠協助拓展盲人教育工作,於是樺山男爵寫封信給當
時負責台灣事務的兒玉源太郎子爵,讓甘為霖帶回來給他。1900年台
6 這點感謝王秀雲的提醒,也請見郭衛東(2005)的記載。7 《台灣教會公報》第1955期,1989年8月20日。
017為什麼馬殺雞?
南官方以縣令第二十五號指定「台南慈惠院」(今私立台南仁愛之家)附
設教育部接辦「訓瞽堂」,並將學校移至於台南文昌祀(今岳帝廟),改
稱「盲人教育部」(吉野秀公1997) 。1902年8月公布「鍼灸術按摩取締
規則」,原本一直在台灣民間本島人從事的一種「掠龍骨」的按摩便無
法再公開營業 8。1905年台南慈惠院制定盲生教育規定,分五年制普通
科和三年制技藝科,普通科的課程包括修身、國語、算術、體操、唱
歌等,到第三年才開始學習日式按摩,技藝科則授予日本按摩術(劉寧
顏1994)。台灣盲人在日本老師的教導下,開始學習新的生活技術。
不過,甘為霖認為按摩在日本是盲人的傳統行業,且日本人已經
習慣求助治療按摩,所以日本盲人才能夠藉此謀生。當時來台定居的
日本人不多,本地人對按摩也還陌生,因此台灣盲人並無法靠按摩來
獨立生存。由於當時台灣公學校的入學率 9,完成六年基礎教育者為數
甚少,能進入盲校就讀的視障者的教育程度算是相當的高 10。因此甘為
霖曾建議日本政府,讓受過教育能說流利日語的盲人,在日本政府部
門從事翻譯工作,不過並未被當局採納(Campbell 1915/1996)。1905年
「臨時台灣戶口調查」的統計顯示,當時全台15582名盲人中有9359人
從事農林漁牧業(佔60.0%),而無業者僅381人(佔約2.4%)11。也許從
日本政府的角度來看,台灣盲人失業的情況並不嚴重。甘為霖也曾嘗
試引進當時英國曼徹斯特(Manchester)專為盲人設計的紡織機器,不
過這些努力都沒有成功(Campbell 1915/1996) 。
1915年,台灣第六任總督安東貞美撥款25000圓予台南慈惠院,
在台南壽町一丁目(今台南啟聰學校現址)闢地興建校舍,增設啞生部
並更名為「私立台南盲啞學校」,盲生部課程傳授針炙與按摩。1922年
8 〈台北の鍼と按摩〉,《台灣日日新報》,1905-03-09(明治38年),第五版。9 1918年公學校的學生就學比例仍僅15.7%(山崎繁樹、野上矯介 1988)。10 許多受訪的視障者也都提到,他們的教育程度是兄弟姐妹中最高的。11 臨時台灣戶口調查部(1908)《臨時台灣戶口調查結果表》,明治四十一年。
台灣社會研究 第八十三期 2011年8月018
「私立台南盲啞學校」由台南州政府接辦,改名為「台南州立盲啞學
校」,分普通科、技藝科與專修科,盲生部之技藝科與專修科設「鍼按」
分科(劉寧顏1994)。普通科招收對象是八歲以上盲生,專修科為十五
歲以上的學生,入學申請書必需附上戶籍抄本或是戶口調查簿抄本 12。
當時盲生鍼按科畢業生即可開業,不需經過考試即有檢定資格。生於
1915年的楊老太太,於12歲時到台南盲啞學校就讀,她回憶道:
那個警察都找說,你看不到,你要來盲啞學校讀書這樣。⋯⋯日
據時代那個管區的警察,如果他們那區如果有看不見的,他就會
叫盲啞學校的老師來鼓勵我們去讀書。13
⋯⋯
在四月一日的時候,父母就帶我們入學,入學時在父母要回去的
時候,大家都會不想留在學校就哭成一團,老師就會來說沒關
係,妳們就必須留在這裡唸書,以後才會有工作,不唸書的話日
後妳們怎麼生活。老師就來跟我們說,父母都已經回去了,妳們
就在這裡好好唸書。14
1917年6月25日,日人木村謹吾醫師於大稻埕木村胃腸醫院內設
立「木村盲啞教育所」,自日本聘請針灸按摩教師來台任教。1918年招
收盲生20名(台籍16名,日籍4名),台籍兒童依照公學校令實施教
學,日籍兒童則依據小學校令實施教學 15,並教授中年盲人簡易按摩。
1920年8月30日遷至西門外,改稱為「私立台北盲啞學校」。當時盲生
12 台灣總督府報第3159號(大正十三年)1924年2月10日,第39頁。府報第3460號(大正十四年)1925年3月1日,頁2。
13 2006年4月6日訪談紀錄。地點:高雄縣鳳山市。14 2006年4月21日訪談紀錄。地點:高雄縣鳳山市。15 〈盲啞學校計畫 盲啞教育部現狀〉,《台灣日日新報》。大正七年(1918年)3月7日。
第七版。
019為什麼馬殺雞?
部分為普通科、高等科及技藝科,技藝科又分鍼按科(四年)、按摩科
(二年)、音樂科(六年)及按摩專修科(二年)(吉野秀公1997)。當年
的教員包括校長木村謹吾、普通科木村八重、鍼按科星小七、技藝科
林文勝、音樂科郭氏在等。收容的盲生有28名(台籍14男8女,日籍5
男1女)16。1921年出生台北的陳老先生,當時是由普通學校老師轉介到
台北盲啞學校就讀,他在訪問時描述其過程:
問:你剛開始是讀普通學校?
答:對!
問:讀了幾年?
答: 大約一年而已。讀一年級而已。後來就不行了。⋯⋯剛開始
唸小學的時候,老師寫黑板都看不見,老師就想說,就說這
樣也不行啊⋯⋯你眼睛既然不好了,你就去讀盲啞學校。17
台灣的視障者由傳統農村的勞動者,逐漸轉變成現代都市的針灸
或按摩工作者,這是一連串的徵召、說服、連結運作之後所產生的結
果。日治時期警察在衛生事業上具有強制性極高的執行權力(范燕秋
1994),警察和盲校教師們以威脅 (如:「你們不會講日文就沒有用」)
和利誘(如:「來了以後生活會很好過」)的手段,誘使盲人離家到學校
就讀。當然,並不是所有的視障者都會被警察所發現,被發現的視障
者也不一定能夠離開家到遙遠的學校去就讀,盲人及其家長可能抵抗
(resist)也可能順從(give way)。學生家境狀況不佳不願就學時,校方還
必須補貼學生學費或生活津貼,他們才願意來就讀。不過,到學校就
讀的也不一定會順利唸到畢業,畢業後的視障者也不一定會成為理療
16 〈認可となつた盲唖学校 木村盲唖敎育所來月二日から改稱〉,《台灣日日新報》。大正九年(1920年)10月8日。第二版。
17 2006年4月20日訪談記錄。地點:台北市。
台灣社會研究 第八十三期 2011年8月020
師。由於女性較不願意從事按摩這工作,到盲校就讀的男性一直多於
女性。最後畢業時,家庭經濟地位較有困難的女性視障者才會從事按
摩這項工作。當楊老太太被問到同學的情況時表示:
問:你們當時班上有幾個女生?
答:當時男生較多,一個年級16人,女生只有兩三個。
問:畢業後都出去按摩賺錢?
答: 對,(除非)畢業後你的父母不要你去做,就不用(去按摩),
不是每個都去做呀。我剛畢業幫人按一次才五角⋯⋯
問:有沒有人畢業後沒去賺錢?
答: 有,她爸爸是水泥會的什麼,賺很多錢。(她是)女生,所以
就叫她不用按摩。18
日治初期來台日人不多,而本地人對按摩尚陌生,因此一開始盲
人的確難以仰賴按摩維生。加上當時在台灣掠龍(日治後才稱作按摩)
和剃頭、娼女一樣屬於「下九流」的行業 19,因此特別是一般人並不是特
別喜歡從事這項工作。隨著日人來台漸多,台灣社會上按摩的需求也
逐漸增加。1912年台灣視障者從事按摩術者有74人,其中有少數盲人
開始從事鍼灸工作 20。到了1923年,全台從事按摩工作人數已達440
人,其中台籍者占絕大多數,但是從事針灸者仍以日籍者居多(台籍
21人,日籍90人)21。1924年府令第二十號發布「按摩術營業取締規
則」,將按摩術(Massage)、柔道整腹術、接骨術等諸營業許可統歸併
18 2006年4月10日訪談記錄。地點:高雄縣鳳山市。19 根據時任台南地方法院檢察局通譯官片岡巖 ,所完成的《台灣風俗誌》(1921),娼
妓、戲子、巫者、吹鼓手(喪葬樂隊)、牽豬哥、剃頭、婢僕、掠龍(按摩師)、土公
仔(抬棺、撿骨者)在台灣屬於「下九流」的行業。
20 《台灣衛生要覽》(大正十四年),頁115及頁155。21 《台灣衛生要覽》(大正十四年),頁115及頁155。
021為什麼馬殺雞?
於該規則管理。根據1930年的統計,台人從事按摩者有310人,推拿
35人,柔道整復術1人,接骨13人(佐藤會哲 1932)。接骨業者為該令
施行前所許可者,取締規則公布後新加入者一概不為允許。當時日本
人對待「按摩師」的方式和台灣人是不一樣的,1921年出生的陳老先生
回憶道:
以前我們幫日本人按摩,去(他們)就很有禮貌,他們也是叫你先
生啊!日本人說先生就是老師的意思⋯⋯日本人叫我們就是先
生,叫按摩的先生(日語)⋯⋯真的先生(日語)⋯⋯ 他們會這樣
稱呼我們,那個時候受人尊重,那個地位,做這個行業的地位高
很多,光復以後才整個變差。22
日本的視障者能夠從事針術工作,除了歷史淵源外,和日本針術
所使用的針具也有關(中山太郎 1934)。傳說戰國時代一名失明的琵琶
樂師明石覚一(西元1299-1371),除了音樂之外也精通針灸按摩術,曾
治癒過後醍醐天皇的腦疾,因而被認為是盲人與針灸按摩的關聯的開
端。到了德川幕府時期,盲人針灸師杉山和一(1610-1694)發明「管鍼
法」這種獨特的進針方式之後,盲人與針灸工作的連結真正的確立。這
種針法所使用的針較細、較短,進針較準確,也比較不會造成疼痛,
因此頗適合盲人使用(肖永芝 1999; Kobayashi et al 2008; Mestler 1954)。
後來杉山和一的弟子們紛紛被引薦至幕府、將軍府等各地擔任針灸
醫、按摩醫。杉山和一也創辦盲人學校(杉山流鍼治導引稽古所)來傳
授針灸、按摩技術,因而在日本被視為盲人針灸按摩工作地位確立之
始祖。
根據1924年公佈的「針術、灸術營業取締規則」,從事針術、灸術
22 2006年4月20日訪談記錄。地點:台北市。
台灣社會研究 第八十三期 2011年8月022
者必須「通過知事、廳長所實施的針術、灸術考試者,畢業於指定校、
講習所者或是依內務省令針術、灸術營業取締規則而持有資格者」,當
時的指定校為台北州立盲啞學校、台南州立盲啞學校(佐藤會哲
1932;丸山芳登1957)。到了日治末期,按摩和用針在台灣一般人心目
中似乎已經相連在一起的,比方在王順隆製作的閩南與俗曲歌仔冊全
文資料庫中,台灣歌仔戲詞中便出現「叫掠龍來用針」23這樣的說法。
在日治時期曾從事針灸工作的陳老先生回憶道:
問:當時有沒有用針?
答: 有ㄚ,我自己在針,針都不會痛。中國用的針像縫布袋一樣
粗,日本用的非常細,就是現在用的針,是銀線,銀的。用
酒精消毒針和手,保持衛生。
問:按摩的客人是不是比用針的人多?
答:當時顧客日本人多,多為了按摩,只有病人才用針。24
昭和十五年末(1940年),台灣從事針術者有325人,灸術者308
人,從事按摩業者也有587人(丸山芳登1957)。根據栗山茂久(2006)
的「肩凝考」,日本從江戶時代(1600-1868)開始流行一種稱為「肩凝」
(かたこり)的症狀 25。這種症狀主要靠腹診與按摩作為診斷與治療的手
段,在其他文化或地區都沒有相對應的概念。「對於患者來說,時常在
診斷時或按摩時受到的觸摸,養成他們對體內鬱結的高度自覺性」(栗
山茂久 2006: 64)。此外,從日本江戶時代中期便開始流行的「按摩
23 《337冊 暢大先痛後尾歌》,新竹:竹林書局。24 2006年訪談記錄,訪談地點:台北市。25 江戶時代也是日本按摩復興的年代,前面提過的杉山和一就是在這個時期建立世界
上第一所特殊教育學校 — 「杉山流鍼治導引稽古所」,專門訓練盲人從事針灸和按摩工作,許多該所畢業的視障按摩師成為德川幕府的醫療人員。感謝雷祥霖關於「肩
凝考」的提醒,詳見栗山茂久(2006)。
023為什麼馬殺雞?
笛」26, 在電話普及之前也出現在台灣。當時台灣的盲人在夜裡持著三
孔短笛,吹著個人獨特的曲調,在一定範圍內沿著固定的路線行進,
這種招攬生意的方式和十九世紀末日本盲人吹短笛沿路提供按摩服務
是相似的(Mestler 1954)。台灣吟稿合刊詩報社在1941年於《詩報》以
「按摩女」為主題所收錄的七言絕句中,多數都會提到盲人在夜裡吹短
笛這件事 27, 以及按摩所會產生的身體影響 28, 可見按摩在當時已經普
遍為台灣文人所熟悉。至此我們可以看出,日治時期的新「台灣盲人網
絡」已然成形,這個網絡一開始是由警察、教師、家長、盲人、針具、
課本、按摩笛等共同組成,才能使台灣盲人具有能夠從事針灸、按
摩、電療的能力與興趣。另一方面,台灣民眾由原本不熟悉按摩的身
體,到許多人養成的身體不舒服的自覺和按摩習慣,乃致後來人人都
瞭解傳遍街頭巷尾的「按摩笛」聲所代表的意義。這時不只是台灣盲人
被改變,而是整個社會都被轉變了。
視障者工作網絡的建立,還有個常被忽略掉的因素,就是日本殖
民政府對漢醫和民俗療法的管理與壓制(范燕秋 2008)。日本殖民政府
於1896年訂立「台灣醫業規則」,規定中醫應先登記方准營業(張苙雲
1998)。同年(1986年)開始在台灣任命派遣的「公醫」,其主要工作除
26 按摩笛原本的構造是由三支竹管而形成,即一支長笛(又稱男笛,可奏出音階)和兩支短笛(又稱女笛,可產生共鳴)(香取俊光 2006)。
27 例如「夜夜沿街短笛吹」(曾炳元,頁18)、「夜來市上笛頻吹」(曾思陶,頁19)、「入夜沿街一笛吹」(曾炳元,頁19)、「昏夜沿街短笛吹」(翁汝登,頁18)、「短笛沿街信口吹」(陳景崧,頁18)、「信步街衢短笛吹」(陳傳義,頁19)、「短笛無腔依口吹」(蕭泗川,頁18)、「手携銀笛夜頻吹」(吳半樵,頁18)、「笛音入耳覺身疲」(陳坤輝,頁19)等
28 如「摩人骨節便忘疲」(曾炳元,頁18)、「為君療却一身疲」(吳半樵,頁18)、「玉手能蘇民困倦」(陳攀雲,頁19)「願來賣技療人疲」(蕭泗川,頁18)、「試問誰人筋骨苦,奴家手到便忘疲」(陳景崧,頁18)、「十指纖纖摩按後,乞人沉醉不知疲」(翁汝登,頁18)、「纖手摩人鬆骨節,麻姑有爪未為奇」(陳瀠智,頁18)、「按点重輕隨客意,發皆中節自忘疲」(曾思陶,頁18)、「端憑身手起民疲,按節摩筋術自奇」(陳傳義,頁19)、「纖纖春笋麻姑爪、一着儂身便不疲」(陳瀠智,頁19)。
台灣社會研究 第八十三期 2011年8月024
了執行地方的公共衛生及醫事所相關事務之外,就是「對區內漢醫負監
督之責」(莊永明 1998: 160)。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第一任校長山口秀高
認為,「(台灣)本島之所謂『醫生』者⋯⋯他們連生理、病理為何物都
不知;最甚者,更有不識字者⋯⋯他們雖稍像內地(日本)的漢醫,卻
無法相提並論,實更為拙劣。勉強要比的話,就如內地的賣藥郎中」
(莊永明 1998: 172)。1901年頒布「台灣醫生免許規則」與「取締國醫規
則」,要求全台從事漢醫及所謂以祕方執行醫業行為者,須於同年12
月底前向警察機關登記。期限後未登記或新養成的漢醫或其他傳統醫
業者,一律不得執業,否則衛生警察將加以取締(小田俊郎 1995;張
苙雲1998)。1924年公佈「按摩術營業取締規則」,進一步將按摩、柔
道整腹術、接骨術等納入管理。規定必須經過按摩考試合格或者畢業
於按摩學校或講習所者,方得從事按摩業。當時要取得開業許可的資
格相當嚴格,沒有許可的視障者也會被取締。《台灣民報》在1928年10
月14日有則題為「南北署取締按摩 盲人叫苦連天」的新聞報導如下:
台北市南北兩署,近來對於無免許的按摩業者取締非常嚴重。若
受告發聽說罰金拘留以外,尚且要賞巴掌三數個,所以無免許的
按摩盲人多叫苦連天。據一般盲人所說,我們非不要試驗、實因
及第比登天還難⋯⋯ 其最為難者有三:一、要知全身骨骼名稱。
二、要會說日本話。三、要有教授指導者推荐(但被推荐者要被謝
金五十圓至百圓呈贈教授為謝禮)。(鄭志敏2004)
日本統治50年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將中醫或傳統醫療排除於醫
療照顧領域之外」(張苙雲1998: 170)。日本政府「切斷漢醫或國醫的傳
統、壓縮漢醫生存空間」,讓傳統醫療沒有出路、自然凋零。這些措施
當然不是為了保障視障者工作權益,但卻間接為視障者掃除了職業上
的可能競爭者,鞏固了新「台灣盲人網絡」,使得台灣的視障者才能空
025為什麼馬殺雞?
前也是絕後地從事針灸等工作。1920年代末台灣漢醫和藥種商發動
「台灣漢醫復活運動」,以及1928年所成立的「東洋醫道會」台灣支部,
雖然都企圖與日本政府所支持的西洋醫學對抗。但這些抵抗行動最終
都沒有成功,日治時期的漢醫和民俗療法從業者只好接受其他行動者
所賦予的角色。日本殖民政府於統治初期的1897年所做的調查中,漢
醫、儒醫、世襲醫者等共2116人,其後中醫人數因老衰死亡逐年減少
(張苙雲 1998)。日本統治末期台灣漢醫人數僅剩97人(台灣省行政長
官公署統計室 1946),這個數目甚至少於當時台籍針灸與按摩從業人
數。
國民政府時期
日本戰敗後,國民政府初期延續過去的政策與作法。台北盲啞學
校改名「台灣省立台北盲啞學校」,「台南州立盲啞學校」改名「台灣省
立台南盲啞學校」,兩校繼續教授按摩、針灸、電療等課程。日治時期
訓練出來的學生留校成為老師,所使用的教材也主要由日本與翻譯而
成(王育瑜1994)。北部數位受訪者都表示,當時許多黨政要員都常會
上門求診接受針灸治療。南部雖然較少這種情形,但是光復後部份視
障者仍繼續從事針治工作。1927年出生的張老先生,十歲到台南盲啞
學校就讀,十七、八歲開始學針灸時台灣已經光復。他回憶當時工作
情形時表示:
問:你當時有在做針灸嗎?
答: 說我出來就在做針灸啦!⋯⋯他(日本)這個針做的很好,阿
我們台灣做的針我不敢針灸⋯⋯因為它(針)很長很粗⋯⋯
問:你剛開業的時候,什麼類型的客人比較多?
答: 那時候來的客人有生意人阿,也有普通在工作的人,做那個
台灣社會研究 第八十三期 2011年8月026
也有啦、工作的,也有女人。有的像說工作過度酸痛的也有
啦!都是酸痛的比較多⋯⋯
問:嗯。
答:在過來有的是疲勞、感冒啦!
問:嗯。
答: 什麼、什麼、什麼,有那個、那個輕微的那個、那個風濕痛
啦齁。
問:嗯。還有治療過什麼其他的毛病嗎?
答:有,我治療過那個小兒麻痺的。29
由於台灣本地的中醫長期受日本壓抑,因此熟悉針灸者不多。加
上當時台灣尚未有物理治療這門專業,因此盲校鍼按科畢業生的技能
在社會有一定的需求。1950年代的報紙曾報導云:
台灣全省現有一萬四千四百多個盲人。能靠一技之長自食其力的
不過一千七百人。他們的職業包括按摩、命卜、道士、賣唱、電
療、和極少的務農、經商以及教員。其中以按摩和命卜的人數最
多,收入則以電療和(按)摩較好,其他的職業祇能換得維持最低
生活的收入。(薛世儀 1958)
不過,國民政府開始解除日治時期對中醫與密醫禁令,開放傳統
中醫之行醫與中藥的使用,對密醫與民俗療法則採半開放政策(吳基福
1980;張珣 1983)。因此光復後台灣視障者從事針灸或電療工作的能
力,便逐漸受到新的挑戰與威脅。1921年生,家住台北的陳老先生回
憶道:
29 2004年訪談記錄,地點:高雄市。
027為什麼馬殺雞?
光復以後,治療所就變成說有人常來找麻煩,說像你們這種是盲
人學校畢業的,是個瞎子怎麼會這種什麼的,說那什麼話!我們
可是有執照的,不然你看看,就這樣鬧到衛生局那邊去,他們就
開會,開會完就說,已經在做的人就繼續讓他做,要新開店的人
就必須要考試這樣子。因為就是這樣雖然我還在做,但是生意卻
沒辦法很好,大家都跑去找中醫,沒生意我才收了才改成按摩院。
1927年生,家住高雄的張老先生也說:
人家日本有在相信這個針的,阿我們這些那個、我們這裡的中國
人就沒有咧!⋯⋯他這邊會說,阿你這個眼睛看不見的不會針灸
啦!⋯⋯說什麼就要申請中醫師執照啦!中醫考試⋯⋯就沒有在
給我們信。我就氣到,我就沒有去申請。⋯⋯沒有申請啦!不要
這麼麻煩啦!
國民政府要求日治時期取得證照的視障理療師重新領照,其實很
類似日本殖民政府來台時對傳統醫療所採的漸禁政策。不同的是日本
所要限制的是傳統醫療工作者,而國民政府所要限制的是視障理療
師。雖然國民政府對未登記者並不會強力取締,但學校教育及相關制
度上的限制,仍則使得視障者的工作範圍和內容逐漸縮小。另一方
面,前面提到過網絡的建立過程中,競爭者的排除對網絡的建立是重
要的。在國民政府來台後,視障者原有的工作網絡秩序開始受到新出
現的競爭者挑戰。
1950年代台灣接受大量來自美國的金錢、物資的援助,同時也自
美國引進醫療和公共衛生的技術與體制,一個新的美援醫學逐漸浮現
(傅大為 2005)。當時正值小兒麻痺大流行,歐美的物理治療人員先後
來台訓練物理治療人員,其中多為當時駐台美軍的眷屬自願義務輪流
台灣社會研究 第八十三期 2011年8月028
至台灣各大醫院協助治療小兒麻痺患者(莊永明 1998)。1957年10月
23日台灣省政府警務處頒布「台灣省各縣市按摩業管理規則」,其中第
二條規定「凡從事按摩業者,需雙目失明」,且該規定第五條第三項並
規定「按摩人除按摩施術外,不得執行醫業類似行為」。1958年,中國
醫藥學院(今中國醫藥大學)成立,開始了台灣中醫正式的學校教育。
1963年台大醫院成立物理治療部,同年復健大樓在美援補助下完工落
成。1964年台灣省醫師公會給立法院的請願文中,關於限制醫師資格
部分表示「我國醫師⋯⋯身體殘障者也從事醫療工作,這應列『缺格』
禁止行醫」(吳基福 1980: 106)。1967年,台大醫學院在世界衛生組織
協助下於醫事技術學系下成立物理治療組,開始了台灣物理治療的大
學教育。1967年新「醫師法」修正公布,視障者被禁止從事針灸與電療
等醫療行為,盲校的相關課程也被迫取消。1973年「殘障福利實施辦
法草案」中將按摩訂為視障者的保障行業的法條,在行政院審查時遭刪
除。當時行政院的理由是「按摩是物理治療的一個項目,按摩醫療非盲
人所能勝任」。
1979年「殘障福利實施辦法草案」再次送交立法院審議,又重新放
回被行政院刪除的「非本法所稱視覺障礙者,不得從事按摩業」之條
文,這次加上了但書「⋯⋯但醫護人員以按摩為病患治療者,不在此
限」。因此此條文在二讀、三讀時均照案通過,未再遭到刪除。同年7
月16日在立法院所舉行的座談會中,台灣盲人重建院代表林幸夫曾提
議「已取得先進國家之針灸、按摩、物理治療等立案機構結業證書、及
國家考試合格資格之證明者,政府應准予營業」(周建卿,1992)。然
而台灣醫界對視障者的能力充滿不信任與歧視,不斷透過政府立法與
政策,限制視障所能從事按摩工作項目。另一方面,台灣醫學院全面
拒斥視障者報考的規定,也剝奪視障按摩者步入主流醫療之訓練與教
育的機會。1988年行政院衛署保字第758836號函再次重申:
029為什麼馬殺雞?
視覺殘障者所從事之「按摩業」宜以「正常人」為對象,且應以「手
技」為職業範圍。而「復健」是利用各種治療技術與訓練,幫助病
患回復運動功能,應經醫學專業訓練,屬醫療行為。兩者不同,
不宜歸屬同一行業。所舉辦之「按摩業職業訓練」,亦不得涉及醫
療行為。
當然,法律的力量並不在條文本身,而要看其它行動者順從的程
度(Latour 1988)。法規的約束力到底有多強,則必須由實際操作中來
瞭解,也就是有多少行動者願意跟隨。萬明美(1991)曾由台灣省、台
北市、高雄市按摩職業工會的會員中,抽取300名視障按摩師進行實
地訪視。結果發現,按摩師的服務項目以一般按摩為主,其次為腳底
按摩、指壓、和全身經穴按摩,少數視障者也使用針灸和電療。有
50%的視障者師以「消除疲勞」為其主要經營方向,6 %實際上以治療
復健為主,其餘44%則是保健與治療兼有之。換句話說,直到90年代
仍有近一半的視障按摩師自認所從事的是醫療行為。
那麼,網絡中其他行動者又是如何?雖然法律禁止視障者從事「具
有醫療性質」的按摩,但是受過嚴謹中醫傷科訓練,具備推拿、整脊、
接骨等技術與知識的中醫師其實並不多。有能力且會親自操作處理傷
科業務者,更是少數(高宗桂 2005)。為了因應患者的需求,中醫傷科
便雇用「推拿技術員」來協助。推拿技術員不必具有醫事人員資格,但
可以在中醫師指導下執行推拿等工作。推拿技術員的來源背景相當多
元,出身包括國術館拳頭師傅、西醫復健科治療人員、民間短期訓
練、醫療院所自行招考與培養、以及原有醫療院所內的工作人員轉業
擔任(喻淑蘭1999)。雖然依規定中醫傷科之推拿應由中醫師為之,然
而實際上病人可能進入診斷室後,只是醫師隨便摸一下,然後交由推
拿師全程處理。或者,病人可能只是掛號後與醫師打個招呼,交換彼
此的默契,然後各自找熟悉的推拿技術員。這類不當診療型態,一直
台灣社會研究 第八十三期 2011年8月030
是中醫在健保給付上較常受到批評的問題。不過關於推拿整復應由中
醫師親自操作,或由在中醫師指導下從事之規定並非沒有爭議,有些
中醫師就表示衛生署允許推拿在無任何醫師指導下,自行以民俗療法
開業,就沒有道理不准推拿技術員在中醫醫療院所中從事推拿行為(邱
大昕2009)。1993年11月19日衛署醫字第82075656號函公告,不列入
醫療管理之行為包括:
1. 未涉及接骨或交付內服藥品,而以傳統之推拿手法,或使用民
間習用之外敷膏藥.外敷生草藥與藥洗,對運動跌打損傷所為之
處置行為。
2. 未使用儀器,未交付或使用要藥品,或未有侵入性,而以傳統
習用方式,對人體疾病所為之處置行為.如籍按摩、指壓、刮
痧、腳底按摩、收驚、神符、香灰、拔罐、氣功與內功之功術等
方式,對人體疾病所為之處置行為。
在西醫方面,操作治療(或稱徒手治療)在物理治療中也被認為是
比較複雜的專業,只有復健師才可以執行。操作治療主要是用在軟組
織如肌肉、韌帶等,藉放鬆肌肉或減少組織粘黏而達到減輕疼痛的目
的,同時按摩也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加速組織的復原。不過在物理治
療的學校教育裡,教師普遍對徒手治療興趣缺缺,認為用儀器治療就
可以,因此徒手治療的訓練並不是很充足的(高宗桂 2005)。一位受訪
的物理治療師就表示,物理治療在大學只有二學分手療相關課程,而
且只教手法沒有理論,不同老師或者工作場所不同學長教的,也會是
不同的手法 30。另一位資深物理治療師,同時也是大學物理治療學系的
講師也表示,若單就按摩而言學校養成教育的必修課不多,通常被打
30 2004年訪談紀錄,PT02,地點:高雄市。
031為什麼馬殺雞?
散在各個課程中,如骨科物理治療學或操作治療學等 31。西醫復健師對
傳統推拿或按摩的態度是矛盾的。許多西醫骨科或復健人員認為,操
作治療屬於物理醫學範圍,不容與中醫的整脊治療、推拿、按摩等混
淆。其手法技巧或許相類似,但背後基本理論、處理方式,以及目的
都大不相同的(朱美滿1977)。由於物理治療的教育過程中,手療部分
的訓練較為缺乏,因此也有物理治療人員對中醫推拿或視障按摩持肯
定的態度。一位受訪的物理治療師表示:「PT(物理治療)手技不如視
障按摩,也不如國術館師傅⋯⋯明眼人按摩師較花俏,運用的手法較
多種。視障按摩較規矩,運用手法較正統。」32因此,有些物理治療師
其實仍會將中醫的穴道原理加入他的治療過程當中。
結語
如同要穩定網絡有時需要發展出更多的網絡一樣,要回答「為什麼
盲人會從事按摩」這一開始提出的問題,也需要先回答另外的一些問
題:到底誰是「視障者」?什麼又是「按摩」?由本研究所呈現的歷史演
變過程可以看出,這些問題無法用形式主義的定義來回答。「視障者」
和「按摩」都沒有確定不變的本質,而是透過一連串的中介的位移,和
不斷轉變的實體。過去百年來,台灣「視障者」的判定方式和判定標準
經歷了多次變化。英國傳教士甘為霖牧師在台南設立第一所盲人學校
時,主要是透過打聽的方式來尋找盲童。日本佔領台灣後,「盲人」的
判定轉移到警察、教師或醫生這些專門人員手中。這種情況一直持續
到國民政府時期,但是期間盲人的標準卻不斷變化著。1980年殘障福
利法公佈後開始發放殘障手冊,身心障礙鑑定交由公立醫療院所來負
責,醫生成為障礙身分的「守門人」。可是在世界衛生組織推動的「國
31 2004年訪談紀錄,PT03,地點:高雄市。32 2004年訪談紀錄,PT02,地點:高雄縣岡山鎮。
台灣社會研究 第八十三期 2011年8月032
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簡稱 ICF)影響下,2007年通過的「身
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決定未來台灣身心障礙的鑑定工作,將改由跨專
業的評鑑小組來共同完成。
「按摩」這項技術本身也是網絡的產物,必須從其所處網絡內的人
與非人行動者的實作來瞭解。中醫的推拿、物治的手療,和視障的按
摩並沒有「本質」或「必然」的面貌,而是透過一連串中介轉譯所產生的
實體,共同創造出最後的多重實體。中西醫各自創造了不同的實體世
界,而那個實體之所以有力,是因為它拉攏建立了許多的聯盟,比視
障的實體更能夠抵抗任何的考驗。他們對視障按摩的頑強,它不只在
於聯考簡章報考資格上「禁止盲人報考」這樣的條文來限制。他們靠著
更多中介技術物來抵抗來自視障者的考驗—他們的大學沒有無障礙
設施、沒有輔具、沒有盲人用的點字書,儀器上也沒有點字或聲音,
因此盲人根本無法進入他們以視覺訊息為主的世界。但是,反過來中
醫、物理治療卻很容易進入視障按摩的世界,並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將
視障按摩轉譯成他們的語言。中醫說他們的推拿和盲人的按摩不同,
物理治療也說他們的手療和盲人的不一樣。中醫西醫都說只有他們的
按摩才具有醫療功能,盲人做的就沒有。中西醫還說他們做的必需有
大學程度才能學習,盲人的不用。所以,中西醫的按摩可以享有保險
或(後來的)健保給付,盲人的就不行。
然而在ANT的分析中,研究者並不去判斷網絡行動者的觀點或立
場,而是承認實體的多重存在。因此本文並不是站在西醫或中醫的立
場,認為物理治療是比較「科學」的,或中醫教育是比較有系統的訓
練,所以只有受過高中教育的盲人不應該從事電療和針灸。同樣的,
本文也不是站在視障按摩者這邊,說中醫針灸師或物理治療師只是為
了擴張地盤,因此提出「盲人沒有能力從事醫療行為」這樣偏頗荒謬的
說法,來限制視障者的工作權。在追蹤「視障按摩」的萌生過程中,我
033為什麼馬殺雞?
們可以看到日治時期台灣盲人如何轉變為從事針灸、按摩、電療的理
療師,以及在國民政府來台後,盲人又如何由理療轉變為現在所從事
的按摩工作。在這轉變過程中,法律規範或許發揮了某種程度的影
響,但是具體工作內容的轉變還是發生在相對應的技術網絡之內。倘
若沒有管針的出現,視障者不會這麼容易從事針術工作;但是如果日
本殖民政府如果沒有限制漢醫,視障者進入醫療市場的阻力也許就會
大許多。日本統治結束後,日本教師離台、盲校教科書的缺乏,以及
後來中西醫對針灸電療器具的壟斷,視障者便逐步被驅離理療網絡之
外。2008年10月31日司法院釋字第六四九號解釋,宣告視障按摩保障
違憲之後,許多視障按摩團體希望能改變視障者就業訓練過程,重新
進入醫療體系從事理療工作。從本研究ANT的分析角度來看,這雖然
不是不可能或不切實際,但卻是個百廢待舉重新建構網絡的龐大工程。
參考文獻
小田俊郎 (1995)《台灣醫學五十年》,洪有錫譯。台北市:前衛出版社。
中山太郎 (1934)《日本盲人史》,東京市:昭和書房。
丸山芳登 (1957)《日本領時代に遺した台灣の医事衛生業績》。橫濱市。
王育瑜 (1994)《台灣視障者的職業困境:以按摩業為例的分析》,國立政治大學社會
學系碩士論文。
甘為霖 (2006)《福爾摩莎素描:甘為霖牧師台灣筆記》,台北:前衛出版社。
永井彰子 (2002)〈東北アジアにみる盲人文化〉,《동북아 문화연구》,3: 89-104。
朱美滿 (1977)〈簡介操作治療法及其對下背疼痛的施用〉,《物理醫學會雜誌》2:11-
13。
吉野秀公 (1997)《台灣教育史》,台北市:南天書局。
肖永芝 (1999)〈日本古代針灸醫學源流概論〉,《中國針灸》,第五期。
佐藤會哲 (1932)《台灣衛生年鑑》。台北:台衛新報社。
邱大昕 (2009)〈被忽略的歷史事實:從視障者工作演變看大法官釋字第六四九號解
釋〉,《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3(2): 55-86。
林文源 (2007)〈論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行動本體論〉,《科技、醫療與社會》4:65-108。
周建卿 (1992)《中華社會福利法制史》。台北:黎明。
台灣社會研究 第八十三期 2011年8月034
吳基福 (1980)《中國醫政史上的大革命:「醫師法」修正始末》。台北:中華民國醫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
高宗桂 (2005)〈台灣中醫推拿的源流與發展〉,《中華推拿與現代康復科學雜誌》,
2(1): 1-6。
栗山茂久 (2006)〈肩凝考〉,《古今論衡》15: 50-70。
范燕秋 (1994)《日據前期台灣之公共衛生:以防疫為中心之研究(1895-1920)》,頁
42-58。台北: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2008)〈新醫學在台灣的實踐(1898-1906):從後藤新平《國家衛生原理》談
起〉。《帝國與現代醫學》,李尚仁編,頁19-53。台北:聯經。
傅大為 (2005)《亞細亞的新身體:性別、醫療、與近代台灣》,台北:群學。
莊永明 (1998)《台灣醫療史:以台大醫院為主軸》,台北:遠流。
張苙雲 (1998)〈從不穩定的口碑到主要的求醫場所:台灣西醫的制度信任建構〉,
《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8(1): 161-183。
張妙娟 (1999)〈《台灣府城教會報》教育資料選譯〉,《台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
http://140.109.185.220/taiwan_history/pdf/eduhis2.pdf。
張珣 (1983)〈台灣漢人的醫療體系與醫療行為:一個台灣北部農村的醫學人類學研
究〉,《中央研究院歷民族學研究所集刊》。56: 29-58。
喻淑蘭 (1999)《醫療專業的變遷與互動:以中醫傷科醫師、國術館拳頭師傅與推拿
技術員為例》,台灣大學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1946)《台灣省51年來(民國前十七年至民國三十四年)
統計提要》。台北: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
鄭志敏 (2004)《日治時期〈台灣民報〉醫藥衛生史料輯錄》。台北:中國醫藥究所。
萬明美 (1991)〈視覺障礙者從事按摩業之現況及影響其收入之相關研究〉,《彰化師
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暨研究所特殊教育學報》6: 1-47。
劉寧顏 (1994)《重修台灣省通志 卷六 文教志教育行政篇》。南投:台灣省文獻會。
薛世儀 (1958)〈長笛一聲人依杖 曲巷十里夜未央〉,《聯合報》。1958年11月2日,
第四版
戴麗娟 (2004)〈馬戲團、解剖室、博物館:黑色維納斯在法蘭西帝國〉,《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54: 177-212。
Barnes, Colin (1991) Disabled People in Britain and Discrimination. London: Hurst and Co.Bendelow, A. Gillian and Simon J. Williams (1995) Transcending the Dualisms: Towards a
Sociology of Pain.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17(2): 139-165.Bolt, David (2005) From Blindness to Visual Impairment: Terminological Typology and the
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 Disability & Society, 20(5): 539-552.
035為什麼馬殺雞?
Bury, Mike (2000) On Chronic Illness and Disability. In Handbook of Medical Sociology, 5th ed. edited by C. Bird, P. Conrad and A. Fremont.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Callon, Michel (1986).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In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edited by John Law.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p. 19-233.
— (1991) Techno-Ecnomic Networks and Irreversibility. In A Sociology of Monsters: Essays on
Power, Technology and Domination. London: Routledge, pp. 132-158.Callon, Michel (1999). Actor-Network Theory: The Market Test. In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After, edited by John Law and John Hassard. Oxford: Blackwell, pp.1-14. Campbell, W. (1915/1996) Sketches from Formosa. London, Edinburgh & New York: Marshall
Brothers, Ltd. Reprinted by SMC Publishing Inc.Corker, Mairian (1999) Conflations, Differences and Foundations: The Limits to ‘Accurate’
Theoretical Representation of Disabled People’s Experience? Disability & Society, 14(5): 627-642.
Doolittle, Justus (1868)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edited by P. Hood. London: Sampson Low, Son & Marston.
Finkelstein, Vic (1980) Attitudes and Disabled People. NY: World Rehabilitation Fund.— (1981) Disability and the Helper/Helped Relationship: An Historical View. In Handicap
in a Social World. Edited by A. Brechin, P. Liddiard, and J. Swain. England: Hodder and Stoughton.
— (2001) A Personal Journey into Disability Politics. The Disability Studies Archive UK,
Centre for Disabilities Studies, University of Leeds.Foucault, Michael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0)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Gamble, Sidney D. and Burgess, John S. (1921) Peking: A Social Surve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hn, Harlan (1993)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Disability Definitions and Data. Journal of Disability Policy Studies. 4(2): 41-52.
Hughes, Bill and Kevin Paterson (1997) The 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 and the Disappearing Body: Towards a Sociology of Impairment. Disability & Society, 12(3): 325-340.
Kobayashi, Akiko, Miwa Uefuji and Washiro Yasumo (2008) History and Progress of Japanese Acupuncture,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eCAM, doi:10.1093/ecam/nem155.
Latour, Bruno (1983/2004).〈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林宗德譯,見吳嘉苓、傅大為、雷祥麟編,《科技渴望社會》。台北:群學,頁219-263。
— (1988)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and John Law. MI:
台灣社會研究 第八十三期 2011年8月036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Law, John (2004) After Metho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Material Semiotics, available at http://www.
heterogeneities.net/publications/Law-ANTandMaterialSemiotics.pdf,(downloaded on 18th May, 2007).
— (2009a) “Meltdown: Why ANT?” Workshop i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March 27-28, 2009.— (2009b) “Engineering Practice and STS” Workshop i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March 31, 2009.Mestler, Gordon E. (1954) A Galaxy of Old Japanese Medical Books with Miscellaneous
Notes on Early Medicine in Japan: Part II.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Bathing, Balneotherapy and Massage, Nursing, Pediatrics and Hygiene,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Bulletin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42 (4): 468-500.
Mol, Annemarie (1999) Ontological Politics: A Word and Some Questions. In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After. Edited by J. Law and J. Hassar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pp.74-89.
Oakley, Ann (1972) Sex, Gender and Society. London: Maurice Temple Smith.Oliver, Michael (1990) The Politics of Disablement: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NY: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6) Understanding Disability: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Basingstoke: Macmillan.
Shakespeare, Tom and Nicholas Watson. (2002) The 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 An Outdated Ideology?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 and Disability, 2: 9-28.
Thomas, Carol (1999) Female Forms: Experiencing and Understanding Disability.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Thomson, Rosemarie Garland (1996) Introduction: From Wonder to Error—A Genealogy of Freak Discourse in Modernity. In Freakery: Cultural Spectacles of the Extraordinary Body. Edited by R.G. Thoms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p.1-19.
— (1997) Extraordinary Bodies: Figuring Physical Disability in American Culture and
Literature.Turner, Bryan (1984) The Body and Society: Explorations in Soci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試探《維摩詰經》的原語面貌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Original Language of the Vimalakīrtinirdeśa]](https://static.fdokumen.com/doc/165x107/633d34a9a508153b280699b4/-an-investigation-into-the-original-languag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