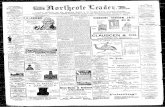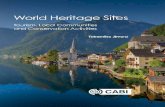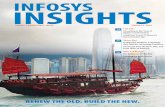Renew the past by deep mapping historical space on heritage sites
Transcript of Renew the past by deep mapping historical space on heritage sites
DNWH
《东南文化》2014年第4期总第240期
收稿日期 2013-07-29作者简介 钦白兰(1987-),女,浙江大学外语学院与威斯康辛大学教育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化遗产与话语、地方与
教育空间。
吴宗杰(1957-),男,浙江大学跨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银行文化遗产咨询专家,主要研究方向:文化遗产与话
语、场所与经义。
丰 杨(1986-),男,曲阜市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处助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大遗址保护展示实践与鲁文化。
基金项目 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古迹经注”:曲阜鲁国故城遗迹考,项目号:15)。
内容提要:文化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如果仅限于西方遗产话语,往往导致时间与空间、物质遗迹与
人文精神被分割为两个不同方面,致使遗址在传承文化、教化当下的功能上难以充分体现。以鲁故城
“泮水”遗址作为例,借用“深度绘图”方法,梳理遗址承载的历代文本源流,则能更好地显露沉积在遗
址空间里的意义层及其传承关系。因此,中国文化遗址的保护,不只是关注“物质原真性”,还可以用
“历史空间”这一概念,把物质遗迹和历史文脉打通,实现贯通古今、德泽当下的遗址文化传承功能。
关键词:文化遗址 历史空间 深度绘图 曲阜泮水 经义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遗产保护理论
遗址历史空间的深度绘图及其经义接续
钦白兰 1 吴宗杰 1 丰 杨 2
(1.浙江大学跨文化研究所 浙江杭州 310058;
2.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处 山东曲阜 273100)
作为跨学科的研究对象,文化遗址(culturalheritage site)的理解、管理与利用始于西方[1],因
此,遗址开发很多方面也受制于考古、历史、地理
学科的概念理论,这套范式常被看作普世科学,
使得国内遗产实践很难摆脱福柯(Michel Fau⁃cault)所言的话语操纵[2]。文化遗址的现代保护与
修复章程始于《威尼斯宪章》,1964 年,根据对意
大利文化遗产的认识,国际古迹理事会(ICO⁃MOS)确立了国际公认的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
段的遗产保护原则。此后几十年,在联合国科教
文组织(UNESCO)及国际古迹理事会的推动下,
各国纷纷效仿并以此原则作为本国遗产认定、表
述与保护的法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2002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
(2009 年)等,大都在这一遗产范式下建立起来。
遗址保护常用西方物质原真性(material authen⁃ticity)等概念将其凝固在过去,时间与空间往往
被分割为两个不同方面[3]。遗址利用也局限于后
工业时代的旅游化、博物馆化及遗址公园化等[4],
遗址作为文化传承的功能不能得以充分体现。诚
然,不可否认“遗产运动”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
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地方(场所)”
(place/site)、“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文
化路线”(cultural route)等概念推动了我国的“文
化遗址”认识,一定程度促进大遗址[5](文化遗址
重地)保护,如《西安共识》(2009年)、《洛阳宣言》
(2010年)、《荆州宣言》(2011年),中国考古界、遗
产界以及博物馆界为保护中国文化遗产做出了
重要贡献。但对遗产实践的西学路线仍然有必要
进行反思,这有利于保护中国文化特色的遗产,
比如众多在物质上无法界定、面临危机的文物遗
址,如古迹、商铺、街巷、民居等。这也回应近几十
年里,遗产界对西方权威遗产话语(AuthorizedHeritage Discourse)[6]及各种遗产实践所进行的反
思[7]。
带着如何续接西学东渐以来失落的华夏文
15
DNWH
遗址历史空间的深度绘图及其经义接续
明传统的思考和探寻中国历史传统的本土遗产
实践途径的目的,我们走进曲阜鲁国故城,这块
称之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地。“鲁国故城”在
今山东省曲阜市,指周公之子(伯禽)“代父就封”
所建的“鲁国都城”(800余年)遗址。三千多年来,
除宋代改仙源县移至鲁国故城东郊之外,曲阜历
代城市空间转变基本都在鲁国故城遗址内。今
天,曲阜市还保留着明清故城的格局,有文物保
护点 825 处,其中的碑碣与瓦砾般的历史痕迹无
论在地方史志、还是乡老口传中,都或隐或现、可
感亦可观。鲁国故城遗址上,有黄帝少昊的帝迹、
周公之子的君迹、孔孟颜曾的圣迹、孔学 72 弟子
的贤迹以及历代帝王大儒驻留的足迹,可以说道
冠古今、泽披中华,千古精神如见。但是,今天人
们对这块土地的理解,大都局限于孔庙、孔府、孔
林。更遗憾的是,鲁国故城是中国经义(以六经为
基础)产生之地,但今天走在这块土地上,很难充
分体验到鲁故城空间的道统源流。为此,如何通
过鲁故城遗址的保护,重新彰显经义源流,实现
物质与精神、过去与当下的互通?如何让文化遗
址更好地承担起传承中国文化的教育作用?这便
是本文关注的研究问题。
本文将吸收国际史学界最前沿的“空间历史
学”(spatial history)[8]理论以及相关的“深度绘图”
(deep mapping)遗址研究与叙述方法,结合“辨章
学术,考镜源流”[9]的本土史学传统,对古鲁城的
“泮水”遗址做一个深入剖析,以此为当下中国文
化遗址保护与利用提供启迪。
一 历史空间:深度绘图和经义接续
就文化遗址而言,它总是指向历史的,可理
解为过去依附空间的存在。近几十年里,历史学
经历了不同的理解过去的方式,如:量化转向、文
化转向、语言转向;今天,历史学正在经历空间转
向(spatial turn)。作为一种最前沿的学术视角,空
间(space)概念试图消解历史学的意识形态禁锢,
包容不同文化思维的多样性话语(discourse)。空
间是一种跨越时间长廊的现实存在,打破了过去
与现实的界限;一批引领空间转向研究的学者认
为:宏大的、系统的、普世的历史叙述已经转向文
化、经验、地方的空间叙述。这种思想也将深刻影
响人们对文化遗址的认识方式,其中,历史空间
理念衍生出的深度绘图法,可展现遗址不同时代
的多元话语,形成遗址上“空间中的历史”(spatialhistory)。空间中的历史指历史问题不再是线性的
时间和历史事件问题,而是放置在空间中的意义
问题,这是一种后现代的历史观[10]。由此,像博登
海默(Bodenhamer)等历史学者在西方国家推动一
门新兴学科,称之为“空间人文学”[11],该学科提
出空间历史、深度绘图、空间叙述等多种历史空
间研究理念,他们的实地研究项目已在欧美等国
家开展。这些研究中,空间成为承载历史话语的
场所,层层地方历史可以在深度绘图中得以展
现。就遗址而言,地方(place)可成为多层次杂糅、
微观叙事的历史空间。深度绘图提出者博登海默
教授[12]指出:“‘深度绘图’不是要将简单的意义
变得深邃难懂,而是利用人文社科的空间转向,
将历史置于空间中来思考。”深度绘图指把沉淀
在一个点(地方/遗址)的丰富历史意义彰显出来
的方法。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它把过去或现
在细节的“文本碎片”(实物、图片、记忆、文字、声
音等)多层次、多视角、多模态地展现出来。深度
绘图打破了西方逻辑中心,历史不再是围绕时间
的宏大叙述,而是一种寄托于空间的微观叙述,
它是历史的、也是现在的,是学者的、也是普通人
的,是高雅的、也是通俗的。在这一视角下,文化遗
址则被赋予多样性、即时性、复杂性和开放性的展
陈方式。我们不再借助遗址去讲述宏大的民族主
义、怀旧主义或文化发展史等,而是在空间视角下
得到遗址的文化感悟。“这种感悟是碎片化的、流
动的、有深度的多重声音与多元故事。”[13]为此,我
们借鉴历史空间和深度绘图理论的启示,在曲阜
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地探索符合中国本土文化
思维的历史空间(即遗址的经义传承)。
曲阜为孔子故乡,上述夏、商、周三代之道
行,下启中华两千多年的文脉,而贯穿其中的是
以六艺为精神内涵的经义。先圣孔子生活于此,
他删六经,使之成为后人最重要的阐释文本。秦
汉以来,五经(关乎鲁地及周礼)是古代任何学问
及意义之源,历史上的十三经(南宋形成)被不断
解读,以适合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的需要。而历代
帝王大儒、文人墨客,为体验经义源流而踏足曲
阜这一块圣地,他们为此空间留下无数经史记载
和碑刻铭文。可以这么说,曲阜就是经义之地,鲁
国故城整个空间渗透经义源流。实际上,中国传
统史地学著作中,有关鲁国故城遗迹经义探寻方
式叫“地名考”。明清之际,基于经书的地名考专
著众多,是一项依托地方的制义探索,如:《春秋
地名考》、《春秋地名考略》、《春秋地理考实》、《尚
书地理今释》、《诗地理考》[14]。这类古籍内容并非
今日的地方知识汇编,体例也与现代的地方志目
16
DNWH
《东南文化》2014年第4期总第240期
录(科教文卫)不同,它的特点在于释经而梳理地
史地话语,为古迹做经注。比如:《春秋地理考实》
的分类,有国(鲁、蔡、曹、魏、藤),有地(雉门、两
观、棠、洙),文本展示背后是“微言大义”的编排
思维[15]。《尚书地理今释》将州、河、海分类,并加以
“五服图考”,将地理信息注入伦理的思考范围[16]。
《诗地理考》中,“鲁颂”有关曲阜,在鲁地现场以
“诗言志”[17]。我们发现,地名考对地方的认识灵
活,特别之处在于它常用“碑”、“林”、“祠庙”、
“水”、“城”等作为经义保护的“空间记号”(spatialmarker)。这些编撰模式都有为传承经义且述而不
作的特点,指孔子及以后古代贤人,用不加历史
评论的话语为后世留下穿越古今、开放通达的实
录空间绘图。古代大型类书(如宋《太平御览》)、
地方志(如杭州《武林坊巷志》)也继承这一传统,
其中,贯穿话语碎片的是续接过去与当下的经
义。
那么,如何理解经义之地的历史空间呢?“效
法天地,天人合一”是鲁故国城市空间开发/修复
的理念。传统城市建置及规划中遵守“崇礼尚德”
的原则。然而,民国以降,政治因革,道统渐隐,尤
其是近几十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保留千年的曲阜
古城面貌已发生重大变化,遗迹/遗存在五十年前
的文化动荡中大都荡然无存。现在,特别具有经
济利用价值的街区,经受着被拆迁、被旅游的遭
遇,原住居民无奈面临支持复兴工程被迫搬迁。
虽如此,空间作为一种遗产仍可被界定和传承,
因为国人明白:空旷的土地,空空如也;祠庙、城
墙等人为建筑随着时间流逝,时过境迁,常常几
经破坏,修复或搬迁,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最
重要的是,这个空间中只要存有经义,就算只有
一棵小树,那也是令人敬仰的遗迹,这正是“忠孝
所在、寸土皆香”的遗产地方意义与价值所在[18]。
曲阜鲁国故城大遗址的中心“太庙”处,我们还能
见到 1978 年 11 月曲阜县革命委员会树立的“故
城中部宫室基址”(14 万平方米)标志碑。也就是
说,在中华文化遭受最严酷的动荡与解构之际,
革命委员会依旧为保护这一经义空间而竖立下
一块石碑。实际上,中国传统遗迹的认识就是其
空间视角下的经义,“叙曰:代与时移,物随世变,
居今考古,匪迹曷因”[19]。在古人眼中,时间流逝,
任何古的东西,都会消失,今日的寻古为的是探
幽。我们祖先早知道,就算是能抵抗时间侵蚀的
石刻也无法永恒,石碑会风化、断裂,甚至消失,
唯一永恒不变的是空间以及其中仁义礼智信的
文脉。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就是这份穿越时空的
经义,得以万世长存、为人景仰。下面我们以“泮
水”遗址这一经义空间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展开
泮水历史空间的经义叙述和深度绘图。
二 寄托泮水“历史空间”中的经义源流
首先,我们应界定泮水的位置,也就是考证
泮水的方位与所在,形成空间指向为意义找到历
史停靠的位置。据考证,2500多年前,泮水是鲁国
都城内的一条小河,经现在的“古泮池”蜿蜒向
西,经过孔庙泮水桥,从明故城正南门西的水门
流出[20]。史料中,“泮水”赓续不辍地见载于大量
文献,此类历史文本的话语表述不计其数但多有
不一[21],形成展现各时代印记的空间话语。现代,
经义空间中话语流转后形成民间“泮水”的文化
记忆[22],比如:古泮池是孔子课余与弟子游憩之
处;民间口耳相传“乾隆驻跸古泮池”的故事;当
地人回忆孔家府院的人曾来此乘凉,还有流传
“古泮池”畔乃是“哑巴坑”的说法;20世纪 50年代
“池水周围杨柳依依,中间亭台水榭,红白莲分泮
池左右”[23];池门口街一家三代在文昌阁(曾作古
泮池小学)念书的家族记忆[24];“泮水流向,由东
至西,是‘圣人门前倒流水’”[25]。总之,沉淀在“泮
水”里的古今话语不可穷尽,兹举数例,姑记其
事。重要的是,这些话语碎片给后人一种历史层
次感,可以说,当今的“泮水”意义是话语的不断
叠加,构成泮水遗址“深度绘图”。尽管泮水遗址
中的历史话语是多样的,但贯穿其中的是一条永
不枯竭的经义源流。泮水意义最深处可追溯至
《诗经》,源于《诗经·鲁颂·泮水》的“经义之源”。
泮水,诸侯之学,乡射之宫,已成为中国文化“学”
的象征,体现了周王朝行礼乐、宣德化,文治武功,
令四方观而化之。该经义也影响全国各地,比如历
朝历代中国城市空间里都修有文庙泮池。总之,贯
穿泮水遗址的历史空间的是“折中于夫子”[26]的经
义对每个时代的关照。
我们可将历史空间深层价值定于中国经典
文本内的大义,它是中国传统史学实践留给后世
的经世致用的遗产价值观。中国古代有注疏传
统,指对经书(十三经)的意义阐释[27],因泮水记
载于五经之一的《诗经》,各时代文人学士多对其
进行再解读,以图理解圣人之意,达到鉴古开今
的当下意义建构。有关泮水,我们可看见不同历
史时期、不同形式但关乎教化的物质遗迹/遗址。
《诗经·鲁颂·泮水》载,“思乐泮水”,指的是鲁僖
公在此做泮宫,“济济多士,克广德心”,体现“鲁
17
DNWH
遗址历史空间的深度绘图及其经义接续
国崇周礼、重教化、尚德义、重节操等文化传统”[28]。
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载,“遂因鲁僖基兆而
营焉”[29],说明西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在泮水
遗址上重建宫殿,“然其规矩制度,上应星宿,亦
所以永安也”[30],这是作者对西汉“经义空间”重
树的赞美,说明其空间布局顺应天时而得国运畅
达。之后,唐宋元间,人们在此凭吊古迹、作诗写
赋之时,每每忆及“鲁灵光殿”,反复记载灵光殿
的空间布局,感叹当下“德音昭乎?”[31]明清之间,
泮水遗址上建立了衍圣公孔宏绪别墅和乾隆行
宫,一定意义上也表达了清代帝王和孔氏家族接
续春秋鲁僖公泮宫、西汉鲁恭王(刘余)灵光殿的
文脉;乾隆数次驻跸古泮池,留下辩疑经义空间
的“认错诗”[32]。到了民国,经学遭受挑战,西方传
教士试图在此建造教堂,为此衍圣公抢先修建了
文昌祠,以保护这一经义空间以续文脉。这些遗
迹的变化,都是各个时代依据“经义”对此空间的
具体改造。可以说,“思乐泮水”一诗便是“泮水”
空间的语义源头,行使着用“礼”教指导遗产实
践,每个时代都体现“经义空间”的当代续接。
我国各地文庙前的泮水,也来自上述鲁国故
城泮水的“教育”经义。明初,皇帝曾下诏全国立
学校,各府、州、县也都在学校前开挖半圆形的水
池,名曰泮水,上面建泮水桥,它的文化寓意来源
就是曲阜春秋的泮宫。泮池建立后,据科举礼尚,
考取功名的人过泮桥、入文庙祭拜孔子。今天,全
国各文庙旅游点也还能见到“泮水桥”及“泮水”
的格局,似乎还留有古代经义对教育文化的影
响。有意思的是,20世纪 50年代时,“泮水西流”还
曾串联有教育意义“文化场所”。据今天家住“泮
水”南的彭先生回忆[33],“泮水”的“根”在文献泉,
流经中国古代学府的古泮宫和近代的曲阜师范
学院(清考棚),直到古之学者“入泮”的孔庙前的
“泮水桥”。这些人文景观(建筑、标示物、纪念碑
等)排列形成空间感,如同一系列“教育”故事情
节,环环相扣,似乎隐含着具有教育象征意义的
空间表征[34]。此外,为了留存此“经义”,古人不断
地用石碑标记此空间。清代乾隆《曲阜县志》载:
“泮宫台,一曰‘书云台’,俗谓‘钓鱼台’,台北有
水,即泮水也。明周天球书碑曰泮宫。”[35]《大清一
统志》载:“乾隆十三年,圣驾幸鲁于泮池,旧基建
有行宫,恭邀清跸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二十七
年,三十六年,四十九年,俱有御製古泮池诗,与
御制古泮池正疑,並勒石按:泮宫台,亦谓之书云
台。”[36]由此可见,明清地方志中西汉灵光殿结石
为诗、明周天球书碑曰“泮宫”、乾隆勒石按泮宫
台,都是古人“树碑记德”的空间意识。可惜的是,
这些石碑“多有遗落时,或存于世焉?”[37]我们注
意到“古泮池风貌区修建规划”有复建方案,涉及
了乾隆行宫,还有部分古泮池,但灵光殿、孔宏绪
別墅、文昌祠以及历代无数传承遗迹又将如何体
现?今天古泮池一带除文昌祠已经完全夷为平
地,等待再一次的空间改造,那么这一次改造将
如何体现被认为是万世不竭的经义源流?这个问
题不仅是曲阜市政府所关心,也是全国与孔庙相
关的地方都要关心的重大课题。
三 泮水“历史空间”的深度绘图
受深度绘图理论的启示,我们将对寄托于
“泮水”遗址上的历代文本进行梳理,展示其多声
部的历史话语层积,使遗址成为接续经义的空间
叙述(spatial narrative)[38]。“深度绘图”关注的是在
这一空间里产生的不同时代的“话语”源流,它把
对物质遗迹的关注置于其精神命脉之中。任何一
个时代的“场所”面貌都不足代表此地全部历史
意义。我们将通过具历史层次的表格,有选择地
展现“泮水”空间的文脉源流,以此来展示泮水
“经义空间”。整个表格围绕话语(文本)而非内
容,文脉而非物质遗迹考证。它也不试图还原遗
址的“历史真相”(historical facts),其目的在于理
解各时代“话语”的叠加方式。表一由时间和空间
两个维度构成,所指“年代”和“名称”均以文本为
出发点,而不是“泮水”不同时代的物质形态。“时
间”仅表示文本产生的时间。“文脉层解读”是我
们从文脉的源流解读这一碎片的意义,同时附上
相关的“文本摘录”以供直接体验。但我们也不忽
视遗址的物质空间。因此最后一栏,我们依据相
关碎片的提示,勾勒遗址的空间变迁轨迹。限于
篇幅,我们无法全面展现寄托在这块遗址上的所
有文本,只能选择代表性的加以展现。但一个全
面的深度绘图应包括所有可以采集到的文本(文
本也指图片、石碑、口述等等有意义的符号)。
表一展现泮水的历史空间,或者说空间中的
历史,贯穿其中的是经义源流在不同时代的表
现。它显示该历史空间里的物质性是变化莫测
的,不同时代呈现不同模样。但作为意义源头,
“思乐泮水”的教化大义深刻影响历代该遗址的
利用方式,具体表现在春秋的泮宫,西汉灵光殿,
明代孔宏绪別墅,清代乾隆行宫,民国文昌殿、国
民小学,建国后的古泮池小学等等。中国有句古
话:“教化流行于东西、朔南之间,譬如风”,说的
18
DNWH
《东南文化》2014年第4期总第240期
基于文本的遗址文脉(时间维度)
年代对应
春秋鲁僖公
(公元前
659-前627年在位)
东汉桓帝时
(约140-165年前后)
南北朝北魏
(386-534年)
隋大业七年
(611年)立
南宋朱熹时
(1130-1200年)
元杨奂时
(1186-1255年)
明永乐至崇
祯
(1403-1644年)
文本名称
《诗经·鲁
颂·泮水》
王延寿
《鲁灵光
殿赋》
郦道元
《水经注》
陈叔毅
《修孔子
庙碑》
朱熹《春
日》、《观
书有感》
杨奂《东
游记》
《明一统
志》及明
崇祯《东
野志》
文脉层解读
(1)经义起源,修泮宫,崇礼
教。(2)泮宫之水,诸侯之学,中
国文化中“学”的象征。
(1)汉代宫殿赋的名篇,以经义
解读建筑细节背后的大义。
(2)经义的辞赋表达:王延寿为
因周公、孔子,为六艺而来鲁
国,观此宫殿惊愕,由此感物而
作。
《水经注》是古泮池的历史空间
杰出记述,它把当时的物质遗
存与文脉(《诗经》、《鲁灵光殿
赋》)贯通,在空间布局上做了
实证性的记载。
建立泮水与《诗经》、灵光殿基
与其赋对于传承孔庙文脉的空
间关系。石碑是保护经义空间
的意义来源和传世文物。
朱熹拜谒曲阜, 以古泮池为原
点, 盛日寻芳泗水滨。[42]
杨奂(称紫阳先生)登泮宫台,
在圣迹上感怀,他的修学经历
是一次经义空间的体悟。之
后,很多文人墨客至曲游览,在
古泮作诗留赋,叹“德音昭乎”。
明代彭泽人陶钦皋拜谒周公
庙,第一次提及灵光殿基是在
周公庙边,明崇祯年《东野志》
也如此记载,由此形成不同说
法。明万历知县孔弘复迁“三
氏学”于按察司行署东”,也就
是古泮池衍圣公别墅内。
文本摘录
思乐泮水,薄采其芹,鲁
侯戾止,言观其旂。
(1)初,恭王始都下国,好
治宫室,遂因鲁僖基兆而
营焉。
(2)详察其栋宇,观其结
构。规矩应天,上宪觜
陬。[39]
孔庙东南五百步有双石
阙,即灵光之南阙……故
王延寿《赋》曰:周行数
里,仰不见日者也……台
池咸结石为之,《诗》所谓
思乐泮水也。[40]
接士迎宾,登临游赏。睹
泮水而思歌,寻灵光而想
赋,加以祗虔圣道,致敬
明神。[41]
《春日》:胜日寻芳泗水
滨,无边光景一时新。《观
书有感》:问渠哪得清如
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台之下水自西而南,深丈
许而无源……读圣人之
书游圣人之里,幸之幸者
也。[43]
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
阜县治西南,西流至兖州
府城,东入泗水。诗“思
乐泮水”即此。(《明一统
志》)[44]
周公宪王庙在曲阜县城
东二里故太庙之墟……
汉鲁灵光殿旧基即此。
(《东野志》)[45]
基于文本记载的物质遗迹变迁
(空间维度)
鲁僖公在鲁城南兴建宫殿,由此形
成礼教空间,包括泮水、泮林、泮宫、
辟雍、芹、藻、茆、鸮等等。今物质遗
迹已全部消失,但其意义见于经传,
传承至今。
鲁南宫灵光殿遗迹“北陛石”现收藏
在曲阜孔庙汉魏碑刻陈列馆内。
(钦白兰摄,2013年8月29日)
灵光殿遗址,石阙,浴池,钓台,泮
宫,泮水,今钓鱼台与泮水尚有记
忆。
传世石碑,石碑标记。
泮水作为经义源流的空间体验场
所。
灵光殿基、泮宫台、泮水。
明代曲阜由今旧县村搬至今明故城,
围庙为城,对“泮水”第一次大规模改
造,命名的空间有:鲁泮宫遗址,雩
水、南溪、泮池、孔宏绪别墅、孔庙前
泮水,三氏学。明嘉靖“古泮宫”石
碑,现收藏曲阜孔庙“永乐碑亭”。
(钦白兰摄,2012年12月10日)
表一// “泮水”历史空间源流深度描绘
19
DNWH
遗址历史空间的深度绘图及其经义接续
明弘治至清
康熙
(1488-1722年)
清乾隆
(1711-1799年)
清光绪至民
国年间
(1871-1934年)
1951年
《明史·李
东阳传》及
《南溪赋》
清乾隆《曲
阜县志》;
乾隆诗《驻
跸古泮
池》、《古泮
池》、《古泮
池杂咏六
首》
《续修曲阜
县志》(民
国二十三
年,1934年)
《曲阜鲁城
の遗蹟》
(日文)
孔庙的格局明代形成,泮水
这时在意义上与孔子对接,
在空间上与孔庙相连,并因
此影响全国孔庙庙制格局。
从大量地方“重修儒学记”
看,全国上下“门前为池,池
上为桥”,孔庙形成过泮水桥
的“入泮仪式”。
清代对于泮水遗址的改造记
载最多,且多为景观植入。
古泮空间的“教化大义”使得
皇帝及文人,“适符在泮之
义,因成过鲁之篇。”乾隆皇
帝曾经对古泮池的地理空间
有过误读,认为明代新城不
应有泮池,但基于经义空间
感,他对泮池治国之道有比
清代任何帝皇更加强烈的追
求。
20 世纪初,中国与西方文化
激烈碰撞,西方话语入侵中
国。古泮池面临空间被改
造,衍圣公孔令贻、知县孙国
桢等在泮池北岸建筑文昌
祠,借以抵制西人。古泮遗
址出现现代学校作为近代教
化经义的接续形式。
古泮池经历“经义空间”到
“考古遗址”的话语转型。
1942-1943 年,日本东亚文
化协会和东京大学对鲁国故
城进行的两次考古调查。参
与学者驹井和爱在周公庙附
近发现“北陛石”。此后至
今,“考古”成为鲁故国遗址
的权威话语。古泮池一带由
于缺乏物质原真性逐渐被民
居侵蚀。民国以后现代教育
观念代替古泮池教化经义。
弘治十七年,重建阙里庙成,(李东阳)奉命往祭。(《明史·李东阳
列传》)[46]
此周封之遗墟,汉国之故地也,
其前则两观之门,其后则灵光之
基也。地以人胜,事随代更,逮
我故公,而南溪是名。(《南溪
赋》)[47]
修泮池者,壮学宫也;壮学宫者,
尊孔子也;尊孔子者,崇其道
也。(沈良才《修儒学泮池记》)[48]
曲阜城南隅,清池亩许,上有古
柏数株,盖千余年物,相传为鲁
泮水之旧所司,即其地构室数
楹,以存古迹。(《曲阜县志》)
十里东郊旧鲁城,
新城安得泮池名?
(乾隆《古泮池杂咏六首》)[49]
光绪二十四年,西人觊觎其地,欲
立耶稣教堂……(衍圣公孔令贻)
即于池之北岸建筑文昌祠借以抵
制西人也。民国十二年,孔繁洁
劝募重修,于池之中央筑亭一座,
仍名曰四明亭。其北文昌祠,明
德中学设附属小学于此。[50]
两块刻石按东西方向并排列着,
长 94 、宽 40、厚 19 厘米。表面
排刻着直径 20 厘米的璧纹,侧
面刻着数字,北面刻着几何形花
纹。东面已裂为 3 段,西面裂成
多块,但内容较详细。仔细观
察,东边的一块在其侧面上刻着
“鲁六年九月所造北陛”字。鲁
六年(公元前 149年)为汉景帝子
刘馀(鲁恭王)修建曲阜灵光殿
之年,因知刻石当为该殿上所
用。(译自《曲阜鲁城の遗蹟》“刻
石”,第12页)[51]
康熙十六年(1677 年)修孔庙前
的泮水桥,后经康熙准奏,开挖
河渠,让古泮池泉水流经孔庙棂
星门前,由此在空间上形成孔庙
与泮水的对接。
泮池边新建文昌祠;1919 年,重
修四明亭。并设小学于此。
1920年古泮池照片:
(出自百度百科“古泮池”词条)
鲁国故城考古发现砖瓦等遗迹,
包括灵光殿北侧台阶“北陛石”。
从日本运回,现收藏在汉魏碑刻
陈列馆内。
1947 年文昌祠用作“第二中心
国民小学”校址
北陛石纹饰:
(出自曲阜市文物局)
(接上表)
泮池经历景观化改造,有南池、
南溪、马跑泉、雩水、泮宫台(书
云台),古柏、溪堂、水谢、花坞、
钓台、长堤、
溪桥,里外
二湖等。乾
隆多次驻跸
古泮行宫,
留下两块石
碑 。 建 国
后,很多人
都见过石碑
与 古 泮 美
景。
(出自乾隆
《曲阜县志》
卷三“图考”)
20
DNWH
《东南文化》2014年第4期总第240期
1977年
1986年
1993年
2006年
2012年
2013年
考古报告
专 集《曲
阜鲁国故
城》
《曲 阜 历
史名城城
市规划建
设 纲 要》
(讨论稿)
1986年10月,第5页
《曲 阜 市
志》
《曲 阜 市
明故城控
制性详细
规 划 》;
《曲 阜 历
史文化名
城保护规
划》
《曲 阜 明
故城古泮
池风貌区
修建性详
细规划及
建 筑 方
案》
考古话语专业化。《曲阜鲁国
故城》是一部系统的鲁国故城
遗址考古报告。以考古视角,
做遗址钻探试掘,文化层分
析,文物遗存保护修缮工作。
考古发现不是用来彰显经义,
而是依照现代线性时间观,为
研究鲁国和两周时期的历史,
提供佐证。而口述及地方史
料关于本地的记载大都在遗
忘边缘。
受城市规划话语影响,该纲要
第一次提及“恢复古泮池、行
宫为城市公园”,遗迹保护开
始走进城市建筑话语“公园
化,旅游化,遗址化”之路。以
后,多次城市规划都沿用此话
语。
虽然“而今池亦存,小学仍
在。”古泮池“历史空间”多样
性的话语及嵌入当地人生活
的回忆,都正在慢慢消失。
“生态与环境话语”下的“泮
水”保护与规划。泮水意义成
为一种水治理的技术对象,并
指导遗产实践。世界银行项
目审核高级城市专家提议“把
该区域定位为建设控制地带
加以保护”。
2013 年 6 月,古泮池 205 亩面
积,除了文昌祠外,已完全被
夷为平地。与此同时消失掉
的是不同时代沉积起来的空
间记忆标识载体。
在建筑基址上面,出土了大量
的筒瓦,板瓦和瓦当。板瓦以
II,III式布纹瓦为主……有些瓦
片被火烧成了红或蓝色,此建
筑可能毁于火灾……这里可能
是汉灵光殿东面“廊庑别墅”的
一部分。[52]
目前仍有水面24亩,长年不涸,
规划要求恢复泮池行宫,逐步
建成明城公园,使其成为中外
游客及本市人民现代文明游乐
场所。[53]
山东省人民政府对曲阜县城总
体规划的批复:较大型的宾馆
近期仍可考虑建在古泮池南,
远期在雪泉建临水庄园式大型
宾馆。[54]
现状泮池水体与外界水体之间
的沟通几乎不存在。[55]
杂草丛生、乱倒垃圾、杂乱无章
……总之,本片区内生态环境
恶劣,亟待整治。[56]
(周公庙上层建筑遗迹)灵光殿考
古遗址。许多学者质疑考古结论
把灵光殿位置看作是周公庙一
带。
解放后文昌祠改为“古泮池国民
小学”,1953 改名为“曲阜师范学
校附属小学”。
20世纪 50年代后,“古泮宫”石碑
移入孔庙。
1981 年龙卷风袭击古泮池,卷走
文昌祠屋顶;古泮池成为“明故
城”城市保护及规划用地;1986年将古泮池列为“曲阜市文物保
护单位”。
家庭宾馆,古泮池塘,“古泮池小
学”。清末民居开始进入古泮池,
20 世纪 90 年代形成“池涯社区”
与“阙里社区”。
(钦白兰摄,2013年4月27日)
古泮池水道淤废,孔孟文化遗产
地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将古泮池整
治列为子项目,水道纳入城市水
系加以疏通。世界银行修复项目
审核专家建议此地作为遗产缓冲
区。
今日古泮池:
(钦白兰摄,2013年8月25日)
(接上表)
21
DNWH
遗址历史空间的深度绘图及其经义接续
是教育话语悄无声息的影响力,这就是古代经义
对当下永恒不变的关照。我们看到,直到民国,这
一空间走向总是贯穿着经学大义,我们将其表述
为“文脉流通”,但遗憾的是,从日本学者驹井和
爱考古报告(表一:1951 年)问世后,“经义空间”
从表述到思维突然发生历史突变,考古话语成为
理解遗址的权威甚至唯一方式。近几十年来,在
西方权威遗产话语操控下(政府话语、专家话语
等),此地空间认识及遗产实践则困在文物保护
与科学治理中。今天,泮水遗址的经义空间已被
隐藏,取而代之的是“文物保护单位”、“遗产缓冲
区”、“旧城改造区”、“生态宜居水城”、“旅游景
点”、“宾馆”、“水治理”等等现代话语。目前古泮
池居民搬迁已经完成,这里的空间即将得到再次
整修,专家多次论证的结论是“古泮池地区最好
恢复清代时期的范围”[57],但依照历史空间的深
度绘图,我们觉得任何一个时代的物质布局都不
足以成为当下遗产修复的依据,但任何时代的遗
迹都值得以某种残缺的方式加以再现。显而易
见,物质遗迹以文物形式存在远远不如小学更加
能够对接经义文脉源流,这也是为何我们说今天
文物遗产观不能实现文化传承的功能。我们还可
以看到,遗产实践决策话语中对于生态环境的重
视,而对于历史遗址的复杂性及本土多元意义却
有所忽视,如此一来,碑刻瓦当成为供人鉴赏的
艺术收藏品,今天曲阜论语碑苑、汉魏碑刻陈列
馆收藏的大都是古人为了保护文脉而留下的空
间标识。如今石碑尚存,空间已被遗忘。而那些永
远都无法抹去的经义空间,如今让人感觉不到“令
人敬畏”的空间厚重感,这样的遗址利用方式与“中
国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力”[58]是不
吻合的。
四 结语
遗址的开发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如何让它成
为令人敬仰的“历史空间”。今日,中国文化遗址
保护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伴随而来的是借用西
方话语范式的博物馆、文化馆、遗址公园纷纷建
立,全国各个历史文化名城中,大量“非标志性”
(non-monumental)的古迹、商铺、街巷、民居等在
近百年的改造中大都消失殆尽,以致体现仁里坊
巷文化脉络的有形承载物和空间布局毁于一旦。
博物馆最大贡献在于它带来了美学、艺术的视觉
享受,但是,它也将生活与文化割裂开来,留下的
仅仅是过去化石的展陈[59];遗址公园的开发将历
史场所转换为一道城市景观古旧风景线,但这一
风景线要传承的古意在哪里却缺乏思考[60]。旅游
化的结果使遗址成了市场经济的附庸,一方面,原
住民的生活方式被边缘化,多元文化空间转化为
旅游景点;另一方面,游客匆匆到此一游,地方多
元文化体验成了线性排列似的走马观花[61]。总而
言之,中国大遗址与意大利古遗址比,价值与意
义截然不同。古罗马斗兽场的可贵在于珍视久远
的过去,因为千年之前留下的石块不可再生;而
中国文化遗产不因物质原真性而珍贵,它关心的
历史空间里留下的经义如何贯穿古今,以见先圣
之德泽之远,惠济当下。
一百多年前,因为西方传教士意图于“古泮
池”边建教堂,该空间的文脉(经义)很有可能被
割断,所以衍圣公孔令贻挺身而出,“于池之北岸
建筑文昌祠,借以抵制西人也”[62];在西方工业引
入中国之时,他还曾阻止铁路通过曲阜古城区,
以免破坏孔林之圣脉。今天,仍然有人认为孔令
贻的做法是阻碍时代的进步,阻碍了曲阜经济文
化发展。殊不知,他保护了曲阜历史空间免遭现
代化的破坏,如果没有这种“文脉”空间意识,曲
阜早已与中国圣地无关了。今天古泮池的历史空
间正面临深度改造,地方政府在不同的规划版本
中劳心劳力。我们如何能从深度绘图中看到寄托
于这一空间里的不同时代的历史碎片?如何让这
些碎片,以多样性的方式叙述不同时代的教化故
事?如何能够恢复续接经义文脉的教育场所?最
重要的是,如何让“思乐泮水”的经义源流,以通
古达今的空间语言再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至
于孔孟,圣圣相承的中华文脉?这是遗址保护和
利用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致谢:我们的田野考察及史料搜集,得到曲
阜市文物局、曲阜文史资料文员会、曲阜市图书
馆,仓巷与龙虎社区居民,浙江大学跨文化研究
所文化遗产研究团队,以使命感精神的大力协
助,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1]侯松、吴宗杰:《遗产研究的话语视角:理论·方法·展
望》,《东南文化》2013年第3期;吴宗杰:《话语与文化遗
产的本土意义建构》,《浙江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2]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 M.Sheridan Smith (trans.) 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2.
[3]The Venice Charter:International Charter for The Conserva⁃
tion and Restoration of Monuments and Sites,1964. Con⁃
22
DNWH
《东南文化》2014年第4期总第240期
vention of Heritage Protection: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1972. The Burra Charter:The Australia ICOMOS Char⁃
ter for Places of CulturalSignificance,2013.[4]“大遗址”概念始见于《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
知》(1997 年),付建:《大遗址保护的历程》。[EB/OL][2011-04-27]http://www.wenwu.gov.cn/contents/234/13019.html.
[5]Smith,L. Uses of Heritage. London:Routledge,2006;侯松、吴宗杰:《遗产研究的话语视角:理论·方法·展望》,
《东南文化》2013年第3期;吴宗杰:《话语与文化遗产的
本土意义建构》,《浙江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6]Laurajane Smith.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Heritage. London:Routledge,2004.[7]钦白兰、吴宗杰:《历史的空间转向与遗址的古今会
通》,《文化艺术研究》2013年第 3期;彭兆荣:《遗产:反
思与阐释》,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8年;吴宗杰、侯松:《批
评话语研究的超学科与跨文化转向——以文化遗产的
中国话语重构为例》,《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2年
第 6 期;Waterton,E. 2010. Politics,Policy and the Dis⁃
courses of Heritagein Britain.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
[8]Warf,B.,& Arias,S.(eds).The Spatial Turn:Interdisci⁃
plinary Perspectives.New York:Taylor & Francis,2008;Bodenhamer D. The Potential of Spatial Humanities. In:Bodenhamer D.J.,Corrigan J. and Harris TM(eds)The
Spatial Humanities:GIS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ies
Scholarship.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0;Bol PK. On the Cyberinfrastructure for GIS-Enabled
Histori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2013;103(5):1087-1092.
[9]乔好勤:《行走书林 乔好勤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第141页。
[10]Bodenhamer D. The Potential of Spatial Humanities. In:Bodenhamer D.J.,Corrigan J. and Harris TM(eds)The
Spatial Humanities:GIS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ies
Scholarship.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0.
[11][13]Bodenhamer D.J. Beyond GIS:Geospatial Technolo⁃
gies and the Future of History. In:von LünenA. and Trav⁃is C.(eds)History and GIS Epistemologies,Consider⁃
ations and Reflections. New York:Springer, 2010;Bodenhamer D,Corrigan J,and Harris TM.(eds)Deep
Maps and Spatial Narrative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4.
[12]David J. Bodenhamer 教授系美国“空间人文学”创始
人,美国印第安纳普渡大学地理信息中心主任,国际
杂志《人文艺术与计算机技术》,《人文艺术电子技术》
主编,著有《空间人文学:地理信息系统与未来人文
学》(2013)等。
[14]此文献来自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数据库。
[15]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清·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清皇清经解本。
[17]宋·王应麟:《诗地理考》明津逮秘书本。
[18]吴宗杰:《重建坊巷文化肌理:衢州水亭门街区文化遗
产研究》,《文化艺术研究》2012年第2期。
[19]王云五主编:《圣门志》(4),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89页。
[20]孔庆第(曲阜市住建局规划科原科长):《明城保护规
划资料·古泮池》,2005年,第2页。
[21]“泮水”名称与位置数经变迁,史料显示不一,比如:明
代《兖州府志》泮水,又曰:雩水,乾隆《兖州府志》雩
水,即:泮水;乾隆《曲阜县志》泮水,名曰:文献泉。
[22]据田野调查笔记整理(2013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7 日)。
参见:Young,Sara B. Cultural Memory Studies:An Inter⁃
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 eds. AstridErll,and AnsgarNünning. Vol. 8. Walter de Gruyter,2008.
[23]据池北街 73号李家爷爷口述。2012年 4月 27日,我们
来到正在拆迁的古泮街区,李家是唯一几户还滞留未
离开的家庭。
[24]据古泮池张家爷爷、女儿口述。2012年 4月 27日,我们
经过五马祠街与池北街路口,采访了正在搬家的张家
爷爷,4月 28日,再次经过他们家,我们采访了张家女
儿。
[25]据原池东街 2号孔凡成口述。现孔凡成一家老小,现租
房住在青年路3巷5号。
[26]西汉·司马迁:《全本史记大全集》(珍藏本),华文出版
社2010年,第198页。
[27]周光庆:《由中国训诂学走向中国解释学》,《长江学
术》2009年第3期。
[28][42]李鸿渊:《孔庙泮池之文化寓意探析》,《学术探
索》2010年第2期。
[29][39]吴孟复、蒋立甫主编:《古文辞类纂评注》(下册),
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303页。
[30]曲英杰:《汉鲁城灵光殿考辩》,《中国史研究》1994年
第1期
[31]高莉芬:《图写神圣: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与辞赋宫
殿书写的转变》,《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32]车吉心、梁自洁、任孚先:《齐鲁文化大辞典》,山东教
育出版社1989年,第902页。
[33]据田野调查笔记和采访录音整理(2013年5月1日)。
[34]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Blackwell,1991.
[35]清·潘相修:《(乾隆)曲阜县志》,康熙十二年刻本。
[36]清·穆彰阿:《(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六十五、一
23
DNWH
遗址历史空间的深度绘图及其经义接续
百六十六,《四部丛刊续编》景旧钞本。
[37]陈戌国点校:《四书五经》(上册),岳麓书社,1991年,
第419页。
[38]Bodenhamer D.,Corrigan J. and Harris TM.(eds)Deep
Maps and Spatial Narrative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4.
[40]陈庆元编:《水经注选注译本》,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1年,第144页。
[41]孟继新:《孔子家史》,远方出版社2003年,第162页。
[43]清《曲阜县志》(乾隆刻本)卷二十七,第三之十三页。
[44][45][48][51][52]浙江大学跨文化研究所:《古泮池
通义辑览》(《鲁国故城古迹经注》),浙江大学跨文化
研究所2014年。
[46]《明史》卷一百八十一,”列传”第六十九。同文书局石
印本。
[47]明·李东阳:《南溪赋》,《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
方典》,第二百四十五卷“兗州府部”,“艺文”三。
[49]清《曲阜县志》(乾隆刻本),卷二(“奎文”第一之二)
“圣祖仁皇帝御制诗”,《古泮池杂咏六首》。
[50][62]李经野等纂修:《续修曲阜县志》(民国 23 年铅
本),成文出版社印行。
[53]孔庆第(曲阜市住建局规划科原科长)提供,2013年 12月29日。
[54]山东省曲阜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曲阜市志》,
齐鲁书社1993年,第146页。
[55][56]《曲阜市明故城控制性详细规划》、《曲阜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规划》(2011 年 12 月 28 日),政府文件,曲
阜市文物局提供。
[57]《曲阜明故城古泮池片区改造工程方案》专家论证意
见(2013 年 10 月 24 日),政府文件,曲阜市文物局提
供。
[58]《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EB/OL][2005-10-22],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
content_185117.htm.[59]Gimblett,B. K.(eds)Destination Culture:Tourism,Mu⁃
seums,and Herit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60]Smith,L.&Waterton E. Heritage,Communities and Ar⁃
chaeology. London:Gerald Dockworth& Co.,2009.[61]Smith L.,Waterton E.and Watson S.(eds), The Cultural
Moment in Tourism. New York:Routledge,2012.
Renew the Past by Deep-Mapping the Historical Space on Heritage SitesQIN Bai-lan1 WU Zong-jie1 FENG Yang2
(1.Institute of Cross-cultural Studies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2.Management Office of the Capital-City-of-the-Lu-State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 Qufu, Shandong,
273100)Abstract: The current conservation and use of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CHS) have been domi⁃
nated by western“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AHD), which often leads to the dichotomy between timeand space as well as material forms and intangible values. As a result, heritage sites are often prevented fromfunctioning as a cultural interplay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Drawing on a case study from the PanRiver, a sacred site in ancient Lu Kingdom of Confucius’home place, this paper adopts the idea of“deepmapping”to explore the canonical meanings conveyed by the site through historical textual data. The vari⁃ous layers of meanings that were hidden in the historical space of the site as well a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are thus unfolde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nservation and use of heritage sites in China should break downthe boundaries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and of the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so as to construct a space where ca⁃nonical meanings are brought in view for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insights.
Key words: cultural heritage site; historical space; deep mapping; Pan River; canonical meaning
(责任编辑、校对:王 霞)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