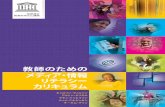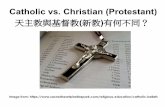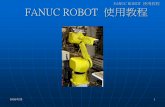“Is It not Pleasant to Learn with a 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 English Translations...
Transcript of “Is It not Pleasant to Learn with a 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 English Translations...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晚清新教传教士的《论语》英译 43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晚清新教传教士的《论语》英译
姜 哲
一 晚清时期的《论语》英译
第一部在西方刊印的《论语》译本,是由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 Philippe Couplet,1623—1693) 等人用拉丁语完成的,其书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子,或以拉丁语表述中国人
的智慧》(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 ,1687 年出版于
法国巴黎。① 除《论语》之外,这部书中还包括《大学》和《中庸》的译文以及译者们撰写或
编译的一些资料。② 次年,在阿姆斯特丹又出版了该书的法语编译本,书名为《中国哲学
家孔子的道德教训》( La Morale de Confucius,philosophe de la Chine) 。③ 而 1691 年这个法
*
①
②
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经典英译本汇释汇校”( 项目批准号: 10&ZD108 ) 的阶
段性研究成果。Philippe Couplet et al. ,trans.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
Parisiis: Apud Danielem Horthemels,1687.按: 以西文对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进行翻译的历史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详情可参见[法]
梅谦立( Thierry Meynard) :《〈孔夫子〉: 最初西文翻译的儒家经典》( 见《中山大学学报》,2008 年第 2 期,
第 131—142 页) 及李新德:《耶稣会士对〈四书〉的翻译与阐释》( 见《孔子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98—107 页) 。
按: 很多中国学者都认为该书的中文书名为《西文四书直解》,笔者手里有该书的电子版,翻检
几遍却并未发现这个所谓的中文书名。查找相关资料而得之,这一说法似应源于法国学者费赖之
( Louis Pfister)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1552—1773) 》(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 - 1773) ,在该书 1932 年法文版第 311 页确有这一表述,但未
作具体说明。于是,笔者就此问题先后请教了中山大学法国学者梅谦立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学者罗莹。梅谦立在信中表示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里面没有汉字,因为在当时欧洲无法使用。但是,该书
的注释确实大都依据明人张居正( Cham Kiu Chim) 的《四书直解》,至于费赖之是否看到所谓的中文书
名,他也无从得知。罗莹也非常确定地表示,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一书,不管是现在藏于法国巴
黎国家图书馆的手稿,还是现在 Google Book 上不同图书馆所藏的印本,都没有出现过“西文四书直解”的字样。此外,她还进一步指出,费赖之的著 作 所 本 的 是 柏 应 理 用 拉 丁 文 编 纂 的 Catalogus patrumSocietas Jesu( 1686) 一书,而柏应理所本的又是韩霖、张庚的《圣教信证》( 1647) ,该书在“殷铎泽”的传记
部分列出了他的一部著作为《西文四书直解》( 三卷) 。韩、张二人作此书时,柏应理还未在巴黎出版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这说明“西文四书直解”这一标题最早可能是用于指称殷铎泽当时已经完
成的一些“四书”拉丁文译本。Jean de La Brune,trad. ,La Morale de Confucius,philosophe de la Chine,Amsterdam: Pierre
Savouret,1688.
44 《中国文化研究》2013 年春之卷
语编译本的英语转译本又在英国伦敦出版,书名为《孔子的道德箴言———一位中国哲学
家,他的鼎盛期在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降生前 500 多年———本书是该国知识遗产的精
粹之一》( 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Who Flourished Above Five HundredYears Before the Coming of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 Being One of the Most ChoicestPieces of Learning Remaining of That Nation. ) 。①
既然《孔子的道德箴言》是一个转译本,那么,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论语》英译本,应
该归于在印度传教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士曼( Joshua Marshman = J. M. ,1768—1837 ) 。1809 年,马士曼在印度塞兰坡出版了《孔子的著作,包括原文及译文》( The Works ofConfucius,Containing the Original Text,with a Translation) 的第一卷。② 然而,该书并非
《论语》的英文全译本,因为这一卷中只包括《论语》“学而”第一至“乡党”第十的内容,而
第二卷则始终未见刊印发行。《论语》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可能要记在另一位英国新教
传教士高大卫( David Collie = D. C. ,? —1828 ) 的名下。1828 年,高大卫的“四书”英译
本在当时为英国殖民地的马六甲出版,其书名为《通常被称为“四书”的中国经典著作,译
文及注释》( 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 Translated,andIllustrated with Notes) 。③ 该书既可能是《论语》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也可能是“四书”的
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在此之后,新教传教士的《论语》英译主要有理雅各( James Legge =J. M. ,1815—1897 ) 、④詹 宁 斯 ( William Jennings = W. J. ,1847—1927 ) ⑤和 苏 慧 廉
(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 W. S. ,1861—1935) ⑥。当然,在此期间也有一些其他的译本出现,它们分别是威妥玛(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 的《论语: 被西方世界作为 Confucius 而知晓的孔子的言论》( The Lun Yü:
Being Utterances of Kung Tzǔ,Known to the Western World as Confucius) 、⑦翟林奈( LionelGiles,1875—1958) 的《孔 子 的 言 论: 包 括〈论 语〉大 部 分 的 新 译 本》( The Sayings ofConfucius: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onfucian Analects ) ⑧和 赖 发 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Who Flourished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Coming of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 Being One of the Most Choicest Pieces of Learning Remaining ofThat Nation. ,London: Randal Taylor near Stationers Hall,1691.
Joshua Marshman,trans. ,The Works of Confucius,Containing the Original Text,with a Translation,
vol. I,Serampore: The Mission Press,1809.David Collie,trans. ,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 Translated,and
Illustrated with Notes,Malacca: The Mission Press,1828.James Legge,trans.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and Copious Indexes,vol. I,Hong Kong: At the Author’s; London: Trübner & Co. ,1861.William Jennings, trans. , The Confucian Analects: A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 and an
Introduction,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1895.William Edward Soothill,tran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Yokohama: Fukuin Printing Company,
1910.Thomas Francis Wade,trans. ,The Lun Yü: Being Utterances of Kung Tzǔ,Known to the Western
World as Confucius,Hertford: S. Austin,1869.Lionel Giles,trans. ,The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onfucian Analects,London: J. Murray,1907.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晚清新教传教士的《论语》英译 45
( Leonard A. Lyall,1867—?) 的《论语》( The Sayings of Confucius) 。① 上述译者虽然也都
应该有着某种宗教背景,但是由于他们的身份并不是传教士,所以本文在此暂不论及。此
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史景迁( Jonathan Spence,1936—) 在一篇有关比利时裔澳大
利亚学者西蒙·莱斯( Simon Leys,1935—) 《论语》英译本②的“书评”中,似乎认为英国公
理会传教士( Congregationalist missionary) 麦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 ) 在
1840 年也有一个《论语》译本,其中《新约》、《旧约》的段落常常被插入其中以引出道德和
宗教的教训。③ 考之英国新教传教士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1815—1887) 所著的《来
华新教传教士备忘录: 著作列表及已故者讣告》(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史景迁所
说的“译本”应为《论语新纂》( Lún Yù Sin Tswan) ; 然而,在麦都思这一条中,所列著作按
语言类别分为三类: 汉语、马来语和英语,《论语新纂》被列在汉语著作之中; ④所以,史景
迁在讨论《论语》英译的语境下,突然提到这部著作确实令人感到有些“言之不当”。
二 “学习”汉字与以“思”释“习”: 马士曼与高大卫的《论语》英译
在对晚清《论语》英译的情况有了一个大致了解之后,本文即将对这一时期新教传教
士的《论语》译本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 然而,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仅以《论语》“学而”篇
第一章第一节为例,⑤即“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来具体展开这一分析,并期望能够得
到些许“管窥”之见。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需提及同一时期一位中国学者的《论语》英译本,即辜鸿铭( Ku
Hong-Ming = Ku,1857—1928) 的《论语: 新颖而别致的译本,以引用歌德和其他作家来进行阐
释》(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 。⑥ 由于辜鸿铭的译本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源于对
新教传教士《论语》英译的不满( 尤其是对理雅各) ,⑦所以本文也将他的译文列在最后,而
其他译文则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现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英译文本排列如下:
J. M. I. 1. Chee says,learn; and continually practise. Is it not delightful!D. C. I. 1. Confucius says,to learn and constantly digest,is it not delightful!J. L. I. 1. The Master said,‘Is it not pleasant to learn with a 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
①②③
④
⑤⑥
⑦
Leonard A. Lyall,trans. ,The Sayings of Confucius,London: Longmans,Green and Co. ,1909.Simon Leys,tran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New York: W. W. Norton,1997.Jonathan Spence,“What Confucius Said,”rev.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by Simon Leys,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0 Apr. 1997,p. 8.Alexander Wylie,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Shangha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p. 31.按: 后文所列六种《论语》译文,其章节划分悉按理雅各在《中国经典》中的方式。Ku Hong-Ming,trans.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New Special Translation,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Shanghai: Kelly and Walsh,1898.Ku Hong-Ming,preface,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New Special Translation,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by Ku Hong-Ming,trans.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1898,p. vii.
46 《中国文化研究》2013 年春之卷
W. J. I. 1‘To learn,’said the Master,‘and then to practise opportunely what onehas learnt—does not this bring with it a sense of satisfaction?
W. S. I. 1 The Master said; “Is it not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constantly to exercise oneself therein?
Ku. I. 1 Confucius remarked,“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asyou go on acquiring,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在上述文本中,我们首先来看马士曼的译文。在与其他译文相较之后,我们即会发现,马
士曼《论语》英译的最大特点就是其译文的语序几乎与汉语原文完全一致,并且对应的中
英文之间还标有相同的数字号码。显然,这是出于汉语学习的一种需要,诚如其在该译本
的“献词”中所言: 他的译介所采用的形式,不仅希望可以传达中国文学的观念,而且要对
学习这种奇妙而繁难的语言有所助益。① 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士曼译本的注解
( comment) 是对朱熹( 1130—1200) 《四书章句集注》的直接翻译,而他本人的观点则体现
在注释( notes) 和对汉字的附注( remarks on the character) 中。② 《四书章句集注》对“学
而”一句的注释为:
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
复其初也。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说,喜意也。既学而又时时习之,
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程子曰:“习,重习也。时复思绎,浃洽
于中,则说也。”又曰: “学者,将以行之也。时习之,则所学者在我,故说。”谢氏曰:
“时习者,无时而不习。坐如尸,坐时习也; 立( 一) 如齐,立时习也。”③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高大卫的译文,这句译文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对“习”的翻译上,其他译
本大都将其译为“practise /practice”,而高大卫则译为“digest”。其在页下对此句的注释
为:“当由学习而获得的知识通过长久反复的冥想而完全成熟并精美地铸刻于内心之时,
它就成为了纯粹的快乐之源。”( When the knowledge we acquire by study,is by long andrepeated meditation perfectly matured,and wrought into the mind,it becomes a source of puredelight. ) ④尽管高大卫在“序言”中曾表明,“页下的脚注并非是对任何一个注释者的逐字
翻译,而是体现了各种不同注释的主旨”; ⑤然而,我们还是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一注释
与《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所引程颐( 1033—1107 ) 之说———“时复思绎,浃洽于中,则说
①
②
③④
⑤
Joshua Marshman,dedication,The Works of Confucius,Containing the Original Text,with aTranslation,vol. I,by Joshua Marshman,trans. Serampore: The Mission Press,1809,p. ii.
Joshua Marshman,trans. ,The Works of Confucius,Containing the Original Text,with a Translation,
vol. I,p.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47 页。David Collie,trans. ,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 Translated,and
Illustrated with Notes,Gainesville: Scholars’Facsimiles & Reprints,1970,p. 63.按: 该书的初版本为 1828 年版,但本文使用的是 1970 年版。这主要是因为该版前增加了威廉·斯
坦( William Bysshe Stein) 的“导言”,并在保留原书每一部分使用单独页码的同时还增加了连续页码,这
使得引用出注变得更加方便,本文使用的即为连续页码。David Collie,trans. ,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 Translated,and
Illustrated with Notes,p. 8.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晚清新教传教士的《论语》英译 47
也”———极为接近。实际上,此句原出于《河南程氏经说·卷第六·论语解》。① 而《四库
全书总目·经部·五经总义类·程氏经说》则指出: “不著编辑者名氏,皆伊川程子解经
语也。……其中若诗书解、论语说,本出一时杂论,非专著之书。”②可见,此句为程子一时
之感发,并非着意解经。而朱熹之所以又在其后补上程子之另一说,就是为了避免读者仅
观前一说而失于偏颇。此后一说之全文在《河南程氏外书》中为:“学而时习之。所以学
者,将以行之也。时习之,则所学者在我,故说。习,如禽之习飞。”③综合程子之二说,我
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学”、“思”、“行”、“习”在程子的思想中具有内在一贯的特
点。当然,我们若以此作为《论语》中孔子思想的重要特征,大概也不会导致太大的偏差。至于高大卫为什么以“digest”来译“习”,而又以“meditation”来解释“习 /digest”,我认
为这与他对《论语》及孔子的理解有关。在该译本的“序言”中,高大卫认为: “《论语》中
充斥着人们所谓的老生常谈 ( truisms) ,重复的话语也随处可见。”④而在“孔子略传”( “Memoirs of Confucius”) 中,高大卫又表示: “在他( 孔子) 全部著述的范围之内,从未向
我们展现出一个独创的观念,可以超越任何一个常人所惯于思考的领域。”⑤高大卫这种
“质疑基督教传统以外所有道德体系之合法性”的立场,⑥使得我们不难理解他对“习”这
一《论语》中的重要概念进行翻译和释义时所表现出的粗疏与草率。“思”固然是一种
“习”,然而绝非其全部。程子虽可以说是以“思”释“习”,但又以“行”释之,而后者显然
更为妥当与全面,也更符合儒家“学”、“行”一致的特点。威廉·斯坦( William ByssheStein) 在为高大卫译本 1970 年版所写的“导言”中对孔子的思想给出了下面的评述:
孔子对道德的形而上定义几乎毫无兴趣。他首先关注的是经验性( empirical) 的
现实———人类的行为对于减轻苦难和增进幸福所具有的影响力。对于他而言,知识
本身没有任何意义,除非它可以使社会和政治生活变得富有活力。⑦我认为威廉·斯坦的这段评述在某种意义上恰好纠正了高大卫以“思”释“习”的狭隘化
解释。而另一方面,高大卫的这一解释本身也典型性地暴露了他在翻译 /诠释儒家经典时
的“诠释态度”和“先入之见”。
①②
③④
⑤
⑥
⑦
《河南程氏经说·卷第六·论语解》,同治十年六安求我斋刊板,第 1 页 a。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年影印浙江杭州本,第 270 页下栏—第
271 页上栏。《河南程氏外书·第七·胡氏本拾遗》,同治十年六安求我斋刊板,第 4 页 a。David Collie,trans. ,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 Translated,and
Illustrated with Notes,p. 6.David Collie,trans. ,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 Translated,and
Illustrated with Notes,p. 14.按: 括号里的字为笔者所加。
William Bysshe Stein,introduction,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Translated,and Illustrated with Notes,by David Collie,trans. Gainesville: Scholars’Facsimiles & Reprints,1970,p. xvi.
William Bysshe Stein,introduction,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Translated,and Illustrated with Notes,by David Collie,trans. p. x.
48 《中国文化研究》2013 年春之卷
三 “学”、“行”合一与“适时”而“习”: 理雅各与詹宁斯的《论语》英译
与高大卫以“思”释“习”不同,理雅各对“学而”一句中“习”的理解明显强调了其作
为“实践”、“践履”的意义内涵。与马士曼相同,理雅各也主要参考了朱熹的注释,将
“习”解释为“鸟数飞也”,并进一步指出其表示“to repeat”、“to practise”。① 然而,值得注
意的是,在正文的翻译中理雅各并未使用较为常用的“practise /practice”来翻译“习”,而
是同时使用了两个英文单词“perseverance”和“application”。② 不过,理雅各对这两个词
的选用似乎并不像高大卫选用“digest”那样随意。我们首先来看“perseverance”,它源于动词“persevere”,《牛津英语大辞典》(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对该词的解释主要为:“持续而坚定地处于某一行动过程之中( 过去也
可以指处于某种处境、状态或意志之中) ,尤其指面对困难或阻碍; 保持忠诚或始终如
一。”③因此,作为名词的“perseverance”,其主要意义即为“坚定”、“固守”、“毅力”等等。然而,“perseverance”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也许正是这个意义才促使理雅各选用该
词———“持续地蒙受神恩( grace) 并最终达至荣耀( glory) ”。④ 但对于这一意义,《国际标
准〈圣经〉百科全书》(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又给出了两种解释:
通过引用约翰福音( 6: 37; 10: 28; 17: 6 - 11) 和罗马书( 8: 31 - 39) ,一些解释者
认为某人 一 旦 得 救,便 不 会 再 失 于 获 救。而 其 他 解 释 者 则 坚 称 只 有 那 些 坚 持
( persevere) 到最后的人才能成圣。他们引用路加福音( 8: 9 - 15) 、加拉太书( 5: 4) 和
希伯来书( 2: 1 - 4; 3: 7 - 4: 13; 6: 4 - 6) 来证明,如果某人拒信基督耶稣便会因此而
失于获救。⑤
鉴于《论语》的诠释语境,我认为理雅各似乎更应该趋向于后者。此外,在“perseverance”之后还有“application”一词,《牛津英语大辞典》对该词的一个重要解释为: “使某事物对
另一事物产生实际的影响,在神学中特指‘基督完成的救赎( redemption) ’。”⑥
通过上述的词义分析,我们似乎很容易得出“过度诠释”( overinterpretation) 的结论,
或者从后殖民主义( post-colonialism) 的角度指出理雅各是在有意以基督教的概念替换甚
至歪曲儒家思想中所固有的概念。然而,问题似乎并非如此简单。杨慧林在《理雅各: 文
①
②
③
④⑤
⑥
James Legge,trans.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Prolegomena,and Copious Indexes,vol. I,p. 138.
按: 理雅各的《中国经典》有三个最重要的版本: 第一个是 1861—1872 年的初版本,第二个是前两卷
经过重要修订的 1893—1895 年版,第三个是香港大学编辑修订的 1960 年版。本文使用的即为最后一
个版本。James Legge,trans.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and Copious Indexes,vol. I,p. 138.John Simpson and Edmund Weiner,eds.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vol. XI,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9,p. 593.John Simpson and Edmund Weiner,eds.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vol. XI,p. 593.Geoffrey W. Bromiley,ed.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K-P,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1986,p. 776.John Simpson and Edmund Weiner,eds.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vol. I,p. 575.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晚清新教传教士的《论语》英译 49
学与宗教之间》( “James Legg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一文中即已指出: 由于基
督教的背景,理雅各在老子《道德经》的翻译上常常比中国的现代译者们具备更好的“前
理解”( pre-understanding ) 。① 其 实,这 也 同 样 适 用 于《论 语》,以“perseverance”和
“application”来翻译“习”就特别能体现出儒家“学”、“行”一致中所蕴涵的“坚韧”与“勇
毅”。《论语·里仁》载曰:“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
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
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正是因为“perseverance”中包
含着强烈的宗教内涵,所以才更加突出了儒家君子无论“造次”还是“颠沛”都不改于
“仁”的践履精神。而明人焦竑( 1540—1620) 在《焦氏笔乘》所辑之语录中,亦有以此句解
“学而时习之”之例。③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詹宁斯的译文,他的特别之处体现在对“时”的翻译上。其他译
者大都使用“continually”( 不断地) 或“constantly”( 经常地) 及“constant”( 经常的) ,而詹
宁斯却使用了“opportunely”( 适时地) 。在其译本的“导言”中,詹宁斯曾指出:
我绝对不能忘记表示我对理雅各博士的感激之情,他在《中国经典》中提供了宝
贵的资料。然而,我还是经常敢于表达出与他相左的意见; 你们也会看到我还独立阅
读了大量的汉语注释,有时我也敢于表现出不同于它们的观点。④尽管詹宁斯在“时”的翻译上与理雅各不同,但是他的译文选择仍然可以在中国传统注疏
中找到根源。《礼记·学记》即曰:“当其可之谓时。”⑤这个“时”就有“适时”的含义。清
人焦循( 1763—1820) 在《论语补疏》中亦以此来解“学而”一句,其曰: “当其可之谓时。说,解悦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时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
时也。‘求也退,故进; 由也兼人,故退’,时也。学者以时而说,此大学之教所以时也。”⑥众所周知,新教传教士的《论语》译文大都参考朱熹的注释,如前文所引,朱熹将“时”
解释为“时 时”,因 此 才 有 了“continually”或“constantly”的 翻 译。然 而,近 人 杨 伯 峻
( 1909—1992) 在《论语译注》中业已指出:
“时”字在周秦时候若作副词用,等于《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的
“以时”,“在一定的时候”或者“在适当的时候”的意思。王肃的《论语注》正是这样
解释的。朱熹的《论语集注》把它解为“时常”,是用后代的词义解释古书。⑦因此,詹宁斯在这里将“时”译为“opportunely”确实更为接近《论语》原文的意义内涵。而
朱熹以“时时”或“时常”来释“时”字,似乎亦与宋儒所谓的“功夫论”不无关系。
①
②
③④
⑤⑥⑦
YANG Huilin,“James Legg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Religion,”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2011 /1,No. 337,p. 89.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见《十三经注疏》,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世界书局阮元
校刻本( 下册) ,第 2471 页上栏。焦竑辑:《焦氏笔乘·卷一》,见粤雅堂丛书( 第一集) ,清道光三十年刻本,第 1 页 a—b。William Jennings,introduction,The Confucian Analects: A Translation,with Annotations and an
Introduction,by William Jennings,trans.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1895,p. 36.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见《十三经注疏》,第 1523 页上栏。焦循:《论语补疏》,见《皇清经解》( 卷一千一百六十四) ,清咸丰十年补刊本,第 1 页 a。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1 页。
50 《中国文化研究》2013 年春之卷
四 “人伦”之“学”与“知识”之“学”: 苏慧廉与辜鸿铭的《论语》英译
尽管苏慧廉在其《论语》译本的“序言”中,曾明确表示这是“一个全新的译本”; ①然
而,仅就“学而”一句来说,其译文并无多少新意,只是在“习”的翻译上稍显特别。当然,
苏慧廉并非如高大卫那么轻率,也不如理雅各那么大胆,他只是选择了一个与多数译者所
用的“practise /practice”较为接近的词汇“exercise”。这一选择是否为了与其他译本相区
别,我们已不得而知。不过,苏慧廉在上述“序言”中已经指出,在翻译之时他“对前辈们
的解释未作任何参考”,只是在译罢之后,才参照理雅各、意大利耶稣会士晁德蒞( AngeloZottoli,1826—1902) 、辜鸿铭以及法国耶稣会士顾赛芬( Séraphin Couvreur,1835—1919) 的
译本进行了修正和校释。② 在这四个译本中,晁德蒞的为拉丁语译本,③而顾赛芬的则是
法语和拉丁语的双语译本。④尽管如此,苏慧廉对“exercise”的选用是否与这四个译本有直接关系,我们仍旧很难
得出定论。不 过,其 中 晁 德 蒞 的 拉 丁 语 译 文 很 值 得 我 们 注 意,“学 而”一 句 被 译 为
“Confucius ait: studere sapientiae et jugiter exercere hoc,nonne quidem jucundum”。⑤ 很明
显,英语“exercise”正是源于拉丁语“exercere”。“exercere”是不定式形式,它的现在时第
一人称单数为“exerceo”,其主要意义之一是“训练”( to train by practice) ,既包括身体上也
包括智力上的活动; 此外,它还有“运用”、“应用”、“实践”等意义内涵。⑥ 而苏慧廉自己
对“习”的解释则为“practice,exercise,a verbal noun,( Kuan. 操练) ”。⑦ 可见,二者在意义
内涵上确实较为接近。至于苏慧廉将“习”理解为“exercise”或“操练”是否恰当与准确,
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暂且不论。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前述柏应理主编的拉丁语译本
中,“习”被译作“exercitare”,⑧该词与“exercere”是同源词,而且意义也基本相同。在辜鸿铭的译本中,其将“习”译作“put into practice”,这与“practise”的意义并无多
少分别。平心而论,“put into practice”确实要比理雅各的“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更
为通俗和流畅。然而,由于理雅各《中国经典》的读者对象首先是传教士,⑨所以他们必
①
②
③④
⑤⑥⑦⑧
⑨
William Edward Soothill,preface,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by William Edward Soothill,trans.Yokohama: Fukuin Printing Company,1910,p. ii.
William Edward Soothill,preface,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by William Edward Soothill,trans. pp.ii-iii.
Angelo Zottoli,trans. ,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vol. II,Chang-hai: Missionis Catholicae,1879.Séraphin Couvreur,trad. ,Les Quatre livres: avec un commentaire abrégé en chinois,une double
traduction en franais et en latin,et un vocabulaire des lettres et des noms propres,Ho Kien Fou: Imprimerie dela Mission catholique,1895.
Angelo Zottoli,trans. ,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vol. II,p. 211.Alexander Souter,et al. ,eds. ,Oxford Latin Dictionary,Oxford: Clarendon Press,1968,p. 640.William Edward Soothill,tran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p. 119.Philippe Couplet et al. ,trans. ,Ratiocinantium Sermones,in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Parisiis: Apud Danielem Horthemels,1687,p. 2.James Legge,preface,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and Copious Indexes,vol. I,by James Legge,trans. Hong Kong: At the Author’s; London:
Trübner & Co. ,1861,p. ix.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晚清新教传教士的《论语》英译 51
然会对这两个语词中所蕴涵的宗教意义感到十分熟悉和亲切。而颇为有趣的是,这种熟
悉和亲切之感也正是辜鸿铭《论语》英译的主要目标,只是他的读者对象首先是不懂中文
的普通英语读者。在《论语》英译本“序言”中,辜鸿铭表达了自己的翻译目的:
因此,翻译这本小书的目的……在于使这本獉獉
书所给予中国人的智慧和道德,对于
普通的英语读者而言也是唾手可得的。以此为目标,我们力求使孔子及其弟子以与
有教养的英国人相同的方式来进行言说,如果他不得不表达与这些中国圣贤相同的
思想。……最后,为了确保文本中思想的重要性,我们还引用了许多熟悉的欧洲作家
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一系列已经熟知的思想,这些引用也许会引起了解这些作家的
读者们的兴趣。①对于最后一种处理方式,辜鸿铭译本的书名就是最好的标志,其为《论语: 新颖而别致的
译本,以引用歌德和其他作家来进行阐释》。值得一提的是,西蒙·莱斯于 1997 年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也采用了与辜鸿铭相似
的方法,其在注释中大量引用了西方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言论与著作。而且,在译本“前
言”中西蒙·莱斯也表达了与辜鸿铭相近的翻译初衷: “它( 《论语》译本) 所面对的不仅
仅是学者,其首要的对象是非专业的读者———他们仅想扩大自己的文化视野,但无法直接
接触原文。”②同样,西蒙·莱斯的《论语》译文也是较为通俗和口语化的。然而,王国维
( 1877—1927) 在《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中,已对引用西方文学家来附会《论
语》的作法提出了批评:“又译本中为发明原书故,多引西洋文学家之说,然其所引证者,
亦不必适合。”③此“译本”虽指《中庸》,然而这一批评对《论语》译本也是极为适用的。让我们再次回到“学而”一句的译文上来,在前文所列六家《论语》英译本中,唯独辜
鸿铭未加任何注释。也许,正是出于读者对象的考虑,出于对译文平易、流畅的要求,才使
得辜鸿铭译本中的注释量过小。然而,对“学而”一句不加任何注释与之作为整部《论语》之开篇的地位实在是很不相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没有注释,辜鸿铭在译文中将
“knowledge”( 学) 和“practice”( 习) 相对应,这极易引起西方读者的误解,即将其理解为把
某种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慧廉在其译本“导言”中将
儒家之“学”解释为“道德研习”( the study of morals) ,并指出“学”意谓“‘知’( wisdom) 之
获得与‘行’( conduct) 之表现”,进而又引明末清初清孙奇逢( 1584—1675) 《四书近指》所
录宋人游酢( 1053—1123) 之语,即“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来解释儒家之“学”。④ 因
①
②
③④
Ku Hong-Ming, preface,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by Ku Hong-Ming,trans. Shanghai: Kelly andWalsh,1898,p. viii.按: 加着重号的字在原文中为斜体。
Simon Leys,foreword,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by Simon Leys,tran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p. xi.按: 括号里的字为笔者所加。
王国维:《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见《学衡》,1925 年第 43 期,第 12 页。William Edward Soothill,tran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Yokohama: Fukuin Printing Company,
1910,p. 108.按: 游酢之语似亦化用《孟子·滕文公上》“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一句。
52 《中国文化研究》2013 年春之卷
此,对于《论语》“所给予中国人的智慧和道德”而言,我们似乎只能说,辜鸿铭的译本“所
存者其肤廓耳”。①
结 语
苏慧廉和王国维都对辜鸿铭的翻译有所批评,而且在某些地方还表现得相当一致。苏慧廉认为:“辜鸿铭的译本……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解释。他允许自己自由地表达
以便呈现其对《论语》的认识———绝不总是孔子的思想———在更受公认的经典之限制的
译者那里,我们无法找到这样的认识。”②同样,王国维也指出: “要之,辜氏此书,如为解
释《中庸》之书,则吾无间然。……若视为翻译之书,而以辜氏之言即子思之言,则未敢信
以为善本也。”③然而,对于“翻译”与“解释”之关系问题,现代诠释学已经告诉我们,“翻
译”绝不仅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而总已经是一种“解释”。在《真理与方法》( Wahrheit und Methode) 一书中,伽达默尔 ( 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 对“翻译”的诠释学特点给出了重要表述:
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无论翻译者如何想要进入作者及与作者感同身受,对于文本
的翻译并不是简单地重新唤起( Wiedererweckung) 作者原初的写作心理过程,而是对文本的仿造
( Nachbildung) ,这一仿造受到翻译者所理解的文本内容的引导。无可否认,翻译所
涉及的是解释( Auslegung) ,而不是纯粹的共同经历( Mitvollzug) 。④
既然“翻译”总已经是一种“解释”,那么“翻译者”也必然是“解释者”; 而在解释的过程
中,“解释者自身的视域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并且有助于我们真正占有文本中所言
之物”。⑤ 所以,作为翻译者和解释者的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经典的翻译过程中其理解的
先行视域,尤其是基督教神学的文化背景,必然会有意无意地被带入。然而,与此同时,中
国经典强大的注疏传统亦会在他们的翻译过程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两种视域的碰撞
与融合,又必然会催生出许多新的意义。因此,从诠释学的角度而言,翻译研究的首要任务并非判断译文的所谓“正确性”或
者评价诸种译本的优劣,而是要在不同语言和文化相交汇的过程中对一种翻译何以可能
以及新的意义何以可能的条件予以阐明。
( 作者通讯地址: 姜哲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100872)
( 责任编辑 晓 宁)
①②
③④
⑤
王国维:《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William Edward Soothill,preface,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by William Edward Soothill,trans.
Yokohama: Fukuin Printing Company,1910,p. iii.王国维:《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Hans-Georg Gadamer,Hermeneutik I: Wahrheit und Methode,in Hans-Georg Gadamer Gesammelte
Werke,Bd. 1,Tübingen: J. C. B. Mohr ( Paul Siebeck) ,1990,s. 389.Hans-Georg Gadamer,Hermeneutik I: Wahrheit und Methode,in Hans-Georg Gadamer Gesammelte
Werke,Bd. 1,Tübingen: J. C. B. s. 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