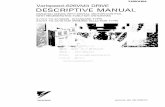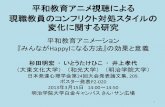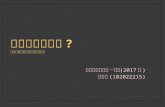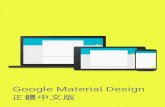聯合國犯罪預防與司法正義非政府組織聯盟」 (The Alliance of NGOs on Crime...
Transcript of 聯合國犯罪預防與司法正義非政府組織聯盟」 (The Alliance of NGOs on Crime...
1
修復式正義應用於家庭暴力事件之初探計畫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
修復式正義(Rrestorative Justice)自 1970年代崛起,在世界各地逐漸引起討論
並開始發展許多施行方案。各非政府組織與宗教團體除了積極推廣修復式正義的價值,
也藉由參與受刑人矯治、監獄教誨事工、以及受害人關懷之方案,來促進理念的落實。
因此除了地區性非政府組織及宗教團體的試辦與推行,甚且發展為跨國運動,進而於
2002年推動聯合國制定相關守則,按「聯合國犯罪預防與司法正義非政府組織聯盟」(The
Alliance of NGOs on Crime Preven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下設之「修復式正義
工作小組」(The Working Party on Restorative Justice)之定義,修復式正義「是一
種程序,舉凡在特殊犯刑中相關的涉及利害關係者皆可參與,並共同決定如何解決犯行
帶來的後果,以及其對未來的影響。」
這個風潮之第一個案例,是在 1974年 5月 28日加拿大安大略省 Kitcher市,因兩
個年輕人酒後侵入民宅鬧事,不僅是非法入侵也損壞 22位受害者的財務,在法庭上這兩
位青年承認犯罪並放棄抗辯,因此此案受派起草判決建議書之假釋官,寫信建議他倆應
拜訪所有受害人,了解其犯行對他們的傷害,並以此做為他們是否得以假釋的條件之一。
後來法官同意將此案延後宣判,以一個月時間在保釋官及門諾會中央委員會(Mennonite
Central Committee,簡稱 MCC)一位社區工作者陪同下,逐一造訪受害者,除保險理賠
部分外,他們亦籌款賠償受害者的財物損失,此案獲被害者的滿意,也成為後來受害者
與被害者復合方案(Victim Offender Reconciliation Programme)之前身。
修復式正義應用於司法制度,乃相對於傳統以刑罰為中心的現行刑事司法程序,是
視犯罪為對他人造成傷害,而非僅對國家法律的違反,主張司法的目的是醫治與關係的
修復,強調加害者必須負起責任彌補犯行所造成的傷害,並以提供受害者所需之各項服
務,最終讓加害人及被害人成功的復歸於社會,對社會的永續和平與安全做出貢獻(Van
Ness and Strong,1997)1。其關注的重點不在懲罰當事人或報復對方,而是如何在犯罪
事實發生之後,進行以療傷止痛、恢復平衡、復原破裂的關係為主要焦點的修復工作,
並賦予「司法」一種多元的可能性,而非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傳統的報復方式,而是尋
求真相、道歉、撫慰、負責與復原中伸張正義的司法內涵2,從應報式司法轉型成為修復
式司法,邁向轉型正義的新運動。
1 Van Ness, D. and Strong, K.H. (1997) "Restoring Justice" http://mereps.foresee.hu/en/segedoldalak/news/152/0b54190072/281/ 2 參見法務部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施計畫 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199866&ctNode=28162&mp=001
2
司法轉型的概念在 70年代於西方興起已近 40年,修復式正義使關注的重點轉型為
協助被害人、加害人及雙方家庭、社區進行充分的對話,其目的是讓當事人之間有機會
充分的陳述與傾聽、進一步澄清事實、了解對方的感受、提出對犯罪事件的疑問並獲得
解答。也讓被害人有機會描述其所經驗的犯罪過程、被害感受並能直接詢問加害人,以
及表達他們的需求且參與決定程序,以達到情感修復及填補實質損害之目的。對於加害
人一方也期望藉此機制能促進其認知及承擔自己的過錯,有機會主動向被害人、雙方家
庭及社區真誠道歉及承擔賠償責任,並經歷自我認知及情緒之正向轉變,以改善自己與
家庭、被害人以及社區之關係,俾助其復歸社會。透過對話程序,讓被害人得以重新感
受自己仍有掌握自己生活的能力,且能進一步了解加害人的行為原因,而減少因被害產
生的負面情緒。這是以提供一個非敵對、無威脅的安全環境,讓被害人、加害人及社區
(群)能完整表達其利益及需求,並獲致終結案件的共識及協議的制度。
20世紀末,澳洲、紐西蘭、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等國的刑事政策掀起修復式正義的
風潮,主張不以懲罰和矯治為處理犯罪的核心,而是藉由發現問題、回復損害、治療創
傷等方式處理犯罪問題,尋求犯罪人、被害人及社區共同參與修復及治療,避免刑罰對
犯罪人的標籤,使之能夠復歸社會。修復式正義之實施模式,分為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
(Victim Offender Mediation,簡稱 VOM)、家庭協商會議(Family Group Conferencing)、
和平圈(Peace Making Circle,或稱量刑圈,Sentencing Circle)、社區修復委員會
(Community Restorative Boards),國際上已有逾 20個國家運用修復式司法,亦各依國
情發展不同的模式,其中,以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VOM,其不同於我國現行調解制度)
之運用最為廣泛。我國亦於不同的專業範疇運用其精神與作法,發展修補復原的機制,
例如我國運用家庭協商會議(Family Group Conferencing)於兒童虐待事件之處理即是。
雖修復式正義是方興未艾的司法改革潮流,但無論是其正義論或執行的方案,也引
發不少的爭議。
因此若修復式正義應用在家庭暴力事件上,其核心信念為幫助個人真誠地與他人或
群體建立健康的新關係,從一個自私並傷害他人的人轉型成為一個有利他思想信念的
人,因此修復式正義對家暴犯而言,是價值觀念及行為的轉型。當然被害人應有絕對的
自主性決定其意願與選擇,若被害人拒絕,則應以尊重其意見及決定為首要考量。
依據法務部現有之資料顯示,為了逐步推動修復式司法、建立以人為本的柔性司法
體系,於 98 年 7月已核定「法務部推動修復式正義─建構對話機制、修復犯罪傷害計畫」,
並在暫不修法之前提下,規劃推動以「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為主要模式之修復式司法
方案,擇定所屬檢察機關辦理試行方案,實施成果將作為未來執行模式之參考。
就現實層面而言,刑事司法制度尚未能有效處理或解決親密關係暴力問題。此外依
據華人重視家族社會系統、面子與關係和諧的價值或信念,被害人常選擇其他的解決方
式替代。縱使強制性介入例如強制逮捕、強制起訴等方式的確減少了親密關係暴力,然
而,在暴力之層次上,親密暴力之狀況卻並沒有改善,反而惡化了(Sherman,Schmidt,
Rogan, Smith, Gartin, Cohn, Collins & Bacich, 1992)。按現行刑事司法系統雖是支持被害
人的利益,卻仍無法將被害人之聲音及需求整合到法律及社會的介入方式中。因此,在
現行之刑事司法實踐下,一位女性必須將逮捕、法律提告其伴侶作為受助的起點,但是
3
此人卻和她一同分享了過去、家庭、子女及未來。然而如果她不這麼做,法律及社會系
統便不會支持她,亦即將她的服務法律化(黃志中,2008a)。親密關係暴力案件類型除
典型的男性對女性之外,尚包括一般伴侶衝突、同志關係暴力或女性對男性暴力等行為
態樣,而傳統強調司法介入之處遇模式於上開案件類型之處理效果有限。因此,近幾年
部分西方國家提倡將修復式正義的轉型概念應用於特定之親密關係暴力案件處置,強調
以社區為基礎,透過專業人員、家庭暴力事件雙方當事人及其親友、社區鄰里、重要他
人等共同參與討論,促使加害人為暴力虐待行為負起責任及擬定改善計畫,讓彼此在過
程中達到建立健康關係的價值信念及行動。
由於我國社會十分重視家庭人際關係,中國儒家對家庭關係講禮治,禮不是一般所
以為的禮貌,而是指一種真誠共同體,也就是有愛的動力,這是暴力家庭最難以了解的
微意。中國儒家認為禮是一種道德,以仁為本。基於中國的文化背景,多數親密關係被
害人並不願意見到因為暴力虐待而導致家庭關係破裂或是家醜外揚,因此暴力發生時大
都仍選擇隱忍,或拒絕其他專業協助介入。根據國內實務工作者分析,親密關係暴力案
件中高達七成被害人仍與施虐的伴侶同住,且六成以上仍希望繼續維持關係,顯示多數
被害人並不願透過司法強力介入懲罰加害人來處理暴力問題,但希望透過外在力量同聲
譴責暴力行為,達到制止加害人再犯。因此,國內近一、二年亦逐漸浮現將修復式正義
概念應用於家庭暴力事件處遇之相關討論,為建立國內相關實徵資料,增進防治網絡人
員認識修復式正義轉型概念應用於家庭暴力事件之操作模式與相關配套措施等,宜積極
執行本計畫。
第二節 計畫目的
基於上述之計畫緣起,本計畫有下列三項目的:
(一)蒐集並整理國內外有關修復式正義應用於家庭暴力事件之相關研究成果。
(二)發展國內推動修復式正義應用於家庭暴力事件之相關作業流程與相關配套措施。
包括:
1、個案篩檢機制:哪些個案類型適合應用修復式正義概念?應透過何種哪些篩檢程
序等。
2、工作團隊成員組織與角色分工:應包含哪些團隊成員以及各自的角色職責與分工。
3專業人員之資格與訓練:擔任修復式正義促進者之資格條件與應接受之相關專業訓
練。
4、相關輔助評估書表與成效評估指標。
(三)提出修復式正義應用於家庭暴力事件之具體政策建議。
4
第二章、文獻探討
本研究蒐集國內外相關著作、期刊、論文、統計數據及網路資料等,進行文獻整理
以探討修復式正義應用於家庭暴力事件之現象及脈絡背景。本章將分以下三個層次進行
論述:第一為修復式正義之理論架構,主要乃是探索修復式正義的基本內涵;第二為探
討國內外修復式正義應用於家庭暴力事件之實施現況及相關研究;第三為透過相關研究
之比較與分析,發展國內推動修復式正義應用於家庭暴力事件之實務運作策略。
第一節 修復式正義之理論架構
修復式正義(Rrestorative Justice)是一個看似新卻是舊的概念,可謂由 1980年代的
司法改革潮流所帶動,但其哲學與倫理意涵,卻又能呼應諸多傳統文化相關於衝突解決
的教導。修復式正義的價值理念可以上溯希臘羅馬文化的架構,其正義觀則是強調對於
犯罪行為所導致的傷害,透過具包容性的合作過程進行修補。
一、修復式正義的起源
20世紀末,澳洲、紐西蘭、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等國的刑事政策掀起修復式正義的
風潮,主張不以懲罰和矯治為處理犯罪的核心,而是藉由發現問題、回復損害、治療創
傷等方式處理犯罪問題,尋求犯罪人、被害人及社區共同參與修復及治療,避免刑罰對
犯罪人的標籤,使之能夠復歸社會。
回顧歷史上犯罪被害人權益運動的軌跡,正義的概念既複雜且多元,然而,正義始
終是刑事司法的主軸與哲學根基,亦是被害人保護的主要理論基礎。而運用正義的概念
將被害保護作為分為四類:包括被害人復歸、補償與協助、被害預防及重複被害預防(黃
蘭媖,2007)。當懲罰式正義已呈現諸多缺失及困境,傳統刑事司法制度亦難以令雙方當
事人得以復歸及整合,且對於和諧社會之建立並無完全之助益;此外,刑事司法系統首
重證據取得,因此常因著重於發掘起訴加害人之證據,使得操作時易忽略被害人之需求、
期望及感受,甚至對於被害人及其家庭產生負面影響,或使其家庭頓失經濟來源,造成
家庭關係破裂,甚或是形成與社區之隔閡,而導致被害人懷有無助感及罪惡感。由是,
修復式正義之概念因應而生。基於上述論點,學者歸納相關因素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並導
致了修復式正義之興起:(1)對於懲罰式刑事司法之不滿;(2)民意向背與學者專家之支
持;(3)被害者學之興起;(4)宗教團體之推動;(5)司法多元主義之影響;(6)刑罰學觀點
之轉變等(許春金,2003)。
參閱國外修復式正義之相關研究,其述及理論建構及實務各應用之處境,顯現南非、
加拿大、澳洲、香港、牙買加等國正積極發展此概念之應用。其中論及修復式司法之執
行,亦一致的提及須對較為嚴重的案件,例如性侵害、謀殺和家庭暴力等罪行限制其使
5
用。反觀國內,有鑑於修復式正義思潮之復興及正式刑事司法系統之有限,近年來國內
關於修復式正義之相關研究正逐漸地累積,其中當亦包括有對於調解之相關探究。就國
內論文及期刊之查閱,目前修復式正義之應用研究方向,有多數是針對校園滋事、青少
年犯罪及更生保護之運用等,亦有對於原住民部落文化、儒家影響等之探討,再者即是
應用於家事調解制度之策略與效能之研究;可見國內有關修復式正義之基礎研究仍處於
起步階段,仍有極大的努力空間。
二、修復式正義之定義詮釋
所謂的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乃為犯罪問題解決導向,其涵括的範圍為涉入
事件之個體本身,以及整個社區,其間具有互動之關聯性(Marchall, T. E , 1999)。運用修
復式正義理論於司法制度中,可充分關注被害人、加害人及其家庭、社區間的溝通及協
商,以釐清事件之本質,尋求真相及復原;透過充分的對話,讓被害人及加害人以對等
的立場完整闡述其心路歷程,進而促使加害人承認過錯,負起責任,被害人則於過程中,
達到情感修復之效。
修復式正義 (restorative justice) 一詞係由 Albert Eglash 在“Beyond
Restitution: Creative Restitution”書中開始引用。國內司法界、法律界引用時,將
其翻譯成「修復式司法」,主要是從司法體系及其運作層面來探討,意指「特殊犯行的所
有利害當事人共同聚在一起,共同處理犯罪後果及其未來意涵 (implication) 的過
程」,也可以說「任何主要目的為回復犯罪所造成的損害之活動」。
運用修復式正義於司法體系中,需依循四項原則(Marchall, T. E , 1999):(1)開啟加害
人、被害人以及其家庭、社區之對話空間;(2)納入整體社會脈絡之角度探討犯罪問題;
(3)前瞻性及預防性之問題解決導向;(4)富彈性及創新性的實踐與運用。
透過上述四項原則,以落實修復式正義概念於犯罪事件之處理中;依此,可視修復
式正義為一嵌於整體社會脈絡中之犯罪正義,強調事件涉入之個體間具有關聯性,而非
獨立且封閉之系統(Marchall, T. E , 1999)。而「正義」可被定義為應報、矯治或修復、補
償,檢視目前處理犯罪事件的方式,仍以應報式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或懲罰模式
(Punitive Model)為主(許春金,2009)。故由修復式正義的理論得知,主導現今司法體系
的懲罰模式已非唯一法則,過度的強調處罰犯罪加害人,往往忽略了社會結構面之問題,
以及對於被害人之補償及修復。由是,納入修復式正義的概念於司法制度中,實為刻不
容緩之要務。
修復式正義強調建立對等關係,並回復傷害,重建社會關係及促進群體、社區間之
互動,故欲將其概念融入司法體系中,除依循上述四項原則外,更需具備五項要素(許春
金,2009):(1)以「社會」、「衝突」的觀點,而非「法律」的觀點來看待犯罪事件;(2)
修復式正義是一種回復損害的「關係式正義(Relational Justice)」;(3)修復式正義主張,藉
著發現問題、回復損害、治療創傷而能進行廣泛有意義的社會 革新,從而為社會創見
更多更好的「和平及福祉」;(4)修復式正義尋求加害者、被害者及社區的共同參與修復
及治療;(5)犯罪處理的場域在社區。
分析上述五項要素,可發現「社區」之於修復式正義的重要性;加害人、被害人、
6
社區及政府的關係及責任互為牽動,所謂的「犯罪事件」被認為是影響社區生活的「社
會事件(Social-events),這些事件並非僅僅是違反法律而已,而是違法者未盡到對社區及
被害者的道德與責任。修復式正義即為回復整體社區結構,並強調結構面的修復,以及
透過回復的過程,讓加害者承認錯誤、避免再犯,以獲得社區之諒解,並重回社區生活,
亦可透過事件的處理,檢視發生之原因及討論因應對策,以降低類似犯罪事件之發生率;
對於被害者來說,透過問題解決的過程,了解其所受到的所有傷害,並探究回復之方法,
以復原至未受傷害之狀態;整體目標即為促使社區之平衡運作,及彌補社會網絡之缺陷
(許春金,2009)。
三、修復式正義與其他正義模式之比較
修復式正義與其他模式之主要不同處在於關注之焦點以及欲達成之目的,以下就三
種不同之正義模式進行說明:
(一)賠償式正義(Restitution Justice)
許春金(2009)提到賠償式正義和修復式正義於本質和目的上主要的差異為:(1)賠償
式正義在本質上仍可能是報應式懲罰,(2)賠償式正義在本質上亦有可能是威嚇式的,(3)
賠償式正義在本質上亦有可能是矯治式的。此正義模式關注的焦點在於被害者之物質性
賠償,然卻無法合理反映其受損失後之相對價值,亦即忽略了被害者於社會關係中的無
形損害,致使其喪失之安全感無法透過此模式得到復原。反觀修復式正義,其強調回復
受害者至原來的樣子,並將加害者角色納入考量,以促使事件發生後,仍竭力回復至一
理想境界。
(二)矯治式正義(Correctional Justice)
矯治式正義是考慮受害者的心理層面,認為犯罪所造成的損害不僅有物質上的傷
害,亦有心理上的傷害。故要平衡兩者間的關係,勢必要使加害者之心理亦受到一些損
害,方可回復到「社會平衡(Social equality)」(許春金,2009)。此模式與修復式正義不同
之處在於解決方式,其主要以損害加害者使其與被害者達到一平衡關係,致使雙方面均
受到損害,表面上似乎符合某種程度之公平。然實質上,對於被害者之修復及彌補無濟
於事,甚或無法增進兩者回復社區生活的品質。
(三)應報式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
應報式正義指任何以懲罰達到平衡之理論,是一個統稱。應報式正義在基本上也是
關心社會關係的平復,這是與修復式正義相同的概念(許春金,2009)。此正義模式著重
於對於加害者之個別「懲罰({Punishment)」,透過此機制讓侵害或犯罪事件受到制裁,藉
以逃避回復社會關係之責任。然修復式正義並非完全的否定「懲罰」所帶來之效應,反
而看重應報式正義仍帶有「補償」的「替代性懲罰」意味(陳祖輝,2004);修復式正義
即透過調解(Mediation)、補償(Restitution)、擔負責任(Accountability)等方式,修復並重建
對等的社會關係,以促進彼此間之尊重及關懷。
上述三種不同的正義模式中,以應報式的正義與修復式正義進行比較,引述修復式
司法之父 Howard Zehr 的觀點,認為應報式司法與修復式司法的差異主要可從「看待犯
罪的觀點不同」及「處理犯罪的方式不同」進行比較:
7
表一:應報式正義與修復式正義之比較
應報式正義 修復式正義
看待犯
罪的觀
點不同
◇犯罪是對國家與法的侵害
◇犯罪帶來罪責
◇司法是國家決定加害人罪責與刑罰
的過程
◇關注焦點:加害人應受到何種懲罰
◇犯罪破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犯罪帶來回復的責任
◇司法是加、被害人與社區成員共同
努力修復傷害的過程
◇關注焦點:被害人的需求、加害人
修復傷害的責任
處理犯
罪的方
式不同
◇確認犯罪行為違反哪些法律
◇誰是犯罪者
◇犯罪者應受何種懲罰
◇注重過去的犯罪事實
◇誰受到傷害
◇被害者的需要
◇回復傷害是誰的責任
◇注重未來關係的修復
註:整理自 The Little Book of Restorative Justice, Howard Zehr,p21,2002
四、修復式正義之實施模式
修復式正義強調傷害修復以及社會關係之回復,因此回復要件為牽動事件整體的所
有元素,故參與修復式正義的角色有被害者、加害者、警察、檢察官、辯護律師、法官、
矯治人員、區(人員),以及調解員(許春金,2009),與事件相關聯之利害當事人皆為參與
修復之對象。
修復式正義並無固定之實施模式,端視文化脈絡之變遷而有所異同,學者歸納現行
之實施模式,以下分述之(許春金,2009):
(一)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Victim Offender Mediation,VOM):
此調解過程提供被害人與加害人一個安全且具有結構性之協商機會,讓彼此坦然面
對所造成之傷害,並以各自立場表述,探討復原損害之具體辦法。在北美,有超過 300
個以上之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方案,在歐洲則有超過 500 個以上的方案正執行中。相關
研究證實,參與調解方案之被害人與加害人具有相當高的滿意度,且被害人不因參與此
調解方案而感到害怕;相較於一般司法程序而言,調解方案可促使加害人完成其應盡之
義務,並降低再犯率。
(二)家庭協商會議(Family or Community Group Conferencing):
家庭協商會議中集合了被害人、加害人、雙方之家庭成員、朋友以及主要支持者,
用以協議傷害發生後之處理策略。其主要目的為:給予被害人一個直接回應損害之機會,
並增進加害人意識到其行為所致使之影響,為其所作所為負責;此外,律訂加害人之支
持系統相關成員,負責重塑、規範加害人未來之行為,以促使其與被害人建立在社區支
持系統中之關聯性。
8
(三)和平圈或審判圈(Peacemaking or Sentencing Circles):
和平圈或審判圈乃將被害人(及其支持者)、加害人(及其支持者)、法官、檢察官、辯
護律師、警察及社區相關人士聚集在一起,以誠懇的態度共同對事件尋求了解,並探討
治療被害人及預防加害人再度犯罪之必要步驟(許春金,2009)。其主要達成之目的包含:
治癒受損害影響之個體,並給予加害人改過自新的機會,以及給予被害人、加害人、家
庭成員及社區一個對話的空間,使其共同承擔、負責損害的後果,以找出具體的解決方
案;除此之外,強調犯罪行為所造成之後果,擬建立一個分擔社會成本之運作機制。
(四)社區修復委員會(Community Restorative Boards):
社區修復委員會的組成成員為受過專業訓練之社區居民,其具有公開與加害人面對
面討論及協商的能力;除分析、探討事件發生後所產生之不良影響外,亦著手研擬一套
修復補償計畫,以促使加害人承諾於特定時間內完成此計畫之要求事項,社區修復委員
會則擔任監督之責,向法院提出執行成果及報告。
除上述模式之外,類似之實施模式亦有賠償命令(Restitution Order)、社區服務命令
(Community Service Order)、親密虐待圈(Intimate Abuse Circles)(潘雅惠、陳建宏,2009),
以及為消弭南非種族隔離政策所實施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以下就各模式之參與者、
執行程序、目的以及適用案件等面向,進行歸納與比較:
表二、修復式正義實務型態模式比較
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 家庭協商會議 和平圈、審判圈 社區修復委員會
參與者 被害人及其利害關
係人(團體)、加害人
被害人、加害人
(即各自的支持
者)以及家庭成員
被害人、加害人(及
其支持者)、法官、
檢察官、辯護律師、
警察,以及社區相關
人士
一小群受過專業訓練
之地方百姓
執行
程序
由訓練有素之仲裁
者召集協議,展開
被害人與加害人之
對話(dialogue)
由加害人開始描
述事件,其次由每
個參與人述說受
到的影響及傷害
1、由法官轉介進行
審判圈,以達成
的協議做為判決
的建議
2、法官、檢察官、
辯護律師等共同
參與審判圈,以
其協議作為判決
與加害人面對面公開
討論,討論犯罪事件造
成之不良後果,以擬定
修復及補償計畫,由加
害人於特定時間內完
成此計畫,委員會則向
法院報告加害人之執
行狀況
9
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 家庭協商會議 和平圈、審判圈 社區修復委員會
目的
呈現事件造成之損
害及影響,並進行
賠償協議
了解事件對每個
人所造成之影響
及傷害,並透過周
詳討論,以表達補
償損害之看法,最
後簽署共同同意
之協議
改變與影響事件各
方當事人的生活型
態、態度及行為,並
對該社區、人文環境
等有所助益
1、被害人復歸與治療
2、社區復歸
3、加害人了解其犯罪
之危害
4、加害人學習避免再
犯
5、社區提供加害人再
整合的機會
適用
案件 少年案、成年案
少年案、輕微犯
罪、排除暴力及性
犯罪
少年案、成年案 少年案、輕微犯罪、成
年案
共通點 呈現事實→抒發情感→補償及修復行為
註:整理自許春金,2009
不論修復式正義之實踐模式為何,其共通點為呈現犯罪事件之事實,透過事件關係
人之傾訴、討論,以抒發情感,宣洩事件所造成之不良影響,進行研擬一套解決模式,
以補償及進行行為之修復。
第二節 國內外修復式正義應用於家庭暴力事件
之實施現況及相關研究
一、家庭暴力事件的定義
家庭暴力事件的定義不勝枚舉,學者(劉默君,2004)引用美國華盛頓特區婦女虐待
預防方案(National Woman Abuse Prevention Project, Washington, D.C., 1991) 之定義為:家
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 Family violence),即婚姻暴力(Marital violence)、配偶虐待
(spouse abuse)、太太毆打(wife battering;wife beating;wife assault)、婦女虐待(woman
abuse)…等,舉凡虐待性與暴力性行為發生在已婚或同居者,其有正在進行或曾有過親
密性關係。以下分述國內家庭暴力以及親密關係暴力之定義:
(一)家庭暴力:
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3第二條第一項,所謂的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上
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而家庭暴力罪,則為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
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其中,家庭成員之定義為:(1) 配偶或前配偶,(2)現有或曾
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3)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4)現為或
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
3家庭暴力防治法,民國 98 年 4 月 29 日修正。
10
(二)親密關係暴力(姚淑文、溫筱雯,2004):
親密關係暴力的定義是:「在浪漫的關係(romantic relationship)裡,不論是發生在異
性或同性戀上,舉凡任何過度的(abusive)控制或攻擊行為(aggressive),無論藉著言語、
情感、身體、性關係或綜合形式出現,可稱為戀愛暴力」(The National Centre for Victims
of Crime)。大致上可分為以下四種:(1)身體暴力(Physical Dating Violence);(2)言語暴力
(Verbal Dating Violence);(3)心理暴力(Psychological Dating Violence);(4)操控暴力
(Manipulative/Possessive Dating Violence);(5)性暴力(Sexual Violence)。親密關係暴力案
件類型除典型男性對女性基於權控關係之暴力行為態樣,尚包括一般伴侶衝突、同志關
係暴力或女性對男性暴力等。
家庭暴力以及親密關係暴力事件,於真實現況中屢見不鮮,然以目前之刑事司法制
度來看,仍尚未能有效處理與解決親密關係暴力問題。且華人極重視家族社會系統,及
面具性格表徵於面子與和諧的高度價值,加上整體社會十分重視家庭人際關係,多數親
密關係被害人並不願意因為揭發暴力或虐待事件而導致家庭關係破裂;因此暴力發生時
大都選擇隱忍,或拒絕其他專業協助介入的方式。根據國內實務工作者分析,親密關係
暴力案件中高達七成被害人仍與施虐的伴侶同住,且六成以上仍希望繼續維持關係,顯
示多數被害人並不願透過司法強力介入懲罰加害人來處理暴力問題,但希望透過外在力
量同聲譴責暴力行為,達到制止加害人再犯,顯然地,須有其他的替代解決方式可供被
害人選擇為當。
二、國內家庭暴力現況
依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自 2006 年起至 2011年4,國內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案件數
除 2011年外,皆呈現逐年上升之趨勢(參表三、圖一),相關研究報告皆指出家庭暴力對
於家庭成員及整體家庭結構造成諸多不良之影響,甚或延伸至社會層面,產生社會問題,
故家庭暴力事件之防治以及運用修復式正義理論觀點進行司法矯治,或社政體系之處遇
模式,乃本研究需致力探討之議題。
表三、2006 年至 2011年 7月 31日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案件數
註:整理自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網站統計資料
4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統計資訊網頁:
http://dspc.moi.gov.tw/lp.asp?CtNode=776&CtUnit=79&BaseDSD=7&mp=1&xq_xCat=a 2011/9/6
年(月)別 通報數
2006 66635
2007 72606
2008 79874
2009 89253
2010 105130
2011 104315
11
圖一、2006年至 2011 年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案件數趨勢圖
若以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案件類型統計分析,以婚姻、離婚以及同居關係暴力、兒少
保護、老人虐待,以及上述以外之其他通報案件類型進行區分(表四、圖二),可發現不
論何種類型之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次數皆呈現上升之趨勢;其中以婚姻、離婚以及同居
關係暴力之案件最多,其次為兒少保護,老人虐待事件則最少。另,若以兩造關係(表四、
圖三)進行分類,則顯示以配偶間之家庭暴力事件最多,其次為曾有或現有之其他家庭成
員,最後則為前配偶間之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數。
面對逐年上升之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數,法務單位著手研擬有效之預防及解決之道乃
為刻不容緩之要務。須於現有之司法制度中,研議出另一套更適宜之因應對策,而修復
式正義之概念及實踐,可為深入探討之重點。
表四、2006 年至 2011年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案件類型統計
年(月)別 案件類型 通報數 兩造關係 通報數
2006
婚姻/離婚/同居關係暴力 41517 配偶 33637
兒少保護 10952 前配偶 2473
老人虐待 1573 曾有其他家庭成員 13721
其他 12593 現有其他家庭成員 16804
2007
婚姻/離婚/同居關係暴力 43788 配偶 35182
兒少保護 14243 前配偶 2745
老人虐待 1952 曾有其他家庭成員 16147
其他 12623 現有其他家庭成員 18532
2008 婚姻/離婚/同居關係暴力 46530 配偶 35862
12
年(月)別 案件類型 通報數 兩造關係 通報數
兒少保護 17086 前配偶 2850
老人虐待 2271 曾有其他家庭成員 22022
其他 13987 現有其他家庭成員 19140
2009
婚姻/離婚/同居關係暴力 52121 配偶 38906
兒少保護 17476 前配偶 3193
老人虐待 2711 曾有其他家庭成員 23557
其他 16945 現有其他家庭成員 23597
2010
婚姻/離婚/同居關係暴力 59704 配偶 42967
兒少保護 22089 前配偶 3708
老人虐待 3316 曾有其他家庭成員 29610
其他 20021 現有其他家庭成員 28845
2011
婚姻/離婚/同居關係暴力 56734 配偶 39530
兒少保護 25740 前配偶 3399
老人虐待 3193 曾有其他家庭成員 34489
其他 18648 現有其他家庭成員 26897
註:整理自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網頁統計資料
圖二、2006年至 2011 年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案件類型統計圖
13
圖三、2006年至 2011 年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案件兩造關係統計圖
三、修復式正義運用於家庭暴力事件之迷思及觀點
修復式正義應用於司法體系中,其糾結之迷思與弔詭,實有待進一步的釐清。誠如
運用修復式正義於家庭暴力事件中,須先行審思:家庭暴力處遇的核心價值為何?家庭
暴力防治的功能及定位為何?家庭暴力處遇的最終目的為何?家庭暴力利害相關的兩造
如何尋找可能的權力互動關係平衡點5?家庭暴力事件牽涉範圍極其複雜,依系統觀點,
除生理層面外,舉凡個體人格特質、氣質、情緒、家庭關係互動經驗、社區連結、社會
文化因素,對於被害人及加害人之心理、社會層面皆有所影響。由是,其事件之處遇模
式須經過審慎評估及衡量上述相關疑問後,方可決定以何種模式執行處遇。
Menkel-Meadow (2007)提到儘管修復式正義可做為傳統司法制度的相對選擇,然而
女性主義者以及兒童權益倡導者對於運用修復式正義於傳統的司法領域中,仍做出相關
之批判與質疑;反之,許多研究則認為透過修復式正義模式中的家庭協商會議,可降低
再犯率。因此,產生了修復式正義應用於家庭暴力事件之論戰,當贊成推動修復式正義
者主張刑事司法系統以標準化介入模式來處理犯罪問題,將使得被害人中心的基礎被忽
略,若以修復式正義為基礎之調解模式,則是為加害人、被害人及社區三者間關係之修
復與復歸注入更多新的可能性及希望。但另一方面,隨著愈來愈多婚姻暴力事件進入刑
事司法程序,使得相關專業人士發現,刑事司法人員之處理若失當,不僅不利於被害人
及其家庭,並常造成長期的負面影響,也恐將對於被害人造成二度傷害(高鳳仙,1998;
柯麗評、王珮玲、張錦麗,2005;黃翠紋,1999)。
5 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蘭馨婦幼中心網頁:
http://www.roton.tw/index.php?menu=view&mode=timenews&timenewsid=73 2011/9/17
14
當受暴婦女選擇逃離時,受父權文化形塑之女性更被提醒須投注寬容於婚姻、家庭,
以及承擔維持家庭完整的責任等影響,受虐婦女若使用司法權力則必須背負遺棄家庭的
罪名,為脫離關係付出代價,這常使受虐婦女陷入兩難,同時亦常因此淡化及合理化施
暴者的行為(陳源湖,2004)。因此,協助家暴事件的各項專業人員,應該充分了解暴力
議題的探討絕不能忽略性別差異在心理社會的處境,更不能忽略社會文化及價值觀對性
別角色的影響,避免偏見迷思,以提供完善與適切的協助。
在臨床實務工作上亦可發現求助之受暴婦女缺乏信心、缺乏資訊、缺乏自保能力、
容易原諒對方、害怕離開後再也回不去、不甘心、恥辱等情形,這些無論是外顯或內隱
行為,可能是她們在長期的受虐環境中逐漸形成的特質,因為他們必須求生存,而委屈
自己以減少傷害(劉婌齡,2003)。Lloyd 與 Emery(2000)對遭遇親密攻擊婦女之情境
脈絡的研究發現大部分婦女相信攻擊永遠不會發生在她們的親密關係中,攻擊不代表關
係的障礙或不滿意,有時候被害人反倒是因心理機轉而認為那是一種愛,「原諒和忘記
(to forgive & to forget)」是被害人常有的行為。Ferraro(1996)認為身為受害者首先帶著
「應得」的想法;受害者是把問題歸於她們的舉止和未盡力保護她們自己,而不斷責備
自己為何在知道他有激烈情緒時還讓他發怒(引自 Lloyd&Emery,2000)。這些心理歷
程和感受,則需要專業工作者更敏銳的覺察,才能真正了解及同理其立場。
而且親密關係暴力的發生其歷程不僅是循環的,而且是像漩渦一樣(spiral),向內
捲入的力量是毀滅性的,使被害人更無助,失去自信,失去希望。向外捲出的力量象徵
被害人力量的增強,更多的覺醒,更了解暴力是控制的內涵。因此從治療的角度,被害
人的療傷止痛就像是向上捲出的螺旋運動一樣(Chaplin, 1988)。而這股力量還需要許
多因素的配合,尤其是受暴者週遭的支持與資源的多寡,可以決定捲出之力量的強度多
寡。其中服務提供者(如社工、律師、法官、醫師、心理師、警察、檢察官等)便是這
股力量重要關鍵,也是決定案主被二度傷害或再次重生的樞紐。
但衡諸目前之法官、檢察官或其他刑事司法實務人員大多數並未接受過關於被害輔
導之相關訓練,既無法傾聽雙方當事人之心聲與煩惱,亦不能體會被害人猶豫不決之情
緒,即使運用法律程序亦往往無法解決婚姻暴力雙方當事人之情感困擾及家事紛爭。因
此,亦常有諮商輔導人員認為,於婚姻暴力問題之處理上,訴諸於法律之程序愈晚愈好
(黃翠紋,2001),此亦顯示出當前刑事司法系統對於處理婚姻暴力問題之有限。因此國
內許多家庭暴力相關學術及專業實務工作者,對於修復式正義之實施,仍有許多疑慮及
躊躇,深恐因專業不足或執行失當,造成被害人的勉強或屈辱,以至於十多年來建構之
網絡效能遭遇質疑。
四、台灣現行調解制度作用於婚姻暴力案件之觀點
(一)調解介入的適用性
黄翠紋(2001;2002;2004)則曾以婚姻暴力為研究主軸,探討調解制度、受暴當
事人接受調解意願或滿意度,以及從法官的觀點看調解現況等研究。也由於婚姻暴力常
涉及隱私,同時具有非理性與流動性的特質,不若財產關係可以明白確定當事人的意思,
如欲藉由一般劃一性訴訟程序處理,可能難以得到妥適解決(黃翠紋,2004)。然而就婚
15
姻暴力事件是否適合以調解方式來處理,過去學者專家之間的意見有很大的紛歧,反對
者認為雙方當事人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將會延續到調解的程序中。以法規來看,家
庭暴力防治法第 12條第 4 項規定:保護令事件不得進行調解或和解,而審理或調解保護
令以外的民刑事事件,如認為有家庭暴力情事時,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9 條規定,原
則上禁止和解或調解(高鳳仙,2007)。但是調解措施的倡導者主張,只要妥當的設計將
可避免此種權力不對等現象的發生(黃翠紋,2004;2006a)。
(二)家暴議題牽涉層面廣泛
有鑒於家暴的複雜性與危險性,為保護當事人,調解程序應有所調整,而調解前的
篩選機制更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調解員需蒐集有關過去、現在及潛在家庭暴力的資訊,
如嚴重程度、頻率次數、暴力的致命程度、加害人與受害者的接觸程度、環境的整體安
全、其他形式的受害狀況等。此外還要了解當事人對事件的解釋、想法、感受與意義,
作為辨別是否適宜進入調解的參考(楊康臨、鄭維瑄譯,2007;黃翠紋,2002;2004)。
經過評估篩選後,如果當事人能從調解中受益,維護當事人安全便是調解中的重要策略。
Winslade 與 Monk 提出幾點安全計畫,包括安全的座位安排、立即辨識出威脅與虐待
的論點、在調解時協商安全契約、讓當事人在不同的會談室會談,以及有一名能提供當
事人心理安全支持的人參與調解,除此之外更主張除了暴力行為,更應思考其背後的父
權文化、階級、性別、種族的偏狹認知(引自楊康臨、鄭維瑄譯,2007)。
(三)調解員的角色
有鑒於婚姻暴力的複雜性與嚴重性,大都有關調解機制運用於家庭衝突事件處置之
研究,皆主張調解程序的完整性與調解員的素質在此扮演重要角色,建議透過合宜的調
解程序,讓適當的當事人進入調解,配合調解員的專業介入與敏感度,才能實際發揮調
解的功效。因此家事調解員專業化訓練是重要且必須的,藉由足夠的知能,以及本身對
性別的敏感度,形成完整合宜的調解策略,才能使當事人在調解中受益。而親密關係暴
力案件是否適合以調解方式處理至今仍有許多爭議,以目前台灣調解制度未臻健全下,
家事調解員仍有機會面臨婚姻暴力存在的狀況,而調解員的專業素質及其對暴力成因之
認知,將影響當事者之利益,一般認為暴力其實是權力的展現,好讓受暴者順從,而調
解制度是否成為加害者運用權力與控制的工具,亦有疑慮(柯麗評、王珮玲、張錦麗著,
2005)。因此除了需具備調解專業能力外亦應評估家事調解員之性別意識,篩選出具性別
敏感度之家事調解員。在進行調解時,家事調解員應提醒自己減少個人偏見、避免過度
影響當事人,敏覺當事人性別在婚姻關係中的角色與行為表現,並在調解中看見其性別
處境,以促進當事人的平等,才能確實達到調解所主張之公平正義的目標。我國亦可參
照加拿大家庭調解委員會(Family Mediation Canada)的做法,在調解員的資格審核中測
量其對於性別、文化、性取向、虐待等議題的敏感度(李秋霞、卓紋君,2005)。在調解
員的調查中,發現大都以社會衝突觀點,而非法律觀點來看待調解事件,並認為調解制
度具有紓解訟源、情緒抒發、充分溝通、填補損害、重建關係等功能。調解過程中調解
委員理性情緒及公正立場對於達成調解是很重要的,並應給予受調解人情緒的抒發及充
分陳述的機會。而受調解人間的充分對話與協商,亦能提昇其自身對於調解的程序以及
結果的滿意度,因此受調解人之間的互動不容忽視(許春金、陳玉書、黃政達,2007)。
16
五、國內外應用修復式正義於家庭暴力事件現況分析
(一)國內現況
自 1970 年代開始,北美、歐洲、紐西蘭、澳大利亞等,已逾 20個國家運用修復式
司法,以及陸續採用各類具有修復式司法精神的實務方案,甚至發展成為與應報式司法
並行的另一種司法制度。國內亦順應潮流,逐步採用修復式正義之概念執行司法任務或
採用修復式正義於家防中心行動方案,目前法務部試辦方案選定部分適用之案件類型,
以做為運用修復式正義於司法體制之先導研究,桃園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亦選定適用案件
類型,做為修復式正義應用於家庭暴力事件之行動方案,以下分述之6:
表五、各試辦地檢署選定適用的案件類型
試辦
機關 案件類型
士林 過失傷害、過失致死、(重)傷害、財產、少年犯罪及其他輕微或經評估適宜案件
板橋 刑事訴訟法第 376條所定各罪(有被害人者)
苗栗 人身犯罪、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所定各罪(有被害人者)及其他經評估適宜案件、其
他輕微或經評估適宜案件
台中 刑事訴訟法第 376條所定各罪(有被害人者)、重罪、少年犯罪及其他經評估適宜案件
台南 經評估適宜之案件、家其他輕微或經評估適宜案件
高雄 車禍案件及其他經評估適宜案件、其他輕微或經評估適宜案件
宜蘭 過失致死、傷害及其他經評估適宜案件、其他輕微或經評估適宜案件
澎湖 刑事訴訟法第 376條所定各罪(有被害人者)、少年犯罪及其他經評估適宜案件、其他
輕微或經評估適宜案件
上表所述之案件類型中,以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所定各罪」為主要之適用類
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376條訂定之罪為7:(1)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專科罰金之罪,(2)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三百二十一條之竊盜罪,(3)刑法第三百三十五
條、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之侵占罪,(4)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百四十一條之詐欺
罪,(5)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之背信罪,(6)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之恐嚇罪,(7)刑法第三百
四十九條第二項之贓物罪。於以上 8個試辦地檢署選定之案件類型中,除已明確表列之
案件項目外,並未提及家庭暴力事件,然皆包含「其他輕微或經評估適宜案件」,由是,
部分之家庭暴力事件,若經評估後符合執行修復式正義之條件,則可進入試行階段。目
前各地地檢署採用兩種工作模式,即是委外或自行操作,委外操作之地檢署包括台南與
高雄,台南地檢署委外執行單位由台南女權會執行,高雄則由呂旭立基金會執行。苗栗
地檢署由現代婦女基金會駐地檢署被害人服務處擔任案件管理。桃園縣家庭暴力防治中
心之工作模式則是自行操作,促進者以外聘心理諮商資深工作者任之。
6 法務部網頁: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205769&ctNode=28162&mp=001 2011/8/3
7 刑事訴訟法,民國 96 年 12 月 12 日修正。
17
執行修復式正義與否,其評估標準及啟動時機實屬重要;故運用修復式正義之概念
於司法體系中,須考量其執行的時間點;值得強調的是,修復式正義並非用於取代原有
之司法制度,而為補充及調整相關制度流程,使用之時機及作法,將視案件不同而異。
大體而言,修復式正義方案可實施或啟動於刑事司法的四個節點(許春金,2009):(1)在
警察階段(起訴前),(2)起訴階段(審判前),(3)審判階段(定罪或量刑前),(4)矯治階段(當
作監禁的替代性措施,或非監禁措施的一部分或附加部分);於上述任何一個節點的刑事
司法人員均可運用其裁量權轉介加害人及被害人至修復式正義方案中。
法務部現行推動之「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實施計畫,其轉介時機為8:檢察官發現
加害人有意願、監所發現收容人有意願、觀護人發現受保護管束人有意願、更生保護協
會發現更生人有意願、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發現被害人有意願、法院發現當事人有意願,
以及加害人、被害人自行申請;啟動修復式司法機制的主要關鍵點在於加害人或被害人
具有接受修復的意願,故不論時間點或角色為何,皆可受理,惟須經由開案流程評估後,
方可決定是否正式進入修復式司法。
開案評估之指標為9:有認錯或承擔責任之意、無重大前科、未因罹患精神疾病致減
損溝通表達能力、未因藥物濫用致有影響對話之虞、未成年之被害人或加害人,應經監
護人同意或陪同參加、無被害人之犯罪及兒虐案件,暫不列入。若為家暴案件需施作危
險評估量表(台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TIPVDA),經評估為低度危險程度者始能進
入對話程序。
(二)國外現況
探究國內試辦方案流程得宜與否,仍須佐以各國執行修復式正義之方法、程序,並
考量各國文化、宗教以及民族性等相關因素之異同,納入本研究進行探討,以研擬推動
修復式正義之執行策略,進而運用於家庭暴力事件之處遇。以下概述各國應用修復式正
義於家庭暴力事件之相關研究報告,並分別說明其操作模式及成效評估(Liebmann, M. &
Wootton, L., 2010):
1.英國:英國用以處理家庭暴力事件的方案為整合性家庭暴力方案(Integrated
Domestic Abuse Programme,IDAP),此方案用以降低家庭暴力事件之再犯率,其促使多
種單位(包含內在與外在)參與工作,並透過風險管理措施提供婦幼安全之保護,此方案
具有以下九個特點:(1)非暴力的,(2)非威脅性行為,(3)尊重,(4)支持與信任,(5)責信
與誠實,(6)性別保護,(7)夥伴關係,(8)子女扶養之責,(9)協商與公正。
2.奧地利:奧地利有一個良好的家庭暴力調解方案,其調解員除須接受調解相關專
業訓練外,亦受過社會工作的訓練。在家庭暴力案件處遇流程中,由檢察官轉介案件至
調解員,由其進行調解作業;在取得家暴事件雙方之同意後邀請至調解中心,其後由一
男一女的調解員分別進行協調,在分開協調之後,再將四個人集合在一起進行故事交流,
以了解事件雙方之看法以及對於未來的期待;此模式乃以”距離”的效果促進“承
認”,於調解中平衡現有的權力不平衡和支持較弱的一方。進行此調解模式前,具有以
8 法務部網頁: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199866&ctNode=28162&mp=001 2011/8/30
9 法務部網頁: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207793&ctNode=28162&mp=001 2011/8/30
18
下先決條件:(1)被害人同意,(2)暴力行為終止,(3)加害人承擔責任,(4)僅加害人接受
譴責,而非被害人,(5)在認錯之後方可執行。
3.比利時:比利時由 SUGGNOME 所執行之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模式(VOM)處理部
分的家庭暴力事件,以做為其家庭暴力事件處遇服務之一。
4.芬蘭:芬蘭已有家庭暴力事件轉介調解。一項研究自 2001年至 2003年間,從四
個不同城鎮的法院中,彙整 416件案件審查案,其中有 116件保留法院處置,而 242件
則轉介調解,而後被判刑的共計 116例,19 人轉介輔導(Liebmann, M. & Wootton, L.,
2010)。
這項研究包括採訪者,受害者,調解員,法官和計畫工作人員。研究的主要目標為
將個案轉介調解的罪行嚴重程度分級,某種嚴重程度以上的案件由法院處理。法官認為
“調解並不能使暴力合理化”,其希望看到以調解恢復家庭關係,但不做為法律的替代
處遇。
各方參與調解的動機分別是:(1)被害人:不想去法院(如羞愧)、不想看到處罰作
為解決問題的結果、需要改變關係、想為家庭暴力找出原因。(2)加害人:如果暴力是偶
然,調解似乎是一個合理的前進方向、處罰將削弱家庭的財務狀況、法院無法處理複雜
之關係、部分被害人要求且同意調解、期待調解導致較輕的判決。
目前芬蘭對於家庭暴力事件進行調解的先決條件為:(1)參與過程乃真正自願,(2)
在各階段的過程中,獲得志願調解員及專業工作人員之指導和支持,(3)亦需要其他相關
義工支持,(4)可詢問是否需要其他服務,(4)在家庭暴力案件處遇過程中,專業工作人員
的調解服務始終與其他機構密切合作。而執行家庭暴力事件調解的過程為:(1)家庭暴力
案件只有警察或檢察官可以轉介調解。(2)由專業工作人員決定是否將案件轉介調解,(3)
由家暴事件處理之專業人員選定調解員,(4)調解員於案件執行前與合作成員進行聯繫,
(5)調解員和家暴事件雙方進行個別會議,其目的是:第一時間與被害人交談、獲取家
庭暴力的信息、解釋調解其性質、可能性和影響、傾聽家暴事件雙方並給予支持與激勵,
(6)進行聯合會議,其目的是:探索調解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聽取家暴事件雙方的意見和
目標、幫助“改變”工作的啟動,(7)達成協議,(8)遞呈該協議至警察或檢察官,(9)持續
追蹤該協議。
5.德國:德國具有Waage 計畫,其漢諾威是一個非政府的組織,其提供成人和青少年
被害人與加害者者調解制度,在過去的幾年中亦參與家庭暴力案件,可推行此制度的原
因為具網絡性的地方組織,各盡其責:警方接受特別訓練,社會工作者在早期階段介入,
檢察機關針對此類案件考量特殊利益,婦女團體給予支持服務以協助受害者(通常是婦
女),以及提供課程予施暴者。Waage提供了一個公正的服務:先和加害人訪談之後,了
解未來調解可能進行的方向,無論是間接或面對面。該服務採用了聯合調解模式,以一
男一女做為調解員。該服務一年約處理 200 份案件,包括偶然性的暴力行為以及長期暴
力關係。調解的目的和結果將因家暴事件雙方的期望而異,有些希望關係結束,有些則
期望和解,有些問題亦涉及兒童或賠償;有些女性要求男性參加治療團體,例如酒精成
癮問題,並尋求改變其行為。通常在協議後三至六個月間,舉行一個追蹤會議進行與協
議結果之相關檢討。
19
6.希臘:2006年頒布了一項法律進行家庭暴力案件調解,此法律之緣由乃經過 1999
年和 2003 年的調查後,確定家庭暴力是一嚴重的問題,故提出此法。法律規定調解必須
由檢察機關進行起訴前或起訴後開始,只要加害人承諾以下事項即可進行:(1) 未來不
再有任何家庭暴力的行為,(2)將參加特殊輔導或治療方案,(3) 若可能,即對被害人提
出賠償。針對這項計劃的評價指出,因為角色的矛盾(檢察官不是調解員)造成必然之失
敗,且該國家暴的專業領域,尚未有此訓練。亦無監管或專項經費,所以一切都為紙上
談兵。
7.荷蘭:荷蘭運用家庭協商會議於處理家庭暴力事件之成功,且該報告亦提在幾個歐
洲國家所進行的類似方案。
8.羅馬尼亞:隨著歐盟相關學組及民間社會組織的鼓勵,羅馬尼亞開始進行被害人與
加害人調解方案,以作為法院在處理某些案件之替代方案,其中包括有關家庭暴力的處
遇亦納入法律規範中。其法規中第 5章,第 19-22節,編號 217/2003之法律條文明文規
定,家庭暴力事件可於某種情況下進行調解;第 21節闡明家庭會議由家庭成員或社會工
作者組成,其協商會議的結果將不影響有關家庭暴力事件之刑事審判,目的為使家庭成
員中受到虐待的人提供機會,以滿足和討論一個適當的解決方案。
9.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分析家庭暴力事件經調解後,其加害人於兩年內的再犯罪
率,以 100 件調解達成協議的案件與 118 件訴訟案件進行比較。結果顯示,在 100件調
解案件中,再犯罪率為 16%。而 118件訴訟案中,由於缺乏證據導致解除 59個案例,
因此僅分析進入司法程序的其他 49個案件,結果顯示其再犯的比率為 43%。
10.美國:和平計畫中提及,參與修復式正義的婦女在符合五個條件的狀況下,對其
較為有利:(1)相對於加害人的復原狀況,優先將被害人的安全納入考量,(2)提供被害人
相關社會支持,(3)協調工作之一為社會層面的回應,(4)判決中反對性別暴力統治,(5)
過程中不以”原諒”做為目標。
11.美國─夏威夷:夏威夷的 Pono Kaulike 方案,其意義為”平等的權利和正義”,該
計劃於 2003 年開始實施,並有以下相關措施:(1)恢復性會議:被害人、加害人和雙方
支持者組成一小組,討論每個成員所受之危害和可能如何被修復。(2)恢復對話:參加者
僅限被害人與加害人,而不包含家人或朋友;被害人往往只是想知道,加害人對於其犯
罪行為是如何的懊悔。(3)恢復會話:討論如何修復傷害,並引出被害人對於未來的期待。
除此之外,亦注入問題解決導向的修復式介入方案。
12.加拿大:Pennell 和 Burford 發展了一個修復式正義模式的家庭會議,用以保障家
庭。計 32 個家庭參與,執行 37場次的會議,共有 472人參加,其中 384 人是家庭成員。
這項研究包括比較組,以及進行前、後測比較分析。主要發現為執行修復式正義模式的
家庭會議,具有以下成果:兒童虐待和家庭暴力之減少、促進兒童發展,以及擴展社會
支持。
13.加拿大:此地的原住民社區具有一套發展完善的處理家庭暴力事件之修復式正義
系統。他們認為任何不當行為皆須受到教育和治療。Edwards和 Haslett 描述一個計劃,
其重點為強調損害的解決、確保參加者的安全、加害人的責任,以尋找進行對話和恢復
的機會。經由審慎的評估後,由加害人與被害人自願參與,加害人對被害人的安全須負
20
全責,並希望自己的行為改變;對於被害人來說,提供一個安全的空間講述其故事為一
艱困的體驗。此模式積極的成果包括和解、寬恕,和恢復,但重要的是不要製造任何期
望。其目的並不在於恢復到“暴力前狀態”,而是為了創造社會平等的關係。結果顯示,
大多數被害人和加害人傾向單獨與調解員召開會議,而非與家暴事件涉及的朋友和家人。
14.澳大利亞:土著及家庭暴力研究計畫網絡成員包括從事與原住民法律服務、社區
發展、就業計劃、法庭服務、原住民遊客計劃以及原住民醫療服務…等;由一群人組成
一個鬆散的協調指導委員會,監督早期階段的計畫。該計畫借鑒了加拿大計畫,開發了
一個康復式的模範社區,集結來自家庭的支持和更廣泛的社會基層輔導員,提供協助和
治療,而非法院和監獄。該計畫發現,當地的人願意參與整個過程,以認識其面臨的困
難,由當地居民和研究人員共同合作,產生一種模式,堅決採用原住民方法,通過血緣
關係和家庭成員提供了一個高度的領導,尋求解決犯罪和反社會活動。澳大利亞的土著
婦女,其比非洲土著婦女接受高達 45倍的家暴,為了因應此狀態,設計了一個家庭治療
中心,其共有一中央的空間及四個公共空間(婦女和兒童、男性、老人,以及年輕人)。
當家庭暴力事件發生後,事件關係人至其指定的空間,相互交談,隨後一起走到中央的
公共空間,共同解決問題。
15.紐西蘭:1995年懷卡托調解服務協議起草一個修復式正義計劃,並於漢密爾頓進
行試驗。其設計了一個混合模式的調解服務,包括:(1)單獨會議:被害人與其支持者、
加害人與其支持者分別進行單獨會議。其目的為解決家庭暴力事件對當事人和他們各自
家庭、朋友所帶來的影響,並試圖終止暴力。(2)聯合會議:討論共同問題。(3)後續會議:
監督家暴事件雙方是否遵守所作的任何協定。此計畫的報告顯示,調解制度不適合運用
於家庭暴力事件,除非少數獨立事件或特殊情況以及具有完備的安全防範措施。
此外,紐西蘭司法部推動 The Mana 社會服務方案,此乃一司法判刑前的修復式正
義方案。其進行的流程為:
(1)轉介:由法官或律師或在某些情況下將案子轉介調解,調解員每兩個星期參加地
方法庭聽證會,並於聽證會上針對法官提供之內容進行評估;當被告認罪之前,
通常律師會要求其委託調解員,先行評估是否適合修復式正義,此為修復式司法
的最佳實踐。
(2)會前會:此會議由加害人、促進者以及其支持者共同參加,促進者確定加害人是
否適合修復性會議,並強調其須接受的事實和需對其行為負責,並維護被害人的
觀點。
(3)接觸被害人:由促進員聯繫被害人,解釋修復式正義的過程及安全,並告知被害
人具有參加會議的選擇權,亦尊重其選擇。
(4)會議:除非加害人和被害人同意一起出席,一般促進者將安排罪犯和受害者分別
在交錯的時間到達,以確保受害者的安全,促進者將針對特殊需求開始一個儀式
(例如 Karakia 毛利禱文及咒語),並概述會議的過程,促進者將詢問被害人的故
事以及暴力對其影響,此時,促進者不發表任何評論,並詢問被害人之需求,讓
對方因為暴力而能補償或贖罪,若加害人願意達成條件,修復會議即完成。
(5)向法院提出報告:促進者將撰寫一份報告給法庭,概述會議的結果和達成的協
21
議,法官經常會休庭直到達成雙方皆滿意的協議;若協議失敗,亦需向法院提出
報告,以進行後續之量刑判決。
16.南非:在南非,許多案件皆涉及家庭暴力,而其家庭暴力法在 1998 年推出,制
定保護婦女免受家庭暴力之法律,並舉行加害人與被害人會議(VOC)。於此背景下,加
害人皆熱衷於選擇 VOC方案,因其認為,法院處罰將造成其家庭經濟狀況衰退,且服
監的恥辱則使其無法再度就業。因此,透過調查發現修復式正義模式在南非的執行可減
低阻抗,增加調解的滿意度,減少再犯率,並使其有更多的機會講述自己的故事和尋求
解決方法。
17.甘比亞:甘比亞提倡社區治安和恢復性司法計畫,此計畫亦包括家庭暴力案件的
處遇。
18.牙買加:為打擊牙買加犯罪上升率,於 1994年成立分別提出三個計畫:爭議解決
基金會、校園和平與愛方案,以及警察調解單位,後者的設立乃為因應家庭暴力問題之
發生。
19.哥倫比亞:1995年,哥倫比亞政府在美國國際開發署的財政支持下,設立了兩個
Casas de Justicia,其目的是提供市政服務於刑事和家庭暴力事件,並協助解決問題,提
供的服務有:心理、警政、法律顧問、檢察官、家庭服務、醫療保健以及受害者服務。
如調解為解決衝突之主要處遇模式,透過對話而非暴力,更有助於創造更加和平的社區。
以實務面歸納修復式司法之型態以及執行國家,主要可分為以下類型10:
(1) 調停或和解:比利時、法國、土耳其、紐西蘭、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美國
部分州,多數拉丁美洲國家、西班牙、泰國。
(2) 家族集團會議與量刑圈(Sentencing Circle):大部分運用於原住民族中。
(3) 社區型判決:英國。
(4) 少年事件的特別程序與處遇措施:紐西蘭、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美國部分
州,多數拉丁美洲國家、西班牙、泰國。
(5) 宗教儀式或族長會議(council of chiefs):阿拉伯半島的阿曼、大洋州的薩摩亞。
表六、各國執行模式比較
執行模式 執行國家
調停或和解 比利時、法國、土耳其、紐西蘭、澳大利亞、英國、加拿
大、美國部分州,多數拉丁美洲國家、西班牙、泰國
家族集團會議與量刑
圈(Sentencing Circle) 原住民族
10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網頁:http://www.tyc.moj.gov.tw/ct.asp?xItem=120502&ctNode=22014&mp=012
2011/8/31
22
社區型判決 英國
少年事件的特別程序
與處遇措施
紐西蘭、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美國部分州,多數拉
丁美洲國家、西班牙、泰國
宗教儀式或族長會議
(council of chiefs) 阿拉伯半島的阿曼、大洋州的薩摩亞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南非(種族隔離議題)
第三節 相關研究之比較與分析
一、相關研究之比較
Mills(2003)和平圈及療癒圈背後的理論架構包括 William Bridge的轉型架構
(Transition Framework)、恢復公平公正的研究、改變之階段 (Stages of Change
model)。紐約大學暴力與康復中心(Center on Violence and Recovery,簡稱 CVR)進行
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的研究,比較傳統家庭暴力處遇方式和療癒圈處遇的對照
組,以評估修復式正義對親密暴力的有效性,這項研究提供的數據表明,修復式正義的
處遇方法,對家庭暴力而言是一個安全的選項。
國內社會暴力案件逐年在增加,但通報率幾乎只有 17%左右,原因之一是(黃翠紋,
2010)法律對加害人的嚇阻效果有限,家庭暴力發生的原因相當複雜,施虐者的特質多樣
性及法律懲罰與被害人需求的相互衝突以及大家認為家暴是家務事,法不入家門等,這
與猶太社會的認知很類似,因此療癒圈或許是發展本土應用修復式正義在家暴事件上,
值得參考的模式之一。
黃蘭媖、許春金、黃翠紋(2010)在華人文化下的溝通模式會受命運、人情、面子等
影響,在修復會議的實踐中,對話促進者首先必須瞭解當事人的價值觀是較接近傳統或
較接近現代,接近傳統者促進對話技巧必須對集體主義,五倫關係,中庸之道,外在和
諧有更高的敏感度,華人對於感情的表達較不精準,且較容易以瑣碎而跳躍的方式表達,
當事人難以說出感受則需要促進員引發當事人的情緒以及增加其感受性用語,並注意非
語言的暗示。
學者黃蘭媖、許春金、黃翠紋(2010)提及各國在施行修復式正義的初期,有些是由
宗教性質的非政府組織所推動,如美國的 MCC,這是由門諾教徒 Howard Zehr所主導的
宗教團體,又如加勒比海地區由耶穌信徒所組成的 CURB。如澳洲的維多利亞州施行的修
復式正義,由基督教聖公會推動。
23
在各國持續發展修復式正義的過程中,非宗教性質的非政府組織,也開始扮演修復
式正義的推動者角色,如北美的 PACT及各大學成立的修復式正義研究中心,這些非政府
組織與政府結合,扮演修復式正義推動者的角色也成為政府合作夥伴。協助政府推動修
復式正義的教育,以及創新方案模式,培訓,評估和研究等任務,如加拿大的 (The Centre
for Restorative Justice)修復式司法中心,這是一個由加拿大懲教局資助西蒙弗雷澤
大學犯罪學學院所所設立,以支持和促進修復式正義應用在司法制度的原則和做法。另
外如南非的 Khulisa,這是南非的預防犯罪組織,在預防犯罪,取得了重大進展,當南
非在面臨犯罪顯著增加的時期,該組織對促進社會應用修復式司法在預防犯罪有其貢
獻。並也使用數組方案,以協助瀕危兒童的保護和青少年罪犯。
各國的非政府組織也提供各種服務和活動,在社政和司法系統實施修復式正義的各
個階段,扮演重要角色,包括預防犯罪、履約成效、技術執行、追蹤關懷等不同階段的
執行,如 MCC透過新聞稿、手冊、訓練營、年會等方式致力將加害人、被害人調解方案
導向制度化,英國也致力於 FGC家庭小組會議調解模式的訓練,並推動帶有修復式精神
的公共政策提案。紐西蘭法院的轉向執行單位就是以地區性社會團體為主,這些團體接
受政府的補助,並與政府簽訂契約,成為修復會議的執行單位,而國際監獄團契(Prison
Fellowship)則在犯罪人服刑階段及出獄初期提供服務,因此 NGO的參予在執行的層面佔
有重要的位置,NGO提供服務包括:研究方案和做法、資源中心服務、網站的發展、方
案的制定和評估服務、教育服務、修復式司法主題的培訓班,研討會和工作坊、焦點會
議發展(工作會議)包括學者和研究人員的參與、原住民方案的發展、婦女的女權主義
倡議等。
各國的修復式正義方案,初期多以試行方案開始,因此多有委託非政府組織作方案
成效之評估及資料的收集等,先有實務而後有理論的發展,甚至是實務方案深度與廣度
的拓展,如美國的 MCC,在研究中朝如何提高受害者和他們的支持者參與修復式正義的
意願而累積更多的實務研究因此將來實施修復式正義,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結合,發揮資
源整合的功能,以奠定本土化修復式正義的基礎。
二、運用修復式正義於家庭暴力事件之優劣分析
運用修復式正義於家庭暴力事件處遇中,除須評估事件之適切性外,更應審慎掌握
加害人與被害人之精神狀態,並進行暴力危險評估,以預防執行過程之失當,造成憾事。
相關實症研究針對 135位家庭暴力被害人,於其接受修復式正義之司法模式後,進行滿
意度之調查,發現其中 44 位認為修復式正義之執行過程公平,並給予正向肯定;另 45
位被害人則未明確表示對於修復式正義之主要觀感為何;其餘之 46位被害人,則因相關
因素,並未接受後續之實證研究(Julie Stubbs,2010);由此研究顯示,對於修復式正義
運用於家庭暴力事件中,針對其處遇結果之優劣與否,仍需進一步探討。
學者(洪英花,2011)引述麥克蓋瑞爾教授之研究,其針對美國印第安納州首府
(Indianapolis)自 1996年至 1999年的少年刑案被告取樣,區分實驗/處遇組(232名)
及對照組(226名),以實施修復式司法方案滿意度、參與度、行動認知、價值觀及正義
意識等等變項進行比較,經過為其一年期之追蹤調查後,研究結果顯示,曾經修復式司
24
法程序者的犯罪者,比較接受一般傳統刑事司法程序者,略有較低的再犯罪率
(12.3%<22.7,P< 0.05)。由上述之實證研究得知,實踐修復式正義於犯罪處遇上具有
部分效果,然若依此正向之效果,即推衍運用於家庭暴力事件中,實為草率,亦不可貿
然行事。學者(潘雅惠,2009)認為,現行之家庭暴力防治法明文禁止保護令事件進行調
解或和解,如此的規定及令函有其值得探討的空間,顯現其於家庭關係崩解之修復與法
令制度僵化之改善,身陷兩難之泥沼。
修復式正義運用於家庭暴力事件處遇之必要性與可行性,可由家暴行為之特性以及
現行司法體制之運作進行探討(潘雅惠,2009):
(一)從家暴行為之特性談其適用修復式司法程序之必要性:
首先,就人的特質而言,家庭暴力事件中,加害人與被害人具有情感依附之關係,
被害人因家暴事件訴諸法律,主要目的為遏止加害人之暴力行為,並回復情感之聯繫,
而非斷絕婚姻或正常家庭關係。其次,就事件的發生,多起因於錯綜複雜之家庭關係,
且非為單一獨立發生之事件,往往具有重複性及週期性,整個家庭暴力的循環為醞釀期、
爆發期以及蜜月期,究竟司法制度介入之階段為何,須審慎評估,若以修復式正義之觀
點視之,於家庭暴力的每個週期中介入,啟動家庭成員及整體社區之修復機制,應可達
到預防及減低家暴再犯之成果。再來就時間性來看家庭暴力的發生具有長期、連續、不
定時的特性(潘雅惠,2009),然通常保護令的時效有限,須視情況提出延長聲請,對於
被害人來說,此非為實質解決之道,因此須有關係修復工作之介入,較能促使家庭關係
回復。此外就地點來看家暴發生的場域在社區中,而加害人與被害人亦須於社區中繼續
生活,因此,若家暴處遇的模式由傳統的司法仲裁或訴訟,取而代之為社區中的修復方
案,應可取得更多之資源,讓整體事件之關係人能在原處之社區中進行關係之修復,以
達更好的效果。最後,就結果而言,修復式司法所注重的增權展能(empower)以被害人為
核心,傾聽被害人的聲音,重視被害人的地位,同時也尊重加害人,讓加害人可以為其
行為負責(潘雅惠,2009);此賦權之過程,可使家暴被害人更有能力挺身面對問題之所
在,以其自主、自決之立場,與加害人對話,透過互相了解與溝通的過程,重建兩者間
的關係,以達成事件雙方所預期之結果。
(二)修復式司法的理念與程序有助於改善家暴當事人之關係:
修復式正義關注的重點是協助被害人、加害人及雙方家庭、社區進行充分的對話,
讓當事人之間有機會充分的陳述與傾聽、進一步澄清事實、了解對方的感受、提出對犯
罪事件的疑問並獲得解答。因此,運用於司法制度中,其理念與程序將有助於改善家暴
當事人之關係,學者(潘雅惠,2009)歸納修復式正義之理念,對於改善家暴事件關係人
有所助益之相關因素:○1 修復式司法試以衝突的觀點,而非從法律的觀點來看待紛爭,○2
修復式司法是一種回復損害的關係式正義(Relational Justice),○3 修復式司法主張藉著發
現問題、弭平紛爭、填補損害、治療創傷以進行廣泛且有意義的社會革新,從而為社會
創建更多更好的和平及福祉,○4 修復式司法尋求加害者、被害者及社區共同參與修復及
治療的歷程,○5 修復式司法程序處理紛爭的場域在社區。上述之五大因素,推使修復式
正義運用於家暴處遇中,應可達到與傳統司法制度不同之果效,以解決現行司法制度中,
缺乏人性及關係脈絡之疏漏。
25
(三)家暴事件在現行體制適用修復式司法之可行性:
學者(潘雅惠,2009)認為運用修復式正義於家庭暴力事件中有其可行性;其分別自
法令、制度、修復機制以及資源取得與運用等面向進行分析,闡述於現行體制中,進行
修復式司法之可行性:以法令面來說,雖家暴法明文規定保護令事件不得進行和解或調
解,但在符合特定要件時,仍可進行和解程序,由是,以修復式正義的模式進行家庭暴
力事件的處遇,於目前法令上仍具有某種程度之可行性。於制度面中,修復式正義符合
訴訟制度中的公平正義需求,且民事訴訟法將具一定親屬關係之糾紛列為強制調解之事
項,故運用修復式正義的概念於調解制度中,應可解決以強制力介入家庭暴力案件所造
成之局限。就修復的機制而言,修復式正義讓被害人有機會描述其所經驗的犯罪過程,
以及表達他們的需求且參與決定程序,以達到情感修復及填補實質損害。對於加害人一
方也藉此機制承擔己身之過錯,並主動道歉及承擔賠償責任,以經歷自我認知及情緒之
正向轉變,進而改善自己與家庭、被害人以及社區之關係,俾助其復歸社會。透過此公
開、平等之對話程序,提供一個非敵對、無威脅的安全環境,讓被害人、加害人及社區
(群)能完整表達其利益及需求,並獲致終結案件的共識及協議。最後,就資源的取得
及運用而言,修復式正義需結合眾多資源,如警政、社政、衛政及司法等相關實務人員
共同努力,以逐步建立修復式正義之網絡。
基於上述之說法,修復式正義運用於家庭暴力處遇中,具有某種程度之可行性,然
因家庭暴力涉及之問題層面較為廣泛且複雜,更牽涉背後龐大之權力、利益之糾葛,故
於程序面以及實質面上皆須謹慎行事(潘雅惠,2009):於程序面向而言,應注意慎選適
當的案件類型,如現行之試辦方案開案條件中,家暴案件需施作危險評估量表
(TIPVDA)11,且經評估為低度危險程度者始能進入修復程序;此外,應保障參與者之人
身安全,且執行修復前,須徵詢被害人與加害人之參與意願,並以面對面對話的機制進
行關係之回復;於執行修復前,須成立程序團隊進行充分的事前準備工作,並挹注大量
資源,確保整體程序之彈性與反應能力,並由司法體系站在中立角色配合協調結果的出
現;如此一來,得以在保障當事人安全之前提下,達到其希冀之修復目標。
除程序面向外,於實質面向亦須強調被害人與加害人必須受到充分的尊重,並鼓勵
當事人雙方實質的參與決定,並使其在不受壓力的情況下願意坦承一切,以確實負起責
任;而執行單位亦須規劃供當事人選擇修復的方案,並落實非以達成特定協議為主要目
標,以避免造成其壓力,朝向建立良好互動及溝通模式之發展,進而形成和解或調解之
修復結果。修復式司法之執行,須考量現行制度與可行性等相關面向,進而以修復式正
義的相關模式開展於多元的家庭暴力事件處遇。未來,修復式正義可運用於預防性工作
及方案中,納入的範疇為低度危險、非群聚關係(非操控性關係)、非易怒、衝動類型、
雙方具有意願等之個案,並妥善掌握調解之內容,以非暴力之部分為主要修復重點;此
外,調解之過程超脫司法程序,以更長期的時間進行工作,如此一來,除彌補現行司法
制度之不足外,更可使家庭暴力事件之關係人,得到情感與社會脈絡之修復。
11法務部網頁: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207793&ctNode=28162&mp=001 2011/8/30
26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修復式正義應用於家庭暴力事件之可行與否,而進行國內實證
與深入探討,為達資料的豐富性,採用立意取樣,依據研究目標,聚焦於我國修復式司
法試行方案運用在家庭暴力事件之運作過程及結果,並以試行方案在未來與在地的、本
土的思維方式或操作模式來拓展的可行度進行意見之蒐集及討論分析,並以進行深度訪
談,期建構適用台灣在地性之修復式正義實施模式的相關建議。
深度訪談的對象包括目前試行方案司法體系之主任檢察官、檢察官、觀護人、專案
管理員、修復促進員,以及目前執行家暴防治之婦女團體領袖及家庭暴力防治實務工作
者與修復式正義領域專研的學者專家等。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文獻探討及深度訪談、焦點團體訪談,輔以漸進式焦點訪談做為研究工
具,透過文獻探討與深度訪談,將所得的資料加以系統性的整理,再輔以漸進式焦點訪
談及調查問卷,採用三角交叉檢驗法,強化研究的可信度,並從訪談內容分析修復式正
義應用於家庭暴力事件之可行性的探討,做為將來如何建構適用於台灣之修復式正義模
式之參考。
(一)研究工具介紹
1.文獻探討
本研究在第一階段蒐集國內外之相關著作、期刊、論文、統計及網路資料等,透過精
讀、整理與分析之方式,作為本研究之基礎。透過相關研究及文獻之整理與對照,以便
了解研究現象及脈絡背景。研究團隊以跨國比較十餘國實施修復式正義應用在家庭暴力
事件之經驗,在本文中概要介紹 19個國家之修復式正義於司法體系內應用於家庭暴力事
件之實務運作。首先了解各國以修復式正義應用於家庭暴力事件之方法、程序,並考量
各國文化、宗教以及民族性等相關因素之異同,進行探討,以研擬國內推動修復式正義
之執行策略,進而連結運用於家庭暴力事件之可能性研究。
2.深度訪談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以焦點團體訪談,個人深度訪談等方式執行,先擬定訪
談大綱,訪談大綱之內容主要依據文獻探討與本研究的目標而發展出主題,以收集於目
前執行之實務中,學者專家與實務工作者個人主觀感受與問題的發掘,主要有:與「修復
式正義之司法制度」的核心價值及執行經驗及感受,實施上權能分工、工作流程、案件
評估、聯繫溝通、相關表單填寫等之看法;修復促進員應具備之專業、特質及訓練;家
27
庭暴力事件執行「修復式正義」之條件、指標、成效、實施階段及實施模式;華人社會
「和諧」與「面子」之文化心理社會現象之影響,及對話之平台之基礎與因素;非政府
組織在我國推行修復式正義可扮演之角色任務及施行之實務模式等議題,藉著半結構式
之開放性問題的回答以獲取全面而完整的資料。
第二節 研究程序
一、實施程序
(一)取樣:依據研究目的,邀請受訪者,受訪者名單如下表。
表七、受訪者代號及基本資料一覽表
序號 代號 性別 訪談次數 專業領域/職稱
1 A7 女 1 法律/律師
2 A4 女 2 社工(婦女團體)/執行長
3 A5 女 1 社工(婦女團體)/執行長
4 A1 女 2 社工(婦女團體)/專員
5 A3 女 1 司法/法官
6 A2 女 1 社工行政/秘書
7 A6 女 1 司法行政/主管
8 B1 男 1 大學教育/校長
9 B2 男 1 神學教育/院長
10 B3 女 1 社工教育/教授
11 B4 女 1 社工教育/教授
12 B5 男 1 衝突研究/主任
13 B6 女 2 神學教育/教授
14 E 男 1 犯防教育/教授兼主任
15 C2 男 1 社工教育/助理教授
16 C1 女 1 犯防教育/助理教授
17 C4 女 1 司法教育/副教授
18 C3 女 1 司法教育/教授
19 H1 女 1 社工行政/組長
20 C5 女 1 社工行政/專員
21 D6 女 2 司法/主任檢察官
22 D2 男 2 社工/個管員
23 D4 女 2 心理/修復促進員
24 O2 女 2 心理/修復促進員
25 N2 女 1 社工/修復促進員
26 O1 男 2 醫療/修復促進員
28
27 D7 女 1 社工/組長
28 F3 女 1 社工/督導
29 F4 女 1 社工(婦女團體)/社工師
30 F1 女 1 社工(婦女團體)/主任
31 F2 女 1 司法社工/社工師
32 G2 女 1 社工/主任
33 G3 女 1 社工/督導、修復陪伴員
34 G4 女 1 社工/督導、修復陪伴員
35 G1 男 2 社工/修復個管員
36 D3 女 2 心理/管理者、修復促進員
37 D1 女 2 心理/修復促進員
38 D5 女 2 司法/觀護人、修復促進員
39 H2 女 1 司法/主任檢察官
40 H8 女 1 司法/觀護人、修復促進員
41 H5 女 1 社工(婦女團體)/執行長、修復
促進員
42 H6 女 1 社工(婦女團體)/理事長、修復
促進員
43 H7 男 1 社工(婦女團體)/修復促進員
44 H4 女 1 社工/修復專案管理
45 L 男 1 社工教育/助理教授
46 H3 女 1 社工/主任
47 H9 男 1 司法/主任觀護人
48 I1 女 1 社工教育/助理教授
49 I2 女 1 心理/執行長
50 I3 女 1 社工教育/副教授
51 I4 女 1 司法行政/主管
52 I5 女 1 社工/主任
53 P1 女 1 司法/家調員、修復促進員
54 P2 女 1 司法/家調員、修復促進員
55 D7 女 1 司法/觀護人、修復促進員
56 K 女 1 社工/組長
57 J 女 1 法律/律師
58 M 女 1 司法教育/副教授
59 N 男 1 犯防教育/教授
60 Q 女 1 醫療/社工師
共計訪談 60人 (72人次)
29
(二)邀請訪談:訪談前以電話或電子郵件邀請受訪者,並經受訪者同意後,將訪談錄
音。訪談分為:學者專家焦點團體訪談及個別深度訪談。
1.學者專家焦點團體訪談
運用焦點團體訪談方式,透過多元專業專家學者之立場、意見及經驗等互動討論,
針對本計劃所列之問題深入表達。焦點團體訪談對象就已進行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
之地檢署研究及執行人力,以及各地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主管及婦女團體領袖進行邀
約及深入訪談,訪談對象包括研究學者、檢察官、觀護人、修復促進者、修復陪伴
者(支持者)、專案管理員、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主管及專業人力等。共辦理十場,共
計 53位(65人次)學者專家參加,所有焦點團體訪談都由計畫主持人親自主持。
2.學者專家個別深度訪談:
就未能參與焦點團體之學者專家,訪談對象包括修復式正義研究學者、檢察官
及家庭暴力專業學者專家等,並在恪遵專業倫理下訪談當事人,所有個人深度訪談
工作都由計畫主持人親自訪談。
3.半結構式訪談題綱:
分為兩階段進行,初次訪談以(1)~(6)執行,待整理及初步分析後,再進行漸進
式訪談,訪談題綱為(7)~(10),題綱如下:
(1)在您參與「修復式正義之司法制度」的執行過程中,您的經驗及感受為何?您
覺得此制度之核心價值為何?您有何實施上之發現?
(2)您認為執行「修復式正義」司法革新計畫之修復促進員應具備何種專業、特質
及訓練?以國內的司法處境,培訓課程應含哪些內容?
(3)您認為以家庭暴力事件執行「修復式正義」,若在什麼條件下將成為一個適切
的選擇?而在哪些條件下則不可行?
(4)您認為如何評估修復正義應用於家庭暴力事件之成效?其須建立之成效評估指
標為何?
(5)您對於目前「修復式正義之司法制度」的執行,在權能分工、工作流程、案件
評估、聯繫溝通、相關表單填寫等之看法為何?
(6)您認為華人社會相當強化社會心理學「和諧」與「面子」之文化現象,在執行
修復式正義時應注意之事項為何? 且國內外資料顯示其應用於宗教及部落已
有實證上之成效,但若信仰提供對話之平台乃因其共同信仰之基礎,那台灣
社會在缺乏此等共同基礎之處境下,執行修復式司法該注意哪些因素?
(7)您認為以家庭暴力事件執行「修復式正義」程序,若以可實施或啟動於刑事司
法的四個節點,即警察階段(起訴前)、起訴階段(審判前)、審判階段(定罪獲
量刑前)、矯治階段(當作監禁的替代性措施,或非監禁措施的一部分或附加
部分)等,你贊成實施於哪個階段為宜?為什麼?
(8)依據文獻及焦點會議之意見,在以被害人意願為考量呈非權控關係之系統
30
評估加/受害人對關係的延續有期待暴力非為高危險型態家庭關係具
支持性等因素,則可考慮以修復式正義為處遇模式之考量,對此您的見解及
回應為何?
(9)以修復式正義之實施模式分為:被害人與加害人調解(VictimOffender
Mediation,簡稱 VOM)家庭協商會議(Family Group Conferencing)
和平圈(Peace Making Circle,或稱量刑圈,Sentencing Circle)社區
修復委員會(Community Restorative Boards),您覺得以我國在家庭暴力
事件實施修復式正義可推行的模式及其理由為何?
(10)您認為非政府組織在我國推行修復式正義可扮演之角色任務,與可施行之實
務模式為何?
(三)紀錄與整理:將錄音謄為逐字稿,以做為資料分析,逐字稿完成後以代號編碼,
避免透露受訪人員身分,資料匿名呈現,以符合研究倫理。
(四)實施受訪者基本資料及培訓課程意見調查(如附件ㄧ),將文獻蒐集與深度訪談之
發現,彙整成調查表,期能透過受訪者之意見,能針對本國修復式正義執行人力
之培訓,提出建議。
二、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資料之收集以修復式正義應用於家庭暴力事件之可行與否為核心,透過文獻
會議提出問題,持續修改與增添最新資訊,比較各國實施之特色以作為我國政策借鏡,
並以焦點訪談及個人深度訪談蒐集現行試行方案遇到的困難,反思並提出解決辦法,及
將來發展本土性之架構。
資料分析的基礎包括焦點團體訪談及個人深度訪談,以觀察筆記及逐字稿、錄音檔
等,了解受訪談者意念之來龍去脈, 就其內容進行進行分類,並根據所討論的議題與內
容的關連性,做初步的概念化定義,詮釋分析其現象並把握其真實性。
將上述歷程及訪談之質性文字資料,經過開放編碼與意義萃取過程,編織研究對象
的處境與經驗,而凝聚其核心意識,概念化其生命經驗。文字整理與意念發展之結果,
提供予研究對象閱讀,以檢視研究成果之真實性。而研究所產生之結果,均由研究對象
審閱同意之後,始得對外以匿名方式公開發表。執行面主要依逐字稿進行分析。在計畫
進行過程中,研究工作團隊透過田野筆記及訪談過程中受訪者的反應,再加上訪談內容
(即依錄音所謄寫的逐字稿)作為分析本文的依據;分析資料的過程分五個步驟:
(一)逐字譯
將訪談資料、內容、錄音帶,以逐字譯的方式謄寫下來,所必須謄寫的內容除了錄
音帶的文字外,還包括:語言的助詞、停頓聲、旁景說明以及非語言訊息(如肢體動作
等)。此部分的資料分析需與小組人員共同討論,整個訪談內容也須作多次聆聽,體會其
語調、重音、停頓、國台語交替使用之意思,以及整體意涵,並將每一段訪談內容視為
單一事件。
31
(二)資料縮減(data reduction)
接著進行資料縮減,將討論後的結果認為屬於下列如:『斷句與主題無關之詞句』予
以刪除。去除重複過多意義類似的句子,保留有意義的句子。
(三)編碼與概念分類
在一開始收集資料及分析的階段,焦點團體活動紀錄及個別訪談記錄均作開放性編
碼及初步歸類。即先根據其意義進行編碼(coding),接著再逐字分解的過程中,認定某
一社會現象是重要的(即其重要事件),甚至藉理論性的觸覺認定某一現象許多其他現象
有關,並給予分類名稱(naming),形成概念分類。在編碼分類後,研究者不斷地在初步
篩選分類的系統資料中,進行思考及次級歸類。將資料來回持續不斷比較每一段原始資
料,將相似的資料及編碼歸類在一起,成為概念類組(category)。
(四)彙整概念成主題
接著先歸納出數個主題,再從數個主題之中,再群聚出一個核心問題。將數個訪談
作跨個案分析,產生一般性共通主題及部分個案獨特性問題。將分析出來的主題,置於
研究整個脈落或背景之中。接著,連結各個概念主題的意念,而形構出研究現象之核心
意涵。
(五)意義萃取、詮釋資料
最後將所發現的議題或關聯加以整理詮釋,並決定論文撰寫架構大綱、研究結果、
詮釋、討論、結論及建議。
第三節 研究倫理與限制
一、信度及研究倫理
為求研究的可信度,本研究採用三角交叉檢視法,以多元的方法期能獲得可靠的結
果,藉著資料多重收集,包括文獻探討、個人深度訪談、焦點團體深度訪談、漸進式深
度訪談、受訪者基本資料及意見調查等,訪談對象亦採用多元性包括修復式正義及家庭
暴力防治領域之學者專家及實務工作者,並以多個分析者檢驗分析發現來詮釋資料。在
資料呈現時,基於保護受訪者隱私,以符合研究倫理,採用編碼的方式呈現。
二、研究限制
本計畫進行焦點團體訪談邀約時,皆是以學有專精且於修復式正義運用於我國司法
革新上以及長期在家庭暴力防治及政策上鑽研之專家學者,而實務人員深度訪談之邀
約,則以目前法務部修復式司法試行階段之參與執行者及全國唯一由社政(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防治中心)主導之研究方案執行者,以及各參與家暴防治的婦女團體主管為對象,因
此場場討論熱烈,每場皆超出所定之時間,並在有限時間內,每位受訪者皆貢獻專精,
在實施修復式正義與家庭暴力事件之議題上,提出許多可貴的現階段執行意見。惟因邀
約不易,因目前國內投入修復式正義之研究亦同時熟諳家庭暴力議題之學者專家相當有
32
限,試行方案之執行人員仍因能成案進入修復階段之案量也相當有限,經驗累積不易,
模式尚待建立,反而在訪談過程中表達極需督導之期望。
本計畫之文獻資料收集,來自國內外,大量資料中各國對修復式正義應用於家庭暴力
事件之親密關係家庭暴力與非親密關係家庭暴力,在實施的流程、措施與模式均有其特
色,但大都仍在行動嘗試、修正與累積經驗之階段,尚未能完成厚實的理論及技術之建
構,也有某些國家的分析包括比較組與對照組,但數據無法實證,是資料分析的侷限。
33
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
針對受訪者意見,本研究團隊透過嚴謹的整理及意義萃取,將之分類為「本土之修
復式正義原則與工作模式」、「對修復式正義的迷思」、「修復式正義與權控」、「修
復式正義與非政府組織」、「修復式正義的個案評估與類別」、「修復式正義的執行」、
「修復式正義的成效評估」、「修復式正義的執行人員」、「修復式正義的專業訓練」
等,以下則分節加以分析詮釋。
第一節 本土之修復式正義原則與工作模式
受訪者針對台灣本土性的修復式正義實施原則與工作模式,提出「台灣華人文化與
民族性的影響」、「修復式正義的精神」、「修復式正義是相對人處遇的一環」、「修復式正
義是被害人保護的一環」、「尊重當事人的期待與意願」、「不同修復式正義的工作型式」、
「修復工作作為親密關係衝突工作的平台」等七個議題的討論,茲分述如下:
一、台灣華人文化與民族性的影響
華人社會相當重視家族社會系統,強化社會心理學「和諧」與「面子」之文化現象,因
此是否文化規範及文化習俗慣例能涵容修復式正義之理念及工作架構於文化脈絡中,並
在執行修復式正義時,以其文化調適力提升犯罪預防及被害人保護之目的,成為重要的
關注。由受訪者之意見發現文化及民族性確有影響及意義。
修復式正義對於台灣親密關係衝突的正向意義
在親密關係衝突的事件中,父權體制下對男性自尊的推崇,及文化視角下維護面子的民
族性格12,甚且是 Pye教授批評華人沒有自我分析、自我檢討的雅量13,因此若於修復式
正義具司法性之施行中,協助加害人表達歉意,是有其正向意義的。
修復式正義的部分,我覺得我喜歡它的目標跟它的過程,因為有一個家庭其實就像在一個華人的社會裡
面,在一個家庭成員中間去 say sorry這件事情上面其實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關係越親密我越困難去跟
你說抱歉這件事,然後如果之後又要在一起,所以那個相對人是不是這麼容易做,如果其實像在司法裡面
我覺得,司法有一個部份可以做是,它其實後面附帶了一些有利的條件。(F3)
12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feb/1/today-o3.htm 13
http://www.ylib.com/search/ShowBook.asp?BookNo=UR0Z0033-00-01-01# 取自華人性格研究(keb.koobe版
電子書)
34
台灣處遇親密關係暴力的低度強制性使得修復式正義有其需要
本國家庭暴力防治法為注重及時保護制度的民事法規,雖有保護令之設計,但是屬低強
制性,對多樣性的暴力類型宜發展多元服務模式,以符所需。
基本上台灣不走強制性,我們台灣已經融合了東方這樣一個道德觀念,我們在家事案件上是尊重當事人的
選擇,所以我們在家暴法的設計上強制性的東西是很少的。相對人的面向是多元的,有很權控的,有很暴
力的,另一種是反擊型的,現在我們做相對人處遇,本來就可以開放一個多元的選擇。我覺得用這樣的角
度思考就比較能接受這樣處遇的關係。(I1)
強調合諧
若以華人性格之價值觀論之,其終極社會價值顯示出追求和諧為重要的立場,因此於家
庭關係及人際行為間極為強調和諧的行動與價值,並在社群間之低隱匿性及權威導向之
核心特質,常使得當事人在司法機構表達修復意願,以符合社會價值,也遵從和諧的社
會期望,但是卻未必有利於其自我保護之處境。
就是台灣人很看待所謂修復這件事情,還有其一這個要件因為我會覺得有些部分就是說其實,因為華人那
個儒家文化,其實我們認為中國人應該從小禮義廉恥,知恥近乎勇,整個感受應該是深厚的,所以華人應
該是比較願意去試的,可是也因為其實對於這個詞,其實他是兩面的,他可能是一個我因為如此所以盡量
達到一個和諧的關係,那是因為華人區域,我們所謂人和人之間的隱密性太低了,因為在別人面前沒有什
麼樣所謂隱私性可言的,可能那這樣問題容易被曝光。(M)
他會不會為了和諧或者是給執行者面子,甚至給後續這案子要回到司法這些執行者比如說檢察官交代,他
可能會委屈的去做一些他自己認為不可能,或者是哪些他不是那麼願意去接受的條件,然後讓施暴者可以
透過這樣一個修復式正義,達到他再一次控制被害人的目的。(I)
但是我覺得那個責備,那個不願意在這種狀況下,可能(台語)阿人家都好心好意,阿而且這是一個社
會制度,怎樣有的沒的,阿你這個人不要,表示什麼,你就是不受教,你就是偏執,你就怎麼樣,會帶
來很多東西。(O1)
重視面子
華人社會之終極價值是以社會為中心或人際之間的價值,因此追求受他人尊重、超越他
人的成就、要對社會有貢獻、維護個人或家族的尊榮、身分、名譽、地位、權勢之面子
文化。雖禮記中「知恥近乎勇」也是主張存羞恥之心以表氣度與修為,這也是與修復式
正義實施中運用恥感而提升修正行為的勇氣相呼應,但以加害者的臨床表徵,卻常是為
35
了重視面子而致惱羞成怒。
其實在那個修復的時候對那個相對人來講其實有ㄧ個部分,就是那個對羞恥感這個部分會提供他知恥近乎
勇,所以會道歉,那好像這是一種方向,就是在理論上來講也會提到那個對於這個加害行為更加促進,可
是對於我們國家以這樣的界說來講,反而沒面子,加害人很不容易說講好就好,道歉不道歉。(M)
我在思考因為我會覺得說我後來發現其實每個人解讀這件事情是不同的,所以這就是又回到罪惡感,如果
他有罪惡感他就會剷除無利社會的行為,他只是一個惱羞成怒的概念,我認為這件事情是別人加註個人的
一個因素而已。(M)
家庭系統的影響深遠
家庭以其系統和動力影響其成員的發展,並創造及維持一共同的文化。家庭也是一個規
則管理(rule-governed)的系統,每個人均要學習什麼是被允許的,什麼是被期待的。
家庭的規則決定了其成員行為的模式,提供互動模式的準則,並成為家庭形成其各自傳
統的基礎。修復式正義實施修復會議時,是否讓家庭其他成員擔任申請人或當事人的支
持者,必須衡量其家庭系統運作與心理動力現象,避免家族過度涉入,將助力變成了阻
力。
假如好了我今天決定這件事情我要不要跟對方離婚,我可能必須有一方親屬條件,妳應該跟他離婚或者你
不應該跟他離婚,他會因為這個參與過程當中遭受其他就是那個家族系統壓力很大的問題。(M)
修復正義裡面其他參與角色的慎選,我會覺得那個所謂的評估者在這過程當中一定要很清楚這些所謂其他
參與者對雙方當事人來說關係為何,那有時候是助力,有時候是個非常大的阻力在這件事情上很清楚知道
他跟那個家庭其它系統的關係的壓力,跟他其他參與者的壓力,還有她本身對自己期待進入到家庭一個後
續的壓力。(M)
從一旦新人組織了一個家庭是那麼的純粹,就他們為主體,恐怕不是,因為其實原生家庭在新人組成家庭
之後都不會放了他們,那個糾葛其實是很複雜的,那後面都有藏鏡人在那邊繼續得操控著他們著他們的子
女。(I)
若單純從加害人跟被害人的調解做當然是一個方法,但如果真的要充分解決當事人的問題,他們的關係複
雜到連家庭都一起糾葛進來的話,那這個部份可以要考慮一起進來做處理。(I)
其實我覺得回來應該是,就剛才講到那個沒錯阿,那個關係其實是包括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包括自己跟
自己的關係嘛,所以那個,那個具支持性只是讓我們在這樣的工作啟動的過程當中,我們有多一些其他
資源。不過這變成說在台灣可能要注意一個現象就是說,具支持性的結果,或是說不具支持性的結果可
能出現一個狀況就是,台灣的家庭裡面出現一個狀況,我很關心所以我來參與一個陪伴的工作,可是這
36
個過程裡面,通常同時也帶來了我跟這個人的界限模糊。(O2)
說私底下就跟他講,(台語)阿你就怎樣,就怎樣阿,因為那種其實對於在台灣的親密關係的一個權控,
不只來自於雙方彼此,還包括家庭裡面比較 close的經常會出現。(O2)
司法對於親密關係處遇的不足可以由修復式正義處理
當刑事司法制度尚未能有效處理或解決親密關係暴力問題,而現行之刑事司法實踐下,
一位女性必須將逮捕、法律提告其伴侶作為受助的起點,而保護令亦需將禁制或遠離的
命令加諸於其伴侶身上,但是此人卻和她一同分享了過去、家庭、子女及未來。因此法
律化處遇服務內容後,多樣性的暴力面貌及其影響,也被劃一了,這將因與當事人期待
的歧異,帶來家暴防治成效上的折損。因此發展較為符合當事人處境的多元處遇模式,
亦為當務之急。
處理這個家暴議題也常常發現到,當事人雖然在這個事件過了,可是那個創傷好像都還是在彼此的身上,
然後這樣其實會影響到他們跟孩子的一些互動,那當然孩子也會受到一些的影響,那我們比較是基於說,
看到台灣在這邊浮現出來這種家暴案件的類型,越來越多元,除了傳統的這種所謂的配偶的這些暴力,然
後對於這個權控的關心的這種暴力虐待之外,那慢慢有浮現一些,比如說子女對父母的暴力啦,或者是夫
妻之間比較平等的絆口角衝突事件,那我覺得面對這樣類型的家暴案件,它處理的方式不再適用就是我們
傳統的,就是走入到司法這樣子的一個處理的方式。(H1)
修復式司法制度的核心價值,尤其是家暴案件,執行保護令之後把爸爸或公公,把加害人趕出這個家庭,
這個家庭的關係並沒有獲得解決,那結果這個刑事案件,我們可能把這個加害人去法院判刑,進去關了,
關出來之後他的行為更加惡劣,他會想要報復,因為他覺得他居然被隔離了,所以案子一而再,再而三,
越來越加的嚴重,以傳統的訴訟的制度來懲處加害人,能不能達到家庭糾紛的解決,可能並不能達到解決。
(H2)
華人社會相當重視家族社會系統,強化社會心理學「和諧」與「面子」之文化現象,由
受訪者之意見發現文化及民族性確有影響及意義。在親密關係衝突的事件中,父權體制
下對男性自尊的推崇,及文化視角下維護面子的民族性格14,甚且是 Pye教授批評華人沒
有自我分析、自我檢討的雅量15,且本國家庭暴力防治法為注重及時保護制度的民事法
規,雖有保護令之設計,但是屬低強制性,對多樣性的暴力類型宜發展多元服務模式,
因此若於修復式正義具司法性之施行中,協助加害人表達歉意並重建無暴力生活,是有
其正向意義的。
價值觀反應了文化和性格,若以華人性格之價值觀論之,其終極社會價值顯示出維護社
14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feb/1/today-o3.htm 15
http://www.ylib.com/search/ShowBook.asp?BookNo=UR0Z0033-00-01-01# 取自華人性格研究(keb.koobe
版電子書)
37
群及關係之和諧與追求受他人尊重、超越他人的成就、維護個人或家族的尊榮、身分、
名譽、地位、權勢之面子文化為重要的立場,因此於家庭關係及人際行為間極為強調和
諧的行動與維護男性尊嚴之價值,並在社群間之低隱匿性及權威導向之核心特質,常使
得當事人在司法機構表達修復意願,以符合社會價值,也遵從和諧的社會期望,但是卻
未必有利於其自我保護之處境。
家庭以其系統和動力影響其成員的發展,並創造及維持一共同的文化。家庭的規則決定
了其成員行為的模式,提供互動模式的準則,並成為家庭形成其各自傳統的基礎。修復
式正義實施修復會議時,是否讓家庭其他成員擔任申請人或當事人的支持者,必須衡量
其家庭系統運作與心理動力現象,避免家族過度涉入,將助力變成了阻力。
當刑事司法制度尚未能有效處理或解決親密關係暴力問題,而現行法律化處遇服務內容
之防治系統,使得多樣性的暴力面貌及其影響,也被劃一了,這將因與當事人期待的歧
異,帶來家暴防治成效上的折損。因此發展較為符合當事人處境的多元處遇模式,亦為
當務之急。因此受訪者針對台灣華人文化與民族性的影響提出執行面宜留意之本土議
題,也認為修復式正義能以其於多元處遇之正向意義,成為當事人的選項之一。
二、修復式正義的精神
有關修復式正義實施於家庭暴力事件之精神意涵,受訪者亦針對修復式正義之核心信
念,是協助被害人、加害人及雙方家庭、社區進行充分的對話,讓當事人之間有機會充
分的陳述與傾聽、進一步澄清事實、了解對方的感受、提出對犯罪事件的疑問並獲得解
答,提出實施上的關注要點。
著重於當事人的關係
修復式正義強調的是「關係的」、「社會的」,而非僅「法律的」層面,因此對關係中的權
力與控制議題,在修復解決歷程應被重視。
修復式正義並不是用司法的概念而是用關係性解決雙方關係存在與否的問題,雖然 I1、I3說權控不是家
暴的主要原因,但他們覺得權控是一個很重要的因子,所以權控在這個問題上會有兩個部份,關於夫妻本
身權控的議題,然後是修復式的操作模型裡面的權控,如何去面對這兩種權控…英國的和平鴿計畫可以有
效的解決權控議題,更 empower被害者。(I5)
當事人的自我察覺與關係修復
受訪者提出加害人與被害人在家庭暴力傷害中都必須覺知自己在關係中的損傷,那除了
是傷人或受傷的兩端,也須看待動力性的影響,以便能先與自己修復,包括與自己過去
的傷害修復,進而在對話平台中找到關係修復的力量。
38
我們的被害人需要跟自己的關係修復,加害人也要跟自己的關係修復,怎樣看待自己在關係中傷害,先回
到個人的部份,去跟自己修復,我覺得那個部份才能去處理人本質的東西,願不願意改變自己的行為,願
不願意覺知到自己的行為造成別人的傷害,不管是不是暴力的起因,被害人被激怒,某部份也傷害到施虐
的這個人,那施虐的人以行動來表達他暴怒的時候,其實我們看到的是傷害的不可收拾,其實我很認同的
是這樣的平台是給大家一個機會。(H3)
注重當事人的意願
受訪者表示,兩方面之意願都是需要重視的。被害人若因人身安全議題有所顧慮,則應
協助其澄清或給予必要之資源,但絕不可強迫;若加害人之意願曖昧不明,也需澄清與
確認,以防止被害人之二度受害。
當初是放在被害人的角度看這個執行,講的是單純的婚暴個案,可是我們到最後會發現說,如果是修復式
司法它對加害人也是需要的,所以我們最後才說出於兩造意願的選擇不能有強迫,進行中任何一造不願意
都可以中止。(I4)
考慮到被害人會不會是被迫來參加修復式司法,所以說我們也會在檢察官確認第一次之後再傳真到家防中
心,那請被害人的主責社工再第二次的確認,確認這個被害人真的是有意願要參與修復式司法,才會再轉
到修復促進者,由修復促進者來做第三次確認。(H2)
案主的自願性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那如果說當他在檢察官的要求下他覺得好像應該陷入,但是事
後他反悔,像我在第一次出差的時候,有很多的被害人就告訴我說他不敢,那我這個時後會引導他說我覺
得有些部分你可以表達你的想法,那如果說在我們的安全的一些安排下,有很多的東西你是可以當面跟他
講,而且這個東西是不會有安全上的困難的,或者是說你要不要找支持者進來一起幫你,但是如果在這些
我提供這些安全上的訊息,還有保證,他還是沒有辦法接受的話,那我也會告訴他說,那我也會把這樣的
結果就是直接回給檢察官,我們就不會進行修復會議,然後來確保他的安全,所以說這個自願性我覺得是
說是一個重要的工作。(H4)
只要是修復式對話的執行,都必須要有一個前提就是雙方都有意願談一談,然後主持人促進者,有一個很
重要的任務就是他必須要讓會議的當下是很安全的,很開放的很平和的。在這個情況下的話案件就可以進
行。(H8)
關注當事人的關係位置
既然是刑事司法案件,加害人與受害人之位置應是清楚,被害者也應該是聽見有助於創
傷復原及問題解決的說詞,而非加害者推責或漠然的態度。
你今天是為甚麼而來?被害人聽到是有助於她的創傷跟問題。所以他的操作程序代表的是加、被害人的位
39
置跟哲學概念。(A4)
提升被害人的積極角色
受訪者認為修復會議能使被害者的角色由消極轉為積極,藉由積極地陳述傷害,讓加害
者成為承擔改變責任的主體,並能真誠致歉。
把被害人的角色,從消極的變成積極的,積極的陳述然後希望對方道歉,不是永遠的原諒你,而是說要改
變行為。你沒有改變,我未來還是不希望跟你和下去。然後讓被害者說出你傷害我,我需要你某部份的賠
償,這些賠償我在身上能真正的受益,這對被害人也是很大的一個可以療傷的方式。(H5)
關照加害人的內在困境
受訪者提醒若是修復式正義之評估與促進(預備)會議,能關照到加害人的內在困境,讓
他有機會陳述其失衡的心理情緒與生活,對被害人的安全也是另一種關照。
過去我們只注意被害人沒有注意加害人,看那個于美人訪的那個事件就是這樣子,加害人傷害很多人,他
自己,所以我們讓他有機會說出他心裡不平衡的地方。(H5)
關注當事人意見充分表達
受訪者覺得修復式正義的核心價值是讓當事人都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感受及需求,而且在
修復會議的過程中能協助他們發現自己有解決問題的能力。當雙方能建立對話,促成了
解及責任承擔,事件即有了處理或改變的契機。
只要有機會讓雙方能釐清當時發生的情況,然後能夠很安全的說出自己的想法,在這情況下可以很開放的
說出自己的想法,有做到發聲他的價值就已經有做到有存在了。然後呢彼此不管是加害人、被害人都一樣,
他們能夠說出內心真正的想法讓對方知道,然後再來就是說願意承擔責任,因為在這樣的事件裡面,誰對
誰錯都有可能,也都有責任在,不是完全的偏向一方,那在說明的過程當中,就能夠了解到這樣的演變,
這樣的舉止,顯現出彼此都有一些責任,那願意承擔這樣責任的話,達成一個協議,我覺得這樣的話至少
事件已獲得一些處理或改變。(H8)
我會覺得修復式司法的核心價值是讓當事人都有機會表達自己的需求,而且在復合會議的過程中還可以引
發他們發現自己可以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是把這樣的能力來交待給法官或檢察官來做這樣的判決而已,
而是他們會相信說很多的部分,是我自己可以為我自己負擔負責的,然後我自己可以來達到一個自己想要
的結果,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是過去的刑事方式,就是我們都完全交給法官的方式一個很不同的部分。(H4)
受訪者認為修復式正義既強調的是「關係的」、「社會的」,而非僅「法律的」層面,因此
40
對關係中的權力與控制議題,在修復解決歷程應被重視。既然是刑事司法案件,加害人
與受害人之位置應是清楚,被害者也應該是聽見有助於創傷復原及問題解決的說詞,而
非加害者推責或漠然的態度。加害人與被害人都必須覺知自己在關係中的損傷,除了傷
人或受傷的兩端,也須看待動力性的影響,以便能先與自己修復,進而在對話平台中找
到關係修復的力量。因此兩方面之意願都是需要重視的。被害人若因人身安全議題有所
顧慮,則應協助其澄清或給予必要之資源,但絕不可強迫;若加害人之意願曖昧不明,
也需澄清與確認,以防止被害人之二度受害。
受訪者也認為修復會議能使被害者的角色由消極轉為積極,藉由積極地陳述傷害,讓加
害者成為承擔改變責任的主體,並能真誠致歉。因此在評估與促進(預備)會議,若能關
照到加害人的內在困境,讓他有機會陳述其失衡的心理情緒與生活,對被害人的安全也
是另一種關照。修復式正義的核心價值既是讓當事人都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感受及需求,
而且在修復會議的過程中能協助他們發現自己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當雙方能建立對
話,促成了解及責任承擔,事件即有了修復或改變的契機。
三、修復式正義是加害人處遇的一環
受訪者對於修復式正義的目的有了探討,其中亦主張修復式正義是加害人處遇的一種選
項或方法。
修復工作可促發加害人因了解被害人的傷害而改變其暴力行為
實施修復會議能讓加害者傾聽及覺知到自己行為造成被害者之身心影響,特別是初期暴
力之暴力週期循環中,加害者之道歉及被害者之原諒,皆源自於害怕失去的心理機轉所
啟動之否認系統作用,無益於暴力行為之改變,若能實施修復工作或可促發加害人因了
解被害人的傷害而改變其暴力行為。
把修復視為相對處遇的一環,初期暴力或低度暴力很容易被被害人原諒,這種無效的原諒之下,縱容暴力
的結果,今天我讓那個相對人今天因為你參與修復式正義,而去理解到自己的行為已經傷害到被害人,這
個被害人被傷害的事實你能能夠產生同理,引發罪惡感才能改變行為。(A4)
修復工作以加害人為對象可積極終止暴力
修復會議實施之目的若能納入加害人的處遇意涵,則對終止暴力之正義本質亦相符合。
如果把它當成是相對人處遇的一個選擇,那是我們社會為了終止暴力而做的努力,可是如果我是為了
empower被害人,它不是終止暴力而是有一個正義的位置在那裡,社工有時會問那婦女要回家了,那我們
能做甚麼?那另一個是檢察官也很痛苦保護不了被害人,那我們還能做甚麼?有時候我覺得第一線會有這個
狀況,那有時候我覺得是暴力的本質所帶來的難度,也許上帝才能解決。(I5)
41
被害人參與的加害人處遇
受訪者認為協助家暴事件的過程當中,應有多元的價值,不僅是修復情感和關係,也是
提供被害者重新作選擇的機會,是被害者參與至加害者處遇歷程的機會。
被害人其實在參與過程當中,評估者要讓她知道,其實你是從相對人進來,他的談話、他的行為、都是妳
在評估這個人是不是妳未來要在一起的一個歷程,我是說不要把它當成治療,其實沒有那麼小的價值,更
大的價值是今天這個人願不願意進來就是一個打分數的開始,他今天承認多少到他今天有沒有去履行,原
來所答應的承諾跟承諾的實踐,這整個過程當中都是你在學習看到,其實是不是一個值得妳原諒的對象這
樣子而已啦,所以我覺得這是給被害人背後更重要的意涵。因為打分數告訴妳,最後妳心裡有數,這個修
復式正義它是失敗的,因為我操作的目的一個是關係恢復一個是和平分手,那和平分手比較沒有問題啦,
可是關係恢復的過程當中,對方值不值得原諒是自己在打分數,我覺得在協助的過程當中要有多元的價
值,重點放在相對人的處遇比被害人的療癒可能更為重要。(A4)
受訪者認為實施修復會議能讓加害者傾聽及覺知到自己行為造成被害者之身心影響,可
促發加害人因了解被害人的傷害而改變其暴力行為。因此修復會議實施之目的若能納入
加害人的處遇意涵,則對終止暴力之正義本質亦相符合。並認為協助家暴事件的過程當
中,應有多元的價值,不僅是修復情感和關係,也是提供被害者重新作選擇的機會,是
被害者參與至加害者處遇歷程的機會。
四、修復式正義是被害人保護的一環
受訪者表示修復式正義是被害人保護的一種處遇服務方式,可協助被害人處理現行司法
系統之不足,並對被害人賦權以作出對未來的選擇。
修復工作可以協助被害人處理現行司法系統無法處理的親密關係衝突
以現行司法制度無法解決婚姻中親密關係之糾葛,因此修復會議之實施是為了被害者的
情感與需求,特別對離不開家庭的受害者,給與另一種支持性的選擇。
在法務部的界定裡面,它不會是一個加害人的處遇,為甚麼地檢署都想要做家暴案件,因為它有它的多樣
性,顯然陷在的法律系統無法解決婚姻中的糾葛,我們看到很多被害人他是離不開家庭的,我們也看到很
多強制逮捕,保護令其實也保護不了被害人,然後那種心中的怨阿!恨阿!雙方不甘心引發的更多的糾紛,
檢察官要做這種事情,是因為目前的機制無法滿足被害人的需求。讓離不開家的被害人或相對人不知道要
如何處理自己的情緒。(I4)
修復工作在自願的情況下讓被害人更有力量
42
修復會議實施之前提應在雙方的意願下進行,也在加害者的責任承擔下,被害者將獲力
量前行。
司法體系裡面希望給被害人另外一種選擇,我們可不可以讓被害人在過程當中更有一些力量,就是我們後
來講的修復視司法。那其實你要談修復式司法的前提就是雙方都要有意願,任何一方都不能強迫,任何一
方都可以中止說我不要再談下去,那要談下去的前提當然是加害人這一方他對於他做的事情,法務部寫認
罪,我說是承擔,因為認罪有法律上的意義在,基本上是願意承認有這樣的事實發生,然後願意走下去才
有一個談修復式正義的一個可能性。(I4)
修復工作提供被害人有不同選擇
修復式司法提供被害人保護之積極作為,也是讓被害者能有自主的選擇機會。
法務部的保護司裡面是五科承辦,是保護被害人業務,所以當初的角度是從被害人的角度做出發點,而不
是從加害人的角度做出發點,在修復式正義的過程當中讓被害人有選擇的機會,從頭到尾沒有原諒,不認
為被害人一定要原諒加害人。(I4)
修復工作關注的重點是被害人賦權
修復式正義關注的是被害者的賦權,所有的修復程序應當照顧到被害者的權力維護及安
全提升。
目前台灣的操作系統不是加害人處遇,我們 care的是被害者的賦權,那台灣也可以思考,台灣繼續走下
去,那有沒有可能它是兼顧二者的,或是加害處遇這部份是強化的,或有民間團體能提供這樣的服務,它
不必進到司法體系裡面,是選項之一。(I4)
以現行司法制度並無法解決婚姻中親密關係之糾葛,因此修復會議之實施是為了被害者
的情感與需求,是提供被害人保護之積極作為,也是讓被害者能有另一種支持性的、自
主的選擇機會。其實施之前提應在雙方的意願下進行,也需強化加害者的責任承擔,關
注被害者的賦權,所有的修復程序應當照顧到被害者的權力維護及安全提升。
五、尊重當事人的期待與意願
修復式正義應關注及尊重當事人的期待與意願,特別是被害人對於關係改善方向的主觀
意願應積極了解及接納。
43
了解被害人對於關係改善方向的主觀意願
修復會議之實施應了解被害人的意願及其對關係的感受和看法,會議之目的不應建立在
復合的期待上,也不盡然須有道歉—原諒的形式,被害者之主觀意願應充分被了解。
可是這在進行修復式正義之前,即便是你關係的評估建立出來之後,還是希望是說,先有我們修復式正義
之前有一個叫會前會,那個會前會其實還是會去 touch到當事人的主觀意願的問題,包括比如說這個受暴
者,她到底願不願意再繼續跟他相處,在同一個屋簷下,還是說她覺得持保護令對她是比較有保障的。(C2)
因為講到這個我要先澄清一下,RJ不是一定要叫他們復合,第一個不是只有要復合的才能進來,第二個
就是說我進來的目的不是要復合,這個可能要先澄清一下。(C1)
我要講的意思是說,專業評估說,暫時不適宜進 RJ,即便他已經 treatment完成, 可視當事人雙方他們
還有一份情在,然後他們可能是說我只想跟我先生表達一件說,你只要能確保我安全,然後
你也保證以後不要再打我,我可能可以考慮跟你坐下來做一個對談。(C2)
其實所有的會議的目的都不一定就是說,一定要修復,或是大家以為一定要道歉,一定要接受,其實這只
是一個形式。(C1)
那個狀況裡面我發覺兒子是恨他的,恨到爸爸最好在眼前消失,不在這個世界上,他就 free了,他就有
自己的前途了,那這樣的 case在實務上是沒辦法做的,連因為問了母子,他們兩個人說不要再看到他,
不要面對面,永遠不要,然後我知道,那沒有辦法進行下去 。(E)
接納被害人對於關係改善方向的主觀意願
修復會議的進行不能使用強制力,也不能限約短期達成之要求,須接納被害人的意願、
期望及速度。
比如說我們一百年一月開始做了一個夫妻對談,以前我們怎麼兜都兜不攏兩造,因為對於被害人我們沒有
任何強制力,即便找到她們也不同意,那我們就慢慢磨,磨到最後居然有四對夫妻願意,然後我們就從這
四對夫妻開始做,現在已經快一年了,成效非常好,所以,其實他們也會影響到其他的家庭。(D5)
修復會議之實施應了解及接納被害人的意願及其對關係的感受和看法,會議之目的不應
建立在復合的期待上,也不盡然須有道歉—原諒的形式。修復會議的進行不能使用強制
力,也不能限約短期達成之要求,須接納被害人的意願、期望及速度。
六、不同修復式正義的工作型式
44
有關本國修復式正義之實施模式,受訪者提出原則性之建議,其中包括權力關係之平衡、
在地文化之考量及修復過程社區及家庭介入之評估等議題。
考量修復過程中的權力關係平衡而使用不同的修復形式
受訪者表示無論是以哪種修復方案之執行,重點在於如何讓雙方達到權力的平衡,如何
使用其他參與者(如支持者或陪伴者)之加入,以及依案件類型之多元運用等。
VOM、FGC、PC是屬於多元應用,只不過他是運用在哪些角色上。我覺得他們都有基本的概念,只是在場
的人必須要適時作一個運用,比如說 VOM,有時為了達到權力的平衡,我會期待有更多的參與者進來,參
與者所扮演的角色,跟促進者在整個的過程當中就需要用 Circle的概念操做,那 FGC是在處理家庭一個
很重要的議題,那社區是大家共同面對要解決的問題,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這些都是從 VOM的角色出來。(A4)
適合本土的介入模式
受訪者表示對本國文化及資源處境而言,和平圈較構成情感療癒性之修復,家庭協商會
議讓家人參與修復歷程,對重視家庭認同的文化特性而言,是值得信賴的工作模式。但
這都需花時間去嘗試與發展。
我是比較贊成和平圈跟家庭協商會議,我的出發點是我們華人對於家庭跟家族的認同還是比較大,那社區
修復,我覺得現階段不適合是因為我們根深蒂固還有那種家醜不可外揚,可能在初期階段,事情剛爆發的
時候,根本不願意社區介入或知道,所以會有一些阻力,那我覺得和平圈又優於家庭協商會議是我覺得在
操作上,在情感上是比較完整。(D5)
大概有一些了解和平圈的部份大概在做甚麼,就是相關的人,針對這樣的事件,然後來討論,我會比較覺
得它的目的比較不像協商,協商好像是有甚麼目的,達成我的目的,有一個目的性的達成,那調解也是,
和平圈比較是在情感的,有一個和平的狀態,覺得這一個概念我會比較接受。不是有個目的而是達到關係
的合諧。那我覺得台灣要做到社區很難,要把那麼多人找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覺得不太可能也不知
道它怎麼做這樣子。(D3)
就我們現在的模式,我們去嘗試跟發展,我覺得這是我比較能夠去信賴的,也是我們有辦法去照顧得到,
所以我們去年實踐的標準,其實我們有幾個改變點可以做,所謂可以做就是說,第一個,時間的問題,好
那我必須講說人力對訴訟的期待有時候是會有衝突,因為那可能是希望精確而精緻,但是卻又希望快速有
效率,那有時在調查上這兩種往往會有點衝突,要同時兼顧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們只能針對案件
45
的類型去看,如果他的需要是希望得到一個快速的處理,可能是他需要花點時間去經營。(D6)
社區修復委員會
受訪者提出現行鄉鎮區公所調解委員會是一個很值得開發的資源,此調解委員會相當是
社區的、可近性的,我們可以在既有的基礎上再讓它發芽成長。
那至於說第四個社區修復委員會吼,那這個讓我想到其實台灣三百多個鄉鎮區公所都有調解委員會,那調
解委員會大部分都是處理民事車禍賠償,但是依照我們法律的規定吼,這個公所的調解委員會也可以處理
刑事案件,只是限於告訴乃論的刑事案件,那這個告訴乃論的刑事案件這個包括像是通姦罪啦!或者是說
傷害罪,然後毀謗罪,妨害名譽等這一些,毀損罪都是吼,那這部份後來也可以值得觀察就是說,公所在
告訴乃論刑案的部份吼,它發揮怎樣的機能。(L)
台灣三百多個公所吼,那它都設有調解委員會,那其實這是一個很值得開發的資源,因為就是說,公所它
是最社區性的,然後在交通上,公所的可近性也很高,所以這一塊我們怎樣去開發,很值得在既有的基礎
上再讓它發芽成長吼。(L)
所以在我們整個思維還沒有完全很清楚,認知到就是一般家暴本質的時候,這個我覺得倒是可以考慮就社
區的部份來做推動這個委員會的這個部分;那家庭協商會議是可以跟這個 VOM一起做具體個案的結合。(I)
家庭協商會議
受訪者表示家庭協商會議可兼具 VOM之加害人及被害人調解,並加入家庭成員來共同
關切與支持加害者的改變,為可考慮之模式,唯因家庭成員之篩選及時間之配合較為
複雜,是有待克服的問題。
我會覺得是在那個家庭協商的會議比較有可能性,那因為和平圈的一個在處理協助的一個範圍是比較大
的,其實在那個,呃,在前面的工作會比較多,那加害人跟被害人的一個調解,這也是可以行的,就是
等於一跟二的這個方式比較可行,那社區修復委員會,我覺得這個,是比較接近於我們的一個調解系統,
所以是以一二為主。(O2)
理想上應該是 VOM跟那個家庭協商會議這個為主啦吼。但是在實務上啦,因為家庭協商會議其實牽涉到
一個問題,那些人你到底要多少人來?阿你要湊那個時間對不對,那就變成說,我會覺得說如果以執行
度容易與否來講的話,反而是社區吼,假設是社區裡面有一些,譬如說具有,對他們具有影響力的人,
譬如說在部落裡面啦。或者是那種傳統性社區裡面,有一些地方的真的是,真的是耆老之類的。(O1)
受訪者表示無論是以哪種修復方案之執行,重點在於如何讓雙方達到權力的平衡,如何
46
使用其他參與者(如支持者或陪伴者)之加入,以及依案件類型之多元運用等。有人主張
對本國文化及資源處境而言,和平圈較構成情感療癒性之修復,家庭協商會議讓家人參
與修復歷程,對重視家庭認同的文化特性而言,是值得信賴的工作模式。亦有人提出現
行鄉鎮區公所調解委員會是一個很值得開發的資源,他是社區的、可近性的,也有受訪
者認為家庭協商會議可兼具 VOM之加害人及被害人調解,並加入家庭成員來共同關切與
支持加害者的改變,為可考慮之模式,但這都需花時間去嘗試與發展,才能開發出適合
本土實踐及具文化脈絡之修復程序。
七、修復工作作為親密關係衝突工作的平台
受訪者認為修復式正義提供一個對話的平台,在修復會議中權力關係是對等的,帶給當
事人有一些不同解決問題的方法,讓他們在一個安全的環境裡面可以來進行對話,而修
復就是一個對話的歷程,以作為親密關係衝突工作的平台。
他們如果想要針對這個問題去討論,我們讓他們有這個平台去討論,那我們有幾個是成功的例子,那成功
的例子是說其實他們的權力關係是對等的,就是他也願意針對他過去這些部分去做一些處理,另一個是在
婚姻的過程他可能是比較確定的,就是他可能說就是要分開了,只是說針對孩子的部分,因為我們發現說
這個的確影響了孩子,那這個部份我們比較是以孩子為前提在跟他做一些討論,那讓我發現說有一種他們
其實是有孩子的,那也願意針對這個部分有一些處理,那當然這個處理是因為說他們希望帶給孩子有一些
不同解決問題的方法,因為他們過去是這樣的方式,因為我們有跟他們討論說孩子可能或多都有看到或是
目睹,那這個對孩子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傷害,所以對於這個部分他們是怎麼看待,他們願不願意用別的方
式來處理他這個部分,所以我們有幾個案子是成功的,就是他們願意在這個過程裡面互相。(A2)
現在家庭暴力案件甚麼都要處裡.其實這跟我們傳統狹隘的是不一樣的, 可是這些人為甚麼要變成今天走
到這個地步,這怎麼出人命的地步,第一我們沒有前端這個機制,我們也沒有提供一個對話的平台讓他們
在一個安全的環境裡面可以來進行對話,或者他覺得關係很薄弱,權力關係很低,所以它沒有一個葉大師
來做靠山,他也不敢,類似這樣的他應該都要放在這個體系裡面,那是要往前推就是,家防會可能需要再
去釐清,這可能是內政部將來推,或必須我們現在有很多社區。(C4)
所以我覺得修復式正義,他不見得要有一個很清楚的目標,其實修復就是一個歷程,他曾經走到, 反正
我只有五次嘛,五次資源就是走完這個歷程,可是這歷程我想可以減緩他的傷害,或者他將來接司法會接
甚麼,他有另外一個歷程,所以我覺得這歷程不必然一定要設計一個偉大目標就是降低兩造雙方彼此的傷
害即可就好了,而且我們要定位說,它沒有一定要甚麼結果,它就是一個歷程.提供一個修復的歷程這樣。
(C4)
那個對話的機制啦,我想家防會在努力說,因你要他馬上就喜歡也是很困難的,那時候是因為進到法院,
因為早期我們也會有這種障礙,那進到法院看到很多相對人我們就開始看,這個家暴事件又會有不一樣的
47
視角,所以我覺得說,你起碼是一個平台,像家防會在推嗎,之前不是委託顏老師在推加害人關懷計畫嘛,
找被害人出來,然後就澄清彼此的一些疑慮之後,或者起碼你了解我,我瞭解妳,那個部份之後,要讓加,
被害人相互了解之前,應該要讓團體相互了解,那個其實是很重要,但是你了解那個經驗之後,後面才能,
因為我們專研的那個。(C4)
修復式正義裡面其實是提供一個被害人一個的平台跟機制,除了在形式上面的處理之外,她有這個機制讓
她有機會、有能力去面對這一個加害人,然後她可以說的清楚,不一定是爲了道歉,就是如果你只是問他
說你要不要道歉,才進入那個,其實不是,因為真正他也有可能她的過程裡面她比較知道說你怎麼能這樣
對我,你這樣對我造成我很大的傷害,我有能力去告訴對方,這是在被害人,但是對加害人而言他不是為
了道歉而進來的,因為這也會有一個剛剛講的家族的壓力,因為也有可能人家道歉你為什麼不接受他的道
歉。(M2)
她其實不論是在加害人或是什麼階段,它都可以進來,那問題是我現在我到底是我們個別做還是配合司法
做,如果配合司法就有這些程序,可是如果說這只是一個我們社會工作裡面,其實它是可以去增加資原、
平台(M)
小結
華人社會相當重視家族社會系統,強化社會心理學「和諧」與「面子」之文化現象,
在親密關係衝突的事件中,父權體制下對男性自尊的推崇,及文化視角下維護面子的民
族性格,以及缺乏自我分析、自我檢討的雅量,若於修復式正義具司法性之施行中,協
助加害人表達歉意並重建無暴力生活,是有其正向意義的。
家庭以其系統和動力影響其成員的發展,並創造及維持一共同的文化。修復式正義
實施修復會議時,是否讓家庭其他成員擔任申請人或當事人的支持者,必須衡量其家庭
系統運作與心理動力現象,避免家族過度涉入,將助力變成了阻力。
當刑事司法制度尚未能有效處理或解決親密關係暴力問題,而現行法律化處遇服務內容
之防治系統,使得多樣性的暴力面貌及其影響,也被劃一了,這將因與當事人期待的歧
異,帶來家暴防治成效上的折損。因此發展較為符合當事人處境的多元處遇模式,亦為
當務之急。因此受訪者針對台灣華人文化與民族性的影響提出執行面宜留意之本土議
題,也認為修復式正義能以其於多元處遇之正向意義,成為當事人的選項之一。
受訪者認為修復式正義既強調的是「關係的」、「社會的」,而非僅「法律的」層面,
因此對關係中的權力與控制議題,在修復解決歷程應被重視。既然是刑事司法案件,加
害人與受害人之位置應是清楚,被害者也應該是聽見有助於創傷復原及問題解決的說
詞,而非加害者推責或漠然的態度。加害人與被害人都必須覺知自己在關係中的損傷,
除了傷人或受傷的兩端,也須看待動力性的影響,以便能先與自己修復,進而在對話平
台中找到關係修復的力量。因此兩方面之意願都是需要重視的。被害人若因人身安全議
題有所顧慮,則應協助其澄清或給予必要之資源,但絕不可強迫;若加害人之意願曖昧
不明,也需澄清與確認,以防止被害人之二度受害。
48
受訪者也認為修復會議能使被害者的角色由消極轉為積極,藉由積極地陳述傷害,
讓加害者成為承擔改變責任的主體,並能真誠致歉。因此在評估與促進(預備)會議,若
能關照到加害人的內在困境,讓他有機會陳述其失衡的心理情緒與生活,對被害人的安
全也是另一種關照。修復式正義的核心價值既是讓當事人都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感受及需
求,而且在修復會議的過程中能協助他們發現自己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當雙方能建
立對話,促成了解及責任承擔,事件即有了修復或改變的契機。 受訪者認為實施修復會議能讓加害者傾聽及覺知到自己行為造成被害者之身心影
響,可促發加害人因了解被害人的傷害而改變其暴力行為。因此修復會議實施之目的若
能納入加害人的處遇意涵,則對終止暴力之正義本質亦相符合。並認為協助家暴事件的
過程當中,應有多元的價值,不僅是修復情感和關係,也是提供被害者重新作選擇的機
會,是被害者參與至加害者處遇歷程的機會。
以現行司法制度並無法解決婚姻中親密關係之糾葛,因此修復會議之實施是為了被害者
的情感與需求,是提供被害人保護之積極作為,也是讓被害者能有另一種支持性的、自
主的選擇機會。其實施之前提應在雙方的意願下進行,也需強化加害者的責任承擔,關
注被害者的賦權,所有的修復程序應當照顧到被害者的權力維護及安全提升。
修復會議之實施應了解及接納被害人的意願及其對關係的感受和看法,會議之目的
不應建立在復合的期待上,也不盡然須有道歉—原諒的形式。修復會議的進行不能使用
強制力,也不能限約短期達成之要求,須接納被害人的意願、期望及速度。修復式正義
是提供一個對話的平台,在修復會議中權力關係應是對等的,且帶給當事人有一些不同
解決問題的方法,讓他們在一個安全的環境裡面可以來進行對話,而修復就是一個對話
的歷程,以作為親密關係衝突工作的平台。
受訪者也表示無論是以哪種修復方案之執行,重點在於如何讓雙方達到權力的平
衡,如何使用其他參與者(如支持者或陪伴者)之加入,以及依案件類型之多元運用等。
有人主張對本國文化及資源處境而言,和平圈較構成情感療癒性之修復,家庭協商會議
讓家人參與修復歷程,對重視家庭認同的文化特性而言,是值得信賴的工作模式。亦有
人提出現行鄉鎮區公所調解委員會是一個很值得開發的資源,他是社區的、可近性的,
也有受訪者認為家庭協商會議可兼具 VOM之加害人及被害人調解,並加入家庭成員來共
同關切與支持加害者的改變,為可考慮之模式。這些討論尚未能聚焦或形成共識,需花
時間更多的嘗試與發展,才能開發出適合本土實踐及具文化脈絡之修復程序。
第二節 對修復式正義的迷思
受訪者提出「修復與調解之間的糾葛」、「尋求被害人的原諒」、「修復被認為是一種
復合」、「修復式正義與家事調解的定位與差異性」等常見的迷思。
49
修復與調解之間的糾葛
修復促進與調解的角色應是分立,若將修復會議流於充滿主觀式、道德式的勸說,將會
誤解調解成立就是一個成效。因此修復式正義不應只是一個理念的宣導,若能變成一個
制度,一個法令的時候,就須詳加設計程序與規範,避免因使用以調解的模式實踐修復
工作,卻失去了正義。
香港是講雙調解的,所以他那個促進者跟調解員的角色是分明的,角色各有不同。可是你知道嗎,來到我
們台灣就會混淆,如果我要調解要很中立,那我要講什麼話都不行,整個氣氛、氛圍、被害人能夠講跟不
能講,沒有那麼多的限制,但因為我們沒有去做。(A1)
修復式正義不是只是一個理念的宣導,而是變成一個制度,而且是一個白紙黑字的制度,甚至是一個法令
的時候,他會讓在這裡面的司法人員、參與司法的人員都有所依憑,這是我覺得法律最關鍵的,否則我們
在談的時候,很容易被操做成就去談調解,再想一想、在談一談,他就很容易會流於這種很多是主觀式、
道德式的勸說,而沒有一個是社會科學,我覺得他必須有一些社會科學的討論去處理這件事情,那麼他就
不回到這麼原制、這麼可能被利用的說詞,而且這麼光明正大的說詞,我基本上對於修復式司法這一部分,
必須講就是說他是一個很好的平台,但我也必須很感慨說他事實上就是一個妥協,也就是當我在倡導家庭
暴力是一種犯罪行為的時候,我可能在修復式正義裡模糊這樣的想法,這個事實的造就是我們認為司法是
無法實踐正義的。(A7)
我對修復式正義很強的觀點就是不要調解平台,就不會誤導整個修復式正義的方向。我聽到調解兩個字,
就是不要擺在調解這樣的平台上。否則他就會誤解調解成立就是一個成效。(A5)
尋求被害人的原諒
一般人常誤以為修復式正義之施行最後一定要被害人表現寬恕的行為,若被害人無法原
諒則常因此被攻擊或惡意解釋,其實加害者的道歉是對其行為的承認與承擔,被害者並
沒有責任要去原諒他。Howard Zehr (2002)指出寬恕或和解不是修復式正義的首要原則
或重點,修復式正義提供了一個背景,成為參與者的一種自主性的選擇,因此不應該有
選擇原諒或尋求和解的壓力。
我的焦慮感是說要被害者去原諒,會覺得說我沒這麼做好像是我的錯,這個很容易運做到變成這樣一個氛
圍。不論是法官的說法,說你可以不要,你在這樣子講的時候,每個當事人還是被這樣子暗示的,被害者
還是被暗示,你要這麼做,對你才是好的。你沒這麼做是你想得不夠透徹,你不會放下,你就會被暗示很
多這樣的價值,那我必須說我在處理這樣家暴、性侵這樣原諒的歷程時,是真的要很小心。小心是說沒有
任何人可以去跟他們講原諒這一句話,可是我也必須承認就是說對被害者而言,他的原諒是對他最大的修
復,我也必須承認這件事。但是實際上我不知道由誰做這件事情。我會覺得司法或是有權威的人或局外人
其實都不太適合,那這是我對這件事情最大的疑慮。(A7)
50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被澄清,大家都以為修復式正義裡面一定要被害人寬恕,他沒有這回事,我覺得沒有,
但是你知道法務部一開始大家都用那個在講被害人原諒,好像那個原諒的價值就在那邊,那個印象就很深
刻。其實透過這個機會讓被害人可以傾訴的機會,他其實有機會被 empower我的創傷在哪裡、我的問題在
哪裡,這件事情要加害人已經到了,因為在司法判決的過程中,加害人他是 defense的,他是充滿仇恨,
他也會對加害人有更多的傷害,其實在過程中被害人整個創傷透過說的過程有所修復,重點在被害人修復
這一塊,而不是在於原諒。可是我在看很多我們現在目前大家很多在對談的時候,就會把他跟原諒畫上等
號(A4)
修復裡面走的是原諒,其實我覺得這是種迷思,就是你剛才提到說你聽聞的部分,就是因為很強調婦女的
原諒,其實修復司法不會這樣子做,真正的回到修復司法的核心的時候,他比較強調的是犯罪責任的負責,
就是他自己對自己行為的負責;他必須先承認他自己的犯行,然後他要提出他的負責;可是他提這些東西
的時候,其實是讓被害人聽聞之間他可以在情感上得到一些修復;但是被害者並沒有責任要去原諒他。(F1)
修復其實對被害人來講,他要承認我就原諒他;其實我們做婚暴那麼多年,其實常問我們的婦女說,欸妳
現在在等什麼,妳期待什麼?她就會希望說,我等先生打電話來跟我說他錯了,我就會回家就會原諒他再
給他一次機會。(F1)
修復被認為是一種復合
修復工作的目的不是復合(reconciliation),在實務工作上雙方也未必有意願復合,在
修復的價值理念強調的是參與、醫治、尊重、修補、賦權、負責、復歸、對遇、及道歉16,
其中操作性的價值是促進積極負責、修補傷害、以及衝突解決等,其關係修復指的是和
平相處或合作解決問題,那可能是繼續共處也可能是好好分手,這是需釐清的。
任何一個只要是人際互動的話,是有他的必要,修復式司法不要以為他只有在復合,他有很重要的是和平
的分手,所以這一點我覺得常常會被誤解就是大家以為是要求他們復合,其實並沒有。就是婦女被要求分
手,但是我要安全的分手,可是我的創傷要讓對方知道,我重點是在這一塊。就是他能理解我的創傷,放
我一條生路。我覺得這是必要的。(A4)
修復式正義與家事調解的定位與差異性
修復式正義不僅是個調解,他是一個工作方法,是一種修復式的精神理念,是一套發展
對被害人、對加害人、對社區、對群體之修復式的改變,因此評估者和促進者個人價值
須能符合此工作的信念。在我國修復促進者跟社區或家事調解員的角色應是分明的,其
調解目的和操作程序也不一樣,不該混淆。
16
John Braithwaite,”Shame and Criminal Justice”,Canad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2000:42(3),293.
51
所以到底訓練的時數裡面包含他要不要到修復正義的內涵,我覺得我們現在很多人都把它認為是個調解,
其實修復式正義、修復式司法的促進,他根本不僅僅只是個調解、他只是一個工作方法,透過這樣子的因
為我們有 VOM嘛,對不對,大家認為都是調解很容易把過去以往調解連結再一起,可是我覺得最根本那種
修復式的精神,對被害人、對加害人、對社區、對這個群體修復式的改變,甚至影響到評估者和促進者個
人價值的部分,他其實都有很大的影響,可是我們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所以只是覺得我只要幫忙兩個談
到和解就好,其實不只是這樣子而已(。M)
可是我會認為家事調解的目的跟修復正義的目的不太一樣,還有我很強調的是修復正義裡面那個所謂的那
個條件裡面最好能有夠行動的方案,因為我覺得很多都只會道歉,勇於認錯絕不改過,所以那個家暴循環
裡每一個都有蜜月期都有認錯,認錯不是最好的辦法,我覺得讓他進入某個場域或讓他執行某個方案,看
他行為的付出,行動力的付出,我覺得甚至我再後續評估裡面要有的。(M)
小結
受訪者認為修復促進與調解的角色應是分立,修復式正義不僅是個調解,他是一個
工作方法,是一種修復式的精神理念,是一套發展對被害人、對加害人、對社區、對群
體之修復式的改變,因此評估者和促進者個人價值須能符合此工作的信念。在我國修復
促進者跟社區或家事調解員的角色應是分明的,其調解目的和操作程序也不一樣,不該
混淆。若將修復會議流於充滿主觀式、道德式的勸說,將會誤解調解成立就是一個成效。
因此修復式正義不應只是一個理念的宣導,若能變成一個制度,一個法令的時候,就須
詳加設計程序與規範,避免因使用以調解的模式實踐修復工作,卻失去了正義。
一般人常誤以為修復式正義之施行最後一定要被害人表現寬恕的行為,若被害人無
法原諒則常因此被攻擊或惡意解釋,其實加害者的道歉是對其行為的承認與承擔,被害
者並沒有責任要去原諒他。Howard Zehr (2002)指出寬恕或和解不是修復式正義的首要
原則或重點,修復式正義提供了一個背景,成為參與者的一種自主性的選擇,因此不應
該有選擇原諒或尋求和解的壓力。
修復工作的目的不是復合(reconciliation),在實務工作上雙方也未必有意願復
合,在修復的價值理念強調的是參與、醫治、尊重、修補、賦權、負責、復歸、對遇、
及道歉,其中操作性的價值是促進積極負責、修補傷害、以及衝突解決等,其關係修復
指的是和平相處或合作解決問題,那可能是繼續共處也可能是好好分手,這是需釐清的。
第三節 修復式正義與權控
受訪者對於修復式正義工作與權控關係有高度的關切,認為被害者的人身安全是任何工
作模式的絕對底線,因此對於處理關係之間的權控議題應非常小心,包括處理權力與動
力的特定機制,以及透過雙方心理與家庭歷史,了解與處遇權控的態度與行為的成因。
52
親密關係的權控本質不易經由修復處理
女性主義覺得親密關係暴力幾乎是權控的議題,如何在被害者受到權控的狀態下做修復
會議,受訪者指出其困難,而如何在修復程序中處理權力平等的議題,也受到關注,因
此親密關係暴力若緣自於權力與控制的失衡,則不易經由修復式正義獲致有效處理。
女性主義覺得婚姻暴力幾乎是權控的議題,怎麼在權控議題做修復式正義,其實是很困難的,今天她原諒
這個,其實回到家裡,其實很多還是會有變動,因為他是隨時都可以復原的。那所以我們就是非常的擔心,
會不會在實施上造成被害人有更嚴重權控的感覺?(A1)
另外一個重要的是權力平等的議題,我知道大家也不會很擔心,在家暴的關係裡面,他的雙方的權力其實
是比較不對等的,而且是有權控關係議題很重的,所以單復合會議的產生不是只有加害人跟被害人坐下來
談而已,他們也可以邀請他們自己平常陪伴的人、支持者一起進入這個復合會議裡面,所以我們在這個中
間會希望能夠重視到權控的關係,還有安排到一個比較平等的場域,那當然有的時候在加害人跟被害人共
同出席復合會議的時候,到底誰的權力大,誰的權力小,其實並不一定,就像我們的家暴事件,被害、加
害這麼完整,因為其實當有一個人是被告的時候,他有很多的狀況其實是會覺得擔心自己是會變得比較弱
勢的,他在那個當下他不見得他的權力就是完全的一定比被害人來得更強,所以有的時候這個部分的話我
們會要做更多的評估。(H4)
社會文化的權控處境對女性的不利影響
社會文化加諸於女性的期望,使得受害者的賦權(empower)工作相當不容易,在權控的壓
迫及失權的處境中,受害者在修復程序中是否能恢復較佳的權力位置,是需要受到重視
的。
其實我們有對裡面的權力結構其實是有很多的擔心的,很大的根源我們認為暴力還是屬於「權控」的問題。
這樣子婦女的族群的特質,事實上她回到平等的關係上面,她其實是需要有一大段路要走的。那我確實會
有一些擔心說,我們算一直希望用 empower的部分希望她在權力位置上面,是可以回到比較自己能力比較
好的她才有辦法對話,婦女都希望是回家,因為其實希望一開始就希望離婚的人是很少的,即使即便來住
庇護所你馬上就覺得我要獨立生活的比例,是低到不能再低的。(F1)
執行修復的專業系統及人員本身的權控本質
修復式正義的施行若造成受害者被強求參加,或在拒絕進入時被歸責的理由,整個機制
就充滿權控的工具性,執行修復的專業系統及修復評估及促進人員須有性別與權力的敏
感度,以免成為權控的工具。
53
制度本身立意良好,但是執行人員的能力和他整個操作的部分,有時候反倒是帶給當事人非常大的壓力,
好像我今天不修復式我的錯、是當事人的錯,這個讓我覺得說我們本來立意是要幫助他,結果讓當事人覺
得,尤其是被害人,我不但受到我先生暴力的權控,我還受到司法單位的權控,我還受到執行人員的權控,
就是讓我很訝異也覺得要很慎重的地方,我覺得本來都是好意,但是後來傷害人而不自知。(A3)
權力的關注應包括修復過程中的氛圍
權力展現在任何環境及互動的氛圍,不單是外在結構更可以是內在動力,修復促進之執
行要能關注權力議題於任何安排之中。
權力議題不是那麼直接看到權力的行使,而是氛圍的營造包括支持者的角色,那被害人如何有力量說不
要。(I3)
修復歷程中的互動可能會不利處於權控關係下的弱勢
修復歷程中若不能積極敏於權控關係議題,將會是引發受害者於權力弱勢中更為自責的
處境。一般而言,受害者於受暴處境中連結其情感與關係之解釋及調適,常不利於建立
安全及自尊的生活,若修復歷程中對被害者的不適切要求或互動,可能會不利於其處於
權控關係下的弱勢角色。
親密關係暴力這件事情,在本質上是很多被害者就已經認為她應該去妥協了,就是被害者本身就會去圓滿
這些關係,就是說權力共構關係下的一個弱勢者,他本身就會去找尋一個可不可以不要再這樣下去了,也
許我做得不夠好。那個自責的東西他做得夠多了,其實一開始他就開始這麼做了。那當然修復式正義就更
容易導引他到這個想法。(A7)
親密關係暴力的本質不只是權控
親密關係暴力防治的最終目的,是終止暴力,重建被害者無暴力的安全生活。因此無論
是哪個學理派別,都需以此為工作目標。若親密關係暴力的本質不只是權控,那其他相
關阻礙安全的議題仍須被重視。
我想大家在做婚暴防治工作的時候,都已經同意說權控也不是唯一解釋暴力的方式,本來婚暴就很複雜,
很難用單一來解釋,牽扯的不只是關係,有的是金錢,有的是性別或者是小孩,各種各樣的家族議題。在
美國有兩個主要的觀點,一個是女性主義者,是從權控的角度來解釋婚暴,另一個不從這個角度來討論,
所以是兩大派。這兩大陣營有一個共同的東西它其實是希望,能夠終止暴力,那被害人不管是男的或是女
的是以安全議題為考量的。那另外一個我覺得不管哪一個方法可以預期的是效果都不會百分之百的好,不
管是相信權控、相信關係、其實陣營不同沒有關係,反正就是要終止暴力。(I3)
54
小結
女性主義覺得親密關係暴力若緣自於權力與控制的失衡,則不易經由修復式正義獲
致有效處理。在社會文化加諸於女性的期望,使得受害者的賦權(empower)工作相當不容
易,在權控的壓迫及失權的處境中,受害者在修復程序中是否能恢復較佳的權力位置,
是需要受到重視的。因此施行修復式正義若造成受害者被強求參加,或在拒絕進入時被
歸責的理由,整個機制就充滿權控的工具性,權力的展現是存在於任何環境及互動的氛
圍,不單是外在結構更可以是內在動力,修復促進之執行要能關注權力議題於任何安排
之中。執行修復的專業系統及修復評估及促進人員須有性別與權力的敏感度,以免成為
權控的工具。
修復歷程中若不能積極敏於權控關係議題,將會是引發受害者於權力弱勢中更為自
責的處境。一般而言,受害者於受暴處境中連結其情感與關係之解釋及調適,常不利於
建立安全及自尊的生活,若修復歷程中對被害者的不適切要求或互動,可能會不利於其
處於權控關係下的弱勢角色。
親密關係暴力防治的最終目的,是終止暴力,重建被害者無暴力的安全生活。因此
無論是哪個學理派別,都需以此為工作目標。若親密關係暴力的本質不只是權控,那其
他相關阻礙安全的議題仍須被重視。
第四節 修復式正義與非政府組織
有關非政府部門的角色與任務之意見,受訪者提出「適合執行修復式正義的機構」、
「非政府組織介入的時點」、「非政府政府組織介入的限制」、「由司法啟動修復會不利女
性當時的狀態」、「司法體系與修復式正義」、「傳統司法與修復式司法的歧見」、「非政府
組織介入的重要提醒」等七個向度的想法,分述如下:
一.適合執行修復式正義的機構
到底非政府組織適不適合成為修復式正義之執行機構,於焦點訪談中出現了支持的
意見。但是當刑事司法體系,委託非政府組織在系統外執行司法工作時,其定位及優勢
應是結合資源,以家庭、社區為服務場域,為當事人及其家屬創造支持與接納的社會環
境。但非政府組織於公權力行使及專業權力範圍,能否因應修復司法之目的而達成具成
效之執行,有以下之意見:
修復式正義適合由非政府組織來推動
受訪者支持非政府組織適合參與推動修復式正義之實施,認為既然修復思維是一種
55
哲學,也需以較為中立客觀之角度促進對話平台,因此由非政府部門來推動與施行,有
其優勢。
修復式正義,我覺得它是一種法律哲學的概念,我覺得由司法主導是一件非常怪異的事情,所以我贊同由
NGO走一種小型試驗的東西。慢慢走起,然後篩選案子,然後慢慢累積人員的經驗和素質再轉換成台灣的
經驗,千萬不能大規模的推動。(I1)
我覺得非政府組織在某一部分是比較中立客觀,沒有任何的裁定權,我可以剝奪你任何的權利義務之類
的。我覺得它比較能促成關係平台的這一塊。所以角色即使沒有做到促進,但是也可以幫助加、被害者去
澄清彼此的狀況,我覺得在某個程度已達到修復了。(D3)
受訪者也認為社區加入犯罪事件的處置及再犯預防,對加、受害者提供社區之資源
介入,是十分重要的功能。但社區資源之連結以非政府組織能力較佳,也因具資源提供
之特性,加害者及受害者之接受度將會提升。
也許它還可以連結社會資源去協助經濟的困難或社會上的需要。那我覺得這是非政府組織才能辦到的。甚
至後面轉向的部份它也沒有強制性,提高他的意願度。(D3)
NGO在司法箝制的部份是比較小,所以要切入兩造是比較容易,因為它的威脅性是比較小,比較快速可以
切進。(D5)
受訪者提出既然是柔性司法之轉型,更著重在復歸及關係修復,那在執行處所之空
間,以及申請人與當事人心理情緒之處境,及人際心理的專業協助,應由非政府之專業
組織來操作為佳。
你今天作修復式,顯然不應該在辦公處所或像偵查法庭,而必須是一個比較柔性的地方,我們也不希望跟
司法完全的連結,他是一個刑事案件,但是我們不希望有疑慮就是被告覺得檢官還在哪裡看著我,可能我
在這棟建築物,那被害人會不會說阿我的感覺就是說,在情感的部份比較沒有辦法在這一部分去突顯,然
後一點我們希望他很專業很深入,有辦法去做一個經驗整合。(D6)
民眾接受度較高
由民間團體來推動修復式正義將符合其公益性及公正性,若能有專業性及社區性的
特性,再與公部門聯繫合作,將是很好的發展。
民間來做這他不是為了什麼,就是他的角色會讓人想說阿你是…你是一個熱心…熱心公益的角度進來,來
56
做這樣的一個促進會讓民眾覺得說很…就是說他幾本上就是排斥感就會比較少,他會覺得說那個宗教團體
或是 NGO在做,他們我覺得民眾的接受度會好一點,只是說那這個 NGO他來介入處理,他還是要有一些…
阿…就是說能力啦,嘿,這能力跟人力上要能夠…就注意訓練到有這樣的能力來介入。因為我覺得政府…
政府在那個角色,尤其是我們家防中心介入裡外不是人耶阿,他就是認為阿你就是跟那個被害人阿,他總
不認為你是一個公正的第三者。(N1)
我覺得說非營利組織可以做,他絕對是一個適合做的,但是要開創出一個什麼,如果我的心理衛生中心他
是以社區為中心的,這個所謂的一個家庭協談或是我透過不同機構的轉介,我不要多啦,只要就是說以各
縣市,我假設以家暴案件的家暴中心,他們能夠擇一個團體,然後來做轉介的一個單位的話,然後好好去
訓練,實驗期投入去做,然後跟社工之間有個良好的配合機制,我覺得他是可以做的,可是他就是要有這
樣訓練的一個基礎在。(M)
由上述意見整理得知,受訪者認為非政府組織在實踐修復式正義的理念及哲學,有
別於司法之審判,較能維持中立客觀性,並具提供公益性之社區資源介入的能力,及對
人際心理處境之了解與處理專業上,將成為推動與執行修復式正義的優勢部門。
二.非政府組織介入的時點
到底非政府組織可介入的時機為何?受訪者提出當司法程序完結時,是可行的且有
極大的獨立施展空間。若在司法偵審仍進行中,司法仍具主導性,則非政府組織之介入,
則須與司法連結及合作。
司法程序完結
非政府組織以其公益性之特性,在司法程序完結後,針對非法律性之情感及關係修
復將有其施展空間。
非政府組織的一個角色吼,那嗯我想就是說,如果我們把修復式正義吼,把它分成兩塊吼,一塊就是說它
司法程序已經走完了,是已經判決確定了,那這部份吼,比如說有一些夥伴的作法是說,請一些監獄的受
刑人寫信給被害人,那這一塊我想 NGO、NPO他們就是有非常大的施展空間,然後可以相當的獨當一面這
樣子。(L)
司法程序仍進行中
如果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中,因司法偵審仍具對案件當事人之設限與壓力,也具備其
主導性與掌控權,則民間非政府組織與司法聯繫合作之定位與方式,將應持續在民主化
及法治社會的推動中被注意及討論。
那如果這個 CASE的節點是定在一個司法流程還沒走完的,比如說偵查審判階段吼,那這時候案件還沒有
57
確定,那它就是還處於司法程序中的案件,那這時既然在司法程序中,那各級法院或地檢署它就無法去釋
放百分之百的主導和掌控。這時候可能就是說由 NGO、NPO或地檢署和法院來做一個合作這樣一個模式這
樣子,那當然就是說在這一塊,台灣因為長期戒嚴,有兩個情況遺留下來,一個就是說,司法過去是統治
者的工具,所以回歸民主化,人性化也是這幾年才開始,然後人民的集會結社權被限制,所以很多的 NGO、
NPO也待發展,那這些都是我們在推行修復式司法的一些困境,也就是未來要更加努力的地方這樣子。(L)
由上述討論可知,目前修復式正義實施之節點,仍有許多討論與實驗之必要,有關
非政府組織介入之最佳時點,亦尚未有共識。但是民間團體積極及持續與司法系統的互
動與聯繫,將有助於建構各不同的司法程序節點之介入模式。
三.非政府政府組織介入的限制
由於家庭暴力行為乃為犯罪事件,具備其司法性之處理需求,若由非司法部門及非
司法專業人力來處理違法行為,其妥適性及效能性亦成為受訪者之疑慮,且我國在家庭
暴力防治工作是以被害人保護為核心價值,而家庭暴力行為具有其成因的複雜性,及長
期與重複性發生之特性,對申請人及當事人之評估及促進工作應審慎與精實,也需耗時
耗力,以現行體制非政府組織參與此工作之限制,受訪者的意見如下:
經費來源的受限
以台灣民間團體對政府經費補助之依賴,其獨立性、自主性與公正性,常需因財政
的拮据及經費來源之顧慮,而被牽制。但非政府組織之經費來源若都來自於募款,
以目前社會處境呈現募款不易之困境,將使具非營利性之非政府部門,難能經營。
他不太像香港或歐美的 NGO是真的以自己的力量來自己的一個捐助,然後用朝自己的中心...使命去做這
個,就比較不會變,那可是我覺得台灣這個現在的民間的…他還是會有蠻大的依賴政府的補助。所以他會
被政府牽制那個是應該還是會有的習慣,不能那麼完全按照他的那個原始的那個使命去做,可能會有所比
較。(N1)
我覺得 NGO,恩…第一我記得這幾年看到的 NGO跟政府都已經互相的太靠攏,他的財務的關係。他太靠攏
了,所以他們是一個叫作ㄟ…共生、附帶的關係太強了。所以他們如果要有一個團體來承接這個的話,某
部分我希望他的財力是沒有這麼依靠。(K)
因為事實上如果這件工作不是從公部門來提供經費跟計畫支持,那你要靠民間部門就這樣慢慢找慢慢找
吼,那也沒有任何經費的狀況下我還能想像,可是一旦公部門提供經費他就會開始很多的要求,阿那個要
求就要成效。(O1)
缺乏監導系統
58
非政府部門之監督除來自於人民,也因目前非政府組織經費多數來自於政府部門補
助,政府源於公信力之維護,亦都祭出了督導與管理的系統,唯修復式正義之施行無論
政府與非政府部門都仍處摸索試探階段,缺乏足以監督輔導之體系。
不然的話,第一他們如果沒有公部門好好的監督,因為公部門往往也沒有人力沒有監督,阿那個素質萬一
不好的話,會把國家的公信力蹧蹋了。(K)
服務內涵的受限
以目前我國非政府組織投入於修復式正義知司法革新試行方案之現況,這些非政
府組織之服務都具有其服務內涵之局限性,要完成犯罪修復的司法性及關係修復的處
遇性,以及實質補償所需的協議性,都有所不足。
如果單純從台灣的民間 NGO來做兩個事情的話,其實我覺得真的是不行啦因為,不是都不能做,只是做
的那個限,那個非常的 limited非常限制,而且可能針對是某些,譬如說我相信台灣 NGO可以做一件事
情,譬如說教會裡面去做。(O1)
這變成一個馬上出現的困境,那當然○○基金會這樣做是 ok,可是簡單講,他的一個社會的那個根著的
力道不夠,他是一個以諮商輔導或倡議為主的民間團體,(台語)他沒有一個,社會的認同感不是在這
邊,所以你這樣的狀況下要去給 NGO做這件事情,事實上除非他要五年十年這樣的 create,不然現階段
來講的話,他如果沒有一個公權力撐在那邊,根本做不了。(O1)
只是說 NGO要做什麼準備,因為目前是說 NGO的困境,他目前的發展過程裡面的狀況,在這工作裡面的
困境,那如果簡單講就是要把他們的困境再擴充,就是要把…,可是第一個 NGO願不願意改變他?或是
要 create一個新的 NGO嗎?我要講的是說,我們不去否認過去,因為必須要去承認過去的一個貢獻,
他對被害人的倡議,但是問題是說在被害人的倡議那個過程當中,其實就落入一個我要講的是,他缺乏
一個已經到達某種程度,已經缺乏一個後殖民的概念。(O1)
公民意識不顯著
台灣社會歷經移民、殖民的歷史,雖法治社會的建構,在民主運動及經濟發展的
努力下,已在法制面具備架構,但公民意識與素質仍尚待建立,因此人民對家庭、社
會及國家的責任感及尊重民主人權、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以至於守法精神、社會倫
理、禮貌與尊重的人際行為等,都仍需持續努力建構。
對於一個以移民社會為主的台灣,還沒有落地生根的,整個社會,我說整合性不好的社會,他的社會共
識性除了說我們有一套法律,有一套制度角色,大家按時繳稅以外,其他是沒有的,我想沒有不能說完
全沒有啦,就是說(台語)零零落落啦,而且那個不是在我們 daily life裡面發生的也不是說到信仰,
也不是叫做什麼…(咳嗽)然後也沒有一個長期的一個,都沒有的時候這樣的情況下,這樣的力量就不
足以存在…(O1)
59
家暴中心執行修復工作的困境
我國在家庭暴力防治工作既是以被害人保護為核心價值,保護性社工的工作即環繞
在被害者的需求上,加害者之評估處遇則為另一套機制,無法合軌進行。
一般對於相對人加入也會有一套評估機制。因為相對人本身也要有社工來工作。我們在各縣市家暴中心的
社工就是因為跟相對人沒有關係,所以很難做。所以我們那時候有設計上的部分,我一直沒辦法做就是這
樣子。(A1)
家庭暴力行為具有其成因的複雜性,及長期與重複性發生之特性,目前我國家庭暴
力防治中心工作的重心仍擺在被害人危機處置及人身安全防護上,而保護性社工之職責
也以被害人為中心,因此為避免不中立的疑慮,受訪者認為應以中立部門為實施機構。
家暴的成因很複雜,我們中心保護性的工作沒有辦法做到這麼多積極的治療或那個部份,大部分還是在調
查或危機的控管上,大部分社工人力在做這一塊的部份,那時候我們也有跟老師反應我們覺得我們的困
境,第二個困境是說,因為我們要邀請雙方來,當然所受到服務的是有被通報的那一端,另外那一端家暴
中心處理,會有覺得有不中立的。我們找一些已經通過司法經過訓練的促進者,那我們會告訴他說我們是
擔任陪伴者的角色,會有獨立的第三人來協助或促進。(G3)
社工執行修復工作因社政的非強制性而常被拒絕
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社工因被害者保護之基礎,常在進行兩造之邀約會談及服務協助
上,不易獲得加害人的信任,且社工在不具司法的強制性基礎下,常被加害者拒絕。
社政為出發點,就有別於行政式司法,其實在邀請加、被害雙方,有相當的高難度,其中碰到的情況不外
乎就是家裡人拒絕是最多的,被害人拒絕率是比較低,但是也是有拒絕,但是被害人都是有同意的,困難
度都是在加害人那邊。(G1)
由上述意見得知,以我國家庭暴力防治工作而言,若要進行修復式司法之推動與執
行,非政府部門因經費來源之依賴,服務內容之受限,以及缺乏監督輔導系統,在推行
修復司法的自主性及完整性將有所不足。也因公民社會尚待建構,公民意識有待提升,
修復式正義之對話平台基礎仍顯薄弱。而非司法部門及人力難能取得執行上的利基,且
對目前的家庭暴力防治體系而言,恐難具備成效。
四.由司法啟動修復會不利女性當時的狀態
司法具備維護法律、確保法律被正確的執行、對法律的解釋權及解決爭議等之特性,
因此也具備審判與裁決的實權。一般人民咸少接觸司法系統,唯在衝突無法解決或長期
60
的壓迫造成損害,才求助於司法。而家庭暴力之發生於家庭這私領域,在法不入家門的
古訓,受害婦女的求助已有多方之掙扎,當求助於司法則易被污名化,因此在面對司法
過程,對受害者而言不啻是一段煎熬的歷程,因此受訪者提出以下之看法:
司法的權控本質不利被害人處境
在司法歷程中,若司法成為權控之工具,在詢問被害人及說明修復式正義實施的好
處上,使得被害人對其司法處境產生之恐懼或誤解,將造成非政府部門執行修復會議之
阻礙。
實施上的顧慮當然是權力上的問題,包括檢察官問當事人你要不要進入修復式司法,那當事人尤其是被告
可能會認為不進去的話檢察官可能會求處很重的刑阿,那太太也會覺得如果我不進去的話,尤其是違反保
護令的時候,那我先生會不會被判很重,到時候錢還是我要繳阿!(A3)
法官或檢察官對自己權力的認知也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要把當事人又陷入另一個權控的氛圍。這是我在實
施上的顧慮,除非當事人很有意願,或事先請社工人員對兩造進行一段工作時間之後,他們兩造都有意願
或是他們想要維持這個關係,或者是他們想要處理他們問題或是情緒,或是他們想要讓對方知道我心裡的
感想或感受,這時候再讓他們進去,他們會覺得這是我自己願意的,而不是檢察官或法官或任何人叫我這
麼做的。(A3)
處於權控關係中弱勢的女性不易區辨司法體制中的修復與避免暴力
當被害者攜帶著婚姻暴力的創傷而進入司法歷程,對於同住或仍續為婚姻關係維持
的女性,許多複雜的內外在議題,非為司法的程序所能處理。一般而言,婦女求助司法
的動機多為想要借助司法協助以停止被暴力攻擊的處境,因此若對長期處於權控關係之
弱勢女性施行修復會議,將使她需再面對加害人的陳述,也擔憂自己的表達是否會再引
發未來的暴力。
不管今天是在地檢署做或是在其他司法機構去做這個東西(修復式正義),某個程度它對於這個族群他在
認知上面,事實上是不夠清楚的。婦女在協調這個部份,有很多內在的東西是很複雜的,因為那如果她的
部分是希望維持這個婚姻關係跟未來希望繼續同住,這個複雜的議題就很高。那如果她今天已經是 OK,
其實他們已經是不同住而且是已經離婚了,因為小孩,她需要去面對這個暴力關係,那顯然你會覺得她的
議題會單純很多。(F1)
在婚姻暴力這個部份會覺得在實行修復式正義這件事情有很大的擔心;第一個是她已經到司法案件了,婦
女要到違反保護令或者是到要到提出保護令申請都已經是一個很不容易的過程了;然後再來是我們自己怎
麼去讓婦女能夠區辨這個的差異度其實是有困難的。(F1)
由上述意見可發現,若司法的權控本質及被害人長期處在權控關係中的現象不被注
意,則修復式正義之實施將會成為另一種壓迫。既然由司法作為修復工作之啟動,不利
61
於女性在創傷與失權中的處境,在此現象中應提出更完整的配套措施及相關資源以創造
改變的轉型架構,方能為非政府組織參與施行產生有利之機會。
五.司法體系與修復式正義
受訪者對於司法體系將修復式正義視為革新司法的制度,對於以司法為基礎的正義
論,及目前台灣施行的模式是局限在刑事系統中,以及司法長期與人民的生活疏離,與
社區的資源連繫不足,且司法執行之落實度仍被人民質疑的情況,作出以下之討論:
以司法基礎出發建立修復式正義架構
修復式正義之理念及架構由司法之執行基礎出發及實踐,因此受訪者認為目前以修
復式司法界定工作架構是可行的。
修復式司法跟修復式正義沒有甚麼區分,因為它是從司法的背景出發,每個人講到修復式正義都有無限的
想像,那其實都對,如果從修復式正義高層的理念來看都對,既然這是從司法的系統出來的,所以我們就
把它界定為修復式司法,不希望它是無限的上綱。(I4)
侷限於刑事案件的不足
受訪者認為既然所實施的是修復式的司法制度,卻由法務部主導,將侷限案件之類
型與執行的架構。
這件事是由法務部來提,我會覺得有視角下的不足,也就是修復式的司法制度,法務部能做的真的有限,
因為他的角色,其實觀護人也很有意見,對不起,我對觀護人非常有意見,就是他只能停留在刑事案件,
保護令部分他不能參與,只能參與到刑事案件,看來也只能在一個認罪起訴跟緩起訴的案件,至於調解的
話就辯方,事實上確實也可以送調解,但是我覺得那部分還沒有少年法庭成熟。(A7)
司法體系與網絡聯繫互動不足
司法體系與非政府組織之聯繫與工作核對確認,向來處於疏離及斷層,民間團體只
能作斷面式的處理,案件執行過程中之聯繫及轉介後之回覆相當不足。
○○地檢不跟我們家暴事件服務處連絡,也不跟我們做確認,所以他不知道我們這邊是有在做操作的,可
是實際上是我們這裡的案件是有進去的,所以我在網絡其中一環的工作者會不知道我們的案件為什麼會進
到這樣的程序裡面。(A4)
司法的落實度不佳
62
以一般民眾對司法公信力之信賴不足,對司法執行於加害者之配套工作未臻完整之
疑慮,顯見司法體系仍難取信於民。
那司法連結我想到的是可能是刑法那一部分,那保護令的部分,在保護令的強制方面,對於加害人外控,
我們就會擔心是不是可行,用什麼法規或是一些狀況,就是在執行上有時候會不是那麼,就是不是那麼完
整(A1)
由上述意見,受訪者認為目前以修復式「司法」界定工作架構是可行的。但受訪者
也認為既然所實施的是修復式的司法制度,卻由法務部主導,將侷限案件之類型與執行
的架構。也因司法體系與非政府組織之聯繫與工作核對確認,向來處於疏離及斷層,而
一般民眾對司法公信力之信賴不足,對司法執行於加害者之配套工作未臻完整之疑慮,
顯見司法體系執行修復式正義仍難取信於民。
六.傳統司法與修復式司法的歧見
傳統司法及修復式司法在哲學、信念基礎及實施程序上,有相當之分歧,在其試行方
案中更反映出傳統司法系統過度與不切實際之期待,司法人員對於修復式司法的誤解及
誤用,以及制度彈性與制式的差異,司法系統並被期待回到對人的整體,包括看見家庭、
關係及社區的意義。
司法系統過度與不切實際期待
由於司法體系仍以傳統司法執行程序加入修復司法的配套,在告知申請人及當事人
的資訊中增強了他們不切實際的期待,以及在轉介給非政府部門執行時,亦有過度之要
求。
所以他們會不會是因為對我們這樣的人,也讓被害人,就是當事人他會有一個錯誤的想法,會認為是只要,
法官開口了好像我這個…我這個案子有一些期待。(N2)
嗯,如果以現在的那個檢察官所啟動的這個所謂的修復式司法裡面,喔…因為我覺得,像上次我們去你不
是在稍微再分享的時候,我的感受是…ㄜ…檢察官他已經跟當事人講了,所以他才把案子丟給○○去進
行,所以他才有個期待要成功。(N1)
然後到後面看到那個數字的時候,他就覺得有點失望,呵,那我覺得這個…這個就讓網絡工作很辛苦啦,
因為你已經是好像說阿我都已經把你促進到這個階段,怎麼後面後繼無力阿。(N1)
司法人員對於修復式司法的誤解/誤用
63
司法人員並未針對當事人受到暴力攻擊之處境深入調查,對受暴的歷程和傷害之嚴
重度亦毫無了解,受訪者表達了對司法人員處理態度之存疑,也認為他們未能清楚修復
式正義的意涵與處理程序。
但是檢察官可能沒有去注意到這個部份,沒有看到施行暴力期間有多長、有多久了,還有這一次施暴的嚴
重程度是如何?他只就到底是不是有一方有這樣的一個意願他就送了,他所謂的意願是什麼?是希望撤回
告訴為主要的訴求,還是他真的是有心希望他能夠去對於施暴這個部份的違法性有一定的認知,或者是可
責性有一定的認知,沒有。這部份在偵查庭裡面我們是沒看到的,所以對於檢察官他是不是了解,真的清
楚修復式正義的內涵、意涵,要處理的部分是什麼?我們也是存疑,所以基本上來說如果真的要去執行,
我們司法改的這一塊修復式正義的部分,可能檢察官他所以需要的文獻資料要更完整一些;還有檢察官應
該要有更清楚的概念,到底什麼是修復式正義?他要處理的是哪個區塊?他是為了什麼目的?而不是單純
「就是因為法務部有這樣的一個計畫,所以我們為了配合執行這樣的計畫,我們就做這樣做這樣就有數字
出來,已經轉銜到什麼單位我們有在做。」但是這個是空泛的,有時候往往會造成被害人的二度傷害,所
以這個部分應該再慎重一點。(I)
所以這種狀況下真的是覺得,我覺得要做都可以做,其實只要…我覺得有一點在人屋簷下啦,就是說那
個是真的進入司法體系,所以起始點啟動點那個法官,如果他能夠弄清楚的話,後面這些我們接軌是沒
有問題的。(O1)
制度彈性與制式的差異
傳統刑事司法制度是依照刑事訴訟法所執行之的流程,甚為僵化,整個過程只著眼
於被告的犯罪行為,因此司法的歷程常更為撕裂雙方關係。而修復式司法則能提供更有
彈性的選擇,更具人性化的考量,更看見雙方的人,雙方的家庭,以及雙方的關係,因
此司法人員實需重新調整思考模式。
那在這過程中,對這個制度的核心價值吼,我覺得它的核心價值主要可以跟傳統刑事審判的流程,刑事司
法流程比較下,來凸顯出它的價值吼,那傳統刑事司法的流程其實是依照刑事訴訟法,它是一個很僵化的
流程,也是一個幾乎百分之百司法執行的流程,我覺得它好像是一個糕餅模子,所有的個案都是用這套流
程然後把麵團一直蓋一直蓋,形成一個同樣的月餅一個樣子,但實際上我們知道就是說,每一個 case有
相當多不同的情境,需要更多的理解。(L)
那相較於傳統司法,他提供一些選擇,那包括一些雙方可以調解的一些方案,當然這些選擇在目前的司法
架構下,主要是比較依附在緩起訴吼,緩起訴的選項當中吼,不過比起傳統的司法,他已經是吼,更有彈
性,更人性化這樣子。(L)
它更希望司法專業人員本身,也可以重新去調整它的思考模式,那包括我們看到說比方說,整個過程不是
著眼於被告的犯罪行為,而是看到雙方的人,雙方的家庭,雙方的關係。那地檢署這邊在偵查階段,來做
這樣一個措施方案這樣子吼,那偵查階段當然有它的好處,那就是說,其實傳統司法這樣子一直走下來吼,
64
通常是撕烈雙方關係的一個制度,一個情境啦! (L)
坦白講,除非檢察官法官非常的有突破啦!但是現在載案量的壓力之下吼,然後司法就是重證據,傳統司
法被告的目的,還有律師的目的就是希望被告獲得輕判吼,所以任何能夠推卸責任的就推卸,那這個會讓
被害者不斷的再遭受傷害,雙方的關係一直惡化,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可以提早進行,提早引入這樣的機
制吼,會比較好,尤其是不要等雙方關係已經撕裂到一個程度吼再來補救會比較好這樣子。(L)
司法系統的理解與看見
傳統司法系統以違法行為之偵查與裁判為著眼點,並未能理解這錯誤行為在整體家
庭及其環境脈絡之影響,修復式司法則期待回到對人的整體,包括看見家庭、關係及社
區的意義。
那所以說修復式司法我覺得,傳統司法是針對一個人錯誤的行為,它去評價這個行為吼,那這個修復式司
法他更看到就是說,他這個人,甚至看到他這個家庭,還有雙方的關係吼,加害者和被害者的關係吼,我
覺得這是一個關鍵,像過去我們說醫學,醫生看到最後只認得傷口不認得病人,只認得某張 X光片,就是
像傳統司法有可能走到這樣一個情形吼,那修復式司法重新喚回一個人本的,重視關係的,重視情境的,
重視家庭的,這樣一個路線,我覺得這是一個關鍵價值。(L)
傳統司法系統以違法行為之偵查與裁判為著眼點,傳統刑事司法制度是依照刑事訴
訟法所執行之的流程,甚為僵化,整個過程只著眼於被告的犯罪行為,因此司法的歷程
常更為撕裂雙方關係。而修復式司法則期待回到對人的整體,包括看見家庭、關係及社
區的意義。由於目前我國之司法體系仍以傳統司法執行程序加入修復司法的配套,在告
知申請人及當事人的資訊中常增強了他們不切實際的期待,也在轉介給非政府部門執行
時,亦對其有過度之要求。且司法人員常未針對當事人受到暴力攻擊之處境深入調查,
對受暴的歷程和傷害之嚴重度亦毫無了解,因此受訪者表達了對司法人員處理態度之存
疑,也認為他們未能清楚修復式正義的意涵與處理程序。如果司法體制未得以革新,則
非政府組織在附庸關係下亦難有作為。
七.非政府組織介入的重要提醒
當非政府組織投入修復式正義之推動與施行,受訪者提出宜採取合作之態度而非競
爭關係,強調非營利系統間的相互合作,建構整合性的工作方式,避免偏頗任一方等重
要原則。
65
採取合作而非競爭關係
非政府組織受委託辦理修復式正義之施行,需要建立合作關係,並避免因為資源多
寡產生不必要之競爭與衝突,若能以專業分工逐步構建資源網絡,將有助於修復正義之
實施及轉向工作的完備。
其實我是覺得他們如果說是民間單位,他們來承包做這樣子的工作的時候,那個轉向的工作…那個網絡是
需要連結起來,大家才願意合作。(N 2)
如果大家以競爭心理,那很難做啦,如果你有利益給人家做,人家才會說我願意跟你合作嘛,阿你…我這
邊這樣子這整套的東西,我這邊做,就像老師這樣講,那我轉向給你,譬如說有心理諮商就給心理諮商,
或是我要志願服務就去志願服務,或是我要去做什麼樣的就…就…就有這個資源都建立起來,這個網他才
有辦法說把這個…這個…大家才有合作的可能啦,如果當你一個人自己這樣做,那東西會只有一半,因為
後面像我們上次也討論說那轉向的部分沒有阿,後面可能還沒有發展出來。(N 2)
非營利系統間的相互合作
非營利系統之間有許多專業分工,若能彼此配搭合作,統合綜效,將能一起發展修
復正義之整合性工作。
諮商人員很習慣一對一的工作,很少心理師可以做到夫妻,然後他們做夫妻裡面沒有做評估,可能就是作
夫妻就是夫妻這樣子,然後我會覺得社工跟心理之間其實他是一個合作的,這應該是銜接不中斷的,可是
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我們現在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說,社工在做修復正義的過程當中,就忘了心
理諮商的配合,我覺得兩造是可以同時進行,心理諮商同時做修復正義。(M)
整合性的工作方式,非偏頗任一方
修復式正義將情感與關係之修復視為要務,雖在受害者保護之基礎下服務,也須因
應不同的需求創造出多元的服務模式。因此只要有經費之支持,並制定合宜的指標,增
加人力培訓,發展工作技術和方法,以整合性的網絡工作加以實驗性之推展計畫,將可
逐漸架構本土性之實施模式。
我會覺得第一個工作經驗較少,因為我們都是以單方,我選擇被害人或加害人的工作組織,所以很少兩造
共同唯一的。我們現在的組織是只做單一被害人,我們已經很多婦女團體都不做男性被害人了,你還叫他
做男性加害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覺得這會是一種限制,就是說那個機構價值的取向是他在做這
件事情的一種限制。(M)
婦女團體很生氣說不應該放家暴,可是我不認為不可以作,我認為可以作,因為這個社會有太多人太多不
同的需求,那我們都用自己專業的框架,我覺得是不對的,所以我覺得因應不同的需求應該創造出不同服
務的模式。(M)
66
會正視那塊確實也是重要的力量,但是…但是…但是我就覺得他有時候會辯解,就是說我可能在你受暴的
那個狀態我是幫助你被害人的,可是就是你回到一個檯面上的時,因為他…我可能是加害人的什麼什麼
人,所以我就變成我的角色會讓我可能我也不能完全偏向於這邊,我也必須要站在加害人的這個立場,然
後為她說一點話,所以我覺得那個在不同的場合裡面他的角色會變化,他不一定是助力有可能他是個拉
力。(N 1)
那我如果把他想像成一個三度空間,這樣應該是每個定點都會,每個角色功能都會要有不同的機構來發
揮,這樣才比較會完整。阿但是如果,譬如來講,倒不如務實一點,本來就啟動阿,然後現階段可以做就
是一個整合型,融合型的,那當然如果家暴防治委員會或法務部願意支持,那你只要 NGO願意做,他只要
有一定的 criteria,一定的方法,那他給他比較充分的經費,看你會長出什麼樣,這是一個可以嘗試的,
但是我覺得 anyway還沒有存在(O1)
受訪者認為修復式正義將情感與關係之修復視為要務,雖在受害者保護之基礎下服
務,也須因應不同的需求創造出多元的服務模式。非營利系統之間有許多專業分工,若
能彼此配搭合作,統合綜效,將能一起發展修復正義之整合性工作。而非政府組織受委
託辦理修復式正義之施行,需要建立合作關係,並避免因為資源多寡產生不必要之競爭
與衝突,若能以專業分工逐步構建資源網絡,將有助於修復正義之實施及轉向工作的完
備。因此只要有經費之支持,並制定合宜的指標,增加人力培訓,發展工作技術和方法,
以整合性的網絡工作加以實驗性之推展計畫,將可逐漸架構本土性之實施模式。
小結
傳統司法系統以違法行為之偵查與裁判為著眼點,傳統刑事司法制度是依照刑事訴
訟法所執行之的流程,甚為僵化,整個過程只著眼於被告的犯罪行為,因此司法的歷程
常更為撕裂雙方關係。而修復式司法則期待回到對人的整體,包括看見家庭、關係及社
區的意義。受訪者皆能認同修復式正義之實施,在衝突解決的途徑上,提供了新思維及
新方法。
受訪者也認為由非政府組織推行及實施修復式正義的理念及哲學,能有別於傳統司
法之審判,較能維持中立客觀性,並因非政府部門具提供公益性之社區資源介入的能力,
及專業上對人際心理處境之了解與處理,足可成為推動與執行修復式正義的優勢部門。
但以我國家庭暴力防治工作而言,若要進行修復式司法之推動與執行,非政府部門
因經費來源之依賴,服務內容之受限,以及缺乏監督輔導系統,在推行修復司法的自主
性及完整性將有所不足。也因台灣之公民社會尚待建構,公民意識有待提升,修復式正
義之對話平台基礎仍顯薄弱。設若司法的權控本質及被害人長期處在權控關係中的現象
不被注意,則修復式正義之實施將會成為另一種壓迫。受訪者也觀察到目前既然由司法
作為修復工作之啟動,將不利於女性在創傷與失權中的處境,針對此現象政府應提出更
完整的配套措施及相關資源以創造改變的轉型架構,方能為非政府組織參與施行產生有
67
利之機會。
受訪者也認為既然所實施的是修復式的司法制度,卻由法務部主導,將侷限案件之
類型與執行的架構。也因司法體系與非政府組織之聯繫與工作核對確認,向來處於疏離
及斷層,而一般民眾對司法公信力之信賴不足,對司法執行於加害者之配套工作未臻完
整之疑慮,顯見司法體系執行修復式正義仍難取信於民。
受訪者亦指出目前我國在家庭暴力事件之處理,司法人員常未針對當事人受到暴力
攻擊之處境深入調查,對受暴的歷程和傷害之嚴重度亦毫無了解,因此受訪者表達了對
司法人員處理態度之存疑,也認為他們未能清楚修復式正義的意涵與處理程序。因此若
司法體制未得以革新,則非政府組織在附庸關係下亦難有作為。
受訪者並認為修復式正義將情感與關係之修復視為要務,雖在受害者保護之基礎下
服務,也須因應不同的需求創造出多元的服務模式。非營利系統之間有許多專業分工,
若能彼此配搭合作,統合綜效,將能一起發展修復正義之整合性工作。而非政府組織受
委託辦理修復式正義之施行,需要建立合作關係,並避免因為資源多寡產生不必要之競
爭與衝突,若能以專業分工逐步構建資源網絡,將有助於修復正義之實施及轉向工作的
完備。因此只要有經費之支持,並制定合宜的指標,增加人力培訓,發展工作技術和方
法,以整合性的網絡工作加以實驗性之推展計畫,將可逐漸架構本土性之實施模式。
第五節 修復式正義的個案評估與類別
修復式正義之實施首重評估工作,評估的目的在於為修復會議作出篩選和準備,受訪者
提出「修復式正義個案之評估原則」、「修復式正義案件的評估需求」、「修復式正義案件
的評估問題」、「女性被害人評估的困境」、「男性加害人評估的困境」、「當前加害人工作
不足對於修復工作的影響」、「目前修復工作中評估個案的問題」、「合宜進入修復式正義
的個案類別」、「不適合進入修復式正義的個案類別」等九個面向之討論。
一、修復式正義個案之評估原則
受訪者提出實施修復方案前應針對申請人及當事人進行評估,評估需針對其安全性(危險
評估)、互動溝通狀況、暴力成因及模式、物質濫用程度等,認為應有適當的篩選與準備,
以符當事人獲修復之效。
釐清關係的危險程度以評估其修復式正義介入的適切性
針對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問題,受訪者提出執行親密關係危險評估的重要性,以作為修復
式正義介入之適切性與否的指標。
68
對,她認為說如果要用修復式正義之前,先要做關係的危險評估,她認為觀念要先建立起來,也就是說先
把關係的危險程度先釐清楚之後再來談是不是適合進行修復式正義 (C2)
雙方溝通型態
如果是低度危險又源於溝通問題或溝通型態差異的個案,應可考慮進行修復。
一個是被害人申請進來的話,但是我還要經過高危險會議,危險評估裡面,那危險評估裡面如果說他只叫
做,因為我們危險評估裡面五分以下是佔了一半,然後我們只看到,其實的家暴案件全是權控嗎?大概只
有一半,另外一半是叫做權力相當溝通型的,所以我如果對他家庭本身一個案主的人力,相對人能力,還
有他們兩個所謂的暴力發生的主因,如果是因為溝通或對價值不同的觀點而引發的爭議或暴力的話,然後
他的危險程度是低度的話,其實反而是我會把它納入為對於所謂加害人在這個案件中能不能進來的案件,
或啟動案件的一個基本機制。(M)
呃…我想回答一件蠻重要的就是說,還是要概念化他們的關係狀態,他們的變化,還有概念化他們關係中
個別成員的狀態,那從裡面他就要 catch到一個部分,這樣的狀態下,他如何去跟對方溝通一個跟他有關
係的事情。(O1)
權控關係/遇境施暴
受訪者提出在本國已全面施行依台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填表計分後,作為危險分
級並召開家庭暴力高危機案件網絡會議之模式,因此若高危機個案且有權控問題應不適
合進入修復會議。若遇境施暴類型則應重視雙方在對等的情境與條件下才適用。
家暴案件可以區分為就是說比較是權控型的或是說遇境施暴,那遇境施暴也佔了一些比例,就是說一些夫
妻並沒有權力控制的情形,但是在一些情境下可能一方在情緒控制這樣有施暴吼,但因為家庭暴力的範圍
也很廣啦,在家暴法關於身體、心理不法的心態啦吼,如果是權力控制的部分我個人就是說就要特別留意
是否要適用。因為修復式正義既然跟調解有一些精神上的類似,它是重視雙方在一個對等的情境跟條件
下,可以去協談,那如果雙方的情境是不對等的,或者是說在協談室是對等的,出了協談室是不對等的,
那這個委員必須要有這個敏銳度,那就要排除適用啦。那至於說非權控這個也很重要,因為協談嘛雙方要
在一個對等的情境下去對話。(L)
這種權控加害人,我們社工的敏感度知道,如何去分辨不要陷入那種關係,所以不是哪些被害人不能做,
還有包含哪些加害人,我們必須要作好評估,他適不適合進入的,所以這種情景之下我覺得也不會讓他進
去…有加害人處遇計畫相對對他的犯行是嚴重的,所以他可能是一群都比較權控型的加害人,那也不適合
69
進去(M)
評估加害人的暴力程度、情緒控制能力、藥物濫用情形、酒癮狀況
受訪者提出應訂定指標以作為篩選之依據,如果程度嚴重之暴力或有衝動情緒致無法控
制,以及酗酒與藥物濫用情形者,都不適合進入修復調解。
那這個部份就引發到我那時候去跟我香港的朋友聊的時候,香港的作法它有幾個 index幾個指標,他說第
一個也就是說先談家暴者的部份,那些情況是不能做調解的,第一個就是說他有暴力明顯的証明,就像警
政單位或相關的醫療醫院他有一些身體無法控制的情緒控制啦,行為控制,他有一個明顯的醫療證明說,
他現在必須要做 treatment所以他有這種情形先不可以做 mediation。(C2)
第二個就是他有酗酒,吸毒,這種情況也是不行,第三個是他對家中的成員比如說對她的父母親,對小孩
曾經有所謂的暴力相向的舉動,這種也不行吼,那看起來好像限縮了很多條件,看起來幾乎都不行,可是
他說如果這些條件,他有先接受 treatment處理之後,那這個時候就可以重新評估說他可不可以進行
mediation(C2)
二、修復式正義案件的評估需求
受訪者表示修復式正義案件之評估在連繫階段及修復階段皆有其需求,評估上須針對其
之前的家庭與生活脈絡加以了解,對整體事件的動態性歷程也須掌握。
修復評估工作在聯繫階段及修復階段均予以評估
我國目前施行之修復方案,在聯繫階段是由專案管理員負責,也進行初步評估,若認能
進一步促進,則轉給修復促進員評估,受訪者認為無論是連繫階段或修復階段都均予以
評估為當。
在評估的部分在前端,聯繫和評估是合在一起的,包括我們從篩選案件、聯繫個案跟評估案件都是跟我們
前端這邊先完成,完成之後才轉介到促進者那邊。原本應該說由促進者來做評估,促進者要做較適合,但
是執行是有困難的,所以我們才拆成兩種方式來進行處理,那我們確實認為我們可以在轉介到他們手上的
時候會再做評估的動作,後來她們也有發現過,他們之後再評估不太適合,發生新的狀況,不適合進入會
議,所以最後被否決了,然後又退出來這樣子,也是有的。(G1)
修復前的關係脈絡與歷程應列入評估
評估時宜針對申請人與當事人之前的家庭與生活脈絡加以探問,也須對整體事件的動態
70
性歷程加以掌握。
他可能是忍很久,但是旁邊有太多的約束讓他就是「打某豬狗牛」的一些傳統的東西所以他不會,可是有
一天他終於打了,所以我覺得是不是要從偶發事件或是第一次發生的案件類別下去處理,我現在其實也有
點擔憂。(F3)
三、修復式正義案件的評估問題
在評估家庭暴力案件是否進入修復式正義方案時,準確評估的壓力及長期糾葛與衝突關
係下的複雜動力,使得評估甚為不易。
修復評估不易
若在求助初期階段執行修復方案,因尚未進入司法,社工須接手進行評估,而評估之準
確性常成為社工之壓力。若雙方在長期的衝突關係中,已經歷許多無效的處理,如何發
展評估工具以辨別其進入修復方案之可能性,亦屬不易。
現在很多家防中心在我們這個階段就開始做,還在家防中心還沒進到司法的階段,裡面就有做了一些個案
如果我們要去推這個方案的話,其實我覺得工作人員會有壓力,因為我不知道自己評估的對不對。(F3)
我們可能會希望ㄧ旦遇到家庭暴力案件,我們就希望設計一個問卷,那這樣的問卷,其實有許多的當事人
會覺得,它的問題已經糾葛了二十幾年了,他們夫妻可能說檢官無效,都已經好幾十年的事情,那可能這
些問題我們有沒有可能在最初的問卷中篩出來,那這樣的問卷篩出來之後我們才啟動說明會,然後當事
人,這樣期待的人,他已經參加過說明會,那我們才正式進入偵查庭,去召開的時候才問他們要不要進入
修復。(D6)
個案的衝突處境比其暴力案件更為複雜
當刑事司法單位轉介至修復方案時,不盡然能確定其人格或精神狀況,有時在修復促進
員深入會談評估,始發現個案之衝突處境比走進司法之暴力案件更難處理,也更為複雜。
當初篩案的條件在比較輕微的案件,我們的服務過程時間沒有這麼長,也沒有這麼深入,當移給促進員之
後,可能需要花時間了解那個案情,可能就也會發生一個狀況就是說,對方可能會夾雜事件以外的情緒或
是很多一些歷程,也一併告訴促進員,越講越多之後,促進員就想說與當初我們所說的我們給她的狀態是
不一致的,然後他們就會覺得,像上次開審查會的時候,有一位老師就問了一個問題說反社會的人格為何
會篩進來?當初我們在看的時候並不覺得他有反社會人格,但是他在跟促進者對話過程中,越談越多之
後,他有很多的情緒性或對社會有很多負面的想法。(G2)
71
輕微的親密關係衝突可能會有不易評估的複雜內容
對個案嚴重度之預估,常在修復會議進行過程,才發現有更多的原生家庭問題或早期的
創傷經驗浮現,而須修正,看似犯行輕微的親密關係衝突案件,也可能有不易評估之複
雜內容。
事實上輕微的案件,是我們花費人力和精神最少的案件,可能就是案件進來,我們就做簡短式的服務就結
案了,所以我們對被害人的認識或是暴力史的歷程不見得會了解的這麼深入,我們就只是表面看通報表,
或當時收集到的資訊來做評估,那我們會發現說,事實上我們也有一對促成第一次的會議,可是呢,你知
道嗎你進去陪伴後才知道,原來家庭的創傷不會是你表面看到的那個單一事件,華人的面子,為了維持合
諧的價值,那個部份會跑出來,他會有些顧慮會持續這個婚姻,但事實上對於這個,對方可以被改變的事
情?!雖然對方也同意進入這個會議,要進入會談前才發現說,原來不期待對方會有改變,甚至會期待說
不要有這個會議,因為他報警了之後,對方還是有一些收斂。(G3)
仍共同生活的案件不易評估
非家庭暴力之一次性傷害事件,修復會議結束後即可各自返回自己的生活圈互不干預,
但家暴案件仍須共同生活者,其於會議中所談論的內容,於返家後是否能一致,難以確
認。
不管是司法的修復式案件,像是車禍事件,他們在這裡講完了,當下被對方的真心有感動了,最後還是回
到各自生活去了,可是家暴不一樣,是要回到共同的生活圈裡,這個東西也許不知道,有人反省了有人成
長了,也許有人會不認同什麼的,那當下沒有辦法去確認。(G3)
案件評估不宜僅單次就完成
家暴案件有其複雜且循環之模式,困難一次評估即確認安全無虞,實不宜僅單次就完成
或決定。
對○○地院來講,他的案件可能經過一次評估後就結束了,所以我覺得太草率,非常草率的一件事情,當
兩個人已經到司法,對簿公堂的情況之下,都已經是非常撕破臉了,所以你跟他談什麼修復都是很單方面
的事情了,因為只是用單一次的處理,我就看過重大案件分享的,我就很 shock說為什麼沒有危險評估,
為什麼這麼的草率,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上我會覺得評估的人出了一些問題。(A4)
案件的發展及意義的流動使得評估不易
家暴案件具有動態性的變化,無法因其為一次性傷害就斷定適合修復。
72
針對個案的部份,我覺得個案是改變的,是變動的,不代表一次性傷害的部份家暴案件,不代表說一定適
合。(G4)
四、女性被害人評估的困境
被害者在受暴歷程產生身心社會的改變,其源於女性經驗及創傷影響而反應在自我概
念、表達方式、求助行為及認知模式等之不易了解,在評估工作易生困境。
缺乏對於親密關係當事人特質與行為模式的充分瞭解
社工人員與被害人工作,但對被害人的特質跟行為模式仍未能充份瞭解,被害人因受長
期性、重複性暴力攻擊,其身心社會歷程所發展出來的生存調適行為,常令周邊的人無
法真實瞭解及評價。
我覺得大家其實對被害人的特質跟行為模式還是不夠了解,我們在跟被害人工作裡面,其實被害人對社工
有迷思,相對人對社工其實有投射,這個東西其實是我覺得因為我們也被攻擊。大家其實都會希望是防治
暴力的再發生,只是大家都很害怕變成共犯結構。(F1)
被害人因情境或創傷因素而未能提供完整情況
在具安全信任的專業關係中,透過會談與觀察,評估者較能蒐集充分資料進行完整的評
估,唯因被害人在情境或創傷因素下,常未能提供其真實與完整情況,致生評估上產生
落差。
評估者其實對被害人的一些評估也是很重要的,可是評估應該是他要很了解他的狀況來獲得他的認可,才
可能比較全面的作評估。其實很多女性的被害人對於評估是會害怕或是不會講全部,所以評估就產生了一
些落差。(A5)
親密關係暴力具有再犯性的可能使得評估困難度高
因親密關係具有反覆發生之週期循環特性,因此被害人常因害怕再遭毆打而不敢道出真
相及提出要求,以致評估工作困難性增高。
修復式正義它要進行的儀式,是為了過去犯的造成的傷害做道歉跟願意負責,那我們綁住的是因為這樣的
邏輯,是大部分假設之後會再有同樣的傷害,比如說我撞死一個人不會再撞死他第二次嘛,因為他已經死
了,所以我進行對家屬的道歉請他原諒我與負責賠償。可是對親密暴力裡面有很多的擔心是,沒有人百分
之百願意確認是,這個傷害事件是以後不會發生的。(F1)
73
五、男性加害人評估的困境
男性當事人缺乏自我揭露能力導致評估困難
傳統文化所形塑之男性於自我概念、表達方式、求助行為及性別認知上常因壓抑及自尊
需求,造成低度的自我揭露,不但評估困難,也可能修復會議之參與及發言也將受限。
會擔心說他確實在這邊有達成一些共識,那到底有沒有做阿,或者是說他為什麼要來,那我們現在意願普
遍低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沒有什麼誘因,或是強制性,那我幹嘛要來,那我來我覺得特別是像我們那天的經
驗,那個男性,就是話很少,就是表達的東西很少,我真的懷疑說他有沒有把他真正想講的東西都講出來,
他就是講了半天,生不出五個字,氣氛有一點硬,他在等他說,事實上我覺得他也很可憐,那個可憐是說
他也沒有在我們的文化裡被訓練說他是可以表達自己,他可以適度的表達自己的東西,那這個東西在前端
沒有直接做引導或是協助,他一下子進入到這個會議裡面。(G3)
六、當前加害人工作不足對於修復工作的影響
有關當前加害人工作不足對於修復工作的影響,受訪者表示因缺乏加害人服務的配套工
作、加害人的有效約制機制及對加害人的充分瞭解,而不利修復的進行。
因缺乏加害人服務的配套工作以致難以進行修復
本國在相對人服務方案及相關服務配套措施都極為有限,以致難以進行修復。
在台灣相對人的服務上其實很少的,那你要怎麼在很少的情況之下,邀請他進入其實是很困難的。(A1)
缺乏加害人的有效約制機制以致進行修復困難
本國缺乏加害人的有效約制機制,因此修復過程之被害人安全議題,仍需嚴謹評估,以
致進行修復是有困難。
目前我們對加害人的約束機制跟本非常的不足,如果我們要去負責整個修復過程中婦女的安全跟暴力的再
發生,我們有沒有辦法去做到嚴密的評估。(A5)
缺乏對於加害人的瞭解而不利修復的進行
以司法系統啟動修復的話,因對加害者的瞭解並不充分,則不利修復之進行。
74
修復式這一塊的相對人的部分的話,其實他的資源是少的。我會比較擔心是說,我們直接推這一塊下去就
是從司法下去做的話,那我們對於相對人他們的那些文化其實都會不了解,然後不了解他之後,妳要讓他
承認自己犯錯然後還願意負責任,那我覺得會比較困難。(F2)
七、目前修復工作中評估個案的問題
受訪者針對目前我國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之評估問題,提出未能連結既有家暴網絡服務
資源及評估指標建立不足之看法。
僅有修復工作計畫但缺乏整體性的個案修復評估工作
受訪者指出本國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針對家暴個案實施修復工作時,在評估程序上並未
能納入整體家暴防治網絡已建構之服務內涵,且因家暴體系未有機會充份對話及參與,
產生資源連繫整合之不足。
整個評估的機制都沒有很嚴謹,我就覺得那是很大的問題。你評估但你不知道現行的家暴中心在做危險評
估、親密關係危險評估,那他都不知道,怎麼來做?如果是這樣,我們就把它擺在兄弟打架、四親等的就
好,對不對?可是又不是阿,又偏愛做夫妻,我就覺得太多事情那個程序裡面沒有先思維清楚,那法務部
其實有找我們,找婦女團體、家暴中心來開個會,可是因為那個東西就是太簡單了,就是會議上面,如果
你很明確的告訴我,我們要做,可是我們需要你的配合,那我們就來想程序怎麼做,可是那時候是我們聽
你們的意見,像我們現在我們沒有說反對,你可以做但要更仔細。所以為了要知道你有沒有做仔細,參與
期間就給你觀察、監督、了解,所以我們才能知道問題跟程序出在哪裡,我們才能給後續的建議,可是問
題是如果我們很多中心沒有被邀請進來,像每次就都不知道,那就不知道我們的案件怎麼被操作。(A1)
修復個案評估的指標建立不足
受訪者指出目前之試行方案篩選個案上建立排除修復之指標,但對於會前會(預備會議期
間) 之任務及評估指標上未建立。
促進員本來是要在聯繫會前會嘛,本來是要分別召開會前會的,我們是會期待我們是做這個部份評估,請
促進者來做第二階段的評估,可能跟促進者的風格,我們沒有一個制式的評估的指標,好像沒有什麼指標
耶!第一次篩案有指標,但第二次篩案,第二階段促進者那裡卻沒有。(G2)
八、合宜進入修復式正義的個案類別
有關合宜進入修復式正義的個案類別,受訪者提出加害者態度、暴力危險度、暴力關係
型態、家庭類型、家庭衝突成因、修復意願、未來關係發展等向度之討論。
75
具真誠且負責的態度
受訪者提及當調解過程發現加害人的偽裝或說謊,將會選擇將實情開放地討論,就算無
法達成協議,也須堅持加害者需有具真誠且負責的態度。
就是說你覺得他是完全是假的,完全是沒有誠意的,那可能我們要比較尊重這個女的,就會把這個實情告
訴這個女的,這樣你願不願意進入到會議,我…我…我是覺得是這樣拉,就是全部都要攤開,因為這個好
處就是在我們委員之間溝通很好,然後我們會替雙方…我們不是在做那個績效或做…不該進入就不要進
入。(P2)
那當然我們在過程中,我們的言語…我們言語的過程中當然也是希望把雙方的誠意帶出來,也是…也是希
望這樣子,也是跟他們說調解不是法庭阿,不要攻防齁、沒有輸贏齁,或者是我們…我們會朝這個方向走,
可是畢竟不像那個…那個我們修復齁,這麼注重情感的修復,我們其實修復是把情感的修復當做第一要
件。(P2)
於施暴者的這個部份可能也要評估他到底對家暴的本質清不清楚,就是列為一個指標的參考,他有沒有承
認他是施暴的?還有在他什麼情況之下他會去施暴這個部份是不是也可以,那既然這個部份他都可以承認
了他要去面對,就他期待修復正義這裡他期待的是什麼?(I)
我覺得是不一樣所以就是要看評估那加害人對於所謂的誠實這件事情有沒有什麼意義存在,他怎麼去定義
他,所以我就再思考如果我現在要作修復正義的時候我都必須詢問加害人,我可能不是問他,你覺得這件
事情有沒有錯,因為在回答老師的時候可能會講實話,可是但他面對對方的時候不見得會如此對待。(M)
屬低度危險且非操控性強者
受訪者指出一旦進到刑事系統的家庭暴力事件,幾乎都是高危機特性的案件,若再有權
控關係,則執行修復方案可能會有潛在或立即危險。因此主張低度危險且非操控性的案
件,可考慮執行。
其實到司法體系都是高度危機的咧,否則根本不會進來咧,我們都希望是中低度危機的,甚至我還覺得做
低度,因為我們做試行那個標準可以更嚴,它做小,做很小,我們不是做很大做很小,那我們在做的過程
再去修正,所以第一我覺得做低度危險的就好了,中度危險有風險的我們先不要做,那另外一部份我覺得
只要有明確的清楚的權控關係的都不能做,因我覺得那個權控關係很複雜,那問婦女要不要她說要,但是
你不知道他到底是要還是不要,妳很難去檢驗,很難去了解你現在講的是真的還是假的,因為有些婦女很
多她也不知道自己在講甚麼,這才是我們最大頭痛的地方,對,我想那權控關係是基本上是就少很多啦,
權控關係也不能,又是低度危險的,權控關係也沒有的,或是很少很低的,那這個部份, 當然祖輝老師
前面講的全部都成立,包含意願啦甚麼甚麼那個都全部都成立,其實成立之後還要加上權控關係不明的,
低度危險的。(C4)
76
ㄚ還有一種,我覺得會說,我們過去都有這種經驗,那種衝動易怒那種加害者,雖然他說他溝通能力也可
以喔,他也說他很有意願要跟她維繫關係,那種也不行,那種而且操控性很強的,那種操控性很強的基本
上是權控關係,可是也有一種衝動易怒的,那種反社會性或邊緣性人格的我覺得那也不行,不是只有精神
疾病那種也不行。(C4)
當事人對於關係改善方向的意願
受訪者表示當事人是否對未來關係改善的方向具備意願去討論,是評估的重點之一。如
果當事人想維繫婚姻關係,或需為撫育兒女而有合作關係,或是當關係結束時避免傷害
之持續存在,則修復方案的確是一個可能嘗試的方法。
我看到都是兩造有意願要對這個婚姻是還要繼續的,我相信這也有可能也有這樣的例子,可是我看到更多
是別再相害了。喔,切的一乾二淨然後大家就不相往來,這是最好的,只是說那個,不相往來不是單方的
意願,如果另一方不願意放。(N1)
我們怎麼做,對,因為他前面的工作很重要,因為她去了解到這些人對他的了解,他才能夠找到這些適當
的人出來,因為你要評估嘛。(N2)
對,但我們會說如果有這樣的機會我們都會這樣問,但其實他那個想法,好,假設好了我一開始到底誰來
主導,你是因為誰而來,那我們把這第一句話讓加害人先談,因為我們評估的過程他有意願,他承認錯誤
嘛,今天是因為什麼案件,因為他主動去提什麼事件,發生什麼樣的問題,其實對於被害人他有放心的作
用,但同樣的道理就是說,你今天讓被害人知道,其實加害人有意願而來的。(M)
當然在被害人意願這部分在操作上,有一些特別注意的地方比如說,我們不會先問被害人的意願,我們會
先問加害人的意願,那加害人願意我們再問被害人,因為若先問被害人,被害人願意,問加害人,那加害
人不願意的話,對被害人又是一個傷害這樣子。(L)
雙方關係的延續有期待的確這個是在很多違反保護令的案件裡面,那雙方的孩子都還小,然後縱使離婚
了,也有撫養費的問題要處理吼,在這種情況下,希望雙方關係不要太徹底的撕裂吼,有一定程度的延續,
那如果是暴力,高危險就不納入。因為這是司法要展現公權力的時候,那這個家庭關係的支持性也是吼,
所以這幾點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考量。(L)
直到他回到自己,對,在這個事件上,我自己的部分是什麼,而不是一直都是別人別人別人,他也…被害
者也一直覺得是他是他是他,對,然後當有這個意願,那他也覺得說,對,那他感覺到自己這個部分,他
對這個關係裡面,他想要得到的是什麼,這是第三個,他必須要能聚焦到他在修復會議裡面…(J2)
77
那他們說 OK的話,我就說 OK,然後才找施虐者進來再談,談…我就跟他們講,等一下任何的講話只要有
一方不願意講,我們都要停止。(K)
家庭議題是合宜啟動修復工作
受訪者認為家庭關係議題是能透過修復程序而獲得較好的結果,無論是婚姻或親屬關
係,若能進行修復,則無論好好分手或維繫關係,都是有價值的。
我是覺得說家庭是滿值得做的,因為家庭的影響很大,很深遠,尤其是我在陪被害人的時候,有調解幾個
經驗,發現說夫妻很容易在調解裡面,我就碰過夫妻硬要把兩個小孩拆開,你知道嘛,如果說可以透過這
個好好修復個關係,即便是決定要離婚,是可以好好的離,最大的受益會是這個家庭中,可能是這個孩子
的部份,雙方也不用帶著恨或仇恨的心態離開婚姻,我會覺得說其實是親密關係或親屬關係,都有值得可
以做的部份。(G2)
那家暴案件我看起來其實,因為家庭中有的可能是有血緣關係,有的有婚姻關係,那如果以婚姻關係來講,
如果他有小孩子存在的部份,然後雙方不想離婚的話,其實都是可以去考量的。(G3)
權控關係相當者
受訪者表示若夫妻關係中權力過度傾斜,使得受害者失權被控制,則貿然進行修復,將
不利被害人的處境,甚且造成被害人之二度傷害。因此若雙方為權控關係相當者,或雙
方都能先行處理自身的創傷或難題,再來進入修復方案,應是更安全或有效。
如果說在甚麼樣的條件下會成為一個比較適切的選擇,我覺得兩造權力過度傾斜的時候,對於被害人顯然
不公平,我覺得這樣的關係就不能貿然的進行,被害人可能要做一些輔導創傷的部份,加害人可能要做先
行介入的部份是處遇的部份,當兩造比較接近有接軌的可能性的時候,再來作程序我覺得是比較安全,再
來對被害人是比較公平的,因為有一些被害人聽到加害人的名字的時候已經批批欻(抖),她根本不知所措
甚至是發抖很多很多我們看到的,那你貿然要兩個人對話,對被害人來說是非常不公平的。(D5)
不是每一對夫妻都適合這樣的方式,就是像○○說的他們有他們的立場,態度不是那麼平權的話,願意去
面對他們這樣的婚姻或問題,要給他們一段緩衝的時間讓他們先做個人的議題再回來看互相的互動和關
係,那所以要篩選不是每一對都適合,那可以先做分開的訓練,然後再看他們是不是適合回到面對面的關
係裡面。(D1)
因限於資源而先不考慮無子女的離婚夫妻
78
因修復式正義處遇模式需更多量的資源揖注,因此受訪者亦表示因限於資源有限,實施
上應先不考慮無子女的離婚夫妻。
如果是雙方沒有小孩子離婚的,那以我們有限的資源來講的話,我們的社政如果要做所謂的修復式正義的
處遇模式,要不要把這樣的東西納進來,我打一個問號,因為我們資源是如此的有限。(G3)
因教養子女的衝突
夫妻因管教子女而生之衝突,為未來需發展的工作方向之一。
夫妻間的爭吵,就是教養孩子上面的,我們覺得是爭吵但他們就會覺得是語言暴力跟壓力,那通常這樣發
生的都是在高社經地位的人,很少承認他有錯的,而且是怎樣打死都不會說。這一塊其實也是需要發展。
(F2)
互為相對人者
若其親密關係暴力為互毆的型式,雙方權力亦相當則應是可以進入修復式正義程序的案
件類型。
互毆的、互為相對被害的部分其實越來越多,那其實從被害人的口中也得到一些訊息,可能我在這個過程
裡面其實我們從我們看到的被害人身上,其實也得到了一些訊息,可能是相處上的一些因為有些生活事件
上的衝突,那其實會覺得相對人應該需要被協助,那如果有一些協助的資源進來的時候,也許他有更多好
的選擇。(F3)
初期暴力個案
受訪者表示若能在親密關係暴力的初期,或婚姻關係早期的衝突吵架中,就能以修復式
正義介入處遇,將避免其暴力週期循環的固著,達成修復之效。
把它放在初期的發生,早期的介入,療癒危險因子的存在,早期的介入是很重要的。人因罪惡感而有改變
的動力,如果我要做的話,我會把它放在初期的發生,而不是多年暴力的結果。所以我就放在親密關係暴
力的初期,早期的衝突吵架就應該介入,才能夠達到改變的績效。(A4)
如果是在初期或者是這樣子的一個暴力關係剛形成,他們是用暴力來解決他們這樣子問題的時候,我覺得
是不是有一些機會,讓他們不要幾年之後繼續在這個循環裡滾,到最後是誰變得越來越嚴重。(F3)
有血緣的家庭關係成員衝突合宜進行修復
79
有血緣之親屬關係,若在衝突分裂中,有修復方案協處,將有助於其家庭維繫或重整。
像其他的親等像手足阿,母子、父子或是上對上那種的,因為我覺得他們有血緣關係,那考慮到家庭重整
這一塊,是可以去考量的,我會站在比較實質的利益上去看待這件事,因為我覺得我們資源真的不是那麼
足夠。(G3)
九、不適合進入修復式正義的個案類別
有關不適合進入修復式正義的個案類別,受訪者表示高危機、嚴重暴力、嚴重精神疾患、
長期施虐者應排除進入修復式正義方案。
高危機者應排除
受訪者提出台灣親密關係危險評估或 DA危險評估高分者,既是高危機的家暴犯,則應排
除使用修復式司法。
一個是很嚴重的家暴,一個是很輕微的家暴,那目前文獻是有這兩方面,那在我們的服務裡面我們是認為
說如果他是正在暴力當中其實是不適合的,正在居住下更不適合,居住就是可能今天我跟你調解過後到家
裡,其實什麼都可能發生,在嚴重的權控之下不太可能也不適合,因為他有權控的顧慮。(A1)
家暴防治安全網就區分出一個,所以大於 8就直接出來,低於 8就有(進入修復)評估的要件。(A4)
不適合修復的,DA高或高危機我們就直接排除,有藥酒癮的部份我們也是排除,還有精神疾病。那個條
件上它是寫說,沒有罹患精神疾病,減損溝通表達能力。所以就那個正常表達,表達他內心的想法。(G4)
所以我會比較慣用危險評估量表,就是說在危險評估量表裡面第一個只要是高危機絕對不可能去做,因為
我要處理安全議題,所以不要讓被害人陷入於他要不要這樣子…安全永遠都是我最大的考量。我覺得修復
要進來還是要考慮人身安全才可以進來,那個前面就要三…就要…就要…就要…人生安全的評估是要跑在
前面的。(K)
嚴重精神疾患者應排除
受訪者提出因嚴重精神疾患者自我功能未得健全,不適合進入修復式正義方案。
妳看有精神疾病跟妄想症的人是絕對不可以的ㄚ。(E)
在司法體系那邊要先篩選,像是那個很嚴重的,我接觸到的第一個個案是哥哥吼用盡方法吼,甚至把弟弟
的行為吼,那是無中生有出來的,他弟弟也沒有這樣做,還把它弄到蘋果日報,讓弟弟上報紙,讓弟弟就
80
是,沒有, 就是壞到極點就對了啦,就那個弟弟其實後來,我們都幫他做諮商,因為他有嚴重的憂鬱症,
他沒有做這些事,可是哥哥這樣子侵害他,那種東西,那種的仇恨怎麼去修復嘛,這種東西就不要再過來
修復了,不可能的。(E)
長期施虐不適合修復
受訪者指出長期施虐、長期權力不對等的個案不適合以修復方案處遇其困境。
如果是那種已經長年的施虐的那個部份,就覺得你應該是我的附屬的那一種人,或者是我就是把你買來你
就是要聽我的,這個部份我覺得這個就是要給他一個最嚴格的司法制裁。(F3)
如果他不是施虐成性的這種,其實你會覺得會希望有一些機會,好像也會感覺上還有機會,讓他們其實如
果有願意去承認他這樣的行為,那我是不是給了一些協助讓他其實是可以去改變、去修正他的一些行為這
樣子;然後給了他一些資源,他其實可以在他們的兩造互動的過程的裡面,其實是比較平等的去有一些機
會改變。(F3)
也比較會擔心說家庭的關係,若是長期不對等的,若是這樣的狀況、這樣的會議,我們也是會很怕,因為
他們也是要共同生活,會議也引發他們思考一些問題,那些東西一旦被引出來之後沒有妥善的處理,怕回
家後他們的情緒會有衝突。所以這也是在篩選案件上比較掙扎的一個一部份。(G3)
嚴重權控或暴力者不適合修復
受訪者提出嚴重權控關係或暴力者,不適合進入修復程序。
另外一部份我覺得只要有明確的清楚的權控關係的都不能做,因我覺得那個權控關係很複雜,。(C4)
那種已經是權控的很嚴重或者是暴力情況很嚴重,而他基本上也不認知的那個部份,我覺得這其實就很大
方就讓最嚴厲的部份去處理去約束他,而不進行修復。(F3)
偶發輕度的親密關係衝突可能已經自行修復
受訪者提出偶發性、輕度的親密關係衝突或輕微暴力互毆型之夫妻,可能一邊求助另一
邊已經自行修復,亦不需再進行修復方案。
進入到我們篩選案的目標,像是偶發性、輕微的暴力衝突,像是雙方都有通報,但是通報是比較輕微的,
可是我們在實際上邀請的,遇到比較大的困難是比較小的案件可能是自己就會修復了,像是夫妻有共同的
目標就自行有一些修復,那當然會覺得說我們重起這個修復式會議,他們再把不愉快的事情拿出來,早期
的事件我們都找比較已經完成的個案,所以就等於已經是服務過了或者是已經結案了,那衝突已經不是當
下的衝突了,對他們來說事情已經過了,他們想在大家的面前拿出這樣的事情來重講,那被害人最多的擔
81
心是不知道對方會有什麼樣的反應,為什麼好像已經這件事好像已經過了,為什麼還要拿出來重講。(G3)
小結
修復式正義之實施首重評估工作,評估的目的在於為修復會議作出篩選和準備,受
訪者提出「修復式正義個案之評估原則」、「修復式正義案件的評估需求」、「修復式正義
案件的評估問題」、「女性被害人評估的困境」、「男性加害人評估的困境」、「當前加害人
工作不足對於修復工作的影響」、「目前修復工作中評估個案的問題」、「合宜進入修復式
正義的個案類別」、「不適合進入修復式正義的個案類別」等九個面向之討論,其發現如
下。
以修復式正義個案之評估原則,應於實施修復方案前,針對申請人及當事人進行評
估,評估需針對其安全性(危險評估)、互動溝通狀況、暴力成因及模式、物質濫用程度
等,認為應有適當的篩選與準備,以符當事人獲修復之效。針對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問題,
應確實執行親密關係危險評估,以作為修復式正義介入之適切性與否的指標。但如果是
低度危險又源於溝通問題或溝通型態差異的個案,應可考慮進行修復。在本國已全面施
行依台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填表計分後,作為危險分級並召開家庭暴力高危機案
件網絡會議之模式,因此若高危機個案且有權控問題應不適合進入修復會議。若遇境施
暴類型則應重視雙方在對等的情境與條件下才適用。也需積極訂定指標以作為篩選之依
據,如果程度嚴重之暴力或有衝動情緒致無法控制,以及酗酒與藥物濫用情形者,都不
適合進入修復調解。
在修復式正義案件的評估需求上,在連繫階段及修復階段皆有其需求,評估上須針
對其之前的家庭與生活脈絡加以了解,對整體事件的動態性歷程也須掌握。但我國目前
施行之修復方案,在聯繫階段是由專案管理員負責,也進行初步評估,若認能進一步促
進,則轉給修復促進員評估,受訪者認為無論是連繫階段或修復階段都均予以評估為當。
評估時宜針對申請人與當事人之前的家庭與生活脈絡加以探問,也須對整體事件的動態
性歷程加以掌握。
有關修復式正義案件的評估問題,準確評估的壓力及長期糾葛與衝突關係下的複雜
動力,使得評估甚為不易。而如何發展評估工具以辨別其進入修復方案之可能性,亦屬
不易。當刑事司法單位轉介至修復方案時,不盡然能確定其人格或精神狀況,在深入會
談評估,始發現個案之衝突處境比走進司法之暴力案件更難處理,也更為複雜。對個案
嚴重度之預估,常在修復會議進行過程,才發現有更多的原生家庭問題或早期的創傷經
驗浮現,而須修正,看似犯行輕微的親密關係衝突案件,也可能有不易評估之複雜內容。
若家暴案件仍須共同生活者,其於會議中所談論的內容,於返家後是否能一致,難以確
認。家暴案件有其複雜且循環之模式,案件的發展及意義的流動也使得評估不易,困難
一次評估即確認安全無虞,實不宜僅單次就完成或決定。
有關女性被害人評估的困境,因被害者在受暴歷程產生身心社會的改變,其源於女
性經驗及創傷影響而反應在自我概念、表達方式、求助行為及認知模式等之不易了解,
在評估工作易生困境。被害人因受長期性、重複性暴力攻擊,其身心社會歷程所發展出
82
來的特質跟行為模式,常令周邊的人無法真實瞭解及評價。而被害人在情境或創傷因素
下,也常未能提供其真實與完整情況,致生評估上之落差。因親密關係具有反覆發生之
週期循環特性,因此被害人更常因害怕再遭毆打而不敢道出真相及提出要求,以致評估
工作困難性增高。
有關男性加害人評估的困境,因傳統文化所形塑之男性於自我概念、表達方式、求
助行為及性別認知上常因壓抑及自尊需求,造成低度的自我揭露,不但評估困難,也可
能修復會議之參與及發言也將受限。
有關當前加害人工作不足對於修復工作的影響,受訪者表示因缺乏相對人服務的配
套工作、相對人的有效約制機制及對相對人的充分瞭解,而不利修復的進行。
受訪者針對目前我之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之評估問題,提出未能連結既有家暴網絡
服務資源及評估指標建立不足之看法。指出本國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針對家暴個案實施
修復工作時,在評估程序上並未能納入整體家暴防治網絡已建構之服務內涵,且因家暴
體系未有機會充份對話及參與,產生資源連繫整合之不足。目前之試行方案篩選個案上
建立排除修復之指標,但對於會前會(預備會議期間) 之任務及評估指標上仍有待建立。
有關合宜進入修復式正義的個案類別,受訪者提出加害者態度、暴力危險度、暴力
關係型態、家庭類型、家庭衝突成因、修復意願、未來關係發展等向度之討論。亦即修
復過程須堅持加害者需有具真誠且負責的態度,低度危險且非操控性的案件,當事人對
未來關係改善的方向具備意願,當事人想維繫婚姻關係,或需為撫育兒女而有合作關係,
或是當關係結束時避免傷害之持續存在,則修復方案的確是一個可能嘗試的方法。因此
家庭關係議題,無論是婚姻或親屬關係,則無論想好好分手或維繫關係,有修復方案協
處,將有助於其家庭維繫或重整。若雙方為權控關係相當者,親密關係暴力為互毆的型
式,或在親密關係暴力的初期,或婚姻關係早期的衝突,能以修復式正義介入處遇,將
避免其暴力週期循環的固著,達成修復之效。
有關不適合進入修復式正義的個案類別,受訪者表示高危機、嚴重暴力、嚴重精神
疾患、長期施虐者應排除進入修復式正義方案。意即台灣親密關係危險評估或 DA危險評
估高分者,既是高危機的家暴犯,則應排除使用修復式司法。再者,因嚴重精神疾患者
自我功能未得健全,長期施虐、長期權力不對等的個案,嚴重權控關係或暴力者,不適
合進入修復程序。
第六節 修復式正義的執行
受訪者在修復式正義之執行提出「修復式正義工作的網絡準備」、「修復的當事人準
備工作」、「針對受害者的介入工作」、「針對相對人的介入工作」、「修復式正義工作中的
當事人處境」、「關係修復會議介入的適切時機」、「修復式正義工作之啟動」、「修復工作
需要花費較長時間」、「修復的評估與促進工作」、「進行修復會談」、「修復與社區工作」
等十一項之準備程序及執行工作之討論。
83
一、修復式正義工作的網絡準備
受訪者提出修復式正義工作的網絡準備需規劃行政成本,並提早加入跨網絡與多網絡參
與修復之評估與執行工作。
網絡工作的行政成本投入準備
受訪者表示實施修復工作需啟動的網絡服務,行政耗費是巨大的,司法體制或執行機
構須對行政成本有準備或共識,才有可能落實實施。
耗費最大行政成本的問題,所以一個機構或一個司法體制要來做這樣建議的時候,他應該考量到成本
的問題,這個成本就是我到底法院能夠組成多大的網絡成員來介入,我們這些網絡人員是不是有共同
的共識,我是不是有一定的條件、評估的標準跟訓練的模式,那我們對這個的期待跟要求是不是一樣,
那我覺得如果沒有在基本的行政體制之下,會讓人有誠意過高,在落實上有過大的過失,那影響就是
在兩造權力的問題。(A4)
需要跨網絡與多網絡參與修復工作
受訪者指出若修復歷程能有跨網絡或多網絡的參與,將使評估及資源運用更為周全完
整,特別是在會前會之階段就啟動網絡合作參與,將更收其效。
案件應該進到多一點的網絡,這樣子的處理回來裡面的話,我覺得都是比較樂觀其成的,因為一個人
在面對他要的糖吃的時候他是一個面向,當另外一個人要糖吃的時候又是另外一個面向;所以就是網
絡間為什麼要合作,部分也是要讓那個訊息就有點類似照妖鏡啦,充分的去看到這個人是 O不 OK的,
那我在想說這一塊也能不能拉到會前會去做確定。(F2)
二、修復的當事人準備工作
受訪者提出修復工作之預備階段,應讓當事人充分了解修復方案的意義及流程等相關
資訊,去除迷思,得到力量去自由選擇。對於修復會議的目的及當事人的意願和權利,
應有尊重及詳盡的說明。要了解他們彼此之間權力的狀態,讓他們以自由的意願、在
雙方都同意下進行,因此須給予充分的考慮時間。
提供資訊尊重其選擇
受訪者提出修復式正義之預備階段十分重要,應讓當事人充分了解修復方案的意義
及流程等相關資訊,去除迷思,得到力量去自由選擇。
84
前端可能一定要有一些準備,不然他可能會以為我們是要來勸和不勸離,這個部分可能是要讓他非常
清楚的。那不然他帶著的可能是希望他也能得到正義,就是說在那個過程,他也可以跟對方講說你這
樣對我是不對的,那我會覺得那是他有力量的地方。(A2)
我都覺得它只是個被害人其中ㄧ個的選項,而這資訊是你把它變成一種讓被害人可以自由選擇,它如
果說她去報案,她去社工,她在哪裡他都有聽到這個資訊,她未來她自己想不想,她得到這個資訊更
完整之後自然可以做個決定(M)
我覺得最多就是向雙方當事人清楚說明,刑事司法的流程,還有我們提供新的選擇這樣,比方說違反
保護令,不是告訴乃論,是不能撤回,所以沒有撤回這樣一個選項,那我們今天作協談吼,那如果談
的好的話,看怎樣來搭配緩起訴制度,但是呢如果雙方不接受緩起訴的一些選項,那法官這邊如果證
據很明確,那檢察官這邊可能會起訴等等,那這些會跟雙方充分的告知,那告知以後他們會有怎樣的
選擇吼,我覺得這要充分的尊重。(L)
詳盡說明修復式會議
受訪者表示在進行修復式正義之前,可以先讓當事人充分了解與預備,對於修復會議
的目的及當事人的意願和權利,應有尊重及詳盡的說明。
就是說你再進入三方之前,你應該先做個別的…的那個會談,對對尤其是那個比較弱的,就是說比較…
就是比較弱勢的那一方可能那個促進者必須要更多讓他 empower出來的,那樣的能量,再進入對談。
(N1)
要說明啦,我是覺得很重要,準備期他…因為如果他要進入修復司法他也要去做一些準備麻。(N2)
實際上是這個修復,但是修復會議最主要是讓他們關係的修復,因為很多時候ㄟ…一個感受一個…造
成事件所帶來的一個影響,已經造成說不管他們是受害者或者是被害者,其實雙方在…雙方在這個事
件所帶出來的這個影響力其實是蠻大的,那我們評估之後,可以進入會議之後,那我們當然會告訴他
在會議裏面你們可以得到的…事前先讓他們知道他們希望在會議裏面得到什麼樣的結果。(P1)
那如果說是在進行修復式正義之前,可以讓當事人充分先了解,比如說他們可以拿到一定的資訊,很
清楚知道什麼叫修復式正義,我是被害人角色我可以透過這個得到什麼,或者是我是加害者我可以透
過這個我可以幫助自己什麼,讓他們充分了解之後然後再讓他們填這樣一個評估表、評估的一些資
料,可能對於修復式正義後續的執行會比較有幫助。(I)
了解雙方的權力狀態
受訪者表示要做修復調解之前應該要先處理一些預備工作,要了解他們彼此之間權力
85
的狀態,有關修復工作之訊息是否已夠清楚完整,對受害人的需求是否了解,加害人
有否承認他的家暴行為並願意負責等。
對個案,他也應該要清楚的了解他們彼此之間權力的狀態,因為通常在銜接在轉接案件的時候,他們
可能是沒有得到完整的訴訟資料,檢察官可能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公文告訴他,有兩造雙方要來進行這
樣的一個修復式正義的一個處理,那他們的訊息可能是片斷的不夠清楚、不夠完整的,那在這種狀況
下他們要多花一點時間,來跟受害人這一方做了解,了解他的需求是什麼?另外他對加害人這一方,
他要清楚了解施暴者到底他有沒有去承認他的家暴的這個行為,那有沒有認知到這一塊,那願意為這
一塊負責;這都是要做 VOM之前應該要先具備的。(I)
給予充分的考慮時間
受訪者表示應讓雙方能充份了解修復式正義的目的和程序,不可有任何強迫,應讓他
們以自由的意願、在雙方都同意下進行,因此須給予充分的考慮時間。
但是一定要去尊重到當事人的意願,雙方而不是只有單方面,絕對不能單方面都貿然的去做處理,還
要在雙方都同意的狀況下去評估有沒有那個出於自由的意願,當事人是不是充份了解就是修復式正義
怎麼做,他為了什麼而做之外沒有強迫的,是出於自由意願,但這根本跟有沒有辦法調解成沒有關係,
這也不是給法院面子,給調解員面子,是真的發自內心願意的,那可能也不適合貿然比如說調解同時
就讓他們簽同意書就過去了,可能讓他們回去再思考,我們講有一個猶豫期間,我們在買東西的時候
不是有一個猶豫期間,而是一個省略期間這裡其實也可以納入思考與思維。(I)
三、針對受害者的介入工作
受訪者主張修復會議的促進員應讓被害人找到敘說創傷故事的力量,專注於觀察被害
人的權力是否有行使出來,其自主性是否足夠,她是否有被充分地賦權增能,自由地
決定其參與。也讓修復成為較長期且細緻的微調歷程,積極尋求中立者角色成為修復
工作的關鍵人物。
敘說創傷故事的力量
受訪者認為應協助被害人把創傷的故事化為一種述說的聲音,因述說是一種治療平復
的過程,因此應鼓勵備害人找到敘說創傷故事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婦女要將自己的創傷化為是一種聲音,能夠表現出來的,我現在用兩種方法,一個是其他
參與者的協助,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一封信,我不一定要求面對面,因為我發現面對面不是所有人都
可以做得到,所以我覺得如果她願意作,她給條件但是他有其他參與者頂替他的位置,幫他述說它的
影響,可是他有他的故事,是他自己整理出來創傷的部分的,這封信我就覺得夠了。(M)
86
那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當事人有更多訴說的機會,傳統的不管你是開偵查庭,開審
判庭,有時法官問一問,他覺得他看完了它可以寫判決的,他可以寫起訴不起訴分書了,他覺得就 OK
了,你當事人要講其實是沒有機會的,但其實在傷害及被傷害的過程中,加害人、被害人訴說其實是
一種治療平復的過程,那修復式司法重視到這一塊。(L)
但是,讓說方去充分的訴說,然後修復促進者引導他們雙方去對於雙方對於認知上的一個共識吼,起
碼拉近那個距離,我覺得蠻重要的。(L)
長期且細緻的微調
受訪者提出在修復過程中不要催促加害人道歉或承諾,也不合適急躁地鼓勵被害人接
受或答應,應給更多的時間讓加害人去努力,讓修復成為較長期且細緻的微調歷程。
促進者在過程當中,我會讓大家知道今天的道歉不代表最後的結果,因為畢竟我們所有的條件都要經
過雙方共同努力,那因此我們不是在修復式司法那裡不是有列嗎?就是那個問題是什麼?需求是什
麼?承諾是什麼?對不對,就是有一個需求跟承諾,那加害人的承諾要能夠做到,所以我會覺得說那
這件事情上來講的話我不會特別去強調那個被害人要不要答應,因為有時候我會把那個時間拉出來,
先去看他有沒有做到嘛,再來作最後那個,因為我認為要慢慢來,要看他的條件。(M)
從關鍵人物介入
受訪者表示尋求中立者角色成為修復工作的關鍵人物,這個人較不受任何一方排擠,
將有助於順利修復。
所以一定要有中立者,但是 CIRCLE裡面要有一個中立者的角色,怎麼來的?所以我都認為說我找的
是 KEY PERSON,而不是找所有的家庭成員,什麼叫 KEY PERSON,經由評估的過程當中,其實有些這
件事情主要關鍵人物,但是如果關鍵人物都會太偏自己的立場,所以我就要中間人物,而這中間人物
怎麼找,我就要在他那個所謂問題的參與的其他成員裡面,去找到一些其實比較中立立場,甚至可以
來促進這個會議順利進行的一個主要靈魂人物。那個中立者角色部分要用安插,而這裡面不是,所以
我說其實 CIRCLE這種東西找的不是所有參與人員,找的是叫做關鍵人物。要找關鍵人物,然後我要
找這裡面有重要的人,安插人物要進來,他是講中立的或是促進這個會議可以順利進行的人物,而且
你要這些人講這些話的時候也比較不會被任何一方給排擠,但是一定要有這些人講出有助於順利。(M)
賦能
受訪者主張執行修復會議的促進員應專注於觀察被害人的權力是否有行使出來,其自
主性是否足夠,她是否有被充分地賦權增能,自由地決定其參與。
87
除了給被害人自信心之外還要讓他知道,即使這樣一個行為人他是希望和諧的,那也不必要去為了面
子問題或者是要給這個執行者好處裡的這個狀況,去勉強自己去做不可能,或者是自己打心理意願上
是不願意的這些條件約定;那其實這些都是執行面上的狀況,這個要執行者有概念。(I)
我們會發現被害人自主性有沒有存在,所以說我如果要去除所謂和諧和面子問題的時候,第一個我覺
得我仍然要看到那個被害人權力是否有使出來,他的自主性是夠的,他能夠被 EMPOWER到,那如果修
復式社會力的整個過程當中是削減他的能力,因為他只是進入到這個歷程,他只是為了給大家一個答
案或者是說他只是配合大家的程序而來,那我會覺得對被害人而言其實這個修復沒有真的修復,因為
他能夠講可是他被很多人其實過程當中不同的聲音掩蓋掉了。(M)
四、針對加害人的介入工作
加害人的支持系統
受訪者認為讓加害者的家人或朋友成為修復會議的參與者,使他的支持系統成為安全
的監督者,並能提供他們的觀點,增加修復的力量。
其實那個相對的人,因為我也是要給他權力做,他有一些朋友或是家人怎麼看到這件事情,我覺得那
個也很重要,讓被害人也看到,我覺得那個部分也是可以參與的。(N2)
那要讓他們也必要讓他們進來啦,我是覺得啦,可以讓他們…讓他因為有時候…恩…因為我們做家暴
比較站在被害人的立場來看事情,有很多事情,所以我覺得說,相對人那邊的支持者,我們也可以讓
他自己找,因為我們在那個過程裡面也讓他支持者出來,看到讓被害人也可以聽聽看他那個支持者對
這個被害人,這個加害者他的做這個作為的時候一些什麼樣的說法,我覺得這樣的話也可以…也可以
增加在這個會談裡面的一些…他的之間的一些問題可以比較透徹,我是這麼認為啦。(N2)
我若是被害人沒有其他參與者來支撐我的 POWER,其實不足的,然後那個加害人要有監控的人物,我
們都忘了,你讓加害人自己一個人,沒有監控的人物來監督他。加害人要找的是有能力的監控人,要
在旁邊,被害人要有人幫助他 EMPOWER在那裡面。(M)
五、修復式正義工作中的當事人處境
在實施修復程序時,雙方的身心社會處境與彼此間的關係也正經歷動態性的變化,因此
在調解程序中,則必要留意親密關係暴力的被害人之安全問題,也應注意面對加害人正
向改變時被害人受創經驗之反應,以及面對加害人的原諒可能會對於受虐婦女造成不利
等現象,並且有關修復促進與後續司法作為應為雙軌模式,避免加害人誤用修復式正義
規避其責。
88
修復過程中親密關係暴力的被害人安全問題
受訪者認為安全仍是極為重要的議題,特別在修復過程若加害者再犯,會增加修復的
困難,因此修復過程中親密關係暴力的被害人安全問題應被重視。
談這件事情的時候,如果是從被害人的角度、立場來談這件事情的話,我覺得就不好了。不應該從被
害人的立場來談論這件事情,應該站在更高的立場,讓雙方都能夠。當然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不能讓
被害人受傷,所以我們應該為他多做一些設計,我覺得這是應該的。(A4)
更重要的是在關係修復的過程當中,如果有暴力再發生,我們再執行這樣修復式正義的時候,是不是
有機制可以馬上介入,去保護婦女的安全,去約制加害人,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覺得我
們要能夠做到這件事情,我們才能開始來談說我們要做修復式正義。(A5)
被害人有一些憂慮,說了以後,萬一沒有達到要的效果,會不會有一些衝突,擔心再一次的衝突。(G3)
暴力的初期可能要處理安全的議題,可能說他們關係比較緊張,或者說這個社政單位的介入可能跟相
對人的關係,或是警政那邊,他們其實是比較敵對的,那比較容易引起對抗的部份,這個階段來談修
復可能比較…,不是說不可行,而是說我覺得確實是有難度,不可掌握的變數比較高。(G3)
所以我會比較慣用危險評估量表,就是說在危險評估量表裡面第一個只要是高危機絕對不可能去做,
因為我要處理安全議題,所以不要讓被害人陷入於他要不要這樣子…安全永遠都是我最大的考量。我
覺得修復要進來還是要考慮人身安全才可以進來,那個前面就要三…就要…就要…就要…人生安全的
評估是要跑在前面的。(K)
修復會議中應注意面對加害人正向改變時被害人受創經驗反應
受訪者反思在修復會議中加害者的道歉認錯及承諾,常促使促進者加速催促被害人回
報對方之善意,被害人若無立即的回應,則促進員常不斷提醒甚至責備,形成另外一
種形式的壓迫,因此提醒修復會議中應注意面對加害人正向改變時,被害人受創經驗
之反應。
好像我們也得 push被害人,你要多點同理,感受一下相對人有一些善意的部份,就像我說的那個個
案,背著加害人打電話給我,我就會敏感到這一個,就那一次的會議談完,她沒有長出同理對方的關
係,我很小心處理這個,我在提醒她這個,會不會我在責備她這樣子,你來了以後,對方也有表達一
些期待的東西,她為什麼這麼做的一些原因,她沒有長出那個東西來的話,我會變成是責備她的人這
樣子,人家都願意認錯了,比較示好了,你怎麼還沒有放下一些東西。(G3)
89
現階段要推動修復式正義在家暴案件當中,我還是覺得要謹慎而行, 如同 A1提到的在家暴的過程當
中被害人受到很多的傷害,一方面是很難得到司法上的正義,一方面是如果我們不謹慎操作的話,這
個修復式正義會是我們另外一個讓被害人講說好,就這樣子啦!你現在就已經道歉認錯,就這樣結
束。我覺得這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壓迫,我還是覺得我們應該要謹慎一點,那剛剛提到謹慎的部分就包
括說這個修復式正義具體要達到的目標到底是什麼,那另一個前端是什麼樣的加害人可以進到這樣的
條件,我覺得是要更謹慎設立評估機制。(A2)
修復會議中面對相對人的原諒可能會對於受虐婦女造成不利
受訪者提出在加害人道歉時,即便受害人明瞭她的原諒未必能真實帶來加害人停止暴
力的改變,仍存有迷思及期待,但若是促進員也在營造這種迷思,可能會對於受虐婦
女造成不利。
問她說妳覺得先生道歉妳就要原諒他嗎?那個動力真的很有趣;我們就會說她可以不要原諒他阿!她
為什麼要原諒他?可是你就會發現說,婦女就是在等先生說「我錯了,妳回來我願意改。」,那其實
問她們說,妳真的相信有幾成?她們自己也都知道很低,可是那個動力對她們來講,我都會覺得很心
痛耶…結果實務上已經是這樣,結果專業人員又在營造這樣的一個迷思我會更難過。(F1)
修復與後續司法作為
受訪者提出修復式正義與既有司法體制之結合,其分際與策略應進一步研究,以目前
之試行方案,應採雙軌模式為佳,司法仍應有其中立價值及流程,以避免加害人利用
修復掩護其犯行。
後續的部份我覺得說司法怎麼抱持自己的中立跟應該的做為,不要因為他們已經經過修復的會議然後
就比較草率處理,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還是要一定的處理。(A4)
六、關係修復會議介入的適切時機
受訪者提出關係修復會議介入的適切時機,有關通報初期/起訴前、司法介入前/中/
後期階段、假釋前及司法執行階段、專業服務歷程進行中皆適切,但認偵查階段不適
合,並提醒修復的時機應考慮長期受虐被害人當時的身心狀況及加害人對於完成修復
在司法上的期待之扭曲問題。
通報初期/起訴前適切
受訪者認為在求助被通報的初期,應給予充分的資訊供其選擇;也可在起訴前進入,
讓他們有一個互動,可預防進階或更嚴重的暴力再發生,讓加害人瞭解再繼續的衝突
90
對他是不利的。
我還是比較建議在初期。對,就是在通報那個時候。(N1)
我想就刑事案件來講,基本上當被害人他到醫院去驗傷,那開始願意勇敢的去承認他是一個家暴的受
害人,醫院現在原則上都要通報 113,113接到以後轉家暴中心,家暴中心在處理這個個案的時候做
這個基礎的了解,如果說有一個機會讓他們去做這樣一個修復式正義,雙方當事人也會有意願的,那
透過這個社工的評估如果認為這個部份是可行的,其實不一定要等保護令的申請再去做,這個其實能
夠早一點跑就早一點做,他們的裂痕傷害或者是那個關係的惡化可以早一點去做處理。(I)
我現在很多戀愛暴力個案,當第一次初期犯錯的人來的時候,他那時候願意認錯、願意改變是最好療
效的時候,才有用。(M)
我現在補充一下因為我想在初期的那個階段可能他們的需求是比較真實的。就是說他到檢察官、到法
官面前,我覺得那些都有一點迫於這個司法的威權。(N1)
所以如果說今天刑事採取可能是在警政,叫做一開始窗口就有了的話,那我不會把它那我認為這是個
選擇的資訊,認識跟了解,在任何的窗口都可以進來,例如:我現在到警察局去報案,可是他會讓她
知道因為你現在報案屬於告訴乃論,另外一個我們這邊有一個什麼樣的機制,如果你有的話可以去申
請,或許這是個不同的選擇,所以我覺得它反而只是個資訊的傳達,如果再加上要有好的書面資料,
如果說今天有意願的婦女她能進來就進來了,或者是說當我今天是社工我們都在工作裡面都有這樣的
思維,這樣那我就可以因應案主她在尋求在司法不同階段,然後把這樣的機制運用進去。(M)
那在起訴之前,我覺得這個其實可以預防進階的暴力,或是更嚴重的暴力再發生,如果說在這個階段
可以讓他們有一個互動,至少瞭解他們再繼續的衝突對他們是不利的。(O2)
司法介入前/中/後期階段
受訪者提出在司法介入的任何節點都可行,但也都有其利弊,重點不在何時進入修復
而是其評估及配套措施之情況是否能有效達成修復的目的。
偵查、審判、執行跟最後保護管束,那其實他每個階段在試行的時候,像我在台中那邊的話,台中那
邊我們討論說先把流程的機制先討論出來,比如說在偵查中的時候就是檢察官把案子轉交出來,他認
為把這個案子送出來給大家討論專業評估說,適不適合運用 RJ,但是也有一種是說在法院審理的時
候,法官可能就轉交出來說,爺,他可以審後再作調解,或審前作調解,他都是個轉向制度嘛,到監
獄, 監獄現在是最難做的,但不是不能做,國外它也有成功的案例,那在監獄像我們在台中市做監
獄的,監獄的是說他已經判刑確定了,那他是不是有機會讓那個兩造雙方在監獄裡面或在適當的昶所
進行 RJ,那到他出獄了,更生保護管束這個階段,在觀護體系他適不適合再作 RJ, 就等於說法務部
91
他的作法,一個流程,然後每個階段每個階段可能可用 RJ來列入進行的方法跟作法,那學姊剛講的
是說,如果以家防會的定位,你希望是在,如果你要嗎可能配合法務部的流程,還是你要獨立出來,
你自己要在哪個階段,怎麼去做,就是會有很大的問題。(C2)
我覺得我的角度會比較是說從這個角度來看,是說,現在的制度有甚麼欠缺的地方,或哪些人士需要
受到服務但是在目前的方案裡面他是沒辦法受到,這部份才可以從這個角度去思考,然後或者這些人
需要提前的干預這樣子,然後我們才去考慮這件事情,剛吳老師也講說其實現在很多制度裡面都已經
有了。(C1)
這四個階段,我會認為都是適合的,因為每一個案件,會去意識到比如說被害人她意識到需要情感修
復,像我們常在討論的一個創傷症候,可能在第一時間她並不是意識到她的創傷,可是也許在整個審
判的過程,或者在後階段執行的過程,可能有意會到或是經過這樣的一個過程,意會到帶給被害人的
一個後果,其實我個人會贊成這四個階段都是 OK的,只是在處理上以現階段,我個人覺得在偵查起
訴階段機會比較多,或者是說它沒有經過警察階段,警察有它的考量,比如說我今天案件遲遲不送,
那別人會認為你是不是打算吃掉這個案件,或者是其他的一個問題。(D6)
在偵查起訴的一個狀況就是,可能檢官必須綜合以前的階段,當世人至少先經過偵查,你做了甚麼,
證據攤開你到底顯現多少,兩邊或許要接觸,那這個時候,那這個時候來評估是不是來進入修復,我
認為這一點是可以考慮的,那進入審判當然還是 OK,還是可以的,那進入矯治也是可以,但是如果在
審判期作修復就撤掉案件,沒有後面矯治的問題,那已經進入執行矯治的話,那就是我講的又是另外
一個問題,因為這時候被害人通常已經消失在司法的案件裡,她出現法官還要問她,可是到執行對象
是被告,我們修復單位有沒有辦法找到被害者,然後再去跟她,距離案發已經一段時間,你是不是又
要叫她去回顧,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我認為每個個案,都有不同的情節發展,就像我講的有的剛
好到執行,她有這樣一個機緣,我認為這時候在行動也 OK,只是每個階段都有它需要去面對的問題,
那如果要清礎就是兩造當事人,要出現那可能是起訴審判前,這一個部份是比較找不到的。(D6)
在流程中是到矯治階段然後去修補,到那個階段已經有蠻多離婚就是報復的,關係已經破壞了,事實
上我們在處遇的階段,法官有流程的壓力,所以他們判的有時候蠻快的,就像你剛說的在警察的階段
可以給夫妻一個空間,機會,我覺得那是一個最好的對談的一個時機啦!可能彼此還有一些感情在,
並不是完全沒有,只是一些小小的事件,然後就提出申請,那時候可以協助介入的機會比較多,在後
面可能分開的比較多,我會期待說可以做的話是在前面那個階段。給彼此機會去面對這樣的難題。(D1)
我覺得這種沒有嚴重的暴力事件,只是家庭不斷的衝突,他們的家庭動力也不利於雙方的發展,我覺
得這種案件在起訴的階段做較不適合,因為我有感覺到那個先生之所以進到修復式司法,他想在這裏
面討好諮商師,我真的有這感覺。(D4)
假釋前
92
受訪者主張在矯正後期,仍未假釋前,若能進入修復方案,對未來更生及與家人修復
都是好的選擇。
那這個我就不論但是,我的意思是說這些人不是等到他快要假釋才做,其實在他平常就可以去做,然
後這個部份就可以說如果,內政部家防會願意去跟這個單位接觸,或是說更生保護這個單位去做接觸
的話,其實在監所那部份每一個情況即便還沒假釋之前跟家人都有機會作對話,那這個時候假如如果
法務部他的執行中的那個階段,我們那時候有建議說,到最後要修復的話要選擇場地,那法務部初步
考量可能是監所,因為提借提受刑人風險會比較高,會說由被害人她去監所,如果換成家人去監所那
更好,那因為法務部矯正署,家人的力量對他們在裡面的囚刑比較有正面助力的,那如果等到他快要
假釋釋放之後,或是結束出去再跟家人修復太慢了。(C2)
司法執行階段適切
受訪者提出在司法執行階段,修復方案是可行的,一方面是已完成司法程序,另一方
面也是有觀護人的管束,及已進行認知處遇,將比較願意對這樣的問題去做一些處理。
對,那…在…在第二個選擇,可能在執行面。就在最後一端,就是他整個司法流程都走完了。到後面
是執行那一端,也可以考慮。(N1)
嗯…其實我現在的想法是說,如果以目前的架構來講,應該是發生…啟動點應該是他整個,如果以
刑事案件的話,應該是在保護管束那個階段是最佳狀況。應該是說,對啦,我有強調保護管束,因
為他還有觀護人嘛吼。(O1)
那因為保護管束其實我們看到那些那些加害人或做這樣一個重複性的關係,當中,那他們還是有相
當比例的,第一個因為他還是跟對方住在一起…而且他們,或者是說沒有維持,但都有連絡…那而
且他在團體裡面也,因為我們做一些認知教育輔導,他在團體裡面也對他的一個過去的經驗,有很
多的整理跟探索…那他也比較願意對這樣的問題去做一些處理。(O1)
那因為吼,我覺得在矯治的階段是其實他們還有很多議題,實際生活當中會遇到的那個,那個可以
適度去避免就是說因為那些點的接觸,再有更多的傷害發生,譬如監護權阿,探視的部分,或是孩
子的養育的一些費用。(O2)
專業服務歷程進行中時適切
受訪者認為受害人正經歷專業服務之歷程時,若已走出混亂期,自主性已被增強,且
對自己的處境與需求都更清楚時,則進行修復工作是適切的。
如果說一個婦女本身來講的話當中,她本身的自主性是不夠的,那我會覺得他根本她不清楚她要的條
93
件是什麼,婦女是混亂的,那我覺得不可以用,所以我說修復正義不是擺在前端,他可能是你個案服
務的過程當中,它會在不同歷程裡面而必要去作的,她可能在前段很清楚的告訴你我就是要怎樣,而
且我為什麼要這樣作,她很清楚就擺在前段,可是我可能是個別諮商好長一段時間後,婦女最後才認
為其實她放不下的是婚姻和家庭,但是他在裡面的問題是什麼,它的需求是什麼,而我才作的,有可
能是在這樣子,有可能是在後端,因為到後來他其實雙方有一定契機,已經拖很久了,但是我用修復
正義幫他們作一個 ending,關心的 ending而已,那可能是個和平的分手。(M)
所以我會覺得說修復正義基本上來講的話,在某些婦女混亂不清楚的情況之下,它不是一個即刻,就
是因為她根本不清楚他要什麼,所以案主的自覺是在於他資源的分析,不是在於當下的決定,所以這
點是雙方都清楚的,所以先講就是說他不一定出現在前端,他可能是在妳的服務歷程當中的謀個契機
他是要擺出來的,他是一種選項。(M)
偵查階段不適合
受訪者表示在刑事偵查階段是最不適當的,因為他們帶太多想要討好期待的部分進
來修復。
那第二部份我覺得說,如果因為有些刑事階段,我覺得太…偵查啦,或起訴,那個…或者在警察那
個階段,我覺得其實很多人都帶著很多的目的來,倒覺得說,以目前的話這個是最不適當的,因為
他們帶太多那個想要討好期待的部分。(O1)
修復的時機應考慮長期受虐被害人當時的身心狀況
受訪者認為親密關係暴力有其長期性、慢性化、非單次性及反覆循環的特性,修復的
時機應考慮長期受虐被害人當時的身心狀況。
很多修復式司法案件可能是一次犯罪,或許是嚴重犯罪。但是婚姻暴力裡面都不會是只有一次,是一
個長期性的部分,加上說因為長期性然後如果剛發生又可能之前發生三個月到半年,這其實都是屬於
非常不穩定狀況的時機點。你要去做修復其實有很多其實都屬於非理性的。我會覺得我會有一些擔心
的是婦女的一些身心狀況,她要到那樣子的理解其實是比例不會那麼的高。把這些區別到長期受暴又
是急迫性受暴,那個我們最大的考量其實是婦女進入這樣子的一個關係裡面,或者是相對在這樣的關
係裡面,它的立基點就是不是對等的這個部份。(F1)
加害人對於完成修復在司法上的期待扭曲
受訪者指出加害人對司法是懼怕的,這會反映在對修復式正義的利益趨向,也表現在
加害人對於完成修復在司法上的期待之扭曲。
94
有一些相對人他會不會也有一些利益趨向的部分,當我願意聽從你的改變然後之後我去接受我願意承
認,但是我怎麼去認知他那個承認是願意去彌補的那個真偽,那他後面帶著一個附帶而來的我可能被
緩刑或者是減低刑期的這個部份,那這是一個我比較擔心的。(F3)
在司法系統裡面說可能是加害人是願意有所期待的,他可能覺得我進入修復式會議,會不會有另外一
項他可能覺得本身是一種利益,才有所期待。(G2)
他可能還在走司法程序,他們會期待說是不是透過這樣的修復有可能回應在司法上面,有緩起訴或什
麼之類的,因為實務上我們有聯絡一個個案,本來他們雙方都有這個意願,剛好保護令裁了,裁了加
害人要上處遇課程,他就爆了,他就說”「這有什麼好修復的呢!」還要他去上課。(G3)
七、修復式正義工作之啟動
修復式正義工作之啟動,須留意誰來告知及如何告知的問題,也須對加害人及被害
人之服務提供有平衡服務的基礎。
誰來向當事人說明
受訪者認為向當事人說明修復式正義之內涵,是重要的過程,但若由檢察官來告知及
詢問,容易因其態度和角色,使當事人感受到壓力,因此若啟動修復關係的方案, 是
由被害者信任的服務單位來說明,較能讓被害人放心。
誰來說明修復式正義、修復式司法的內涵,如果今天是檢察官自己轉介的,他能夠清楚嗎?他就會造
成被害人就有壓力了,所以我就會期待○○地檢署的檢察官不要說明那麼多,因為這個東西讓我們有
訓練的人來講。檢察官說明的話會形同法官的態度跟角色,就會讓人有威嚇感。所以我們就會讓被害
人來服務處,我們就會說明,那是可以拒絕的。這裡面我們考量你的權力、你的關係、你的議題,然
後如果你覺得不放心,還有,面對面不是唯一的條件,我都不認為面對面是一定要操作的,面對面有
助於關係的修復,但是家暴案件有一個特殊點就是說他最後還是要面對面,但是有這樣的關係是現在
在庇護的過程裡面,我覺得面對面這是件事情不是絕對的要求。面對面對於思考的程度有一點點的緩
頰,他最後還是可以面對面,但是我可以先透過不面對面的方法來操作。(A4)
須重視修復程序之正義性
在修復程序之設計,須留意誰先被徵詢與告知,及如何徵詢與告知的問題,以避
免對受害人產生二度傷害。
包括被害人意願,當然在被害人意願這部分在操作上,有一些特別注意的地方比如說,我們不會先問
被害人的意願,我們會先問加害人的意願,那加害人願意我們再問被害人,因為若先問被害人,被害
95
人願意,問加害人加害人不願意的話那對被害人又是一個傷害這樣子。(L)
加害人與被害人服務的平衡作為修復起點
受訪者提及在修復工作中,對加害人與對被害人之服務的平衡,使得修復工作有好的
起點。
被害人願意接受服務這其實很理所當然,就像加害人就會覺得社政單位提供被害人服務這樣子,很多
的加害人我其實有點想是我們要做一些什麼樣的方式,才可以讓加害者覺得接受社政單位的服務,是
理所當然的但還不要到司法這個階段,然後當我覺得能夠達到這樣子,比較是在接受服務的平等性自
己都有認知的時候,我覺得修復式的這個部分它其實是可以開始啟動的。(F3)
這個婦女為什麼會一直留在這個婚姻裡面,其實有他自己的需要,那我們提供什麼給她是她真的可改
善她跟她先生之間的關係,那我有一次就是真的出面對她的先生,有一些對話,我才知道說他裡面有
很多經濟的困難、孩子的教養,還有就是夫妻之間互動上遇到很大的困難,那裏面他們都需要有一些
被扶持啦!(A2)
八、修復工作需要花費較長時間
修復工作的進行需要花較長的時間來進行,修復的會前會須有充分的評估和協助,以
達成預備階段,而促進會議也要有充分的時間,完整的分享及討論,才能有細緻的品
質。
修復工作的進行需要花時間來進行
受訪者表示在修復的程序不僅充滿必要的步驟,每個步驟也需花時間仔細地處理,才
能讓雙方在具備成熟度的條件下操作。
修復式正義在整個事件的處理,不是案件發生派案操作,它其實有一段時間的陪伴了解,然後雙方有
一個成熟度的條件下操作,它是需要時間的。(A4)
促進會議要有充分的時間
受訪者表示進行修復會議室需要較長時間的評估預備促進,如受限於時間,則在壓力
中將限制其處理上的品質。
不是評估會議就是預備會議,就是其實它有些期程是可以拉長的,而不是受限於兩三個月,這有時候
兩三個月的一個時間,這其實會有一些壓力。如果又不是很密集的去接觸,其實會找不到很多的點。
96
不要有時間點的約束而是有一些指標的部分,可以看這兩造雙方到什麼樣子的狀況,而不要受限於一
些時間上的約束。(F3)
修復的會前會
受訪者表示應重視會前會甚於修復會議之執行,如果會前會之預備工作完備,修復的
完成,在會議中將更容易共識。
修復會前會的那一塊一定都會有完善,就是說要緊密性去做這一塊,不會讓當事人進入這樣子的體系
中,不會說很貿然什麼案件都丟丟丟丟丟進來,因為第一個成本的耗竭然後再來就是一個傷害或是一
種損失。(F2)
會前會很重要,如果當事人沒有被賦與這個會議的用意是甚麼,明確的說明,或是可以告訴她,她可
以這麼做,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沒有去鼓勵她,沒有這些動作的話,其實她也不知道在婚姻裡她該扮
演甚麼角色。或者我們要明確說明這會議是為他而開的。(H8)
九、修復的評估與促進工作
受訪者提及評估若為兩階段執行則應確實及處理轉銜上的連結,以完成整體評估。若
為同一人進行評估,在關係及促進,較為有利。
評估者跟促進者的切割使得訊息傳遞不足而不利修復促進
受訪者提及評估若為兩階段執行,每一階段之評估都應確實,並應有轉銜上的連結,
以完成整體評估。
評估會議必須有評估者,評估者針對相對人、被害人都有了解,了解她的傷害是甚麼,她的問題解決
策略是甚麼,然後再讓促進者做一個整個評估,那這樣的二階段裡面。現在促進者會有一個執行上的
困難,他們有很多東西是切割的,社工評估這案子可以做然後就 PASS出去了,所以促進者從書面資
料裡面去操作,這樣是很危險的,促進者很多資訊是掌握不夠的。(A4)
評估者與促者同最好為一人
受訪者提及若為同一人進行評估,在了解案情及雙方處境,以及促進彼此瞭解上較為
有利。
我個人經驗覺得評估者也是促進者是最好的,了解這兩人的需求,問題解決能力跟方法。(A4)
97
十、進行修復會談
受訪者提及修復會談議題不易聚焦,表現出加害人與被害人在修復會談中的權力互動
議題,因此促發修復會談中的當事人意願與意見交集,並應催化加害人在會談中面對
修復主題,積極說明及澄清。
修復會談議題不易聚焦
受訪者提及當事人很難聚焦在此傷害事件,嘗試將關係中各項議題連結傾吐,使修復
會談不易聚焦。
原來事件通報的單子是說不會是一個單一事件,當初我們設定這個研究方案是說希望可以聚焦在單一
事件的衝突上,可是很難阿,真的很難就不斷的說從結婚的那天說起,有發現這個會議裏面這個,他
們所講的事件不會是通報的事件,就是把過去很多的事件撈進來在同一個會議裏面想要來處理,我自
己個人就會覺得說好像在做家族,有點危險又有一點害怕。(G3)
加害人與被害人在修復會談中的權力互動議題
受訪者提及在來回互動性的陳述中,雙方可能會自說自話且不認同對方的敘說,這也
表現出他們間的權力互動關係議題。
修復式正義在操作過程裡面,當被害人說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們去看相對人的回應,相對人的回應不
一定完全認同你說的話,他會去解釋,一定會解釋如何的,如果他解釋出來的理由是歸責於被害人,
被害人一定會不高興,再創造另外一個故事出來,所以他是來來回回的,可是你這個促進者,我等於
是怎麼把這個東西去回應到,其實我不認為沒有暗示性,一定有暗示性,因為我什麼時間該休息,什
麼時間該結束,今天什麼時候再來一次,就是在我本身的掌控範圍。所以促進者怎麼樣去衡斷這件事
情,兩者之間的一個權力關係,什麼時候應該喊卡,或是我應該給被害人或相對人,我覺得其實是要
有的,但是這樣的技巧跟能力就是說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敏感度,在這個專業裡面我了解特質、也清楚
知道那個案件裡面其他的網絡資源在哪裡。(A4)
促發修復會談中的當事人意願與意見交集
受訪者提及整個修復過程應促發當事人覺得有能力及權力做決定,當事人的意願與意
見交集的方式及時間,應被充分尊重。
在什麼條件之下是成為一個適切的選擇,當事人有意願,我覺得一定要尊重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如
果真的不想要或已經談不下去了,那就應該 stop了,整個過程應該讓當事人覺得有能力決定我要不
要做下去,那哪些不能,就像剛才前面講得,權力的懸殊、對話的能力有沒有,或者是他前面都沒有
98
做就直接近兩造對話,這個是很可怕,而且成功率也不太高,因為他們都各說各話,各說各話在法庭
上面、在夫妻的爭吵上面大家都是各說各話,但就是說他們如何去有一個想法就是說我今天如果我決
定做這樣的事情,就是我們兩個都想要至少有一個共識,或至少有一個想法是我想要說出來我內心的
感受。(A3)
催化加害人在會談中面對修復主題
受訪者提及加害者以他的內在歷程決定願意坦承之程度,修復促進員應催化加害人在
會談中面對修復主題,積極說明及澄清。
重點是相對人有沒有回應,因為修復式正義的內涵並沒有要求今天加害人是百分之百說實話,他是被
允許這個實話裡面是有彈性跟空間的,這個彈性跟空間是藉由催化的過程當中,所謂修復的會議當中
得到澄清跟說明。(A4)
十一、修復與社區工作
受訪者表示社區及家庭生活的復歸,需有修復連結的機制,並應持續追蹤其落實與
成效。
目前在台灣的家暴事件,其實社區這個部分是很難動起來的。我們會很擔心當加害人在修復正義的調
解過程中,那後面執行誰去跟他落實?當場道歉他可能會願意,後面是他對於社區的恢復,他對於被
害人補償的部分,那誰去作業、誰去執行?(A1)
我們同時要有社區跟家庭支持的原因是在修復的過程當中,雙方的家庭都會帶來很大的壓力,我們自
己有沒有辦法去跟這些家庭、社區一起工作?我覺得這都是我們需要評估的。(A5)
小結
受訪者提出修復式正義工作的網絡準備需規劃行政成本,並提早加入跨網絡與多網
絡參與修復之評估與執行工作。修復工作之預備階段,應讓當事人充分了解修復方案的
意義及流程等相關資訊,修復會議的目的及當事人的意願和權利等也需澄清,以去除迷
思,得到力量去自由選擇,因此須給予充分的考慮時間。
受訪者主張修復會議的促進員應讓被害人找到敘說創傷故事的力量,專注於觀察彼此
之間權力的狀態,其自主性是否足夠,她是否有被充分地賦權增能,自由地決定其參與。
也讓修復成為較長期且細緻的微調歷程,積極尋求中立者角色成為修復工作的關鍵人物。
受訪者認為讓加害者的家人或朋友成為修復會議的參與者,使他的支持系統成為安全
的監督者,並能提供他們的觀點,增加修復的力量。
在關照修復式正義中當事人之處境,則必要留意修復過程中親密關係暴力的被害人安
99
全問題,也應注意面對加害人正向改變時被害人受創經驗之反應,以及面對加害人的道
歉可能會對於受虐婦女造成被催促原諒等現象。
有關修復會議介入的適切時機,有關通報初期/起訴前、司法介入前/中/後期階段、
假釋前及司法執行階段、專業服務歷程進行中皆適切,但認偵查階段不適合,並提醒修
復的時機應考慮長期受虐被害人當時的身心狀況及加害人對於完成修復在司法上的期待
之扭曲問題。因此有關修復促進與後續司法作為應採雙軌模式,避免加害人誤用修復式
正義規避其責。
修復式正義工作之啟動,須留意誰來告知及如何告知的問題,也須對加害人及被害
人之服務提供有平衡服務的基礎。修復工作的進行需要花較長的時間來進行,修復的會
前會須有充分的評估和協助,以達成預備階段,而促進會議也要有充分的時間,完整的
分享及討論,才能有細緻的品質。評估若為兩階段執行則應確實及處理轉銜上的連結,
以完成整體評估。 主張若為同一人進行評估,在關係及促進,較為有利。
受訪者表示修復會談議題不易聚焦,表現出加害人與被害人在修復會談中的權力互動
議題,因此促發修復會談中的當事人意願與意見交集,並應催化加害人在會談中面對修
復主題,積極說明及澄清。而社區及家庭生活的復歸,需有修復連結的機制,並應持續
追蹤其落實與成效。
第七節 修復式正義的成效評估
本節針對受訪者提出有關修復之後的親密關係暴力防治成效及修復工作的成效評估
參考指標等意見。
一、修復之後的親密關係暴力防治成效
有關修復之後的親密關係暴力防治成效,受訪者提出應以開放架構建構成效評估、
以覺察與觀察做為關係修復成效的評估方式,而對於修復之後暴力再犯的發生不確定及
修復之後的處境脈絡未改變,親密關係暴力本質未能在修復關係中充分揭露以致將影響
修復成效,因此應建立促使相對人履行其承諾的機制,因而建立修復後的追蹤機制以了
解修復之落實及成效,但修復成效不應只以有無暴力再犯做為成效認定,也應看待修復
工作的啟動可帶給當事人反思,而無需僅著重有無達到修復協議等。
以開放架構建構成效評估
受訪者表示修復會議讓雙方有對話的平合,若加害人承擔責任,或是雙方能達成協議
及履約,都是很好的成效評估方式,但覺得重點應以開放架構建構成效評估為當。
我採取比較開放的想法評估成效,因為我們都還在試辦,都還在建立本土化的模式,所以在初期的話
100
我會認為說,怎樣能夠讓雙方有平合的對話,就已經有這樣的成效在。可是我覺得達成協議的話比較
是具體的,可以看出來的雙方是否願意改變或承擔責任,這是比較具體的可以看出來的成效,那將來
如果後續有更多的資源,可以有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的話,對於履約情況我可以覺得是更好,可以顯
現出來承擔責任是一時的情緒,還是別有目的,還是真正的願意承擔責任。(H8)
以覺察與觀察做為關係修復成效的評估方式
受訪者表示在修復過程中能促進被害者看到自己的問題,學習如何提升判斷及操作模
式,了解自己的資源和資訊分析能力,但同時能看到妳的加害人是什麼角色與性格,
看到他行動力的展現及他能察覺到自己行為狀況的能力,他願意做出的改變是什麼?
因此即是以覺察與觀察做為關係修復成效的評估方式。
我不會建議被害人馬上協調後回到兩個人關係,我會認為會去訓練被害人要有一段獨立的能力再回
來,好縱使加害人答應妳了可是我要能夠學會去觀察,所以我其實我在作這件事情我把被害人都訓練
為不論今天修復正義的過程裡面談的好,談的不好,可是妳都在學著看妳的相對人是什麼角色的人,
包含他有沒有意願談入,他能不能跟體制合作看他跟人的合作關係,人際關係,我都跟被害人講,他
答不答應都有意義喔。(M)
所以我覺得那個相當程度的已經進入到一個狀況,因為目前出狀況的對數不多,可是他們在談到最
後的時候,我跟他做這部份的工作,很多人其實是會去看到自己的問題的…(O1)
有縱使已經承認條件了,後續的追蹤裡面,然後讓她看到他行動力的展現在哪裡,用行動力的好跟不
好,你自己想問什麼,可是我前面都告訴她很清楚,就是我講的,我案主自覺過程當中有個非常好的
操作模式資源跟資訊分析的清清楚楚,所以在那裏面她也在學習如何判斷事情,而且這些所有判斷都
是她親眼聽到、看到、目睹他的行動,自己決定連結的學習。(M)
其實一個蠻重要的就是說,如果分不同階段,如果他能在這樣的過程裡瞭解到自己,其實可以(台語)
不要再說對方不對了,他自己也有一些錯誤,其實他已經瞭解有錯誤,他自己有要努力有不足的地方,
但是,他願不願意進入,那是 another story,但是從不同階段每個人的需求還是有不一樣,因為這
個人他可能開始察覺到自己的行為狀況,那他也願意去做一些自己的改變,那他可能有下段婚姻或者
是什麼,還是他未來的跟他的家人的相處,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應該,應該 expand修復式的概念…
(O1)
對於修復之後暴力再犯的發生不確定
受訪者表示對於修復之後暴力再犯的發生並不確定,也無保障,因此很難放心促進被
害者參加修復方案。
101
修復式司法的本意是美意,可是為什麼親密暴力裡面大家都有很多 OS,是因為沒有人敢保證之後不會
再發生,那如果之後再發生那這件事情,我們是共犯結構。因為大家都想降低那個再傷害的激勵,那
今天最大的限制就是沒有人敢說,這件事件他是為他過去的發生賠償負責,而不是為他之後的行為保
證我不會再打妳。(F1)
比較擔心是,其實我實在是太沒有信心跟把握他在這樣一個會議之後,他是不是因著很多的因素我們
能不能夠有那麼足夠的東西去判斷,他其實這個時候是願意的還是因為很多因素的考量而願意去接受
這樣一個促成。(F3)
修復之後的處境脈絡未變容易影響修復成效
受訪者表示當修復之後的處境脈絡未有改變,則容易影響修復成效,被害人之服務提
供者認為親密關暴力是在最為私密的場域和關係中發生,萬一加害者再犯,會讓被害
者落入更危險的情境中。
儘管我們前面已經提供非常多縝密的評估,針對相對人、針對被害人都提供很多縝密的評估,可是然
後後面又發生了。對婦女的部分她其實又回到一個最私密、最初的地方,甚至是她受到的傷害可能會
來得更不容易被發現,她還是又再度落入那個危險。(F3)
工作人員的壓力其實會來自這一塊,儘管我覺得我前端做了很多縝密的評估、詳細的確認,那 F1提
的就是多數的婦女其實選擇回到家裡面去,因為他可能其實還是不夠,可能她今天很堅定她希望去
聽,但可能她背後帶的她可以自立的那個部份還是弱的,所以回到家裡面去之後其實又發生了一些狀
況,那這個部份其實是我們自己工作人員沒有辦法去確認,所以其實工作人員擔憂的是那個部份。(F3)
親密關係暴力本質未能在修復關係中充分揭露以致影響修復成效
受訪者表示親密關係暴力本質及權控關係的議題,若未能在修復會議中充分揭露,將
致影響修復成效,甚而引發更大的危險性。
我們都會知道說「場子說話一回事,回家是一回事。」所以你怎麼在場子相對人跟被害人在的場子裡
面,你會知道這個東西的弔詭的地方,這個是我覺得更擔心的。那假設今天好講完然後是各自回家不
會有任何交集的,那可能你的危險度是降低的;假設這修復之後他們其實是還要共同生活的,那我對
工作人員的責任其實是很擔心的,如果他們場面上講的話可是回去增加她的危險性,那對我們的社工
人員可能又會增加更大的痛苦嘛,因為我們本身是支持他去的,那我們又更是承受對不對。(F1)
修復工作的啟動可帶給當事人反思而無需僅著重有無達到修復
受訪者表示修復工作的啟動可帶給當事人反思,讓他們看到自己行為的樣貌和影響,
102
也看見對方的痛苦,這都有其意義,而無需僅著重有無達到修復協議。
沒有成的過程帶給雙方至少在過程中看到他們自己的行為,也看到他們痛苦的原因,然後他們會開始
反思,那沒有成是因為還沒有辦法在那麼快的時間裡放下彼此心裡的怨氣。(A4)
建立促使相對人履行其承諾的機制
受訪者表示應建立後續追蹤與評估,促使相對人履行其承諾的機制。
修復式正義有一個很重要就是後續追蹤跟評估的部份,相對人所做的承諾是不是有被履行,這履行的
過程就是要引薦許多的資源來協助他,這就是為什麼要有這麼多的角色在做支持。(I5)
建立修復後的追蹤機制以了解修復成效
受訪者表示後續追蹤與評估模式的建立及執行須積極建構,以了解修復成效。
成效的部分我是在想說可能真的是要 follow,因為我也在想可能要 follow一段時間,我們透過這樣
一個模式,然後你覺得對你有什麼樣的不一樣跟改變,不然的話,因為過去我們也發現有一些個案他
其實有他的想像,然後真的進去跟結果是有一些不同的歷程。(A2)
修復成效不應只以有無暴力再犯做為成效認定
受訪者表示修復成效不應只以有無暴力再犯做為成效認定,當事人對自我及關係的省
思,都是成果。
成效的評估就是說,最主要應該是說關係修復的程度,那當事人對自我關係的省思還有結果是不是他
們想要還有需要的。那關於,尤其是刑事方面,再犯的防止是不是主要成效,外國的學者,像日本的
學者是不贊成說以再犯的防止做為成效的認定,就是他們的關係有修復,有時候打人不是他們的關係
還很惡化,而是他還是沒有辦法控制他的情緒, 所以我曾經看過日本的學者是不贊成再犯的防止不
是很重要的一個評估的點。(A3)
建立修復後的落實機制
受訪者表示履行條件的實踐力應該成為重要的修復要件,再犯率是重要,還有雙方的
合作程度等,履行完成修復條件的內涵,仍是一個重要的評估標準。
在國外來講的話,履行條件的實踐力應該成為他很重要的修復要件,就是除了剛剛講關係、講再犯率,
另外一個部份來講,國外的評估裡面再犯率是重要,還有雙方的複合,那我認為相對人履行所謂的條
103
件有非常多種模式,不一定是金錢,不只是打人,還有他應該做什麼事情,所以他是履行完成修復條
件的內涵,是一個重要的評估標準。(A4)
二、修復工作的成效評估
有關修復工作的成效評估,可以其情緒宣洩釋放、同理能力的增加、關係改善程度、面
對與承認的態度、當事人重新得力、當事人之間產生對話的可能等。
情緒宣洩
受訪者表示應以被害人的感受為成效的指標,意即被害人的負面情感獲得釋放,情緒
得以宣洩。
這個成效的評估指標應該以被害人的感受為設定的指標,為甚麼?例如說,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是不
是讓這個被害人的負面情感獲得釋放,充分的釋放,其實那也是治療的一種。(D5)
同理能力的增加
受訪者表示成效指標中應讓加害者了解被害人在被害過程中的痛苦、悲傷的情緒,增
加其同理的能力。
讓加害者了解說被害人在被害過程中的痛苦、悲傷的情緒,不管他承不承認對對方是有傷害,可是至
少要讓他知道我在加害這個人的時候,對方是如何的痛苦和悲傷。我覺得這部份要讓加害人了解。以
這個為成效指標,我覺得它的指標可能會比較看得見。(D5)
關係改善
受訪者表示雙方是否獲得新的學習,關係是否逐步在改善, 也是成效之一。
他們是不是還有發生暴力,主觀的就是他們的關係有沒有比較改善,這是我想到的評估…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新的學習,過去都習慣使用那種固定的行為模式,這個部分他們可能還在吸收還在內化,沒有
這麼快就達到那個境界,那個成效是說他有慢慢在鬆動在改變,那也是一種成效(D1)
面對與承認的態度
受訪者表示讓被害者透過修復歷程提升其面對真相及現實的機會,也透過了解加害人
的心態與承認的態度,能在抉擇上做出準備。
104
他承認的態度,他是部分承認、完全承認,還是找理由承認,妳都可以加害人都在作些什麼事情,因
為以前我們告訴她這個,她都不相信,我沒有預測他的立場,可是我假設這種情景之下妳來看他是屬
於哪種人,講給我聽她是屬於哪種人,我講這 ABC妳覺得他是哪種人,實做之後妳看他道歉都道一半,
那妳心裡怎麼想,就知道這種人妳後面要作好可能很不可能。(M)
當事人重新得力
受訪者表示當事人可透過這個修復歷程重新得力。
這過程裡面我都會讓如果我是促進者我就會讓我的社工去作我剛才講的那些事,一定要作,因為妳叫
她看待在那個會議真正的精神跟奧妙問題,其實讓被害人去學習。(M)
當事人之間產生對話的可能
受訪者表示修復會議之核心價值是讓當事人之間產生對話的可能,並因此了解被害人
在暴力事件中的感受和所受的影響。
這部分我們會先幫他們做釐清,所以這個部分評估之後我們才會進入會議,那進入會議我覺得一個很
大的一個不同的部分,而且非常有意義,也可以說是一個核心價值,那就是讓每一方…讓他們去抒發
他們自己的一個感受。(P1)
以及這個事件所帶出來的一個影響,因為那個是一個機會,一個…就是說一個機會讓每一個…每一方
都能夠聽到對方因為事件帶出來的個人產生的感受,以及因為事件所帶出來可能周遭影響到第三者以
外或家庭的一些的影響。(P1)
然後去做了一個這個樣子的…等於是說在正式的會議裏面去釐清了,然後也讓他們去…齁…去了解到
其實對方…對這個事件來講其實都有…那個感受、那個影響都是傷的。(P1)
小結
有關修復之後的親密關係暴力防治成效,受訪者提出應以開放架構建構成效評估、以覺
察與觀察做為關係修復成效的評估方式,而對於修復之後暴力再犯的發生並不確定及修
復之後的處境脈絡未能改變,親密關係暴力本質未能在修復關係中充分揭露等,以致將
影響修復成效,因此應建立促使相對人履行其承諾的機制,因而建立修復後的追蹤機制
以了解修復之落實及成效,但修復成效不應只以有無暴力再犯做為成效認定,也應看待
修復工作的啟動可帶給當事人反思,而無需僅著重有無達到修復協議等。
有關修復工作的成效評估,建議以被害人之情緒宣洩釋放、加害人同理能力的增加、雙
方關係改善程度、被害人面對自身現實與加害人承認負責的態度、當事人之重新得力、
105
當事人之間產生對話的可能等加以衡估。
第八節 修復式正義的執行人員
受訪者提出有關修復促進者、輔助促進者、陪伴者、督導、修復工作執行人員的體
認及建議等五種執行修復工作之角色、任務與原則加以探討。
一、修復促進者
受訪者表示修復促進者為修復促進程序中重要的人物,不僅可能須擔負評估責任,
也是修復會議之主持人,要致力於營造讓被害者與加害者安心對話的環境。因此修
復促進者也是對話促進者,其應具備之以下之條件:修復促進者應具專業性、修復促
進者應具有平權及性別概念並且熟悉家庭暴力、修復促進者要有充分加害人及被害
人的工作經驗、促進者能充分了解親密關係、促進者的人際衝突處理、促進者的協
調與溝通能力、促進者的信念特質、促進者的性別考量等,作為促進者角色、知能
及考量因素。
修復促進者應具專業性
受訪者表示絕對是專業,不可能是志工的角色來扮演,須認知他的義務權力,若能由
諮商輔導及法律的專業背景來成為雙搭配,應是最佳的組合。
促進者必須要有角色的認知他的義務權力,促進者絕對是專業,不可能是志工的角色來扮演。(I2)
促進者雙搭配是最佳的組合,那這個搭配主持人比較需要具備的是諮商輔導的專業背景,然後還需要
一個副的協同主持的話,他比較需要具備法律的專業,因為隨時在案件當中,他可能都會有法律上的
問題做諮詢。那協助的人就可以馬上提供這樣的服務,不求外援馬上就可以獲得一些資訊或處哩,那
對雙方也需要做這樣的一個服務。所以我也覺得促進者的話,當然可以有一些他們自己的專業背景,
但是雙搭配,有諮商輔導背景跟法律背景搭配是最佳的組合。(H8)
修復促進者應具有平權及性別概念並且熟悉家庭暴力
受訪者表示修復促進者應具有平權及性別概念,並且要能熟悉家庭暴力之本質與模
式,因此最好要有諮商及家暴專業的人來擔任促進者,避免被害人在權力的壓迫下讓
步,造成她跟孩子額外的傷害。
修復者他怎麼去運用,他是不是有權段、控段性,他是不是有性別概念,而且他做很多很多的了解,
106
對於家庭暴力有很多的了解,那他才不會說被帶著走,那其實現在法院很多在調解家庭暴力的時候,
他會要求被害人讓步,因為調解一定要雙方,可是雙方讓步的情況下,就可能沒有很合理就是要求被
害人,就是說加害人的提議被害人應該要了解,那被害人在權力的壓迫下,他會害怕如果他沒有遵照
這樣,可能會怎麼樣怎麼樣,所以他就會很擔心,就因為這樣讓步,就造成他跟孩子另外的傷害。(A1)
家暴的修復我認為需要有諮商專業的人來做,非家暴專業不一定要有,有家暴專業,最好有這樣的訓
練過。(E)
修復促進員他基本上他應該第一個對於家暴的本質,應該要充份完整的了解跟認知。(I)
這一個調解員本身的一個背景,具有相當背景我們真的同意他這樣的一個執行,擔任執行者角色之前
還是應該有相當對於暴力本質課程認知,還有如何進行真的如何做修復式正義調解,這一個部份恩...
一些性平的概念還有一些諮商的技巧他都應該要具備。(I)
因為其實很多調解員對這部份是沒有概念的,他還是傳統的父權思維主義在作祟,才會不經意的在運
作的過程當中會加入:比如說"欸妳就不要回答他啦!拳頭不會跑過來阿!又或者是他在外面工作的
那麼辛苦,妳回來又碎碎念阿等等的",他沒有辦法去真的同理到家暴受害人,或者是施暴者和那一
個威權的觀念。(I)
修復促進者要有充分加害人及被害人的工作經驗
受訪者表示如果要成為一個恰如其分的促進者,有充分加害人及被害人的工作經驗,
是十分必要的歷練,如果只具備單方服務處遇之經驗,較容易有所偏頗。
今天如果你是在家暴案件來處理的話,你加害人要做過,你被害人一定也要做過,不能只是你的社工
經歷的話,你只有單純的做被害者,事實上我覺得我們現在實務上可能做被害者的經驗會比較多一
點,那對於加害者這一塊,可能比較沒深入去有一些真正的處遇經驗,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擔任一個恰
如其分的促進者,你這方面的歷練其實也要足夠,我覺得如果還可以再深入一點,法律部分的素養我
會覺得他是一個必要的條件,我個人是這樣子在看這件事。(G2)
促進者能充分了解親密關係
受訪者表示促進者要能充分了解親密關係的本質及被害人在家暴關係中之心理社會
處境的評估。
那就回到一個就是說,促進者對於,修復者對於那個關係本質的概念化,有沒有夠寬廣。那我會覺
得如果用另外一個比較心理層面,心理社會層面來講說,他對他這樣的過程當中,他其實這個事件
他內心充滿了一些不解以及相關的一些不舒服那這個或許叫做創傷,那這樣的過程裡面,他也感受
107
到他想去,想去對這個部分吼,或是一些罪惡感,或是有一些這個地方想要換,我是說心理社會來
看,那他這個部分,不管對方接下來跟他關係如何,但是他覺得我們如果太自己覺得他自己會做,
這個部分如果沒有去處理的話,那對他未來的,包括對他自己的關係,對他未來的關係,或者是這
個才有他的一個,而且這個包括,不是只有我們評估,因為我們在討論修復式正義的過程,他們的
瞭解出來的,他們所期待的,或是對他們的問題,其實需求是 match的時候。(O1)
看到夫妻如果說他們有可能不願意在一起,可是他們有一些話沒有說清楚,就帶著彼此之間的那個裂
痕就離開,夫妻治療是不可能處理這件事的,但是這中間呢?所以那時候因為做修復式司法我才看
到,哇原來有一個可能性在這裡,對,所以才願意試試看。(O3)
促進者的人際衝突處理
受訪者表示修復促進員應受人際衝突處理及協商談判訓練,也須了解華人文化對衝突
處理的性格與方法,以增加處理效能。
還有我覺得,人際衝突,我們有上過人際衝突的東西,協商談判也要有一些…自己有沒有受到這個的
限制吼,自己本身有這樣子的包袱,我好像我自己沒有這樣子的包袱.所以在華人社會裡面來講,好
像還要跟那個,跟?諮商師自己的那個有關係耶,所以我就不知道在訓練裡面,有沒有要做這部份.有
沒有多一個這個訓練.因為你自己是在做華人社會的修復式司法,妳這個包袱是不是要先把它拿掉會
比較好一點.就不會說掉到那裡面去自己都不知道.或沒看到。(E)
促進者的協調與溝通能力
受訪者表示促進者協商談判及協調溝通的能力是處理衝突的重要知能,當透過會議處
理衝突時,宜注意文化及性別的干擾,也須讓雙方學習傾聽對方的聲音,以先處理情
緒再處理事情會更有效果。
協商談判的能力,對,然後衝突處理的能力,我覺得這個的訓練是目前無論是在社工也好,或者是調
解委員會也好,我覺得這一塊是比較弱的(O3)
修復式主持人很重要,但是主持人他的言語,她的能力,在會前會裡面去做多一點的發揮,但在會議
的當下她似乎不該太多話,讓雙方多說一些話,因為重點是在彼此讓對方聽到彼此的聲音。(H8)
修復促進者很重要,除了主持會議的功力,能引導雙方當事人願意談出來,所以我就覺得合諧跟面子
當然是中國人的傳統文化,修復促進者的本身修養就很重要,如何去引導雙方當事人願意說出來,情
緒總是比理智先到,然後情緒的背後都會有一個故事,所以有時候應該事先處理情緒再處理事情。(H9)
促進者的信念特質
108
受訪者表示促進者的信念特質將影響其處遇的目標。
我覺得那個信仰有支持我,就是妳說我會看到希望,我們的信仰就是告訴我們信望愛這三個啦,要有
信心,要有希望…我覺得頭腦要很清楚的不被一個人左右…自己本身也知道修復式正義核心的價值,
他也是努力跟這促進員兩個一起朝那個目標去走的,也就是他心裡面也有那個目標的,即便他自己不
是做促進者.他心是有那個,有那個,有那個大的方向的.覺得那個很重要.個管員對整個那個制度是
清楚的,而且知道他在做些甚麼事情是對整個事情是有幫助的,這個也很重要。(E)
促進者的性別考量
受訪者表示依案件特性考量促進者的性別,有時促進者一男一女的配搭,也能幫助夫
妻各有相同性別者之服務,在促進經驗覺察或溝通上亦有好處。
嗯…我…我們那次是一個男性的委員就去陪伴那個男的,那我就去陪伴那個女的,那我們當然是了解
這個女的這邊了解很多,那那個男的…那我們兩個之間…這委員跟委員之間溝通就很重要了。(P2)
那而且我們溝通的過程中一對話,我們大概就可以抓住誰在講謊話,誰講的比較真,那還有就是說,
這個男的在陪伴這個男性的家暴者的時候,已經有點…變成他會有點依賴他,因為這個男的本身的問
題出在他平常沒有真正的朋友,他沒有依靠,所以他所有的情緒什麼東西它沒有出口的,所以變成他
會三不五時就去找那個男的,就是說可能會出去喝喝咖啡,或者有心事要跟他吐露,我覺得這個委員
這個角色扮演得滿好的,他就變成他一個傾訴的對象,那他在傾訴的過…因為是你來找我的喔,這個
最好介入了拉,在傾訴的過程之中可能給他一些觀念。(P2)
二、輔助促進者的角色
受訪者表示增加輔助促進者的角色,特別是律師專業者的投入,是相當具助益性。輔
助促進者可提供法律諮詢並協助維持會議程序。
這輔助促進者三位都是律師,除了這個我們還加了司法背景的促進者,設定一個輔助者 co-leader部
分,來提供這個部份的說明,如果他們有在這個法律上的疑問的話,那就是有專業的律師可提供意見。
(G4)
三、陪伴者
受訪者主張社工合宜擔任被害人的陪伴者、家族或社區成員做為修復工作落實的監
督者、以犯保或更保做為加害人的陪伴者或個管者。
109
社工合宜擔任被害人的陪伴者
受訪者表示當事人的個管社工擔任陪伴者,對被害者而言是較能放心敘說的。
甚至社工都可以進來當個陪伴者,一個陌生的人來當我的陪伴者,我不一定是要的,我要的是我的社
工員,所以家暴中心的合作是絕對要的。(A4)
所以被感動是因為內心的話被催化出來,一個是促進者的角色或是說今天誰來幫助他,這沒有很好的
協助的話,雙方當事人的故事說得七零八落的,讓人更生氣,所以這個說故事的東西可不可能被建立
起來,就是需要他的陪伴者也支持,他的陪伴者唯有社工人員是最清楚的,我為什麼一直強調網絡人
員的合作是很重要的。(A4)
家族或社區成員做為修復工作落實的監督者
受訪者表示可廣邀家族或社區成員,做為修復工作的陪伴者,以便也成為落實的監督
者。
監督評估的部分,我覺得他可能是一個監督也可能是 push的,所以參與者可以成為他很重要監控的
人,如果是社區會議就是社區裡面的成員,如果是家族會議的話就是家族裡的其他成員,在這種情形
之下,我們現在目前的操作是我們陪伴者,我們陪伴者第一個沒有廣邀其他參與者。(A4)
以犯保或更保做為被害人與加害人的陪伴者或個管者
受訪者表示以犯保或更保做為受害人或加害人的陪伴者或個管者,但須加入更完整的
訓練才能落實。
我們用陪伴者,陪伴者為犯保跟更保,這兩個初步建立關係,尤其更保後續要做犯罪加害人的評估跟
那個,我覺得那一塊都缺訓練,我們目前保護司在這一塊沒有,就是我不是只有完成而已,我還去追
蹤他,我們期待家暴中心能做得更好,因為家暴中心都是做被害人,去理解他怎麼,那相對人這一塊
我們就在思考是誰來做,如果當時有更保進來,更保才能做陪伴者,那他去做後續的評估跟有沒有去
履行的評估,但他如果沒有進來的話等於是要家暴中心去做這一塊,他其實不可行,可是司法更不會
去做,所以更不會去做那一塊了。所以那一塊監督上,目前看起來是沒有落實的。(A4)
四、修復式正義工作的督導需求
受訪者提出修復工作過程中的督導及建立修復工作督導機制的需要性應被重視。
修復工作過程中的督導
110
受訪者表示修復工作過程中的督導是重要的,可協助促進者覺察自身的問題,做好準
備因應程序中的挑戰與危機,特別是調解的操作,如何避免落入家事或社區調解時之
概念和操作。
其實修復式正義要督導機制,在調解前要總評估,其實在評估跟再評估的時候要做一個叫督導的機
制,這個督導要去問說你被問到什麼問題的時候要怎麼回應,他其實要去訓練,把這個建立出來。甚
至在調解過程還要有一個憤怒的準備,我要準備一個安全的問題,如果有人發脾氣、脾氣來了,一個
是場域安全,一個適合處理憤怒的準備,還有一個就是焦慮跟情緒的準備,那個其實都要有的,但是
你知道嗎,我們在操作的過程裡,大家都是試辦,然後又用家事調解的概念去做,還用很 local的鄉
鎮調解的概念去做,所以我就更擔心把原來一個很好的東西,變得很糟。(A1)
建立修復工作督導機制的需要性
受訪者表示應建立修復工作之督導機制,以符目前促進員訓練不足、經驗累積不易,
且家暴案件具特殊性及複雜性的需求。
有沒有可能督導的機制,隨時可以討論或這麼做到底適不適合,或者說我評估到這裡,我聯繫有沒有
困難,那個點我們卡住的地方是什麼,有沒有可能透過與督導討論有沒有改變。(G2)
五、修復工作執行人員的體認及建議
受訪者表示因應修復工作的專業性,修復式正義的執行人員不應以志工職擔任,也應
留意因社工對於當事人有態度差異,因此非為社工均合宜擔任,因而也進一步提醒社
工與當事人的互動角色將使修復工作面臨一些困境及其必須做出的準備,且進一步探
討社工及心理專業執行修復工作的困境,提出調解委員逕為修復工作的知能與經驗顯
不足等議題討論。
修復式正義的工作人員不應以志工職擔任
受訪者表示修復式正義的工作人員不應以志工職擔任,也不應以拉進許多專業人力就
以為能辦理好,重要的是他們對修復式正義的了解與認同,以及能受完整的訓練。
我覺得就是說促進者不要每一次都是用公益,用志工來做,這是地檢署的問題,因為他們都用志工,
可是事實上志工他們有時候都是有一些也是鄉紳,剛剛不是有誰講到犯保、更保嗎,通常都有一個秘
書、志工,這些志工是來報名,然後上過了幾堂課,就開始去做志工、作關懷被害人,可是他們講得
話不一定都是那個阿!所以我都會覺得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是只要有人來就好了,因為各地檢署抓
不到、拉不到人,所以他們怎麼去拉人,像○○他們有一個還把所有精神科、心理師一大群人拉進去,
111
問題是這裡面哪一個能來,那我會去是因為我就是一定要做,所以我要進去。那另外一個是促進者今
天你要不就給他費用,那你就可以評估他的資格,然後我們還可以說要做一個小小的測試,你可以做、
了解一下。(A4)
因為社工對於當事人的態度差異而非社工均合宜
受訪者表示因為社工對於當事人的態度是因其價值觀而有差異,有些社工遇到相對人
就要發狂,因此並非社工均合宜擔任促進員。
社工要走自由業的沒幾個,我們都綁在機構裡面,你機構出來有些要機構同意,有些機構還表明你不
可以兼差,所以有時候社工會考慮比較多,還有另一個部分,其實社工有些極端的,極端的相對人不
認同也是可以的。因為他對相對人是憎惡的,或是對被害人是很不屑的,社工是比較有原則、比較中
立,雙方都能夠聽到意見,能夠同理並回應他們。因為我遇到幾個社工遇到相對人就要發狂的,所以
這樣評估的機制就沒有評估到,那相對如果遇到比較會操弄被害人,所以也不是所有社工都適合。(A2)
社工與當事人的互動及工作角色致使修復工作產生之困境與準備
受訪者表示社工成為促進者,會干擾到目前的社工個案管理角色,而社工通常都是資
源擁有者,當事人也容易會有過多的要求,這些情形都是促進者須避免的。
我覺得畢竟我們(社工)都是資源擁有者,所以就不管是加害人還是被害人看到我們的時候,其實某
個層面他們都,我們覺得看到糖會喊要吃的人就會有糖可以拿走,就是說我們那邊有碰到就是一開始
來就是要要求很多,可是到後來就說我不要這個、我不要那個我什麼都不要,那我們(社工)就幫他
鋪了很多的路,然後之後一條一條再收回來,就是這樣的案件其實在我們的服務櫃台常常會看見。所
以我剛才這邊就有想到一個部份就是說,其實他們面對不同的助人者他們難免都會有不同的樣貌;那
我覺得在修復式的這樣子的路途中,我也會擔心有這樣子的情況會發生。(F2)
社工成為促進者,會干擾到成為目前的現在社工這個角色,是實務上同仁就有這種感覺。(G2)
社工執行修復工作的困境
受訪者表示目前社工年輕化,社工也普遍對自我沒有信心,面對整個修復調解,其實
訓練仍不足夠,以致於目前要由社工擔任修復促進工作,仍有顧慮。
台灣在做這一件事情,最大的困難是如果我們今天是用社工的人來做這一件事情,第一社工太年輕,
社工對自我沒有信心,他面對整個協調其實訓練要更足夠。(A4)
心理專業執行修復工作的困境
112
受訪者表示心理諮商目前的訓練仍以個別諮商為主,若要以調解概念,並加入多元人
力合作模式之操作,心理專業執行修復工作將出現困境。
那如果從心理諮商的背景來做的話,心理諮商目前被訓練還是一對一的模式,處理夫妻都有一定的空
間跟困難了,更何況是要站在調解的概念來做,我現在在學校推是他們不會做兩造間的問題,所以修
復視司法要在家庭暴力上來做的話,我覺得要小心,人員要如何被訓練,它不是治療,它只是一個方
法策略,所以要有心理師的資格來做,如果我今天沒有心理師的資格的話,要如何訓練。(A4)
調解委員逕為修復工作的知能與經驗顯不足
受訪者表示很多調解委員都不是專業,也不是很了解家庭動力,更不是很了解家庭暴
力,或者也不是很懂得諮商,不懂心理動力等,因此以調解委員逕為修復工作者,其
知能與經驗將顯不足。
第一個我覺得他們的調解委員他們都很多調解委員都不是專業的,所以他們也不是很了解家庭動力也
不是很了解家庭暴力,或者也不是很懂得諮商,不懂這個心裡的動力等等他們就近到這個調解了,他
們其實每一個調解委員有十二個小時的課程,可是這十二個小時不見得要上,比如他做家庭暴力不一
定要做家庭暴力,他就可以隨便選,然後我們也要看各地的法院說, 我提供你甚麼課程,因為它有
很多調解阿,他不是只有調家暴阿,所以他不可能說為你特別辦一個甚麼樣的活動來告訴你怎樣調家
暴也不是,所以基本上他的在職訓練上也不足,但是他近來的素質條件也不足,在職訓練也不足,然
後這個訓練的時數又很短,12個小時他就滿了。(C4)
而且很多人真的很威權啦,他就是威權的性格嘛,妳說進到這個裡面要維持一個平等的關係,那完全
不符合修復式正義的精神可是他就進到這個調解程序裡面,進行調解,所以很多人以為這是調解, 其
實並不是.但是他確實有個部份是喔,他也會希望降低對被害者的傷害, 調解如果真的很成功的話,
而他們真的也可以調到三四次也可以調比較長的時間, 但是他的篩選是有問題的。(C4)
家庭動力是一定要了解的,因我常覺得家庭動力你在表象可能看不太出來,可是這很有趣,你會影響
我,我會影響妳,我們的互動是怎樣相互影響的.可是很多我覺得可能欠缺心理動力或家庭動力這樣
的知能,她可能覺得這是一個法律議題,因為像現在我們很多都是從法律的角度來進入的,或者是他
是社會聲望或歷練足夠,可是再這一塊對他他們來講,她們就很容易被表象所迷惑,她其實很難去了
解他的內在動力是怎麼形成的,怎麼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我覺得他不會具備這樣的知能,她可能具
備調解的知能,可能對於家暴法有相關的了解,可是他對於家庭動力是明顯不足的。(C4)
那這裡我覺得,因為這裡我們沒有涉及到全控的關係, 所以他有很多不平等的關係而且是相互影響
的,可是這一塊,對很多他們自認為他們是專家的,這些調解或促進者,她其實沒辦法,甚至我覺得
我們初步的社工員心理師他都做不到這一塊,她很容易被表象,喔他已經道歉,他已經怎樣,那我事
113
情已經完成了,那他可能只是他的一個手段而已,在國外不是這樣嗎,他太習慣他會操縱調解員,他
知道你要甚麼,就答你要的,那這樣你就滿意了嘛,所以那個部份可能都是未來要避免的.我覺得啦,
因為其他我覺得比較容易講。(C4)
其實就是要有跟加害人,被害人衝突接觸機會, 現在有些人接觸加害人步接觸被害人,有些接觸被
害人不接觸加害人,所以這部份可能是要再學習的部份,因為我們開始在討論這個方案的時候社工他
們都很不想接觸加害人,結果後來會有加害人敏感症.就是很負面,我幹麻跟那些人。(C1)
因為他剛剛講其實我們現在各縣市,還是,的確吼,我們真的司法偏離了嘛,我們主要還是觀照被害
人拉吼,加害人這部份,加害人處遇這部分我們還是比較有限的啦,那對我們這方面的知識是不夠的,
那個男性專線他們辦了這麼多年,他們有沒有在這方面累積出來的一些對於男性加害人他們有一些特
質啦,或是她門的問題啦,它也可以提供我們在做這個的時候吼,因為要找跟家暴有服務經驗的喔,
或了解家庭動力的喔,非常有可能落入社工師啦心理師拉之類的,還是跟加害人接觸有限啦,所以我
覺得要做到整體的一定要了解他們的說法。(C3)
反觀目前法務部的訓練,裡面他其實我認為那是不足夠的,因為很多基本裡面價值的理清是不清楚
的,所以每個人都帶來不同領域裡面的人,帶來自己學的技巧,而我看到的技巧的東西都不一樣,是
沒有被整合出來的。另外就是說我們沒有一個非常完備叫做對修復正義的認識訓練,所以帶著一個迷
思,或對於調解的一個新仇舊恨,然後來看待這種事情的話,其實會有偏頗,他不了解他要促進的內
涵是什麼,所以用一般的調解我覺得會太偏頗了,就是那個價值其實是一個刻板化的印象,所以沒有
辦法被釐清。(M)
小結
受訪者表示修復促進者應具專業性、具有平權及性別概念並且熟悉家庭暴力議題,
修復促進者要有充分對加害人及被害人的工作經驗,並能充分了解親密關係,增強對人
際衝突處理及協調與溝通能力,因此促進者的信念特質、經驗能力及性別意識,應作為
成為促進者角色、知能及考量因素。
一般主張社工合宜擔任被害人的陪伴者,而家族或社區成員做為修復工作落實的監
督者亦是好的安排,若以犯保或更保做為受害人或加害人的陪伴者或個管者,在強化訓
練下仍是好的選擇。
受訪者特別提出修復工作過程中的督導是重要的,可協助促進者覺察自身的問題,
做好準備因應程序中的挑戰與危機,特別是調解的操作,如何避免落入家事或社區調解
時之概念和操作等。因此應建立修復工作之督導機制,以符目前促進員訓練不足、經驗
累積不易,且家暴案件具特殊性及複雜性的需求。
修復式正義的工作人員不應以志工職擔任,也不應以拉進許多專業人力就以為能辦
理好,重要的是他們對修復式正義的了解與認同,以及能受完整的訓練。受訪者表示目
前社工年輕化,社工也普遍對自我沒有信心,面對整個修復調解,其實訓練仍不足夠,
114
以致於目前要由社工擔任修復促進工作,仍有顧慮。受訪者亦表示心理諮商目前的訓練
仍以個別諮商為主,若要以調解概念,並加入多元人力合作模式之操作,心理專業執行
修復工作將出現困境。
受訪者強烈表示很多調解委員都非專業,也無法了解家庭動力,更是不了解家庭暴
力,或者也不懂諮商及心理動力等,因此以調解委員逕為修復工作者,其知能與經驗將
顯不足。
第九節 修復式正義的專業訓練
既然修復式正義之實施人員需一方面兼顧其精神及哲學意涵之彰顯,另一方面也須
完備修復程序之執行,因此其所需接受之專業訓練,應能支應修復工作執行的知識能力。
受訪者針對於修復式正義相關執行人力所需接受之專業訓練提出看法,研究者亦進一步
加入本國於各地實施修復式正義專業訓練之課程彙整,以受訪者問卷調查表(附件一)進
行調查,將受訪者之意見及統計分析整理,以下則以三部分說明專業人員應具備之知能
與學習準則、專業訓練內容領域及課程意見。
一、修復式正義專業人員的知能與學習準則
受訪者表示專業人員應具備「保持價值觀中立」、「了解權控關係」、「同理當事人的
心理狀態」、「家庭系統觀點的理解」、「修復訓練對於安全議題應重視」、「修復訓練不應
與心理諮商輔導混淆」、「修復訓練要能區辨修復與調解」、「司法專業訓練應為整體參與」
等知能與態度。
保持價值觀中立
受訪者認為修復促進者的價值觀要中立,不僅對婚姻家庭的體認和觀點,也對性別在婚
姻關係與角色之影響,有合適的態度和立場,才能在介入家庭問題時,能有妥適的處理。
他的價值一定要很中立,因為是不是有婚姻不盡然,可是他對家庭的體認是什麼,我覺得這件事情必須要
很清楚的去知道(M)
或是他覺得說這些事情其實你就是要兩照,應該要介入家庭去做…做處理,確實有些事在變,那我比較支
持你應該站在要介入…介入家庭來符合,而不是維持…維持著只是站在被害人的立場,如果是這樣的話就
會不妥適了。(N1)
了解權控關係
115
受訪者提出在雙方權力不對等的處境下,被害人在權控的關係中可能歷時多年,加害人
亦習以為常其高操控性,在進行修復方案時,修復促進者若不敏覺其權控關係特性,依
加害人意願及表現,強加復合之促進,將使被害人再次被操控。
安全和權力的關係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在一個安全權力不對等的或是對被害人權控的關係裡面,你要知道
你會不會被加害人操弄,因為我覺得我本來要教的是慎選評估加害者部分,因為如果你發現相對人是操弄
的,他也知道在復合體制下他才能生存,所以今天他跟被害人道歉的蜜月期,他也會跟評估者促進者產生
一種協調上的關係,他會利用這種良善關係達到他的目的。(M)
同理當事人的心理狀態
受訪者提出受害人因受暴力虐待而影響其身心及人格表現,也歷經暴力週期之一再循
環,對其作決定及判斷危險的能力常有損傷,以致影響其認知及表達,若修復程序中其
主體經驗未被同理,將無助於協助被害人修復其情感與關係。
我們不是為了修復而修復厚,那個程序的進行還是要去幫當事人看他的…他的狀態合不合,就是說社工應
該還有一個把關的機制在裡面,而不是說每個個案進來我都要問,阿你要…你要…你要講看看沒有。(N1)
而不是這樣,因為我覺得在…在這樣的…ㄜ…暴力循環裡面或是這樣的環境裡面,被害人我看到的蠻多被
害人都還是比較居於弱勢的姿態,那這個弱勢還來自於他自己本身沒有力量。(N1)
所看到一個面向,那他比較理解為什麼…為什麼有些人…就像有些人進來這個領域就說,阿她明明就可以
走,為什麼不要走,就是他不能理解,為什麼他就是擺脫不了那個暴力環境,那我覺得你進到體系裡面來,
你才能理解。(N1)
家庭系統觀點的理解
受訪者認為修復促進員應對家庭暴力的成因及家庭系統與關係動力有相當的理解,才能
適切及完整評估雙方。
那他對家庭暴力的原因、成因要很熟悉,他要很清楚的知道,其實我們那個家庭關係對系統當中所有人的
影響在哪裡。(M)
修復訓練對於安全議題應重視
受訪者在人身安全議題上表現高度關切,認為修復促進員的訓練應加入對被害者人身安
全控管的評估、方法及資源使用的學習,以確保修復方案的進行,不致引發受害者心理
或身體上的更大危機。
116
會擔心的是那個安全上的議題,我們怎麼去控管安全上的議題,也許如果說教育訓練裡面,告訴我們怎麼
去評估,更完整的評估,或者說控制那個東西,會比較安心。(G2)
如果說在甚麼樣的條件下會成為一個比較適切的選擇,我覺得兩造權力過度傾斜的時候,對於被害人顯示
公平,我覺得這樣的關係就不能貿然的進行,被害人可能要做一些輔導創傷的部份,加害人可能要做先行
介入的部份是處遇的部份,當兩造比較接近有接軌的可能性的時候,再來作程序我覺得是比較安全,再來
對被害人是比較公平的,因為有一些被害人聽到加害人的名字的時候已經批批欻(抖),她根本不知所措甚
至是發抖很多很多我們看到的,那你貿然要兩個人對話,對被害人來說是非常不公平的(D5)
那另外一些危險指標比如說他的暴力行為、頻率可能要納進來,讓這個修復式正義的執行者了解,他這個
家庭暴力的受害狀況,就是時間的長短、施暴的頻率、施暴的方式(I)
修復訓練不應與心理諮商輔導混淆
受訪者提出修復訓練應使課程內容與修復式正義實施之目的清楚連結,訓練的目的是栽
培哪種人才,訓練的結果是要做修復方案或諮商輔導,應有清楚的界定,免致混淆。
在○○部第一場訓練的部分,理論上是針對你想參與的都可以進來訓練,因為現在很多,大家都不清楚自
己的角色,都以為自己要擔任促進者,那其實有一些他被報出去的名字不是促進者,他是陪伴者,所以那
是一個混淆。(A1)
第二個混淆是在上那個課程的時候,下午講得是夫妻協談,是心理學的東西、是家事商談的內涵,所以大
家就變成說修復式正義第一場談的不是那個嗎?談什麼同理心、談什麼,那其實根本就不是修復式正義,
敘事療法裡面其實有一個部分,我們講復原力、講敘事、講修復式正義,他其實某一些東西是雷同的,那
心理師我們把他放在夫妻的部分談,有操作的意像在,那他那個內涵,那因為你是做促進、做調解的內涵
也不到那種程度,所以下午安排那堂課讓所有人更搞不清楚。(A1)
修復訓練要能區辨修復與調解
受訪者表示有關修復會議中的調解與現行制度中社區或家事調解之區辨,應有清楚的釐
清,並在訓練過程說明清楚,以避免以復合的概念進行修復方案,這訓練亦要針對司法
人員執行。
有多少法官根本沒有聽過這個,後來像○○部他們要推,就以為修復式司法就是和解、就是調解,這是最
典型的。有多少法官是根本就不知道,都沒有聽過這種東西,然後修復,這樣子就是修復了。可是當你去
了解那個內涵的時候,你會發現整個過程才是重點,其實到最後到底有沒有跟他道歉或是有沒有原諒這不
是重點,就是被害人他爽不爽這才是重點。(A1)
117
司法專業訓練應為整體參與
受訪者認為既然司法部門要推動修復式正義,應先讓所屬人員熟諳其精神意涵、推動之
目的與價值、修復程序之設計意義,以及相關實施的配套和資源,免得以績效壓力推促
被害人同意,因此司法專業訓練應以全體參訓為目標。
現在訓練去聽的,他們是主任檢察官,每一個派去主任檢察官也不太一樣,有些是以婦幼為主。我們現在
實際操作是所有檢察官都面臨案件分配,但有些檢察官會不理解那個內涵,就會跑去問那個婦幼的檢察
官,那個主檢每次都會說不要問我,我也說不清楚,我不知道怎麼跟你說,他確實不容易聽清楚的,所以
我覺得真的要做到就有魄力,一個一個地檢署就專門來上你們的課,你們檢察官就全部要到。不然他們就
我們地檢署有個方案你們參考看看,要去找誰?另一種是講了老半天聽不懂,我當事人就嚇得要死了,然
後就好好好就去了,被威嚇的。因為主檢就會很擔心說他們承擔業績的壓力,就會拜託檢察官,但是真的
不需要有壓力。(A4)
二、修復工作相關專業訓練
有關修復工作之相關訓練,受訪者提出「文化與性別」、「輔導與諮商技巧」、「相關的法
律知能」、「加害人與被害人服務實務」、等四項課程內容。
修復相關訓練須著重文化與性別部份
受訪者表示文化及性別議題之概念性的訓練,及多元文化下之性別現象對家庭關係及成
員角色之影響,皆須納入為訓練的內容。
其實修復促進員的部分,我個人覺得就不管是性別議題或是文化,這樣概念性的訓練我覺得都必須要加進
來;因為其實在實務上接觸到有關於一些相對人的部分阿,其實自己都會覺得很恐怖,那根本就不用說婦
女的那一塊;然後會講到文化的部分是因為其實像客家的部分,他們就是比較多會用家族的部分,但是有
一些聲音還是會被壓下去,就是比如說今天施暴者是男性,然後受暴者是女性的部分的話,那其實他們還
是父權比較為主的體制;所以其實往往的部分的話,女性都會在一個強迫下去接受這樣子的原諒跟道歉。
(F2)
具備輔導與諮商技巧
受訪者表示修復促進員應具備輔導與諮商的技巧、同理心、專注傾聽的能力等,讓當事
人能充分敘說真實的感受和受暴的過程,並能感受到修復促進員對其生命重要經驗的理
解和尊重。
118
那在這過程中,我覺得訴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歷程吼,那所以同理心、還有協談的技巧、還有傾聽的能力吼,
這些都很重要。(L)
那另外就是說那嗯真實的追求吼,那也許促進員沒有調查證據的權責啦吼,但是也要了解很多人對於傳統
司法的一個抱怨,或是二度傷害是因為,他所認知到的真實被扭曲了,那加害人有一些論述是在譴責被害
人,被害人的論述可能又過度的誇大,在這過程中,真實被扭曲了,所以我覺得就是說,對於一個真實的
重視吼,一個真相吼,有時候雖然不能調查證據。(L)
嗯,對!像你今天跟我講的,那是讓我有…觸到我,就是說我們不是只有拿專業的技巧,我們要用的是生
命的態度,那生命的態度跟專業的技巧老實說是相輔相成的。(K)
具備相關的法律知能
受訪者認為修復促進員需接受法律相關的訓練,熟悉刑事司法流程及司法相關的知能,
在修復實踐及操作較能平穩有效。
那另外就是說,那一些跟司法相關的知能吼,那也值得培育吼,那他必須知道這是司法流程他必須知道動
力。(L)
在法律知能,它有一些技術層面的東西,那這個也值得重視,那比方說哪一些刑事犯罪吼,它是告訴乃論,
那如果是告訴乃論,那再修復方案就又多了一個被害人可以撤回,這樣一個選項,哪一些是被害人不能撤
回的,那緩起訴、緩刑它有哪一些選項,那它適用的範圍是在哪一些罪,那這可能就是說有需要了解吼,
那在操作上會比較穩健一點。(L)
加害人與被害人服務實務經驗
受訪者提出若進行家暴案件之修復方案,修復促進員最好有被害人的輔導服務工作經
驗,及加害人的輔導處遇經驗,如此將對家庭暴力事件之本質與模式,及加害人與被害
人的心理社會歷程與行為特性較能正確的認知及詮釋。
如果這一塊的機制是要放在家暴這裡這一塊的話,那當然我會覺得他如果有被害人的輔導工作經驗,或是
相對人的輔導經驗,當然他不是一定…一定就是互斥,是說如果有這個或有這個其實也可以,因為會比較
有機會看到那個家庭的動力在暴力循環的這一塊。(N1)
很多個案的類型,那如果你有在這裡面工作過的經歷,那會讓你在做這個修復式正義這一塊,應該是會比
較妥適啦。所看到一個面向,那他比較理解為什麼…為什麼有些人…就像有些人進來這個領域就說,阿她
119
明明就可以走,為什麼不要走,就是他不能理解,為什麼他就是擺脫不了那個暴力環境,那我覺得你進到
體系裡面來,你才能理解。(N1)
三、受訪者問卷調查之意見及統計分析整理
本研究之受訪對象皆為長期投入於家庭暴力事件處遇服務及修復式正義研究與實踐
的學術或專業人員,參與訪談者計 60人,問卷回收 56份,遺漏值 4份,回收比率 93.3%。
問卷共分為四大部分,結果呈現如下(表八)。
基本資料統計為女性 78.6 %、年齡 40~49歲佔 46.4 %、職稱為「社工類」39.3 %、
學歷「碩士」39.3 %、服務於南區 44.6 %,為參與此調查之多數。
從第二部分開始至第四部分第一小題,均為複選題的形式,因此每一細項的選擇數
不以「人數」計,而是以「總數」計次,且母群體以 56名計算,故百分率相加會有大於
100% 之情形。
專業領域中,也以「社工」51.8 % 佔半數最高,其次為「犯罪學」21.4%、「法律」
19.6%,「其它」項有 2位提到其專業領域分別另有:「社會政策」和「宗教」。參與者之
專業領域年資以 10年以上佔 55.4 % 最多。在修復式正義及家暴防治的專業經驗中,前
三高依序為「家庭暴力被害人處遇」46.4 %、「家庭暴力防治政策」44.6 %、以及「修復
式司法實施」和「家暴加害人處遇」均為 39.3 %,另外有 4位提到另有專業經驗,分別
是:「家暴研究」、「家暴網絡訓練」、「兒少保護服務」以及「衝突管理與衝突轉型」。
在修復式正義或修復式司法制度之角色,為「學者(含研究者)」和「其它」均佔
33.9 % 並列最高,「其它」項之詳細內容為:「方案負責人員」4位,「本市尚未執行本
項工作方法」2位,其餘「目前未參與司法院的修復式方案」、「政策規劃」、「監督旁觀」、
「在調解時會帶著修復式的概念」、「學習中」和「轉介者」各有 1位,以及 7位勾選此
項但無作答。
對於實施修復式正義於家庭暴力事件之修復者培訓的必修課程中,以「衝突管理實
務(含協商與談判技術)」以及「家庭動力與家庭系統」均佔 89.3 % 並列最高,接著是
「家庭暴力本質、模式及影響」佔 87.5%,而「加害人心理動力」、「多元文化適應與尊
重」、「會談與評估技巧」皆為 82.1%,在「其它」項,建議必修課程還可參考以下:「性
別與權力」、「危險評估」、「民法親屬編(擇要)、刑法(與家暴、緩刑相關)」以及「倫
理」。此調查相當呼應本研究以深度訪談蒐集之專家學者對培訓課程之意見。
最後的「繼續教育課程的建議」為開放式作答,邀請參與者集思廣益,為不同面向
提出建議。因原始資料有許多課程名稱重覆,或意思相近者,將其歸納整理後以條列呈
現。
表八、受訪者基本資料及課程意見調查與統計結果(N=56)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項目別 人數 百分比% 項目別 人數 百分比%
120
性別 所屬機關或團體
男 12 21.4 % 教育機構 16 28.6%
女 44 78.6 % 民間組織 12 21.4 %
年齡 社會行政 14 25.9 %
無透露 1 1.8 % 醫療機構 4 7.1 %
20~29 1 1.8 % 司法 9 16.1 %
30~39 12 21.4 % 婚姻狀況
40~49 26 46.4 % 已婚 40 71.4 %
50~59 13 23.2 % 未婚 11 19.6%
60~69 3 5.4 % 離婚 4 7.1 %
學歷 再婚 1 1.9 %
學士 16 28.6 % 服務區域
碩士 22 39.3 % 北區 21 37.5 %
博士 18 32.1 % 中區 2 3.6 %
職稱 南區 25 46.3 %
社工 22 39.3 % 東區 1 1.8 %
心理 6 10.7 % 全國 7 12.5 %
學者 16 28.6 % 曾否擔任家事調解員
律師 2 3.6 % 是 15 26.8 %
醫師 1 1.8 % 否 41 73.2 %
司法人員 9 16.1 %
第二部分:專業領域
項目別 總數 百分比% 項目別 總數 百分比%
專業領域 在修復式正義及家暴防治的專業經驗
法律 11 19.6 % 家庭暴力防治政策 25 44.6 %
心理 5 8.9 % 修復式正義研究 17 30.4 %
社工 29 51.8 % 法律議題 9 16.1 %
醫療 3 5.4 % 修復式司法實施 22 39.3 %
教育 6 10.7 % 家事調解 16 28.6 %
犯罪學 12 21.4 % 家庭暴力被害人處遇 26 46.4 %
其它 2 3.6 % 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 22 39.3 %
專業領域年資 其他 4 7.4 %
1年以下 5 8.9 %
1~3年 12 21.4 %
4~6年 12 21.4 %
7~9年 9 16.1 %
121
10年以上 31 55.4 %
第三部分:您在修復式正義或修復式司法制度之角色是
項目別 總數 百分比% 項目別 總數 百分比%
學者/研究者 19 33.9 % 支持者 5 8.9 %
專案管理員 5 8.9 % 督導 3 5.4 %
修復促進者 10 17.9 % 其它 19 33.9%
第四部分:您對實施修復式正義於家庭暴力事件之修復者培訓課程之意見是:
一、你覺得現階段實施之課程哪些適合做為必修課程為必修?
項目別 總數 百分比% 項目別 總數 百分比%
民刑事訴訟程序介紹 36 64.3 % 多元文化適應與尊重 46 82.1 %
檢察官在家暴案件上的
處理流程
34 60.7 % 家庭動力與家庭系統 50 89.3 %
觀護人如何與加害人互
動與緩起訴制度介紹
31 55.4 % 家庭暴力本質、模式及
影響
49 87.5 %
衝突管理實務(含協商
與談判技術)
50 89.3 % 家庭溝通 41 73.2 %
精神疾病與診斷 25 44.6 % 表達能力訓練 28 50.0 %
加害人心理動力 46 82.1 % 會議主持 38 67.9 %
認識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45 80.4 % 會談與評估技巧 46 82.1 %
失落者的悲傷歷程 31 55.4 % 其他(建議) 6 10.7 %
二、請提出修復促進者繼續教育課程的建議(請提課程名稱)
面向 建議課程
修復式正
義之概念
與實務
1.修復式正義之理論、模式、實務發展、成效以及困境之解決
2.各國修復式正義的理論、發展及成效之比較
3.修復之對話平台的建構
4.修復式正義個案之追蹤
5.修復式正義與日常生活衝突處理
6.修復式正義應用在親密關係暴力之導論與操作概念
7.修復式正義運用於家暴事件之理念及技術
8.修復提問技巧
9.修復會議主持工作坊
10.學習多種會議支持模式(VOM、和平圈、家庭會議等)
11.定期個案研討
12.修復會議實地觀摩
13.促進者的角色定位及自我察覺
122
家庭衝突
事件相關
法律
1.民法親屬編(擇要,如監護、繼承、扶養等)
2.刑法(與家暴、遺棄、傷害、緩刑等相關部分)
3.外籍配偶相關法律課程(包括居留、國籍等)
4.家事事件法之理論與運作
5.家暴防治法之內涵與相關流程
6.保護令程序與功用及違反後的相關法律
7.人權相關課程
8.少年事件處理法之理論與運作
協商談判
相關技術
1.協商會談與談判技巧
2.建立關係技巧
3.正向心理學
4.情緒察覺與同理
5.情緒安撫與衝突化解
6.會議程序及共識建立
7.衝突/危機調解技巧與實務
8.修復式取向之調解
9.應對衝突之新觀念(分析、解決、預防衝突)
家庭暴力
理論及實
務
1.暴力的定義、成因、態樣以及案例分享
2.家庭暴力本質、模式及影響
3.親密關係危險評估指標辨識
4.暴力對婦女及兒童的影響
5.不法侵害之定義與內涵
6.高度權控關係之處置與修復式正義
7.家庭衝突現象與處理
8.女性主義觀點下之親密關係暴力防治
文化與性
別敏感度
1.社會文化的變遷與改變
2.儒家文化與華人性格
3.本土文化與多元文化(閩.客.外省.原住民.新住民等)之介紹與差異
4.文化、性別偏見之覺察與省思
5.多元文化與諮商
6.性別敏感度訓練
7.性別平等的實踐(性別主流化)
8.性別與壓迫
9.新移民在臺灣文化適應的困境: 跨國婚姻衝突樣貌及新移民婚姻與家
庭
10.父權主義與女性主義
11.性別與暴力
123
12.權力與控制
家庭系統
評估
1.家庭中權力結構與關係
2.家庭動力觀點下的婚姻暴力處置
3.親密關係衝突歷程與家庭動力
4.婆媳問題合併親密關係暴力之關係動力
5.暴力家庭系統與家庭規則
6.家庭的多元面貌
7.阻力與助力
8.重要他人
認識加害
者/受害
者
1.犯罪學理論
2.變態心理學
3.加害者之特質、權控、處遇、心理動力與臨床表徵
4.失落與悲傷歷程
5.被害人創傷及療癒
6.依附關係與自我認同
7.目睹暴力兒童之心理歷程與處遇
8.心理衡鑑之運用
9.認識物質濫用
個案轉向
措施之資
源
1.公部門及各民間團體對家暴案件之服務項目、內容
2.社會資源和社會福利法規之介紹、運用、整合與轉介
3.家暴處理流程及網絡資源
4.被害者支援網絡服務以及認識法律扶助/犯罪被害人保護制度
5.後續追蹤
6.心理諮商(夫妻諮商、兒童諮商、精神治療)運用於修復式司法
7.壓力調適與生活重建
8.就業服務與福利資源介紹
小結
有關修復工作之相關訓練,受訪者提出「文化與性別」、「輔導與諮商技巧」、「相關
的法律知能」、「加害人與被害人服務實務」、等四項課程領域內容。受訪者表示文化及性
別議題之概念性的訓練,及多元文化下之性別現象對家庭關係及成員角色之影響,皆須
納入為訓練的內容。若能具備輔導與諮商的技巧、同理心、專注傾聽的能力等,讓當事
人能充分敘說真實的感受和受暴的過程,並能感受到修復促進員對其生命重要經驗的理
解和尊重。且主張促進員需接受法律相關的訓練,熟悉刑事司法流程及司法相關的知能,
在修復時建及操作上會較為平穩有效。並建議若進行家暴案件之修復方案,修復促進員
最好有被害人的輔導服務工作經驗,或是加害人的輔導處遇經驗,如此將對家庭暴力事
124
件之本質與模式,及加害人與被害人的心理社會歷程與行為特性較能正確的認知及詮釋。
有關專業人員應具備之知能與態度,「保持價值觀中立」、「了解權控關係」、「同理當
事人的心理狀態」、「家庭系統觀點的理解」、「修復訓練對於安全議題應重視」、「修復訓
練不應與心理諮商輔導混淆」、「修復訓練要能區辨修復與調解」、「司法專業訓練應為整
體參與」等為受訪者之意見。
受訪者提出在雙方權力不對等的處境下,被害人在權控的關係中可能歷時多年,加
害人亦習以為常其高操控性,在進行修復方案時,修復促進者若不敏覺其權控關係特性,
依加害人意願及表現,強加復合之促進,將使被害人再次被操控。且受害人因受暴力虐
待而影響其身心及人格表現,也歷經暴力週期之一再循環,對其作決定及判斷危險的能
力常有損傷,以致影響其認知及表達,若修復程序中其主體經驗未被同理,將無助於協
助被害人修復其情感與關係。因而修復促進員應對家庭暴力的成因及家庭系統與關係動
力有相當的理解,才能適切及完整評估雙方。
受訪者在人身安全議題上表現高度關切,認為修復促進員的訓練應加入對被害者人
身安全控管的評估、方法及資源使用的學習,以確保修復方案的進行,不致引發受害者
心理或身體上的更大危機。
有關修復訓練應使課程內容與修復式正義實施之目的清楚連結,訓練的目的是栽培哪
種人才,訓練的結果是要做修復方案或諮商輔導,應有清楚的界定,免致混淆。有關修
復會議中的調解與現行制度中社區或家事調解之區辨,應有清楚的釐清,並在訓練過程
說明清楚,以避免以復合的概念進行修復方案。且既是司法部門有心推動修復式正義司
法革新,應先讓所屬人員熟諳其精神意涵、推動之目的與價值、修復程序之設計意義,
以及相關實施的配套和資源,免得以績效壓力推促被害人同意,因此司法專業訓練應以
全體參訓為目標。
125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計畫之目的係探討修復式正義應用於家庭暴力事件之本土性意見,並嘗試發展未
來設若我國推動修復式正義應用於家庭暴力事件之相關作業流程與相關配套措施及具體
政策建議。本計畫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採取多元的,包括以文獻探討、個人深度訪談、焦
點團體訪談,將所得的資料加以系統性的整理,再輔以漸進式焦點訪談及調查問卷,採
用三角交叉檢驗法,以強化研究的可信度。共計訪談六十名(七十二人次)學者專家,亦
有五十六名受訪者填寫調查問卷,經詮釋與整理其意見,歸納研究之發現分為: 本土之
修復式正義原則與工作模式、對修復式正義之迷思、修復式正義與權控議題、修復式正
義與非政府組織、個案評估與類別、修復式正義的執行、相關成效評估指標、工作團隊
成員組織與角色分工及專業人員之資格與訓練等九個議題,並分述如下。
壹、本土之修復式正義原則與工作模式
華人社會相當重視家族社會系統,強化社會心理學「和諧」與「面子」之文化現象,
因此是否文化規範及文化習俗慣例能涵容修復式正義之理念及工作架構於文化脈絡中,
並在執行修復式正義時,以其文化調適力提升犯罪預防及被害人保護之目的,成為重要
的關注。以下七項重點,發現文化及民族性確有其影響及意義,因此本土之修復式正義
實施之原則或模式的建構須重視下列因素。
一、重視華人文化與民族性的影響
(一)修復式正義對於台灣親密關係衝突現象及其解決具有正向意義。
(二)本國處遇親密關係暴力的低度強制性使得修復式正義有其需要。
(三)司法對於親密關係處遇的不足可以由修復式正義處理。
(四)華人社會強化「和諧」之文化現象,若被害人遵從和諧的社會期望,卻
未必有利於其自我保護之處境。
(五)父權體制下對男性自尊的推崇,及文化視角下維護面子的民族性格,雖
修復式正義實施中以運用恥感而提升修正行為的勇氣相呼應,但以加
害者的臨床表徵,卻常是為了重視面子而致惱羞成怒。
(六)華人社會家族社會系統的影響深遠,因此運用家庭成員之參與,須衡量
其家庭系統運作與心理動力現象,避免其過度涉入,助力反成阻力。
二、修復式正義的精神
修復式正義實施於家庭暴力事件之精神意涵及核心信念,是協助被害人、加害人及
雙方家庭、社區進行充分的對話,讓當事人之間有機會充分的陳述與傾聽、進一步澄清
事實、了解對方的感受、提出對犯罪事件的疑問並獲得解答,因此提出以下實施上的關
126
注要點。
(一)著重於當事人的關係
(二)當事人的自我察覺與關係修復
(三)注重當事人的意願
(四)關注當事人的關係位置
(五)提升被害人的積極角色
(六)關照加害人的內在困境
(七)關注當事人意見之充分表達
三、修復式正義是相對人處遇的一環
實施修復會議能讓加害者傾聽及覺知到自己行為造成被害者之身心影響,因此若修
復式正義納入加害人的處遇意涵,可促發改變其認知及終止暴力行為,其重點如下。
(一)修復工作可促發相對人因了解被害人的傷害而改變其暴力行為
(二)修復工作以相對人為對象可積極終止暴力
(三)是被害人參與的相對人處遇
四、修復式正義是被害人保護的一環
修復式正義是被害人保護的一種處遇服務方式,可協助被害人處理現行司法系統之
不足,並對被害人賦權以作出對未來的選擇,其意見如下。
(一)修復工作可以協助被害人處理現行司法系統無法處理的親密關係衝突
(二)修復工作在自願的情況下讓被害人更有力量
(三)修復工作提供被害人有不同選擇
(四)修復工作關注的重點是被害人賦權
五、尊重當事人的期待與意願
修復式正義應關注及尊重當事人的期待與意願,特別是被害人對於關係改善方向的
主觀意願應積極了解及接納,避免以法律化及劃一性之服務替代被害者的選擇,其重點
如下。
(一)了解被害人對於關係改善方向的主觀意願
(二)接納被害人對於關係改善方向的主觀意願
六、不同修復式正義的工作型式
有關本國修復式正義之實施模式,受訪者提出原則性之建議,其中包括權力關係之
平衡、在地文化之考量及修復過程社區及家庭介入之評估等議題如下所述。
(一)考量修復過程中的權力關係平衡而應使用不同的修復形式
(二)應積極發展適合本土的介入模式 (三)現行鄉鎮區公所調解委員會是社區的、可近性的,可在既有的基礎上再
127
讓它發芽成長。
(四)在家庭協商會議加入家庭成員來共同關切與支持加害者的改變,為可考
慮之模式。
七、修復工作作為親密關係衝突工作的平台
修復式正義提供一個對話的平台,在修復會議中權力關係是對等的,帶給當事人有
一些不同解決問題的方法,讓他們在一個安全的環境裡面可以來進行對話,而修復就是
一個對話的歷程,以作為親密關係衝突工作的平台。
貳、對修復式正義的迷思
針對修復式正義常見的迷思,提出討論如下:
一、修復與調解之間的糾葛: 修復促進與調解的角色應是分立,若將修復會議流
於充滿主觀式、道德式的勸說,將會誤解調解成立就是一個成效。
二、尋求被害人的原諒: 寬恕或和解不是修復式正義的首要原則或重點,修復
式正義提供了一個背景,成為參與者的一種自主性的選擇,因此不應該有
選擇原諒或尋求和解的壓力。
三、修復被認為是一種復合: 修復工作的目的不是復合(reconciliation),在實
務工作上雙方也未必有意願復合,在修復的價值理念強調的是參與、醫治、
尊重、修補、賦權、負責、復歸、對遇、及道歉,其中操作性的價值是促
進積極負責、修補傷害、以及衝突解決等,其關係修復指的是和平相處或合
作解決問題,那可能是繼續共處也可能是好好分手,這是需釐清的。
四、修復式正義與家事調解的定位與差異性: 修復式正義不僅是個調解,他是一
個工作方法,是一種修復式的精神理念,是一套發展對被害人、對加害人、
對社區、對群體之修復式的改變,因此評估者和促進者個人價值須能符合此
工作的信念。在我國修復促進者跟社區或家事調解員的角色應是分明的,其
調解目的和操作程序也不一樣,不該混淆。
叄、修復式正義與權控
修復式正義針對權控關係表現了高度的關切,認為被害者的人身安全是任何工作模
式的絕對底線,因此對於處理關係之間的權控議題應非常小心,包括處理權力與動力的
特定機制,以及透過雙方心理與家庭歷史,了解與處遇權控的態度與行為的成因,其重
點如下。
(一)親密關係的權控本質不易經由修復處理
(二)社會文化的權控處境對女性有不利影響
(三)執行修復的專業系統及人員本身的權控本質須被檢視
(四)權力的關注應包括修復過程中的氛圍
128
(五)修復歷程中的互動可能會不利處於權控關係下的弱勢者
(六)親密關係暴力的本質不只是權控,親密關係暴力防治的最終目的,是終
止暴力,有關阻礙人身安全的議題仍須被重視。
肆、修復式正義與非政府組織
當刑事司法案件,由非政府組織在系統外執行修復性工作時,其定位及優勢應是結
合資源,以家庭、社區為服務場域,為當事人及其家屬創造支持與接納的社會環境。但
非政府組織於公權力行使及專業權力範圍,能否因應修復司法之目的而達成具成效之執
行,有以下之意見:
一、認為非政府組織為適合執行修復式正義的機構
既然修復思維是一種哲學,也需以較為中立客觀之角度促進對話平台,因此由非政
府部門來推動與施行,有其優勢,其意見如下:
(一)修復式正義適合由非政府組織來推動
(二)由非政府組織執行,民眾接受度較高
二、非政府組織介入的時點
到底非政府組織可介入的時機為何?受訪者提出當司法程序完結時,是可行的且有極
大的獨立施展空間。若在司法偵審仍進行中,司法仍具主導性,則非政府組織之介入,
則須與司法連結及合作。
三、非政府政府組織介入的限制
由於家庭暴力行為乃為犯罪事件,具備其司法性之處理需求,若由非司法部門及非
司法專業人力來處理違法行為,其妥適性及效能性亦有疑慮,以現行體制非政府組織參
與此工作之限制,意見如下:
(一)經費來源的受限: 以台灣民間團體呈現募款不易之困境,且對政府經費
補助之依賴,其獨立性、自主性與公正性,常需因財政的拮据及經費來
源之顧慮,而被牽制。
(二)缺乏監導系統:修復式正義之實施仍處摸索試探階段,缺乏足以監督輔
導之體系。
(三)服務內涵的之局限性:要完成犯罪修復的司法性及關係修復的處遇性,
以及實質補償所需的協議性,目前非政府組織仍有所不足。
(四)公民意識不顯著: 台灣社會歷經移民、殖民的歷史,雖法治社會的建
構,在民主運動及經濟發展的努力下,已在法制面具備架構,但公民
意識與素質仍尚待建立。
(五)家暴中心執行修復工作的困境: 目前保護性社工的工作即環繞在被害
者的需求上,加害者之評估處遇則為另一套機制,無法合軌進行。
129
(六)社工執行修復工作因社政的非強制性而常被拒絕,不僅不易獲得加害人
的信任,且社工在不具司法的強制性基礎下,常被加害者拒絕。
四、由司法啟動修復會不利女性當時的狀態
一般人民咸少接觸司法系統,唯在衝突無法解決或長期的壓迫造成損害,才求助於
司法。而家庭暴力之發生於家庭這私領域,在法不入家門的古訓,受害婦女的求助已有
多方之掙扎,當求助於司法則易被污名化,因此在面對司法過程,對受害者而言不啻是
一段煎熬的歷程,因此提出以下二點看法:
(一)司法的權控本質不利被害人處境
(二)處於權控關係中弱勢的女性不易區辨司法體制中的修復與避免暴力
五、司法體系與修復式正義
司法體系將修復式正義視為革新司法的制度,對於以司法為基礎的正義論,及目前
台灣施行的模式是局限在刑事系統中,以及司法長期與人民的生活疏離,與社區的資源
連繫不足,且司法執行之落實度仍被人民質疑的情況,作出以下之討論:
(一)贊成以司法基礎出發建立修復式正義架構
(二)侷限於刑事案件的不足
(三)司法體系與網絡聯繫互動不足
(四)司法的落實度不佳
六、傳統司法與修復式司法的歧見
傳統司法及修復式司法在哲學、信念基礎及實施程序上,有相當之分歧,反映出以
下的看法:
(一)司法系統過度與不切實際期待: 在告知申請人及當事人的資訊中增強
了他們不切實際的期待,在轉介給非政府部門執行時,亦有過度之要求。
(二)司法人員對於修復式司法的誤解/誤用: 認未能針對當事人受暴力攻擊
之處境深入調查,未能清楚修復式正義的意涵與處理程序。
(三)制度彈性與制式的差異: 傳統刑事司法制度是依照刑事訴訟法所執行
之的流程,而修復式司法則能提供更有彈性的選擇,更具人性化的考量。
(四)司法系統的理解與看見: 傳統司法系統以違法行為之偵查與裁判為著
眼點,修復式司法期待回到對人的整體,包括看見家庭、關係及社區
的意義。
七、非政府組織介入的重要提醒
修復式正義將情感與關係之修復視為要務,雖在受害者保護之基礎下服務,也須因
應不同的需求創造出多元的服務模式。非政府組織參與修復式正義實施應有的態度如下:
(一)採取合作而非競爭關係: 非政府組織受委託辦理修復式正義之施行,需
130
要建立合作關係,並避免因為資源多寡產生不必要之競爭與衝突,若能
以專業分工逐步構建資源網絡,將有助於修復正義之實施及轉向工作的
完備。
(二)非營利系統間的相互合作: 非營利系統之間有許多專業分工,若能彼此
配搭合作,統合綜效,將能一起發展修復正義之整合性工作。
(三)採取整合性的工作方式,非偏頗任一方:大部分家庭暴力服務組織都有
其明確宗旨,視加害人與受害人之服務是分立的專業,因此也有各自之
工作價值和模式,若非政府專業組織執行修復方案,實需敏覺於原服務
模式之限制,並採取整合性的工作方式,照顧雙方復歸社會的需求。
伍、修復式正義的個案評估與類別
修復式正義之實施首重評估工作,評估的目的在於為修復會議作出篩選和準備,因
此個案之評估原則及標準,成為能否執行修復工作的基準。以下則針對個案評估之原則、
需求、問題及能否進入修復方案的類別因素提出意見。
一、修復式正義個案之評估原則
實施修復方案前應針對申請人及當事人進行評估,評估需針對其安全性(危險評
估)、互動溝通狀況、暴力成因及模式、物質濫用程度等,認為應有適當的篩選與準備,
以符當事人獲修復之效。原則如下:
(一)釐清關係的危險程度以評估其修復式正義介入的適切性: 應重視執行
親密關係危險評估的重要性,以作為修復式正義介入之適切性與否的指
標。
(二)雙方溝通型態: 如果是低度危險又源於溝通問題或溝通型態差異的個
案,應可考慮進行修復。
(三)權控關係/遇境施暴: 高危機個案且有權控問題應不適合進入修復會
議,遇境施暴類型則應重視雙方在對等的情境與條件下才適用。
(四)評估加害人的暴力程度、情緒控制能力、藥物濫用情形、酒癮狀況,嚴
重者不宜進入修復調解。
二、修復式正義案件的評估需求
修復式正義案件之評估在連繫階段及修復階段皆有其需求,評估上須針對其之前的
家庭關係與生活脈絡加以了解,對整體事件的動態性歷程也須掌握。
三、修復式正義案件的評估問題
在評估家庭暴力案件是否進入修復式正義方案時,準確評估的壓力及長期糾葛與衝
突關係下的複雜動力,使得評估工作常出現難題如下:。
(一)暴力與衝突關係之修復評估因其長期及無效之處理歷程而更困難不易
131
(二)個案的衝突處境比其暴力案件更為複雜
(三)輕微的親密關係衝突可能會有不易評估的複雜內容
(四)仍共同生活的案件不易評估
(五)案件評估不宜僅單次就完成
(六)案件的發展及意義的流動使得評估不易
四、女性被害人評估的困境
被害者在受暴歷程產生身心社會的改變,其源於女性經驗及創傷影響而反應在自我
概念、表達方式、求助行為及認知模式等之不易了解,在評估工作易生困境。對評估者
而言困境如下:
(一)缺乏對於親密關係當事人特質與行為模式的充分瞭解
(二)被害人因情境或創傷因素而未能提供完整情況
(三)親密關係暴力具有再犯性的可能使得評估困難度高
五、男性加害人評估的困境
男性加害人常因缺乏自我揭露能力,導致評估上的困難。傳統文化所形塑之男性於自
我概念、表達方式、求助行為及性別認知上常因壓抑及自尊需求,造成低度的自我揭露,
不但評估困難,也可能修復會議之參與及發言也將受限。
六、當前加害人工作不足對於修復工作的影響
當前針對加害人服務處遇工作之不足,對於修復工作之啟動與執行造成影響,若以
下三項因素未加克服,則不利修復方案的推動。
(一)因缺乏加害人服務的配套工作以致難以進行修復
(二)缺乏加害人的有效約制機制以致進行修復困難
(三)缺乏對於加害人的瞭解而不利修復的進行
七、目前修復工作中評估個案的問題
在評估個案的問題時,未能連結既有家暴網絡服務資源,以及未建立完整的評估指
標,造成目前家暴服務體系的疑慮,並提出二項亟待解決之問題。
(一)僅有修復工作計畫但缺乏整體性的個案修復評估工作
(二)修復個案評估的指標建立不足
八、合宜進入修復式正義的個案類別
有關合宜進入修復式正義的個案類別,發現以加害者之態度、暴力危險度、暴力關
係型態、家庭類型、家庭衝突成因、修復意願、未來關係發展等向度之討論是重要方向。
本研究發現具備以下九項因素,可考慮進入修復方案。
(一)加害人具真誠且負責的態度
(二)暴力屬低度危險且非操控性強者
132
(三)當事人(被害人)對於關係改善的方向具備意願
(四)屬家庭衝突議題
(五)雙方權控關係相當者
(六)因教養子女的衝突
(七)互為加害人者
(八)初期暴力個案
(九)有血緣的家庭關係成員之衝突事件
九、不適合進入修復式正義的個案類別
有關不適合進入修復式正義的個案類別,受訪者表示高危機、嚴重暴力、嚴重精神
疾患、長期施虐者應排除進入修復式正義方案。其排除適用之類別如下:
(一)嚴重精神疾患者
(二)長期施虐者
(三)具權控關係者
(四)高危機之嚴重暴力者
陸、修復式正義的執行
修復式正義之執行應重視網絡準備、當事人準備、針對受害人及加害人的介入工作、
當事人處境之了解、修復會議的適切時機及啟動點之選擇、修復工作之費時、評估與促
進並行、進行修復會談及修復與社區工作等準備程序及執行工作要項,分述如下。
一、修復式正義工作的網絡準備
修復式正義工作的網絡準備需規劃行政成本,並提早加入跨網絡與多網絡參與修復
之評估與執行工作。
二、修復的當事人準備工作
修復工作之預備階段,應讓當事人充分了解修復方案的意義及流程等相關資訊,去
除迷思,得到力量去自由選擇。對於修復會議的目的及當事人的意願和權利,應有充分
的尊重及詳盡的說明。要評估他們彼此之間權力行使的狀態,讓他們以自由的意願、在
雙方都同意下進行,因此須給予充分的考慮時間。預備階段之四大要點如下:
(一)提供資訊尊重其選擇
(二)詳盡說明修復式會議
(三)了解雙方的權力狀態
(四)給予充分的考慮時間
三、針對受害者的介入工作
修復會議的促進員應讓被害人找到力量,專注於觀察被害人的權力及自主性,其四
項介入工作重點如下:
133
(一)讓被害人得著敘說創傷故事的力量
(二)讓修復成為較長期且細緻的微調歷程
(三)尋求中立者角色成為修復工作的關鍵人物
(四)以賦權增能讓被害人自由地決定其參與
四、針對加害人的介入工作
讓加害人的家人或朋友成為修復會議的參與者,使他的支持系統成為安全的監督
者,並能提供他們的觀點,增加修復的力量。
五、修復式正義工作中的當事人處境
在修復程序中應高度注意被害者之家庭及社會脈絡及身心社會反應,要點如下:
(一)修復過程中親密關係暴力的被害者人身安全問題
(二)修復會議中應注意面對加害人正向改變時被害人受創經驗再現之反應
(三)修復會議中面對加害人的原諒可能會對於受虐婦女造成不利
(四)修復促進與後續司法作為應為雙軌模式,避免加害人誤用修復式正義規
避其責。
六、關係修復會議介入的適切時機
在求助前期或司法介入的任何節點都可為修復會議介入的適切時機,但也都
有其利弊,因此重點不在何時進入修復而是其評估及配套措施之情況是否能有效達成修
復的目的。但咸認偵查階段不適合,並提醒修復的時機應考慮長期受虐被害人當時的身
心狀況,及加害人對於完成修復協議將在司法裁判上之扭曲的期待問題。
七、修復式正義工作之啟動
啟動修復工作時,應重視之兩項重要之事項如下:
(一)誰來向當事人說明: 向當事人說明修復式正義之內涵,是重要的過程,但若由檢
察官來告知及詢問,容易因其態度和角色,使當事人感受到壓力,因此若啟動修復
關係的方案, 是由被害者信任的服務單位來說明,較能讓被害人放心。
(二)以被害人與加害人服務的平衡作為修復起點:須對加害人及被害人之服務提供有
平衡服務的基礎。
八、修復工作之費時是必要的體認
修復式正義在評估及促進雙方的意願及共識上,須體認其費時費力是必然的,須體
認以下三點:
(一)修復工作的進行需要花費時間來進行
(二)促進會議要有充分的時間
(三)應重視會前會甚於修復會議之執行
134
九、修復的評估與促進工作
修復式正義實施之會前預備會議階段,包含評估及促進之工作本質,在執行上需注意
之意見如下:
(一) 評估者跟促進者的切割使得訊息傳遞不足而不利修復促進: 每一階段
之評估都應確實,並應有轉銜上的連結,以完成整體評估。
(二) 評估者與促進者同最好為一人,在了解案情及雙方處境,以及促進彼此
瞭解上較為有利。
十、進行修復會談
當進行修復會談時宜留意下述四種現象:
(一)當事人很難聚焦在此傷害事件,通常將關係中各項議題連結傾吐,使修
復會談議題不易聚焦。
(二)加害人與被害人在修復會談中的權力互動議題。
(三)修復會談中應促發當事人覺得有能力及權力做決定,當事人的意願
與意見交集的方式及時間,應被充分尊重。
(四)催化加害人在會談中面對修復主題,積極說明及澄清。
十一、修復與社區工作
社區及家庭生活的復歸,需有修復連結的機制,並應持續追蹤其落實與成效。
柒、修復式正義的成效評估
有關成效之評估,常是整體工作價值評定之所在,而評估指標是否能反映成效,或
成效之界定及範圍為何,都需有更廣泛的討論,以下有兩點與成效相關之討論:
一、修復之後的親密關係暴力防治成效
有關如何評估修復會議後的親密關係暴力防治成效,以了解修復之落實,應注意
下列建議,但本研究發現修復成效不應只以有無暴力再犯做為成效認定,也應看待修復
工作的啟動可帶給當事人反思,而無需僅著重有無達到修復協議等。建議須留意之現象
及須發展之機制如下:
(一)以開放架構建構成效評估
(二)以覺察與觀察做為關係修復成效的評估方式
(三)對於修復之後暴力再犯的發生不確定
(四)修復之後的處境脈絡未變容易影響修復成效
(五)親密關係暴力本質未能在修復關係中充分揭露以致影響修復成效
(六)修復工作的啟動可帶給當事人反思而無需僅著重有無達到修復
(七)建立促使相對人履行其承諾的機制
(八)建立修復後的追蹤機制以了解修復成效
135
(九)修復成效不應只以有無暴力再犯做為成效認定
(十)建立修復後的落實機制
二、修復工作的成效評估
有關修復工作的成效評估內容,
(一)情緒宣洩:應以被害人的感受為成效的指標,即被害人的負面情感獲得
釋放。
(二)同理能力的增加:成效指標中應讓加害者了解被害人在被害過程中的
痛苦、悲傷的情緒,增加其同理的能力。
(三)關係改善:是否獲得新的學習,關係是否逐步在改善。
(四)面對與承認的態度:透過修復歷程提升被害者面對真相及現實的機會,
以了解加害人的心態與承認的態度,能在抉擇上做出準備。
(五)當事人重新得力:是否當事人能透過這個修復歷程重新得力。
(六)當事人之間產生對話的可能:讓雙方產生對話,產生新的了解。
捌、修復式正義的執行人員
受訪者提出有關修復促進者、輔助促進者、陪伴者、督導、修復工作執行人員的體
認及建議等五種執行修復工作之角色、任務與原則加以探討。
一、修復促進者
修復促進者為修復促進程序中重要的人物,不僅可能須擔負評估責任,也是修復會議
之主持人,要致力於營造讓被害者與加害者安心對話的環境。因此修復促進者也是對話
促進者,其應具備之條件如下:
(一)修復促進者應具專業性: 不宜由志工的角色來扮演,若能由諮商輔導及法律的專
業背景來成為雙搭配,應是最佳的組合。
(二)修復促進者應具有平權及性別概念並且熟悉家庭暴力
(三)修復促進者要有充分加害人及被害人的工作經驗
(四)促進者能充分了解親密關係的本質及被害人在家暴關係中之心理社會處境
(五)促進者應具備人際衝突處理及協商談判能力,也須了解華人文化對衝突處理的性
格與方法,以增加處理效能。
(六)促進者的協商談判及協調溝通的能力是處理衝突的重要知能,並應注意文化及性
別因素的干擾。
(七)促進者的信念特質將影響其處遇的目標
(八)宜依案件特性考量促進者的性別
二、輔助促進者的角色
若在修復會議時增加輔助促進者的角色,特別是律師專業者的投入,是相當具助益
136
性。輔助促進者可提供法律諮詢並協助維持會議程序。
三、陪伴者
在修復會議實施中,可選取適當人選成為修復陪伴者(支持者),以協助會議歷程及
協議後之工作落實,其角色如下:
(一)個案管理社工合宜擔任被害人的陪伴者
(二)家族或社區成員可做為修復工作落實的監督者
(三)以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或更生保護協會人員做為被害人及加害人的陪
伴者或個管者
四、修復式正義工作的督導需求
在台灣實施修復方案之初期,修復促進過程中的督導角色不可或缺,以提供實施單
位及修復促進團隊之諮詢與督導實務,而積極建立修復工作督導培訓及督導機制的需要
性應被重視。
(一)修復工作過程中的督導:督導可協助促進者覺察自身的問題,做好準備
以因應程序中的挑戰與危機,特別是如何避免 VOM之調解落入家事調解
或社區調解之概念和操作。
(二)建立修復工作督導機制的需要性:應建立修復工作之督導機制,以符目
前促進員訓練不足、經驗累積不易,且家暴案件具特殊性及複雜性的需
求。
五、修復工作執行人員的體認及建議
因應修復工作的專業性,修復式正義的執行人員應有的體認及建議如下:
(一)修復程序具高度專業性
(二)修復式正義的工作人員不應以志工職擔任
(三)因為社工對於當事人的態度差異而非社工均合宜
(四)社工與當事人的互動及工作角色致使修復工作產生資源過度使用之困
境,因此須有因應之準備。
(五)社工執行修復工作因經驗及服務屬性常產生困境
(六)心理專業執行修復調解工作因原屬獨立性及個別化之經驗而常有困境
(七)調解委員逕為修復促進工作,其知能與經驗顯然不足
玖、修復式正義的專業訓練
既然修復式正義之實施人員需一方面兼顧其精神及哲學意涵之彰顯,另一方面也須
完備修復程序之執行,因此其所需接受之專業訓練,應能支應修復工作執行的知識能力,
以下則以三部分說明專業人員應具備之知能與學習準則、專業訓練內容領域及課程建議
等。
137
一、專業人員應具備之知能與學習準則
修復促進工作專業人員之知能與態度,將直接影響修復程序之實施及成效,須維持
以下所提醒之要點:
(一)保持價值觀中立:應對婚姻家庭的體認和觀點,對性別在婚姻關係與角色之影
響,有合適的態度和立場,方能在介入家庭問題時,有妥適的處理。
(二)了解權控關係:在雙方權力不對等的處境下進行修復方案時,修復促進者若不敏
覺其權控關係特性,依加害人意願及表現,強加復合之促進,將使被害人再次
被操控。
(三)同理當事人的心理狀態: 受害人因受暴力虐待而影響其身心及人格表現,以致影
響其認知及表達,若修復程序中其主體經驗未被同理,將無助於協助被害人修
復其情感與關係。
(四)家庭系統觀點的理解: 應對家庭暴力的成因及家庭系統與關係動力有相當的理
解,才能適切及完整評估雙方。
(五)修復訓練對於安全議題應重視:應加入對被害者人身安全控管的評估、方法及資
源使用的學習,以確保修復方案的進行,不致引發受害者心理或身體上的更大
危機。
(六)修復訓練不應與心理諮商輔導混淆: 修復訓練應使課程內容與修復式正義實施
之目的清楚連結。
(七)修復訓練要能區辨修復與調解:修復會議中的調解與現行制度中社區或家事調解
應有清楚的區辨,並在訓練過程說明清楚,以避免以復合的概念進行修復方案。
(八)司法專業訓練應為整體參與:司法部門要推動修復式正義,應先讓所屬人員熟諳
其精神意涵、推動之目的與價值、修復程序之設計意義,以及相關實施的配套
和資源,免得以績效壓力推促被害人同意,因此司法專業訓練應以全體參訓為
目標。
二、修復工作相關專業訓練
修復促進人員之專業訓練應重視以下四項領域課程:
(一)修復相關訓練須著重文化與性別部份:文化及性別議題之概念性的訓練,及多元
文化下之性別現象對家庭關係及成員角色之影響,皆須納入為訓練的內容。
(二)具備輔導與諮商技巧:強化輔導與諮商的技巧、同理心、專注傾聽的能力等,讓當
事人能充分敘說真實的感受和受暴的過程,並能感受到修復促進員對其生命重要
經驗的理解和尊重。
(三)具備相關的法律知能:增加法律相關訓練,熟悉刑事司法流程及司法相
關的知能,在修復實踐及操作較能平穩有效。
(四)相對人與被害人服務實務經驗:具有被害人及加害人的輔導處遇經驗,
對家庭暴力事件之本質與模式,加害人與被害人的心理社會歷程及行為
138
特性較能正確的認知及詮釋。
三、修復人員專業訓練課程
對於實施修復式正義於家庭暴力事件之修復者培訓的必修課程、選修課程及繼續教育
課程建議如下:
(一) 必修課程
1.衝突管理實務(含協商與談判技術)
2.家庭動力與家庭系統
3.家庭暴力本質、模式及影響
4.加害人心理動力
5.多元文化適應與尊重
6.會談與評估技巧
7.認識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8.性別與權力
9.危險評估
10.相關法令:民法親屬編(擇要)、刑法(與家暴、緩刑相關)
11.專業倫理
12.家庭溝通
(二) 選修課程
1.會議主持
2.民刑事訴訟程序介紹
3.檢察官在家暴案件上的處理流程
4.觀護人如何與加害人互動與緩起訴制度介紹
5.失落者的悲傷歷程
6.表達能力訓練
7.精神疾病與診斷
(三) 繼續教育課程
面向 建議課程
修復式正
義之概念
與實務
1.修復式正義之理論、模式、實務發展、成效以及困境之解決
2.各國修復式正義的理論、發展及成效之比較
3.修復之對話平台的建構
4.修復式正義個案之追蹤
5.修復式正義與日常生活衝突處理
6.修復式正義應用在親密關係暴力之導論與操作概念
7.修復式正義運用於家暴事件之理念及技術
139
8.修復提問技巧
9.修復會議主持工作坊
10.學習多種會議支持模式(VOM、和平圈、家庭會議等)
11.定期個案研討
12.修復會議實地觀摩
13.促進者的角色定位及自我察覺
家庭衝突
事件相關
法律
1.民法親屬編(擇要,如監護、繼承、扶養等)
2.刑法(與家暴、遺棄、傷害、緩刑等相關部分)
3.外籍配偶相關法律課程(包括居留、國籍等)
4.家事事件法之理論與運作
5.家暴防治法之內涵與相關流程
6.保護令程序與功用及違反後的相關法律
7.人權相關課程
8.少年事件處理法之理論與運作
協商談判
相關技術
1.協商會談與談判技巧
2.建立關係技巧
3.正向心理學
4.情緒察覺與同理
5.情緒安撫與衝突化解
6.會議程序及共識建立
7.衝突/危機調解技巧與實務
8.修復式取向之調解
9.應對衝突之新觀念(分析、解決、預防衝突)
家庭暴力
理論及實
務
1.暴力的定義、成因、態樣以及案例分享
2.家庭暴力本質、模式及影響
3.親密關係危險評估指標辨識
4.暴力對婦女及兒童的影響
5.不法侵害之定義與內涵
6.高度權控關係之處置與修復式正義
7.家庭衝突現象與處理
8.女性主義觀點下之親密關係暴力防治
文化與性
別敏感度
1.社會文化的變遷與改變
2.儒家文化與華人性格
3.本土文化與多元文化(閩.客.外省.原住民.新住民等)之介紹與差異
4.文化、性別偏見之覺察與省思
5.多元文化與諮商
6.性別敏感度訓練
140
7.性別平等的實踐(性別主流化)
8.性別與壓迫
9.新移民在臺灣文化適應的困境: 跨國婚姻衝突樣貌及新移民婚姻與家
庭
10.父權主義與女性主義
11.性別與暴力
12.權力與控制
家庭系統
評估
1.家庭中權力結構與關係
2.家庭動力觀點下的婚姻暴力處置
3.親密關係衝突歷程與家庭動力
4.婆媳問題合併親密關係暴力之關係動力
5.暴力家庭系統與家庭規則
6.家庭的多元面貌
7.阻力與助力
8.重要他人
認識加害
者/受害
者
1.犯罪學理論
2.變態心理學
3.加害者之特質、權控、處遇、心理動力與臨床表徵
4.失落與悲傷歷程
5.被害人創傷及療癒
6.依附關係與自我認同
7.目睹暴力兒童之心理歷程與處遇
8.心理衡鑑之運用
9.認識物質濫用
個案轉向
措施之資
源
1.公部門及各民間團體對家暴案件之服務項目、內容
2.社會資源和社會福利法規之介紹、運用、整合與轉介
3.家暴處理流程及網絡資源
4.被害者支援網絡服務以及認識法律扶助/犯罪被害人保護制度
5.後續追蹤
6.心理諮商(夫妻諮商、兒童諮商、精神治療)運用於修復式司法
7.壓力調適與生活重建
8.就業服務與福利資源介紹
141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旨在發展國內推動修復式正義應用於家庭暴力事件之相關作業流程與相關配
套措施及具體政策建議。因此就研究目的,本研究團隊提出相關建議如下:
一、個案篩檢機制:哪些個案類型適合應用修復式正義概念?應透過何種哪些篩檢
程序? 有關修復個案評估的指標建立,本研究建議以下九項因素,可考慮進入修復
方案。
1.加害人具真誠且負責的態度
2.暴力屬低度危險且非操控性強者
3.當事人(被害人)對於關係改善的方向具備意願
4.屬家庭衝突議題
5.雙方權控關係相當者
6.因教養子女的衝突
7.互為加害人者
8.初期暴力個案
9.有血緣的家庭關係成員之衝突事件
但更為重要的是釐清應排除適用修復式正義之家庭暴力案件之類別,除被害者無意
願外,其餘為:
1.精神疾患者
2.長期慣性施虐者
3.具權控關係者
4.高危機之嚴重暴力者
二、工作團隊成員組織與角色分工:應包含哪些團隊成員以及各自的角色職責與分工。
有關工作團隊成員應包含修復促進者、輔助促進者、陪伴者、個案/方案管理人員及督導
等執行修復工作之角色及任務。
(一)修復促進者
修復促進者為修復促進程序中重要的人物,不僅可能須擔負評估責任,也是修復
會議之主持人,要致力於營造讓被害者與加害者安心對話的環境。因此修復促進者也是
對話促進者,其應具備之條件如下:
1.修復促進者應具專業性: 不宜由志工的角色來扮演,若能由諮商輔導及法律的專
業背景來成為雙搭配,應是最佳的組合。
2.修復促進者應具有平權及性別概念並且熟悉家庭暴力。
3.修復促進者要有充分加害人及被害人的工作經驗。
4.促進者能充分了解親密關係的本質及被害人在家暴關係中之心理社會處境。
142
5.促進者應具備人際衝突處理及協商談判能力,也須了解華人文化對衝突處理的性
格與方法,以增加處理效能。
6.促進者的協商談判及協調溝通的能力是處理衝突的重要知能,並應注意文化及性
別因素的干擾。
7.促進者的信念特質將影響其處遇的目標。
8.宜依案件特性考量促進者的性別。
(二)輔助促進者的角色
若在修復會議時增加輔助促進者的角色,特別是律師專業者的投入,是相當具助
益性。輔助促進者可提供法律諮詢並協助維持會議程序。
(三)陪伴者
在修復會議實施中,可選取適當人選成為修復陪伴者(支持者),以協助會議歷程及
協議後之工作落實,其角色如下:
1.個案管理社工合宜擔任被害人的陪伴者
2.家族或社區成員可做為修復工作落實的監督者
3.以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或更生保護協會人員做為被害人及加害人的陪伴者或個管
者
(四)個案/方案管理人員
此人員為收案之直接服務者,其職責為執行初步評估並篩選符合修復方案篩選要件之
服務對象,也須積極進行修復促進員之聯繫及相關行政協助,並作為方案實施的個案管
理者。
(五)督導需求
在台灣實施修復方案之初期,修復促進過程中的督導角色不可或缺,以提供實施單
位及修復促進團隊之諮詢與督導實務,而積極建立修復工作督導培訓及督導機制的需要
性應被重視。
1.修復工作過程中的督導:督導可協助促進者覺察自身的問題,做好準備以因應程
序中的挑戰與危機,特別是如何避免 VOM之調解落入家事調解或社區調解之概念
和操作。
2.建立修復工作督導機制的需要性:應建立修復工作之督導機制,以符目前促進員訓
練不足、經驗累積不易,且家暴案件具特殊性及複雜性的需求。
三、專業人員之訓練:擔任修復式正義促進者之相關專業訓練,分為必修課程、選修課
程及繼續教育課程,建議如下:
(一) 必修課程
1.衝突管理實務(含協商與談判技術)
143
2.家庭動力與家庭系統
3.家庭暴力本質、模式及影響
4.加害人心理動力
5.多元文化適應與尊重
6.會談與評估技巧
7.認識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8.性別與權力
9.危險評估
10.相關法令:民法親屬編(擇要)、刑法(與家暴、緩刑相關)
11.專業倫理
12.家庭溝通
(二) 選修課程
1.會議主持
2.民刑事訴訟程序介紹
3.檢察官在家暴案件上的處理流程
4.觀護人如何與加害人互動與緩起訴制度介紹
5.失落者的悲傷歷程
6.表達能力訓練
7.精神疾病與診斷
(三) 繼續教育課程:
宜因應修復促進員之原專業養成背景,選取其較為生疏之領域課程,以究其發展修
復式正義實施之效。例如司法人員亟需以家庭暴力理論及實務、家庭系統與動力理論、
文化與性別敏感度訓練、認識轉向措施社會資源系統等訓練,然社工心理人員則須強化
修復式正義理論與實務、協商談判與衝突管理,以及相關法令課程為繼續教育之方向。
面向 建議課程
修復式正
義之概念
與實務
1.修復式正義之理論、模式、實務發展、成效以及困境之解決
2.各國修復式正義的理論、發展及成效之比較
3.修復之對話平台的建構
4.修復式正義個案之追蹤
5.修復式正義與日常生活衝突處理
6.修復式正義應用在親密關係暴力之導論與操作概念
7.修復式正義運用於家暴事件之理念及技術
8.修復提問技巧
9.修復會議主持工作坊
144
10.學習多種會議支持模式(VOM、和平圈、家庭會議等)
11.定期個案研討
12.修復會議實地觀摩
13.促進者的角色定位及自我察覺
家庭衝突
事件相關
法律
1.民法親屬編(擇要,如監護、繼承、扶養等)
2.刑法(與家暴、遺棄、傷害、緩刑等相關部分)
3.外籍配偶相關法律課程(包括居留、國籍等)
4.家事事件法之理論與運作
5.家暴防治法之內涵與相關流程
6.保護令程序與功用及違反後的相關法律
7.人權相關法令課程
8.少年事件處理法之理論與運作
協商談判
相關技術
1.中性第三者訓練(進階協商會談與談判技巧)
2.建立關係技巧
3.正向心理學
4.情緒察覺與同理
5.情緒安撫與衝突化解
6.會議程序及共識建立
7.衝突/危機調解技巧與實務
8.修復式取向之調解
9.應對衝突之新觀念(分析、解決、預防衝突)
家庭暴力
理論及實
務
1.暴力的定義、成因、態樣以及案例分享
2.家庭暴力本質、模式及影響
3.親密關係危險評估指標辨識
4.暴力對婦女及兒童的影響
5.不法侵害之定義與內涵
6.高度權控關係之處置與修復式正義
7.家庭衝突現象與處理
8.女性主義觀點下之親密關係暴力防治
文化與性
別敏感度
1.社會文化的變遷與改變
2.儒家文化與華人性格
3.本土文化與多元文化(閩.客.外省.原住民.新住民等)之介紹與差異
4.文化、性別偏見之覺察與省思
5.多元文化與諮商
6.性別敏感度訓練
7.性別平等的實踐(性別主流化)
8.性別與壓迫
145
9.新移民在臺灣文化適應的困境: 跨國婚姻衝突樣貌及新移民婚姻家庭
10.父權主義與女性主義
11.性別與暴力
12.權力與控制
家庭系統
評估
1.家庭中權力結構與關係
2.家庭動力觀點下的婚姻暴力處置
3.親密關係衝突歷程與家庭動力
4.婆媳問題合併親密關係暴力之關係動力
5.暴力家庭系統與家庭規則
6.家庭的多元面貌
7.阻力與助力
8.重要他人
認識加害
者/受害
者
1.犯罪學理論
2.變態心理學
3.加害者之特質、心理動力、臨床表徵與處遇
4.失落與悲傷歷程
5.被害人創傷及療癒
6.依附關係與自我認同
7.目睹暴力兒童之心理歷程與處遇
8.心理衡鑑之運用
9.認識物質濫用
個案轉向
措施之資
源
1.公部門及各民間團體對家暴案件之服務項目、內容
2.社會資源和社會福利法規之介紹、運用、整合與轉介
3.家暴處理流程及網絡資源
4.被害者支援網絡服務以及認識法律扶助/犯罪被害人保護制度
5.後續追蹤
6.心理諮商(夫妻諮商、兒童諮商、精神治療)運用於修復式正義
7.壓力調適與生活重建
8.就業服務與福利資源介紹
四、成效評估指標
有關修復式正義實施方案的成效評估,提出下列六項內容:
1.情緒宣洩:應以被害人的感受為成效的指標,即被害人的負面情感獲得釋放。
2.同理能力的增加:成效指標中應讓加害者了解被害人在被害過程中的痛苦、悲傷的情
緒,增加其同理的能力。
3.關係改善:是否獲得新的學習,關係是否逐步在改善。
4.面對與承認的態度:透過修復歷程提升被害者面對真相及現實的機會,以了解加害人
146
的心態與承認的態度,能在抉擇上做出準備。
5.當事人重新得力:是否當事人能透過這個修復歷程重新得力,復歸社會。
6.申請人與當事人之間產生對話的可能:讓雙方產生對話,產生新的了解。
五、其他政策建議
(一) 支援本土性實驗方案及研究
按本計畫之研究結果分析,因修復式正義之理論與實踐在國內仍在初步實驗性實施
階段,因此無論觀點的厚實度及實作經驗之累積度,似仍無法交織建構具共識或趨一致
的意見及態度,有待未來更多的本土性實驗方案及研究,以提供發展性的拓植基礎。因
此只要有充足經費之支持,並制定合宜的指標,增加人力培訓,發展工作技術和方法,
以整合性的網絡工作加以實驗性之推展計畫,將可逐漸架構本土性之實施模式。
依研究結論亦可看出在地性意見與國外實作經驗及相關研究所得確有差異,可見國
內的參與者已經做出更本土的觀察,建議能續為辦理小規模相關實驗性方案及行動研
究,以開發及聚焦具本土性作為的修復式正義實施方案。且賴以時日,將能堆疊累積本
土性之實務能量,方能於未來採德懷研究(Delphi)之實施,匯集家庭暴力應用修復式正義
處遇方案之相關學者專家、修復程序執行人員、相關司法人員以及法律專業人員之意見,
進而整合專家共識,作為未來對於修復式正義應用於家庭暴力事件之施行建立準則之
用,並利建構推展與落實家庭暴力處遇工作之可行制度。
(二) 釋放資源給非政府組織,以協助其參與實踐修復式正義之行動
因國內修復式正義之啟動及推展,是由國家司法部門領軍,這與各國不論在理論及
實務上,是典型以「由下而上」之司法改革運動之姿而拓展,有相當之差異。因此如何
結合非政府組織及宗教團體,厚植基層意見及經驗,實有多溝通與再規畫之必要。
截至 2003年,國際間已有八十個以上的國家開始實施修復式正義,其實施也建基在
聯合國和平締造委員會起草「簡介修復式正義之和平締造」文件之四項原則:聚焦傷害、
關係導向、參與及民主。肯定修復式正義在轉型期及後轉型期的施用。各國之 NGO也開
始更多具轉型正義向度的司法改革方案出現,跨領域及跨組織地促進個人及社會的轉型。
面對此一草根性強、以修復式正義進行司法改革之潮流,並作為轉型正義的歷程,
我們的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工作模式,需進一步思考如何與整體大環境結構互動,並創造
權力結構的翻轉及集體意識的邁進,提升社會支持的責任,期能真實回應受害者修復療
癒的需求。
(三)強化自我監督之倫理,制定修復式正義倫理守則
隨著修復式正義之實施,若無相關的監督機制,則將如保羅‧佛萊迪(Paul C.
147
Friday)針對隨之而來的危機而提出:「守則及標準乃是迫切且必須的。所謂危機,及是
指有些方案在初行之時,看似具修復性,但實質上卻複製了法庭審理的程序,結果則是
損害而非修復之促進;第二項危機則在於修復程序的法律基礎並不存在;第三項危機則
是導致犯罪之社會成因(etiological factors)如:貧窮、種族、文化與社會價值、以及個人
主義等因素,在過程中未被指陳。」17
因此為保障人權及確保修復式正義程序之倫理正當性,從歐洲會議第 99項決議第
19條(Council of Europ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Mediation in Penal Matters,"
Recommendation No. R(99)19)、魯汶宣言(Declaration of Leuven)、英國修復式正義
Consortium 的「修復式正義標準」(Standard for Restorative Justice issued by UK Restorative
Justice Consortium),VOMA倫理守則(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Association
Recommended Ethical Guidelines)、美國律師協會受害者與加害者調解/對話方案要求
(ABA Victim-Offender Mediation/Dialogue Probram Requirements )等文件,及後來聯合國
犯罪預防及刑事司法委員會於 1997年第十次大會議程,也討論「加害者與受害者:司法
程序的責任與公平」,並因此後續發展相關標準及規範。18
由於我國在修復式正義之進路及司法社會處境,與西方國家顯有差異,因此我國
如何在修復程序及修復結果之評量價值與標準,以及建立修復式正義實施之倫理守則與
規範,作出積極的努力,應是迫切及無可規避的責任。
(四) 為達評估與執行效能,應加入跨科際與多元網絡之對話與參與
在我國實施修復式正義之脈絡中,台灣能有何種反思及連結,使目前修復式司法
試行階段能回應轉型正義的要求? 在評估目前司法體系試辦方案的修復性,必須同時重
視其程序及結果。程序部分則重視包容、利益均衡、自願參與及問題解決取向。結果部
分其指標性價值則包括對遇、 修補、整全、及完整真相19。目前試行方案之修復性須賴
持續追蹤始能評估。若司法系統能進行跨部門跨專業合作,程序間邀請相關部會提供專
業訓練及技術,並在修復結果之轉向措施及追蹤輔導能積極與跨專業體系合作互助,將
能更積極維護被害者保護之核心價值。
17
Van Ness, Daniel.“Proposed UN basic principles on restorative justice”, http://www.restorativejustice.org/10fulltext/vanness7 18 參考陳文珊教授發表於 2012 年 3 月 6 日長榮大學辦理之「正義女神的新天平:修復式正義、人權與和平教育」研討會中發表之「全
球的視野與在地的關懷-談 NGO 推動修復式正義之角色扮演與相關爭議」乙文。 19 Van Ness, Daniel.“Proposed UN basic principles on restorative justice”, http://www.restorativejustice.org/10fulltext/vanness7
148
參考文獻
專書及期刊論文:
中文部分:
史考特‧派克 楊韻泉譯(1999)。真誠共識─等待重生的新契機。台北:張老師出版社。
李秋霞、卓紋君(2005)。離婚調解之理念與實施。 2005 家事商談國際研討會
會議手冊,2005/5/27,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主辦。
李浩然(2007)。從修復式正義探討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之婚姻暴力調解策略。國
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美薰(2001)‧勇者的塑像-談婚姻暴力倖存者的心路歷程‧律師雜誌12月號
(167),pp30-35。
吳慈恩(1999)。邁向希望的春天-婚姻暴力受虐經驗之分析與防治實踐。高雄:高
雄家庭協談中心出版。
吳慈恩、黃志中 (2008)。婚姻暴力之醫療處遇。台南:復文。
吳慈恩 (2008)。婚姻暴力加害人處遇在台灣的發展與演變。台北:內政部家庭暴力防
治法十週年回顧與展望-「從各國經驗談台灣推動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之過去、現
在與未來」研討會。2008。頁:67-98。
吳慈恩 (2009)。打造安全防護網—談防治網絡未來的建構與運作(台灣家暴防治的第
二個10年)。南投:暨南大學「2009年金融海嘯、家庭與社區實務與學術研討會」。
2009.10.15.
吳慈恩 (2010)。向愛傾斜的正義—促進法院裁定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手冊。台北:
內政部。
吳慈恩 (2010)。溫柔正義的實踐—建構本土化家庭暴力加害人強制處遇模式之反思。
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觀摩研討會。台北: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2010.08.09,頁:103-120。
吳慈恩 (2011)。忍耐與寬容?—從基督信仰回應婦女的家暴問題。女宣雜誌。台北:台
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婦女事工委員會。2011.11,396:4-10。
洪英花(2011)。實踐修復式正義-以士院試辦刑事案件流程管理為例。臺灣法學雜誌,
175,5-34。
胡幼慧(1996) 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圖書。
姚淑文、溫筱雯(2010)。開心談戀愛,理性談分手─親密關係暴力防治手冊。內政部家庭
149
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柯麗評、王珮玲、張錦麗(2005)。家庭暴力理論政策與實務。臺北:巨流。
高鳳仙(1998)。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專論。臺北市:五南。
高鳳仙(2007)。諮商與調解在家庭暴力事件之法律界限。應用心理研究,33,
1-7。
張曉文 (2004)。從全球治理探討非政府組織之角色:一個人權與人道救援之觀點。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許春金(2003) 犯罪學。台北:三民。
許春金(2003) 修復式正義的實踐理念與途徑:參與式刑事司法。犯罪與刑事司
法研究,1,37-66。
許春金;陳玉書;黃政達(2007)。調解制度中受調解人修復性影響因素之研究
--修復式正義觀點。《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9:1-54。
許春金(2009)。人本犯罪學─控制理論與修復式正義。台北:三民。
陳婷蕙(1997)。婚姻暴力中受虐婦女對脫離受虐關係的因應行為之研究‧東海
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陳祖輝(2004)。淺談社區司法的理念與實踐:復歸式正義的取向。社區發展季刊,107,
445-458。
陳源湖(2004)。跨國婚姻婦女教育中的教學者角色。社區發展季刊,107,359-376。
陳源湖(2004)。婚姻暴力中的性別意識形態與權力,載於知識型構中性別與權力的
思想與辯證(308-321頁)。台北:唐山。
黃怡瑾(2001)。婚暴中的權力控制—個人自覺與社會結構的互動歷程‧婦女與
兩性學刊(12),pp95-137。
黃志中 (2008)。婚姻暴力-醫療社群現象之探討。台北:合記,1-255。
黃志中 (2008)。婚姻暴力防治之醫療處遇-過去、現在、展望。第七屆性別遇醫療工
作坊論文集。高雄:高雄縣政府衛生局,231-237。
黃志中(2008)。風驟卻雨疏:家庭暴力加害人認知教育輔導專業發展困境之省思。「從
各國經驗談台灣推動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之過去、現在與未來」研討會。台北:內
政部,59-175。
黃志中(2008)。省思原鄉在家庭暴力防治中的失落現象。原鄉部落家庭暴力急性侵害防
治實務研習會手冊。台北:內政部,69-70。
黃志中、吳慈恩 (2010)。「某可以再娶,但媽媽只有一個」-婆媳衝突與婚姻衝突交錯
150
下的男性婚暴加害人處遇困境。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觀摩研討會。台北:內政部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10.08.09,頁:10-28。
黃蘭媖(2007)。追尋犯罪被害人的正義之路:從福利到修復、從控制到重分配。社會政
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1(2),35-78。
黃蘭媖(2011)。修復式正義理念運用於刑事司法制度之探討。台北:法務部(委託論文)。
黃翠紋(1999)。家庭暴力防制策略之探討--兼論台灣地區警察處理家庭暴力問題之現
況。警學叢刊,29(5),151-172。
黃翠紋(2001)。婚姻暴力調解措施之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中央警察大學,桃園縣。
黃翠紋(2002)。婚姻暴力受虐婦女接受調解意願影響因素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學報,
39,251-279。
黃翠紋(2004a)。婚姻暴力嚴重性影響因素之研究—我國婚姻暴力加害人之危險評估。犯
罪學期刊,7(1),127-154。
黃翠紋(2004b)。婚姻暴力受虐婦女對於保護令滿意度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中央警察大
學學報,41,231-254。
黃翠紋(2006a)。以調解方式處理離婚事件之研究。警學叢刊,37(2),119-154。
黃翠紋(2006b)。修復式正義理念在婚姻暴力案件調解上的應用,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
文集,9,35-60。
楊康臨、鄭維瑄譯(2007)。家庭衝突處理─家事調解理論與實務。臺北:學富。
廖家陽(2008)。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研究─以民事保護令制度為中心(未出版之碩士論
文)。國立高雄大學,高雄市。
趙淑珠(1999)。家庭系統研究中之性別議題。應用心理研究,2,125-139。
劉默君(2004)。從生態學的觀點探討當代家庭婚姻暴力暨受虐婦女脫離受虐關係之因
素。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41。取自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41/41-40.htm
廖婉喻(2008)台灣家事調解員的性別意識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
商學系所碩士論文。
廖家陽(2008)。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研究─以民事保護令制度為中心。國立高雄大學
法律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婌齡(2003)。公部門婦女保護服務社工之協助效益-從受暴婦女角度探討(未出版之碩
士論文)。東海大學,臺中市。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運用。台北:心理出版社。
潘雅惠、陳建宏(2009)。修復式司法運用於家庭暴力事件之探討。司法週刊,1461-1463。
151
魏英珠(1995)。受虐婦女介入方案發展暨評估研究。私立東吳大學社工研究所
碩士論文。
英文部分:
Altrichter,H. , Posch, P. & Somekh, B. 1995。Teachers investigate their
work。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utledge。
Catherine, K. (1993). Leaving Abusive Partners: From the Scars of Survival to the
Wisdom for Change. Newbury Park, CA: Sage.
Chaplin, J. (1988). Feminist Therapy. Innovative therapy in Britain.
Ferraro, K. F. (1996). Women’s fear of victimization? Social Forces, 75(2), 667-691. Julie Stubbs (2010). Relations of Domination and Subordination: Challenges for Restorative
Justice in Responding to Domestic Violence.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 10/61
Centre for Justice & reconciliation (2008). What is Restorative Justice?, Prison
Fellowship International, 1-4.
Julie Stubbs (2007). Beyond Apology? Domestic Violence and Critical Questions for
Restorative Justice. Criminology & Criminal Justice, 169-187.
Kirkwood, C.(1993)Leaving Abusive Partners. London:Sage.
Liebmann, M. &Wootton, L. (2010).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Domestic Violence Abuse. A
Report Commissioned by HMP Cardiff Funded by the Home Office Crime Reduction Unit
for Wales。
Lloyd, S. A. & Emery, B. C. (2000). The dark side of courtship: Physical and sexual
aggress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Menkel-Meadow, C. (2007). Restorative Justice: What Is It and Does It Work? The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3: 10. 1-10,27.
Mills, L. G. (2003). Insult to injury: Rethinking our responses to intimate abus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ills, L. G..(2008). Violent Partners:A Breakthrough plan for Ending the Cycle of Abuse.
NY: A Member of the Perseus Books Group.
Marchall,T. E. (1999). Restorative Justice: An Overview. A Report by the Home Offic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Statistics Directorate.
Stubbs, J. (2007). Beyond Apology? Domestic Violence and Critical Questions for Restorative
Justice. Criminology & Criminal Justice, 169-187.
Stubbs, J. (2010). Relations of Domination and Subordination: Challenges for Restorative
152
Justice in Responding to Domestic Violence.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 10/61.
Peggy Grauwiler.(2004). Moving beyond the criminal justice paradigm: a radical restorative
justice approach to intimate abuse. Journal of Sociology & Social Welfare (Refereed),
31(1), 49-60。
Swift, C. F.(1988). Stopping the violence: Prevention strategies for families. In C. A. Bond,
B. M. Wanger(Eds.),Families in transition(pp.252- 285).Beverly Hills, CA: Sage.
Sherman, L.W., Schmidt, J. D.,Rogan, D. P., Smith, D. A., Gartin, P.R., Cohn, E. G., Collins,
D.J. & Bacich, A. R. (1992). The variable effects of arrest on criminal careers: The
Milwaukee domestic violence experiment,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83(160), 137-69.
Tony E. Marchall (1999). Restorative Justice: An Overview. A Report by the Home Offic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Statistics Directorate.
法律條文:
刑事訴訟法,民國 96年 12 月 12日修正。
家庭暴力防治法,民國 98 年 4月 29日修正。
家庭暴力防治法施行細則,民國 96年 10 月 2日修正。
網頁資料:
修復式正義之評估 - 醫林漫話 - udn 部落格http://blog.udn.com/wangkwo/4697052#ixzz1S8gpzbSr
http://mypaper.pchome.com.tw/probationology/post/1321425868
http://www.restorativejustice.org/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統計資訊網站:http://dspc.moi.gov.tw/lp.asp?CtNode=776&CtUnit=79&BaseDSD=7&mp=1&xq_xCat=a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網頁:http://www.tyc.moj.gov.tw/ct.asp?xItem=120502&ctNode=22014&mp=012 2011/8/31
法務部網頁: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207793&ctNode=28162&mp=001
2011/8/30
http://www.ice8000.org:81/china/ngo/2.htm 2012/02/28
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蘭馨婦幼中心網頁:
http://www.roton.tw/index.php?menu=view&mode=timenews&timenewsid=73 2011/9/17
Ministry of Justice 網頁:http://www.justice.govt.nz/publications/global-publications/r/review-of-the-use-of-restorative-
justice-in-family-violence-cases-in-the-rotorua-district-may-2007/the-restorative-justice-progr
amme-for-domestic-violence 2011/9/19
153
附件資料(附件一)
修復式正義應用在家庭暴力事件之初探計畫 受訪者問卷調查表
您好:
謝謝您參與本計劃之焦點訪談與個人訪談,您實質的經驗與深刻的洞見對本方案
貢獻良多,為進行受訪者個人基本資料分析,煩請協助填寫您個人資料,您個人資料
僅供本計劃分析使用,絕不對外公開個人資料造成任何困擾,請安心填寫。
長榮大學 吳慈恩上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 您的性別: □男 □女
2. 您的出生年:民國 年
3. 所屬機構或社會團體:
□教育機構 □民間組織 □社會行政 □醫療機構 □衛生行政
□其他
4.您的職稱是:
5.您的學歷: □學士 □碩士 □博士 □其他
6.您參與服務之區域: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其他
7.您的婚姻狀態: □已婚 □未婚 □離婚 □再婚 □其他
8. 您曾否擔任家事調解員: □ 是,年資 年 □ 否
第二部份:專業領域
1.您的專業領域:□ 法律 □心理 □社工 □醫療□教育□犯罪學□司法
2.您在修復式正義及家庭暴力防治的專業經驗是: (可複選)
□家庭暴力防治政策 □修復式正義研究 □法律議題 □修復式司法實施
□家事調解 □家庭暴力被害人處遇 □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
□其它
2. 在以上領域您的年資有:
(若有多個專業領域,請於下列項目勾選後方註明領域)
□一年以下
□一年~三年
□四年~六年
□七年~九年
□十年以上
□其它
154
第三部份:您在修復式正義或修復式司法制度之角色是
□學者(含研究者) □個案管理員 □修復促進者 □支持者 □督導 □其它
第四部份:您對實施修復式正義於家庭暴力事件之修復促進者培訓課程之意見是
一、你覺得以現階段實施之課程(如下)哪些課程為必修? (必修之課程請打勾,
可複選)
□ 民刑事訴訟程序介紹
□ 檢察官在家暴案件上的處理流程
□ 觀護人如何與家暴加害人互動與緩起訴制度的介紹
□ 衝突管理實務(含協商與談判技術)
□ 精神疾病與診斷
□ 加害人心理動力
□ 認識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 失落者的悲傷歷程
□ 多元文化適應與尊重
□ 家庭動力與家庭系統
□ 家庭暴力本質、模式及影響
□ 家庭溝通
□ 表達能力訓練
□ 會議主持
□ 會談與評估技巧
□ 其他
二、請提出修復促進者繼續教育課程的建議(請提課程名稱)
修復式正義之概念與實務面向課程:
家庭衝突事件相關法律面向課程:
協商談判相關技術面向課程:
家庭暴力理論及實務面向課程:
文化與性別敏感度面向課程:
家庭系統評估面向課程:
認識加害者/受害者相關面向課程:
個案轉向措施之資源面向課程:
其他:
作答結束 謝謝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