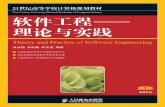记忆、体验与社交媒介:流行音乐与小康村新生代劳工的主体性
Transcript of 记忆、体验与社交媒介:流行音乐与小康村新生代劳工的主体性
研 究 生 毕 业 论 文
(申请硕士学位)
论 文 题 目 记忆、体验与社交媒介
——流行音乐与小康村新生代劳工的主体性
作 者 姓 名 李 胜
学科、专业名称 人类学
研 究 方 向 社会人类学
指 导 教 师 杨德睿 副教授
2013 年 5 月 20 日
1
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中文摘要首页用纸 毕业论文题目: 记忆、体验与社交媒介
——流行音乐与小康村新生代劳工的主体性1
人类学 专业 2010 级硕士生姓名: 李胜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杨德睿 副教授
中文摘要
本文旨在探寻流行音乐对于新生代劳工的意义,希望能藉此为这一群体的主
体性与尊严做一注脚。为进行此项田野研究,作者亲身到苏州常熟古里镇小康村
的某纺织业工厂打工了数月的时间,名副其实地参与观察了新生代劳工在工厂车
间、宿舍和小康村夜市等地点架构出的空间中展开的生活,以及流行音乐在这种
生活中呈现的样貌。
基于上述观察体验,本文呈现了流行音乐的传播、分享、消费如何被新生代
劳工配置在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他们建构自主的空间、表达自我情感和记忆的工
具。换言之,流行歌曲的意义是这些第一线的传播者兼消费者赋予的——通过把
它们与脱域了的地域(对家乡的朦胧想象)关联起来,与他们的工作、婚姻、过
往生涯的记忆和自我认同关联起来,与信息科技变革如智能手机的普及带来的生
活方式变迁关联起来。结果,新生代劳工们跌宕多端的生命历程遂被汇聚成红歌、
港台流行歌、网络歌曲/农业金属等风格拼贴混杂而成的声境。
作为结论,本文通过还原新生代劳工在传播和消费流行音乐过程中彰显的主
体性,一方面批判了既往“中国的流行音乐研究”所预设的城市中心主义、生产
方中心主义(以经纪公司、唱片公司、创作者和歌手为中心的书写)和产品拜物
教(“音乐的意义在于其本身的形构”这种意识形态),同时也批判了时下的劳工
研究以“关怀弱势”的启蒙解放者姿态贬抑新生代劳工的自主能动性的倾向。
质言之,本文希望能藉着如实呈现一群新生代劳工的音乐生活,说明他们不
是仅能默默承受剥削或者被彻底无视的客体,也不是阶级意识觉醒后奋起反击的
1 本研究受中华回教慈善基金会和社会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基金资助,特此鸣谢。
3
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英文摘要首页用纸
THESIS:Memory, Experience and Social Media: Pop Music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Xiaokang Village
SPECIALIZATION: Anthropology
POSTGRADUATE: LI Sheng
MENTOR: Professor YANG Der-Ruey
Abstract
This thesis aims at questing the meaning of popular music to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nd intends to mark a footnote for their subjectivity and dignity. In
order to make a better field research, the author spent several months in a textile
factory located in Xiaokang Village, Guli town, Changsu, Suzhou City, in which he
veritably experienced, lived and observed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lives in
on-site workshop, in temporary living quarters as well as in local night fair,
meanwhile, he traced for various manifestations of popular music in the environment
of such life.
The in-person journey of life there witnessed the formation of knowledge of how
do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dispose of the transmission, sharing and
consumption of popular music in their real life and what role does popular music play
in their construction of private space, expression of emotions and memories. Or, this
real experience educated the author that the meaning of popular, by initial sense, are
endowed by this group, who combines music with disembeded space however
mentally bind land, associates self-cognition with their work, marriage and passed
lives, and connects with the vicissitudes of life styles resulted from transformations of
advanced technology.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he ups and downs of this group are
mixed and composed into a sound pool of Revolution songs, Taiwan and Honkong
4
pops, Internet songs and Agricultural Metal.
In conclusion, this thesis, through restoration of this group’s subjectivity
manifest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mitting and consuming popular music, not only
criticizes the preset Urban Centrism, Producer Centrism and Product Fetishism in
previous studies, but also lashes the current tendency of depreciating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the group in labor researche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author intends to truthfully present the music life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fighting for the silent fact that they are being
exploited and ignored, proving for the truth that they are not the revolt group after the
wake of class consciousness, however, defining the status quo that they are blood and
flesh who are constantly striving for colorful life.
Key Words: Pop Music;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Memory;
Experience; Social Media
1
目 录
导言 ................................................. 1
一、研究缘起 ...................................................... 1
(一)歪打正着..................................................................................................... 1
(二)初次田野札记............................................................................................. 2
二、文献阅读与疑问 ................................................ 4
(一)人类学中的音乐研究................................................................................. 4
(二)音乐人类学中的流行音乐研究................................................................. 8
(三)中国作为地方的流行音乐研究............................................................... 11
三、田野地点概况 ................................................. 13
(一)常熟市的区域简介................................................................................... 13
(二)古里镇与小康村的行政沿革................................................................... 13
(三)小康村的地景深描................................................................................... 17
四、研究方法 ..................................................... 18
五、论文框架结构 ................................................. 18
第一章 流行音乐在小康村工厂 ......................... 20
一、再回小康,做工人,音乐在哪里? ............................... 20
二、工厂生活中流行音乐的日常呈现 ................................. 23
三、音乐狂欢:厂里的歌唱比赛 ..................................... 28
第二章 流行音乐在小康村夜市 ......................... 32
一、日常生活的情感表达:音乐及其他 ............................... 32
二、恋爱、婚姻生活中的流行音乐 ................................... 34
三、回到点唱机:音乐展示的社会空间 ............................... 38
第三章 农业金属/网络歌曲缘何流行? .................. 43
一、流行音乐作为青年文化的社会记忆 ............................... 43
二、手机作为流行音乐的传播媒介 ................................... 46
三、小康村流行音乐的类型分析 ..................................... 48
第四章 那些人,那些事——与音乐有关 ................. 53
一、永远的张老板 ................................................. 53
2
二、卖手机,替人下载音乐的小丁们 ................................. 55
三、爱唱歌的小超 ................................................. 57
结论与讨论:歌唱的意义 .............................. 61
参考文献 ............................................ 65
致谢 ................................................ 72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4
1
Roll Over Beethoven and tell Tschaikowsky the news.
——1956 Chuck Berry Roll Over Beethoven
导言
一、研究缘起
(一)歪打正着
初遇小康村纯属偶然。2011 年 8 月,那时我原本打算从事江南民间信仰的
田野工作,研究一位在常熟古里颇有名气的谭姓法师及其信徒的宗教活动。由于
住所难寻,谭法师便将我安排在离古里镇不远的父母家。谭法师的父母住在小康
村,一个典型的苏南村庄。
每日从谭法师家回小康村时多半已是下午时分。回到谭法师父母家,整理完
上午的田野资料已经约摸傍晚六七点,我的肚子咕咕叫了,实在不想麻烦谭法师
家人便独自去街上觅食。
谁知,甫一入街,华灯初上,我便为眼前的场景惊诧了。街两边都是小吃,
整条整条的小吃摊就这么排着,麻辣烫、炒菜、炒面、炒饭、炸串、凉皮、凉面
等不一而足。一时间竟不知道吃什么好。我骑着电动车一路前行,身旁霓虹灯闪
烁,耳旁混杂着各家店铺用来揽客的音乐,神思有些恍惚。夏日小康村的夜晚实
在太迷人。许多幼时童年的记忆扑面而来:那时我们家门前的那条街也很热闹,
周遭是最时兴的港台流行音乐。人们三两成群结伴去广场乘凉。到夜晚八九点,
空气不再那么灼闷时,便各回各家。
逛至购物中心,也就是小康村菜市场附近时,我的感官迅速被打开。迥异的
叫卖声、讨价还价声、笑声、歌声混杂着食物的香味、人群的气息,当然包括眼
前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与摊铺,还有五光十色的光线与色彩让你无法辨认当下此景
所处的时代与地域。农村?城镇?抑或是城乡结合部的光景?我一时竟找不到语
词来指称我经历的当下。
正当我恍惚时,耳边传来气势磅礴的女声。定睛一看,原来是两个穿着厂服
的女生正在一个点唱摊前唱着某种旋律节奏非常快的歌曲。摊前一群人围着,我
2
也凑了过去。大家像看演出一样,朗朗上口的旋律让我也不禁打起节拍,身体跟
着摆动起来。后来我才知道她们唱的是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身为一个人
类学学生,我本能地观察起周围的人。他们很多都穿着厂服,上面依稀写着“新
世电子”、“相互电子”等字样,也有没穿制服的。男的很多有纹身,穿着都很
时尚,女的似乎没那么讲究,但也看得出来出门前是收拾了下自己的。他们或蹲
或站或坐,大多成群结伴,应该就是附近工厂的工人。
我在点唱机前驻足了很久,摸清了眼前这幅景象大概的流程。摊主分别把经
典的红歌老歌、港台流行歌及时下最流行的网络歌曲,和它们的编号写在三个硬
纸壳上供人选择。来者也可以报上歌名与演唱者名,摊主便在电脑前搜索 Excel
数据库以便确认有没有所需歌曲。如果有的话,摊主便把歌曲编码输入机器,依
次序播放。如果没有,摊主便会要求顾客换其他的歌。顾客也可以要求摊主回去
下载,这样明天再过来时就可以唱了。如果仅唱一首歌得花费四元,三首的话就
会稍便宜,十元。
伫立听久了我发现,一个叫“凤凰传奇”的组合很流行,人们很爱唱。《最
炫民族风》、《我从草原来》、《荷塘月色》大概是 2010 年那个夏天我听着听
着都要会唱了的歌。在那里,我从来没有听过人们演唱在都市 KTV 中最受欢迎
的那些歌曲——如王菲、梁静茹、张惠妹抑或是陈奕迅的歌。而红歌以及如《父
亲》、《烛光里的妈妈》这类通俗老歌,抑或是刘德华、张学友等人的港台流行
老歌也常被人点唱。当然,最流行就是如凤凰传奇那种类型的歌手演唱的歌曲。
我不由地好奇,为何人们很爱唱这种类型的歌曲?他们在这么多人面前唱歌是什
么感觉?
(二)初次田野札记
那晚回到住处,我的心情大好,觉得点唱机以及周围的人群着实引人入胜。
于是此后每天都会期待晚上的吃喝唱之行。
一来二往,我跟老板以及老板的侄女还有经常来唱歌的两三个人都熟络了起
来。闲聊中才知道,小康村最早有点唱机是 2008 年,是一位张姓男子从北京购
得的设备。后来他自己做大了,办了个小纺织厂,便把点唱机转手给了现在的王
老板。
3
王老板是江苏扬州人。之前在一家服装厂打工,后来攒了点钱,也觉得打工
太累,不自由,便辞职拉了自己侄女一起开了现在这个点唱摊。
其实 2011年时小康村还有另外一个点唱摊。摊主是一对情侣,我跟他们聊
过几次天。他们两年间去了六个地方,去一个地方就找个事情做做,攒攒钱然后
就去下一个地方。我曾戏称他们真能折腾。女主人说年轻嘛,两个人不趁着结婚
前折腾,生了孩子就没时间折腾了。我其实很喜欢他们洒脱的生活态度。只是后
来他们没多久就走了,我想找他们访谈也再无机会。
说到前一位王老板,他总是乐呵呵的,一副和气生财的样子。他和他的侄女
都很爱唱歌,并且唱得不错。王老板自己出来打工前还在家乡的歌唱比赛获过奖。
侄女高中没读完便也出来打工,后来也嫌工厂又累又赚不着钱便跟着王老板出来
做点唱机生意。
一辆改装过的小型卡车上放置一台屏幕不算大的电视,侧面隔层放置
Karaoke 播放机。播放机下侧摆放着一张简易钢桌,桌上的电脑则供摊主查询歌
曲编码使用。王老板的这台露天卡拉 OK 点唱机并不算先进,甚至比较简陋,但
王老板人很和气,点唱机的人气也很旺。
(图 1 小康村夜市的点唱机)
2011 年在小康村待着的整个 8 月,我发现来王老板这唱歌的人如潮汐,晚上
6 点多一拨,9 点多一拨,晚些时候,十一点多还会有一拨。这引起了我的兴趣。
仔细观察和攀谈,才发现,原来这是与工厂的作息时间相关联。6 点多的那拨人
是上长白班的,一般四点或五点下班,吃完饭,待在宿舍无趣便来夜市转转。9
4
点多那拨一般是 8 点下班的工人。出来吃个夜宵顺便逛逛玩玩。而最后十一点多
那拨一般则是从夜市附近的餐馆或者小吃摊点吃完饭喝完酒,但还未尽兴便前来
唱歌的工人们。
小康村的打工者多来自河南、四川、重庆、安徽等内陆省份,这一点完全可
以从小康村商业街上餐馆的名称看出来。例如随处可见的河南小吃、四川小吃,
有些点名中间则加个“皖”字。此外,小康村还有个店家经营长途客运,终点都
是内陆省份的城市或县乡。来小康村打工的人大多很年轻,20 岁左右。他们或
拖家带口或因着亲戚朋友的介绍前来谋一份薪水。比如在点唱机不远卖棉被的阿
龙,他来小康村已经五年了,一直在淮海工作,因为升职为班长,不能也不用长
时间加班。为了“不浪费时间”和“多赚些钱”,每日四点下班后,他便把货从
宿舍和合伙人——陈课长在小康村的租所拉到夜市来卖。阿龙是安徽宿州人,
1991 年出生,初中毕业便辗转出来打工。阿龙后来告诉我,他那段时间早上六
点前就得起床去市里的招商城进货,然后赶在 8 点上班前把货拉回来。阿龙的故
事让我很想也去工厂体验一把。但 9 月我得归校继续学业,只好作罢。
当时我列下了以下我感兴趣的问题:
1、 露天卡拉 OK 点唱机缘何如此受村里的工人们欢迎?
2、 音乐与这些工人的生活究竟有何关联?
二、文献阅读与疑问
(一)人类学中的音乐研究
音乐由于其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而成为人类学家经常关注的方面。自现代
人类学产生之日起,人类学家们在田野报告/民族志中均对音乐予以不同程度的
关注。事实上,人类学音乐研究中三国传统(德国、美国和英国)的变迁是值得
玩味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人类学传播论派中的文化圈流派(Kulturkreis
School)代表人物Wilhelm Schmidt、Fritz Graebner等人深受民族音乐学家Erich
von Hornbostel、Curt Sachs等人的影响。那时德国文化圈流派的人类学借用民族
音乐学的研究成果阐明其理论,并视民族音乐学的同事为其团队中必不可少的一
份子1。
1 Schneider, Albrecht. Musikwissenschaft und Kulturkreislehre : zur Methodik und Geschichte der Vergleichenden
5
而受博厄斯影响笼罩着的美国人类学,很重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特别是博
厄斯的弟子们。最突出的是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他开
创了美国文化人类学中的非洲研究1。赫斯科维茨在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黑人
昔日的神话》中先锋性地讨论了非裔美国人与非洲人音乐的关联,并比较了美洲
新大陆源自非洲大陆不同的文化。
其他人如罗伯特·洛维(Robert H. Lowie)在其有关Crow的民族志中,分析
了歌曲以及当地人如何讨论音乐2。洛维将音乐作为文化的一个领域予以单独分
析。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在“Song Recitative in Paiute Mythology”一文
中讨论了语言与音乐的关系3;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研究了Manus人关
于音乐的文化期待(cultural expectation)和其音乐观和习得音乐的方式4。米德
的名著《萨摩亚人的成年》也有简短但富有洞见的音乐民族志描写5。应该说20
世纪40年代的德国和美国人类学中音乐研究还是占据一定地位的。
英国人类学中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我们甚少可以从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
夫·布朗的著作中找寻到专门论述音乐的痕迹。这大抵和当时英国人类学身处结
构功能主义的漩涡中有关,在试图进行面面俱到的村落/部落民族志书写时,音
乐往往成为陪衬,淹没在琐细的社会事实中。音乐还没能成为英国人类学大家们
所关注的重点。
但是,正如布鲁诺·内特尔(Bruno Nettl)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和欧洲的大学
教授们摇摆于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和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之间6。在研究异文化中审美性的文化领域,如宗教、艺术、饮食穿衣风格,包
括音乐时,他们多持民族中心主义的视角。他们可能愿意将非洲的雕塑放置于家
中,却不愿尝试《人类学家的食谱》中的菜品7;他们阅读《源氏物语》,却不
会聆听gagaku8。应该说,那时的西方人类学家并不认为其在非洲大陆所见到的
音乐演奏者是一个音乐家。
Musikwissenschaft. Bonn-Bad Godes- berg: Verlag fiir systematische Musikwissenschaft, 1976. 1 M. Herskovits. The Myth of the Negro Past.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1. 2 Lowie, Robert. The Crow Indians. New York : Farrar and Rinehart, 1935. 3 Edward Sapir. Song Recitative in Paiute Mythology.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23, 1910: 455-72. 4 Margaret Mead. Growing Up in New Guine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rimitive Educatio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30. 5 Margaret Mead. Coming of Age in Samo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28. 6 Nettl, Bruno. Nettl's Elephant: On the History of Ethnomusicolog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0. 7 Jessica Kuper, ed. The Anthropologists' Cookbook.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77. 8 gagaku 是日本兴盛于平安时代的一种传统音乐(宫廷雅乐),也是以大规模合奏型态演奏的音乐。
6
这样的民族中心主义偏见在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著作中也
可见一斑。在列维的那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生食与熟食》中,他通过对南美印
第安人的神话分析,讨论了音乐和神话的同源问题1。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音乐
和神话均为文化普遍性的(cultural universal),但是这普遍性的音乐实为19世纪、
20世纪欧洲古典音乐的风格。与列维斯特劳斯相似的人类学家还有Oscar Lewis,
他们都过于局限在西方音乐中,并把音乐视为文化中的一个独立领域,而
Siegfried Nadal虽在民族音乐学中颇有建树,但并未将音乐整合进文化中。
无论如何,早期的人类学家还会关注到音乐,还会在其田野调查中录制音乐
以供音乐学家研究,但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颇具影响力的人类学著作中,有关视
觉艺术讨论的著作不断增多,而有关音乐的讨论则不断减少。这与民族音乐学作
为独立学科的兴起有关,非西方的音乐研究多被民族音乐学家包办。
真正意义上的音乐人类学奠基者是美国人阿兰·梅里亚姆(Alan P. Merriam)。
梅里亚姆于1964年出版了《音乐人类学》一书。该书提出了音乐、行为和概念的
三位一体模式,开启了音乐人类学的学科范式,试图将民族音乐学归置于人类学
的研究范式之下2。但梅里亚姆的努力遭致主流人类学家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
“任何音乐的研究从技术方面看都应该是由音乐学院专门从事的工作,人类学家
不应该将自己对音乐之外的关注强加给音乐理论家”3。
毫无疑问,人类学取向的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本体取向的民族音乐学还是存在
着巨大的差异。虽然,数十年来学者们都在致力于弥合两者之间的缝隙。
人类学家重新拾起音乐这一主题与梅里亚姆、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
等人的努力颇有关系。20世纪70年代,布莱金的研究阐明了“音乐的外部因素如
何规定着音乐的结构,同时反对不顾或割裂音乐的内部或正式分析与音乐同社会
生活之间的关系”4。
随着人们对现代宏大叙事理论的不断消解,人类学家开始更多地将目光聚焦
在流行于群体中的音乐性的实践、理念和类型之中。人类学家在研究音乐时多认
为音乐活动是被社会文化建构的,并且由不同的制度和社会传统所形塑。音乐的
价值与意义就在于它其实是社会文化的某种隐喻。无论乡村还是城市,人类学家 1 Lévi-Strauss, C., The Raw and the Cooked. Mythologiques, Volume On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2 Merriam, Alan P. 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4 3 戴维·科普兰,音乐学,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8,(4).153-154 页. 4 戴维·科普兰,音乐学,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8,(4).154 页.
7
倾向于研究非商业性的音乐与口头传统,并将音乐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予以关
注。这样的研究与民族音乐学研究有着紧密的关系。不过也有学者拒绝将音乐视
为社会文化的领域之一,如安东尼·西格尔(Anthony Seeger)在《苏亚人为什么
会歌唱》1一书中将音乐与社会等同起来,音乐具有解读苏亚人社会的功能。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克利福德·格尔茨与文化批判理论的影响下,特别
是在马尔库斯、詹姆斯·克利福德等人发起的写文化风潮之后,人类学家开始强
调民族志应该是人类学家与信息报道人之间的遭遇、关系和对话。人类学者在研
究音乐时也多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共生关系,如Jocelyne Guilbault在她
的《zouk》一书中强调了与信息报道人共同作者(coauthor)的观点2。无疑,这样
的“写文化”反思带给音乐人类学的是一种范式的转型。
“写文化”之后的音乐研究具有高度的反身性,在众多研究中克里斯多夫·斯
莫(Christopher Small)提出的“Musicking”这一概念颇有人类学的意味。斯莫认
为音乐活动中的乐曲创作者和听众的地位是平等的,并且音乐的本质不在于音乐
作品(musical works)中,而在于每个人参与的展演中,在社会行动中3。换言之,
斯莫提出我们应该将music动词化,应该把音乐意义放置于考量每个人日常生活
中所卷入的音乐之网中,如听歌、唱歌、看电影和广告时接触的背景音乐甚至如
张贴音乐海报等诸事。斯莫的研究意义在于把我们从音乐本体中解放出来,提醒
我们应该关注音乐所建构的社会结构。
通过人类学音乐研究史的扼要回顾我们会发现,近百年来,人类学家们要么
视音乐还是音乐,要么将音乐视为文化的一部分,要么将音乐视为文化本身。本
文处理的视角在后两者之间,即认为音乐活动作为小康村的新生代劳工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可以帮助我们读解他们的生活与文化。
不过值得我们警醒的是,视觉中心主义的人类学界对于音乐仍未给予足够的
重视。20世纪80年代前,身体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缺场/沉默的状况已经得到
改善,现在有大量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透过身体视角来进行研究。只不过,正
如费尔南德斯(James Fernandez)所反思的那样,当下的民族志研究仍然是“一
1 安东尼·西格尔,苏亚人为什么会歌唱,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 2 Jocelyne Guilbault. Zouk: World Music in the West Ind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 3 Small Christopher."Musicking: the Meanings of Performing and Listening.". Music Education Research . 1999;
Small, C. Musicking: the meanings of performing and listening. Hanover and London, University,1998.
8
屋子的谬误”1,因为,我们知识生产的来源几乎完全借助于我们的视觉感官,
而对于听觉等其他感官的忽视已经影响到了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我们所要回归
的是突破视觉霸权掌控的整体(whole),以全面地探索人类文化所展示的丰富
多样的身体感觉和认知方式2。
我的小康村田野调查中,歌唱作为身体经验的曝露表征,凸显了空间、时间
以及时代背景的更迭。因此我们应该关注声音,关注音乐,关注他们的身体经验。
(二)音乐人类学中的流行音乐研究
流行音乐在音乐人类学研究中的兴起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大体与写文化思潮
对人类学学科自身殖民化反思的历史同步。20世纪70-80年代,西方人类学家开
始从研究非西方的异文化转而关注西方社会自身文化,进而发展到将自我他者
化。随着千禧年降临,全球一体化的深入,人类学家亦开始关注移民、离散与流
行音乐之间的关联3。
倘若我们要回顾人类学中的流行音乐研究就不得不回顾整个西方的流行音
乐研究。国外有关流行音乐的研究多集中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及文化研究学派
的研究震荡中。他们研究旨趣的分野从对大众文化的命名开始,即究竟是popular
culture还是mass culture。
法兰克福学派领军人物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在批判文化工业时着力
抨击了当时的流行音乐产业。主力干将洛文塔尔则似乎略显摇摆,他对mass
culture并没有那么鄙夷的态度。但其立足点还是没有脱离阿多诺开启的大众文化
批判的思路。对流行音乐不置可否的阿多诺、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等人从
未展开过任何经验研究,他们多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有关理性与资本主
义的关联4以及本雅明有关机械复制时代灵韵(aura)消失的论述5出发,认为文化工
业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而不是促进批判性思维与提升人的自由。流行
1 James W. Fernandez. “The Argument of Images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turning to the Whole”, in 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 Victor W. Turner and Edward M. Bruner, eds., pp. 159-187.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6 2 Bendix, Regina. “The Pleasures of the Ear: Toward and Ethnography of Listening.” Cultural Analysis 1, 2000:
33-50 3 Martin Stokes. Music and the Global Order.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33, 2004:47-72 4 Weber, Max . The Rational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Music, trans. Don Martindale, Johannes Riedel and
Gertrude Neuwirth.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58. 5 Benjamin, W.,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Benjamin, W. Illuminations.
Fontana,1977.
9
音乐作为文化工业的产物,也令大众日益行尸走肉,丧失独立思考的可能1。
发轫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研究学派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开辟了一
条与大众文化批判不一样的研究思路。该学派主要有当时任职于伯明翰大学的雷
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斯图亚
特·霍尔(Stuart Hall)等。他们试图为劳苦大众代言,并指出他们并不是资本主义
一味的牺牲品,其实际日常生活中亦是在抵抗。
的确,文化研究学派影响下的诸多研究给我们打开了观看包括劳工阶级在内
的底边阶级的某种视角。可问题是,在阅读过程中,你会体会到一种既成范式的
无趣感。劳工阶级都是铁板一块的么?他们所描述的是劳工阶级自我主体话语表
述还是研究者的研究话语生成?
20世纪80年代,流行音乐的研究开始深受其他哲学思潮的影响,例如越来越
多的研究者挪用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认为流行音乐产业中的许多成员(如歌手、唱片公司等)、音乐类型
和媒介构成了彼此关联的行动者网络世界2。这些行动者没有主客之分,没有中
心边缘之分,彼此之间构成了具有主体间性的依存网络。拉图尔的这一理论因为
打破二元对立和强调平权而走红社会理论界,但拉图尔的理论在给我们有益启示
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人性(humanity)在拉图尔的理论中消失了,无论人还是非
人的媒介都转变为网络中的结点(knot)。因此,在人类学的视域中,拉图尔的
理论是很难应用的。
与此同时,流行音乐的理论也在发展中3。翻开任何一份流行音乐的研究论
文,其中都会充斥着有关观众(audience)、工业(industry)、沉思/冥想(meditation)、
认同(identity)、地理学(geography)、政治(politic)、表演(performance)以及消费
(consumption)等主题。无疑,这些论题的讨论对于我们讨论当下江南农村地区的
流行音乐是有助益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西方工业社会城市高度发展,区
域不及广袤中国的西方都市必然会带来贫民窟和大量跨国移民的诞生,这其中所
蕴涵的理论背景与文化较为同质化的中国汉人文化传统是有出入的。
1 Adorno, Theodor W. 1941, “On Popular Music”, in Frith, S. & Goodwin, A. eds. On Record. Routledge, 1990.
Adorno, Theodor W. “Music and Language”, pp. 1–6 in Quasi una Fantasia: Essays on Modern Music,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2. 2 如,Gianni sibilla, “when new media was the big idea” : Internet and the rethinking of pop-music languages, in
Erkki Pekkilä, David Neumeyer & Richard Littlefield (eds.), Music, Meaning and Media. University of Helsinki,
2006.等。 3 Negus, Keith. Popular Music in Theory :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 Polity Press, 1996
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学家越来越关注在快速变迁和工业化语境下的商业
性流行音乐。1这之中有学者研究音乐听众和家庭生活的流行音乐2、特殊的音乐
事件,如英国伦敦的诺丁山嘉年华会(Notting Hill Carnival)节庆日3;以及特定流
行音乐风格的当地风情(local scene)4。
此处,我将着重回顾Alexander Dent和Ruth Finnegan的研究。因为他们的研
究和我即将展开的一样,都在处理转型社会中乡村与城市中音乐的具身性
(embodiment)表达。
Alexander Dent的《泪之河》分析了巴西圣保罗的乡村音乐5。Dent认为,乡
村音乐的类型折射了一种对快速激进变迁的焦虑。虽然生活在都市,但巴西乡村
音乐家将“乡村”视为一种音乐类型,实际上是对不可避免的压抑情绪与麻木的
都市生活方式的批判。他们的表演述说着有关“丧失”的泪之河,诉说着对爱、
乡村生活以及人与自然联系的泪之河。
Ruth Finnegan的《隐匿的音乐家们》6一书关注了当今城市化和工业化生活
中业余草根的音乐创作。她的田野地点是一个名叫Milton Keynes的英国小镇。她
认为人们之所以深嵌音乐中是因为音乐为他们的活动和关系提供了一个表达个
人和集体认同的语境以及形塑价值的方式,因为音乐伸延了行动在时空中的意义
建构。
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传播学、人类学研究者开始注意到网络改变了大众
的音乐社会,学者们逐渐强调日常生活中主创、明星、榜单、乐迷、MTV的重
要性7。但是,在进行文献阅读时,我却发现大量理论在中国农村应用的不适性。
在中国农村地区青年群体中的流行音乐中,是没有歌手偶像、乐迷与MTV视觉
主宰的。而这其中的理论缝隙也是我们在本文中需要予以讨论的。
不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20世纪末音乐人类学保持开放的姿态来接 1 “Popular Music Studies” in John Shepherd, David Horn, Dave Laing, Paul Oliver and Peter Wicke Continuum.
Encyclopedia of Popular Music of the World Volume 1 : Media, Industry and Society. London : Continuum, 2003 2 Daniel Cavicchi. Tramps Like Us: Music and Meaning Among Springsteen Fa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 Abner Cohen. Masquerade Politics: Explorations in the Structure of Urban Cultural Movem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4 其中较为出色的研究有 Sara Cohen. Rock Culture in Liverpool: Popular Music in the Mak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Christopher Waterman. Juju: a Social History and Ethnography of an African Popular
Mus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5 Dent, Alexander Sebastian. River of Tears: Country Music, Memory, and Modernity in Brazi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6 Ruth Finnegan. The Hidden Musicians: Music-Making in an English Tow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7 Roy Shuker. Understanding Popular Music, Seco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8
11
受新的问题,包容各种不同的方法论,研究范式的不断变化已经成为了常态化”。
1因此,我们在做研究时也不必墨守成规,依据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形进行主体间
性的描述才是最为重要的。
(三)中国作为地方的流行音乐研究
反观中国的音乐人类学研究,学者们关注的几乎全部都是少数民族的音乐或
都市音乐2。
中国作为地方的流行音乐研究关注的对象多为中国都市的流行音乐。此类研
究多聚焦于改革开放前后进入中国大陆的港台流行音乐,如金兆均以其业内人士
的身份对中国流行音乐所做的回顾3;付林以一个音乐家的视角进行了细致梳理4;
王思琦则爬梳了大量报刊杂志,对中国流行音乐进行了详实的社会史研究5。从
这些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明白地知晓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脉络,熟知一些脍炙
人口的流行歌曲问世的台前幕后,也能清晰地把握诸如崔健6、王菲等流行音乐
歌星的个人演艺生涯。
除却这些流行音乐史的研究之外,中国流行音乐研究中最主流的取向就是
“音乐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music)。他们或将中国作为地方的流行音乐视为一
种族群性、性别与文化政治性的表达7,或挖掘通俗歌曲与摇滚歌曲迥异风格背
后的意识形态8,抑或将中国整个的流行音乐/摇滚音乐放置于后天安门事件这一
政治背景下予以考察9。再如冯应谦(Anthony Fung)研究了中国城市中的卡拉OK消
费,指出中国的年轻人在唱卡拉OK时接受了来自中年阶层的“老歌”(oldies),
1 洛秦,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导论,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30 页 2 汤亚汀,城市音乐景观,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0;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上海:上海音
乐学院出版社,2007;萧梅,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3 金兆均,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4 付林,中国流行音乐 20 年,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5 王思琦,中国当代城市流行音乐——音乐与社会文化环境互动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 6 Paul Friedlander. China's “Newer Value” Pop: Rock-and-Roll and Technology on the New Long March. Asian
Music Vol. 22, No. 2, 1991: 67-81. 7 Bernoviz, Nimrod. China's New Voices: Politics, Ethnicity, and Gender in popular Music Culture on the
Mainland, 1978-1997. Ph.D. Dissertation, Univ. of Pittsburgh, 1997.
Ting Chunchun. Rock under the red flag :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Chinese rock music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phil. Disserta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1. 8 Andrew F. Jones.Like a Knife: Ideology and Genr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pular Music. Ithaca: Cornell
East Asia Program. 1992 9 Jianying Zha.China Pop:How Soap Operas,Tabloids,and Bestsellers are transforming a Culture[M].New
York:The New Press,1995;
Huang, Hao.“Voices from Chinese rock, past and present tense: social commentary and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yaogun yinyue , from Tiananmen to the present.” Popular Music & Society.2003, 26(2): 183-202.
Jones, Andrew.“The politics of popular music in post-Tiananmen China.” In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2nd ed., Wasserstrom and Perry e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148-165.
12
并未有任何形式的抵抗1。应该说“音乐的政治”这一取向的流行音乐研究开启
了中国流行音乐研究的重要范式。研究者多将目光聚焦于流行音乐的创作者和经
纪公司,分析歌曲中所体现的后毛时代的意识形态以及知识分子、音乐创作者的
政治性表达,而忽视音乐的聆听者作为传播者的重要性,并且他们的研究也并未
关涉到在农村地区流行音乐传播过程中所体现的政治意涵。
当然,中国流行音乐研究中的性别研究也是另外一条较为主流的范式脉络。
如周倩漪讨论了王菲与菲迷之间的隐匿的性别主体构成2。曲舒文则就“与中国
摇滚厌女症协商”这一主题展开了历时性的讨论3。
其他角度亦有学者如陆正兰、王亦高等人从符号学的角度对流行歌曲的文本
进行解读4,这类研究多局限于歌曲文本,虽试图用符号学理论去解析民众在音
乐活动中参与的重要性,但其研究并未把重心放置于民众在音乐的意义生产过程
中的作用与位置,并无很强的说服力。
这众多的城市流行音乐研究中,Jeroen de Kloet的研究最具人类学的趣味,
其对20世纪90年代盛行中国的打口碟这一文化意象予以深描和诠释,描绘了“下
海”和“与世界接轨”语境下催生的中国流行音乐5。
但是甚少有文献论及中国农村地区的流行音乐传播的现状。少数乡村研究的
文献提到农村地区的闲暇方式如卡拉OK等形式,但也只言片语地一笔带过6。甚
至还有研究者写作时仍然认为乡村的民众还在唱着山歌/民歌,还发出要抢救性
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号召。
因而,当下中国农村地区的音乐研究实为一种萨义德所言的东方主义,抑或
是一种内部殖民主义。至少在中国苏南地区,随着城乡一体化以及工业全球化的
深入,行政性质上仍属农村的地区已变成市镇模样,和过往学者所描述的农村情
境已迥然不同。因而在这样的地景上发生的一切也混杂得极其有趣。我们不能想
1 Fung, Anthony. Consuming Karaoke in China: Modernities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s.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42(2), 2010: 39-55. 2 周倩漪,从王菲到菲迷——流行音乐偶像崇拜中性别主体的搏成,新闻学研究第 56 期,1998:105-134 3 曲舒文,谁的“摇滚精神”——警惕中国摇滚音乐研究的定式思维,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
版),2012(3). 4 如陆正兰今年来的一系列有关中国流行音乐歌词的研究:陆正兰,传唱者拍板:流行歌曲歌众的文化角
色,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陆正兰,从符号学看当代歌词中的女性自我矮化,当代文坛,
2012(5);陆正兰,歌词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再如,王亦高,在时间中聆听:作为符号
而传播的音乐,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 Jeroen de Kloet, China with a Cut: Globalisation, Urban Youth and Popular Music.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6 游俊、龙先琼,湘西农民闲暇生活方式变革的文化审视,吉首大学学报,2000(01):52-56 页
13
当然地带着那些人应该是什么模样的思维定势来进行先验的观察与书写。
至此,在阅读中,我发现我的研究要描述当下活生生的农村地区的流行音乐
现状,并且打破视觉经验的桎梏,将音乐与人的身体经验相联结。
因此,我们还必须借鉴现象学,现象学号召我们悬搁(epocho)研究者自我的
主观臆断,悬搁自然主义的态度,走向事物本身。因为诸如“音乐政治”这类视
角很容易让我们的研究滑入既有成见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只见音乐中的政治,
而不见Musicking中所蕴涵的丰富的日常生活意义,所以我也将努力从主体间性
与他者出发来理解小康村的新生代劳工与他们的音乐。
三、田野地点概况
本文研究的田野调查地点位于江苏省常熟市古里镇小康村。依循人类学民族
志书写的惯例,我将根据地方志等文献爬梳出常熟、古里和小康村的区域梗概并
根据自己田野调查的实地观察予以扼要介绍,以给大家一个直观印象。
(一)常熟市的区域简介
常熟市位于江苏省东南部长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地处东经 120°33ˊ~
121°03ˊ,北纬 31°30ˊ~31°50ˊ。东邻太仓,距上海 100 千米;南接昆山、苏州;
西连无锡、江阴;北濒长江黄金水道,与南通隔江相望;西北境与张家港接壤。
地势低平,海拔大都在 3-7 米间。气候适宜,雨量充沛,四季分明。2005 年平均
气温 16.5 度,比历年平均偏高 0.9 度,年总降水量 934.7 毫米,比常年平均偏少
11.5%,全年日照时数为 1991.1 小时,略少于常年。
常熟自然资源丰富。境内水网交织,各河流湖荡均属太湖水系,其分布呈以
城区为轴心向四乡辐射状,东南较密,西北较疏。1
常熟市经济以轻工业而声名远扬。2012 年,常熟市完成全部工业总产值
4405.52 亿元,同比增长 3%。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361.18 亿元,同比增长
5.0%。2
(二)古里镇与小康村的行政沿革
1 此处常熟市简介摘引自常熟政府网,http://www.changshu.gov.cn/zgcs/zjcs/001001/001001001/,2013 年 2
月 18 日。 2 此处常熟市简介摘引自常熟政府网,http://www.changshu.gov.cn/zgcs/zjcs/001003/001003001/,2013 年 2
月 18 日。
14
古里镇位于常熟市东部,东与支塘镇、董浜镇相连,南毗沙家浜镇、昆山市
巴城镇,西与虞山镇接界,北倚常浒河,东北与梅李镇为邻。白茆塘、青墩塘、
苏家渝、清水港、淼泉塘、雉浦塘纵横贯通全境。204 国道在古里、白茆两集镇
穿过。淼虹公路经大虹桥衔接常浒公路,古淼公路南达 204 国道,北抵梅李镇。
全镇总面积 116.66 平方公里。在籍户数 22 054 户,人口 74 404 人。设 3 个社
区居委会、19 个村委会。古里镇人民政府驻古里集镇。1
宋代,古里境域属开元乡二十五都怀仁里、二十六都德仁里,双凤乡四十二
都集贤里,思政乡二十七都道文里及积善乡四十四都青村里。元代改里为图。
清雍正四年(1726 年)析常熟县东境为昭文县,境内属昭文县开元乡、双凤乡
及积善乡。1910 年常、昭两县设 35 乡、市,境内属罟苏乡(辖罟里村、苏家尖村)、
虹桥乡(辖淼泉、兴隆桥、塘口)、白茆乡(辖白茆新市、瀚上、李市等)。
辛亥革命后,常昭两县合并为常熟县,乡之建置未变。民国 18 年(1929 年)
实行以区辖乡,古苏乡属古虞区,虹桥乡属梅塘区,白茆乡属红豆区。民国 23
年全县调整区划,古里镇、苏尖乡、钱仓乡、南洙乡、鲇鱼乡、思念乡等属城厢
区;淼泉镇、虹桥乡、古段乡、塘桥乡等属梅李区;白茆镇、李市镇、瀚上乡、
蒋桥乡、芙蓉乡、紫霞乡、坞蚯乡等属唐市区。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古里境域分属常熟县梅南区、
苏州县唐市区、李白区。其时,日伪政权设置的区划,基本上参照抗战前的区乡
制。抗战胜利后,恢复战前区划。民国 35 年(1946 年)5 月,区以下乡镇进行
扩并:南洙乡、钱仓乡并人古里镇,属城区;思念乡、鲇鱼乡并人苏尖乡,古段
乡、寨角乡并人淼泉镇,属梅李区;紫霞乡、芙蓉乡、蒋桥乡、坞蚯乡并人白茆
镇,属唐市区。民国 37 年 5 月撤区缩乡,古里镇与苏尖乡合并为古苏乡。淼泉
镇一部分与塘桥镇合并为塘淼乡,另一部分与虹桥乡合并为虹桥乡。民国 38 年
2 月,再度设区,古苏乡、白茆镇属唐市区,虹桥乡、塘淼乡属梅李区。
新中国建立后,区乡(镇)建置多次调整。1950 年 3 月,境内古里乡、新
苏乡、莫陆乡、复兴乡、吴庄乡一部分(新桥、新泾、钱南、钱北)、淼泉乡、
章湖乡、陆浦乡属古苏区;清水乡、陈塘乡、塘淼乡属梅李区;白茆乡、李市乡、
坞蚯乡、紫芙乡属唐市区。1956 年,古里、淼泉、新苏、塘奎四乡划入古里区,
1 此处古里镇简介摘引自密永良、吴志刚、周永洪,古里镇志,《古里镇志》编纂委员会,2003
15
紫芙乡、白茆乡、李市乡一起并人支塘区。1957 年,撤区并乡,设古里、淼泉、
白茆 3 乡。1958 年秋,全县以乡建立人民公社,分别建立古里、淼泉、白茆 3
个人民公社。1983 年,恢复乡建制,分别为古里乡、淼泉乡、白茆乡。1992 年
12 月,撤乡建镇,分别为古里镇、淼泉镇、白茆镇。2003 年 2 月、10 月,原古
里镇、淼泉镇、白茆镇先后合并,仍名古里镇。
小康村,是苏州市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成立于 2005 年 3 月,由原南滃、北
滃、大滃、珠泾四个行政村整体拆迁后合并而成。1小康村位于古里镇南省级东
南开发区内,北靠 204 国道,南依锡太一级公路,东邻苏嘉杭高速,西接常熟市
区,交通便捷,位置优越。小康村(社区)以白茆塘为界分为庐山苑和珠泾苑两
个居住小区。新村规划面积 2085 亩,规划户数 2500 户,目前已入住 2284 户,
在册人口 8898 人,村委会设在陆家宅基。
1 此处小康村简介摘引自小康村党务村务公开信息系统,http://www.china-csdz.com/kc/xk/about.php
17
(三)小康村的地景深描
透过小康村地名图,我们会发现小康村当下的地景其实是江南地区推行的城
乡一体化政策的产物。因着区划,居民居住在两个小区,并且居民集居地的四周
被大大小小的工厂所包围。由于小康村同时也是江苏省常熟东南经济开发区的所
在地,所以小康村的交通很发达,陆路直通上海、张家港、苏州等地。水路也和
上海港连通。位于两个小区中间的小康村中宏新农中心也就成为整个新村落的中
心。这也是小康村夜市的所在地。通常而言,白天的小康村商业街人群稀疏,显
得空旷,但到了夜晚则是热闹非凡,人群涌动。而这样差异的地景与小康村的工
业园区性质也是暗合的。
(图 3 小康村中宏新农中心和白天的商业街)
此外,小康村庐山苑和珠泾苑两个小区的建筑格局都是统一的别墅样式。如
前所述,小康村是合并而成的,村民们被集中安置。一般而言,各家都在自己重
新分得的宅基地上根据村里统一给的图纸盖的三层别墅洋楼。因而,各家各户的
房子从外观上来看都差不多。不过,村民拥有的住房空间要比以前的老房子大得
多。所以,如果不把自己的小洋楼改造成一个个小型的纺织工厂的话,村民们通
常会将房屋出租给周围工厂打工的工人们。
18
(图 4 小康村地名图)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人类学传统的田野工作(field work)参与观察法。此外,涉及
中国三十余年流行音乐变迁历程部分则应用文献资料分析法。
我曾四度前往小康村进行我的田野调查,分别是:
2011年8月3日—9月20日,这期间我主要熟悉小康村的地理位置以及观察小
康村夜市点唱机的运作状况。
2012年1月10—13日,我再度前往小康村与之前认识的工友联络感情并进行
初次访谈。
2012年7月3日—9月3日,此阶段是我田野调查的主要时期,我在小康村淮海
兴业(常熟)有限公司加工课上班观察流行音乐在工厂的日常呈现,并在夜晚时
前往小康村夜市观察点唱机的点唱曲目与围观人群。
2012年9月24日—26日,前往淮海公司观看公司举办的联谊活动——歌唱比
赛,并进行相关补充访谈。
五、论文框架结构
本研究通过数月的田野实地参与观察,旨在探寻流行音乐对于新生代劳工的
意义,希望能藉此为这一群体的主体性与尊严做一注脚。本文共分六章,分别是
19
导言、流行音乐在小康村工厂、流行音乐在小康村夜市以及农业金属/网络歌曲
缘何流行、那些人,那些事——与音乐有关以及结论与讨论。
导言部分我将扼要简介我与田野地的渊源、田野地点相关具体情况以及我在
文献阅读中的疑问和本文理论立场。
第一章将回顾我在小康村某纺织业工厂的车间、宿舍等地点的日常生活中发
现的流行音乐与新生代劳工的生命相勾连的意义所在,以及厂里举办的歌唱比赛
这一仪式性狂欢背后颠倒的权力结构与新生代劳工的真实自我展现。
第二章将描述我在小康村夜市所观察到的新生代劳工藉由流行音乐所展现
的日常情感表达以及流行音乐是如何与脱域了的地域(对家乡的朦胧想象)、他
们的婚姻以及过往的生涯相关联。并指出流行歌曲的意义是这些第一线的传播者
兼消费者赋予的。
第三章将分析流行音乐是如何成为记忆的工具并与自我认同关联起来、与信
息科技变革如智能手机的普及带来的生活方式变迁关联起来。其结果是,新生代
劳工们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被汇聚成红歌、港台流行歌、网络歌曲/农业金属等
风格拼贴混杂而形成的声境。
第四章将追溯小康村中与音乐有关的张老板、“小丁们”以及小超的音乐故
事,进一步剖析身体经验与记忆是如何与音乐发生关联,为何新生代劳工产生不
了阶级意识以及流行音乐与自我认同的关联。
作为结论,最后一章将进一步阐明本文作者的立场以及所要批判的对象,并
通过反身性故事说明流行音乐中新生代劳工所彰显的主体性,他们是一群不断在
努力追求和表达丰富多彩的人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20
第一章 流行音乐在小康村工厂
一、再回小康,做工人,音乐在哪里?
2012 年 6 月底,学校一结课我便盘算着田野行程。7 月 3 日清晨我乘坐最早
一班从南京驶往常熟的大巴,于午时抵达常熟,再转乘城乡公交辗转到达小康村。
一下车,熟悉的空气扑面而来,熟悉的建筑映入眼帘,仿佛我从不曾离开过这里。
我即将要去工厂,去体验一名真正工人的生活。
因为不想麻烦去年结识的谭法师,我便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旅馆住下,开始了
我的找工作生涯。
走出旅馆,在小康村的街上四处张望,我一时也不知道去哪家中介,就随便
走进一家中介机构,表达了我想找工作,特别想进“新世电子”的念头。中介让
我交了 100 元中介费,并另交 30 元办了个中专毕业证。但是始料不及的是,7
月初学生工大量涌入小康村,特别是电子企业,我根本就无法找到工作。中介一
日一日拖着。无奈之下,我只好求助刚刚从淮海1离职的阿龙,请他把我介绍到
他们厂。虽然不能进拥有数万人的“新世电子”厂进行参与式观察,但也比耗着
没有任何进展强。
(图 5 小康村商业街中某职业介绍所)
1 淮海兴业(常熟)有限公司为笔者田野工作所呆的工厂,秉承学术研究的伦理,故用此化名来指称。该
公司位于常熟市东南开发区澎湖路,由淮海兴业(台湾)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占地面积 328.2 亩,其中厂
房面积 64 亩,公司主要生产的产品为棉纶布和涤纶布,产品主要用于服装、伞布及箱包等。
21
在阿龙的帮助下,在笔试、面试以及体检后,7 月 8 日下午,我终于与淮海
兴业(常熟)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
找工作之余,我丝毫没有忘记自己的田野工作。抵达小康村的当晚,我早早
便去夜市找点唱机了。可让我心冷的是,去年那个摊位的点唱机不见了。“完了,
不会连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都没了吧。”内心惶恐了起来。围着夜市转了一圈后,
我终于发现了点唱机摊位,原来它已经从夜市靠着居民区的一边转移到了夜市靠
着马路的一边。它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摊位面积也缩至原来的一半,局促得很。
周遭的摊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道路两旁的小吃摊点全部被取缔,并迁至夜
市的指定位置。摊主和工人们都在抱怨政府的这一举措。夜市空间的变化毫无疑
问体现着现代性与国家权力的渗透。
在摊点驻足了几天,我发现来唱歌的很多年轻男女不是情侣,而是夫妻,因
为他们时常带着自己的小孩。此外,让我惊愕的是,去年甚至在城市都风靡的凤
凰传奇不火了,取而代之的是《十一年》、《走天涯》等歌曲。港台流行国语老
歌方面,人们很爱唱张信哲的《过火》以及邰正宵的《女人是老虎》。
在淮海扎根下来后,没过几天,我发现我根本无法兼顾工作与在点唱机前的
参与观察。因为从 6 月开始,淮海的羽绒服面料订单就不断增加,根本做不完,
所以我这个刚进厂不久的人也被要求加班,并开始白、夜两班倒,我亦身处赶工
游戏的漩涡之中。
这样的遭遇迫使我临阵改变研究计划,转而观察工厂里的流行音乐。但后来
发现,厂里好像没有音乐。我进厂的那几天,根本找不到人听歌。这简直是打击。
难道我的研究计划统统要破灭了么?但既来之则安之,别无他法,我只能如此安
慰自己。
跟我一批进厂的有四个人,学锋哥、猴哥、马兄还有小刘。其中学锋哥、猴
哥、马兄因为没有熟人的荫庇就被分配去了染整车间,负责染布,成天与化学试
剂打交道。这是全厂最毒最累的地方,人员流动率很高。小刘因为他哥在厂里,
被分到了他哥的那个车间。而我由于阿龙的举荐,则被分到了加工课压光机组。
刚一进厂,老员工就跟我说,我的这个岗位是厂里最好的岗位,因为可以经常加
22
班。于是,每个人的心声——“我要加班!”成为我对淮海的第一印象。讲实话,
与我之前读到的富士康研究报告中对强制员工加班的描述截然不同1。
我在加工课2的工作从拉拖头开始,也就是帮工友拖拉等待压光的布料。从
来没有在工厂工作过的我,根本无法掌握用力技巧,这数千斤布料拉得东倒西歪,
凭得全是蛮劲。即使这样,别人轻轻松松就能拉到位的拖头,我怎么也摆不好。
轰隆隆的压光机声、闷热的环境,常常让我神情恍惚,我也常常莫名被老员工
“骂”。我着实不知道他们冲我喊的“把这个拿给我”、“把拖头放到那边去”、
“去把布排下”到底是什么意思,没有人有闲心跟你解释到底该怎么做,挫败感
升腾地快让我窒息。一天下来,回到宿舍的我已是浑身油污,洗完澡洗完衣服爬
上床就想睡觉。
我的脑子竟然也不想音乐了,只想每天能够把工作应付下来,不能被人瞧不
起。后来我发觉,其实我刚刚进厂时这样没有音乐的身体体验恰恰能说明问题。
初始时,我的身体经历着一种剧烈的声境(soundscape)文化震惊。因而我很容易
就得出这样一种判断,对于为了生计奔波的工人而言,音乐是一种隐匿的奢侈品。
而工厂里机器的噪声也悄然暗合了贾克·阿达利所言的“声音的政治”的结论,
并且认为工厂里的声景直接建构了情感的现代性,人们习惯机器的声响驯化着身
体,从和声细语到大声喊叫,含蓄私密的情感表达方式淹没在现代机器直接粗暴
的生产方式之中。工业化直接侵入改写了我们身体的律动与表达。不过后来发现,
这是我一个“文明化”了的身体初遇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时所遭遇的身体阵痛,
而他们——我的工友们并无我这样的痛苦感,因为我们过往的个人生命历程是不
一样的。当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不禁想问,新生代劳工真的被资本主义奴役埋葬
从而毫无生机和自主性么?劳工的流行音乐也如学者所评判的那样,毫无营养可
言么?我不能用我羸弱的身体登上道德的高地然后挥舞着无力的双手高呼新工
人的运动与解放。
不过正如苏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所认为的那样,我们从音乐中获得
的愉悦与音乐表达了我们身体的节奏有关3。工业社会中的身体节奏与工业社会
1 潘毅、卢晖临、郭于华、沈原,我在富士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2 日本人把企业部门称之为课,台企沿袭了日本的企业管理模式。加工课就是指该厂将布匹经过压光定型
等程序加工成羽绒服布料成品的部门。 3 尼古拉斯·加汉姆,解放·传媒·现代性——关于传媒和社会理论的讨论,李岚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5:252-253 页
23
中的音乐节奏是暗合的,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流行音乐作为一种“诊断依据”,显
现着当下社会的脉搏。
二、工厂生活中流行音乐的日常呈现
见我每日干得辛苦,甚至把腹部都划伤了。车间里的工友小郭便跟我说,“别
蛮干,你看你那么拉拖头不把自己累死才怪。你要学会偷懒,知道不?偷懒就是
会巧劲,会省力。”我呆呆地冲他们笑,一副无奈无力的样子。在小郭和他哥大
郭的指点下,我慢慢会拉拖头了。每日的工作也渐渐能应付,一周后便开始学开
压光机了。
因为小郭和大郭肯跟我说事情,我便跟他们走的很近。他们俩是亲兄弟,宿
迁泗洪人。弟弟小郭先进厂,觉得厂里效益不错,能经常加班,便把哥哥大郭也
介绍进来了。小郭是 90 年的,孩子一岁多了。夫妻两人没有领证,但在老家办
了婚礼。哥哥大郭和我同年,1986 年生人,已经是两个女儿的父亲。大女儿快
十岁,小女儿四岁了。车间里 16 个人,就我、大花、大海和组长阿波没有谈婚
论嫁,其他工友基本上都已结婚,并且生了小孩。所以每次一闲聊起来,我总是
那个被挞伐和质疑的对象。
他们总不相信我没有结婚,甚至没有女朋友,因为我已经 27 岁了,这是一
件太不正常的事情了。另外他们很好奇为啥我要从南京到这打工,我那笨手笨脚
的样子,也让他们总探问我之前是做啥职业的。被逼无奈之下,我只好告诉他们
实情,我就是来做毕业论文的。他们不能理解,怏怏道,你硕士?脑抽了?来体
验生活的?我只好点头。
不过这样也好,我不会跟剩下几个还没升班长的工友争抢升迁机会,再加上
自己脸皮厚,跟车间里的工友们也打得火热起来。我也觉察自己放松了很多,慢
慢知道每个布种都有什么样的特质,怎么样注意压光面来避免可能会发生的状
况,如压伤、压折、压花、沾污等等。
淮海染整厂主要有五个课室:染色、中检、染整、压光、后检,领导可以在
自己的电脑上看到每台机器的运作情况,并制定了一个考核指标:架动率,也就
是单位时间里机器的运行效率。工人们被要求每天工作的架动率必须达到一定的
标准。如果哪个科室的架动率能达标或超标,那么这个课室的每个人就可以获得
额外奖励。
24
尽管如此,厂里磨洋工式的工作方式并未消失,听歌就是其中之一。按照我
第一个星期在厂里接受培训的内容,上班听歌、玩手机是明令禁止的,但我很惊
讶地发现,每个人都会找到玩手机的机会和方式。我们压光车间比较吵,隔壁定
型机就比较安静些。阿刚开定型机时,耳朵里总会塞个耳机,因为无线耳麦的缘
故,你不走近跟他聊天是不大容易能发现他正在听歌的。大郭他们喜欢等机器跑
顺了,请旁边机器的工友帮忙照看下,然后跑去一个偏僻的角落抽烟听音乐放松
下,或者蹲很长时间的厕所,边听歌边玩手机。
我们课室的机器大体上需要你经常去查看生产状况,所以大家还算收敛。学
锋哥他们在染色课则有大把的空档时间,只要自己计算得好,几缸布可以一起进
一起出,机器染布期间通常会有一到三个小时不等的空档时间。因为他们有台湾
来的干部监工,不能经常玩手机,因此通常这个时间,就是他们听歌闲聊的时间
了。我几次去找他们都发现都左耳或右耳塞着耳机站在那听歌发呆。
我们都是一线工人,听歌闲聊玩手机好像是在打游击,但实际上领导都是心
知肚明的。对他们来说,只要你不过分,能把本职工作做好,架动率达标,他们
也不会太过问。当然如果你自己不能掌握这个平衡也很容易被批。那些做销售和
文职,可以天天面对电脑的,听歌就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
技术化时代的工厂工作往往被高层领导以信息化的方式进行全景化的监控,
既有的劳工研究多认为,“在强大而且受到内部劳动力市场保护的传统组织中,
工人会进行‘自发’的抵制,往往是个人地或集体地、短期地或永久地从工作中
撤退,这取决于替代性劳动力市场机会、集体资源以及制度背景等1”。“抵抗”
的姿态与国内劳工学界重新拾起的阶级分析话语,召唤新工人的崛起相契合2。
可是问题在于,福柯式的权力分析法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彻
底抛弃了那些存留于权力缝隙中的差异化细节,忽略了(音乐的)意义生产过程
3,空有政治正确的道德感。这一点,正是本文所要警惕的。而布尔迪厄的实践
理论则会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透过实践中时间的意义来审视劳工的日常生活。
布尔迪厄在《帕斯卡尔式的沉思》一书中曾有过这样一段很明晰的论述:
我们通常会遗忘使得实践尤其是经济世界的实践的一般秩序成为可能的经 1 马立克•科尔钦斯基等,工作社会学,姚伟,马永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91 页 2 如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任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吕途,中国新工人
——迷失与崛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3 Chaney, D. 1994. The Cultural Turn: Scene-Setting Essays on Contemporary Cultural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5
济和社会条件。贫民从游戏中被排除,被剥夺拥有一个职位或一项任务、成为什
么活做点什么的根本幻想,为了逃避一种平淡无奇、百无聊赖的生活的非时间
(non-temps),他们通常会求助于这些活动,如赛马前三名的彩金、足球彩票
等。这些活动重新建立时间的矢量,并暂时引进期待,这样就有可能摆脱一种无
理由尤其无投入可能的一种生活的无效时间。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尤其是年轻
人,也会在暴力行为或死亡游戏中寻找一种绝望手段,以便在别人面前为了别人
而存在,进入一种被认可的社会存在形式。1
如果说工厂上班时,音乐通常以一种隐匿的方式出现的话,那么下班后的业
余生活中还是可以发现音乐的存在和功用的。
我刚进厂的第二天,就见王班长双眼惺忪地回到宿舍,对大郭说,昨晚“炸
鸡”输了五百块。大郭笑他,准备回去跪搓衣板吧。
“炸鸡”也就是“炸金花”,一种常见的民间赌博游戏。淮海虽然也明文禁
止,但每到发工资前后,这项活动就特别盛行。我很好奇地跟他们去过几次。他
们玩得时候,很小心翼翼,把门关上,闲人不能入内。不能出老千,全凭运气,
玩得爽了也喜欢放上音乐助兴。他们很喜欢放那首《爱拼才会赢》的闽南语老歌。
欢快昂扬的节奏催生出人们内心的欲望,一种对于金钱的渴望。音乐和“炸鸡”
一起把人催生至一种可期待的时间范畴中。
流行音乐见证了工厂中时间与非时间的分野与转换。不止如此,音乐还成为
工厂劳作中个人历史与生命经验的表达。
小鹏是河南舞钢人,进厂已经三年多了。我刚进厂时,组长让他做我的师傅,
教我开压光机。但我那时我总觉得他一副淡淡冷冷的样子,时常无法理解他教给
我的操作说明,所以虽然也是一个宿舍的,但我和小鹏并未走得太近。直到后来
有一次我们俩一起上夜班,跑的布都是三四个小时的,也不大容易出岔子,就坐
在一起闲聊。
小鹏问我,你这个大研究生,跑我们厂研究流行音乐干什么呢?我无奈地表
示还没有想清楚。言谈中,我才知道,小鹏是舞钢体校毕业的,早先是练长跑的,
后来因为伤病,没能拿到省运动会前八名获得国家运动员的荣誉就退役了。小鹏
很爱田震的那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以前练长跑时就靠着这首歌把一圈又
1 布尔迪厄,帕斯卡尔式的沉思,刘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262 页
26
一圈的训练跑下来,现在开压光机时也常常在心中默念这首歌。虽然小鹏在工作
时没有塞着耳机听歌,但是小鹏内心一直飘荡着这首歌的旋律。
一切美好只是昨日沉醉
淡淡苦涩才是今天滋味
想想明天又是日晒风吹
再苦再累无惧无畏
身上的痛让我难以入睡
脚下的路还有更多的累
追逐梦想总是百转千回
无怨无悔从容面对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再多忧伤再多痛苦自己去背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纵横四海笑傲天涯永不后退
思绪飘飞带着梦想去追
我行我素做人要敢做敢为
人生苦短哪能半途而废
不弃不馁无惧无畏
桃李争辉飒爽英姿斗艳
成功失败总是欢乐伤悲
红颜娇美承受雨打风吹
拔剑扬眉豪情快慰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芳心似水激情如火梦想鼎沸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纵横四海笑傲天涯风情壮美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再多忧伤再多痛苦自己去背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27
纵横四海笑傲天涯永不后退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芳心似水激情如火梦想鼎沸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纵横四海笑傲天涯风情壮美
“人生苦短哪能半途而废,不弃不馁无惧无畏”是小鹏最爱的两句歌词,它
们会让小鹏觉得,曾经身为一个运动员的自己不能放弃那种拼搏的精神,所以他
在工作中也很拼命。小鹏的工作是我们课最好的,架动率最高,残次率最低。歌
曲对于小鹏而言是工作动力的源泉之一,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小鹏现在也是
一个女儿的父亲,《风雨彩虹、铿锵玫瑰》这首歌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音乐的
意义不仅源于音乐本身的结构(musical structure)1,更源于个体在生活中能动性的
遭遇与赋义。
(图 6 上夜班时的小鹏)
工厂生活中的流行音乐像一把多棱镜,每个侧面折射出的光影都透露出不一
样的生命情感与旋律。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考量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以及国家权
力是如何挤压他们的生命空间的,是怎样改变他们对音乐的认知的,也即阿帕杜
莱所言的,培养消费者转瞬即逝的愉悦,是现代消费规训的核心2。但是,我们
也应多去倾听他们自我的音乐故事,这才是流行音乐真正意义的所在。
1 Marshall, L 2011, ‘The Sociology of popular music,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aesthetic autonom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62., pp. 154 - 174 2 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刘冉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2
28
三、音乐狂欢:厂里的歌唱比赛
2012 年 9 月,中秋节前夕,淮海公司举办了“中秋联谊活动”。活动前,
工友大海就兴冲冲地给我电话了,“淮海要办唱歌比赛了,你来不来”。我虽然
有点犹豫,但还是一口答应了,“来!”电话那头的大海高兴地直跳起来,“好
啊,又能看到哥们了,我跟他们说下。”
我从衣柜里又拿出了我在淮海上班的工作服,匆匆从南京前往小康村。到小
康村时已是下午,我虽大模大样地走进淮海的宿舍区,但过保安的时候我还是出
了一身冷汗。
虽然离开差不多有一个月了,但是淮海的一切依然如旧。行政楼前面的空地
已经布置好了,一排排的桌子已经准备就绪。伴奏音乐也响了起来,是喜庆的进
行曲。我去宿舍转了转,我的床铺已被在我后进厂的小胡“霸占”。和大海、阿
刚、小郭他们聊了会天,便约着去广场准备边吃烧烤边看晚会。
据大海说,淮海每年都会在中秋节前举办联谊晚会,也就是所谓的唱歌比赛。
之所以在这个时节办活动是因为淮海(常熟)公司最主要的业务是从事羽绒服面
料生产,而同处古里镇的波司登羽绒服集团,则是淮海的最大主顾。每年 9 月底、
10 月初,随着羽绒服陆续上市,淮海厂里的生意也开始走向淡季。此后两三个
月的工作主要是为各大羽绒服厂商补货以及生产研发明年的新面料。并不太忙的
9 月底前后也是中秋节所在的日子,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淮海每年的忙碌生产
季之后的狂欢嘉年华。
事实上,这样联谊活动的仪式性味道很足。此处我将把淮海每年的歌唱比赛
/联谊活动置于仪式研究的情境下。
今年的联谊活动一共有十五组选手参赛。我随手拿起桌上的节目单,看了下,
很有趣。我把今年的演出节目兼比赛曲目做了一个简表如下:
29
表 1 淮海兴业(常熟)有限公司中秋联系活动演出节目(2012)
演唱者 曲名 歌曲原唱歌手 歌手所属地区 歌曲发行年代
张茜 你看 你看月亮的脸 孟庭苇 中国台湾 1991
马振 练习 刘德华 中国香港 2002
贺凯 东风破 周杰伦 中国香港 2003
徐杰 大海 张雨生 中国台湾 1992
曹春晓 我会好好的 王心凌 中国台湾 2005
孟祥风 新贵妃醉酒 李玉刚 中国大陆 2010
马志光 心如刀割 张学友 中国香港 1999
卢梦娇 盛夏的果实 莫文蔚 中国香港 2001
许涛 爱夏 胡夏 中国大陆 2010
耿晓杰 奔跑 黄征、羽泉 中国大陆 2003
贺娟 擦身而过 林心如 中国台湾 2003
王立强 简单爱 周杰伦 中国香港 2001
郁琪珍、吴莹 暖暖 梁静茹 马来西亚 2006
王启阳 痴心绝对 李圣杰 中国台湾 2002
张页锋 望乡 满文军 中国大陆 1999
郭振芳(高专) 无言的结局 李茂山、林淑容 中国台湾 1988
从上表我们即可看出,十五位参赛者中有四位演唱了大陆歌手的歌曲,其余
演唱的都是港台歌手的歌曲。此外,歌曲的年代上来说,多为十余年前的老歌。
我跟大海说,你咋不上去唱首《忘情水》。大海回我,你不懂了吧,人家上
去的都是干部,我算啥。我很惊讶,这样啊。不过看到我们课上去唱歌的是班长
和课长1,又看了下节目单,大部分演唱者都是陆干。事后,我问过马课长,咋
都是你们干部去唱。马课长无奈地说,如果我们不上就没有人上啊,厂里要求每
个课室至少上三个人啊,只好我们上了呗。他们两个人迥异的说法,实际上呈现
出工厂权力结构下不同的角色之间的缺乏足够的互动与沟通。
1 课长就是一课之长,部门主管的意思,相当于大陆的科长。
30
不管怎样,那晚的“中秋联谊”活动俨然变成了巴赫金意义上的狂欢节。“狂
欢节是全民性的一种演出,其中没有表演者和观赏者之分。在巴赫金看来,狂欢
不是供人们驻足观赏的,它甚至也不是供人们来表演的,它的参与者们置身其中,
根据有效规则来狂欢,每人都过着一种狂欢式的生活”1。
舞台上各个课室的大小领导轮番登台献唱,台下已经变成烧烤与酒精的海
洋。不必因为你是领导而鼓掌喝彩,不必因为你唱得不好而虚心假意。几巡过去,
我和工友们边聊边喝边吃边唱,已经有点搞不清台上唱的人是谁。再后来,不光
是自己桌自己车间的人喝,大家抱着酒瓶到处乱串,或去找老乡或去找兄弟。而
让我惊讶的是,中检和后检的女工们也加入到我们恣意的行列中。淮海举办的这
次联谊活动俨然变成了狂欢派对,领导们从过往记忆里抽拉出经典歌曲,原本打
算一本正经比赛,但当时的状况是台下已经沸腾,台上估计也一本正经不起来。
台上台下已然没有表演者与观赏者之分。甚而,当有自己熟识的领导演唱时,还
有人上去敬酒,大家欢乐成一团。王班长后来跟我说,干,本来紧张兮兮的,往
台上一站发现没人鸟你,你自己也就没啥顾虑,自爽起来。
那晚,我、大海和原本内向的阿刚还跑上台做了几把游戏,挣了些洗发水。
借着酒精站在台上回答那些与歌曲有关的题目时,我都觉得自己完全没有怕自己
已然不是淮海工人的身份被拆穿,也许那时根本也没有人管这件事。
最后登场的郭高专的演唱原本理应获得众人捧场欢呼。但仪式性的狂欢结果
就是,她的演唱变成了鸡肋,甚至最后谁也分不清谁,更枉论认出高专,只是偶
有些人鼓掌。用维克多·特纳从范·杰内普引申发展而来的仪式理论来说,那个
晚上我们都处于分化/阈限/再整合(separation/liminality/reintegration)的过程中。
在联谊活动这一近阈限(liminoid)阶段中没有人压着你去做工作,没有人催着你的
架动率,异质、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被予以颠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平等被拉平,
因而处于反结构/共态(communitas)之中2。音乐比赛作为狂欢节,为年轻的劳工
们构建了一个戏谑的公共空间,而这也恰恰暗合了特纳所言的舞台剧这样题中之
义。
1 陆道夫,狂欢理论与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02(4):23 页 2 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2-104
页
31
如果说前文认为在福柯权力分析话语体系的缝隙中,我们需要看见布迪厄所
言的实践中时间在意义生产过程中作用的话,那么此处,我们会发现,透过巴赫
金所言的狂欢节理论与特纳的仪式理论,虽不论仪式的主办者意欲如何,但对劳
工而言,这场没有自己的音乐比赛俨然变成了自我另一面的呈现,这样的呈现暂
时性地颠破了权力结构的束缚,在共态的时间中直指当下真实的自我。
那晚我们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回去的,只记得散落一地的烧烤串,而明天之
后,我们还是得回到“结构”之中,该干嘛干嘛。音乐盛宴的狂欢也将转入地下,
成为隐藏的文本,正如我在之前描述的那样。
32
第二章 流行音乐在小康村夜市
一、日常生活的情感表达:音乐及其他
七八两月的小康村格外热闹,人头攒动。如前文中所言,音乐随处可拾。人
潮的熙熙攘攘,三三两两意味着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繁盛?恐怕不是,在我看来
是躁动与不安。
躁动可以通过点唱机前演唱者的歌曲反映出来——或为了示爱,或因找不到
工作而徘徊,或因厂里工作让人倦累等等,人们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唱歌。亦可
以通过不时呼啸而过的摩托机车或电动车承载的音乐和各个摊主店家此起彼伏
的音乐声看出来。也许我们可以习惯性地套用布迪厄的“区隔理论”,将我在小
康村听闻的音乐映射整个小康社会的阶层,得出“音乐是他们社会身份再生产标
志”的结论。但我着实无意如此,因为,事情没那么简单。
还记得我七月初去找中介时遇见的那几个一同来找工作的工友。他们都有亲
戚朋友在小康村打工,还能跟中介耗得起,因为至少住宿的问题可以解决。晚上
在夜市也时常能碰到他们。他们的神情中跟我一样充斥着焦急与渴望,无论唱歌
还是购物,神色中总是透露着不安。
学生工——他们也郁闷——和我一样,知道总有一天会离开,所以虽然工资
低点,倒还可以忍受。不过,是留在实习的厂里还是另谋出路,到了选择的关口
总还是会让人感到不安。
而那些工友在结婚生子后压力也会陡增。他们都有兄弟姐妹,很少是独生子
女。父母大多也是朴实的农民,家底也不足以荫庇两个以上的子女。音乐作为一
种闲暇的消费文化,学生时代是最容易汲取和浸润的,初中毕业便出来打拼的工
友自工作后甚少会一个人独自聆听音乐,更不用说婚后了。
如果我们只是考察音乐,似乎其是微不足道的。因为音乐的消费活动并不会
成为一个独立的娱乐活动,其总是和其他娱乐项目相关联,也穿插在诸如吃饭、
喝酒、聊天、逛街等活动中。但是音乐的重要性也就在于其的不可或缺性,其虽
很少独立出现,但绝不可缺少。
我们如果把音乐与酒精、工作、赌博并置在一起,便会发现,音乐中的躁动
与不安其实是物化社会的真实写照,也即哈贝马斯所言的,“社会关系、社会经
33
历与事物的一种特有的同化,就是说与我们可以知觉和支配的客体的同化。这三
种世界通过生活世界的先天十分复杂地合作化了”1。
小康村最不缺的就是吃饭的地方,夜市的主体也是一排排的大排档和小吃摊
点。我常常问自己在田野中干得做多的是一件事是什么。我想除了工作就是喝酒
唱歌了。几乎每天都会和几个工友一起出来在小康村夜市的大排档或是小店小酌
几杯。喝酒唱歌不仅是打发时光、舒压的方式,更是应对生活抑或未来空洞茫然
不确定的一种方式。
我和工友们时常会聊起未来,但他们总会和我谈论现在:这个月加班费谁谁
谁拿了多少,我才多少;布做的差不多了,马上又要到淡季了,那时就没那么多
钱了;老婆一下班就打麻将也不帮我洗衣服,等等。甚至初为人夫的胡胖子也会
经常和我吐槽他怎么纠结于与妻子、丈母娘的关系。即便谈及未来,他们也说,
再干几年,把家里结婚盖房时欠下的钱还了。然后自己单干,做做小生意。在我
的淮海田野中,大海不止一次跟我说起他要离职创业的想法,并时常与我讨论到
底做什么赚钱。但当我与其他工友说起大海的这个想法时,大家都不屑一顾。原
来大海从进厂不久便开始散播要离职创业的消息,但一直都赖在厂里。当我后来
又问起大海怎么不走时,大海跟我说,“我现在好歹能拿上三千多块,要是走了
自己干,不一定比现在好啊”。当下的理性算计让大海时刻想走却又不得不留在
了淮海。
虽说社会性的结构给定了小康村新生代劳工的音乐语境(context),但事实上
小康村的流行音乐始终与个体/“我”的情感生活相关。即便是 2010 年流行的凤
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歌中与爱情无关的歌词“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
我用心把你留下来”也常常被男工友用来向女工友来表白。音乐的意义在聚焦和
互动的空间被生产出来,指向社会情境与个人境况的混杂体。不过,当下中国
“‘我’终究是不可化约、不可抹去的强大存在,快速而深刻的社会变迁极大地
扩大了机缘、命运无常变幻的限度和个人选择的空间,‘我’在境遇的剧烈变化
中被赋予了更突出的位置,同时,社会变迁已经整体性地把‘家乡’所在的农村
推向了价值位阶的底部——如果说还没有变成负值的话,于是,相对于价值虚空
化了的‘家’,‘我’的重量便更形突出2。”因而,音乐活动的趋“我”化也
1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上册),洪佩郁、蔺青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4. 2 杨德睿,在家、回家:冀南民俗宗教对存在意义的追寻(香港树人大学当代中国研究论文系列第二辑).
34
是当下小康村音乐分布的一个重要面向。
石瑞 (Charles Stafford) 曾用两套相辅相成的“模式 —认知操作”
(pattern-recognition exercises)来阐释中国人面对不确定时的情境1。一套是“数字
指向”的认知,比如算命、看八字、看日期;另外一套则是人际关系“互惠”的
认知,重点是“往来”,其更具体的含义是“分离与重聚”(separation and reunion),
这里包含了更多的道义,欠债、还情、重新整合的关系。在“分离和重聚”模式
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要不断铺垫建构自己的(拟)亲属关系网
络,因为通过来往,社会生活才会有可能性和未来。
显然,通过音乐、酒精和赌博等活动,来自内陆地区的年轻工人不断在小康
村构建着自己的亲属关系网络。但日益扁平化的亲属关系实践,以及经由九年义
务教育阶段所树立的具有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无神论,并不能解决人内心的焦
虑,亦并不能通过过去或当下的经验/经历(experience)提供选择来指示未来,相
反,可能会面临另外一种状况就是“自由的眩晕”(the dizziness of freedom)。
因而,音乐连同其他消费文化的功用之一就是让个体在当下这个时代的不确
定的茫然感得以获得暂时的凝固,让胆小羞怯焦虑的自我转向肯定放松与自信,
因为音乐构建并勾连了自我和共同体的关联。换言之,音乐成为新生代劳工面对
趋“我”化的自我情感与企图掌控未来的一种实践。
二、恋爱、婚姻生活中的流行音乐
当慢慢习惯每日十二个小时的工作,慢慢不再纠结有没有音乐的时候,我竟
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
大概是我进厂的第十天,我在宿舍四楼的公共淋浴间洗澡,耳边传来了一个
幼童的声音,“爸爸,帮我后背擦下”。我很好奇的扫了下对面的淋浴间,门开
着,一个比我年纪还小模样的工友在给儿子洗澡。孩子大概五六岁的样子。我不
禁神伤起来,厂里的男工友 20 岁左右基本上都已经娶妻生子了,虽然很多没去
领证,但是人家毕竟结婚了啊。我这个剩男还是孑然一身。
香港:香港树人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2010. 1 Stafford, Charles .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next? In: Astuti, Rita and Parry, Jonathan and Stafford, Charles,
(eds.) Questions of anthropology. Berg, Oxford, UK, 2007: 55-76
35
晚上夜班,我乘着机器跑顺起来,不大可能出异常的时候跟一旁的小郭说起
这个事。他笑我,“羡慕了吧,过两天我媳妇也要来看我了。你说你还念书有啥
意思?”。
我虽无语,但也在琢磨个中名堂。音乐和他们的婚姻有没有关联呢?
上白班时,晚上八点下班常常会叫上阿刚和大海出去吃夜宵。他们喜欢喝点
啤酒,我们就在“河南小吃”点上一盆凉拌菜,一人两三瓶啤酒开喝起来。喝完
我们借着微微酒意,功放起手机里的音乐,我这才发现大海手机里存有很多颇具
“农业金属”风格的网络歌曲。歌词多是“妹妹寂寞哥哥来陪你”等等之类,伴
着歌声,各种空虚寂寞感在有些闷热的夏日空气中飘荡。大海是甘肃人,比我小
两岁,一直马不停蹄地找女朋友。在老家舅舅的帮忙介绍了个对象,自己在小康
村的新世电子厂还谈了个老乡,然后自己在网上还和两位女性网友暧昧着。除了
我之外,大海是当时车间没有女友的工人当中是年纪最大的,他每天一有空就跑
到楼下宿舍区的黑网吧上网或者躺在宿舍床上给某个身份不明的女生打电话。有
次大海来我们宿舍玩,就我一个人还在睡觉,等着上夜班。他见我睡觉,无聊之
余就在我们寝室给他网上的一个女朋友在电话里念起诗,唱起歌,弄得我立刻睡
意全无。
跟大海不同,阿刚平时是一个内向不多话的人。他是 1992 年出生的山东汉
子,个头不高,瘦瘦的,但非常精神。阿刚的宿舍跟我的宿舍挨着,下班休息时
我经常去串门。阿刚宿舍有个大专生黄寺,比我早进厂两周。黄寺很爱聊他在苏
州某物流公司工作的见闻以及他为了他在常熟上大学的女友来淮海打工的故事。
那日我、阿刚还有黄寺三人去 2011 年我经常吃饭的那家河南小吃店喝酒。在黄
寺狂侃下,我们酒喝得特别多,阿刚也聊得很开。尽兴时,阿刚给我们看他山东
老家的照片,讲起了他去年在老家的一段往事。
阿刚两年前在亲姐夫的介绍下来淮海工作,去年因为家里催得紧,通过相亲
给他介绍了个女人。阿刚觉得还合眼,不是很讨厌,就辞了淮海的工作,回老家
结婚了。
阿刚家里是做生意的,家境不算差。父母给阿刚和他弟弟一人盖了一栋楼房。
楼下做生意楼上住人。阿刚的婚礼办得很隆重,虽然两人没有到年纪不能领证,
但在乡亲邻里看来这段婚事很美满。可一个月后,还是出状况了。阿刚的老婆迟
36
迟没有怀孕的迹象,就被阿刚就带他老婆去市里的医院看,医院诊断为不能生育。
阿刚就急了,问他老婆怎么回事。他老婆这才告诉他,婚前就知道自己不能生育。
阿刚和他的家人怒气冲天地跑到女方家里,痛揍了老丈人,把婚给离了。
阿刚说到这里还是愤恨,连喝了两杯。阿刚这个算“离婚”过的男人后来去
北京转了一圈,还是没什么好工作可做,又累又无趣。就辗转二进宫回到淮海继
续开定型机。
那晚,我们一人差不多喝了一箱啤酒,十一点多才结束,走出小吃店大门时,
已经踉跄地需要互相搀扶,情不自禁地狂吼着《伤不起》。
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
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
恩爱过后 就不来找我
总说你很忙 没空来陪我
你的微博里面辣妹很多
原来我也只是其中一个
万分难过 问你为什么
难道痴情的我不够惹火
伤不起 真的伤不起
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到昏天黑地
电话打给你 美女又在你怀里
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心如血滴
伤不起 真的伤不起
我算来算去算来算去算到放弃
良心有木有 你的良心狗叼走
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彻底忘记
粗看起来,这首歌的歌词文本内容和阿刚的感情生活很不搭,但“伤不起,
真的伤不起;我算来算去算来算去算到放弃;良心有木有,你的良心狗叼走;我
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彻底忘记”这四句节奏鲜明、朗朗上口得让我觉得很应景、很
好听。我们不断重复狂吼着这几句。我的工友们,那些“不专门从事音乐活动、
以此谋生的人,与那些行色匆匆追赶车船的音乐家相比,没有那么高超的技术水
37
平来演奏乐器,成为行家里手,而只是在周末玩玩而已,但却有更丰富的内容要
表达1”。歌曲对于个体的意义如同后现代性所言的破碎性,歌曲中的某句歌词
便可和一个人的生命故事相连接,“伤不起”亦成为当下全球化市场化变迁中国
当下个体的内心独白。
阿刚和黄寺也打开手机功放着这首歌,我们三个醉汉“伤不起”地回去了。
达内西引用 W.B.基所做的关于迈克尔·杰克逊歌曲《Beat It》的调查,发现没有
人知道“beat it”是男性手淫的口头俚语2。再如《爱拼才会赢》这首歌当年是台湾
政党候选人的广告歌,夜市台湾劳工进步工会的抗议歌曲3。歌曲的意义在传播
中潜移默化地发生了转换,甚至面目全非。
因而,我们会发现流行歌曲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其“意义仅仅存在于它们的
传播过程中,而不是存在于其文本中;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文本是至关重要的,
需要将它们放在与其他文本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中来理解,而不是因为或通过它们
自身来理解,因为这确保了它们的传播4”。
大海和阿刚算是婚途不顺的,小郭则不然,他正处在婚姻甜蜜期。2012 年 8
月底,厂里的订单忙得差不多了,小郭也不想加班,就让老婆带着儿子过来看他。
小郭没在工厂住,在离工厂不远的村民别墅中租了个单间。那日,我一个人无趣,
和大海跑到点唱机那儿玩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原来,小郭正在给他老婆献
歌一曲,深情款款,让我和大海很是羡慕。小郭和他老婆算是先结婚后恋爱的那
种。而这样的个案在淮海厂里不胜枚举,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即便像我们车间的郝兄,他的妻子虽是经人介绍的,但他们是之前从未说过
话的小学同学。婚后他的妻子也来淮海上班,在中检部门核检前工程布匹的异常。
他们的恋爱和婚姻生活也是在小康村进行的。他们夫妇俩一般都会选择一起加
班、一起下班、一起做饭、一起逛小康村夜市唱歌。小康村热闹的夜生活中各个
店面用来招徕顾客的流行音乐及其空气漂浮的各种迥异声响无疑作为一种能指
接合(articulate)了小康村外来打工者的生活经历和个体记忆,这之中自然也包括
他们的恋爱经历。
1 戴维·科普兰,音乐学,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8(4). 2 马塞尔·达内西,酷——青春期的符号和意义,孟登迎、王行坤译,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62
页 3 夏铸九,休闲的政治经济学——对台湾的 KTV 之初步分析,户外游憩研究,第五卷,第二期,
1992:1-11 页 4 约翰·菲斯克,杨全强译,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3
38
大郭在有第二个女儿后,格外节约,甚少和我们这些单身汉出去喝酒唱歌。
阿刚和大海说,以前大郭也经常和他们一起的,几乎每天都出来。我和大郭一个
寝室,他确实很少花钱。每日下了班吃完饭就窝在宿舍看看都市言情小说,看累
了倒头就睡。婚姻不仅意味着两个人的结合,更意味着音乐消费的空间转向。大
郭看书时会随便放点音乐听听,我有问过他,你看书时为啥放歌呢?他说,不然
太冷清,你们都出去了嘛。
音乐从外而内的空间转向与内外互动的空间肌理实际上也勾连了年轻打工
者的日常生活。年轻的劳工肩负着养家糊口的重担,在繁重的工厂劳动与生活压
力之下,宿舍与夜市迥异的音乐空间消费——清冷与热闹的差异也呈现了工作与
婚姻、家庭的双重影响的关联。对他们而言,音乐是婚姻生活中的润滑剂,也是
日常生活中一个常在的他者,打发着无人对答的寂寞感。
三、回到点唱机:音乐展示的社会空间
2011 年从小康村回来,我就一直在想,小康村为什么有点唱机但是没有 KTV
包房?人们为何要在点唱机唱歌?点唱机和都市里的 KTV 有何不同?答案一直
都不甚明了。2012 年在小康村待的这两个月让我慢慢有了自己的答案。
工厂里的工作确实比较单调无聊。拿我自己干的活来说,每天除了要拉拖头
之外,最重要的是把压光机开好。开压光机一个很简单也很要命的动作是,查检
经由机器压光的布有没有瑕疵。虽然每日压的布种不一,但是机器过布的速度在
20-30m/s 之间。初期,我连布面都看不清,更别说布面可能出现的瑕疵。慢慢地,
在郭氏兄弟的示范帮助下,我虽然能够看到瑕疵,并且知道机器的哪个部位沾上
了什么东西,该怎么处理,但一天下来身体也会有很强的疲倦感。厂里每天都会
通报每个台机器压布的异常率,也就是每一万码布的次品率,与工资奖金挂钩。
因此大家虽会偷懒,但还是很认真的。
每天早八点到晚八点,或者晚八点到早八点,十二个小时的工作时长雷打不
动。工友们也特别希望能在双休日、法定节假日上班,因为有双倍或三倍的工资。
因此,无论我们在下班后怎么狂欢喝酒唱歌打牌,每个人都是深知那个底线的,
就是不能让自己第二天上不了班。
因而,我们没有整段整段的时间可以泡在 KTV,点唱机唱歌十元三首,十
几分钟的时间刚好可以满足我们的内心情绪疏泄与表达的需求,再加上喝喝酒唠
39
唠嗑,最迟十一点半也躺下了。碎片化、商品化的时间连同音乐展示着资本主义
经济洗礼下的社会空间逻辑。因而我们可以通过音乐消费窥见工厂劳工体制规训
下的身体——现代性的身体。
(图 7 点唱机前熙攘的人群)
点唱机前的歌唱展演(performance)最受欢迎的无疑是女性。我们厂男工多,
但周围诸如新世电子之类的电子厂数万人中有一大半都是女工。女工也会成群结
伴来唱点唱机,那时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不管这个女的唱得有多难听,
都没有什么人会离开点唱机的摊位。倘若是男性,若是不好听,没唱两句,围观
的人群就会走掉一半。大海说,很多男的过来就是来想“泡马子”的。真是一语
中的。女性在点唱机前的唱歌活动成为一种被他者凝视/观看(gaze)的展演,正如
劳拉·马尔维认为的那样,“在通过两性的不平衡而得以组建的世界中,观看的
愉悦已经分裂为:主动/男性与被动/女性。这决定了男性的凝视将其幻想投射
在被相应地设计的女性形象上1”。不过更进一步,我们可以从黑格尔互为主客
体的主奴辩证法将之视为一种相互凝视,正如那天我和大海的老乡,也就是大海
的绯闻女友一起吃饭聊天时说到的这个话题。她说,那些女的难道就不想找男人
吗?大家各取所需嘛。我在诧异之余也明白,“窗户纸”的背后就是点唱机所构
建的社会空间裹挟了年轻打工者的原初性欲,从而以歌唱展演的方式展开罢了。
此外,点唱机前的打工男女,每个人都怀揣着各自的情绪经验,如前所述,
或与工厂的生活有关,或与过往有关,或与感情有关。因而,他们所演唱的歌曲
的意义是当下的,是在互为主客体的当场互动中实现的。“歌众与歌曲生产者,
这两个群体之间,没有谁是意义的主宰者。歌众可能也意识到生产意图,但不会
1 转引自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90 页
40
把词曲作者的意图作为意义的指归1”。构筑点唱机音乐墙(music wall)的音符此
时亦如皮尔士所言2,“指号或者表象(representamen)是这么一种东西,对某人而
言,其在某个方面或以某种身份代表某个东西。它对某人讲话,在那个人心中创
造出一个相当的指号,或许是一个更加展开的指号3。”而这样的指号亦在这些
新生代劳工的身体上扎下根,不断累积,转而成为他们的记忆与体验的一部分。
点唱机所创造的社会空间如同林文刚(Casey Man Lum)所言,是一种卡拉 OK 场
景(karaoke scene)4。在这样的场景之中,人们之间形成了二元角色,即围观的人
群形成了一个流动的社群,且这之中演唱者与观看者的角色是不断切换的。倘若
我们关照戈夫曼的舞台(stage)戏剧理论,那么小康村夜市点唱机创造的社会空间
中前台和后台的之间的关联是很模糊的,每个人都是一出戏剧,都戴着一个假面
(persona)。
来唱歌或围观的三两成群的年轻劳工如我和大海,或是阿刚,抑或小郭和他
老婆,我们的社会关系是扁平的,因而,还算平等和放松,但也创造了一个近似
个体化的生存空间。小康村的每个工厂,每个月都有大量劳工进进出出。我们司
空见惯了生面孔,在点唱机那儿唱歌也不觉得丢人。与都市里的 KTV 不同,一
个貌似开放空间矗立着一个个小小的私密空间。音乐展现的情绪在那里滋长与传
达。因而,点唱机所创造的公共领域其实被流动的利己性/私密性(mobile privacy)
占据5。
当然,扁平化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小康村的工厂很多都是台企,例如淮海、
新世电子。台企模仿日企,有一整套严格的晋升体制,且重要干部基本都是台干。
台企一般的科层结构由高到低是这样的:董事长、总经理、副总、协理、副理、
襄理、厂长、课长、组长、副组长、班长。大陆的工人能干到组长就不错了,多
数课长级别(及以上级别)的都是台干6。
1 陆正兰,传唱者拍板:流行歌曲歌众的文化角色,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 2 Charles Sanders Peirc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vol. 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228 页 3 该段原文如下:A sign, or representamen, is something which stands to somebody for something in some
respect or capacity. It addresses somebody, that is, creates in the mind of that person an equivalent sign, or perhaps
a more developed sign. 4 Casey Man Lum, In Search of a Voice: Karaok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Chinese America,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6 5 保罗·杜盖伊、斯图加特·霍尔等,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霍炜译,商务印书馆,2005:
24 页 6 台干是指由台湾母厂派遣至大陆工厂来进行企业管理的干部。
41
台干是陆干或溜须或打点的对象,换句话说,陆干必须和台干打交道。因而
很多场合,长时间的交往也让陆干沾染了一些台干的生活方式。比如唱歌、骑车
远足。我们加工课的组长陈胖是陆干,有时他也跟我们一起跑到点唱机那儿唱歌,
我发现他通常会选比较经典的台湾老歌,并且唱得很是那么回事。后来他跟我说,
“跟台干在一起你总要有一两首拿手的歌的”。所以你会发现在小小的点唱机的
那些音乐其实还包含了工厂科层体系文化在个人身体之上的投射。
而事实上,除却性别和工厂权力结构的差别之外,点唱机所构建的公共空间
中我们还能发现一种源于地域的类族群差异。
在小康村工作的劳工大多都因自己的老乡/朋友滚雪球式的介绍而带进来。
除了平常的沟通和交流之外,在小康村夜市喝酒吃饭唱歌也是联络感情的重要方
式。因而,我们会发现点唱机前结伴唱歌的小群体在他们所演唱时的互动也透露
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以及他们内部的微观权力关系。
此外,音乐终究会透露很多秘密,这些秘密在迁徙漂泊的人身上就会显得格
外清晰,只是不自察罢了。还记得我曾问过在点唱机前听过一位连唱三首粤语歌
的年轻小哥,你在广东呆过?他惊诧地问我,你怎么知道?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轰轰烈烈的普通话运动席卷全国,导致了当下普通话
歌曲的流行,而那些方言流行歌曲则昭示着年轻打工者浓郁的漂泊地域色彩。闯
入一个不属于自己语言区域的地方是很难找寻到认同感的。方言流行歌曲就成为
打工者试图融入当地社会的一个痕迹。正如曾在广州打过工的工友阿黄有次跟我
说的,“你刚去的时候,总听人讲粤语,当地人都不怎么瞧得起我们这些人的,
因为我们讲不起粤语。不过经常会听些粤语歌。后来,时间久了,周围老乡也会
跟你说,就会了那么点点,不过也不大敢说。”
为何是粤语、闽南语的歌曲,而不是吴语或是中国其他地区方言除却普通话
歌曲之外最流行,原因很多。一来,港台与广州是中国流行歌曲的发源地,大量
的粤语、闽南语歌曲在八九十年代就传入内地,并红极一时,如《爱拼才会赢》;
二来,港台和广州(珠三角地区)是改革开放后被国人艳羡的地区,经济发达、
生活富裕。会粤语、闽南语一度是高人一等的身份象征,对南中国的想象与向往
使得珠江三角洲成为中国农民以及内地小知识分子纷纷下海、争相前往的“朝圣
地”。因而,流行歌曲实为国家政治权力与市场经济逻辑的双重隐喻,述行着中
42
国当下芸芸众生的心态与欲望。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流行音乐从无差别的国家
威权意识形态走向了后革命时代欲望与情感的符码1。空间、时间、记忆深嵌于
生命谱写的音乐中。
1 周志强,声音的政治——从阿达利到中国好声音,中国图书评论,2012 (12):34 页
43
第三章 农业金属/网络歌曲1缘何流行?
前两章笔者关注的是工厂以及小康村夜市中流行音乐的不同存在形式和其
与新生代劳工日常生活之间的关联。本章我将把视角转向小康村流行音乐传播的
特征及其原因上。
很多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研究都指出:不同于建国后,举国上下都是毛主义式
用于政治宣传的红歌2,后毛时代开启的邓丽君、张明敏流行音乐世代经历了单
一到多元的音乐形态3。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那种一首歌能红遍大江南北,
妇孺皆喜的时代。而进入新世纪,这种现象已经很难发生。
我和阿刚、大海聊起这个话题时,惊异地发现,我七八岁时听到的邰正宵,
他们七八岁在其老家还是很火,要知道我们的年纪差了有 3-6 岁。再如小虎队和
刘德华的歌也是这样。个中传播的时空延异显而易见。儿时的我身处苏北,但相
较阿刚、大海这些中西部出来的孩子,接受讯息还是要早些。毕竟父亲很爱听音
乐,并且家里很小时候就买了“燕舞牌”收音机和“熊猫牌”黑白电视机。音乐
由此也在记录着文化时间上的差异以及背后深刻的社会经济差异。
一、流行音乐作为青年文化的社会记忆
农村地区的青年文化研究散见于学者们所做的各类农村、农民工研究的书
籍、报刊中,如瑞雪·墨菲认为,流行文化产品尤其受到一些年轻农民工的追捧,
他们购买名牌产品、流行音乐录音带、衣服、化妆品和时尚杂志,以便参与到一
种跨越城乡区隔的青年文化中4;这种(农村)青年文化实际上是城市文化在农
村社会的投影;它之所以采取青年文化的形式仅仅是由于乡村中国的特殊社会情
境5。
1 这里我必须对农业金属与网络歌曲进行一个说明。农业金属这种曲风的歌曲能够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
流行与“凤凰传奇”的盛行相关。本文中的农业金属是指类似凤凰传奇这个组合的《月亮之上》、《最炫民
族风》等曲风的歌曲。笔者田野期间,小康村最流行的歌曲大多都是网络歌曲。我这里所言的网络歌曲是
狭义的网络歌曲,是一种由网络原创的,借助 MP3、Flash 的制作技术,反映青年人生活、思想、心境在网
络上广为流传的歌曲,往往伴随着幽默、调侃、讽刺的意味。不过小康村流行的网络歌曲大多都有农业金
属的味道,并且凤凰传奇这个组合的歌曲也算是网络歌曲的典型。 2 Arnold Perris, "Music as Propaganda: Art at the Command of Doctrin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thnomusicology 27, no. 1, 1983: 1-28 3 Ho, W. C. Social change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s popular songs. Social History, 31(4), 2006:435-453 页 4 瑞雪·墨菲,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黄涛、王静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112 页 5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58 页
44
值得注意的是,与第一代农民工甚少接受过现代教育不同,新生代劳工在外
出打工前大多在学校受过九年义务教育,这一段正规教育为“青年人提供了在家
庭以外发展同龄人关系的重要社会空间”1。既往新生代工人/新工人研究甚少关
注工人出来打工前的那段历史,藉由音乐我们会发现音符穿透了历史的肌理,内
含了身体化了的历史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音乐是一种集体记忆,听者各以
不同的节奏录下他们从中塑成的个人化、特殊化的意义——一种秩序与系谱的集
体记忆,言语与社会乐谱的贮存所”2。
在新生代工人外出打工前接受义务教育这段时光里,流行音乐成为朋辈群体
追逐城市文化的一种印记。阿刚和大海都跟我说起他们以前在学校里的故事:他
们不爱读书,碍于课堂上不能说话的规矩,只能抱着廉价的随身听趴在桌上听歌、
抄歌词、看小说。大海说,那时老师说了,只要你不说话、不影响到别人,干什
么都行。他们所说的现象,我也深有体会。中国教育的精英化通常会把学生分成
两类:好学生和差学生。差学生在升学中是属于被抛在一边没人管的。班级中的
好生跟好生一起玩,差生和差生一起玩。我念初中那会差生们总是上课睡觉看小
说听音乐,下课追逐打闹;好生们上课认真听讲,下课埋头学习。那时我的成绩
不好不坏,三十几个人里排十几名,游离在好生和差生之间。而我们班当时按成
绩排座位的规定使得差生不论身高高矮,一律坐在最后排,好生坐前排。我坐中
间,时常和所谓的差生们一起听歌看小说。
因而,排斥与无趣构成了差生们的生活主色调。阿刚说,那时他们比较爱听
四大天王的歌,特别是古惑仔系列的主题曲,而那些好学生多喜欢听张雨生、小
虎队的歌。虽然同在一个学校一个教室,音乐陪伴并给予不同学生以差异性的个
人体验。
我和大海他们回忆起这段时光时总是会唏嘘,过去有点遥远,有点模糊。从
集体去村头看电影到录像带再到 VCD,赌神、古惑仔、黄飞鸿……我们不断找
寻记忆里那个年代的痕迹。电影里的刀光剑影和无厘头伴随着那些经典的主题曲
在我们的身体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比我们小五六岁的阿刚,说他上学就没干过
什么学习的活,上课睡觉看小说听音乐,放学回家找片子看,或者出去跟朋友一
起打电动。
1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64 页 2 贾克•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宋素凤、翁桂堂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0 页
45
电玩店是一个在我们中学时代读书时差生聚集玩耍的“圣地”。烟雾缭绕,
吵吵嚷嚷,不知何时会蹦出砸机器的声音,“拳皇 97”、老虎机等等都占据了
我和工友们年少记忆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这些机器动感的音乐和激烈的游戏声
音至今仍然回荡耳边。
图海纳(Alain Touraine)在分析工业社会中制度的衰落时曾用“马拉松”作比
喻来形容那些被抛掷出社会结构的被排斥者或穷人1。大海和阿刚就是中国主流
教育马拉松的掉队者,自愿不念书,转而东上,成为一名产业工人。与父辈隐忍
并坚持辛苦劳动不同的是,新生代劳工的社会再生产已发生了变化2。很多新生
代劳工无须通过乡村仪式、宗族行为、亲属之间的往来以及乡邻之间日常的交往
来实现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他们遭遇的是扁平化社会关系的重构。如果说,教育
的失利还可以让年轻的打工者可以去找寻工作上的成就,那么当工作上的无趣和
挣扎折磨掉他们的冲劲时,过往读书岁月的惬意又会涌上心头,家庭的照顾亦会
让他们体认父母的艰辛。
我还记得那日夜班和郝兄闲聊,郝兄和我说起他的家庭。郝兄来自河南安阳,
他有三个姐姐,他最小,母亲最宠他。或者说,全家人都很宠他。小时候,只要
郝兄喜欢吃的菜,母亲都会另做一份单独给他。有时他任性耍赖不吃饭,母亲便
会问他想吃什么,只要他报出菜名,母亲便会立刻去做。小时候家里很穷,但是
母亲还是努力供郝兄读书。在郝兄成绩不好、读不下去,便告诉母亲想外出打工
的时候,母亲也没有责备,只是叹了口气。母亲溺爱的意义在郝兄出来闯荡摸爬
滚打后,让郝兄觉得弥足珍贵。所以,在和我说起过往时,郝兄总会提起母亲;
提到现在所拿的工资时,郝兄也会说到过几个月就会寄钱给母亲还当年结婚盖房
子欠下的债。对于母亲的记忆随着那首儿时就时常听到《母亲》,在郝兄的心中
荡漾开来。好多次,我们都会一起唱起这首歌。
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
你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
你爱吃的(那)三鲜馅有人(他)给你包
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
1 Touraine, A. Can we live together?: equality and difference, Polity, Cambridge, 2000:42. 2 黄斌欢,跳跃式换工——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体制与就业策略,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六辑),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13:314 页
46
啊这个人就是娘
啊这个人就是妈
这个人给了我生命
给我一个家
啊不管你走多远
无论你在干啥
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
咱的妈
用卢梭的话来说,“这里的音乐,在这种方式中并不是音乐,而是一种记忆
的符号”1。
二、手机作为流行音乐的传播媒介
二十一世纪之前,继广播之后,电视机逐渐在全中国家家户户普及,加之由
于电视界老大哥——中央电视台话语霸权日益膨胀所带来的主流文化的高度渗
透性,政治性的歌曲以及弘扬时代精神的主旋律透过声波与画面响彻大江南北。
其时,歌曲中所传达的声音政治无疑深深烙在生活于转型中国的每个个体身上。
而千禧年前后,随着地方卫视的崛起,特别是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
《超级女声》等娱乐节目的风靡,再加上网络时代的降临,中国的大众文化空间
似乎快速从中央电视台所表征的“一家独大”转向了“百家争鸣”的时代。从录
音机到随身听到 MP3 再到智能手机,年轻一代接收音乐的媒介随着科技变迁也
在发生巨变,而这样的变迁不仅指涉信息传达方式的更迭,更意味着情感空间的
私人化,从政治的公共空间转向了私人的生活空间。
2012 年 7 月我进淮海上班后不久就发现,很多工友用的手机都很昂贵。时
下最流行的苹果 iPhone、三星、HTC 等手机品牌见诸各个车间。这与我 2011 年
来常熟做田野时的印象也有出入。2011 年小康村夜市随处可见山寨机售卖处。
我还曾和几个山寨机卖主打得火热,在人多的时候帮不能上网的工友下载歌曲。
2012 年小康村夜市只有一家店主还在贩卖山寨手机。苹果手机风行全球,小康
村各大工厂的工友们也在追逐苹果手机。
1 安东尼·西格,音乐民族志理论,载张伯瑜等编译,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央音乐学
院出版社,2007:84 页
47
与我熟识的阿刚虽然没舍得买 iPhone,但他花了大半个月的工资——3100
元买了同车间大胖刚刚买了不到两个月的 HTC17,而大胖转手又买了 iPhone4。
因为智能手机很耗流量,大胖和阿刚每个月的手机费都要三百多。手机成为工友
打发时间,应对无聊的最佳玩伴。
后来,在厂里呆的久了,和大家熟络起来后,我有时会拿阿刚和大胖的手机
玩,发现他们手机里都有很多歌,都是时下最流行的歌曲。因为淮海的宿舍里没
有安装网络,工友们获取歌曲的来源主要就是宿舍楼下的黑网吧、在外租房有网
络的工友们以及小康村夜市中收费下载歌曲的地方。
歌曲同电影、电视剧一样都藉由同一层楼几个买了电脑的人传播开来。阿刚
就买了电脑,我们时常会拿着他的电脑当中转站往手机里拷歌听,拷电影看。有
次我从隔壁阿伟那听到了侃侃的《滴答》,觉得很好听,就问他从哪找来的。他
说,不知道,买了新手机,空得很,从老乡那把放歌的文件夹都拷来了。
音乐依循着工厂里的种种拟/亲属关系网络传播开来。阿伟是安徽合肥的一
名大专生,学染色工艺的,大三了,同我一样,都面临着毕业找工作的难题。阿
伟的表哥在淮海的营业部上班,负责和波司登谈羽绒服面料生意。借由哥哥的关
系,阿伟便顺理成章地进了淮海实习上班。初始,人事部门那边看阿伟是个大专
生,想把他分配去开定型机,可阿伟觉得自己的专业是学染色的,如果不做这方
面的实习,专业就白学了,便要求去了染一车间。阿伟是厂里为数不多的大专生,
到了染一也迅速挑起重担,去开 TB 染色机。
染色课的车间里时常弥漫着各种化学染剂混杂的味道,刺鼻,与此同时,染
色需要高温高压,TB 机也有一定的危险性。阿伟的手和脚不知被烫伤多少次。
我和阿伟同病相怜,同为新人,一来淮海不久便受伤,再加上就住我隔壁宿舍,
我们也算聊得蛮多。有时宿舍不开空调,我便跑到他们宿舍睡觉,顺便蹭空调。
一来二往也算不错的朋友。阿伟上高中时就谈了个女朋友,现在在东北农大上学,
两人天南海北,就靠手机聊天保持联系。
阿伟每天下班洗完澡就会躺在床上一边听音乐一边陪女朋友聊天。阿伟有两
个手机,老手机用来发短信打电话,新手机则主要用来上网听歌。由于刚进厂工
作不久,我和阿伟都在经历从学生到工人的身份转换。记得某个晚上,我问起阿
伟,“你觉得来厂里,最大的变化是啥?”阿伟说,“变简单了。以前在学校会
48
跟很多人一起出去玩或者打游戏到通宵。现在每天生活就会很规律吧。每天除了
上班,就剩听歌和陪女朋友了。”
有学者曾认为“房子、电视和汽车成了构成具体的微型乌托邦的三大要素,
既能够自给自足,又能够与外界保持沟通。大众文化的实际能量就集中在这三大
要素上,集中在这一微观的天地里1”。那么,对于流动迁移漂泊的打工者而言,
智能手机就是一种微型乌托邦元素,而个人的音乐实践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实
践。
如果说随身听肇始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模糊,那么用智能手机听歌也无
疑将个人私人领域的情感带入了公共空间。而当工厂老板试图用种种条款与罚款
制止这种个人实践在工厂公共生产领域发生时,由于其私密性和流动性又形成了
某种意义上的戏谑。如果我们挪用 20 世纪女性主义一条很著名的口号:“个人
的就是政治的”2来说,工厂里借由手机实现的音乐实践,是转型中国当下个人
情感空间的政治实践。因而,“手机是迷你型公共场合的建筑模块,……因其灵
活性,加之快速又不费力的调整和刷新及其对密切监视和管理的欺骗性顺
从,……似乎为个人的自由打开了崭新和更广阔的田地,而不会陷进分散于整个
公共领域的承诺3。
只不过,小康村流行音乐呈现出“块茎式”的传播样态,其仰赖实践性的亲
属关系,通过流动的个人与集体不断交叉与融合。既往用来框定和描绘生活世界
(Lebenswelt)概念的所指对象,即那个作为生活和经验的世界也是年轻人亲自经
历的世界,已经渐渐但稳步地从网下世界移植到网上世界了4。音乐作为网上世
界的一部分,无论存在于网络游戏的背景音乐抑或电视/电影的插曲甚或铁血网
上流传的农业金属摇滚都在年轻劳工的身体血液中流淌着,如同空气般,隐匿地
暗指着那个不同于父辈的生活世界。
三、小康村流行音乐的类型分析
我曾用空白的笔记本跟点唱机的王老板换了他那写得密密麻麻的点歌单本。
每一个顾客点的歌曲他都会用笔记下来,一方面方便排序叫号,另一方面也好提
醒自己有没有收钱。
1 艾德加莫兰,社会学思考,阎素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95 页 2 谢丽期·克拉马雷,路特里奇国际妇女百科全书精选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941 页 3 齐格蒙·鲍曼,来自液态现代世界的 44 封信,鲍磊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41-43 页 4 齐格蒙·鲍曼,来自液态现代世界的 44 封信,鲍磊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20 页
49
我花了很久的时间来翻看这本满是歌名的点歌单,里面漂浮着浓厚的文化记
忆。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那样,点唱机前演唱的歌曲大致可以分为经典红歌(老
歌)、港台经典老歌、以及农业金属摇滚/网络歌曲三种类型。
经典红歌,多为年长的如四五十岁的劳工和某些企业的老板演唱。年轻的劳
工基本是不唱的。这些歌曲很讲究气息的绵长以及高音的嘹亮,因而很容易展现
自己的歌喉。点唱机的王老板自己就很爱唱这类歌曲。
港台经典老歌,我很诧异的是九零年前后出生的这些人竟是如此爱唱这些歌
曲。很多歌曲几乎是深埋在我记忆里的老歌。比如,邰正宵的《女人是老虎》、
《九百九十九朵玫瑰》,比如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农业金属摇滚/网络歌曲,这些歌曲通俗直白,生活中的任何情感不分雅俗
都可以入歌。《伤不起》、《做我老婆好不好》、《十一年》、《最炫民族风》
等等是在小康村传唱度最高的部分歌曲。当下的网络歌曲曲式曲风上延续并混杂
了红歌、西北风、中国风等文化元素,我们可以从歌曲本身来考察农业重金属/
网络歌曲为何如此流行1。
表 2 2012年 7-8月流行歌曲曲目概况
曲目 歌曲发行年代 演唱者 调性 节拍
等一分钟 2006 徐誉滕 降 e 小调 2/4 拍
做我老婆好不好 2007 徐誉滕 G 大调 2/4 拍
老婆老婆我爱你 2006 火风 A 大调 2/4 拍
爱情买卖 2009 慕容晓晓 a 小调 4/4 拍
伤不起 2011 王麟 f 小调 4/4 拍
十一年 2009 邱永传 a 小调 4/4 拍
最炫民族风 2009 凤凰传奇 降 b 小调 转 #c 小调 4/4 拍
荷塘月色 2010 凤凰传奇 G 大调 转 D 大调 4/4 拍
我的好兄弟 2009 高进、小沈阳 d 小调 4/4 拍
滴答 2010 侃侃 降 E 大调 2/4 拍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2007 阿木 g 小调 4/4 拍
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 2008 T.R.Y. F 大调 4/4 拍
樱花草 2006 Sweety D 大调 4/4 拍
走天涯 2008 叶贝文 #c 小调 4/4 拍
Dan Sperber 曾用表征(representation)来阐释文化现象的传播问题2。根据他的
理论,表征分为心智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与公共表征(public representation)。
心智表征存在于每个人的大脑中,我们接触不到,接触到的其实都是公共表征。 1 本部分的写作要感谢我的朋友南京艺术学院的姚鹭同学,感谢他对我的指导。 2 Dan Sperber, Explaining Culture: A Naturalistic Approach, Oxford: Blackwell, 1996.
50
Sperber 提出用“流行病学”作为隐喻用来理解文化表征的传播。人的思想面对
文化表象,与人的身体面对疾病有着同样的方式。然而,他指出,疾病很少出现
变异,而文化传播在传递过程时常出现变形/转变(transformation),而这种转变是
认知过程建构的结果。文化表征倾向于由强势的一方向弱势的一方传递。而且,
尽管主导文化的文化样式易于出现变异,但此变异受制于迎合被“传染”文化的
已知的基本准则。将这一理论放置于说明农村地区,为何诸如农业重金属/网络
歌曲流行的语境中,我们会发现,易感染性(susceptibility)的文化表征除了当下中
国新生代劳工中弥散的流动的不安与压抑,还包括了一脉相承的音乐调性与节
奏。民族音调成为一种元表征(meta-representation),通过存在于个体内部的心智
表征与公共表征之间的转换机制,人们消化理解、过滤与传递不同的流行歌曲。
而几乎所有这些流传甚广的流行歌曲都具有这样的元表征。
首先从调式上分析。几个音(一般不超过七个,不少于三个)按照一定的关
系(高低关系,稳定与不稳定关系等)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体系,并以某一音
为中心,这个体系就叫做调式1。调式作为一种乐音的组织结构形式,在人类不
同的历史阶段、民族和区域的实践中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调式。但是随着现代音乐
工业的发展,原本源自欧洲古典音乐的大小调也为流行音乐所采纳,再加上新媒
体时代中信息的迅达,互联网音乐也多以大小调式来组织音乐。
我从王老板的点歌本里抽选了 2012 年 7-8 月份点唱度较高的一些曲目。根
据歌曲发行年份来看发行较早的歌曲大调占较多比例,随着时间推移,现如今已
呈现大小调式分布均匀的模式。从主题上划分:爱情主题类的歌曲基本采用小调
式,小调式有助于作者通过歌曲抒发忧郁,思念的情感,如《爱情买卖》(a 小
调)、《有一种爱叫做放手》(g 小调)。
再观选曲,大部分都是采用的中国民族调式(即宫商角徵羽),正如俄国美
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认为的那样,真正的最高的美是人在现实世界中所遇到的
美,而不是艺术所创造的美,即美是生活2。因而,扎根民众生活的美才会为人
所体认,换言之,美也是有当地性或民族性的。若是歌曲采用日本民族调式或是
美国蓝调,想必在中国听众间很难流传开来。所以共同的文化背景是歌曲流传的
基础。
1 苗金海,基本乐理课教学中的几个疑点、难点解析,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6(4). 2 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周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1 页
51
从写作技巧上分析,距今时间越近,作者采用的写作技巧越娴熟。例如凤凰
传奇组合,选曲中的《最炫民族风》、《荷塘月色》、《开门大吉》,都采用了
转调的写作手法。通过转调,可以避免和声的单调与静止,推动音乐的发展,构
成乐曲发展的起伏、层次,形成乐曲各部分之间的对比平衡,从而使得音乐作品
更具有丰富的色彩对比,这又让听者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旋律的研究中,学者们通常认为旋律包含曲调线和节奏两个方面。曲调线
指涉的是“不同音高的一组音相继出现而形成的音高起伏感”。至于节奏则为“声
音按不同时值和强弱相继出现而组成的节拍感和律动感。音高线是苍白如蜡的图
像,节奏使它有了生命,节奏使它有了灵魂。……一条旋律,如果没有节奏就很
难或者根本不能成为旋律,相反,经验说明,单单节奏在许多情况下就能足以成
为旋律”1。因而,我们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节奏上。节奏是音乐在时间上的组织,
它是有一定规律的运动。音乐的节奏是通过音的时值长短和强弱的交替来体现时
间关系和力度关系。曲调的风格、特点是通过节奏的特点来体现的,尤其是不同
风格的通俗歌曲,更是由不同的节奏型体现出来的2。通过表 2,我们会发现,小
康村流行的这些歌曲多采取 4/4 拍和 2/4 拍,4/4 拍是两个 2/4 拍合成。心理学家
研究表明:人们对于 2 拍子好像有种天然的偏好3,因而这两种节奏型通常容易
让人接受,也同时能抒发自己的情绪,高昂的、忧愤的或者舒缓的。2/4 拍的歌
曲,具有一强一弱的节拍强弱规律和每小节一个重音的特点,表现了一种欢快的
情感。4/4 拍属于复拍,由两个 2/4 拍合成,每个小节不止一个强拍,还有次强
拍,在强弱交替的效果上比二拍子更细微深刻一些,具有叙事抒情性。因而,2
拍子的农金/网络歌曲一方面朗朗上口,听几遍就会,不需要工友们掌握任何声
乐技巧。
甚而一些欧美流行音乐也是这样。我们车间的阿黄平时不大爱说话,一副很
清高的样子。他是湖北人,和组长一个地方的。原来曾在老家舅舅的纺织厂里做
管理,但是因为和舅舅的经营理念不同,也不自由,便经由老乡介绍来淮海上班。
那日下了夜班,我洗完澡在床上躺着,准备入睡。他推开我们宿舍的门,在我的
床边坐下,给我放起他手机里的歌。大黄爱听英文歌,问我听得懂歌词不。我虽
1 薛艺兵,旋律学建设的一些理论思考.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98(4). 2 王冠群,通俗歌曲创作十讲,长春市:长春出版社,1993:13. 3 欧阳玥、戴志强,音乐节拍认知的研究评述,心理科学进展,2010(18):1697.
52
困,但很讶异我曾经以为没有音乐的淮海员工宿舍还是有音乐的,音乐隐匿在每
个工友的手机里。我发现阿黄爱听的歌曲也多是 2/4、4/4 拍的,尽管是英文歌曲,
但强烈的节奏感总让我想起中文的农村重金属歌曲。在市场化的逻辑和资本主义
的影响下,“‘声音’开始变成一种‘纯粹的能指’,用千差万别的差别来去差
别化,用种种色彩斑斓的个性来塑造普遍的无个性,正是这种特定的抽象的声音,
才如此丰富多样灿烂多姿,而又如此空洞无物、苍白单调1”。
如果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后中国流行音乐这三十多年的历史,那么我们会发现
在历史盘根错节的背后,隐含了一条清晰的流行音乐发展脉络。对于民众而言,
20 世纪 80 年代国门打开之后,港台流行歌曲比欧美流行音乐具有更易接近性。
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大陆和港台都共享着语言、审美与文化传统;二是,
政府严禁了大部分的欧美音乐,因为当权者认为这些音乐太暴力、太具有性暗示
和太个体主义了 。不过后来港台流行音乐也遭致中共政府的批判,因为港台音
乐的靡靡之音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因而后来一批歌颂党、歌颂祖国、歌
颂军旅生活、歌颂亲情的通俗歌曲出现在主流媒体上,再加上北京摇滚、西北风
等风格的流行音乐的横空出世,使港台流行音乐被取代的趋势更加明显。之后,
虽还有一波“中国风”从台湾刮向大陆,但港台流行音乐的一家独大局面一去不
复返。
此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推进,后毛时代个体
化的演进,社会分层的差异性扩大,不同个体的情感表达的方式也不能为某一单
一形式的歌曲类型所表达,去政治化、趋“我”化的情感表达需要差异化的出口。
后来,网络音乐的出现,使得流行音乐的大工业的链条上出现了一匹黑马。
网络音乐内所包含的歌曲样态也很繁杂,借由更为便捷的媒介:网络和智能手机,
网络音乐渗透进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几乎每个角落。应该说,2010 年前后凤凰传
奇等一批所谓农业金属摇滚音乐的流行折射了“政党—国家—市场经济”模式
(party-state-market complex)与全球化现代性侵蚀下个体情感上的无力、无奈与撕
裂感。此类歌曲表达方式上的直接、裸露,与我在工厂上班时,工厂机器轰鸣之
下,现代机械与劳动强度重压之下的说话与情绪表达方式一脉相承。
1 周志强,声音的政治——从阿达利到中国好声音,中国图书评论,2012(12).
53
第四章 那些人,那些事——与音乐有关
文章至此,我并没有对点唱机着墨太多,而这样的变化与我在小康村遭遇的
身体体验有关。毫无疑问,点唱机是重要的,它使得别人在听什么,在想什么在
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得以呈现。用一个不恰当的比方,点唱机似乎就是小康村的流
行音乐榜。久了,你就会发现形形色色歌曲中流行元素的变迁。而点唱机占据了
构成我前引的 Dan Sperber 所指称诸多公共表征中的重要一环。本章中,我将追
溯小康村夜市出现的与音乐有关的那些人,因为,按照克里斯托弗·斯莫的
“musiking”观点,我们必须也把那些卷入与音乐相关事项的人也予以描述,他
们生活中的音乐也同样与生命勾连,生产出或异或同的意义都会有助于我们理解
小康村新生代劳工的生存图景。
一、永远的张老板
关于点唱机老板,第一章中我曾简述过王老板的故事。而这,我想说说那个
张姓男子的故事。
算起来,张姓男子和我是老乡,并且年纪也相仿。我们用苏北方言聊天时总
能畅怀大笑,亲切又不失有趣。张老板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老板。小学的时候,他
就开始开动生意头脑了。他第一笔生意是卖矿泉水。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上完
体育课满头大汗时会想喝水。小时候,对我们来说,一块钱也不是一笔很小的数
字,所以总会舍不得。他就想,一块钱你舍不得花,那一毛你总舍得了吧。于是,
当时的小张就买了几瓶矿泉水,一块钱一瓶的那种,分给同学喝,一毛钱一口。
张老板说,那时他卖过很多东西,从矿泉水到冰棍再到卡牌,一茬一茬的,零零
总总也挣了不少。初中时他的积蓄已经有好几千了。不过他的学习一直不好,没
能升学,初中毕业便出来打工了。
几年前,他辗转来到小康村,刚下车就嗅到了钱的味道。那时小康村刚刚合
并兴建不久,于是,他一边在一家电子厂上班,一边寻思在这做什么赚钱。本来
想做个新奇食品——夹心蛋糕,但是工序和投入都比较麻烦。后来,因着自己也
爱唱歌的缘故,加上小康村并没有什么可以让他痛快唱歌的地方,让他有提供唱
歌场所的打算。正好一日在电视上看到卡拉 OK 机的广告,张老板便联系北京的
厂家,把点唱机买了回来。那是小康村的第一台点唱机,也是延续到现在最先进
54
的机器。后来,张便辞了工作专心做点唱机生意。每日下午六点,他把点唱机用
拖拉机开到夜市摊位,工作到凌晨一点收工回去,每日工作七小时。而时令不好
时,如冬季,则从下午四点营业到六七点也就作罢了。
点唱机的生意很火,十块钱三首的价格就是从张老板那时定下来的。张说,
刚开始都是五块钱一首的。后来有人眼红,也想做这个生意,他便把价格调成十
块钱三首了。张开点唱机的策略是会邀上三五个朋友在工人下班前后便来摊点暖
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人都有从众效应的嘛。张是情歌王子,唱那些八九十年
代的歌曲着实不错,而也正是这样的机缘,他收获了他的第一段婚姻。
张老板的前妻,以前在小康村附近的银行上班,做出纳。那时她时常来张的
摊位唱歌,张老板见她第一眼便动心了。一来二往,再加上张老板的猛烈攻势,
没两个月,两人便在一起了。婚后,两人育有一子。
可是,也许是如张所言,一个大学本科生,一个初中生,是学历间的差距,
使得两个人的婚姻生活一直都磕磕绊绊的,每日都会争吵,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
争个高下。孩子一岁多的时候,两个人终是分手。张的妻子带着孩子回到了老家
——四川,而张老板选择了留在小康村。
也许正是这段过往,张老板越来越无心经营点唱机生意,便把摊子盘给了同
在小康村打工的王老板。而张自己则在古里镇盘了一块地方开厂做起了服装包装
袋生意。
2011 年我在小康村和张老板认识的时候,那时他已经渐渐从前一段失败的
婚姻中走出来,享受单身的生活,时不时来王老板的点唱机这唱唱歌,聊聊天,
打发夜晚无趣的时光。我们最常聊起的就是婚姻,他说其实一个人过也挺好的,
就是有时会想起孩子。我时常会从张老板的《忘情水》中听出一种苍凉感和无奈
感。一个在外面打拼了这么多年的汉子,事业上虽不错,但终是孤独落寞的。米
尔斯认为媒介并非仅仅影响人的投票行为、潮流时尚、行动方式以及购物选择,
而是为普通人带来希望、赋予身份,甚至直接构成生活经验1。张老板在点唱机
的遭遇,凸显了他生存状态中的抵牾,一方面生意虽不错,但另一方面却也时常
被看成是没什么文化的土老帽。学历因而也成了张老板挂在嘴边的话,“虽然我
是初中生,但是我做生意还是有一手的”。
1 伊莱休·卡茨,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29 页
55
2012 年我重回小康村的某日,在点唱机摊位碰到张老板时,他指着旁边的
一个打扮新潮时尚的女人跟我说,来,介绍下,这是你嫂子。我笑笑,叫了声,
嫂子好。那日,我怂恿张老板给她现在未过门的女友来一首《老婆老婆我爱你》。
张说,“那歌太那啥了,那还是来个《纤夫的爱》吧。”那一刻,我觉得那个爽
朗自信的张老板又回来了。在聆听中,我突然顿悟舒茨所言的“内在时间和绵延
就是音乐的存在形式”1。我作为一个外人,借助声音,“通过生动的现在而共
享他人那直接存在的意识流”2。我确然感受到发生在张兄身上的一幕幕过往,
仿佛这一切我亲历了般。身体经验与记忆如同徜徉在德勒兹笔下的“褶皱”着的
音乐的“千高原”上,绵延跌宕。
后来,张老板还张罗着让我去参加在常熟市举办的相亲大会,他说他和嫂子
就是某次相亲大会上认识的,而我则疲于奔波在工厂和夜市之间而未能成行。
二、卖手机,替人下载音乐的小丁们
之所以称之为小丁们,是因为,我发现夜市中那些受雇于卖手机的小伙们经
常换面孔。2011 年我在小康村的时候,那时夜市里有四五家卖手机的,摊位旁
都会竖个小牌子,上下写着“卖手机/下载歌曲、电影”。我每次早早去夜市的
时候,他们已经在摆摊。那日我的手机数据线坏了,便打探数据线的价格。那时
才过六点,夜市还没什么人。我便和摆摊的小伙聊起来。原先我以为他是老板,
还夸他这么年轻就把生意做得这么好。小伙连忙纠正我,我哪里是什么老板,打
工的。这让我很惊异。我原先以为,打工的都应该去工厂,怎么会在夜市这么流
动的摊点上打工。
后来才知道,小伙姓丁,安徽人,之前也在附近的电脑厂里上班,后来觉得
不自由,工作强度也受不了,怎么都不顺心。正好有朋友的朋友做生意缺人,便
应了缺,来干这个活,卖手机及其衍生产品。我指着他们的牌子,“你们还帮人
下歌什么的哦?”小丁应道,“嗯,不过要是你在我们这买手机的话就免费给你
下。不然的话,五毛一首。”“好贵,不过真有人来下啊?”小丁说,很多刚来
这打工的,没买电脑也不舍得去网吧,就在这下两首歌或者拷两部片子。初见我
时,小丁刚干这行不久,从下午五点到晚上十二点,一天七个小时。小丁说他很
享受小康村的夜生活。说到这,我就转而问小丁,“对了,你帮他们下的歌你都
1 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理论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91 页 2 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理论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97 页
56
听过么?”小丁瞅了我一眼,答道,“你刚来打工吧。你说,干我这行的,怎么
会没听过。平时我也听歌啊,他们有时记不住歌名,说两句歌词,我就知道他们
要下啥歌了。挺没劲的。”
2011 年 8 月我几乎每晚都会在小康村夜市晃荡。跟小丁他们从脸熟到每次
都会打招呼聊天。小丁的身影渐渐也显得疲惫与倦怠。愈渐城市化的小康村的夜
生活,哪怕音乐成为工作的一部分,“现代性使得对于满足的找寻无法实现……
生命的可能与选择都彻底困于物化了的形式1”。小丁的生活转而变得无趣,一
方面因为生意越来越难做,很少有人再愿意来买山寨的手机,都会跑到市里专卖
店或者大卖场买品牌机,因此小丁的工资还不如在工厂里上班拿的一半多;另一
方面,黑夜白天颠倒的作息让他很难有时间谈恋爱。小丁的女友在一家电子厂上
班,通常上的是长白班。两人之间很难有交集,或者交集很短,这也让小丁越来
越不爽。这样的境遇使得在我准备离开小康村时向小丁道别时,发现摊位那儿已
经换了别人。上前询问,这才知道,小丁已经不干了,进女友的那个厂里上班了。
而这之后,我再没见小丁,也不知道此时的他漂泊在何处。2012 年的夏天,
我又来到小康村时,夜市里的卖手机摊位已经萎缩到两三家了,也没见到那个顶
替小丁的小伙。
2012 年 7 月和 8 月,我虽然无法像 2011 年一样那么常去小康村夜市,但是,
我知道小丁们走得越来越快。那天我跟摊位老板聊天,问他最近生意怎么样?他
无奈地直摇头,“你没看我现在主要卖啥了,卖手机套、手机膜、手机配件了!
现在周围厂里都涨工资,他们(工人)手里都有钱了,不爱买山寨货了!”老板
随后也表示出对于小丁们的无奈,能吃苦的不愿来,都愿留在厂里上班。愿来的
都吃不了苦,干不了多久就不干了。
一度,老板雇了个“小丁”,他和别的小丁不同。他白天还上班,想多挣钱
就兼了这份工作,但他也明确表示干不久,等厂里忙起来,就要回厂里加班了,
毕竟加班有双倍工资的。“小丁”让我想起阿龙,那个介绍我进淮海的好友。阿
龙四处漂泊着,每次和他电话,他都会抱怨现在的工作累,挣得也不多。一年间,
阿龙没少折腾,从钢铁厂到 KTV 再到自己开店,试图比以前做得好,但一直都
无法超越离开淮海时的成就:班长,月薪四五千。
1 基思·特斯特,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43 页
57
移动互联网如联通 3G 以及电脑的普及,再加上工友中在外面租房子,通上
宽带的工友越来越多,小丁们给周围工人下歌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富士康出事后,
有像小丁一样在富士康门口替人下歌的人撰文反思自己也参与到剥削工人的行
列中,加剧了他们生存的困境。在我看来,当富士康成为“血汗工厂”的代名词
后,大量的研究也就丧失了原有的张力,把劳工置于资本家的对立面,并不能解
释当下中国发生在新生代劳工身上的阵痛感。
小丁们不会产生学者们所期待的阶级意识,也并没有试图去争取什么权益,
原因诸多,但有一点是我认为需要着力关注的,即前文所述的,年龄二十岁上下
的小丁们所共同型构并委身其中的青年文化。他们正处在寻找满足及认同的年
纪,渴望证明自己,但又不想让自己太辛苦。他们不需要确认自己到底是农村人
还是城里人,但他们总想证明自己能在远离家乡的城市有个落脚之处。就像他们
不需要去知道自己听得是哪种音乐类型的歌曲,不需要标榜自己喜欢爵士、还是
摇滚,只有好听的和不好听的。没有处于政治经济中心的小康村,在边缘处而得
以渐渐形成落脚城市——乡村中的城市,见证着一拨又一拨的连锁式移民1。而
小康村的流行音乐作为一种边缘化的主流声音,流转着这些劳工移民的两难的身
体记忆。
三、爱唱歌的小超
我和小超的相识缘于点唱机,我们俩算是最常去点唱机唱歌的人。熙攘人群
中只有我们经常性地光顾。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注意到了他。不过应该和小超喜欢唱快乐男声魏晨的歌
有关。小超唱的歌用网络上流行的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比较小清新。在港台老歌或
是农业金属风盛行的小康村,小超唱的歌算是比较另类。
小超一周七天至少会有三四天来王老板的点唱机唱歌,每次默默唱完歌,站
着听上一会别人唱的歌之后就会骑上电动车回去。
小超真是爱唱,每次来点唱的歌都不大一样,听得出来有些歌熟悉,有些歌
像是刚学的。熟识后,小超常会给我放手机里他录唱的歌。看着他手机里满屏的
歌曲我不禁有点惊叹,这大概是我在小康村看到的最热爱音乐的青年了。
1 道格·桑德斯,落脚城市,陈信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41-42 页
58
小超是个九零后,来自四川,高中没读完就来古里镇了。他的父母在古里镇
上租了一栋民房开了间小型的纺织厂,楼上住人,楼下生产。他自己每天早上八
点起床对着电脑听歌练歌。一直折腾到十一、二点,吃完饭便去楼下的厂房帮忙
干活。这样的建筑格局也使得楼上吵闹的音乐声在楼下机器的轰鸣声中也不会显
得很突兀。再加上小超的父母并不干涉他的这个爱好,所以小超一直也乐得自在。
与我在厂里的工友不同,小超已经把音乐当成他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如同每天的必修课一样。我问过小超,“你有没有想过也去参加歌唱比赛?”“有
啊,不过我唱得还不够好,当然我也不帅啦。”当时他回答问题时的羞怯表情让
我至今记忆犹新。
小超对我的研究很感兴趣,他见到一次就会问我一次,“你得出什么结论没
有?”我每次都很无奈地对他摇摇头,答他,“就像我问你为啥会喜欢魏晨那种
类型的歌曲,你回答我的那样,不知道哎,没想过,就是听到了就很喜欢。我就
是很感兴趣,还没想清楚哎。”
我时常会想小超的身份,他算人们传统归类的新生代劳工么?如果是的话,
他和我的那些工友们又有很大的差异,这怎么解释?抑或者我们的分类范畴体系
本就是很无趣的。
小超在评论点唱机前其他人唱的歌曲时,总会说,“那首***歌我们楼下的
谁谁谁也很喜欢听哎。唱得还行/唱得算那么回事。”我问他,“你喜欢农业金
属那种风格的歌曲么?”“算不上喜欢,平时也听,有时也会有喜欢的,不过这
种类型的歌歌词有时太那啥了,不好。”
小超喜欢一首歌更加看重歌词。例如他很喜欢唱的那首《少年游》。歌词就
会显得雅致,很有青春少年遭遇爱情懵懂朦胧的感觉。
朱门半掩谁家庭院 我骑白马路过门前
只闻见 一曲琵琶点破 艳阳天
待字闺中谁家小姐 琴声幽幽拨我心弦
盼相见 日日在她门前 放纸鸢
不过茫茫人海 偶然的遇见
谁知(踏破所有铁鞋) 只在一瞬间
注定沦陷你眉间
59
佳人少年 前世种下的纠结
姻缘红线 邀你人世共并肩
RAP:夕阳下我拉着你一起望着天
慢慢的静静地度过旧旧的时间
真的好想让你永远留在我的身边
数着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翩翩
今生与你相遇 前世柔情继续
你的身影为何消失得这样了无音讯
曾经为你写满那封相思的信啊
再也不会变成我心里那道忧伤的印
待字闺中谁家小姐 琴声幽幽拨我心弦
盼相见 日日在她门前 放纸鸢
不过茫茫人海 偶然的遇见
谁知(踏破所有铁鞋) 只在一瞬间
注定沦陷你眉间
佳人少年 前世种下的纠结
姻缘红线 邀你人世共并肩
佳人少年 前世种下的纠结
姻缘红线 邀你人世共并肩
看起来,小超的音乐世界是和我的工友们不一样的,对他而言,在音乐中他
会找到内心的宁静,找到他想要的东西。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你看魏晨的音乐
里就很干净,没有现实生活中的那么多七七八八的事情,听音乐时总会自己可以
暂时摆脱些什么。我的工友们则是常常借由音乐表达些什么。但实际上,有一点
是共同的,音乐的意义是与生命中的经历相关联的,“意义的归因要求除了参考
当下,还要参考过去和未来,也就是必须考虑‘前摄’和‘滞留’”1。
1 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杨德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72 页。
60
不过对小超而言,他的音乐世界意义的所指是模糊与含混的,他没有像我的
工友们有尽早进入婚姻的念头,也没有现在就谈恋爱的想法,但是他对于爱情又
是向往的。因而音乐对他的意义更多地会指涉向自我认同(self-identity)的建构过
程。
我曾戏称小超为准富二代,小超坚决不赞同,说自己就是个三无青年。小超
很少会考虑未来,在听了我一堆对未来的憧憬时,他损我,你们文化人就是不一
样,我就想简简单单地唱唱歌,然后把厂子弄弄。唱歌是小超最擅长的事,用他
的话说,有时不知道自己除了会唱歌还会做什么。
小超喜欢时不时来小康村唱歌的原因是他喜欢把在点唱机那唱歌当成是自
己的练歌场,而我则把这样的经验视为试图一个进入当地人视角的努力,不过我
们之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让我们都达至这样的共识,在点唱机前唱歌
的氛围还是和在家一个人独处时听歌唱歌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差异源自于我们在
找寻歌唱意义时所面对着的与他者互动的自我展演。
61
结论与讨论:歌唱的意义
我喜欢这些钢铁工人,对于他们来说劳动就是一切,没有劳动他们简直无法
想象自己生活。……在波尔迪钢铁厂我还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理解别人才能理
解自己,跟我一起干活的还有其他人,他们的命运比我更加艰难,然而他们却一
声不吭。
——赫拉巴尔《我为什么写作》1
2008 年张彤禾(Leslie Chang)写了一本书《工厂女孩》2,她还在 TED 上做了
一个简要分享。应该说,张彤禾试图刻画一个活生生的多样化的女工群体,她们
不仅有大学毕业的,也有初中毕业的,她们有从事一线工作的,也有坐办公室的
等等。她们个性而脆弱,试图挣脱远离贫穷落后家乡的束缚,追求自我的存在感。
张彤禾的立场是我们不应该一味批判资本家的压榨,而更应该走进新生代劳工的
内心,倾听他们的声音。
我得承认,我在阅读张彤禾这本书时,时常会比较我在厂里的生活。我时常
觉得自己在摇摆,正如我感受到小康村的音乐声境。是“我”在唱歌吗?还是歌
在唱“我”?小康村所流行的混杂的音乐形态究竟说明了什么?总而言之,流行
音乐对于小康村地区的众生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流行音乐研究者通常关注的是那些音乐家、那些音乐创作者,而当下中国农
村地区流行音乐的创作者并非迁徙的劳工也非当地居民,新生代劳工浸淫在文化
大工业所给予他们的音乐消费中么?我挣扎于三种全然不同的立场中:1、我们
可以用自己道德去批判研究对象的文化么?2、我们可有权利/权力去判定哪种类
型的音乐可以作为这个地区音乐的代表么?3、我们是不是可以不做任何的道德
评判呢?
这之中唯一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可以站在道德的高地上,驾驭自己的身
体经验去评点他者的文化与认知。除了压迫与微弱的反抗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
些什么呢?
1 博·赫拉巴尔,我是谁,星灿、劳白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37-38 页 2 Leslie T. Chang. 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 New York: Spiegal & Grau
Trade,2008.
62
持无政府主义立场的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提醒研究者
反思那些不假思索就套用“消费”进行分析的行径,而应该重新思考“消费”究
竟是什么?为何人类自我表达或自我欢娱的各种形式都被当成与吃食物是一类
的?我们摆脱这样把凡事都归类为消费的迷宫的途径之一就是把消费作为应该
被研究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一个分析性的概念1。这对于我们的启发是,如果说
人类的欲念本质是个体与魅影(phantasm)之间的关联。一方面我们试图去建立某
种自主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在试图撕裂周遭权力掌控。那么我们个体间的关系则
是在之间的张力中展开的。在这样张力中,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意义的生产过程。
在小康村的日子里,有两个画面特别触动我。一个跟我一同进厂的小刘有关。
那日,得知我要离开淮海回去继续学业,小刘把我拉到他们宿舍,给我放了首歌,
那首歌名叫《我的好兄弟》。
在你辉煌的时刻
让我为你唱首歌
我的好兄弟
心里有苦你对我说
前方大路一起走
哪怕是河也一起过
苦点累点
又能算什么
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我来陪你一起度过
我的好兄弟
心里有苦你对我说
人生难得起起落落
还是要坚强的生活
哭过笑过
至少你还有我
朋友的情谊呀比天还高
1 Graeber, David. “Consump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2011(52): 489–511.
63
比地还辽阔
那些岁月我们一定会记得
朋友的情谊呀我们今生
最大的难得
像一杯酒 像一首老歌
我们曾一起在点唱机那听过这首歌,也一起唱过。刚进厂时我们一起接受培
训考核的日子迅速浮现起来。刚为人父的小刘和我这个老男孩一起飙着吼着,眼
泪不住地流下来。工厂里总有人进进出出,生活中难得会有人打动你。“在流动
的、迅速移动而又不可预测的环境里,我们比以前更需要坚实可信的友谊纽带,
更需要相互间的信任”1。我明白小刘,兄弟之情真是不舍。
还有就是那次九月底在淮海举办的中秋联谊活动。那天,见到了久违的兄弟,
也见到了一同进厂的猴兄。我们坐在一起喝酒吃烧烤叙起旧来。猴哥穿得很齐整,
西装领带人模人样,我便笑他,不至于为了迎接我穿成这样吧。他笑着说自己刚
参加完老妹的婚礼回的淮海。猴哥其实不用出来打工,他在河南安阳老家有辆大
吊车,以前光靠开这个月收入就可近万。今年经济不好,总淡季,便把车三千一
个月租给别人,自己出来打工。我以前特好奇猴哥为啥出来打工。他那日问我,
知道我给老妹送了啥么?我奚落他,一万块?他回我,一辆车。我顿时愣在那。
这么贵重?我问他。后来我才知道,老妹,也就是猴哥的亲妹妹当年为了猴哥结
婚,把在外面打工几年挣的积蓄都给他了,还欠了一屁股债让哥哥娶上媳妇。打
那时起,猴哥就琢磨着以后不能亏待妹妹。那晚,猴哥说着说着落泪了。我赶忙
端起酒杯,说我们喝酒,然后出去嚎两嗓子。我们两个大老爷们便默默喝起酒来,
什么都不用说。
人,在全球化的经济与国家经济浪潮中究竟能怎样?这远不是结构性与能动
性能够洞察的。杰姆逊在北大的讲演中说道,“身体是资产阶级文化在消耗殆尽
之前的最后现实,是转变、变化和变异的最后发生地,是主体的昂扬自信的激情
消退后残留的一点点心情。”2
本文呈现了流行音乐的传播、分享、消费如何被新生代劳工配置在日常生活
之中,成为他们建构自主的空间、表达自我情感和记忆的工具。换言之,流行歌 1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生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117. 2 参见《著名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教授在北大发表演讲》http://pkunews.pku.edu.cn/2012-12/13/content_260768.htm
64
曲的意义是这些第一线的传播者兼消费者赋予的——通过把它们与脱域了的地
域(对家乡的朦胧想象)关联起来,与他们的工作、婚姻、过往生涯的记忆和自
我认同关联起来,与信息科技变革如智能手机的普及带来的生活方式变迁关联起
来。结果,新生代劳工们跌宕多端的生命历程遂被汇聚成红歌、港台流行歌、网
络歌曲/农业金属等风格拼贴混杂而成的声境。
作为结论,本文通过还原新生代劳工通过传播和消费流行音乐过程中彰显的
主体性,一方面批判了既往“中国的流行音乐研究”所预设的城市中心主义、生
产面中心主义(以经纪公司、唱片公司、创作者和歌手为中心的书写)和产品拜
物教(“音乐的意义在于其本身的形构”这种意识形态),同时也批判了时下的
劳工研究以“关怀弱势”的启蒙解放者姿态贬抑新生代劳工的自主能动性的倾向。
质言之,本文希望能藉着如实呈现一群新生代劳工的音乐生活,说明他们不
是仅能默默承受剥削或者被彻底无视的客体,也不是阶级意识觉醒后奋起反击的
主体,而是不断在努力追求和表达丰富多彩的人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65
参考文献
一、中文文献
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理论研究,霍桂恒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刘冉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2
艾德·加莫兰,社会学思考,阎素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安东尼·西格,音乐民族志理论,载张伯瑜等编译,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北京: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安东尼·西格尔,苏亚人为什么会歌唱,洛秦译,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
保罗·杜盖伊、斯图加特·霍尔等,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霍炜译,商务印书
馆,2005
博·赫拉巴尔,我是谁,星灿、劳白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布尔迪厄,帕斯卡尔式的沉思,刘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周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戴维·科普兰,音乐学,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8(4)
道格·桑德斯,落脚城市,陈信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付林,中国流行音乐 20 年,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上册),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黄斌欢,跳跃式换工——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体制与就业策略,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六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基思·特斯特,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贾克·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宋素凤、翁桂堂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金兆均,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陆道夫,狂欢理论与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02(4)
陆正兰,歌词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陆正兰,传唱者拍板:流行歌曲歌众的文化角色,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
陆正兰,从符号学看当代歌词中的女性自我矮化,当代文坛,2012(5)
洛秦,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导论,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66
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马立克·科尔钦斯基等,工作社会学,姚伟、马永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马塞尔·达内西,酷—青春期的符号和意义,孟登迎、王行坤译,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
苗金海,基本乐理课教学中的几个疑点、难点解析,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6(4)
尼古拉斯·加汉姆,解放•传媒•现代性——关于传媒和社会理论的讨论,李岚译,北京:新
华出版社,2005
欧阳玥、戴志强,音乐节拍认知的研究评述,心理科学进展,2010,(11):1692-1699.
齐格蒙·鲍曼,来自液态现代世界的 44 封信,鲍磊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生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曲舒文,谁的“摇滚精神”——警惕中国摇滚音乐研究的定式思维,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
乐与表演版),2012(3).
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任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潘毅、卢晖临、郭于华、沈原,我在富士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瑞雪·墨菲,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黄涛、王静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杨德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汤亚汀,城市音乐景观,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0
汤亚汀,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王冠群,通俗歌曲创作十讲,长春市:长春出版社,1993
王思琦,中国当代城市流行音乐——音乐与社会文化环境互动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9
王亦高,在时间中聆听:作为符号而传播的音乐,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夏铸九,休闲的政治经济学——对台湾的 KTV 之初步分析,户外游憩研究,第五卷,1992
(2)
萧梅,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谢丽期·克拉马雷,路特里奇国际妇女百科全书精选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薛艺兵,旋律学建设的一些理论思考,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98(4).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67
杨德睿,在家、回家:冀南民俗宗教对存在意义的追寻(香港树人大学当代中国研究论文系
列第二辑),香港:香港树人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2010
伊莱休·卡茨,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游俊、龙先琼,湘西农民闲暇生活方式变革的文化审视,吉首大学学报,2000(01)
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周倩漪,从王菲到菲迷——流行音乐偶像崇拜中性别主体的搏成,新闻学研究第 56 期,1998
周志强,声音的政治——从阿达利到中国好声音,中国图书评论,2012(12)
68
二、英文文献
Abner Cohen. Masquerade Politics: Explorations in the Structure of Urban Cultural Movem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Adorno, Theodor. Music and Language, pp. 1–6 in Quasi una Fantasia: Essays on Modern Music,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1992.
Adorno, Theodor. On Popular Music, in Frith, S. & Goodwin, A. eds. On Record. London:
Routledge, 1941/1990.
Andrew F. Jones. Like a Knife: Ideology and Genr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pular Music.
Ithaca: Cornell East Asia Program. 1992.
Andrew F. Jones. “The politics of popular music in post-Tiananmen China.” In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2nd ed., Wasserstrom and Perry e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148-165.
Arnold Perris. “Music as Propaganda: Art at the Command of Doctrin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thnomusicology 27, no. 1, 1983: 1-28
Bendix, Regina. The Pleasures of the Ear: Toward and Ethnography of Listening. Cultural
Analysis 1. 2000.
Benjamin, W.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Benjamin, W.
Illuminations. Fontana, 1977.
Bernoviz, Nimrod. China's New Voices: Politics, Ethnicity, and Gender in popular Music Culture
on the Mainland, 1978-1997. Ph.D. Dissertation, Univ. of Pittsburgh, 1997.
Brace, Tim. Popular Music in Contemporary Beijing: Modernism and Cultural Identity. Asian
Music, 1991, 22(2):43-66.
Casey Man Lum, In Search of a Voice: Karaok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Chinese
America,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6.
Chaney, D. The Cultural Turn: Scene-Setting Essays on Contemporary Cultural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4.
Charles Sanders Peirc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vol. 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69
Christopher Waterman. Juju: a Social History and Ethnography of an African Popular Mus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Dan Sperber. Explaining Culture: A Naturalistic Approach, Oxford: Blackwell, 1996.
Daniel Cavicchi. Tramps Likes Us: Music and Meaning Among Springsteen Fa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Dent, Alexander Sebastian. River of Tears: Country Music, Memory, and Modernity in Brazi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Edward Sapir. Song Recitative in Paiute Mythology.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23, 1910:
455-72.
Frith, Simon. Performing Rites: On the Value of Popular Mus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Fung, Anthony. Consuming Karaoke in China: Modernities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s.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42(2), 2010: 39-55.
Gianni Sibilla. When new media was the big idea: Internet and the rethinking of pop-music
languages, in Erkki Pekkilä, David Neumeyer & Richard Littlefield (eds.), Music,
Meaning and Media. University of Helsinki. ,2006
Graeber, David. Consump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2011(52).
Ho, W. C. Social change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s popular songs. Social History, 31(4), 2006
Huang, Hao.Voices from Chinese rock, past and present tense: social commentary and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yaogun yinyue, from Tiananmen to the present. Popular Music
& Society.2003, 26(2): 183-202.
James W. Fernandez. The Argument of Images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turning to the Whole, in
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 Victor W. Turner and Edward M. Bruner, eds., pp.
159-187.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6.
Jeff Packman. Singing Together/Meaning Apart: Popular Music,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Salvador, Brazil. Latin American Music Review 31, no. 2 (2010): 241-267.
Jeroen de Kloet. China with a Cut: Globalization, Urban Youth and Popular Music.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Jessica Kuper, ed. The Anthropologists’ Cookbook.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77.
70
Jianying Zha. China Pop: How Soap Operas, Tabloids, and Bestsellers are transforming a
Culture,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5.
Jocelyne Guilbault. Zouk: World Music in the West Ind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Johansson, O. and Bell, T. L. (Eds.). Sound, Society, and the Geographies of Popular Music.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2009.
John Shepherd, David Horn, Dave Laing, Paul Oliver and Peter Wicke. Continuum Encyclopedia
of Popular Music of the World Volume 1: Media, Industry and Society. London:
Continuum. 2003
Latham, Kevin. Pop Culture China! Media, Arts and Lifestyle.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2007
Leslie T. Chang. 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 New York: Spiegal &
Grau Trade, 2008.
Lévi-Strauss, C. The Raw and the Cooked. Mythologiques, Volume On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Lowie, Robert. The Crow Indians. 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 1935.
M. Herskovits. The Myth of the Negro Past.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1.
Machin, David. Analysing Popular Music: Image, Sound and Text.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10
Margaret Mead. Coming of Age in Samo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28.
Margaret Mead. Growing Up in New Guine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rimitive Educatio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30.
Marshall, L. The Sociology of popular music,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aesthetic autonom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1 vol. 62.
Martin Stokes. Music and the Global Order.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33, 2004.
Merriam, Alan P. 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4
Moskowitz, Marc L.. Cries of joy, songs of sorrow: Chinese pop music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s.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0:21.
Negus, Keith. Popular Music i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71
Nettl, Bruno. Nettl's Elephant: On the History of Ethnomusicolog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0.
Paul Friedlander. China's "Newer Value" Pop: Rock-and-Roll and Technology on the New Long
March. Asian Music, 1991, 22(2): 67-81.
Roy Shuker. Understanding Popular Music, Seco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8
Ruth Finnegan. The Hidden Musicians: Music-Making in an English Tow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Sara Cohen. Rock Culture in Liverpool: Popular Music in the Mak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Schneider, Albrecht. Musikwissenschaft und Kulturkreislehre : zur Methodik und Geschichte der
Vergleichenden Musikwissenschaft. Bonn-Bad Godes- berg: Verlag fiir systematische
Musikwissenschaft, 1976.
Schutz, A. “Fragments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Music”, in F. J. Smith (ed.) In Search of Musical
Method, pp. 23–71. London: Gordon and Breach Science Publishers, 1976.
Small, Christopher. Musicking: the meanings of performing and listening. Hanover and London,
University,1998.
Small, Christopher. Musicking: the Meanings of Performing and Listening. Music Education
Research . 1999.
Stafford, Charles.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next? In: Astuti, Rita and Parry, Jonathan and Stafford,
Charles, (eds.) Questions of anthropology. Berg, Oxford, UK, 2007
Ting Chunchun. Rock under the red flag :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Chinese rock music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phil. Disserta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1.
Touraine, A. Can we live together?: equality and difference. Cambridge: Polity, 2000.
Weber, Max . The Rational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Music, trans. Don Martindale, Johannes
Riedel and Gertrude Neuwirth.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58.
Willis, Paul. Common Culture.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0.
72
致谢
入夜,雨声侧畔,思绪延异。三年的研究生生涯即将划上休止符。这个句点
意味着按照惯例,我得写点什么。
我要感谢杨德睿老师。跟随师父研习人类学的这三年,是师父耳提面命的三
年,是与师父对饮坐谈的三年,也是弟子学会内省吾身的三年。能够忝列师父门
下是弟子的荣幸,但弟子素来愚钝,不敢说业已习得皮毛,但愿这篇习作没有辜
负恩师的心血。师母待我亦如家人,数度邀我做客,您对我学习生活的关心弟子
也感怀于心。
我要感谢邵京老师。初识人类学就缘于您所讲授的亲属制度研究和乙肝的医
疗人类学研究这两门课程。是您为我叩开了人类学这座殿堂的大门,让我产生了
无尽的好奇;是您提点我人类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应该半颗脑袋做学问,一颗
心做人的道理。您对学生的教导,学生铭感于心。
我要感谢范可老师。如果说三年来学生还有些许进步的话,一定与您对学生
的教导和帮助有关。蒙您不弃,从翻译到申请到参加学术会议再到奖学金,每一
步都有老师您的提携。您时常鼓励学生,这也让学生能够鼓足勇气在人类学的道
路上走到现在。日后虽不能继续学术,但您的教诲,学生铭记于心。
我要感谢杨渝东老师。感谢您在鼓楼召集的读书会,那时您领着我们阅读人
类学史,那时我也遭遇了未完成的黄文山。每当习作自己都不忍卒读时,您都能
耐心读完并给出很多建议。这篇习作也凝聚了您的心血,感谢您从北京大学图书
馆帮我复印的那批英文书籍。没有它们的启发,这篇习作恐是另外一个模样。
我要感谢褚建芳老师。您的谦和、爽朗、真诚一直是我求学道路上的榜样,
感谢您在去年申请时给予我的帮助。
我要感谢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诸师的学识之渊博自不待言。于学生而言,
能够在这个严谨、深邃、温馨的集体中求学,是学生三生修来的福气,谢谢诸位
老师的谆谆教导。
我要感谢中华回教慈善基金会对我论文的资助,正是因为这笔资助本文研究
中很多外文文献才能得以购买与复印,最后一次田野回访调查才能得以成行。应
73
该说,在当下与国家政经不相关的经验性研究越来越不受待见的时候,中华回教
慈善基金会对学子的资助显得难能可贵。
我要感谢首都大学东京大学院的川濑由高、香港中文大学的袁长庚、香港科
技大学的钱霖亮、华中师范大学的刘杰。正是你们仔细的阅读,才让我深知民族
志写作的不易以及自己文字的拙劣。
天齐、春媚、罗敏、子暄,此去经年,犹记得我们在鼓楼一起痛苦挣扎的课
业时光,还有我们四处觅食的吃货时光。春媚、罗敏、张磊、维颖、双德、李郴,
正因为你们的陪伴,我想 364给我留下的美好足够让我细数到老。师妹方梦茜,
谢谢你的春生,让我在最后奋战的夜晚不至于显得难熬。傅琦师姐,胡艳华师姐,
谢谢你们对我学习生活工作的关心。
从二零零五年九月到二零一三年六月,我在南京学习生活了近八年,这已然
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要感谢我的本科老师李义波老师,朱考金老师,屈勇老师,
是你们把我领进社会理论的大门,包容我年少懵懂时的恣意。我要感谢沈辉,同
学五年,一辈子的好兄弟,还有栗治强、黄洋、肖海逍、杜俊圣、赵蕾、陈启、
董强诸位本科同学对我的关照。陈昌、林晓、金鹏、史程、金沂、施光军、窦伟、
曹学伟、张琦,你们见证了我这八年青涩温暖的南京岁月。
我要感谢我在淮海的工友们,阿刚、大海、大郭、小郭、小刘、猴哥、阿花……
因为你们,我这两个多月的工厂生活一点都不孤单;因为你们,我感受到了活着
的意义;因为你们,才有了这篇文字现在的模样。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你们的养育之恩。从高中时离家求学迄今已
经整整十二个念头。十二年来,你们日渐花白,年近耳顺,却还在为我奔波。虽
然至今你们也不知道我的这个专业叫什么,有何用,但你们一直都拼尽全力支持
我的学业。孩儿不孝,几近而立也未能侍奉双亲,树欲静而风不止,日后孩儿定
加倍努力!
李胜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于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河仁楼 364 无用斋
74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1、 李胜,命以载史:民间信仰与个体生命——以江苏南京高淳叔村出菩萨仪式
为例,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2 期;
2、 李胜,Pop Music in Xiaokang Village,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办的第五届
“亚洲青年人类学论坛”宣读,2013 年 1月 18-19日;
3、 LI Sheng. Marriage Customs in Nanjing. in Ryoko SAKURADA and Meari
HIRAI ed., Social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Belief, Life, and the Family in
Present-Day Nanjing. Kyoto: Kyoto University, 2010
http://www.econ.kyoto-u.ac.jp/daikokai/research%20outcome/outcome_nanjingdu
shi.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