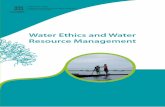瀟湘八景:東亞共同母題的文化意象 Eight Views of Xiao-Xiang: The Culture Image of East Asia
Two Issues on Zheng Xuan's Studies of Rituals【鄭玄禮學二題】
Transcript of Two Issues on Zheng Xuan's Studies of Rituals【鄭玄禮學二題】
‧65‧
鄭玄禮學二題
刁小龍*
提 要 東漢鄭玄之禮學解釋體系一以《周禮》文本解釋為基準,今以鄭玄藏
冰、用冰與五祀說二例以證之,可知此言不虛。唯鄭玄所據之「周禮」恐非僅據
今所見文本之《周禮》,而是一秩序井然、決無矛盾之純粹「周禮」,以定經義、
別禮制,暢通其說,彌縫諸經。 關鍵詞 鄭玄 周禮 藏兵 用兵 五祀
東漢鄭玄為《周禮》、《儀禮》、《禮記》三部禮學經典作注解,影響巨
大。鄭玄之前,遍注三禮者或有其人,但說多散佚,難得其詳。至鄭玄出,
承前賢眾說而賸意迭出,取而代之,或有以也。後學一尊鄭氏三禮注,有所謂
「禮是鄭學」之說。禮學之會通仰賴鄭氏注解久矣。雖然,學者亦嘗指出,
鄭玄禮學解釋乃以《周禮》為基準,調和禮學經典中相互牴牾記載,禮學體系
因此得以建立,禮學典籍卻也因此相互雜糅,難辨原委。是說陳義頗高,舉
證詳言則頗不易;亦因禮學自來艱澀難通,鮮乏問津者所致。筆者問學,體玩
鄭注,頗有感於斯言,思有以申明之。今乃不揣譾陋,試以二例證之,略窺鄭
*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講師 傳馬融、盧植等人於鄭玄之前已遍注三禮。《後漢書‧馬融傳》云其曾注《三禮》,又〈盧
植傳〉云其撰述有《三禮解詁》,然皆逸。後人攟拾殘文,或未可盡信。 「禮是鄭學」說三見《五經正義》,是漢末至隋唐之際數百年間學術理論自然選擇之明證。 沈文倬先生曾有云「鄭玄注《禮》在箋《詩》之前,怵於本經殘闕,戴記蕪雜,而《周官》
所述名物甚富,遂援之以入經若記者,其卒也不特三書渾然一體,不復知其抵牾,抑且以古
《周禮》說強解十七篇之文(《儀禮》),使其旨若明若晦,而西漢今文經亦遂其學浸微而
其本湮沒矣。」可謂知言。說參沈文倬〈序陳戍國點校《周禮‧儀禮‧禮記》〉,湖南嶽麓
書社出版。
‧書目季刊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2011 年 6 月‧
‧66‧
玄禮學解釋體系暨《周禮》學之一斑。倘得博雅方家匡謬是正,幸何如哉。
一、藏冰、用冰說
經典之中於上古之時藏冰、用冰一事記載頗富。繙撿所知,約得五處:
(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
冰。冰以入。(〈月令〉)
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中略)夏,頒冰,掌事。秋,
刷。(《周禮‧天官‧凌人》)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詩‧
豳風‧七月》)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
冱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
藏之也,黑牲、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
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
(《左傳‧昭公四年》)
(三月)頒冰。頒冰也者,分冰以授大夫也。(《大戴禮記‧夏小正》)
上述所見,〈夏小正〉一篇文字鄭玄不用─三月頒冰明與《周禮‧凌人》「夏
頒冰」相互牴牾,餘者鄭玄注經皆有涉及。四者之中,或因《左傳》文字最為
詳盡:藏冰時節、處所;用冰之節、用冰之人;藏冰前之祭祀,用冰時之禮儀;
公始用、復次頒眾之次第等等一一盡舉,故鄭玄屢次援引以詮解其他經文,〈月
令〉注中更全引上段《左傳》文字以為說明。
康成諸注初看之下,不過以《左傳》之詳補充他經之文不備而已,似無深
論。詳攷之,實或未必。
《豳風‧七月》文字敘述時節順序的井然不亂,依毛傳所述,則此「一之
日」、「二之日」云云皆周正,若以此為順序,或可將〈七月〉、〈月令〉、
〈凌人〉藏冰、用冰時節表之如下:
‧鄭玄禮學二題‧
‧67‧
周正 《豳風‧七月》 《禮記‧月令》 《周官‧凌人》
二月 二之日,鑿冰沖沖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
冰。冰以入。 正歲,十有二月,斬冰
三月 三之日,納於凌陰
四月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五月
六月 夏頒冰
如上表所示,則《詩‧七月》十二月鑿冰、正月納冰、二月即用冰;〈月令〉
所述則十二月取冰藏之,至二月用之;《周禮‧凌人》則十二月取冰,至夏乃
頒冰。以〈月令〉並〈凌人〉言則《詩‧七月》正月納冰、二月用冰殊覺短促,
故《毛傳》以為豳地晚寒,鄭玄更以為「由寒晚得晚納冰,依禮須早開放」也。
《左傳》說當如何置入此表中?
按之《左傳》所述藏冰、用冰時節,其要在「北陸」、「西陸」、「火」
等關鍵詞語訓釋。此條解說,鄭玄之前尚存服虔說逸文,此後則有杜預注。三
家之說略有出入,今並舉諸家說如下:
服虔:陸,道也。北陸言在十二月,日在危一度。西陸朝覿,不言在則
不在昴,謂二月,在婁四度,為春分時奎、婁晨見東方而出冰,是公始
用之(《凌人疏》引)。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凌
人疏》並《宮正疏》引)。
鄭玄: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凌人疏》引
鄭玄答孫皓語)四月之時,日在昴畢之星,朝見東方。于時出冰,以頒賜
百官。若其初出薦廟,時在二月。(《詩‧七月正義》隱括鄭玄說)
杜預:陸,道也。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
鄭玄注「孟春」為「斗建寅之辰」,是謂〈月令〉用夏正。 鄭玄謂「正」為夏正。 《詩‧七月正義》引鄭玄答弟子孫皓。 服虔說參考重澤俊郎《左傳賈服注攟逸》坤卷。日本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報告第八
冊,昭和十一年(1936 年)印行。又孫詒讓謂服注「火出而畢賦」云云實出《左傳》昭十七
年梓慎語,甚是。《周禮正義》卷十,頁 378。王文錦、陳玉霞點校,中華書局出版。
‧書目季刊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2011 年 6 月‧
‧68‧
方。(中略)二月春分獻羔祭韭,開冰室。(中略)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
月中。
北陸、西陸之說,服、杜不取《爾雅‧釋天》「北陸,虛也」、「西陸,
昴也」說,而徑釋陸為道,邵晉涵以為:「北陸者,四陸之一也。古以星紀日
月之行,分為四象,亦謂之四陸。」郝懿行則據孫炎「西方之宿,昴為中也」
「北方之宿,虛為中也」,以為《爾雅》以虛、昴釋北陸、西陸者,乃「舉中
以包之」。如是說則北陸、西陸並為泛指。故服說以為「奎、婁晨見東方」,
杜預以為「奎星朝見東方」,稍別而大同。而鄭玄說以為西陸乃四月,所以然
者,「以西陸為昴,《爾雅》正文。西陸朝覿當為昴星朝見,不得為奎星見也,
故知出之為四月。」「火出」之解釋,服說三月,杜則三月四月中,亦略別,
而鄭說無明文,付之闕如。若依前揭時節說,將服虔、鄭玄、杜預三說表之,
則如下圖所示:
北陸 西陸 火
服虔 危,十二月 婁,二月 火三月
杜預 虛危,十二月 昴畢,三月 火出,三月四月中
鄭玄 虛也,十二月 昴畢,四月
復觀《左傳》本文,北陸藏冰、西陸出冰(用冰)、火出則「畢賦」─當用者
皆與,其大體順次如此。是服虔說以為十二月藏冰,二月出冰而公始用之,三
月「畢賦」,次第井然,與《左傳》本文最協;杜預則十二月藏冰,二月出冰
(「春分獻羔祭韭,開冰室」),至三月「蟄蟲出而用冰」,三月四月中乃「畢賦」,
說略別於服說,然亦允當。鄭玄則以為十二月藏冰,二月用冰(「初出薦廟」),
至四月乃出冰,「火出而畢賦」雖不詳言,然亦已「于理難通」。
邵晉涵《爾雅正義》,續修四庫全書本 187 冊,頁 173。 郝懿行《爾雅義疏‧中之四‧釋天》,中華書局影四部備要本,頁 122。又孫炎注《爾雅》
釋「陸」為「中」,與眾說不同,疑舉義釋訓,非常訓。 孔穎達《正義》,頁 392,中至下欄。 孫詒讓語,《周禮正義》卷十,頁 378。此條鄭玄說《左傳》別於服說,前賢已有論及,詳
參重澤俊郎《左傳服、鄭異義說》,《東方學報(京都)》第四冊,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
所,1934 年 1 月。中譯文參看彭林主編《中國經學》第二輯,石立善譯文。廣西師範大學出
‧鄭玄禮學二題‧
‧69‧
鄭玄何以別於眾說,竟至如此奇怪立論?略言之,其旨歸則在遷就《周禮‧
凌人》「夏頒冰」之說。若以服虔說,則「畢賦」用冰則在三月,當季春之時,
顯然不與此合;如鄭玄說則用冰已至四月,頒冰「畢賦」自然在此後,而四月
以後已然入「夏」,是恰與〈凌人職〉所述合。是知服虔、鄭玄二人所以去取
《爾雅‧釋天》文字不同者在於此:鄭取之乃因其「昴畢四月」正在「夏」;
而服去之,亦因若從之則《左傳》文本次第錯亂;服、鄭於「火出而畢賦」條
取去《左傳》本文「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亦在於此:
其取者為《左傳》之次第井然;其去者乃嫌其與《周禮》「夏頒冰」說相違。
是以一為《周禮》立說,一為《左傳》立說,其差異乃至於此。而杜預適為二
者調和之論:其說北陸、西陸不從鄭而從服,乃《左傳》本文次第所需;其釋
三月四月中「畢賦」用冰者,正為遷就《周禮》「夏頒冰」之說而依違於《左
傳》「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者,是其處於兩雄之間,
無可奈何矣!
又《左傳》「火出而畢賦」條,鄭玄無說。按此「火」乃指心星,而火見
(出)則有季春、季夏二候之說。以火為季夏之候者,如《國語‧周語中》:「火
見而清風戒寒」,「火之初見,期於司里」,韋昭前文下注「謂霜降之後,清
風先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又《詩‧豳風‧七月》「七月流火」,鄭箋「大
火者,寒暑之候也」;《禮記‧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等等。此皆以
火為季夏之候。以火為季春之候者,《左傳‧昭公十七年》梓慎「火出於夏
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又《詩‧召南‧小星》「嚖彼小星,三
版社 2007 年 5 月出版。
孫詒讓已述此。詳參《周禮正義》卷十,頁 378。 《尚書‧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火謂大火,夏至,南之中星」,說與鄭玄
不同。按《豳風‧七月正義》引《鄭志》「孫皓問:『〈月令〉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
盡以為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
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為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
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禮經‧月令正義》約引上文作
「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為大火」,詞異而義同,並以〈堯典〉中「火」為大火之
次,非確指心星之名,而有別於〈月令〉等文。今或以為此所以一在仲夏(〈堯典〉文)、
一在季夏(〈月令〉)者,乃因歲差所致,而康成不曉。參看黃焯《詩疏平議》五,頁 205,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書目季刊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2011 年 6 月‧
‧70‧
五在東」,鄭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又《周禮‧天官‧宮正》「春
秋以木鐸脩火禁」,鄭注:「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戒;」又《夏
官‧司爟》「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注引鄭司農說
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
使民內火」,又《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云:「季春昏,心星出東方,
(中略)季秋星入則出火,以順天時,救民疾」等等。邵晉涵嘗為上二說協調之
云:「火出在三月」,「九月之昏火始入,十月之昏則伏」,似頗允當。
然則,鄭玄之解《左傳》「火出」當作何說?依《左傳》文序,「畢賦」
在用冰之後,是春寒入夏之際。以上文火見為季夏之候例之,則與《左傳》時
間相隔懸遠,不可援用;若以季春之候例之,《左傳》文順而與《周禮》立論
迥異。據此或可推斷,鄭玄所以默不言者,實無法為此詳說,非無說耳。問曰:
何以至此?答曰:正《周禮》與《左傳》、〈夏小正〉文本根本差異所致。此
二者決不可調合。欲其兩存之則可,必如鄭玄依《周禮》為指歸遷合二說,乃
不可通如此。孫詒讓云:「(《周禮‧凌人》)頒冰是夏非春,與《左傳》、〈夏
正〉之文不能強合也」,誠哉斯言。
鄭玄援《左傳》說詮釋他經藏冰、用冰文字略如上述。其所以援引《左傳》
者,蓋因他經文字簡略,不能賅備其禮儀制度,鄭玄不得不如此耳;而通觀其
所闡述《左傳》文字者,則其本旨乃在以《周禮》為指歸,調和《左傳》、《周
禮》文字差異,疏通群經。求諸形式則辯證經義、補全禮文;求諸內核,仍欲
一以貫之於《周禮》,藉此調和群經,甚至不惜犧牲《左傳》說,強為之辯以
通《周禮》,乃造新論,甚至扞挌難通。如此用心,不可謂不深矣。
二、五祀說
三禮之中,五祀之說散見諸書,記載頗多。《儀禮》中唯一見於〈既夕禮〉
邵晉涵《爾雅正義》,頁 171。 《周禮正義》卷十,頁 378。
‧鄭玄禮學二題‧
‧71‧
篇末記文,「乃行禱于五祀」;《周禮》則散見於〈春官‧大宗伯〉、〈司
服〉、〈小祝〉職、〈夏官‧小子〉職等處;《禮記》則有〈曲禮下〉、〈王
制〉、〈月令〉、〈曾子問〉、〈禮運〉、〈祭法〉等篇涉及五祀。按覈三禮
經典文本,則《儀禮》、《周禮》並未有五祀之詳細解釋;具體說明其內容者
唯見於《禮記》相關篇章記載。其中,尤以〈祭法〉篇言之最詳:
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
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
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
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依上說,則五祀祭祀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之神,為諸侯之制。然而
同書〈月令〉篇所說五祀則與此略異。〈月令〉篇中,將五祀分置四季之中,
分別與五行相對應:春氣木,祀戶;夏氣火,祀竈;中央(季夏)土,祀中霤;
秋氣金,祀門;冬氣水,祀行。從此說則五祀所祭為門、戶、中霤、行、竈五
神。
二文所載之別,鄭玄認為「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
察小過,作譴告者爾」(〈祭法〉注),是五祀所祭皆為小神,等級不高;又「司
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周禮‧小祝》注),似不為常祀。如其說,則
〈祭法〉與〈月令〉所述大同小異,實可歸為一旨。
然而〈月令〉文字「記十二月政之所行」(《月令正義》引鄭玄《目錄》),
則五祀當為王(天子)之制度,與〈祭法〉所云諸侯之制實不相同。若依此等級
之別,則三禮經典中所載五祀之說,略可分為如下五說:
天子(王)制度:《周禮》諸文、《禮記‧月令》、〈曾子問〉、〈禮運〉
〈既夕禮〉為〈士喪禮〉下篇,鄭玄〈祭法〉注即引作〈士喪禮〉。 《白虎通》記載五祀文字與諸經略異,然不在本文討論之列,暫置不論。 曾子與孔子問答天子(王)喪禮之變例事。其一: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
(中略)孔子曰:「大宰命祝史,以名遍告于五祀、山川」;其二:曾子問曰:「天子甞、
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中略)天子
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啟至于
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書目季刊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2011 年 6 月‧
‧72‧
;諸侯制度:〈祭法〉;大夫制度:〈王制〉;士之制度:《儀禮‧既夕
禮》;天子、諸侯與大夫皆用制度:〈曲禮下〉。
諸說究竟何者為是,僅以上述文獻記載實難判定。
前文所示禮學經典記載之牴牾,鄭玄作三禮注之時,一一為之調和化解。
若先揭櫫結論,大而言之則正如前賢所云,鄭玄乃以《周禮》說為本,條理諸
說;就五祀解釋細言之,則鄭玄創以五祀兩系、異代之說,以《周禮》說條貫
其他禮文。
鄭玄解釋《周禮》之五祀,別為兩系:一則中祀,祭祀五官(五行)之神;
一則小祀,祭祀門、戶、中霤、行、竈等五神。〈小祝〉「凡事,佐大祝。大
喪,贊渳,設熬,置銘;乃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鄭玄注為「王七祀,
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即後者小祀之屬。
鄭玄以五祀為中祀、五官(五行)之神之說見於《周禮‧大宗伯》下注:
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
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
金;脩及熙為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火
土。
此釋五祀為五官之神,說實從《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傳》:
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
是尊是奉。
孔子答弟子言偃先王之制度:其一:「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中略)降於五祀之謂制度」;
其二:「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中略)五祀所以本事也。(中略)禮行於五祀而正法
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或謂此所祭者乃祭祀其極,其餘並兼而祭之,
《公羊傳》僖公三十一年何休注云:「天子所祭莫重於郊」,「諸侯所祭莫重於社。卿大夫
祭五祀,士祭其先祖。」《續禮記集說》引姚際恆說「天子祭天地,自得兼祭社稷、五祀可
知;諸侯祭社稷,自得兼祭五祀可知」。誠如此說,則此與〈曲禮下〉所云並無二致。理或
當然。姚說轉引自杭世駿《續禮記集說》卷二十二,頁 331,續修四庫全書 101 冊。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
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鄭玄禮學二題‧
‧73‧
鄭玄依《左傳》說解釋五祀為祭祀五官之神,前無古人。但氏說未嘗無可疑之
處。孫詒讓即以為「《左氏》之五官乃五人神,五示(〈大宗伯〉中五祀所祭)與
五官名同而實異」,「蓋重、該等五人官雖亦配食五祀,而五祀主神,實非五
人官,鄭掍為一,非也」。孫說固有道理,然而鄭玄非不知此人、神本或有
別:〈月令〉「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句下鄭注即云:「此蒼精之君(謂太皥),
木官之臣(謂句芒)。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既云「著德立功」則本初皆
為人身,但經文明言「其帝」「其神」,則皆已由人入神,代其神名,故所
謂「蒼精之君」、「木官之臣」皆已非人官、不僅配食而已。
所以別五祀為二系者,在於鄭玄以為《周禮》文本邏輯縝密,等級區別森
然所致。攷〈大宗伯〉文云: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
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
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
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是經文區別天神、地示、人鬼祭祀禮儀,各有不同,而同一部類之中祭法復又
有別。社稷以下雖同為「地祇,祭地可知」,但社稷、五祀、五嶽經文言「以
血祭」;山林川澤言「以貍沈」;「四方百物」則言「以疈辜」。祭法既別,
所祭之神祇不能不有隆殺等差。究其原委,鄭玄以為,在於「陰祀自血起,貴
氣臭也。」貴者為先,後者自然等次漸殺。地祇陰祀以社稷、五祀為首,則此
文五祀必非小祀可知。故〈肆師〉鄭玄即依此〈大宗伯〉文為注云:
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岳,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
師、山川、百物。
可知《周禮‧大宗伯》大、次、小祀之次第即鄭玄另立五祀為五官之神說根本
《周禮正義》卷三十三,頁 1323。 孔穎達以為互文之例,即太皥稱帝則句芒為臣(鄭注所謂木官之臣);句芒言神則太皥屬神
不言可知。
‧書目季刊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2011 年 6 月‧
‧74‧
所在。清黃以周嘗謂:
《周禮》五祀有二。一為中祀,《左傳》所云句芒、祝融、蓐收、玄冥、
后土是也。在王者宮中,曰戶、竈、中霤、門、行,群小祀也。〈大宗
伯〉「五祀」文在「五嶽」上,為中祀,故鄭據《左傳》文以釋之。〈小
祝〉所掌五祀為群小祀,故鄭據〈月令〉文以釋之。
此即本鄭玄之說立論。
鄭玄解《周禮》中五祀即如上述。鄭氏復以之解說其他禮文。《禮記‧曲
禮下》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
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鄭玄即本《周禮》五祀兩系
說為之別解云:
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
玄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五
祀,戶、竈、中霤、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
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
所以解四方為五祀、五官之神者,蓋四方既類《周禮》地祇之屬,又絕非社稷
之別名,且序在山川之上,按之〈大宗伯〉所云,唯有「五祀(五官之神)」足
以當之。誠如此,則〈曲禮下〉乃適與〈祭法〉所述前後不一。在鄭玄看來,
《周禮》所述禮制既然邏輯縝密,等級森然,絕無混亂,是以〈曲禮下〉所云
天子乃至諸侯、大夫皆五祀之說則毫無等差,不若〈祭法〉記載之井然有序,
頗與《周禮》體系近似,因此定〈曲禮下〉所云為「殷時制」,別與周時。於
是,鄭玄遂有殷、周兩代禮制之說。如此五祀體系中為五官之神之說亦周人兼
採前代制度,未為新法。
而〈祭法〉中所云天子、諸侯、大夫、士小祀七、五、三、二等差之說,
既為鄭玄納入周代之制;其它如〈月令〉王五祀之說自然歸屬別代禮制;而〈王
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鄭玄則以為「此祭謂大夫有
《周禮正義》卷五十,頁 2041。
‧鄭玄禮學二題‧
‧75‧
地者,其無地祭三耳」,所謂「三」正出〈祭法〉大夫三祀之說;而〈既夕禮〉
「乃行禱于五祀」,鄭注則曰「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士二
祀以下文字亦本〈祭法〉文,而云「五祀博言之」者,蓋鄭玄並不以之為實指
之謂。賈公彥疏云「今禱五祀,是廣博言之,望助之者眾」,疑非鄭旨。
綜上所云,可為鄭玄五祀說概括如下云:一,三禮經文之中,五祀有二系,
一則中祀,祭祀五官之神,亦謂四方。此或為殷、周並用之制;案之《周禮》
次第,次社稷之下而在山川等之上,是以鄭注《禮記‧曲禮下》從之;再則
小祀,祭祀門、戶、中霤、行、竈等五神之屬,此則位居山川之下,是以鄭注
《禮記‧曲禮下》、〈禮運〉等皆以此當之。後者之中又有周禮與他禮之別,
周代之制,天子、諸侯、大夫、士等級秩然,七、五、三、二各有所祭;他朝
制度則或未能如此盡善盡美。需附言者,鄭玄以〈祭法〉中所云大夫三祀為無
地大夫,而〈王制〉五祀者為有地大夫,此又一論。
鄭玄五祀之說可略為表之如下:
〈曾子問〉君薨世子生條,五祀在山川之上,鄭玄仍以小祀當之,此為特例。所以然者,孔
疏引鄭說:「稱世子生,喪在殯,告五祀山川耳。五祀,殯宮之五祀;山川,國鎮之重。不
可不告。故越社稷告之。既葬而世子生,三月而名,葬後三月,於禮巳祔廟,故告可及廟。
廟與社稷相連,不得不告社稷。」(《禮記正義》卷十八,頁 360,臺灣藝文印書館景嘉
慶阮元刻本《十三經註疏》)又同篇嘗禘郊社祭祀遭天子或后之喪條,五祀位郊社之下,鄭
注以小祀當之,謂「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知者,孔疏云:「嘗、禘者謂宗廟之祭
也,郊社謂天地之祭,舉天地宗廟,則五祀以上之祭皆在其中。」(《禮記正義》卷十九,
頁 375)
‧書目季刊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2011 年 6 月‧
‧76‧
鄭玄五祀說折中眾禮經矛盾,條分縷析,井然有當。尤其《禮記》諸篇原
本紛紜複雜記述,經鄭玄整理之後,禮制體系清晰明瞭,合理得當。其中周代
天子至士小祀七、五、三、二之說,尤其秩序井然,令人印象深刻。
鄭玄以其所理解之《周禮》文本邏輯闡發五祀體系之說;同時,《周禮》
五祀之說也因鄭玄解釋,廓清前儒、時賢說解之謬,使《周禮》內在邏輯更趨
明顯。下文試辯明此旨。
《周禮‧大宗伯》篇五祀之註解,除卻鄭玄之說,另有兩說。其一即徑以
《禮記》所云之五祀當之。持此說者甚夥,鄭玄之前有賈逵、馬融、許慎,其
後則有高誘、杜預、袁准等。雖鄭玄《周禮》注出仍不乏擁躉:
《左傳》昭二十九年杜注「后土,在家則祭中霤」;(中略)又《禮器》
孔疏云「按《異義》:竈神,今《禮》戴說引此燔柴盆瓶之事,古《周
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為竈神。許君謹按:同《周禮》。
鄭駮之云:『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為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
之,但就竈陘,一何陋也!』」據孔引《異義》,是《周禮》舊說有謂
此五祀即以五官食於〈月令〉之五祀者。《史記‧孝武本紀索隱》引《說
文》亦云「《周禮》以竈祠祝融」是也。《通典‧吉禮》引馬融說及袁
五 祀
五官之神 (中祀,或曰四方) 五祀(小祀)
殷代之制(等級混亂) 周代之制(等級秩然)
有地大夫(五祀)
無地大夫(三祀)
‧鄭玄禮學二題‧
‧77‧
准《正論》說、《左傳》昭二十九年孔疏引賈逵說、《呂氏春秋‧孟冬
季》高注及《風俗通義‧祀典》篇說竈神並同。
舊說本五祀之說以為即五官之神,以此解釋《周禮》。但同為天子制度,《周
禮》文字與〈祭法〉所云矛盾,是此必致非彼,不知〈祭法〉之說又當何解;
且即如鄭氏所云,〈大宗伯〉前後所云地祇中神,如此則群小祀之屬;而依舊
說則勢必「五官貴神下配戶竈」,如此皆於理難協,鄭玄駁許慎所云「一何陋
也」即為此發。
別於鄭玄說者,其二則為鄭玄《周禮》注中所引鄭司農之說:
鄭司農云:「(中略)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
鄭司農說亦不用舊說而別為之解;但仍於《周禮》文本邏輯扞格難通,賈疏云:
先鄭意,此五祀即《掌次》云祀五帝,一也,故云五色之帝。後鄭不從
者,案〈司服〉云,祀昊天與五帝皆用大裘,當在圜丘與四郊上,今退
在社稷之下,於王者宮中,失之遠矣。且五帝天神,當在上經陽祀之中,
退在陰祀之內,一何陋也!
賈說前文引〈司服〉職文,證明五帝與五祀祭祀之禮所行場所有別,理或當然;
然而以為五祀於王者宮中,實非鄭玄本旨─所謂「五官之神在四郊」,則非
宮中之祭明甚;至於下文本《周禮》之說以五帝之祀屬於天神,而陽祀之屬;
社稷、五祀等既退在其下,均地祇之類,不得相混。後者實是鄭司農《周禮》
五祀說無法圓融之痼疾所在。
又需附言者,清人皮錫瑞《鄭志疏證》以此條為鄭玄兼採今古文之謂。皮
氏謂「五祀,今古文有兩說」,故鄭玄不煩援引《左傳》、《周禮》之古文入
《禮記》今文。今案,皮氏之說似是而非:若云鄭玄兼採今古文,則鄭玄之
前已有賈逵、馬融、許慎諸人,已依《左傳》解《禮記》五祀─以五官之神
等同門、戶、竈、行、中霤等小祀之說─解釋《周禮》,則混同今、古固不
《周禮正義》卷三十三,頁 1324。 《鄭志疏證》卷六《禮記疏證》。臺灣世界書局景印本,1982 年再版。
‧書目季刊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2011 年 6 月‧
‧78‧
始於鄭玄;而鄭玄所以援《左傳》五官之神說注《周禮》者,實因舊說或以《禮
記》為釋,或如賈、馬、許諸人混同二說,皆於《周禮》文理難協,是不得不
另闢蹊徑,將二說分為不同體系,至此《周禮》文理通暢,其他文字亦一一落
實,大致無礙。皮氏謂鄭玄混同今古之說,頗疑皮相之論,實未能窺及鄭玄禮
學之根本所在。
進言之,鄭玄之解釋皆以《周禮》之文本邏輯─等級差別秩序井然為基
本前提。縱觀五祀之說,則鄭玄實本《周禮‧大宗伯》文字,而深信其中天神、
地祇、人鬼祭祀記載,是其明證。
鄭玄於其禮學體系解釋之中,兼顧禮文經典之不同記述,巨細無遺。就其
中牴牾矛盾或語焉不詳者,鄭玄或徑以時代或社會等級差別等調和諸說;或不
惜另倡新說,圓融其間。但其根本依據,則一本自《周禮》。若以本文五祀說
言,可知鄭玄五祀說是本〈大宗伯〉祭祀等級之差別,另立五官之神祭祀之說;
又以天子、諸侯、大夫、士群小祀等級井然之〈祭法〉為本,定其為周代之制,
條理其他禮文制度。由是可見,鄭玄目中周代之制─即如〈祭法〉與〈大宗
伯〉所云─皆等級制度井然不紊,秩序合理。如此解釋既能兼顧《周禮》、
《禮記》記述,同時將《禮記》文本之中前後矛盾牴牾消解殆盡,頗能圓融己
說。
前文略析鄭玄三禮注中五祀之說,並申述其優於諸家說法之合理性。為求
調和諸禮文記載牴牾矛盾或語焉不詳,協調眾說,圓融其間,鄭玄遂造說兩系、
異代五祀之說為之會通。然若細繹鄭玄之說,則或仍有未安。雖條理井然而矛
盾牴牾仍舊存之。試述之如下。
鄭玄五祀兩系之說立足於《周禮》文本井然等級秩序,著實調和文本差異,
但盡棄陳說,前無古人,獨創新說。於理雖通,其說則不無可疑,此其一;再
者,鄭玄注解〈王制〉篇文字,因其制度明文多別於《周禮》之說,鄭玄多以
「夏殷之制」釋之。前揭五祀說所出「天子諸侯宗廟之祭」一章,鄭玄注即云
「此蓋夏殷之祭名」,是明以此為夏殷禮制;而釋此五祀則以為周代之制。前
後牴牾,未克統一,不詳究竟。其三,〈祭法〉所云天子乃至庶人群小祀之制
度等級森然,鄭玄既以之為周代禮制一般,不知〈祭法〉為何竟以「無地大夫」
為基準,而不取〈王制〉中「有地大夫」為說?而〈王制〉中「有地大夫」五
‧鄭玄禮學二題‧
‧79‧
祀之制復又與〈祭法〉所記載諸侯之制五祀相等,誠如此,豈非又等級紊亂?
不知此處鄭玄又何以無說。以上種種均鄭玄五祀解釋體系中所未能圓滿者。
鄭玄五祀之說並非完璧無瑕。前揭諸多問題,實際亦因鄭玄禮學體系而致。
其他註解之中類此者亦不在少數。鄭玄意在會通三禮,實則亦將本非一體之三
部經典混同雜糅,莫知其原。然而,經典之中牴牾難通之處,在在多有,雖同
篇之中前後扞格亦不足稱奇,何況三部煌煌經典!故即便盡從鄭玄所為調和之
論亦難盡掩之。尤其鄭玄所深信之《周禮》,每每於其等級森然處顯其文本矛
盾,恐非如鄭玄所深信之不刊之論。僅舉本篇所論相關者獻疑如下。〈大宗伯〉
云「社稷、五祀」為地祇之首─「以血祭祭之」,鄭玄以為「陰祀自血起,
貴氣臭也」;但《春官‧司服》則云: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
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
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
據此,則「社稷、五祀」已在「四望山川」之下,不同〈大宗伯〉次第。二者
等級之別究竟如何,孰者為上,孰者為下,竟難分別。雖以鄭玄之善辯,而無
一言及之。清人孫詒讓博引諸人之說亦未能定讞,終以「疑事無質,宜從蓋闕
也」結句。此非他,《周禮》經文前後牴牾所以然者也。誠如此,或當另文詳
論《周禮》一書之究竟。
結 論
鄭玄之禮學解釋體系一以《周禮》文本解釋為基準,今以鄭玄藏冰、用冰
與五祀說二例驗之,可知此言不虛。或正因鄭玄禮學解釋有前揭之特徵,故其
禮學體系闡釋之合理,顯然優於前人,庶幾於經典之經義、禮文制度均能暢通
無礙。遂為後世學者所推崇,並及禮典實踐之奉用。三禮之學皆從鄭玄之說而
黜他說,實有其必然性與合理性所在。禮是鄭學良有以也。然亦正因此,研讀
《三禮》參考鄭注尚須留心於此,或乃不至因佞鄭而失其本旨。
余又思之。鄭玄遍注群經之際,固嘗持《周禮》文字而定他經諸說;然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