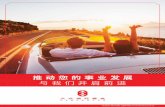1.论文题目:微信红包,消费者抢还是不抢?基于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 ...
-
Upload
khangminh22 -
Category
Documents
-
view
0 -
download
0
Transcript of 1.论文题目:微信红包,消费者抢还是不抢?基于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 ...
1
1.论文题目:微信红包,消费者抢还是不抢?基于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中介模型
2.作者简介:
1、李东进(1957,9-),男(朝鲜族),吉林延边人,南开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消费者行为学。E-mail:[email protected]。
2、刘建新(1979,1-),男(土家族),湖北恩施人,南开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系博士生,
研究方向:消费者行为学。E-mail:[email protected]
3.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产品虚位现象与消费者反应机制的研究
(2014.1-2017.12)”(71372099)和西南大学“中央高校青年基金项目:重庆市低碳经济发
展研究:基于消费者行为视角(2014.1-2016.12)”(SWU1009030)资助。
4.通讯作者
刘建新
通讯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南开大学西区公寓8A-3-403
通讯邮件:[email protected]
2
微信红包,消费者抢还是不抢?
基于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中介模型
摘 要:随着移动互联网络技术和移动金融支付方式的迅猛发展,2015 年“微信红包”活动
赢得了广泛的参与和巨大的成功。它的成功在于有效地唤醒了消费者[1]的参与动机且有效地
弱化了消费者的心理抗拒。根据目标-途径理论和信息加工理论,当面对不同类型的“微信红
包”信息(商业型 vs.人际型)时,消费者会同时考虑作为行为目的的参与动机与作为行为自
由的心理抗拒,并以不同的路径进行信息加工和调节聚焦,从而产生不同的参与意愿。通过
四个实验,我们发现:(1)参与动机和心理抗拒会分别独立部分中介“微信红包”信息对消
费者参与意愿的影响,并且均会受到自我建构的调节影响;(2)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也会共
同中介“微信红包”信息对消费者参与意愿的影响,而且共同中介过程也会受到自我建构的
调节影响。该研究结论不仅揭开和解释了消费者参与“微信红包”活动的心理作用机制,而
且也将对商业企业开展“微信红包”活动赢得客户资源或竞争优势的营销操作和消费者的理
性参与行为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微信红包;参与动机;心理抗拒;自我建构;参与意愿
0.引言
发红包是中华民族逢年过节的传统习俗,其主要意涵是长辈对晚辈的奖励和鼓励,或者
是晚辈对长辈的祝福或孝敬,在中国甚至形成了有名的“红包文化(Red-envelop Culture )”
(包昌善,2013)。但随着移动通讯网络技术和移动金融支付方式的迅猛发展,“微信红包
(Red-envelop within Wechat)”异军突起并大放异彩,赢得了广泛的参与和巨大的成功。据“微
信红包”技术开发公司中国腾讯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 年除夕当日“微信红包”收发总
量达 10.1 亿次,摇一摇互动量达到 110 亿次,红包峰值发送量为 8.1 亿次/分钟;2015 年整个
春节期间“微信红包”收发总量为 32.7 亿次,所发“微信红包”总金额超 100 亿元(腾讯公
司,2015)。“微信红包”的出现和盛行不仅改变了红包的派发对象和派发方式,也悄然改变
了红包的内在意涵和红包文化,甚至正在挑战和重构传统的人际网络、金融秩序和商业生态。
“微信红包”是随着微信技术发展应运而生的一款网络应用,是一种通过网络微信平台
向特定或不特定的人际群落发放的具有收发、查询和提现等功能的电子现钞或电子礼券。按
[1]“微信红包”的商业目的是锁定目标消费者的支付工具、培育消费者微信支付习惯和增强用户黏度,因此参与者本质上也是“微信红包”移动支付工具的消费者。同时,目前很多企业员工通过“微信红包”工具发展关系营销,建构消费者关系和培育消费者忠诚,因此“微信红包”的参与者可能是“微信红包”派发者的潜在消费者。据此,本文把“微信红包”参与者一律称之为“消费者”。
3
照派发主体和派发动机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商业型“微信红包”(Commercial Wechat
Envelop,CWE)和人际型“微信红包”(Interpersonal Wechat Envelop,IWE),前者派发的主
体主要是商业企业,派发对象具有不特定性,派发的动机和目的主要包括扩大企业或品牌声
誉、亲近潜在客户、促进产品或服务销售、增强消费者的微信支付意愿等,因此其派发时往
往负载商业企业品牌或产品等商业化信息,具有总金额较高、竞争比较激烈、抢中概率低、
形式礼券化等特点;而后者派发的主体主要是人际个体,派发对象具有特定性,派发的动机
和目的主要包括娱乐朋友、活化关系、增进友谊等,因此其派发时负载更多的是祝福或幽默
等社会化信息,具有总金额较低、竞争不太激烈、抢中概率高、形式电子现钞等特点。可见,
二者存在显著的区别。遗憾的是,由于“微信红包”属于新鲜事物(邵晓莹,2015),有关它
的学术关注和学术研究非常少,而从消费者的角度进一步关注不同类型“微信红包”对消费
者参与意愿影响的心理机制研究更为鲜见。因此,我们对“微信红包”参与者心理机制的研
究不仅能有效地弥补该现象学术关注或学术研究的严重不足,而且对指导“微信红包”的良
性发展和帮助消费者的理性参与有重要作用。
目标-途径理论认为,消费者在面对呈现的信息刺激时会同时思考行为的最终目的(行为
目的)与目的的实现途径(行为自由);而信息加工理论认为,这两个方面会以不同的路径进
行信息加工和调节聚焦。当面对不同类型的“微信红包”(CWEvs.IWE)信息时,消费者的
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会分别作为行为目的与行为自由进行不同路径的信息加工与调节聚焦,
从而导致不同的参与意愿。本文将利用基于信息加工理论的自我决定理论和心理抗拒理论探
索与检验不同“微信红包”(CWEvs.IWE)信息是否会造成消费者不同的参与意愿、参与动
机与心理抗拒是否会独立或共同中介“微信红包”(CWEvs.IWE)信息对消费者参与意愿的
影响以及独立中介或共同中介是否会受到消费者自我建构的调节影响等问题。研究结论将对
探寻与解构消费者参与“微信红包”活动的心理机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改善商业企
业“微信红包”活动的营销操作和提高消费者参与的理性水平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论文将
首先阐释理论基础和发展研究假设,然后进行实验操纵并解释实验结果,最后总结整个研究
结论与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1.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理论基础
1.1.1 自我决定理论
目前对于游戏参与行为最具解释力的理论是自我决定理论(Ryan,Rigby,and Przybylski,
2006),而自我决定理论的核心是动机理论(Ryan and Deci,2000)。参与动机(Participation
4
motivation)是指由内在或外在需要引起的,个体或群体通过参与某项活动来满足各种需要的
特殊心理状态和意愿(Deci,1971,1975)。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体或群体一般存在内部动机、
外部动机和内部化动机等三种主要动机(Deci and Ryan,1985),并连同无动机(Amotivation)
一起形成动机连续体(Motivation Continuum)(Ryan and Deci,2000)。其中,内部动机是指
参与某项活动本身带来的愉悦与满足感(Deci and Ryan,1987),是一种内在的满足而不是外
在可分离的结果(Ryan and Deci,2000),例如参与“微信红包”活动带来的愉悦感、成就感等;
外部动机是指由于参与某项活动而带来的额外回报(Deci and Ryan,1987),是一种外在可分
离的结果而不是内在的满足(Ryan and Deci,2000),例如参与“微信红包”活动带来的红包奖
励、任务完成等;而内部化动机是指由外部因素引起的逐渐转化为个体内在需要的调节过程
(Ryan,1985),它包括外在调节、内摄调节、认同调节和整合调节等四个过程,例如参与“微
信红包”活动带来的竞争性、胜利感等。Deci(1975,1981)和Rynn等人(1981,2000)均认为,
无论是内部动机、外部动机还是内部化动机,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自主、能力和关系等需要。
Przybylski、Rigby和Ryan(2010)进一步指出,玩家参与电子游戏仍然是受基于自主、能力
与关系等需要的内部动机、外部动机与内部化动机驱动。因此,“微信红包”本质上作为一种
在线游戏,参与动机是消费者参与的主要驱动力。
1.1.2 心理抗拒理论
心理抗拒(Psychological Reactance)是指“当一个人的自由被剥夺或被威胁剥夺时所表
现出的动机状态”(Brehm,1968;Brehm and Brehm, 1981)。它分为“特质抗拒(Trait Reactance)”
和“状态抗拒(State Reactance)”,前者是指个体内生的、稳定的人格特质,而后者是指在特
定的情境下被唤起的个体内在动机表现(Dowd et al.,1991;Silvia,2006),本文所指的心理
抗拒感属于后者。心理抗拒理论认为,心理抗拒感的形成包括自由、自由威胁、抗拒和重获
自由等四个核心要素,其中自由和自由威胁是抗拒发生的前因,包括态度抗拒和行为抗拒是
具体表现,而重获自由是最终目的(Clee & Wicklund,1980;Brehm & Brehm, 1981)。已有
研究发现,操控性的广告、不可得的产品、销售人员的推荐、政府规定等都常被消费者视为
潜在的自由限制(Clee & Wicklund,1980),消费者对此的回应包括直接做禁止做的事情
(Dillard & Shen,2005)等直接回应和间接地增强寻求受威胁的选择(Brehm, Stires, Sensenig &
Shaban, 1966; Hammock & Brehm, 1966)、贬低威胁的来源(Kohn & Barnes,1977; Schwarz, Frey
& Kumpf, 1980; Smith, 1977;Worchel, 1974)、否认威胁的存在(WoRchel & Andreoli,
1974;Worchel, Andreoli & Archer, 1976)或行使一个不同的自由以获得控制感或选择权
(Wicklund, 1974)等间接回应。同时,心理抗拒会给消费者带来消极认知(不利评价)和消
极情绪(生气),并进而会影响消费者的态度和行为(Silvia,2006;Dillard and Shen,2004)。
5
当然,消费者心理抗拒是否真正产生取决于他或她对限制其自由的动机或目的的感知与判断
(Brehm and Brehm, 1981),当限制其自由者期望消费者行动而消费者不行动或者期望消费者
不行动而消费者行动均是心理抗拒的具体表现,即所谓的“敌视态度”(Clee and
Wicklund,1980)。在“微信红包”活动中,由于派发动机或派发形式可能与消费者的价值观
相悖,可能会被消费者视为对其自由或自尊的侵犯,从而触发消费者心理抗拒。
1.2 研究假设
1.2.1“微信红包”信息与参与意愿
“微信红包”信息作为重要的外部刺激,其呈现会给消费者在认知、情绪、动机等方面
带来一系列的反应,并进而会影响参与者的态度、评价和行为(Arnold,1950;Lazarus,1968;
Bettman,1979)。Higgins(1997,2001)提出的调节聚焦理论(Regulatory Focus Theory)认为,
人们在享乐动机的基础上会产生趋利避害心理。各种信息一旦出现,人们就会根据信息内容、
呈现形式、追求目标等对信息进行识别和加工,如果能够产生进步、成就和抱负等积极结果
人们就会采取促进聚焦(Promotion Regulatory)的策略,追求积极结果的出现;如果可能产
生责任、义务和安全等消极结果人们机会采取预防聚焦(Prevention Regulatory)的策略,避
免消极结果出现(Higgins,2001)。而无论是促进聚焦还是预防聚焦,都会产生相应的情绪反
应(例如兴奋、期待、生气、失落、后悔等)(Higgins et al.,1997)、价值感知(Markman and
Brendl,2000)和预期结果的敏感反应(期待预期结果出现或害怕消极结果出现)(Brendl et
al.,1995)等。趋避目标成就理论(Approach-avoidance Achievement Goals Theory)和情绪认
知评价理论(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 of Emotion)亦持相同的认知逻辑。
按照这些理论的逻辑推理与判断,一旦出现“微信红包”信息,消费者就会对信息刺激
进行辨识与加工,并呈现与之相应的认知与情绪反应。但由于 CWE 与 IWE 在派发主体、派
发动机、呈现形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消费者的心理认知、情绪反应、聚焦倾向和行为选
择亦会存在很大的不同。当呈现 CWE 时,消费者首先联想到的是商业促销,实证研究已经
证实带有促销性质的商业信息会诱发消费者的自我防御动机(Self-defense),从而会降低信任
程度和参与意愿;同时,消费者会对抢中红包概率进行判断,CWE 较低的抢中概率容易让消
费者对其失去吸引力,因为有奖促销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只有较高的中奖概率才能使消费者
产生更高的兴趣和参与意愿(Gonzalez et al.,1999;Chen and Jia,2005)。此外,CWE 往往不直
接全部派发现钞,而以电子礼券或购物时抵扣现钞的形式派发红包,非现钞化与使用的局限
性使得消费者对 CWE 的感知吸引力与参与意愿不高(Campbell and Diamond,1990;Folk and
Wheat,1995;Chen and Shi,2011)。与此相反,IWE 更加契合游戏的“娱乐化”本质,关系的社
会化、人际的熟悉性、派发的现钞化、较高的中奖概率等都让消费者对 IWE 有更高的感知吸
6
引力,因此参与意愿也更高。据此,我们假设:
H1:呈现“微信红包”信息时,IWE 较之于 CWE 更能激发消费者的参与意愿。
1.2.2“微信红包”信息、参与动机与参与意愿
“微信红包”类似于抽奖、赌博、网络游戏等娱乐活动,信息一旦出现就会引起潜在消
费者的“选择性注意”,且会唤醒他们的认知和情绪,并最终诱发他们的参与动机(Gee,2003;
Ryan et al. 2006;Wang et al. 2008; Warren et al. 2008)。按照自我决定理论的观点,自主、能力
与关系是构成动机的三大核心要素,也是参与动机的主要驱动力(Deci and Rynn,1985 ;Rynn
and Deci,2000)。 已有研究发现,游戏会唤醒并有效满足参与者的自主、能力与关系需要(Ryan
et al.,2006 ; Przybyski,2009 ;Przybyski et al.,2009a ;Przybyski et al.,2009b ; Przybyski et
al.,2010)。 “微信红包”作为一种娱乐游戏,自然也能唤醒并有效满足消费者的自主、能力
和关系需要,增强消费者的满足感与幸福感(Przybyski et al.,2010),从而产生参与动机。
但不同类型的游戏唤醒与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与动机存在差异(Przybyski et al.,2010)。例
如 CWE 与 IWE 都能给消费者带来兴趣满足、愉悦体验、竞争取胜、金钱获取、人际建构等
心理满足与物质需求,从而诱发消费者的内部动机、外部动机或内部化动机,但唤醒与满足
的需要与动机会在动机强度、结构、方向等方面存在差异。IWE 更能唤醒与满足消费者的自
主需要和关系需要,更加契合“微信红包”娱乐化本质,常常会给消费者带来紧张、刺激、
惊喜、激动和应激等情绪体验(Wang et al., 2008),因此更容易诱发消费者的内部动机;而
CWE 更能唤醒与满足消费者自主需要和能力需要,其参与目标更多地是赢得竞争与物质报
酬,与之相伴随的是竞争胜利感与物质占有感(Przybyski et al.,2010),因此更容易诱发消费
者的外部动机与内部化动机。按照自我决定理论,内部动机较之于外部动机与内部化动机更
加本源与持久,对行为的内驱力与持续性更强,对行为的可诊断性与预测性也更强(Rynn and
Deci,2000)。观察也发现,相比较于 CWE 的关系非对称性、参与商业性、低抢中概率、高
竞争性、派发非现性和使用受限性等特征,具有关系对称性、参与社会性、高抢中概率、低
竞争性、派发现钞化与使用灵活性等特征的 IWE 更具有感知吸引力与内部动机。据此,我们
假设:
H2:呈现“微信红包”信息时,IWE 较之于 CWE 更能诱发消费者的参与动机。
参与意愿反映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参与某项活动(Triandis,1980),是能够有效预测人
们真实行为的前因变量(Conner and Armitage,1998),同时也是主要受参与动机决定的结果
变量(Sheeran,2002)。合理行为理论(Fishbein and Ajzen,1975;Fishbein,1980)、计划行为
理论(Ajzen, 1985, 1991)、态度—行为理论(Triandis,1980)等理论均意愿是决定行为的核
心要素或关键变量,并在消费与休闲(Warshaw and Davis, 1984)、身体锻炼(Norman and
7
Smith,1995;Sheeran and Orbell,2000)、减肥(Bagozzi and Warshaw,1990)、吸烟(Norman et
al.,1999)、学术活动与成就(Manstead and Eekelen,1998;Sheeran et al.,1999)、非法药品使用
(Conner et al,1998)、赌博(Conner et al.,1998)、竞选(Bassili,1995)、诸如献血亲社会行
为(Warshaw et al.,1986)等实证研究中得到有效支持;同时,自我决定理论(Deci and
Ryan,1985;Ryan and Deci,2000)、成就动机理论(McClelland,1953)、保护动机理论(Rogers,
1983)等动机理论也认为意愿和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动机,并且在学生学习(Ryan and
Holt,1984;Deci and Ryan,1985;Ryan and Lyan,1994)、身体锻炼(Jarvis,2006; Ryan,2006; Roberts
et al., 2007)、游戏活动(Garris et al,2003;Yee,2007; Hoffman and Nadelson,2010)等领域中也
获得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支持。基于此,可以认为在“微信红包”游戏中无论是CWE还是IWE
所诱发的参与动机均会促发消费者的参与意愿,并且参与动机越强,消费者的参与意愿、参
与承诺与参与韧性会越高(Fredricks et al.,2004;Hoffman and Naderson,2010)。据此,我们
假设:
H3:呈现“微信红包”信息时,消费者的参与动机会正向影响参与者的参与意愿。连同
H2 一起,我们认为参与动机在“微信红包”信息与“微信红包”参与意愿中起中介作用。
1.1.3“微信红包”信息、参与动机、参与意愿与自我建构
“微信红包”信息对消费者参与动机和参与意愿的影响可能会受到自我建构的调节。自
我建构是指“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人们在多大程度上看待自己与他人相
分离或者相联系”(Markus and Kitayama, 1991)。Markus 和 Kitayama(1991)研究发现,欧
美国家的个体更加强调自我独立与自主,更加注重自我利益和自我内心表达,并将其称之为
“独立型自我建构(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INDSC)”;中日等国家等个体更加强调自我
关联和人际和谐,更加注重人际关系和社会规范,相应地被称之为“依存型自我建构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INTDSC)”。两种不同类型的自我建构不仅在行为表现上不一
致,而且在在认知、情感和动机等方面也存在显著的区别(Markus and Kitayama,1991)。例
如,INDSC 呈现的是有界的、单一的、稳定的特征,更加注重内在的、自我的(能力、想法
和情绪)表达,其自尊的基础是有能力表达自我和自信等内在特质;而 INTDSC 呈现的是柔
性的、可变的特征,更加注重外在的、公开的(身份、角色和关系)的表达,其自尊的基础
是有能力调整、约束自己和维持与社会环境的和谐(Markus and Kitayama, 1991; Aaker and Lee,
2001;Polyorat and Alden, 2005; Ng and Houston, 2006; Fernández et al.,2005)。Nisbett 等人
(2001)认为,INDSC 与 INTDSC 之间的差异主要是思维模式造成的,INDSC 更倾向于分析
性思考,更加关注于目标本身及其分类,更擅长于使用形式逻辑等规则去理解行为,且更容
易被进取性信息说服;而 INTDSC 更倾向于全面性思考,更加关注整体背景与因果关系,更
8
擅长于使用辩证逻辑等法则理解行为,而更容易被防御性信息说服(Nisbett et al,2001;Lee et
al,2004)。双信息系统加工理论则从信息加工的角度阐述了两种不同类型自我建构信息加工
方式或路径的差异(Constantine,2001; Haberstroh et al,2002; Kim and Markman,2006;Kuhnen et
al., 2001; Kuhnen and Oyserman, 2002; Baaren et al., 2003),INDSC 做决策与判断时更加依赖
于情绪和附情境化线索的边缘路线,而 INTDSC 则更加依赖于认知和去情境化线索的中心路
线(Hong and Chang,2015)。正式因为思维模式与信息加工方式的差异,导致不同自我建构
倾向的消费者存在不同的调节聚焦与行为选择(Higgins, 2001; Arsena et al., 2010)。依循此
逻辑与判断,对于 INDSC 而言,CWE 较之于 IWE 更容易唤醒他的分析性思考与进取性行为,
情绪化与竞争性情境也更容易促发他的竞争性与侵略性(Przybyski et al.,2010),同时弱化其
自我控制,从而会产生更大的主要由外部动机与内部化动机占主导的参与动机与参与意愿;
而对于 INTDSC 而言,IWE 较之于 CWE 更容易唤醒他的全面性思考与防御性行为(防御被
群体孤立),认知化与娱乐化情境更容易促发他的关系性与参与性,同时弱化其自我控制,
从而会产生更大的以内部动机为主导的参与动机与参与意愿。据此,我们假设:
H4:自我建构会调节“微信红包”信息对消费者参与动机的影响,并进而调节消费者的
参与意愿。具体而言,在 INDSC 倾向下 CWE 更能激发消费者参与动机并进而影响参与意愿,
而在 INTDSC 情境下 IWE 更能激发消费者参与动机并进而影响参与意愿。
1.1.4“微信红包”信息、心理抗拒与参与意愿
心理抗拒理论认为,当个体的自主或自由被剥夺或被威胁剥夺时就会表现出心理抗拒
(Brehm and Brehm, 1981)。它不同于参与动机(Shen and Dillard,2005),参与动机更多的是
基于行为目的认知性动机状态,例如在“微信红包”活动中得到享乐娱乐、赢得竞争、获取
报酬等;而心理抗拒更多的是基于行为自由的综合性动机状态,例如在“微信红包”活动中
对与价值观相悖、自主操控受限、感知自由损失等。心理抗拒并不一定存在行为表现,但通
常会做相反于限制者的选择,以满足自己重申自由的心理需要(Brehm and Brehm, 1981),例
如 Brehm(1966)、Lessne(1987)与 Lessne et al(1988,1989)和 Fitzsimons 与 Lehmann(2004)
分别发现选择集中不可得的选项、限时或限量等营销措施、消费人员对不想要商品的推荐行
为都会导致心理抗拒,要么觉得更具吸引力而增强购买欲望,要么产生心理厌恶而拒绝购买。
“微信红包”信息也会让消费者产生心理抗拒。关系的对称性、推荐的厌恶感、抢中概
率的高低、金钱态度的差异、社会规范的约束、红包的使用限制等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剥夺或威胁剥夺消费者的参与自由。例如在 CWE 中,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厌恶推荐行为、
抢中概率过低和红包使用限制受限等都威胁到了消费者的参与自由,从而导致消费者心理抗
拒感更强;与此相反,在 IWE 中,尽管可能存在社会规范约束和金钱态度掩饰等限制参与自
9
由,但人际关系的平等性、没有商业推荐、抢中概率较高和红包使用限制较少等会松弛甚至
扩展消费者的参与自由,从而减弱消费者参与的心理抗拒感。据此,我们假设:
H5:呈现“微信红包”信息时,消费者对 CWE 较之于 IWE 会表现出更高的心理抗拒。
心理抗拒属于典型的负面心理,不仅会带来例如有偏差的信息加工、消极评价等不利认
知,而且会带来内部控制点(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Brehm and Brehm,1981)、侵略性(Hong
and Faedda,1996)、沮丧(Dowd and Wallbrown,1993)、生气(Hong and Giannakopoulos, 1993)
等相关的消极情绪(Dillard and Shen,2005)。心理抗拒信息加工模型(Quick,2005)认为,不
利认知一方面会导致消费者带有刻板进行信息加工,扭曲对目标的客观评价(Petty and
Cacioppo,1986);另一方面不利认知也会增加消费者的个人卷入与信息搜寻(Petty and
Cacioppo,1981;Petty et al.,1990),增加信息加工的深度,从而导致拒绝被说服的可能性更高
(Sherif and Sherif,1967)。同时,消极情绪也同不利认知一样,一方面会直接导致拒绝被说服
的行为反应,以修复与平衡自我情绪(Breham and Breham,2001;Quick,2005);另一方面消极
情绪更容易促发更加系统的、狭窄的、聚焦的分析性信息加工(Schwarz and Clore 1996),同
样导致拒绝被说服的可能性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心理抗拒感导致的不利认知与消极情绪
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相互交织的(Dillard and Shen,2005),因此会产生叠加或叠减效应。基
于此推断,无论是 CWE 还是 IWE 诱发的心理抗拒感,都会降低消费者的参与意愿。据此,
我们假设:
H6:呈现“微信红包”信息时,参与者的心理抗拒会负向影响参与者的参与意愿。连同
H5,我们认为心理抗拒在“微信红包”信息与“微信红包”参与意愿中起中介作用。
1.1.5“微信红包”信息、心理抗拒、参与意愿与自我建构
自我建构不仅会调节作为行为目的的参与动机,而且也会调节作为行为自由的心理抗拒。
已有大量的研究发现,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INDSC)相较于集体主义文化(INTDSC)背景
下的个体更关注自己的自由与自主,因此当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INDSC)感知到个
体自由被剥夺或被威胁剥夺时表现出更高的心理抗拒,而群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
(INTDSC)感知群体自由被剥夺或被威胁剥夺时表现出更高的心理抗拒(Hofstede,1980;
Kitayama et al.,2004; Hoshino-Browne et al.,2005 ;Johnson and Buboltz,2000 ;Jonas,et al.,2009)。
与此同时,研究也发现,自我建构对个体的影响不仅仅仅存在于文化差异上,而且也存在个
体差异和情境差异上,在 INDSC 个体或情境下,当对高度重视自己的自主与自由的个体感知
到个体而非群体自由被剥夺或被威胁剥夺时会表现出更高的心理抗拒,而在 INTDSC 个体或
情境下,对高度重视人际关系与社会规范的个体感知到群体而非个体自由被剥夺或被威胁剥
夺时会表现出更高的心理抗拒(Jonas et al.,2009)。 因此,在“微信红包”活动中,对于 INDSC
10
而言,CWE 较之于 IWE 更加迎合消费者的自由追逐与物质追求,同时有效地弱化了人际关
系与社会规范的约束,于是会表现出更低的心理抗拒;而对于 INTDSC 而言,IWE 较之于
CWE 更加契合消费者人际关系与社会规范的追求与遵从,同时也有效地弱化了自主表达与物
质追求的影响,于是也会表现出更低的心理抗拒。据此,我们假设:
H7:自我建构会调节“微信红包”信息对消费者心理抗拒的影响,并进而会调节消费者
的参与意愿。即在 INDSC 倾向下 CWE 会唤醒更少的心理抗拒并进而影响参与意愿,而在
INTDSC 情境 IWE 会唤醒更少的心理抗拒并进而影响参与意愿。
1.3 概念模型
通过假设 H1、H2、H3、H4、H5、H6 和 H7,我们提出如图 1 所示的概念框架模型,并将
通过四个实验检验七个假设与整个概念框架研究模型。
2.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果
2.1 实验 1:参与动机的独立中介效应和自我建构的调节作用
2.1.1 预实验
预实验的主要目的是检测 CWE 与 IWE 之间的区别。采用的检测方法是情境模拟的实验
方法。实验设计为首先给所有被试分别呈现两个“微信红包”信息,让其判断是 CWE 还是
IWE 的程度(1=CWE,7=IWE)?“微信红包”信息一是“我公司(大型国有企业,主要提
供有形的产品)为了回馈社会公众和新老客户,特在除夕夜晚上 22:00 派发 1 亿元的红包,
每份红包的最大金额为 200.00 元,最小金额为 1.00 元,红包形式为一半是现金、一半是优
惠券。热忱欢迎大家摇一摇,共度新春佳节”;“微信红包”信息二是“我是你的朋友小李,
为感谢大家过去一年的关心和支持,今晚(除夕夜晚上 22:00)将向大家派发 1000.00 元的
红包,每份红包的最大金额为 200.00 元,最小金额为 1.00 元,红包形式全部是现金。真诚
欢迎大家摇一摇,共度新春佳节”。然后,让被试判断和选择两个“微信红包”信息究竟属于
哪类“微信红包”信息?最后,我们将根据被试判断和选择的评定进行统计和分析,确定“微
信红包”信息类型。我们在北方某高校招募了 35 名被试,男性被试为 15 名,女性被试为 20
图 1 整个概念框架模型
H6
H5
H7
H4 H3
H2 H1
参与动机
心理抗拒
“微信红包”
参与意愿
自我建构
“微信红包”信息
CWEvs.IWE
11
名,其中有 5名被试根本不熟悉“微信红包”予以剔除,因此预实验有效被试为 30 名,平均
年龄为 20.70 岁(SD=0.75)。
T 检验的结果显示,30 名被试认为信息一属于 CWE 的均值 M 信息一=1.57,信息二属于 IWE
的均值为 M 信息二=6.37,二者之间差异显著(t(29)=-11.03,p<0.05)。而且二者均远离均值
4(M 信息一=1.57,t(29)=-10.66,p<0.05;M 信息二=6.37,t(29)=9.78,p<0.05),分别趋近
于 1(CWE)和 7(IWE)。据此,我们将“微信红包”信息一判定为 CWE,“微信红包”信
息二判定为 IWE,并将其用于所有主实验中。
2.1.2 实验设计
实验 1 的主要目的是检测“微信红包”信息通过参与动机的中介效应影响消费者的参与
意愿,并受自我建构的调节作用,即主要检测假设 H1、H2、H3 和 H4。实验设计是 2(“微信
红包”信息:CWEvs.IWE)×2(自我建构:INDSCvs.INTDSC)组间因子设计。实验设计为
将招募的被试随机分为大致同质的四组,首先让他们阅读相关“微信红包”信息,然后填写
单维参与意愿量表、参与动机量表和自我建构量表,最后填写多维参与意愿量表并完善个人
相关的统计信息。其中,单维参与意愿量表题项为“你愿意参与抢该‘微信红包’吗?”,量
表尺度为 Likert7 点制量表;参与动机量表分别改编自 Demetrovics 等人(2011)和 Lafrenière
等人(2012)等编制的游戏动机量表,分别包括有趣性(例如“我参加‘微信红包’游戏是
因为它有趣。”)、愉悦性(例如“我参与‘微信红包’游戏是为了娱乐。”)、竞争性(例如“我
参加‘微信红包’游戏是因为我喜欢竞争。”)、物质性(例如“我参加‘微信红包’游戏是因
为它能给我带来收益。”)和人际性(例如“我参加‘微信红包’游戏是因为它可以增进感情。”)
等条目,量表尺度为 Likert7 点制量表;自我建构量表改编自 Singelies(1994)和 Singelies et
al.(1995)等开发的“自我建构测量量表”,并且进行了有效的情境化,情境启动方法为设想
“你【你的团队】正在打一场网球竞标赛并且打到了总决赛。……。无论输赢,我都将为我
自己【我的团队】证明我的价值。”该方法在 Ma、Yang 和 Mourali(2014)等论文中得到了
有效的应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多维参与意愿量表改编自 Agarwal 和 Karahanna(2000)
的“游戏意愿量表”。(见附录 B)我们在北方某高校招募了 107 名大学生被试,其中男性被
试为 51 名,女性被试为 56 名。所招被试被随机地分为四个实验组,分别为 A 组(CWE,
INDSC)、B 组(CWE,INTDSC)、C 组(IWE,INDSC)和 D 组(IWE,INTDSC)。各组
被试独立且同时进行实验。
实验操纵的具体过程为先给 A 组和 B 组呈现预实验中的 CWE、C 组和 D 组呈现 IWE,
接着被试填写各自的单维参与意愿量表,然后分别启动 A 组和 C 组的 INDSC、B 组和 D 组
的 INTDSC,最后被试填写参与动机测量量表、自我建构测量量表和多维参与意愿量表,以
12
及个人的相关统计信息。经过实验操纵后,我们将对问卷进行仔细检查和复核。经过检查和
评定,发现 A 组、B 组、C 组和 D 组等四组有效问卷分别为 23 份、24 份、21 份和 24 份,
共计 92 份,所剔除的被试或问卷皆因不熟悉“微信红包”、问卷缺失值太多或回答有效性不
高的问卷(例如所有评定均是“1”、“7”等)。有效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20.64 岁(SD=0.69)。
2.1.3 实验结果
“微信红包”信息对消费者参与“微信红包”意愿的影响结果分析如表 1 所示。进行独
立样本 T 检验分析,结果显示,CWE 和 IWE 对消费者参与意愿(单维)的影响差异显著
(MCWE=5.13;MIWE=6.36;t(90)=-4.87,p<0.05),消费者参与 IWE 较之于 CWE 有更高的
参与意愿。假设 1 得到有效的支持。
表 1 “微信红包”信息对消费者参与意愿(单维)的影响
95%CI N M SD T-test p
LLCI ULCI
CWE 47 5.13 1.28
IWE 45 6.36 1.31 -4.87 0.00 -1.7288 -0.7270
自我建构对“微信红包”信息对消费者参与动机的调节效应分析如表 2 所示。首先分析
自我建构的启动效果。INDSC 和 INTDSC 的信度系数 Cronbach’s α 分别为 0.85 和 0.79,均大
于要求的 0.70。在启动 INDSC 情境下(A 组和 C 组)INDSC 与 INTDSC 差异显著(MINDSC=5.93,
MINTDSC=3.34,t(43)=11.84,p<0.05),在启动 INTDSC 情境下(B 组和 D 组)INTDSC 与 INDSC
差异显著(MINTDSC=5.69,MINDSC=3.65,t(47)=10.71,p<0.05),表明自我建构操纵是成功的。
然后分析“微信红包”信息对消费者参与动机的影响。数据结果显示,IWE 比 CWE 更能诱
发消费者的参与动机(MIWE=5.16,MCWE=4.47,t(90)=-2.24,p<0.05),假设 H2 因此得到有效
支持。最后分析自我建构的调节效应。双因素 ANOVA 结果显示,自我建构与“微信红包”
信息对参与动机的交互效应显著(F(1,88)=45.47,p<0.05),同时“微信红包”信息的主
效应(F(1,88)=5.67,p<0.05)和自我建构的主效应均显著(F(1,88)=6.74,p<0.05),
这表明在激活 INDSC 情境下,消费者参与 CWE 较之于 IWE 有更强的参与动机(MCWE=5.00,
MIWE=3.90);而在激活 INTDSC 情境下,消费者参与 IWE 较之于 CWE 有更强的参与动机
(MIWE=6.25,MCWE=3.96)。(图 2)进一步对“微信红包”信息与自我建构影响消费者参与
意愿进行双因素 ANOVA 分析,结果显示交互效应也显著(F(1,88)=43.80,p<0.05)。因
此,假设 H4 得到有效支持。
表 2 自我建构对“微信红包”信息影响消费者参与动机的调节作用
因素 ⅢSS DF MS F p
“微信红包”信息 8.21 1,88 8.21 5.67 0.02
13
自我建构 9.74 1,88 9.74 6.74 0.01
微信红包信息×自我建构 65.76 1,88 65.76 45.47 0.00
图2 自我建构的调节作用
5.00
3.903.96
6.25
3.00
4.00
5.00
6.00
7.00
CWE IWE“微信红包”信息
参与
动机
INDSC INTDSC
图3 自我建构的调节作用
2.96
4.003.58
1.67
1.00
2.00
3.00
4.00
5.00
CWE IWE“微信红包”信息
心理
抗拒
INDSC INTDSC
参与动机对“微信红包”信息影响消费者参与意愿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参
与动机和参与意愿(多维)的信度分析结果 Cronbach’s α 分别显示为 0.91 和 0.86,均大于 0.70,
证明测量量表是可信的(Churchill,1979)。对消费者参与动机对其参与意愿(多维)的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参与动机对参与意愿(多维)的正向影响显著(F(1,90)=414.30,p<0.001),
标准化的回归系数为 β=0.91(t(90)=20.35,p<0.001)。假设 H3 前半部分得到有效支持。
将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后,按照 Zhao 等(2010)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程序,参照 Preacher
(2008)和 Hayes(2013)提出的 Bootstrap 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选择模型 7,样本量选
择为 5000,取样方法为选择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在 95%置信区间下,在 INDSC 倾
向下,中介效应的结果不包含 0(LLCI=-0.5644,ULCI=-0.1115),且中介效应大小为-0.32,
说明参与动机的中介效应显著;在 INTDSC倾向下,中介效应的结果也不包含 0(LLCI=0.4484,
ULCI=0.9219),且中介效应大小为 0.67,说明参与动机的中介效应也显著。在控制中介变量
参与动机后,“微信红包”信息对消费者参与意愿(多维)的影响也显著(LLCI=0.0167,
ULCI=0.1939,不包含 0),直接效应量为 0.11,表明参与动机在“微信红包”信息对消费者
参与意愿(多维)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假设 H3 后半部分得到有效支持,连
同得到已经得到支持的前半部分,整个假设 H3 得到完整的有效支持。
表 3 参与动机对“微信红包”信息影响消费者参与意愿的中介效应
95%CI 效应类型 自我建构 Effect SE t p
LLCI ULCI
直接效应 − 0.11 0.04 2.36 0.02 0.0167 0.1939
INDSC -0.32 0.11* − 不包含 0 -0.5644* -0.1115* 中介效应
INTDSC 0.67 0.12* − 不包含 0 0.4484* 0.9219*
注:1.“微信红包”(分别编码为 1 和 0)、自我建构(分别编码为 1 和 0)、参与动机和参与意愿(多维)均为标准化数据;
2.*为“Boot”。
2.1.4 实验结论
14
通过实验 1 检验了假设 H1、H2、H3 和 H4,结果表明,“微信红包”信息(IWEvs.CWE)
对消费者的参与意愿存在差异,IWE 较之于 CWE 更能促进消费者的参与意愿;参与动机对
“微信红包”信息影响消费者参与意愿的中介作用显著,同时在控制中介变量后“微信红包”
信息对消费者参与意愿的影响仍然显著;自我建构对“微信红包”信息通过参与动机的中介
效应并最终影响消费者参与意愿的调节作用显著,在 INDSC 情境下 CWE 较之于 IWE 更能促
进消费者的参与动机并进而最终影响消费者的参与意愿,在 INTDSC 情境下 IWE 较之于 CWE
更能促进消费者的参与动机并进而最终影响消费者的参与意愿。因此,假设 H1、H2、H3 和
H4 全部得到有效支持。但实验结果也发现,参与动机对“微信红包”信息影响消费者参与意
愿的中介效应仅仅是部分中介效应,而非完全中介效应。为此,我们将通过实验 2 检验另一
个中介变量——心理抗拒的中介效应。
2.2 实验 2:心理抗拒的独立中介效应与自我建构的调节作用
2.2.1 实验设计
实验 2 的主要目的是检测“微信红包”信息通过心理抗拒的中介效应影响消费者的参与
意愿,以及自我建构的调节作用,即主要检测假设 H5、H6 和 H7。实验设计采用的是 2(“微
信红包”信息:CWEvs.IWE)×2(自我建构:INDSCvs.INTDSC)组间因素设计。实验内容
和实验过程跟实验 1 一样,主要区别在于实验 2 用“心理抗拒测量量表”替代了“参与动机
测量量表”。其中心理抗拒量表改编自 Hong(1992)、Hong 和 Faedda(1996)的研究;自我
建构量表和激活采用同实验 1 的量表和方法;多维参与意愿量表也采用同实验 1 的量表。(见
附录 C)我们在北方某高校招募了 115 名大学生被试,其中男性被试为 53 名,女性被试为 62
名。所招被试被随机地分为四个实验组,分别为 A 组(CWE,INDSC)、B 组(CWE,INTDSC)、
C 组(IWE,INDSC)和 D 组(IWE,INTDSC)。各组被试独立且同时进行实验。
实验操纵的具体过程为先给 A 组和 B 组呈现预实验中的 CWE、C 组和 D 组呈现 IWE,
接着被试填写各自的单维度参与意愿量表,然后分别启动 A 组和 C 组的 INDSC、B 组和 D
组的 INTDSC,最后被试填写心理抗拒测量量表、自我建构测量量表和多维参与意愿测量量
表,以及个人的相关统计信息。经过实验操纵后,我们将对问卷进行仔细检查和复核。经过
检查和评定,发现 A 组、B 组、C 组和 D 组等四组有效问卷分别为 24 份、26 份、23 份和 24
份,共计 97份,所剔除被试和问卷的理由同实验 1。有效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20.68岁(SD=0.64)。
2.2.2 实验结果
“微信红包”信息对消费者参与“微信红包”意愿的影响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同样将
A 组和 B 组合并也称之为 CWE,将 C 组和 D 组合并称之为 IWE。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
结果显示,CWE 和 IWE 对消费者参与意愿(单维)的影响差异显著(MCWE=5.00,MIWE=5.49;
15
t(95)=-2.13,p<0.05),表明消费者参与 IWE 较之于 CWE 有更高的参与意愿。假设 H1同样
得到有效的支持。
表 4 “微信红包”信息对消费者参与意愿(单维)的影响
95%CI 因素 N M SD t p
LLCI ULCI
CWE 50 5.00 1.14
IWE 47 5.49 1.12 -2.13 0.04 -0.9460 -0.0328
自我建构对“微信红包”信息对消费者心理抗拒的调节作用分析如表 5 所示。首先同样
分析自我建构的启动效果。INDSC 和 INTDSC 的信度系数 Cronbach’s α 分别为 0.89 和 0.82,
均大于要求的 0.70。在启动 INDSC 情境下(A 组和 C 组)INDSC 与 INTDSC 差异显著
(MINDSC=5.94,MINTDSC=3.17,t(46)=16.55,p<0.05),在启动 INTDSC 情境下(B 组和 D 组)
INTDSC 与 INDSC 差异显著(MINTDSC=5.42,MINDSC=3.30,t(49)=10.23,p<0.05),表明自我
建构操纵是成功的。然后分析“微信红包”信息对消费者心理抗拒的影响。数据结果显示,
CWE 比 IWE 更容易诱发消费者的心理抗拒(MCWE=3.28,MIWE=2.81,t(95)=1.61,p>0.05),
因此假设 H5 并未得到有效支持。最后分析自我建构的调节作用。双因素 ANOVA 结果显示,
自我建构与“微信红包”信息对心理抗拒的交互效应显著(F(1,93)=38.12,p<0.05),同
时“微信红包”信息的主效应边缘显著(F(1,93)=3.30,p=0.07)和自我建构的主效应显著
(F(1,93)=12.86,p<0.05)。这表明在激活 INDSC 情境下,消费者参与 IWE 之于 CWE 有
更高的心理抗拒(MIWE=4.00,MCWE=2.96);而在激活 INTDSC 情境下,消费者参与 CWE 较
之于 IWE 有更高的心理抗拒(MCWE=3.58,MIWE=1.67)。(图 3)进一步对“微信红包”信息
与自我建构影响消费者参与意愿进行双因素 ANOVA 分析,结果显示交互效应显著(F(1,
93)=43.82,p<0.05)。因此,假设 H7 得到有效支持。
表 5 自我建构对“微信红包”信息影响消费者心理抗拒的调节作用
因素 ⅢSS DF MS F p
“微信红包”信息 4.57 1,93 4.57 3.30 0.07
自我建构 17.79 1,93 17.79 12.86 0.00
微信红包信息×自我建构 52.72 1,93 52.72 38.12 0.00
心理抗拒对“微信红包”信息影响消费者参与意愿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心
理抗拒和参与意愿(多维)的信度分析结果 Cronbach’s α 分别显示为 0.89 和 0.87,均大于 0.70,
证明测量量表是可信的(Churchill,1979)。对消费者心理抗拒对其参与意愿(多维)的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心理抗拒对参与意愿(多维)的负向影响显著(F(1,95)=141.56,p<0.001),
标准化的回归系数为 β=-0.77(t(95)=-11.90,p<0.001)。假设 H6前半部分得到有效支持。
将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后,按照 Zhao 等(2010)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程序,参照 Preacher
16
(2008)和 Hayes(2013)提出的 Bootstrap 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选择模型 7,样本量选
择为 5000,取样方法为选择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在 95%置信区间下,在 INDSC 倾
向下,中介效应的结果不包含 0(LLCI=-0.4793,ULCI=-0.0920),且中介效应大小为-0.27,
说明心理抗拒的中介效应显著;在 INTDSC倾向下,中介效应的结果也不包含 0(LLCI=0.3052,
ULCI=0.7294),且中介效应大小为 0.50,说明心理抗拒的中介效应也显著。在控制中介变量
心理抗拒后,“微信红包”信息对消费者参与意愿(多维)的影响仍然显著(LLCI=0.0003,
ULCI=0.2580,不包含 0),效应大小为 0.13,表明心理抗拒在“微信红包”信息对消费者参
与意愿(多维)的影响中也只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假设 H6后半部分得到有效支持,
连同得到已经得到支持的前半部分,整个假设 H6 得到完整的有效支持。
表 6 心理抗拒对“微信红包”信息影响消费者参与意愿的中介效应
95%CI 效应类型 自我建构 effect SE t P
LLCI ULCI
直接效应 − 0.13 0.06 1.99 0.05 0.0003 0.2580
INDSC -0.27 0.10* − 不包含 0 -0.4793* -0.0920* 中介效应
INTDSC 0.50 0.11* − 不包含 0 0.3052* 0.7294*
注:1.“微信红包” 信息(分别编码为 1 和 0)、自我建构(分别编码为 1 和 0)、心理抗拒和参与意愿(多维)均为标准化
数据;
2.*为“Boot”。
2.2.3 实验结论
通过实验 2 我们检测了假设 H5、H6 和 H7,结果表明,“微信红包”信息(CWEvs.IWE)对
消费者的参与意愿存在差异得到再次验证,IWE 较之于 CWE 更能促进消费者的参与意愿;
心理抗拒对“微信红包”信息影响消费者参与意愿的中介作用显著,但仅为部分中介作用,
在控制中介变量后“微信红包”信息对消费者参与意愿的影响仍然显著;自我建构对“微信
红包”信息通过心理抗拒的中介作用并最终影响消费者参与意愿的调节作用显著,在 INDSC
情境下 IWE 较之于 CWE 更能唤起消费者的心理抗拒并进而最终影响消费者的参与意愿,在
INTDSC 情境下 CWE 较之于 IWE 更能唤起消费者的心理抗拒并进而最终影响消费者的参与
意愿。但假设 H5 并未得到有效支持,即 IWE 与 CWE 对消费者的参与意愿并没有显著差异,
原因可能在于 INDSC 的外部动机减弱了心理抗拒。与此同时,实验 1 和实验 2 检验结果均显
示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均只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那么它们在一起会发挥怎样的中介作用
呢?为此,我们通过实验 3 将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同时纳入到模型中,进行共同中介效应检
验。
2.3 实验 3: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的共同中介效应
2.3.1 实验设计
17
实验 3 的主要目的是检测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在“微信红包”信息对消费者参与意愿的
影响中的共同中介效应。实验设计是单因素组间设计,即将被试随机分配为大致同质的两组,
其中一组被呈现 CWE,另一组被试呈现 IWE;然后两组被试均填写参与动机测量量表、心理
抗拒测量量表和多维参与意愿测量量表,最后完善个人相关统计信息。参与动机测量量表、
心理抗拒测量量表和多维参与意愿测量量表均与实验 1 和试验 2 一样。我们在北方某高校招
募了 70 名被试,其中男性被试 30 名,女性被试 40 名。实验完成后,经过操作检查和仔细评
定,CWE 和 IWE 等两组被试的有效问卷分别为 28 和 35 份,共计 63 份,所剔除被试和问卷
的理由同实验 1。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20.82 岁(SD=0.58)。
2.3.2 实验结果
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对“微信红包”信息(CWEvs.IWE)对消费者参与意愿的共同中介
效应如表 7 所示。参与动机、心理抗拒和多维参与意愿的信度分析结果 Cronbach’s α 分别显
示为 0.92、0.87 和 0.89,均大于 0.70,证明测量量表是可信的(Churchill,1979)。所有变量标
准化后按照 Zhao 等(2010)提出的中介分析程序,参照 Preacher 和 Hayes(2008)提出的多
个并列的中介变量检验方法,进行 Bootsrap 中介变量检验,选择模型 4,样本选择量为 5000,
设置置信区间为 95%,Bootstrap 取样方法为选择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数据结果表明
两个中介变量共同发挥的中介效应显著(LLCI=0.1084,ULCI=0.5416,不包含 0),作用大小
为 0.30;参与动机和心理抗拒各自均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大小分别为 0.25
(LLCI=0.0971,ULCI=0.4627,不包含 0)和 0.05(LLCI=0.0045,ULCI=0.1320,不包含 0);
在控制共同中介效应后,“微信红包”信息对消费者参与意愿的影响不再显著(LLCI=-0.0446,
ULCI=0.1507,包含 0)。(图 4)
表 7 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的共同中介效应
95%CI 效应类型 中介变量 Effect SE t p
LLCI ULCI
直接效应 − 0.05 0.05 1.09 0.28 -0.0446 0.1507
参与动机 0.25 0.09* − 不包含 0 0.0971* 0.4627* 中介效应
心理抗拒 0.05 0.03* − 不包含 0 0.0045* 0.1320*
注:1.“微信红包”信息(分别编码为 1 和 0)、参与动机、心理抗拒和参与意愿(多维)均为标准化数据;
2.*为“Boot”。
18
2.3.3 实验结论
通过实验 3 我们检测了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对“微信红包”信息影响消费者参与意愿的
共同中介过程。检验结果显示,不仅它们各自的独立中介效应显著,而且它们的共同中介效
应也显著;同时在它们的共同中介效应下,“微信红包”信息对消费者参与意愿的直接效应已
经不再显著。但该共同中介过程是否也会受到自我建构的调节影响呢?为此,我们将通过实
验 4 检验自我建构对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共同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2.4 实验 4:共同中介效应的自我建构调节作用
2.4.1 实验设计
实验 4 的主要目的是检测自我建构对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对“微信红包”信息影响消费
者参与意愿的共同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实验设计采用的是 2(“微信红包”信息:CWEvs.IWE)
×2(自我建构:INDSCvs.INTDSC)组间因素设计。模拟情境跟预实验一样,实验设计为将
招募的被试随机地分配给大致同质的四组,然后给四组被试呈现不同的“微信红包”信息和
启动不同的自我建构情境,最后被试填写“参与动机测量量表”、“心理抗拒测量量表”、“自
我建构测量量表”和“参与意愿测量量表”,所用量表都与前面的实验一样。我们在北方某高
校招募了 125 名被试,其中男性被试为 52 名,女性被试为 73 名。所招被试被随机地分为四
个实验组,分别为 A 组(CWE,INDSC)、B 组(CWE,INTDSC)、C 组(IWE,INDSC)
和 D 组(IWE,INTDSC)。各组被试独立且同时进行实验。
实验过程为首先向 A 组和 B 组呈现 CWE、C 组和 D 组呈现 IWE,然后运用实验 1 中的
方法启动 A 组和 C 组中的独立型自我情境、启动 B 组和 D 组中的 INTDSC 情境,然后所有
被试填写“参与动机测量量表”、“心理抗拒测量量表”、“自我建构测量量表”和“参与意愿
测量量表”,以及完善个人相关统计信息。实验完成后,经过检查和评定,发现 A 组、B 组、
C 组和 D 组等四组有效问卷分别为 22 份、27 份、28 份和 29 份,共计 106 份,所剔除被试和
问卷的理由同实验 1。有效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20.83 岁(SD=0.84)。
2.4.2 实验结果
0.33*
0.05(ns)
-0.17*
0.77*
-0.27*
图 4 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的共同中介效应
注:*代表 P<0.05
“微信红包”
信息
“微信红包”
参与意愿
参与动机
心理抗拒
19
自我建构对“微信红包”信息(CWEvs.IWE)通过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共同中介效应影
响消费者参与意愿的调节作用如表 8 所示。参与动机和心理抗拒的信度系数 Cronbach’s α 分
别为 0.87 和 0.85,均大于 0.70,证明测量量表是可信的(Churchill,1979)。首先同样分析自
我建构的启动效果。T 检验数据结果显示,INDSC 和 INTDSC 的信度系数 Cronbach’s α 分别
为 0.86 和 0.83,均大于要求的 0.70。在启动 INDSC 情境下(A 组和 C 组)INDSC 与 INTDSC
差异显著(MINDSC=6.04,MINTDSC=3.20,t(49)=20.57,p<0.05),在启动 INTDSC 情境下(B
组和 D 组)INTDSC 与 INDSC 差异显著(MINTDSC=5.13,MINDSC=3.39,t(55)=12.74,p<0.05),
表明自我建构操纵是成功的。然后把所有变量标准化并按照 Zhao 等(2010)提出的中介分析
程序,参照 Preacher 等(2007)和 Hayes(2013)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分析模型进行 Bootsrap
中介变量检验,模型选择 7,样本选择量为 5000,设置置信区间为 95%,Bootstrap 取样方法
为选择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数据结果显示,在 INDSC 情境下,“微信红包”信息
(CWEvs.IWE)通过参与动机的中介作用进而影响消费者参与意愿的间接效应显著(LLCI=
-0.3195,ULCI=-0.0218,不包含 0),作用大小为-0.15;而“微信红包”信息(CWEvs.IWE)
通过心理抗拒的中介作用进而影响消费者参与意愿的间接效应不显著(LLCI=-0.1158,
ULCI=0.0037,包含 0)。在 INTDSC 情境下,“微信红包”信息(CWEvs.IWE)通过参与动
机的中介作用进而影响消费者参与意愿的间接效应显著(LLCI=0.2147,ULCI=0.6122,不包
含 0),作用大小为 0.38;同时,“微信红包”信息(CWEvs.IWE)通过心理抗拒的中介作用
进而影响消费者参与意愿的间接效应也显著(LLCI=0.0153,ULCI=0.2927,不包含 0),作用
大小为 0.13。此外,在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的共同中介作用下,“微信红包”信息对消费者参
与意愿的主效应已经不显著(LLCI=-0.0551,ULCI=0.1668,包含 0)。由此可见,在共同中
介模型中,心理抗拒的中介作用会受到自我建构的调节作用。
表 8 自我建构对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共同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95%CI 效应类型 自我建构 Effect SE t p
LLCI ULCI
直接效应 − 0.06 0.06 1.00 0.32 -0.0551 0.1668
INDSC -0.15 0.08* − 不包含 0 -0.3195* -0.0218* 中介效应
(参与动机) INTDSC 0.38 0.10* − 不包含 0 0.2147* 0.6122*
INDSC -0.04 0.03* − 包含 0 -0.1158* 0.0037* 中介效应
(心理抗拒) INTDSC 0.13 0.07* − 不包含 0 0.0153* 0.2927*
注:1.“微信红包”信息(分别编码为 1 和 0)、自我建构(分别编码为 1 和 0)、参与动机、心理抗拒和参与意愿(多维)
均为标准化数据;
2.*为“Boot”。
2.4.3 实验结论
通过实验 4 我们检测了自我建构对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共同中介“微信红包”信息影响
20
消费者参与意愿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在 INDSC 还是 INTDSC 情境下,参与动
机都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但心理抗拒只在 INTDSC 情境下起着中介作用,而在 INDSC 情境
下不起中介作用。可见,自我建构会对心理抗拒起着调节作用。原因可能在于消费者的 INDSC
倾向被启动后,会增强消费者的情境融入和进取倾向(Aaker & Lee,2001; Hong & Chang,
2015),从而减弱了自我抑制或自我控制,(Zhang & Shrum, 2008;Hong & Chang, 2015)导致
无论是对 CWE 还是 IWE 都表现出较强的参与动机与参与意愿。此外,检验结果也显示,在
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的共同中介作用下,“微信红包”信息对消费者参与意愿的直接效应已经
不再显著。
3.主要讨论与研究展望
3.1 主要结论
(1)“微信红包”信息会激发消费者的参与意愿,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会中介“微信红包”
信息对消费者参与意愿的影响。实验 1 和实验 2 表明“微信红包”信息会激发消费者的参与
意愿,并且 IWE 较之于 CWE 会激发消费者更高的参与意愿;实验同时表明 IWE 较之于 CWE
会诱发消费者更强的参与动机,但并没有表明 CWE 较之于 IWE 会诱发有更强的心理抗拒;
而且两个实验分别表明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会部分独立中介“微信红包”信息对消费者参与
意愿的影响。同时,实验 3 和实验 4 进一步地表明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会共同中介“微信红
包”对消费者参与意愿的影响,在共同中介下,“微信红包”信息的直接效应不再显著。
(2)自我建构会调节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对“微信红包”信息影响消费者参与意愿的中
介效应。实验 1 和实验 2 分别表明自我建构会调节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对“微信红包”影响
消费者参与过程的独立中介过程;实验 4 表明,自我建构会调节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对“微
信红包”信息影响消费者参与意愿的共同中介过程,即在 INTDSC 情境下参与动机与心理抗
拒共同中介“微信红包”信息对消费者参与意愿的影响,而在 INDSC 情境下参与动机起着中
介作用,但心理抗拒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对此的解释是 INDSC 倾向启动后,会诱发消费者更
强的情境融入与进取倾向,减弱了自我抑制或自我控制,导致消费者心理抗拒感减弱。
3.2 理论意义
(1)研究发现了消费者参与“微信红包”活动的重要中介机制,解释了“微信红包”信
息的诱发机理。“微信红包”信息会激发消费者的参与意愿,但研究发现,它们之间的影响会
受到参与动机和心理抗拒的独立中介和共同中介作用。“微信红包”信息诱发消费者参与中介
机制的发现,不仅揭开了消费者参与“微信红包”活动的心理机制,弥补了国内外对“微信
红包”参与心理机制研究的缺失;而且为有效操纵“微信红包”促销活动和正确引导消费者
21
参与提供了理论基础。
(2)研究发现了消费者参与“微信红包”活动的重要调节机制,拓展了“微信红包”营
销操作的适用边界。“微信红包”是传统文化与网络技术的有机结合,移动终端与移动支付助
推其病毒式扩散,并最终赢得了广泛的参与与巨大的成功。其中,作为重要文化差异、个体
差异与情境差异变量的自我建构,被发现无论是在参与动机和心理抗拒独立中介还是共同中
介“微信红包”信息影响消费者参与意愿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这不仅是对“微
信红包”信息影响消费者参与意愿模型的应用完善,也是对自我建构、自我决定和心理抗拒
等理论适用边界的重要扩展。
3.3 实践意义
(1)研究结论会对厂家或商家进行“微信红包”操作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研究结论
发现,CWE 并不总是吸引消费者的积极参与,只有在 INDSC 情境下它才更能启动消费者的
参与动机和更有效地降低他们的心理抗拒,从而增强消费者的参与意愿,才能实现预期的商
业目的;而如果要实施去显性商业目的的隐性关系营销,采用让管理人员或销售人员派发 IWE
或许更为有效,因为在 INTDSC 情境下 IWE 更具有吸引力。这也说明,在进行“微信红包”
营销活动时, 不仅要关注“微信红包”类型,更要关注诱发消费者的自我建构情境。因此,
本文对“微信红包”参与活动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的发现将为更为有效的操作“微信红包”
营销提供理论基础。
(2)研究结论会对消费者参与“微信红包”活动有重要的启发帮助作用。“微信红包”
出现后一方面给消费者带来了游戏娱乐、人际联系、增进效能等积极影响,但另一方面也给
消费者带来了失落、生气、后悔等消极情绪,甚至出现游戏成瘾等不良影响,因此正确地看
待和理性地参与“微信红包”活动至关重要。“微信红包”本质上是一项社会娱乐活动,兴趣
和愉悦才是“微信红包”游戏的本质和目的。如果过于强调参与的结果并由此产生负面情绪
或消极行为将会有违“微信红包”的本质和目的。本文对“微信红包”中介机制与调节机制
的发现将为消费者正确认识与理性参与“微信红包”游戏有重要的启发和帮助作用。
3.4 研究展望
(1)研究不足。本文的研究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影响消费者参与“微信红包”活
动的心理机制和情境因素非常多,例如预期后悔、感知竞争性、个性特质等,但我们只研究
了参与动机与心理抗拒等两个中介变量和自我建构调节变量,毫无疑问无法全面解构“微信
红包”的所有参与心理和参与行为;二是没有对参与动机和心理抗拒等中介变量结构维度的
作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和实证检验,例如内部动机、外部动机和内部化动机等的影响;三是
实验的对象和样本分别是模拟企业或个人和学生样本,难免会影响模型的生态效度。
22
(2)未来研究。未来进一步地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继续探索和检验消费者参与“微
信红包”意愿或行为的影响因素、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力争构建出更为契合消费者参与“微
信红包”意愿真实情境的综合模型,从而增强所构建模型的有效性;二是更加深入地探索和
检验参与动机和心理抗拒等中介变量的结构维度的影响,深化对中介机制或调节机制的解构。
此外,增强所构建模型的生态效度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 1 ] Aaker, J. L., and Lee, A. Y. 2001. ‘I’ Seek Pleasures and ‘We’ Avoid Pains: The Role of
Self-regulatory Goals i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Persuasion [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8(1):33-49.
[ 2 ] Arsena, A.R., J.Lee, Shrum, L. J., Zhang; Row J.L.2010. Differences in Self-Regulatory
Strength as a Function of Self-Construal [J].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37(10).
[ 3 ] Arthur B. Markman, C. Miguel Brendl.2000. The Influence of Goals on Value and Choice [J].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39:97-128.
[ 4 ] Bensley, L. S., & Wu, R. 1991.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in Drinking Following
Alcohol Prevention Messages [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1:1111-1124.
[ 5 ] Brehm, J. W. 1966. A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6 ] Brehm, J. W., & Brehm, S. S. 1981.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A Theory of Freedom and
Control [M].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7 ] Brendl, C. M., Higgins, E. T., & Lemm, K. M. 1995. Sensitivity to Varying Gains and Losses:
The Role of Self-discrepancies and Event Framing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6):1028-1051.
[ 8 ] Brewer, M. B., & Gardner, W. 1996. Who is this’ We’? Level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elf-representation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83–93.
[ 9 ] Brock, T. C. 1968. Implications of Commodity Theory for Value Change [M]. In A. Greenwald,
T.Brock, & T. Ostrom,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Attitud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215-243.
[ 10 ] Buller, D. B., Borland, R. and Burgoon, M. 1998.Impact of Behavioral Intention on
Effectiveness of Message Features Evidence From the Family Sun Safety Project [J].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4: 433–453.
[ 11 ] Campbell,L.,& Diamond,W.D.1990.Framing and Sales Promotions: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23
“Good Deal” [J].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7:25-31.
[ 12 ] Chandon, P., B. Wansink & G. Laurent .2000. A Benefit Congruency Framework of Sales
Promotion Effectivenes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64(4):65-81.
[ 13 ] Chirkov, V. I., & Ryan, R. M. 2001. Parent and Teacher Autonomy Support in Russian and
U.S. Adolescents [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2(5):618-635.
[ 14 ] Churchill, G. A., Jr.1979. A Paradigm for Developing Better Measures of Marketing
Construct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6 (2):64–73.
[ 15 ] Davis F.D., Bagozzi R.P., Warshaw P.R. 1992. Extrinsic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to Use
Computers in the Workplace[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2:1111-1132.
[ 16 ] Deci, E. L. (1975). Intrinsic Motivation [M]. New York: Plenum.
[ 17 ] Deci, E. L., & Ryan, R. M. 1985.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Human
Behavior [M]. New York: Plenum
[ 18 ] Derryberry, D., & Tucker, D. M. 1994. Motivating the Focus of Attention [C]. In P. M.
Niedenthal & S. Kitayama (Eds.), The heart’s eye: Emotional influences in perception and attention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167-196.
[ 19 ] Dillard, J. P., Plotnick, C. A., Godbold, L. C., Freimuth, V. S., and Edgar, T. 1996. The
Multiple Affective Outcomes of AIDS PSAs: Fear Appeals do More Than Scare People [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3:44–72.
[ 20 ] Dillard J.P., Shen L.2005).On the Nature of Reactance and its Role in Persuasive Health
Communication [J]. Common Monogr, 72:144–168.
[ 21 ] Doob, A., & Zabrack, M.1971. The Effect of Freedom – threatening Instructions and
Monetary Inducement on Compliance [J].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 3:408–412.
[ 22 ] Dowd, E. T., Milne, C. R., &Wise, S. L.1991. The Therapeutic Reactance Scale: A Measure of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J].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69:541–545.
[ 23 ] Eva Jonas, Verena Graupmann, Daniela Niesta Kayser, Mark Zanna, Eva Traut-Mattausch,
Dieter Frey.2009. Culture, Self, and the Emergence of Reactance: Is There a “Universal” Freedom?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9):1068–1080.
[ 24 ] Fiske, A. P. 1991. Structures of Social Life: The Four Elementary Forms of Human Relations
[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25 ] Fiske, A. P.1992. The Four Elementary Forms of Society: Framework for a Unified Theory of
Social Relations [J]. Psychological Review, 99(4):688-723.
24
[ 26 ] Fitzsimons, G.J. and Lehmann, D.R.2004, Reactance to Recommendations: When Unsolicited
Advice Yields Contrary Responses [J]. Marketing Science,23(1):82-94.
[ 27 ] Fredricks, J. A., Blumenfeld, P. C., & Paris, A. H.2004. School Engagement: Potential of
the Concept, State of the Evidence [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4(1):59-109.
[ 28 ] Gardner, W. L., Gabriel, S. and Lee, A. Y. 1999. “I” Value Freedom, but “We” Value
Relationships: Self-construal Priming Mirrors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Judgment [J].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7): 321-326.
[ 29 ] Gary Goertz.2006. Social Science Concept: A User’s Guide [D].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30 ] G.M. Allenby & Peter E. Rossi.1991 . Quality Perceptions and Asymmetric Switching
Between Brands [J]. Marketing Science, 8:185-204.
[ 31 ] Gonzalez, Richard & George Wu.1999. On the Shape of the Probability Weighting Function.
Cognitive [J]. Psychology, 38: 129-166.
[ 32 ] Hayes A F.2013. An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33 ] Harackiewicz, J. M., & Sansone, C. 1991. Goals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You Can Get There
From Here [C]. In M. L. Maehr & P. R. Pintrich (Eds.). Advances in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
Greenwich: JAI Press, 9:21-49.
[ 34 ] Higgins, E. T., James, S., & Ronald, S. F.1997. Emotional Responses to Goal Attainment:
Strength of Regulatory Focus as Moderator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2(3):515-512.
[ 35 ] Hoffman, B.& Nadelson, L.2010.Motivational Engagement and Video Gaming: A Mixed
Methods Study [J].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58:245-270.
[ 36 ] Hong, S. - M.., & Faedda.1996. Refinement of the Hong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Scale [J].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56:173-182.
[ 37 ] Hoshino-Browne, E., Zanna, A.S., Spencer, S. J., Zanna, M. P., Kitayama, S., Lackenbauer,
S.2005. On the Cultural Guises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 case of Easterners and Westerner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9: 294-310.
[ 38 ] Iacobucci, D., & Ostrom, A.1996. Commercial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Using the
Structur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o Understand Individual-to-individual, Individual-to-firm,
and Firm-to-firm Relationships in Commerc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
25
33(2): 53–72.
[ 39 ] Kimiecik, J. C., Harris, AT.1996 .What is Enjoyment ? A Conceptual/Definitional Analysis
with Implications for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J]. Journal of Sport Exerc Psychol, 18:
247–263.
[ 40 ] Kitayama, S., Snibbe, A.C., Markus, H.R., Suzuki, T., 2004. Is There Any “Free” Choice?:
Self and Dissonance in Two Cultures [J].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 527-533.
[ 41 ] Krueger D. W.1991.Money Meanings and Madness:A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 [J].
Psychoanalytic Review, 78(2):209-224.
[ 42 ] Kuhnen, U., Hannover, B., & Schubert, B. 2001. The Semantic Procedural-interface Model of
the Self: The Role of Self-knowledge for Context-dependent versus Context-independent Modes of
Thinking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0:397–409.
[ 43 ] Kuhnen, U., & Oyserman, D.2002. Thinking about the Self Influences Thinking in General: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Salient Self-concept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8:492–99.
[ 44 ] Lee, M.K.O., Cheung, C.M.K., & Chen, Z.2005. Acceptance of Internet-based Learning
Medium: the Role of Extrinsic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42:1095-1104.
[ 45 ] Liberman, N., Idson, L. C., Camacho, C. J., & Higgins, E. T.2001. Promotion and Prevention
Focus on Alternative Hypotheses: Implications for Attribution Function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0:5-18.
[ 46 ] Lynn, M. 1991. Scarcity Effects on Value: A Quantitative Review of the Commodity Theory
Literature [J]. Psychology and Marketing, 8 (1):43-57.
[ 47 ] Malley, L., and C. Tynan.1999. The Uti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Metaphor in Consumer
Markets: A Critical Evaluation [J]. Journal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15:587-602.
[ 48 ] Markus, H. R., & Kitayama, S.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8:224–253.
[ 49 ] Moon, J., & Kim, Y.2001. Extending the TAM for a World-wide-web Context [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38(4), 217-230.
[ 50 ] Mowen, J. C.2000. The 3M Model of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Theory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 to Consumer Behavior [M]. Boston: Kluwer Academic.
[ 51 ] Nisbett, Richard E. et al 2001.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s. Analytic
26
Cognition [J]. Psychological Review, 108:291-310.
[ 52 ] Preacher K J, Hayes A F.008. Asymptotic and Resampling Strategies for Assessing and
Comparing Indirection Effects in Multiple Mediator Models[J].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40:879-891.
[ 53 ] Preacher K J, Rucker D D., Hayes A. F.2007. Assessing Moderated Mediation Hypotheses:
Theory, Methods and Prescriptions[J].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42:185-227.
[ 54 ] Quick, B. L., & Stephenson, M. T. 2007. Further Evidence that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can
be Modeled as a Combination of Anger and Negative Cognition [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4:255-276.
[ 55 ] Richard M. Ryan & Edward L. Deci.2000.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s: Classic
Definitions and New Directions [J].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5:54–67.
[ 56 ] Sansone, C., & Harackiewicz, J. M.1996. “I don’t feel like it”: The Function of Interest in
Self-regulation [C]. In L. L. Martin & A. Tesser (Eds.), Striving and Feeling: Interactions among
Goals, Affect, and Self Regulation. Mahwah, NJ: Erlbaum, 203-228.
[ 57 ] Schwarz, N., Frey, D. & Kumpf, M.1980. Interactive Effects of Writing and Reading a
Persuasive Essay on Attitude Change and Selective Exposure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6:1–17.
[ 58 ] Singelis, T. M. 1994. The Measurement of Independent and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s [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580-591.
[ 59 ] Tauer, J. M., & Harackiewicz, J. M.2004. The Effects o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on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6:849–861.
[ 60 ] Wernimont P.F.& Fitzpatrick S.1972. The Meaning of Money [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56(3):218-226.
[ 61 ] Wicklund, R. A.1974. Freedom and Reactance [M]. Potomac, MD: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62 ] Worchel, S., Andreoli, V. A., & Archer, R.1976. When is a Favor a Threat to Freedom: The
Effects of Attribution and Importance of Freedom on Reciprocity?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44:294-310.
[ 63 ] Worchel, S., & Brehm, J.1970. Effects of Threats to Attitudinal Freedom as a Function of
Agreement with the Communicator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4:18-22.
27
[ 64 ] Worchel, S., Lee, J., & Adewole, A. (1975). Effects of Supply and Demand on Ratings of
Object Value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2(5):906.
[ 65 ] Yamanchi K.L.&Temple D. I.1982. The Development of a Money Attitude Scale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46 (5):522—528.
[ 66 ] Yanamandram, V., & White, L.2006. Switching Barriers in Business-to-business Services: A
Qualitative Stud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rvice Industry Management, 17(2):158–192.
[ 67 ] Zhang, Shi and Gavan J. Fitzsimons.1999. Choice-Process Satisfaction: The Influence of
Attribute Alienability and Option Limitation [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77 (3):192-214.
[ 68 ] Zhao X, Lynch J G, Chen Q.2010. Reconsidering Baron and Kenny: Myths and Truths about
Mediation analysis[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7:197-206.
Wechat Envelop! Do Consumers Grab or not? An Explanation
Based on Mediating Role of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bile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mobile financial payment, Wechat
envelopment campaign won widespread participation and great success in 2015. Its success lied in effectively
arousing and inducing consumers’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participation enthusiasm, however, consumers in
fact underwent complicated psycholog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when seeing the information on wechat
envelopment.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found that consumers had great difference in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enthusiasm toward different types of wechat envelopment(Commercial or Interpersonal), the main among reasons
lied in consumers’ different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toward different wechat
envelopments. Across four experiments, we found that (1)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separately mediated alone the influence of wechat envelopment information on consumers’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and furthermore the process was both moderated by self-construal; (2)They also commonly
mediated their influence and so did by self-construal. The findings did not only uncover and explain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consumers’ participation in wechat envelopment, but also there were great
managerial implication for business to operate successfully marketing campaigns concerned wechat envelopment
to obtain consumer resource and competing advantage and for consumers to improve consumer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Keywords: Wechat envelop;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Self-construal;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