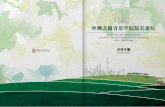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 - Ghub . org
-
Upload
khangminh22 -
Category
Documents
-
view
0 -
download
0
Transcript of 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 - Ghub . org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 Name of Section2封面图片: Emperor penguins, Eastern Antarctica. Image by John B. Weller.
此页: Chinstrap penguins. Image by John B. Weller.
2011年10月,南极海洋联盟(Antarctic Ocean Alliance, AOA)建议在南极洲周围的南大洋范围内的19个特定区域建立一个海洋保护区(MPAs)网络和禁捕保护区(no take marine reserve)1。基于选定区域的生态价值以及对罗斯海的关注,南极海洋联盟通过这个题为《南大洋的传承:罗斯海和环极保护的愿景》的报告全面表达了对这个保护区网络的愿景。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是管理南大洋生物资源的团体。该委员会将2012年确立为建立初期的南大洋保护区网络的目标日期。本报告列出了建议作为海洋保护区和禁捕保护区的区域,并阐述了选择这19个区域的依据。
南极海洋联盟的这份报告,首先对南极地区作了简介,然
后从地理学、海洋学和生态学的角度阐述了选定的19个区域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是气候变化和资源掠取造成的,并且列举了一些保护实例。报告提出了可行的海洋保护的规模和范围的建议。
南极海洋联盟认识到,对于最终的保护区网络的决定,在
国际进程上还必须做出很多努力。七年来,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的成员和科学家,在制订南大洋的海洋保护区和禁捕保护区规划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南极海洋联盟提供的本报告,是为长期以来的持续努力做出的一点贡献,希望能够帮助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实现在2012年的目标。南极海洋
执行者摘要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Name of Section 3
南极海洋联盟是由环境保护组织和慈善家组成的一个国际联盟,其成员包括:南极与南极海洋联盟(ASOC)、蓝色海洋基金会(英国)、绿色和平(Greenpeace)、蓝色使命(MissionBlue,美国)、Oceans5(美国)、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最后的海洋、森林与鸟类组织(新西兰)、ECO (新西兰)、深浪(Deepwave,德国)、国际人道协会、韩国环保运动联盟(KFEM)、鲸与海豚保护学会。南极海洋联盟的合作伙伴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创绿中心(中国)、世界海洋保护组织(Oceana)、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海洋星球(OceanPlanet,澳大利亚)、国际海洋状况计划(IPSO)和其他国际性的团体。
联盟希望跟南大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成员和科学机构共同努力,对这些独特的、珍贵的生态系统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本报告只是对部分区域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对于那些没有确定边界的区域,本报告敦促南大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成员在决定保护的程度时考虑到每个区域独特的环境因素。
在本报告中,南极海洋联盟提议在南大洋对生态系统和物
种保护至关重要的的大型生态系统的进程进行保护。已经选定的这些区域,总体上涵盖了广泛且有代表性的动植物栖息地和生态系统,包括了主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这些区域亦包括了不同的环境类型和不同的深海以及海底景观,例如海底山峰、山脊和低谷。本报告的提议包括了对于一些特有物种的生命周期具有关键作用的地区。南极区域最主要的鱼类捕食者南极犬牙鱼(Antarctic toothfish)和其他一些捕食生物,都是特有物种的例子。这些生物构成了处于生物营养链较高层次的动物——例如企鹅和海豹繁殖、觅食的基础。建议予以保护的不少地区,比如罗斯海和东南极洲,将作为关键的气候参照区和依赖冰冻环境的物种的气候避难所。
对于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环境的变化,包括关于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希望本报告的提议能够促进支持这些方面关键研究的长期资料积累的持续与扩展。此外,鲸、海豹和鱼类的数量迄今仍未从历史上的过渡捕捞恢复过来,本报告在这方面也会有所帮助。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世界公园大会建议,所有海洋生物的栖息地,至少有30%应该包括在海洋禁捕区网络之内2。根据《南极条约》的科学价值观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的原则和授权,南极海洋联盟的研究显示,超过40%的南大洋海域应该在禁捕保护区和海洋保护区的网络中得到切实保护。这些海域包括了现有的海洋保护区和以往的保留规划分析当中所确定的区域,以及在本报告所描述的额外的关键环境栖息地3。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的成员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机,就是在南极周围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保护区和禁捕保护区网络,作为遗产传承给后世。有了这样一个网络,南大洋的生物栖息地和野生动植物将受到更好的保护以免受人类的干预。南极海洋联盟相信,在具有远见的政治领导力之下,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可以抓住这个时机。
目前中国在南大洋拥有一支由三艘船组成的小型船队,从事对磷虾的捕捞。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拥有尖端科技的新兴现代化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实际上,中国正在考虑投资扩展自己在南极的业务,其中以磷虾捕捞为重点。
考虑到远洋捕捞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中国在南大洋的未来利益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中国政府有责任以可持续、负责任的方式参与全球的公共物品和相关生物多样性的管理。同时中国还是一个注重科研的国家,在南极开展着重要的研究,在南极保护的国际舞台上发挥着关键性的领导作用。
对中国政府来说,现在是时候来展示领导力,在国家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平衡了,包括支持在南大洋建立禁捕保护区和海洋保护区。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4
Iceberg in the Southern Ocean. Image © Greenpeace / Jiri Rezac.
气候变化渔业其他威胁
CCAMLR的机会
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
1. 南极半岛2. 威德尔海
南斯科舍海地区:
3. 南奥克尼群岛4. 南乔治亚岛5. 南桑威奇岛弧 6. 毛德海隆7. 布韦岛
德尔卡诺-克罗泽地区:
8. 鄂毕-勒拿海底斜坡9. 德尔卡诺地区公海
克尔格伦公海地区:
10. 克尔格伦高原公海地区11. 班扎尔海底斜坡12. 克尔格伦产区13. 南极东部大陆架14. 印度洋海底环境
罗斯海地区:
15. 罗斯海16. 太平洋海底山17. 巴雷尼群岛18. 阿蒙森海和别林斯高晋海19. 彼得一世岛
结论: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
致谢
目录:
威胁 5
689
10
12
1415
1616161819
20
2020
22
2222222426
27
2727272931
目录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 5
Image by John B. Weller
虽然南极洲经常被描绘成一片由美丽惊人但是没有生气的冰川主宰的冰冻区域,其实它充满了生命,不过大部分是海洋生物。在结冰的洋面下,颜色鲜亮的海星、海绵动物和其他形状大小各异的底栖生物像毯子一样铺满整个海底。体内含有清澈的白色血液和防冻液的奇异鱼类潜藏在水体中各处。在海洋表面,企鹅、飞翔的海鸟、海豹和鲸类充斥在冰块之间,在磷虾丰富的水体中觅食。
许多深水中或冰面下的海洋栖息地还有待于研究,不过几乎每支南极研究探险队都会发现过去科学界未知的新物种。南大洋许多物种在地球其他区域都没有出现过。南极洲的确是这个世界最后的野生疆域之一。
尽管有着严酷的疾风和寒冷,南极洲仍然哺育了大量的海鸟和海洋哺乳动物,其中许多物种在陆地繁殖,在水中觅
食。如今世界上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和鸟类的数量都在急剧减少,而南极洲仍然拥有大型企鹅繁殖聚集地,企鹅数量极多,叫声震耳欲聋。南极洲还拥有数百万只食蟹海豹(crabeater seal),它被认为是地球上数量第二多的哺乳动物4。
可能是由于地处偏远、气候严酷,南大洋的一些区域仍然是地球上仅存的最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罗斯海(Ross Sea)和威德尔海(Weddell Sea)这两大海域依然免于大面积污染、入侵物种、海底拖网捕鱼作业和其他大规模商业捕鱼操作5的影响。由于现在这样的生态系统所剩无几,可供科学家研究生态系统在免于大规模人类干扰的情况下如何运行的地区也 越来越少。
在其他区域,过去的捕鲸业、海豹猎捕和过度捕鱼已经导致种群数量大幅度下降。幸运的是,通过全球的保护努力,一些鲸类种群正在逐步恢复当中。自从叫停对海豹的捕猎后,海豹种群的数量已经大量回升。从1982年起,商业捕鱼在很大程度上被南大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CCAMLR)纳入国际管控之下,但是非法的、不受管制的、不作报告的(IUU)捕捞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南大洋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是它的地理特性。众所周知,海底山是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中心枢纽,而南大洋到处分布着海底山,包括鄂毕-勒拿海底斜坡(Ob and Lena Banks)区域,南大洋的东印度洋部,包含布韦岛(Bouvetøya)在内的大西洋中脊,以及罗斯海以北地区。克尔格伦高原(Kerguelen Plateau),毛德海隆(Maud Rise)和班扎尔海底斜坡(BANZARE Bank)是海底上升区域,这一地势为它们成为非常高产和生物丰富的地区提供了基础。此外,环绕大多数南大洋岛屿的水体是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为食肉动物提供了觅食区域广阔的重要繁殖场所。
在规划一个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和禁捕海洋保护区的代表性网络的过程中,南极海洋联盟(AOA)识别出了一些区域。这些区域包含大范围的栖息地和生态系统,包括海底和水层生态区以及罕见的生物景观。对于尚未得到广泛研究的南极地区,本报告集中讨论其地貌特性和生物地理学的表现和多样性,来呈现其作为重要生物栖息地的潜在可能。
引言
南大洋约占全球海洋面积的十分之一,然而
全球海洋只有不到1%以海洋保护区或禁捕保护
区的形式得到严格保护。禁捕保护区和海洋保护
区与南大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CCAMLR)
的主要目标相一致,即保护南极海洋生命,管
理对其的合理利用,依据南大洋生物资源养护
(CAMLR)公约第二条款中的三大原则:
1.防止过度捕捞导致种群数量降低到无法延续的水
平;
2.维持并在必要时修复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中被捕捞
种群,依赖种群和相关种群之间的生态关系;
3.依据现有最可靠的科学研究,预防或最小化海洋
生态系统变化的风险。¬
引言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 威胁6
Image by John B. Weller
南极鱼 图片来源 John B. Weller.
南大洋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气候变化和随之而来的温度、洋流以及冰面变化的改变持续不断地瓦解着这一错综复杂的极地生态系统。曾经的过度捕捞带来的影响挥之不去,大多数鲸类和许多鱼类的数量还没有完全恢复。现有保护措施不足以充分地保护南大洋独特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禁捕保护区和海洋保护区将帮助最小化甚至消除一些南大洋生态系统面临的最紧迫的威胁。
气候变化
人类活动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由此引起的急速气候变化正在影响地球的每个角落6,而由冰主宰的南极洲地区则是地球上变化最快的地区之一7。不过气候变化对南极洲各地区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南极大陆西部地区的温度在1950年到2005年期间平均上升了2.8℃8,这是地球上观测到的最快温度上升。然而南极大陆的其他部分却在变冷9。这一证据也表明南极洲的持久季节性臭氧层空洞(20世纪80年代初被发现)可能会加剧气候变化的影响10。
冰架
冰架是从陆地冰川和冰原延伸而来的浮动厚冰平台。这些巨物有几百米厚,然而在南极洲的许多地方它们正在迅速地崩塌。随着冰架崩离,它们的主体冰川会以更快的速度从陆地浮动到海洋,然后融化。巨大的拉森B冰架(Larsen B Ice Shelf)于2002年崩裂,随后威尔金斯冰架(Wilkins Ice Shelf)于
2008年部分断裂11。流入阿蒙森海(Amundsen Sea)的松岛冰川(Pine Island Glacier)正在迅速融化12,可以预计其主要部分将在未来100年内变为浮冰13。如果这变为现实,可能会引发整个南极大陆西部冰架的解体14。其后果,包括海平面上升和海洋盐度变化,将对全球环境造成毁灭性影响。
海冰
每年南极洲周边都会形成海冰,有效地使大洲的面积加倍。这种年度消长驱动了生态系统进程,包括初级生产力和为大量物种提供贯穿生命史各阶段的栖息地15。在南极半岛和别林斯高晋海(Bellingshausen Sea)周边,海冰出现消融,冰季缩短了三个月16。半岛以北的斯科舍海(Scotia Sea)可能是南大洋上海冰退缩最严重的地区17。这些海冰的变化可能导致斯科舍海的磷虾数量减少,减少程度可能多达38%至81%18。
威胁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威胁 7
在南设得兰群岛捕获的南极犬牙鱼 图片来源: Darci Lombard.
海冰的存在对磷虾的生命史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磷虾幼虫来说,它们以冰下的微生物为生19。磷虾数量的减少会对整个生态系统造成连锁效应,因为磷虾是许多鲸类、海豹、企鹅、鱼类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冰退化也会影响到许多海洋动物,特别是那些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十分依赖于海冰的物种,比如食蟹海豹20。相反,在大陆另一侧的罗斯海,如今海冰形成更早、融化更晚,海冰季延长了两个多月21。这可能部分归咎于持久臭氧层空洞,而冰季延长意味着初级生产力会降低22。海冰的变化会对当地野生动物造成很大压力。例如,罗斯海的一些阿德利企鹅(Adélie penguin)种群现在必须到离冰缘更近的地方觅食过冬,而这离他们的传统聚集区越来越远23。
持续的冰架崩塌和海冰消融将引起海洋环境的剧变,包括依赖冰冻环境生存的物种失去家园,从温暖纬度地区而来的邻近物种或引进物种可能会迁移过来居住。同时,科学家刚刚开始揭示这些变化对当地动植物群的影响。在海冰严重消融的地区,例如南极半岛西部,必须研究海冰消融对物种的相关影响来支持政策的制定。
在过去的200年间,海洋酸度上升了30%,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钙化生物将受到有害影响。酸度增加会溶
解钙化生物的甲壳和骨骼。
海洋酸化
随着人类燃烧化石燃料,不断地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进入大气层,海洋吸收了二氧化碳,引起PH值降低,海水酸度增加。在过去短短的200年间,海洋酸度上升了30%,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钙化生物将受到有害影响24。酸度增加会溶解钙化生物的甲壳和骨骼,同时二氧化碳大量涌入会降低碳酸离子的可得性。这会进一步阻碍钙化生物生长甲壳和骨骼。
与温暖的水体相比,南大洋的冷水中的碳酸钙含量自然较低,因而更接近生物体遭受有害影响的临界点25。科学家们预测,在未来二十年内,主要浮游生物物种,例如翼足类动物(pteropod)(如:小型海洋蜗牛),将无法生长出强健的甲壳26。最后,他们可能根本无法长成甲壳。如果翼足类动物或其他甲壳类动物灭亡,其不良后果将对南大洋生态系统上下造成连锁影响。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 威胁8
南极磷虾 图片来源: Lara Asato.
渔业由于地处偏远,南大洋是最后遭受人类直接开发的全球性海洋之一。然而自18世纪
80年代人类发现南大洋之后不久,商业猎人迅速开始捕猎南极洲沿岸冻水里生存的动物。海狗(fur seal)首先遭到捕杀,然后是象海豹(elephant seal),接着是巨鲸和几个长须鲸物种。到19世纪末,一些海豹物种几乎被捕猎殆尽。到20世纪最后25年,一些鲸类物种也由于产业开发而接近灭绝。尽管现在一些物种规模显示了恢复的迹象,大多数鲸类仍然只有原来种群规模的极小部分。一些鱼类目标物种,例如花纹南极鱼(marbled rockcod),也依旧没有恢复27。
鉴于过去不受管控的渔业的教训,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南极磷虾渔业引起了南极条约缔约国和科学家的严重忧虑。考虑到磷虾在南大洋食物链中的核心地位,许多人担心类似模式的过度开采将危害到巨鲸种群的恢复并对其他南大洋物种造成灾难性影响28。作为回应,南极条约各方启动了关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CAMLR公约)的谈判。该公约于1980年完成,1982年生效,其任务是确保渔业不会对目标物种和泛南大洋生态系统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CAMLR公约提出了“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原则,这是海洋生物资源管理方面的一个重要进展29。
磷虾磷虾是一种类似虾的甲壳纲动物,分布于整个南大洋,最大的种群位于西南大西
洋。1973/74年渔汛期起,一些国家开始在这一地区捕捞磷虾,包括南极半岛、南乔治亚岛(South Georgia)、南奥克尼群岛(South Orkneys)周边。渔业发展迅速,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捕获量达55万吨;之后开始下降,20世纪90年代初平均年产量仅为10万余吨30。近年捕获量再次回升,2009/10汛期约为21万吨,2010/11汛期约为18万吨。过去四年平均年产量达17万吨,比历史平均值增长了将近42%31。
种种因素导致人们担忧未来磷虾渔业可能会继续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是对磷虾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包括Ω-3脂肪酸在保健品和水产养殖中的应用。也许是对该需求的回应,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磷虾渔业产生了兴趣。捕捞技术的进步也提高了渔业的效率。目前捕捞活动已经从夏末持续到冬季中期,并逐渐向深冬延长。南极半岛附近海冰的持续变化和减少可能会很快允许渔汛期进一步延长32。
近年的磷虾捕捞量估计只是当地磷虾储量的一小部分,但磷虾却可能是南大洋食物网中最重要的角色。南大洋的食肉动物非常依赖磷虾,包括许多企鹅,海鸟,许多鱼类和海豹,以及定居型和过境型鲸类。此外,人类仍然没有完全摸清磷虾种群动态,一些地区的种群数量年年都会剧烈波动。磷虾渔业管理应该考虑到这些生态系统因素。包括将气候变化对磷虾种群的潜在影响纳入考虑当中。
有鳍鱼渔业20世纪60年代,捕鱼者开始在一些
亚南极岛屿周边进行拖网捕鱼作业,捕捞花纹南极鱼(marbled rockcod)、鲭冰鱼(mackerel icefish)、灰石斑鱼(grey rockcod)、巴塔哥尼亚石斑鱼(Patagonian rockcod )、亚南极灯笼鱼(subantarctic lanternfish)以及威尔逊冰鱼(Wilson’s icefish)33。鱼类种群被严重捕杀,特别是花纹南极鱼——最初的几个渔汛期就捕杀了几十万吨鱼34。
截止1990年,花纹南极鱼的数量急剧下降到捕捞前的5%,至今尚未恢复。花纹南极鱼并不是唯一的案例。大多数被捕捞的南极鱼类都在缓慢恢复35,尚未回升
到原有水平36。
随着浅水物种灭绝,20世纪80年代捕鱼者开始把目标锁定在深水鱼类巴塔哥尼亚犬牙鱼(Patagonian toothfish)上,在亚南极岛屿周围使用多钩长线捕捞作业37。这种鱼长寿多脂,可以长到身长两米以上,被以“智利海鲈鱼”的名义推向市场,迅速成为昂贵饭店菜单上的热门菜,主要是在美国和欧洲。犬牙鱼的合法渔业处于CCAMLR管理之下,然而IUU(非法的、不受管制的、不作报告的)捕鱼者也注意到这一“白色黄金”——捕鱼者通常用这个名称来形容这一利润丰厚的鱼类。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南极的犬牙鱼捕捞总量超过每年10万吨,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为非法捕捞38。这导致当地巴塔哥尼亚犬牙鱼种群数量锐减,相关渔业随之终止39。这些种群中的许多都尚未恢复。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威胁 9
在钩网中腐烂的幼鱼 图片来源 © Greenpeace / Roger Grace. 拉森B冰架上的裂缝 图片来源 © Greenpeace / Steve Morgan.
其他威胁除了气候变化和渔业的威胁,南极洲
也易受污染、不受监管的旅游业和外来入侵物种的损害。在过去,科学作业的废物经常丢弃入海或留在陆地。如今,废物处理处于高度管控之下,科学家和旅游者必须将废物随身带走。尽管已有这些规则,仍有一些废物进入了南大洋。塑料污染也开始出现在半岛区域45。
采矿业被南极条约体系所禁止,但有可能将于2048年的商讨中重启46。南极旅游业每年吸引3万多游客47,尽管受到南极条约缔约方的管控,且负责任的行为受到旅游产业贸易协会(IAATO)鼓励,多方仍担心旅游者会打扰当地环境和相关野生动植物。旅游业引起的最大的风险之一是船只触礁,撞冰或沉没引起的意外石油泄漏。渔业船只也有同样的风险。外来入侵物种已经进入南极大陆,经常来自卡在游客和科学家的设备和服装上以及船只外壳和压舱水中的种子。少数植物物种已经毫不费力地定居在少数无冰区域,尤其是在南极半岛上。气候变暖可能会帮助它们传播48。
为 了 满 足 市 场 需 求 , 渔 轮 挺 进 南极 海 域 的 更 南 区 域 , 寻 求 南 极 犬 牙 鱼(Antarctic toothfish)——巴塔哥尼亚犬牙鱼的一种南方近亲。不幸的是,IUU捕鱼者也追随他们的脚步,并由多钩长线改为深海刺网捕鱼40。刺网的使用被CCAMLR所禁止,因为其副渔获物水平甚至比多钩长线还高,而且具有“幽灵渔捞”的风险,即渔网遗留或掉落在海洋中后将继续捕鱼长达几十年,从而对环境造成严重威胁。IUU捕鱼者的刺网捕获了多少犬牙鱼仍然未知,不过可能是个庞大的数字41。举例来说,澳大利亚官方于2009年查获的刺网跨度达130千米,网住了29吨南极犬牙鱼42。
自从公约生效开始,CCAMLR采取了多种措施实现可持续渔业管理。因为鱼类种群的减少,该委员会正式关闭了大多数受管控的有鳍鱼渔业,包括在南极半岛和南奥克尼群岛周围水域,以及南
印度洋地区。CCAMLR还通过一系列措施减少IUU犬牙鱼捕捞,包括成员国定期在许多合法渔场巡逻。除了禁止刺网捕鱼外,CCAMLR也禁止了海底拖网捕鱼作业,因为后者对海底有不良影响;同时CCAMLR实行了保护脆弱海底栖息地的措施43。
尽管做出了以上努力,从前的过度捕捞和持续进行的IUU捕捞导致很多渔场被捕捞殆尽,其整体生态系统影响尚未可知。大多数犬牙鱼捕鱼者使用海底多钩长线,这种长线仍然会严重影响海底栖息地,特别是当长线作业集中在一片区域长达几十年时。CCAMLR制定的识别和禁止脆弱海底栖息地捕鱼作业的措施仍然不足44。一个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和禁捕海洋保护区的代表性网络将是一个保护生态系统功能的宝贵工具,可以帮助维持现有生物种群,并促进枯竭种群的恢复。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南极犬牙鱼捕捞总量超过每年10万吨,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为非法捕捞。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 威胁10
Image by John B. Weller
位于澳大利亚荷巴特的CCAMLR总部大楼 图片来源: Richard Williams for the AOA.
海洋保护区日渐成为政策制定者、科学家和捕鱼者的有力工具,来确保我们海洋的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利用49。其价值在2002年于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SSD)上得到正式承认,峰会期间世界各国承诺在2012年前在全球海洋建立海洋保护区代表
性网络50。
请注意,在这篇报告中,海洋保护区(MPA)是指为满足特定的环境保护、栖息地保护或渔业管理目标而限制或禁止某些活动的区域。而禁捕海洋保护区(no-take marine reserve)特指被高度保护的区域,禁止一切提取利用,包括渔业。禁捕海洋保护区为海洋生态系统的所有成分提供最高级别的保护。
依据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CAMLR公约),成员国被要求采取一种生态系统管理的手段来确保在 南 大 洋 的 活 动 不 会 影 响 到 南 极 生 态 系 统 的 整 体 健康。CCAMLR应该运用现有最好的科学方法来制定预防性甚至是过度保护生态系统功能的管理决策51。海洋保护区和禁捕保护区是实施预防性和生态系统方法的必要工具。此外,CAMLR公约第九条款2(g)部分明确地规定“出于科学研究或保护的目的,指定地区、区域或次区域的开放和封闭”。
认识到海洋保护区和禁捕保护区对于支持生态系统健康的价值,CCAMLR已同意于2012年实现WSSD目标52。该承诺得到一系列里程碑事件的支持,包括:
•2005年CCAMLR海洋保护区研讨会;•首次南大洋生态分区绘图(2007年)•识别出了11个海洋保护区优先区域,并且正在筹划
另外9个领域;•2009年指定南奥克尼群岛南海架海洋保护区;•2011年CCAMLR海洋保护区研讨会;•2011年会议上同意了一项保护措施,为CCAMLR
海洋保护区建立提供了总体框架。
2011年海洋保护区保护措施总体框架确认了以下标准:
CCAMLR的机遇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威胁 11
南乔治亚岛上的王企鹅 图片来源: John B. Weller.
1. 保护典型的海洋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适当的规模,保持它们的长期生存能力和完整性;
2. 保护关键的生态系统进程、栖息地和物种,包括种群数量和生命史各阶段;
3. 建立科学参考区域,监测自然变异性和长期变化,或监测捕捞和其他人类活动对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以及它们所组成的生态系统的影响;
4. 保护易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区域,包括独特的、罕有的或高度生物多样性的栖息地和特性;
5. 保护对当地生态系统功能有关键意义的特性;6. 保护各区域,维持其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恢复力或
适应能力53。
CCAMLR具有重要的机遇和责任去帮助实现WSSD提出的2012年海洋保护区网络目标。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就必须秉承CAMLR公约的原则、价值观与精神,而这些原则、价值观与精神则反映了南极条约的中心理念。尽管过去过度捕捞时有发生,南大洋仍然存有生态活跃的地区,比如罗斯海和威德尔海,几乎依然是完好无损的。如果不尽快推进有效管理,将有可能失去这些宝贵的区域,尤其是在面对气候变化威胁的时候。
很明显,气候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海冰变化和海洋酸化将给南极海洋生态系统增加压力。人类需要依据科学界提供的清晰指导,提前适应这些巨大的挑战。许多科学家提出南极是一个收集此类数据的理想地点。
南极在没有人类定居的情况下演变了千百万年,一些地区一直没有受到人类的干扰和破坏。这给了科学家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理解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物种的适应力和可能的减缓策略,避免结果参杂其他人类活动的影响54。将海洋保护区和禁捕海洋保护区作为参照区域可以帮助科学家清楚地了解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的影响。此外,这些受保护区域有助于提升南大洋生态系统的恢复力和适应力。特定的“气候参照”区域构成了一个有效的禁捕保护区网络的重要部分。最后,变暖速度
最慢的区域可以作为“避难所”——那些依赖冰和低温水域生存的物种最后的适宜栖息地。
现在通过实施适当的保护,可以将南极条约系统的传统和信念、价值观和精神发扬光大。过去,这些价值观和规定使得CCAMLR成员国得以在国际空间的管理上展示出可圈可点的领导力。CCAMLR很有动力去抓住这次机会。
中国在南大洋保护上的作用中国的捕捞业发展应该与国家的长期科研计划和国
际社会的利益保持一致。中国可以在支持和发展南大洋禁捕保护区和海洋保护区网络方面发挥领导性作用,在
在南奥克尼群岛的俄罗斯磷虾拖网渔船 图片来源: © Greenpeace / Roger Grace.
国际舞台上展现其保护环境方面的领导力。如果中国的决策者有决心支持保护措施,留出一系列大规模区域用于科学研究和生态保护,良好管理的渔业和生态保护之间就可能实现平衡。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本报告建议中国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支持在南大洋建立海洋保护区和大规模禁捕保护区网络的呼声,确保对南大洋环境和众多物种的长期保护。
2.明确地支持AOA的呼吁,在罗斯海建立一个360万平方公里大小受到全面保护的禁捕保护区。
3.遵照CCAMLR体系和流程,监控中国在南大洋的捕捞业,并在其违反国际法律法规时施以惩罚。
AOA希望能与中国政府并肩合作,来实现这些目标,以保证中国的南极捕捞业保持生态可持续性。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 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12
Image by John B. Weller
一对南方皇家信天翁 图片来源: John B. Weller.
要取得最好的效果,海洋保护区和禁捕海洋保护区就必
须达到一定的规模,足以覆盖和保护到各种重要的生态
过程和当地动物的生活史55。由大型海洋保护区和禁捕
海洋保护区组成的网络能够将所有这些海洋进程联系起
来,从而发挥出最大化的功效,确保南大洋及南极洲附
近海域拥有长期的恢复力。自从2002年设定目标以来,
包括CCAMLR成员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机构就一直在为
实现WSSD提出的2012年目标而努力。AOA感谢所有科
学家以及南极相关项目在推动建立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
禁捕海洋保护区等重要区域方面所做的贡献。
单个的海洋保护区和禁捕海洋保护区只能保护那些从局部来看比较重要的地区,而由各种保护区组成的保护网络则可以增强整个南大洋生态系统的恢复力。这一网络不仅能够保护海底山、海底斜坡和潮间带等具有代表性的动物栖息地类型,还能保护供动物觅食和繁衍的开放水域。动物在生长、觅食和繁殖的过程中往往会不断地迁徙。在这一过程中,由大型海洋保护区和禁捕海洋保护区组成的保护网络能够为它们提供全程的保护。为了保障长期的恢复力,保护网络内的各保护区在保护范围上也应有一定的重叠,比如由若干个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共同保护某种相似的栖息地类型,以此来抵御人为因素及自然灾害(如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56。在保护其他大型海洋生态系统(如澳大利亚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的过程中,这种类型的保护网络取得了很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57。
AOA建议在南极的19个地区建立海洋保护区和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这些区域能够覆盖生物多样性和生物繁殖的热点地带、重要的栖息地以及独特的地理景观。这一网络所覆盖的区域既有过度开发之后尚处于恢复阶段的地区,也有从未遭受过大规模开发的地区。有了这样一个海洋保护区和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南大洋富饶的野生动物资源以及许多特有的物种就能得到良好的保护。
需要强调的是,要了解和改善海洋环境对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也许是我们唯一的希望58。南极洲的一些地区已经在气候变化的作用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能够消除人类在这一地区造成的影响,那么南大洋的动植物
就能拥有更多的机会去适应未来的变化。南大洋是一片公海,它所蕴藏的财富属于全人类。海洋保护区和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能够有效地保护这笔财富,造福子孙后代。
AOA所选择了19片海域,共同组成一个全面且有生物学意义的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对上述19个区域逐一进行介绍,概述各个区域的地理学、海洋学及生态学特征。我们在每个区域都提出了一个保护案例(或者说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 13
1 南极半岛
2 威德尔海
3 南奥克尼群岛
4 南乔治亚岛
5 南桑威奇岛弧
6 毛德海隆
7 鄂毕-勒拿海底斜坡
8 鄂毕-勒拿海底斜坡
9 德尔卡诺地区公海
10 克尔格伦高原公海地区
11 班扎尔海底斜坡
12 克尔格伦产区
13 南极东部大陆架
印度洋海底环境
15 罗斯海
太平洋海底山
17 巴雷尼群岛
18 阿蒙森海和别林斯高晋海
19 彼得一世岛
AOA建议通过划定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来保护南大洋的19个区域。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 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14
食蟹海豹 图片来源: Cassandra Brooks.
南极半岛
南极半岛及其附属岛屿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59,分布着南大洋最大的几块南极磷虾聚集地60。由于拥有丰富的磷虾资源,这一地区成为了许多企鹅、海豹和鲸类繁殖与觅食的场所61。
南极半岛西部是地球上变暖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其年平均气温与1950年相比升高了2.8℃62。气候变暖与海冰减少构成
南极半岛
了一种正向反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气候变化63。变暖造成了大量冰川融化,最近几十年来南极半岛87%的冰川都已消失64。在乔治王岛(King George Island)的马克斯韦尔湾(Maxwell Bay),每年海冰覆盖的持续时间已从1968年的六个月下降到了2008年的三个月。在同一时期,俄罗斯别林斯高晋站(Bellingshausen station)附近的固定冰(与延伸入海的海岸相连的海冰)厚度也从90厘米下降到了30厘米65。
如果这种变暖趋势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地区大部分的冬季海冰都将完全消失,会对南极半岛西部的生态系统和生物种群造成严重的影响。海冰减少可能也是造成磷虾数量下降的原因之一66。由于南极半岛西部是重要的磷虾繁殖地,当地磷虾数量的下降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南大洋地区67。另外,这一地区
帽带企鹅(chinstrap penguin)与阿德利企鹅的数量也在急剧减少,其原因可能与磷虾数量下降有关68。与此同时,南大洋磷虾捕捞业(主要在南极半岛附近海域作业)却取得了近二十年来最大的丰收69,其捕获量甚至还有可能进一步提高。
渔业对生态系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而气候变化又使得栖息地的面积不断下降,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对当地的鸟类与哺乳动物产生强烈的冲击。要在未来抵御住这样的冲击,我们就需要扩大和连接起南极半岛西部原有的几个保护区域,建立起新的海洋保护区和禁捕海洋保护区。AOA计划对这一地区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以明确最具保护价值的区域。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 15
威德尔海
威 德 尔 海 是 南 极 洲 东 西 部之间一片广袤而深邃的海湾。部分得益于威德尔环流(Weddell Gyre,庞大的龙尼-菲尔希纳冰架北边的一个巨型顺时针环流)的影响,这一地区生意盎然。冰架北边的海面往往漂满海冰,这就为磷虾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也为哺乳动物、鱼类和海鸟提
威德尔海
供了良好的捕食场所。威德尔海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从浅海大陆架直至深海区域,到处都是生命的痕迹,每次取样探险都能发现数十种新物种。威德尔海深海区独特而多样的生态环境尚未遭受人类的破坏,建立大型的海洋保护区能够保护该地区的深海生物多样性,确保磷虾和大型肉食动物的数量持续增加。
威德尔海域也是磷虾和各种捕食磷虾的肉食动物的栖息地。然而气候变化使得这一地区的气温不断上升,有可能扰乱当地以冰为基础建立起的生态环境。海冰的变化对于磷虾和食
蟹海豹来说尤其致命。食蟹海豹的整个生活史都需要以浮冰为基础展开。威德尔海拥有多样化的栖息地,其中包括菲尔希纳海槽(Filchner Trough)。该海槽是威德尔海大陆架上最深的区域。
把威德尔海纳入南大洋海洋保护区与禁
捕海洋保护区网络可以有效保护当地生活的
各种濒危动物,包括许多鲸类以及马氏深海
鳐(McCain’s skate)。同时,这种做法
也能保护当地丰富的海底生物资源以及在尚
未开发的威德尔海西部海域生活的各种未知
生物70。随着南极半岛西部海域温度的持续升
高,威德尔海大陆架及深海区域生活的各种
动物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建立海洋保护区
刻不容缓。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 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16
南斯科舍海地区:
沿斯科舍岛弧(Scotia Sea Arc)南侧分布的南奥克尼群岛为许多鸟类、哺乳动物、鱼类以及无脊椎动物提供了重要的繁殖与觅食场所。这一地区十分富饶,拥有丰富的深海生物多样性,鱼类种类繁多,并且是鲸类的季节性捕食地。
南 乔 治 亚 岛 是 斯 科 舍 海 上 的一个亚南极岛。虽然只有170公里长,这座岛上却孕育着大量的野生动植物,包括四百多万只海狗和上百万只海鸟。南乔治亚岛周围的水域同样生机盎然,生活着许多的浮游生物和磷虾,为岛上的鸟类与哺乳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研究表
明,南乔治亚岛周围的海床上生活着很多种类的动物,而且很多动物都是本地特有的物种。
南 桑 威 奇 群 岛 ( S o u t h Sandwich Islands)位于斯科舍海最东端,是本地区群岛中最偏远、最崎岖的一个。尽管自然条件严苛,南桑威奇群岛却为全世界近三分之一的帽带企鹅提供了繁殖场所 。这片群岛同时也是许多海鸟、海豹以及其他种类的企鹅繁殖的场所71,而在群岛周围水域的大型磷虾
聚集地觅食的动物数量则要更多72。在这片水域里,大型食肉动物在海面附近捕食,海底则由各种各样的鱼类所占据。最近,研究者在群岛西部的深海中还发现了一批神奇的热液喷口生物群。
两个多世纪以来,这一地区捕猎鱼类、鲸类和海豹的活动一直十分活跃,致使当地鱼类、鲸类和海豹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同时,渔业间接捕获和杀死了大量鸟类,因而也造成了鸟类数量的下降。现在,海豹和鲸类的数量正在持续恢复。然而,自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过度捕捞之后,南奥克尼群岛附近海域的鲭冰鱼、驼背鲈(humped rockcod)和花纹南极鱼的数量却一直没有能够恢复起来73,而该地区针对磷虾、巴塔哥尼亚犬牙鱼以及鲭冰鱼的捕捞活动仍旧还在继续。
考虑到本地区丰富的资源,英国提出在南奥克尼群岛以南建立一个海洋保护区。这一提议在2009年获得通过。南奥克尼群岛成为了CCAMLR南大洋海洋保护区网络中的第一个禁捕海洋保护区。另外,英国还提出在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群岛建立海洋保护区,将每个岛周围的水域划定为禁捕区。然而这一提议没有得到CCAMLR的支持,一些国家也就英国的提议提出了反对意见。
地球上几乎没有任何地方的顶级捕食者数量能与南乔治亚地区相媲美。要确保这几个硕果仅存的生态系统继续发展壮大,我们就需要采取大胆的行动。AOA计划对这一地区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以明确最具保护价值的区域。
南奥克尼群岛
南乔治亚岛
南桑威奇岛弧
冰鱼幼鱼 图片来源: Uwe Kils / wikimedia commons.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 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18
毛德海隆
毛德海隆
毛德海隆是位于南大洋大西洋扇区南部的一个洋中海台,海拔从海平面以下3000米抬升至海平面以下1000米。毛德海隆上方海冰较少,形成了一个冰间湖(一片开放水域),因而与周围地区形貌迥异。南大洋大部分的冰间湖都与南极大陆相邻,开放海
域反复出现的冰间湖只有两个,毛德海隆上方的冰间湖就是其中之一74。毛德海隆地区生物资源丰富,拥有大型的磷虾聚集地、独特的海底生物以及为数众多的鱼类、海鸟和哺乳动物。最新研究表明,在各种海洋学因素、海底地形因素以及海冰的相互作用下,毛德海隆地区的生态系统与南大洋其他地区的生态系统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独立于周围地区之外。
随着越来越多的时间与资源投入,毛德海隆对于南大洋生
南极的被囊动物 图片来源: Cassandra Brooks.
态系统的重要性以及该地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毛德海隆海域海冰较少,并且还形成了一个反复出现的开放海域冰间湖,这在南大洋是十分罕见的。这样的环境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而又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同时,这片远洋区域又在威德尔环流的影响下与大西洋盆地紧密相连。把毛德海隆纳入南大洋海洋保护区与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可以有效保护该地区独特的海洋景观与生物多样性。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 19
布韦岛
豹形海豹 图片来源: Cassandra Brooks.
布韦岛
布韦岛是世界上最为偏远的一个岛75,也是大西洋中脊上最靠南的一个火山岛76。这座岛面积不大,大部分地区被冰川覆盖。它距离南极大陆1600公里,距离好望角2600公里。尽管地处偏远,布韦岛及其附近水域却生活着南
大洋地区绝大部分的主要动物种群,包括象海豹、海狗、长冠企鹅(macaroni penguin)、帽带企鹅和巨海燕(giant petrel)77。水面以下的世界则由巴塔哥尼亚犬牙鱼、磷虾以及各种深海动物所占据78。在布韦岛周围的大陆架和大陆斜坡上发现的鱼类物种有将近20个,包括巴塔哥尼亚犬牙鱼、长尾鳕(grenadier)以及一种遗传基因十分特别的灰石斑鱼。这里也生活着大量的南极磷虾,它们为各种海鸟及哺乳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由于布韦岛位置偏僻,科学家们对其海底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但当地独特的海底生态环境可能已经受到了多钩长线捕鱼的影响。
意识到布韦岛的生物价值与独特意义之后,挪威(布韦岛是其附属地)在1971年宣布将该岛及其附近12海里的水域划定为自然保护区。然而在保护区以外,针对巴塔哥尼亚犬牙鱼和南极犬牙鱼的商业捕捞仍在继续,并有可能将磷虾也纳入捕捞范围。当地企鹅的数量也在下降,因而我们有必要采取紧急行动,保护企鹅的觅食场所,确保企鹅的食物供给不受影响。对布韦岛周围海域的保护将是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的重要一环。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 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20
德尔卡诺-克罗泽地区
德尔卡诺-克罗泽地区海域图
鄂毕-勒拿海底斜坡是南大洋上印度洋扇区南部的两个海底高原。自从南大洋捕鱼业兴起以来,这两个区域的捕鱼活动就一直十分活跃。人们一开始捕捞的主要是灰石斑鱼。近年来,巴塔哥尼亚犬牙鱼也成为了主要的捕捞对象。我们对于鄂毕-勒拿海底
斜坡的了解大多来自于渔业及其相关研究。长期以来的IUU捕捞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本地区鱼类的种群数量。本地区不仅是重要的巴塔哥尼亚犬牙鱼产区,也是许多哺乳动物及其他野生动物觅食的场所。
德尔卡诺隆起(Del Cano Rise)是印度洋西南部的一个深海高原。由此往西是南非的爱德华王子群岛(Prince Edward Islands),往东是法国的克罗泽群岛(Crozet Islands)。德尔卡诺隆起处在这两大群岛之间的中轴上,为在岛上进行繁殖的海
鸟与海豹提供了重要的捕食场所79。南非业已提出在爱德华王子群岛周围的专属经济区(EEZ)内设立海洋保护区,法国也有可能扩大其在克罗泽群岛专属经济区内的海洋保护区范围。但德尔卡诺隆起上方的大部分海域都属公海,这一重要的动物觅食场所并没有得到保护,仍然处于危险之中。保护好德尔卡诺
鄂毕-勒拿海底斜坡 德尔卡诺地区公海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 21
王企鹅幼鸟群 图片来源: John B. Weller.
南大洋的虎鲸 图片来源: © Greenpeace / Daniel Beltrá.
海底的海星和底冰 图片来源: John B. Weller.
地区可以使数百万哺乳动物及鸟类的栖息地免受破坏80,其中包括许多濒危或近危的信天翁种群81。
由于过度捕捞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鄂毕-勒拿海底斜坡海域现已全面禁止捕捞有鳍鱼类。对灰石斑鱼的捕捞始于从二十世
纪七十年代,每年的捕捞量高达30000吨,这使得灰石斑鱼的种群数量迅速下降。到了八十年代,CCAMLR接管了当地渔业的管理工作,并且立刻对灰石斑鱼的捕捞上限做出了限制。到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当地的捕鱼活动就被完全禁止了。尽管已经禁渔了十五年,灰石斑鱼的数量却仍然没有能够恢复。针对巴塔哥尼亚犬牙鱼的合法捕捞是从1997年开始的,但非法捕捞者很快也注意到了这一区域。由于捕捞量太大,合法捕捞在2002年被叫停,但IUU捕捞可能仍然存在。
在CCAMLR禁渔工作的基础之上,我们还应将鄂毕-勒拿
海底斜坡纳入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加以保护。目前,爱德华王子群岛和克罗泽群岛已经成为了自然保护区,每年去那里繁殖的数百万只鸟类及哺乳动物因此得到了保护。然而群岛周围的水域,包括富饶的德尔卡诺隆起地区及西南印度洋中脊上方海域,都是重要的捕食场所,因而也应一并加以保护。
南非与法国的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科学家正在开展各项合作,保护爱德华王子群岛及克罗泽群岛周边的水域。认识到了德尔卡诺隆起的价值以后,这些机构与个人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愿意与CCAMLR一道进一步加强对这片公海区域的保护82。将德尔卡诺隆起纳入到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有助于保护在此繁殖的各种海豹、企鹅和海鸟,包括十二种濒危或近危的信天翁83。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 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22
克尔格伦公海地区:
近摄灯笼棘鲛的眼睛,虽然此图摄于大西洋,但此物种在亚南极的海域非常丰富 图片来源: David Shale/naturepl.com.
冰山上的巴布亚企鹅 图片来源: John B. Weller.
克尔格伦海底高原(Kerguelen Plateau)独特的地理特征造就了当地生机勃勃的生态环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以及庞大的顶级捕食者种群。尽管这一地区捕猎鱼类、海豹以及鲸类的活动十分活跃,当地的海洋生物数量却仍然十分可观,而且不断还有新的物种为人们所发现。在克尔格伦高原的生态系统中,浮游生物的数量十分庞大,因此该地区的物产十分富饶而多样。也正因为如此,当地的鱼类和哺乳动物资源经历了长期的过度捕捞,致使海狗在当地完全绝迹,座头鲸(humpback)与南露脊鲸(southern right whale)的数量也至今尚未恢复。
班 扎 尔 海 底 斜 坡 位 于 克 尔 格 伦 高原南部,有着与克尔格伦高原其他地区类似的野生动物种群,是巴塔哥尼亚犬牙鱼和南极犬牙鱼的主要栖息地之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班扎尔海底斜坡可能是一种特殊种群南极犬牙鱼的产卵地。本地区的大型鱼类资源比较丰富,因而也就成为了各种合法捕捞船队及IUU捕捞船队经常光顾的渔场。这些船队在作业过程中往往会间接捕获一定数量的鳐鱼和长尾鳕。尽管本地区的商业捕捞活动只是从近几年才开始的,但犬牙鱼的数量还是因此大为减少。现在,除科学研究以外,针对犬牙鱼的多钩长线捕
鱼已被完全禁止。但IUU捕捞有可能还在继续。鉴于班扎尔海底斜坡对于犬牙鱼的重要意义,我们有必要将其纳入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来加以保护。
克 尔 格 伦 产 区 ( K e r g u e l e n Production Zone)是一片物产丰富的开放水域。它位于克尔格伦高原的东北偏东方向,东南印度洋中脊系统的南部。这一地区正好处在南极辐合带与南极绕极流的线路上,底端是一片崎岖不平的深海栖息地,生活着大量的乌贼和鱼类。这些鱼和乌贼为迁徙过程中行经
克尔格伦高原公海地区
班扎尔海底斜坡
克尔格伦产区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 23
克尔格伦公海地区海域图
南大洋的冰山 图片来源: John B Weller.
此地的鲸和海鸟提供了食物。同样以此为食的还有许多陆地上的捕食者。这些捕食者的捕食范围包括附近的克尔格伦高原、赫德岛(Heard Island)和麦克唐纳群岛(McDonald Islands)。国王企鹅(king penguin)、南极海狗和象海豹对克尔格伦产区的依赖程度特别高84。
法国对克尔格伦群岛、澳大利亚对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拥有领土主权,因而克尔格伦高原的大部分地区都不在CCAMLR的管辖范围内,而是处于这两个国家各自的专属经济区内。法国和澳大利亚都已在各自的领土范围内开辟了海洋保护区。其中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周围的保护区范围达到了65000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保护区之一。这一保护区覆盖了澳大利亚在当地的整个领海范围(离岸12海里以内的海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海底生物种群 。法国的保护区则包括克罗泽群岛周围的全部领海(不属于克尔格伦高原)以及克尔格伦群岛领海的大部分地区85。对于本地区的海洋保护区建设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除了上述这些措施以外,我们还应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新的保护措施不仅能够保护那些尚未研究的区域,还能保障动
物的栖息地及觅食场所不受侵扰,从而帮助那些种群数量严重下降的鱼类、海鸟及海洋哺乳动物休养生息。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海洋保护区是在2002年建立的,东临克尔格伦产区。克尔格伦产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多样的海底特征使其拥有了极为丰富的物产,成为了鸟类、哺乳动物和鱼类的生命之源。对克尔格伦高原公海地区的保护范围应当包括克尔格伦产区,克尔格伦群岛、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南边的班扎尔海底斜坡以及西边的公海地区。这些区域共同构成了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的重要一环。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 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24
与海豹同潜 图片来源: John B. Weller.
南极东部大陆架南极大陆东部沿海地区居住着数百万的海豹和海鸟。尽管
关于这一地区的资料十分有限,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本地区为大量的企鹅、海燕以及食蟹海豹提供了捕食与繁育的场所,意义十分重大。对现有资料的分析表明,南极大陆东部有着许多独特而多样的海底生态区87。保护好这些地区能够确保当地各种栖息地及捕食地的现有状态不被打破。这些地区也可以为研究气候变化的科学家提供参照,帮助他们衡量在没有人为因素对生态系统加以干扰的情况下气候变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88。
澳大利亚提交给CCAMLR的分析表明,南极东部大陆架上很多地区的物理及生物特征各不相同。这些地区被分别命名为Gunnerus、Enderby、Prydz、Drygalski、Wilkes、MacRobertson以及d’urville Sea-Mertz89。作为一个整体,这些地区拥有许多独特的海底和深海景观,包括大陆架深海生态系统、大陆脊、软体动物生物多样性“热点”、海底山、峡谷以及一个很可能是幼年磷虾繁育场的地区90。这里的南极磷虾吸引了大批的雪海燕、食蟹海豹和企鹅。至少有5000对帝企鹅(emperor penguin)在此繁殖后代,上万只帝企鹅在此地区栖息91。
与南大洋其他地区相比,我们对南极大陆东部地区的研究并不充分,但澳大利亚与法国业已提出在此地区建立一系列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澳法两国提议对现已发现的许多不同种类的海底生物区加以保护92。提议所涉及的保护范围还包括几个潜在的育幼场。犬牙鱼、磷虾和其他种类的冰鱼可能在这些地区哺育后代。AOA建议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加强保护措施。在澳法两国提议的范围之外,AOA又追加了几处南极大陆东部的地区和景观,希望将它们纳入一个全面的网络来加以保护。这里提到的景观包括Cosmonaut冰间湖等几个重要的冰间湖、一片向北延伸到普里兹湾(Prydz Bay)的开阔地(此处有一个独特的海槽口扇状区以及若干峡谷)、南极大陆东部边界附近的海底山以及陆缘高原。加入这些地区可以更好地保护南极大陆东部某些独特的生态系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Cosmonaut冰间湖和其他几个冰间湖都是物产十分丰富的地区;保护好这些冰间湖有助于防止重要的觅食场所遭到破坏。
海底山地区往往生活着丰富的生物种群,d’Urville Sea-Mertz地区东部的海底山理应得到更多的保护。另外,AOA建议扩大现有的保护面积,从而更加全面地保护阿德利企鹅、帝企鹅、食蟹海豹、豹斑海豹和象海豹的觅食场所。更多的海底及远洋区域也应一并加以保护。上面所提到的某些区域还具有潜在的科学价值,可以作为观察气候变化的指针;同时,当某些物种因气候变化的影响而流离失所时,这些区域也可以为它们提供庇护93。南极大陆东部的犬牙鱼数量并不丰富,不管是合法捕捞还是IUU捕捞都能造成这种鱼类的迅速消亡。这也更加有力地说明,这片水域应当被纳入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来加以保护94。AOA即将出台的报告将专门阐述关于南极大陆东部地区(包括上面提到的这些需要保护的地区)的某些具体问题。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 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26
印度洋海底环境海域图
印度洋海底环境是指东经150°至70°、南纬60°至55°的广大区域,包括太平洋-南极海岭系统的西部边缘以及澳大利亚-南极海盆的大部分地区。在这片广大的区域中,有四个地区拥有特别独特而多样的海底栖息地,它们对于南大洋的生物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95。
这四个地区是North Mertz、南印度洋海盆、North Drygalski和东印度洋海底山。其中,North Mertz有着形形色色
印度洋海底环境
的海岭与海底山;南印度洋海盆的水温比其他深海海盆要高;North Drygalski拥有该地区唯一的一条海槽;东印度洋海底山是其所处海盆中的唯一海底山,有可能蕴藏着世界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新物种。
North Mertz、南印度洋海盆、North Drygalski和东印度洋海底山有着很大的潜在价值,应当纳入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和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来加以保护。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 27
罗斯海地区:
从太空拍摄的罗斯海的海藻 图片来源: NASA.
AOA认为包括巴雷尼群岛、太平洋海底山以及罗斯海湾在内的罗斯海地区是一块十分重要的区域,必须加以保护。罗斯海是南极锋以南最大的大陆架生态系统96。虽然罗斯海的面积只占到南大洋总面积的2%,但那里的生物多样性却要比南极大部分其他地区都要丰富得多97。当地的生态系统具有很多特质,而且较少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因此有人将这里称为生物多样性“热点”。可见,罗斯海是南大洋上极其具有生态学重要性的一个区域。
罗斯海的生态系统并未受到人类破坏,这一点十分罕见。一些最为人们所熟知也最富魅力的南极物种大多就生活在这一地区,其中至少包括98:
• 全世界38%的阿德利企鹅• 全世界26%的帝企鹅• 全世界30%以上的南极海燕• 全世界6%的南极小须鲸(Antarctic Minke whale)• 南太平洋45%的威德尔海豹• 全世界50%的罗斯海虎鲸(C型)
处于罗斯海食物链最顶端的鱼类掠食者是南极犬牙鱼。这种鱼在罗斯海生态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其他生态系统中鲨鱼所扮演的角色比较类似。尽管人们已经对这种鱼的生理构造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但关于其生活史的许多细节问题还是没有能够得到确证。人们从未见过这种鱼的鱼卵、鱼苗或是幼鱼。从我们有限的知识来看,南极犬牙鱼可能是冬春季节在太平洋-南极海岭附近产卵。鱼卵可能在罗斯海环流的作用下朝几个方向移动:向西去往巴雷尼群岛,向南去往罗斯海大陆架,或者向东去往南极大陆东部的大陆架和大陆斜坡99。当个头长到一定大小时,半成年的南极犬牙鱼会游到大陆架地区生活;在那里成年之后,它们又会游回深海地区,开始新一轮的循环100。南极犬牙鱼的寿命很长,最高可达50年。它们的成年时间在17岁左右。这种鱼的身形也很大,体长可达175厘米,体宽可达80厘米。但南极犬牙鱼可能并不会每年都产卵,再加上它们到达成熟期所需经历的时期较长,这就使得它们在过度捕捞面前显得尤为脆弱。
罗斯海
太平洋海底山
巴雷尼群岛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 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28
罗斯海地区海域图
南方信天翁 图片来源: John B. Weller.
磷虾是罗斯海地区许多顶级捕食者的主要捕食对象,也是当地食物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透明鳞虾生活在罗斯海大陆架上方的浅海区,以浮游植物为食。Euphausiatriacantha是另一种种类的磷虾。它们生活在罗斯海大陆架北部水温更低、水深更深的地区。南极磷虾则大量生活在罗斯海大陆架坡折沿线、海槽外部和巴雷尼群岛周围。
罗斯海最特别的一点在于它拥有一群种类齐全而又未受破坏的顶级捕食者,包括大型的鱼类、鸟类、海豹和鲸101。作为地球上人类影响最小的一块海洋地带102,罗斯海可以作为一个天然的实验室,供科学家研究气候变化的影响和海洋物种的进化,了解大型生态系统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是如何运行的103。这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知识,帮助我们了解生态系统的运行模式,探索如何将人类的影响降到最小。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 29
小须鲸 图片来源 John B. Weller.
针对罗斯海地区,AOA提议建立一个能够提供全方位保护的海洋保护区,其面积大约为三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这一提议的科学依据来自于各国科学家、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在过去五年所做的研究。这些研究清楚地揭示了本地区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意义。鉴于本地区重要的环境和科学价值,现在已有超过500名科学家发表声明,支持对罗斯海地区重要的栖息地加以保护。这些栖息地包括整个大陆斜坡和大陆架区域。
AOA关于建立海洋保护区的提议旨在对大型生态系统的全过程都加以切实的保护。这就包括:
1. 保护与罗斯海环流相关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过程。
2. 保护与南极犬牙鱼(本地区的顶级鱼类捕食者)生活史各阶段关系密切的地区,包括其觅食和产卵的场所。
3. 保护重要的地理景观,包括太平洋-南极海岭地区的海底山、海岭和海槽。保护与之相关的生命形式。
4.加大保护力度,以推进和加强长期资料库建设。有了完善的资料库,很多重要的研究才能得以进行,从而帮助我们了解生态系统运行与环境变迁方面的情况。我们由此也可以更好地认识气候变化的影响,特别是海洋酸化的问题。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比如罗斯海大陆架和大陆斜坡、巴雷尼群岛、太平洋-南极海岭以及斯科特海底山。
6. 保护罗斯海地区作为气候变化指针与冰川物种避难所的功能。
处 于 上 层 营 养 级 的 动 物 ( 比 如 企鹅、犬牙鱼和威德尔海豹)每年的生命循环会覆盖整个罗斯海大陆架以及大陆斜坡地区。AOA关于罗斯海的提案考虑到了这一问题。我们对各国现有的海洋保护区提案进行了分析,发现如果能够综合新西兰与美国的提案,并对其加以拓展与提升,那么我们就可以为罗斯海这片重要、独特而珍贵的生态系统提供切实的保护。
阿蒙森海和别林斯高晋海
阿蒙森海与别林斯高晋海是两片难以接近而又富于变化的神秘地带。这两片海域离研究船队停靠的海港比较远,而当地的海冰情况又十分复杂,因此它们就成为了南大洋上人迹最为罕至的地区之一。同时,气候变化也正改变着当地的环境。这两片海域与极不稳定的南
极西部冰盖相邻,冰川消融正愈演愈烈,其中以阿蒙森海的松岛冰川最为严重。从防患于未然的角度做好这一地区的保护工作,科学家们就能更加深入地了解当地各种相互交织的变化过程。随着南极大陆西部气温的上升,这些变化不仅已经发生,而且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虽然我们对这一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知之甚少,但从最近的海底生物种群调查中可以看出,阿蒙森海96%的甲壳纲等足目动物都是全新的物种104。阿蒙森海域生活的海鸟主要是帝企鹅、阿德利企鹅和雪海燕,除此之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南极海燕、蓝鹱(blue petrel)和鸽锯鹱(Antarctic prion)105。对当地鲸类的调查则表明,虎鲸和小须鲸是当地最常见的鲸类,其中小须鲸的数量最多106。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 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30
阿蒙森海和别林斯高晋海域图
海星 图片来源: John B. Weller.
阿蒙森海与别林斯高晋海严酷的海冰环境使得当地几乎难以开展任何形式的商业捕捞。阿蒙森海的大部分地区都处在禁渔区内,但别林斯高晋海却有一小块地区处于磷虾捕捞场内。随着海冰环境的改变,这些地区的捕捞活动可能会逐渐抬头,而某些磷虾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比如别林斯高晋海大陆架上方水域)则会首当其冲107。
最近,英国提出应当从预防的角度出发,把阿蒙森海、别林斯高晋海以及其他一些地区冰架以下的水域划定为禁捕海洋保护区,以防止冰架垮塌108。英国知道,冰架垮塌会造成一系列的改变,导致该地区被附近的物种所占据,甚至遭受其他遥远地区物种的入侵109。如果能将人类活动挡在这一地区之外,科学家就能对上述这些变化有一个更好的认识110。CCAMLR已在阿蒙森海上划出了一片“脆弱海洋生态系统”(Vulnerable Marine Ecosystem, VME);在此基础上再建立一个海洋保护区将此VME涵盖其中,总的保护力度就能获得大幅提升。将阿蒙森海与别林斯高晋海纳入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可以使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赶在人类活动大规模进入以前得到充分的研究。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 31
彼得一世岛海域图
彼得一世岛 图片来源: John B. Weller.
ⓒ ⓒⓒⓒⓒⓒⓒⓒ 2012
彼得一世岛彼得一世岛是别林斯高晋海上距离南极大陆450公里的一个火
山岛。该岛几乎完全被浮冰所环绕。岛上生活着少量的海鸟和海豹。由于缺少针对该地区的科学研究,我们对彼得一世岛周围水域的情况所知不多。但这一水域似乎蕴藏着独特的生态景观,包括各种海底山、岛屿生境以及特有的远洋环境。从仅有的几次针对该地区的科考活动所取回的海水样本来看,当地无脊椎动物种类多样,鱼类数量可观。挪威对彼得一世岛拥有主权主张,岛上环境因此受到保护,但该岛周围的水域却不在保护范围之内。本地区有着大量的海鸟、鲸类、海豹以及许多种类的鱼类,包括拉森氏拟南极鱼(painted notie)和南极犬牙鱼。
对彼得一世岛周围的水域加以保护不仅可以覆盖到许多的海底物种及远洋物种,还能保护到当地独特的区域景观,为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的建设增砖添瓦。Belgica和Lecointe这两个平顶海底山是十分罕见的景观,那里有可能生活着某些特有的物种。浅海底山的地理分布十分有限,我们有必要对这一地区加以全面保护。如果将保护范围从彼得一世岛朝向南极大陆的一侧延伸至CCAMLR的南纬60°边界附近,那么上述的这些景观就都能涵盖在内。扩大后的保护区域还将覆盖阿蒙森海近海水温较高地区的海底栖息地以及太平洋海盆中的生态区111。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 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32
结论: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
南极海洋联盟以现有的科学依据为基础,提出南大洋有40%以上面积的区域应当被纳入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来加以保护。这些区域涵盖了现有的海洋保护区、以往策划与分析所确定的地区以及本报告新提出的重要环境栖息地。我们所识别出的19个地区能够从物种、栖息地以及生态系统的水平形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保护网络。这些地区中甚至还包括了当今世界上受人类活动影响最小的几处海洋生态系统(在威德尔海和罗斯海)。由这些地区组成的网络可以保护南大洋众多捕食动物的繁殖与觅食场所。另外,水层物种所面临的威胁正日益增大,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可以为这些物种提供一个庇护所。尽管我们现有的知识水平还很有限,对提议所涉及的许多地区都还不是十分了解,但AOA还是认为应当从预防的角度出发对这些地区加以保护,以存续独特的生态系统和尚未发现的生物多样性。在某些地区,保护好那些曾经遭受过过度捕捞的鱼和哺乳动物可以促使它们的数量进一步恢复。在另一些地区,保护好犬牙鱼及其他鱼种的产卵地则可以保障这些物种长期的生存与安全。
我们知道,海洋保护区网络的最终确立需要经过漫长的国际讨论与磋商,因此本报告并不是针对上述所有地区的最终提案。但就上面提到的某些地区而言,本报告所持的立场是不容退让的。这份报告同时也对几个重要的栖息地进行了概述,以供讨论。AOA会继续与CCAMLR各成员国及其科研机构展开合作,进一步探索适当的途径,对所有这些独特而珍贵的生态系统加以妥善保护。我们的目标是将南大洋40%以上面积的地区都纳入到海洋保护区及禁捕海洋保护区网络之中。
AOA寻求保护南大洋重要的大型海洋生态系统进程。这就包括对以下要素的保护:
1. 广泛而又富于代表性的一系列栖息地和生态系统;2. 南大洋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过程;3. 包括海底山、海岭和海槽在内的重要地貌景观;4. 些有助于搜集和存续长期资料的地区。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之上,关于生态系统运行与环境变迁的重要研究才能得以进行,探究气候变化的影响、海洋的酸化等问题;5. 本地区特有物种(比如本地区的顶级鱼类捕食者犬牙鱼及其他捕食者)生活史各阶段所涉及的重要地区;6. 上层营养级动物(比如帝企鹅、阿德利企鹅、巴布亚企鹅、食蟹海豹、威德尔海豹和南极海狗)的繁殖和捕食场所;7. 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8.几个发挥着气候变化指针与冰川物种避难所作用的重要地区,如罗斯海和南极大陆东部大陆架;9. 经历长期过度捕捞之后正处于恢复状态的鲸、海豹和鱼类种群;
致谢 南极海洋联盟感谢所有对此报告作出贡献的人,包括报告的作者团队、参引团队、采访团队和研究助理团队:Cassandra Brooks、Anna Cameron、Blair Palese、Barry Weeber、Steve Campbell、Amanda Sully、陈冀俍、王海博、周薇、Alex Wong
翻译:关晓宇
排版:詹育锋
地图:The Centre for Conservation Geography (CCG)。非常感谢由WWF英国和 WWF 瑞典的 海洋项目资助、由WWF和 CCG原创的AOA“19个地区地图”。由Arc Visual Communications设计。
数据与分析:AOA对本报告所参引的科学家以及为本报告做出贡献的CCAMLR成员国政府表示敬意与感谢。
照片:大部分的照片都是由John B. Weller、Cassandra Brooks、David Shale、Daniel Beltrá、Roger Grace、Uwe Kils、Richard Williams、Steve Morgan、Lara Asato、Darci Lombard、Jiri Rezac慷慨提供的。
封面照作者John B. Weller
本报告采用再生纸打印。
©南极海洋联盟 2012
10. 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比如南极半岛西部地区;11. 受人类活动影响最小的结海洋生态系统,包括罗斯海和威德尔海。
中国是考虑扩大南大洋渔业的国家之一,如果CCAMLR想要建立南大洋海洋保护区网络,来维持那里依旧繁荣、独特而完整的生态系统,那么中国的领导力将至关重要。AOA希望能和中国政府共同努力,支持大规模禁捕保护区和海洋保护区网络的建立,来确保对南大洋及其众多物种的长期保护,包括AOA倡议的在罗斯海建立一个360万平方公里受到全面保护的禁捕保护区。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 33
后注1. Antarctic Ocean Alliance. 2012. Antarctic Ocean Legacy – A Marine
Reserve for the Ross Sea.
2. IUCN. 2003. World Parks Congress Recommendation 22: Building a global system of marine and coastal protected area networks.
3. Constable AJ, B Raymond, S Doust, D Welsford, P Koubbi, and AL Post. 2011. Identifying 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 in data-poor regions to conserve biodiversity and to monitor ecosystem change: an Antarctic case study. WS-MPA-11/5. Hobart: CCAMLR; Douglass LL, D Beaver, J Turner and R Nicoll. 2011. An identification of areas within the high seas of the Southern Ocean that would contribute to a representative system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Submitted to the CCAMLR Marine Protected Area workshop held in Brest, France in 2011. Document number: WS-MPA-11/16; Douglass LL, J Turner, HS Grantham, S Kaiser, R Nicoll, A Post, A Brandt, and D Beaver. In press. A hierarchical classifcation of benthic biodiversity and assessment of protected areas in the Southern Ocean. PLoS One; Lombard AT, B Reyers, LY Schonegevel, J Cooper, LB Smith-Adao, DC Nel, PW Froneman, IJ Ansorge, MN Bester, CA Tosh, T Strauss, T Akkers, O Gon, RW Leslie, and SL Chown. 2007. Conserving pattern and process in the Southern Ocean: designing a Marine Protected Area for the Prince Edward Islands. Antarctic Science 19(1): 39-54; Antarctic Ocean Alliance 2012.
4. Australian Antarctic Division. 2012. Crabeater seals. Accessed on April 29 2012 from http://www.antarctica.gov.au/about-antarctica/wildlife/animals/seals-and-sea-lions/crabeater-seals.
5. Halpern BS, S Walbridge, K Selkoe, CV Kappel, F Micheli, C D’Agrosa, JF Bruno, KS Casey, C Ebert, HE Fox, R Fujita, D Heinemann, HS Lenihan, EMP Madin, MT Perry, ER Selig, M Spalding, R Steneck, and R Watson. 2008. A global map of human impact on marine ecosystems. Science 319(5865): 948-952.
6.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07.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 Stammerjohn SE, DG Martinson, RC Smith, X Yuan, and D Rind. 2008. Trends in Antarctic annual sea ice retreat and advance and their relation to El Nino–Southern Oscillation and Southern Annular Mode variability.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13: C03S90; Meredith MP and JC King. 2005. Rapid climate change in the ocean west of the Antarctic Peninsula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2: L19604.
8. Turner J, SR Colwell, GJ Marshall, TA Lachlan-Cope, AM Carleton, PD Jones, V Lagun, PA Reid, and S Iagovkina. 2005. Antarctic climate change during the last 50 yea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matology (25): 279-294.
9. Stammerjohn et al. 2008.
10. Thompson DWJ, S Solomon, PJ Kushner, MH England, KM Grise, and DJ Karoly. 2011. Signatures of the Antarctic ozone hole in Southern Hemisphere surface climate change. Nature Geoscience 4: 741-749.
11. The National Snow and Ice Data Center. 2010. Ice Shelve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Accessed September 1 2011 from http://nsidc.org/sotc/iceshelves.html.
12. Rignot E. 2006. Changes in ice dynamics and mass balance of the Antarctic ice Sheet.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364: 1637-1655; Rignot E. 2008. Changes in West Antarctic ice stream dynamics observed with ALOS PALSAR data.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5: L12505; Shepherd AD, DJ Wingham, and E Rignot. 2004. Warm ocean is eroding West Antarctic Ice Sheet.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1: L23402.
13. Wingham DJ, DW Wallis, and A Shepherd. 2009.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Pine Island Glacier thinning, 1995-2006.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6: L17501.
14. Rignot E. 1998. Fast recession of a West Antarctic Glacier. Science 281: 549– 551.
15. Parkinson CL and P Gloersen. 1993. Global sea ice coverage. In Atlas of satellite observations related to global change, RJ Gurney, JL Foster, and CL Parkinson,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71–383.
16. Stammerjohn et al. 2008.
17. de la Mare WK. 2009. Changes in Antarctic sea-ice extent from direct historical observations and whaling records. Climate Change 92: 461-493.
18. Atkinson A, V Siegel, E Pakhomov, and P Rothery. 2004. Long-term decline in krill stock and increase in salps within the Southern Ocean.
Nature 432:100-103.
19. Smetacek V, R Scharek, and EM Nöthig. 1990. Seasonal and regional variation in the pelagial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life cycle of krill. In Antarctic Ecosystems, Ecological Change and Conservation, KR Kerry and G Hempel, eds. Berlin: Springer-Verlag. Pp 103-114.
20. Forcada J, PN Trathan, PL Boveng, JL Boyd, JM Burns, DP Costa, M Fedak, TL Rogers, and CJ Southwell. In Press. Responses of Antarctic pack-ice seals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increasing krill fishing.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1. Stammerjohn et al. 2008.
22. Arrigo KR and GL van Djiken. 2003. Phytoplankton dynamics within 37 Antarctic coastal polynya systems.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08(C8): 3271.
23. Penguin Science. 2012. Antarctic penguins: Bellwether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Accessed on April 29 2012 from http://www.penguinscience.com/clim_change.php.
24. Orr J, VJ Fabry, O Aumont, L Bopp, SC Doney, RA Feely, A Gnanadesikan, N Gruber, A Ishida, RM Key, K Lindsay, E Maier-Reimer, R Matear, P Monfray, A Mouchet, RG Najjar, GK Plattner, KB Rodgers, CL Sabine, JL Sarmiento, R Schlitzer, RD Slater, IJ Totterdell, MF Weirig, Y Yamanaka, and A Yool. 2005. Anthropogenic ocean acidification ove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d its impacts on calcifying organisms. Nature 437: 681-686.
25. Ibid.
26. Ibid.
27. Marschoff ER, ER Barrera-Oro, NS Alescio and DG Ainley. 2012. Slow recovery of previously depleted demersal fish at the South Shetland Islands, 1983-2010. Fisheries Research 125-126: 206-213; Croxall JP and S Nicol. 2004. Management of Southern Ocean Fisheries: global forces and future sustainability. Antarctic Science 16(4): 569-584.
28. Kock KH, K Reid, J Croxall, and S Nicol. 2007. Fisheries in the Southern Ocean: An ecosystem approach.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 of the Royal Society 362: 2333-2349.
29. CCAMLR. 1980. Text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See Article II.
30. Kock et al. 2007.
31. CCAMLR. 2002. Statistical Bulletin 14 (1992-2001). Hobart: CCAMLR. CCAMLR. 2011. CCAMLR Statistical Bulletin 23 (2001-2010). Hobart: CCAMLR.
32. Nicol S, J Foster, and S Kawaguchi. 2012. The fishery for Antarctic krill – recent developments. Fish and Fisheries 13: 30-40.
33. Kock KH. 2000. Understanding CCAMLR’s Approach to Management. Hobart: CCAMLR.
34. Kock et al. 2007.
35. Croxall and Nicol 2004.
36. Marschoff et al. 2012.
37. Kock K 2000.
38. Lack M and G Sant. 2001. Patagonian Toothfish – Are Conservation and Trade Measures Working? TRAFFIC Oceania.
39. Agnew D, D Butterworth, M Collins, I Everson, S Hanchet, KH Kock, and L Prenski. 2002. Inclusion of Patagonian toothfish Dissostichus eleginoides and Antarctic toothfish Dissostichus mawsoni in Appendix II. Proponent: Australia. Ref. CoP 12 Prop. 39. TRAFFIC East Asia, TRAFFIC East/Southern Africa-South Africa. TRAFFIC Oceania, TRAFFIC South America.
40. TRAFFIC. 2009. Australia confiscates 130 km long deepwater gillnet. Accessed April 25 2012 from http://www.traffic.org/home/2009/11/6/australia-confiscates-130-km-long-deepwater-gillnet.html.
41. Österblom H, UR Sumaila, Ö Bodin, HJ Sundberg and AJPress. 2010. Adapting to Regional Enforcement: Fishing Down the Governance Index. PLoS ONE 5(9): e12832.
42. TRAFFIC 2009.
43. CCAMLR Conservation Measures 22-06 and 22-07.
44. Ibid.
45. Ivar do Sul JA, DKA Barnes, MF Costa, P Convey, ES Costa, and L Campos. 2011. Plastics in the Antarctic Environment: Are we looking only at the tip of the iceberg? Oecologia Australis 15(1): 150-170.
46. The Antarctic Treaty System. 1991. The Protocol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the Antarctic Treaty.
47.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ntarctica Tour Operators. 2012.
后注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34
Accessed April 25 2012 from http://iaato.org/
48. Chown SL, AHL Huiskes, NJM Gremmen, JE Lee, A Terauds, K Crosbie, Y Frenot, KA Hughes, S Imura, K Kiefer, M Lebouvier, B Raymond, M Tsujimoto, C Ware, B Van de Vijver, and DM Bergstrom. 2012. Continent-wide risk assessmen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onindigenous species in Antarctic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doi:10.1073/pnas.1119787109
49. Lubchenco J, SR Palumbi, SD Gaines, and S Andelman. 2003. Plugging a Hole in the Ocean: the Emerging Science of Marine Reserves.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13(1): S3-S7.
50.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2. Agenda 21 Plan of Implementation, paragraph 32 (c).
51. Kock 2000; Kock et al. 2007.
52. CCAMLR. 2009. Report of the XXVIII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 Hobart: CCAMLR.
53. CCAMLR Conservation Measure 91-04.
54. Constable AJ and S Doust. 2009. Southern Ocean Sentinel – an international program to assess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marine ecosystems: report of a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Hobart, April 2009. ACE CRC,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and WWF-Australia: 4.
55. Gaines S, C White, M Carr, and S Palumbi. 2010. Designing marine reserve networks for both conservation and fisheries managemen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7(43): 18286-18293.
56. Ibid.
57. McCook LJ, T Ayling, M Cappo, JH Choat, RD Evans, DM De Freitas, M Heupel, TP Hughes, GP Jones, B Mapstone, H Marsh, M Mills, FJ Molloy, CR Pitcher, RL Pressey, GR Russ, S Sutton, H Sweatman, R Tobin, DR Wachenfeld, and DH Williamson. 2010. Adaptive management of the Great Barrier Reef: A globally significant demonstration of the benefits of networks of marine reserv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7(43): 18278-18285.
58. McLeod E, R Salm, A Green, and J Almany. 2009. Designing marine protected area networks to address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7: 362-370.
59. Griffiths HJ. 2010. Antarctic Marine Biodiversity –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distribution of life in the Southern Ocean? PloS ONE 5(8): E11683.
60. Nicol S. 2006. Krill, currents, and sea ice: Euphausia superba and its changing environment. Bioscience 56(2): 111-120.
61. Ducklow HW, K Baker, DG Martinson, LB Quetin, RM Ross, RC Smith, SE Stammerjohn, M Vernet, and W Fraser. 2007. Marine pelagic ecosystems: the West Antarctic Peninsula.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362: 67-94.
62. Turner et al. 2005.
63. Meredith and King 2005.
64. Cook AJ, AJ Fox, DG Vaughan, and JG Ferrigno. 2005. Retreating Glacier Fronts on the Antarctic Peninsula over the Past Half-Century. Science 308(5721): 541-544; CCAMLR 2011.
65.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Antarctic Research. 2011. Antarctic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 – 2011 Update.
66. Atkinson et al. 2004.
67. Forcada et al. In Press.
68. Trivelpiece WZ, JT Hinke, AK Miller, CS Reiss, SG Trivelpiece, and GM Watters. 2011. Variability in krill biomass links harvesting and climate warming to penguin population changes in Antarctic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8(18): 7625-7628.
69. Nicol et al. 2012.
70. Trivelpiece WZ, JT Hinke, AK Miller, CS Reiss, SG Trivelpiece, and GM Watters. 2011. Variability in krill biomass links harvesting and climate warming to penguin population changes in Antarctic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8(18): 7625-7628.
71. Convey P, A Morton, and J Poncet. 1999. Survey of marine birds and mammals of the South Sandwich Islands. Polar Record 35: 107-124.
72. Kasatkina SM, AP Malyshko, VN Shnar, and OA Berezhinsky. 2002. Characteristic of krill aggregations in the South Sandwich Islands sub-area in January – February 2000. CCAMLR Science 9: 145-164.
73. Ainley DG and LK Blight. 2008. Ecological repercussions of historical fish extraction from the Southern Ocean. Fish and Fisheries 9: 1-26.
74. Adams B, R Arthern, A Atkinson, C Barbante, R Bargagli, D Bergstrom,
N Bertler, R Bindschadler, J Bockheim, C Boutron, D Bromwich, S Chown, J Comiso, P Convey, A Cook, G di Prisco, E Fahrbach, J Fastook, J Forcarda, JM Gili, M Gugliemin, J Gutt, H Hellmer, F Hennion, K Heywood, D Hodgson, D Holland, S Hong, A Huiskes, E Isla, S Jacobs, A Jones, A Lenton, G Marshall, P Mayewski, M Meredith, N Metzl, A Monaghan, A Naveira-Garabato, K Newsham, C Orejas, L Peck, HO Pörtner, S Rintoul, S Robinson, H Roscoe, S Rossi, T Scambos, J Shanklin, V Smetacek, K Speer, M Stevens, C Summerhayes, P Trathan, J Turner, K van der Veen, D Vaughan, C Verde, D Webb, C Wiencke, P Woodworth, T Worby, R Worland, and T Yamanouch. 2009. The Instrumental Period. In Antarctic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 A Contribu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Polar Year 2007-2008, J Turner, ed. Cambridge: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Antarctic Research. Pp 183-298.
75. Siebert L, T Simkin, and P Kimberly. 2010. Volcanoes of the World, 3rd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76. Holdgate MW, PJ Tilbrook, and RW Vaughan. 1968. The Biology of Bouvetøya. British Antarctic Survey Bulletin 15: 1-7.
77. Huyser O. 2001. Bouvetøya (Bouvet Island). In Important Bird Areas in Africa and associated islands: Priority sites for conservation, MI Evans and LDC Fishpool, eds. Newbury and Cambridge: Pisces Publications and BirdLife International (BirdLife Conservation Series 11). Pp. 113-115.
78. Jacob U, T Brey, I Fetzer, S Kaehler, K Mintenbeck, K Dunton, K Beyer, U Struck, EA Pakhomov, and WE Arntz. 2005. Towards the trophic structure of the Bouvet Island marine ecosystem. Polar Biology 29(2): 106-113; Rogers AD, S Morley, E Fitzcharles, K Jarvis, and M Belchier. 2006. Genetic structure of Patagonian toothfish (Dissostichus eleginoides) populations on the Patagonian Shelf and Atlantic and western Indian Ocean Sectors of the Southern Ocean. Marine Biology 149(4): 915-924.
79. Ansorge IJ, PW Froneman, and JV Durgadoo. 2012. The Marine Ecosystem of the Sub-Antarctic, Prince Edward Islands. In Marine Ecosystems, A Cruzado, ed. InTech Press. Pp 61-76.
80. Ibid.
81. Crawford RJM and J Cooper. 2003. Conserving Surface-nesting Seabirds at the Prince Edward Islands: The Roles of Research, Monitoring and Legislation. African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25(1): 415-426.
82. CCAMLR. 2011. Report of the Workshop on MPAs. From section 2.35 “Dr Lombard by WWF-South Africa and th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ffairs, South Africa. The initiative was begun by WWF in 2008, and the intention is to work toward a jointly-managed MPA on the del Cano plateau, between South Africa’s Prince Edward Islands and France’s Crozet Islands. The first step is promulgation of the Prince Edward Islands MPA which is currently under review by th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ffairs, South Africa. Dr C. Bost (France) indicated that this collaborative project has been extremely productive with respect to science.”
83. Crawford and Cooper 2003.
84. Bost CA, T Zorn, Y Le Maho, and G Duhamel. 2002. Feeding of diving predators and diel vertical migration of prey: King penguins’ diet versus trawl sampling at Kerguelen Islands. Marine Ecology Progress Series 227: 51-61; Lea M, C Guinet, Y Cherel, M Hindell, L Dubroca, and S Thalmann. 2008. Colony-based foraging segregation by Antarctic fur seals at the Kerguelen Archipelago. Marine Ecology Progress Series 358: 273-287; Meyer et al 2000.
85. Welsford DC, AJ Constable, and GB Nowara. 2011. The Heard Island and McDonald Islands Marine Reserve and Conservation Zone – A model for Southern Ocean marine reserves? In The Kerguelen Plateau: marine ecosystem and fisheries, G Duhamel and D Welsford, eds. Société Française d’Ichtyologie. Pp 297-304.
86. Falguier A and C Marteau. 2011. The management of the natural marine reserve of the Terres australes francaises (French Southern Lands). In the Kerguelen Plateau: marine ecosystem and fisheries, G Duhamel and D Welsford, eds. Société Française d’Ichtyologie. Pp 293-296.
87. Constable AJ and S Doust. 2009. Southern Ocean Sentinel – an international program to assess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marine ecosystems: Report of a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Hobart, April 2009. ACE CRC,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and WWF-Australia
88. Ibid.
89. Constable et al. 2011.
90. Constable et al. 2011; Clarke et al. 2007.
91. Woehler 1993.
92. Constable et al. 2011.
后注
南大洋的传承:环极海区和罗斯海保护愿景 35
93. Ibid.
94. WG-FSA. 2010. Fishery Report: Exploratory Fishery For Dissostichus Spp. In Division 58.4.1. Working Group on Fish Stock Assessment. Hobart: CCAMLR.
95. Douglass et al. 2011.
96. Smith et al, 2007.
97. Eastman J. T. And Hubold G. 1999. The “sh fauna of the Ross Sea, Antarctica. Antarctic Science. 11:293-304.
98. Ibid.
99. Hanchet S.M., Rickard G.J., Fenaughty J.M., Dunn A. and Williams M.J. 2008. A hypothetical life cycle for Antarctic tooth”sh Dissostichus mawsoni in Antarctic waters of CCAMLR Statistical Area 88. CCAMLR Science 15: 35-54.
100. Ibid.
101. Ainley 2010.
102. Halpern B.S., Walbridge S., Selkoe,K.A., Kappel C.B., Micheli F., D’Agrosa C., Bruno J.F., Casey K.S., Ebert C., Fox H.E., Fujita R., Heinemann D., Lenihan H.S., Madin E.M.P., Perry M.T., Selig E.R., Spalding M., Steneck R. and Watson R. 2008. A global map of human impact on marine ecosystems. Science 319: 948-951. Supporting Online Material for A Global Map of Human Impact on Marine Ecosystems, Halpern et al., (2008) http://www.sciencemag.org/content/suppl/2008/02/12/319.5865.948.DC1/Halpern_SOM.pdf.
103. Smith W.O. Jr., Ainley D.G., Cataneo-Vietti R. and Hofmann E.E. 2012. The Ross Sea continental shelf: regional biogeochemical cycles, trophic interactions, and potential future changes. In Antarctic Ecosystems: An extreme environment in a changing world. J. Wiley and Sons, London.
104. Kaiser S, DKA Barnes, CJ Sands, and A Brandt. 2009. Biodiversity of an unknown Antarctic Sea: assessing isopod richness and abundance in the first benthic survey of the Amundsen continental shelf. Marine Biodiversity 39: 27- 43.
105. Ainley DG, SS Jacobs, CA Ribic, and I Gaffney. 1998. Seabird distribution and oceanic features of the Amundsen and southern Bellingshausen seas. Antarctic Science 10: 111-123.
106. Ainley DG, KM Dugger, V Toniolo, and I Gaffney. 2007. Cetacean occurrence patterns in the Amundsen and southern Bellingshausen Sea sector, Southern Ocean. Marine Mammal Science 23: 287–305.
107. Holm-Hansen O, M Kahru, and CD Hewes. 2005. Deep chlorophyll a maxima (DCMs) in pelagic Antarctic waters. II. Relation to bathymetric features and dissolved iron concentrations. Marine Ecology Progress Series 297: 71-81.
108. United Kingdom. 2011. Climate change and precautionary spatial protection: ice shelves. SC-CAMLR-XXX/13. Hobart: CCAMLR.
109. Ibid.
110. Ibid.
111. Douglass et al. 2011.
后注